城市上下水
| 内容出处: | 《肃州文史·百年巨变访谈录》 图书 |
| 唯一号: | 292220020220006524 |
| 颗粒名称: | 城市上下水 |
| 分类号: | K294.23 |
| 页数: | 5 |
| 页码: | 303-307 |
| 摘要: | 柴廷国和张永良讲述城市上下水的发展过程。 |
| 关键词: | 肃州 酒泉 文史资料 |
内容
城市上下水
采访对象:柴廷国,生于1954年12月,肃州区人。1972年9月参加工作,先后在红山乡政府、县二轻局、灯具电器厂工作,1983年担任灯具电器厂副厂长、代理厂长、书记职务。2011年提前退休。
张永良(见前)采访人:周聪德采访日期:2021年7月2日采访地点:民主街社区采访人:跟您聊一聊城市上下水的发展过程,从您自己吃水用水的切身体会说起。
柴廷国:城市居民一开始吃的是渗水井,院子里挖一口井,深大概有三米左右,低处两米左右就出水了,用水桶从井里打水吃。有的一个院子一口井,有的几个院子一口井,一个院子少些五六户人,多的二三十户人。我住的大众巷36号只有五六户人家,也有一口渗水井。1979年我搬进去的时候,已经废弃不用了,对面院子里有个手压井,我们就在那里压水,不用从渗水井里吊水了。压水井也是一样,有的一个院子打一个,有的打在院子外面,几个院子里的人共用一个,都是自己打的,只有部分街巷有。再后来就通了自来水,修了水房,一个片区居民一个水房,全部集中到水房接水。西关坡地区医院外科楼那里有个水塔,大众巷也有一个水塔,全城大概有两三个水塔,水塔里的水供到水房,居民再从水房里取水。水房就多了,一条街上少些有一个,多些有两三个,共和街和邮电街交叉的那个拐拐就有一个水房,邮电街饮食服务公司那些也有个水房。
采访人:水塔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水房里的水是怎么分配的?张永良:水塔抽的是地下水,用水泵从井里抽到塔里,再从塔里分散到各个水房。我记得最清楚,大概八十年代初期,酒泉城里停了三天电,纯粹没水了,全城人都慌了,供电所连夜奋战才恢复了供电。水房里打水一分钱两桶,都挑的担子去打水。我在共和街15号住的呢,出来大约有一百多米就到了水房,距离水房是最近的。我是1983年到灯具电器厂的,在此之前在皮革厂。1983年,我老娘搬走了,我们小两口没个水桶子,还是从灯具厂买了个水桶子,一次只能买一个,没那么多的钱,两个月才买了两个。那时候水房有人看水的呢,我们这个水房的看水师傅姓李,态度特别好,是个好老人家。过去吃水艰难的呢,在没有水房之前,有的院子没有水井,到处找的拉水。我家周边五六个院子,加起来有六十多户人家。记得有一两年,水位浅下了,唯独就有一个院子的渗水井水多些,能打出水来了,井里的水往往供不应求,打出的水沙子儿一层,每次吊出小半桶,先倒进脸盆里澄一会,让沙子儿沉下去,再倒进水桶里。而且,院子门锁着,本院子里的人优先打完水,才开门容许周围的人进来打水。我们小时候,拉水基本上是娃娃的事,娘母子下班回来做饭,如果没有水,就得挨收拾。我娘在砖瓦厂上班,忙得很。
采访人:娃娃还要上学呢,取水又那么艰难,啥时间取水?张永良:上学跟取水没关系,做儿女的必须给老娘把做饭的水存下,不然回家就是干缠捻头子,搁啥做饭呢!远处拉水我也拉了,最远的时候到灯具场的院子里,那个院子里有个水井,水比较旺。行署大院我也拉过水。一百八十公斤的那种盛汽油的圆桶子,用架子车拉水,桶盖子上取个方框框加水,找一截管子流水。一个院子十几户,就一个桶,天天得拉,每次出三个人,轮流拉水,架子车还有主人呢,拉水的时候还得去借,不借给就得另想办法。八十年代以前就这个样子,以后才有了水房。
采访人:以前吃水那么艰难,洗衣服用水是怎么解决的?张永良:那时候城市不大,城里有个河坝,从现在的彩虹桥那里由西南通向东北,现在市二院家属院那里就有河坝经过。河里有水,但不宜饮用,也太远了,但可以洗衣服。我们就在河里洗衣服,拿上个盆子,有洗衣粉那是高档的,一般拿上些碱面子,衣服洗过挂在树丫条上,就玩去了,抓鱼儿去了,等衣服晾干了,再拿回家。妇女洗床单、被子的,也拿到河坝里去。
采访人:上下水是哪一年入户的?张永良:八十年代以前,城市没有下水,生活用水靠地下渗漏和自然蒸发。一到冬天,脏水泼到地上,地面就结冰了,路上成了冰滩,有的地方鼓起个冰鼓堆。1985年以后,水房开始改造撤销,自来水开始入户,但管沟得自己出力挖,材料得自己掏钱买,供排水公司只负责安装。自来水进到户里就方便多了,再不用为吃水发愁了。但厕1979年7月洪水进入酒泉城南门所还是茅坑,我们那个院子里住着十四户,就一个厕所,厕所平时锁的呢。一个茅坑男女混搭,一次只能进一个人。为啥要锁呢,因为我们是15号,旁边17号、19号的人有时候也钻进去上厕所,人家钻进去不出来,我们院子里上厕所的人在外面等的失急呢。污水处理从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居民大院里的旱厕在八九十年代以后陆续改成外面的水厕,但那时的水厕设施比较简陋,水存在水箱里,压力小,冲厕不利索。户里通下水就更晚了,这跟住房改造密切相关,以前的土坯房先通了自来水,直到拆掉修建了楼房才通了下水,卫生间也随之入户了。是楼房的下水带动了平房的下水,后来没有住楼房的居民院落门前都留有倒污水的漏口。
采访对象:柴廷国,生于1954年12月,肃州区人。1972年9月参加工作,先后在红山乡政府、县二轻局、灯具电器厂工作,1983年担任灯具电器厂副厂长、代理厂长、书记职务。2011年提前退休。
张永良(见前)采访人:周聪德采访日期:2021年7月2日采访地点:民主街社区采访人:跟您聊一聊城市上下水的发展过程,从您自己吃水用水的切身体会说起。
柴廷国:城市居民一开始吃的是渗水井,院子里挖一口井,深大概有三米左右,低处两米左右就出水了,用水桶从井里打水吃。有的一个院子一口井,有的几个院子一口井,一个院子少些五六户人,多的二三十户人。我住的大众巷36号只有五六户人家,也有一口渗水井。1979年我搬进去的时候,已经废弃不用了,对面院子里有个手压井,我们就在那里压水,不用从渗水井里吊水了。压水井也是一样,有的一个院子打一个,有的打在院子外面,几个院子里的人共用一个,都是自己打的,只有部分街巷有。再后来就通了自来水,修了水房,一个片区居民一个水房,全部集中到水房接水。西关坡地区医院外科楼那里有个水塔,大众巷也有一个水塔,全城大概有两三个水塔,水塔里的水供到水房,居民再从水房里取水。水房就多了,一条街上少些有一个,多些有两三个,共和街和邮电街交叉的那个拐拐就有一个水房,邮电街饮食服务公司那些也有个水房。
采访人:水塔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水房里的水是怎么分配的?张永良:水塔抽的是地下水,用水泵从井里抽到塔里,再从塔里分散到各个水房。我记得最清楚,大概八十年代初期,酒泉城里停了三天电,纯粹没水了,全城人都慌了,供电所连夜奋战才恢复了供电。水房里打水一分钱两桶,都挑的担子去打水。我在共和街15号住的呢,出来大约有一百多米就到了水房,距离水房是最近的。我是1983年到灯具电器厂的,在此之前在皮革厂。1983年,我老娘搬走了,我们小两口没个水桶子,还是从灯具厂买了个水桶子,一次只能买一个,没那么多的钱,两个月才买了两个。那时候水房有人看水的呢,我们这个水房的看水师傅姓李,态度特别好,是个好老人家。过去吃水艰难的呢,在没有水房之前,有的院子没有水井,到处找的拉水。我家周边五六个院子,加起来有六十多户人家。记得有一两年,水位浅下了,唯独就有一个院子的渗水井水多些,能打出水来了,井里的水往往供不应求,打出的水沙子儿一层,每次吊出小半桶,先倒进脸盆里澄一会,让沙子儿沉下去,再倒进水桶里。而且,院子门锁着,本院子里的人优先打完水,才开门容许周围的人进来打水。我们小时候,拉水基本上是娃娃的事,娘母子下班回来做饭,如果没有水,就得挨收拾。我娘在砖瓦厂上班,忙得很。
采访人:娃娃还要上学呢,取水又那么艰难,啥时间取水?张永良:上学跟取水没关系,做儿女的必须给老娘把做饭的水存下,不然回家就是干缠捻头子,搁啥做饭呢!远处拉水我也拉了,最远的时候到灯具场的院子里,那个院子里有个水井,水比较旺。行署大院我也拉过水。一百八十公斤的那种盛汽油的圆桶子,用架子车拉水,桶盖子上取个方框框加水,找一截管子流水。一个院子十几户,就一个桶,天天得拉,每次出三个人,轮流拉水,架子车还有主人呢,拉水的时候还得去借,不借给就得另想办法。八十年代以前就这个样子,以后才有了水房。
采访人:以前吃水那么艰难,洗衣服用水是怎么解决的?张永良:那时候城市不大,城里有个河坝,从现在的彩虹桥那里由西南通向东北,现在市二院家属院那里就有河坝经过。河里有水,但不宜饮用,也太远了,但可以洗衣服。我们就在河里洗衣服,拿上个盆子,有洗衣粉那是高档的,一般拿上些碱面子,衣服洗过挂在树丫条上,就玩去了,抓鱼儿去了,等衣服晾干了,再拿回家。妇女洗床单、被子的,也拿到河坝里去。
采访人:上下水是哪一年入户的?张永良:八十年代以前,城市没有下水,生活用水靠地下渗漏和自然蒸发。一到冬天,脏水泼到地上,地面就结冰了,路上成了冰滩,有的地方鼓起个冰鼓堆。1985年以后,水房开始改造撤销,自来水开始入户,但管沟得自己出力挖,材料得自己掏钱买,供排水公司只负责安装。自来水进到户里就方便多了,再不用为吃水发愁了。但厕1979年7月洪水进入酒泉城南门所还是茅坑,我们那个院子里住着十四户,就一个厕所,厕所平时锁的呢。一个茅坑男女混搭,一次只能进一个人。为啥要锁呢,因为我们是15号,旁边17号、19号的人有时候也钻进去上厕所,人家钻进去不出来,我们院子里上厕所的人在外面等的失急呢。污水处理从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居民大院里的旱厕在八九十年代以后陆续改成外面的水厕,但那时的水厕设施比较简陋,水存在水箱里,压力小,冲厕不利索。户里通下水就更晚了,这跟住房改造密切相关,以前的土坯房先通了自来水,直到拆掉修建了楼房才通了下水,卫生间也随之入户了。是楼房的下水带动了平房的下水,后来没有住楼房的居民院落门前都留有倒污水的漏口。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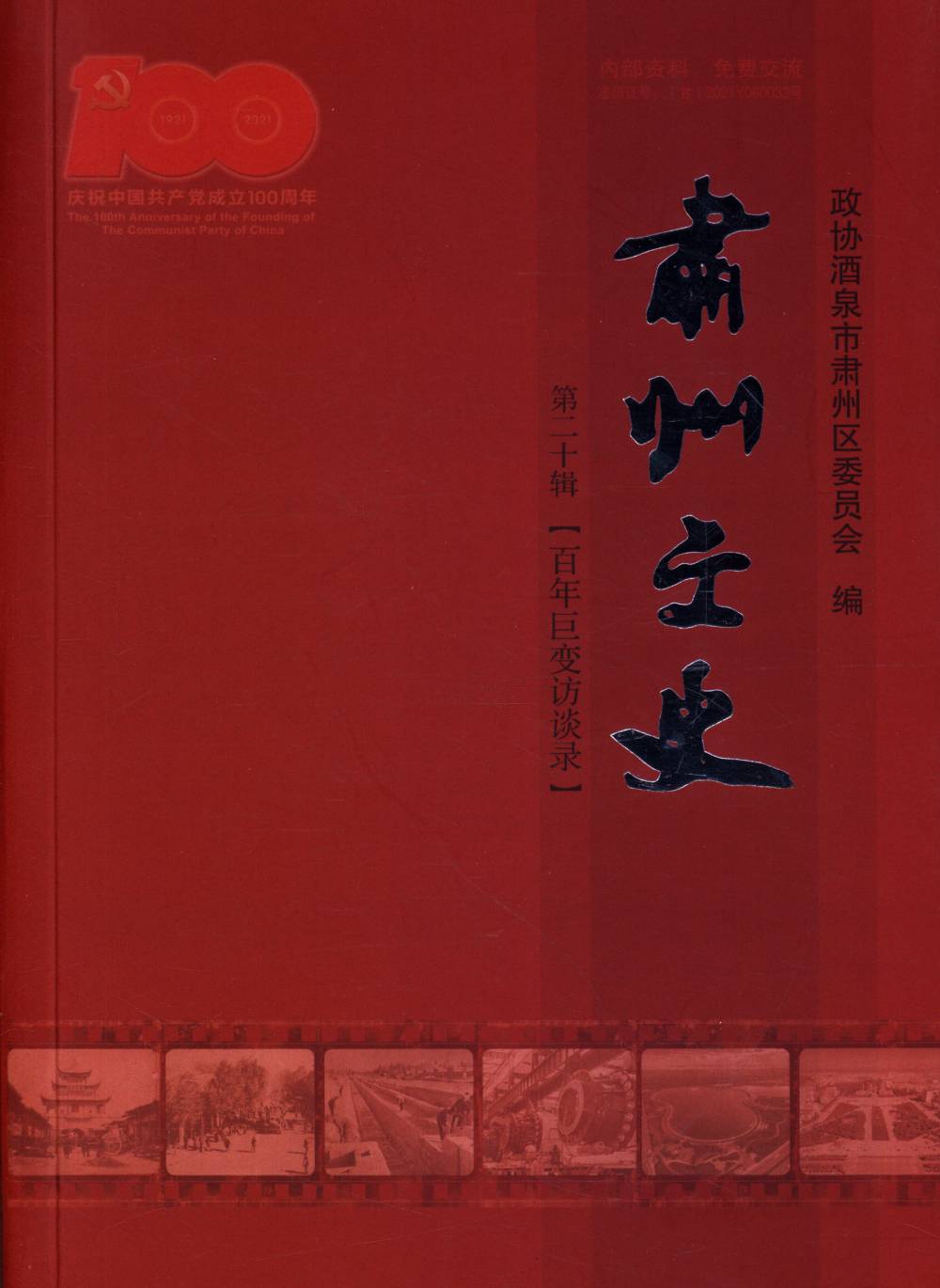
相关人物
周聪德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