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的亲历
| 内容出处: | 《肃州文史·百年巨变访谈录》 图书 |
| 唯一号: | 292220020220006521 |
| 颗粒名称: | 医者的亲历 |
| 分类号: | K294.23 |
| 页数: | 11 |
| 页码: | 281-291 |
| 摘要: | 王长春回忆作为一个医生在酒泉工作的经历。 |
| 关键词: | 肃州 酒泉 文史资料 |
内容
医者的亲历
采访对象:王长春,生于1938年4月,宁夏银川人。曾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先后任怀茂卫生院院长、原酒泉市防疫站站长、卫生局局长。1997年4月退休。
采访人:刘永丰采访时间:2017年9月29日采访地点:阳光小区采访人:王老您好!请您谈谈初到酒泉工作时的路途见闻。
王长春:好的。我是宁夏银川人,1955年从宁夏卫生学校毕业时,刚赶上甘肃省和宁夏省合并,我们班的同学都被划到甘肃省卫生厅,在这里等待分配工作。我们在兰州等了十天,天天都有雨,第十一天,我被分配到酒泉,包括玉门油矿一共20多个人。出发那天,先是走铁路,乘坐闷罐车到武威,车厢里没有窗户,也没有座位,只能坐自己的行李。上车时天就黑了,整个车厢挂一盏马灯,光线十分昏暗。车门都从外面上了锁,火车开动后,只能听见有节奏的唯嘡声。里面没有厕所,尿憋了就顺着门缝往外尿。第二天中午到达武威时,外面还在下雨。当时的武威很难找到能住下20多个人的旅店,最大的是汽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虽然是新盖的平房,也还是住不下我们,带队的干部又在武威城里找了另一家旅店。这个旅店大一些,房子很破旧,是一院子土坯房,屋里只有土炕和席子,再没有别的东西,墙上爬着许多臭虫。当时,再向西走只能坐汽车,但汽车很少。我们在武威等了两天,最后找了一辆烂卡车。破车走路慢,走的又是砂石路,走一段就要修一次。就这样,我们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了整整两天才到酒泉。
当时,酒泉地区卫生处在现在的军分区院子里办公,里面还有地委党校和地委机关。我们被安排住进了地区招待所,就是现在的酒泉中学对面,吃饭在地委党校。说是招待所,其实就是个四合院,房子门是双扇的,都用铁镣鼻子锁着,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房子里睡人的地方,是用土坯码成的圈子,里面就地铺着一层用旧了的碎麦草,住进去的人将自己的行李就地一铺,这叫地铺。等了三天,我被分配到卫生街工会对门的酒泉地区医院。
采访人:当时酒泉城的大街上是什么情景?王长春:当时,我在鼓楼附近见过一段柏油马路,这是我第一次见柏油马路,我想,这可能是酒泉离玉门油矿近的缘故。那时城里人夜间照明靠的是煤油灯,酒泉城里最繁华的地段就是卫生街口到邮电街口,因为这里有个和平影院和祁连剧院,晚上卖东西和逛街的人比较多。卫生街口卖吃头的生意人卖的主要是油茶、元宵、凉粉、干果等,这些人都在用一种叫“气死风”的电石灯,有几个摊位,就有儿点亮光。
采访人:请您谈谈初到酒泉时的医疗卫生状况。
王长春:当时的酒泉地区医院在卫生街的工会对门,就是后来的市二院鼓楼分院旧址。门诊部是一个200多平米的二层小楼,后面的住院部都是土坯房,一共有七八十张床位。医护人员吃住都在东北斜对面的四合院内。
地区医院是1953年建立的,医护人员大体上有三部分组成:一是私人诊所过来的。如东大街夜光杯厂附近有个敦友诊所,所长于敦友,山东人;还有共和街南山疗养院的兄妹俩,男的叫楚慧宗,女的叫杨琼书,昆明人。他们两家都是西医。起初以他们两家私人诊所为主,又合并了另外几家私人诊所,搭起了医院的架子,院长是于敦友,副院长是杨琼书。二是国民党驻酒泉军队收编后转业的旧军医。酒泉和平解放后,参加起义的国民党旧部有一部分人转业到酒泉,其中有4个旧军医被安置到地区医院。三是陆续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主要来源是兰州医学院和兰州卫校,如后来的院长王振国,就是解放后第一批分配到地区医院的学生。
1955年酒泉城里还没有电,晚上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医院做手术用的是旧卡车的发电机照明,因为性能不稳定,灯光时明时暗。这种老式发电机靠手摇发动,常常发动不起来,患者和做手术的大夫只能干着急。1956年后半年,酒泉电厂开始发电,一发电,全城都能听见巨大的唯瞠声。电厂在面粉厂对面,发出的电主要是供街上的路灯和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照明。电到晚上十二点就停了,全城照旧是黑咕隆咚。这时,遇到急诊手术,还得用旧发电机照明,一听见窟嗵窟嗵的响声,全院的人都知道又来了急诊手术。当时,地区医院能做的手术是常见的阑尾炎、疝气等三四种,复杂一些的手术,如胃切除、胆囊手术都做不了。
解放初期,酒泉的大多数人还不相信西医,有了病习惯看中医。酒泉城里的中医主要有现在百货大楼东侧的广泰堂等几家。到1956年地区医院成立中医部时,合并了广泰堂的张明德等人,据说张明德还给盛世才看过病。在我的印象中,老中医的形象都是长袍子、长胡子、长指甲,手里拿个长长的旱烟锅子,看病没有定价,全看患者的意思和条件,这叫端钱,因此,生活富裕的并不多。
由于很多人经济条件差,再加上对西医还不了解,所以住院的患者比较少。当时我在外科工作,外科和妇产科一共30张床,内科30张床,就这还经常有空床,特别是内科的床位空的比较多,住进来的病人都是比较重的。当时,我的月工资是40多元,患者动个阑尾十来块钱,看个感冒也就几块钱。农村患者一般到病痛实在抗不住了才来住院,进城看病都赶着大车古辘老牛车,胶皮车古辘的驴拉车到了六十年代末期才出现。
我在地区医院一直工作到1964年。后来酒泉张掖两个专区合并,地区医院搬到张掖,原地区医院与县卫生院合并成为县医院。解放初期的县医院位于鼓楼西南,就是现在的文旅局所在地。当时的县卫生院不到10个人,六十年代初又改为劳改医院,办了五六年时间,合并到县医院后,这里成为县文教局和卫生局的办公场所。
采访人:您对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有哪些感触最深的见闻?王长春:我感触最深的事情还是到农村下乡以后。1965年,毛主席发表“六二六”指示,全国掀起了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的高潮。当时,酒泉地区第一批带头报名下乡的有18名医生,我也在其中,这批医生都派到了酒泉县各公社卫生院,第二批和第三批下去的医生派到了周边其他县市的偏远农村。我去的是怀茂卫生院,在那里我工作了15年时间,亲身经历了农村卫生事业的起步和发展。
解放后,酒泉县农村设有9个区,怀茂公社属河北区。解放初期,县卫生院选派了5名能独立开展医务工作的医生,每人给了价值500元的药品作为开办费,让他们去开办5个区的卫生所,房屋桌凳等基础设施由各区公所提供,主要来源是庙产和公产,现在各乡镇称为中心卫生院的,就是当时开设的区卫生所。这几个卫生所初建时,农村普遍缺乏人才,尤其是缺西医,选派的医生大都是酒泉和平解放时的国民党旧军医,除了清水中心卫生院的杨富贵曾在新疆跟俄罗斯人学过一些西医外,金佛寺中心卫生院的赵芝宝、临水中心卫生院的徐茂斋、银达中心卫生院的胡孝蒲、果园中心卫生院的徐明等都是旧军医,医院的其他缺员陆续吸收或等待国家分配。比如,1956年酒泉安置了一批河南移民,迁来时议定给他们当中有文化的子女安排工作,这批人被分配到各个学校和医院。分配到医院的移民子女在县医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培训学习后,县医院留下了一大批,多数是护理人员,其他的都分配到了各区卫生所。因此,“六二六”指示以前,像河北区卫生所也就四五个人。不在区公所所在地的公社,农民看病主要是去找当地土生土长的中医,这些中医一般都在自己家里行医。
我下乡时,怀茂公社没有大夫。以前有过两个大夫,一个因犯法被捕,一个调回原籍。卫生院设在怀茂学校内 (现在怀下6组),是借学校的3间伙房开设的,房子的墙都快要倒了,库存的全部中西医药品现在最多也就值2000多元。我和公社派来的一名会计在这里干了两年多,此后才开始陆续分配医务人员,再加上自己培训的医务人员,队伍慢慢壮大起来。当时,小孩百日咳、麻疹、猩红热等传染病特别多,每年春季猩红热泛滥,成群结队的小孩都涌进医院。到了秋季,百日咳、麻疹又泛滥起来,再加上脑膜炎患者比较多。我白天坐诊,晚上还要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上门出诊,虽然工作局面打开了,但确实忙得不可开交。看病的人一多,医药的进出速度也快了,在医药公司提药时,从一开始两三天攒两三百元钱买一背包药,到两三天买一箱子药,再到买四五箱子药。1966年,县上和公社领导同意在东坝大队一座破庙的底子上拆旧庙新建卫生院。修建时除了自筹的一点钱,又向卫生局要了几百元,利用旧庙的木头,修了12间砖土木结构的房子。
1970年底,医院已经有医务人员十几个,能坐诊的医生3人,原有的12间房子已经无法满足群众的医疗需要,公社党委向卫生局申请,又扩建了20间房子,把门诊和住院分开,初步形成了规模。就这样,医院还是经常住满病人。1976年,县上又在怀茂滩上划了七八十亩地,用于搬迁卫生院,这次一共修了87间房子,也是砖土木结构。
新建的卫生院把门诊、住院、传染病房彻底分开了,卫生院从一开始只能看头痛感冒,发展到外科、内科、妇科、儿科常见病都能医治。怀茂卫生院是酒泉各公社卫生院第一个做手术的医院。第一次手术就是1968年我做的阑尾手术,到后来,医院做疝气和计划生育上的放环、刮宫、结扎等常见的手术都不成问题。采访人:请您举例谈谈六十年代农村的卫生状况。
王长春:好的。我到怀茂卫生院工作时,酒泉县刚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社员家里多数人家小孩多,劳力少,条件差,卫生习惯不好。农村的小孩子缺吃少穿,天冷的时候都穿个旧布做的棉筒筒,下面没有贴身的内衣,肯感冒。由于不经常洗脸洗手洗衣服,鼻涕下来用袖子一抹,脸上和袖子上都是层层摞摞的干鼻涕,胸前因为吃饭喝水锈成了硬壳子,很容易得病。看病的小孩身上、女孩头上虱子蛆子乱跑,衣服缝里虱子蛆子锈得密密麻麻。有时候到社员家里出诊,主人把油泼葱花甜面条端上来,这就算是农村最好吃的了,只有客人能吃,家里的一群孩子都在一旁围观,一个个眼馋得直流口水。到了冬天,取暖条件好一些的用火盆,从外面拾一点干柴点着,屋子里烟雾弥漫,门窗都开着,一点也不保温,就这样还是呛得坐不住人。农家的炕上铺的都是芨芨草打的炕席,北乡产过水烟,抽水烟的人特别多,抽烟时习惯用芨芨棍子拨烟丝,有好多人家的炕席边上都被抽成了大豁裸。怀茂公社的土地碱性大,人家屋里和院子里都是夯土地,许多农户院子里泛着白白的碱灰,家家户户的墙壁都是不粉刷的土坯墙。到后来搞卫生宣传,开展爱国卫生月运动,先是动员农户刷白灰墙,拆洗被褥,灭虱子,再就是除“四害”。比如说灭虱子,八十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人身上都有虱子,有些甚至是比较体面的人。可以说,生活在农村的人,身上不见虱子蛆子的很少。虱子这种寄生虫盯人很痒,有时还疼,它主要是通过吸食人的血液维持生命。因为小孩子细皮嫩肉,所以小孩身上的虱子蛆子特别多,在生产队忙碌了一天的父母亲,晚上还要就着煤油灯捉虱子。到了冬天,身上的虱子蛆子实在太多了,就拿出去冻。对于灭虱子,卫生系统想过各种办法,包括勤洗衣服、用开水烫、撒六六六粉等,效果都不理想。最管用的是后来商店卖的一种粉笔状的灭虱灵,在有虱子蛆子的地方一涂抹就行。后来,随着布票和粮票的废除,农民有钱买穿戴了,再加上各种农药的大量使用,虱子蛆子才彻底绝迹。
采访人:您对肃州区防疫灭病的发展历程非常清楚,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和体会。
王长春:好的。解放前后,虽然天花通过种牛痘基本灭绝,但那时的防疫手段十分落后。受医药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人们在种牛痘预防天花时,先把前一个人大胳膊上种牛痘所结的痂放到水里泡,然后把后一个人的大胳膊用小刀划一个十字,再拿个小筒筒用嘴把这种泡痂的水吹到伤口上,就这样一直往下种。这种方法很不科学。解放初,种牛痘的剂型和方法得到改进,不久又增加了小儿麻痹糖丸,常见的防疫就这两种。当时,农民群众对防疫还没有什么概念,小孩的百日咳、麻疹、猩红热等传染病都以治疗为主。以后,又有了麻苗、卡介苗、百白破苗,常见的传染病才得到了控制。总体上看,七十年代以前,我们这里传染病的发病比较高,儿童死亡率也比较高。比如沿山因为气候寒凉,冬天小孩穿得单,盖得薄,加上治疗不及时,麻疹转为肺炎的特别多,病死率也比较高。那时候,医疗水平有限,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也比较高。大人患的地方病和传染病主要是大脖子病、布鲁氏杆菌病、结核病。大脖子病学名叫甲状腺肿大,因为高原人的食物链缺碘的缘故,农村特别是沿山患这种病的比较多,有顺口溜说:“沙山马营,嗦袋皮一层”。这种病的防治开始于六十年代,通过持续普及碘盐,经过漫长的过程,到了九十年代才基本控制。当时因为卫生条件不好,人畜交叉传染的疾病发病率也很高,如布鲁氏杆菌病就是这样,先是牛羊患病,然后再传染给人,人患这种病以后浑身困乏无力,什么活也干不了,俗称“懒汉病”。我记得这种病发病最厉害的时候,有一年春天,怀茂六分大队传染布鲁氏杆菌病的人太多了,连麦子都种不到地里。结核病也是农村比较流行的传染病,一度曾引起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派新西兰专家到西峰公社实地调查结核病患者。再就是痢疾,过去一到秋天,痢疾拉肚非常普遍,大人小孩都很难幸免,严重的甚至拉脓血,这是因为饮用水中含有痢疾杆菌等病菌。随着酒泉农村普及人畜饮水工程,沿山从涝池改成水窖,中北部从大口井改成机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饮用水质量不断提高,痢疾已经很少见了。如原临水乡人饮水含氟量高,很多人害氟斑牙和氟骨症,临水乡政府、临水乡北沟村的两口机井和两座水塔的费用,就是从地方病防治经费中支付的。
防疫工作的冷链系统,对疫苗的运输和储藏过程要求很严格,温度既不能高,也不能低,发放到各公社的疫苗用冰镇包领回去必须在24小时之内用完,否则就要失效。1979年,我到防疫站任站长,一直干到1984年调到卫生局任局长,这期间始终都在关注防疫工作。我认为,我们国家的防疫工作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做得好,这一点我体会很深。可以说,防疫上儿童常见病的预防效果非常明显,天花、白喉灭迹了,百日咳、小儿麻痹很少见。因为过去常见的传染病大多数都绝迹了,个别的现在也很少见,我曾见过本科毕业的年轻大夫坐诊时认不得麻疹和猩红热。在我的亲眼目睹中,无论是防疫冷链装备还是管理体系建设,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都很大,这是我们国家文明进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直到目前,对好多国家来说,传染病的防治,他们还做不到,但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却做到了,人的平均寿命从解放初期的四十几岁提高到现在的七十多岁,这是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采访对象:王长春,生于1938年4月,宁夏银川人。曾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先后任怀茂卫生院院长、原酒泉市防疫站站长、卫生局局长。1997年4月退休。
采访人:刘永丰采访时间:2017年9月29日采访地点:阳光小区采访人:王老您好!请您谈谈初到酒泉工作时的路途见闻。
王长春:好的。我是宁夏银川人,1955年从宁夏卫生学校毕业时,刚赶上甘肃省和宁夏省合并,我们班的同学都被划到甘肃省卫生厅,在这里等待分配工作。我们在兰州等了十天,天天都有雨,第十一天,我被分配到酒泉,包括玉门油矿一共20多个人。出发那天,先是走铁路,乘坐闷罐车到武威,车厢里没有窗户,也没有座位,只能坐自己的行李。上车时天就黑了,整个车厢挂一盏马灯,光线十分昏暗。车门都从外面上了锁,火车开动后,只能听见有节奏的唯嘡声。里面没有厕所,尿憋了就顺着门缝往外尿。第二天中午到达武威时,外面还在下雨。当时的武威很难找到能住下20多个人的旅店,最大的是汽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虽然是新盖的平房,也还是住不下我们,带队的干部又在武威城里找了另一家旅店。这个旅店大一些,房子很破旧,是一院子土坯房,屋里只有土炕和席子,再没有别的东西,墙上爬着许多臭虫。当时,再向西走只能坐汽车,但汽车很少。我们在武威等了两天,最后找了一辆烂卡车。破车走路慢,走的又是砂石路,走一段就要修一次。就这样,我们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了整整两天才到酒泉。
当时,酒泉地区卫生处在现在的军分区院子里办公,里面还有地委党校和地委机关。我们被安排住进了地区招待所,就是现在的酒泉中学对面,吃饭在地委党校。说是招待所,其实就是个四合院,房子门是双扇的,都用铁镣鼻子锁着,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房子里睡人的地方,是用土坯码成的圈子,里面就地铺着一层用旧了的碎麦草,住进去的人将自己的行李就地一铺,这叫地铺。等了三天,我被分配到卫生街工会对门的酒泉地区医院。
采访人:当时酒泉城的大街上是什么情景?王长春:当时,我在鼓楼附近见过一段柏油马路,这是我第一次见柏油马路,我想,这可能是酒泉离玉门油矿近的缘故。那时城里人夜间照明靠的是煤油灯,酒泉城里最繁华的地段就是卫生街口到邮电街口,因为这里有个和平影院和祁连剧院,晚上卖东西和逛街的人比较多。卫生街口卖吃头的生意人卖的主要是油茶、元宵、凉粉、干果等,这些人都在用一种叫“气死风”的电石灯,有几个摊位,就有儿点亮光。
采访人:请您谈谈初到酒泉时的医疗卫生状况。
王长春:当时的酒泉地区医院在卫生街的工会对门,就是后来的市二院鼓楼分院旧址。门诊部是一个200多平米的二层小楼,后面的住院部都是土坯房,一共有七八十张床位。医护人员吃住都在东北斜对面的四合院内。
地区医院是1953年建立的,医护人员大体上有三部分组成:一是私人诊所过来的。如东大街夜光杯厂附近有个敦友诊所,所长于敦友,山东人;还有共和街南山疗养院的兄妹俩,男的叫楚慧宗,女的叫杨琼书,昆明人。他们两家都是西医。起初以他们两家私人诊所为主,又合并了另外几家私人诊所,搭起了医院的架子,院长是于敦友,副院长是杨琼书。二是国民党驻酒泉军队收编后转业的旧军医。酒泉和平解放后,参加起义的国民党旧部有一部分人转业到酒泉,其中有4个旧军医被安置到地区医院。三是陆续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主要来源是兰州医学院和兰州卫校,如后来的院长王振国,就是解放后第一批分配到地区医院的学生。
1955年酒泉城里还没有电,晚上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医院做手术用的是旧卡车的发电机照明,因为性能不稳定,灯光时明时暗。这种老式发电机靠手摇发动,常常发动不起来,患者和做手术的大夫只能干着急。1956年后半年,酒泉电厂开始发电,一发电,全城都能听见巨大的唯瞠声。电厂在面粉厂对面,发出的电主要是供街上的路灯和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照明。电到晚上十二点就停了,全城照旧是黑咕隆咚。这时,遇到急诊手术,还得用旧发电机照明,一听见窟嗵窟嗵的响声,全院的人都知道又来了急诊手术。当时,地区医院能做的手术是常见的阑尾炎、疝气等三四种,复杂一些的手术,如胃切除、胆囊手术都做不了。
解放初期,酒泉的大多数人还不相信西医,有了病习惯看中医。酒泉城里的中医主要有现在百货大楼东侧的广泰堂等几家。到1956年地区医院成立中医部时,合并了广泰堂的张明德等人,据说张明德还给盛世才看过病。在我的印象中,老中医的形象都是长袍子、长胡子、长指甲,手里拿个长长的旱烟锅子,看病没有定价,全看患者的意思和条件,这叫端钱,因此,生活富裕的并不多。
由于很多人经济条件差,再加上对西医还不了解,所以住院的患者比较少。当时我在外科工作,外科和妇产科一共30张床,内科30张床,就这还经常有空床,特别是内科的床位空的比较多,住进来的病人都是比较重的。当时,我的月工资是40多元,患者动个阑尾十来块钱,看个感冒也就几块钱。农村患者一般到病痛实在抗不住了才来住院,进城看病都赶着大车古辘老牛车,胶皮车古辘的驴拉车到了六十年代末期才出现。
我在地区医院一直工作到1964年。后来酒泉张掖两个专区合并,地区医院搬到张掖,原地区医院与县卫生院合并成为县医院。解放初期的县医院位于鼓楼西南,就是现在的文旅局所在地。当时的县卫生院不到10个人,六十年代初又改为劳改医院,办了五六年时间,合并到县医院后,这里成为县文教局和卫生局的办公场所。
采访人:您对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有哪些感触最深的见闻?王长春:我感触最深的事情还是到农村下乡以后。1965年,毛主席发表“六二六”指示,全国掀起了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的高潮。当时,酒泉地区第一批带头报名下乡的有18名医生,我也在其中,这批医生都派到了酒泉县各公社卫生院,第二批和第三批下去的医生派到了周边其他县市的偏远农村。我去的是怀茂卫生院,在那里我工作了15年时间,亲身经历了农村卫生事业的起步和发展。
解放后,酒泉县农村设有9个区,怀茂公社属河北区。解放初期,县卫生院选派了5名能独立开展医务工作的医生,每人给了价值500元的药品作为开办费,让他们去开办5个区的卫生所,房屋桌凳等基础设施由各区公所提供,主要来源是庙产和公产,现在各乡镇称为中心卫生院的,就是当时开设的区卫生所。这几个卫生所初建时,农村普遍缺乏人才,尤其是缺西医,选派的医生大都是酒泉和平解放时的国民党旧军医,除了清水中心卫生院的杨富贵曾在新疆跟俄罗斯人学过一些西医外,金佛寺中心卫生院的赵芝宝、临水中心卫生院的徐茂斋、银达中心卫生院的胡孝蒲、果园中心卫生院的徐明等都是旧军医,医院的其他缺员陆续吸收或等待国家分配。比如,1956年酒泉安置了一批河南移民,迁来时议定给他们当中有文化的子女安排工作,这批人被分配到各个学校和医院。分配到医院的移民子女在县医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培训学习后,县医院留下了一大批,多数是护理人员,其他的都分配到了各区卫生所。因此,“六二六”指示以前,像河北区卫生所也就四五个人。不在区公所所在地的公社,农民看病主要是去找当地土生土长的中医,这些中医一般都在自己家里行医。
我下乡时,怀茂公社没有大夫。以前有过两个大夫,一个因犯法被捕,一个调回原籍。卫生院设在怀茂学校内 (现在怀下6组),是借学校的3间伙房开设的,房子的墙都快要倒了,库存的全部中西医药品现在最多也就值2000多元。我和公社派来的一名会计在这里干了两年多,此后才开始陆续分配医务人员,再加上自己培训的医务人员,队伍慢慢壮大起来。当时,小孩百日咳、麻疹、猩红热等传染病特别多,每年春季猩红热泛滥,成群结队的小孩都涌进医院。到了秋季,百日咳、麻疹又泛滥起来,再加上脑膜炎患者比较多。我白天坐诊,晚上还要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上门出诊,虽然工作局面打开了,但确实忙得不可开交。看病的人一多,医药的进出速度也快了,在医药公司提药时,从一开始两三天攒两三百元钱买一背包药,到两三天买一箱子药,再到买四五箱子药。1966年,县上和公社领导同意在东坝大队一座破庙的底子上拆旧庙新建卫生院。修建时除了自筹的一点钱,又向卫生局要了几百元,利用旧庙的木头,修了12间砖土木结构的房子。
1970年底,医院已经有医务人员十几个,能坐诊的医生3人,原有的12间房子已经无法满足群众的医疗需要,公社党委向卫生局申请,又扩建了20间房子,把门诊和住院分开,初步形成了规模。就这样,医院还是经常住满病人。1976年,县上又在怀茂滩上划了七八十亩地,用于搬迁卫生院,这次一共修了87间房子,也是砖土木结构。
新建的卫生院把门诊、住院、传染病房彻底分开了,卫生院从一开始只能看头痛感冒,发展到外科、内科、妇科、儿科常见病都能医治。怀茂卫生院是酒泉各公社卫生院第一个做手术的医院。第一次手术就是1968年我做的阑尾手术,到后来,医院做疝气和计划生育上的放环、刮宫、结扎等常见的手术都不成问题。采访人:请您举例谈谈六十年代农村的卫生状况。
王长春:好的。我到怀茂卫生院工作时,酒泉县刚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社员家里多数人家小孩多,劳力少,条件差,卫生习惯不好。农村的小孩子缺吃少穿,天冷的时候都穿个旧布做的棉筒筒,下面没有贴身的内衣,肯感冒。由于不经常洗脸洗手洗衣服,鼻涕下来用袖子一抹,脸上和袖子上都是层层摞摞的干鼻涕,胸前因为吃饭喝水锈成了硬壳子,很容易得病。看病的小孩身上、女孩头上虱子蛆子乱跑,衣服缝里虱子蛆子锈得密密麻麻。有时候到社员家里出诊,主人把油泼葱花甜面条端上来,这就算是农村最好吃的了,只有客人能吃,家里的一群孩子都在一旁围观,一个个眼馋得直流口水。到了冬天,取暖条件好一些的用火盆,从外面拾一点干柴点着,屋子里烟雾弥漫,门窗都开着,一点也不保温,就这样还是呛得坐不住人。农家的炕上铺的都是芨芨草打的炕席,北乡产过水烟,抽水烟的人特别多,抽烟时习惯用芨芨棍子拨烟丝,有好多人家的炕席边上都被抽成了大豁裸。怀茂公社的土地碱性大,人家屋里和院子里都是夯土地,许多农户院子里泛着白白的碱灰,家家户户的墙壁都是不粉刷的土坯墙。到后来搞卫生宣传,开展爱国卫生月运动,先是动员农户刷白灰墙,拆洗被褥,灭虱子,再就是除“四害”。比如说灭虱子,八十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人身上都有虱子,有些甚至是比较体面的人。可以说,生活在农村的人,身上不见虱子蛆子的很少。虱子这种寄生虫盯人很痒,有时还疼,它主要是通过吸食人的血液维持生命。因为小孩子细皮嫩肉,所以小孩身上的虱子蛆子特别多,在生产队忙碌了一天的父母亲,晚上还要就着煤油灯捉虱子。到了冬天,身上的虱子蛆子实在太多了,就拿出去冻。对于灭虱子,卫生系统想过各种办法,包括勤洗衣服、用开水烫、撒六六六粉等,效果都不理想。最管用的是后来商店卖的一种粉笔状的灭虱灵,在有虱子蛆子的地方一涂抹就行。后来,随着布票和粮票的废除,农民有钱买穿戴了,再加上各种农药的大量使用,虱子蛆子才彻底绝迹。
采访人:您对肃州区防疫灭病的发展历程非常清楚,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和体会。
王长春:好的。解放前后,虽然天花通过种牛痘基本灭绝,但那时的防疫手段十分落后。受医药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人们在种牛痘预防天花时,先把前一个人大胳膊上种牛痘所结的痂放到水里泡,然后把后一个人的大胳膊用小刀划一个十字,再拿个小筒筒用嘴把这种泡痂的水吹到伤口上,就这样一直往下种。这种方法很不科学。解放初,种牛痘的剂型和方法得到改进,不久又增加了小儿麻痹糖丸,常见的防疫就这两种。当时,农民群众对防疫还没有什么概念,小孩的百日咳、麻疹、猩红热等传染病都以治疗为主。以后,又有了麻苗、卡介苗、百白破苗,常见的传染病才得到了控制。总体上看,七十年代以前,我们这里传染病的发病比较高,儿童死亡率也比较高。比如沿山因为气候寒凉,冬天小孩穿得单,盖得薄,加上治疗不及时,麻疹转为肺炎的特别多,病死率也比较高。那时候,医疗水平有限,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也比较高。大人患的地方病和传染病主要是大脖子病、布鲁氏杆菌病、结核病。大脖子病学名叫甲状腺肿大,因为高原人的食物链缺碘的缘故,农村特别是沿山患这种病的比较多,有顺口溜说:“沙山马营,嗦袋皮一层”。这种病的防治开始于六十年代,通过持续普及碘盐,经过漫长的过程,到了九十年代才基本控制。当时因为卫生条件不好,人畜交叉传染的疾病发病率也很高,如布鲁氏杆菌病就是这样,先是牛羊患病,然后再传染给人,人患这种病以后浑身困乏无力,什么活也干不了,俗称“懒汉病”。我记得这种病发病最厉害的时候,有一年春天,怀茂六分大队传染布鲁氏杆菌病的人太多了,连麦子都种不到地里。结核病也是农村比较流行的传染病,一度曾引起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派新西兰专家到西峰公社实地调查结核病患者。再就是痢疾,过去一到秋天,痢疾拉肚非常普遍,大人小孩都很难幸免,严重的甚至拉脓血,这是因为饮用水中含有痢疾杆菌等病菌。随着酒泉农村普及人畜饮水工程,沿山从涝池改成水窖,中北部从大口井改成机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饮用水质量不断提高,痢疾已经很少见了。如原临水乡人饮水含氟量高,很多人害氟斑牙和氟骨症,临水乡政府、临水乡北沟村的两口机井和两座水塔的费用,就是从地方病防治经费中支付的。
防疫工作的冷链系统,对疫苗的运输和储藏过程要求很严格,温度既不能高,也不能低,发放到各公社的疫苗用冰镇包领回去必须在24小时之内用完,否则就要失效。1979年,我到防疫站任站长,一直干到1984年调到卫生局任局长,这期间始终都在关注防疫工作。我认为,我们国家的防疫工作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做得好,这一点我体会很深。可以说,防疫上儿童常见病的预防效果非常明显,天花、白喉灭迹了,百日咳、小儿麻痹很少见。因为过去常见的传染病大多数都绝迹了,个别的现在也很少见,我曾见过本科毕业的年轻大夫坐诊时认不得麻疹和猩红热。在我的亲眼目睹中,无论是防疫冷链装备还是管理体系建设,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都很大,这是我们国家文明进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直到目前,对好多国家来说,传染病的防治,他们还做不到,但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却做到了,人的平均寿命从解放初期的四十几岁提高到现在的七十多岁,这是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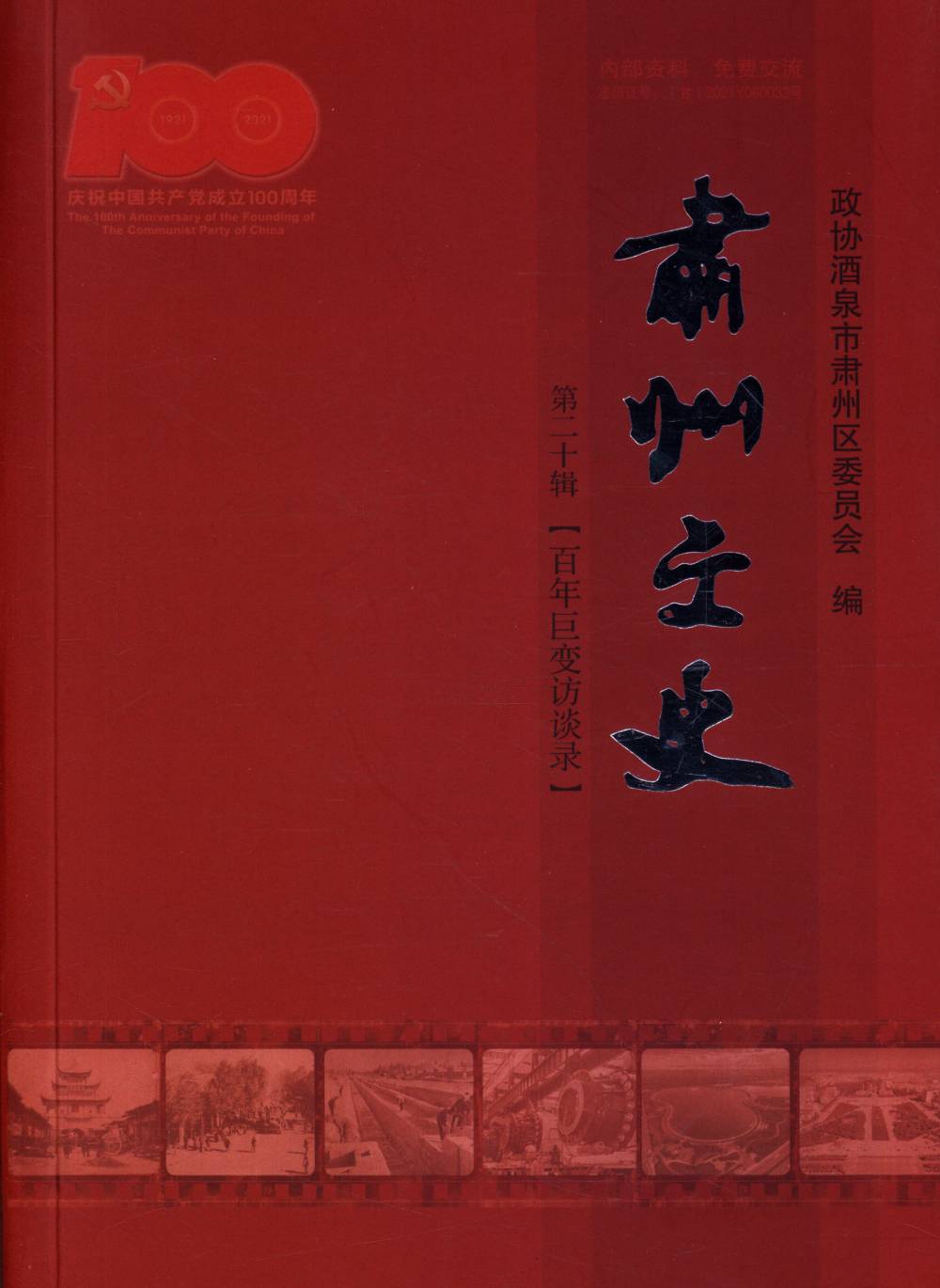
相关人物
刘永丰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