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冰河入梦来
| 内容出处: | 《肃州文史第十六辑》 图书 |
| 唯一号: | 292220020220005221 |
| 颗粒名称: | 铁马冰河入梦来 |
| 分类号: | K294.23 |
| 页数: | 24 |
| 页码: | 14-37 |
| 摘要: | 作者自传。 |
| 关键词: | 肃州 文史资料 |
内容
铁马冰河入梦来段生茂童年时代1936年1月,我出生在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怀茂乡东坝村一个农民家庭。老家的旧地名叫东坝圪塄,明长城从这里穿过,向东迤逦而去。因年代久远,长城仅剩下若干残存的土堆,当地人称“边墙”。东坝圪塄这个地名,究竟是根据历史上的水渠方位还是“边墙”走向而来,我不太清楚, 反正很早的时候人们就这么叫,叫得时间久了就成了地名。21世纪初进行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打破了原来的行政区划,怀茂乡与银达乡合并,统称为银达镇;东坝村并入了六分村,东坝这个地名就不复存在了。随着时间的流逝, 怀茂、东坝圪塄之类的老地名,或许就永远成了历史,只能一14一◎世龙面留在史书中和老人们的记忆中。
六七岁时,父亲送我到东坝庙读私塾,因年幼不懂事,看到别的孩子上三年级,我也要报三年级,私塾先生孙喜庆让我写出10个阿拉伯数字,结果我没有写全,闹了一场笑话。断断续续上了一年多私塾,接着又放了一年多羊,然后才到怀家沟公办全日制小学读了几年书。我的老师名叫祁世卿,是当地一个很有学问、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满打满算,我上学读书的时间不超过6年。但我非常勤奋,学习特别认真,经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当时和我一起读书的学童中后来也出过一些人才。从积善和我是邻居,年龄比我大, 人很机灵,后来当过甘肃省劳改局局长;段治本,论起来是我的本家叔叔,他当了兵,后来做到解放军的团政委。
1949年9月,解放大军西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与国民党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发表联名通电,宣布驻酒泉、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酒泉和平解放。但普通老百姓对这些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也很不了解。那一年,我刚13岁。
■ 当时,听说酒泉城里的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散兵游勇四处抢掠祸害百姓,直到王震的二兵团进驻酒泉后情况才有所好转。那段日子,城里的姨表姐要生孩子,为安全起见,就来到乡下,住在我家里坐月子。有一天,父母让我到-15-Su Zhou Wen Shi酒泉城里探听一下情况到底如何,我骑上从积善家的一匹马就向县城方向跑去。那是我第一次单独骑马走长路,胆子小,技术也很差,况且光身子马很不好骑,生怕掉下来。过去在家门上只骑过毛驴,没怎么骑过马,后来当了骑兵才知道了骑马的艰辛。走了半天,才来到北崖头,这里离县城已经不远了。忽然,我看见一溜马拉着炮车的国军队伍从北城门开出来,正向沙坝路槽方向行进,走在最前面的已经到了离我不远的地方。那些当兵的显然已经看见了我。我听见有个当兵的说,那个尕娃子骑的马好像是我们队伍上的。我吓坏了,赶紧打马躲进了路边的一条深沟,蹲了半天,等队伍过去了才骑马赶紧往回跑。回到家里,把情况告诉了父母,他们也为我的遭遇而感到后怕。多年以后, 我从李敬煊老先生的口中得知,我遇见的那支炮车队伍是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的一个炮兵营,在城北肖家花园驻防。敬煊老先生原系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的中校秘书, 属起义人员,他对当时军队的布防情况比较了解。
大哥段生才所在的金塔县自卫队,是当时的地方武装,也随同驻酒泉的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归向了共产党的阵营。大哥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军骑兵大队3连当了一名战士,他们的部队驻酒泉城南香庄庙,也就是现在的肃州区西峰乡张良沟村。
随着王震的二兵团进驻酒泉,地方秩序迅速安定下来,人民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二兵团紧接着要进军新疆,很多群众都自愿加入了拥军支前的行列。
母亲和爱霞姐姐也到城里看热闹,在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兴致勃勃地上街观看解放军宣传队的演出,心情十分高兴。当时,部队宣传动员地方女青年同解放军干部自由谈对象,结了婚就能随同大军进疆落户。16岁的爱霞姐姐,一来二去认识了一个名叫张政的河北籍营长,两人结婚后就跟随部队去了新疆。从那时起,我家就和解放军结下了紧密的亲缘关系。
替兄从军1950年,我刚满14岁。
那一年6月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两名解放军,是一个名叫段生辉的排长,还有一名战士。那位段生辉排长,听名字好像和我是本家弟兄,其实不是,后来得知他是个外' 地人。排长进门后就不断地打量我,经向我父母询问,得知我是这个家里的老二,就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想,排长满意地点了点头。排长告诉我父母,他是3军骑兵大队3连的,段生才就是他手下的兵。然后跟我父母商量说,既然段生才已经成了家,能不能让你家二儿子跟我们去当兵,把你家老大换回来,一来能让他照顾妻子,二来还可以帮助家里干农活。父母一听这话说得入情入理,马上就高兴地答应了。
段排长把我捎在马后边,来到了城南部队驻地香庄庙,领我进了一间屋子,说让我先待在这里,明天再给我办入伍手续,安排住的地方。说完,把门一关就走了。我一看,屋子里已有五六个人,都是当兵的,一个个神情沮丧,一言不发地蹲在墙角落里。
后来我才逐渐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那一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这个部队里有一些刚被收编不久的解放战士,听说中国马上要派兵入朝参战,心中顾虑重重,因而出现了开小差的现象。屋子里关着的那儿个兵,都是开小差后又被追回来的。我的大哥段生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私自脱离了部队。大哥离开部队后没敢回家,跑到县城东关一家米铺当了伙计。段排长他们明明是到我家里去找人,没见到我大哥的面,却突发奇想,带我来顶了缺。
火热的军营生活很快吸引了我,我也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在新中国灿烂的阳光下,我这个出生在农家院的孩子,心甘情愿地做了部队的一名小兵,开始了漫长的人生之路。
部队就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军事训练,我虽然年纪小,但训练很刻苦,逐步学会了骑马、射击、劈杀等战术动作。最初,杜占才是我们的排长(这个人后面我还要提到), 连长名叫段三儿(又是一个姓段的,也许是他们和我有缘吧)。段三儿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曾把几个开小差的士兵抓来吊在树上,让人打得吱哇乱叫o他时常板着个脸,不苟言笑;有时候为某一件事情发了火,还要扯着嗓门子骂人。然而连长对我却非常地和蔼可亲,除了手把手地给我传授军事技能外,生活上也是百般照顾。他曾对大家说,段生茂是全连年龄最小的战士,所有的人都要关心爱护他。现在想来,在我10年的军旅生涯中,与我朝夕相处过那些首长和战友,每个人都给予过我兄弟般的关心和照顾。从刚入伍时的排长杜占才、连长段三儿,到后来的山西籍连长尉庆、指导员范澜元,还有团长王三新、政委黄世源以及文化教员孔庆云、卜国云、炊事员刘华林等,我与他们在充满硝烟的战场和日常生活中结下的深情厚意,此生是永远难以忘怀的。我后来转业到地方,是石油师师长张复振亲自发的话,对这位身经百战的部队首长,我至今怀有深深的敬意。
训练结束后,因我年龄小,处事机灵,被分派到连部当了通讯员。那段日子,我们连离开酒泉到嘉峪关驻防。有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杜连长命令我独自一人外出执行任务,说有一份很重要的军事情报,放在远处乱坟岗坟碑里的一本书中,让我迅速取回。为给我壮胆,连长把他的手枪交给了我。老实说,我心里真的有些害怕。我把手枪上了顶门火,小心翼翼地摸到乱坟岗上,从坟碑的书中取了信,掉头就往回跑。回来后连长很高兴。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根本就没有什么情报,是他特意选择了一个恶劣的气候和环境来锻炼我的胆量。
参与剿匪时隔不久,部队奉命向西开进,参与剿匪行动。
当时,敦煌海子一带经常有土匪出没,袭扰地方政权,抢劫当地百姓的牛羊财物。他们中,除了部分散兵游勇外,主要是从新疆境内流窜过来的乌斯满股匪。关于这个人的情况,后面我还要详尽叙述。我们从嘉峪关出发,连续行军到达敦煌,大约用了半个月时间。骑马长途行军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小小年纪的我,第一次在马背上走这么远的路,其艰苦程度就更不用说了。出发第一站,从嘉峪关到玉门火烧沟,用了整整一天,长时间在马上颠簸,人都有点僵硬了,下马都很困难。但再苦再累,我都咬牙坚持着,不仅没有掉队,而且经常跑在最前面。当时我们的装备比较简单,除战马外,每人一支“七九”式步枪、几十发子弹、4颗手榴弹,脚上穿的是帆布长筒马靴,还有随身携带的部分干粮。部队到达敦煌后,驻城东王家庄子,又给每人配发了一把日式马刀,出鞘后寒光闪闪,锋利无比,确实是好刀。
有一天,部队得到报告,敦煌西湖瓦窑洞一带有土匪抢劫,我连奉命迅速出击追剿。我们顺着一片很开阔的湿地一路追下去,发现约有40多名土匪(从装束上看全是哈萨克人)正在远处打马拼命奔逃,边跑边转身向我们开枪射击。忽然,有一颗子弹从我坐骑黑马的项下前胸处穿皮而过,黑马受惊,但只是轻伤,并无大碍。我那匹黑马可真是一匹好马,身体伟岸挺拔,毛色光亮如漆,跑起来小走大颠,又快又稳,战友们都很喜欢它,我和它自然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关于坐骑黑马的故事,后面我还要说到。那次,我们没有追上土匪,只在沿途收容了很多被土匪抢劫后遗弃的牛羊,交给地方政府发还给了受害群众。
资料记载,从1951年1月下旬至3月,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统一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第2军、第3军、第4军的骑兵团、骆驼兵团和步兵第27团,由第3军军长黄新廷指挥,会剿流窜于柴达木盆地一带的乌斯满残余股匪,将其全歼。
我所在的部队是第3军骑兵大队(后改为团),我所参与的正是资料中说的那次剿匪战斗。
关于乌斯满这个人,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后来从有关资料中得知,他是西北现代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
乌斯满,大约出生于1895年,是新疆柯克托海莫勒和部落阿依吐罕小部落的普通牧民,崛起于四十年代阿山民变,从此半官半匪,盘踞北疆10年。此人在当地哈萨克族民众中具有较大影响,至今一些有关他的传奇故事还在哈萨克族牧民中口口相传。假使他不是站错了阵营、反对三区、袭击解放军的话,或许他会成为哈萨克人心目中的“嘎达梅林”。1939年,乌斯满参与第一次柯克托海牧民暴动后就被授予“巴图尔”(英雄、勇士)称号;1941年第二次柯克托海暴动被盛世才平息后,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大多被盛世才秘密杀害,他侥幸逃脱,带领少数人枪跑到布尔根河一带,啸聚山林,继续与新疆官府作对。新疆政局及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他曾得到外蒙等国的军事援助,势力迅速扩张。吴忠信、张治中等主新期间,均对其采取怀柔安抚策略,但都未能凑效。三区革命后,乌斯满被选举为阿山专员,但并未履行其职,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与人民政权为敌。1946年4月底,乌斯满被三区民族军击败后,一路向奇台败退,期间曾得到国民党军骑兵第1师的接应。1947年3月,新疆警备司令部送给乌斯满枪200支,子弹4万发,助其与民族军作战。1948年,在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的支持下,乌斯满策划成立了“反苏反共反三区革命委员会”,自任“副委员长”1949年春天,美国驻迪化代理领事马克南同乌斯满三次密商“反共”事宜。1949年9月25日,新疆国民党军由陶峙岳将军领衔宣布和平起义。在这种形势下,乌斯满仍然匪性不改,继续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1949年10月,乌斯满帮助美国间谍马克南出逃。12月26日,马克南在偷渡印藏边境时被藏军击毙。同时,乌斯满还加紧联络煽动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发动武装叛乱。1949年10月5日,包尔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极密,北京……乌斯满等反动分子,仍希率部集中青新交界之宿莽山,企图与国民党反动派联络。总之,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就在解放军入疆部队大举进入新疆之际,乌斯满联络哈密专员尧乐博士和国军骑7师少数军官,决定趁解放军立足未稳,迅速发动叛乱,企图以巴里坤为基地,东向哈密切断解放军与内地的联系,西向迪化夺取新疆省会。1950年2月,乌斯满指挥20多个部落约25000多不明真相的哈、维牧民发动了武装暴乱,从乾德、阜康开始,随即蔓延到东疆各地。叛军围攻奇台,袭击孚远,血洗九运街,杀害解放军政工人员和群众多人。2月5日,原国军骑5师20团千余人在昌吉叛乱;3月6日阜康骑7师特务营、镇西骑兵营全部,19、21团大部,共约4000余人叛乱;3月19日,尧乐博士指挥手下向哈密伊吾等地发动突然袭击,伊吾3000多人口,仅留下一个小孩,其余全部随匪逃走。到1950年4月,哈密、奇台等地叛匪已达6000多人,裹胁牧民近5万人。1950年4月1日,解放军16师副师长罗少伟等5人在七角井车帖辘泉被乌斯满杀害。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新疆军区迅速组建了剿匪总指挥部,王震为总指挥,张希钦为参谋长,下辖南、北两个前线剿匪指挥部,6军军长罗元发为北疆前线剿匪指挥部前敌总指挥,胡鉴为参谋长,其主要任务是“肃清乌斯满股匪和骑7师部分叛军”。3月16日,王震下达了围剿乌斯满的作战命令,经大、小红柳峡、二道白杨沟等数次激战,乌匪主力大部被歼。乌斯满在新疆无法立足,于1950年7月,带领残余人马,越过茫茫戈壁,逃到甘肃,经马鬃山、安西、敦煌,进入祁连山海子地区。解放军第3军奉命堵截乌斯满,立即在酒泉组建了剿匪支队,以3军驼兵团和27团为主力,高东生为支队长,安骏为政委。在此之前,3军骑兵团之1、2、3连,3军9师骑兵连和3军侦察连组成骑兵大队,李文彭为大队长,负责清剿安西、敦煌一带匪患,后因骑兵大队兵力不足,又派驼兵团和27团支援。这就是我们骑兵3连随大队提前进入敦煌的原因所在。
27团乘汽车抵达安西与驼兵团会合后,得到情报说乌斯满已经窜至红柳园一带,剿匪支队决定在芦草沟口阻击。当天入夜,27团跑步急行军抵达十工附近时,前锋发现芦草沟口以西有火光出现,剿匪部队迅速占领芦草沟口,但乌斯满已经率部从西面逃走。解放军两个团同时展开追击,从夜间2点一直追击到第二天13时,部队人困马乏,步兵无法再追击,只好撤往安西休整。安骏带领驼兵和骑兵继续前进,到鳖盖与先前部署在那里的骑兵大队会合。
1950年7月,三支剿匪部队在桥子击溃了企图袭击安西县城的骑5军残匪和当地土匪武装后,我们骑兵大队一路追击到祁连山方才停止。这部分残匪越过祁连山后仅余38人,1950年8月与尧乐博士残部会合,11月结伙向西藏逃窜,尧乐博士进入拉达克逃往台湾,骑5军残匪未能进入拉达克,掉头返回青海,1951年被当地公安部队歼灭。
安骏带领驼兵和骑兵部队深入祁连山搜寻乌斯满,发现乌匪残部已翻山进入海子地区,因剿匪部队无进山准备,只好经党城湾、石包城返回安西县城。
乌斯满逃亡甘、青,引发了新一轮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南迁浪潮。1950年8月,乌斯满带领40多人进入阿克塞海子地区后,又有加纳布里部350多人、沙拉黑坦部280多人、哈布德里部130多人、则拉提巴依部150多人先后抵达海子地区;另外还有近千名哈萨克族牧民从新疆镇西迁移到敦煌安南坝一带游牧。这些哈萨克牧民的到来,给当地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乌斯满残匪不断进行骚扰和破坏,给当地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共酒泉地委专门成立了“争取哈萨克族工作委员会”,多次派人进入海子地区寻找哈萨克部落,说服他们脱离乌斯满的控制,搬迁到敦煌附近居住。
就在乌斯满抵达海子不久,敦煌县派出已两次进入过海子地区的李万祥和来推福第三次前往海子,侦察乌斯满的动静并争取受蒙蔽的哈族牧民。李、来二人不顾生命危险,曾两次见到乌斯满,并送给他茶叶、面粉等物,说明当时政府对乌斯满仍抱有政治争取的良好愿望。
李万祥、来推福此行成果颇大,首先弄清了乌斯满的确在海子,并准备在那里过冬;其二敦煌南山哈族乱民虽多,但大部分是主动入伙者,政治争取的可能性不大,必须辅之以强有力的军事进剿。1951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发出指示:“对乌斯满……不能只当作一个落后民族部落与土匪处理,据各方材料证明,是边疆国特及惯匪与大土耳其相结合,反苏反共最坚决的反动集团。……进行谈判与招抚工作并不能因而影响我原来的军事部署……” 活捉匪首根据原来的军事部署,我所在的3军骑兵大队和驼兵团合并为一个团(战后,我团成为西北军区独立骑兵第3团,李文彭为团长,安骏为政委),担负起主要的攻击战斗任务,27团因为是步兵,则被分配担任运输和驻剿任务。为了配合这次军事进剿行动,酒泉地区动员了7个县的干部,组建了50多个骆驼大队,给部队运送给养、弹药。
1951年2月14日,3军骑兵团在敦煌集结完毕,15日由3军军长黄新廷亲自带领,悄悄向南湖运动,准备进山。在南湖,剿匪部队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李文彭带领骑兵大队,派来推福担任向导,经五个泉子、后塘,奔袭海子;西路由安骏指挥驼兵团,经大鄂博图向海子运动。时值严冬,茫茫戈壁荒漠,到处是冰天雪地,我们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子,仍然冷得受不了,人人都在咬牙坚持着。由于天气恶劣,部队行进十分困难,穿越一条15公里的山沟就花费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我们骑兵大队行军速度相对快些,仅用一天时间就到达了指定地点,而驼兵团从南湖到大鄂博图走了整整两天。2月19日拂晓,两路部队在突击位置会合。部队首先活捉了敌人的哨兵,然后在俘虏的带领下,悄无声息地摸掉了数个帐篷,终于接近了乌斯满部落的宿营地。
就在距离我们大约2华里的山包下,是一个小湖滩,中间隔着一道冰河,两岸平坦地带,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很多颜色不一的帐篷。听说大名鼎鼎的乌斯满就藏在这里,我们的心情都非常兴奋。我们采用了侦察兵常用的战术,3人一组向分散的帐篷摸去,1人担任警戒,1人开门揭帘,另外1人进帐篷收缴枪支解除对方武装。我骑兵大队的行动十分顺利,到天亮的时候,已经解决了大约50多顶帐篷,里面的人在熟睡中全部被缴械做了俘虏。
这时天已大亮,群山沉静在飘渺的晨雾中尚未完全醒来。忽然传来几声沉闷的枪响,原来是加纳布里最先听到了动静,他以为是蒙古人寻机偷袭哈萨克人,于是仓惶开枪。枪声一起,驼兵团的重机枪和追击炮一齐开火,压制住对方的火力,驼兵和骑兵同时展开攻击,向指定的目标前进。帐篷里的哈萨克人听到枪声顿时乱作一团,蜂拥而出,或骑马,或徒步,夺路四处狂奔。剿匪部队穷追不舍,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3点左右,共俘虏、收容了2500多人,经过仔细甄别,这些人中间没有乌斯满。剿匪部队将俘虏或收容的人员陆续押解、转移出山。那个加纳布里被活捉后态度死硬,在押解途中试图夺取解放军战士的枪支进行反抗,被当场击毙。
剿匪部队紧急分析了乌斯满可能逃走的路线:马海方向已经有青海骑兵第2团守卫;昆仑山方向有近400公里的亚巴尔戈壁,唯一的通道已经被我驼兵团2连先期占领无法通过;惟有向西北安南坝方向逃走的可能行最大。
黄新廷军长当即决定,由我们骑兵大队率先追击。
李文彭带领骑兵大队两个连及一部电台追击了数公里,抓获了一个名叫沙发阿里的掉队土匪,此人供出乌斯满骑着白马就在前面不远处。得知这一消息,我们全体战士群情振奋,忘却了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首长一声令下,个个奋勇争先,拍马追了上去。
我的坐骑黑马关键时刻一点也不甘落后,跑得又快又稳,加上我年小体轻,一度竟跑到了队伍的最前头。
部队追击了几个小时后,跟随乌斯满奔逃的最后约50人陆续掉队做了俘虏,唯有乌斯满仍然沿着海子南岸向安南坝方向狂奔。又追了一阵,我们渐渐人困马乏,与乌斯满的距离越拉越大,眼看就要被他甩掉。就在这时,我和文化教员孔庆云、炊事员刘华林急中生智,拍马跃上海子冰面,抄捷径向南岸的乌斯满追去,这样一来,双方的距离马上就缩短了不少。我连战士宋兴、黄银娃、朱生仓等人也紧随其后追了上来。虽然我们的战马四蹄上都有带钉的铁掌,可以起到较好的防滑作用,但海子冰面实在是太光滑了,马踩上去小心翼翼,不敢放开来跑。尽管如此,我的坐骑黑马还是始终保持着一马当先的位置。这时,我身后的两名战士连人带马滑倒在冰面上。乌斯满边跑边向我们开枪射击,子弹不时地擦着我的头皮飞过,但我仍然毫不犹豫地拼命追赶。近了,更近了,我已经看清了乌斯满肥胖的身材和那张生满横肉的脸,当时那种兴奋豪迈的心情,今天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但是,就在我快要接近乌斯满的时候,乌斯满回马一枪,子弹擦着黑马前蹄下的冰面呼啸而过,黑马受惊跃起,蹄下打滑,紧接着就重重地倒在了冰面 ±0我从马背上被摔了出去,虽然没有受伤,但却摔得很重,一时头昏眼花,难以站立起来。此时,乌斯满又接连开了两枪,炊事员刘华林和另一名战士的马也先后被击倒,我方追兵只剩下文化教员孔庆云一个人。孔庆云没有放弃,继续紧紧追赶乌斯满。乌斯满在拍马狂奔中频频侧身射击。也许是乌斯满气数已尽,这个曾经是神枪手的“巴图尔”,竟然屡射不中。他见追兵只有一个人,竟然翻身下马,把叉子枪支在地上射击,第一枪提前量太多,打在孔庆云马前蹄的冰上,第二枪只射穿了孔庆云的裤管。这时孔庆云已经策马上岸,来到了乌斯满的近前。
事后,孔庆云向我们讲述了当时那段惊心动魄的场面: “乌匪见势不妙,急忙从地上爬起来,双手紧握叉子枪,恶狠狠地向我的双眼戳来,我本能地将头一偏,一股枪叉戳伤了我的面颊。我强忍剧痛,一把抓住了乌匪的枪管死死不放,乌匪拼命把我往马下拽,我趁下跌的惯力把自己的枪搂在怀里,狠命地夺过了乌匪的枪,然后一跃而起,乌匪此时狂怒至极,像个凶神恶煞,气急败坏地将我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趁势骑在我身上。我试图把乌匪翻在身下,但体重100多公斤的乌匪,犹如一头野牛死死地压住我。在动弹不得的情况下,我赶忙把手中的枪甩了出去。此时,乌匪突然从靴筒里拔出一柄带鞘的匕首,我急中生智,趁其脱去刀鞘的空当,一把抓住乌匪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狠狠的向后撅,使其无法脱去刀鞘;我更加用力地向后撅他的两根手指,乌匪负痛,匕首被甩了出去……” 后面的情景是这样的: 就在万分危急的关头,炊事员刘华林飞马赶到。刘华林的马被乌斯满打伤后,他急忙换乘了另一匹马,但这匹马性子烈,他刚骑上去,马就脱缰飞奔而去,速度之快竟使刘华林没有来得及接过战友递给他的枪。赤手空拳的刘华林赶到后,从地上捡起乌斯满的叉子枪,向乌斯满的后背狠狠地一枪捅去,乌斯满像野兽一样惨叫一声倒在了一边。孔庆云、刘华林和随后赶到的战友,七手八脚地把乌斯满捆了起来。
活捉匪首乌斯满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
我当时被摔晕后,经战友们救起,又换乘了一匹战马随后赶了上去。假如不是中间出现那个小插曲,首先同乌斯满只身搏斗的很可能就是我。我的坐骑黑马经历了那次变故,虽然暂时不能负重,但始终没有离开过部队,回到驻地后,在我的悉心照料下很快得到康复,又同我一起投入了新的战斗。
乌斯满被活捉后,从其身上搜出新疆警备司令部印章一枚、委任状数张。剿匪部队将乌斯满捆在骆驼背上押回海子,随后又押至敦煌。
新华社于1951年2月23日发布消息:“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某部,「本月19日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以北、甘青两省交界的海子,一举生擒为西北各族人民痛恨入骨的美帝国主义武装特务乌斯满匪首。” 海子一战,全歼乌斯满、哈巴斯、加纳布里、沙拉黑坦、木沙巴等5个部落,俘虏乌斯满、哈巴斯以下263人,毙加纳布里以下39人,俘虏叛匪家属11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19支,短枪8支,冲锋枪1支,各种子弹6874发,马5710匹,骆驼533峰,牛20头,羊8300只,并威慑、争取了其他3个部落向解放军投降。
1953年3月14日,乌斯满被押解到迪化。1951年4月29日,新疆各界召开万余人参加的乌斯满公审大会,王震讲话后,审判长包尔汉、副审判长饶正锡分别以维、汉两种语言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3、4、5、7、9、10、17条之规定,判处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匪首乌斯满死刑,当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乌斯满被活捉后,海子一带的哈萨克牧民纷纷外逃,藏匿于深山荒漠之中,期间经人民政府耐心说服教育,大部分集中于安南坝和敦煌附近,50年代中期陆续返回新疆。
乌斯满的儿子谢尔德曼在海子战斗中逃脱,他带领乌斯满手下残存的数人向新疆逃窜。剿匪部队派骑兵随后追赶,我也参加了这次追剿行动。我们追了10多天后,只在途中见到被残匪烧毁的3辆军车残骸,听说谢尔德曼已过了星星峡,只好奉命返回。
谢尔德曼于1951年5月逃到新疆奇台一带,鼓动当地已归附政府的几个哈萨克部落重新叛乱,遭到解放军剿匪部队和当地政府民兵痛击后,流窜到自己的老家阿山青河、富蕴一带,又鼓动胡尔曼部落重新叛乱,一度围攻青河、焚烧粮仓、啸聚山林,颇有乃父深山为匪的气势,解放军屡次围剿,均无法将其全歼。1952年9月15日,谢尔德曼在阿山专署的多次劝说下到承化向人民政府投降。随后,新疆方面派专人到甘肃敦煌将谢尔德曼的家属接回,并安排谢尔德曼在阿勒泰专区畜牧科任副科长,后调任伊犁州畜牧局任副局长直到病逝。
追剿残匪海子战斗后,上级给孔庆云记了特等功,给刘华林记了大功,给我记了二等功。由于我年纪小,当时在整个骑兵团一度名气很大,几乎人人都知道3连的通讯员段生茂是个小英雄,新任团长王三新则亲切的称我为“我们的少年英雄”。
追剿乌斯满的战斗经过,后来被载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戈壁凯歌——西北大剿匪》等文献书籍,电影工作者还以此为题材拍摄了故事片《沙漠追匪记》在全国上映。活捉乌斯满后,当地还有一些残匪没有肃清,这些人隐藏在哈萨克牧民中间,鼓动重新叛乱,伺机制造事端。我们的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后,又投入了二次剿匪战斗。
1952年,酒泉军分区的两名干部在长草沟被杀害。听说这两个人死得很惨,被掏了心、扒了肺、割了生殖器。酒泉军地双方立即展开调查,结果证实,长草沟的残匪的确鼓动当地哈萨克牧民发动了重新叛乱,他们裹胁哈萨克群众,扶老携幼,日夜兼程逃往南山和青海柴达木一带。长草沟附近驻有驼兵团的一个排,叛匪出逃时把驼兵排的骆驼也赶走了。驼兵排随后追至马海,又遭到埋伏在这里的土匪袭击,死伤数人。我连奉命追剿,在戈壁荒漠中奔波了数日,只收容了部分老弱妇孺和散落的牛羊牲畜。那些受土匪蒙蔽出逃的哈萨克牧民,后来大部分又陆续回到了原地,其中个别有罪恶的都受到了相应惩处。2004年,我陪同省人大常委李善平到阿克塞县视察,午间在一户哈萨克牧民家里吃饭,喧谈中得知,那家的男主人正是当年长草沟叛逃的残匪之一,曾被人民政府依法判刑13年。攀谈中,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我和那个已经变得极其衰老的哈萨克牧人都感慨颇多。
当时的情况那真叫艰苦。我们剿匪部队一连好几个月都在茫茫戈壁荒漠中奔走,人和马都疲惫至极,顾不上洗脸,人人蓬头垢面,只看见两只眼睛在动。战友们说,灰尘是老天爷为我们擦的护肤霜,一旦洗净,又白又亮。那只不过是我们的战士在特殊的环境下自我安慰、苦中作乐罢了。无论是烈日炎炎的正午,还是刮风下雨的夜晚,部队始终没有停止过追剿敌人的步伐。白天人不离枪、马不离鞍,无休止地奔跑;夜晚头枕马鞍、怀抱枪支、裹上皮大衣随便就地一躺,还不能睡得太死,一有动静就要马上出发…… 时间一长,人人身上虱子成堆,连马靴里都是。偶尔遇上白天宿营,我们就把内衣、马靴脱下来放到石头上砸,一砸一片血.. 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他67岁时作过一首诗,题目叫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我觉得这首诗堪称是我们那段军旅生活的真实写照。战士心目中的“轮台”,不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吗?后来,每当我听到蒋大为演唱的《骏马奔驰保边疆》时,当年的那种豪情壮志就禁不住油然而生。没当过骑兵的人,决不可能有这种体会和感受。在那段时间内,新疆剿匪部队的一排人马在大戈壁上失踪,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帮助寻找。我们深入到冷湖、柴达木一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旷野中四处搜寻。由于队伍远离驻地且行踪不定,给养供应不上,没有吃的,只能就地猎取野牛、野羊充饥,真是历尽了艰辛。经数日搜寻,我们只在一个小河沟的坡坎处找到了一名战士的遗体,其余的人没一点踪迹。那一带野狼成群,夜里围着我们的宿营地嗥叫不止。根据情况判断,那一排新疆骑兵已无生还的可能,我们只好草草掩埋了那个战士的遗体后撤回。
1954年,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石油部的一个勘探队深入到青海芒崖一带勘探石油,因为那里渺无人烟,且经常有土匪出没,我们奉命前往担负保卫任务,在芒崖驻守了半年。期间,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是一片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我们所处的环境可想而知。
那一年,我们连改为西北军区独立骑兵第3团第5连,我被上级选调到团里当了一名文书,部队驻敦煌西云观,是当地的一个道教场所。同年,全国人民慰问团组织西安易俗社赴敦煌慰问演出,我有幸见到了孟娥云、肖若兰、肖玉玲等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
1956年,上级任命我为骑兵团特务连通讯排排长。
六七岁时,父亲送我到东坝庙读私塾,因年幼不懂事,看到别的孩子上三年级,我也要报三年级,私塾先生孙喜庆让我写出10个阿拉伯数字,结果我没有写全,闹了一场笑话。断断续续上了一年多私塾,接着又放了一年多羊,然后才到怀家沟公办全日制小学读了几年书。我的老师名叫祁世卿,是当地一个很有学问、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满打满算,我上学读书的时间不超过6年。但我非常勤奋,学习特别认真,经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当时和我一起读书的学童中后来也出过一些人才。从积善和我是邻居,年龄比我大, 人很机灵,后来当过甘肃省劳改局局长;段治本,论起来是我的本家叔叔,他当了兵,后来做到解放军的团政委。
1949年9月,解放大军西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与国民党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发表联名通电,宣布驻酒泉、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酒泉和平解放。但普通老百姓对这些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也很不了解。那一年,我刚13岁。
■ 当时,听说酒泉城里的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散兵游勇四处抢掠祸害百姓,直到王震的二兵团进驻酒泉后情况才有所好转。那段日子,城里的姨表姐要生孩子,为安全起见,就来到乡下,住在我家里坐月子。有一天,父母让我到-15-Su Zhou Wen Shi酒泉城里探听一下情况到底如何,我骑上从积善家的一匹马就向县城方向跑去。那是我第一次单独骑马走长路,胆子小,技术也很差,况且光身子马很不好骑,生怕掉下来。过去在家门上只骑过毛驴,没怎么骑过马,后来当了骑兵才知道了骑马的艰辛。走了半天,才来到北崖头,这里离县城已经不远了。忽然,我看见一溜马拉着炮车的国军队伍从北城门开出来,正向沙坝路槽方向行进,走在最前面的已经到了离我不远的地方。那些当兵的显然已经看见了我。我听见有个当兵的说,那个尕娃子骑的马好像是我们队伍上的。我吓坏了,赶紧打马躲进了路边的一条深沟,蹲了半天,等队伍过去了才骑马赶紧往回跑。回到家里,把情况告诉了父母,他们也为我的遭遇而感到后怕。多年以后, 我从李敬煊老先生的口中得知,我遇见的那支炮车队伍是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的一个炮兵营,在城北肖家花园驻防。敬煊老先生原系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的中校秘书, 属起义人员,他对当时军队的布防情况比较了解。
大哥段生才所在的金塔县自卫队,是当时的地方武装,也随同驻酒泉的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归向了共产党的阵营。大哥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军骑兵大队3连当了一名战士,他们的部队驻酒泉城南香庄庙,也就是现在的肃州区西峰乡张良沟村。
随着王震的二兵团进驻酒泉,地方秩序迅速安定下来,人民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二兵团紧接着要进军新疆,很多群众都自愿加入了拥军支前的行列。
母亲和爱霞姐姐也到城里看热闹,在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兴致勃勃地上街观看解放军宣传队的演出,心情十分高兴。当时,部队宣传动员地方女青年同解放军干部自由谈对象,结了婚就能随同大军进疆落户。16岁的爱霞姐姐,一来二去认识了一个名叫张政的河北籍营长,两人结婚后就跟随部队去了新疆。从那时起,我家就和解放军结下了紧密的亲缘关系。
替兄从军1950年,我刚满14岁。
那一年6月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两名解放军,是一个名叫段生辉的排长,还有一名战士。那位段生辉排长,听名字好像和我是本家弟兄,其实不是,后来得知他是个外' 地人。排长进门后就不断地打量我,经向我父母询问,得知我是这个家里的老二,就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想,排长满意地点了点头。排长告诉我父母,他是3军骑兵大队3连的,段生才就是他手下的兵。然后跟我父母商量说,既然段生才已经成了家,能不能让你家二儿子跟我们去当兵,把你家老大换回来,一来能让他照顾妻子,二来还可以帮助家里干农活。父母一听这话说得入情入理,马上就高兴地答应了。
段排长把我捎在马后边,来到了城南部队驻地香庄庙,领我进了一间屋子,说让我先待在这里,明天再给我办入伍手续,安排住的地方。说完,把门一关就走了。我一看,屋子里已有五六个人,都是当兵的,一个个神情沮丧,一言不发地蹲在墙角落里。
后来我才逐渐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那一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这个部队里有一些刚被收编不久的解放战士,听说中国马上要派兵入朝参战,心中顾虑重重,因而出现了开小差的现象。屋子里关着的那儿个兵,都是开小差后又被追回来的。我的大哥段生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私自脱离了部队。大哥离开部队后没敢回家,跑到县城东关一家米铺当了伙计。段排长他们明明是到我家里去找人,没见到我大哥的面,却突发奇想,带我来顶了缺。
火热的军营生活很快吸引了我,我也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在新中国灿烂的阳光下,我这个出生在农家院的孩子,心甘情愿地做了部队的一名小兵,开始了漫长的人生之路。
部队就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军事训练,我虽然年纪小,但训练很刻苦,逐步学会了骑马、射击、劈杀等战术动作。最初,杜占才是我们的排长(这个人后面我还要提到), 连长名叫段三儿(又是一个姓段的,也许是他们和我有缘吧)。段三儿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曾把几个开小差的士兵抓来吊在树上,让人打得吱哇乱叫o他时常板着个脸,不苟言笑;有时候为某一件事情发了火,还要扯着嗓门子骂人。然而连长对我却非常地和蔼可亲,除了手把手地给我传授军事技能外,生活上也是百般照顾。他曾对大家说,段生茂是全连年龄最小的战士,所有的人都要关心爱护他。现在想来,在我10年的军旅生涯中,与我朝夕相处过那些首长和战友,每个人都给予过我兄弟般的关心和照顾。从刚入伍时的排长杜占才、连长段三儿,到后来的山西籍连长尉庆、指导员范澜元,还有团长王三新、政委黄世源以及文化教员孔庆云、卜国云、炊事员刘华林等,我与他们在充满硝烟的战场和日常生活中结下的深情厚意,此生是永远难以忘怀的。我后来转业到地方,是石油师师长张复振亲自发的话,对这位身经百战的部队首长,我至今怀有深深的敬意。
训练结束后,因我年龄小,处事机灵,被分派到连部当了通讯员。那段日子,我们连离开酒泉到嘉峪关驻防。有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杜连长命令我独自一人外出执行任务,说有一份很重要的军事情报,放在远处乱坟岗坟碑里的一本书中,让我迅速取回。为给我壮胆,连长把他的手枪交给了我。老实说,我心里真的有些害怕。我把手枪上了顶门火,小心翼翼地摸到乱坟岗上,从坟碑的书中取了信,掉头就往回跑。回来后连长很高兴。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根本就没有什么情报,是他特意选择了一个恶劣的气候和环境来锻炼我的胆量。
参与剿匪时隔不久,部队奉命向西开进,参与剿匪行动。
当时,敦煌海子一带经常有土匪出没,袭扰地方政权,抢劫当地百姓的牛羊财物。他们中,除了部分散兵游勇外,主要是从新疆境内流窜过来的乌斯满股匪。关于这个人的情况,后面我还要详尽叙述。我们从嘉峪关出发,连续行军到达敦煌,大约用了半个月时间。骑马长途行军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小小年纪的我,第一次在马背上走这么远的路,其艰苦程度就更不用说了。出发第一站,从嘉峪关到玉门火烧沟,用了整整一天,长时间在马上颠簸,人都有点僵硬了,下马都很困难。但再苦再累,我都咬牙坚持着,不仅没有掉队,而且经常跑在最前面。当时我们的装备比较简单,除战马外,每人一支“七九”式步枪、几十发子弹、4颗手榴弹,脚上穿的是帆布长筒马靴,还有随身携带的部分干粮。部队到达敦煌后,驻城东王家庄子,又给每人配发了一把日式马刀,出鞘后寒光闪闪,锋利无比,确实是好刀。
有一天,部队得到报告,敦煌西湖瓦窑洞一带有土匪抢劫,我连奉命迅速出击追剿。我们顺着一片很开阔的湿地一路追下去,发现约有40多名土匪(从装束上看全是哈萨克人)正在远处打马拼命奔逃,边跑边转身向我们开枪射击。忽然,有一颗子弹从我坐骑黑马的项下前胸处穿皮而过,黑马受惊,但只是轻伤,并无大碍。我那匹黑马可真是一匹好马,身体伟岸挺拔,毛色光亮如漆,跑起来小走大颠,又快又稳,战友们都很喜欢它,我和它自然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关于坐骑黑马的故事,后面我还要说到。那次,我们没有追上土匪,只在沿途收容了很多被土匪抢劫后遗弃的牛羊,交给地方政府发还给了受害群众。
资料记载,从1951年1月下旬至3月,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统一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第2军、第3军、第4军的骑兵团、骆驼兵团和步兵第27团,由第3军军长黄新廷指挥,会剿流窜于柴达木盆地一带的乌斯满残余股匪,将其全歼。
我所在的部队是第3军骑兵大队(后改为团),我所参与的正是资料中说的那次剿匪战斗。
关于乌斯满这个人,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后来从有关资料中得知,他是西北现代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
乌斯满,大约出生于1895年,是新疆柯克托海莫勒和部落阿依吐罕小部落的普通牧民,崛起于四十年代阿山民变,从此半官半匪,盘踞北疆10年。此人在当地哈萨克族民众中具有较大影响,至今一些有关他的传奇故事还在哈萨克族牧民中口口相传。假使他不是站错了阵营、反对三区、袭击解放军的话,或许他会成为哈萨克人心目中的“嘎达梅林”。1939年,乌斯满参与第一次柯克托海牧民暴动后就被授予“巴图尔”(英雄、勇士)称号;1941年第二次柯克托海暴动被盛世才平息后,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大多被盛世才秘密杀害,他侥幸逃脱,带领少数人枪跑到布尔根河一带,啸聚山林,继续与新疆官府作对。新疆政局及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他曾得到外蒙等国的军事援助,势力迅速扩张。吴忠信、张治中等主新期间,均对其采取怀柔安抚策略,但都未能凑效。三区革命后,乌斯满被选举为阿山专员,但并未履行其职,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与人民政权为敌。1946年4月底,乌斯满被三区民族军击败后,一路向奇台败退,期间曾得到国民党军骑兵第1师的接应。1947年3月,新疆警备司令部送给乌斯满枪200支,子弹4万发,助其与民族军作战。1948年,在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的支持下,乌斯满策划成立了“反苏反共反三区革命委员会”,自任“副委员长”1949年春天,美国驻迪化代理领事马克南同乌斯满三次密商“反共”事宜。1949年9月25日,新疆国民党军由陶峙岳将军领衔宣布和平起义。在这种形势下,乌斯满仍然匪性不改,继续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1949年10月,乌斯满帮助美国间谍马克南出逃。12月26日,马克南在偷渡印藏边境时被藏军击毙。同时,乌斯满还加紧联络煽动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发动武装叛乱。1949年10月5日,包尔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极密,北京……乌斯满等反动分子,仍希率部集中青新交界之宿莽山,企图与国民党反动派联络。总之,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就在解放军入疆部队大举进入新疆之际,乌斯满联络哈密专员尧乐博士和国军骑7师少数军官,决定趁解放军立足未稳,迅速发动叛乱,企图以巴里坤为基地,东向哈密切断解放军与内地的联系,西向迪化夺取新疆省会。1950年2月,乌斯满指挥20多个部落约25000多不明真相的哈、维牧民发动了武装暴乱,从乾德、阜康开始,随即蔓延到东疆各地。叛军围攻奇台,袭击孚远,血洗九运街,杀害解放军政工人员和群众多人。2月5日,原国军骑5师20团千余人在昌吉叛乱;3月6日阜康骑7师特务营、镇西骑兵营全部,19、21团大部,共约4000余人叛乱;3月19日,尧乐博士指挥手下向哈密伊吾等地发动突然袭击,伊吾3000多人口,仅留下一个小孩,其余全部随匪逃走。到1950年4月,哈密、奇台等地叛匪已达6000多人,裹胁牧民近5万人。1950年4月1日,解放军16师副师长罗少伟等5人在七角井车帖辘泉被乌斯满杀害。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新疆军区迅速组建了剿匪总指挥部,王震为总指挥,张希钦为参谋长,下辖南、北两个前线剿匪指挥部,6军军长罗元发为北疆前线剿匪指挥部前敌总指挥,胡鉴为参谋长,其主要任务是“肃清乌斯满股匪和骑7师部分叛军”。3月16日,王震下达了围剿乌斯满的作战命令,经大、小红柳峡、二道白杨沟等数次激战,乌匪主力大部被歼。乌斯满在新疆无法立足,于1950年7月,带领残余人马,越过茫茫戈壁,逃到甘肃,经马鬃山、安西、敦煌,进入祁连山海子地区。解放军第3军奉命堵截乌斯满,立即在酒泉组建了剿匪支队,以3军驼兵团和27团为主力,高东生为支队长,安骏为政委。在此之前,3军骑兵团之1、2、3连,3军9师骑兵连和3军侦察连组成骑兵大队,李文彭为大队长,负责清剿安西、敦煌一带匪患,后因骑兵大队兵力不足,又派驼兵团和27团支援。这就是我们骑兵3连随大队提前进入敦煌的原因所在。
27团乘汽车抵达安西与驼兵团会合后,得到情报说乌斯满已经窜至红柳园一带,剿匪支队决定在芦草沟口阻击。当天入夜,27团跑步急行军抵达十工附近时,前锋发现芦草沟口以西有火光出现,剿匪部队迅速占领芦草沟口,但乌斯满已经率部从西面逃走。解放军两个团同时展开追击,从夜间2点一直追击到第二天13时,部队人困马乏,步兵无法再追击,只好撤往安西休整。安骏带领驼兵和骑兵继续前进,到鳖盖与先前部署在那里的骑兵大队会合。
1950年7月,三支剿匪部队在桥子击溃了企图袭击安西县城的骑5军残匪和当地土匪武装后,我们骑兵大队一路追击到祁连山方才停止。这部分残匪越过祁连山后仅余38人,1950年8月与尧乐博士残部会合,11月结伙向西藏逃窜,尧乐博士进入拉达克逃往台湾,骑5军残匪未能进入拉达克,掉头返回青海,1951年被当地公安部队歼灭。
安骏带领驼兵和骑兵部队深入祁连山搜寻乌斯满,发现乌匪残部已翻山进入海子地区,因剿匪部队无进山准备,只好经党城湾、石包城返回安西县城。
乌斯满逃亡甘、青,引发了新一轮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南迁浪潮。1950年8月,乌斯满带领40多人进入阿克塞海子地区后,又有加纳布里部350多人、沙拉黑坦部280多人、哈布德里部130多人、则拉提巴依部150多人先后抵达海子地区;另外还有近千名哈萨克族牧民从新疆镇西迁移到敦煌安南坝一带游牧。这些哈萨克牧民的到来,给当地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乌斯满残匪不断进行骚扰和破坏,给当地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共酒泉地委专门成立了“争取哈萨克族工作委员会”,多次派人进入海子地区寻找哈萨克部落,说服他们脱离乌斯满的控制,搬迁到敦煌附近居住。
就在乌斯满抵达海子不久,敦煌县派出已两次进入过海子地区的李万祥和来推福第三次前往海子,侦察乌斯满的动静并争取受蒙蔽的哈族牧民。李、来二人不顾生命危险,曾两次见到乌斯满,并送给他茶叶、面粉等物,说明当时政府对乌斯满仍抱有政治争取的良好愿望。
李万祥、来推福此行成果颇大,首先弄清了乌斯满的确在海子,并准备在那里过冬;其二敦煌南山哈族乱民虽多,但大部分是主动入伙者,政治争取的可能性不大,必须辅之以强有力的军事进剿。1951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发出指示:“对乌斯满……不能只当作一个落后民族部落与土匪处理,据各方材料证明,是边疆国特及惯匪与大土耳其相结合,反苏反共最坚决的反动集团。……进行谈判与招抚工作并不能因而影响我原来的军事部署……” 活捉匪首根据原来的军事部署,我所在的3军骑兵大队和驼兵团合并为一个团(战后,我团成为西北军区独立骑兵第3团,李文彭为团长,安骏为政委),担负起主要的攻击战斗任务,27团因为是步兵,则被分配担任运输和驻剿任务。为了配合这次军事进剿行动,酒泉地区动员了7个县的干部,组建了50多个骆驼大队,给部队运送给养、弹药。
1951年2月14日,3军骑兵团在敦煌集结完毕,15日由3军军长黄新廷亲自带领,悄悄向南湖运动,准备进山。在南湖,剿匪部队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李文彭带领骑兵大队,派来推福担任向导,经五个泉子、后塘,奔袭海子;西路由安骏指挥驼兵团,经大鄂博图向海子运动。时值严冬,茫茫戈壁荒漠,到处是冰天雪地,我们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子,仍然冷得受不了,人人都在咬牙坚持着。由于天气恶劣,部队行进十分困难,穿越一条15公里的山沟就花费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我们骑兵大队行军速度相对快些,仅用一天时间就到达了指定地点,而驼兵团从南湖到大鄂博图走了整整两天。2月19日拂晓,两路部队在突击位置会合。部队首先活捉了敌人的哨兵,然后在俘虏的带领下,悄无声息地摸掉了数个帐篷,终于接近了乌斯满部落的宿营地。
就在距离我们大约2华里的山包下,是一个小湖滩,中间隔着一道冰河,两岸平坦地带,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很多颜色不一的帐篷。听说大名鼎鼎的乌斯满就藏在这里,我们的心情都非常兴奋。我们采用了侦察兵常用的战术,3人一组向分散的帐篷摸去,1人担任警戒,1人开门揭帘,另外1人进帐篷收缴枪支解除对方武装。我骑兵大队的行动十分顺利,到天亮的时候,已经解决了大约50多顶帐篷,里面的人在熟睡中全部被缴械做了俘虏。
这时天已大亮,群山沉静在飘渺的晨雾中尚未完全醒来。忽然传来几声沉闷的枪响,原来是加纳布里最先听到了动静,他以为是蒙古人寻机偷袭哈萨克人,于是仓惶开枪。枪声一起,驼兵团的重机枪和追击炮一齐开火,压制住对方的火力,驼兵和骑兵同时展开攻击,向指定的目标前进。帐篷里的哈萨克人听到枪声顿时乱作一团,蜂拥而出,或骑马,或徒步,夺路四处狂奔。剿匪部队穷追不舍,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3点左右,共俘虏、收容了2500多人,经过仔细甄别,这些人中间没有乌斯满。剿匪部队将俘虏或收容的人员陆续押解、转移出山。那个加纳布里被活捉后态度死硬,在押解途中试图夺取解放军战士的枪支进行反抗,被当场击毙。
剿匪部队紧急分析了乌斯满可能逃走的路线:马海方向已经有青海骑兵第2团守卫;昆仑山方向有近400公里的亚巴尔戈壁,唯一的通道已经被我驼兵团2连先期占领无法通过;惟有向西北安南坝方向逃走的可能行最大。
黄新廷军长当即决定,由我们骑兵大队率先追击。
李文彭带领骑兵大队两个连及一部电台追击了数公里,抓获了一个名叫沙发阿里的掉队土匪,此人供出乌斯满骑着白马就在前面不远处。得知这一消息,我们全体战士群情振奋,忘却了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首长一声令下,个个奋勇争先,拍马追了上去。
我的坐骑黑马关键时刻一点也不甘落后,跑得又快又稳,加上我年小体轻,一度竟跑到了队伍的最前头。
部队追击了几个小时后,跟随乌斯满奔逃的最后约50人陆续掉队做了俘虏,唯有乌斯满仍然沿着海子南岸向安南坝方向狂奔。又追了一阵,我们渐渐人困马乏,与乌斯满的距离越拉越大,眼看就要被他甩掉。就在这时,我和文化教员孔庆云、炊事员刘华林急中生智,拍马跃上海子冰面,抄捷径向南岸的乌斯满追去,这样一来,双方的距离马上就缩短了不少。我连战士宋兴、黄银娃、朱生仓等人也紧随其后追了上来。虽然我们的战马四蹄上都有带钉的铁掌,可以起到较好的防滑作用,但海子冰面实在是太光滑了,马踩上去小心翼翼,不敢放开来跑。尽管如此,我的坐骑黑马还是始终保持着一马当先的位置。这时,我身后的两名战士连人带马滑倒在冰面上。乌斯满边跑边向我们开枪射击,子弹不时地擦着我的头皮飞过,但我仍然毫不犹豫地拼命追赶。近了,更近了,我已经看清了乌斯满肥胖的身材和那张生满横肉的脸,当时那种兴奋豪迈的心情,今天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但是,就在我快要接近乌斯满的时候,乌斯满回马一枪,子弹擦着黑马前蹄下的冰面呼啸而过,黑马受惊跃起,蹄下打滑,紧接着就重重地倒在了冰面 ±0我从马背上被摔了出去,虽然没有受伤,但却摔得很重,一时头昏眼花,难以站立起来。此时,乌斯满又接连开了两枪,炊事员刘华林和另一名战士的马也先后被击倒,我方追兵只剩下文化教员孔庆云一个人。孔庆云没有放弃,继续紧紧追赶乌斯满。乌斯满在拍马狂奔中频频侧身射击。也许是乌斯满气数已尽,这个曾经是神枪手的“巴图尔”,竟然屡射不中。他见追兵只有一个人,竟然翻身下马,把叉子枪支在地上射击,第一枪提前量太多,打在孔庆云马前蹄的冰上,第二枪只射穿了孔庆云的裤管。这时孔庆云已经策马上岸,来到了乌斯满的近前。
事后,孔庆云向我们讲述了当时那段惊心动魄的场面: “乌匪见势不妙,急忙从地上爬起来,双手紧握叉子枪,恶狠狠地向我的双眼戳来,我本能地将头一偏,一股枪叉戳伤了我的面颊。我强忍剧痛,一把抓住了乌匪的枪管死死不放,乌匪拼命把我往马下拽,我趁下跌的惯力把自己的枪搂在怀里,狠命地夺过了乌匪的枪,然后一跃而起,乌匪此时狂怒至极,像个凶神恶煞,气急败坏地将我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趁势骑在我身上。我试图把乌匪翻在身下,但体重100多公斤的乌匪,犹如一头野牛死死地压住我。在动弹不得的情况下,我赶忙把手中的枪甩了出去。此时,乌匪突然从靴筒里拔出一柄带鞘的匕首,我急中生智,趁其脱去刀鞘的空当,一把抓住乌匪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狠狠的向后撅,使其无法脱去刀鞘;我更加用力地向后撅他的两根手指,乌匪负痛,匕首被甩了出去……” 后面的情景是这样的: 就在万分危急的关头,炊事员刘华林飞马赶到。刘华林的马被乌斯满打伤后,他急忙换乘了另一匹马,但这匹马性子烈,他刚骑上去,马就脱缰飞奔而去,速度之快竟使刘华林没有来得及接过战友递给他的枪。赤手空拳的刘华林赶到后,从地上捡起乌斯满的叉子枪,向乌斯满的后背狠狠地一枪捅去,乌斯满像野兽一样惨叫一声倒在了一边。孔庆云、刘华林和随后赶到的战友,七手八脚地把乌斯满捆了起来。
活捉匪首乌斯满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
我当时被摔晕后,经战友们救起,又换乘了一匹战马随后赶了上去。假如不是中间出现那个小插曲,首先同乌斯满只身搏斗的很可能就是我。我的坐骑黑马经历了那次变故,虽然暂时不能负重,但始终没有离开过部队,回到驻地后,在我的悉心照料下很快得到康复,又同我一起投入了新的战斗。
乌斯满被活捉后,从其身上搜出新疆警备司令部印章一枚、委任状数张。剿匪部队将乌斯满捆在骆驼背上押回海子,随后又押至敦煌。
新华社于1951年2月23日发布消息:“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某部,「本月19日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以北、甘青两省交界的海子,一举生擒为西北各族人民痛恨入骨的美帝国主义武装特务乌斯满匪首。” 海子一战,全歼乌斯满、哈巴斯、加纳布里、沙拉黑坦、木沙巴等5个部落,俘虏乌斯满、哈巴斯以下263人,毙加纳布里以下39人,俘虏叛匪家属11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19支,短枪8支,冲锋枪1支,各种子弹6874发,马5710匹,骆驼533峰,牛20头,羊8300只,并威慑、争取了其他3个部落向解放军投降。
1953年3月14日,乌斯满被押解到迪化。1951年4月29日,新疆各界召开万余人参加的乌斯满公审大会,王震讲话后,审判长包尔汉、副审判长饶正锡分别以维、汉两种语言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3、4、5、7、9、10、17条之规定,判处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匪首乌斯满死刑,当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乌斯满被活捉后,海子一带的哈萨克牧民纷纷外逃,藏匿于深山荒漠之中,期间经人民政府耐心说服教育,大部分集中于安南坝和敦煌附近,50年代中期陆续返回新疆。
乌斯满的儿子谢尔德曼在海子战斗中逃脱,他带领乌斯满手下残存的数人向新疆逃窜。剿匪部队派骑兵随后追赶,我也参加了这次追剿行动。我们追了10多天后,只在途中见到被残匪烧毁的3辆军车残骸,听说谢尔德曼已过了星星峡,只好奉命返回。
谢尔德曼于1951年5月逃到新疆奇台一带,鼓动当地已归附政府的几个哈萨克部落重新叛乱,遭到解放军剿匪部队和当地政府民兵痛击后,流窜到自己的老家阿山青河、富蕴一带,又鼓动胡尔曼部落重新叛乱,一度围攻青河、焚烧粮仓、啸聚山林,颇有乃父深山为匪的气势,解放军屡次围剿,均无法将其全歼。1952年9月15日,谢尔德曼在阿山专署的多次劝说下到承化向人民政府投降。随后,新疆方面派专人到甘肃敦煌将谢尔德曼的家属接回,并安排谢尔德曼在阿勒泰专区畜牧科任副科长,后调任伊犁州畜牧局任副局长直到病逝。
追剿残匪海子战斗后,上级给孔庆云记了特等功,给刘华林记了大功,给我记了二等功。由于我年纪小,当时在整个骑兵团一度名气很大,几乎人人都知道3连的通讯员段生茂是个小英雄,新任团长王三新则亲切的称我为“我们的少年英雄”。
追剿乌斯满的战斗经过,后来被载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戈壁凯歌——西北大剿匪》等文献书籍,电影工作者还以此为题材拍摄了故事片《沙漠追匪记》在全国上映。活捉乌斯满后,当地还有一些残匪没有肃清,这些人隐藏在哈萨克牧民中间,鼓动重新叛乱,伺机制造事端。我们的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后,又投入了二次剿匪战斗。
1952年,酒泉军分区的两名干部在长草沟被杀害。听说这两个人死得很惨,被掏了心、扒了肺、割了生殖器。酒泉军地双方立即展开调查,结果证实,长草沟的残匪的确鼓动当地哈萨克牧民发动了重新叛乱,他们裹胁哈萨克群众,扶老携幼,日夜兼程逃往南山和青海柴达木一带。长草沟附近驻有驼兵团的一个排,叛匪出逃时把驼兵排的骆驼也赶走了。驼兵排随后追至马海,又遭到埋伏在这里的土匪袭击,死伤数人。我连奉命追剿,在戈壁荒漠中奔波了数日,只收容了部分老弱妇孺和散落的牛羊牲畜。那些受土匪蒙蔽出逃的哈萨克牧民,后来大部分又陆续回到了原地,其中个别有罪恶的都受到了相应惩处。2004年,我陪同省人大常委李善平到阿克塞县视察,午间在一户哈萨克牧民家里吃饭,喧谈中得知,那家的男主人正是当年长草沟叛逃的残匪之一,曾被人民政府依法判刑13年。攀谈中,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我和那个已经变得极其衰老的哈萨克牧人都感慨颇多。
当时的情况那真叫艰苦。我们剿匪部队一连好几个月都在茫茫戈壁荒漠中奔走,人和马都疲惫至极,顾不上洗脸,人人蓬头垢面,只看见两只眼睛在动。战友们说,灰尘是老天爷为我们擦的护肤霜,一旦洗净,又白又亮。那只不过是我们的战士在特殊的环境下自我安慰、苦中作乐罢了。无论是烈日炎炎的正午,还是刮风下雨的夜晚,部队始终没有停止过追剿敌人的步伐。白天人不离枪、马不离鞍,无休止地奔跑;夜晚头枕马鞍、怀抱枪支、裹上皮大衣随便就地一躺,还不能睡得太死,一有动静就要马上出发…… 时间一长,人人身上虱子成堆,连马靴里都是。偶尔遇上白天宿营,我们就把内衣、马靴脱下来放到石头上砸,一砸一片血.. 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他67岁时作过一首诗,题目叫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我觉得这首诗堪称是我们那段军旅生活的真实写照。战士心目中的“轮台”,不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吗?后来,每当我听到蒋大为演唱的《骏马奔驰保边疆》时,当年的那种豪情壮志就禁不住油然而生。没当过骑兵的人,决不可能有这种体会和感受。在那段时间内,新疆剿匪部队的一排人马在大戈壁上失踪,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帮助寻找。我们深入到冷湖、柴达木一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旷野中四处搜寻。由于队伍远离驻地且行踪不定,给养供应不上,没有吃的,只能就地猎取野牛、野羊充饥,真是历尽了艰辛。经数日搜寻,我们只在一个小河沟的坡坎处找到了一名战士的遗体,其余的人没一点踪迹。那一带野狼成群,夜里围着我们的宿营地嗥叫不止。根据情况判断,那一排新疆骑兵已无生还的可能,我们只好草草掩埋了那个战士的遗体后撤回。
1954年,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石油部的一个勘探队深入到青海芒崖一带勘探石油,因为那里渺无人烟,且经常有土匪出没,我们奉命前往担负保卫任务,在芒崖驻守了半年。期间,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是一片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我们所处的环境可想而知。
那一年,我们连改为西北军区独立骑兵第3团第5连,我被上级选调到团里当了一名文书,部队驻敦煌西云观,是当地的一个道教场所。同年,全国人民慰问团组织西安易俗社赴敦煌慰问演出,我有幸见到了孟娥云、肖若兰、肖玉玲等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
1956年,上级任命我为骑兵团特务连通讯排排长。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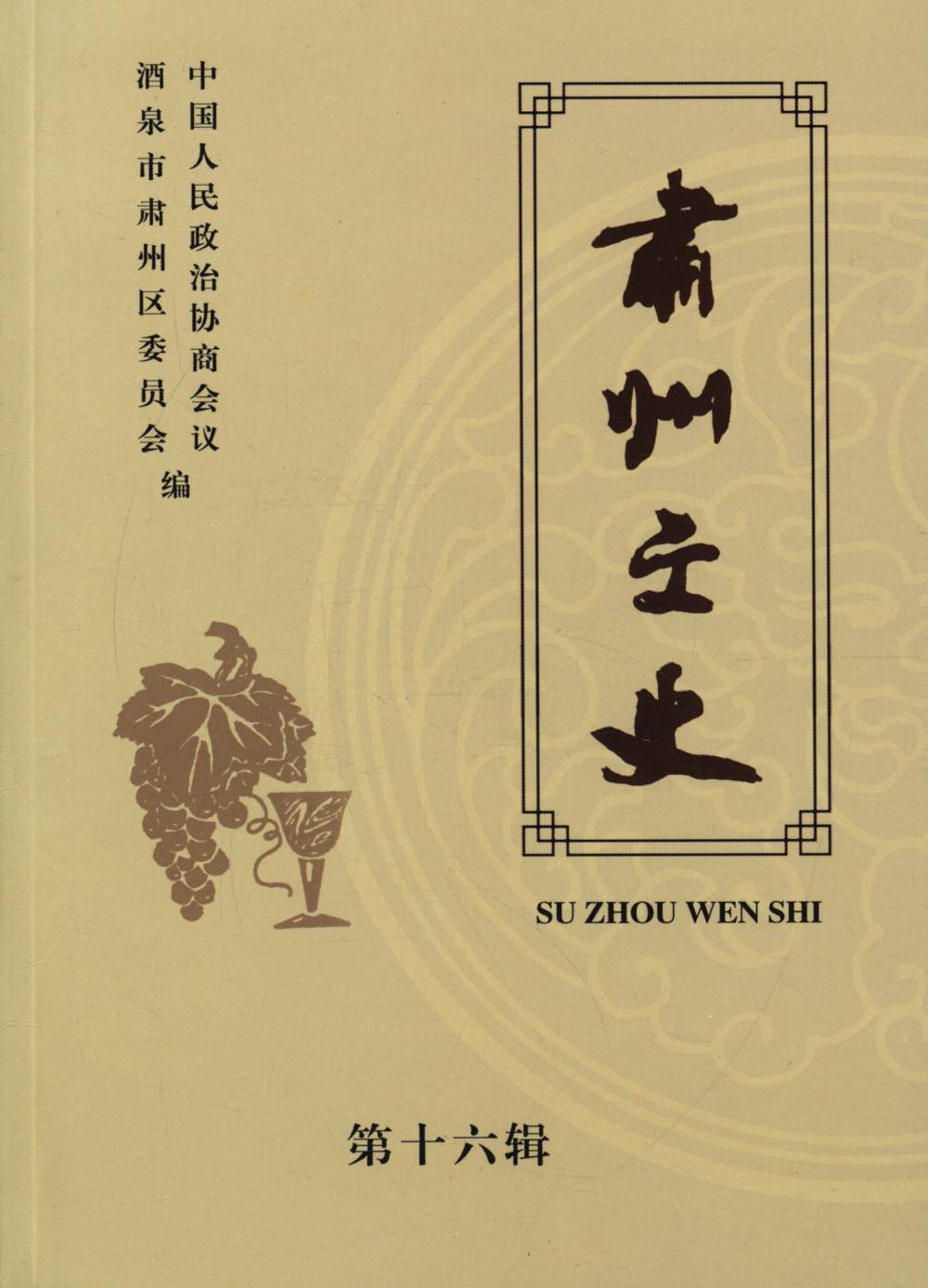
相关人物
段生茂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