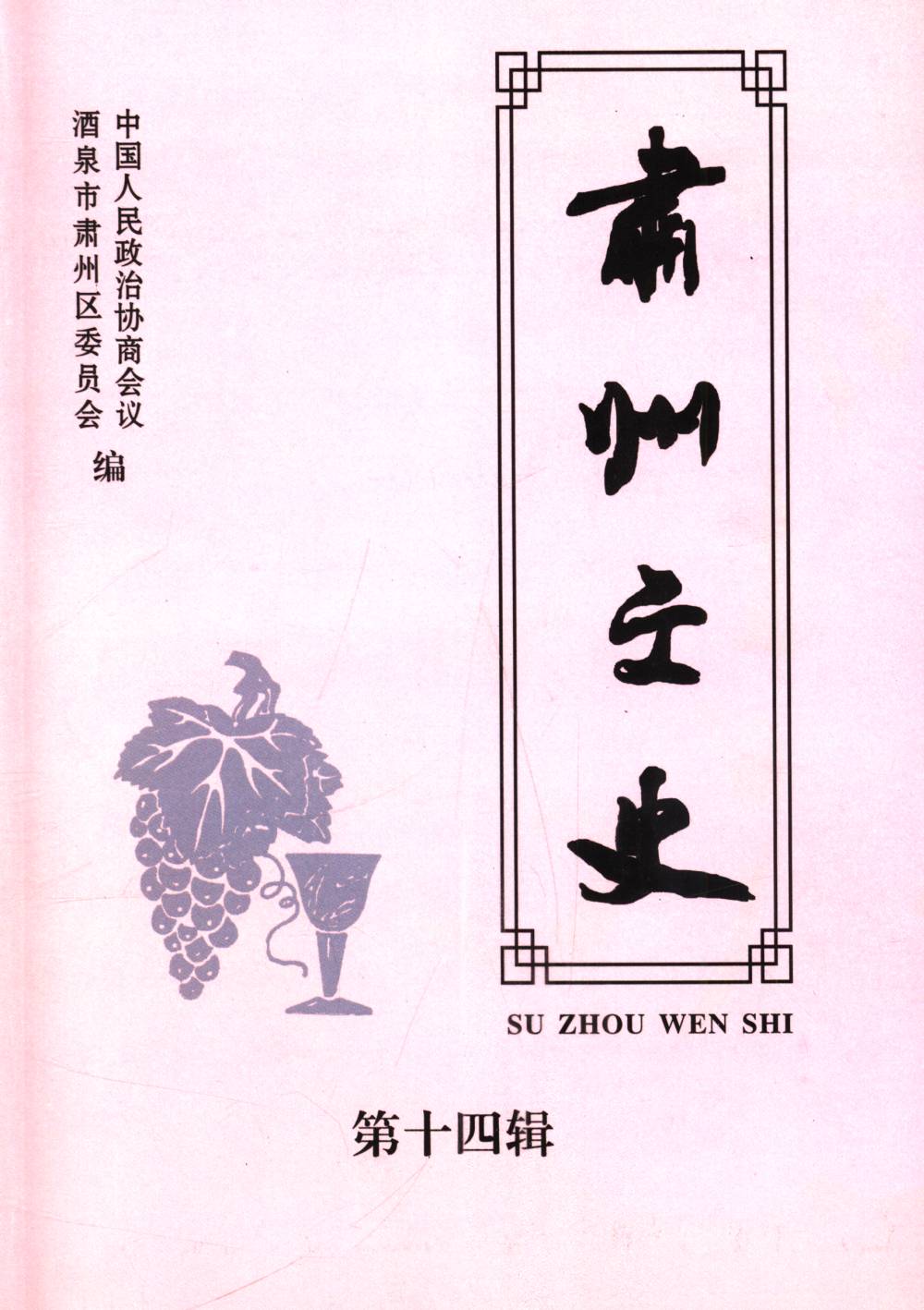又到酒泉
| 内容出处: | 《肃州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图书 |
| 唯一号: | 292220020220004663 |
| 颗粒名称: | 又到酒泉 |
| 分类号: | K294.23 |
| 页数: | 14 |
| 页码: | 60-73 |
| 摘要: | 讲述高尔泰又到酒泉工作的情况。 |
| 关键词: | 文史资料 肃州 |
内容
又到酒泉
高尔泰 我第二次到酒泉,是在1969年春天。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宣布了上级革委会给我的处分:“工资降三级”,这是维持1966年工作组的原判。没再戴帽子,算是解放了。叫我搬出牛棚,到酒泉去,为地区革委会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同行的,还有两个原美术组的同事。一个是当了文革组长和革委会主任的何山;一个是当了项目组负责人的孙纪元。
酒泉地区,属甘肃省最西部的一个行政区。管辖范围包括酒泉、玉门、安西、金塔、敦煌五个农业县,以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额济纳旗蒙古族自治县。文革前,领导机关叫地委,文革中叫地区革委会。酒泉军分区政委张哲岚、司令员吴占祥都在地区革委会任职O 听何、孙路上议论,张的军衔比吴高,由于同上级关系不好,上不去,现在是同级。他们说军分区是师级,地区机关也相当于师级。我们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部、省、军同级,算下来,我们所也相当于师级。作为师级单位的负责人,何山和他们同级,孙纪元起码也是团级。此去协助办展览,带有兄弟单位之间互相支持的性质。
但是到了酒泉,没有人对我们另眼相看。地区各级领导,大都是留下的军代表和一些“三结会”的老干部,不认识我们。展览会上,大都是从境内各县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人,也都不认识我们。同大家一样加班加点,排队买饭,睡通铺房。他们俩委屈得气呼呼的,不好好干。展览会上上下下,都对他们很恼火。我则相反,能不受歧视,已很意外。当时我想创造条件把妻子、女儿从下放地办出来,就拼命工作,加之业务能力也确实比他们强些,所以很受欢迎。
人际关系如此,似有些时空倒错。两位老同事提醒我:“别望了思想改造,别一到新环境,趁大家不了解,就来假积极”。一味讨好外行,指出我画的画不是艺术,若不脱胎换骨,还会栽跟斗,要是再栽一次跟斗,就八辈子都起不来了。他们还说:“我们是自己人,才这么关心帮助你,你要好好想想。”二 展览会上有个人叫刘光深,只有一米来高,四肢短小,我对他格外恭敬。成了朋友,才知道他不是个简单人物。以前当地委秘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是有名的才子。书记作大报告,都是照他写的稿子念。文革中揪斗后,在革委会招待所当门房。常邀我到他家(门房)坐坐,告诉我地区机关的各种人和事。信息、动态、派系背景、交往方式和办事门路,都是很实用的学问。他无所不知,成了我这个书呆子在这个官场迷津中的指路明灯。遇到这事,就去问他。
他说这只是个开头,麻达还在后头。现在干革命靠“说嘴”,一件事到底咋的,这不重要,把它说成是咋的才重要。有了“说头”就会有麻烦,你别大意。但是也别着急,现在的局势,我看是要弛了。一张一弛的弛。天时对你有利。你又人在酒泉,都说你干得好,地利人和也有。别人说什么都别吭气,画好你的画就行。
那天他找了一辆“吉普”,陪我到夹边沟农场满目荒凉的遗址转了一圈。行前说,开车的不知道你是哪个,去干吗。路上别说从前,别照相,看可骨头什么的别大惊小怪,回来也不提这事,就亍了。一路上,他介绍酒泉的物产、地理、历史,井了不少故事。都很有趣。
短短十年,我们开的那些沟渠都已被风沙填V。住过的土屋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矮墙,黄少簇拥,如同荒丘。大自然又回复到原来的面而。有些地方白骨露出地面,时不时拉住那些随双滚动的草球。驾驶员说,这里有过一个农场,E了很多人。我说是吗?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意的。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事实。多少文明多少星球有了又没了,谁能证明? 回到城里,天已黑了,展厅里灯火辉煌,大家正在加夜班。一整天不在,何、孙两位彳艮关心。正鱼问我到哪里去了,刘光深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好象地下冒出来的。向我说,你怎么走了?还没完呢。又向他们说,我们临时拉差,请他帮了个忙。刘是材料组组长,二位老同事把他拉到一边,提醒他我是右派分子,劳改释放犯从宽处理的,表现不老实,不可以接触重要材料,特别是战备数据C 刘说,听那口气,好象我刘光深犯了错误,要找我麻达的架势。同革命知识分子说嘴没用,我惹不起躲得起。同他们一起,去我展览会的总负责人、宣传部长王仁。王也不敢负责,又四个人—起,去找吴司令,吴又打发我们去找张政委。
张听何、孙陈述意见完毕,说了两点,第一,办展览是搞宣传,到了展览会上的材料,都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不存在保密的问题。第二,要团结大多数。问题查清楚了,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就不要再当敌人对待了,要放手使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问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意见。他又说,我是个当兵的,大老粗,不懂艺术,难得碰到你们专家,给我说说好吗?比方同一个字,我写出来不是艺术,你写出来就是,什么道理?静场片刻,他转向王仁,你当宣传部长的,总该知道一点,说来听听。王说他忙着抓革命大批判,还没顾上研究。张说,看来这事有点儿玄。不管怎么说吧,我的第三点意见是:反正我们的展览不是艺术展览,画是用来说明问题的,是不是艺术没关系。问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意见。他又说,依我看,能够说明问题,也是一种艺术。打仗能老打胜仗,就是有军事艺术。炒菜炒得人人爱吃,就是有烹饪艺术。菜炒出来没法子吃,你硬说那是艺术,强迫人家吃,能行吗?我想写文章、画画,道理该一样吧?我们做什么都有个目的,我想那最能达到目的的做法,就该算是艺术。你们说呢? 刘光深问我,你说他说得对么?我说很难说,什么是艺术,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刘说,张政委就是这样,说话很随便。
三 刘说,张政委平时爱看个书,知道得多些。做报告不看讲稿,天南地北说到哪里是哪里。讲理论扯到河外星系,讲形势又扯到太极两仪,就像牵藤。举起例子来,地方志,世界史,《孙子兵法》,《世说新语》,还有《茶花女》什么的,都有。现在反对他的人多起来了,抓他个“辫子”容易得很。真要追究,都是大问题。
我问谁反对他,刘说多了去了,都是他自找的。历来做官靠后台,讲究个人脉,讲究个空间袍泽的拥戴,他都不认,只认死理。你支不支持他,他不在乎。他只是看你对不对。他有个老部下姓袁,是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军代表,跟他跟得很紧。哈萨克人骑马打仗厉害得很,四九年打不下来,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头人木斯托发当了自治县的县长,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逃进山去,猎到五只猗狗。回来给袁送了五张猞猁皮,袁结合他当了.县革委会的宣传部长。平常小事一桩,张知道后,就发脾气,把袁叫来训了 一顿。叫把五张猞猁皮还给了木斯托发。木斯托发也不高兴,把皮扯了。
刘说,我感到奇怪,现在谁都知道,军队里贪污、盗窃、违法、乱纪样样有,地方上有的军队里都有,地方上没有的军队里也有。他当兵的出身,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听到一丁点儿就跳起来,你说怪不怪?要不然就是看书看迷糊了。年时我为了平反的事,到他家去过一次。好家伙,整整两面墙,满满都书。他家住军分区大院,给大院门卫打了招呼,谁来都不让进。不管什么事,叫上了班到办公室谈去。他要看书! 刘说,可是来喊冤的他见,还叫领到他家门上。有个被打断了腿的肃北牧民,还在他家住了一夜。同这些人打交道,麻达大了。帮了一个,就都来了。越帮越多,越帮他越觉得冤,越像欠人家什么,没完没了,缠不清,还挨骂。最后他没辙了,还是交给了信访办。本来么,这些事情都有信访办管着,你招揽个什么?信访办的人说,有的案子本来不难办,他一插手就难了,得往上追,只好不了了之。我在政府机关里十几年,没见过这样子的。他要不是军代表,要不是资格在那里,军衔在那里,早就给做掉了。
在地区大院里,有时会遇见这位张政委。矮小瘦弱,满头白发,一脸的忧思。同高大肥胖、笑口常开的吴司令员站在一起,反差之大惹人发笑。他有时带着一些官,到展厅来看看。见了讲解员、电工、木工、打杂的、写材料的和我们画画的,都要说辛若了 0笑容作派,像个老农。虽然矮小瘦弱,虽然老农一般,后面跟着那么一群,也自有一种威仪,展厅里鸦雀无声。直要等他们走了,才又嘈杂起来。
四 何山、孙纪元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大串联时又同兰州军区建立了联系,不把他们放在跟里,同他们干上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兰州军区告状,说酒泉地区革委会丧失阶级立场,业务挂帅,排斥革命知识分子,重用阶级异己分子。送去一大包材料,其中包括抄家抄去的我的一本日记。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女)看了,说我极端顽固反动,不可放手使用。说还是要政治挂帅,不能业务挂帅。
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说地区革委会受了上级的批评。说还是拿笔杆子的比拿枪杆子的厉害,现在是兵遇到秀才,有理说不清了。我很发愁,问怎么办。刘光深说,你什么事也没有,好好干就是了。本来就没你的事,是敦煌那蒂子同地区革委会的矛盾,现在就更没你的事了,现在是兰州军区同酒泉军分区的矛盾了。说你坏是为了说酒泉坏,酒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就会说你好。你只要人在酒泉,就什么事都没有。
我说军队令出必行,小小军分区,怎敢和大军区对抗?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军队里政治部和司令部,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不同兵种不同派系,关系非常复杂。加上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就更复杂了。别说是你,连我都雾煞煞。总的来说一句话:这里面谁是谁非不重要。人同人打交道,是凭实力,不是凭正确。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
我说,你不是说把事情说成昨的才重要吗?他说那是说干革命。现在是又一码子事了。说不清的理可以不说。有实力就可以不说。能不说,你自然有了理了。真理不是只有一个,也不是没有它就没法子过。你的招数再厉害,我不接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就厉害不起来了,对吧? 听着我觉得,个儿矮小的是我,不是他。
五 夏天到来的时候,展览准备就绪,要开幕了 。抽调来的人,除了当讲解员的,和一个画画的,都要回原单位去。画画的留谁,地区一直没说。我们三个,都希望能留自己(到底城里比沙漠里好过)。何是我顶头上司,有本单位的人事权,只因人在酒泉,一时动用不得。我趁此机会,正在为被下放劳动的妻子办“农转非”侬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若回敦煌,不但此事无望,而且会被关起门来打狗。那怎么能行?! 未几,让我和何山各画一幅大油画,限期一个月。王仁说是打擂台,谁画得好谁留下。刘光深估什,是吴司令员出的点子。事虽荒唐,在文革中也属正常。何山问好坏谁裁判?王仁答曰工农兵。于是各占一方(何在地区革委会礼堂,我在地区招待所会议室)鸣锣开战。起初我莫名其妙,觉得像马戏团里的猴子披挂上阵。接着就发起愁来:一幅“民族大团结”何先挑去了。我这幅“潭家湾全景图”,实际上是鸟瞰平面地图,不宜于画油画。画面4x4公尺,无法从门进出。得画成四幅,再拼起来,中间有一道十字缝,怎么着都难看。
潭家湾是酒泉农村里的一个生产大队,当了西北学大寨的“样板”。我去住了几天,画了许多速写回来,使舞台上充满了剧情:马厩里修车铜草,猪场上起肥垫土,井边洗菜饮驴。吆车的老汉拾粪,看场的娃子赶鸡,息晌的婆姨抓紧时间纳鞋底……豆人寸马,房屋像火柴盒。门上有对联,窗上贴着窗花。屋顶上晒着果脯瓜干豆瓣酱,屋檐下挂着辣椒大蒜玉米棒。大路两边有杂草,中间有车辙。有的车辙里汪着水,水中有倒影。总之是力求生动有趣,精细逼真。小眉小眼,只差没用放大镜了。
不管是不是艺术,成败关系着安危离合。我白天黑夜加班。先是务求必胜,后来就画出了兴趣。天气酷热,脱光了衣服画,只穿一条短裤,仍旧挥汗如雨。看画的来来去去,都不知道谁是谁。西北人没有赤膊的习惯,看不惯我赤膊,背后有议论,骂我不文明,疯疯癫癫。我听到反映,也不理会。本来是要哗众取宠,却又旁若无人起来。似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真有点儿疯疯癫癫的了。
限期过了几天,画才全面完成。抬走的前一天,刘光深来,一脸的焦虑,说,那两位到处说,你把学大寨样板画成了小农经济,把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画成了悠闲落后的老村古调。这个意见,可是正确得歹呀!我很着急,一通夜没睡。工地加上红旗,墙头加上标语,大路边加上语录碑和正副统帅并肩像。四处加上许多观光取经的队伍,记者挎着照相机,学生仔捧着红宝书,机关干部围成一圈听介绍经验。村门口各色大客车一字排开,气氛似热烈多了。天亮了一看,色彩不协调,花里胡哨。来不及调整,给抬走了。
展览开幕日,正逢“三级干部大会”开幕,参观人潮汹涌。谁都没有想到,居然是潭家湾全景图最受欢迎,观众沿着有车辙的大路一路看过去,就像看连环画,兴味极浓烈。加上小而逼真,又是熟悉的生活,以前没在画上见过,更有一分惊喜。一大群人挤着边看边议论,争相指出新发现,引起轰动,引来更多人围观。虽有人说贴上革命标签没改变老村古调,但是没人爱听。潭家湾大队支书、九犬代表杨柱基来参加三级干部会,看了说好极了。一锤定音,再硬的道理也没关系了。张哲岚很高兴,在大会上做报告,提到展览时,还说了个“解衣磅礴”的故事,说庄子说过,只有那个赤膊画画的人,才是真画师。
何山那画,画得很好。但“民族大团结”的画到处都有,这一带火车站汽车站上都有,印刷品更随处可见,全是各民族代表把一个毛泽东围在当中。怎么画都像见过,没人要看了。观众从画底下经过,头都不回。刘光深说,何这会子算是背了运了。他说人都有个时运,顺起来事事都顺,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背起来事事都背,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今时舆论都向着你,该是你走运了。
三级会后不久,刘光深当了地区民政局局长。农转非的事,正好归他管。我很庆幸。长期以来小眉小眼地钻,拼死拼活地干,唯一的目的,不也就是个平安团聚么!能如愿以偿,那就什么代价都值了。
但是妻子在下放地,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刚拿到她的准迁证,就得到她垂危的消息。日夜兼程赶去,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只有三岁的女儿跟着我,离开了那沙漠边缘的荒凉小村。
展览会闭幕以后不久,张哲岚、吴占祥和其它军代表撤离了地方机关,回部队去了。我们父女俩到了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在那里待到1978年。79年我在北京,接到张哲岚的一封信,说他已离休,邀我到西安市红缨路31号他家作客。说要给我介绍几位著名的作家画家和书法家,“都是很有意思的人”。因为太忙,没能去。写了幅对联寄给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刘光深还在酒泉,一直没有升官。1983年,我在兰州大学,他托家在酒泉的学生带给我一个玉石笔筒,墨绿色,有云纹,温润古朴。可惜我没有一张配得上它的书桌可以放它。离开西北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先是听说,他退休后很孤独,日在醉乡。后又听说,他无疾而终,身后萧条。
酒泉陈少沛御赐倾泉泉水香,谪仙天地杯中量。
汝阳封恨岂三斗? 今日走廊变酒廊。
高尔泰 我第二次到酒泉,是在1969年春天。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宣布了上级革委会给我的处分:“工资降三级”,这是维持1966年工作组的原判。没再戴帽子,算是解放了。叫我搬出牛棚,到酒泉去,为地区革委会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同行的,还有两个原美术组的同事。一个是当了文革组长和革委会主任的何山;一个是当了项目组负责人的孙纪元。
酒泉地区,属甘肃省最西部的一个行政区。管辖范围包括酒泉、玉门、安西、金塔、敦煌五个农业县,以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额济纳旗蒙古族自治县。文革前,领导机关叫地委,文革中叫地区革委会。酒泉军分区政委张哲岚、司令员吴占祥都在地区革委会任职O 听何、孙路上议论,张的军衔比吴高,由于同上级关系不好,上不去,现在是同级。他们说军分区是师级,地区机关也相当于师级。我们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部、省、军同级,算下来,我们所也相当于师级。作为师级单位的负责人,何山和他们同级,孙纪元起码也是团级。此去协助办展览,带有兄弟单位之间互相支持的性质。
但是到了酒泉,没有人对我们另眼相看。地区各级领导,大都是留下的军代表和一些“三结会”的老干部,不认识我们。展览会上,大都是从境内各县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人,也都不认识我们。同大家一样加班加点,排队买饭,睡通铺房。他们俩委屈得气呼呼的,不好好干。展览会上上下下,都对他们很恼火。我则相反,能不受歧视,已很意外。当时我想创造条件把妻子、女儿从下放地办出来,就拼命工作,加之业务能力也确实比他们强些,所以很受欢迎。
人际关系如此,似有些时空倒错。两位老同事提醒我:“别望了思想改造,别一到新环境,趁大家不了解,就来假积极”。一味讨好外行,指出我画的画不是艺术,若不脱胎换骨,还会栽跟斗,要是再栽一次跟斗,就八辈子都起不来了。他们还说:“我们是自己人,才这么关心帮助你,你要好好想想。”二 展览会上有个人叫刘光深,只有一米来高,四肢短小,我对他格外恭敬。成了朋友,才知道他不是个简单人物。以前当地委秘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是有名的才子。书记作大报告,都是照他写的稿子念。文革中揪斗后,在革委会招待所当门房。常邀我到他家(门房)坐坐,告诉我地区机关的各种人和事。信息、动态、派系背景、交往方式和办事门路,都是很实用的学问。他无所不知,成了我这个书呆子在这个官场迷津中的指路明灯。遇到这事,就去问他。
他说这只是个开头,麻达还在后头。现在干革命靠“说嘴”,一件事到底咋的,这不重要,把它说成是咋的才重要。有了“说头”就会有麻烦,你别大意。但是也别着急,现在的局势,我看是要弛了。一张一弛的弛。天时对你有利。你又人在酒泉,都说你干得好,地利人和也有。别人说什么都别吭气,画好你的画就行。
那天他找了一辆“吉普”,陪我到夹边沟农场满目荒凉的遗址转了一圈。行前说,开车的不知道你是哪个,去干吗。路上别说从前,别照相,看可骨头什么的别大惊小怪,回来也不提这事,就亍了。一路上,他介绍酒泉的物产、地理、历史,井了不少故事。都很有趣。
短短十年,我们开的那些沟渠都已被风沙填V。住过的土屋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矮墙,黄少簇拥,如同荒丘。大自然又回复到原来的面而。有些地方白骨露出地面,时不时拉住那些随双滚动的草球。驾驶员说,这里有过一个农场,E了很多人。我说是吗?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意的。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事实。多少文明多少星球有了又没了,谁能证明? 回到城里,天已黑了,展厅里灯火辉煌,大家正在加夜班。一整天不在,何、孙两位彳艮关心。正鱼问我到哪里去了,刘光深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好象地下冒出来的。向我说,你怎么走了?还没完呢。又向他们说,我们临时拉差,请他帮了个忙。刘是材料组组长,二位老同事把他拉到一边,提醒他我是右派分子,劳改释放犯从宽处理的,表现不老实,不可以接触重要材料,特别是战备数据C 刘说,听那口气,好象我刘光深犯了错误,要找我麻达的架势。同革命知识分子说嘴没用,我惹不起躲得起。同他们一起,去我展览会的总负责人、宣传部长王仁。王也不敢负责,又四个人—起,去找吴司令,吴又打发我们去找张政委。
张听何、孙陈述意见完毕,说了两点,第一,办展览是搞宣传,到了展览会上的材料,都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不存在保密的问题。第二,要团结大多数。问题查清楚了,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就不要再当敌人对待了,要放手使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问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意见。他又说,我是个当兵的,大老粗,不懂艺术,难得碰到你们专家,给我说说好吗?比方同一个字,我写出来不是艺术,你写出来就是,什么道理?静场片刻,他转向王仁,你当宣传部长的,总该知道一点,说来听听。王说他忙着抓革命大批判,还没顾上研究。张说,看来这事有点儿玄。不管怎么说吧,我的第三点意见是:反正我们的展览不是艺术展览,画是用来说明问题的,是不是艺术没关系。问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意见。他又说,依我看,能够说明问题,也是一种艺术。打仗能老打胜仗,就是有军事艺术。炒菜炒得人人爱吃,就是有烹饪艺术。菜炒出来没法子吃,你硬说那是艺术,强迫人家吃,能行吗?我想写文章、画画,道理该一样吧?我们做什么都有个目的,我想那最能达到目的的做法,就该算是艺术。你们说呢? 刘光深问我,你说他说得对么?我说很难说,什么是艺术,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刘说,张政委就是这样,说话很随便。
三 刘说,张政委平时爱看个书,知道得多些。做报告不看讲稿,天南地北说到哪里是哪里。讲理论扯到河外星系,讲形势又扯到太极两仪,就像牵藤。举起例子来,地方志,世界史,《孙子兵法》,《世说新语》,还有《茶花女》什么的,都有。现在反对他的人多起来了,抓他个“辫子”容易得很。真要追究,都是大问题。
我问谁反对他,刘说多了去了,都是他自找的。历来做官靠后台,讲究个人脉,讲究个空间袍泽的拥戴,他都不认,只认死理。你支不支持他,他不在乎。他只是看你对不对。他有个老部下姓袁,是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军代表,跟他跟得很紧。哈萨克人骑马打仗厉害得很,四九年打不下来,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头人木斯托发当了自治县的县长,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逃进山去,猎到五只猗狗。回来给袁送了五张猞猁皮,袁结合他当了.县革委会的宣传部长。平常小事一桩,张知道后,就发脾气,把袁叫来训了 一顿。叫把五张猞猁皮还给了木斯托发。木斯托发也不高兴,把皮扯了。
刘说,我感到奇怪,现在谁都知道,军队里贪污、盗窃、违法、乱纪样样有,地方上有的军队里都有,地方上没有的军队里也有。他当兵的出身,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听到一丁点儿就跳起来,你说怪不怪?要不然就是看书看迷糊了。年时我为了平反的事,到他家去过一次。好家伙,整整两面墙,满满都书。他家住军分区大院,给大院门卫打了招呼,谁来都不让进。不管什么事,叫上了班到办公室谈去。他要看书! 刘说,可是来喊冤的他见,还叫领到他家门上。有个被打断了腿的肃北牧民,还在他家住了一夜。同这些人打交道,麻达大了。帮了一个,就都来了。越帮越多,越帮他越觉得冤,越像欠人家什么,没完没了,缠不清,还挨骂。最后他没辙了,还是交给了信访办。本来么,这些事情都有信访办管着,你招揽个什么?信访办的人说,有的案子本来不难办,他一插手就难了,得往上追,只好不了了之。我在政府机关里十几年,没见过这样子的。他要不是军代表,要不是资格在那里,军衔在那里,早就给做掉了。
在地区大院里,有时会遇见这位张政委。矮小瘦弱,满头白发,一脸的忧思。同高大肥胖、笑口常开的吴司令员站在一起,反差之大惹人发笑。他有时带着一些官,到展厅来看看。见了讲解员、电工、木工、打杂的、写材料的和我们画画的,都要说辛若了 0笑容作派,像个老农。虽然矮小瘦弱,虽然老农一般,后面跟着那么一群,也自有一种威仪,展厅里鸦雀无声。直要等他们走了,才又嘈杂起来。
四 何山、孙纪元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大串联时又同兰州军区建立了联系,不把他们放在跟里,同他们干上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兰州军区告状,说酒泉地区革委会丧失阶级立场,业务挂帅,排斥革命知识分子,重用阶级异己分子。送去一大包材料,其中包括抄家抄去的我的一本日记。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女)看了,说我极端顽固反动,不可放手使用。说还是要政治挂帅,不能业务挂帅。
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说地区革委会受了上级的批评。说还是拿笔杆子的比拿枪杆子的厉害,现在是兵遇到秀才,有理说不清了。我很发愁,问怎么办。刘光深说,你什么事也没有,好好干就是了。本来就没你的事,是敦煌那蒂子同地区革委会的矛盾,现在就更没你的事了,现在是兰州军区同酒泉军分区的矛盾了。说你坏是为了说酒泉坏,酒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就会说你好。你只要人在酒泉,就什么事都没有。
我说军队令出必行,小小军分区,怎敢和大军区对抗?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军队里政治部和司令部,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不同兵种不同派系,关系非常复杂。加上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就更复杂了。别说是你,连我都雾煞煞。总的来说一句话:这里面谁是谁非不重要。人同人打交道,是凭实力,不是凭正确。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
我说,你不是说把事情说成昨的才重要吗?他说那是说干革命。现在是又一码子事了。说不清的理可以不说。有实力就可以不说。能不说,你自然有了理了。真理不是只有一个,也不是没有它就没法子过。你的招数再厉害,我不接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就厉害不起来了,对吧? 听着我觉得,个儿矮小的是我,不是他。
五 夏天到来的时候,展览准备就绪,要开幕了 。抽调来的人,除了当讲解员的,和一个画画的,都要回原单位去。画画的留谁,地区一直没说。我们三个,都希望能留自己(到底城里比沙漠里好过)。何是我顶头上司,有本单位的人事权,只因人在酒泉,一时动用不得。我趁此机会,正在为被下放劳动的妻子办“农转非”侬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若回敦煌,不但此事无望,而且会被关起门来打狗。那怎么能行?! 未几,让我和何山各画一幅大油画,限期一个月。王仁说是打擂台,谁画得好谁留下。刘光深估什,是吴司令员出的点子。事虽荒唐,在文革中也属正常。何山问好坏谁裁判?王仁答曰工农兵。于是各占一方(何在地区革委会礼堂,我在地区招待所会议室)鸣锣开战。起初我莫名其妙,觉得像马戏团里的猴子披挂上阵。接着就发起愁来:一幅“民族大团结”何先挑去了。我这幅“潭家湾全景图”,实际上是鸟瞰平面地图,不宜于画油画。画面4x4公尺,无法从门进出。得画成四幅,再拼起来,中间有一道十字缝,怎么着都难看。
潭家湾是酒泉农村里的一个生产大队,当了西北学大寨的“样板”。我去住了几天,画了许多速写回来,使舞台上充满了剧情:马厩里修车铜草,猪场上起肥垫土,井边洗菜饮驴。吆车的老汉拾粪,看场的娃子赶鸡,息晌的婆姨抓紧时间纳鞋底……豆人寸马,房屋像火柴盒。门上有对联,窗上贴着窗花。屋顶上晒着果脯瓜干豆瓣酱,屋檐下挂着辣椒大蒜玉米棒。大路两边有杂草,中间有车辙。有的车辙里汪着水,水中有倒影。总之是力求生动有趣,精细逼真。小眉小眼,只差没用放大镜了。
不管是不是艺术,成败关系着安危离合。我白天黑夜加班。先是务求必胜,后来就画出了兴趣。天气酷热,脱光了衣服画,只穿一条短裤,仍旧挥汗如雨。看画的来来去去,都不知道谁是谁。西北人没有赤膊的习惯,看不惯我赤膊,背后有议论,骂我不文明,疯疯癫癫。我听到反映,也不理会。本来是要哗众取宠,却又旁若无人起来。似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真有点儿疯疯癫癫的了。
限期过了几天,画才全面完成。抬走的前一天,刘光深来,一脸的焦虑,说,那两位到处说,你把学大寨样板画成了小农经济,把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画成了悠闲落后的老村古调。这个意见,可是正确得歹呀!我很着急,一通夜没睡。工地加上红旗,墙头加上标语,大路边加上语录碑和正副统帅并肩像。四处加上许多观光取经的队伍,记者挎着照相机,学生仔捧着红宝书,机关干部围成一圈听介绍经验。村门口各色大客车一字排开,气氛似热烈多了。天亮了一看,色彩不协调,花里胡哨。来不及调整,给抬走了。
展览开幕日,正逢“三级干部大会”开幕,参观人潮汹涌。谁都没有想到,居然是潭家湾全景图最受欢迎,观众沿着有车辙的大路一路看过去,就像看连环画,兴味极浓烈。加上小而逼真,又是熟悉的生活,以前没在画上见过,更有一分惊喜。一大群人挤着边看边议论,争相指出新发现,引起轰动,引来更多人围观。虽有人说贴上革命标签没改变老村古调,但是没人爱听。潭家湾大队支书、九犬代表杨柱基来参加三级干部会,看了说好极了。一锤定音,再硬的道理也没关系了。张哲岚很高兴,在大会上做报告,提到展览时,还说了个“解衣磅礴”的故事,说庄子说过,只有那个赤膊画画的人,才是真画师。
何山那画,画得很好。但“民族大团结”的画到处都有,这一带火车站汽车站上都有,印刷品更随处可见,全是各民族代表把一个毛泽东围在当中。怎么画都像见过,没人要看了。观众从画底下经过,头都不回。刘光深说,何这会子算是背了运了。他说人都有个时运,顺起来事事都顺,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背起来事事都背,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今时舆论都向着你,该是你走运了。
三级会后不久,刘光深当了地区民政局局长。农转非的事,正好归他管。我很庆幸。长期以来小眉小眼地钻,拼死拼活地干,唯一的目的,不也就是个平安团聚么!能如愿以偿,那就什么代价都值了。
但是妻子在下放地,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刚拿到她的准迁证,就得到她垂危的消息。日夜兼程赶去,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只有三岁的女儿跟着我,离开了那沙漠边缘的荒凉小村。
展览会闭幕以后不久,张哲岚、吴占祥和其它军代表撤离了地方机关,回部队去了。我们父女俩到了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在那里待到1978年。79年我在北京,接到张哲岚的一封信,说他已离休,邀我到西安市红缨路31号他家作客。说要给我介绍几位著名的作家画家和书法家,“都是很有意思的人”。因为太忙,没能去。写了幅对联寄给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刘光深还在酒泉,一直没有升官。1983年,我在兰州大学,他托家在酒泉的学生带给我一个玉石笔筒,墨绿色,有云纹,温润古朴。可惜我没有一张配得上它的书桌可以放它。离开西北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先是听说,他退休后很孤独,日在醉乡。后又听说,他无疾而终,身后萧条。
酒泉陈少沛御赐倾泉泉水香,谪仙天地杯中量。
汝阳封恨岂三斗? 今日走廊变酒廊。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