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夏、商、周时代,主要实行民军制。兵役寓于田制之中,有受田权利的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平时耕牧为民,战时出征为兵。这一制度,西周时比较完善,规定每家出一人为“正卒”,随时准备出征,其余为“羡卒”,服后备兵役。出征时“以七家相更替,七征而役方一遍”(《汉书•食货志》)。春秋后期,又出现了一种考选勇士从军的办法。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各诸候国进行激烈的兼并战争,竞相扩充常备军,开始实行征兵制。
第二节征兵制征兵制的实行,始于西汉。征兵制是男子到一定年龄,由官府登记,需要时出征服兵役,服役期满后还乡为民做为后备兵,遇有大的战事再应征出战。规定男子在23至56岁期间服兵役两年。其中一年在本郡服役,学习骑射等军事技术,称“正卒”;一年守护京都或戍守边防,称卫士或戍卒。汉武帝开发河西,征战和屯田的士卒都从内地征发而来,有时还征被征服的少数民族青壮年从事征战。如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广利击大宛,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14年)赵充国西击先零羌,主要兵员就是“杂胡”。
金元时期,蒙古族统治华夏,由于连年大规模的征战及战后占领地统治的需要,本民族人远不够用,也实行征兵制。征集其他民族兵员供其驱使,“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 。完颜亮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为进攻南京,下令凡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一律纳入军籍”,以汉族兵在第一线作战,女真兵在后督战。元时规定汉人“强者充军,弱者出钱” 。
第三节募兵制实行过募兵制的,有汉、北魏、唐、宋、清。募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种原因“自愿”为军。如逢国家有难挺身报国的;生活所迫,当兵吃粮,养家糊口的;投身军伍,希图建功疆场、博取功名富贵的等。
西汉王朝抵抗匈奴侵略的战争,符合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因此,人民愿意应召从军,有的还自己带良马,要求从军参战。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西汉王朝开始大规模讨伐匈奴,陇西成纪人李广,就自动应募从军,后来成为有名的“飞将军”。骑都尉李陵从楚地招募“勇士、奇才、剑客”5000多名,在酒泉、张掖间驻防练兵,防备匈奴入侵。这些勇士都是自愿来保卫国家边疆的,一般都有较高的武艺,而且体格强健,任侠好义,重名轻利,作战勇敢。到东汉时,由于朝廷长期废弛地方军事工作,致使民不习战,官不知兵,发生外族犯边和内乱等突发事件后,各郡无以承担作战任务,朝廷只好实行募兵制度,招募能战之兵。从安帝永初起,“羌乱”不止,募兵的规模越来越大。募兵,往往是临战前的应急措施,无暇严格选择,以致有很多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痞子无赖等社会渣滓,都应召从军。这样招募来的士卒,素质不高,无论是军纪,还是武艺,都远远赶不上西汉时招募的兵员。有些官员还纵容士兵掠夺民间财物,为非作歹,以引诱更多的人应募从军。招募的士兵一般都是终身从军,因而军队中老弱之卒越集越多,大大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以致在多次“征羌” 战争中遭受失败,这是东汉王朝衰败的突出表现。
北魏在北中国确立统治地位后,由于不断对南朝和西北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用兵,光靠鲜卑人当兵,已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到太武帝拓拔焘时,开始实行募兵制,招募大量汉人服兵役,补充常备军。
唐代前期,在实行府兵制的同时,也实行募兵制,但这时的募兵,仅是府兵制的一种补充手段、辅助措施,府兵制遭到破坏后,募兵制就成了唐王朝的主要兵役制度。高宗李治执政时期,府兵制就已经开始衰落,而边防又多事端,边境之军、守捉、镇大量增加,常年驻戍的军队有60多万人。这些戍第四篇兵役工作边兵大多是招募来的。玄宗李隆基时,罢边镇兵20多万人,使之还农,但戍边兵仍然不少。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河西节度使,即辖10军、14守捉,统兵7.3万人;陇右节度使,辖18军、3守捉,统兵7.5万人。两镇合计28军、17守捉,共有边兵14.8万余人,这些边兵全靠招募而来的。
公元848年,张议潮率众起义时,其基本部队都是招募的“瓜沙子弟”(今敦煌市、安西县),被唐王朝命名为“归义军”。张议潮依靠这支队伍,驱逐吐蕃势力,每到一地,广大人民一呼百应,纷纷参加归义军,吐蕃兵望风披靡,河西、陇右很快光复。
宋代时期募兵制比较盛行。北宋时,朝廷直接管辖的禁军,从全国各地招募;守卫各州的厢兵,在本州范围内招募;守卫边疆地区的蕃兵,从当地少数民族中招募;保卫家乡的乡兵,由各地按户籍抽调的壮丁组成。此外, 还强迫罪徒当兵,士兵的社会地位低下。
第四节世兵制世兵制,即一入军籍,世代为兵之意。早在三国、两晋时代就实行这种制度,把士兵之家列为军户,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服兵役。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割据,军阀混战不止,全国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鼎立的三方为了扩大军队,战胜对手,都强制实行世袭兵役制,简称“世兵制”。其要旨是把所有的户口分为三种:一是普通户,归郡县官府管理,从事农耕,为国家交租粮、出劳役;二是屯田户,归典农都尉管理,为国家种田,生产粮食;三是军户,或称“士家”,归军府或州郡的军事官员管理,为国家服兵役。这一制度的特点是军民分离,把士兵全家从普通百姓中分离出来,脱离民籍,变为军籍。士兵本人终身为兵,其家子子孙孙世代为兵。
西晋时,规定军户要世世代代为兵。晋代军户的兵役、劳役负担,比三国时期更为繁重,朝廷规定,军户男子“年十六为全丁,十三为半丁”。全丁戍守,半丁漕运(军事水运)。这样,军户既服兵役,又服劳役,而且父子同时服役,父南子北,长期分离,使军户“咸更不宁”,生活极端困苦,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再娶者” 。于此同时,晋代还实行“或缘一衍,滴辱累•152•第一章古代兵役世”的政策,老百姓稍微出点差错,就被强制当兵,其家也沦为军户,以此来补充世袭兵。士兵形同刑徒,地位低贱,除非官家特许,不能取得平民身份。
北魏统治北中国长达一百多年,其兵役制度,基本上是世兵制。把原来的鲜卑部族成员变为职业兵,世代相传,称为“营户”和“镇户”,家属随士兵聚居于各营堡中,由国家供给粮饷。营户和镇户另编户籍,不属地方官员管辖,而由军队直接管辖,实同军户。由营户和镇户组成的部队为常备军,是国家的基本武装力量。北魏军队成员属统治阶级,政治地位高,待遇优厚,军士 “乐为战死”,部队战斗力很强。
元代开国初期,规定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蒙古族男子“尽佥为兵”,后因兵源不足,又规定汉人二十户出一兵,“丁力强者充军,弱者出钱”,凡当过兵的“壮士及有力之家”都列为军户,世代为兵。
第五节府兵制隋唐时代主要实行府兵制。这一制度始于西魏,隋唐时逐渐完善。所谓府兵,即属于各级兵府领导的兵。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政权,今酒泉地归西魏。府兵制的创建者宇文泰,出身于南匈奴贵族,世为宇文部首领,西魏时任大将军、大丞相,长期专制西魏朝政。大统八年(公元524年),宇文泰把他统率的5万名军队改编为“六军”,分别由六柱国府统领,宇文泰为总领,初步形成了府兵系统。他规定:凡在府兵中服役的士卒和军官,均不列入户籍,因而府兵家庭也就没有其它赋役的负担。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度,是汉武帝实行募兵制后,我国历史上兵役制度的重大创新。
西魏是靠武力维持统治的,因此,内外战争比较频繁。为了及时补充军队的缺额,宇文泰不得不“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征集大量汉人到军队服役,以充实其军事力量。宇文泰把关陇地区地方豪强的私家武装,陆续归并到府兵中去。委汉族地方豪强为“乡绅”,利用汉族地方势力增强其统治力量。并把加强其军事力量的目标转向“乡兵”。乡兵是分散在乡间的地方武装,主要由各地青壮年农民组成。西魏朝廷规定,乡兵要服从调遣,有事出战,无事居乡耕田。乡兵在西魏初便迅速发展起来,组织虽不严密,却第四篇兵役工作是遍及各地的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宇文泰鼓励乡兵、乡团参战,把乡兵的编制与指挥纳入六柱国(即府兵)系统,使乡兵“正规化”、“中央化”。
府兵的政治地位比平民高,经济生活也比较好,因而士气比较旺盛。宇文泰用府兵的办法,建立起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左右了西魏的朝政。公元556年,宇文泰死。次年,其子宇文觉依靠这支军事力量取代西魏,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北周时,府兵制又有新的发展。后来,北周王朝的上柱国、丞相杨坚,又以府兵为工具,代周自立,建立了隋王朝。
杨坚代周后,沿行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并作了较大的改进,将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普遍开设军府。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灭陈朝,统一全国,文帝即下诏书,规定所有户口一律归州县管理,“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从此,府兵编入民籍,改“兵民异籍”为“兵民合一”,改“兵民分治”为“兵民合治”。隋朝还规定,18岁以上的男性为丁,人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60岁为老,免除兵役义务。隋分全国12卫,各卫设大将军,分别统领所属府兵。
在此之前的府兵家庭被称为“军户”,军户家属随营居住,随军调动,不能长居久安。军户编入民户后,改属州县管理,和一般居户一样从事生产劳动,因而军府和民户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这种变革给人民生活和发展生产带来很大好处。军户编入民户后可依《均田令》分给土地,并保有自己的产业,家属也能在一地长居久安,从事生产,家庭经济生活较前有明显改善。这种把军户世代服兵役的政策改为人民普遍服兵役的政策,不仅使原来军户的兵役负担大为减轻,同时也扩大了兵源,有利于军队建设和征战行动。
唐朝前期盛行的府兵制,是在隋朝府兵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开始设置军府,到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府兵制的改革基本完成,主要是降低了军府的等级,把过去由大将军、将军统领的军府改为“折冲府”,即把过去统兵数万人的大府改为只统兵千把人的小府。内设16卫,培植将才;外设折冲府,分镇四方,储兵备武。各府设折冲、果毅、都督等军事官员,分别担任领兵作战、训练府兵、教民习战等任务。府兵的来源是军府所辖地区的成丁农民。这些府兵,平时散居乡间务农,农隙进行训练;战时奉命集中,由朝廷任命的将领统率,离境出征;战争结束后,“兵丁散于府,将归于朝”。
•154•第一章古代兵役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后,由于与府兵制紧密相关的户籍管属和土地授受等制度被废弃,使府兵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府兵制日渐衰落,到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完全废弃。
第六节举族皆兵历史上曾在安西一带角逐的匈奴、月氏、羌族、吐蕃等少数民族,因其本族人口较少,长期的生活习俗是“上马为兵,下马驻牧”,凡有征战,一般都是举族皆兵。部落首领就是军事指挥官,部落成员中的男性丁壮都是战斗兵,老弱妇孺也都驱赶着牛羊,跟在部队后面行动,担负后勤供应保障工作。部族兵员是他们征战和统治其他民族依靠的基本力量。这些“胡军”军民一体,行动迅速,有家族、民族、亲缘关系维系,因而战斗力都很强。曾在安西境内称雄的匈奴、月氏、吐蕃、五凉、大夏、金、元、辽等都是如此。
“胡人”奉行的举族皆兵,或曰全民皆兵,是以其社会自下而上形成的“军事部落”式所决定的,由于军队经常流动作战,使其家眷老幼也经常处在游移流动之中,不能过安定的生活,有时部队要作大幅度流动,老弱妇孺和牛羊常常甩在后面,遭受敌军袭击,造成极大伤亡。因而其一旦建立了统治政权,这种兵役制度就日渐退居其次,由其他兵役制度所替代。
第七节卫所兵制明朝在边疆地区实行卫、所军管制,归省都司(或行都司)管辖。在卫、所服役的兵丁称为军士,其来源,有随从朱元璋起义的义军;有从元军方面收容的归附兵;有从农民征调来的垛集兵;还有因犯罪而被谪发的罪徒兵。垛集兵是卫、所兵的主要来源。明初规定,“民出一丁为军”者,称为正军,其子弟原籍族人顶替。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世兵制。
按明代世兵制的规定,平民只要被签发为兵,子孙世代都要列入军籍,不许变易。民籍和军籍的区分是极其严格的,军籍属都司及卫所管理,民籍属府、州、县管理,军和民截然分开。卫、所军士不受行政官吏管辖,其身份第四篇兵役工作和经济地位与民不同。但是,如果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一家就要转入军籍,便永远为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并豁免一定的徭役。成祖(朱棣)即位后,“遣给事等管分阅天下各军,重定垛集兵更代法”,规定垛“正军”,要定“贴户”若干;正军死,以贴户丁壮补充。后来又对垛集兵更代法进行修订,增加贴户数量,以扩充兵员。这样,军户世袭,轮流当正军出征、执勤,至期返卫,可使军丁及军户安心生产,军户生活有了保障。因此,明朝早期军队兵员充裕,战斗力较强。
明代中期,随着土地兼并日烈,卫、所屯田遭到严重破坏,兵源不继,卫所之兵战斗力大减,遂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改行募兵制。
第八节清代的几种兵役
一、八旗兵的世袭制清军入关前,沿袭辽、金、元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实行“举族皆兵”的制度。初期,满洲贵族将满人部落编为红、黄、蓝、白4旗,后又增编镶红、镶黄、镶蓝、镶白4旗,合称满八旗;公元1635年,又将蒙古人编为蒙古八旗;以后又将归降的汉人编为汉军八旗,共为24旗。旗兼有政治、经济和军事3种,而最主要的是战备、出征。旗兵战时集合旗下,披甲骑马出征;平时散处各户,参与生产和社会活动。“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满洲贵族就是依靠这种旗兵制度,统一了全国,并维持其统治。
八旗兵的编役,清廷曾规定,凡年龄在16岁以上的男性旗人皆为兵,《清通典•兵志》载:“我朝八旗之制,……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于旗者,皆可为兵”。八旗兵为世袭兵役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为兵。
二、绿营兵的收编和募集清军入关后,由于旗兵数量太少,远不能在全国布防,故大力收编明军,招募汉人为兵,以绿旗为营标,称为“绿营兵”。绿营兵是清朝统治甘肃的基本力量。
三、新军的招募•156•第一章古代兵役清朝末年,中国屡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中,清王朝深受兵力不济、军威不振之苦。有鉴于此,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将领及人士提出,依照日本及西方国家的做法,编练新式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实行募军制,招募对象为20~25岁之壮丁。编练新军时规定:新军士兵服役3年, 期满后,发给凭证,资遣回乡,列为“续备兵”,月给饷银一两,自谋职业;每年定期集中于州府,训练一月;如遇战事,即应召服现役。但自新军组建后, 并未如期资遣。民国成立后,这批新军又被改编为民国军队。
第九节其他征兵方法在古代长期有连年征战中,兵员征集除上述数种兵役制度外,尚有招降纳叛、罪兵谪守等。
招降纳叛招收降兵和纳编叛军,是古代各朝兵员的重要制度之一。汉前长居安西一带的少数民族,征战中所得虏卒降兵,一是“悉数杀之”;二是分诸部属,充作奴隶,驱其苦役。自汉始,每有降兵,即编入己军,以扩大自己的队伍。汉族用少数民族兵、将戍边,“以胡制胡”;少数民族收降汉兵,弥补本部族人少兵乏的缺陷;汉族各封建统治集团间也招降纳叛,壮大军威。由汉至清,莫不如此。
罪兵谪守河西边防远离朝廷,自然条件恶劣,战事频繁,在此戍守征战,是苦上加苦,而朝廷要保边扩土,开拓河西,需大量兵员,除征调“正卒”外,还要大量谪发罪人、奴隶征战、戍边。汉武帝时,在河西地区“列四郡,置两关”,修筑长城,屯田戍边,经营开发,动用的军队多达二、三十万人,其中有许多是征发的“刑徒”和奴隶。许多在押囚犯,朝廷赦免其罪,让他们与妻子儿女一起到边疆地区落户定居,屯田戍边。
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朝廷派遣执金吾将军马适建等,率三辅、太常所属“罪徒”,“皆免刑”,“以击氐人”。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诏三辅、中都“官徒”,免刑出征,“以击西羌”。西汉后期,这种情况更为普遍,除大量“谪发罪人”投入战争或戍边外,还大量征发奴隶服兵役。“谪发”扩大了汉朝的兵源。被谪发的都是“罪人”、奴隶、违法商贾和“恶少年”。朝廷规定,罪囚、奴隶打了胜仗后能获得自由,因而他们作战勇敢。
第二节征兵制征兵制的实行,始于西汉。征兵制是男子到一定年龄,由官府登记,需要时出征服兵役,服役期满后还乡为民做为后备兵,遇有大的战事再应征出战。规定男子在23至56岁期间服兵役两年。其中一年在本郡服役,学习骑射等军事技术,称“正卒”;一年守护京都或戍守边防,称卫士或戍卒。汉武帝开发河西,征战和屯田的士卒都从内地征发而来,有时还征被征服的少数民族青壮年从事征战。如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广利击大宛,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14年)赵充国西击先零羌,主要兵员就是“杂胡”。
金元时期,蒙古族统治华夏,由于连年大规模的征战及战后占领地统治的需要,本民族人远不够用,也实行征兵制。征集其他民族兵员供其驱使,“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 。完颜亮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为进攻南京,下令凡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一律纳入军籍”,以汉族兵在第一线作战,女真兵在后督战。元时规定汉人“强者充军,弱者出钱” 。
第三节募兵制实行过募兵制的,有汉、北魏、唐、宋、清。募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种原因“自愿”为军。如逢国家有难挺身报国的;生活所迫,当兵吃粮,养家糊口的;投身军伍,希图建功疆场、博取功名富贵的等。
西汉王朝抵抗匈奴侵略的战争,符合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因此,人民愿意应召从军,有的还自己带良马,要求从军参战。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西汉王朝开始大规模讨伐匈奴,陇西成纪人李广,就自动应募从军,后来成为有名的“飞将军”。骑都尉李陵从楚地招募“勇士、奇才、剑客”5000多名,在酒泉、张掖间驻防练兵,防备匈奴入侵。这些勇士都是自愿来保卫国家边疆的,一般都有较高的武艺,而且体格强健,任侠好义,重名轻利,作战勇敢。到东汉时,由于朝廷长期废弛地方军事工作,致使民不习战,官不知兵,发生外族犯边和内乱等突发事件后,各郡无以承担作战任务,朝廷只好实行募兵制度,招募能战之兵。从安帝永初起,“羌乱”不止,募兵的规模越来越大。募兵,往往是临战前的应急措施,无暇严格选择,以致有很多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痞子无赖等社会渣滓,都应召从军。这样招募来的士卒,素质不高,无论是军纪,还是武艺,都远远赶不上西汉时招募的兵员。有些官员还纵容士兵掠夺民间财物,为非作歹,以引诱更多的人应募从军。招募的士兵一般都是终身从军,因而军队中老弱之卒越集越多,大大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以致在多次“征羌” 战争中遭受失败,这是东汉王朝衰败的突出表现。
北魏在北中国确立统治地位后,由于不断对南朝和西北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用兵,光靠鲜卑人当兵,已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到太武帝拓拔焘时,开始实行募兵制,招募大量汉人服兵役,补充常备军。
唐代前期,在实行府兵制的同时,也实行募兵制,但这时的募兵,仅是府兵制的一种补充手段、辅助措施,府兵制遭到破坏后,募兵制就成了唐王朝的主要兵役制度。高宗李治执政时期,府兵制就已经开始衰落,而边防又多事端,边境之军、守捉、镇大量增加,常年驻戍的军队有60多万人。这些戍第四篇兵役工作边兵大多是招募来的。玄宗李隆基时,罢边镇兵20多万人,使之还农,但戍边兵仍然不少。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河西节度使,即辖10军、14守捉,统兵7.3万人;陇右节度使,辖18军、3守捉,统兵7.5万人。两镇合计28军、17守捉,共有边兵14.8万余人,这些边兵全靠招募而来的。
公元848年,张议潮率众起义时,其基本部队都是招募的“瓜沙子弟”(今敦煌市、安西县),被唐王朝命名为“归义军”。张议潮依靠这支队伍,驱逐吐蕃势力,每到一地,广大人民一呼百应,纷纷参加归义军,吐蕃兵望风披靡,河西、陇右很快光复。
宋代时期募兵制比较盛行。北宋时,朝廷直接管辖的禁军,从全国各地招募;守卫各州的厢兵,在本州范围内招募;守卫边疆地区的蕃兵,从当地少数民族中招募;保卫家乡的乡兵,由各地按户籍抽调的壮丁组成。此外, 还强迫罪徒当兵,士兵的社会地位低下。
第四节世兵制世兵制,即一入军籍,世代为兵之意。早在三国、两晋时代就实行这种制度,把士兵之家列为军户,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服兵役。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割据,军阀混战不止,全国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鼎立的三方为了扩大军队,战胜对手,都强制实行世袭兵役制,简称“世兵制”。其要旨是把所有的户口分为三种:一是普通户,归郡县官府管理,从事农耕,为国家交租粮、出劳役;二是屯田户,归典农都尉管理,为国家种田,生产粮食;三是军户,或称“士家”,归军府或州郡的军事官员管理,为国家服兵役。这一制度的特点是军民分离,把士兵全家从普通百姓中分离出来,脱离民籍,变为军籍。士兵本人终身为兵,其家子子孙孙世代为兵。
西晋时,规定军户要世世代代为兵。晋代军户的兵役、劳役负担,比三国时期更为繁重,朝廷规定,军户男子“年十六为全丁,十三为半丁”。全丁戍守,半丁漕运(军事水运)。这样,军户既服兵役,又服劳役,而且父子同时服役,父南子北,长期分离,使军户“咸更不宁”,生活极端困苦,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再娶者” 。于此同时,晋代还实行“或缘一衍,滴辱累•152•第一章古代兵役世”的政策,老百姓稍微出点差错,就被强制当兵,其家也沦为军户,以此来补充世袭兵。士兵形同刑徒,地位低贱,除非官家特许,不能取得平民身份。
北魏统治北中国长达一百多年,其兵役制度,基本上是世兵制。把原来的鲜卑部族成员变为职业兵,世代相传,称为“营户”和“镇户”,家属随士兵聚居于各营堡中,由国家供给粮饷。营户和镇户另编户籍,不属地方官员管辖,而由军队直接管辖,实同军户。由营户和镇户组成的部队为常备军,是国家的基本武装力量。北魏军队成员属统治阶级,政治地位高,待遇优厚,军士 “乐为战死”,部队战斗力很强。
元代开国初期,规定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蒙古族男子“尽佥为兵”,后因兵源不足,又规定汉人二十户出一兵,“丁力强者充军,弱者出钱”,凡当过兵的“壮士及有力之家”都列为军户,世代为兵。
第五节府兵制隋唐时代主要实行府兵制。这一制度始于西魏,隋唐时逐渐完善。所谓府兵,即属于各级兵府领导的兵。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政权,今酒泉地归西魏。府兵制的创建者宇文泰,出身于南匈奴贵族,世为宇文部首领,西魏时任大将军、大丞相,长期专制西魏朝政。大统八年(公元524年),宇文泰把他统率的5万名军队改编为“六军”,分别由六柱国府统领,宇文泰为总领,初步形成了府兵系统。他规定:凡在府兵中服役的士卒和军官,均不列入户籍,因而府兵家庭也就没有其它赋役的负担。宇文泰创立的府兵制度,是汉武帝实行募兵制后,我国历史上兵役制度的重大创新。
西魏是靠武力维持统治的,因此,内外战争比较频繁。为了及时补充军队的缺额,宇文泰不得不“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征集大量汉人到军队服役,以充实其军事力量。宇文泰把关陇地区地方豪强的私家武装,陆续归并到府兵中去。委汉族地方豪强为“乡绅”,利用汉族地方势力增强其统治力量。并把加强其军事力量的目标转向“乡兵”。乡兵是分散在乡间的地方武装,主要由各地青壮年农民组成。西魏朝廷规定,乡兵要服从调遣,有事出战,无事居乡耕田。乡兵在西魏初便迅速发展起来,组织虽不严密,却第四篇兵役工作是遍及各地的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宇文泰鼓励乡兵、乡团参战,把乡兵的编制与指挥纳入六柱国(即府兵)系统,使乡兵“正规化”、“中央化”。
府兵的政治地位比平民高,经济生活也比较好,因而士气比较旺盛。宇文泰用府兵的办法,建立起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左右了西魏的朝政。公元556年,宇文泰死。次年,其子宇文觉依靠这支军事力量取代西魏,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北周时,府兵制又有新的发展。后来,北周王朝的上柱国、丞相杨坚,又以府兵为工具,代周自立,建立了隋王朝。
杨坚代周后,沿行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并作了较大的改进,将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普遍开设军府。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灭陈朝,统一全国,文帝即下诏书,规定所有户口一律归州县管理,“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从此,府兵编入民籍,改“兵民异籍”为“兵民合一”,改“兵民分治”为“兵民合治”。隋朝还规定,18岁以上的男性为丁,人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60岁为老,免除兵役义务。隋分全国12卫,各卫设大将军,分别统领所属府兵。
在此之前的府兵家庭被称为“军户”,军户家属随营居住,随军调动,不能长居久安。军户编入民户后,改属州县管理,和一般居户一样从事生产劳动,因而军府和民户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这种变革给人民生活和发展生产带来很大好处。军户编入民户后可依《均田令》分给土地,并保有自己的产业,家属也能在一地长居久安,从事生产,家庭经济生活较前有明显改善。这种把军户世代服兵役的政策改为人民普遍服兵役的政策,不仅使原来军户的兵役负担大为减轻,同时也扩大了兵源,有利于军队建设和征战行动。
唐朝前期盛行的府兵制,是在隋朝府兵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开始设置军府,到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府兵制的改革基本完成,主要是降低了军府的等级,把过去由大将军、将军统领的军府改为“折冲府”,即把过去统兵数万人的大府改为只统兵千把人的小府。内设16卫,培植将才;外设折冲府,分镇四方,储兵备武。各府设折冲、果毅、都督等军事官员,分别担任领兵作战、训练府兵、教民习战等任务。府兵的来源是军府所辖地区的成丁农民。这些府兵,平时散居乡间务农,农隙进行训练;战时奉命集中,由朝廷任命的将领统率,离境出征;战争结束后,“兵丁散于府,将归于朝”。
•154•第一章古代兵役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后,由于与府兵制紧密相关的户籍管属和土地授受等制度被废弃,使府兵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府兵制日渐衰落,到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完全废弃。
第六节举族皆兵历史上曾在安西一带角逐的匈奴、月氏、羌族、吐蕃等少数民族,因其本族人口较少,长期的生活习俗是“上马为兵,下马驻牧”,凡有征战,一般都是举族皆兵。部落首领就是军事指挥官,部落成员中的男性丁壮都是战斗兵,老弱妇孺也都驱赶着牛羊,跟在部队后面行动,担负后勤供应保障工作。部族兵员是他们征战和统治其他民族依靠的基本力量。这些“胡军”军民一体,行动迅速,有家族、民族、亲缘关系维系,因而战斗力都很强。曾在安西境内称雄的匈奴、月氏、吐蕃、五凉、大夏、金、元、辽等都是如此。
“胡人”奉行的举族皆兵,或曰全民皆兵,是以其社会自下而上形成的“军事部落”式所决定的,由于军队经常流动作战,使其家眷老幼也经常处在游移流动之中,不能过安定的生活,有时部队要作大幅度流动,老弱妇孺和牛羊常常甩在后面,遭受敌军袭击,造成极大伤亡。因而其一旦建立了统治政权,这种兵役制度就日渐退居其次,由其他兵役制度所替代。
第七节卫所兵制明朝在边疆地区实行卫、所军管制,归省都司(或行都司)管辖。在卫、所服役的兵丁称为军士,其来源,有随从朱元璋起义的义军;有从元军方面收容的归附兵;有从农民征调来的垛集兵;还有因犯罪而被谪发的罪徒兵。垛集兵是卫、所兵的主要来源。明初规定,“民出一丁为军”者,称为正军,其子弟原籍族人顶替。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世兵制。
按明代世兵制的规定,平民只要被签发为兵,子孙世代都要列入军籍,不许变易。民籍和军籍的区分是极其严格的,军籍属都司及卫所管理,民籍属府、州、县管理,军和民截然分开。卫、所军士不受行政官吏管辖,其身份第四篇兵役工作和经济地位与民不同。但是,如果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一家就要转入军籍,便永远为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并豁免一定的徭役。成祖(朱棣)即位后,“遣给事等管分阅天下各军,重定垛集兵更代法”,规定垛“正军”,要定“贴户”若干;正军死,以贴户丁壮补充。后来又对垛集兵更代法进行修订,增加贴户数量,以扩充兵员。这样,军户世袭,轮流当正军出征、执勤,至期返卫,可使军丁及军户安心生产,军户生活有了保障。因此,明朝早期军队兵员充裕,战斗力较强。
明代中期,随着土地兼并日烈,卫、所屯田遭到严重破坏,兵源不继,卫所之兵战斗力大减,遂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改行募兵制。
第八节清代的几种兵役
一、八旗兵的世袭制清军入关前,沿袭辽、金、元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实行“举族皆兵”的制度。初期,满洲贵族将满人部落编为红、黄、蓝、白4旗,后又增编镶红、镶黄、镶蓝、镶白4旗,合称满八旗;公元1635年,又将蒙古人编为蒙古八旗;以后又将归降的汉人编为汉军八旗,共为24旗。旗兼有政治、经济和军事3种,而最主要的是战备、出征。旗兵战时集合旗下,披甲骑马出征;平时散处各户,参与生产和社会活动。“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满洲贵族就是依靠这种旗兵制度,统一了全国,并维持其统治。
八旗兵的编役,清廷曾规定,凡年龄在16岁以上的男性旗人皆为兵,《清通典•兵志》载:“我朝八旗之制,……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于旗者,皆可为兵”。八旗兵为世袭兵役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为兵。
二、绿营兵的收编和募集清军入关后,由于旗兵数量太少,远不能在全国布防,故大力收编明军,招募汉人为兵,以绿旗为营标,称为“绿营兵”。绿营兵是清朝统治甘肃的基本力量。
三、新军的招募•156•第一章古代兵役清朝末年,中国屡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中,清王朝深受兵力不济、军威不振之苦。有鉴于此,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将领及人士提出,依照日本及西方国家的做法,编练新式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实行募军制,招募对象为20~25岁之壮丁。编练新军时规定:新军士兵服役3年, 期满后,发给凭证,资遣回乡,列为“续备兵”,月给饷银一两,自谋职业;每年定期集中于州府,训练一月;如遇战事,即应召服现役。但自新军组建后, 并未如期资遣。民国成立后,这批新军又被改编为民国军队。
第九节其他征兵方法在古代长期有连年征战中,兵员征集除上述数种兵役制度外,尚有招降纳叛、罪兵谪守等。
招降纳叛招收降兵和纳编叛军,是古代各朝兵员的重要制度之一。汉前长居安西一带的少数民族,征战中所得虏卒降兵,一是“悉数杀之”;二是分诸部属,充作奴隶,驱其苦役。自汉始,每有降兵,即编入己军,以扩大自己的队伍。汉族用少数民族兵、将戍边,“以胡制胡”;少数民族收降汉兵,弥补本部族人少兵乏的缺陷;汉族各封建统治集团间也招降纳叛,壮大军威。由汉至清,莫不如此。
罪兵谪守河西边防远离朝廷,自然条件恶劣,战事频繁,在此戍守征战,是苦上加苦,而朝廷要保边扩土,开拓河西,需大量兵员,除征调“正卒”外,还要大量谪发罪人、奴隶征战、戍边。汉武帝时,在河西地区“列四郡,置两关”,修筑长城,屯田戍边,经营开发,动用的军队多达二、三十万人,其中有许多是征发的“刑徒”和奴隶。许多在押囚犯,朝廷赦免其罪,让他们与妻子儿女一起到边疆地区落户定居,屯田戍边。
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朝廷派遣执金吾将军马适建等,率三辅、太常所属“罪徒”,“皆免刑”,“以击氐人”。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诏三辅、中都“官徒”,免刑出征,“以击西羌”。西汉后期,这种情况更为普遍,除大量“谪发罪人”投入战争或戍边外,还大量征发奴隶服兵役。“谪发”扩大了汉朝的兵源。被谪发的都是“罪人”、奴隶、违法商贾和“恶少年”。朝廷规定,罪囚、奴隶打了胜仗后能获得自由,因而他们作战勇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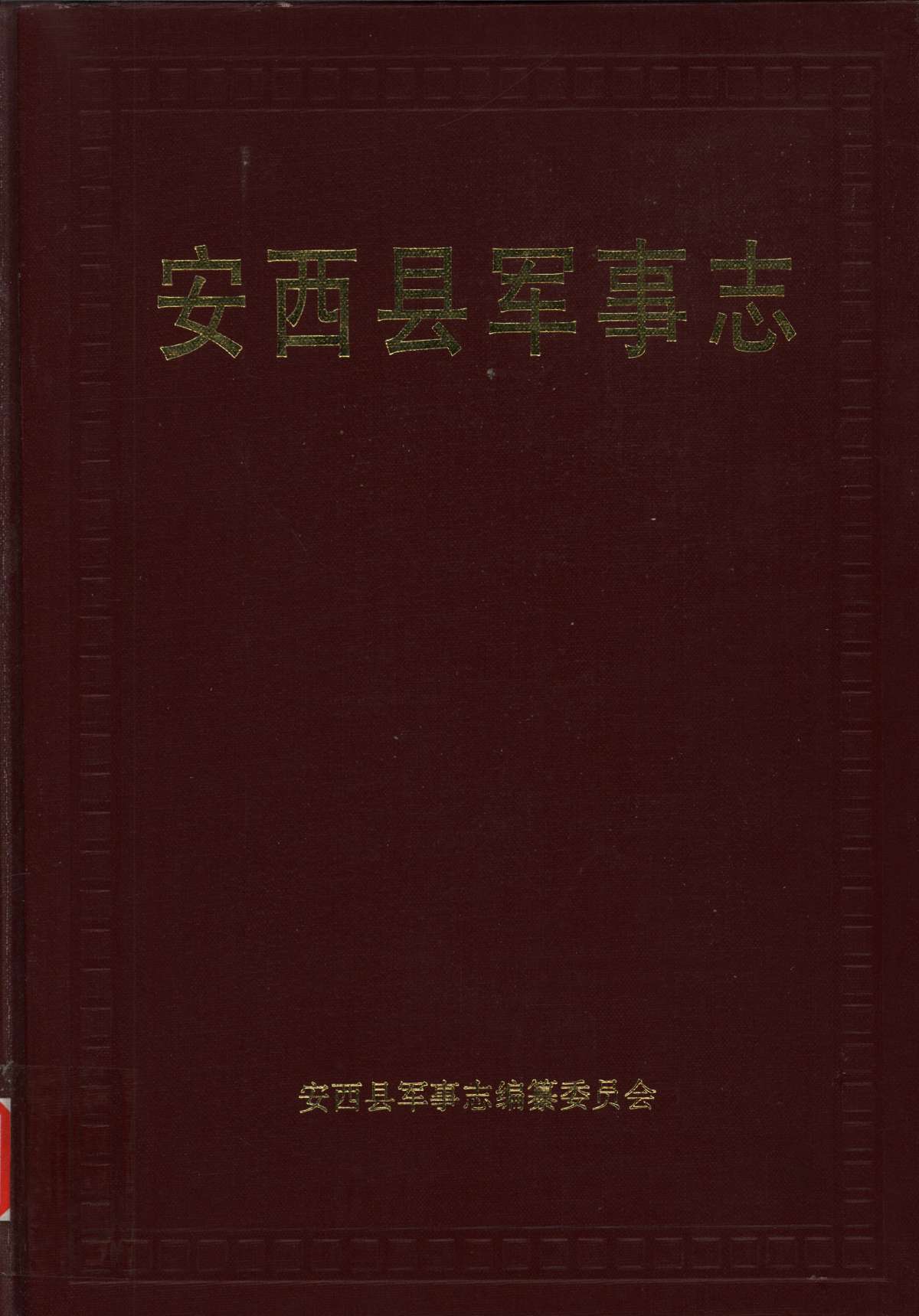
《安西县军事志》
安西,地处甘肃西北,东屏玉门,西邻敦煌,南望祁连,北依大漠,地扼甘新,物产丰阜。早在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西汉时就设有行政建置。南北有祁连山、马鬃山群山环绕,滔滔的疏勒河中流西去,潺潺的榆林河向北蜿蜒,众多绿洲东西分布,山蕴金银铜铁,地产粮棉瓜果,自古即为中央政府控扼甘新之锁钥,经略西域之基地,丝绸之路之重镇,故而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伴随着人类的涉足繁衍,军事活动贯穿古今,干戈频仍,烽火不息,少数民族豪强争草逐水,相互攻杀争斗;历代中央王朝拓土开边,大举征战,各族人民保家卫国,浴血疆场,乃至红军西路军悲歌西进,马家军横行暴虐,军事活动几成历史发展的主线,直至1949年和平解放,这里的人民才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