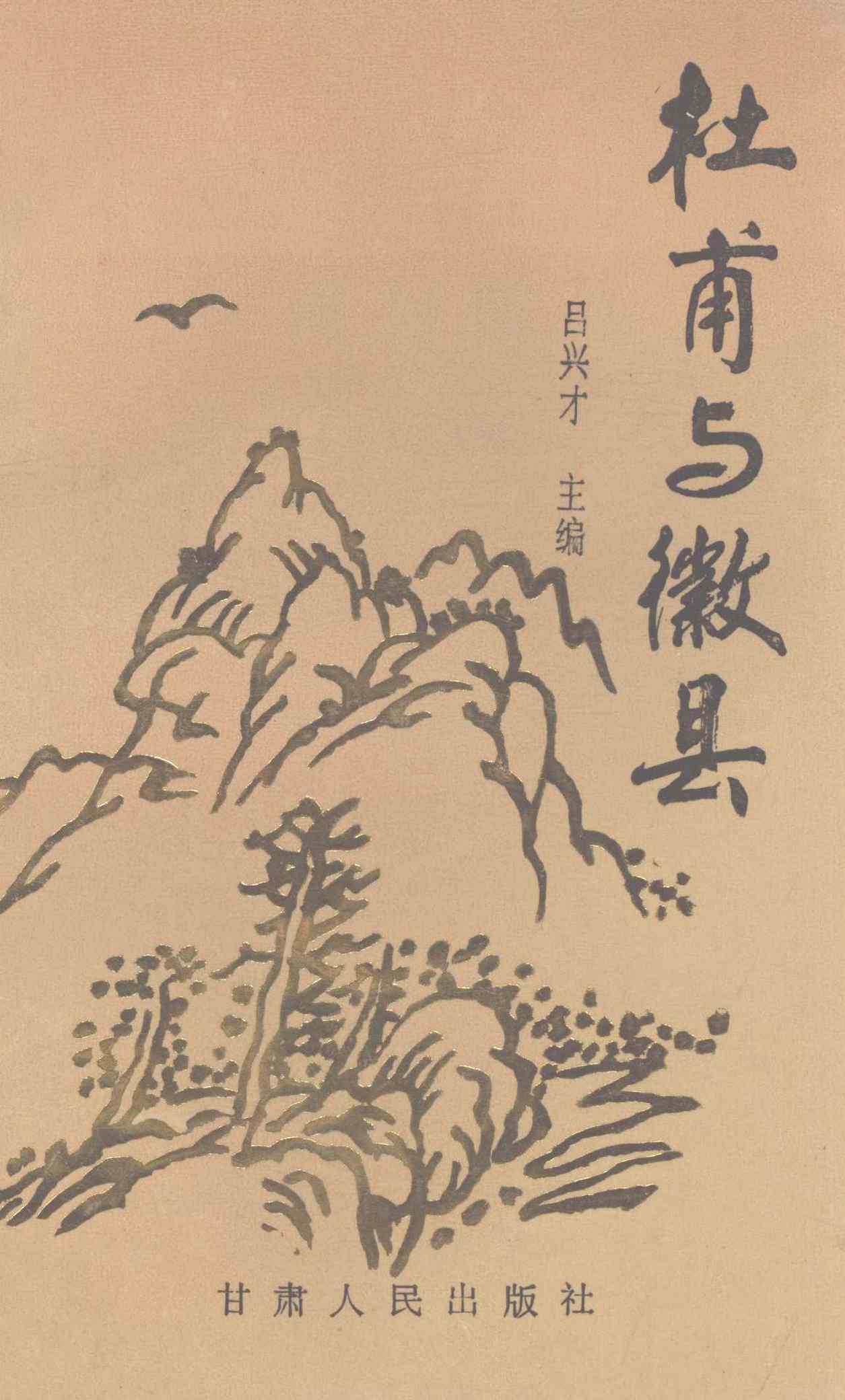内容
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是杜甫一生最困苦的一年,也是他诗歌创作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继《三吏》、《三别》之后,杜甫又创作了独具特色的陇右诗作。诗人在饱经战乱、颠沛流离、间关秦陇之际,挥如椽巨笔,蘸满腔激情,写下了诸如《秦州杂咏二十首》、《同谷七歌》、《陇右纪行诗》等大量脍炙人口、传之不朽的陇右诗作,从而开拓了他诗歌创作的新领域。正如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指出的:“在杜甫的一生,公元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了最高的成就。”可以说,没有陇右之行,就没有陇右诗作,也就没有他在成都乃至晚年在夔州等地的光辉诗篇。因而,陇右诗作是诗人前期和后期诗歌创作的“练环”,在杜甫一生创作中占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研究杜甫诗作的价值,考证杜甫客秦赴蜀路线等方面问题的专家学者不乏其人。就杜甫入蜀路线而言,历来众说纷纭,目前观点尚不统一。作为一个杜诗爱好者,我想就杜甫入蜀是否经过两当县作一考证,并试图阐述自己浅薄的见解,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历来对杜甫入蜀路线的争议
关于杜甫入蜀是否经过两当县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杜甫发秦州,入同谷,赴成都。冯至先生早在1962年出版的《杜甫传》中就提出了这种观点:“他从秦州西南的赤谷起始这段行程,路过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入同谷界内的积草岭,直到同谷附近的泥功山、凤凰台”“..他一起身便得翻度木皮岭,夜半渡过水会渡,走过飞,仙阁的云栈,到了绵谷县(今四川广元)东北八十里的龙门阁。”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杜甫自秦州入蜀没有经过河池县(今徽县),也没有经过两当县。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杜甫从秦州出发,经同谷,道两当,尔后赴成都。持这种观点的依据大约是因为杜甫有一首《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明末清初学者王嗣奭撰写的《杜臆》(顺治年间)中对这首诗是这样注的;“公作诗时,侍御尚谪长沙,此过其空宅而思及旧事也,起来因主人不在,故写其空宅舍凄凉光景。”清人杨伦笺注的《杜诗镜铨》(乾隆年间)完全承袭了《杜臆》注释的全部文字。而清人施鸿保著《读杜诗说》(同治年间)中注为“且此是过侍御宅诗”。清代《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十一·名宦(下)载:“..寓成州同谷县,道两当县嘉陵江上,寓吴侍御宅,时侍御贬长沙,甫怀之作江上宅诗,遂入蜀。”卷十四·人物(二)载:“杜甫自秦州入蜀,道两当,过吴郁宅。”这些历史记载告诉人们,杜甫当年离秦赴蜀是取道两当县的。
翻阅手头有限的几本关于杜甫研究专著和方志,又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杜甫入蜀路线是否经过两当县这个问题上,同一本书中前后就有相互抵触、自相矛盾的地方。《两当县志》:(一)“杜甫子美..暂寓成州同谷县,随多去之,道两当嘉陵江上,寓吴侍御宅,时侍御贬长沙,子美怀之作江上宅诗,遂入蜀”;(二)唐吴郁,邑人,善书法,..当时官侍御史,以直言被谪,初在凤翔与杜子美善,子美客秦州时,常往来其家”。冯至先生的《杜甫传》55页:“后来他在从秦州到同谷的途中,路过吴郁的故乡两当县,访问吴郁的空宅,深深感到良心的谴责。”79页又:“杜甫在初冬十月从秦州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左右,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入蜀,年底到了成都。”
二、杜甫客秦州赴两当县的考证
根据以上资料来看,关于杜甫自秦州入蜀是否经过两当县,的确是一个疑点,同时也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那么杜甫入蜀是否到过两当县?如果去过,是入蜀途中经过两当县,还是在寓居秦州、同谷期间去过?笔者认为,杜甫确实到过两当县,但不是在寓居同谷时,更不是在自同谷到成都的旅途中,而是在寓居秦州时,也就是说,是在发秦州之前,不是经过,而是专程寻访两当县吴郁空宅。
本着“以杜证杜”的原则,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寒城朝烟淡,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鹍鸡号枉渚,日色傍阡陌”。诗一开头,就先勾勒出了一幅陇南山区秋景图:清晨山城上空迷漫着淡淡的雾气,幽谷里经霜而落下的片片红叶,顺江吹来的飒飒秋风,洲上鹍鸡在悲鸣,朝日洒在田畴上。诗人用浓墨重彩渲染了吴郁宅周围的环境,为我们点明了吴郁故宅的地理位置——嘉陵江上游的“枉渚”,同时也透露出诗人隐隐不安的苍凉心情。枉渚,即今甘肃省两当县西坡乡琵琶洲。《杜臆》载:“枉渚,两当地名,见一统志,想其宅在此。”《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注:“枉渚,名琵琶洲,在甘肃两当县南三十里,其地洲渚迂回,人迹罕至,故名”。杜甫在秦州正是秋冬之交,“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别赞上人》)。和“寒城朝烟淡,山谷落叶赤”所写都是深秋季节,这就说明这两首诗都作于此年秋天,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北风吹,鹍鸡号,日色不到,读之惨然”(《杜臆》)。此诗不仅写出了吴郁宅人去宅空,破败凄凉的景象,同时也写出了诗人睹物思人,暗悔自责的心境。他追怀与好友的情谊,“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想象友人被贬后的失意情景,“哀哀失木狖,矫矫避弓翮”。吴郁当初在凤翔处理间谍案时,秉公直言,不滥杀无辜,因而得罪权贵,被贬长沙。而杜甫时为左拾遗,本应替吴郁辩白,但因刚受到房琯事件的打击,不敢多发一言,只能忍看好友含冤。此时他深深受到良心的谴责,“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想到自己目前处境,竟无法补过,不禁仰天长叹。低首徘徊,“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读完全诗,我们不难感受到诗人还有许多不尽之言见于诗外,令人回味无穷;又见出诗人品德的高尚、胸襟的坦荡。如果杜甫没有到过两当,那么他对吴郁宅周围的环境不可能如此了如指掌,也不可能描写得如此细腻而真实。只有亲临其境,才会有这样实际的观察和深刻的感受,现实主义的诗人杜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这首诗的。
杜甫弃官,携家带口流落陇右,其目的是要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在秦州长期居住下去。此时,他并没有到成都去的打算,可以说秦州是杜甫流离的目的地。因此,他满怀希望到城南西枝村寻找建造草堂的基地,但没有成功;靠采药卖钱也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打算另投别处。“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飘荡,何时有终极?(《别赞上人》)杜甫为求生存而四处奔波,可以说只要哪里能有温饱便在哪里栖身。秦州生活虽苦一点,全家尚有安身之处,所以他们能在那里居住近四个月。在发秦州之前,他抽身到两当一行,不论是从在秦州居住的时间上说,还是从秦州的生活条件上说,都是很有可能的,也在乎情理之中。而在同谷,他的处境则更加困苦不堪,全家人几濒绝境。这时正是大雪封山的严冬,为了觅取食物,杜甫“短衣数挽不掩胫”,扛着锄头到深山去挖“黄独”(山芋),但“黄独无苗山雪盛”,只好“此时与子空归来”。回家后但见“男呻女吟四壁静”,“邻里为我色惆怅”(《同谷七歌之二》)。试想生活到了家徒四壁、女儿啼饥号寒的地步,又明知友人(吴郁)远谪长沙,两当县又再无亲可投,无人可依,诗人怎么会携带家小绕道前去两当县呢?另外,杜甫诗中所写访两当吴郁宅时是“山谷落叶赤”的秋天,而寓居同谷时却是“黄独无苗山雪盛”的严冬,季节上相去甚远,这一点不正说明了杜甫到两当不是在寓居同谷期间吗?杜甫发同谷,赴成都,是为艰难的生活所迫,此时他的心情是无限的凄凉和悲伤,“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发同谷县》)。他哪里还有远道去寻访友人的兴趣呢?对于杜甫来说,攀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到成都去寻找生路,这无疑是关系到全家人性命的重大抉择,自然是道路愈近、行期愈短愈好。从同谷到栗亭,翻木皮岭,渡白沙渡,自古就是一条入蜀近道。从《徽县志》的记载来看:西魏时在今白水江镇设明水县,小河厂为槃头故郡,唐时王铎曾于大河店设置木皮关(木皮关因木皮岭在其西南而得名),以遮秦陇。小河厂(槃头郡)、大河店(木皮关)、白水江镇(鸣水县)呈丁字形分布在方围不到百里的狭窄地带,如此郡县相连,驿站、关隘相接,不正说明这里是入蜀门户之险要吗?杜甫一家怎么会舍近求远,绕道两当而后入蜀呢?况且从同谷到两当,不管走哪一条路,都必须穿越古河池(今徽县城),至今,我们在任何史书和古籍中都没有发现杜甫入蜀经过徽县的文字记载,杜诗本身亦没有只字提及。因此,笔者认为杜甫发同谷,道两当之说尚缺乏一定的历史资料依据,也不符合杜甫当时的生活境遇。
杜甫从秦州到成都历尽了艰辛,但他的诗歌创作却得到惊人的收获。这半年内仅流传下来的诗歌约有一百二十多首,若是把这些诗从全集中抽出来,便可自成一集。我们揣想,诗人写这些诗是有一定计划性,除去秦州诗以外,便都是离秦赴蜀旅途纪行诗。所谓纪行诗,就像现在的旅行日记,每经一地即写一篇,有一定的时间、地点。这些诗具体地描绘了祖国西北边塞的秀丽山川,风土人情,诚如宋人林亦之所说——“杜陵诗卷是图经”。《杜诗镜铨》、《杜臆》、《读杜诗说》等研究杜诗的专著,对杜甫在这段时间里的诗歌排列顺序是基本一致的,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那就是按照成诗的时间先后依次排列的。这从诗歌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也能表现出来,从《秦州杂诗》到《别赞上人》可以看出诗人由原先准备在秦州久居的希望变成失望,不得不远涉同谷的思想变化轨迹。诗人将赴同谷,分别去向好友叙别,相互勉励,“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别赞上人》后下一首就是《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一诗,紧接着就是《发秦州》,这两首诗在内容和反映作者的思想上有内在联系,而又都是临行叙怀之作,很可能是杜甫访吴郁空宅后留在秦州的最后一篇诗作。因此,它排列在杜甫秦州诗的最末,是较合理的。人所共知,从清初到鸦片战争二百多年间,清王朝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累兴文字狱,因而清代考据之风大盛。这虽然阻碍了诗文创作的发展,却产生了大量有关诗、词、文的理论批评著作,对前代作品的编选、整理、注释和研究工作有很大建树。清代几部杜诗研究专著都将这首诗排列在秦州诗的结尾,却没有将它排在纪行诗中去,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前代学者的失误?这一点我们在目前还不能作出肯定结论,但这首诗在任何版本的杜诗集中都没有排在纪行诗中去,这就说明其体裁、风格和内容都与纪行诗有明显的差异。这样,以地名为题目,以反映诗人在旅途所见所闻,以及抒发个人情怀为主要内容的陇右纪行诗,其排列顺序本身就从另一个角度基本否定了杜甫自同谷到两当之说。笔者认为杜甫陇右纪行诗的排列在这一段的主要部分是基本符合实际地理情况的。杜甫是非常珍视朋友之谊的,他在秦州写了不少怀念友人的诗。他写诗给薛据和毕曜、高适和岑参等人,其中感人至深的要算《梦李白二首》,这两首诗抒发了对李白死生未卜的无限疑惧和关怀之情,字里行间使人感到杜甫身处逆境却关心别人疾苦的高尚人品,他以同样的真挚的感情来关心吴郁,“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想到此去关山万重,蜀道艰辛,恐怕再也不能返回秦州,那么在别赞上人后,前往两当县寻访吴郁空宅,也是人之常情。明知故人不在而寻访之,越发显示出杜甫对友情的珍重,对故人的眷恋,仿佛他只要去看一下吴郁空宅,便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慰籍。再者吴郁远谪长沙,生死未卜,如果在发秦州之前不到两当去一睹吴郁故宅,这对注重友情的杜甫来说,将是终生的遗憾。这样,杜甫此举的目的与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地理形势上说,秦州距两当走小路仅二百多里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远行主要靠步行,二百多里路往返也用不了几天时间。况且杜甫在流亡的日子里安步当车已成习惯,正如《同谷七歌》中所云:“三年饥走荒山道”,他在长安、凤翔作官时就曾徒步回到奉先县(陕西蒲城)、鄜州(陕西富县)去探视妻子家人,“青袍朝士最困苦,白头拾遗徒步归”(《徒步归行》)。他这时身为普通难民,就更不能备车马走大道,只有取小路前往两当。尽管山路曲折艰难,也难以阻止杜甫寻访友人故宅的急切心情。《秦州志》记载,两当县北至秦州界仅九十里路程。另据徽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绘制的红二方面军(1936年)和王震部队(1945年)从两当入徽县境,经过韩家湾(韩家湾在徽县柳林乡境内,是嘉陵江上游的自然村落,为两当走天水小路的必经之地,附近甘沟村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庙坪村有三五九旅烈士纪念碑,1981年韩湾曾出土罐藏古钱币近千枚,囊括朝代甚多,证明这里古代商品货币贸易较活跃。相隔近十年,两支大部队行军都经过这里,不能不引起笔者对这条路线的重视)、太白乡、高桥乡进入天水境的行军路线图推测,这条路应是天水到两当的一条近道,至今这条路上尚有人行走。不管朝代更替,人事变迁,江河地理的变化毕竟是微乎其微的。杜甫当年是否就从这条路前往两当,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在抄近路,省时间这一点上,古人和今人大概是相通的。《两当县志》记载“子美客秦州时,常往来其家”(疑“常”应为“尝”)。这就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杜甫寓居秦州时到过两当县,我们不能不认为它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证据。
杜甫公元759年的陇右之行,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诗文,这些诗饱含着诗人的血泪,它是杜甫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千古不朽的陇右诗篇将同杜甫的名字一起,永远铭刻在陇右人民的心间。
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研究杜甫诗作的价值,考证杜甫客秦赴蜀路线等方面问题的专家学者不乏其人。就杜甫入蜀路线而言,历来众说纷纭,目前观点尚不统一。作为一个杜诗爱好者,我想就杜甫入蜀是否经过两当县作一考证,并试图阐述自己浅薄的见解,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历来对杜甫入蜀路线的争议
关于杜甫入蜀是否经过两当县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杜甫发秦州,入同谷,赴成都。冯至先生早在1962年出版的《杜甫传》中就提出了这种观点:“他从秦州西南的赤谷起始这段行程,路过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入同谷界内的积草岭,直到同谷附近的泥功山、凤凰台”“..他一起身便得翻度木皮岭,夜半渡过水会渡,走过飞,仙阁的云栈,到了绵谷县(今四川广元)东北八十里的龙门阁。”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杜甫自秦州入蜀没有经过河池县(今徽县),也没有经过两当县。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杜甫从秦州出发,经同谷,道两当,尔后赴成都。持这种观点的依据大约是因为杜甫有一首《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明末清初学者王嗣奭撰写的《杜臆》(顺治年间)中对这首诗是这样注的;“公作诗时,侍御尚谪长沙,此过其空宅而思及旧事也,起来因主人不在,故写其空宅舍凄凉光景。”清人杨伦笺注的《杜诗镜铨》(乾隆年间)完全承袭了《杜臆》注释的全部文字。而清人施鸿保著《读杜诗说》(同治年间)中注为“且此是过侍御宅诗”。清代《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十一·名宦(下)载:“..寓成州同谷县,道两当县嘉陵江上,寓吴侍御宅,时侍御贬长沙,甫怀之作江上宅诗,遂入蜀。”卷十四·人物(二)载:“杜甫自秦州入蜀,道两当,过吴郁宅。”这些历史记载告诉人们,杜甫当年离秦赴蜀是取道两当县的。
翻阅手头有限的几本关于杜甫研究专著和方志,又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杜甫入蜀路线是否经过两当县这个问题上,同一本书中前后就有相互抵触、自相矛盾的地方。《两当县志》:(一)“杜甫子美..暂寓成州同谷县,随多去之,道两当嘉陵江上,寓吴侍御宅,时侍御贬长沙,子美怀之作江上宅诗,遂入蜀”;(二)唐吴郁,邑人,善书法,..当时官侍御史,以直言被谪,初在凤翔与杜子美善,子美客秦州时,常往来其家”。冯至先生的《杜甫传》55页:“后来他在从秦州到同谷的途中,路过吴郁的故乡两当县,访问吴郁的空宅,深深感到良心的谴责。”79页又:“杜甫在初冬十月从秦州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左右,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入蜀,年底到了成都。”
二、杜甫客秦州赴两当县的考证
根据以上资料来看,关于杜甫自秦州入蜀是否经过两当县,的确是一个疑点,同时也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那么杜甫入蜀是否到过两当县?如果去过,是入蜀途中经过两当县,还是在寓居秦州、同谷期间去过?笔者认为,杜甫确实到过两当县,但不是在寓居同谷时,更不是在自同谷到成都的旅途中,而是在寓居秦州时,也就是说,是在发秦州之前,不是经过,而是专程寻访两当县吴郁空宅。
本着“以杜证杜”的原则,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寒城朝烟淡,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鹍鸡号枉渚,日色傍阡陌”。诗一开头,就先勾勒出了一幅陇南山区秋景图:清晨山城上空迷漫着淡淡的雾气,幽谷里经霜而落下的片片红叶,顺江吹来的飒飒秋风,洲上鹍鸡在悲鸣,朝日洒在田畴上。诗人用浓墨重彩渲染了吴郁宅周围的环境,为我们点明了吴郁故宅的地理位置——嘉陵江上游的“枉渚”,同时也透露出诗人隐隐不安的苍凉心情。枉渚,即今甘肃省两当县西坡乡琵琶洲。《杜臆》载:“枉渚,两当地名,见一统志,想其宅在此。”《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注:“枉渚,名琵琶洲,在甘肃两当县南三十里,其地洲渚迂回,人迹罕至,故名”。杜甫在秦州正是秋冬之交,“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别赞上人》)。和“寒城朝烟淡,山谷落叶赤”所写都是深秋季节,这就说明这两首诗都作于此年秋天,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北风吹,鹍鸡号,日色不到,读之惨然”(《杜臆》)。此诗不仅写出了吴郁宅人去宅空,破败凄凉的景象,同时也写出了诗人睹物思人,暗悔自责的心境。他追怀与好友的情谊,“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想象友人被贬后的失意情景,“哀哀失木狖,矫矫避弓翮”。吴郁当初在凤翔处理间谍案时,秉公直言,不滥杀无辜,因而得罪权贵,被贬长沙。而杜甫时为左拾遗,本应替吴郁辩白,但因刚受到房琯事件的打击,不敢多发一言,只能忍看好友含冤。此时他深深受到良心的谴责,“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想到自己目前处境,竟无法补过,不禁仰天长叹。低首徘徊,“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读完全诗,我们不难感受到诗人还有许多不尽之言见于诗外,令人回味无穷;又见出诗人品德的高尚、胸襟的坦荡。如果杜甫没有到过两当,那么他对吴郁宅周围的环境不可能如此了如指掌,也不可能描写得如此细腻而真实。只有亲临其境,才会有这样实际的观察和深刻的感受,现实主义的诗人杜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这首诗的。
杜甫弃官,携家带口流落陇右,其目的是要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在秦州长期居住下去。此时,他并没有到成都去的打算,可以说秦州是杜甫流离的目的地。因此,他满怀希望到城南西枝村寻找建造草堂的基地,但没有成功;靠采药卖钱也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打算另投别处。“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飘荡,何时有终极?(《别赞上人》)杜甫为求生存而四处奔波,可以说只要哪里能有温饱便在哪里栖身。秦州生活虽苦一点,全家尚有安身之处,所以他们能在那里居住近四个月。在发秦州之前,他抽身到两当一行,不论是从在秦州居住的时间上说,还是从秦州的生活条件上说,都是很有可能的,也在乎情理之中。而在同谷,他的处境则更加困苦不堪,全家人几濒绝境。这时正是大雪封山的严冬,为了觅取食物,杜甫“短衣数挽不掩胫”,扛着锄头到深山去挖“黄独”(山芋),但“黄独无苗山雪盛”,只好“此时与子空归来”。回家后但见“男呻女吟四壁静”,“邻里为我色惆怅”(《同谷七歌之二》)。试想生活到了家徒四壁、女儿啼饥号寒的地步,又明知友人(吴郁)远谪长沙,两当县又再无亲可投,无人可依,诗人怎么会携带家小绕道前去两当县呢?另外,杜甫诗中所写访两当吴郁宅时是“山谷落叶赤”的秋天,而寓居同谷时却是“黄独无苗山雪盛”的严冬,季节上相去甚远,这一点不正说明了杜甫到两当不是在寓居同谷期间吗?杜甫发同谷,赴成都,是为艰难的生活所迫,此时他的心情是无限的凄凉和悲伤,“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发同谷县》)。他哪里还有远道去寻访友人的兴趣呢?对于杜甫来说,攀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到成都去寻找生路,这无疑是关系到全家人性命的重大抉择,自然是道路愈近、行期愈短愈好。从同谷到栗亭,翻木皮岭,渡白沙渡,自古就是一条入蜀近道。从《徽县志》的记载来看:西魏时在今白水江镇设明水县,小河厂为槃头故郡,唐时王铎曾于大河店设置木皮关(木皮关因木皮岭在其西南而得名),以遮秦陇。小河厂(槃头郡)、大河店(木皮关)、白水江镇(鸣水县)呈丁字形分布在方围不到百里的狭窄地带,如此郡县相连,驿站、关隘相接,不正说明这里是入蜀门户之险要吗?杜甫一家怎么会舍近求远,绕道两当而后入蜀呢?况且从同谷到两当,不管走哪一条路,都必须穿越古河池(今徽县城),至今,我们在任何史书和古籍中都没有发现杜甫入蜀经过徽县的文字记载,杜诗本身亦没有只字提及。因此,笔者认为杜甫发同谷,道两当之说尚缺乏一定的历史资料依据,也不符合杜甫当时的生活境遇。
杜甫从秦州到成都历尽了艰辛,但他的诗歌创作却得到惊人的收获。这半年内仅流传下来的诗歌约有一百二十多首,若是把这些诗从全集中抽出来,便可自成一集。我们揣想,诗人写这些诗是有一定计划性,除去秦州诗以外,便都是离秦赴蜀旅途纪行诗。所谓纪行诗,就像现在的旅行日记,每经一地即写一篇,有一定的时间、地点。这些诗具体地描绘了祖国西北边塞的秀丽山川,风土人情,诚如宋人林亦之所说——“杜陵诗卷是图经”。《杜诗镜铨》、《杜臆》、《读杜诗说》等研究杜诗的专著,对杜甫在这段时间里的诗歌排列顺序是基本一致的,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那就是按照成诗的时间先后依次排列的。这从诗歌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也能表现出来,从《秦州杂诗》到《别赞上人》可以看出诗人由原先准备在秦州久居的希望变成失望,不得不远涉同谷的思想变化轨迹。诗人将赴同谷,分别去向好友叙别,相互勉励,“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别赞上人》后下一首就是《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一诗,紧接着就是《发秦州》,这两首诗在内容和反映作者的思想上有内在联系,而又都是临行叙怀之作,很可能是杜甫访吴郁空宅后留在秦州的最后一篇诗作。因此,它排列在杜甫秦州诗的最末,是较合理的。人所共知,从清初到鸦片战争二百多年间,清王朝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累兴文字狱,因而清代考据之风大盛。这虽然阻碍了诗文创作的发展,却产生了大量有关诗、词、文的理论批评著作,对前代作品的编选、整理、注释和研究工作有很大建树。清代几部杜诗研究专著都将这首诗排列在秦州诗的结尾,却没有将它排在纪行诗中去,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前代学者的失误?这一点我们在目前还不能作出肯定结论,但这首诗在任何版本的杜诗集中都没有排在纪行诗中去,这就说明其体裁、风格和内容都与纪行诗有明显的差异。这样,以地名为题目,以反映诗人在旅途所见所闻,以及抒发个人情怀为主要内容的陇右纪行诗,其排列顺序本身就从另一个角度基本否定了杜甫自同谷到两当之说。笔者认为杜甫陇右纪行诗的排列在这一段的主要部分是基本符合实际地理情况的。杜甫是非常珍视朋友之谊的,他在秦州写了不少怀念友人的诗。他写诗给薛据和毕曜、高适和岑参等人,其中感人至深的要算《梦李白二首》,这两首诗抒发了对李白死生未卜的无限疑惧和关怀之情,字里行间使人感到杜甫身处逆境却关心别人疾苦的高尚人品,他以同样的真挚的感情来关心吴郁,“借问持斧翁,几年长沙客?”想到此去关山万重,蜀道艰辛,恐怕再也不能返回秦州,那么在别赞上人后,前往两当县寻访吴郁空宅,也是人之常情。明知故人不在而寻访之,越发显示出杜甫对友情的珍重,对故人的眷恋,仿佛他只要去看一下吴郁空宅,便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慰籍。再者吴郁远谪长沙,生死未卜,如果在发秦州之前不到两当去一睹吴郁故宅,这对注重友情的杜甫来说,将是终生的遗憾。这样,杜甫此举的目的与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地理形势上说,秦州距两当走小路仅二百多里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远行主要靠步行,二百多里路往返也用不了几天时间。况且杜甫在流亡的日子里安步当车已成习惯,正如《同谷七歌》中所云:“三年饥走荒山道”,他在长安、凤翔作官时就曾徒步回到奉先县(陕西蒲城)、鄜州(陕西富县)去探视妻子家人,“青袍朝士最困苦,白头拾遗徒步归”(《徒步归行》)。他这时身为普通难民,就更不能备车马走大道,只有取小路前往两当。尽管山路曲折艰难,也难以阻止杜甫寻访友人故宅的急切心情。《秦州志》记载,两当县北至秦州界仅九十里路程。另据徽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绘制的红二方面军(1936年)和王震部队(1945年)从两当入徽县境,经过韩家湾(韩家湾在徽县柳林乡境内,是嘉陵江上游的自然村落,为两当走天水小路的必经之地,附近甘沟村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庙坪村有三五九旅烈士纪念碑,1981年韩湾曾出土罐藏古钱币近千枚,囊括朝代甚多,证明这里古代商品货币贸易较活跃。相隔近十年,两支大部队行军都经过这里,不能不引起笔者对这条路线的重视)、太白乡、高桥乡进入天水境的行军路线图推测,这条路应是天水到两当的一条近道,至今这条路上尚有人行走。不管朝代更替,人事变迁,江河地理的变化毕竟是微乎其微的。杜甫当年是否就从这条路前往两当,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在抄近路,省时间这一点上,古人和今人大概是相通的。《两当县志》记载“子美客秦州时,常往来其家”(疑“常”应为“尝”)。这就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杜甫寓居秦州时到过两当县,我们不能不认为它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证据。
杜甫公元759年的陇右之行,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诗文,这些诗饱含着诗人的血泪,它是杜甫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千古不朽的陇右诗篇将同杜甫的名字一起,永远铭刻在陇右人民的心间。
相关人物
孙士信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唐代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