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崇拜者的纯女性化
| 内容出处: | 《陇蜀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1820020220000588 |
| 颗粒名称: | 一、崇拜者的纯女性化 |
| 分类号: | K892.2 |
| 页数: | 5 |
| 页码: | 390-39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乞巧自然是女性的活动,崇拜的神灵也是织女(或巧娘娘),为什么还要提出“纯女性化”的命题呢?因为从历代的乞巧风俗来看,崇拜的偶像不止织女,也包括牛郎或其他男性神灵。所以参与乞巧活动者不止女性,亦不乏男性的参与。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中,不仅崇拜织女,也崇拜牛郎;不仅用瓜果祭祀牵牛、织女,而且画牛郎、织女的画像。这种崇拜传统在处于封建社会盛期的汉唐及两宋时期,显然不是为了歌颂牛郎、织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是延续了人文始祖崇拜的含义,因为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都是传统农耕经济时代的杰出人物,其劳动技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 |
| 关键词: | “巧娘娘” 地域特色 崇拜者 |
内容
西汉水上游乞巧风俗中崇拜的唯一偶像是“巧娘娘”,从当地乞巧歌的内容来考察,巧娘娘其实就是织女,是这一带民间对织女的地域性称呼。但这里的巧娘娘又和当地人崇拜的“××娘娘”不同,巧娘娘中的“娘”读音为“nia”,而不是“niang”。前一种读音的“娘”是西汉水上游一带方言中对母亲的称呼;后一种读音的“娘娘”则往往是对女性神灵的称呼,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花儿娘娘等,有时也是对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女性、贵妇人、官太太的称呼。同一个字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读音,表达的含义也截然不同。前者体现出亲密无间的亲情关系,后者则用来称呼高高在上的高贵的女性神灵或者贵族女性。从整个乞巧活动期间年轻姑娘的情感活动来看,巧娘娘与她们达到了精神与情感的交融,这种真挚的感情甚至超越了现实中的母女感情,对母亲不敢说、不能表白的心声,却能在乞巧活动中向巧娘娘倾诉,有时尽管是无声的,但实现了真正的心灵沟通。尤其是七月七日夜晚送巧娘娘上天的时候,全体姑娘都流着眼泪,唱着悲情的送巧歌将巧娘娘的纸偶像烧掉,俨然一种生离死别的凄婉场景。
乞巧自然是女性的活动,崇拜的神灵也是织女(或巧娘娘),为什么还要提出“纯女性化”的命题呢?因为从历代的乞巧风俗来看,崇拜的偶像不止织女,也包括牛郎或其他男性神灵。所以参与乞巧活动者不止女性,亦不乏男性的参与。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中,不仅崇拜织女,也崇拜牛郎;不仅用瓜果祭祀牵牛、织女,而且画牛郎、织女的画像。这种崇拜传统在处于封建社会盛期的汉唐及两宋时期,显然不是为了歌颂牛郎、织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是延续了人文始祖崇拜的含义,因为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都是传统农耕经济时代的杰出人物,其劳动技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
从秦简《日书》《诗经》等历史文献可知,牛郎织女的传说至迟在春秋时期已基本形成,且具备了基本的情节要素。①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牛郎织女的传说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在民间流传了。②由此可知,牛郎织女传说的主人公原型可能更早,或许是远古氏族部落时期的人物。如吴天明认为,牛郎织女就是华夏族的先祖神和先妣神。③赵逵夫先生考证认为,牛郎应源于周族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织女源于擅织的秦人始祖女修④,《史记·秦本纪》中的“女修织”正包含了“织女”的基本含义。从敦煌文书中有关乞巧风俗的记载来看,乞巧风俗源于秦人。唐代陈鸿《长恨歌传》:“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附《丽情集》:“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五更转》中也有“哪边见牵牛?看看东方动,来把秦筝弄”的诗句。⑤可见,乞巧就是秦人的传统风俗,因而将织女的早期渊源考证为女修,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早期的牛郎织女崇拜其实是人们对氏族社会中有杰出贡献的人文始祖的崇拜,随之将其与天象中的星座建立关联,尔后才演变为爱情故事,从而丰富了传说的内容。刘宗迪先生则认为,七夕故事和民俗源于古人观象授时,“织女”源于七月为妇女绩纺之月,“牵牛”之名则源于“牺牲”或八月为“视牲”之月的含义,夏秋之交,二星双双升于中天,隔银河相望,牛郎织女故事由此而来。⑥这个认识也很有道理。从情理来讲,肯定是人类根据现实生活来命名星座,赵逵夫是将牛郎、织女与人文始祖关联起来,从早期神话历史的角度,提出人们根据氏族中杰出人物来命名牵牛、织女星的观点;而刘宗迪则是将其与民俗事象关联起来,认为视牲和妇女绩纺为牵牛、织女星名的来源。观点虽然不同,但共同之处是织女都与人类的纺织劳动密切相关。“女修织”与“织女”关联顺理成章,妇女绩纺与织女联系也理所当然。“叔均”是牛耕的发明者,所以和“牵牛”有关,这与后来牛郎织女传说中牛郎从事的“牛耕”有内在的关联性。
总之,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中同时崇拜牛郎和织女,正是因为牛耕和女织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的骨针、陶纺轮、骨纺轮、印纹陶以及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的纺织品遗迹等资料信息来看,织布技术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成熟了,且有相当的发展⑦;从甲骨文内容可知,至迟在商代已经使用牛耕了⑧。所以,虽然牛郎织女故事中的牛郎、织女源于牛耕和女织崇拜的观点还缺少必要的证据链条,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和发现,但这种认识是可以肯定的。由此可见,从牛郎织女传说的生发一直到后来的七夕节、乞巧活动,都贯穿着对牛耕和女织的崇拜。
这种崇拜习俗在部分地区近现代的七夕乞巧风俗中仍有遗留。例如,叶春生先生所引《广州岁时记》中就明确记载:“初七日陈设之物,仍然不移动,至夜仍礼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则童子为主祭,而女子不与焉。”时间范围大约为清末至辛亥革命期间。①应该说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风俗中同时崇拜牛郎和织女,织女和牛郎都具有各自的智慧和灵巧,织女擅织,牛郎擅耕,男子向牛郎祈求的也是劳动智慧和灵巧。后来随着传统节日风俗的逐渐退化,形式和内容趋于简化,许多地区则没有了拜牛郎的仪式。同时,也因为许多地方的《地方志》等文献对七夕民俗的记载过于简略,遗漏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仪式,致使拜牛郎的习俗被逐渐忽略。在东南浙、闽、赣、台等地区,长期以来则流传着七夕拜魁星的风俗,魁星其实就是文曲星,主文章、文运,七月七日也是魁星的生日,尤为读书人所敬仰崇拜。②所以在七夕之夜跟织女一道接受人们祭拜的,不是牛郎,而是一位面目诡异的魁星神。祭拜织女的照例是女子,而祭拜魁星的则是男儿;女子向织女祈求的照例是聪慧灵巧,男子向魁星祈求的则是科场功名。③这种崇拜习俗其实也是牛郎崇拜的一种变体,封建社会的男子除了从事耕种这种重体力劳作以外,最好的出路就是读书求取功名,富贵人家的男子则主要是读书求功名,因此,男子的天职就是“耕读传家”。宋代的乞巧风俗中也同时崇拜牛郎织女,乞巧活动则不仅有女郎呈巧,也有儿童裁诗,可见当时的拜牛郎中也可能包含了读书与功名的寓意。④所以拜魁星可能是由拜牛郎演变而来,只是拜魁星的功利性目的更明确了。在陕西凤翔糜杆桥镇曹家庄村的乞巧节庙会中,男性也参与其中,主要是担任会长进行收布施、请乐队、接待还愿等世俗性事务⑤,虽然没有男人拜牛郎的习俗,但男性的参与应该还是过去拜牛郎的遗俗。
在西汉水上游的七夕乞巧风俗中,所有活动的内容和仪式都已与男性无关,男性不仅不视七夕为节日,甚至有些还对乞巧活动持反对态度。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宗教信仰的神灵谱系中,也无巧娘娘的一席之地,既没有专门的庙宇,也无永久的造像,只是在乞巧活动的七天中,才临时选定一个居民家庭作为暂时的神堂来坐巧。坐巧地点的选择也往往颇费周折,多数人家都不欢迎巧娘娘和乞巧者,可能怕吵闹,同时也可能与巧娘娘没有较高的神灵地位有关。多数村庄在女子乞巧的活动中,男性也旁观看热闹,但男性从来不敬拜巧娘娘,只在乞巧过程中和年轻女性调笑取乐,甚至还拿不敬的语言来打趣巧娘娘像。总之,这里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已完全成为年轻女子祭祀只属于女性的神灵“巧娘娘”的纯女性活动,崇拜的主客体都呈现出纯女性化。这是西汉水上游一带乞巧风俗中的普遍情形。近年来,随着西和县被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和乞巧民俗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的扩大,这种现象有所变化,少数中老年男性也在乞巧期间开始敬拜巧娘娘。
这种情形的形成,是有历史文化根源的,应该说中国的神灵信仰体现的恰恰是母性化特征。从女娲造人的创世神话可知,母性是人类的创造者,具有很高的地位。再从原始神话中的西王母到后来的王母娘娘,直至感生神话中的殷商始祖简狄、周人始祖姜原、秦人始祖女修等,都体现了母性的伟大和神圣。①观世音菩萨中国化以后更是成为中国民众普遍敬仰的女性神灵,她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远远胜过了她的导师释迦牟尼。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信仰的神灵中,母性神灵也很多,除了国人普遍信仰的王母娘娘、观音菩萨以外,地方母性神灵还有香山妙善菩萨、云华山老母以及民间信仰的送生娘娘、花儿娘娘等,这些母性神灵是当地男女共同信仰的神灵,信众并无男女之别。
巧娘娘——织女,作为传说中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应该说亦具有尊贵的地位,为何在民间成为只能供女子信仰的神灵?这应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牛郎织女传说的演变有关。如前所述,早期的牛郎织女崇拜反映的是人们对氏族杰出人物的敬仰,织女是杰出的女织的发明创造者,自然受到全体民众的崇拜。而当牛郎织女之间发展为男女关系并演变为爱情传说以后,这种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男女婚姻有悖日趋完备的封建伦理道德,所以织女在民间的地位逐渐下降,并最终成为年轻女性崇拜的对象就理所当然了。应该说男女情爱是神圣的,否则就不会有人类的繁衍,尤其在氏族社会时期,人类对生殖繁衍充满了敬畏,人口的增长与氏族的壮大繁盛息息相关,所以自由的婚姻关系不曾被视为野蛮和耻辱。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一夫一妻制形成,才逐渐有了男女关系的规约和限制。尤其是随着封建礼法制度的建立,人类社会等级制度逐渐形成,从神到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男女情爱和婚姻讲求门当户对,地位相称,原始的婚姻关系逐渐淡出人类生活。但在后来的礼法社会中,这种原始婚姻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由蒙昧时代的原始婚俗发展到文明社会的婚礼,标志着社会理性对人类原欲的约束,而一些遗留的原始婚俗体现了对礼的反作用,也意味着被礼压抑的人性本然状态及原欲的适当表露和宣泄。②诗经中就有许多反映这种思想的内容,儒家圣人孔子则从政治和礼法的角度对这些内容进行了重新阐释,但也掩盖了其中的一些本真思想。直至汉代的画像石中,仍有一些表现男女野合的作品,这些都反映了人类原欲与礼法之间的冲突,也表达了人类对礼法的一种超越意识。
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虽然和原始婚俗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本质上亦是一种自由的男女关系,它跨越了神、人界限的情爱,是一种超越了封建礼法规范的不合理爱情,所以自然会受到当权者的干预而最终成为悲剧。自西汉中期以来,随着封建礼法规范体系的日趋完备,从民间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行为和思想也逐渐被禁锢,人的自由意识被压抑到底层。七夕节也由早期庆牛郎织女相会逐渐演变为以妇女乞巧为核心,织女也由此成为妇女们倾诉屈衷的唯一对象。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礼法规范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空前严酷,甚至连年轻女子的乞巧也被视为不守本分,有时也会受到家长的反对。西汉水上游一带的乞巧歌中,依然较多地反映了被压抑的民间妇女对不平等婚姻的怨愤和无奈。①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者,织女自然也就难登正统神灵谱系的大雅之堂。西汉水上游一带由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故保留的古风和传统民俗较多,人们的封建意识和发达地区相比还较浓厚,因此巧娘娘在男性心中也就不是正统的母性神灵了。
乞巧自然是女性的活动,崇拜的神灵也是织女(或巧娘娘),为什么还要提出“纯女性化”的命题呢?因为从历代的乞巧风俗来看,崇拜的偶像不止织女,也包括牛郎或其他男性神灵。所以参与乞巧活动者不止女性,亦不乏男性的参与。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中,不仅崇拜织女,也崇拜牛郎;不仅用瓜果祭祀牵牛、织女,而且画牛郎、织女的画像。这种崇拜传统在处于封建社会盛期的汉唐及两宋时期,显然不是为了歌颂牛郎、织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是延续了人文始祖崇拜的含义,因为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都是传统农耕经济时代的杰出人物,其劳动技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
从秦简《日书》《诗经》等历史文献可知,牛郎织女的传说至迟在春秋时期已基本形成,且具备了基本的情节要素。①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牛郎织女的传说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在民间流传了。②由此可知,牛郎织女传说的主人公原型可能更早,或许是远古氏族部落时期的人物。如吴天明认为,牛郎织女就是华夏族的先祖神和先妣神。③赵逵夫先生考证认为,牛郎应源于周族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织女源于擅织的秦人始祖女修④,《史记·秦本纪》中的“女修织”正包含了“织女”的基本含义。从敦煌文书中有关乞巧风俗的记载来看,乞巧风俗源于秦人。唐代陈鸿《长恨歌传》:“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附《丽情集》:“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五更转》中也有“哪边见牵牛?看看东方动,来把秦筝弄”的诗句。⑤可见,乞巧就是秦人的传统风俗,因而将织女的早期渊源考证为女修,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早期的牛郎织女崇拜其实是人们对氏族社会中有杰出贡献的人文始祖的崇拜,随之将其与天象中的星座建立关联,尔后才演变为爱情故事,从而丰富了传说的内容。刘宗迪先生则认为,七夕故事和民俗源于古人观象授时,“织女”源于七月为妇女绩纺之月,“牵牛”之名则源于“牺牲”或八月为“视牲”之月的含义,夏秋之交,二星双双升于中天,隔银河相望,牛郎织女故事由此而来。⑥这个认识也很有道理。从情理来讲,肯定是人类根据现实生活来命名星座,赵逵夫是将牛郎、织女与人文始祖关联起来,从早期神话历史的角度,提出人们根据氏族中杰出人物来命名牵牛、织女星的观点;而刘宗迪则是将其与民俗事象关联起来,认为视牲和妇女绩纺为牵牛、织女星名的来源。观点虽然不同,但共同之处是织女都与人类的纺织劳动密切相关。“女修织”与“织女”关联顺理成章,妇女绩纺与织女联系也理所当然。“叔均”是牛耕的发明者,所以和“牵牛”有关,这与后来牛郎织女传说中牛郎从事的“牛耕”有内在的关联性。
总之,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中同时崇拜牛郎和织女,正是因为牛耕和女织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的骨针、陶纺轮、骨纺轮、印纹陶以及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的纺织品遗迹等资料信息来看,织布技术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成熟了,且有相当的发展⑦;从甲骨文内容可知,至迟在商代已经使用牛耕了⑧。所以,虽然牛郎织女故事中的牛郎、织女源于牛耕和女织崇拜的观点还缺少必要的证据链条,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和发现,但这种认识是可以肯定的。由此可见,从牛郎织女传说的生发一直到后来的七夕节、乞巧活动,都贯穿着对牛耕和女织的崇拜。
这种崇拜习俗在部分地区近现代的七夕乞巧风俗中仍有遗留。例如,叶春生先生所引《广州岁时记》中就明确记载:“初七日陈设之物,仍然不移动,至夜仍礼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则童子为主祭,而女子不与焉。”时间范围大约为清末至辛亥革命期间。①应该说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风俗中同时崇拜牛郎和织女,织女和牛郎都具有各自的智慧和灵巧,织女擅织,牛郎擅耕,男子向牛郎祈求的也是劳动智慧和灵巧。后来随着传统节日风俗的逐渐退化,形式和内容趋于简化,许多地区则没有了拜牛郎的仪式。同时,也因为许多地方的《地方志》等文献对七夕民俗的记载过于简略,遗漏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仪式,致使拜牛郎的习俗被逐渐忽略。在东南浙、闽、赣、台等地区,长期以来则流传着七夕拜魁星的风俗,魁星其实就是文曲星,主文章、文运,七月七日也是魁星的生日,尤为读书人所敬仰崇拜。②所以在七夕之夜跟织女一道接受人们祭拜的,不是牛郎,而是一位面目诡异的魁星神。祭拜织女的照例是女子,而祭拜魁星的则是男儿;女子向织女祈求的照例是聪慧灵巧,男子向魁星祈求的则是科场功名。③这种崇拜习俗其实也是牛郎崇拜的一种变体,封建社会的男子除了从事耕种这种重体力劳作以外,最好的出路就是读书求取功名,富贵人家的男子则主要是读书求功名,因此,男子的天职就是“耕读传家”。宋代的乞巧风俗中也同时崇拜牛郎织女,乞巧活动则不仅有女郎呈巧,也有儿童裁诗,可见当时的拜牛郎中也可能包含了读书与功名的寓意。④所以拜魁星可能是由拜牛郎演变而来,只是拜魁星的功利性目的更明确了。在陕西凤翔糜杆桥镇曹家庄村的乞巧节庙会中,男性也参与其中,主要是担任会长进行收布施、请乐队、接待还愿等世俗性事务⑤,虽然没有男人拜牛郎的习俗,但男性的参与应该还是过去拜牛郎的遗俗。
在西汉水上游的七夕乞巧风俗中,所有活动的内容和仪式都已与男性无关,男性不仅不视七夕为节日,甚至有些还对乞巧活动持反对态度。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宗教信仰的神灵谱系中,也无巧娘娘的一席之地,既没有专门的庙宇,也无永久的造像,只是在乞巧活动的七天中,才临时选定一个居民家庭作为暂时的神堂来坐巧。坐巧地点的选择也往往颇费周折,多数人家都不欢迎巧娘娘和乞巧者,可能怕吵闹,同时也可能与巧娘娘没有较高的神灵地位有关。多数村庄在女子乞巧的活动中,男性也旁观看热闹,但男性从来不敬拜巧娘娘,只在乞巧过程中和年轻女性调笑取乐,甚至还拿不敬的语言来打趣巧娘娘像。总之,这里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已完全成为年轻女子祭祀只属于女性的神灵“巧娘娘”的纯女性活动,崇拜的主客体都呈现出纯女性化。这是西汉水上游一带乞巧风俗中的普遍情形。近年来,随着西和县被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和乞巧民俗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的扩大,这种现象有所变化,少数中老年男性也在乞巧期间开始敬拜巧娘娘。
这种情形的形成,是有历史文化根源的,应该说中国的神灵信仰体现的恰恰是母性化特征。从女娲造人的创世神话可知,母性是人类的创造者,具有很高的地位。再从原始神话中的西王母到后来的王母娘娘,直至感生神话中的殷商始祖简狄、周人始祖姜原、秦人始祖女修等,都体现了母性的伟大和神圣。①观世音菩萨中国化以后更是成为中国民众普遍敬仰的女性神灵,她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远远胜过了她的导师释迦牟尼。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信仰的神灵中,母性神灵也很多,除了国人普遍信仰的王母娘娘、观音菩萨以外,地方母性神灵还有香山妙善菩萨、云华山老母以及民间信仰的送生娘娘、花儿娘娘等,这些母性神灵是当地男女共同信仰的神灵,信众并无男女之别。
巧娘娘——织女,作为传说中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应该说亦具有尊贵的地位,为何在民间成为只能供女子信仰的神灵?这应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牛郎织女传说的演变有关。如前所述,早期的牛郎织女崇拜反映的是人们对氏族杰出人物的敬仰,织女是杰出的女织的发明创造者,自然受到全体民众的崇拜。而当牛郎织女之间发展为男女关系并演变为爱情传说以后,这种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男女婚姻有悖日趋完备的封建伦理道德,所以织女在民间的地位逐渐下降,并最终成为年轻女性崇拜的对象就理所当然了。应该说男女情爱是神圣的,否则就不会有人类的繁衍,尤其在氏族社会时期,人类对生殖繁衍充满了敬畏,人口的增长与氏族的壮大繁盛息息相关,所以自由的婚姻关系不曾被视为野蛮和耻辱。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一夫一妻制形成,才逐渐有了男女关系的规约和限制。尤其是随着封建礼法制度的建立,人类社会等级制度逐渐形成,从神到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男女情爱和婚姻讲求门当户对,地位相称,原始的婚姻关系逐渐淡出人类生活。但在后来的礼法社会中,这种原始婚姻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由蒙昧时代的原始婚俗发展到文明社会的婚礼,标志着社会理性对人类原欲的约束,而一些遗留的原始婚俗体现了对礼的反作用,也意味着被礼压抑的人性本然状态及原欲的适当表露和宣泄。②诗经中就有许多反映这种思想的内容,儒家圣人孔子则从政治和礼法的角度对这些内容进行了重新阐释,但也掩盖了其中的一些本真思想。直至汉代的画像石中,仍有一些表现男女野合的作品,这些都反映了人类原欲与礼法之间的冲突,也表达了人类对礼法的一种超越意识。
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虽然和原始婚俗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本质上亦是一种自由的男女关系,它跨越了神、人界限的情爱,是一种超越了封建礼法规范的不合理爱情,所以自然会受到当权者的干预而最终成为悲剧。自西汉中期以来,随着封建礼法规范体系的日趋完备,从民间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行为和思想也逐渐被禁锢,人的自由意识被压抑到底层。七夕节也由早期庆牛郎织女相会逐渐演变为以妇女乞巧为核心,织女也由此成为妇女们倾诉屈衷的唯一对象。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礼法规范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空前严酷,甚至连年轻女子的乞巧也被视为不守本分,有时也会受到家长的反对。西汉水上游一带的乞巧歌中,依然较多地反映了被压抑的民间妇女对不平等婚姻的怨愤和无奈。①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者,织女自然也就难登正统神灵谱系的大雅之堂。西汉水上游一带由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故保留的古风和传统民俗较多,人们的封建意识和发达地区相比还较浓厚,因此巧娘娘在男性心中也就不是正统的母性神灵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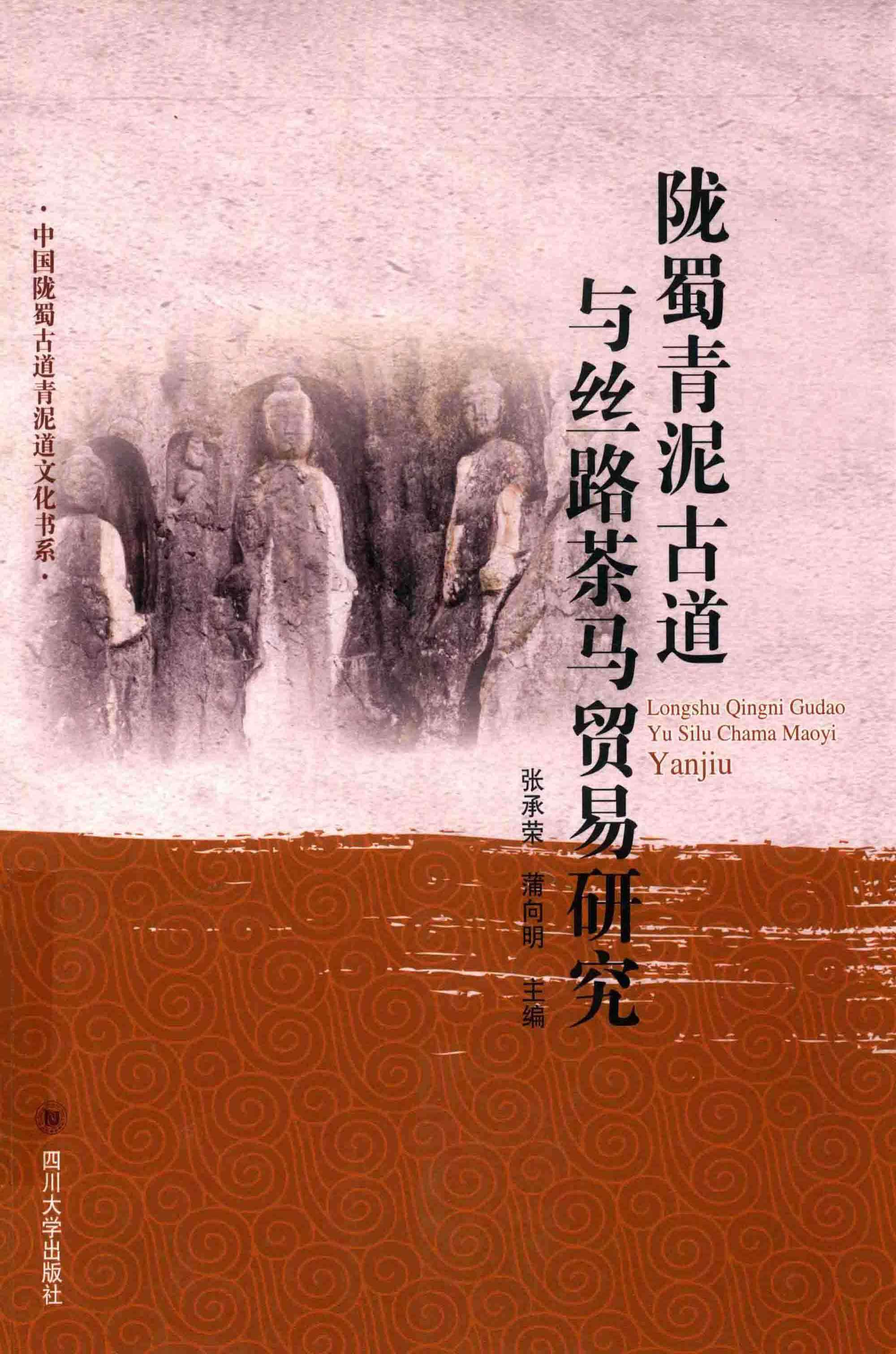
《陇蜀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研究》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丝绸之路与陇蜀青泥古道”“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蜀道申遗与陇蜀秦蜀交通”“青泥古道与陇南地域文化”四部分,是近年来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陇南本土在陇蜀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重点在陇蜀青泥古道自汉唐以来政治、军事、交通、商贸诸方面的文化研究,兼顾青泥道在丝绸之路茶马贸易方面的历史地位、历史文献、文化遗存以及沟通南北丝绸之路廊道路网方面的研究。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