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水上游“巧娘娘”崇拜的地域特色
| 内容出处: | 《陇蜀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1820020220000587 |
| 颗粒名称: | 西汉水上游“巧娘娘”崇拜的地域特色 |
| 分类号: | K892.2 |
| 页数: | 12 |
| 页码: | 389-40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西汉水上游乞巧风俗中崇拜的唯一偶像是“巧娘娘”,从当地乞巧歌的内容来考察,巧娘娘其实就是织女,是这一带民间对织女的地域性称呼。但这里的巧娘娘又和当地人崇拜的“××娘娘”不同,巧娘娘中的“娘”读音为“nia”,而不是“niang”。 |
| 关键词: | “巧娘娘” 地域特色 民间传说 |
内容
织女是中国传统四大传说之一“牛郎织女”中的女主人公,该传说在四大传说中影响最大、流传范围最广,在民间的普及程度高,在中国家喻户晓。牛郎织女传说影响大、普及度高的主要原因,笔者以为有二:①四大传说中唯有牛郎织女传说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文化,“织女”名字本身就是“女织”的代名词,“牛郎”“牵牛”就是“牛耕”的代名词,因此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根基;②四大传说中唯有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了与之相应的节日和民俗,并使七夕节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节日和民俗。虽然学者们对七夕节的形成各有看法,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七夕节的宗教祭祀活动和民俗活动也丰富多样,但当七夕节和牛郎织女传说结合在一起后,其影响就更大了。其后,“牛郎织女”几乎成为七夕节内容的全部,七夕节的“乞巧”活动也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民俗仪式。
对于汉代以来七夕节和乞巧活动的基本主题,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有些认为是以爱情、婚姻为主,也兼具生殖崇拜方面的含义;有些认为是祈求五谷丰登,指出织女是主瓜果谷物之神;也有些认为是以女织崇拜为主,强调女红含义。从历代七夕节和乞巧的内容、仪式来看,这些方面的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七夕节自形成以后,其内容和仪式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处于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对于这个问题,赵逵夫先生认为,七夕节最初的主题也是倾向于庆祝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后来由于封建礼教的进一步系统化、顽固化,这种超越礼教的婚姻显然有悖伦理道德,所以七夕的主题逐渐演变为以女红为核心的乞巧。②纵观自汉代以来的历代七夕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妇女的乞巧活动。乞巧的核心主题又是对织女的祭祀和崇拜,这种崇拜中当然也包含对婚姻、命运的祈祷,但主体方面则是妇女们对灵巧和智慧的祈求,以使自己心灵手巧,受到家人和社会的尊重,实现封建社会妇女的自我价值。传说中的织女是智慧和灵巧的女神,能织出天上美丽的云锦,具有女红文化始祖神的性质,所以受到广大劳动妇女的崇拜。
中国各地民间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织女崇拜的基本主题,同时由于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各异,所以又形成了各地不同的崇拜形式,对织女的称呼也各具特色,有织女、七姐、七娘、巧媳妇、巧娘娘等。西汉水上游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悠久,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从大地湾一期(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周秦文化、汉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许多古老的民俗民艺至今犹存,乞巧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带的乞巧风俗不仅没有退化,而且得到了地域文化的滋养,传承良好。西汉水上游地区的乞巧风俗历时七天八夜,从农历六月三十日晚一直延续到七月七日晚,乞巧活动形式丰富,包括迎巧、坐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等复杂的环节,同时还有独具地域特色的“跳麻姐姐”活动。抛开这些外在的仪式,从神灵崇拜的角度来考察,这一带的“巧娘娘”崇拜亦显示出与其他地区织女崇拜不同的独特性,体现了织女崇拜的本土化特色。
一、崇拜者的纯女性化
西汉水上游乞巧风俗中崇拜的唯一偶像是“巧娘娘”,从当地乞巧歌的内容来考察,巧娘娘其实就是织女,是这一带民间对织女的地域性称呼。但这里的巧娘娘又和当地人崇拜的“××娘娘”不同,巧娘娘中的“娘”读音为“nia”,而不是“niang”。前一种读音的“娘”是西汉水上游一带方言中对母亲的称呼;后一种读音的“娘娘”则往往是对女性神灵的称呼,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花儿娘娘等,有时也是对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女性、贵妇人、官太太的称呼。同一个字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读音,表达的含义也截然不同。前者体现出亲密无间的亲情关系,后者则用来称呼高高在上的高贵的女性神灵或者贵族女性。从整个乞巧活动期间年轻姑娘的情感活动来看,巧娘娘与她们达到了精神与情感的交融,这种真挚的感情甚至超越了现实中的母女感情,对母亲不敢说、不能表白的心声,却能在乞巧活动中向巧娘娘倾诉,有时尽管是无声的,但实现了真正的心灵沟通。尤其是七月七日夜晚送巧娘娘上天的时候,全体姑娘都流着眼泪,唱着悲情的送巧歌将巧娘娘的纸偶像烧掉,俨然一种生离死别的凄婉场景。
乞巧自然是女性的活动,崇拜的神灵也是织女(或巧娘娘),为什么还要提出“纯女性化”的命题呢?因为从历代的乞巧风俗来看,崇拜的偶像不止织女,也包括牛郎或其他男性神灵。所以参与乞巧活动者不止女性,亦不乏男性的参与。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中,不仅崇拜织女,也崇拜牛郎;不仅用瓜果祭祀牵牛、织女,而且画牛郎、织女的画像。这种崇拜传统在处于封建社会盛期的汉唐及两宋时期,显然不是为了歌颂牛郎、织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是延续了人文始祖崇拜的含义,因为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都是传统农耕经济时代的杰出人物,其劳动技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
从秦简《日书》《诗经》等历史文献可知,牛郎织女的传说至迟在春秋时期已基本形成,且具备了基本的情节要素。①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牛郎织女的传说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在民间流传了。②由此可知,牛郎织女传说的主人公原型可能更早,或许是远古氏族部落时期的人物。如吴天明认为,牛郎织女就是华夏族的先祖神和先妣神。③赵逵夫先生考证认为,牛郎应源于周族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织女源于擅织的秦人始祖女修④,《史记·秦本纪》中的“女修织”正包含了“织女”的基本含义。从敦煌文书中有关乞巧风俗的记载来看,乞巧风俗源于秦人。唐代陈鸿《长恨歌传》:“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附《丽情集》:“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五更转》中也有“哪边见牵牛?看看东方动,来把秦筝弄”的诗句。⑤可见,乞巧就是秦人的传统风俗,因而将织女的早期渊源考证为女修,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早期的牛郎织女崇拜其实是人们对氏族社会中有杰出贡献的人文始祖的崇拜,随之将其与天象中的星座建立关联,尔后才演变为爱情故事,从而丰富了传说的内容。刘宗迪先生则认为,七夕故事和民俗源于古人观象授时,“织女”源于七月为妇女绩纺之月,“牵牛”之名则源于“牺牲”或八月为“视牲”之月的含义,夏秋之交,二星双双升于中天,隔银河相望,牛郎织女故事由此而来。⑥这个认识也很有道理。从情理来讲,肯定是人类根据现实生活来命名星座,赵逵夫是将牛郎、织女与人文始祖关联起来,从早期神话历史的角度,提出人们根据氏族中杰出人物来命名牵牛、织女星的观点;而刘宗迪则是将其与民俗事象关联起来,认为视牲和妇女绩纺为牵牛、织女星名的来源。观点虽然不同,但共同之处是织女都与人类的纺织劳动密切相关。“女修织”与“织女”关联顺理成章,妇女绩纺与织女联系也理所当然。“叔均”是牛耕的发明者,所以和“牵牛”有关,这与后来牛郎织女传说中牛郎从事的“牛耕”有内在的关联性。
总之,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中同时崇拜牛郎和织女,正是因为牛耕和女织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的骨针、陶纺轮、骨纺轮、印纹陶以及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的纺织品遗迹等资料信息来看,织布技术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成熟了,且有相当的发展⑦;从甲骨文内容可知,至迟在商代已经使用牛耕了⑧。所以,虽然牛郎织女故事中的牛郎、织女源于牛耕和女织崇拜的观点还缺少必要的证据链条,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和发现,但这种认识是可以肯定的。由此可见,从牛郎织女传说的生发一直到后来的七夕节、乞巧活动,都贯穿着对牛耕和女织的崇拜。
这种崇拜习俗在部分地区近现代的七夕乞巧风俗中仍有遗留。例如,叶春生先生所引《广州岁时记》中就明确记载:“初七日陈设之物,仍然不移动,至夜仍礼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则童子为主祭,而女子不与焉。”时间范围大约为清末至辛亥革命期间。①应该说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风俗中同时崇拜牛郎和织女,织女和牛郎都具有各自的智慧和灵巧,织女擅织,牛郎擅耕,男子向牛郎祈求的也是劳动智慧和灵巧。后来随着传统节日风俗的逐渐退化,形式和内容趋于简化,许多地区则没有了拜牛郎的仪式。同时,也因为许多地方的《地方志》等文献对七夕民俗的记载过于简略,遗漏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仪式,致使拜牛郎的习俗被逐渐忽略。在东南浙、闽、赣、台等地区,长期以来则流传着七夕拜魁星的风俗,魁星其实就是文曲星,主文章、文运,七月七日也是魁星的生日,尤为读书人所敬仰崇拜。②所以在七夕之夜跟织女一道接受人们祭拜的,不是牛郎,而是一位面目诡异的魁星神。祭拜织女的照例是女子,而祭拜魁星的则是男儿;女子向织女祈求的照例是聪慧灵巧,男子向魁星祈求的则是科场功名。③这种崇拜习俗其实也是牛郎崇拜的一种变体,封建社会的男子除了从事耕种这种重体力劳作以外,最好的出路就是读书求取功名,富贵人家的男子则主要是读书求功名,因此,男子的天职就是“耕读传家”。宋代的乞巧风俗中也同时崇拜牛郎织女,乞巧活动则不仅有女郎呈巧,也有儿童裁诗,可见当时的拜牛郎中也可能包含了读书与功名的寓意。④所以拜魁星可能是由拜牛郎演变而来,只是拜魁星的功利性目的更明确了。在陕西凤翔糜杆桥镇曹家庄村的乞巧节庙会中,男性也参与其中,主要是担任会长进行收布施、请乐队、接待还愿等世俗性事务⑤,虽然没有男人拜牛郎的习俗,但男性的参与应该还是过去拜牛郎的遗俗。
在西汉水上游的七夕乞巧风俗中,所有活动的内容和仪式都已与男性无关,男性不仅不视七夕为节日,甚至有些还对乞巧活动持反对态度。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宗教信仰的神灵谱系中,也无巧娘娘的一席之地,既没有专门的庙宇,也无永久的造像,只是在乞巧活动的七天中,才临时选定一个居民家庭作为暂时的神堂来坐巧。坐巧地点的选择也往往颇费周折,多数人家都不欢迎巧娘娘和乞巧者,可能怕吵闹,同时也可能与巧娘娘没有较高的神灵地位有关。多数村庄在女子乞巧的活动中,男性也旁观看热闹,但男性从来不敬拜巧娘娘,只在乞巧过程中和年轻女性调笑取乐,甚至还拿不敬的语言来打趣巧娘娘像。总之,这里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已完全成为年轻女子祭祀只属于女性的神灵“巧娘娘”的纯女性活动,崇拜的主客体都呈现出纯女性化。这是西汉水上游一带乞巧风俗中的普遍情形。近年来,随着西和县被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和乞巧民俗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的扩大,这种现象有所变化,少数中老年男性也在乞巧期间开始敬拜巧娘娘。
这种情形的形成,是有历史文化根源的,应该说中国的神灵信仰体现的恰恰是母性化特征。从女娲造人的创世神话可知,母性是人类的创造者,具有很高的地位。再从原始神话中的西王母到后来的王母娘娘,直至感生神话中的殷商始祖简狄、周人始祖姜原、秦人始祖女修等,都体现了母性的伟大和神圣。①观世音菩萨中国化以后更是成为中国民众普遍敬仰的女性神灵,她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远远胜过了她的导师释迦牟尼。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信仰的神灵中,母性神灵也很多,除了国人普遍信仰的王母娘娘、观音菩萨以外,地方母性神灵还有香山妙善菩萨、云华山老母以及民间信仰的送生娘娘、花儿娘娘等,这些母性神灵是当地男女共同信仰的神灵,信众并无男女之别。
巧娘娘——织女,作为传说中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应该说亦具有尊贵的地位,为何在民间成为只能供女子信仰的神灵?这应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牛郎织女传说的演变有关。如前所述,早期的牛郎织女崇拜反映的是人们对氏族杰出人物的敬仰,织女是杰出的女织的发明创造者,自然受到全体民众的崇拜。而当牛郎织女之间发展为男女关系并演变为爱情传说以后,这种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男女婚姻有悖日趋完备的封建伦理道德,所以织女在民间的地位逐渐下降,并最终成为年轻女性崇拜的对象就理所当然了。应该说男女情爱是神圣的,否则就不会有人类的繁衍,尤其在氏族社会时期,人类对生殖繁衍充满了敬畏,人口的增长与氏族的壮大繁盛息息相关,所以自由的婚姻关系不曾被视为野蛮和耻辱。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一夫一妻制形成,才逐渐有了男女关系的规约和限制。尤其是随着封建礼法制度的建立,人类社会等级制度逐渐形成,从神到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男女情爱和婚姻讲求门当户对,地位相称,原始的婚姻关系逐渐淡出人类生活。但在后来的礼法社会中,这种原始婚姻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由蒙昧时代的原始婚俗发展到文明社会的婚礼,标志着社会理性对人类原欲的约束,而一些遗留的原始婚俗体现了对礼的反作用,也意味着被礼压抑的人性本然状态及原欲的适当表露和宣泄。②诗经中就有许多反映这种思想的内容,儒家圣人孔子则从政治和礼法的角度对这些内容进行了重新阐释,但也掩盖了其中的一些本真思想。直至汉代的画像石中,仍有一些表现男女野合的作品,这些都反映了人类原欲与礼法之间的冲突,也表达了人类对礼法的一种超越意识。
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虽然和原始婚俗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本质上亦是一种自由的男女关系,它跨越了神、人界限的情爱,是一种超越了封建礼法规范的不合理爱情,所以自然会受到当权者的干预而最终成为悲剧。自西汉中期以来,随着封建礼法规范体系的日趋完备,从民间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行为和思想也逐渐被禁锢,人的自由意识被压抑到底层。七夕节也由早期庆牛郎织女相会逐渐演变为以妇女乞巧为核心,织女也由此成为妇女们倾诉屈衷的唯一对象。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礼法规范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空前严酷,甚至连年轻女子的乞巧也被视为不守本分,有时也会受到家长的反对。西汉水上游一带的乞巧歌中,依然较多地反映了被压抑的民间妇女对不平等婚姻的怨愤和无奈。①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者,织女自然也就难登正统神灵谱系的大雅之堂。西汉水上游一带由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故保留的古风和传统民俗较多,人们的封建意识和发达地区相比还较浓厚,因此巧娘娘在男性心中也就不是正统的母性神灵了。
二、崇拜方式的巫傩化
西汉水上游地区的乞巧风俗中,乞巧的主要形式有迎神、送神、祭拜、占卜、跳神等,其中最主要的祭拜活动以姑娘们的唱跳为主,在现代的乞巧活动中,受时代的影响也有跳唱现代流行歌舞的内容。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甚至改革开放以前乞巧的祭拜活动中,以姑娘们手拉手边摆边唱为基本形式,七天八夜一直如此唱歌祭拜。据当地的老年妇女讲,这种唱歌祭拜的形式是从过去一直流传下来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地区比较少见,邻近的陇东地区流行乞巧歌,天水地区则流行《巧娘娘》歌②,但陇东地区乞巧的时间短,且唱乞巧歌的形式已不得而知了。这种手拉手唱歌祭拜巧娘娘的方式,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年轻姑娘们节日期间的一种娱乐,无需深究其含义和来源;但笔者以为,既然这种形式从古至今一直这样传承,必然有其内在的文化基础。郑土有先生也指出,西和乞巧活动完全继承了祭、歌、舞三位一体的人类社会早期的祭祀传统,毫无疑问是一项传承历史悠久、仪式保留较为完整的古老习俗。③只是这种祭拜形式的形成时间无从考证,其自然而然地形成,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人们也习以为常了。
在西汉水流域,民间举行宗教活动的形式主要有三种:①是佛教僧侣们做佛事,主要以诵经忏悔和超度为主,属于佛家。②请法师(当地称为“法官”)念咒语来驱鬼捉妖,从咒语内容中总是呼唤“太上老君”来看应属于道家。当地的阴阳先生也是施行宗教活动的主体,但阴阳先生也有“释门”和“玄门”的区分,释门以诵念佛教经典为主,玄门则多使用道家咒语,故阴阳先生也分属于佛家和道家。③巫师(当地称为“师公”或“师公子”)的传神活动,既不诵经也不念咒语,而是身穿长袍,后脑缀长辫,手拿羊皮扇鼓敲打,甩动长辫,边舞边唱,就是以歌舞的形式来娱神,以达到宗教目的。这种宗教形式被当地民间形象地称为“花儿道场”。所谓“花儿道场”就是以歌舞为主要祭祀形式的宗教活动,“花儿”正是西北地域少数民族的民歌,汉族称“山歌”,少数民族称“花儿”。据此,笔者以为,西汉水流域的这种宗教形式应该源自少数民族,善于歌舞是少数民族的特点,也是他们宗教活动的特色。
西汉水流域是古代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地区,也是民族迁徙的主要通道,西北甘青高原的氐羌族群正是经过这一带向南迁徙的。更有趣的是,在西汉水上游地区,属于氐羌民族的寺洼文化和周秦文化隔河对峙分布①,而西汉水下游的深山峡谷中就只有寺洼文化了。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认为西汉水流域寺洼文化的族属就是白马氐。②因此,西汉水流域也就是一条民族迁徙融合的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势力范围不断扩张,一度成为统治北方的强大民族。在西汉水流域,氐人在仇池山一带建立了地方政权仇池国,羌人也在相邻的白龙江流域的宕昌建立了宕昌国,西汉水与白龙江仅一山之隔。在后来的民族矛盾中,氐羌人在被迫南迁的同时也就地汉化,从而将氐羌文化的基因注入了西汉水流域,所以这里的民俗文化包含着浓郁的氐羌文化的因素。
师公其实就是当地氐羌民族巫傩文化的一种延续。陇南文县的白马藏族被认为是古代氐族的遗裔,他们至今依然保持着傩舞祭祀的传统。他们的傩舞被称为“池哥昼”,“池哥”身穿羊皮袄,头戴狰狞的面具,手拿牦牛尾和木刀迈步挥舞,和西汉水流域汉族师公的祭祀仪式颇为相似。宕昌藏族其实是古代羌族的遗裔,他们也有着类似的巫舞“羌巴舞”。而且他们都是善歌的民族,虽然现代巫傩舞中不唱歌,但在祭祀结束后的火圈舞中,男男女女则围着篝火,手拉手,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所谓的“花儿道场”也可能与善歌的氐羌民族文化有关,乞巧仪式中手拉手唱歌祭拜巧娘娘的形式也可能是受当地氐羌文化的影响。
在西汉水上游地区民众自发的敬神活动中,有一类人被当地民众称为“神婆”(以中老年女性为主,有时也有个别男性参与),她们在农闲时间主要以到处敬神拜佛为业。她们不识字,也不会诵经,敬神的形式主要是“唱神歌”。不管是在寺庙中还是在行走途中,也有时是在家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唱。唱神歌敬神的方式和乞巧活动中唱乞巧歌在形式上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宗教艺术的形式来达到娱神的目的。这种娱神的形式也体现在当地的民间戏曲和社火中,这里民间的戏曲和社火不是随意演出的纯娱乐活动,而是一种娱神活动。有些村庄的戏曲和社火每年必须举行,否则就会惹怒神灵,于整个村子不利。戏曲和社火的主要形式也是歌舞,这和所谓的“花儿道场”的性质是相同的。尤其是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社火的演出时间、组织结构、角色构成、装饰特征、宗教祭祀等和白马藏族的傩舞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显然是长期以来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③
在西汉水流域的乞巧仪式中,还有一项独特的内容,“跳麻姐姐”,即在乞巧的姑娘中挑选一位替神灵巧娘娘或麻姐姐传话。这项活动有一定的风险,因此,一般要在有经验的中老年妇女的主持下进行。挑选麻姐姐的方法有三:①平时曾经梦见自己跳麻姐姐的人;②认为自己当年有厄运,为求平安愿意跳麻姐姐的人;③大家公认神灵会附在其身,也就是其有神性或灵性之人。在开始跳之前,先烧香纸祷告,选定的跳神主角站在巧娘娘桌前,左右各有一位陪跳者,其他姑娘则跪于神桌两旁,一时气氛严肃紧张,鸦雀无声。随后一位装扮麻姐姐的姑娘钻到神桌下,开始与外面的乞巧姑娘相互问答(外面的姑娘问,桌下的姑娘答):
“麻姐姐,做(西汉水流域方言读zu)啥着呢?”
“簸粮食着呢。”
外面的姑娘用数板调快速齐唱:“簸东了,簸西了,簸下的粮食鸡噆(西汉水流域方言读can)了。”
“麻姐姐,做啥着呢?”
“磨面着呢。”
外面的姑娘又齐唱:“东磨面,西磨面,渠里无水磨不转。”
“麻姐姐,做啥着呢?”
“擀面着呢。”
外面的姑娘则又相互问答对唱:“多么少?”“两盆呢”“薄么厚?”“照人呢。”“长么短?”“噎人呢。”
紧接着神桌下的姑娘一边往外钻,一边拖长音大喊:“麻姐姐的神——来——了——”
神桌旁的姑娘则齐唱《跳麻姐姐歌》:
麻姐姐,虚空来,脚(西汉水方言读jue)上穿的登云鞋(西汉水方言读
hai)。
麻姐姐,隔河来,手里打着响锣来。
麻姐姐,翻山来,脚踏铺下(西汉水方言读ha)的红毡来。
一直反复唱,跳神者则不断地蹦跳,幅度越来越大,直至神灵巧娘娘或麻姐姐附体为止。“神灵附体”的标志就是跳神者浑身酥软,四肢无力,神志不清,口吐白沫,哭笑无常。旁边的人则乘机向神灵问话,而跳神者的回答往往语无伦次,难以听清,有时也偶尔能说一两句较明白的话。随后旁边的主持者向神祷告,祈求神灵归位,跳神者慢慢苏醒。①
有学者认为这种仪式在乞巧活动中显得较为突兀,和其他环节似有脱节之嫌,西和学者黄英先生也提出麻姐姐和巧娘娘毫无关系。②从这个仪式过程来看,麻姐姐也是一位地方神灵,这和一般的“神灵附体”现象又不同,多数跳神活动只有神、人以及沟通神人的中介跳神者三个环节;而这里显然又多出了一个麻姐姐,也就是跳神者有可能是巧娘娘“附体”,也有可能是麻姐姐“附体”,也有可能巧娘娘的神旨要通过麻姐姐和跳神者的双重环节向世人传达。对于麻姐姐的来历问题,目前还没有较为可信的解释,有学者提出麻姐姐是否与麻姑有关,但遭到西和地方学者的反对,认为一个称姑,一个称姐,与麻姑无关。①但以“姑”和“姐”的称呼区别来作为反驳理由似乎还不够充分,如前文所述,巧娘娘也有多种称呼,既可称“娘”,也可称“姐”,这个问题还需以专文形式进行进一步的考察。赵逵夫先生在《飞天》上发表的《牛郎织女的传说》一文中,就有麻姐姐的情节,其中的麻姐姐是一位手巧、善于织麻布且善良的民间妇女,这是赵逵夫先生于1958年采集的流传于西汉水流域西和、礼县一带部分地区的民间传说。②但有关麻姐姐的传说在西汉水流域其他地区并未广泛流传。
笔者以为,跳麻姐姐的活动在西汉水流域的宗教活动中同样能找到文化基础。除了专职的僧侣、阴阳先生、法师、巫师以外,西汉水流域的民间也有跳神的活动,当地也称为“发爷”或“发神”,跳神者被称为“厥玛”,但厥玛已不仅仅限于女性,男性也很多。厥玛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由神灵挑选的传话者,也是具有神性或灵性的人,“神灵附体”以后他就会从众人中跳出来,“附体”后的表现和跳麻姐姐者一样。有些“神婆”也被公认为有神性,所以在唱神歌时还会“神灵附体”,无需经过剧烈的跳跃过程就可进入神灵附体的状态,当地人将这种形式也称为“发神”或“发爷”。
西汉水上游一带的这一类宗教活动,无论是传神、发神、发爷还是跳麻姐姐,其性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古代巫文化的一种遗留,和佛教、道教以及阴阳先生的宗教活动完全不同,保留了原始宗教的基本特征。巫师其实就是沟通神与人的中介,段玉裁解释“巫”字的构成是:“直中绳,二平,中准,是规矩也。”其中“二平”乃天地之形,上平为天,下平为地;“中绳”乃天柱之形,上接于天,下接于地。而巫居其中,右为巫,左为觋,一男一女,通人事,达鬼神,沟通天人。由此可以看出,巫就是“事无形”(即人眼看不见的鬼神)的人,其降神的方式就是舞蹈。③
在西汉水上游一带信仰的地方神灵中,有一位神灵称为“杨氏(当地方言读si)爷”,杨氏爷信仰活动的主要形式就是神灵附体的跳神,当地也称为“降爷”,据说跳神的“厥玛”是由神灵杨氏爷挑选的。“杨氏爷”舞棍弄棒,跳上蹿下,口中念念有词,进行驱鬼活动。当地人也称杨氏爷为“杨将军”,看来是一位武将。无独有偶,陇南的白马人也信仰杨氏爷,白马人也称为“杨氏大将”,且信仰的方式基本相同。④结合白马人的民间传说和西汉水流域的仇池杨氏政权来看,这位“杨将军”应该源于古代氐人中的一位武将,由于民族文化的融合而在整个陇南及周边地域具有广泛的信仰。而且信仰活动的形式也是神灵附体的巫的形式,因此,这一带的巫文化应与氐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说手拉手摇摆唱歌祭拜巧娘娘是受巫傩文化的影响的话,那么跳麻姐姐则体现了纯粹的巫文化特征。不管麻姐姐的来源如何,她和麻姑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无碍于跳麻姐姐巫文化的本质。黄英先生提出跳麻姐姐源于西戎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氐羌文化的观点,他同时认为麻姐姐就是古代氐族妇女中纺织麻布的能手。①《魏略·西戎传》记载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南史·夷貊传》记载氐人“地植九谷,种桑麻”②。被学术界称为氐羌后裔的白马人直至20世纪70年代还大量穿麻布长衫,西汉水上游一带汉民在新中国成立前大多都穿麻布衣服,从而被戏称为“麻郎”。由此看来,麻姐姐也是心灵手巧的人,因此,在乞巧仪式中加入麻姐姐,虽在形式上有突兀之感,但主题上并不矛盾,巧娘娘是天上的智慧灵巧之女神,麻姐姐是凡间的纺织能手,她们都能向民间妇女赐予或传授灵巧。
三、偶像造型的民艺化
宗教造像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提倡偶像崇拜的佛教也不例外,而且佛教神灵造像是中国古代宗教造像的主体,其他如道教神灵的造像则无处不有。宗教造像的主要形式有雕塑和绘画两种基本形式,多置于石窟、庙宇中,供信众随时参拜敬奉。人们之所以要凿窟立庙塑造神灵形象,是为了有一个相对长期固定的精神寄托场所。
如前所述,西汉水上游一带的巧娘娘没有固定的庙宇,也就是说,在人间如此众多的石窟、庙宇中没有织女的立足之地,这与牛郎织女传说的爱情主题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而使织女的神灵地位下降有关。在西汉水上游的乞巧活动中,巧娘娘与凡人相聚的时间只有七天,其余时间则无任何与此有关的宗教活动。有鉴于此,巧娘娘也就没有固定的庙宇,也没有永久的塑像或画像。笔者在一篇论文中曾列举了牵牛和织女造像在历代的发展情况,最早是西汉时期昆明池牵牛和织女像,东汉画像石中也有牵牛织女星象图,宋元时期也有七夕节刻画牵牛织女像的风俗,明清以后就没有相关记载了。③但在乞巧风俗盛行且传承最完整的西汉水上游地区却没有牵牛织女塑像或画像,也没有巧娘娘的固定塑像和画像。西和县被评为“中国乞巧民俗文化之乡”以后,在晚霞湖畔立了一尊巧娘娘的大理石雕像,其在本质上只是当代人们宣传乞巧文化的一种符号,并非乞巧文化的传统。传统的巧娘娘造像既不是雕塑,也不是绘画,而是一种纸偶。纸偶和宗教雕塑、绘画相比没有永久性,也便于在乞巧结束后送巧娘娘上天时烧掉,也不必考虑平时无处安置的问题。在西和县大柳乡的文化大院中,长期供奉着一尊巧娘娘坐姿纸偶像,造像置于一顶花轿中,但这亦是近年来乞巧文化宣传的结果,实际只是供游人和文化学者观赏的乞巧文化符号,与巧娘娘信仰关系不大。
巧娘娘纸偶像不是由专职的民间画师制作,而是由纸活店的民间艺人制作。造像多为站立状,也有些为坐姿,但制作程序相同。其制作的基本方法是:先制作头部,这也是最关键的环节,一般是在人面模子上用当地特产的麻纸层层裱糊,达到一定的厚度要求后晒干,最外层再用白纸裱糊,干后打磨光洁,再描画五官。脸蛋用淡桃红晕染,樱桃小嘴用大红描画,柳眉、眼睛用墨笔描成。用黑纸剪成细长条装饰头发,再用彩纸装饰金银花簪。身躯部分以竹竿和秸秆绑扎成骨架,外用各色彩纸做成衣服、裙子的基本形,裙下露出三寸金莲,手用白纸剪出,两臂向前弯曲,一手拿拂尘,一手提帕,脚下踩莲花台。造像虽为纸偶,但还是表现出了巧娘娘的巧秀与端庄。①民间艺人在制作巧娘娘像时由于需求量大,所以多为流水线式的成批制作,他们技艺熟练,就像民间剪纸、刺绣、编织一样,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这正是民间艺术的特色所在。每年农历六月下旬,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城镇街道处处是花花绿绿的巧娘娘像,因此,巧娘娘像已成为当地民间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和其他专门的宗教造像相比,巧娘娘纸偶像不仅材质不同,制作方法不同,而且制作的仪式也不同。在西汉水流域,在其他宗教雕塑和绘画制作之前,民间画师首先要斋戒沐浴,请阴阳先生诵经,然后才能开始制作。如果是泥塑,内部的骨架要用有香味的柏木,同时要在骨架上写上五脏六腑,然后用泥裹塑。造像完成后,还要进行开光仪式,也就是招神,通过诵经或咒语让神的灵魂附在造像上,这样才能灵验。整个仪式都充满了庄严、神圣和神秘的气氛。而民间艺人的巧娘娘纸偶制作则没有这些讲究,他们制作和出售巧娘娘像,就和平时制作出售纸活明器一样,完全是一种程式化了的民间艺术造型。因此,巧娘娘纸偶像不仅没有神秘庄严的特征,反而充满了稚气、活泼、喜庆的民俗文化气息和民间艺术品质。
巧娘娘造像从形式上来看应属于纸扎的范畴。纸扎在我国历史悠久,自从纸得到了发明以来,除了主要用于书写外,就是用于各种纸造型。纸扎在古代主要用于制作明器,于南北朝时期基本形成,在宋代,由于手工业的发展,纸扎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宋代民间的七夕乞巧风俗中还搭建“乞巧棚”,用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乞巧棚上还刻有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②在明清时期,纸扎更是达到鼎盛,不仅用于丧葬、宗教活动中,还广泛运用于民间杂戏、社火等民俗活动的装饰。纸扎中的纸人早在新疆吐鲁番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就已出现了,唐代墓葬中也有纸人,但早期的纸人多为平面剪纸形式,具有招魂的寓意。③宋代的纸人则多为刻板印刷的平面体,由此可见,乞巧棚上刻画的牛郎织女像亦为这种形式。明清时期的纸人则演变为立体型,里面以竹子扎成骨架,外用彩纸裱糊,形成立体的人俑,小者高尺许,大者与真人相等④,这就是完整的纸偶了。但纸偶多用于丧葬习俗中的“奴仆”造型,或俗称“仆人”,其性质与奴隶社会的人殉、陶俑是一样的,只是纸偶轻巧且造价较低,因此在民间流传广泛。
但将纸偶用于神灵造像还较为少见,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宗教活动和丧葬习俗中至今还有剪纸的纸人和纸偶仆人,但用于神灵造像则只有巧娘娘。而纸偶巧娘娘像的形成,也与清代纸扎的盛行和纸仆人的出现有关。但纸仆人因丧葬性质而给人以凄悲神秘之感,而巧娘娘造像则如民间剪纸、刺绣、花灯一样,体现一种喜庆祥和的气息。从一些地方志的零星记载来看,巧娘娘纸偶像主要流行于陕甘一带。陇东乞巧风俗中就有同样的纸偶巧娘娘像,《正宁民俗》中有“以竹木扎成人形,艳服盛装作巧娘娘”的记载①;同时,一些地区也有用面塑制作的巧娘娘或巧娃娃,可能与宋代以来流行的摩睺罗有关。②陕西凤翔糜杆桥镇曹家庄的乞巧风俗中也有类似的巧娘娘像,但由乞巧姑娘们自己制作,精明能干的姑娘们事先用新收的麦草秆扎成一个女性模样的草人,给它穿上漂亮的衣服,俗称“巧媳妇”或“巧娘娘”,大家争相跪拜。③浙江东阳的东白山七夕节有拜彩斗的习俗,也是一种民间纸扎造型,但无涉纸偶。④广东乞巧风俗中有“摆七娘”的仪式,但只是摆一些工艺品和祭品之类,实际无“七娘”造像。⑤目前,只有西汉水上游地区还在盛行巧娘娘纸偶像,大多数地区则随着乞巧风俗的衰退都已销声匿迹了。
四、结语
总之,西汉水上游一带乞巧风俗中的巧娘娘崇拜,既有国内其他地区织女崇拜的一些基本特征,也体现出十分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地方特色的形成,既与西汉水上游地区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也与当地相对封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作为史前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灿烂的历史文化。源自东夷嬴姓族群的秦人自迁居西汉水上游以后,逐渐壮大起来,随后进入中华民族历史的舞台并最终成为主角,同时也缔造了秦文化。织女崇拜其实就是秦文化的遗风⑥,后来随着西汉水流域民族迁徙融合的复杂历史,又融入了氐羌少数民族文化因素,随之形成了这一带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乞巧风俗和巧娘娘崇拜。这里的巧娘娘崇拜既有以女红、爱情、婚姻等为基本内核的织女崇拜普遍意义,又体现了崇拜形式巫傩化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巧娘娘的造像也表现出独特的民间艺术情趣,彰显着西汉水上游地区独特的文化魅力。
对于汉代以来七夕节和乞巧活动的基本主题,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有些认为是以爱情、婚姻为主,也兼具生殖崇拜方面的含义;有些认为是祈求五谷丰登,指出织女是主瓜果谷物之神;也有些认为是以女织崇拜为主,强调女红含义。从历代七夕节和乞巧的内容、仪式来看,这些方面的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七夕节自形成以后,其内容和仪式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处于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对于这个问题,赵逵夫先生认为,七夕节最初的主题也是倾向于庆祝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后来由于封建礼教的进一步系统化、顽固化,这种超越礼教的婚姻显然有悖伦理道德,所以七夕的主题逐渐演变为以女红为核心的乞巧。②纵观自汉代以来的历代七夕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妇女的乞巧活动。乞巧的核心主题又是对织女的祭祀和崇拜,这种崇拜中当然也包含对婚姻、命运的祈祷,但主体方面则是妇女们对灵巧和智慧的祈求,以使自己心灵手巧,受到家人和社会的尊重,实现封建社会妇女的自我价值。传说中的织女是智慧和灵巧的女神,能织出天上美丽的云锦,具有女红文化始祖神的性质,所以受到广大劳动妇女的崇拜。
中国各地民间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织女崇拜的基本主题,同时由于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各异,所以又形成了各地不同的崇拜形式,对织女的称呼也各具特色,有织女、七姐、七娘、巧媳妇、巧娘娘等。西汉水上游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悠久,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从大地湾一期(老官台文化)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周秦文化、汉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许多古老的民俗民艺至今犹存,乞巧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带的乞巧风俗不仅没有退化,而且得到了地域文化的滋养,传承良好。西汉水上游地区的乞巧风俗历时七天八夜,从农历六月三十日晚一直延续到七月七日晚,乞巧活动形式丰富,包括迎巧、坐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等复杂的环节,同时还有独具地域特色的“跳麻姐姐”活动。抛开这些外在的仪式,从神灵崇拜的角度来考察,这一带的“巧娘娘”崇拜亦显示出与其他地区织女崇拜不同的独特性,体现了织女崇拜的本土化特色。
一、崇拜者的纯女性化
西汉水上游乞巧风俗中崇拜的唯一偶像是“巧娘娘”,从当地乞巧歌的内容来考察,巧娘娘其实就是织女,是这一带民间对织女的地域性称呼。但这里的巧娘娘又和当地人崇拜的“××娘娘”不同,巧娘娘中的“娘”读音为“nia”,而不是“niang”。前一种读音的“娘”是西汉水上游一带方言中对母亲的称呼;后一种读音的“娘娘”则往往是对女性神灵的称呼,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花儿娘娘等,有时也是对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女性、贵妇人、官太太的称呼。同一个字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读音,表达的含义也截然不同。前者体现出亲密无间的亲情关系,后者则用来称呼高高在上的高贵的女性神灵或者贵族女性。从整个乞巧活动期间年轻姑娘的情感活动来看,巧娘娘与她们达到了精神与情感的交融,这种真挚的感情甚至超越了现实中的母女感情,对母亲不敢说、不能表白的心声,却能在乞巧活动中向巧娘娘倾诉,有时尽管是无声的,但实现了真正的心灵沟通。尤其是七月七日夜晚送巧娘娘上天的时候,全体姑娘都流着眼泪,唱着悲情的送巧歌将巧娘娘的纸偶像烧掉,俨然一种生离死别的凄婉场景。
乞巧自然是女性的活动,崇拜的神灵也是织女(或巧娘娘),为什么还要提出“纯女性化”的命题呢?因为从历代的乞巧风俗来看,崇拜的偶像不止织女,也包括牛郎或其他男性神灵。所以参与乞巧活动者不止女性,亦不乏男性的参与。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中,不仅崇拜织女,也崇拜牛郎;不仅用瓜果祭祀牵牛、织女,而且画牛郎、织女的画像。这种崇拜传统在处于封建社会盛期的汉唐及两宋时期,显然不是为了歌颂牛郎、织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是延续了人文始祖崇拜的含义,因为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都是传统农耕经济时代的杰出人物,其劳动技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
从秦简《日书》《诗经》等历史文献可知,牛郎织女的传说至迟在春秋时期已基本形成,且具备了基本的情节要素。①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牛郎织女的传说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在民间流传了。②由此可知,牛郎织女传说的主人公原型可能更早,或许是远古氏族部落时期的人物。如吴天明认为,牛郎织女就是华夏族的先祖神和先妣神。③赵逵夫先生考证认为,牛郎应源于周族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织女源于擅织的秦人始祖女修④,《史记·秦本纪》中的“女修织”正包含了“织女”的基本含义。从敦煌文书中有关乞巧风俗的记载来看,乞巧风俗源于秦人。唐代陈鸿《长恨歌传》:“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附《丽情集》:“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五更转》中也有“哪边见牵牛?看看东方动,来把秦筝弄”的诗句。⑤可见,乞巧就是秦人的传统风俗,因而将织女的早期渊源考证为女修,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早期的牛郎织女崇拜其实是人们对氏族社会中有杰出贡献的人文始祖的崇拜,随之将其与天象中的星座建立关联,尔后才演变为爱情故事,从而丰富了传说的内容。刘宗迪先生则认为,七夕故事和民俗源于古人观象授时,“织女”源于七月为妇女绩纺之月,“牵牛”之名则源于“牺牲”或八月为“视牲”之月的含义,夏秋之交,二星双双升于中天,隔银河相望,牛郎织女故事由此而来。⑥这个认识也很有道理。从情理来讲,肯定是人类根据现实生活来命名星座,赵逵夫是将牛郎、织女与人文始祖关联起来,从早期神话历史的角度,提出人们根据氏族中杰出人物来命名牵牛、织女星的观点;而刘宗迪则是将其与民俗事象关联起来,认为视牲和妇女绩纺为牵牛、织女星名的来源。观点虽然不同,但共同之处是织女都与人类的纺织劳动密切相关。“女修织”与“织女”关联顺理成章,妇女绩纺与织女联系也理所当然。“叔均”是牛耕的发明者,所以和“牵牛”有关,这与后来牛郎织女传说中牛郎从事的“牛耕”有内在的关联性。
总之,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中同时崇拜牛郎和织女,正是因为牛耕和女织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的骨针、陶纺轮、骨纺轮、印纹陶以及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的纺织品遗迹等资料信息来看,织布技术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成熟了,且有相当的发展⑦;从甲骨文内容可知,至迟在商代已经使用牛耕了⑧。所以,虽然牛郎织女故事中的牛郎、织女源于牛耕和女织崇拜的观点还缺少必要的证据链条,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和发现,但这种认识是可以肯定的。由此可见,从牛郎织女传说的生发一直到后来的七夕节、乞巧活动,都贯穿着对牛耕和女织的崇拜。
这种崇拜习俗在部分地区近现代的七夕乞巧风俗中仍有遗留。例如,叶春生先生所引《广州岁时记》中就明确记载:“初七日陈设之物,仍然不移动,至夜仍礼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则童子为主祭,而女子不与焉。”时间范围大约为清末至辛亥革命期间。①应该说早期的七夕节和乞巧风俗中同时崇拜牛郎和织女,织女和牛郎都具有各自的智慧和灵巧,织女擅织,牛郎擅耕,男子向牛郎祈求的也是劳动智慧和灵巧。后来随着传统节日风俗的逐渐退化,形式和内容趋于简化,许多地区则没有了拜牛郎的仪式。同时,也因为许多地方的《地方志》等文献对七夕民俗的记载过于简略,遗漏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仪式,致使拜牛郎的习俗被逐渐忽略。在东南浙、闽、赣、台等地区,长期以来则流传着七夕拜魁星的风俗,魁星其实就是文曲星,主文章、文运,七月七日也是魁星的生日,尤为读书人所敬仰崇拜。②所以在七夕之夜跟织女一道接受人们祭拜的,不是牛郎,而是一位面目诡异的魁星神。祭拜织女的照例是女子,而祭拜魁星的则是男儿;女子向织女祈求的照例是聪慧灵巧,男子向魁星祈求的则是科场功名。③这种崇拜习俗其实也是牛郎崇拜的一种变体,封建社会的男子除了从事耕种这种重体力劳作以外,最好的出路就是读书求取功名,富贵人家的男子则主要是读书求功名,因此,男子的天职就是“耕读传家”。宋代的乞巧风俗中也同时崇拜牛郎织女,乞巧活动则不仅有女郎呈巧,也有儿童裁诗,可见当时的拜牛郎中也可能包含了读书与功名的寓意。④所以拜魁星可能是由拜牛郎演变而来,只是拜魁星的功利性目的更明确了。在陕西凤翔糜杆桥镇曹家庄村的乞巧节庙会中,男性也参与其中,主要是担任会长进行收布施、请乐队、接待还愿等世俗性事务⑤,虽然没有男人拜牛郎的习俗,但男性的参与应该还是过去拜牛郎的遗俗。
在西汉水上游的七夕乞巧风俗中,所有活动的内容和仪式都已与男性无关,男性不仅不视七夕为节日,甚至有些还对乞巧活动持反对态度。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宗教信仰的神灵谱系中,也无巧娘娘的一席之地,既没有专门的庙宇,也无永久的造像,只是在乞巧活动的七天中,才临时选定一个居民家庭作为暂时的神堂来坐巧。坐巧地点的选择也往往颇费周折,多数人家都不欢迎巧娘娘和乞巧者,可能怕吵闹,同时也可能与巧娘娘没有较高的神灵地位有关。多数村庄在女子乞巧的活动中,男性也旁观看热闹,但男性从来不敬拜巧娘娘,只在乞巧过程中和年轻女性调笑取乐,甚至还拿不敬的语言来打趣巧娘娘像。总之,这里的七夕节和乞巧活动已完全成为年轻女子祭祀只属于女性的神灵“巧娘娘”的纯女性活动,崇拜的主客体都呈现出纯女性化。这是西汉水上游一带乞巧风俗中的普遍情形。近年来,随着西和县被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和乞巧民俗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的扩大,这种现象有所变化,少数中老年男性也在乞巧期间开始敬拜巧娘娘。
这种情形的形成,是有历史文化根源的,应该说中国的神灵信仰体现的恰恰是母性化特征。从女娲造人的创世神话可知,母性是人类的创造者,具有很高的地位。再从原始神话中的西王母到后来的王母娘娘,直至感生神话中的殷商始祖简狄、周人始祖姜原、秦人始祖女修等,都体现了母性的伟大和神圣。①观世音菩萨中国化以后更是成为中国民众普遍敬仰的女性神灵,她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远远胜过了她的导师释迦牟尼。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信仰的神灵中,母性神灵也很多,除了国人普遍信仰的王母娘娘、观音菩萨以外,地方母性神灵还有香山妙善菩萨、云华山老母以及民间信仰的送生娘娘、花儿娘娘等,这些母性神灵是当地男女共同信仰的神灵,信众并无男女之别。
巧娘娘——织女,作为传说中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应该说亦具有尊贵的地位,为何在民间成为只能供女子信仰的神灵?这应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牛郎织女传说的演变有关。如前所述,早期的牛郎织女崇拜反映的是人们对氏族杰出人物的敬仰,织女是杰出的女织的发明创造者,自然受到全体民众的崇拜。而当牛郎织女之间发展为男女关系并演变为爱情传说以后,这种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男女婚姻有悖日趋完备的封建伦理道德,所以织女在民间的地位逐渐下降,并最终成为年轻女性崇拜的对象就理所当然了。应该说男女情爱是神圣的,否则就不会有人类的繁衍,尤其在氏族社会时期,人类对生殖繁衍充满了敬畏,人口的增长与氏族的壮大繁盛息息相关,所以自由的婚姻关系不曾被视为野蛮和耻辱。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一夫一妻制形成,才逐渐有了男女关系的规约和限制。尤其是随着封建礼法制度的建立,人类社会等级制度逐渐形成,从神到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男女情爱和婚姻讲求门当户对,地位相称,原始的婚姻关系逐渐淡出人类生活。但在后来的礼法社会中,这种原始婚姻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由蒙昧时代的原始婚俗发展到文明社会的婚礼,标志着社会理性对人类原欲的约束,而一些遗留的原始婚俗体现了对礼的反作用,也意味着被礼压抑的人性本然状态及原欲的适当表露和宣泄。②诗经中就有许多反映这种思想的内容,儒家圣人孔子则从政治和礼法的角度对这些内容进行了重新阐释,但也掩盖了其中的一些本真思想。直至汉代的画像石中,仍有一些表现男女野合的作品,这些都反映了人类原欲与礼法之间的冲突,也表达了人类对礼法的一种超越意识。
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虽然和原始婚俗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本质上亦是一种自由的男女关系,它跨越了神、人界限的情爱,是一种超越了封建礼法规范的不合理爱情,所以自然会受到当权者的干预而最终成为悲剧。自西汉中期以来,随着封建礼法规范体系的日趋完备,从民间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行为和思想也逐渐被禁锢,人的自由意识被压抑到底层。七夕节也由早期庆牛郎织女相会逐渐演变为以妇女乞巧为核心,织女也由此成为妇女们倾诉屈衷的唯一对象。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礼法规范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空前严酷,甚至连年轻女子的乞巧也被视为不守本分,有时也会受到家长的反对。西汉水上游一带的乞巧歌中,依然较多地反映了被压抑的民间妇女对不平等婚姻的怨愤和无奈。①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者,织女自然也就难登正统神灵谱系的大雅之堂。西汉水上游一带由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故保留的古风和传统民俗较多,人们的封建意识和发达地区相比还较浓厚,因此巧娘娘在男性心中也就不是正统的母性神灵了。
二、崇拜方式的巫傩化
西汉水上游地区的乞巧风俗中,乞巧的主要形式有迎神、送神、祭拜、占卜、跳神等,其中最主要的祭拜活动以姑娘们的唱跳为主,在现代的乞巧活动中,受时代的影响也有跳唱现代流行歌舞的内容。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甚至改革开放以前乞巧的祭拜活动中,以姑娘们手拉手边摆边唱为基本形式,七天八夜一直如此唱歌祭拜。据当地的老年妇女讲,这种唱歌祭拜的形式是从过去一直流传下来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地区比较少见,邻近的陇东地区流行乞巧歌,天水地区则流行《巧娘娘》歌②,但陇东地区乞巧的时间短,且唱乞巧歌的形式已不得而知了。这种手拉手唱歌祭拜巧娘娘的方式,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年轻姑娘们节日期间的一种娱乐,无需深究其含义和来源;但笔者以为,既然这种形式从古至今一直这样传承,必然有其内在的文化基础。郑土有先生也指出,西和乞巧活动完全继承了祭、歌、舞三位一体的人类社会早期的祭祀传统,毫无疑问是一项传承历史悠久、仪式保留较为完整的古老习俗。③只是这种祭拜形式的形成时间无从考证,其自然而然地形成,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人们也习以为常了。
在西汉水流域,民间举行宗教活动的形式主要有三种:①是佛教僧侣们做佛事,主要以诵经忏悔和超度为主,属于佛家。②请法师(当地称为“法官”)念咒语来驱鬼捉妖,从咒语内容中总是呼唤“太上老君”来看应属于道家。当地的阴阳先生也是施行宗教活动的主体,但阴阳先生也有“释门”和“玄门”的区分,释门以诵念佛教经典为主,玄门则多使用道家咒语,故阴阳先生也分属于佛家和道家。③巫师(当地称为“师公”或“师公子”)的传神活动,既不诵经也不念咒语,而是身穿长袍,后脑缀长辫,手拿羊皮扇鼓敲打,甩动长辫,边舞边唱,就是以歌舞的形式来娱神,以达到宗教目的。这种宗教形式被当地民间形象地称为“花儿道场”。所谓“花儿道场”就是以歌舞为主要祭祀形式的宗教活动,“花儿”正是西北地域少数民族的民歌,汉族称“山歌”,少数民族称“花儿”。据此,笔者以为,西汉水流域的这种宗教形式应该源自少数民族,善于歌舞是少数民族的特点,也是他们宗教活动的特色。
西汉水流域是古代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地区,也是民族迁徙的主要通道,西北甘青高原的氐羌族群正是经过这一带向南迁徙的。更有趣的是,在西汉水上游地区,属于氐羌民族的寺洼文化和周秦文化隔河对峙分布①,而西汉水下游的深山峡谷中就只有寺洼文化了。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认为西汉水流域寺洼文化的族属就是白马氐。②因此,西汉水流域也就是一条民族迁徙融合的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势力范围不断扩张,一度成为统治北方的强大民族。在西汉水流域,氐人在仇池山一带建立了地方政权仇池国,羌人也在相邻的白龙江流域的宕昌建立了宕昌国,西汉水与白龙江仅一山之隔。在后来的民族矛盾中,氐羌人在被迫南迁的同时也就地汉化,从而将氐羌文化的基因注入了西汉水流域,所以这里的民俗文化包含着浓郁的氐羌文化的因素。
师公其实就是当地氐羌民族巫傩文化的一种延续。陇南文县的白马藏族被认为是古代氐族的遗裔,他们至今依然保持着傩舞祭祀的传统。他们的傩舞被称为“池哥昼”,“池哥”身穿羊皮袄,头戴狰狞的面具,手拿牦牛尾和木刀迈步挥舞,和西汉水流域汉族师公的祭祀仪式颇为相似。宕昌藏族其实是古代羌族的遗裔,他们也有着类似的巫舞“羌巴舞”。而且他们都是善歌的民族,虽然现代巫傩舞中不唱歌,但在祭祀结束后的火圈舞中,男男女女则围着篝火,手拉手,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所谓的“花儿道场”也可能与善歌的氐羌民族文化有关,乞巧仪式中手拉手唱歌祭拜巧娘娘的形式也可能是受当地氐羌文化的影响。
在西汉水上游地区民众自发的敬神活动中,有一类人被当地民众称为“神婆”(以中老年女性为主,有时也有个别男性参与),她们在农闲时间主要以到处敬神拜佛为业。她们不识字,也不会诵经,敬神的形式主要是“唱神歌”。不管是在寺庙中还是在行走途中,也有时是在家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唱。唱神歌敬神的方式和乞巧活动中唱乞巧歌在形式上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宗教艺术的形式来达到娱神的目的。这种娱神的形式也体现在当地的民间戏曲和社火中,这里民间的戏曲和社火不是随意演出的纯娱乐活动,而是一种娱神活动。有些村庄的戏曲和社火每年必须举行,否则就会惹怒神灵,于整个村子不利。戏曲和社火的主要形式也是歌舞,这和所谓的“花儿道场”的性质是相同的。尤其是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社火的演出时间、组织结构、角色构成、装饰特征、宗教祭祀等和白马藏族的傩舞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显然是长期以来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③
在西汉水流域的乞巧仪式中,还有一项独特的内容,“跳麻姐姐”,即在乞巧的姑娘中挑选一位替神灵巧娘娘或麻姐姐传话。这项活动有一定的风险,因此,一般要在有经验的中老年妇女的主持下进行。挑选麻姐姐的方法有三:①平时曾经梦见自己跳麻姐姐的人;②认为自己当年有厄运,为求平安愿意跳麻姐姐的人;③大家公认神灵会附在其身,也就是其有神性或灵性之人。在开始跳之前,先烧香纸祷告,选定的跳神主角站在巧娘娘桌前,左右各有一位陪跳者,其他姑娘则跪于神桌两旁,一时气氛严肃紧张,鸦雀无声。随后一位装扮麻姐姐的姑娘钻到神桌下,开始与外面的乞巧姑娘相互问答(外面的姑娘问,桌下的姑娘答):
“麻姐姐,做(西汉水流域方言读zu)啥着呢?”
“簸粮食着呢。”
外面的姑娘用数板调快速齐唱:“簸东了,簸西了,簸下的粮食鸡噆(西汉水流域方言读can)了。”
“麻姐姐,做啥着呢?”
“磨面着呢。”
外面的姑娘又齐唱:“东磨面,西磨面,渠里无水磨不转。”
“麻姐姐,做啥着呢?”
“擀面着呢。”
外面的姑娘则又相互问答对唱:“多么少?”“两盆呢”“薄么厚?”“照人呢。”“长么短?”“噎人呢。”
紧接着神桌下的姑娘一边往外钻,一边拖长音大喊:“麻姐姐的神——来——了——”
神桌旁的姑娘则齐唱《跳麻姐姐歌》:
麻姐姐,虚空来,脚(西汉水方言读jue)上穿的登云鞋(西汉水方言读
hai)。
麻姐姐,隔河来,手里打着响锣来。
麻姐姐,翻山来,脚踏铺下(西汉水方言读ha)的红毡来。
一直反复唱,跳神者则不断地蹦跳,幅度越来越大,直至神灵巧娘娘或麻姐姐附体为止。“神灵附体”的标志就是跳神者浑身酥软,四肢无力,神志不清,口吐白沫,哭笑无常。旁边的人则乘机向神灵问话,而跳神者的回答往往语无伦次,难以听清,有时也偶尔能说一两句较明白的话。随后旁边的主持者向神祷告,祈求神灵归位,跳神者慢慢苏醒。①
有学者认为这种仪式在乞巧活动中显得较为突兀,和其他环节似有脱节之嫌,西和学者黄英先生也提出麻姐姐和巧娘娘毫无关系。②从这个仪式过程来看,麻姐姐也是一位地方神灵,这和一般的“神灵附体”现象又不同,多数跳神活动只有神、人以及沟通神人的中介跳神者三个环节;而这里显然又多出了一个麻姐姐,也就是跳神者有可能是巧娘娘“附体”,也有可能是麻姐姐“附体”,也有可能巧娘娘的神旨要通过麻姐姐和跳神者的双重环节向世人传达。对于麻姐姐的来历问题,目前还没有较为可信的解释,有学者提出麻姐姐是否与麻姑有关,但遭到西和地方学者的反对,认为一个称姑,一个称姐,与麻姑无关。①但以“姑”和“姐”的称呼区别来作为反驳理由似乎还不够充分,如前文所述,巧娘娘也有多种称呼,既可称“娘”,也可称“姐”,这个问题还需以专文形式进行进一步的考察。赵逵夫先生在《飞天》上发表的《牛郎织女的传说》一文中,就有麻姐姐的情节,其中的麻姐姐是一位手巧、善于织麻布且善良的民间妇女,这是赵逵夫先生于1958年采集的流传于西汉水流域西和、礼县一带部分地区的民间传说。②但有关麻姐姐的传说在西汉水流域其他地区并未广泛流传。
笔者以为,跳麻姐姐的活动在西汉水流域的宗教活动中同样能找到文化基础。除了专职的僧侣、阴阳先生、法师、巫师以外,西汉水流域的民间也有跳神的活动,当地也称为“发爷”或“发神”,跳神者被称为“厥玛”,但厥玛已不仅仅限于女性,男性也很多。厥玛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由神灵挑选的传话者,也是具有神性或灵性的人,“神灵附体”以后他就会从众人中跳出来,“附体”后的表现和跳麻姐姐者一样。有些“神婆”也被公认为有神性,所以在唱神歌时还会“神灵附体”,无需经过剧烈的跳跃过程就可进入神灵附体的状态,当地人将这种形式也称为“发神”或“发爷”。
西汉水上游一带的这一类宗教活动,无论是传神、发神、发爷还是跳麻姐姐,其性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古代巫文化的一种遗留,和佛教、道教以及阴阳先生的宗教活动完全不同,保留了原始宗教的基本特征。巫师其实就是沟通神与人的中介,段玉裁解释“巫”字的构成是:“直中绳,二平,中准,是规矩也。”其中“二平”乃天地之形,上平为天,下平为地;“中绳”乃天柱之形,上接于天,下接于地。而巫居其中,右为巫,左为觋,一男一女,通人事,达鬼神,沟通天人。由此可以看出,巫就是“事无形”(即人眼看不见的鬼神)的人,其降神的方式就是舞蹈。③
在西汉水上游一带信仰的地方神灵中,有一位神灵称为“杨氏(当地方言读si)爷”,杨氏爷信仰活动的主要形式就是神灵附体的跳神,当地也称为“降爷”,据说跳神的“厥玛”是由神灵杨氏爷挑选的。“杨氏爷”舞棍弄棒,跳上蹿下,口中念念有词,进行驱鬼活动。当地人也称杨氏爷为“杨将军”,看来是一位武将。无独有偶,陇南的白马人也信仰杨氏爷,白马人也称为“杨氏大将”,且信仰的方式基本相同。④结合白马人的民间传说和西汉水流域的仇池杨氏政权来看,这位“杨将军”应该源于古代氐人中的一位武将,由于民族文化的融合而在整个陇南及周边地域具有广泛的信仰。而且信仰活动的形式也是神灵附体的巫的形式,因此,这一带的巫文化应与氐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说手拉手摇摆唱歌祭拜巧娘娘是受巫傩文化的影响的话,那么跳麻姐姐则体现了纯粹的巫文化特征。不管麻姐姐的来源如何,她和麻姑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无碍于跳麻姐姐巫文化的本质。黄英先生提出跳麻姐姐源于西戎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氐羌文化的观点,他同时认为麻姐姐就是古代氐族妇女中纺织麻布的能手。①《魏略·西戎传》记载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南史·夷貊传》记载氐人“地植九谷,种桑麻”②。被学术界称为氐羌后裔的白马人直至20世纪70年代还大量穿麻布长衫,西汉水上游一带汉民在新中国成立前大多都穿麻布衣服,从而被戏称为“麻郎”。由此看来,麻姐姐也是心灵手巧的人,因此,在乞巧仪式中加入麻姐姐,虽在形式上有突兀之感,但主题上并不矛盾,巧娘娘是天上的智慧灵巧之女神,麻姐姐是凡间的纺织能手,她们都能向民间妇女赐予或传授灵巧。
三、偶像造型的民艺化
宗教造像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提倡偶像崇拜的佛教也不例外,而且佛教神灵造像是中国古代宗教造像的主体,其他如道教神灵的造像则无处不有。宗教造像的主要形式有雕塑和绘画两种基本形式,多置于石窟、庙宇中,供信众随时参拜敬奉。人们之所以要凿窟立庙塑造神灵形象,是为了有一个相对长期固定的精神寄托场所。
如前所述,西汉水上游一带的巧娘娘没有固定的庙宇,也就是说,在人间如此众多的石窟、庙宇中没有织女的立足之地,这与牛郎织女传说的爱情主题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而使织女的神灵地位下降有关。在西汉水上游的乞巧活动中,巧娘娘与凡人相聚的时间只有七天,其余时间则无任何与此有关的宗教活动。有鉴于此,巧娘娘也就没有固定的庙宇,也没有永久的塑像或画像。笔者在一篇论文中曾列举了牵牛和织女造像在历代的发展情况,最早是西汉时期昆明池牵牛和织女像,东汉画像石中也有牵牛织女星象图,宋元时期也有七夕节刻画牵牛织女像的风俗,明清以后就没有相关记载了。③但在乞巧风俗盛行且传承最完整的西汉水上游地区却没有牵牛织女塑像或画像,也没有巧娘娘的固定塑像和画像。西和县被评为“中国乞巧民俗文化之乡”以后,在晚霞湖畔立了一尊巧娘娘的大理石雕像,其在本质上只是当代人们宣传乞巧文化的一种符号,并非乞巧文化的传统。传统的巧娘娘造像既不是雕塑,也不是绘画,而是一种纸偶。纸偶和宗教雕塑、绘画相比没有永久性,也便于在乞巧结束后送巧娘娘上天时烧掉,也不必考虑平时无处安置的问题。在西和县大柳乡的文化大院中,长期供奉着一尊巧娘娘坐姿纸偶像,造像置于一顶花轿中,但这亦是近年来乞巧文化宣传的结果,实际只是供游人和文化学者观赏的乞巧文化符号,与巧娘娘信仰关系不大。
巧娘娘纸偶像不是由专职的民间画师制作,而是由纸活店的民间艺人制作。造像多为站立状,也有些为坐姿,但制作程序相同。其制作的基本方法是:先制作头部,这也是最关键的环节,一般是在人面模子上用当地特产的麻纸层层裱糊,达到一定的厚度要求后晒干,最外层再用白纸裱糊,干后打磨光洁,再描画五官。脸蛋用淡桃红晕染,樱桃小嘴用大红描画,柳眉、眼睛用墨笔描成。用黑纸剪成细长条装饰头发,再用彩纸装饰金银花簪。身躯部分以竹竿和秸秆绑扎成骨架,外用各色彩纸做成衣服、裙子的基本形,裙下露出三寸金莲,手用白纸剪出,两臂向前弯曲,一手拿拂尘,一手提帕,脚下踩莲花台。造像虽为纸偶,但还是表现出了巧娘娘的巧秀与端庄。①民间艺人在制作巧娘娘像时由于需求量大,所以多为流水线式的成批制作,他们技艺熟练,就像民间剪纸、刺绣、编织一样,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这正是民间艺术的特色所在。每年农历六月下旬,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城镇街道处处是花花绿绿的巧娘娘像,因此,巧娘娘像已成为当地民间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和其他专门的宗教造像相比,巧娘娘纸偶像不仅材质不同,制作方法不同,而且制作的仪式也不同。在西汉水流域,在其他宗教雕塑和绘画制作之前,民间画师首先要斋戒沐浴,请阴阳先生诵经,然后才能开始制作。如果是泥塑,内部的骨架要用有香味的柏木,同时要在骨架上写上五脏六腑,然后用泥裹塑。造像完成后,还要进行开光仪式,也就是招神,通过诵经或咒语让神的灵魂附在造像上,这样才能灵验。整个仪式都充满了庄严、神圣和神秘的气氛。而民间艺人的巧娘娘纸偶制作则没有这些讲究,他们制作和出售巧娘娘像,就和平时制作出售纸活明器一样,完全是一种程式化了的民间艺术造型。因此,巧娘娘纸偶像不仅没有神秘庄严的特征,反而充满了稚气、活泼、喜庆的民俗文化气息和民间艺术品质。
巧娘娘造像从形式上来看应属于纸扎的范畴。纸扎在我国历史悠久,自从纸得到了发明以来,除了主要用于书写外,就是用于各种纸造型。纸扎在古代主要用于制作明器,于南北朝时期基本形成,在宋代,由于手工业的发展,纸扎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宋代民间的七夕乞巧风俗中还搭建“乞巧棚”,用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乞巧棚上还刻有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②在明清时期,纸扎更是达到鼎盛,不仅用于丧葬、宗教活动中,还广泛运用于民间杂戏、社火等民俗活动的装饰。纸扎中的纸人早在新疆吐鲁番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就已出现了,唐代墓葬中也有纸人,但早期的纸人多为平面剪纸形式,具有招魂的寓意。③宋代的纸人则多为刻板印刷的平面体,由此可见,乞巧棚上刻画的牛郎织女像亦为这种形式。明清时期的纸人则演变为立体型,里面以竹子扎成骨架,外用彩纸裱糊,形成立体的人俑,小者高尺许,大者与真人相等④,这就是完整的纸偶了。但纸偶多用于丧葬习俗中的“奴仆”造型,或俗称“仆人”,其性质与奴隶社会的人殉、陶俑是一样的,只是纸偶轻巧且造价较低,因此在民间流传广泛。
但将纸偶用于神灵造像还较为少见,在西汉水上游一带民间,宗教活动和丧葬习俗中至今还有剪纸的纸人和纸偶仆人,但用于神灵造像则只有巧娘娘。而纸偶巧娘娘像的形成,也与清代纸扎的盛行和纸仆人的出现有关。但纸仆人因丧葬性质而给人以凄悲神秘之感,而巧娘娘造像则如民间剪纸、刺绣、花灯一样,体现一种喜庆祥和的气息。从一些地方志的零星记载来看,巧娘娘纸偶像主要流行于陕甘一带。陇东乞巧风俗中就有同样的纸偶巧娘娘像,《正宁民俗》中有“以竹木扎成人形,艳服盛装作巧娘娘”的记载①;同时,一些地区也有用面塑制作的巧娘娘或巧娃娃,可能与宋代以来流行的摩睺罗有关。②陕西凤翔糜杆桥镇曹家庄的乞巧风俗中也有类似的巧娘娘像,但由乞巧姑娘们自己制作,精明能干的姑娘们事先用新收的麦草秆扎成一个女性模样的草人,给它穿上漂亮的衣服,俗称“巧媳妇”或“巧娘娘”,大家争相跪拜。③浙江东阳的东白山七夕节有拜彩斗的习俗,也是一种民间纸扎造型,但无涉纸偶。④广东乞巧风俗中有“摆七娘”的仪式,但只是摆一些工艺品和祭品之类,实际无“七娘”造像。⑤目前,只有西汉水上游地区还在盛行巧娘娘纸偶像,大多数地区则随着乞巧风俗的衰退都已销声匿迹了。
四、结语
总之,西汉水上游一带乞巧风俗中的巧娘娘崇拜,既有国内其他地区织女崇拜的一些基本特征,也体现出十分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地方特色的形成,既与西汉水上游地区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也与当地相对封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作为史前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灿烂的历史文化。源自东夷嬴姓族群的秦人自迁居西汉水上游以后,逐渐壮大起来,随后进入中华民族历史的舞台并最终成为主角,同时也缔造了秦文化。织女崇拜其实就是秦文化的遗风⑥,后来随着西汉水流域民族迁徙融合的复杂历史,又融入了氐羌少数民族文化因素,随之形成了这一带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乞巧风俗和巧娘娘崇拜。这里的巧娘娘崇拜既有以女红、爱情、婚姻等为基本内核的织女崇拜普遍意义,又体现了崇拜形式巫傩化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巧娘娘的造像也表现出独特的民间艺术情趣,彰显着西汉水上游地区独特的文化魅力。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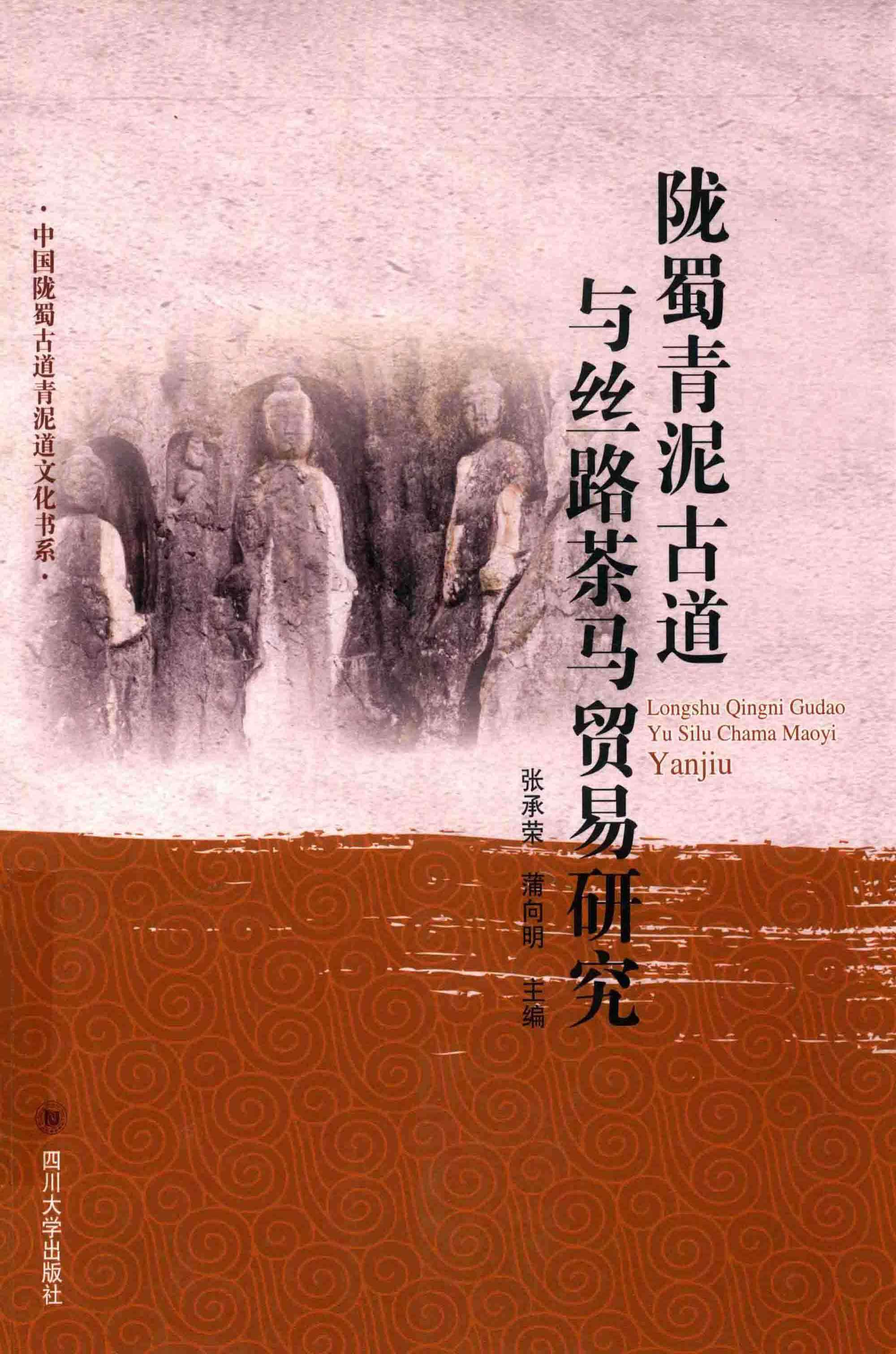
《陇蜀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研究》
出版者:四川大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丝绸之路与陇蜀青泥古道”“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蜀道申遗与陇蜀秦蜀交通”“青泥古道与陇南地域文化”四部分,是近年来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陇南本土在陇蜀青泥古道与丝路茶马贸易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重点在陇蜀青泥古道自汉唐以来政治、军事、交通、商贸诸方面的文化研究,兼顾青泥道在丝绸之路茶马贸易方面的历史地位、历史文献、文化遗存以及沟通南北丝绸之路廊道路网方面的研究。
阅读
相关人物
余永红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