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 内容出处: | 《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图书 |
| 唯一号: | 290920020230002440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
| 分类号: | D614 |
| 页数: | 22 |
| 页码: | 194—215 |
| 摘要: | 全国在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相当落后。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甘南藏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事业,是摆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州(工)委结合甘南的实际,先从对农业、畜牧业和私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入手,积极响应中央关于整风反右派号召,扌欣起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并从河南省招进4万多名支建青年,以便加快甘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
| 关键词: | 社会主义建设 甘南州 |
内容
全国在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相当落后。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甘南藏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事业,是摆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州(工)委结合甘南的实际,先从对农业、畜牧业和私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入手,积极响应中央关于整风反右派号召,扌欣起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并从河南省招进4万多名支建青年,以便加快甘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始末
20世纪50年代,随着我国“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甘南藏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国民经济体制从私有制到全民所有制和劳动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转变,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模式,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初级再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从而使甘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较大成就。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甘南总土地面积388万公顷中,有耕地约68701公顷,占总土面积的1.78%。常年农作物面积在53,360公顷上下。1949年甘南解放初,有农村人口25.8万人,有农业劳动力15万余人。除玛曲、碌曲不种植农作物外,夏河、卓尼是半农半牧区,临潭、西固(舟曲)是农业区。长期以来,甘南在建国前后,境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共有四种形式:一是以夏河为主的喇嘛教寺院土地所有制。大部分土地被寺院占有,全部以出租的形式让当地藏族农民耕种,定期交纳租粮。如夏河拉卜楞镇及附近13庄的土地,基本上属于拉卜楞寺所有。二是土司土地所有制。从元、明朝开始,杨土司在其管辖的卓尼、迭部和舟曲的南部境内,即在总面积为3万多平方公里、拥有3.5万户、近10万人的地域内,所有土地全是杨土司的。群众耕种的土地是"兵马田地”和寺院的“僧田”。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三是西道堂土地所有制。临潭的西道堂从1890年创建以来,既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独立派别,又是集农、工、商、贸、林、牧、副业为一体的经济群体。西道堂的一切财产归集体所有。当时拥有耕地约662公顷。四是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主要存在于临潭县境内。当时,占临潭县农村总人口18.4%的地主占有耕地8.8%,约有1618公顷,人均约1.2公顷。
解放初,甘南各级党政组织遵照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对拉卜楞寺教区、西道堂和杨土司的辖区及广大藏族聚居的半农半牧区,均采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对其土地制度基本保持不变。而在农业区,甘南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20世纪50年代里,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土地改革运动。自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后,甘南藏区先在临潭、西固县的一些农业乡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52年春,遵照省委关于民族地区坚决贯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首先在临潭县的扁都乡和西固县的沙湾乡,进行土改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然后派出10多支土改工作组,分期分批地全面进行土改运动。给9801户贫苦农民分配土地约2430公顷。
二是组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互助组。1950年卓尼新堡区 (今藏巴哇乡)4户农民,在罗进荣的带领下,组成新联互助组。1951年2月转为常年互助组。接着又有5户农民组成了友爱互助组。1952年春,夏河县二区三乡的3户农民成立了尕道光互助组。这些都是在甘南最早出现的、农民自发组建起来的农业互助合作生产形式。1951年9月,党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向全国农民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甘南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中央的《决议》精神,提出“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以各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变工队、互助组。到1953年春天,在甘南各县农村共建立农业互助组3533个,参加农户达12,129户,占总农户的57.4%。其中:常年互助组274个,季节性互助组3259个。这些互助组连年增产,比单干的农户亩产高出20公斤左右。
三是成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春,党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是年9月,工委贯彻执行《决议》精神,首先在临潭县扁都乡和西固县的坪定乡试办了两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典型,总结摸索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1954年2月,全州试办了临潭扁都乡由12户农民组成的哈尕滩初级社和舟曲坪定乡由13户农民组成的坪定初级社。同年10月,工委决定在农业区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号召和教育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到1954年底,全州共办初级农业社11个。1955年底,全州初级社达99个。到1956年12月底,全州农业区共建初级农业社398个,入社农户达2.1万户,占总农户的89.2%。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初级合作化。
四是转建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5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把全国的合作化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甘南的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掀起迅猛发展的热潮,各地把短期内办起的初级社很快转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截止1956年12月,全州已转高级社176个,入社农户20,407户。到1957年底时,全州高级社达到195个,入社农户25,392户,占总农户的90.5%。这样,基本上实现了全州农业的社会主义高级合作化。1958年春,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全州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运动,随之把农业合作化推向了顶峰。1958年8月,舟曲县率先将17个初、高级社合并为9个农村人民公社。接着临潭、夏河、卓尼3个县于9月上旬,合乡并社,全部建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州共建“政社全一”的农村人民公社47个,其中农业区人民公社20个。1959年元月全州将47个人民公社合并为35个,1960年又调整为47个。1962年合并为大公社12个,1969年又扩大为103个,直到1984年撤销时的人民公社有104个。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人民公社这种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在甘南的国民经济里始终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二)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元月,全省第二次牧区工作会议后,党在甘南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政策,通过牧业走互助合作化道路,逐步把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个体经济,改造成为国家所有制和牧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从1956年上半年起,党和政府提出《关于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意见》,首先在夏河、碌曲、玛曲、卓尼4个县分别召开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会议,对牧区开展互助组的时间、步骤和具体方法,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经过省、州、县召开的专题会议,在甘南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掀起大力宣传互助合作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潮。州委抽调200名党政干部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组成工作团,下设3个分团,分赴卓尼、夏河、碌曲、玛曲等县,深入牧区帐圈,广泛宣传互助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党对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通过各种方式说服教育有顾虑的大小部落头人,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解除顾虑。半年之内,很快在夏河、卓尼两县办起了170个以牧民个体经济为基础的牧业互助组。碌曲县也在牧民历来“联群放牧”的基础上,经过加强领导和完善管理制度,组成了12个互助组。
1956年下半年,州委、州政府认真贯彻全省第三次牧区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出:“牧区今后必须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稳步发展畜牧业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现有的互助组、合作社进一步加强领导,进行整顿。对纯牧区和以牧为主的地方,一般暂不发展合作社,个别确已具备办社条件的,须经州委批准后方能建社,尽量减少盲目性。1957年初,州委作了《关于发展畜牧业的十年规划》,提出对全州畜牧业经济改造在10年内完成的设想。即卓尼、夏河两个县在1966年建成高级牧业生产合作社,碌曲、玛曲两个县在1967年达到高级牧业生产合作社。到1965年以前,把牧主经济纳入公私合营牧场或国营牧场、合作牧场,用吸收其加入合作社等办法完成对牧主经济的改造。同时决定在卓尼、夏河两个县进行试办。夏河县选择了有3年创办互助组经验的三区麻当村进行试点。州、县、乡派出联合工作组,很快办起了全州第一个有藏、汉、回3个民族农户参加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联社。卓尼县在135个牧业互助组的基础上,建起了6个全州首批牧业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下半年,受全国、全省蓬勃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影响,甘南牧区也开始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从而加快了甘南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主导思想上放弃“慎重、稳进”的方针。有的牧业初级社成立不到一年,就扩建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有的初级社在筹建中,就一次性地建为高级社。到1958年1月,卓尼全县实现了高级社化,共建高级社314个,其中牧业高级社58个。夏河县的一、二、三、四区(均为半农半牧区)基本上实现了农牧业的初级合作化。1958年下半年,洮江(包括今碌曲、玛曲两地的纯牧区)县及全州结合反封建斗争,根据全体广大农牧民的要求和愿望,于9月15日一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建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47个(其中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27个)。这样,在短短的10多天中,甘南的畜牧业“一步登天”,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甘南由一个带有奴隶制残余痕迹的封建社会直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完成了个体畜牧业经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民主革命任务。
(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6月,党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确定经过国家资本来改造资本主义的工业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形成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也就是实施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
解放前,甘南藏区的商业主要集中在临潭、夏河、卓尼、西固4个县境内的少数集镇。夏河县很早就是安木多藏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逐渐出现了牛、羊、马和皮毛畜产品及民族用品等交易市场,并围绕拉卜楞寺教区形成物资交易中心。临潭新城古有“茶马互市”的商业贸易,是汉、回、藏贸易的重要商阜和集散地。洮河流域随着木材的大量交易,也产生了一些加工木器家具和畜产品及金银手饰、铁铜器皿的手工作坊。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和发展民族贸易,将价廉物美的民族必需品送到广大农牧民手中,又把群众手中的牛羊皮毛肉等畜产品收购上来。购销公平、买卖合理,进一步促进和繁荣了民族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往后,夏河县的集市贸易发展成以拉卜楞寺为主体的寺院贸易,寺院几乎垄断了土特产和畜产品市场。临潭县发展成以西道堂为龙头的对内地辐射的商业贸易。党和政府为繁荣城乡经济,发展民族贸易,一方面保护、扶持个体商贩,定期举办各种物资交流大会。另一方面大力招引内地商贾和商行来甘南进行贸易,提高商品交流的贸易额。使个体私人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50年,甘南共有私营工商业1551户,从业人员2243人,拥有资金107万元。到1954年12月底,私营工商业发展到2805户,从业人员达3800人,拥有资金144万元。
当时,甘南的私营工商业者大多资本小,设备陈旧,货源稀疏,渐感经管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这样,1955年11月党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颁布后,甘南州于1956年1月召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会议,各县相继成立了“私改”办公室。首先,对城乡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调查和摸底。据统计,1956年春全州城乡共有私商1578戶,从业人员2243人,拥有资金166万元。其中农村乡镇有私商247户,从业人员411人,拥有资金66万元。其次,以夏河、临潭两个县为重点,大力宣传党的私改政策,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和登记工作。三是认真开展清产核资。本着自报公议的原则,呈报行业工作委员会审核,并提出意见后通过从业者定价。当时,因受内地公私合营运动的影响,甘南的私改进展很快。遵照省委对民族地区提出的 “统筹兼顾”、“重点改造”、“典型示范"、“多搞经销代销,少搞公私合营”的工作方针,州委决定对藏族流动小商贩,采取“暂不登记,也不改造”的政策措施。同时对外来小商贩尊重本人意见,准许其回原籍或留在当地经商。对农、商兼顾者,实行'‘采取自愿,区别对待”的办法。到1956年6月,全州参加私改的工商业者共有1114户,11,839人,组成了5个公私合店商店,34个合作商店,477个经销、代销点和个体商店。全州私改后,商业日益繁荣,营业额和利润都呈上升趋势,公积金和公益金开始逐渐积累,职工的工资也有明显增加。1958年全州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各县均把公私合店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经店小组并入国店商业,全体职工被吸收进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这样,完全实现了把私店工商业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经验与启迪
回顾甘南藏区农业、畜牧业和私店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始末,经历了一段复杂、曲折而又艰难的历程。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也是完全必要的,它为以后甘南的社会经济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三大改造中,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而辉煌的,但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特别是经过“文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逐步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各族人民相继在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率领下,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寻求,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艰苦拼搏,开扌石创新,尽快完成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联系甘南藏区三大改造的实践过程,应从四个方面汲取有益的经验和启迪。
第一,在政治路线上,甘南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过程中,最初于1956年底以前贯彻执行“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在农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符合甘南实际的,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但从1957年起,甘南受全国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后,党的主导思想改变了“八大”提出的“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正确论断,没有及时地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是提出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反右倾”、“查保守”、“拔白旗”等错误的方针政策及做法。以致在1958年的平叛反封建斗争中,出现严重扩大化的偏差,也导致了在往后的“文革"中,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打倒一切”的重大失误,随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广大干部和农牧民的爱国热情,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甘南的局部农牧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丧失了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土地荒芜,牲畜大量死亡,农牧业生产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贫苦不堪。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甘南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同样受全国大气候的制约和影响,在进程和速度上犯了“急性病”的失误,盲目追求“高指标”、“高标准”、“高速度”,讲求“一大、二公、三纯”,认为“越大越好”、“越大越纯”、“越大越体现社会主义"。在建社和私管工商业的改造中,一味追求数多、量广。有的地方给下级“下指标”、“定任务”,搞“突击建社”和“突击过渡”。有的互助组和初级社成立后,没有经过一个农牧业生产的完整周期,在两三个月内就过渡到高级社或人民公社,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速度太快、太猛。畜牧业纯粹由个体经济“一步登天”地全部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根本没有一个由低级到初级再到高级的实践、巩固、总结、提高过程。这样,既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又让人们在认识上无法理解和接受,更谈不上取得何种经验。在建社规模上,一般一个公社最后达到300〜500户之间,有的甚至把两三个乡(镇)合并成1个人民公社。这种单一的、大规模的经济格式和农牧业综合经济结构体制,一方面极不便于加强组织领导和管理,另一方面扼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起到了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
第三,在基础理论的宣传教育上,当时人们的认识还存在着历史的局限,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界限,给大家在概念上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个体私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三大改造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为了消灭个体和私有经济,而没有把它看成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在''文革”中把个体私有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从各行各业中全部割掉了。人为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不但使全州城乡农牧区集市贸易荡然无存,而且使广大农牧民陷于长期收入低下,生活极满贫困,国民经济倒退或停滯不前的困境。同时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我们完成三大改造后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只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低级或初级阶段,离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还相距甚远。
第四,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甘南藏区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1957年以后的历程中,违犯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等原则。形而上学当道,主观臆断横行,行政命令代替正确的方针政策,不顾甘南的州情、县情、乡情和民情,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内地的一些做法,既脱离甘南当地的实际,又违背农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在畜牧业生产中,改变了“分群放牧”的传统方式,片面推广“大群放牧”、“集中饲养”的不适当做法。致使畜群过大后,牛羊吃不饱,夏季抓不上膘,往往在来年冬春季节遭受雪灾后,渡不过“春乏关”,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这些都是值得注意和汲取的历史经验。
二、整风反右派斗争
自党的"八大“提出全党整风后,1957年4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这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点是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强调这次整风是一次严肃认真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一般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组会、座谈会的方式进行,不开批评大会或群众性的斗争大会。到1957年5月,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基本上是诚恳而正确的。但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这次整风的机会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的进攻。据此,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敌对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当时,甘南的整风反右派斗争,也是在全国的这种大氛围的制约和影响下进行的。仅1957年和1958年两年中,全州划定右派分子392人,绝大多数是文教卫生和科研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国,反抗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也确实存在,但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使反右派斗争愈来愈扩大化了。1957年6月,中央指示全国右派中需要点名批判的大约4000人,10天之后,人数扩大了一倍。8月,中央要求运动进一步在全国的县、市(区)、大厂矿和中小学教职工中展开,要深入“挖掘右派”。9月,全国共划定右派6万余人,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达55万人。并从政治上判定右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与此同时,甘南的反右派斗争在后期是与1958年的平叛反封建斗争交织进行的,特别是在1958年下半年进行了一次“反右补课”,并将反右斗争延续到1966年。10年间,全州共划定右派444人,其中:1957年和1958年划定392人,占总数的88%;从1957年到1965年划定47人,占10.6%;1966年以后划定5人,占1.4%。这样,甘南在长达10年时间的反右派斗争中,无论从数量、性质和方式方法上,都导致了这场斗争的延续扩大化。
和风细雨式的整风
1957年5月,州委根据省委关于“在牧区整风主要是检查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多征求民族上层和当地民族干部意见”的指示精神,对全州的整风运动作了具体的安排部署。首先,州委召开扩大会议,对甘南如何进行整风运动进行讨论研究,统一认识,明确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政策及方法措施。其次,为加强对整风的领导,州委成立了由谢占儒、董宏杰、王如东、李加夫(军)、马宗瀛、香巴才仁、杨培发、马学海、张文献9名领导同志组成的整风领导小组。各县委也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三是确定了甘南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其表现在民族问題上的大汉族主义;检查民族关系、党内外关系、汉族干部与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党与民族宗教上层之间的关系,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检查党的民族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检查领导与群众和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问题。根据甘南的具体情况,州委决定全州的整风运动分三批穿插进行。具体安排是:第一批先在州级(包括军分区)单位的各党组织內开展整风运动,取得经验,予以推广,各县不搞试点。从1957年5月15日开始到10月底结束。第二批在临潭、舟曲、卓尼、夏河4个县的县级机关进行,从1957年11月初开始整风,到1958年2月底结束。第三批在临潭、舟曲、卓尼、夏河4个县的区、乡及碌曲、玛曲两个县进行,从1958年9月初开始到12月底结束。
甘南州、县的整风运动共分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是学习文件阶段。首先组织广大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学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其次由各单位领导根据个人的学习心得和体会,结合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向全体干部作3至5次的辅导报告。临潭、卓尼、夏河、舟曲4个县,在整风中除了学习规定的文件外,还学习有关农业合作化的办社文件等。通过学习文件,提高广大干部对整风的认识,解除顾虑。第二是广泛征求和听取意见阶段。主要通过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让各族各界人士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畅所欲言,广开言路,鼓励批评和提意见。第三是边整、边改阶段。州、县严格遵照省委关于“边学习、边检查、边改正”的指示精神,把整风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对群众提的批评和意见,分类排队,梳成“辫子”,认真研究讨论,做到及时解决。如在半农半牧区着重解决农、牧矛盾问题,在农业区重点解决干群关系等。第四个阶段是严格掌握政策,认真处理整风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一是对已作了处理和改正的个人历史问题,概不追究。二是不纠缠琐碎的生活细节问题,以免发生混乱。三是在运动中发现个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行为时,一律交公安部门侦处,不和整风绞在一起。五是对一般少数民族党员,在检查时不要求太严。对牧区的少数民族党员,只进行有关文件和民族政策的学习,不作检查。六是对非党员干部愿意参加整风的应积极欢迎,并允许他们随时退出。七是对在整风中检查出犯了错误的人,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槪不给予组织处分,并耐心帮助教育他们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八是对在整风中发现的少量贪污问题,尽量帮助其自动交待,退出赃款,一般不给处分。由于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的正确,甘南的第一批整风基本上是平稳健康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敌我矛盾性质的反右派斗争
从1957年8月后,随着全国整风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发展,甘南的整风开始转向反击右派,并逐渐发生了扩大化的倾向,特别是在所谓的“大鸣”、“大放”、“大民主”中,增加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内容,延续到1958年的平叛反封建斗争,两者交错起来进行,矛盾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有的县还在1959年重新进行了“反右补课”。
甘南的整风在运动刚开始时,无论在指导思想和方法步骤等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后来由于受全国整风反右大气候的制约和影响,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偏差。当时,全州各部门及所属单位,召开党内外干部座谈会,号召和引导大家以“大鸣、天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州政协、州委统战部等部门还召开 “神仙会”,即:邀请合作地区的民族宗教人士、工商界的中上层人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会议,鼓励他们向党和政府献计献策,提批评意见。当时许多人出于对党的热爱,提了不少批评意见和建议。但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却曲解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而夸大其辞,无限上纲,把他们视为“右派的进攻”应进行反击,并组织人员内查外调,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以往的发言记录。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同时进行无休止的批判斗争。这样,使运动的矛头由党内转移到了党外,由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整风,迅速转变为敌我矛盾性质的反右派斗争。刹时,那些曾真心诚意向党提出过批评或建议的同志,昼夜之间就被打成了 “右派分子”。截止1958年10月底,州、县和各区、乡参加整风的干部职工共有5315人,其中:党员1548人,团员1187人,非党群众2580人。经过反右斗争共划定“右派分子”279人,其中:州级75人,6个县204人。占全州参加整风干部总数的5.25%。其中党员中右派41人,团员中右派47人,一般干部职工中的右派19人。特别在州直机关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75人中,有州委副书记香巴才仁(藏)、副州长王如东和段耀、卢世义(藏)、韦应文、陆吉庆、兰文选(藏)、刘敏学6位中级干部,使全州和部分部门的工作及个人在政治上、生活上蒙受了很大损失。到1962年后,这些人才被甄别平反,重新恢复了领导工作。
在整风反右中,甘南通过“大鸣”、“大放”,揭示出来的绝大多数问题是正确的,对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全州共提出各种意见20,908条,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单位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工作互相推诿、扯皮;有的单位领导闹不团结;有些部门文件报表繁多;有的领导侧重于开会,发指示,很少到第一线具体指导工作。二是有的领导干部骄傲自满,官僚主义严重,对违纪干部长期不作处理。如临潭县联社的干部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者达12人,占该社职工总数的9.8%,贪污现金达2万元。还有该县粮食科有几位职工严重失职,造成大量粮食被盗和霉烂。三是浪费现象普遍严重。如州商业处附设门市部,因盲目进货使商品滞销,积压货款达10.7万元;州食品公司高价收购牛羊960头(只),仅此一项亏损4469元。州邮电局不就地购材而从东北调来木头,多开支4万多元。四是在粮食问题上丰收年景没有做到多购多收,储备一定的存粮,还销售了部分储备粮。五是在财政收支上有大手大脚的花钱现象,该收的稅没有收上来,而不该支的项目却开支了。针对这些问题,州委、州人委遵照“边整、边改”的原则,进行彻底整顿和处理。但对一些带有片面性或过激的言论,并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却视之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炮弹”。还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现实和理论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设想,即使方向上有偏差,也应该通过讨论和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不应该当作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以打击。还有的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政治历史上有些问题或生活作风方面犯有一定错误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极大地伤害了一部分干部职工的感情,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整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后果及平反改正
通过整风反右派斗争,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大鸣大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这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的”。事实证明整风反右的烈火,不但烧掉了 “敌人”,而且烧掉了各级干部中的 “三风",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此外,在甘南州划定“右派分子”时,由于受全国极“左”思潮的影响,犯了扩大化的失误,使不少对党和革命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族宗教和各界人士朋友,不少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上热情高而不够成熟的青年,在这场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蒙受了长期的冤屈和压抑,未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巨大损失。这一点特别在本来就十分缺乏人才的甘南,就显得更为突出。由于反右派扩大化的后果,从而使更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这是党和国家的政治损失,也是建国后党的历史上应该汲取的一个深刻教训。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州委、州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揭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肃清极“左”流毒和影响,全面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干部政策。1978年4月,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为被错划者平反。截止1979年底,甘南对从1957年至1966年10年间所划定的444名右派分子,除6人维持原定性结论外,其余438人均作了平反改正,其中:1962年前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112人;1979年平反改正326人。在这些平反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员中,重新恢复公职、安置工作的173人;享受退休、退职待遇的11人。对受株连的家属安置工作的有3人。恢复城镇戶口和粮食关系的24户,共计211人。在改正右派后恢复党籍的有21人,承认预备党员资格的9人,解决1962年遗留问题的2人。对州直机关单位原划定的132名“右派分子”,除1962年后改正的41人外,这次对91人全部作了平反改正。州委在改正右派工作结束后,又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政策,使过去长期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受到压抑的同志卸下包袱,重新振奋精神,投身到为甘南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洪流中,发挥他们的余热和重要作用。
三、河南支建青年到甘南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甘肃、河南两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经过两省领导的磋商,决定在甘南安置15万名河南支建青年。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12月底,共有41,697名河南青年来到甘南。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辛勤劳动,艰苦创业,为建设甘南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到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迫使31,000多名青年离开甘南,自动返回河南。留下1万名左右的青年仍然在甘南这块热土上,艰苦拼搏,默默奉献,为甘南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安置
当时,州委、州政府对河南支建青年的到来非常重视,作出具体的安排和部署。一是州、县成立了由一名副书记或党员副州长、副县长负责的接待办公室,配备3至5名工作干部。二是在兰州、陇西火车站设置食宿站,派专人负责接待工作。三是在德乌鲁市(夏河)、洮江(碌曲、玛曲)、临潭(卓尼)、龙迭(迭部、舟曲)4个县(市),建立了24个工、农、牧安置点。四是明确规定,支建青年到来后安置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单位。五是向甘南各族人民,积极宣传支建工作的政治、经济和国防意义。六是发动群众给支建青年筹备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住房等。全州共解决生产工具13,610件,生活用具40,733件,住房8620间,耕畜3898头。甘肃、河南两省的有关部门也对安置支建青年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援助。甘肃省计委调拨钢材30吨、柴油28吨、油桶116个;省农业厅下拨拖拉机80台、农机具298件,蔬菜种子8796公斤;省商业厅拨发胶轮大车44辆、架予车210辆,中小型生产工具7913件,灶具和生活用具5974件,棉布59,078米;兰州军区配备了26名军官和一部分枪支弹药;省卫生部门抽调了医生和大批医疗器械。河南省多次派出工作组到甘南深入各,点进行慰问,同时还支援小型生产工具1万余件,蔬菜籽种2000多公斤。
1958年11月28日,首批750名河南支建青年抵达甘南,受到党政军负责人和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及各族群众的夹道欢迎与热情接待。到1959年底时,全州相继安置河南支建青年41,697名,其中:男性30,836人,女性10,861人。年龄在25岁以下的有35,917人,占总数的86.1%。有党员1846人,团员8451人,党团员占总数的24%。具体安置结果是:各国营农场24,946人,占总数的59.8%;州内地方厂矿企业8203人,占20%;白龙江和洮河林业局7118人,占17%;玛曲渔场1430人,占3.2%。随迁的国家干部141名,其中:县级4人,区级33人,一般104人。他们都被安排在各国营农牧场担任领导工作。
创业
党和政府的关怀及全州各族人民的鼎力支持,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支建青年的劳动积极性,他们在各条战线上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在农业战线上,全州于1959年春建立的14个国营农场的17,344名职工,认真贯彻“边建场、边开荒、边生产、边积累、边扩大”的生产方针,到1959年12月底,累计开垦荒地约10,765公顷,播种3535公顷。其中:粮食作物约1994公顷,当年总产粮食280多万公斤;油料作物约1274公顷,总产油籽61.5万多公斤;种甜菜约67公顷,收获64万公斤;种蔬菜约153公顷,总产117万公斤;种饲料约313公顷,收牧草36.5万公斤。1959年达到粮油自给自足的农场有3个,占春季投入生产14个农场的16.6%;半自给自足的有3个,占总数的16.6%。两者合计达到了33.2%。在畜牧业战线上,1959年底各农牧场共有牛4068头,马491匹,羊3715只,猪2653头。在基本建设方面,到1959年底,各农牧场修建房屋4万多平方米,修建水、旱磨107盘。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使灌溉面积达到约6136.4公顷。在工业战线上,广大支建青年在设备简陋、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忘我工作,大胆革新,推动了生产的迅猛发展。如龙迭县建材厂,原来只有40余名职工,劳力严重不足,在安置了198名有文化、有技术的支建青年后,生产如虎添翼,在两个月内,产值猛增了47.7%。在林业战线上,安置在白龙江和洮河林业局的7000多名支建青年,起早贪黑地奋战在深山老林中,截止1959年10月底,共砍伐木材34.9万立方米,抚育幼林33多公顷,生产烤胶60余吨,修建林区公路80多公里,为国家完成了7100多万元的生产任务。
广大支建青年在勤奋的生产劳动中,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竞赛热潮,涌现出了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同时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进步和锻炼。到1959年底,有52名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93名青年入了团,还有378优秀青年被选送到州外各类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去深造。被选为省、州、县各级党代会、团代会、妇代会和人代会代表的有277人,同时还评选出优秀红旗手和先进工作者1119人,选出红旗单位96个。
返乡
1960年春,由于受全国"大跃进”思潮的影响,甘南改变了“以牧为主”的方针,提出“高速度发展农业”的口号,给全州18个国营农牧场下达“巩固和发展国营农牧场,大力开垦荒地,高速度发展农业,并积极地发展畜牧业和其他多种经营,实现'六自给,(粮、油、肉、菜、饲料和经费)和'四有余,(粮、油、菜、经费)”的生产任务。计划开垦荒地约52,026公顷,连同原有的约9338公顷耕地总数达到62,698公顷,职工人均占有约2.53公顷。为完成这个目标任务,18个国营农牧场组成两万多人的开荒大军,在一年内就地垦荒约18,209公顷,绝大部分是畜牧业草场。同时不顾当地均是3000米以上的高寒山坡地和气候十分恶劣的自然条件,当年播种各类农作物约22,678公顷,比1959年增长了6.8倍。其中:粮食作物约12,206公顷,但年终总产只有208万公斤粮食,平均亩产11.5公斤,连种子都没收回;种油籽约9672公顷,总产27万公斤,平均亩产1.85公斤,几乎是颗粒无收。
农业生产的大欠收,使广大职工的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有的不仅没有吃的油、盐、菜,而且断粮现象频繁发生。日趋严酷的生活形势,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生存,迫使大量支建青年偷跑回家,自动返回河南。到1961年底,全州返乡的农牧场职工达15,562人,其中:请假未归的2366人,偷跑回老家的13,196人。两者占安置总数的37.4%。对此,州委、州政府在进行全面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审时度势,作出“与其开小差和请假不回,不如公开登记,有组织的送回原籍为好”的决定。截止1962年元月30日,分十批(每批1500人)将愿意回河南的支建青年送回老家。全州总共送返的支建青年约3.1万多人。18个农牧场撤销后留下的约1万余人,全州统一调配,安排新的工作岗位。
后记
河南青年支援甘南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艰辛的过程,其方向是对的,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较大失误。特别是在人类赖以生存、生产和生活条件极差的甘南藏区,短期内迁徙4万多名青年,易地繁衍生息和生活,还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长期以来,在科技文化生产力水平都很落后的甘南,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或"靠天养畜”。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左”倾思潮的干扰,使这项工作半途而废,也造成了不良后果。这是个应该汲取的深刻教训。然而,当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课题下,正是通过前辈们艰苦地拼搏和探索,才使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摒弃失误,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当年河南支建青年那种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僻远的地区去创业奋斗,开扌石拼搏,'‘敢为天下先”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树立和赞扬的。
嗣后,留在甘南工交、林业等战线上近万名左右的河南支建青年,30余年来,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厂房、养路道班和茫茫林海之中,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学习,辛勤劳动,为甘南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30多年来为国家经济建设累计提供了665万多立方米的木材和大量林副业土特产品,总产值达10.9亿多元。工交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日夜守护在兰郎公路和喉夏公路上,全长520多公里,他们顶风雪,冒严寒,长年坚守在高原道班上,为保障甘南交通运输的畅通无阻,铺路架桥,栉风沐雨,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所开创的业绩,将伴随着甘南州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而载入史册。
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始末
20世纪50年代,随着我国“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甘南藏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国民经济体制从私有制到全民所有制和劳动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转变,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模式,创造了一系列由低级到初级再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从而使甘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较大成就。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甘南总土地面积388万公顷中,有耕地约68701公顷,占总土面积的1.78%。常年农作物面积在53,360公顷上下。1949年甘南解放初,有农村人口25.8万人,有农业劳动力15万余人。除玛曲、碌曲不种植农作物外,夏河、卓尼是半农半牧区,临潭、西固(舟曲)是农业区。长期以来,甘南在建国前后,境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共有四种形式:一是以夏河为主的喇嘛教寺院土地所有制。大部分土地被寺院占有,全部以出租的形式让当地藏族农民耕种,定期交纳租粮。如夏河拉卜楞镇及附近13庄的土地,基本上属于拉卜楞寺所有。二是土司土地所有制。从元、明朝开始,杨土司在其管辖的卓尼、迭部和舟曲的南部境内,即在总面积为3万多平方公里、拥有3.5万户、近10万人的地域内,所有土地全是杨土司的。群众耕种的土地是"兵马田地”和寺院的“僧田”。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三是西道堂土地所有制。临潭的西道堂从1890年创建以来,既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独立派别,又是集农、工、商、贸、林、牧、副业为一体的经济群体。西道堂的一切财产归集体所有。当时拥有耕地约662公顷。四是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主要存在于临潭县境内。当时,占临潭县农村总人口18.4%的地主占有耕地8.8%,约有1618公顷,人均约1.2公顷。
解放初,甘南各级党政组织遵照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对拉卜楞寺教区、西道堂和杨土司的辖区及广大藏族聚居的半农半牧区,均采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对其土地制度基本保持不变。而在农业区,甘南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20世纪50年代里,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土地改革运动。自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后,甘南藏区先在临潭、西固县的一些农业乡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52年春,遵照省委关于民族地区坚决贯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首先在临潭县的扁都乡和西固县的沙湾乡,进行土改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然后派出10多支土改工作组,分期分批地全面进行土改运动。给9801户贫苦农民分配土地约2430公顷。
二是组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互助组。1950年卓尼新堡区 (今藏巴哇乡)4户农民,在罗进荣的带领下,组成新联互助组。1951年2月转为常年互助组。接着又有5户农民组成了友爱互助组。1952年春,夏河县二区三乡的3户农民成立了尕道光互助组。这些都是在甘南最早出现的、农民自发组建起来的农业互助合作生产形式。1951年9月,党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向全国农民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甘南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中央的《决议》精神,提出“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以各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变工队、互助组。到1953年春天,在甘南各县农村共建立农业互助组3533个,参加农户达12,129户,占总农户的57.4%。其中:常年互助组274个,季节性互助组3259个。这些互助组连年增产,比单干的农户亩产高出20公斤左右。
三是成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春,党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是年9月,工委贯彻执行《决议》精神,首先在临潭县扁都乡和西固县的坪定乡试办了两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典型,总结摸索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1954年2月,全州试办了临潭扁都乡由12户农民组成的哈尕滩初级社和舟曲坪定乡由13户农民组成的坪定初级社。同年10月,工委决定在农业区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号召和教育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到1954年底,全州共办初级农业社11个。1955年底,全州初级社达99个。到1956年12月底,全州农业区共建初级农业社398个,入社农户达2.1万户,占总农户的89.2%。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初级合作化。
四是转建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5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把全国的合作化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甘南的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掀起迅猛发展的热潮,各地把短期内办起的初级社很快转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截止1956年12月,全州已转高级社176个,入社农户20,407户。到1957年底时,全州高级社达到195个,入社农户25,392户,占总农户的90.5%。这样,基本上实现了全州农业的社会主义高级合作化。1958年春,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全州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运动,随之把农业合作化推向了顶峰。1958年8月,舟曲县率先将17个初、高级社合并为9个农村人民公社。接着临潭、夏河、卓尼3个县于9月上旬,合乡并社,全部建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州共建“政社全一”的农村人民公社47个,其中农业区人民公社20个。1959年元月全州将47个人民公社合并为35个,1960年又调整为47个。1962年合并为大公社12个,1969年又扩大为103个,直到1984年撤销时的人民公社有104个。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人民公社这种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在甘南的国民经济里始终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二)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元月,全省第二次牧区工作会议后,党在甘南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政策,通过牧业走互助合作化道路,逐步把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个体经济,改造成为国家所有制和牧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从1956年上半年起,党和政府提出《关于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意见》,首先在夏河、碌曲、玛曲、卓尼4个县分别召开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会议,对牧区开展互助组的时间、步骤和具体方法,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经过省、州、县召开的专题会议,在甘南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掀起大力宣传互助合作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潮。州委抽调200名党政干部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组成工作团,下设3个分团,分赴卓尼、夏河、碌曲、玛曲等县,深入牧区帐圈,广泛宣传互助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党对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通过各种方式说服教育有顾虑的大小部落头人,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解除顾虑。半年之内,很快在夏河、卓尼两县办起了170个以牧民个体经济为基础的牧业互助组。碌曲县也在牧民历来“联群放牧”的基础上,经过加强领导和完善管理制度,组成了12个互助组。
1956年下半年,州委、州政府认真贯彻全省第三次牧区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出:“牧区今后必须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稳步发展畜牧业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现有的互助组、合作社进一步加强领导,进行整顿。对纯牧区和以牧为主的地方,一般暂不发展合作社,个别确已具备办社条件的,须经州委批准后方能建社,尽量减少盲目性。1957年初,州委作了《关于发展畜牧业的十年规划》,提出对全州畜牧业经济改造在10年内完成的设想。即卓尼、夏河两个县在1966年建成高级牧业生产合作社,碌曲、玛曲两个县在1967年达到高级牧业生产合作社。到1965年以前,把牧主经济纳入公私合营牧场或国营牧场、合作牧场,用吸收其加入合作社等办法完成对牧主经济的改造。同时决定在卓尼、夏河两个县进行试办。夏河县选择了有3年创办互助组经验的三区麻当村进行试点。州、县、乡派出联合工作组,很快办起了全州第一个有藏、汉、回3个民族农户参加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联社。卓尼县在135个牧业互助组的基础上,建起了6个全州首批牧业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下半年,受全国、全省蓬勃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影响,甘南牧区也开始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从而加快了甘南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主导思想上放弃“慎重、稳进”的方针。有的牧业初级社成立不到一年,就扩建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有的初级社在筹建中,就一次性地建为高级社。到1958年1月,卓尼全县实现了高级社化,共建高级社314个,其中牧业高级社58个。夏河县的一、二、三、四区(均为半农半牧区)基本上实现了农牧业的初级合作化。1958年下半年,洮江(包括今碌曲、玛曲两地的纯牧区)县及全州结合反封建斗争,根据全体广大农牧民的要求和愿望,于9月15日一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建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47个(其中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27个)。这样,在短短的10多天中,甘南的畜牧业“一步登天”,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甘南由一个带有奴隶制残余痕迹的封建社会直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完成了个体畜牧业经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民主革命任务。
(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6月,党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确定经过国家资本来改造资本主义的工业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形成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也就是实施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
解放前,甘南藏区的商业主要集中在临潭、夏河、卓尼、西固4个县境内的少数集镇。夏河县很早就是安木多藏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逐渐出现了牛、羊、马和皮毛畜产品及民族用品等交易市场,并围绕拉卜楞寺教区形成物资交易中心。临潭新城古有“茶马互市”的商业贸易,是汉、回、藏贸易的重要商阜和集散地。洮河流域随着木材的大量交易,也产生了一些加工木器家具和畜产品及金银手饰、铁铜器皿的手工作坊。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和发展民族贸易,将价廉物美的民族必需品送到广大农牧民手中,又把群众手中的牛羊皮毛肉等畜产品收购上来。购销公平、买卖合理,进一步促进和繁荣了民族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往后,夏河县的集市贸易发展成以拉卜楞寺为主体的寺院贸易,寺院几乎垄断了土特产和畜产品市场。临潭县发展成以西道堂为龙头的对内地辐射的商业贸易。党和政府为繁荣城乡经济,发展民族贸易,一方面保护、扶持个体商贩,定期举办各种物资交流大会。另一方面大力招引内地商贾和商行来甘南进行贸易,提高商品交流的贸易额。使个体私人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50年,甘南共有私营工商业1551户,从业人员2243人,拥有资金107万元。到1954年12月底,私营工商业发展到2805户,从业人员达3800人,拥有资金144万元。
当时,甘南的私营工商业者大多资本小,设备陈旧,货源稀疏,渐感经管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这样,1955年11月党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颁布后,甘南州于1956年1月召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会议,各县相继成立了“私改”办公室。首先,对城乡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调查和摸底。据统计,1956年春全州城乡共有私商1578戶,从业人员2243人,拥有资金166万元。其中农村乡镇有私商247户,从业人员411人,拥有资金66万元。其次,以夏河、临潭两个县为重点,大力宣传党的私改政策,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和登记工作。三是认真开展清产核资。本着自报公议的原则,呈报行业工作委员会审核,并提出意见后通过从业者定价。当时,因受内地公私合营运动的影响,甘南的私改进展很快。遵照省委对民族地区提出的 “统筹兼顾”、“重点改造”、“典型示范"、“多搞经销代销,少搞公私合营”的工作方针,州委决定对藏族流动小商贩,采取“暂不登记,也不改造”的政策措施。同时对外来小商贩尊重本人意见,准许其回原籍或留在当地经商。对农、商兼顾者,实行'‘采取自愿,区别对待”的办法。到1956年6月,全州参加私改的工商业者共有1114户,11,839人,组成了5个公私合店商店,34个合作商店,477个经销、代销点和个体商店。全州私改后,商业日益繁荣,营业额和利润都呈上升趋势,公积金和公益金开始逐渐积累,职工的工资也有明显增加。1958年全州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各县均把公私合店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经店小组并入国店商业,全体职工被吸收进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这样,完全实现了把私店工商业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经验与启迪
回顾甘南藏区农业、畜牧业和私店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始末,经历了一段复杂、曲折而又艰难的历程。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也是完全必要的,它为以后甘南的社会经济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三大改造中,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而辉煌的,但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特别是经过“文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逐步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各族人民相继在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率领下,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寻求,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艰苦拼搏,开扌石创新,尽快完成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联系甘南藏区三大改造的实践过程,应从四个方面汲取有益的经验和启迪。
第一,在政治路线上,甘南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过程中,最初于1956年底以前贯彻执行“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在农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符合甘南实际的,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但从1957年起,甘南受全国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后,党的主导思想改变了“八大”提出的“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正确论断,没有及时地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是提出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反右倾”、“查保守”、“拔白旗”等错误的方针政策及做法。以致在1958年的平叛反封建斗争中,出现严重扩大化的偏差,也导致了在往后的“文革"中,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打倒一切”的重大失误,随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广大干部和农牧民的爱国热情,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甘南的局部农牧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丧失了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土地荒芜,牲畜大量死亡,农牧业生产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贫苦不堪。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甘南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同样受全国大气候的制约和影响,在进程和速度上犯了“急性病”的失误,盲目追求“高指标”、“高标准”、“高速度”,讲求“一大、二公、三纯”,认为“越大越好”、“越大越纯”、“越大越体现社会主义"。在建社和私管工商业的改造中,一味追求数多、量广。有的地方给下级“下指标”、“定任务”,搞“突击建社”和“突击过渡”。有的互助组和初级社成立后,没有经过一个农牧业生产的完整周期,在两三个月内就过渡到高级社或人民公社,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速度太快、太猛。畜牧业纯粹由个体经济“一步登天”地全部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根本没有一个由低级到初级再到高级的实践、巩固、总结、提高过程。这样,既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又让人们在认识上无法理解和接受,更谈不上取得何种经验。在建社规模上,一般一个公社最后达到300〜500户之间,有的甚至把两三个乡(镇)合并成1个人民公社。这种单一的、大规模的经济格式和农牧业综合经济结构体制,一方面极不便于加强组织领导和管理,另一方面扼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起到了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
第三,在基础理论的宣传教育上,当时人们的认识还存在着历史的局限,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界限,给大家在概念上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个体私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三大改造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为了消灭个体和私有经济,而没有把它看成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在''文革”中把个体私有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从各行各业中全部割掉了。人为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不但使全州城乡农牧区集市贸易荡然无存,而且使广大农牧民陷于长期收入低下,生活极满贫困,国民经济倒退或停滯不前的困境。同时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我们完成三大改造后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只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低级或初级阶段,离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还相距甚远。
第四,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甘南藏区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1957年以后的历程中,违犯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等原则。形而上学当道,主观臆断横行,行政命令代替正确的方针政策,不顾甘南的州情、县情、乡情和民情,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内地的一些做法,既脱离甘南当地的实际,又违背农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在畜牧业生产中,改变了“分群放牧”的传统方式,片面推广“大群放牧”、“集中饲养”的不适当做法。致使畜群过大后,牛羊吃不饱,夏季抓不上膘,往往在来年冬春季节遭受雪灾后,渡不过“春乏关”,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这些都是值得注意和汲取的历史经验。
二、整风反右派斗争
自党的"八大“提出全党整风后,1957年4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这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点是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强调这次整风是一次严肃认真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一般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组会、座谈会的方式进行,不开批评大会或群众性的斗争大会。到1957年5月,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基本上是诚恳而正确的。但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这次整风的机会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的进攻。据此,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敌对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当时,甘南的整风反右派斗争,也是在全国的这种大氛围的制约和影响下进行的。仅1957年和1958年两年中,全州划定右派分子392人,绝大多数是文教卫生和科研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国,反抗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也确实存在,但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使反右派斗争愈来愈扩大化了。1957年6月,中央指示全国右派中需要点名批判的大约4000人,10天之后,人数扩大了一倍。8月,中央要求运动进一步在全国的县、市(区)、大厂矿和中小学教职工中展开,要深入“挖掘右派”。9月,全国共划定右派6万余人,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达55万人。并从政治上判定右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与此同时,甘南的反右派斗争在后期是与1958年的平叛反封建斗争交织进行的,特别是在1958年下半年进行了一次“反右补课”,并将反右斗争延续到1966年。10年间,全州共划定右派444人,其中:1957年和1958年划定392人,占总数的88%;从1957年到1965年划定47人,占10.6%;1966年以后划定5人,占1.4%。这样,甘南在长达10年时间的反右派斗争中,无论从数量、性质和方式方法上,都导致了这场斗争的延续扩大化。
和风细雨式的整风
1957年5月,州委根据省委关于“在牧区整风主要是检查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多征求民族上层和当地民族干部意见”的指示精神,对全州的整风运动作了具体的安排部署。首先,州委召开扩大会议,对甘南如何进行整风运动进行讨论研究,统一认识,明确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政策及方法措施。其次,为加强对整风的领导,州委成立了由谢占儒、董宏杰、王如东、李加夫(军)、马宗瀛、香巴才仁、杨培发、马学海、张文献9名领导同志组成的整风领导小组。各县委也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三是确定了甘南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其表现在民族问題上的大汉族主义;检查民族关系、党内外关系、汉族干部与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党与民族宗教上层之间的关系,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检查党的民族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检查领导与群众和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问题。根据甘南的具体情况,州委决定全州的整风运动分三批穿插进行。具体安排是:第一批先在州级(包括军分区)单位的各党组织內开展整风运动,取得经验,予以推广,各县不搞试点。从1957年5月15日开始到10月底结束。第二批在临潭、舟曲、卓尼、夏河4个县的县级机关进行,从1957年11月初开始整风,到1958年2月底结束。第三批在临潭、舟曲、卓尼、夏河4个县的区、乡及碌曲、玛曲两个县进行,从1958年9月初开始到12月底结束。
甘南州、县的整风运动共分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是学习文件阶段。首先组织广大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学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其次由各单位领导根据个人的学习心得和体会,结合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向全体干部作3至5次的辅导报告。临潭、卓尼、夏河、舟曲4个县,在整风中除了学习规定的文件外,还学习有关农业合作化的办社文件等。通过学习文件,提高广大干部对整风的认识,解除顾虑。第二是广泛征求和听取意见阶段。主要通过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让各族各界人士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畅所欲言,广开言路,鼓励批评和提意见。第三是边整、边改阶段。州、县严格遵照省委关于“边学习、边检查、边改正”的指示精神,把整风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对群众提的批评和意见,分类排队,梳成“辫子”,认真研究讨论,做到及时解决。如在半农半牧区着重解决农、牧矛盾问题,在农业区重点解决干群关系等。第四个阶段是严格掌握政策,认真处理整风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一是对已作了处理和改正的个人历史问题,概不追究。二是不纠缠琐碎的生活细节问题,以免发生混乱。三是在运动中发现个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行为时,一律交公安部门侦处,不和整风绞在一起。五是对一般少数民族党员,在检查时不要求太严。对牧区的少数民族党员,只进行有关文件和民族政策的学习,不作检查。六是对非党员干部愿意参加整风的应积极欢迎,并允许他们随时退出。七是对在整风中检查出犯了错误的人,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槪不给予组织处分,并耐心帮助教育他们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八是对在整风中发现的少量贪污问题,尽量帮助其自动交待,退出赃款,一般不给处分。由于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的正确,甘南的第一批整风基本上是平稳健康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敌我矛盾性质的反右派斗争
从1957年8月后,随着全国整风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发展,甘南的整风开始转向反击右派,并逐渐发生了扩大化的倾向,特别是在所谓的“大鸣”、“大放”、“大民主”中,增加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内容,延续到1958年的平叛反封建斗争,两者交错起来进行,矛盾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有的县还在1959年重新进行了“反右补课”。
甘南的整风在运动刚开始时,无论在指导思想和方法步骤等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后来由于受全国整风反右大气候的制约和影响,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偏差。当时,全州各部门及所属单位,召开党内外干部座谈会,号召和引导大家以“大鸣、天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州政协、州委统战部等部门还召开 “神仙会”,即:邀请合作地区的民族宗教人士、工商界的中上层人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会议,鼓励他们向党和政府献计献策,提批评意见。当时许多人出于对党的热爱,提了不少批评意见和建议。但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却曲解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而夸大其辞,无限上纲,把他们视为“右派的进攻”应进行反击,并组织人员内查外调,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以往的发言记录。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同时进行无休止的批判斗争。这样,使运动的矛头由党内转移到了党外,由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整风,迅速转变为敌我矛盾性质的反右派斗争。刹时,那些曾真心诚意向党提出过批评或建议的同志,昼夜之间就被打成了 “右派分子”。截止1958年10月底,州、县和各区、乡参加整风的干部职工共有5315人,其中:党员1548人,团员1187人,非党群众2580人。经过反右斗争共划定“右派分子”279人,其中:州级75人,6个县204人。占全州参加整风干部总数的5.25%。其中党员中右派41人,团员中右派47人,一般干部职工中的右派19人。特别在州直机关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75人中,有州委副书记香巴才仁(藏)、副州长王如东和段耀、卢世义(藏)、韦应文、陆吉庆、兰文选(藏)、刘敏学6位中级干部,使全州和部分部门的工作及个人在政治上、生活上蒙受了很大损失。到1962年后,这些人才被甄别平反,重新恢复了领导工作。
在整风反右中,甘南通过“大鸣”、“大放”,揭示出来的绝大多数问题是正确的,对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全州共提出各种意见20,908条,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单位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工作互相推诿、扯皮;有的单位领导闹不团结;有些部门文件报表繁多;有的领导侧重于开会,发指示,很少到第一线具体指导工作。二是有的领导干部骄傲自满,官僚主义严重,对违纪干部长期不作处理。如临潭县联社的干部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者达12人,占该社职工总数的9.8%,贪污现金达2万元。还有该县粮食科有几位职工严重失职,造成大量粮食被盗和霉烂。三是浪费现象普遍严重。如州商业处附设门市部,因盲目进货使商品滞销,积压货款达10.7万元;州食品公司高价收购牛羊960头(只),仅此一项亏损4469元。州邮电局不就地购材而从东北调来木头,多开支4万多元。四是在粮食问题上丰收年景没有做到多购多收,储备一定的存粮,还销售了部分储备粮。五是在财政收支上有大手大脚的花钱现象,该收的稅没有收上来,而不该支的项目却开支了。针对这些问题,州委、州人委遵照“边整、边改”的原则,进行彻底整顿和处理。但对一些带有片面性或过激的言论,并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却视之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炮弹”。还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现实和理论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设想,即使方向上有偏差,也应该通过讨论和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不应该当作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以打击。还有的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政治历史上有些问题或生活作风方面犯有一定错误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极大地伤害了一部分干部职工的感情,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整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后果及平反改正
通过整风反右派斗争,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大鸣大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这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的”。事实证明整风反右的烈火,不但烧掉了 “敌人”,而且烧掉了各级干部中的 “三风",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此外,在甘南州划定“右派分子”时,由于受全国极“左”思潮的影响,犯了扩大化的失误,使不少对党和革命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族宗教和各界人士朋友,不少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上热情高而不够成熟的青年,在这场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蒙受了长期的冤屈和压抑,未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巨大损失。这一点特别在本来就十分缺乏人才的甘南,就显得更为突出。由于反右派扩大化的后果,从而使更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这是党和国家的政治损失,也是建国后党的历史上应该汲取的一个深刻教训。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州委、州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揭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肃清极“左”流毒和影响,全面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积极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干部政策。1978年4月,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为被错划者平反。截止1979年底,甘南对从1957年至1966年10年间所划定的444名右派分子,除6人维持原定性结论外,其余438人均作了平反改正,其中:1962年前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112人;1979年平反改正326人。在这些平反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员中,重新恢复公职、安置工作的173人;享受退休、退职待遇的11人。对受株连的家属安置工作的有3人。恢复城镇戶口和粮食关系的24户,共计211人。在改正右派后恢复党籍的有21人,承认预备党员资格的9人,解决1962年遗留问题的2人。对州直机关单位原划定的132名“右派分子”,除1962年后改正的41人外,这次对91人全部作了平反改正。州委在改正右派工作结束后,又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政策,使过去长期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受到压抑的同志卸下包袱,重新振奋精神,投身到为甘南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洪流中,发挥他们的余热和重要作用。
三、河南支建青年到甘南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甘肃、河南两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经过两省领导的磋商,决定在甘南安置15万名河南支建青年。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12月底,共有41,697名河南青年来到甘南。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辛勤劳动,艰苦创业,为建设甘南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到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迫使31,000多名青年离开甘南,自动返回河南。留下1万名左右的青年仍然在甘南这块热土上,艰苦拼搏,默默奉献,为甘南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安置
当时,州委、州政府对河南支建青年的到来非常重视,作出具体的安排和部署。一是州、县成立了由一名副书记或党员副州长、副县长负责的接待办公室,配备3至5名工作干部。二是在兰州、陇西火车站设置食宿站,派专人负责接待工作。三是在德乌鲁市(夏河)、洮江(碌曲、玛曲)、临潭(卓尼)、龙迭(迭部、舟曲)4个县(市),建立了24个工、农、牧安置点。四是明确规定,支建青年到来后安置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单位。五是向甘南各族人民,积极宣传支建工作的政治、经济和国防意义。六是发动群众给支建青年筹备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住房等。全州共解决生产工具13,610件,生活用具40,733件,住房8620间,耕畜3898头。甘肃、河南两省的有关部门也对安置支建青年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援助。甘肃省计委调拨钢材30吨、柴油28吨、油桶116个;省农业厅下拨拖拉机80台、农机具298件,蔬菜种子8796公斤;省商业厅拨发胶轮大车44辆、架予车210辆,中小型生产工具7913件,灶具和生活用具5974件,棉布59,078米;兰州军区配备了26名军官和一部分枪支弹药;省卫生部门抽调了医生和大批医疗器械。河南省多次派出工作组到甘南深入各,点进行慰问,同时还支援小型生产工具1万余件,蔬菜籽种2000多公斤。
1958年11月28日,首批750名河南支建青年抵达甘南,受到党政军负责人和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及各族群众的夹道欢迎与热情接待。到1959年底时,全州相继安置河南支建青年41,697名,其中:男性30,836人,女性10,861人。年龄在25岁以下的有35,917人,占总数的86.1%。有党员1846人,团员8451人,党团员占总数的24%。具体安置结果是:各国营农场24,946人,占总数的59.8%;州内地方厂矿企业8203人,占20%;白龙江和洮河林业局7118人,占17%;玛曲渔场1430人,占3.2%。随迁的国家干部141名,其中:县级4人,区级33人,一般104人。他们都被安排在各国营农牧场担任领导工作。
创业
党和政府的关怀及全州各族人民的鼎力支持,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支建青年的劳动积极性,他们在各条战线上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在农业战线上,全州于1959年春建立的14个国营农场的17,344名职工,认真贯彻“边建场、边开荒、边生产、边积累、边扩大”的生产方针,到1959年12月底,累计开垦荒地约10,765公顷,播种3535公顷。其中:粮食作物约1994公顷,当年总产粮食280多万公斤;油料作物约1274公顷,总产油籽61.5万多公斤;种甜菜约67公顷,收获64万公斤;种蔬菜约153公顷,总产117万公斤;种饲料约313公顷,收牧草36.5万公斤。1959年达到粮油自给自足的农场有3个,占春季投入生产14个农场的16.6%;半自给自足的有3个,占总数的16.6%。两者合计达到了33.2%。在畜牧业战线上,1959年底各农牧场共有牛4068头,马491匹,羊3715只,猪2653头。在基本建设方面,到1959年底,各农牧场修建房屋4万多平方米,修建水、旱磨107盘。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使灌溉面积达到约6136.4公顷。在工业战线上,广大支建青年在设备简陋、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忘我工作,大胆革新,推动了生产的迅猛发展。如龙迭县建材厂,原来只有40余名职工,劳力严重不足,在安置了198名有文化、有技术的支建青年后,生产如虎添翼,在两个月内,产值猛增了47.7%。在林业战线上,安置在白龙江和洮河林业局的7000多名支建青年,起早贪黑地奋战在深山老林中,截止1959年10月底,共砍伐木材34.9万立方米,抚育幼林33多公顷,生产烤胶60余吨,修建林区公路80多公里,为国家完成了7100多万元的生产任务。
广大支建青年在勤奋的生产劳动中,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竞赛热潮,涌现出了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同时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进步和锻炼。到1959年底,有52名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93名青年入了团,还有378优秀青年被选送到州外各类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去深造。被选为省、州、县各级党代会、团代会、妇代会和人代会代表的有277人,同时还评选出优秀红旗手和先进工作者1119人,选出红旗单位96个。
返乡
1960年春,由于受全国"大跃进”思潮的影响,甘南改变了“以牧为主”的方针,提出“高速度发展农业”的口号,给全州18个国营农牧场下达“巩固和发展国营农牧场,大力开垦荒地,高速度发展农业,并积极地发展畜牧业和其他多种经营,实现'六自给,(粮、油、肉、菜、饲料和经费)和'四有余,(粮、油、菜、经费)”的生产任务。计划开垦荒地约52,026公顷,连同原有的约9338公顷耕地总数达到62,698公顷,职工人均占有约2.53公顷。为完成这个目标任务,18个国营农牧场组成两万多人的开荒大军,在一年内就地垦荒约18,209公顷,绝大部分是畜牧业草场。同时不顾当地均是3000米以上的高寒山坡地和气候十分恶劣的自然条件,当年播种各类农作物约22,678公顷,比1959年增长了6.8倍。其中:粮食作物约12,206公顷,但年终总产只有208万公斤粮食,平均亩产11.5公斤,连种子都没收回;种油籽约9672公顷,总产27万公斤,平均亩产1.85公斤,几乎是颗粒无收。
农业生产的大欠收,使广大职工的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有的不仅没有吃的油、盐、菜,而且断粮现象频繁发生。日趋严酷的生活形势,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生存,迫使大量支建青年偷跑回家,自动返回河南。到1961年底,全州返乡的农牧场职工达15,562人,其中:请假未归的2366人,偷跑回老家的13,196人。两者占安置总数的37.4%。对此,州委、州政府在进行全面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审时度势,作出“与其开小差和请假不回,不如公开登记,有组织的送回原籍为好”的决定。截止1962年元月30日,分十批(每批1500人)将愿意回河南的支建青年送回老家。全州总共送返的支建青年约3.1万多人。18个农牧场撤销后留下的约1万余人,全州统一调配,安排新的工作岗位。
后记
河南青年支援甘南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艰辛的过程,其方向是对的,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较大失误。特别是在人类赖以生存、生产和生活条件极差的甘南藏区,短期内迁徙4万多名青年,易地繁衍生息和生活,还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长期以来,在科技文化生产力水平都很落后的甘南,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或"靠天养畜”。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左”倾思潮的干扰,使这项工作半途而废,也造成了不良后果。这是个应该汲取的深刻教训。然而,当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课题下,正是通过前辈们艰苦地拼搏和探索,才使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摒弃失误,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当年河南支建青年那种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僻远的地区去创业奋斗,开扌石拼搏,'‘敢为天下先”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树立和赞扬的。
嗣后,留在甘南工交、林业等战线上近万名左右的河南支建青年,30余年来,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厂房、养路道班和茫茫林海之中,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学习,辛勤劳动,为甘南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业战线上的广大职工30多年来为国家经济建设累计提供了665万多立方米的木材和大量林副业土特产品,总产值达10.9亿多元。工交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日夜守护在兰郎公路和喉夏公路上,全长520多公里,他们顶风雪,冒严寒,长年坚守在高原道班上,为保障甘南交通运输的畅通无阻,铺路架桥,栉风沐雨,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所开创的业绩,将伴随着甘南州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而载入史册。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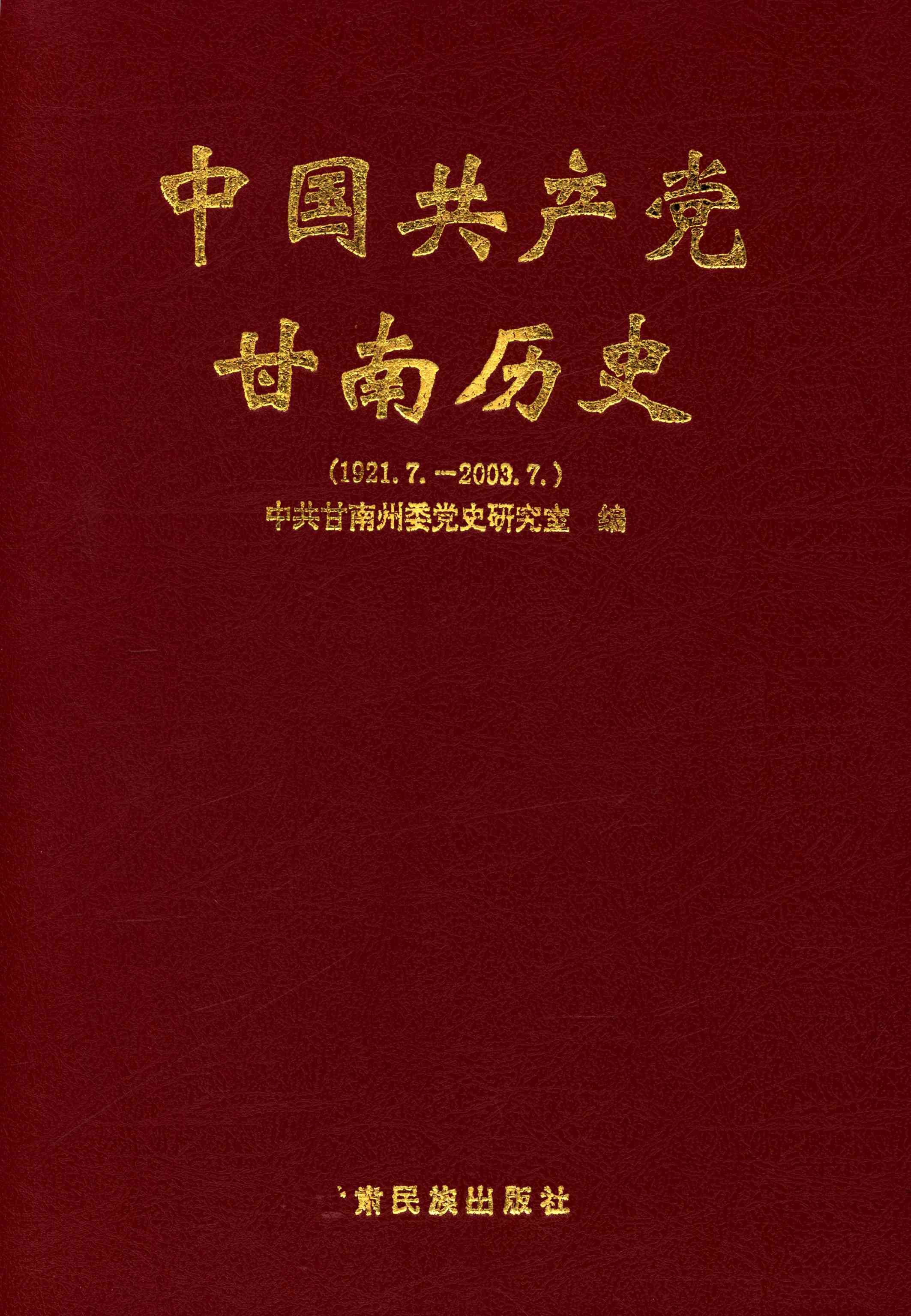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出版者:甘肃民族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记录了甘南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社会主义过度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甘南党史人物等等的详细记载。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