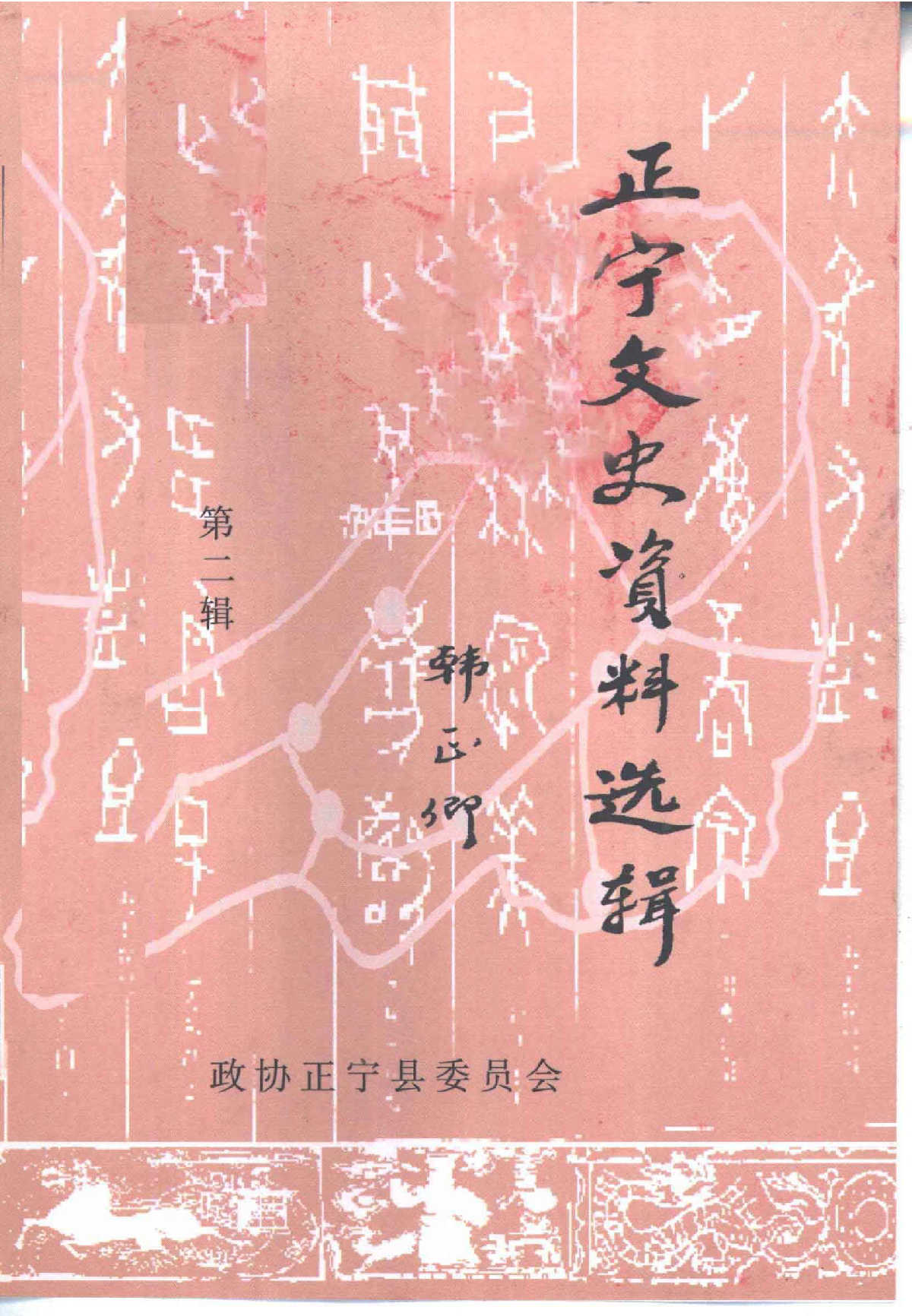赵邦清《游艺海纳集》校注
| 内容出处: | 《正宁文史资料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290720020220000862 |
| 颗粒名称: | 赵邦清《游艺海纳集》校注 |
| 分类号: | I207.23 |
| 页数: | 37 |
| 页码: | 215-251 |
| 摘要: | 《游艺海纳集》由序、自序、正文、后序四部分组成,约1.5万字,以随笔散记的形式记录了师友平日讲书谈文之言论,附以己意,夹叙夹议,内容详尽,笔法朴实,说理透彻,见解独到。 |
| 关键词: | 诗歌评论 诗词 |
内容
[解题]赵邦清:(公元1558年~1622年),字仲一,号乾所,明真宁(今正宁县永和乡于家庄)人。曾任山东滕县知县、吏部稽勋司郎中、四川遵义道监军参议等职。为官清正廉洁,不畏权贵,疾恶如仇,秉公执法;教民稼穑,兴修水利,倡导种树,广栽桑枣,重视教育,大办学馆,政绩卓著,世称“一代清臣”。邦清是因科举而走上仕途的,所以对文学十分钟爱,与明代著名的戏曲家汤显祖过从甚密,常有和歌应答之作,儒雅清趣,风流倜傥。其文学作品有《鹤唳草》、《瞑眩录》、《梦遇仙记》和《神柏记》。据《庆阳地区志》和《正宁县志》载现仅存《神柏记》一篇,而2001年前季在走访文史撰稿员时,笔者在罗川乡代店村赵邦清后裔赵永春家中翻阅家谱时,意外地发现了其又一部著作《游艺海纳集》,喜不自禁,悉心拜读,断句校注,奉献方家以求教,为育人资政以存史。
《游艺海纳集》由序、自序、正文、后序四部分组成,约1.5万字,以随笔散记的形式记录了师友平日讲书谈文之言论,附以己意,夹叙夹议,内容详尽,笔法朴实,说理透彻,见解独到。文章反映出读书人为求上进饱尝辛苦、遍求名师、不耻下问、足不出户、皓首穷经的治学之道和坚韧不拔之志,令人纫佩叹服。特别是赵邦清把作文与做人统一起来,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正色立业,注重道德修养,关心民瘼,憎恶贪赃枉法,鞭挞时弊,透悟性命,宠辱不惊,忧君忧民等思想,在今天来说,对我们为学处世仍大有裨益。同时由于文中所涉及的一些人和事,资料匮乏,无从考证,只能作个浅陋的注释,不尽如人意处,敬请读者谅解。
原文:游艺海纳序文章家虽一艺哉,然有道焉。进乎!艺矣,盖言心声也。所以抒写性灵,发挥其中藏者也。每戒于心之盈,而成于心之虚,盖盈则实,实则中坚。外距往往师心自用,虚则受,受则大罔不入,细罔不收。故末议可以佐圣,问察可成大智。《语》①曰:“江海之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也。”余读漆园吏②《秋水篇》:“百川灌河,两涯(法)渚涯之间,不辨牛马。河伯辄欣然喜曰:‘天下之美止此矣!’”及顺流至北海,不见水端。万壑注之不盈,尾闾泻之不虚,始爽然自失,望洋向若叹曰:“我今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子之门,则殆矣。”今世学者,公患大率类此,拘学牵于所闻,曲士来于所见,学一先生之言,守其师说,国陋而不变,一有所得,即敖(傲)焉。自智翘然,自喜此牛溲马渤行潦之流,“井蛙不可语于海者也。”亦有涉《六艺》③之圃,困百家之智,穷众口之辩,闻道已百第未睹大全,遂以为莫己若者,亦河伯之始自矜,及观海向苦,乃知不足,望洋兴叹者也,必也。穷无穷,极无极,六通四辟④,靡不学也,靡不师也,包裹天地,囊橐万有,注焉而不盈,的焉而不竭。泱泱乎,沧海大观也哉。余观尼父氏著《六经》,兼万善,苞孕上下古今,当时记之者曰:“焉不学无常师,有味哉!”其言之也,盖沧海不择细流,以成其深者也。嘻!斯至矣,蔑以加矣。今先生道德性命无不窥,文章政事靡不卓绝,而且缙绅、先生、长老靡不师,倘所称虚,受以成其大者,非耶。今其以《海纳》名篇也。意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万历甲寅岁仲冬之吉文林郎知合水县事通家门人朱芸顿首拜书道光戊子岁孟春之吉仍孙⑤荫生丕成谨抄敬录游艺海纳序赵邦清曰:“举业⑥,艺也。”习举业,即孔子⑦所谓游艺⑧之学也。游艺胡以《海纳》称?孟子⑨曰:“观于海者,难为水。”学者之心大不如海,则不足纳众善。子贡⑩,卫辉人。越十里,受学曲阜。及孔子没,庐墓六年,彼其学也。既不为仕进谋,彼其庐墓也。六年内,耽阁(搁)若干家事,盖真有见于真师,不可轻弃。当今士风日偷骄悍成俗,孰知学为何事?孰知求师之益无穷哉!邦清八岁时从邻村巩先生守谦学,及能成篇,从巩先生之子裕斋先生学,继从邻村李崇岗先生学。入庠时,在隆庆壬申年。邦清年十五,刘西坡宗师取首卷,乃在裕斋先生门下。后又从裕斋先生之叔寿峰先生学,寿峰先生授邦清以举业。彼时,欲遍师海内豪杰、顾路遥,乏资助,力不从心,独击节想象已耳。三水文少白先生住居丰川村,邦清住居真宁于家庄,两村相距三十里。适文少白先生自京谪归,先生成通《五经》邦清有负笈从学焉,授以举业,又授以性命之指。邦清闭户岁余,饥寒侵肤,苦极性灵,坎离交媾,悟门顿开,举业一艺始有入处。及少白先生赴京补官,邦清又拜庆阳傅太府逊斋先生,傅先生过目成诵,《五经》背记不差一字,天下异人也。时在门墙下几三年,举业稍稍入彀。万历戊子科,余汉城宗师庆阳类考,批邦清卷曰:“独隽逊斋傅先生。”当堂对五学诸生喜而言曰:“邦清卷批一,隽字诸生不知,盖智过千人。”曰:“隽邦清实一府五州县之首,不在真宁一县论后。”余宗师考延安过富州,对本道杜胤台公祖独许,邦清与庆阳府学关云石兄可中。是科初九进场,邦清初五日病,不入试,归来。李先生克庵忽自京来,先生亦通《五经》,邦清北面受业,教之曰:“文幸,艺也。学先立德。”邦清翻然改其旧曰习,检(坚)持于日用常行之际,心颇滋润,虽不讲学,而学之一字,常身亲体之,刻有李先生《语录》一书、《三生交砭录》一书。李先生入京,文少白先生正任湖广。寂寂寥寥,转盼无所资益,邦清同侄养贤闭户本村萧寺中年余,足不愈户限,一则攻习举业,一则修炼性命。久之,理水冲激,邪不能胜正,心窍内白痰从大肠下者升余,侄养贤所亲见者也。白痰下后,自觉五内清洁如玉,日每鼻闻异香,天气甫晚,两眼飞神光若梨华(花)大,累累继续不绝,颇知未来事,如此之兆,道欲成也。而有此矣,乃天发地应耳。此时,见大心泰略,无功名之想。至辛卯科,邦清以正贡搭类考,姜养冲宗师对五学,广文先生大许,邦清中。彼时,场中供事者有安化广文路先生、赵先生过,称邦清为宿学。又称为余汉城宗师得意士。姜文宗坚不与贡,曰:“贡了,他就将中的事误了。”次日,邦清以家贫母老解之,准贡讫。辛卯场中,邦清已在落卷中。八月二十一日,大主考麻十洲先生、于念东先生《诗经》正卷额已取足二十二名,却嫌《诗经》卷弱,特命西安刑厅李惟青先生搜阅《诗经》落卷,为李惟青先生当日原以《诗经》改《礼记》者,李惟青先生得邦清卷,大加称赏,力荐解元。麻十洲先生首肯,于念东先生嫌邦清卷太奇,李惟青先生同长安王念夔先生、及渭南崔际虞先生力在二座师处大讲,欲入五魁内。于念东先生辞曰:“此卷太奇,诚恐礼部细加磨对,我们要担当,姑置之二十名,彼磨至十二三名,力已倦矣,不为此卷之累。此卷高才,必中进士,论中二十名,实非此卷本等地位。”李惟青先生无奈何,随批邦清卷尾曰:“此卷不在魁解中,于予心犹有所不足也。”出场后,李惟青燕(宴)同门诸生,当席笑而言曰:“他的榜首必不中进士,我的赵门生必要连捷中进士,可惜未中个解元。”邦清侍侧,闻其语,亦甚恐。席毕,同门诸兄弟问会试场中文字如何作,李先生指邦清而言曰:“只照赵门生文字做去,必中进士,他的文字,就是会试体制,必定要连捷。”邦清入京住居报国寺一月,扃其户,凿墙以进饮食,不与人往来,果徼(侥)幸中壬辰会试矣。麻十洲先生拊其背,悲喜言曰:“我实实把贤友中解元,你于老师坚执不听。人言蚤(早)将贤友中个解元,连捷进士,我们体面,亦好看。只看贤友文字,必知后日正色立朝事业,勉之,勉之。”夫国朝设科取士,虽孔孟在,今日必从此出身。故举业不精,是不忠也。邦清随笔日所闻于师友者,集为一帙,名曰《游艺海纳》,末有附以己意,敢自曰:“我心如海,能纳万善。”亦惩于士风之骄悍,不敢忘日辛苦之功。晋此,聊为子孙举业性命之式。
万历三十一年岁次癸卯正月吉日赐进士出身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真宁赵邦清撰道光八年戊子二月初三日仍孙荫祀生丕成沐浴敬录于恒心堂中赵乾所游艺海纳真宁乾所赵邦清仲一甫纂著男赵任贤赵崇贤赵淑贤同校寿峰巩先生曰:“汝等看书一字不可轻放过,即如《四书》之外注,各《经》之断章性理通鉴之小注,皆宜仔细推寻。至于作文,即以此看书,细心出之,务要极其精密,若清空说几句便了,或不足胜人,或不足入主司之目。又要时时看新文字,不为旧套缠缚。窗下作文,不可贪多,须苦思推敲,方可上真,即如结题一件,当场考试时,若是草稿上不预先改作停当,场中掌号催卷上真,时促七结,不免苟且信笔写去,必多潦草不雅,何也?窗下草率成习,手段已熟,未有临场能细加点检者,况场中风檐寸善,又非窗下比也。”文少白先生曰:“作文之法,须宏大深入,宏大,则气象不小;深入,则以我之身直钻入题目里面去发挥,岂有不透彻的。盖题须讲开,方才有许多意味。若只求干净,恐家数狭隘,纵是金玉之句,亦不济事。文章须忌旧曰日套子,一翻丢过,各人另寻机轴做去,自是新奇。”我辛未年会试场中,曾犯此病。“生财有大道”一节,破云传者,竭言理财之要,而因著财之所由,裕也。看来千人都是如此比,殊为厌观。故归家,日搜读古文,以变文法。甲戍(戌)年会试场中,如“学如不及”一题,众人皆用知行,我却不用。田钟台先生取本房首卷,以我表句落韵,主考者置之十九名。讲长题不必牵合对股,当以意敷衍下去,圣贤言语皆有次第,岂可只图整齐,不究血脉。如“定之方中”一章,旧文皆以首章为主,下以升彼,虚矣。对“灵雨既零”一章,今却散散说去,归重秉心塞渊,何等联属。自乙酉科之后,长题皆用总括之法,然亦有不必总括者,岂可恃之为常。近在京师,与一二知文者论之,长题当实讲处,须实实讲去,不可架空。先要辨其体格,次要点检轻重所在。大抵长题股法,不得漫长,一层挨一层下去,则意思缜密,气味不断,此当以意深会之,可也。至于缴处,把题目起落处说成一团,尤为妙手。
“文章要老成,然老成者,易失之于古板,殊觉意思不活。汝辈今且从疏散流动处学去,后来再加收敛。不然一意炼句炼字,纵想起数层佳趣,亦不敢用邦清文,老成是矣。然岂可不学宏放流利以济之哉!”“文章是个精纯的物,比不得作论的言语。近见邦清学疏散流动,复觉有不切实处,股数有漫长处,然文字中一句闲话也用不得。‘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至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此题只就本文讲,犹恐说不出,汝却于入题处说许多闲话,岂不泛漫。”“文章最怕有粗句粗字讲理,题逞不得奇,粗题要细做,造句不可长。盖句碎则意密,颇有折转,若几句长话成一股,则直而无文矣,须委婉其致,则佳。”“如讲‘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一题,就宜以桀溺口气讲去,起讲即用想桀溺之意,若曰殊为省力,时人不知此桀溺调,起处既用己意断之,至入题处才用桀溺口气,是一隔矣。此先生之言也。戊子科,余文宗类考庆阳,出‘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一题,众人皆用孟子口气作起讲,至入题处方用曾子之意,是费了多少气力,且意绪不贯。邦清于起讲处即想曾子之意,若日一篇皆曾子之言,至缴后,略点出孟子意。余文宗批曰:‘阅卷惟子独隽。’”“如讲‘鲁无君子者’一题,鲁多君子,分明是正意,然题面却是鲁无君子。文章须从鲁无君子实实讲去,盖鲁有君子,此客语也,客语多,则不像题矣。其余皆以此类推之。”“讲‘齐之以礼’一题,不得不承道德来,然只一处用之,可也。若用道德意多,则客语胜矣。”“讲小题要凌驾,然凌驾之法太烦,则不切题,宜忌之。”‘讲大题须循题目起落去处实讲,其格调有不可那移者,甚不可弄巧凿坏体制。”“近在泰州,见南方文字原与北人不同,北人总不离套子,南方文字一句套子也不用。邦清今须从新做一番,始得超脱。勉之,勉之。”“文章讲毕,虽当有几句余波,然不可太多中间立柱。如知行、道德、事业、物等类,一过目即令人痛恶。况近来虽用柱眼,又却不显然明白露出。此二比,最怕一直说去,要得起承转合之法。”“文章胜人处,原在起讲入题处。与末后二比,并缴题此处,着实要立些意思,发些议论,起讲就说到题目上,与入题处相递接下,此法最高,不见痕迹,尤没间隔。”“一句起题,末后二比古劲,则缴题宜圆,后二比流快,则缴题宜方,又须格调各异,方见顿挫。”“一句题末后二比宜加苦思,极力研磨,则趣味深长。盖中间二比与小讲二比,此皆众人所易。能者惟此二比,则错综(纵)变化,每无定局。”“缴题有单收格,有双收格,有散收格,有反收格。若入题处反了,则缴题不必反,恐犯重复。”“一句题小讲处用流水文法,则末后二大比不必用流水;若小讲处以意对讲,不用流水,末后二大比方可用流水文法。”“文章自起至缴,要意思宽缓,步骤从容,甚勿急促之句。”“文章着实要句句推敲、字字磨炼,一句不妥不必用,一字不雅不必用。”“对股数如上比已成,而下比或字眼难凑,不得合上比,须把上句做成的句法字法,稍加更易,则下比即成矣。不可死执着上比已成,故将下比扭捏强对。”“通篇文字意思要多,议论要大,不然则弱矣。况作一句题入讲处,并二小比,中间二大比,末后二大比,并缴题,亦当用十比方可。”“作一句题,题目字面略略点破,即了。若用他本题字面太烦,则为露骨矣。”“今日之文,纯正典实,是的局也。”“奇崛不平,文之大病,宜戒之。”“作文之法,全凭思索功夫。”“作文之时,要立个排山倒海之势。”“讲‘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七句题,起讲宜浑浑说下,不可露容貌等字样出来。所贵乎道者三稍讲,六句接下去将动容貌,六句的意思总发。二小比亦不可显然露出容貌暴慢等字样来。至容貌三段着实发挥,末段缴题只以意咏叹,亦不可露容貌暴慢等字样出来。众人作此题皆用修己治人意缴之,惟少玄虽用修已治人的意思,却无修己治人的字面,独觉大雅。”“讲‘战伐’题,须用征战等字面出来,不然则腐矣。不见行阵威武的气象。”“文章有当讲毕而一句收之者。如‘一齐人传之’三句,若上文内一一讲日挞字面则不佳,讲完后,当当云此。虽日挞求其齐也,岂可得哉?再咏难(叹)数句,即了。”万历十八年八月内,先生自南京回家,邦清谒之。先生曰:“文章须识体,汝知之乎?”逊斋傅先生曰:“生文章先要净,不可有浮浪之气。”“善作文者,一句有一意思,一字有(一)意思。不善作文者,一篇总是一意,一比总是一意。殊无结构,文以辞胜不如以意胜,修辞不如注意,况一篇文字不过四百言,若非以意翻腾,则单弱无力矣。”“作文全要看朱注,如‘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朱注分明说‘甚言,其不可也。’众人皆云,利亦可为。至缴处方说不可为,岂不背驰。”“题中有的字面亦须点出,如‘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一题,邦清此题文亦佳,但温恭字面未尝说出,似欠分晓。”“破(题)要精而约。”“承题不可说的意思太露了,太露则文章无味矣,此养文之法也。起讲虽不可太骤然,而无用紧的话宜裁之。起讲末接入题处,要极力讲开。此处全看的手段,不可草草便了。至首二小比、中二大比则人皆可到,末二比须要深思。入题处既用反振文法,中二比一句也不可反振,若反振,则又似起头语矣。作文全怕露了,下文汝宜忌之。临场时,将易犯的字面写在稿上,时时对照,也省之一助也。作文要用自家的意思去讲,不必想某人的句法如何、股法如何,旧文章讲此题如何,若用他的唾咳,亦不中用,终不见长进。”“文字太奇,固不雅,然亦不可太平,要平中见奇拔之趣。”“近日起讲用‘盖臣察相’等字,殊为作怪。又如云:‘司政柄者,孰不欲?’某某又云:‘人君享太平而乐盛治者,岂独主德茂也哉。’皆为常套,宜加痛改。起讲末句又云:‘吾有见于某,吾有感于某,吾有慨于某’,深可笑也。所谓诚其意者至下节,故君子慎其独也。见一生将上节总分成好恶二大比,大非体格义理,有次第当轻处,固不可缠他(它)。然亦须挨次第说去,始觉详密。”邦清当应试日,傅先生勉之曰:“汝之文,气清辞爽,是矣。第一意学清,则中无隽永之味,恐题意发挥未透。临场日,须苦心注思,俾淡而不厌,可也。”邦清作“乐天者,保天下,至于时保之”一题,过文用八句,先生面命之曰:“亦宜调剂似此,则太多矣。”克庵李先生曰:“作文之法在不俗、不冗、不浮、不泛,不学套作。长题即当从题目起处下手讲去,若牵扯上文多了,是今之题不从原起处出,而从上文出矣。况题目大了,时时要剂量轩轾。当总括处固不可不总括,若不必总括处只从题目起处说去也。好长题如有问答者,体口气与不体口气皆从临时权衡,不可执定一格常作主意。”“嘉靖年间,文字尚实讲。至万历癸未科以前,稍清空矣。近日请过圣旨,复尚实讲,大抵要把题目讲透。盖各人平日有独得之见,原宜诸此细细说出。”“作文须尚骨力,我与邦清以李崆峒时文正取他骨力,可法也。试细心熟玩之自见。”“作文要有气,所谓气者,不在篇段之长,只是要不弱,不断续耳。”“作论之法,如破题用某字作主,通篇文字全要照管着他(它)。论冒(帽)亦须浑然,不可讲的太露了,太露了则正讲处无味矣。且冒(帽)上又不引证譬喻,又有不作论破论,冒(帽)而直直叙起者,格体甚多,以意会之。可也。”“作长题须一步一步照顾题面,不可只逞一己之论,挥霍出者,去用句用意也。要称量,一不称量,则害事矣。”汉城余宗师考西安府学,出“升车,必正立执绥”一题,有一生中间既讲了正立,讲了执绥,末二比又复讲正立执绥,至缴题又复说出。文宗批曰:“正立执绥中间已讲明了,后二比只宜以意敷衍,若复用正立执绥字面来,则太赘矣。”又曰:“正立、执绥须并重,众人偏重正立,殊失却了题旨。”出“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题。有一生入题处未曾提掇。文宗批曰:“此处步骤似乎太紧。”西安府学生张起凤作此题,既先提掇二小比,末二比后,又复咏叹二小比,则碎点之。有一生中二比用“知其一,不知其他”的字面。末二比复显然露出“知其一,不知其他。”文宗批曰:“太赘。”故置之三等。
考贡出“故曰,域民不以封强之界”二句。有一生点出“故曰”字,诸生俱无,文宗独许之。有一生发题上三“以”字,文宗曰:“将正经题目你不去讲,却发‘以’字,何也?我不责汝,汝亦不改。”朴责十板。
出“邦有道谷”三句题,考贡。朱注曰:“宪之狷介,其于邦道无谷之可耻,固知之矣。至于邦有道谷之可耻,则未必知也。”众人执着此意,皆重无道一边。文宗曰:“夫子当日原是平说,生等何故偏重无道?可恶!可恶!”考庆阳府,出“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一题,众人皆偏重义上。文宗曰:“曾子当日原是说你有你的爵,我有我的义。生等俱重义上讲,岂不左矣。且讲义字俱用心之制事之宜,此用在义以为质上的义字做讲,则可。此义字亦当相题,当云首出庶物之。彼之爵人皆仰其尊,而吾之义则刚方正直,常伸于天地之上,卓冠群伦。彼之爵人皆羡其贵,而吾之义则光明正大,不屈于万物之下,秀才作文全要相题心之制事之宜,怎么与爵相对?且诸生中又有一种,只讲彼以爵,我以义,全然不讲如何是义者,不讲义字,如何对得过爵。”华阳张父母曰:“文章句法全要古径,中间二比须讲九句十句,盖发题全靠此二比,末段缴题不可草草,极力发挥,才见气力优长。作文之法,先要求其匀,以一篇言,自破至缴须匀;以七篇言,自首篇至末篇要如此一样匀。盖文字匀,则中矣。”“作论之法似不必搜罗,要详,详就题上靠实讲去。作文全要识体,近日文体须庄重古雅,若昔年孰话常调,用在今日如何行得。如一句题初头二比极要精确,一个闲字不可用,且平仄又当调之,使读之者有铿锵之声。末二比,近日多用虚实之法,然先虚一比,亦须着题,毋令实胜乎主。束题亦须大发扬之,不可略说几句便了,且如人之说话,虽毕,亦当委婉,其意致没有个齐头故事。”
三水文和一先生曰:“起讲说得几句,就要接到题上,昔人所谓开门见山,是也。”
三水文望云兄曰:“文章全要翻过,时文不为旧套所拘,夜间思索功夫,甚有裨于文字,吾弟图之。”
三水文少玄兄曰:“作文之法,须宏博深邃,纵有一二不妥当处,被阅文者抹之,何害?但场中则不可仔细,若怕人抹,有的话、有的意思不敢写出,只求一是便了,终不得成大器也。”
三水马羲川兄曰:“造句不可大快,须深着些方好,若只求流利,则不见庄严之体矣。”
三水文起旸兄曰:“会中某人文字可法,我等即当效法他,全把我的文章模样丢在一边,做出来全然不似我旧日模样,则大进矣。”邦清一日作“居敬而行,简至雍之言然”一题,起语太烦。三水张醇儒兄驳之曰:“这等大题,只实实靠本题讲去,犹恐说不透,兄何必用此许多闲话?”今日想之,醇儒兄之言,直中吾之膏盲。
庆阳赵寰兄曰:“乾所文字只以意胜,却不着意炼句,然句法古健,亦文中秘诀,乾所何略之?且句中或裁一两字,或添一两字,不腐不庸,则句工矣。冯聚垣兄最善炼句,乾所当则效之。”庆阳赵云衢兄曰:“乾所文字其格调原与我辈不同,然却多不炼,或剪裁其冗漫,或消融其查(渣)滓,则文字便精炼矣。”环县吴诚轩兄曰:“予昔受学于黄葵阳先生,彼教之曰:‘作文之法,纵有想起的好意思,且不必用的蚤(早)了,须一步一步漫漫说去,至末二比与缴题,才宜把前边想起的好意思发之,令阅卷者读至此,精神愈奋,愈称奇矣。’”镇原董昆兄曰:“乾所兄之文,极是认理,然亦不可直头直脑说去,须委婉其致,至于炼句尤当俊雅。”固原赵诚斋兄曰:“作文要将题意发透,须立个大气象,把天地就入在我胸中,则举笔自是宏扩,若求是了,则家数小矣。”一日在京师拜李渐庵老先生,适遇李九我先生来,予请问场中如何阅卷,九我曰:“文字只看半篇就知其人,不待竟篇。大要作文须于末后二比并缴题处,议论趣味滔滔不已,则刮目矣。”又曰:“今旧,时文起讲上就要透出题意。”侄养贤曰:“做文章全要把正题讲透,处处都与他(它)说到圆圆满满。就如写大字的一般,其方法在道径(劲)二字。道者,圆满充实之意;径(劲)者,不腐不弱。若只求光光净净说几句,便了,无大议论,无大结构,何以胜人。”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科六月,邦清尚任滕县知县时,在曲阜伺候。
文宗徐石楼先生类考。夜间书此寄示长男任贤:作文不可用一句佛老之语,亦不可用一句熟套语。你自来未看佛老书,凡坊间所刻时文,有用佛老语者,你就喜他(它)句法新奇,入之于文。主司学问渊深,看见是佛老语,你何自而知其为佛老语也,可笑!可笑!至如熟套赵甲用的固是,钱乙用的亦是,他一见便令人憎恶。凡遇题目,各人就题生意,自家做自家的文章,说自家的话,不得偎人的脚汗,拾人唾咳。昨与福建代振宇年兄讲时文,彼谓全要平正中见奇,太平则庸,太奇则怪。当以意斟酌,如今冯祭酒有本《文章要限》四百字,全要向典实处做去。奉圣旨礼部知道,想是各省主考官都照此旨取士也。发来冯祭酒本,可细心看之。策不过是圣学、圣治、灾异、东倭理财、并北虏战和之说。初三日夜一更时候,我在曲阜公馆内,请曹应聘、张九经两作家到,因问任贤之文,其病症的在何处,今当进场之时,大家实说,使彼知所改图。二生对曰:“大哥之文,不患不高,不患不古,不患不奇,只是欠平正,欠熔炼。”我亦想来,这四字是你对症之药,你进头场时,要将平整、庄重、醇洁、深厚、典实、熔炼十二字写到号房板儿上,字面重复全是你的病症。如“默而识之”,起讲处用了闻见,大讲里面又用闻见,字面偏枯,亦是你的病症。如“默而识之”,以不识不知对意言象数,又浃洽融液对无言不悦,是也。盖意言象数,是四个实字,又是四意。不识不知,只是两意,怎么对得过意言象数乎?浃洽融液又是四实字,无言不悦只是一意,怎么对得过浃洽融液乎?这个谓之偏枯之病,作文一开手(首)就当晓得重复偏枯之病而改之。况做大秀才到今日乎,如此之类,皆当推类而广之,急图改之。
场中作文还有一诀,我之乡试、会试,其头篇完时,都是近午时侯(侯)。盖一句不肯轻说出,一字不肯轻放过,则念头清净,光明如水止一般,刹那,气已定,息已停,纵有不好处,我自家都照得出来,及至二篇三篇,则气愈定,息愈停,口鼻气息全无,元始真性归入祖关,笔下愈神。若到经文上,则本立道生,生机逼,逼而出,真有不容已之势。你若把头篇轻易放过去,则气便粗,息便乱,写出的不好话头,都当作好文章,自认之矣。你那“白雪之白”一作,真是会试场中文字,练之极精,磨之极细,观者便自是认得。如今举子亲手写的乡会墨卷,另束在一边,主司全不经目,只是看那誊录生誊过的红卷。你将七篇誊毕时,且莫心忙,再将七篇文章仔细念诵、推敲一遮,如有闲句、闲字,随即裁剪、锻炼,再改一遍。只要填注的明白,令他誊录生好去誊写,不怕改的黑黑的难看。我乡会两场,全得这个功夫。盖先草(抄)一遍,既仔细改之矣。及至誊过真,再改一遍,便是两遍功夫。到那其间,人人都慌张,谁人肯如此两番做功夫。改至两遍,则闲句、闲字既已剪削净尽,一看便觉古古棱棱是个商彝周鼎,比之寻常,奚啻百倍,再分(吩)付(咐)你草稿上做一篇,就把一篇改定,如一字不稳,且莫做第二篇,就是结中一字不稳,且勿自恕,先做第二篇去也。认(任)他老军叫嗓,切莫心忙,你只将七篇仔仔细细做定,就是到四鼓誊真,盖亦不怕。只恐草稿未定,一听老军催卷乱嚷,就是脚忙手乱也。休听人说,先誊
三篇《四书》,已将精神用过四分去了,却拿甚(什)么精神去做那经文章。一总七篇草稿,都无一字欠缺,方才下笔誊真。
闻说省城有一伙不进学的老童生,结党成群专在院里妓者家行走,日与妓者教曲子正字。妓者将他们打在里手内,着意敬他。每遇科举之年,这一伙老童生引领一伙不做生理的尖儿手油嘴光棍,在舞生坛、迎祥观、开元寺,及桥子口、白鹿湾一带,专一替妓者打听找问某公子在某处住歇。某公子在某处住歇,可以勾引嫖宿、骗钱、吃嘴。当未进场之前,即使赵甲勾钱乙,又令孙丙勾李丁,淫荡人家多少好子弟,败坏人家多少大美事,岂不深可恨哉?三年一次科举,父母之心,并乡党亲戚,谁不满望高进一步?岂意会省之地,有此等无耻之徒,勾引人家好子弟干歪事。汝等当大着眼力,坚定心志,须想父母起送科举之心,攀(盼)望眼穿之心,及乡党亲戚属望之心,家人往来翻沟越岭、过河渡水、接送受苦之心,岂可轻听此辈勾引,而先丧其自己之良心乎!戒之哉!戒之哉!邦清时在曲阜,既寄长男任贤以作文之法。次日,滕门生曹生应聘讨看书稿,因相与问答应聘,遂备录之。
曹生应聘讨看书稿毕,起而问曰:“老师云:‘场中做头篇一句不肯轻说,一字不肯轻放,则念头清净光明。刹那,气已定,息已停,纵有不好处自家都照得出。及至二三篇,气愈定,息愈停,口鼻气息全无,元始真性归入祖关,笔下愈神。若把头篇轻易放过去,气便粗,息便乱,写出的不好话头,自家都认不得。’此其说最玄妙,前乎未之闻也,请明言之。”曰:“昭乎哉,问也。心属火,火能照物,思虑驰,逐则火力分,故不明。试观有等不知道理人,忿欲一萌,热中燥烈飞扬,焦发赤目。船子和尚所谓:‘一波才动万波随。’是也。惟念头并归一路,收敛沉潜,则湛一清虚,无所不照,故本立道生。班亦曰:‘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阳在上,卑阴在下。礼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锐也。人有道心,天本在上,故心下锐也。”应聘又问老师云:“元始真性归入祖关,请问祖关何指?”也曰:“禅门功夫,惟‘心路绝,祖关透’六字为入定之妙诀。心路不绝,则祖关不透,祖关不透,则心路不绝,玄门密诀。”亦曰:“气入玄元,即达本来天真。盖人之所以为人者,呼吸之气也。呼吸之根在两肾中间一虚窍,而鼻特呼吸之门耳,何也?鼻出入气高而有窍。山亦有金石累积,亦有孔穴出云布雨,以润天下,雨则去消。鼻能出纳气也,而其根则在于两肾中间一穴。盖两肾中间,白膜之内一点动气,大如筋头,鼓舞化变,大阖周身,薰蒸三焦,消化水谷,外御六淫,内当万虑,昼夜不停,此之谓祖关。念头清净,则口鼻气息全无,口鼻气息既无,则元始真性归入祖关,就是入定了,定生慧。一道神光勃然磨灭不得如何,文字不精力、不光彩、不超出乎、人也。惟实用其力者,知之真。故言之亲切而有味,这原是举业正脉,彼未尝实用其力者,与之言,云而,云而。如以华语绎番经,投之多不入。”应聘又问老师云:“心路绝者,何说也?”曰:“心有所行之熟路,遇境便迁,故名之曰:‘心猿意马。’《圆觉经》云:‘居一切时,勿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辩真实,到此地位,则一念不生,前后际断,照体独立,物我皆如,心路绝矣。心路绝,则主人归舍,祖关不期透而自透矣。”应聘喜曰:“老师何所闻而言之,亲切若是?”曰:“学不遇异人,则心地不扩大,识见不高远,此岂但为举业之机枢哉!天德王道将一以贯之矣。予鲁遇异人,不敢举其姓命。异人,乃元朝人也。密传口诀,而又十数年来,日下苦功,受过无穷冻馁,冷处生清,清处生明,岂易言哉!《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子思分明以一‘潜’字说在《中庸》一部后,收煞至诚、博厚、高明、悠久之功业,而人不之省,惟朱子见得到。故曰:‘颜子深潜,纯粹潜之’时义大矣哉。”应聘又问曰:“即今大名家都说举业自为举业,老师开口就先说到性命上去,何意也?”曰:“学不深于性命,则悟门不开,胆气不大。就是有当深讲处,自家见理不真,便趑趄踟蹰,不敢深讲。惟透了性命之窍,故横说、竖说、正说、奇说、长焉、短焉、生焉、熟焉、肥焉、瘦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均有一段垂世之语,精光到几时不减。如令的文体一敝不讲理,不发挥题意,专一务为雕镂,神情都失,此不透性命之故也。正各省学道,当力挽其颓风,时也。”应聘又问曰:“性命二字《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不知言之者几朝代,辩之者几万人,卒不得其解,愿详言之。”曰:“世间一切枝(技)艺作能百务之巧,各有专门,况有性命大事乎?性命亦各有专门,专门则精,吾辈书生之据书本子上论性命,犹之画饼充饥,饥卒不可充。且说宇太定者,发乎天光。书生只将天光作做腹内聪明看,殊不知宇太定者,到晚来天光累累,飞出眼来,若梨花大。到此地位,眼底尚有尚书、阁老乎?且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书生只当作冬至子时,谓真下起元一阳来,复便见得天地生生之心。然天是一大天,人是一小天,论及人心之复,则个个罔觉,殊不知人心到复时,忽然心头上一点凉如冰,移时方落入中黄去。此乃火在下,而水在上,水火既济,方自知其复,方自见得天地之心,以一书生欲讲个复其见天地之心,何处入手,且说明心见性。学者必说明了心,便见了性,至诘之。”曰:“如何见性则芒惘然无以对,殊不知天之下,地之上,上下四方纯是块一性,无少欠缺,无少渗漏,故曰:‘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体物而不可遗。’”又曰:“‘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朱子曰:‘如鱼在水,外面水即他(它)肚里水。鳜鱼肚中水,便是鲤鱼肛中水。天之命,是人之性,人之命,是天之性。但太虚之性,谓之母是先天之性,在人之性,谓之子是后天之性,人生而有此性。至于形生神发之后,知诱物化阴,浊胜而阳明。微子不亲母,子日离于母远矣,如何得见,果能物转情空,情反性易。则子渐就母,母必恋子,先天自虚无而来,眼里便亲见得是以子气,而感母气。’张三峰曰:‘万船景界皆非类,一个红光是至真。此个红光生异象,其中若有明窗尘。中悬一点先天药,远似葡萄近似金,到此全凭要谨慎,丝毫念起丧天真。待他(它)一点自归腹,化作身中四时春。一片白雪香一阵,一番雨过一番新。终日绵绵如醉汉,优游只守洞中春。遍体阴精俱剥尽,炼作纯阳一块金。此时气绝如小死,打成一片是全真。’是先天之性,我亲眼见之,而终归我之身。书生荒疏何曾到此方,所与之言,见性不笑,则骂之矣。”应聘又问曰:“性之一字终,何解乎?愿闻其说。”曰:“元始真性,谓之性。”应聘又问曰:“人死则性何在,性亦死乎?”曰:“性者,生也。生之谓性,性何尝死乎?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环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蚀之交有时,达循环之端者,知死生之会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对月而明,夺违对而月朗,是故死之换生,而魂化死过而生,来生之忘死而识,空失忘而死见。然则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见,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见矣。且薄蚀之交,不能伤日月之体,死生之会,不能变至人之神体不伤,故日月无薄蚀之忧。神不变,故至人无死生之恐。《楞严经》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时见恒河水与今无异,是汝皮肉虽皱,见精不皱以明身,有老少而见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问隐者刘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尔不与形俱灭者,固常在也。’《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庄子曰:‘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伊川曰:‘尧舜几千年,其心至令存。’横渠曰:‘物物故能过化,性性故能存神。高峰和尚曰:‘若要脱生死,须透师祖关,毕竟将甚(什)么作关,唤作竹篦则触,不唤作竹篦则背,不得有语,不得无语,若向这里着得一只眼觑得破,转得身,通得气,无关不透,无法不通,头头示显,物物全彰。无边刹境,自他(它)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天如和尚曰:‘裂开烦恼网,击破生死关。幻形幻影,有去有来。侣浮云之出壑,真性真明不迁不变。如皎月之当空,即此是自己根源,即此是故家田地,即此是安身立命处,即此是成佛作祖时。’无用全和尚曰:‘这一点灵光穷劫不坏,永常无朽,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凡圣两忘,中道无拘,空空廓廓,自自然然,辉天鉴地,分毫无碍,佛祖凭此称号世界,凭此安立无有,一般不从此性中所育生也。可(何)以为人,先须悟性,清净无为,皎然明白,生死本无妄尘所惑。性如精金,尘如杂矿,矿净金纯,任君使用。妄尽尘消,情真洞明,随汝作用,若穷性理,分毫无碍,一念也无,受用无量,永劫常存,灵通觉遍,教化众生,了生脱死。满各人悲愿,报佛祖深恩。’达观禅师曰:‘人是有形之鬼,鬼是无形之人。谓人鬼有两,心无是理,只是有形无形差别耳,信乎?性则必生观月之印水,则知性之生气矣。观火之传薪,则知性之生形矣。’顺真子云:‘形不能生形,生形者,非形也,气也。气不能生气,生气者,非气也,性也。’又云:‘形之万殊化而不留,惟气之一者不变。夫气之不变者,殆有所以不变者存,不变者存,盖指性而言也。’”应聘又问曰:“老师云元始真知,谓之性,以知言性,果何谓也?”曰:“知者,性之灵也。知非识察照了分别之谓也。是性之虚圆莹彻清通净妙不落有无,能为天地万物之根,弥六合,亘万古,而炳然独存者也。性不可得而分合增减,知亦不可得而分合增减。圣凡与鸟兽草木异者,惟在明与蔽耳,是故学莫先于致知。”应聘又问曰:“何谓识察照了分别之知?何谓性灵之真知?”曰:“精乎哉!问也。识察照了分别者,意与形之灵也。亦性之末流也。性灵之真知,非动作计虑以知,故无生灭。意与形之灵,必动作计虑以缘外境,则有生灭性灵之真知。无欲意与形之灵,则有欲矣。今人以识察照了分别为性灵之真知,是以奴为主也。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谓圣知者,明也。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者,知也,性也。父母未生以前先有其明,生身之后自染混浊。明而不明,然人性本明,染则浊,净则寂,寂能灵,灵能通达出生死之道,永作长生之至。人也,天之知,日之明,是也。人之知,心之灵是也。朱子亦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日秉阳,精最热。知禀阳明亦最热,热则有所触而必透,必生神仙之体,如火热纯阳故也。’此非大悟人,何可语此?予每清辰(晨)蚤(早)起,精神多不畅。忽然日出东方。一被日光热照,此身则精神顿畅。自思是我之子气,见了天之母气,两相亲洽,天光渗入心光故也。性明而热,是予日久体察悟出的,不在书本子上抄出的,此学惟曾子见得真。孔子没,子夏、子游、子张欲以所事孔子之体,事乎有若。曾子驳曰:‘不可,秋阳以暴之。’周正建子,今之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是周之春,今之二月、三月、四月是周之夏,今之五月、六月、七月是周之秋,今之八月、九月、十月是周之冬。曾子,周人也。曾子所谓秋阳,是以今之五月、六月、七月作秋,乃五月、六月、七月之秋阳也。日中则盛,每日午时,日光甚盛。月中则盛,每月十五,月光甚盛,四时之中则盛,每年五月、六月、七月为时之中,阳气甚盛。人心之中则盛。吾人固守中黄,则心火力全既明,且热而盛。曾子所谓秋阳,乃五月、六月、七月之正阳乎!今人但知性是个明的,不知性则明而热,惟曾子说出‘秋阳’二字。是兼明热而言之也。近日,阎蓬头神仙中之铮铮有名者,王凤洲先生文章性命一代高人,师事阎蓬头。每言蓬头当五月、六月、七月之时,辄裸而暴赤日中不汗。蓬头盖借天日之光,欲渗入本心之光,而人不之省。关云长辞曹操书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之上普照万方,心在人之内以秉丹诚者,性之明而热者也。时人常曰某人好一付热心肠,惟有热心肠,故见善必好,见人必爱,见义勇为。彼见善而不知好,见人而不知爱,见义而不果于勇为者,皆是心力不全、明之不至、热之不至之故耳。汝试细心思之。”应聘又问曰:“自来论性未有敢以明热言之者,老师云性明而热,不亦起人之疑乎?”曰:“论性者,古圣先贤不敢妄议。只说令之论性者,不向自家身上去体察,只据书本子上取,便口头说说之何益。此心之灵明逾乎!日月其照临有甚于日月之照临,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薄屋之下。此心之神无所不通,此心之明无所不照,此明之之说也。一斤熟肉置之锅内,着力武火烹煎三个时候,未必能化为汁末;一斤熟肉吃在肚内,延至三个时候,便化为汁未矣。外面火力有如此之神而速乎?汝试思,此三个时候肚内能化一斤熟肉为汁末者,果有形之胃乎?抑无形之性乎?若与拿书本子的腐儒说他(它),便笑予为迂。孔子曰:‘民不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此热之之说也。”应聘又问:“子路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毕竟何说?”曰:“窘乎哉,问也。当下若明,死后可知。若当下不明,何知死后也。若当下知归,如远客还家,不明径路,终成迷谬。若明路径,不惟知途中境界,亦自见家中事业。若但事口耳言说,欲进此道,则大错矣。所以古人云:‘欲明大事因缘直于衣线下。’日用寻常一一知其从何所来,自何而去,是谁起是谁灭,觉知起灭者,复是何物。如此存养,自知佛真法身不向他求,惟此现前本有自不滞,有不滞无不离,有无了了。常知不妄不变,随缘自在,若生染着,即为非心故般若。《经》云‘若心有住。’即为非心妄心若歇歇,即菩提不从人得。所谓菩提者,即知也、性也、觉也、心也。若悟此心,便识妄有去来,妄有起灭,若实自心,即无攸往不真,待何?”应聘又问:“当今士夫俱碍口,不敢谭(谈)禅老。师论举业,则云作文不可用一句佛老语,至论性命,则多引佛老语,何前后不相顾乎?”曰:“论举业,严禁不用佛老语者,尊朝廷之令甲也。孔子分明知周末文胜不好,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郁郁乎,文盖鄙之也。’然亦必曰吾从周论性命之学,则必引佛老语者。以性命之学,佛老原是专门此学,极精极细。不是真见性命、真拿住性命的人,何敢轻易漫谭(谈)。士夫窃用其语,调理自家性命。至讲论性命,则专辟佛老语,未免有偷心在。学道之人,第一怕偷心安下种子,安下这偷心种子,在内他(它)便会作祸,他便由种而苗,苗而秀,秀而实。明是个无学问的人,诈妆有学(问),明是个奸险诈伪的人,诈妆老实粗朴,明是个不畏王法不怕清议的贪官,顾粗衣、恶食、敝车、羸马妆成清官,明要害某人,害某人遇见某人,某反加意欸,其辞温,其色谦恭,其礼貌委曲,其寒暄,此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一生诈伪到底,至死不见真性,偷心不偷心,君子小人于焉分路,向东路去的必不回头看西,向西路去的必不回头看东。只说人病息要救性命,有时而用人参、桔梗,亦有时而用太黄、巴豆,有时而用雄鸡、班(斑)鸠,亦有时而用全蝎、蕲蛇。孔子尚敬礼,老子若遇世尊岂肯怠慢。佛老性命之说,如何不可兼收而并畜(蓄)之。把你那莫识见的秀才,只着一个大通禅的老和尚一句问倒嘴卢都的,再无第二句还他人。非三世人身,则血气不清,不知好道,不知讲性命。予鄙心好此甚于食色,饭棹(桌)上、枕头边、出门马上、袖子里、桥内扶手上,无不是这性命书,一日不看性命书,五内便不滋润,脸上便觉俗然,实未见个大头脑,只是口耳之学耳!”《游艺海纳》刻毕,适用宁州杜元庵兄到于家庄特来光顾,即取《游艺海纳》一过目,喜动颜色,因问邦清曰:“乡也知兄之苦心举业,苦心性命,大家都说赵乾所兄苦心举业已矣。性命大事,岂易入其阃奥哉!今观兄与滕县曹门生应聘问答,是兄已透性命之窍矣,果何由而入此窍哉?”曰:“欲做天下真事业,须从天下真学问中来。所谓真学问者,乃性命一件大事,是也,试观今之宇宙处处民穷财尽,皆贪官污吏害之也。太祖时赃满二十两,即便剥皮,惟今日惩贪之法轻,故赃官、赃吏满天下,当事者熟于耳目,都当作常事耳,便都因循将就过去,犹鱼在水中行,而不知其为水也。彼此推靠不肯振刷,天下将乱,谁复顾虑。透过性命的人,眼界阔大。自思我娘生下我时,握着两个空拳头,未曾带得一分银来,及至将死闭下眼,又握着两个空拳头回去,亦未曾带得一分银去。何苦将七尺之躯不自爱,昧了本心做恶事,不顾名义、不畏法度。为子孙田产之计,贪了赃,私坏了名节,是卖其身以利子孙,此在不读书的人,则可。可以读书人,日讲天命之谓性,将《大学》、《中庸》、《论语》上下、《孟子》上下一句也不会使,甘自卖其身,入于恶人禽兽之归昏,愚甚矣!弟不才,滕县六年,不罚取百姓一分纸赎,节年拆封羡余银六千两,尽数登报上司;买谷十二万石,买牛一千头;两驿两厂并在县民壮,共计应役者整整一千名,未曾扣取他(它)一分旷役工食。见有滕县士夫董翼明公祖在固原做布政,可问吏部四年不接一分书怕(帕)。见有同僚吴继疏兄、刘石闾兄两个见做中丞,可问是财利关头,弟已打透。万历壬寅年四月五月内,横遭口语,科道并同僚及李对泉堂公一时参弟十八本,弟理直气壮,不少怵惕。权相沈蛟门密使两个心腹士夫探弟气色何如,两士夫回话云:‘好个铁汉子,颜色再不变。’是进退利害关头,弟已打透。人口头只说死,死全不知死时是何光景。盖人将死时,祖关之气先动。弟万历二十九年九月内,卧病九日,大便血块几筒,余血脱神离汗出,气散祖关,始气跳跃而动,自觉中黄好似一蛇游,翻来覆去有一个时候,到此时平日所钟爱的物一件也记不得了。弟用密诀,目光下垂看定中黄。稍时,气息略定。阎蓬头师傅所谓‘目光还而精气复’,只这一句,弟便使得上了,熟能生巧,此于验之。是死生关头弟已打透,弟打透大财利关、大利害关、大生死关,试较量世间事,再莫大过此
三者,为甚(什)么要紧,不一意修大丈夫事,甘为小人之俗行哉!莫说讲举业一艺,不可用滥时套文章格调,只这做人一件事,岂可不斩钉截铁,断绝财利一源。谩借口云:‘某贤者,亦如此,莫贤者,亦如此。’昧了初心,贪赃坏法,学此等滥时套之污行哉!”元庵兄又问:“兄何开口,便恨贪官?”曰:“旧云:‘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今不在官不在民,尽归于士大夫之家,俸粮柴马之外,皆为赃也。试看今之世界,三考吏出身做官者千千万万,无一人晓得义利两字。谁不爱钱?此等官卑禄薄,犹可恕也。吾辈读孔孟书,日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昧了本心,贪财害民做恶事,再不回头返照。我当日做秀才时,宁有十两银到手,俸粮柴马仅可度日养身,胡为如此?宁不深可痛恨哉!只论今时做官的未有一人不富的,则百姓之贫可知也。三原温见吾兄,一日骑一骡拜弟于于家庄,因相与乐谭(谈)两日,见吾兄笑曰:‘乾所兄专好讲性命。’弟应之曰:‘兄试看今之各名山大刹,其老和尚真正有戒行不吃酒肉、不犯淫盗者,约有三百多人,普天下士夫数三百个不要钱的,或屈指数不上来。”元庵兄抚掌一笑。
游艺海纳后序尝谓心思不通乎,性命不可以论,文章学术不贯乎,天人不可以谭(谈)。政事、节义是性命文章,政事、节义一以贯之,非两物也。吾夫子语:“游艺必先之志道。”据德依仁道,德仁即性也,命也。其艺之浑然者乎?艺即性命之灿然者乎?彻上彻下、无精无粗、合内合外,呜乎!游艺岂易言哉!太(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沧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余掩卷而思,乾所先生之《游艺海纳》至精也、至细也、至中也、至正也,有本焉,非一日而得,一蹴而至者,进乎,技矣。先生自做秀才时,好精养玄修,每求异人名公,师事之,不惮负笈之劳、跋涉之苦、冻馁之艰。真积既久,则太宇自宁,太宇既宁,则天光自发,白痰下于肠中,眸光飞若梨花。坎离交媾,复见天心。此其本原盛大而体无不具,是以从心运矩而用自无不周也。其为文也,不饰章绘句而理自工,不标门立户而辞自畅,发之为节义。任滕六年,不罚取一分纸赎,节年拆封羡余银六千两,尽数登报上司;买谷十二万(石),买牛一千头;吏部四年不接一分书帕,措之为政事。其仕滕县也,救荒均地,栽树积谷,垦荒田,立官庄,平道路,修公署,开运河,治仓廪,禁火耗,革税银,痛裁历来相沿浮费无名之征二万两。其任吏部也,进君子,退小人,抑权势,禁貂王珰,祛积蠹,绝苞苴,上疏裁京都吏、户、礼、兵、刑、工都(部)通大并五城各衙门顶收银百万两。其居乡党也,斋宿百日,两上疏,裁盐商,裁协济,裁里甲,裁冗官七员,裁县不属州辖,创陕西行省一条鞭之法,每年省银万余两。余亲见先生手无三分银,悠然自得,不怨不尤,一切尘嚣利名生死皆扫而空之,此非通性命达天德者,其孰能之,嗟嗟。先生惟透性命一窍,故文章、节义、政事,卓然宇宙观。山西抚台吴继疏先生荐举一疏,则先生之一生才品俱可见矣。区区游艺,岂足尽先生哉!故曰:“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先生游于圣人之门,故观于海而难为水,此《游艺海纳》所以立名也。先生筌蹄在笥善与人同,惟高明有志者,当自得之。余虽孳孳景仰,终不敢曰:“窥其藩篱也。”万历四十三岁次乙卯七月吉日宁州贡士辱爱友弟元庵杜春芳拜书注释:①《语》:指《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书。全书主要内容是孔子在谈话中对“仁”、“礼”、“孝弟”、“忠恕”以及其他一些意识形态的说明和解释。《论语》最后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它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定的。汉代曾流传鲁论、齐论、古论三种不同的本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论语》20篇是汉朝人在上述三种本子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论语》的注本为数非常多,影响大的有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
②漆园吏:指庄子(公元前360?~公元前280?年),名周,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秋水》篇载楚王使人聘庄子,庄子不应。从《列御寇》所载的情况看,庄子是一个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人。《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书52篇,现存33篇。后人以《逍遥游》至《应帝王》7篇为内篇,《骈拇》至《知北游》15篇为外篇,《庚桑楚》至《天下》11篇为杂篇。
③《六艺》:即六经,包括《礼》、《乐》、《诗》、《书》、《易》、《春秋》。
④六通四辞:六通谓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四辟指顺应四时,任物自动。后多用来比喻四面八方无不通达。
⑤仍孙:也作“礽孙”。古称从本身下数第八世孙为“仍孙”(八世包括本身)。又称“耳孙”。《尔雅·释亲》:“昆孙之子为仍孙。”亦称为“礽乃孙”。《太玄·玄数》:“九属,一为玄孙,二为曾孙,三为仍孙,四为子,五为身是也。”⑥举业:科举时代称应试的诗文为举业,又称举子业。《金史·元德明传》:“子好问,最知名,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⑦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商后宋国贵族。在宋曾任相礼(司仪)、委吏(管理粮仓)、乘田(管理畜养)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满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去而周游卫、宋、陈、蔡、楚列国,都不为时君所用,归死于鲁。曾长期聚徒讲学,开私人讲学风气,传说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72人。古文学家说他曾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虽未必完全可靠,但他熟悉古代经典,可能作过整理工作。由于他弟子的活动,形成儒家学派,对后世有重要影响。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通过自汉代董仲舒以来儒家的补充修正,他的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本人被尊奉为至圣先师,他的言论事迹见《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
⑧游艺:《论语·述而》:“游于艺。”原为孔子要学生沉湎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中。后亦泛指从事技艺或艺术锻炼。白居易《大巧若拙赋》:“既游艺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⑨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人。春秋鲁公族孟氏之后,受业于子思的门徒。游说于齐梁之间。未见用,退而与其门徒公孙丑、万章等著书立说。继孔子的学说,兼言仁和义,提出“仁政”口号。主张恢复井田制度和世卿制度,同时又谓“民为贵”、“君为轻”,称暴君为“一夫”。认为人本性善,强调养心、存心等内心修养的功夫。成为宋代理学家心性说之本。宋元以后,地位日尊,元至顺元年封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定为“亚圣孟子。”在儒家中其地位仅次于孔子。思想事迹见《孟子》一书。
⑩子贡:(公元前520~公元前?年),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也作子赣,春秋卫人,孔子弟子。能言善辩,善经商,家累千金,所至之虑和王侯贵族分庭抗礼,曾任鲁、卫相。
《五经》:儒家的五部经典。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五经即《易》、《尚书》、《诗》、《礼》、《春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本称“诗”或“诗三百”,经字是汉儒加上去的。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15“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诗经》其中早期作品大多数是宗教性的颂诗,对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但思想内容较差。自周厉王以后,周朝衰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时出现了一些抨击时弊的作品,是《诗经》的精华,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作用。《诗经》秦火焚后,汉代传《诗经》有四家,即齐人辕固所传的叫“齐诗”,鲁人申培所传的叫“鲁诗”,燕人韩婴所传的叫“韩诗”,鲁人毛亨所传的叫“毛诗”。自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后,学毛诗的越来越多,其他三家则逐渐衰废。现在流传的《诗经》是毛诗。历代为《诗经》作注的很多,通行较好的注本有:《毛诗正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诗集传》(宋朱熹著)、《诗毛氏传疏》(清陈奂著)、《毛诗传笺通释》(清马瑞辰著)。
甫:fǔ,古代对男子的美称,多用在名字之后。
《四书》: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南宋理学家朱熹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作为学习的入门书。元仁宗皇庆二年,定考试科目,必须在《四书》内出题,发挥题意以朱熹注为根据,一直到明清相沿不改。晷:gu ǐ,太阳光的影子。
股:即八股,明清科举考试的文体,也称制艺、制义、时文、时艺、八比文。因题目取于四书,古又称四书文。其体源于宋元的经义,明成化以后渐为定式,清光绪年废。八股文以四书的内容作题目。文章的发端为破题、承题,后为起讲。起讲后分起股、中股、后股、末股四个段落发议论。每个段落都有两段相比偶的文字,合称八股,故称八股文。
桀溺:春秋隐士。《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即曾参(shēn),字子舆、孔子的弟子,与闵于骞,是儒家鼓吹的孝子典范。《后汉书·明帝纪》:“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朱注:即朱熹(公元1130年~公元1200年)注,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宋徽州婺源人。晚年徙居建阳考亭,又主讲紫阳书院,故亦别称考亭、紫阳。曾任秘阁修撰等职,历仕四朝,而在朝不满40日。朱熹为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阐发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大学》、《中庸》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二程(程颐、程颢)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后世并称程朱。自元以来,历代王朝科举,均采用朱熹《四书集注》。朱熹整理文献,注释古籍,疑古文《尚书》之伪,不信《诗序》,多有新解。著作有《四书章句集句》、《诗集传》、《周易本义》、《楚辞集注》、《通鉴纲目》及后人编辑的《朱文公集》、《朱子语类》等。本文所说的“朱注”、“朱语”、“朱子”均指朱熹。轩轾:车子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轾。引申为文章的高低、轻重要适中。
李崆峒:即李梦阳(公元1473年~公元1503年),字献吉,号空同子,明甘肃庆阳县人。弘治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子”。文学著作有《空同集》。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曾编修《汉书》。
《圆觉经》:佛经名,全名《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唐朝宾僧佛陀多罗译。有宗秘《略疏》。记释迦应文殊、普贤等十二大士问因地修证之法门,一一对答。以世间种种幻化,生于觉心,幻尽觉圆,心通法遍,故名圆觉。
《中庸》:《四书》之一,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原为《礼记》中一篇。不偏叫中,不变叫庸,儒家以中庸尚最高的道德标准。《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于思:(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孔子之子孔鲣的儿子,名伋,曾为鲁缪公师。著《子思》23篇,唐后佚失。
趑趄:zi jū,亦作“次且”。且前且却,犹豫不进。
《楞严经》:佛经名,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唐天竺沙门刺密谛(华名极量)主译,乌苌国沙门弥伽释伽译语,房融笔授,怀迪证译。经名“首楞严”,华语乃“一切事究竟巩固。”经中阐述心性本体,属大乘秘密部。因经中多长生神仙之书。且标出地、水、火、风、雷、见、识“七大”,与佛教显宗的“四大”,密宗“五大”,宗旨有所不同,此经又不列入唐、宋、元、明四大藏,故后人对其真伪颇有争议。
子夏:(公元前507年~公元前400年),名卜商,字子夏。春秋卫人,孔子弟子。长于文学,相传曾讲学于西河,序《诗》,传《易》,为魏文侯师,有子早死,痛哭失明。
子游:(公元前506年~公元前?年),春秋吴人。姓言,名偃,字子游,孔子弟子。长于文学,仕鲁,曾为武城宰。
子张:(公元前503年~公元前?年)春秋陈阳城人,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孔子弟子。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察之间。《论语》有《子张》篇。
关云长:即关羽,字云长,三国时蜀国名将,以骁勇忠义著称。《三国志》有《关羽传》。
曹操:(公元155年~公元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年二十举孝廉,征拜为议郎,以参加镇压黄巾军起义,迁为济南相。后起兵讨董卓,迎献帝刘协,迁都许昌,又击灭袁述、袁绍,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他采取抑制豪强、推行屯田、督促开垦荒田等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经济的政策。后统一了北方,位至丞相及大将军、封魏王。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喜好文学,有《魏武帝集》。
子路:(公元前542~公元前480年),春秋卞人。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孔子弟子。仕卫,曾为卫大夫孔悝邑宰,因不愿跟从孔悝迎立蒉目贵为卫公,被杀。
貂珰:diāo dān g ,汉代中常侍冠上的两种装饰物。后即用宦官代称。
苞苴:bāo jū指馈赠礼物,后引申为贿赂。
筌蹄:《庄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鱼,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荃即筌,捕鱼竹器;蹄,捕兔器。后来以“筌蹄”比喻达到目的手段。
笥:sì,盛饭或衣物的方形竹器。
《游艺海纳集》由序、自序、正文、后序四部分组成,约1.5万字,以随笔散记的形式记录了师友平日讲书谈文之言论,附以己意,夹叙夹议,内容详尽,笔法朴实,说理透彻,见解独到。文章反映出读书人为求上进饱尝辛苦、遍求名师、不耻下问、足不出户、皓首穷经的治学之道和坚韧不拔之志,令人纫佩叹服。特别是赵邦清把作文与做人统一起来,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正色立业,注重道德修养,关心民瘼,憎恶贪赃枉法,鞭挞时弊,透悟性命,宠辱不惊,忧君忧民等思想,在今天来说,对我们为学处世仍大有裨益。同时由于文中所涉及的一些人和事,资料匮乏,无从考证,只能作个浅陋的注释,不尽如人意处,敬请读者谅解。
原文:游艺海纳序文章家虽一艺哉,然有道焉。进乎!艺矣,盖言心声也。所以抒写性灵,发挥其中藏者也。每戒于心之盈,而成于心之虚,盖盈则实,实则中坚。外距往往师心自用,虚则受,受则大罔不入,细罔不收。故末议可以佐圣,问察可成大智。《语》①曰:“江海之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也。”余读漆园吏②《秋水篇》:“百川灌河,两涯(法)渚涯之间,不辨牛马。河伯辄欣然喜曰:‘天下之美止此矣!’”及顺流至北海,不见水端。万壑注之不盈,尾闾泻之不虚,始爽然自失,望洋向若叹曰:“我今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子之门,则殆矣。”今世学者,公患大率类此,拘学牵于所闻,曲士来于所见,学一先生之言,守其师说,国陋而不变,一有所得,即敖(傲)焉。自智翘然,自喜此牛溲马渤行潦之流,“井蛙不可语于海者也。”亦有涉《六艺》③之圃,困百家之智,穷众口之辩,闻道已百第未睹大全,遂以为莫己若者,亦河伯之始自矜,及观海向苦,乃知不足,望洋兴叹者也,必也。穷无穷,极无极,六通四辟④,靡不学也,靡不师也,包裹天地,囊橐万有,注焉而不盈,的焉而不竭。泱泱乎,沧海大观也哉。余观尼父氏著《六经》,兼万善,苞孕上下古今,当时记之者曰:“焉不学无常师,有味哉!”其言之也,盖沧海不择细流,以成其深者也。嘻!斯至矣,蔑以加矣。今先生道德性命无不窥,文章政事靡不卓绝,而且缙绅、先生、长老靡不师,倘所称虚,受以成其大者,非耶。今其以《海纳》名篇也。意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万历甲寅岁仲冬之吉文林郎知合水县事通家门人朱芸顿首拜书道光戊子岁孟春之吉仍孙⑤荫生丕成谨抄敬录游艺海纳序赵邦清曰:“举业⑥,艺也。”习举业,即孔子⑦所谓游艺⑧之学也。游艺胡以《海纳》称?孟子⑨曰:“观于海者,难为水。”学者之心大不如海,则不足纳众善。子贡⑩,卫辉人。越十里,受学曲阜。及孔子没,庐墓六年,彼其学也。既不为仕进谋,彼其庐墓也。六年内,耽阁(搁)若干家事,盖真有见于真师,不可轻弃。当今士风日偷骄悍成俗,孰知学为何事?孰知求师之益无穷哉!邦清八岁时从邻村巩先生守谦学,及能成篇,从巩先生之子裕斋先生学,继从邻村李崇岗先生学。入庠时,在隆庆壬申年。邦清年十五,刘西坡宗师取首卷,乃在裕斋先生门下。后又从裕斋先生之叔寿峰先生学,寿峰先生授邦清以举业。彼时,欲遍师海内豪杰、顾路遥,乏资助,力不从心,独击节想象已耳。三水文少白先生住居丰川村,邦清住居真宁于家庄,两村相距三十里。适文少白先生自京谪归,先生成通《五经》邦清有负笈从学焉,授以举业,又授以性命之指。邦清闭户岁余,饥寒侵肤,苦极性灵,坎离交媾,悟门顿开,举业一艺始有入处。及少白先生赴京补官,邦清又拜庆阳傅太府逊斋先生,傅先生过目成诵,《五经》背记不差一字,天下异人也。时在门墙下几三年,举业稍稍入彀。万历戊子科,余汉城宗师庆阳类考,批邦清卷曰:“独隽逊斋傅先生。”当堂对五学诸生喜而言曰:“邦清卷批一,隽字诸生不知,盖智过千人。”曰:“隽邦清实一府五州县之首,不在真宁一县论后。”余宗师考延安过富州,对本道杜胤台公祖独许,邦清与庆阳府学关云石兄可中。是科初九进场,邦清初五日病,不入试,归来。李先生克庵忽自京来,先生亦通《五经》,邦清北面受业,教之曰:“文幸,艺也。学先立德。”邦清翻然改其旧曰习,检(坚)持于日用常行之际,心颇滋润,虽不讲学,而学之一字,常身亲体之,刻有李先生《语录》一书、《三生交砭录》一书。李先生入京,文少白先生正任湖广。寂寂寥寥,转盼无所资益,邦清同侄养贤闭户本村萧寺中年余,足不愈户限,一则攻习举业,一则修炼性命。久之,理水冲激,邪不能胜正,心窍内白痰从大肠下者升余,侄养贤所亲见者也。白痰下后,自觉五内清洁如玉,日每鼻闻异香,天气甫晚,两眼飞神光若梨华(花)大,累累继续不绝,颇知未来事,如此之兆,道欲成也。而有此矣,乃天发地应耳。此时,见大心泰略,无功名之想。至辛卯科,邦清以正贡搭类考,姜养冲宗师对五学,广文先生大许,邦清中。彼时,场中供事者有安化广文路先生、赵先生过,称邦清为宿学。又称为余汉城宗师得意士。姜文宗坚不与贡,曰:“贡了,他就将中的事误了。”次日,邦清以家贫母老解之,准贡讫。辛卯场中,邦清已在落卷中。八月二十一日,大主考麻十洲先生、于念东先生《诗经》正卷额已取足二十二名,却嫌《诗经》卷弱,特命西安刑厅李惟青先生搜阅《诗经》落卷,为李惟青先生当日原以《诗经》改《礼记》者,李惟青先生得邦清卷,大加称赏,力荐解元。麻十洲先生首肯,于念东先生嫌邦清卷太奇,李惟青先生同长安王念夔先生、及渭南崔际虞先生力在二座师处大讲,欲入五魁内。于念东先生辞曰:“此卷太奇,诚恐礼部细加磨对,我们要担当,姑置之二十名,彼磨至十二三名,力已倦矣,不为此卷之累。此卷高才,必中进士,论中二十名,实非此卷本等地位。”李惟青先生无奈何,随批邦清卷尾曰:“此卷不在魁解中,于予心犹有所不足也。”出场后,李惟青燕(宴)同门诸生,当席笑而言曰:“他的榜首必不中进士,我的赵门生必要连捷中进士,可惜未中个解元。”邦清侍侧,闻其语,亦甚恐。席毕,同门诸兄弟问会试场中文字如何作,李先生指邦清而言曰:“只照赵门生文字做去,必中进士,他的文字,就是会试体制,必定要连捷。”邦清入京住居报国寺一月,扃其户,凿墙以进饮食,不与人往来,果徼(侥)幸中壬辰会试矣。麻十洲先生拊其背,悲喜言曰:“我实实把贤友中解元,你于老师坚执不听。人言蚤(早)将贤友中个解元,连捷进士,我们体面,亦好看。只看贤友文字,必知后日正色立朝事业,勉之,勉之。”夫国朝设科取士,虽孔孟在,今日必从此出身。故举业不精,是不忠也。邦清随笔日所闻于师友者,集为一帙,名曰《游艺海纳》,末有附以己意,敢自曰:“我心如海,能纳万善。”亦惩于士风之骄悍,不敢忘日辛苦之功。晋此,聊为子孙举业性命之式。
万历三十一年岁次癸卯正月吉日赐进士出身吏部稽勋清吏司郎中真宁赵邦清撰道光八年戊子二月初三日仍孙荫祀生丕成沐浴敬录于恒心堂中赵乾所游艺海纳真宁乾所赵邦清仲一甫纂著男赵任贤赵崇贤赵淑贤同校寿峰巩先生曰:“汝等看书一字不可轻放过,即如《四书》之外注,各《经》之断章性理通鉴之小注,皆宜仔细推寻。至于作文,即以此看书,细心出之,务要极其精密,若清空说几句便了,或不足胜人,或不足入主司之目。又要时时看新文字,不为旧套缠缚。窗下作文,不可贪多,须苦思推敲,方可上真,即如结题一件,当场考试时,若是草稿上不预先改作停当,场中掌号催卷上真,时促七结,不免苟且信笔写去,必多潦草不雅,何也?窗下草率成习,手段已熟,未有临场能细加点检者,况场中风檐寸善,又非窗下比也。”文少白先生曰:“作文之法,须宏大深入,宏大,则气象不小;深入,则以我之身直钻入题目里面去发挥,岂有不透彻的。盖题须讲开,方才有许多意味。若只求干净,恐家数狭隘,纵是金玉之句,亦不济事。文章须忌旧曰日套子,一翻丢过,各人另寻机轴做去,自是新奇。”我辛未年会试场中,曾犯此病。“生财有大道”一节,破云传者,竭言理财之要,而因著财之所由,裕也。看来千人都是如此比,殊为厌观。故归家,日搜读古文,以变文法。甲戍(戌)年会试场中,如“学如不及”一题,众人皆用知行,我却不用。田钟台先生取本房首卷,以我表句落韵,主考者置之十九名。讲长题不必牵合对股,当以意敷衍下去,圣贤言语皆有次第,岂可只图整齐,不究血脉。如“定之方中”一章,旧文皆以首章为主,下以升彼,虚矣。对“灵雨既零”一章,今却散散说去,归重秉心塞渊,何等联属。自乙酉科之后,长题皆用总括之法,然亦有不必总括者,岂可恃之为常。近在京师,与一二知文者论之,长题当实讲处,须实实讲去,不可架空。先要辨其体格,次要点检轻重所在。大抵长题股法,不得漫长,一层挨一层下去,则意思缜密,气味不断,此当以意深会之,可也。至于缴处,把题目起落处说成一团,尤为妙手。
“文章要老成,然老成者,易失之于古板,殊觉意思不活。汝辈今且从疏散流动处学去,后来再加收敛。不然一意炼句炼字,纵想起数层佳趣,亦不敢用邦清文,老成是矣。然岂可不学宏放流利以济之哉!”“文章是个精纯的物,比不得作论的言语。近见邦清学疏散流动,复觉有不切实处,股数有漫长处,然文字中一句闲话也用不得。‘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至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此题只就本文讲,犹恐说不出,汝却于入题处说许多闲话,岂不泛漫。”“文章最怕有粗句粗字讲理,题逞不得奇,粗题要细做,造句不可长。盖句碎则意密,颇有折转,若几句长话成一股,则直而无文矣,须委婉其致,则佳。”“如讲‘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一题,就宜以桀溺口气讲去,起讲即用想桀溺之意,若曰殊为省力,时人不知此桀溺调,起处既用己意断之,至入题处才用桀溺口气,是一隔矣。此先生之言也。戊子科,余文宗类考庆阳,出‘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一题,众人皆用孟子口气作起讲,至入题处方用曾子之意,是费了多少气力,且意绪不贯。邦清于起讲处即想曾子之意,若日一篇皆曾子之言,至缴后,略点出孟子意。余文宗批曰:‘阅卷惟子独隽。’”“如讲‘鲁无君子者’一题,鲁多君子,分明是正意,然题面却是鲁无君子。文章须从鲁无君子实实讲去,盖鲁有君子,此客语也,客语多,则不像题矣。其余皆以此类推之。”“讲‘齐之以礼’一题,不得不承道德来,然只一处用之,可也。若用道德意多,则客语胜矣。”“讲小题要凌驾,然凌驾之法太烦,则不切题,宜忌之。”‘讲大题须循题目起落去处实讲,其格调有不可那移者,甚不可弄巧凿坏体制。”“近在泰州,见南方文字原与北人不同,北人总不离套子,南方文字一句套子也不用。邦清今须从新做一番,始得超脱。勉之,勉之。”“文章讲毕,虽当有几句余波,然不可太多中间立柱。如知行、道德、事业、物等类,一过目即令人痛恶。况近来虽用柱眼,又却不显然明白露出。此二比,最怕一直说去,要得起承转合之法。”“文章胜人处,原在起讲入题处。与末后二比,并缴题此处,着实要立些意思,发些议论,起讲就说到题目上,与入题处相递接下,此法最高,不见痕迹,尤没间隔。”“一句起题,末后二比古劲,则缴题宜圆,后二比流快,则缴题宜方,又须格调各异,方见顿挫。”“一句题末后二比宜加苦思,极力研磨,则趣味深长。盖中间二比与小讲二比,此皆众人所易。能者惟此二比,则错综(纵)变化,每无定局。”“缴题有单收格,有双收格,有散收格,有反收格。若入题处反了,则缴题不必反,恐犯重复。”“一句题小讲处用流水文法,则末后二大比不必用流水;若小讲处以意对讲,不用流水,末后二大比方可用流水文法。”“文章自起至缴,要意思宽缓,步骤从容,甚勿急促之句。”“文章着实要句句推敲、字字磨炼,一句不妥不必用,一字不雅不必用。”“对股数如上比已成,而下比或字眼难凑,不得合上比,须把上句做成的句法字法,稍加更易,则下比即成矣。不可死执着上比已成,故将下比扭捏强对。”“通篇文字意思要多,议论要大,不然则弱矣。况作一句题入讲处,并二小比,中间二大比,末后二大比,并缴题,亦当用十比方可。”“作一句题,题目字面略略点破,即了。若用他本题字面太烦,则为露骨矣。”“今日之文,纯正典实,是的局也。”“奇崛不平,文之大病,宜戒之。”“作文之法,全凭思索功夫。”“作文之时,要立个排山倒海之势。”“讲‘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七句题,起讲宜浑浑说下,不可露容貌等字样出来。所贵乎道者三稍讲,六句接下去将动容貌,六句的意思总发。二小比亦不可显然露出容貌暴慢等字样来。至容貌三段着实发挥,末段缴题只以意咏叹,亦不可露容貌暴慢等字样出来。众人作此题皆用修己治人意缴之,惟少玄虽用修已治人的意思,却无修己治人的字面,独觉大雅。”“讲‘战伐’题,须用征战等字面出来,不然则腐矣。不见行阵威武的气象。”“文章有当讲毕而一句收之者。如‘一齐人传之’三句,若上文内一一讲日挞字面则不佳,讲完后,当当云此。虽日挞求其齐也,岂可得哉?再咏难(叹)数句,即了。”万历十八年八月内,先生自南京回家,邦清谒之。先生曰:“文章须识体,汝知之乎?”逊斋傅先生曰:“生文章先要净,不可有浮浪之气。”“善作文者,一句有一意思,一字有(一)意思。不善作文者,一篇总是一意,一比总是一意。殊无结构,文以辞胜不如以意胜,修辞不如注意,况一篇文字不过四百言,若非以意翻腾,则单弱无力矣。”“作文全要看朱注,如‘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朱注分明说‘甚言,其不可也。’众人皆云,利亦可为。至缴处方说不可为,岂不背驰。”“题中有的字面亦须点出,如‘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一题,邦清此题文亦佳,但温恭字面未尝说出,似欠分晓。”“破(题)要精而约。”“承题不可说的意思太露了,太露则文章无味矣,此养文之法也。起讲虽不可太骤然,而无用紧的话宜裁之。起讲末接入题处,要极力讲开。此处全看的手段,不可草草便了。至首二小比、中二大比则人皆可到,末二比须要深思。入题处既用反振文法,中二比一句也不可反振,若反振,则又似起头语矣。作文全怕露了,下文汝宜忌之。临场时,将易犯的字面写在稿上,时时对照,也省之一助也。作文要用自家的意思去讲,不必想某人的句法如何、股法如何,旧文章讲此题如何,若用他的唾咳,亦不中用,终不见长进。”“文字太奇,固不雅,然亦不可太平,要平中见奇拔之趣。”“近日起讲用‘盖臣察相’等字,殊为作怪。又如云:‘司政柄者,孰不欲?’某某又云:‘人君享太平而乐盛治者,岂独主德茂也哉。’皆为常套,宜加痛改。起讲末句又云:‘吾有见于某,吾有感于某,吾有慨于某’,深可笑也。所谓诚其意者至下节,故君子慎其独也。见一生将上节总分成好恶二大比,大非体格义理,有次第当轻处,固不可缠他(它)。然亦须挨次第说去,始觉详密。”邦清当应试日,傅先生勉之曰:“汝之文,气清辞爽,是矣。第一意学清,则中无隽永之味,恐题意发挥未透。临场日,须苦心注思,俾淡而不厌,可也。”邦清作“乐天者,保天下,至于时保之”一题,过文用八句,先生面命之曰:“亦宜调剂似此,则太多矣。”克庵李先生曰:“作文之法在不俗、不冗、不浮、不泛,不学套作。长题即当从题目起处下手讲去,若牵扯上文多了,是今之题不从原起处出,而从上文出矣。况题目大了,时时要剂量轩轾。当总括处固不可不总括,若不必总括处只从题目起处说去也。好长题如有问答者,体口气与不体口气皆从临时权衡,不可执定一格常作主意。”“嘉靖年间,文字尚实讲。至万历癸未科以前,稍清空矣。近日请过圣旨,复尚实讲,大抵要把题目讲透。盖各人平日有独得之见,原宜诸此细细说出。”“作文须尚骨力,我与邦清以李崆峒时文正取他骨力,可法也。试细心熟玩之自见。”“作文要有气,所谓气者,不在篇段之长,只是要不弱,不断续耳。”“作论之法,如破题用某字作主,通篇文字全要照管着他(它)。论冒(帽)亦须浑然,不可讲的太露了,太露了则正讲处无味矣。且冒(帽)上又不引证譬喻,又有不作论破论,冒(帽)而直直叙起者,格体甚多,以意会之。可也。”“作长题须一步一步照顾题面,不可只逞一己之论,挥霍出者,去用句用意也。要称量,一不称量,则害事矣。”汉城余宗师考西安府学,出“升车,必正立执绥”一题,有一生中间既讲了正立,讲了执绥,末二比又复讲正立执绥,至缴题又复说出。文宗批曰:“正立执绥中间已讲明了,后二比只宜以意敷衍,若复用正立执绥字面来,则太赘矣。”又曰:“正立、执绥须并重,众人偏重正立,殊失却了题旨。”出“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题。有一生入题处未曾提掇。文宗批曰:“此处步骤似乎太紧。”西安府学生张起凤作此题,既先提掇二小比,末二比后,又复咏叹二小比,则碎点之。有一生中二比用“知其一,不知其他”的字面。末二比复显然露出“知其一,不知其他。”文宗批曰:“太赘。”故置之三等。
考贡出“故曰,域民不以封强之界”二句。有一生点出“故曰”字,诸生俱无,文宗独许之。有一生发题上三“以”字,文宗曰:“将正经题目你不去讲,却发‘以’字,何也?我不责汝,汝亦不改。”朴责十板。
出“邦有道谷”三句题,考贡。朱注曰:“宪之狷介,其于邦道无谷之可耻,固知之矣。至于邦有道谷之可耻,则未必知也。”众人执着此意,皆重无道一边。文宗曰:“夫子当日原是平说,生等何故偏重无道?可恶!可恶!”考庆阳府,出“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一题,众人皆偏重义上。文宗曰:“曾子当日原是说你有你的爵,我有我的义。生等俱重义上讲,岂不左矣。且讲义字俱用心之制事之宜,此用在义以为质上的义字做讲,则可。此义字亦当相题,当云首出庶物之。彼之爵人皆仰其尊,而吾之义则刚方正直,常伸于天地之上,卓冠群伦。彼之爵人皆羡其贵,而吾之义则光明正大,不屈于万物之下,秀才作文全要相题心之制事之宜,怎么与爵相对?且诸生中又有一种,只讲彼以爵,我以义,全然不讲如何是义者,不讲义字,如何对得过爵。”华阳张父母曰:“文章句法全要古径,中间二比须讲九句十句,盖发题全靠此二比,末段缴题不可草草,极力发挥,才见气力优长。作文之法,先要求其匀,以一篇言,自破至缴须匀;以七篇言,自首篇至末篇要如此一样匀。盖文字匀,则中矣。”“作论之法似不必搜罗,要详,详就题上靠实讲去。作文全要识体,近日文体须庄重古雅,若昔年孰话常调,用在今日如何行得。如一句题初头二比极要精确,一个闲字不可用,且平仄又当调之,使读之者有铿锵之声。末二比,近日多用虚实之法,然先虚一比,亦须着题,毋令实胜乎主。束题亦须大发扬之,不可略说几句便了,且如人之说话,虽毕,亦当委婉,其意致没有个齐头故事。”
三水文和一先生曰:“起讲说得几句,就要接到题上,昔人所谓开门见山,是也。”
三水文望云兄曰:“文章全要翻过,时文不为旧套所拘,夜间思索功夫,甚有裨于文字,吾弟图之。”
三水文少玄兄曰:“作文之法,须宏博深邃,纵有一二不妥当处,被阅文者抹之,何害?但场中则不可仔细,若怕人抹,有的话、有的意思不敢写出,只求一是便了,终不得成大器也。”
三水马羲川兄曰:“造句不可大快,须深着些方好,若只求流利,则不见庄严之体矣。”
三水文起旸兄曰:“会中某人文字可法,我等即当效法他,全把我的文章模样丢在一边,做出来全然不似我旧日模样,则大进矣。”邦清一日作“居敬而行,简至雍之言然”一题,起语太烦。三水张醇儒兄驳之曰:“这等大题,只实实靠本题讲去,犹恐说不透,兄何必用此许多闲话?”今日想之,醇儒兄之言,直中吾之膏盲。
庆阳赵寰兄曰:“乾所文字只以意胜,却不着意炼句,然句法古健,亦文中秘诀,乾所何略之?且句中或裁一两字,或添一两字,不腐不庸,则句工矣。冯聚垣兄最善炼句,乾所当则效之。”庆阳赵云衢兄曰:“乾所文字其格调原与我辈不同,然却多不炼,或剪裁其冗漫,或消融其查(渣)滓,则文字便精炼矣。”环县吴诚轩兄曰:“予昔受学于黄葵阳先生,彼教之曰:‘作文之法,纵有想起的好意思,且不必用的蚤(早)了,须一步一步漫漫说去,至末二比与缴题,才宜把前边想起的好意思发之,令阅卷者读至此,精神愈奋,愈称奇矣。’”镇原董昆兄曰:“乾所兄之文,极是认理,然亦不可直头直脑说去,须委婉其致,至于炼句尤当俊雅。”固原赵诚斋兄曰:“作文要将题意发透,须立个大气象,把天地就入在我胸中,则举笔自是宏扩,若求是了,则家数小矣。”一日在京师拜李渐庵老先生,适遇李九我先生来,予请问场中如何阅卷,九我曰:“文字只看半篇就知其人,不待竟篇。大要作文须于末后二比并缴题处,议论趣味滔滔不已,则刮目矣。”又曰:“今旧,时文起讲上就要透出题意。”侄养贤曰:“做文章全要把正题讲透,处处都与他(它)说到圆圆满满。就如写大字的一般,其方法在道径(劲)二字。道者,圆满充实之意;径(劲)者,不腐不弱。若只求光光净净说几句,便了,无大议论,无大结构,何以胜人。”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科六月,邦清尚任滕县知县时,在曲阜伺候。
文宗徐石楼先生类考。夜间书此寄示长男任贤:作文不可用一句佛老之语,亦不可用一句熟套语。你自来未看佛老书,凡坊间所刻时文,有用佛老语者,你就喜他(它)句法新奇,入之于文。主司学问渊深,看见是佛老语,你何自而知其为佛老语也,可笑!可笑!至如熟套赵甲用的固是,钱乙用的亦是,他一见便令人憎恶。凡遇题目,各人就题生意,自家做自家的文章,说自家的话,不得偎人的脚汗,拾人唾咳。昨与福建代振宇年兄讲时文,彼谓全要平正中见奇,太平则庸,太奇则怪。当以意斟酌,如今冯祭酒有本《文章要限》四百字,全要向典实处做去。奉圣旨礼部知道,想是各省主考官都照此旨取士也。发来冯祭酒本,可细心看之。策不过是圣学、圣治、灾异、东倭理财、并北虏战和之说。初三日夜一更时候,我在曲阜公馆内,请曹应聘、张九经两作家到,因问任贤之文,其病症的在何处,今当进场之时,大家实说,使彼知所改图。二生对曰:“大哥之文,不患不高,不患不古,不患不奇,只是欠平正,欠熔炼。”我亦想来,这四字是你对症之药,你进头场时,要将平整、庄重、醇洁、深厚、典实、熔炼十二字写到号房板儿上,字面重复全是你的病症。如“默而识之”,起讲处用了闻见,大讲里面又用闻见,字面偏枯,亦是你的病症。如“默而识之”,以不识不知对意言象数,又浃洽融液对无言不悦,是也。盖意言象数,是四个实字,又是四意。不识不知,只是两意,怎么对得过意言象数乎?浃洽融液又是四实字,无言不悦只是一意,怎么对得过浃洽融液乎?这个谓之偏枯之病,作文一开手(首)就当晓得重复偏枯之病而改之。况做大秀才到今日乎,如此之类,皆当推类而广之,急图改之。
场中作文还有一诀,我之乡试、会试,其头篇完时,都是近午时侯(侯)。盖一句不肯轻说出,一字不肯轻放过,则念头清净,光明如水止一般,刹那,气已定,息已停,纵有不好处,我自家都照得出来,及至二篇三篇,则气愈定,息愈停,口鼻气息全无,元始真性归入祖关,笔下愈神。若到经文上,则本立道生,生机逼,逼而出,真有不容已之势。你若把头篇轻易放过去,则气便粗,息便乱,写出的不好话头,都当作好文章,自认之矣。你那“白雪之白”一作,真是会试场中文字,练之极精,磨之极细,观者便自是认得。如今举子亲手写的乡会墨卷,另束在一边,主司全不经目,只是看那誊录生誊过的红卷。你将七篇誊毕时,且莫心忙,再将七篇文章仔细念诵、推敲一遮,如有闲句、闲字,随即裁剪、锻炼,再改一遍。只要填注的明白,令他誊录生好去誊写,不怕改的黑黑的难看。我乡会两场,全得这个功夫。盖先草(抄)一遍,既仔细改之矣。及至誊过真,再改一遍,便是两遍功夫。到那其间,人人都慌张,谁人肯如此两番做功夫。改至两遍,则闲句、闲字既已剪削净尽,一看便觉古古棱棱是个商彝周鼎,比之寻常,奚啻百倍,再分(吩)付(咐)你草稿上做一篇,就把一篇改定,如一字不稳,且莫做第二篇,就是结中一字不稳,且勿自恕,先做第二篇去也。认(任)他老军叫嗓,切莫心忙,你只将七篇仔仔细细做定,就是到四鼓誊真,盖亦不怕。只恐草稿未定,一听老军催卷乱嚷,就是脚忙手乱也。休听人说,先誊
三篇《四书》,已将精神用过四分去了,却拿甚(什)么精神去做那经文章。一总七篇草稿,都无一字欠缺,方才下笔誊真。
闻说省城有一伙不进学的老童生,结党成群专在院里妓者家行走,日与妓者教曲子正字。妓者将他们打在里手内,着意敬他。每遇科举之年,这一伙老童生引领一伙不做生理的尖儿手油嘴光棍,在舞生坛、迎祥观、开元寺,及桥子口、白鹿湾一带,专一替妓者打听找问某公子在某处住歇。某公子在某处住歇,可以勾引嫖宿、骗钱、吃嘴。当未进场之前,即使赵甲勾钱乙,又令孙丙勾李丁,淫荡人家多少好子弟,败坏人家多少大美事,岂不深可恨哉?三年一次科举,父母之心,并乡党亲戚,谁不满望高进一步?岂意会省之地,有此等无耻之徒,勾引人家好子弟干歪事。汝等当大着眼力,坚定心志,须想父母起送科举之心,攀(盼)望眼穿之心,及乡党亲戚属望之心,家人往来翻沟越岭、过河渡水、接送受苦之心,岂可轻听此辈勾引,而先丧其自己之良心乎!戒之哉!戒之哉!邦清时在曲阜,既寄长男任贤以作文之法。次日,滕门生曹生应聘讨看书稿,因相与问答应聘,遂备录之。
曹生应聘讨看书稿毕,起而问曰:“老师云:‘场中做头篇一句不肯轻说,一字不肯轻放,则念头清净光明。刹那,气已定,息已停,纵有不好处自家都照得出。及至二三篇,气愈定,息愈停,口鼻气息全无,元始真性归入祖关,笔下愈神。若把头篇轻易放过去,气便粗,息便乱,写出的不好话头,自家都认不得。’此其说最玄妙,前乎未之闻也,请明言之。”曰:“昭乎哉,问也。心属火,火能照物,思虑驰,逐则火力分,故不明。试观有等不知道理人,忿欲一萌,热中燥烈飞扬,焦发赤目。船子和尚所谓:‘一波才动万波随。’是也。惟念头并归一路,收敛沉潜,则湛一清虚,无所不照,故本立道生。班亦曰:‘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阳在上,卑阴在下。礼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锐也。人有道心,天本在上,故心下锐也。”应聘又问老师云:“元始真性归入祖关,请问祖关何指?”也曰:“禅门功夫,惟‘心路绝,祖关透’六字为入定之妙诀。心路不绝,则祖关不透,祖关不透,则心路不绝,玄门密诀。”亦曰:“气入玄元,即达本来天真。盖人之所以为人者,呼吸之气也。呼吸之根在两肾中间一虚窍,而鼻特呼吸之门耳,何也?鼻出入气高而有窍。山亦有金石累积,亦有孔穴出云布雨,以润天下,雨则去消。鼻能出纳气也,而其根则在于两肾中间一穴。盖两肾中间,白膜之内一点动气,大如筋头,鼓舞化变,大阖周身,薰蒸三焦,消化水谷,外御六淫,内当万虑,昼夜不停,此之谓祖关。念头清净,则口鼻气息全无,口鼻气息既无,则元始真性归入祖关,就是入定了,定生慧。一道神光勃然磨灭不得如何,文字不精力、不光彩、不超出乎、人也。惟实用其力者,知之真。故言之亲切而有味,这原是举业正脉,彼未尝实用其力者,与之言,云而,云而。如以华语绎番经,投之多不入。”应聘又问老师云:“心路绝者,何说也?”曰:“心有所行之熟路,遇境便迁,故名之曰:‘心猿意马。’《圆觉经》云:‘居一切时,勿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辩真实,到此地位,则一念不生,前后际断,照体独立,物我皆如,心路绝矣。心路绝,则主人归舍,祖关不期透而自透矣。”应聘喜曰:“老师何所闻而言之,亲切若是?”曰:“学不遇异人,则心地不扩大,识见不高远,此岂但为举业之机枢哉!天德王道将一以贯之矣。予鲁遇异人,不敢举其姓命。异人,乃元朝人也。密传口诀,而又十数年来,日下苦功,受过无穷冻馁,冷处生清,清处生明,岂易言哉!《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子思分明以一‘潜’字说在《中庸》一部后,收煞至诚、博厚、高明、悠久之功业,而人不之省,惟朱子见得到。故曰:‘颜子深潜,纯粹潜之’时义大矣哉。”应聘又问曰:“即今大名家都说举业自为举业,老师开口就先说到性命上去,何意也?”曰:“学不深于性命,则悟门不开,胆气不大。就是有当深讲处,自家见理不真,便趑趄踟蹰,不敢深讲。惟透了性命之窍,故横说、竖说、正说、奇说、长焉、短焉、生焉、熟焉、肥焉、瘦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均有一段垂世之语,精光到几时不减。如令的文体一敝不讲理,不发挥题意,专一务为雕镂,神情都失,此不透性命之故也。正各省学道,当力挽其颓风,时也。”应聘又问曰:“性命二字《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不知言之者几朝代,辩之者几万人,卒不得其解,愿详言之。”曰:“世间一切枝(技)艺作能百务之巧,各有专门,况有性命大事乎?性命亦各有专门,专门则精,吾辈书生之据书本子上论性命,犹之画饼充饥,饥卒不可充。且说宇太定者,发乎天光。书生只将天光作做腹内聪明看,殊不知宇太定者,到晚来天光累累,飞出眼来,若梨花大。到此地位,眼底尚有尚书、阁老乎?且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书生只当作冬至子时,谓真下起元一阳来,复便见得天地生生之心。然天是一大天,人是一小天,论及人心之复,则个个罔觉,殊不知人心到复时,忽然心头上一点凉如冰,移时方落入中黄去。此乃火在下,而水在上,水火既济,方自知其复,方自见得天地之心,以一书生欲讲个复其见天地之心,何处入手,且说明心见性。学者必说明了心,便见了性,至诘之。”曰:“如何见性则芒惘然无以对,殊不知天之下,地之上,上下四方纯是块一性,无少欠缺,无少渗漏,故曰:‘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体物而不可遗。’”又曰:“‘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朱子曰:‘如鱼在水,外面水即他(它)肚里水。鳜鱼肚中水,便是鲤鱼肛中水。天之命,是人之性,人之命,是天之性。但太虚之性,谓之母是先天之性,在人之性,谓之子是后天之性,人生而有此性。至于形生神发之后,知诱物化阴,浊胜而阳明。微子不亲母,子日离于母远矣,如何得见,果能物转情空,情反性易。则子渐就母,母必恋子,先天自虚无而来,眼里便亲见得是以子气,而感母气。’张三峰曰:‘万船景界皆非类,一个红光是至真。此个红光生异象,其中若有明窗尘。中悬一点先天药,远似葡萄近似金,到此全凭要谨慎,丝毫念起丧天真。待他(它)一点自归腹,化作身中四时春。一片白雪香一阵,一番雨过一番新。终日绵绵如醉汉,优游只守洞中春。遍体阴精俱剥尽,炼作纯阳一块金。此时气绝如小死,打成一片是全真。’是先天之性,我亲眼见之,而终归我之身。书生荒疏何曾到此方,所与之言,见性不笑,则骂之矣。”应聘又问曰:“性之一字终,何解乎?愿闻其说。”曰:“元始真性,谓之性。”应聘又问曰:“人死则性何在,性亦死乎?”曰:“性者,生也。生之谓性,性何尝死乎?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环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蚀之交有时,达循环之端者,知死生之会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对月而明,夺违对而月朗,是故死之换生,而魂化死过而生,来生之忘死而识,空失忘而死见。然则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见,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见矣。且薄蚀之交,不能伤日月之体,死生之会,不能变至人之神体不伤,故日月无薄蚀之忧。神不变,故至人无死生之恐。《楞严经》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时见恒河水与今无异,是汝皮肉虽皱,见精不皱以明身,有老少而见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问隐者刘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尔不与形俱灭者,固常在也。’《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庄子曰:‘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伊川曰:‘尧舜几千年,其心至令存。’横渠曰:‘物物故能过化,性性故能存神。高峰和尚曰:‘若要脱生死,须透师祖关,毕竟将甚(什)么作关,唤作竹篦则触,不唤作竹篦则背,不得有语,不得无语,若向这里着得一只眼觑得破,转得身,通得气,无关不透,无法不通,头头示显,物物全彰。无边刹境,自他(它)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天如和尚曰:‘裂开烦恼网,击破生死关。幻形幻影,有去有来。侣浮云之出壑,真性真明不迁不变。如皎月之当空,即此是自己根源,即此是故家田地,即此是安身立命处,即此是成佛作祖时。’无用全和尚曰:‘这一点灵光穷劫不坏,永常无朽,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凡圣两忘,中道无拘,空空廓廓,自自然然,辉天鉴地,分毫无碍,佛祖凭此称号世界,凭此安立无有,一般不从此性中所育生也。可(何)以为人,先须悟性,清净无为,皎然明白,生死本无妄尘所惑。性如精金,尘如杂矿,矿净金纯,任君使用。妄尽尘消,情真洞明,随汝作用,若穷性理,分毫无碍,一念也无,受用无量,永劫常存,灵通觉遍,教化众生,了生脱死。满各人悲愿,报佛祖深恩。’达观禅师曰:‘人是有形之鬼,鬼是无形之人。谓人鬼有两,心无是理,只是有形无形差别耳,信乎?性则必生观月之印水,则知性之生气矣。观火之传薪,则知性之生形矣。’顺真子云:‘形不能生形,生形者,非形也,气也。气不能生气,生气者,非气也,性也。’又云:‘形之万殊化而不留,惟气之一者不变。夫气之不变者,殆有所以不变者存,不变者存,盖指性而言也。’”应聘又问曰:“老师云元始真知,谓之性,以知言性,果何谓也?”曰:“知者,性之灵也。知非识察照了分别之谓也。是性之虚圆莹彻清通净妙不落有无,能为天地万物之根,弥六合,亘万古,而炳然独存者也。性不可得而分合增减,知亦不可得而分合增减。圣凡与鸟兽草木异者,惟在明与蔽耳,是故学莫先于致知。”应聘又问曰:“何谓识察照了分别之知?何谓性灵之真知?”曰:“精乎哉!问也。识察照了分别者,意与形之灵也。亦性之末流也。性灵之真知,非动作计虑以知,故无生灭。意与形之灵,必动作计虑以缘外境,则有生灭性灵之真知。无欲意与形之灵,则有欲矣。今人以识察照了分别为性灵之真知,是以奴为主也。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谓圣知者,明也。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者,知也,性也。父母未生以前先有其明,生身之后自染混浊。明而不明,然人性本明,染则浊,净则寂,寂能灵,灵能通达出生死之道,永作长生之至。人也,天之知,日之明,是也。人之知,心之灵是也。朱子亦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日秉阳,精最热。知禀阳明亦最热,热则有所触而必透,必生神仙之体,如火热纯阳故也。’此非大悟人,何可语此?予每清辰(晨)蚤(早)起,精神多不畅。忽然日出东方。一被日光热照,此身则精神顿畅。自思是我之子气,见了天之母气,两相亲洽,天光渗入心光故也。性明而热,是予日久体察悟出的,不在书本子上抄出的,此学惟曾子见得真。孔子没,子夏、子游、子张欲以所事孔子之体,事乎有若。曾子驳曰:‘不可,秋阳以暴之。’周正建子,今之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是周之春,今之二月、三月、四月是周之夏,今之五月、六月、七月是周之秋,今之八月、九月、十月是周之冬。曾子,周人也。曾子所谓秋阳,是以今之五月、六月、七月作秋,乃五月、六月、七月之秋阳也。日中则盛,每日午时,日光甚盛。月中则盛,每月十五,月光甚盛,四时之中则盛,每年五月、六月、七月为时之中,阳气甚盛。人心之中则盛。吾人固守中黄,则心火力全既明,且热而盛。曾子所谓秋阳,乃五月、六月、七月之正阳乎!今人但知性是个明的,不知性则明而热,惟曾子说出‘秋阳’二字。是兼明热而言之也。近日,阎蓬头神仙中之铮铮有名者,王凤洲先生文章性命一代高人,师事阎蓬头。每言蓬头当五月、六月、七月之时,辄裸而暴赤日中不汗。蓬头盖借天日之光,欲渗入本心之光,而人不之省。关云长辞曹操书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之上普照万方,心在人之内以秉丹诚者,性之明而热者也。时人常曰某人好一付热心肠,惟有热心肠,故见善必好,见人必爱,见义勇为。彼见善而不知好,见人而不知爱,见义而不果于勇为者,皆是心力不全、明之不至、热之不至之故耳。汝试细心思之。”应聘又问曰:“自来论性未有敢以明热言之者,老师云性明而热,不亦起人之疑乎?”曰:“论性者,古圣先贤不敢妄议。只说令之论性者,不向自家身上去体察,只据书本子上取,便口头说说之何益。此心之灵明逾乎!日月其照临有甚于日月之照临,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薄屋之下。此心之神无所不通,此心之明无所不照,此明之之说也。一斤熟肉置之锅内,着力武火烹煎三个时候,未必能化为汁末;一斤熟肉吃在肚内,延至三个时候,便化为汁未矣。外面火力有如此之神而速乎?汝试思,此三个时候肚内能化一斤熟肉为汁末者,果有形之胃乎?抑无形之性乎?若与拿书本子的腐儒说他(它),便笑予为迂。孔子曰:‘民不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此热之之说也。”应聘又问:“子路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毕竟何说?”曰:“窘乎哉,问也。当下若明,死后可知。若当下不明,何知死后也。若当下知归,如远客还家,不明径路,终成迷谬。若明路径,不惟知途中境界,亦自见家中事业。若但事口耳言说,欲进此道,则大错矣。所以古人云:‘欲明大事因缘直于衣线下。’日用寻常一一知其从何所来,自何而去,是谁起是谁灭,觉知起灭者,复是何物。如此存养,自知佛真法身不向他求,惟此现前本有自不滞,有不滞无不离,有无了了。常知不妄不变,随缘自在,若生染着,即为非心故般若。《经》云‘若心有住。’即为非心妄心若歇歇,即菩提不从人得。所谓菩提者,即知也、性也、觉也、心也。若悟此心,便识妄有去来,妄有起灭,若实自心,即无攸往不真,待何?”应聘又问:“当今士夫俱碍口,不敢谭(谈)禅老。师论举业,则云作文不可用一句佛老语,至论性命,则多引佛老语,何前后不相顾乎?”曰:“论举业,严禁不用佛老语者,尊朝廷之令甲也。孔子分明知周末文胜不好,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郁郁乎,文盖鄙之也。’然亦必曰吾从周论性命之学,则必引佛老语者。以性命之学,佛老原是专门此学,极精极细。不是真见性命、真拿住性命的人,何敢轻易漫谭(谈)。士夫窃用其语,调理自家性命。至讲论性命,则专辟佛老语,未免有偷心在。学道之人,第一怕偷心安下种子,安下这偷心种子,在内他(它)便会作祸,他便由种而苗,苗而秀,秀而实。明是个无学问的人,诈妆有学(问),明是个奸险诈伪的人,诈妆老实粗朴,明是个不畏王法不怕清议的贪官,顾粗衣、恶食、敝车、羸马妆成清官,明要害某人,害某人遇见某人,某反加意欸,其辞温,其色谦恭,其礼貌委曲,其寒暄,此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一生诈伪到底,至死不见真性,偷心不偷心,君子小人于焉分路,向东路去的必不回头看西,向西路去的必不回头看东。只说人病息要救性命,有时而用人参、桔梗,亦有时而用太黄、巴豆,有时而用雄鸡、班(斑)鸠,亦有时而用全蝎、蕲蛇。孔子尚敬礼,老子若遇世尊岂肯怠慢。佛老性命之说,如何不可兼收而并畜(蓄)之。把你那莫识见的秀才,只着一个大通禅的老和尚一句问倒嘴卢都的,再无第二句还他人。非三世人身,则血气不清,不知好道,不知讲性命。予鄙心好此甚于食色,饭棹(桌)上、枕头边、出门马上、袖子里、桥内扶手上,无不是这性命书,一日不看性命书,五内便不滋润,脸上便觉俗然,实未见个大头脑,只是口耳之学耳!”《游艺海纳》刻毕,适用宁州杜元庵兄到于家庄特来光顾,即取《游艺海纳》一过目,喜动颜色,因问邦清曰:“乡也知兄之苦心举业,苦心性命,大家都说赵乾所兄苦心举业已矣。性命大事,岂易入其阃奥哉!今观兄与滕县曹门生应聘问答,是兄已透性命之窍矣,果何由而入此窍哉?”曰:“欲做天下真事业,须从天下真学问中来。所谓真学问者,乃性命一件大事,是也,试观今之宇宙处处民穷财尽,皆贪官污吏害之也。太祖时赃满二十两,即便剥皮,惟今日惩贪之法轻,故赃官、赃吏满天下,当事者熟于耳目,都当作常事耳,便都因循将就过去,犹鱼在水中行,而不知其为水也。彼此推靠不肯振刷,天下将乱,谁复顾虑。透过性命的人,眼界阔大。自思我娘生下我时,握着两个空拳头,未曾带得一分银来,及至将死闭下眼,又握着两个空拳头回去,亦未曾带得一分银去。何苦将七尺之躯不自爱,昧了本心做恶事,不顾名义、不畏法度。为子孙田产之计,贪了赃,私坏了名节,是卖其身以利子孙,此在不读书的人,则可。可以读书人,日讲天命之谓性,将《大学》、《中庸》、《论语》上下、《孟子》上下一句也不会使,甘自卖其身,入于恶人禽兽之归昏,愚甚矣!弟不才,滕县六年,不罚取百姓一分纸赎,节年拆封羡余银六千两,尽数登报上司;买谷十二万石,买牛一千头;两驿两厂并在县民壮,共计应役者整整一千名,未曾扣取他(它)一分旷役工食。见有滕县士夫董翼明公祖在固原做布政,可问吏部四年不接一分书怕(帕)。见有同僚吴继疏兄、刘石闾兄两个见做中丞,可问是财利关头,弟已打透。万历壬寅年四月五月内,横遭口语,科道并同僚及李对泉堂公一时参弟十八本,弟理直气壮,不少怵惕。权相沈蛟门密使两个心腹士夫探弟气色何如,两士夫回话云:‘好个铁汉子,颜色再不变。’是进退利害关头,弟已打透。人口头只说死,死全不知死时是何光景。盖人将死时,祖关之气先动。弟万历二十九年九月内,卧病九日,大便血块几筒,余血脱神离汗出,气散祖关,始气跳跃而动,自觉中黄好似一蛇游,翻来覆去有一个时候,到此时平日所钟爱的物一件也记不得了。弟用密诀,目光下垂看定中黄。稍时,气息略定。阎蓬头师傅所谓‘目光还而精气复’,只这一句,弟便使得上了,熟能生巧,此于验之。是死生关头弟已打透,弟打透大财利关、大利害关、大生死关,试较量世间事,再莫大过此
三者,为甚(什)么要紧,不一意修大丈夫事,甘为小人之俗行哉!莫说讲举业一艺,不可用滥时套文章格调,只这做人一件事,岂可不斩钉截铁,断绝财利一源。谩借口云:‘某贤者,亦如此,莫贤者,亦如此。’昧了初心,贪赃坏法,学此等滥时套之污行哉!”元庵兄又问:“兄何开口,便恨贪官?”曰:“旧云:‘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今不在官不在民,尽归于士大夫之家,俸粮柴马之外,皆为赃也。试看今之世界,三考吏出身做官者千千万万,无一人晓得义利两字。谁不爱钱?此等官卑禄薄,犹可恕也。吾辈读孔孟书,日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昧了本心,贪财害民做恶事,再不回头返照。我当日做秀才时,宁有十两银到手,俸粮柴马仅可度日养身,胡为如此?宁不深可痛恨哉!只论今时做官的未有一人不富的,则百姓之贫可知也。三原温见吾兄,一日骑一骡拜弟于于家庄,因相与乐谭(谈)两日,见吾兄笑曰:‘乾所兄专好讲性命。’弟应之曰:‘兄试看今之各名山大刹,其老和尚真正有戒行不吃酒肉、不犯淫盗者,约有三百多人,普天下士夫数三百个不要钱的,或屈指数不上来。”元庵兄抚掌一笑。
游艺海纳后序尝谓心思不通乎,性命不可以论,文章学术不贯乎,天人不可以谭(谈)。政事、节义是性命文章,政事、节义一以贯之,非两物也。吾夫子语:“游艺必先之志道。”据德依仁道,德仁即性也,命也。其艺之浑然者乎?艺即性命之灿然者乎?彻上彻下、无精无粗、合内合外,呜乎!游艺岂易言哉!太(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沧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余掩卷而思,乾所先生之《游艺海纳》至精也、至细也、至中也、至正也,有本焉,非一日而得,一蹴而至者,进乎,技矣。先生自做秀才时,好精养玄修,每求异人名公,师事之,不惮负笈之劳、跋涉之苦、冻馁之艰。真积既久,则太宇自宁,太宇既宁,则天光自发,白痰下于肠中,眸光飞若梨花。坎离交媾,复见天心。此其本原盛大而体无不具,是以从心运矩而用自无不周也。其为文也,不饰章绘句而理自工,不标门立户而辞自畅,发之为节义。任滕六年,不罚取一分纸赎,节年拆封羡余银六千两,尽数登报上司;买谷十二万(石),买牛一千头;吏部四年不接一分书帕,措之为政事。其仕滕县也,救荒均地,栽树积谷,垦荒田,立官庄,平道路,修公署,开运河,治仓廪,禁火耗,革税银,痛裁历来相沿浮费无名之征二万两。其任吏部也,进君子,退小人,抑权势,禁貂王珰,祛积蠹,绝苞苴,上疏裁京都吏、户、礼、兵、刑、工都(部)通大并五城各衙门顶收银百万两。其居乡党也,斋宿百日,两上疏,裁盐商,裁协济,裁里甲,裁冗官七员,裁县不属州辖,创陕西行省一条鞭之法,每年省银万余两。余亲见先生手无三分银,悠然自得,不怨不尤,一切尘嚣利名生死皆扫而空之,此非通性命达天德者,其孰能之,嗟嗟。先生惟透性命一窍,故文章、节义、政事,卓然宇宙观。山西抚台吴继疏先生荐举一疏,则先生之一生才品俱可见矣。区区游艺,岂足尽先生哉!故曰:“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先生游于圣人之门,故观于海而难为水,此《游艺海纳》所以立名也。先生筌蹄在笥善与人同,惟高明有志者,当自得之。余虽孳孳景仰,终不敢曰:“窥其藩篱也。”万历四十三岁次乙卯七月吉日宁州贡士辱爱友弟元庵杜春芳拜书注释:①《语》:指《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书。全书主要内容是孔子在谈话中对“仁”、“礼”、“孝弟”、“忠恕”以及其他一些意识形态的说明和解释。《论语》最后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它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定的。汉代曾流传鲁论、齐论、古论三种不同的本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论语》20篇是汉朝人在上述三种本子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论语》的注本为数非常多,影响大的有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
②漆园吏:指庄子(公元前360?~公元前280?年),名周,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秋水》篇载楚王使人聘庄子,庄子不应。从《列御寇》所载的情况看,庄子是一个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人。《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书52篇,现存33篇。后人以《逍遥游》至《应帝王》7篇为内篇,《骈拇》至《知北游》15篇为外篇,《庚桑楚》至《天下》11篇为杂篇。
③《六艺》:即六经,包括《礼》、《乐》、《诗》、《书》、《易》、《春秋》。
④六通四辞:六通谓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四辟指顺应四时,任物自动。后多用来比喻四面八方无不通达。
⑤仍孙:也作“礽孙”。古称从本身下数第八世孙为“仍孙”(八世包括本身)。又称“耳孙”。《尔雅·释亲》:“昆孙之子为仍孙。”亦称为“礽乃孙”。《太玄·玄数》:“九属,一为玄孙,二为曾孙,三为仍孙,四为子,五为身是也。”⑥举业:科举时代称应试的诗文为举业,又称举子业。《金史·元德明传》:“子好问,最知名,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⑦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商后宋国贵族。在宋曾任相礼(司仪)、委吏(管理粮仓)、乘田(管理畜养)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满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去而周游卫、宋、陈、蔡、楚列国,都不为时君所用,归死于鲁。曾长期聚徒讲学,开私人讲学风气,传说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72人。古文学家说他曾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虽未必完全可靠,但他熟悉古代经典,可能作过整理工作。由于他弟子的活动,形成儒家学派,对后世有重要影响。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通过自汉代董仲舒以来儒家的补充修正,他的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本人被尊奉为至圣先师,他的言论事迹见《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
⑧游艺:《论语·述而》:“游于艺。”原为孔子要学生沉湎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中。后亦泛指从事技艺或艺术锻炼。白居易《大巧若拙赋》:“既游艺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⑨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人。春秋鲁公族孟氏之后,受业于子思的门徒。游说于齐梁之间。未见用,退而与其门徒公孙丑、万章等著书立说。继孔子的学说,兼言仁和义,提出“仁政”口号。主张恢复井田制度和世卿制度,同时又谓“民为贵”、“君为轻”,称暴君为“一夫”。认为人本性善,强调养心、存心等内心修养的功夫。成为宋代理学家心性说之本。宋元以后,地位日尊,元至顺元年封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定为“亚圣孟子。”在儒家中其地位仅次于孔子。思想事迹见《孟子》一书。
⑩子贡:(公元前520~公元前?年),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也作子赣,春秋卫人,孔子弟子。能言善辩,善经商,家累千金,所至之虑和王侯贵族分庭抗礼,曾任鲁、卫相。
《五经》:儒家的五部经典。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五经即《易》、《尚书》、《诗》、《礼》、《春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本称“诗”或“诗三百”,经字是汉儒加上去的。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15“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诗经》其中早期作品大多数是宗教性的颂诗,对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但思想内容较差。自周厉王以后,周朝衰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时出现了一些抨击时弊的作品,是《诗经》的精华,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作用。《诗经》秦火焚后,汉代传《诗经》有四家,即齐人辕固所传的叫“齐诗”,鲁人申培所传的叫“鲁诗”,燕人韩婴所传的叫“韩诗”,鲁人毛亨所传的叫“毛诗”。自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后,学毛诗的越来越多,其他三家则逐渐衰废。现在流传的《诗经》是毛诗。历代为《诗经》作注的很多,通行较好的注本有:《毛诗正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诗集传》(宋朱熹著)、《诗毛氏传疏》(清陈奂著)、《毛诗传笺通释》(清马瑞辰著)。
甫:fǔ,古代对男子的美称,多用在名字之后。
《四书》: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南宋理学家朱熹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作为学习的入门书。元仁宗皇庆二年,定考试科目,必须在《四书》内出题,发挥题意以朱熹注为根据,一直到明清相沿不改。晷:gu ǐ,太阳光的影子。
股:即八股,明清科举考试的文体,也称制艺、制义、时文、时艺、八比文。因题目取于四书,古又称四书文。其体源于宋元的经义,明成化以后渐为定式,清光绪年废。八股文以四书的内容作题目。文章的发端为破题、承题,后为起讲。起讲后分起股、中股、后股、末股四个段落发议论。每个段落都有两段相比偶的文字,合称八股,故称八股文。
桀溺:春秋隐士。《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即曾参(shēn),字子舆、孔子的弟子,与闵于骞,是儒家鼓吹的孝子典范。《后汉书·明帝纪》:“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朱注:即朱熹(公元1130年~公元1200年)注,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宋徽州婺源人。晚年徙居建阳考亭,又主讲紫阳书院,故亦别称考亭、紫阳。曾任秘阁修撰等职,历仕四朝,而在朝不满40日。朱熹为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阐发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大学》、《中庸》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二程(程颐、程颢)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后世并称程朱。自元以来,历代王朝科举,均采用朱熹《四书集注》。朱熹整理文献,注释古籍,疑古文《尚书》之伪,不信《诗序》,多有新解。著作有《四书章句集句》、《诗集传》、《周易本义》、《楚辞集注》、《通鉴纲目》及后人编辑的《朱文公集》、《朱子语类》等。本文所说的“朱注”、“朱语”、“朱子”均指朱熹。轩轾:车子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轾。引申为文章的高低、轻重要适中。
李崆峒:即李梦阳(公元1473年~公元1503年),字献吉,号空同子,明甘肃庆阳县人。弘治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号称“七子”。文学著作有《空同集》。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曾编修《汉书》。
《圆觉经》:佛经名,全名《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唐朝宾僧佛陀多罗译。有宗秘《略疏》。记释迦应文殊、普贤等十二大士问因地修证之法门,一一对答。以世间种种幻化,生于觉心,幻尽觉圆,心通法遍,故名圆觉。
《中庸》:《四书》之一,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原为《礼记》中一篇。不偏叫中,不变叫庸,儒家以中庸尚最高的道德标准。《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于思:(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孔子之子孔鲣的儿子,名伋,曾为鲁缪公师。著《子思》23篇,唐后佚失。
趑趄:zi jū,亦作“次且”。且前且却,犹豫不进。
《楞严经》:佛经名,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唐天竺沙门刺密谛(华名极量)主译,乌苌国沙门弥伽释伽译语,房融笔授,怀迪证译。经名“首楞严”,华语乃“一切事究竟巩固。”经中阐述心性本体,属大乘秘密部。因经中多长生神仙之书。且标出地、水、火、风、雷、见、识“七大”,与佛教显宗的“四大”,密宗“五大”,宗旨有所不同,此经又不列入唐、宋、元、明四大藏,故后人对其真伪颇有争议。
子夏:(公元前507年~公元前400年),名卜商,字子夏。春秋卫人,孔子弟子。长于文学,相传曾讲学于西河,序《诗》,传《易》,为魏文侯师,有子早死,痛哭失明。
子游:(公元前506年~公元前?年),春秋吴人。姓言,名偃,字子游,孔子弟子。长于文学,仕鲁,曾为武城宰。
子张:(公元前503年~公元前?年)春秋陈阳城人,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孔子弟子。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察之间。《论语》有《子张》篇。
关云长:即关羽,字云长,三国时蜀国名将,以骁勇忠义著称。《三国志》有《关羽传》。
曹操:(公元155年~公元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年二十举孝廉,征拜为议郎,以参加镇压黄巾军起义,迁为济南相。后起兵讨董卓,迎献帝刘协,迁都许昌,又击灭袁述、袁绍,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他采取抑制豪强、推行屯田、督促开垦荒田等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经济的政策。后统一了北方,位至丞相及大将军、封魏王。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喜好文学,有《魏武帝集》。
子路:(公元前542~公元前480年),春秋卞人。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孔子弟子。仕卫,曾为卫大夫孔悝邑宰,因不愿跟从孔悝迎立蒉目贵为卫公,被杀。
貂珰:diāo dān g ,汉代中常侍冠上的两种装饰物。后即用宦官代称。
苞苴:bāo jū指馈赠礼物,后引申为贿赂。
筌蹄:《庄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鱼,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荃即筌,捕鱼竹器;蹄,捕兔器。后来以“筌蹄”比喻达到目的手段。
笥:sì,盛饭或衣物的方形竹器。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