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之道的践行者
| 内容出处: | 《海南历史文化.特辑》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4832 |
| 颗粒名称: | 圣贤之道的践行者 |
| 并列题名: | 邢宥评说 |
| 分类号: | K825 |
| 页数: | 12 |
| 页码: | 275-28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邢宥是明代中前期儒家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其一生主要贯穿了“希贤希圣又希天”的圣贤之道和齐家治国的人生追求。他倡导儒家思想,实践儒家道德,是儒家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
| 关键词: | 海南 历史人物 邢宥 |
内容
邢宥(1416~1481),字克宽,号湄丘(或作“湄邱”),海南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人。青少年时期,走的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进身之途:少而敏,五岁启蒙,始读《三字经》;就读乡校时,月试季考均名列前茅;十四岁补文昌邑庠弟子员;二十六岁省试中举;三十三岁,入京考试,登二甲进士第。此时已是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了,这年邢宥留在京城,虽然只是观政(见习)于刑部,却从此踏上了他20余年的宦途。次年(1449)发生了明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力劝英宗御驾亲征的太监王振被部下杀死。所幸的是,邢宥的仕途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是从刑部的“见习生”顺利地被提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此后历任台州知府、苏州知府、浙江布政司左参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邢宥突然主动上书乞求致仕归乡,用丘濬的话说,“众方俟其有为,乃急流而勇退”。是年,邢宥五十五岁。归休文昌故里后,建湄丘堂,自号“湄丘道人”,十余年间,虽然是“归田遐僻,潜德幽光”(清·缪日藻《邢湄丘先生集序》),但在“优游林泉”之余,也总是“能以言行坊表闾党”,所谓“出处有道,光明卓荦”(清·张岳崧《邢湄丘先生遗集序》)。综其一生来看,邢宥不仅是明代中前期儒家思想的积极倡导者,更是一位杰出的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具体地来做一些分析。
“希贤希圣又希天”
贯穿邢宥一生的主要是儒家思想,在邢宥身上,又具体表现为“希贤希圣又希天”的圣贤之道和齐家治国的人生追求。
据说,邢宥少年时便写了一首流布乡里的《勉学》诗:
希贤希圣又希天,治国齐家此一身。德业文章传世久,我今宜勉自童年。
有人很具体地将这首诗定为1425年,即邢宥十岁时所作①。这首诗其实是个声韵不协而内容深刻的奇怪的混合体。从声韵上说,“身”是“真”韵,“年”是“天”韵,本不相押。倒是首句的“天”与末句的“年”是同韵,所以,如果调换成“治国齐家此一身,希贤希圣又希天。德业文章传世久,我今宜勉自童年”,至少在声韵上是合上了。从内容上说,诗的首句“希贤希圣又希天”,乃源自有“宋代理学开山人物”之称的周敦颐的《通书·志学第十》: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通书》细目为“志学”,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颜渊,乃古之大贤,其所思所学皆在如何为圣为仁。显然,周敦颐这段话,实是为天下为学立志者所发。如果说,从不合韵或根本就还不懂韵这点来说,《勉学》确实像是出于一个十岁的童子之手;然而从其内容来看,这首诗更像是乡村塾师为学童们写的一首勉学励志的诗。重要的是,不管这首《勉学》是邢宥少年所为,还是出自给学童励志的乡村塾师之手,诗中提出的志向学为的目标,竟成了邢宥一生的思想行为的牵引。
因为这首小诗对于理解邢宥一生的思想行为是如此重要,我们不妨顺着诗中内容的线索说开去。诗中首句是“希贤希圣又希天”,“贤”“圣”“天”从来都是儒家士子所志所学所求的目标。在贤、圣、天这一组关系中,依其高低、深浅的秩序来看,周敦颐所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本应该是“士希贤”,而后是“贤希圣”,最后是“圣希天”。
士所志学的首先是“贤”。那么,“贤”的标准及其所为是什么?我们就以周敦颐的《通书》作为理解的基础:如《通书》所说,“贤”者的典范就是伊尹、颜渊,从其行为向外的进取来说是“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从其行为向内的修养来说则是“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伊尹、颜渊的这种行为、修养,正是天下普通士子志学的标准。“希贤”当如此,“圣”比“贤”又高一筹。“希圣”或修成为“圣人”又应该怎样去做呢?
关于“圣人之本”,周敦颐的解释是:
诚者,圣人之本。(《通书·诚上第一》)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通书·诚下第二》)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通书·圣第四》)
“诚”是圣人之本,也是“五常百行”——一切行为及其准则的基础,“诚则无事”,不诚则“邪暗塞”。与诚相关的还有“神”“几”,如果说“诚”是“圣人之本”——心性之本源,所谓“寂然不动者”,也就是心中固有者;神就是指此诚性感物而通的瞬间之动,“几”则是“神”在“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状态。圣人因诚而神,因神而通,通而无形,这些都是圣人的内在品德。
与“圣人之本”相对应的是“圣人之道”,周敦颐同样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说:
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通书·道第六》)
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公第三十七》)
“道”在此指的就是行为方式或法则。周敦颐认为,圣人本于“诚”——在“诚”的基础上,所行所为都必然遵循“仁义中正”“至公”的法则,因为“仁义中正”“至公”的法则,正是“天地”之大道,也就是“天”之本性。所以周敦颐说:“圣同天,不亦深乎!”
对于“天”,周敦颐一方面引述孔子的话,“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通书·圣蕴第二十九》)另一方面也给予具体的解释: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通书·顺化第十一》)
天道之本性就是生、养万物。所谓“圣希天”,就是圣人循天之道而行,所以周敦颐又说:
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通书·顺化第十一》)
邢宥《勉学》第二句的“治国齐家此一身”,在周敦颐的学说中同样能找到具体的解释:
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通书·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希贤”“希圣”“希天”,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一切都再次回到了“诚心”这一“圣人之本”上。周敦颐的思想,显然是宋儒所理解的儒家学说的最高体现和理想化的表达。对于邢宥来说,又是如何具体来理解儒家学说的呢?
那种童时的理想化的圣、贤、天道和治国齐家思想,在邢宥成熟的表述中,其实非常朴素,撮其要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后世斯文宗主,舍吾夫子其谁。
“希圣”的思想,在邢宥身上具体表现为“尊孔”。《琼州府学大成殿记》中,他是这样说的:
夫子没,道在六经。天下郡县凡有学,以崇诗书礼乐之教,必尊吾夫子为先圣,塑其像,祠之庙。……吾夫子固天纵之圣,而不得位于帝王,独与其徒讲明道学,阐圣教于遗经,寓王法于鲁史。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晦而复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礼,坏则复立。天下之人,得不沦于左衽者,谁之力欤?后世斯文宗主,舍吾夫子其谁欤!
在邢宥心目中,孔子是“天纵之圣”。他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晦而复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礼,坏则复立”;使“天下之人,得不沦于左衽”。所以,孔子是后世斯文当之无愧的宗主,当然就是他心中的圣人。
其二,圣人之道,五伦之道也。
邢宥明确提出了“圣人之道”就是“五伦之道”。他在《林教志道字说》中说:“士志于道。道者,圣人之道,五伦之道也。”所谓“五伦之道”就是关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和朋友的五种人伦。在《重修文昌明伦堂记》中他也有同样的表述:
人伦明,则人文成矣。
而成周之文,不外乎三代之所以明人伦。
要必秩然人伦之叙,而后灿然文理之备,斯不愧焉耳。苟反而求之,文采有余,而实行不足,不亦有负于是邑之名斯堂之颜也哉!
如果对比周敦颐的“圣人之道”为“仁义中正”“至公”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邢宥的“圣人之道”,显然将更具理想色彩的理论内涵代之为现实生活中的纯人伦关系。至于周敦颐的“圣人之本”为“诚”的思想,邢宥在理论上则几乎未见任何阐述。那么,圣人所行之道为“五伦之道”,圣人又应本于什么来行此“五伦之道”呢?在《乐会县偶学记》一文中,邢宥似乎想用“彝伦”的概念来补足仅言“人伦”“五伦”的“圣人之道”的欠缺:
予惟圣王之治天下,必本彝伦以纲维风化。彝伦之道,具在六经。学校者,讲经明伦之所。孔子则六经之宗主,彝伦所赖以立而不坠者。彝伦立于子,则能父其父,立于臣,则能君其君。国无之,不足以为国;家无之,不足以为家。周祚修之而延,秦代弃之以促。忠臣烈妇,临变而不可夺者,皆彝伦之道,有以结乎其心也。彝伦之在天下,有是恃如此……
所谓“彝伦”,就是常理、常道。清顾炎武《日知录·彝伦》解释说:“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能尽其性,以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彝伦叙矣。”从顾炎武的解释可以看出,相比“人伦”“五伦”的概念,“彝伦”更倾向于指天下普遍之道理,是天下人皆“有以结乎其心”者,也是天下人“有足恃(心中所依恃)”者,而不仅仅局限于儒家的世俗人伦纲常。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王之治天下,必本彝伦”和“圣人之本”为“诚”的思想,是有内在关系的,因为对周敦颐来说,“诚”就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就是天下之常理、常道,他不过是将天下之常理、常道的“彝伦”更具体地解释为“诚”,而邢宥则将具体的“诚”一般性地理解为“彝伦”而已。当我们将圣人之本的“诚”与天下之常理、常道的“彝伦”相联系时,似乎也能看到圣人与天意,希圣与希天的相通之处和同一性。
从“希贤希圣又希天”到“治国齐家此一身”,反映的都是儒家思想中积极有为的一面。其实,儒家思想中除了“达则兼济天下”外,还有以颜回为代表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处世哲学。这种“独善其身”的人生观,在邢宥致仕归乡以后,完全取代了“希贤希圣又希天,治国齐家此一身”的人生追求。在《湄丘草亭记》中我们看到的是:
丘主人之孙宥,拜官南台,不俟老而致其事。既还故土,喜遂初志。乃伐丘之树为楹,斫丘之竹为椽,筑丘之土为墙。又剪丘之茅以苫盖之。作亭一间于旧所居之前,匾之曰“湄丘草亭”。客至,即延之茶。客退,则亭虚而静。春风秋月,冬暖夏凉。野树垂荫乎前后,梅竹桑麻交翠乎左右。亭主人俯仰瞻盼其间。意方有适,则检床头残简,或唤瓮底新醅,且研且酌,探颐陶情以消闲旷。兴发,则扶筇曳履,从一二童子徐步以出。或登丘隅,或临水湄。望浮云而觇飞鸟,观新涨而玩游鳞。心目以豁,志趣以舒,兴尽而还乎亭。神疲力倦,则隐郭几以徇懒僻,卧陶窗以遂黑甜。出而还,立而坐,睡而起,油油然率从意适,无所羁绊。以乐馀生,志意颇足。……吾将散吾情,故作湄丘之草亭。吾将漫吾游,故合水与山以名吾所居之丘。若谓吾丘无平泉绿野之侈,亭不似休休熙熙之雅,不足以乐,是未知吾之所以乐也。吾之乐,盖将拉无怀氏之民而友之,相与游乎太古。
“无怀氏”是谁?“无怀氏”就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陶渊明在其《五柳先生传》中也提到:“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宋罗泌的《路史·禅通纪三·无怀氏》解释说:“无怀氏,帝太昊之先。其抚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当世之人甘其食,乐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在这篇草亭记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颜回和陶渊明式的“箪食”“瓢饮”、乐在陋巷和“心远地自偏”的人生趣味。《辛丑初度日》诗中的“两间俯仰期无愧,百事修为贵有终”,则将自己的世俗修为与天地间的常理、常道联系在一起,使个人行为的有限性与天理良知的无限性完全相融为一体。
邢宥毕其生都在推崇儒家圣贤之道及其齐家治国的思想主张,与之相对的则是,他一生中都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对世俗生活中佛家信仰的贬黜。如果说,这就是邢宥的宗教观,似乎有点牵强。事实上,邢宥和中国古代大多数人一样,形而上的宗教观并不十分突出,涉及宗教的地方,往往只是在实用主义的现实行为方面。戴缙于邢宥去世当年所作的《文昌湄丘邢公状》中说:邢宥“教子弟有法,谈及祭祷,以为自纾其爱敬且宽病者之心则可,若谓佛能生死人则不可,始终不听异端邪说焉”。同时所作的刘吉的《中顺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邢公墓志铭》也提到,邢宥知苏州时,“率以俭约,诸游晏亭馆,老佛殿阁,一莫之顾”。这一宗教态度,邢宥自己也曾以各种方式表达过。如《琼州府学射圃记》中所云:
嗟夫!世之食公禄而力可为者,曾有几人而知所当为哉?金碧辉煌,有朘民脂而耸老佛之殿阁者;风月潇洒,有殚民力而张宴赏之池亭者。其视圃亭之作孰当耶?抑公之崇儒化,不啻此一事,若学校,若祭器,若揭经程艺,皆切切于心而为之未已。伟哉涂公!
他在大赞广东按察司副使涂伯辅兴建“射圃”“射亭”以崇儒化的同时,把那些“朘民脂而耸老佛之殿阁”与“殚民力而张宴赏之池亭”的人并列着都谴责了一番。在《族伯司训讷斋公墓葬表》一文中,他对族伯邢贵(号讷斋)为父亲做丧葬时“一依乎礼,不作佛事”,“能变旧习,俾治丧者不用浮屠,家信而里行之”,更是大加赞赏。
《安乐乡长寿歌》是邢宥为他的舅舅许伯乔老人八十寿辰所作:
……乌纱白发旧弱冠,云鹤相邀清且焕。自将名利等浮云,物外逍遥何羁绊。流水高山无常住,老翁胸中千古趣。不资金鼎炼神丹,静养清修安分素。此心无欲更无营,六脉清和百窍清。气血连通神秀发,性无戕贼自延龄。世人谋寿痴堪叹,念佛吃斋勤赛祷。不知作事要平心,却罔此心从左道。……
在这首诗中,邢宥既否定了“金鼎炼丹”式的崇道之妄,也批判了“念佛吃斋”式的信佛之痴。在他看来,这些举动都是世俗行为中的左道旁门,长寿的幸福更重要的是来自“作事要平心”,只有“自将名利等浮云”和“此心无欲更无营”,才能真正达到“物外逍遥何羁绊”和“性无戕贼自延龄”的人生境界。
“以公”“以实”“缘情据理”
“以公”“以实”“缘情据理”,以及勇于担当,可以作为邢宥二十余年仕途的总结。
综合同时代人描述的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来看,邢宥一生的政治业绩很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几件事。
1449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力劝英宗御驾亲征的太监王振被部下杀死。次年,即景泰元年,有诬告王振“家人孙太安匿其财者。牵连二十余人,事下锦衣卫鞠,如所诬。上命公(邢宥)往覆之,公辩诬,皆得释。”(刘吉《中顺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邢公墓志铭》)这件事在丘濬的《湄丘邢公墓志铭》中则被记载得更具细节性:“太监王振败,籍其家,有告其家人孙太安匿其财者。公与锦衣卫官于信者鞠之,无实,于必没入之,且曰:‘不然,祸立至。’公曰:‘无其情而文致于法,是我杀之也。’竟辩白被诬者二十余人。”邢宥时为监察御史,在处理这件事时,拒绝“无其情而文致于法”。这里的“情”就是“实情、事实”,“文”就是“文饰、虚构”。他既不落井下石也不屈服于威逼,而是据实处理。
还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邢宥出巡福建时发生的,“先是,巡按御史许仕达与镇守尚书薛希琏交恶,事闻,因命公代仕达,且核其事。公至,一断以公,无所回互。”此处刘吉《中顺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邢公墓志铭》作“公一以实复,不少避”。
二是邢宥出按辽东,“时都御史寇深巡抚其地,副将焦礼有克敌功,寇上其功状,乃先以主将曹义,事下覆之。寇为曹私嘱,公不从,遂与成隙。……时寇深总内台,恨公在辽东时事,多方捃摭之,无所得。及公秩满,需铨曹。适知县甄铎有故勘人命狱,有言忠国公石亨纳其赂纵之者,命下勘之,众皆畏势莫敢犯者。寇以公名奏,委核其实,盖欲假是以中伤公也。公审核允当,讫莫能害。”此处刘吉《中顺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邢公墓志铭》作“公覆以实,竟莫奈何”。
三是邢宥“升知台州府。台俗健讼,公治之,一惟缘情据理,民自信服”。
四是邢宥“改知苏州。苏之田赋甲天下,丁役杂办视他郡盖倍蓰焉,而俗尚浇浮。公治之,一本情理,不出奇,不立苛,惟省役均赋,节浮费,以便民为主。不期月,政化民洽,歌颂之声,播闻远近。公性不乐华靡,且厌浙西俗尚过侈,凡百有为,务从简素。神祠惟涓洁其在祀典者,廨宇惟修葺其切于用者”。
又:“成化丙戌,江南大水,而苏尤甚。公发官储及劝富民,得米八十余万石,赈之。然犹不继。饥民百十持券入富室借之,不与则夺。公即帖示,俾饥民指其闭籴者名赴官,官为之借。明日,争持状赴府,官为署券付乡老,俾同保借,又得米八万石。又不继,乃会计军饷一年之外余二十万石,发以赈之。同官有以事未上闻难者,公曰:‘民命在须臾,奏允而后给,则无及矣。专擅之罪,吾自当之。’是岁,稔活饥民殆四十余万口。”①
在以上各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或利益纠纷,还是教化积久成习的地方陋俗,抑或应对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邢宥或断以公、覆以实,或缘情据理,或勇于担当。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以“诚”为本,以“仁义中正”“至公”为道的儒家精神实质在他身上不同方式的表现。
正如周敦颐所谓“圣,诚而已矣。……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②我们已经知道,在邢宥的理解中,所谓诚,就是“彝伦”——天下之常理、常道,换句话说,就是“仁义中正”“至公”。其实,在邢宥的实际行为中,应该再加上一个“常情”。正是“常理”“常道”“常情”,构成了邢宥所说的“彝伦”——也就是周敦颐所说的“诚”——这才是天地间的真正的大道,是所谓“圣人之本”,也是“圣人之道”的精神实质。从以上举例都能看出,邢宥在他生平仕途中,对许多重要事件的处理,几乎就是在努力地践行“圣人之本”和“圣人之道”。
“天下之士”
各种关于邢宥的评价中,丘濬给邢宥的赠辞和评语中,有两段材料特别值得一提。其中一条材料是明景帝景泰七年(1456)夏四月,邢宥回乡省亲时,丘濬在《送邢侍御克宽归省诗后序》中写的:
余惟吾郡自昔仕于朝,得推恩以荣亲者,固有矣。而及其亲之存者,前此未之有也。有之实自君始。嗟乎!前之无者,至我而肇,后之有者,自我以始,其为荣也,孰尚焉。君之归抵琼也,父子妇姑,相见于久阔之后,载拜载问,欢忻怡愉一堂之间,纱帽豸袍,珠翟锦衣,辉映上下。既而有事于寝,展祭于墓,既毕,而燕宗属姻娅,朋侪故旧,乡人父老,是集是临。兹时也,必有目其实而赍咨叹息,以为自昔未有者矣,亦必有闻其风而感发兴起。为父者思所以教其子,为子者思所以励其志者矣。又有必感其事而悲其生之不幸,有子而不克肖,有亲而不侍养者矣。於戏,君之兹行,此其为乡邦之光,闾里之劝,非特今世为然,后此千百年之久,又安知无传其事以为美谈,播之声诗,纪之图志,以贻无穷者哉。
在这段材料中,丘濬也特意提到了“御史历两考,必有升擢之荣。矧君端严,得宪臣体,使少待旬月间,不次之擢可几矣。……而君一旦不谋于同列,不告于朋友,即决然以去,其视贪荣违亲,以冀非分之望于不可必得,而苟安以徼幸其或至者,真不啻天渊矣”。邢宥在历官七年之久,眼看就有“升擢之荣”时却决然而去,回乡省亲,全然不在意“升擢”的机会。对这位乡里好友的如此举动,丘濬虽也一再赞为“贤也哉”,但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丘濬真正动心动情向往不已的是他立足于吾郡一乡一地的“乡邦之光,闾里之劝”,对邢宥“纱帽豸袍,珠翟锦衣,辉映上下”的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时盛况的欣羡。
在邢宥致仕(成化六年,1479)以后,丘濬在他的《邢湄邱公像赞》里,对至交好友则是这样评价的:
五岭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气,于此焉萃。立朝著蹇蹇之节,出守敷优优之治。总宪网,存法外之仁;制国用,寓利中之义。众方俟其有为,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执,直而不肆。不随时之好,必行己之志。匪但秀出于岭海之间,殆所谓天下之士也与。(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二十二)
在这段评语中,有意思也最富有想象力的是两句总评:“匪但秀出于岭海之间,殆所谓天下之士也与。”很显然,“秀出于岭海之间”依然还是站在“吾郡”“吾乡”的海南的角度,对这位乡里前辈出众的才华、品德及取得的政绩的赞赏。而“所谓天下之士也与”,则是超出于海南一地之见,站在了“天下”的高度对邢宥的评价和肯定,这与一乡地的“乡邦之光,闾里之劝”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什么是“天下之士”,什么样的人才够得上是“天下之士”?
我们知道,“士”有普通之“士”,有“高士”,也有“天下之士”。“士”原本指的不过是普通男子,引申为有身份的男士、官吏等。“高士”,或等同于“高人”,汉代王充《论衡·自记》中说:“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显然是指超出普通“士”之上的出众者。至于“天下之士”,这一提法原出于《战国策·赵策》。秦围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魏。魏慑于秦之强,虽派兵往救却又按兵不动,同时派辛垣衍前去劝赵尊秦为帝。值此存亡攸关之际,齐国人鲁仲连挺身而出,他在与辛垣衍的辩论中,以雄辩之力说服辛垣衍放弃“帝秦”,也使秦人闻风而退,折服后的辛垣衍拜而谢之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故事中,辛垣衍曾称鲁仲连为“高士”,后又改称之为“天下之士”①,区别似乎就在于,作为高士的鲁仲连,只是“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而作为“天下之士”的鲁仲连,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在鲁仲连的时代和鲁仲连的身上是“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一无所取,而邢宥作为明代的朝廷大臣,在丘濬看来,第一次的省亲是面临“升擢之荣”时,决然以去;第二次的致仕则是“众方俟其有为,乃急流而勇退”,邢宥是在“为国”排患、释难、解纷乱而后无所取。这不是天下之士是什么?
然而,在我们看来,丘濬对邢宥许之以“天下之士”,除了指明他为国排患、释难、解纷乱而后一无所取的品格之外,似乎还在暗示,邢宥“匪但秀出于岭海之间”,而且还是“天下之士”。换句话说,邢宥作为一天下之士,与“岭海”之间的一秀出之士相比,除了原有的“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品质,显然还具有一种不拘吾郡一乡之面,而远超出孤岛乃至岭海的能兼济天下的品德和才华。
“希贤希圣又希天”
贯穿邢宥一生的主要是儒家思想,在邢宥身上,又具体表现为“希贤希圣又希天”的圣贤之道和齐家治国的人生追求。
据说,邢宥少年时便写了一首流布乡里的《勉学》诗:
希贤希圣又希天,治国齐家此一身。德业文章传世久,我今宜勉自童年。
有人很具体地将这首诗定为1425年,即邢宥十岁时所作①。这首诗其实是个声韵不协而内容深刻的奇怪的混合体。从声韵上说,“身”是“真”韵,“年”是“天”韵,本不相押。倒是首句的“天”与末句的“年”是同韵,所以,如果调换成“治国齐家此一身,希贤希圣又希天。德业文章传世久,我今宜勉自童年”,至少在声韵上是合上了。从内容上说,诗的首句“希贤希圣又希天”,乃源自有“宋代理学开山人物”之称的周敦颐的《通书·志学第十》: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通书》细目为“志学”,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颜渊,乃古之大贤,其所思所学皆在如何为圣为仁。显然,周敦颐这段话,实是为天下为学立志者所发。如果说,从不合韵或根本就还不懂韵这点来说,《勉学》确实像是出于一个十岁的童子之手;然而从其内容来看,这首诗更像是乡村塾师为学童们写的一首勉学励志的诗。重要的是,不管这首《勉学》是邢宥少年所为,还是出自给学童励志的乡村塾师之手,诗中提出的志向学为的目标,竟成了邢宥一生的思想行为的牵引。
因为这首小诗对于理解邢宥一生的思想行为是如此重要,我们不妨顺着诗中内容的线索说开去。诗中首句是“希贤希圣又希天”,“贤”“圣”“天”从来都是儒家士子所志所学所求的目标。在贤、圣、天这一组关系中,依其高低、深浅的秩序来看,周敦颐所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本应该是“士希贤”,而后是“贤希圣”,最后是“圣希天”。
士所志学的首先是“贤”。那么,“贤”的标准及其所为是什么?我们就以周敦颐的《通书》作为理解的基础:如《通书》所说,“贤”者的典范就是伊尹、颜渊,从其行为向外的进取来说是“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从其行为向内的修养来说则是“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伊尹、颜渊的这种行为、修养,正是天下普通士子志学的标准。“希贤”当如此,“圣”比“贤”又高一筹。“希圣”或修成为“圣人”又应该怎样去做呢?
关于“圣人之本”,周敦颐的解释是:
诚者,圣人之本。(《通书·诚上第一》)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通书·诚下第二》)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通书·圣第四》)
“诚”是圣人之本,也是“五常百行”——一切行为及其准则的基础,“诚则无事”,不诚则“邪暗塞”。与诚相关的还有“神”“几”,如果说“诚”是“圣人之本”——心性之本源,所谓“寂然不动者”,也就是心中固有者;神就是指此诚性感物而通的瞬间之动,“几”则是“神”在“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状态。圣人因诚而神,因神而通,通而无形,这些都是圣人的内在品德。
与“圣人之本”相对应的是“圣人之道”,周敦颐同样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说:
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通书·道第六》)
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公第三十七》)
“道”在此指的就是行为方式或法则。周敦颐认为,圣人本于“诚”——在“诚”的基础上,所行所为都必然遵循“仁义中正”“至公”的法则,因为“仁义中正”“至公”的法则,正是“天地”之大道,也就是“天”之本性。所以周敦颐说:“圣同天,不亦深乎!”
对于“天”,周敦颐一方面引述孔子的话,“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通书·圣蕴第二十九》)另一方面也给予具体的解释: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通书·顺化第十一》)
天道之本性就是生、养万物。所谓“圣希天”,就是圣人循天之道而行,所以周敦颐又说:
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通书·顺化第十一》)
邢宥《勉学》第二句的“治国齐家此一身”,在周敦颐的学说中同样能找到具体的解释:
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通书·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希贤”“希圣”“希天”,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一切都再次回到了“诚心”这一“圣人之本”上。周敦颐的思想,显然是宋儒所理解的儒家学说的最高体现和理想化的表达。对于邢宥来说,又是如何具体来理解儒家学说的呢?
那种童时的理想化的圣、贤、天道和治国齐家思想,在邢宥成熟的表述中,其实非常朴素,撮其要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后世斯文宗主,舍吾夫子其谁。
“希圣”的思想,在邢宥身上具体表现为“尊孔”。《琼州府学大成殿记》中,他是这样说的:
夫子没,道在六经。天下郡县凡有学,以崇诗书礼乐之教,必尊吾夫子为先圣,塑其像,祠之庙。……吾夫子固天纵之圣,而不得位于帝王,独与其徒讲明道学,阐圣教于遗经,寓王法于鲁史。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晦而复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礼,坏则复立。天下之人,得不沦于左衽者,谁之力欤?后世斯文宗主,舍吾夫子其谁欤!
在邢宥心目中,孔子是“天纵之圣”。他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晦而复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礼,坏则复立”;使“天下之人,得不沦于左衽”。所以,孔子是后世斯文当之无愧的宗主,当然就是他心中的圣人。
其二,圣人之道,五伦之道也。
邢宥明确提出了“圣人之道”就是“五伦之道”。他在《林教志道字说》中说:“士志于道。道者,圣人之道,五伦之道也。”所谓“五伦之道”就是关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和朋友的五种人伦。在《重修文昌明伦堂记》中他也有同样的表述:
人伦明,则人文成矣。
而成周之文,不外乎三代之所以明人伦。
要必秩然人伦之叙,而后灿然文理之备,斯不愧焉耳。苟反而求之,文采有余,而实行不足,不亦有负于是邑之名斯堂之颜也哉!
如果对比周敦颐的“圣人之道”为“仁义中正”“至公”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邢宥的“圣人之道”,显然将更具理想色彩的理论内涵代之为现实生活中的纯人伦关系。至于周敦颐的“圣人之本”为“诚”的思想,邢宥在理论上则几乎未见任何阐述。那么,圣人所行之道为“五伦之道”,圣人又应本于什么来行此“五伦之道”呢?在《乐会县偶学记》一文中,邢宥似乎想用“彝伦”的概念来补足仅言“人伦”“五伦”的“圣人之道”的欠缺:
予惟圣王之治天下,必本彝伦以纲维风化。彝伦之道,具在六经。学校者,讲经明伦之所。孔子则六经之宗主,彝伦所赖以立而不坠者。彝伦立于子,则能父其父,立于臣,则能君其君。国无之,不足以为国;家无之,不足以为家。周祚修之而延,秦代弃之以促。忠臣烈妇,临变而不可夺者,皆彝伦之道,有以结乎其心也。彝伦之在天下,有是恃如此……
所谓“彝伦”,就是常理、常道。清顾炎武《日知录·彝伦》解释说:“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能尽其性,以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彝伦叙矣。”从顾炎武的解释可以看出,相比“人伦”“五伦”的概念,“彝伦”更倾向于指天下普遍之道理,是天下人皆“有以结乎其心”者,也是天下人“有足恃(心中所依恃)”者,而不仅仅局限于儒家的世俗人伦纲常。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王之治天下,必本彝伦”和“圣人之本”为“诚”的思想,是有内在关系的,因为对周敦颐来说,“诚”就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就是天下之常理、常道,他不过是将天下之常理、常道的“彝伦”更具体地解释为“诚”,而邢宥则将具体的“诚”一般性地理解为“彝伦”而已。当我们将圣人之本的“诚”与天下之常理、常道的“彝伦”相联系时,似乎也能看到圣人与天意,希圣与希天的相通之处和同一性。
从“希贤希圣又希天”到“治国齐家此一身”,反映的都是儒家思想中积极有为的一面。其实,儒家思想中除了“达则兼济天下”外,还有以颜回为代表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处世哲学。这种“独善其身”的人生观,在邢宥致仕归乡以后,完全取代了“希贤希圣又希天,治国齐家此一身”的人生追求。在《湄丘草亭记》中我们看到的是:
丘主人之孙宥,拜官南台,不俟老而致其事。既还故土,喜遂初志。乃伐丘之树为楹,斫丘之竹为椽,筑丘之土为墙。又剪丘之茅以苫盖之。作亭一间于旧所居之前,匾之曰“湄丘草亭”。客至,即延之茶。客退,则亭虚而静。春风秋月,冬暖夏凉。野树垂荫乎前后,梅竹桑麻交翠乎左右。亭主人俯仰瞻盼其间。意方有适,则检床头残简,或唤瓮底新醅,且研且酌,探颐陶情以消闲旷。兴发,则扶筇曳履,从一二童子徐步以出。或登丘隅,或临水湄。望浮云而觇飞鸟,观新涨而玩游鳞。心目以豁,志趣以舒,兴尽而还乎亭。神疲力倦,则隐郭几以徇懒僻,卧陶窗以遂黑甜。出而还,立而坐,睡而起,油油然率从意适,无所羁绊。以乐馀生,志意颇足。……吾将散吾情,故作湄丘之草亭。吾将漫吾游,故合水与山以名吾所居之丘。若谓吾丘无平泉绿野之侈,亭不似休休熙熙之雅,不足以乐,是未知吾之所以乐也。吾之乐,盖将拉无怀氏之民而友之,相与游乎太古。
“无怀氏”是谁?“无怀氏”就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陶渊明在其《五柳先生传》中也提到:“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宋罗泌的《路史·禅通纪三·无怀氏》解释说:“无怀氏,帝太昊之先。其抚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当世之人甘其食,乐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在这篇草亭记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颜回和陶渊明式的“箪食”“瓢饮”、乐在陋巷和“心远地自偏”的人生趣味。《辛丑初度日》诗中的“两间俯仰期无愧,百事修为贵有终”,则将自己的世俗修为与天地间的常理、常道联系在一起,使个人行为的有限性与天理良知的无限性完全相融为一体。
邢宥毕其生都在推崇儒家圣贤之道及其齐家治国的思想主张,与之相对的则是,他一生中都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对世俗生活中佛家信仰的贬黜。如果说,这就是邢宥的宗教观,似乎有点牵强。事实上,邢宥和中国古代大多数人一样,形而上的宗教观并不十分突出,涉及宗教的地方,往往只是在实用主义的现实行为方面。戴缙于邢宥去世当年所作的《文昌湄丘邢公状》中说:邢宥“教子弟有法,谈及祭祷,以为自纾其爱敬且宽病者之心则可,若谓佛能生死人则不可,始终不听异端邪说焉”。同时所作的刘吉的《中顺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邢公墓志铭》也提到,邢宥知苏州时,“率以俭约,诸游晏亭馆,老佛殿阁,一莫之顾”。这一宗教态度,邢宥自己也曾以各种方式表达过。如《琼州府学射圃记》中所云:
嗟夫!世之食公禄而力可为者,曾有几人而知所当为哉?金碧辉煌,有朘民脂而耸老佛之殿阁者;风月潇洒,有殚民力而张宴赏之池亭者。其视圃亭之作孰当耶?抑公之崇儒化,不啻此一事,若学校,若祭器,若揭经程艺,皆切切于心而为之未已。伟哉涂公!
他在大赞广东按察司副使涂伯辅兴建“射圃”“射亭”以崇儒化的同时,把那些“朘民脂而耸老佛之殿阁”与“殚民力而张宴赏之池亭”的人并列着都谴责了一番。在《族伯司训讷斋公墓葬表》一文中,他对族伯邢贵(号讷斋)为父亲做丧葬时“一依乎礼,不作佛事”,“能变旧习,俾治丧者不用浮屠,家信而里行之”,更是大加赞赏。
《安乐乡长寿歌》是邢宥为他的舅舅许伯乔老人八十寿辰所作:
……乌纱白发旧弱冠,云鹤相邀清且焕。自将名利等浮云,物外逍遥何羁绊。流水高山无常住,老翁胸中千古趣。不资金鼎炼神丹,静养清修安分素。此心无欲更无营,六脉清和百窍清。气血连通神秀发,性无戕贼自延龄。世人谋寿痴堪叹,念佛吃斋勤赛祷。不知作事要平心,却罔此心从左道。……
在这首诗中,邢宥既否定了“金鼎炼丹”式的崇道之妄,也批判了“念佛吃斋”式的信佛之痴。在他看来,这些举动都是世俗行为中的左道旁门,长寿的幸福更重要的是来自“作事要平心”,只有“自将名利等浮云”和“此心无欲更无营”,才能真正达到“物外逍遥何羁绊”和“性无戕贼自延龄”的人生境界。
“以公”“以实”“缘情据理”
“以公”“以实”“缘情据理”,以及勇于担当,可以作为邢宥二十余年仕途的总结。
综合同时代人描述的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来看,邢宥一生的政治业绩很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几件事。
1449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力劝英宗御驾亲征的太监王振被部下杀死。次年,即景泰元年,有诬告王振“家人孙太安匿其财者。牵连二十余人,事下锦衣卫鞠,如所诬。上命公(邢宥)往覆之,公辩诬,皆得释。”(刘吉《中顺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邢公墓志铭》)这件事在丘濬的《湄丘邢公墓志铭》中则被记载得更具细节性:“太监王振败,籍其家,有告其家人孙太安匿其财者。公与锦衣卫官于信者鞠之,无实,于必没入之,且曰:‘不然,祸立至。’公曰:‘无其情而文致于法,是我杀之也。’竟辩白被诬者二十余人。”邢宥时为监察御史,在处理这件事时,拒绝“无其情而文致于法”。这里的“情”就是“实情、事实”,“文”就是“文饰、虚构”。他既不落井下石也不屈服于威逼,而是据实处理。
还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邢宥出巡福建时发生的,“先是,巡按御史许仕达与镇守尚书薛希琏交恶,事闻,因命公代仕达,且核其事。公至,一断以公,无所回互。”此处刘吉《中顺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邢公墓志铭》作“公一以实复,不少避”。
二是邢宥出按辽东,“时都御史寇深巡抚其地,副将焦礼有克敌功,寇上其功状,乃先以主将曹义,事下覆之。寇为曹私嘱,公不从,遂与成隙。……时寇深总内台,恨公在辽东时事,多方捃摭之,无所得。及公秩满,需铨曹。适知县甄铎有故勘人命狱,有言忠国公石亨纳其赂纵之者,命下勘之,众皆畏势莫敢犯者。寇以公名奏,委核其实,盖欲假是以中伤公也。公审核允当,讫莫能害。”此处刘吉《中顺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邢公墓志铭》作“公覆以实,竟莫奈何”。
三是邢宥“升知台州府。台俗健讼,公治之,一惟缘情据理,民自信服”。
四是邢宥“改知苏州。苏之田赋甲天下,丁役杂办视他郡盖倍蓰焉,而俗尚浇浮。公治之,一本情理,不出奇,不立苛,惟省役均赋,节浮费,以便民为主。不期月,政化民洽,歌颂之声,播闻远近。公性不乐华靡,且厌浙西俗尚过侈,凡百有为,务从简素。神祠惟涓洁其在祀典者,廨宇惟修葺其切于用者”。
又:“成化丙戌,江南大水,而苏尤甚。公发官储及劝富民,得米八十余万石,赈之。然犹不继。饥民百十持券入富室借之,不与则夺。公即帖示,俾饥民指其闭籴者名赴官,官为之借。明日,争持状赴府,官为署券付乡老,俾同保借,又得米八万石。又不继,乃会计军饷一年之外余二十万石,发以赈之。同官有以事未上闻难者,公曰:‘民命在须臾,奏允而后给,则无及矣。专擅之罪,吾自当之。’是岁,稔活饥民殆四十余万口。”①
在以上各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或利益纠纷,还是教化积久成习的地方陋俗,抑或应对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邢宥或断以公、覆以实,或缘情据理,或勇于担当。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以“诚”为本,以“仁义中正”“至公”为道的儒家精神实质在他身上不同方式的表现。
正如周敦颐所谓“圣,诚而已矣。……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②我们已经知道,在邢宥的理解中,所谓诚,就是“彝伦”——天下之常理、常道,换句话说,就是“仁义中正”“至公”。其实,在邢宥的实际行为中,应该再加上一个“常情”。正是“常理”“常道”“常情”,构成了邢宥所说的“彝伦”——也就是周敦颐所说的“诚”——这才是天地间的真正的大道,是所谓“圣人之本”,也是“圣人之道”的精神实质。从以上举例都能看出,邢宥在他生平仕途中,对许多重要事件的处理,几乎就是在努力地践行“圣人之本”和“圣人之道”。
“天下之士”
各种关于邢宥的评价中,丘濬给邢宥的赠辞和评语中,有两段材料特别值得一提。其中一条材料是明景帝景泰七年(1456)夏四月,邢宥回乡省亲时,丘濬在《送邢侍御克宽归省诗后序》中写的:
余惟吾郡自昔仕于朝,得推恩以荣亲者,固有矣。而及其亲之存者,前此未之有也。有之实自君始。嗟乎!前之无者,至我而肇,后之有者,自我以始,其为荣也,孰尚焉。君之归抵琼也,父子妇姑,相见于久阔之后,载拜载问,欢忻怡愉一堂之间,纱帽豸袍,珠翟锦衣,辉映上下。既而有事于寝,展祭于墓,既毕,而燕宗属姻娅,朋侪故旧,乡人父老,是集是临。兹时也,必有目其实而赍咨叹息,以为自昔未有者矣,亦必有闻其风而感发兴起。为父者思所以教其子,为子者思所以励其志者矣。又有必感其事而悲其生之不幸,有子而不克肖,有亲而不侍养者矣。於戏,君之兹行,此其为乡邦之光,闾里之劝,非特今世为然,后此千百年之久,又安知无传其事以为美谈,播之声诗,纪之图志,以贻无穷者哉。
在这段材料中,丘濬也特意提到了“御史历两考,必有升擢之荣。矧君端严,得宪臣体,使少待旬月间,不次之擢可几矣。……而君一旦不谋于同列,不告于朋友,即决然以去,其视贪荣违亲,以冀非分之望于不可必得,而苟安以徼幸其或至者,真不啻天渊矣”。邢宥在历官七年之久,眼看就有“升擢之荣”时却决然而去,回乡省亲,全然不在意“升擢”的机会。对这位乡里好友的如此举动,丘濬虽也一再赞为“贤也哉”,但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丘濬真正动心动情向往不已的是他立足于吾郡一乡一地的“乡邦之光,闾里之劝”,对邢宥“纱帽豸袍,珠翟锦衣,辉映上下”的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时盛况的欣羡。
在邢宥致仕(成化六年,1479)以后,丘濬在他的《邢湄邱公像赞》里,对至交好友则是这样评价的:
五岭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气,于此焉萃。立朝著蹇蹇之节,出守敷优优之治。总宪网,存法外之仁;制国用,寓利中之义。众方俟其有为,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执,直而不肆。不随时之好,必行己之志。匪但秀出于岭海之间,殆所谓天下之士也与。(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二十二)
在这段评语中,有意思也最富有想象力的是两句总评:“匪但秀出于岭海之间,殆所谓天下之士也与。”很显然,“秀出于岭海之间”依然还是站在“吾郡”“吾乡”的海南的角度,对这位乡里前辈出众的才华、品德及取得的政绩的赞赏。而“所谓天下之士也与”,则是超出于海南一地之见,站在了“天下”的高度对邢宥的评价和肯定,这与一乡地的“乡邦之光,闾里之劝”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什么是“天下之士”,什么样的人才够得上是“天下之士”?
我们知道,“士”有普通之“士”,有“高士”,也有“天下之士”。“士”原本指的不过是普通男子,引申为有身份的男士、官吏等。“高士”,或等同于“高人”,汉代王充《论衡·自记》中说:“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显然是指超出普通“士”之上的出众者。至于“天下之士”,这一提法原出于《战国策·赵策》。秦围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魏。魏慑于秦之强,虽派兵往救却又按兵不动,同时派辛垣衍前去劝赵尊秦为帝。值此存亡攸关之际,齐国人鲁仲连挺身而出,他在与辛垣衍的辩论中,以雄辩之力说服辛垣衍放弃“帝秦”,也使秦人闻风而退,折服后的辛垣衍拜而谢之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故事中,辛垣衍曾称鲁仲连为“高士”,后又改称之为“天下之士”①,区别似乎就在于,作为高士的鲁仲连,只是“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而作为“天下之士”的鲁仲连,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在鲁仲连的时代和鲁仲连的身上是“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一无所取,而邢宥作为明代的朝廷大臣,在丘濬看来,第一次的省亲是面临“升擢之荣”时,决然以去;第二次的致仕则是“众方俟其有为,乃急流而勇退”,邢宥是在“为国”排患、释难、解纷乱而后无所取。这不是天下之士是什么?
然而,在我们看来,丘濬对邢宥许之以“天下之士”,除了指明他为国排患、释难、解纷乱而后一无所取的品格之外,似乎还在暗示,邢宥“匪但秀出于岭海之间”,而且还是“天下之士”。换句话说,邢宥作为一天下之士,与“岭海”之间的一秀出之士相比,除了原有的“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品质,显然还具有一种不拘吾郡一乡之面,而远超出孤岛乃至岭海的能兼济天下的品德和才华。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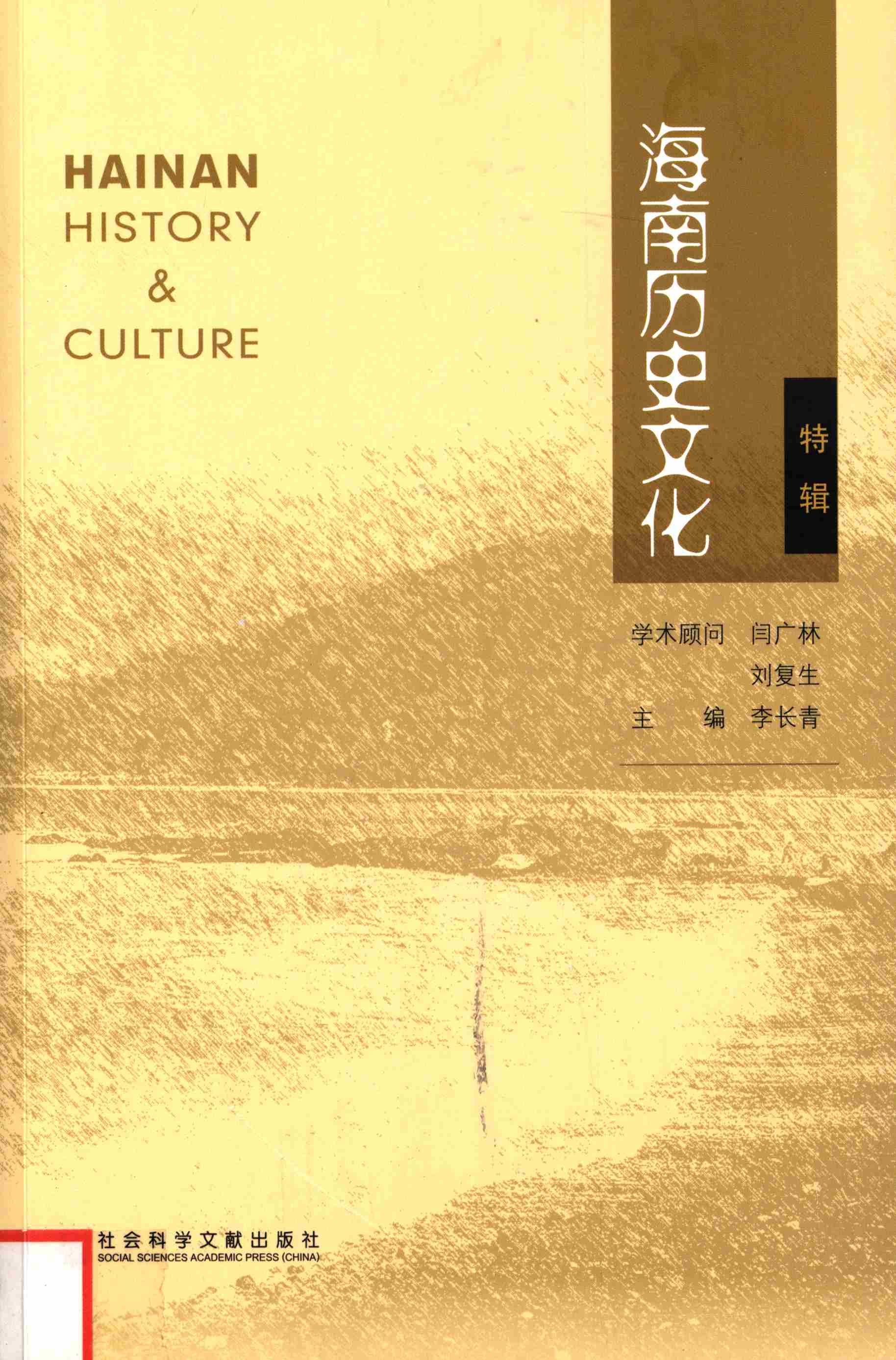
《海南历史文化.特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设有历史渊源、文化嬗变、黎族研究、地方文化、移民文化、历史人物、海洋文化”七个栏目。收录了《海南史前考古概述》《1882年美国人香便文海南岛之行日期考》《黎族文身的抢救性保护与合理利用》《三亚历史上的族群和多元一体文化》《从地名看海南移民文化》等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海南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