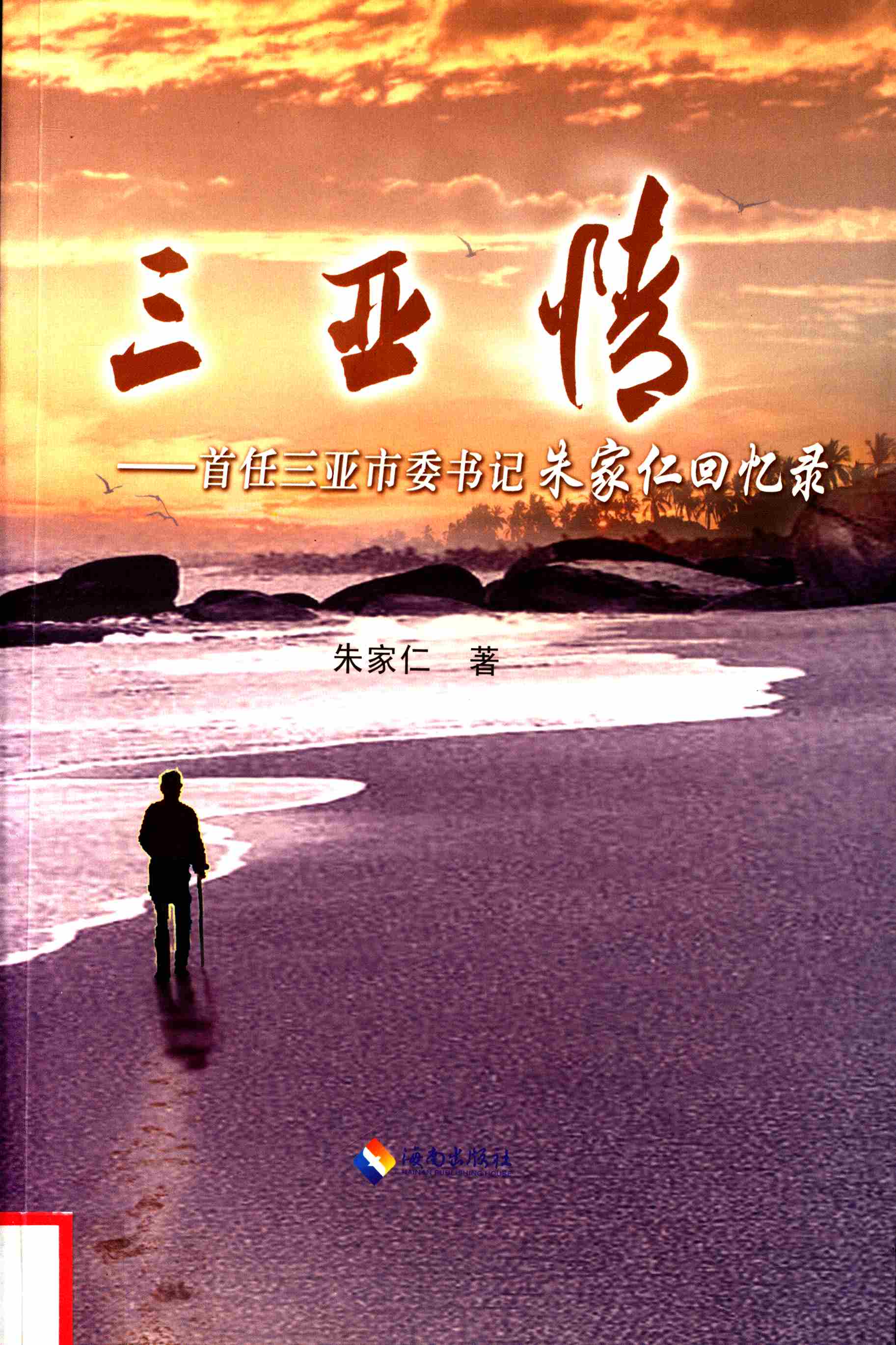内容
大海无痕,但在海岸上留下了潮印。岁月无痕,却在岁月的碟上刻出亘古的歌。人生实际是在触摸岁月的痕,刻画亘古的歌。
——题记
一、我的童年
我是1931年2月(农历辛未年二月十六)出生的。按老百姓的话讲,这个日子很好。我父亲虽然未有读过“四书五经”,但他略懂一些“生辰八字”的常识,很相信人的“命行运程”,他说,二月十六是赵公明(财神)从天庭下凡赐福的日子。再加上我是申时出生,父母亲很高兴,认为儿子命好,希望从此为朱家人带来好运,光宗耀祖,兴旺门庭。
“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我的老家在澄迈县城郊大坡村,原属于“耕读传家”门第。后来,祖父因侍奉本村财主烧“烟泡”而被动地染上了鸦片烟瘾,导致家道中落。到父亲朱儒星长大成人时,已经家无蓄积,指靠父亲终年往返临高、马袅等地运销盐等杂货,赚些运费及蝇头小利维持生活。也许是父亲亲身体会的经验总结,他嘱咐我长大后不要做生意,我也顺从了父母亲的意愿,从小就暗下决心努力读书。
我七岁时,不幸染上了痢疾,二老把所有能用的药方都用过了,医治了半年,仍然未见好转,无休止的病痛把我折磨成面黄肌瘦,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皮包骨。我父母似乎对我已经丧失了医治的信心,认为我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了。吃饭的时候,其他的东西我都不能吃,只能用盐巴拌饭吃。有一天,我父亲买回了一串小咸鱼挂在墙上,我看到后很想吃,向父母亲跪下,要求给我小咸鱼下饭吃。我母亲担心吃小咸鱼不利于治病,父亲说:“给他吃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听天由命了。”也许是小咸鱼很腥、很咸或其他原因,吃了几次小咸鱼之后,竟然止住了痢疾,接着连续半个月,母亲经常给我小咸鱼下饭吃。
未想到,我吃小咸鱼下饭吃出了奇迹,竟然治好了我的“不治之症”,我父母亲既惊讶又欣慰地说:“没想到小咸鱼竟然成了灵丹妙药!”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很忠厚,虽然不懂“道院迎仙客,书堂隐相儒”的哲理,但他却深知“子不教,父之过”等为人父母的责任。我记得在五岁时,就开始了“论交三世久,问字两儿趋”的私塾启蒙学习。
童年,我的父母先后在村里请了两位名叫廖坤迫、廖守承的老先生当我步入书文的启蒙老师,这两位老先生熟读四书五经,精通诸子百家。从他们当时给我起的“朱家仁”学名,即可窥见一斑。按廖坤迫老先生讲,朱家得仁(即德仁)这个名字,是中国古代含义十分广泛的道德范畴,原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即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然,作为父亲、母亲和老师,他们也希望我长大成人之后,经世致用,光耀门庭。比如我小的时候脑袋较大,他们就半开玩笑地说:“大脑袋聪明。”当然,我父亲不仅嘴上对我说,心里也是这样希望的。因此,我在五岁半时,父母亲就让我开始了“学海茫茫,五载索句,辑册成章,耳熟能详”的私塾学习生活。
二、才华初露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孔子格言)
1945年,我14岁,正是我步入青年、视野初开、激情奔放的风华正茂时期。这一年,是日本侵华战争宣告结束、华夏民族坚持八年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一年。值得我个人记述的是,这一年也是我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开始革命斗争的一年。
我的老家在距澄迈县城三公里的农村,叫大坡村(相当于现在的城乡结合部),是当时国共双方活动频繁、斗争力量交错、形势十分复杂的“插花”地带。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期我们村比较特殊:一方面大坡村是伪乡公所的所在地,一方面又是共产党革命斗争十分活跃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无论是国共合作时期,或者是内战时期,我们村经常有共产党员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记得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就开始对共产党员进行反革命屠杀,斗争十分残酷。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转入了秘密的地下斗争。
1946年春节,有几名共产党员在我们村里过夜。由于伪乡公所的报告,正月初二,国民党的兵就把我们村包围得水泄不通。
当时我的叔叔是村长,扮演着“白皮红心”的角色。“白皮”,即表面上是应付国民党,而“红心”实际就是共产党的联络员。
在当时,国民党匪军搜捕共产党的情况十分危急,在既无暗道脱身,又无水路可潜的情况下,这几位共产党员无处藏身。由于时间紧迫,我叔叔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我在一旁看在眼里,也着急在心。幸好,我家的地点在村中心,住房旁边有一间没有后门小房子,海南话叫“包尸房”,平常也没有人住,房子里放的全是稻草。国民党匪军为了搜出共产党,采取了逐户搜查的野蛮办法,他们从村外搜到村内,凡是门关着的房屋他们就抄家。当时,情况紧急,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几名共产党员在实在无处可以隐蔽的情况下,躲进了“包尸房”。眼看着国民党匪军快搜查过来了,叔叔一时没有了主意,问我:“你看门是关着好还是开着好?”
河狭水急,情急生智。
我见叔叔一时没有主意,只好急中生智地说:“你们都躲在屋内的稻草下面,并且把房门开着。”
我想,一般人都很忌讳走进停放死人尸体的房子,倘若是门开着,敌人即认为屋内没有什么可疑之物;倘若门关着,就值得怀疑了。人家(指国民党)一定会进来搜。而且,面对敌人搜捕,开着门可以一目了然,万一不行,也可以通过事前观察好的地形与方位进行突围。也许是天气已晚或其他缘故,结果真如我的想法,包尸房没有被抄,几位共产党员也躲过了国民党匪军的搜捕。
后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给叔叔出“空城计”的主意,帮助共产党躲过敌人搜捕的事,被国民党的人知道了,结果在我上学的问题上制造了麻烦。好在他们在“究竟是谁家的人帮助了共产党”的问题方面“对不上号”,但他们采取了最狠毒的一招——凡是大坡村的学生升学方面都“紧紧地卡住脖子”,不准所有大坡村的子弟升学读书。
1948年,我在澄迈只念了半年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初中,本来成绩很好,但也因为当时在大坡村的“空城计”使我“名落孙山”。后来才知道,澄迈中学校长是国民党,之后又当上了澄迈县县长。我本来升学考试成绩优良,已考上了,可学校就是不录取我。我姑丈在学校当教导主任,他知道考试录取情况,但是,这个国民党的校长坚决把我的名字撤下来。对此,我非常恼火,说实话,我当时心情悲愤,曾想到同这个校长大干一场,甚至想到用炸弹和他同归于尽。但是,由于父母亲担心我只凭一时之气而导致杀身之祸,二老都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民不与官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由于二老坚决不让我去冒险报仇,我也就听从了他们的劝诫。我想到我年迈的父母亲十分辛苦,父亲为了供养我读书,卖猪、卖稻谷,把家里只要是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为了不让二老担忧,我产生了离开澄迈,去县外上学的想法。后来,我有幸在海口汇文中学读了初中,虽说那时候一年要交50元光洋的学费,但是这所中学可是海南岛上的一流中学。
1949年下半年,我读完初中,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当时,全国各地都解放了。但海南岛还未解放,由于渡海战争在即,海口的中学学校情况很乱,几乎没有学生上课了。1949年底,我又转回到澄迈中学。在幼年,我从念小学到念中学的学习成绩我一直是名列前茅,这说明我自小就是勤奋学习的优秀学生。
三、挥斥方遒
伟人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沁园春·长沙》词中写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洋溢着青春的热情奔放和抨击恶浊、褒扬清明的壮志情怀。
我们海南岛是1950年5月1日解放的。在此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在澄迈风门岭战斗中取得了上岛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紧接着,经过“包围和反包围”的几场激战,最终取得解放海南岛的全面胜利。在1950年剿匪斗争中,由于我懂得几句普通话,叫我担任围剿国民党残匪的工作队区小队副队长。在第一次剿匪战斗中我带了30个人,在上级部队和兄弟部队的共同合围之中,部队首战告捷,歼灭了国民党专员的弟弟。那年我刚好满19岁。从此之后,我就坚定地加入了革命队伍。对我个人进步而言,确是我走向革命之路的宝贵经历。
同年9月,我参加了“八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工作队,一直到任命我为土改工作队队长。在当时,土改工作队队长领导100多号人,还是配枪的。虽说是土改工作队,但是权力很大,比如对地主、恶霸、反革命罪犯的枪毙或赦免等人命关天之事都要我签名。
通过上述经历的革命考验,1952年土改结束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先进模范。那年我刚满21岁。
人生总是要在复杂多变的矛盾中进步、发展的。我加入党组织后,由于琼海县的干部和群众对我的工作反映非常好,琼海县要留我当区长。但带队的陈在伦同志要我去海口,让我在海南区机关党委当了一名宣传干事,据他讲是重用了。海南区党委副书记莫燕忠同志点名要我跟他到琼海去办社(农业初级合作社),专门要我当他的翻译,一定要叫我留在琼海。在当时,他为了让我跟他去琼海,还介绍我和一个乡上的女干部见面,我说:“我很年轻,你留我,可以呀。”对此,我口头应承,在心里却不想谈这个“对象”。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区党委干部科长黄儒同志的安排,奉命调到自治州工作,忠实履行“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服从组织安排”。这也是解放初期干部制度和行为品行的基本原则。
到了自治州党委,州党委安排我做书记处秘书。三个月以后,党组织又提拔我担任秘书科副科长,担任理论科副科长,直至担任宣传科科长。
1957年7月,自治州党委又任命我担任自治州师范学校校长,任命我担任校长时,我年仅26岁,有很多学生的年龄比我的年龄还要大。1959年3月,由于自治州党委要加强宣传力量,上级又任命我担任《五指山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现在回想起来,我担任《五指山报》报社社长时,既是社长,又是记者、编辑、编审、校对,是一位身兼五职的“一把手”。很多代表州党委声音的社论、报告文学等大篇幅文章,都是我亲自撰写的。由于当时我年轻,脑子灵,加上平时注重学习,洋洋千言,一挥而就,可谓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当时,我的文笔书写已小有名气,他们说我是“自治州党委的一支笔”。
四、岁月如歌
回忆,往往是一种情感思索,承载的是岁月,品味的是感悟,演绎的是人生。
我在任崖县县委书记之前,特别是1960—1989年之间,值得回忆并记述的,是我人生历程中堪称“重要时期”的经历。
20世纪中期,全身心关注中国农村、被《人民日报》赞誉为“农民作家”的赵树理先生在他的著作《邪不压正》中,称1960年的中国农村是“天聋地哑”,也是中国近代史所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为什么这位历任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著名作家赵树理先生会发出“1960年的中国农村是‘天聋地哑’”的声音呢?
可以说现在凡是50岁以上,特别是55岁以上的农村人都记得,那是一个把人饿得吃光了树皮草根、把一碗米饭看得比现在山珍海味还要金贵百倍、一粒米落在地上也会拾起来吃掉且令旁人“眼馋”的年月。
“大跃进”——浮夸的“高产卫星”。
自从1958年1月,海南区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把粮食生产增长一倍以上的“大跃进”指标之后,海南岛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同年8月4日—6日,海南区委又提出“在全岛实现粮食亩产‘双千斤’的高产指标”。由于这种严重脱离实际、在当时条件下根本不能实现的高产指标,导致下面层层加压的虚报和浮夸。于是,放“高产卫星”的浮夸之风席卷了全岛……最后呢?农村出现了吃光了所有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无米下锅用瓜菜代替粮食做饭的大面积灾荒,形势非常严峻。偏偏在这个艰难时期(1959年)海南岛要组织大县,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和行政机关撤销了,打乱了行政管理,把小东方县、白沙县、昌江县、昌感县四个县组成为一个东方县,县委、县政府驻沙河。之后,县委、县政府在沙河驻半年时间,又奉命迁移到八所。
1959年,我当过东方县县委宣传部部长。1960年东方县又分开了。也就在这“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整风反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深挖”、“深入”和农村“民主补课”等运动,我的父亲在家里出现了问题。
事件的起因是,我当上县委宣传部部长后,我的家乡大坡村里有些仇恨我父亲的人分外眼红。他们趁1960年农村进行阶级成分“民主补课”(即补定家庭成分)运动的机会,一位对我父亲怀有怨气的“贫下中农协会”主要领导,乘机把我家评成了地主成分。并且在暗中煽动了一些人,十分凶狠地将我父亲打倒在地还拳打脚踢……之后,他们把我父亲及全家老少赶出家门,将我家的财产全部没收。
我父亲那天非常气愤,想不开,拿绳子准备上吊自杀。幸好我父亲有个叫廖坤安的好朋友,他担心我父亲受不了这次打击,深更半夜去观察我父亲的动静。当他看到我父亲系好绳子准备上吊之时,他推开房门把我父亲解救下来。他见我父亲气愤不已,好言相劝道:“星爹,你不要自寻短见,你生闷气是不行的,更不能寻死觅活。你的儿子朱家仁是一个懂政策有出息的人,你要把家里受冤屈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你有儿子朱家仁在,你就有出头之日。”
我得知家里遭人报复的情况后,我写信告诉他们,让他们相信我和村里的乡亲。我也同时将村里某些人趁“民主补课”运动,打击报复我家的情况,写信寄给海南区党委李黎明副书记和澄迈县委何友信书记申述反映。后来,经过查三代、五代的核实,三个月之后,村里改定我家为中农成分,家人依原搬回原来的房子。
1961年,农村生活非常困难,主要是家家都无米下锅,指靠“瓜菜”代替粮食做饭吃了。我在东方县的农村工作队也吃不饱饭,早上九点一顿酸瓜粥,晚上九点一顿酸瓜粥,为了避免晚上挨饿,只有拼命地喝饱,把肚子喝得像怀崽的母猪一样。到了晚上十点开始拉尿,到了夜里一点,喝的稀酸瓜粥就拉光了。夜里饿急了,只好又起来喝水。很多人在田里站久了就会晕倒在地,饿了只有喝水充饥,把肚子喝得走起路来都会咣当作响。那种饿的状况现在不堪回首。就在这时候,我不幸得了水肿病,手、脚已经全都肿了,手摸不着腚。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上级还要我到广州去开会,很多人认为我去了就没命了,可能回不来了。
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我到广州之后,有位同志就帮我找医生。医生叫吴华民,广东省中医顾问。他见我得的是要命的慢性肾炎病,而且已到晚期。为了稳定我的情绪,他说:“你生的这个不是常见疾病,是绝症,是不治之症。但现在还不是晚期,如不及时治疗就会送命。”他说,我要他治,必须答应他做到以下五点:
第一,不准跟老婆“同房”(我说这点我能做到);
第二,大量增加营养(我说这点确实很困难,当时什么营养品都没得吃);
第三,不准喝酒(我说这个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从小到大就不喝酒);
第四,不准干重活(我说我尽量做到);
第五,不准感冒,如果感冒,药路就死了;
第六,不准吃盐。
当时,医生给我开了一副药,叫加减归脾汤。我因小时候做过药店的药童,懂得一些中药药性与药方,在广州治病且病情略有好转之后,我按加减归脾汤药方13味中药的剂量,配了多副中药带回家自己调理服用。半年之后,我的肾炎病被彻底地治断根了。因此人们说我是个奇人。
我的病治好后,我又把这方子告诉别人,还治好了另外三个病人。尤其是我把这个治肾病的方子告诉崖县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河山之后,不仅治好了他妻子的肾病,后来他妻子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从此,陈河山见了我就抱拳作揖,喜笑颜开,感激得不得了,称我为“神医”。
五、雾里看花
本来,雾里看花是一个形容对事物看不真切的成语。但长期形成的绝对公有制、平均分配等极“左”思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所出现的过错,人们却讳莫如深,如云如雾……
终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答案,人们从亲身经历的痛苦中“悟”出来了。
后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终于才清楚地认识到,1960年的中国农村“天聋地哑”的原因。
是由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亩田产稻谷一万斤以上的浮夸风——强迫农民把十几亩田生产的水稻堆放在一起,并且连稻草一起计算数量,虚报浮夸。
是“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砍光了大树炼钢铁,树砍完了就拆门窗、砸家具大炼钢铁。后来,为了凑钢铁数量,完不成任务要农民砸锅献铁。“反正已进入社会主义,农民自家不做饭了吃食堂”;于是,除农具之外,农民已“交”光了家里所有含铁物质的金属家具。
是农村全面开展“食堂化”,“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估计。结果呢?先是四菜一汤,后来连稀粥也喝不上了。到了1959年下半年,农村什么都吃光了,人们开始吃树皮、吃草根,成批成批的人被饿得患浮肿病,妇女们被累、被饿得“子宫下垂”,尤其触目惊心的是,1959年冬季之后,很多农民开始被活活饿死……
比如在东方县,一些基层干部为应付检查,就造假了。为了掩盖真相,他们弄虚作假,在竹围囤的下面放谷糠、放沙石,在谷糠、沙石的上面铺一层稻谷让人看,应付“上面派来的干部”检查。实际是假的。
在这种弄虚作假、天灾人祸之后,海南岛农村已陷入饥饿的深渊。没有粮食,农民只能吃“瓜菜代”了。
什么是瓜菜代呢?当时田地里种的庄稼没有收成,食堂在煮饭的时候用蕃薯和菜叶代替粮食充饥,这种“瓜菜代”饭食煮好后基本上看不到米,由于蕃薯在地里晒的时候粘上了很多沙石,虽说已经过筛子,但用水煮过后,蕃薯干上依然残留很多沙粒,咬起来嘎吱嘎吱的响,崩得人牙根发麻,根本吃不下去……
1960年春天,由于饥饿难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饿死人了。那时候人们穿的衣服呢?且不说样式,未有补丁就是最好的衣裳。每人每年只有5市尺布票(每市尺约合33.33厘米),5尺布票不够做一件衣服,只能做条裤叉,很多农民衣不遮体。
1960年夏天,村里开始成批地饿死人了,有的全家人死光了都没有人处理后事。后来所有能吃的都没有了,农民们在饿急了之后,开始想到用杀死帮他们劳动的耕牛、暂且保命的悲哀办法。
牛是当时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毛主席一直不准农村宰杀耕牛。由于上级不准杀耕牛,老牛越来越多。“瘦牛怕过冬,干部怕运动”。耕牛又是集体财产。那时候,人都没有饭吃了哪里还有粮食去喂牛呢?所以,当时的耕牛非常瘦,尤其是冬天,许多牛也快被饿死了。牛要死之前,毛是竖着的。驻村的工作队发现瘦牛问题之后立即向县上作了汇报。县上开会要求一定要做好保护耕牛的工作,县里的主要领导还专门派工作队下乡救牛。
怎么救呢?就是用白米加糖熬粥,再用竹筒向牛嘴巴里灌。但是,老百姓饿急了就不这么想,他们在腰里别着一把刀,围在牛的周围,恨不得牛马上死了割几块肉吃。工作队员下乡,老百姓是“另眼”看待。这时候的老百姓是想活命,认为是工作队把他们整得没有饭吃,他们跟工作队对着干,把工作队当仇人。
1961年,党中央通过大量的专题调查,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之后,农村情况才逐步好转,后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开了一次干部会,他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花明者,自留地也!”准许农民搞一点“救命的自留地”,可以在自留地里种红薯、种玉米,在“打饥荒”时把嫩玉米磨成浆,加南瓜一起煮粥,“南瓜浆,渡粮荒”。农民开始能吃饱饭了,从此,农村人民生活“才得到真正意义的恢复”,避免了农村饿死人的现象。
1962年,广东省委决定恢复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恢复后,为了加强农业,自治州党委又把我调回自治州农村工作部。当时,由于人民公社化的绝对公有制、平均分配、吃大锅饭等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农村粮食不能自给,解决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吃饭的农业问题,一直是各级党委的首要任务。那时候农村工作最重要了,1963年我在农村工作部经营科当科长,1964年任命我担任农业干部学校校长,1965年又任命我担任自治州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这场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岁月里,我在东方县龙卧村当工作队长,我遇到的一个叫苏亚秦的农民,与他的谈话让我至今难忘。
那是1961年下半年,龙卧村几乎家家都饿死了人,唯有这个叫苏亚秦的家里没有饿死人。他是大队长兼保管员,负责管理全村粮食和物质仓库的钥匙。社员们说他家多吃多占才没有饿死人。工作队要我去询问他。苏亚秦说:“朱大哥,我太冤枉。为什么我家没有死人呢?因为我是铁打的心肠才没死人的哟。我俩(夫妻)是全家的主要劳力,我父亲要我们上山去找‘瓜菜代’之前,一定要我俩填饱肚子,保住命,然后才给小孩和父母亲吃。父亲说,就是他们二老和孩子们都饿死了,只要留住我们两个活下去还可以再生。如果都吃一般多,全家人都会饿死,我们家就绝后了。你为我家传宗接代了,不仅不是不孝,是大孝。我按照父亲的意见去做,结果不仅家里没有死人,而且还保住了全家。”
在眼睁睁地看着到处都没有东西吃的年月,我就让苏亚秦把这种保命办法对村里人说,并且在心里暗自肯定了这种保命传人的办法。
六、十年魔魇
“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唐·韩愈《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献杨常侍》)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到后来“革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开始批判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金猴奋起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
就在武斗乱得最厉害的时侯,有些眼红我的同志,认为整我的时机又到了。1968年,这几个人为了把我打成“反革命”,他们以“外调”为名,到处找194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长安小学的档案,他们在这所学校的教师(几乎全是国民党员)的档案上,伪造字迹,把我的名字添加在国民党党员的花名册上。他们以“潜伏的阶级敌人”之罪名把我打倒在地,并且是“证据确凿”。
那时候我惨极了,我的爱人怀孕被打伤流产,赶出原来自己盖的房子,我们被迫另外在山边盖毛草房栖身,我爱人流产了,全家都没有过好年。说我是国民党的骨干分子,说我是在共产党内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是在深挖阶级敌人运动中“挖”出来的,要把我清除出革命队伍。我不服,要上诉,结果我挨斗挨批了。
1976年以后,各地的党组织基本被冲击了,各省、市、县的政权名称是××县革命委员会。到1970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我专门就这件受诬陷事件写信给自治州革命委员会刘荣主任,请求上级调查落实。我因为曾经给刘荣主任当过秘书,所以他对我的为人非常了解。刘荣主任收到我反映情况的书信之后,连夜派人去查阅作为“证据”的档案,专案人员通过笔迹和墨迹比对,认定我那个名字是后来另外(添加)写上去的。为我平了反,把我从五七干校依原调回自治州当革委会新闻报道组组长。之后,又叫我担任革委会政工组宣传办公室副主任。1972年,任命我担任自治州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1976—1979年,我被下放到琼中长征公社搞农村“路线教育”。那时候,在农村搞农业生产的基本上都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弟,也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贫下中农”说他们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可以不搞生产。
农民是要种田的,农民不种田,吃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从1969—1979年,全海南岛各地都缺粮食,导致农民吃不饱饭的农业生产问题,是长期困扰海南岛的首要问题。
我在东方新村公社龙卧村,生产队种的水稻刚刚发黄粒的时候就有人偷。上级叫我们驻村工作队“务必保护劳动果实”,并决定由我带一个工作队和民兵排去检查,要防止老百姓去偷“劳动果实”。去了之后发现,实际去偷稻谷的是民兵的家属,他们不仅不抓,还当掩护。后来,靠民兵守不住了,就叫工作队员“掺沙子”去守。结果呢?逮住的“小偷”,却令工作队既啼笑皆非又心余力绌。
是什么人偷这些刚刚发黄的稻谷谷粒呢?令我痛心的是,这些“小偷”竟然是十岁左右的小孩、中年妇女以及老人。特别是妇女,如果要抓她们,她们不怕,而且当着工作队员的面脱光了裤子!队员苏良跑步向我报告了这个情况,我说:
“撤!马上收队。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苏良不懂,问我:
“为什么?”
我见他不懂,耐心地解释说:
“有句古话道:‘人饿了不要面子,鸡饿了不怕棍子。’鸡要饿了,你拿棍子赶它,它要吃,所以它不怕;当这些农村妇女饿了脸面就不顾了,脱裤子,你就不能再去抓她们,把她们逼急了,她们会说工作队如何如何,你就没有道理了。”
在当时我心里很是难过,尤其是看着那些面黄肌瘦、严重营养不良的小孩子们挨饿,更是让我心痛!他们可正是上学和玩耍的年龄啊!如果不是饥饿,他们是不会在田里“掐谷粒”的。
“民以食为天”,没有饭吃四处颠啊!我心里想,是不是我们的政策出错了?几经考虑,我觉得长期这样搞不行,不包产到户不行了,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我召集了村上几个有威望的老农民和村干部座谈,经过商量,决定按人口分摊生产责任田,责任到户,任务到人,大家都同意我的想法。包产到户后,干多干少都是自己的。大家都争着干活,争着种粮,有了粮食就解决了吃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央包产到户政策下来前,我们已经“大胆”地走了一步,效果很好,人人拼命干,再也没有好吃懒做的现象了。
后来,我在琼中长征公社搞包产到户的事被县上发现了,很多人认为我是搞复辟了,加上我家“民主补课”时曾经被划成过三个月的“地主”,有人背后还酝酿要批斗我,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由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7月6日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9月9日毛泽东主席久病不治),国家连续发生的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上面”对农村包产到户是否是资本主义之类的问题,似乎已不太在意了。并且传出“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可能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责任制实际就是包产到户”等“小道消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也意识到可能会有较大的社会变革了。
结果,那些告我的人告得好,上面要以我抓的这个村为榜样,召开现场会推广。琼中县换届征求各公社党委意见,很多公社书记还要推选我当书记。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不同意,他们派人来找我,并且要调我回自治州。
七、两度“崖州”
把三亚建设成国际著名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是我担任崖县县委书记和首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一心想努力办成的一件大事。
今日三亚,古称崖州。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崖县,后撤销崖县设立为三亚市,这里不仅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还是一座文化积淀十分丰厚的文化古城。据《崖州志》载:仅唐、宋两代就有李德裕、卢多逊等十余名朝廷宰相和王仕熙、范椁等达官名人在崖城“读写”人生。如今,“古崖州”城池所在地崖城,已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1980年12月,经林祖基书记建议,我奉命调到崖县任第一副书记,让我分管城市建设,并且兼任三亚镇党委书记。到任后,我首先想尽快地改变原来三亚镇的脏、乱、差的落后面貌。我向林祖基书记提议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三亚城镇建设和环境治理问题,并且以中共崖县县委【1980】第43号文《关于立即停止在三亚河两岸建房子的通知》“告知全县”,令行禁止。这个文件是我到崖县任县委第一副书记、对治理环境污染、向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迈进的第一道檄文。当时,我工作十分扎实认真,对污染三亚河水、三亚环境的楼堂馆所坚决拆除!不批!不建!一丝不苟!雷厉风行。为此,首战告捷,但负面影响是我因此得罪了一大批人。
我热爱三亚。就是因为我有这份真心真意,达不到目的,决不罢休。我在崖县工作中,逐步发现了这里有国内唯一的热带气候条件,是建设发展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最独特的稀有气候资源。我就想办法宣传,并希望尽快地见到成效。
然而,“点塔七层,不如暗处一灯”。就在我一心想在三亚干出成效、为三亚人民多做点好事的大展宏图之际,在1981年的选举中,由于我太认真(尤其是在撤除违章建筑物中)得罪了一些人,加之在发展观念方面,我的想法(以旅游业为主)与当时“以粮为纲”的方针有分歧,尤其是干部之间的不同地区关系与“派系”,我落选了。可称为一度离开崖县。
当时,我们这一级的干部实行的是双重管理制度,县级干部是海南行政区和广东省管,县级以下是自治州管,崖县在1980年之前是海南岛最偏僻、最贫穷、最南端的一个县。那时候,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加之公路崎岖,交通十分落后。我落选后,心里十分委屈,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腔热情无处诉说之感。1981年夏季,林祖基同志奉命调离崖县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秘书长,我被调离崖县,任州党委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协助州党委王越丰同志修建州政府大楼,1982年12月,大楼竣工之后,州党委任命我担任州委宣传部部长。
1983年12月27日,我在家侍奉重病的父亲。本想在家多尽几天孝道,不料12月30日,自治州党委派车队队长廖坤树同志到我家通知说:
“朱部长,州党委派我通知并接你回自治州,广东省委已任命你担任中共崖县县委书记,要求你立即赴任。”……
接到通知后,我百感交集。忠孝不能两全啊!我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子,酸、甜、苦、辣、涩五味俱全,想起了病重的父亲还卧床不起,我不禁潸然泪下。
然而,我第二次奉命赶赴崖县任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可以说是“天赐良机”。我想,我第一次来崖县工作,选举时有些人居心叵测,让我落选。两年多后,省、地组织仍让我担任崖县书记。我再次来崖县,一定要把这里的热带滨海资源、热带旅游资源等优势得以发挥,并努力宣传出去。我要想办法把崖县建成为市。当年,成立三亚市有很大的争议,有的人说,要成立崖州市,有人说要成立吉阳市,最后我拍板,就叫三亚市,申报热带滨海旅游城,并通过做工作,广东省也批复同意了。
在那个年代,干点事真难。尤其是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背景下,我那时提出搞旅游太超前了,有人说我是“不务正业”。(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调离三亚之后,有一段时间三亚市再不提发展旅游的事了,也不搞旅游了。一直到刘名启主政三亚后,才开始恢复旅游工作。近年来,市委书记姜斯宪一直按照世界级热带滨海度假旅游城市的发展方向把文化旅游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这是后话。)
1984年1月,我再度被任命为中共崖县县委书记,开始了“呼龙唤凤”、着手把三亚建成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的历史征程——现在看来,这一时期也是我一生最得意、最辉煌的施展抱负与大展宏图时期。
——题记
一、我的童年
我是1931年2月(农历辛未年二月十六)出生的。按老百姓的话讲,这个日子很好。我父亲虽然未有读过“四书五经”,但他略懂一些“生辰八字”的常识,很相信人的“命行运程”,他说,二月十六是赵公明(财神)从天庭下凡赐福的日子。再加上我是申时出生,父母亲很高兴,认为儿子命好,希望从此为朱家人带来好运,光宗耀祖,兴旺门庭。
“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我的老家在澄迈县城郊大坡村,原属于“耕读传家”门第。后来,祖父因侍奉本村财主烧“烟泡”而被动地染上了鸦片烟瘾,导致家道中落。到父亲朱儒星长大成人时,已经家无蓄积,指靠父亲终年往返临高、马袅等地运销盐等杂货,赚些运费及蝇头小利维持生活。也许是父亲亲身体会的经验总结,他嘱咐我长大后不要做生意,我也顺从了父母亲的意愿,从小就暗下决心努力读书。
我七岁时,不幸染上了痢疾,二老把所有能用的药方都用过了,医治了半年,仍然未见好转,无休止的病痛把我折磨成面黄肌瘦,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皮包骨。我父母似乎对我已经丧失了医治的信心,认为我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了。吃饭的时候,其他的东西我都不能吃,只能用盐巴拌饭吃。有一天,我父亲买回了一串小咸鱼挂在墙上,我看到后很想吃,向父母亲跪下,要求给我小咸鱼下饭吃。我母亲担心吃小咸鱼不利于治病,父亲说:“给他吃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听天由命了。”也许是小咸鱼很腥、很咸或其他原因,吃了几次小咸鱼之后,竟然止住了痢疾,接着连续半个月,母亲经常给我小咸鱼下饭吃。
未想到,我吃小咸鱼下饭吃出了奇迹,竟然治好了我的“不治之症”,我父母亲既惊讶又欣慰地说:“没想到小咸鱼竟然成了灵丹妙药!”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很忠厚,虽然不懂“道院迎仙客,书堂隐相儒”的哲理,但他却深知“子不教,父之过”等为人父母的责任。我记得在五岁时,就开始了“论交三世久,问字两儿趋”的私塾启蒙学习。
童年,我的父母先后在村里请了两位名叫廖坤迫、廖守承的老先生当我步入书文的启蒙老师,这两位老先生熟读四书五经,精通诸子百家。从他们当时给我起的“朱家仁”学名,即可窥见一斑。按廖坤迫老先生讲,朱家得仁(即德仁)这个名字,是中国古代含义十分广泛的道德范畴,原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即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然,作为父亲、母亲和老师,他们也希望我长大成人之后,经世致用,光耀门庭。比如我小的时候脑袋较大,他们就半开玩笑地说:“大脑袋聪明。”当然,我父亲不仅嘴上对我说,心里也是这样希望的。因此,我在五岁半时,父母亲就让我开始了“学海茫茫,五载索句,辑册成章,耳熟能详”的私塾学习生活。
二、才华初露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孔子格言)
1945年,我14岁,正是我步入青年、视野初开、激情奔放的风华正茂时期。这一年,是日本侵华战争宣告结束、华夏民族坚持八年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一年。值得我个人记述的是,这一年也是我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开始革命斗争的一年。
我的老家在距澄迈县城三公里的农村,叫大坡村(相当于现在的城乡结合部),是当时国共双方活动频繁、斗争力量交错、形势十分复杂的“插花”地带。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期我们村比较特殊:一方面大坡村是伪乡公所的所在地,一方面又是共产党革命斗争十分活跃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无论是国共合作时期,或者是内战时期,我们村经常有共产党员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记得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就开始对共产党员进行反革命屠杀,斗争十分残酷。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转入了秘密的地下斗争。
1946年春节,有几名共产党员在我们村里过夜。由于伪乡公所的报告,正月初二,国民党的兵就把我们村包围得水泄不通。
当时我的叔叔是村长,扮演着“白皮红心”的角色。“白皮”,即表面上是应付国民党,而“红心”实际就是共产党的联络员。
在当时,国民党匪军搜捕共产党的情况十分危急,在既无暗道脱身,又无水路可潜的情况下,这几位共产党员无处藏身。由于时间紧迫,我叔叔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我在一旁看在眼里,也着急在心。幸好,我家的地点在村中心,住房旁边有一间没有后门小房子,海南话叫“包尸房”,平常也没有人住,房子里放的全是稻草。国民党匪军为了搜出共产党,采取了逐户搜查的野蛮办法,他们从村外搜到村内,凡是门关着的房屋他们就抄家。当时,情况紧急,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几名共产党员在实在无处可以隐蔽的情况下,躲进了“包尸房”。眼看着国民党匪军快搜查过来了,叔叔一时没有了主意,问我:“你看门是关着好还是开着好?”
河狭水急,情急生智。
我见叔叔一时没有主意,只好急中生智地说:“你们都躲在屋内的稻草下面,并且把房门开着。”
我想,一般人都很忌讳走进停放死人尸体的房子,倘若是门开着,敌人即认为屋内没有什么可疑之物;倘若门关着,就值得怀疑了。人家(指国民党)一定会进来搜。而且,面对敌人搜捕,开着门可以一目了然,万一不行,也可以通过事前观察好的地形与方位进行突围。也许是天气已晚或其他缘故,结果真如我的想法,包尸房没有被抄,几位共产党员也躲过了国民党匪军的搜捕。
后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给叔叔出“空城计”的主意,帮助共产党躲过敌人搜捕的事,被国民党的人知道了,结果在我上学的问题上制造了麻烦。好在他们在“究竟是谁家的人帮助了共产党”的问题方面“对不上号”,但他们采取了最狠毒的一招——凡是大坡村的学生升学方面都“紧紧地卡住脖子”,不准所有大坡村的子弟升学读书。
1948年,我在澄迈只念了半年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初中,本来成绩很好,但也因为当时在大坡村的“空城计”使我“名落孙山”。后来才知道,澄迈中学校长是国民党,之后又当上了澄迈县县长。我本来升学考试成绩优良,已考上了,可学校就是不录取我。我姑丈在学校当教导主任,他知道考试录取情况,但是,这个国民党的校长坚决把我的名字撤下来。对此,我非常恼火,说实话,我当时心情悲愤,曾想到同这个校长大干一场,甚至想到用炸弹和他同归于尽。但是,由于父母亲担心我只凭一时之气而导致杀身之祸,二老都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民不与官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由于二老坚决不让我去冒险报仇,我也就听从了他们的劝诫。我想到我年迈的父母亲十分辛苦,父亲为了供养我读书,卖猪、卖稻谷,把家里只要是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为了不让二老担忧,我产生了离开澄迈,去县外上学的想法。后来,我有幸在海口汇文中学读了初中,虽说那时候一年要交50元光洋的学费,但是这所中学可是海南岛上的一流中学。
1949年下半年,我读完初中,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当时,全国各地都解放了。但海南岛还未解放,由于渡海战争在即,海口的中学学校情况很乱,几乎没有学生上课了。1949年底,我又转回到澄迈中学。在幼年,我从念小学到念中学的学习成绩我一直是名列前茅,这说明我自小就是勤奋学习的优秀学生。
三、挥斥方遒
伟人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沁园春·长沙》词中写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洋溢着青春的热情奔放和抨击恶浊、褒扬清明的壮志情怀。
我们海南岛是1950年5月1日解放的。在此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在澄迈风门岭战斗中取得了上岛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紧接着,经过“包围和反包围”的几场激战,最终取得解放海南岛的全面胜利。在1950年剿匪斗争中,由于我懂得几句普通话,叫我担任围剿国民党残匪的工作队区小队副队长。在第一次剿匪战斗中我带了30个人,在上级部队和兄弟部队的共同合围之中,部队首战告捷,歼灭了国民党专员的弟弟。那年我刚好满19岁。从此之后,我就坚定地加入了革命队伍。对我个人进步而言,确是我走向革命之路的宝贵经历。
同年9月,我参加了“八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工作队,一直到任命我为土改工作队队长。在当时,土改工作队队长领导100多号人,还是配枪的。虽说是土改工作队,但是权力很大,比如对地主、恶霸、反革命罪犯的枪毙或赦免等人命关天之事都要我签名。
通过上述经历的革命考验,1952年土改结束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先进模范。那年我刚满21岁。
人生总是要在复杂多变的矛盾中进步、发展的。我加入党组织后,由于琼海县的干部和群众对我的工作反映非常好,琼海县要留我当区长。但带队的陈在伦同志要我去海口,让我在海南区机关党委当了一名宣传干事,据他讲是重用了。海南区党委副书记莫燕忠同志点名要我跟他到琼海去办社(农业初级合作社),专门要我当他的翻译,一定要叫我留在琼海。在当时,他为了让我跟他去琼海,还介绍我和一个乡上的女干部见面,我说:“我很年轻,你留我,可以呀。”对此,我口头应承,在心里却不想谈这个“对象”。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区党委干部科长黄儒同志的安排,奉命调到自治州工作,忠实履行“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服从组织安排”。这也是解放初期干部制度和行为品行的基本原则。
到了自治州党委,州党委安排我做书记处秘书。三个月以后,党组织又提拔我担任秘书科副科长,担任理论科副科长,直至担任宣传科科长。
1957年7月,自治州党委又任命我担任自治州师范学校校长,任命我担任校长时,我年仅26岁,有很多学生的年龄比我的年龄还要大。1959年3月,由于自治州党委要加强宣传力量,上级又任命我担任《五指山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现在回想起来,我担任《五指山报》报社社长时,既是社长,又是记者、编辑、编审、校对,是一位身兼五职的“一把手”。很多代表州党委声音的社论、报告文学等大篇幅文章,都是我亲自撰写的。由于当时我年轻,脑子灵,加上平时注重学习,洋洋千言,一挥而就,可谓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当时,我的文笔书写已小有名气,他们说我是“自治州党委的一支笔”。
四、岁月如歌
回忆,往往是一种情感思索,承载的是岁月,品味的是感悟,演绎的是人生。
我在任崖县县委书记之前,特别是1960—1989年之间,值得回忆并记述的,是我人生历程中堪称“重要时期”的经历。
20世纪中期,全身心关注中国农村、被《人民日报》赞誉为“农民作家”的赵树理先生在他的著作《邪不压正》中,称1960年的中国农村是“天聋地哑”,也是中国近代史所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为什么这位历任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著名作家赵树理先生会发出“1960年的中国农村是‘天聋地哑’”的声音呢?
可以说现在凡是50岁以上,特别是55岁以上的农村人都记得,那是一个把人饿得吃光了树皮草根、把一碗米饭看得比现在山珍海味还要金贵百倍、一粒米落在地上也会拾起来吃掉且令旁人“眼馋”的年月。
“大跃进”——浮夸的“高产卫星”。
自从1958年1月,海南区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把粮食生产增长一倍以上的“大跃进”指标之后,海南岛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同年8月4日—6日,海南区委又提出“在全岛实现粮食亩产‘双千斤’的高产指标”。由于这种严重脱离实际、在当时条件下根本不能实现的高产指标,导致下面层层加压的虚报和浮夸。于是,放“高产卫星”的浮夸之风席卷了全岛……最后呢?农村出现了吃光了所有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无米下锅用瓜菜代替粮食做饭的大面积灾荒,形势非常严峻。偏偏在这个艰难时期(1959年)海南岛要组织大县,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和行政机关撤销了,打乱了行政管理,把小东方县、白沙县、昌江县、昌感县四个县组成为一个东方县,县委、县政府驻沙河。之后,县委、县政府在沙河驻半年时间,又奉命迁移到八所。
1959年,我当过东方县县委宣传部部长。1960年东方县又分开了。也就在这“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整风反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深挖”、“深入”和农村“民主补课”等运动,我的父亲在家里出现了问题。
事件的起因是,我当上县委宣传部部长后,我的家乡大坡村里有些仇恨我父亲的人分外眼红。他们趁1960年农村进行阶级成分“民主补课”(即补定家庭成分)运动的机会,一位对我父亲怀有怨气的“贫下中农协会”主要领导,乘机把我家评成了地主成分。并且在暗中煽动了一些人,十分凶狠地将我父亲打倒在地还拳打脚踢……之后,他们把我父亲及全家老少赶出家门,将我家的财产全部没收。
我父亲那天非常气愤,想不开,拿绳子准备上吊自杀。幸好我父亲有个叫廖坤安的好朋友,他担心我父亲受不了这次打击,深更半夜去观察我父亲的动静。当他看到我父亲系好绳子准备上吊之时,他推开房门把我父亲解救下来。他见我父亲气愤不已,好言相劝道:“星爹,你不要自寻短见,你生闷气是不行的,更不能寻死觅活。你的儿子朱家仁是一个懂政策有出息的人,你要把家里受冤屈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你有儿子朱家仁在,你就有出头之日。”
我得知家里遭人报复的情况后,我写信告诉他们,让他们相信我和村里的乡亲。我也同时将村里某些人趁“民主补课”运动,打击报复我家的情况,写信寄给海南区党委李黎明副书记和澄迈县委何友信书记申述反映。后来,经过查三代、五代的核实,三个月之后,村里改定我家为中农成分,家人依原搬回原来的房子。
1961年,农村生活非常困难,主要是家家都无米下锅,指靠“瓜菜”代替粮食做饭吃了。我在东方县的农村工作队也吃不饱饭,早上九点一顿酸瓜粥,晚上九点一顿酸瓜粥,为了避免晚上挨饿,只有拼命地喝饱,把肚子喝得像怀崽的母猪一样。到了晚上十点开始拉尿,到了夜里一点,喝的稀酸瓜粥就拉光了。夜里饿急了,只好又起来喝水。很多人在田里站久了就会晕倒在地,饿了只有喝水充饥,把肚子喝得走起路来都会咣当作响。那种饿的状况现在不堪回首。就在这时候,我不幸得了水肿病,手、脚已经全都肿了,手摸不着腚。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上级还要我到广州去开会,很多人认为我去了就没命了,可能回不来了。
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我到广州之后,有位同志就帮我找医生。医生叫吴华民,广东省中医顾问。他见我得的是要命的慢性肾炎病,而且已到晚期。为了稳定我的情绪,他说:“你生的这个不是常见疾病,是绝症,是不治之症。但现在还不是晚期,如不及时治疗就会送命。”他说,我要他治,必须答应他做到以下五点:
第一,不准跟老婆“同房”(我说这点我能做到);
第二,大量增加营养(我说这点确实很困难,当时什么营养品都没得吃);
第三,不准喝酒(我说这个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从小到大就不喝酒);
第四,不准干重活(我说我尽量做到);
第五,不准感冒,如果感冒,药路就死了;
第六,不准吃盐。
当时,医生给我开了一副药,叫加减归脾汤。我因小时候做过药店的药童,懂得一些中药药性与药方,在广州治病且病情略有好转之后,我按加减归脾汤药方13味中药的剂量,配了多副中药带回家自己调理服用。半年之后,我的肾炎病被彻底地治断根了。因此人们说我是个奇人。
我的病治好后,我又把这方子告诉别人,还治好了另外三个病人。尤其是我把这个治肾病的方子告诉崖县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河山之后,不仅治好了他妻子的肾病,后来他妻子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从此,陈河山见了我就抱拳作揖,喜笑颜开,感激得不得了,称我为“神医”。
五、雾里看花
本来,雾里看花是一个形容对事物看不真切的成语。但长期形成的绝对公有制、平均分配等极“左”思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所出现的过错,人们却讳莫如深,如云如雾……
终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答案,人们从亲身经历的痛苦中“悟”出来了。
后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终于才清楚地认识到,1960年的中国农村“天聋地哑”的原因。
是由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亩田产稻谷一万斤以上的浮夸风——强迫农民把十几亩田生产的水稻堆放在一起,并且连稻草一起计算数量,虚报浮夸。
是“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砍光了大树炼钢铁,树砍完了就拆门窗、砸家具大炼钢铁。后来,为了凑钢铁数量,完不成任务要农民砸锅献铁。“反正已进入社会主义,农民自家不做饭了吃食堂”;于是,除农具之外,农民已“交”光了家里所有含铁物质的金属家具。
是农村全面开展“食堂化”,“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估计。结果呢?先是四菜一汤,后来连稀粥也喝不上了。到了1959年下半年,农村什么都吃光了,人们开始吃树皮、吃草根,成批成批的人被饿得患浮肿病,妇女们被累、被饿得“子宫下垂”,尤其触目惊心的是,1959年冬季之后,很多农民开始被活活饿死……
比如在东方县,一些基层干部为应付检查,就造假了。为了掩盖真相,他们弄虚作假,在竹围囤的下面放谷糠、放沙石,在谷糠、沙石的上面铺一层稻谷让人看,应付“上面派来的干部”检查。实际是假的。
在这种弄虚作假、天灾人祸之后,海南岛农村已陷入饥饿的深渊。没有粮食,农民只能吃“瓜菜代”了。
什么是瓜菜代呢?当时田地里种的庄稼没有收成,食堂在煮饭的时候用蕃薯和菜叶代替粮食充饥,这种“瓜菜代”饭食煮好后基本上看不到米,由于蕃薯在地里晒的时候粘上了很多沙石,虽说已经过筛子,但用水煮过后,蕃薯干上依然残留很多沙粒,咬起来嘎吱嘎吱的响,崩得人牙根发麻,根本吃不下去……
1960年春天,由于饥饿难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饿死人了。那时候人们穿的衣服呢?且不说样式,未有补丁就是最好的衣裳。每人每年只有5市尺布票(每市尺约合33.33厘米),5尺布票不够做一件衣服,只能做条裤叉,很多农民衣不遮体。
1960年夏天,村里开始成批地饿死人了,有的全家人死光了都没有人处理后事。后来所有能吃的都没有了,农民们在饿急了之后,开始想到用杀死帮他们劳动的耕牛、暂且保命的悲哀办法。
牛是当时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毛主席一直不准农村宰杀耕牛。由于上级不准杀耕牛,老牛越来越多。“瘦牛怕过冬,干部怕运动”。耕牛又是集体财产。那时候,人都没有饭吃了哪里还有粮食去喂牛呢?所以,当时的耕牛非常瘦,尤其是冬天,许多牛也快被饿死了。牛要死之前,毛是竖着的。驻村的工作队发现瘦牛问题之后立即向县上作了汇报。县上开会要求一定要做好保护耕牛的工作,县里的主要领导还专门派工作队下乡救牛。
怎么救呢?就是用白米加糖熬粥,再用竹筒向牛嘴巴里灌。但是,老百姓饿急了就不这么想,他们在腰里别着一把刀,围在牛的周围,恨不得牛马上死了割几块肉吃。工作队员下乡,老百姓是“另眼”看待。这时候的老百姓是想活命,认为是工作队把他们整得没有饭吃,他们跟工作队对着干,把工作队当仇人。
1961年,党中央通过大量的专题调查,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之后,农村情况才逐步好转,后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开了一次干部会,他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花明者,自留地也!”准许农民搞一点“救命的自留地”,可以在自留地里种红薯、种玉米,在“打饥荒”时把嫩玉米磨成浆,加南瓜一起煮粥,“南瓜浆,渡粮荒”。农民开始能吃饱饭了,从此,农村人民生活“才得到真正意义的恢复”,避免了农村饿死人的现象。
1962年,广东省委决定恢复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恢复后,为了加强农业,自治州党委又把我调回自治州农村工作部。当时,由于人民公社化的绝对公有制、平均分配、吃大锅饭等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农村粮食不能自给,解决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吃饭的农业问题,一直是各级党委的首要任务。那时候农村工作最重要了,1963年我在农村工作部经营科当科长,1964年任命我担任农业干部学校校长,1965年又任命我担任自治州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这场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岁月里,我在东方县龙卧村当工作队长,我遇到的一个叫苏亚秦的农民,与他的谈话让我至今难忘。
那是1961年下半年,龙卧村几乎家家都饿死了人,唯有这个叫苏亚秦的家里没有饿死人。他是大队长兼保管员,负责管理全村粮食和物质仓库的钥匙。社员们说他家多吃多占才没有饿死人。工作队要我去询问他。苏亚秦说:“朱大哥,我太冤枉。为什么我家没有死人呢?因为我是铁打的心肠才没死人的哟。我俩(夫妻)是全家的主要劳力,我父亲要我们上山去找‘瓜菜代’之前,一定要我俩填饱肚子,保住命,然后才给小孩和父母亲吃。父亲说,就是他们二老和孩子们都饿死了,只要留住我们两个活下去还可以再生。如果都吃一般多,全家人都会饿死,我们家就绝后了。你为我家传宗接代了,不仅不是不孝,是大孝。我按照父亲的意见去做,结果不仅家里没有死人,而且还保住了全家。”
在眼睁睁地看着到处都没有东西吃的年月,我就让苏亚秦把这种保命办法对村里人说,并且在心里暗自肯定了这种保命传人的办法。
六、十年魔魇
“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唐·韩愈《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献杨常侍》)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到后来“革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开始批判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金猴奋起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
就在武斗乱得最厉害的时侯,有些眼红我的同志,认为整我的时机又到了。1968年,这几个人为了把我打成“反革命”,他们以“外调”为名,到处找194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长安小学的档案,他们在这所学校的教师(几乎全是国民党员)的档案上,伪造字迹,把我的名字添加在国民党党员的花名册上。他们以“潜伏的阶级敌人”之罪名把我打倒在地,并且是“证据确凿”。
那时候我惨极了,我的爱人怀孕被打伤流产,赶出原来自己盖的房子,我们被迫另外在山边盖毛草房栖身,我爱人流产了,全家都没有过好年。说我是国民党的骨干分子,说我是在共产党内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是在深挖阶级敌人运动中“挖”出来的,要把我清除出革命队伍。我不服,要上诉,结果我挨斗挨批了。
1976年以后,各地的党组织基本被冲击了,各省、市、县的政权名称是××县革命委员会。到1970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我专门就这件受诬陷事件写信给自治州革命委员会刘荣主任,请求上级调查落实。我因为曾经给刘荣主任当过秘书,所以他对我的为人非常了解。刘荣主任收到我反映情况的书信之后,连夜派人去查阅作为“证据”的档案,专案人员通过笔迹和墨迹比对,认定我那个名字是后来另外(添加)写上去的。为我平了反,把我从五七干校依原调回自治州当革委会新闻报道组组长。之后,又叫我担任革委会政工组宣传办公室副主任。1972年,任命我担任自治州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1976—1979年,我被下放到琼中长征公社搞农村“路线教育”。那时候,在农村搞农业生产的基本上都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弟,也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贫下中农”说他们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可以不搞生产。
农民是要种田的,农民不种田,吃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从1969—1979年,全海南岛各地都缺粮食,导致农民吃不饱饭的农业生产问题,是长期困扰海南岛的首要问题。
我在东方新村公社龙卧村,生产队种的水稻刚刚发黄粒的时候就有人偷。上级叫我们驻村工作队“务必保护劳动果实”,并决定由我带一个工作队和民兵排去检查,要防止老百姓去偷“劳动果实”。去了之后发现,实际去偷稻谷的是民兵的家属,他们不仅不抓,还当掩护。后来,靠民兵守不住了,就叫工作队员“掺沙子”去守。结果呢?逮住的“小偷”,却令工作队既啼笑皆非又心余力绌。
是什么人偷这些刚刚发黄的稻谷谷粒呢?令我痛心的是,这些“小偷”竟然是十岁左右的小孩、中年妇女以及老人。特别是妇女,如果要抓她们,她们不怕,而且当着工作队员的面脱光了裤子!队员苏良跑步向我报告了这个情况,我说:
“撤!马上收队。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苏良不懂,问我:
“为什么?”
我见他不懂,耐心地解释说:
“有句古话道:‘人饿了不要面子,鸡饿了不怕棍子。’鸡要饿了,你拿棍子赶它,它要吃,所以它不怕;当这些农村妇女饿了脸面就不顾了,脱裤子,你就不能再去抓她们,把她们逼急了,她们会说工作队如何如何,你就没有道理了。”
在当时我心里很是难过,尤其是看着那些面黄肌瘦、严重营养不良的小孩子们挨饿,更是让我心痛!他们可正是上学和玩耍的年龄啊!如果不是饥饿,他们是不会在田里“掐谷粒”的。
“民以食为天”,没有饭吃四处颠啊!我心里想,是不是我们的政策出错了?几经考虑,我觉得长期这样搞不行,不包产到户不行了,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我召集了村上几个有威望的老农民和村干部座谈,经过商量,决定按人口分摊生产责任田,责任到户,任务到人,大家都同意我的想法。包产到户后,干多干少都是自己的。大家都争着干活,争着种粮,有了粮食就解决了吃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央包产到户政策下来前,我们已经“大胆”地走了一步,效果很好,人人拼命干,再也没有好吃懒做的现象了。
后来,我在琼中长征公社搞包产到户的事被县上发现了,很多人认为我是搞复辟了,加上我家“民主补课”时曾经被划成过三个月的“地主”,有人背后还酝酿要批斗我,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由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7月6日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9月9日毛泽东主席久病不治),国家连续发生的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上面”对农村包产到户是否是资本主义之类的问题,似乎已不太在意了。并且传出“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可能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责任制实际就是包产到户”等“小道消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也意识到可能会有较大的社会变革了。
结果,那些告我的人告得好,上面要以我抓的这个村为榜样,召开现场会推广。琼中县换届征求各公社党委意见,很多公社书记还要推选我当书记。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不同意,他们派人来找我,并且要调我回自治州。
七、两度“崖州”
把三亚建设成国际著名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是我担任崖县县委书记和首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一心想努力办成的一件大事。
今日三亚,古称崖州。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崖县,后撤销崖县设立为三亚市,这里不仅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还是一座文化积淀十分丰厚的文化古城。据《崖州志》载:仅唐、宋两代就有李德裕、卢多逊等十余名朝廷宰相和王仕熙、范椁等达官名人在崖城“读写”人生。如今,“古崖州”城池所在地崖城,已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1980年12月,经林祖基书记建议,我奉命调到崖县任第一副书记,让我分管城市建设,并且兼任三亚镇党委书记。到任后,我首先想尽快地改变原来三亚镇的脏、乱、差的落后面貌。我向林祖基书记提议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三亚城镇建设和环境治理问题,并且以中共崖县县委【1980】第43号文《关于立即停止在三亚河两岸建房子的通知》“告知全县”,令行禁止。这个文件是我到崖县任县委第一副书记、对治理环境污染、向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迈进的第一道檄文。当时,我工作十分扎实认真,对污染三亚河水、三亚环境的楼堂馆所坚决拆除!不批!不建!一丝不苟!雷厉风行。为此,首战告捷,但负面影响是我因此得罪了一大批人。
我热爱三亚。就是因为我有这份真心真意,达不到目的,决不罢休。我在崖县工作中,逐步发现了这里有国内唯一的热带气候条件,是建设发展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最独特的稀有气候资源。我就想办法宣传,并希望尽快地见到成效。
然而,“点塔七层,不如暗处一灯”。就在我一心想在三亚干出成效、为三亚人民多做点好事的大展宏图之际,在1981年的选举中,由于我太认真(尤其是在撤除违章建筑物中)得罪了一些人,加之在发展观念方面,我的想法(以旅游业为主)与当时“以粮为纲”的方针有分歧,尤其是干部之间的不同地区关系与“派系”,我落选了。可称为一度离开崖县。
当时,我们这一级的干部实行的是双重管理制度,县级干部是海南行政区和广东省管,县级以下是自治州管,崖县在1980年之前是海南岛最偏僻、最贫穷、最南端的一个县。那时候,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加之公路崎岖,交通十分落后。我落选后,心里十分委屈,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腔热情无处诉说之感。1981年夏季,林祖基同志奉命调离崖县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秘书长,我被调离崖县,任州党委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协助州党委王越丰同志修建州政府大楼,1982年12月,大楼竣工之后,州党委任命我担任州委宣传部部长。
1983年12月27日,我在家侍奉重病的父亲。本想在家多尽几天孝道,不料12月30日,自治州党委派车队队长廖坤树同志到我家通知说:
“朱部长,州党委派我通知并接你回自治州,广东省委已任命你担任中共崖县县委书记,要求你立即赴任。”……
接到通知后,我百感交集。忠孝不能两全啊!我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子,酸、甜、苦、辣、涩五味俱全,想起了病重的父亲还卧床不起,我不禁潸然泪下。
然而,我第二次奉命赶赴崖县任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可以说是“天赐良机”。我想,我第一次来崖县工作,选举时有些人居心叵测,让我落选。两年多后,省、地组织仍让我担任崖县书记。我再次来崖县,一定要把这里的热带滨海资源、热带旅游资源等优势得以发挥,并努力宣传出去。我要想办法把崖县建成为市。当年,成立三亚市有很大的争议,有的人说,要成立崖州市,有人说要成立吉阳市,最后我拍板,就叫三亚市,申报热带滨海旅游城,并通过做工作,广东省也批复同意了。
在那个年代,干点事真难。尤其是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背景下,我那时提出搞旅游太超前了,有人说我是“不务正业”。(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调离三亚之后,有一段时间三亚市再不提发展旅游的事了,也不搞旅游了。一直到刘名启主政三亚后,才开始恢复旅游工作。近年来,市委书记姜斯宪一直按照世界级热带滨海度假旅游城市的发展方向把文化旅游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这是后话。)
1984年1月,我再度被任命为中共崖县县委书记,开始了“呼龙唤凤”、着手把三亚建成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的历史征程——现在看来,这一时期也是我一生最得意、最辉煌的施展抱负与大展宏图时期。
相关地名
三亚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