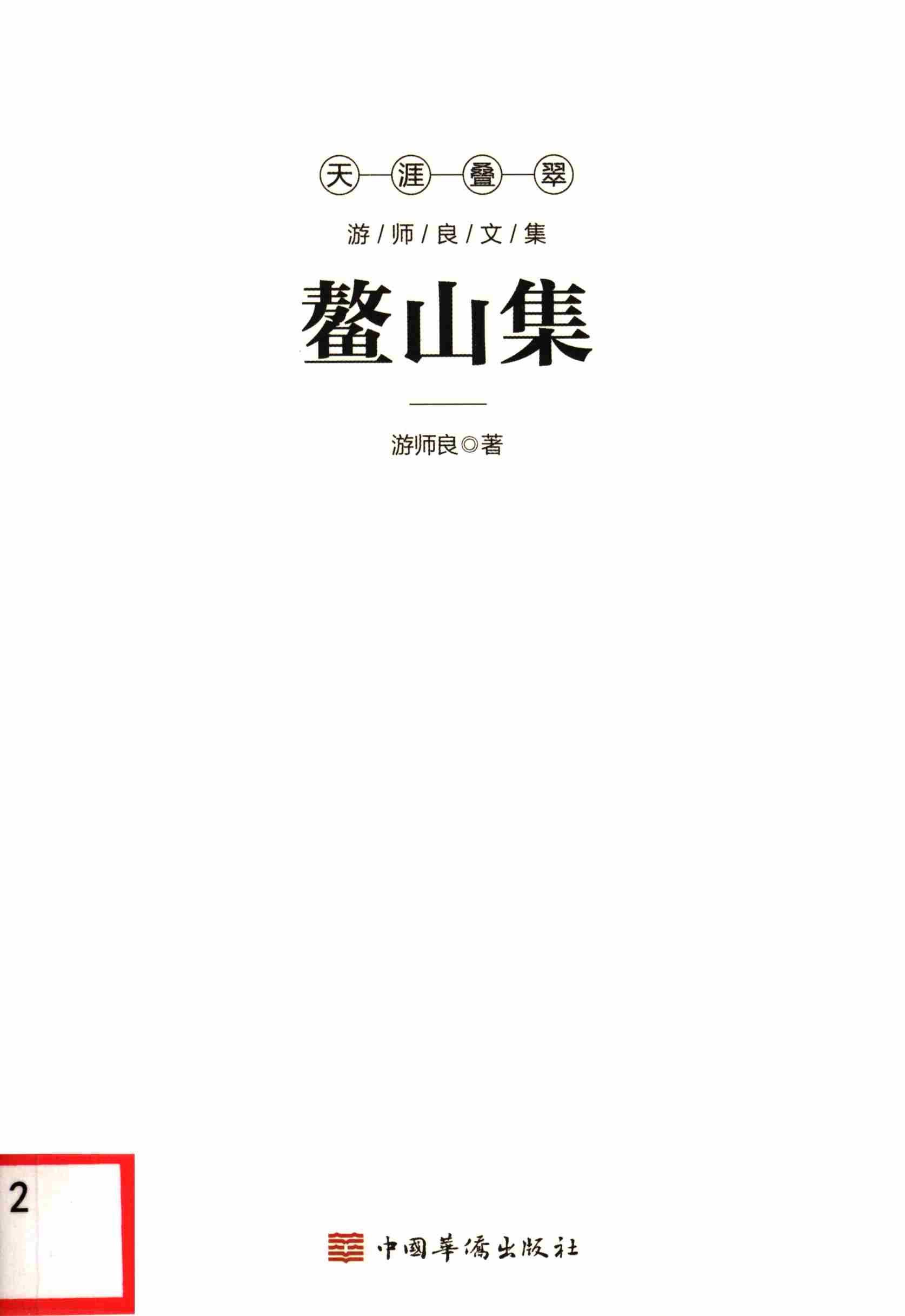内容
我们洪李村是原海南崖县林旺公社(今三亚市海棠湾镇)的一个自然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村人口有2000多,8个生产队。洪李村人都是清代至民国年间从海南文昌县的锦山、迈号、清澜、文教等地陆续迁徙过来的。最早从文昌过来落土定居的是洪姓和李姓两家,因此村名叫“洪李”。文昌移民喜爱琼剧,新中国成立前已有琼剧戏班,班主姓郑,全村人都叫她“郑大婆”。郑大婆戏班逢年过节都为全村人免费演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物质生活不断提高,村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1957年,洪李村琼剧团就在全体村民的一片呼声中自发地组建起来,而且一直坚持下去,直到1982年剧团解散停演,整整25年。这25年间,我都在洪李村琼剧团工作和生活。剧团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记忆和深刻的印象。
印象之一:一个村级剧团的诞生
1957年春,洪李村村民陈宏伟(时年40岁)发起组建洪李村琼剧团。他的这一义举,立即得到全体村民的响应,也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于是,陈宏伟顺利地组织了一支有20多人的剧团。剧团的编导、演员和勤杂人员都是我们洪李村人。陈宏伟担任团长,村民符名德、符名学担任编导,剧目都是从琼海、文昌一带移植过来的。当时我只有16岁,是剧团里年龄最小的女演员,充当“小梅香”角色。我至今还记得剧团组建时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
我们洪李村组建琼剧团的消息,在本村和邻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乡亲们奔走相告,一时间沸沸扬扬。群众对剧团寄予厚望,予以大力支持。生产队给剧团垫付了启动资金,并派人协同剧团业务人员到海口采购演出用品。学校主动给剧团腾出场地,每晚还给剧团点亮两盏大汽灯,供剧团排练。各家各户捐砖献瓦,有的拆下自家的门板,有的砍下自家的竹木,男女老幼挑土搬石,人人动手帮剧团搭建戏台;村里凡有缝纫机的人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为剧团裁缝戏服、鞋帽和幕布。村里和邻村的民间艺人纷纷主动上门,土法上马,为剧团制作各种道具和乐器,如用剑麻叶制作麾羽、用椰子壳制作板胡等。青年民间艺人张国昌,花了两个月时间,义务为剧团精心制作三弦、唢呐、铜锣、铜钹等乐器,还自己掏钱买下一张牛皮为剧团制作一面大鼓、两面小鼓。琼海籍村民陈时道,将家中一台其亲戚从南洋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十张琼剧唱片,无私地赠送给剧团,供演员们学习唱腔。经过近半年的筹备,我们洪李村琼剧团终于如期诞生了。那年的八月中秋之夜,剧团为乡亲们成功公演了第一场琼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晚观众竟达1000多人,大家都赞不绝口。
印象之二:“拿工分”的村级演员
我们洪李村琼剧团,是一个村级业余剧团,剧团的服务对象是洪李村和邻村村民。剧组人员台上是演员,台下是社员,农闲时排练、演出,农忙时和社员一样到田间劳作。在村里演出,每演一场,村里给我们剧团每人记上8分工,年终与社员一样凭工分分红分粮,没有一点点特殊。剧团人员从无怨言,从不叫苦,人人心甘情愿,喜笑颜开。大家都觉得,能把欢乐带给洪李村乡亲们,让乡亲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是一份职责,一种担当。乡亲们看在眼里,都很心疼剧团人员,多次提出给我们剧团人员多记些工分,多分些口粮,可是我们剧团从不接受。记得1960年冬的一晚,我们剧团的演员都饿着肚子,为村民上演琼剧《狗衔金钗》,还未收场,有4名演员就昏倒过去。乡亲们闻讯赶来,给演员们端上热饭热菜。大队和公社也很关心我们剧团,给我们剧团每人每天增补2两米,每人每月增补半斤油。剧团将这些粮油匀出部分,用于救济村里的贫困户和老弱病残。
1963年秋,我们剧团第一次应邀到陵水新村港为渔民演出几场琼剧,收入260多元,回到洪李村后,剧团分文不取,将这笔收入上缴生产队。队长和社员们都过意不去,要求剧团把这笔收入留下来发给大家作生活补贴,大家都一致谢绝。团长说:“我们是村里的剧团,拿工分是我们农民剧团的本色,我们的演出收入无条件归集体,归社员,我们不能私分。”我们这些“拿工分”的演员,就这样凭着为父老乡亲服务的满腔热情,在集体和乡亲们的呵护下,度过了艰难岁月,度过了长长的25年。
印象之三:特殊的奖赏
1963年,我们洪李村剧团因团长年事偏高,大家推举我担任团长并兼导演、演员(旦角)。重任在肩,为了不负众望,我和副团长符泽模、符泽平使出浑身解数,带领剧团继续前行。
作为一个村级业余剧团,我们深知剧团在演艺方面是“先天不足”的。为了提高演艺水平,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即把剧团人员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到琼海民声剧团、澄迈县剧团观看演出,请教取经。在澄迈,我们得到剧作家陈东和多名演员的指导,获益匪浅。我们还把本县琼剧团“台柱子”之一的陈敏初先生(名生)及男女主角演员黎和香(男)、梁娥英等请到村里来做示范演教。陈敏初先生在我们剧团驻团带演了三个多月。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改进,我们剧团从戏台的布置、剧中人物的扮相到演员唱打念做的一招一式,乃至扇子功、水袖功的运用等方面的演艺技巧,都取得突破性的提高,都能让观众耳目一新。我们剧团到本县的藤桥、崖城、红沙、羊栏、马岭等公社演出,各地群众观看演出后说:“你们洪李村琼剧团越演越捧了,吃番薯粥的(业余剧团)和吃大米饭的(专业剧团)一样样了!”1964年,我们剧团参加全县文艺会演,以传统剧目《糟糠之妻》和现代移植剧目《打铜锣》《补锅》力压群芳,获戏剧类节目表演一等奖,县政府给我们剧团颁发了锦旗和奖状。
我们洪李村琼剧团以出色的表现和骄人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赢得了党和政府的赞誉,从生产队、大队、公社到县文化部门,都在资金等方面予以剧团力所能及的扶持。这样一来,我们剧团就更加壮大了。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剧团的名气越来越大,几乎天天都有县内县外的“特派员”到我们洪李村来“绑戏”(预订演出)。乐东县乐罗村前来“绑戏”的陈老伯,当时已七十多岁,为了“绑”到我们剧团,天天跟着我们到各地演出,从陵水的新村、英州,一路随我们到藤桥、崖城,天寒地冻也不在乎。当他得知我们剧团决定当晚在保港头灶村演完《搜书院》一场就到乐罗村演出的消息后,就连口赶回乐罗村,带上10多个乡亲和10多辆牛车在戏场外等候我们,散场后七手八脚帮我们收拾行装,硬是要我们连夜赶到乐罗村。在陈大伯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们全团人员从头灶村步行到乐罗村,这4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摸黑走了足足10多个小时(从晚上12点到次日上午11点)。虽然周身酸软,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因为这是群众对我们剧团莫大的信任、期待,是无声的赞许。
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在乐罗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请我们去做客,请我们去住宿,如遇故人,如逢喜事,人人春风满面。我们演了《张文秀》,又让我们演《秦香莲》;演了《打金枝》,又让我们演《林攀桂》。我们在村里连续上演了11场,村民们还舍不得让我们离去。因为我扮演琼剧《张文秀》剧中人“三姐”,男女老幼白天见到我都亲热地叫我“三姐”。我住宿的人家,只有一对小夫妻。男的被队里派到村外放养鸭子,女的被队里派到水利工地当炊事员,夫妻俩一年难得回家团聚一回。听到风言风语,便互相猜疑,闹别扭,话说不到一块儿,双方都跟我诉说各自的“委屈”。一天,我让这对小夫妻和我一起吃晚饭。饭间,我给小夫妻讲述了琼剧中好几个夫妻释疑的故事,还给他们演唱了琼剧《张文秀》里“三姐”的一个唱段:
劝郎君你莫生气,
为妻跪下愿赔礼。
千万要体谅莫怪你妻,
她含冤受苦度日如年……
一曲未了,小夫妻动情了,丈夫当即放开歌喉,也给我和他妻子演唱了一首崖州民歌:
千错万错哥认错,
恳求妹子原谅哥。
“三姐”请你来作证,
今生今世对妹好……
小夫妻终于和好如初。
离开乐罗村那天早晨,父老乡亲们都来给我们送行,并送上他们精心准备的礼品:生猪1头、鸭子20只、鸭蛋200个。临别时,“绑戏”的陈老伯匆匆赶来,给我送来10包草药,说:“梅侬,老伯我发现你的声音哑了,戏唱得吃力了,特地上山为你采挖这些祖传的清肺润喉草药……”我从陈老伯那双皱巴巴的手中接过草药。此刻,我觉得陈老伯给我送来的不是草药,而是一份暖融融的爱心,一份沉甸甸的希望,一份无比珍贵的特殊的奖赏。我回过头来,还来不及说声谢谢,心头一热,止不住泪水盈盈……
此文应海南省政协文史委之约采写。全文由亲历者符史梅口述,三亚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卢鸿书记录,游师良撰写。收录于2014年12月出版的丛书《琼剧亲历见闻录》,为获奖作品之一。
印象之一:一个村级剧团的诞生
1957年春,洪李村村民陈宏伟(时年40岁)发起组建洪李村琼剧团。他的这一义举,立即得到全体村民的响应,也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于是,陈宏伟顺利地组织了一支有20多人的剧团。剧团的编导、演员和勤杂人员都是我们洪李村人。陈宏伟担任团长,村民符名德、符名学担任编导,剧目都是从琼海、文昌一带移植过来的。当时我只有16岁,是剧团里年龄最小的女演员,充当“小梅香”角色。我至今还记得剧团组建时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
我们洪李村组建琼剧团的消息,在本村和邻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乡亲们奔走相告,一时间沸沸扬扬。群众对剧团寄予厚望,予以大力支持。生产队给剧团垫付了启动资金,并派人协同剧团业务人员到海口采购演出用品。学校主动给剧团腾出场地,每晚还给剧团点亮两盏大汽灯,供剧团排练。各家各户捐砖献瓦,有的拆下自家的门板,有的砍下自家的竹木,男女老幼挑土搬石,人人动手帮剧团搭建戏台;村里凡有缝纫机的人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为剧团裁缝戏服、鞋帽和幕布。村里和邻村的民间艺人纷纷主动上门,土法上马,为剧团制作各种道具和乐器,如用剑麻叶制作麾羽、用椰子壳制作板胡等。青年民间艺人张国昌,花了两个月时间,义务为剧团精心制作三弦、唢呐、铜锣、铜钹等乐器,还自己掏钱买下一张牛皮为剧团制作一面大鼓、两面小鼓。琼海籍村民陈时道,将家中一台其亲戚从南洋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十张琼剧唱片,无私地赠送给剧团,供演员们学习唱腔。经过近半年的筹备,我们洪李村琼剧团终于如期诞生了。那年的八月中秋之夜,剧团为乡亲们成功公演了第一场琼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晚观众竟达1000多人,大家都赞不绝口。
印象之二:“拿工分”的村级演员
我们洪李村琼剧团,是一个村级业余剧团,剧团的服务对象是洪李村和邻村村民。剧组人员台上是演员,台下是社员,农闲时排练、演出,农忙时和社员一样到田间劳作。在村里演出,每演一场,村里给我们剧团每人记上8分工,年终与社员一样凭工分分红分粮,没有一点点特殊。剧团人员从无怨言,从不叫苦,人人心甘情愿,喜笑颜开。大家都觉得,能把欢乐带给洪李村乡亲们,让乡亲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是一份职责,一种担当。乡亲们看在眼里,都很心疼剧团人员,多次提出给我们剧团人员多记些工分,多分些口粮,可是我们剧团从不接受。记得1960年冬的一晚,我们剧团的演员都饿着肚子,为村民上演琼剧《狗衔金钗》,还未收场,有4名演员就昏倒过去。乡亲们闻讯赶来,给演员们端上热饭热菜。大队和公社也很关心我们剧团,给我们剧团每人每天增补2两米,每人每月增补半斤油。剧团将这些粮油匀出部分,用于救济村里的贫困户和老弱病残。
1963年秋,我们剧团第一次应邀到陵水新村港为渔民演出几场琼剧,收入260多元,回到洪李村后,剧团分文不取,将这笔收入上缴生产队。队长和社员们都过意不去,要求剧团把这笔收入留下来发给大家作生活补贴,大家都一致谢绝。团长说:“我们是村里的剧团,拿工分是我们农民剧团的本色,我们的演出收入无条件归集体,归社员,我们不能私分。”我们这些“拿工分”的演员,就这样凭着为父老乡亲服务的满腔热情,在集体和乡亲们的呵护下,度过了艰难岁月,度过了长长的25年。
印象之三:特殊的奖赏
1963年,我们洪李村剧团因团长年事偏高,大家推举我担任团长并兼导演、演员(旦角)。重任在肩,为了不负众望,我和副团长符泽模、符泽平使出浑身解数,带领剧团继续前行。
作为一个村级业余剧团,我们深知剧团在演艺方面是“先天不足”的。为了提高演艺水平,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即把剧团人员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到琼海民声剧团、澄迈县剧团观看演出,请教取经。在澄迈,我们得到剧作家陈东和多名演员的指导,获益匪浅。我们还把本县琼剧团“台柱子”之一的陈敏初先生(名生)及男女主角演员黎和香(男)、梁娥英等请到村里来做示范演教。陈敏初先生在我们剧团驻团带演了三个多月。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改进,我们剧团从戏台的布置、剧中人物的扮相到演员唱打念做的一招一式,乃至扇子功、水袖功的运用等方面的演艺技巧,都取得突破性的提高,都能让观众耳目一新。我们剧团到本县的藤桥、崖城、红沙、羊栏、马岭等公社演出,各地群众观看演出后说:“你们洪李村琼剧团越演越捧了,吃番薯粥的(业余剧团)和吃大米饭的(专业剧团)一样样了!”1964年,我们剧团参加全县文艺会演,以传统剧目《糟糠之妻》和现代移植剧目《打铜锣》《补锅》力压群芳,获戏剧类节目表演一等奖,县政府给我们剧团颁发了锦旗和奖状。
我们洪李村琼剧团以出色的表现和骄人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赢得了党和政府的赞誉,从生产队、大队、公社到县文化部门,都在资金等方面予以剧团力所能及的扶持。这样一来,我们剧团就更加壮大了。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剧团的名气越来越大,几乎天天都有县内县外的“特派员”到我们洪李村来“绑戏”(预订演出)。乐东县乐罗村前来“绑戏”的陈老伯,当时已七十多岁,为了“绑”到我们剧团,天天跟着我们到各地演出,从陵水的新村、英州,一路随我们到藤桥、崖城,天寒地冻也不在乎。当他得知我们剧团决定当晚在保港头灶村演完《搜书院》一场就到乐罗村演出的消息后,就连口赶回乐罗村,带上10多个乡亲和10多辆牛车在戏场外等候我们,散场后七手八脚帮我们收拾行装,硬是要我们连夜赶到乐罗村。在陈大伯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们全团人员从头灶村步行到乐罗村,这4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摸黑走了足足10多个小时(从晚上12点到次日上午11点)。虽然周身酸软,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因为这是群众对我们剧团莫大的信任、期待,是无声的赞许。
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在乐罗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请我们去做客,请我们去住宿,如遇故人,如逢喜事,人人春风满面。我们演了《张文秀》,又让我们演《秦香莲》;演了《打金枝》,又让我们演《林攀桂》。我们在村里连续上演了11场,村民们还舍不得让我们离去。因为我扮演琼剧《张文秀》剧中人“三姐”,男女老幼白天见到我都亲热地叫我“三姐”。我住宿的人家,只有一对小夫妻。男的被队里派到村外放养鸭子,女的被队里派到水利工地当炊事员,夫妻俩一年难得回家团聚一回。听到风言风语,便互相猜疑,闹别扭,话说不到一块儿,双方都跟我诉说各自的“委屈”。一天,我让这对小夫妻和我一起吃晚饭。饭间,我给小夫妻讲述了琼剧中好几个夫妻释疑的故事,还给他们演唱了琼剧《张文秀》里“三姐”的一个唱段:
劝郎君你莫生气,
为妻跪下愿赔礼。
千万要体谅莫怪你妻,
她含冤受苦度日如年……
一曲未了,小夫妻动情了,丈夫当即放开歌喉,也给我和他妻子演唱了一首崖州民歌:
千错万错哥认错,
恳求妹子原谅哥。
“三姐”请你来作证,
今生今世对妹好……
小夫妻终于和好如初。
离开乐罗村那天早晨,父老乡亲们都来给我们送行,并送上他们精心准备的礼品:生猪1头、鸭子20只、鸭蛋200个。临别时,“绑戏”的陈老伯匆匆赶来,给我送来10包草药,说:“梅侬,老伯我发现你的声音哑了,戏唱得吃力了,特地上山为你采挖这些祖传的清肺润喉草药……”我从陈老伯那双皱巴巴的手中接过草药。此刻,我觉得陈老伯给我送来的不是草药,而是一份暖融融的爱心,一份沉甸甸的希望,一份无比珍贵的特殊的奖赏。我回过头来,还来不及说声谢谢,心头一热,止不住泪水盈盈……
此文应海南省政协文史委之约采写。全文由亲历者符史梅口述,三亚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卢鸿书记录,游师良撰写。收录于2014年12月出版的丛书《琼剧亲历见闻录》,为获奖作品之一。
相关人物
史梅
责任者
相关地名
三亚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