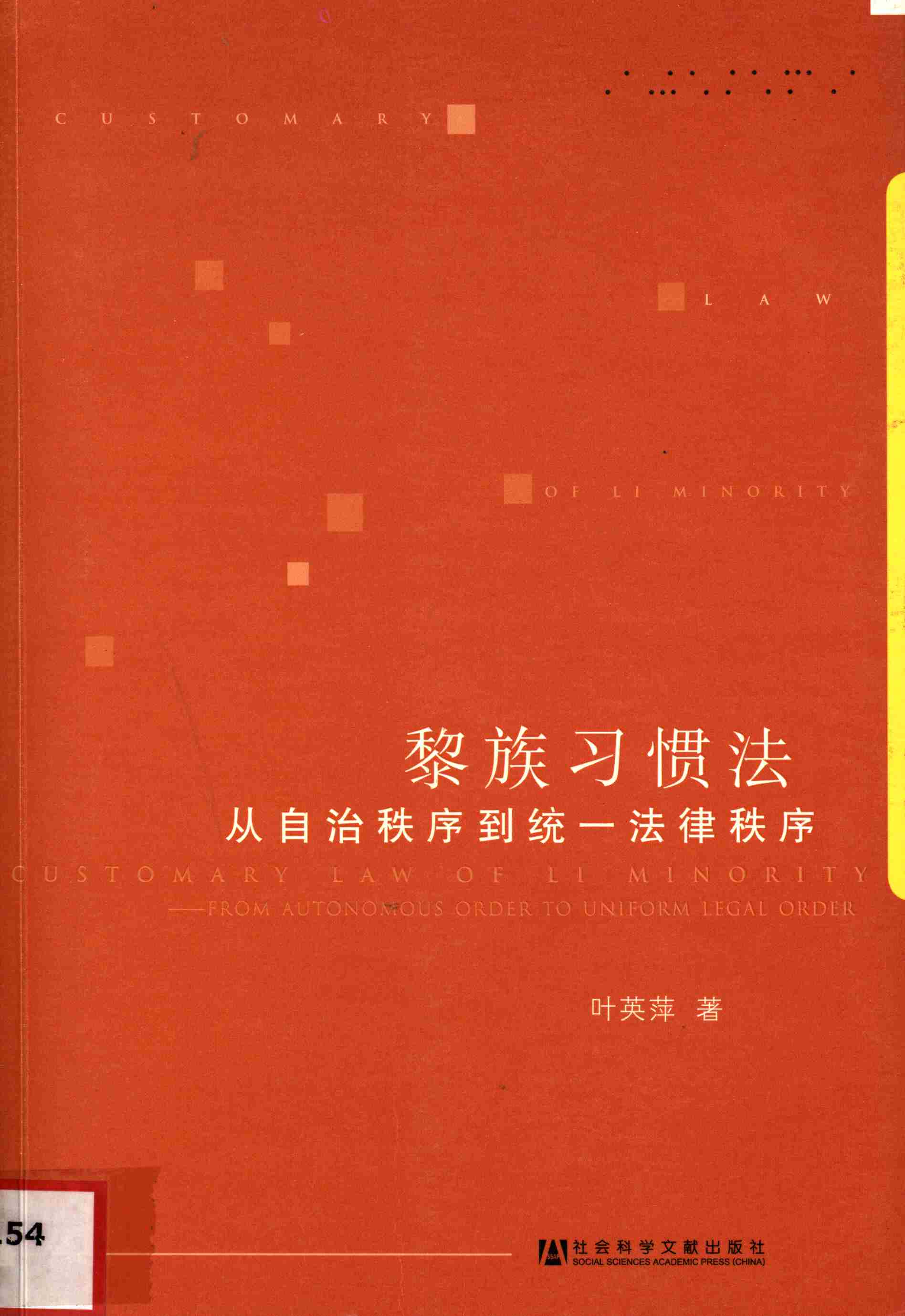内容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越,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建珠崖、儋耳两郡始,海南岛即纳入封建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之内,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密切联系。然而自汉代至南北朝的几百年里,封建王朝对海南岛的统治极不稳定,多数处于遥控或放任状态,海南岛的黎民绝大多数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发展十分缓慢。隋、唐、五代时期,随着海上国际贸易的发展,海南岛的经济与地理地位得到了提升,封建王朝开始积极经营海南,大批中原汉人也纷纷跨海来到海南岛,①参与到海南的建设与开发中来,海南岛发展缓慢的局面因此得到了改变。宋、元、明、清,以及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权逐步向五指山中心地区推进,建立地方政府,不仅实现了中央政权在海岛的全面覆盖,而且实现了对海南岛的真正统治。“宋代置靖海军节度统治全岛……元置乾宁军民安抚司于琼山,属广西中书省,治理全岛……明置琼州府,统治全岛,属广东省……清将琼州府改为崖州道,仍属广东省,统治全岛……民国成立后,设琼崖道于琼山,置道尹治理全岛……十七年由广东政治分会将广东全省分为四善后区,设南区善后公署于琼山,统辖阳、交、雷、钦、廉、琼、崖七属,十八年撤销。二十二年设琼崖绥靖委员会公署于海口市,为全岛军民行政最高机构。二十九年广东全省分为九行政督察区,而以本岛为第九区,由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并于是年六月划黎境为白沙、乐东、保亭三县。”①与中央政权的介入相对应,从宋代开始,黎族地区逐步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统一法律秩序之中,黎族民众的原有生活、生产秩序被不同程度地打破,黎族地区传统的自治秩序发生了变化,加快了融入中原文化和中华法系的步伐。
第一节 黎族地区被中央政府纳入统一法律秩序之中
一 中央政府对黎族人民的剿抚政策
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全面统治,黎族地区被中央政府纳入统一法律秩序之中,是在中央政权对黎区的征服、对黎人的剿抚中逐步完成的。自汉代建制始,中央政府对海南的管理基本上是放任的,只有在发生黎人暴动时才出兵清剿,甚至曾一度取消了建制,至宋代,封建政府明显加强了对黎民的治理。承袭唐之少数民族羁縻政策,宋一方面对犯乱之黎人进行讨剿,另一方面又招降黎人,奖赏对政府统治有功之黎人,奖惩分明,以达到分化黎人、维护地方安定之目的。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安抚使王祖道经广西到海南岛“抚定”黎峒907峒,丁口6.4万人,开通道路200余里。在被征服地区,宋王朝采取了“羁縻政策”,对黎族上层“首领”委以官禄,通过他们来统治黎族人民,并通过他们来吸引更多的黎族头人归降。“宣和间,儋人陈大功招抚符元亨等三十余峒黎入贡,补元亨等承信郎,诰令其子孙各以官名承袭,世为峒首。大功亦补丁班,只应官至融州巡辖。”②“乾道九年八月,乐会黎贼劫省民,焚县治。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陈颜招降之。琼管安抚司上其功,借补承节郎,诏许子孙袭职。”③宋“元祐三年正月,诏广南西路珠崖军开示恩信,许生黎悔过自新”。①宋之所以在被征服黎区推行羁縻政策,与当时宋王朝对黎人的认识不无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如苏过的《论海南黎事书》:“仆以为以力胜者,兵罢而复塞;以利啖者,贼贪而不叛也。朝廷若捐数官以数人,则贤用于师矣。……使赍金帛入喻诸黎,晓以利害,惧以祸福,若能开复故道,使行旅无壅,则籍其众所畏服者,请诸朝,假以一命,而岁与其禄,不过总十余人,岁绢千缗耳。今朱崖屯师千人,岁不下万缗,若取十一以为黎人之禄,可以罢千师之屯矣。”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宋王朝开始大量任用黎族峒首为黎区地方官。在剿抚黎民的同时,宋还将海南作为官员贬谪②、罪犯流放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文化得以随被贬谪之人深入海岛人民的生产生活之中,黎族人民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步伐因此而加快,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封建政府对海南统治方法的改变,即由过去单纯的武力镇压,改变为剿抚结合,并辅以文化影响,以促进海岛及其居民的文明进化和思想改造。
在唐宋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元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即对归附的少数民族及其首领假以爵禄,宠之名号,使之仍按旧俗管理其原辖地区,民族和部落首领服从中央王朝的统治,并承担一定的赋税及军事义务等。在海南,元统治者对黎族人民的政策重在剿上,但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则在海南岛专门设立“黎兵万户符”,下辖千户所,千户所下又辖百户所,在黎族地区实行土官制度,万户以下一般都任用“归降”的黎族上层为“峒首”,统治者给他们封以官爵,付以实权,世袭其职,统管地方上的军事和民政。
明清时期,虽然大多黎峒已编入版图,居户编入里甲,黎人与汉民杂处现象较普遍,但五指山区仍不断有黎为乱,对此,中央政府采取了以抚黎防黎为主,以剿黎平黎为辅的治黎政策。明朝,由于汉、黎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大多黎峒已编入版图,居户编入里甲,在这些地区,黎人与汉民一样,受地方官管辖,受中央政府法律的统一调整。“在一些开发较早的熟黎地区,明初曾实行‘都图’制度,当地官府对他们采取直接治理的方式,他们与汉人一样纳粮当差,到了嘉靖年间,文昌、乐会、琼山等多个黎峒的黎族已和当地汉族一样编入都图,载入黄册与鱼鳞册,其中不少人‘习书句、能正语’,有些土官子弟入县学、大学读书,到明代后期,部分熟黎民族特点日趋减少,逐渐与汉族同化,已不再被视为黎族了。”①在已顺化的熟黎地区则实行以黎治黎的土官政策,选择有能之熟黎峒首,授以官职,管理黎区;对尚未归顺并仍犯乱之生黎实行剿杀,剿杀之后实行善后抚化政策,开通道路。“洪武初,尽革元人之弊:土酋主都者,元帅陈乾富以降免罪,徙为广西平乐通判;州县各另除官,不用土人;兵屯子孙尽革为民,以峒管黎。二十九年,革除广东公差。大理寺丞彭与民等奏言:琼州府所属,周围俱大海,内包黎峒,民少黎多。其熟黎虽是顺化,上纳秋粮各项差役俱系民当。其生黎时常出没劫掠,连年出镇征剿,为害不息。今询访各处熟黎俱有峒首,凡遇公差役,征纳秋粮,有司俱凭峒首催办,官军征捕亦能凭峒首指引。今所属各有防黎及备倭巡检司,如将各处峒首,选其素能抚服黎人者,授以巡检司职事,其弓兵就于黎人内签点应当,令其镇抚熟黎当差,招抚生黎向化,如此则黎民贴服,军民安息矣。诏如所请。明年五月十一日,琼州府宁远县藤桥巡检司添设副巡检黄旗,通远巡检司添设副巡检黎让,十月十一日万宁县莲塘巡检司添设副巡检王钱,陵水县苗山巡检司添设副巡检符森。”②从此,土人被任命为官协助管理黎区被广泛运用,对被招抚之黎头适用,对有功有能之黎人也适用。如宜伦县熟黎峒首王贤祐。中央政府对黎人,“各验其招抚多寡受赏,除官有差,专一抚黎,不预他事”。③土官的任命使用,在黎族地区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已授禄之黎首,主动请缨招黎受降。
清朝对黎族人民的统治仍然沿袭明代的一套办法,剿抚结合。“雍正八年正月,崖州黎峒三十九村生黎王那诚、向荣等,定安县潮村等处十四村生黎王天贵等,琼山县番否等处十八村生黎符天福等,陵水县生黎那萃等,共二千九百四十六人输诚向化,愿入版图,每丁岁纳银二分二厘以供赋役。三月,总督郝玉麟等奏闻,奉旨:‘生黎诚心向化,愿附版图,朕念其无田可耕,本不忍收其赋税,但既倾心依向,若将丁银全行豁免,恐无以达其输诚纳贡之悃忱,将递年每名输纳丁银二分二厘之数,减去一分二厘,止收一分,以作徭赋。地方文武大臣,时时训饬,所属有司员弁等加意抚绥,悉心教养,务令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以副朕胞与地方之至意。’恩诏既颁,黎民感泣,自是琼属诸黎悉化为良民矣。”①朝廷的抚绥政策,显然有利于减轻生活困难的黎民负担。但清代在对待土官的政策上,则有别于明代,采取逐步削弱土官权力之策。清代的黎族土官职低官小,仅在黎族村峒设“峒长、总管、哨官、黎首、黎练、粮长”等类土官。清代后期(1886年)冯子材率兵入琼镇压黎族人民起义,他深入五指山腹地,在黎族地区设立专门管理黎族事务的“抚黎局”,实行一整套维护封建统治的治黎措施:抚黎局下设黎团总长,统辖县属黎境,黎团总长下设总管,统辖所属全峒之事,峒内设哨官,统管一村或若干村,村内的黎户十家为一排,三排为一甲,三甲为一保。所有的排长、甲长、保长、哨官、总管等职均由黎族担任,黎团总长则为黎族头人或汉族地主担任,抚黎局局长由上级委派汉族封建官吏担任。除了加强基层建设、任用黎首外,冯子材还在征服之黎区,修路设寨,设置招商局,发展贸易,号召黎民学习汉文,薙发改装,除弊化俗。此时在海南岛依然有“生黎、熟黎”之说,但已无生黎、熟黎之分,黎族地区完全置于清王朝有效的统治之下。
二 黎族社会的分化
在封建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下,黎族社会发生了分化。
1.黎民被区分为生黎熟黎
将黎民区分为生黎熟黎,是中央政府等外界所为。生黎熟黎的区别是:“熟黎多纳官粮……生黎则各食其土,不入版籍,止设有黎练峒长之类统辖之……”②可见,是否入籍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是否纳粮缴赋,是区分生黎熟黎的标准。随着封建王朝不断征黎、剿黎,中央政权逐步向黎区纵深扩张,黎族人民的生活范围逐步由沿海向中部山区集中,在这个过程中黎民内部发生了分化。按其与汉族同化的程度,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已与汉族融为一体的黎民、熟黎、半熟半生黎和生黎。
与汉族融为一体的黎民,是熟黎的一种,受中央政权管辖较早,与汉族长期杂居,已基本脱离黎之习性,如同汉人,完全汉化,徒有黎称。“澄迈黎南曰南黎,今为一都二都,西曰西黎,今为中正都,澄迈县诸黎村峒凡一百三十有七……县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旧系黎峒,明永乐间抚黎知府刘铭奏以抚黎官王朝冠等招抚生黎,概免徭差,正统间革归有司,弘治十七年副使王继复援前例以黎图仍归土舍,止令防黎,纳粮免差,其后黎地渐归豪民,黎人归化既久与齐民等。现查其地为西黎中正二都,南黎正一二等都,每都编为十图,虽有黎都之名实无黎人之实。……文昌黎曰斩脚峒,治平已久,田地丈入版图,故有文昌无黎之说。”①这一部分黎人长期与汉人混居,如同汉人,已完全汉化,徒有黎称。《道光琼州府志》也有同样的记载:澄迈“县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旧系黎峒,明永乐间,抚黎知府刘铭奏以抚黎官王朝冠等招抚生黎,概免徭差。正统间,革归有司。弘治十七年,副使王继复援前例,以黎图仍归土舍,止令防黎,纳粮免差。其后,黎地渐归豪民。黎人归化既久,与齐民等。现查其地为西黎中正二都,南黎正一、二等都,每都编为十图,虽有黎都之名,实无黎人之实”。②之所以澄迈、文昌已徒有黎称,其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位于海南岛的北部或东北部沿海,中央政府的军队上岛后最先占领的就是这些沿海地区,并在府城、定安、澄迈等地建立了地方政府衙门,原居民黎人有的逐步向中部山区后退,有的则坚持下来,在与汉人长期的杂居生活中,逐步接受了汉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方式,最终与汉人无异。
除了上述已与汉民齐的黎民外,《治黎辑要》还将崖州黎分为三种,生黎、熟黎和生熟各半黎。熟黎系居住在黎区外围,与汉民接壤,归化既久之黎,“生黎者即乾脚歧之类也,裸体兽性穴居鲜食,环居五指山下,与民人隔绝,不为人害。熟黎者归化既久之黎也,饮食衣服与民人同,惟束发于顶,其俗未改,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其户口编入图甲,有司得治之,故亦不为人害。生熟各半者谓可生可熟之黎也,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其中亦分两种,曰大襜小檐,大抵富有者为大襜,贫者为小襜,平时耕田纳赋听官约束与熟黎同,然性嗜酒好斗……”①清人钟元棣创修,张嶲等纂修的《光绪崖州志》亦将黎区分为熟、生、生熟各半三种,“大抵熟黎习俗与生黎同。近民居者,饮食衣服亦与齐民同。惟宅心险恶,常以蛊毒、禁魇杀人。好斗乐乱,不能久安,动欲寻衅开叛,愈抚愈骄。大创一次,可静十年。其杂处生熟黎中者,为半生半熟黎。平时耕田纳赋,与熟黎同。但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常挟火器自卫,杀人与刈草。一有宿怨,辄手刃之。甚则屠牛走箭,负嵎思逞,引生黎以为州患”。②半熟半生黎,也有称为“三星黎”、“四星黎”的,所谓三星、四星,即三分生、四分生,还没有熟透,他们“开险阻,置村峒”,“好斗乐乱”,“不能久安”。显然,生黎、熟黎、半生半熟黎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接受中央政权统治和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的程度,接受汉族的东西越多,其自身原有的特色则失去的越多。
海南岛生黎、熟黎的划分,始自宋代。宋代同中原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一样,将国之四边的少数民族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称之为夷、狄、蛮等,将苗、壮、黎等少数民族分为“生户、熟户”,其中被纳入政府户籍,由地方管辖以及承担封建赋税和徭役的,或是邻近汉区,与汉人较为接近的,称之为熟户,“居深山避远,横过寇略者之生户”。③也就是从宋开始,黎民被区分为生黎和熟黎两种。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在介绍海南时描述道,“四郡十一县,悉隶广南。西路环供黎母山,黎獠蟠踞其中,有生黎、熟黎之别……熟黎峒落稀少,距城五、七里许外,即生黎所居,不啻数百峒,时有侵扰之害”。④宋王象之之《舆地纪胜》对此有所记载:“诸蛮环居号黎人,其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号生黎,耕作省地者号熟黎……”从封建统治阶级的角度看,谁接受其统治谁就是开化的、熟的、与民同的,反之就是生的、不化的。所谓生黎即嚣顽无知,质直犷悍、不服王化、不供赋税。熟黎就是“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识字者”,“近民居者,饮食衣服亦与齐民同,供赋役于官府”。据宋人乐史纂《太平寰宇记》记载:“有黎人,无城郭,殊异居,非译语难辨其言。不知礼仪,须以威服。号曰生黎,巢居洞深。”对于生黎,推行“以蛮夷治蛮夷”的羁縻政策,加以笼络。统治者对黎人的统治重点在于熟黎,因为他们认为“生黎嚣顽无知,伏居深山,质直犷悍,不服王化,不供赋役,亦不出为民患,惟与其类自相仇斗。间有患及居民者,则熟黎导之也。……生黎虽犷悍,不服王化,亦不出为民害。为民害者,惟熟黎与半熟黎”。①
随着中央政权在黎区的深入,黎民的变化进一步加剧,到了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对所谓的“生黎”已感到非常的遥远与陌生,半生半熟黎则分布最广,人数最多,熟黎也在变化,基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完全汉化的黎,一是由半生半熟黎发展而来,在明代中叶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基于生黎与熟黎的划分,中央政权对黎区实行的政治制度与管理方式有较大的不同。②
2.黎头变化为朝廷命官
自恢复黎区建置以后,中央政府不断完善对海南岛的统治措施,一方面继续对抗命扰民之黎进行清剿,另一方面则通过抚黎政策,改造、分化黎民。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黎族社会发生了政治分化,原来的黎头成为朝廷命官。
据史籍记载:“生黎不属官,亦各有主。”③在明、清以前,黎族社会本身并没有出现过统一的政治人物,但各地黎民却有着自己地域内的政治组织机构,如合亩制地区的亩头承担本亩内的管理事务,峒首则是若干黎族村峒的领导者与管理者,“……置村峒。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④宋代黎峒归顺中央王朝不断扩大,中央王朝对黎族的控制大为加强,开始实行土官制度,委任上层黎首为黎族土官,但这些土官大都为虚衔,且品级低下,如宜人、承信郎、校尉等。元朝起,在征剿后对与汉族接邻的边沿地区的黎族同胞进行招抚,“编入图籍,与齐民无异”,起用“归降”的黎族上层为峒首,封以官爵,付以实权,世袭其职,统管地方上的军事和民政。他们当中有任万户、千户、总管、知州、县尹等要职的。明代在黎族地区仍实行土官制度,鉴于元代“黎兵万户府”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封建王朝构成了威胁,遂废除了这种土官制度,实行另一套比较完备的土官制度,即军政分开,自州以下设土官同知、判官、知县、县丞,任用黎族土官或当地有势力的黎族峒首为土舍,专门管理黎兵。清代仍设土官,管辖黎区。清代黎区基层组织为村峒,以峒辖村,在各村峒设峒长、哨官、黎总。据《道光琼州府志》记载,中央政权在黎族地区的基层组织已基本设立,各县下辖黎区均设村峒,设峒长、哨官、黎总管辖生黎、熟黎,乐会县南北两峒皆系熟黎,北峒各村设黎甲一名,南峒分上、中、下三峒,上峒设黎长一名,中峒设黎甲一名,下峒设峒长一名。至清康熙时,开始注意经营中心腹地,开十字道路通至各州县,在汉黎交错处,如琼山设水尾营、陵水设保亭营等军事机构。光绪十三年(1887年),冯子材率兵“平黎”后,除在中心地区增设镇板营、巡亲营、大坡营、番阳营之外,曾设立“抚黎局”,作为统一管辖黎区的最高机构,下设总管(即黎总)、哨官、头家等官职。任用黎族内部原来的公众领袖,通过他们层层统治黎族人民,以达其“以黎制黎”的目的。1932年陈光汉任“抚黎专员”时,改“抚黎局”为“黎务局”,易总管为团董,日本人登陆海南岛,国民党退守黎区,又将团董改为乡长,下设保长、甲长。①
总管、哨官、头家的授受有一定的仪式。总管由“抚黎局”委派,并给委任书、印章、铜牌、衣履、布鼎等物;哨官由总管委派,也有委任书、印章、铜牌、衣履、布鼎等物;头家为哨官口头指派。总管、哨官均为世袭制,头家多由群众推举,但也有少数是世袭的。各人的职责视其所辖范围大小而定,总管一般是管一峒或数峒,哨官管数村,头家管一村。总管、哨官的职责是每年替“官府”催收钱粮,平时根据传统习惯处理峒内事务,维护社会秩序。经过任命和委任,过去的黎头、峒首成为中央政府的命官,传统权威与中央权力合而为一。《元史·刑法志》说:“诸内郡官仕云南,有罪依常律;土官有罪,罪而不废。”尽量保持土官在当地的世袭权力与地位,以便利用这些蛮夷之官传统的地方势力与影响来统治各族人民。
3.基层经济与社会组织发生变化
(1)合亩制的变化。大亩变小亩,甚至出现了个体小农户。合亩制是部分黎族农民从事集体生产、个别消费的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央政权进入黎族地区以后,合亩制发生了变化。根据调查资料显示:这种变化一是合亩组织由大变小,并分化出个体小农户;二是在边沿地带,合亩制分化为个体小农户。“白沙县第二区毛栈乡什够村,在5代以前只有一个‘亩’,40年前也只发展到4个,其中有一个‘亩’最大,由15户组成,但在约15年前,便分化为8个‘亩’,并有一户从‘合亩’内分化出去单干。又如保亭县第三区通什乡福关和毛利两个表(相当于行政村,由一个大的或两个以上小的自然村组成),在10~20年前,各有4个‘亩’,但是现在福关表有11个‘亩’,毛利表有7个‘亩’。”①“如白沙县第二区红星乡番响村一带,据该乡文书王高定(50多岁)说,在清朝乾隆以前当地是以‘合亩’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到乾隆以后便逐渐分解,现在全部是个体小农户了。”②以上合亩制变化的原因,既有内部原因,如人口增长,耕地面积有限,生产产品不能满足亩内人丁生活,不得不分开各自谋生;亩内田多劳动力多的各户在自身具备单干条件后,宁愿单干而不受平均分配产品原则的限制。也有外力影响所致,如边沿地区受汉族地主的欺压比中心地区严重,往往一人得罪了地主,便被罚大量田产和耕牛,牵连到整个合亩,将祖遗田产分给各户是避免牵连的最好办法。③
(2)原始的黎族村峒成为封建王朝的基层组织。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开始在海南设立珠崖郡、儋耳郡,这两个郡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直接隶属于中央封建王朝,从此中央的封建王朝正式在海南行使它的行政管理权。但是珠崖、儋耳仅是郡一级行政建制,中央政权并没有因此到达社会基层,特别是黎族地区的底层,仍然处在原始的以峒为界的氏族部落状态下。汉代两郡的设置只存在了60多年,60多年后,因为黎族多次起义,汉元帝的时候把这两个郡撤销了。之后的500多年间海南又处于无行政建制的状态,但在名义上海南岛仍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到了南朝梁大同年间,高凉郡俚族首领冼夫人奏请朝廷重新设置崖州之后,海南的行政建制再也没有间断过,而且不断改善。“越人俗好攻击,夫人兄南梁周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旁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峒。”①南梁大同冼夫人向朝廷请命置崖州,从此,中央王朝通过“南越首领”冼夫人,与黎族社会组织峒建立了间接联系。隋唐时期不断有黎峒归附于封建中央朝廷。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开始逐步向黎族社会的基层渗透,将已经归化的熟黎纳入到地方建制中,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实行统一的管理,从而进一步紧密了峒组织与中央政权的结合。明朝建立以后,朝廷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海南的行政治理和加快海南的开发。明太祖建朝以后,在海南设立了琼州府,作为全岛最高的行政机关,结束了海南岛的行政机构互不相干、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将海南由广西管辖改为广东管辖;对黎族进一步实行安抚政策,将封建政权深入黎峒,大多数黎峒被编入封建王朝的基层组织——黎图中。明在基层设“黎图”,若干个“黎图”为“黎都”,若干个“黎都”为一乡,乡为流官隶属州县,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使“熟黎”与编户的汉人一样编入都、图,载进鱼鳞册、黄册,要纳粮录差。综合地方文献,海南岛“熟黎”居多,岛的南部被编入黎都黎图者凡28都、75图,包括155峒,它们以岛的北部与沿海地带居多,岛的南部及山区较少。②清代基本承袭明朝在黎族地区的政策不改,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立了专管黎人的机构——抚黎局。广西提督冯子材在平定黎乱后,大行改革原黎族组织,设立抚黎局,抚黎局下设黎团总长,统辖所属黎境,黎团总长下设总管,统辖全峒,峒内黎户十家为排,三排为甲,三甲为保。至此,中央政权基本覆盖了黎族全境,深入到每一户黎族人家,峒成为清政府在黎区的一个行政单位。
峒,原意是“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区域”,黎族的峒组织自宋代以后文献多有记载。在宋代,黎族社会组织称峒,每一宗姓为一峒,全岛黎峒林立,但规模较小,苏轼有诗云,“四州环一岛,百峒蟠其中”。①黎族的峒是一个封闭的集团,它具有一定的区域,每一个峒由若干村落组成,每一个村由若干个父系氏族即“合亩”血缘家庭构成,每一个氏族(“合亩”)由若干个家庭组成,合亩是峒组织的基础。峒内事务及峒与峒之间的事情由峒内各村的长老参加的长老会议处理,村落的内外事务由长老处理。②峒与峒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相属。
从峒的构成我们可以看出,峒是黎族社会的带有血缘联系的原始氏族部落,在封建中央进入黎族地区以后,黎峒成了中央政府在黎族地区的一级行政单位,原由家庭为基础构成的氏族和村落,在中央政权的统治下,变成了以户为单位的都图、保甲编制,黎族社会原始的血缘氏族的村峒划分被彻底打破,黎族社会从此与中原汉族地区一样,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法律秩序之中。
4.形成贫富对立
黎族喜血缘群居,峒首、黎头原本是本氏族选出的有威信的长老,是黎族人民尊重的公众领袖“奥雅”。因履职需要,他们理所当然地占有较多的氏族财富,职位的世袭,黎众的尊敬,使他们逐渐成为黎民中的富人。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这些富裕家族的氏族长老,取得了部落首领的地位,在所管辖的领域内掌握了政治、军事大权,占有了更多的田地、山林、耕牛等氏族资源和财富。中央政权在黎区实行土官制度后,他们的首领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在本氏族拥有了中央赋予的地方政治与军事大权,世袭制又使得其势力不断扩大,权威不断提高,财富不断积累。当与中央政权结合,峒成为中央政府的基层组织以后,黎头峒首则将原有氏族残余的家长制势力与手中政府权力结合起来,侵吞公有土地、山林,通过放贷强占黎胞田地,处理辖区内事务时,除接受宴请外,还收取黎民酬物,暴发起来,成为剥削阶级,对黎族群众进行压迫与剥削,黎族社会中产生了阶级对立。“如保亭县四区加茂乡毛淋村地主黄朝辉父亲和本人都曾任哨官、团董等伪职,处理偷牛、偷米等大小案件,除要鸡、酒外,还要10至100元光洋,如处理人命案,则任意要多少得给多少,否则便按年复利计息,逼得群众用田、牛或人工来抵债。”①除了财产侵占外,这些黎头、峒首还“学会了一套封建性的统治剥削方式,如勒石示禁、私设监牢等,形成一种‘家长制的农村生活的东方野蛮制度’的独特的统治阶级。而且越到近代,封建剥削的成分越重,虽然名为‘奥雅’,但传统的原始色彩已渐趁消失,并逐渐蜕化为封建性的地主恶霸”。②
土官峒首成为普通黎民之害,还可从官员奏议中得到证实。如明弘治时琼山主事韩俊在《革土舍峒首立州县议》中奏道:“为今之计,莫若革去土舍峒首,立以州、县、屯、所,量拨在外军民,杂处于中防引……今土舍峒首皆仗货利肥家,逢迎府县,闻欲立州、县、屯、所,彼愀然不乐……”③明代杨理在《上欧阳郡守四事》中第一事就是,“申明奸弊事。各峒首土舍欲据黎为利本,峒首乘盛饱餍其欲,受害者积恨,异己者互相侵伐仇杀,而祸害相寻于地方”。④与中央政权相结合,政治上有权、经济上有势的这些黎族土舍、峒首的强取豪夺,危害地方,也应是清中央政府改土归流的原因之一。
三 中央权威下的统一法律秩序
自宋中央政权进入黎族地区,逐步加强对黎族的管理以后,黎族地区形成了中央权威下的“以黎治黎”的统一法律秩序。
所谓中央权威,就是中央政府将黎族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之下,实行与中原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中央权威在黎族地区的统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黎族地区的各级管理者,都是经过中央政府的任命,是经中央授权且世袭的在册官员。如“宋朝宣和年间,陈大功招抚符元亨等三十余峒入贡,补元亨等承信郎,诰令其子孙各以官名承袭,世为峒首”。①宋朝对招抚归顺的黎头授予官衔,虽然多为虚职,却是经过任命、为朝廷效命、联结朝廷与黎人、享有世袭爵位的官员。元朝不仅承袭了宋的羁縻政策,继续任用黎人为官,而且还大幅度提高了黎官的品级,掌管军政大权,担任千户、万户的常常有之。明代的黎官任用制度较元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达到了鼎盛阶段,“明永乐六年春二月,琼州府抚黎知府刘铭率生黎峒首王贤祐、王惠、王存礼等来朝,贡马。命贤祐为儋州同知,惠、存礼为万宁主簿,赐冠带、币钞,俾专抚黎人”。②明朝统治者不仅继续任命归顺之黎头为官,而且将黎官管理纳入了国家统一的官吏管理制度中,同时还将黎官区分为军政两类,从而避免了因手中权力过大而造成对朝廷的不利影响。黎官的广泛使用,使封建政府关于黎区管理的政策得以通畅。鉴于“以流官治黎”使政令推行效果不佳,更使黎人未易信从,明统治者采取“以黎治黎”政策,“宣德四年,以黎峒多侵挠,革去抚黎流官”。③元朝的土官制度对明清两代西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施政与立法影响很大,明朝土司制度更在元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将土司官职完全纳入地方官体制之内。清代“改土归流”之前,基本上沿袭了明代旧制,很多原则与具体措施也来自元朝。
清代抚黎之土官政策一直延续到清末始有较大变化,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现了专管黎人的机构——抚黎局。广西提督冯子材在平定黎乱后,大行改革原黎族组织,设立抚黎局,抚黎局下设有黎团总长,统辖所属黎境,黎团总长下有总管,统辖全峒,峒内黎户十家为排,三排为甲,三甲为保,所有排长、保长、总管均由黎人担任,抚黎总长则由黎首或汉族地主充当。抚黎局的业务在于负责处理诉讼、缉拿盗匪、修路垦田、设墟招商、任免村峒土官等事务。有清一代,虽然也实行以黎治黎的政策,但是,黎族土官远没有元、明时期的地位与权限,中央政府对他们及普通黎民实行了比较严密的监督与管理,土官只能是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一个基层代表而已。严密的保甲制度,打破了黎人村峒的血缘划分,转而成为依地缘而分的地方性组织或团体,黎民彼此之间的相互帮助义务因血缘疏远而逐渐消失了。
其次,封建国家的法律对黎族地区统一适用。《宋刑统》是宋朝的基本法典。其“化外人相犯条”就是对宋朝以外的各民族、各国家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宋朝皇帝的诏敕是最有效力的法律形式之一。北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针对一些地方有人杀人祭鬼的现象下诏:“禁川陕、南岭、湖南杀人祭鬼。”①明朝将土官纳入了化外人的范畴,强调国家法律的管辖权,一律适用明律。《大明律集解附例》:“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明正德年间的《大明律集解》中称“凡土官、土吏、化外夷人有犯,与中国一例拟断”。明朝不仅将国朝法律统一适用于黎区,而且还对黎区实行礼仪教化。明初实行重典治国,强调要“明刑弼教”,即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贯彻礼教纲常。朱元璋认为:“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②他又说:“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顽,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遣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③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高度统一和发展的鼎盛时期,祖国的统一比汉唐宋明各朝代更加巩固,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管辖更加深入,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从国家大一统的原则出发,顺治三年(1646年)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化外人有犯”条明确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并注明“化外人既来归服,即是王民,有罪并依律断,所以示无外也”。所谓化外人,包括满汉民族以外蒙古族等所有已经归附清朝的少数民族,这就从根本上明确了国家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少数民族发挥效力,保证了国家法制的统一。
民国时期的保甲条例,不分黎汉,统一实行保甲管理制度。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东政治分会将广东全省划分为四善后区,南区善后公署设于琼山。为加强管理,专门制定了《保甲施行准则》,其中包括《广东南区保甲条例》、《南区各县市长员办理保甲须知》、《团董须知》、《甲长之职务》、《保长之职务》和《家长之职务》。琼、崖属于南区善后公署的管辖范围。《广东南区保甲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各城市墟镇乡村住户,每10家编为一保,置保长一人;10保为甲,置甲长一人;10甲以上为团,置团董若干人。”第三条规定:“保长甲长由该保甲内公举,经甲长、团董之审查,呈由市县地方长官委充之。”该《保甲施行准则》没有区分黎人、汉民,只按自然城市墟镇乡村编入保甲,实行规范化统一管理,中央政府的统一法律制度在黎族地区已然完全建立。
再次,适用于黎族地区管理的特别法。封建中央政府除了为征剿叛乱、招降黎首、抚恤黎民而颁布一些谕旨外,没有专门为黎族地区的管理制定法律。维持黎族地方秩序和地区稳定的,基本上是黎区管理者制定颁布的带有规范性作用的政策、治理措施等,它多以告示形式出现。这些告示内容主要涉及几个方面:一是禁止各峒黎目总管哨长等对黎民勒索苛派;二是悬赏严拿黎匪;三是严禁汉人进入黎区对黎人欺诈抢夺;四是改造、限制或废止黎民陋俗。①黎区这些特别法有的张贴到黎区成为安民告示,有的被刻勒成碑成为禁示碑,有的张贴于府衙,成为布告。这些公布于众的告示、谕旨、禁示碑等,对黎族地区社会治安和百姓生活,都起到了很好的维护与保护作用。此外国家明确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的黎族习惯法,也是管理黎族地区的特别法。
两广总督张之洞与冯子材拟定的《抚黎章程十二条》,是一部比较典型的专门适用于黎族地区的地方特别法:“(1)官军此举专为剿除黎乱、招抚良黎,开通十字大路,以期黎汉永远相安,其良黎秋毫不挠,毋庸畏惧。(2)从前为匪黎人投诚者免,抗拒者诛擒斩,来献者重赏。(3)投诚诸黎无论生熟,一律䕌(ti)发改装。(4)投诚黎首开送户口册,捆献匪徒缴呈枪械。(5)投诚黎众随大军伐木开山前趋响导,仍按计里数酌给赏犒。(6)将来开通生黎大道后,选择要地设官抚治安营,弹压各村黎长,助剿开路有功者授为土目,就中酌设总土目数人,目给顶带,总目授土职,自为约束,仍听地方官选黜,略仿滇黔各省土司之例,不令吏胥索挠。(7)开通后黎人仍安生理有主之田,断不强夺,惟抗拒者籍产入官,充官军屯田之用。(8)开通后田业三年内不收赋税,三年之外务从轻,则起征断不苛敛。(9)开通后黎境有矿,各山由官商开采者,给钱租赁,绝不强行占据,黎汉均享其利。(10)开路通后,人民盐布百货与黎地牛、木、粮、药等物,在各峒口设场集市,来往畅通,公平交易,严禁汉民讹赖盘剥,总令于黎人有益。(1 1)设立土目之后,应各具永远不敢杀掠、抗官、藏匿匪徒切结存案,所属有犯,责成设归该土目拏(na,同‘拿’)送到官按律惩办。(12)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延请塾师,习学汉语汉文宣讲圣谕广训,所需经费就地筹办。”①该章程虽然是关于黎族地区管理与治理的措施与政策,但其中不少条款具有维护一方治安与秩序、对黎民行为具有调整约束作用的法律规范性质。
该《抚黎章程十二条》中,既有对为乱之黎的惩办与招降政策,也有对剿后黎区政治生活、经济生产、商品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规定与要求,既有对黎民百姓的要求,也有对黎族头目的约束,明确了国家法律在黎区的效力。显然它是一个专门针对黎族地区的特别法,该特别法对于被平定之黎区的生产发展、社会治安和人民生活无疑是有重要的规范作用的。
在消除黎族积弊、维护地方安宁方面,黎区地方政府往往联合几个部门共同颁布安民告示,以劝告黎人安分守己:“崖州协政府黄、持授崖州正堂萧、持授都关府鲍:为晓谕各黎峒事照得黎人生于边鄙居近海滨荷……奈近年来人心日坏,抢劫频仍,执铳持枪杀人放火,日肆猖獗,罪不容诛……本州、协、府爱民如子好生为心,固不忍不教而诛,又何肯养奸姑息。兹当春令伊始,即应亲临该乡察看,尔等近来能否安分守法照章给赏……其有从前误为匪徒者概不追究,倘有顽抗不愿就抚,许各峒内人等面禀缉拏,断不干连株累……晓谕为此示,仰尔黎总管哨长及各峒男妇老幼人等知悉,嗣后务宜各安本分各安生业,父诫其子兄勉其弟,毋籍端滋事,毋寻仇报复,毋结党横行……贫者种作耕田,富者读书向学……严刑劝办,勿谓言之不早也,各宜凛遵毋违特示。一发告示一百六十张,安抚西中等处各泛黎峒晓谕崖州正堂、陆路都司会商,会印:州堂协镇光绪十年二月初八日。”①这段安民告示,意图十分明显,安分守法者赏,违法作乱者惩办,总管哨长、男女老幼都有自我约束和劝导他人的责任。在黎区由各基层政权组织颁发的类似安民告示为数不少,其内容不外是对黎人劝诫,对土官约束。这些安民告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法律规范作用。
历代统治阶级虽然对黎族地区的统治没有颁发系统的成文法,但在明清以后,除上述地方基层政府颁发张贴的安民告示外,还有针对某些具体事务而刻的“禁示碑”,立于村头要道,晓谕官民以为警戒,以进一步加强黎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在黎区常有因某一方面的事情而引起纠纷,或两村械斗,或因官员假借官府之名摊派各种劳役,引起民愤而告官、闹事,为此,官府统治者便通过凿刻立碑的方式公布禁示令,禁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奉府道禁碑”:“告示民众严禁外来商民、兵士进入黎村侵挠黎民、索诈黎民,如有违者应告官治罪。”②再如:
奉宪口口口(口为缺字)[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碑:
特受琼州府正堂随带加三级记录五次肖
为严行申禁事,照得衙门官吏、书役人等,入黎索扰久奉明禁。
本府自莅琼南,叠经申明禁令,遵行示晓谕在案。今据昌化县属大员峒、大村峒黎民符那休持呈称,该处从前奉颁示禁,日久无口,以至骚扰复萌,或借官司名色,或借差役横眉饬取贡香、珠料、花梨、大枝渡船木料、豹皮、棉花、黎峒藤、竹、鹿茸鞭、熊胆、花竹、苏木等货,奔走无期,犹索脚步陋规,膏脂尽竭。乞再给示勒碑,永垂严禁。凡遇应时公务,着落峒长办理,毋许书役擅入黎地,借端索扰,至于峒长遵照,无故不得更,以俾得黎民安堵,共享舜日尧天等情,前来当批准,给示严禁并行县遵照。嗣后倘有书役入黎,借端索扰等,捆获送究在案,除行该县遵照外,合行严禁,为此示谕告该黎峒峒长、黎民人等知悉,嗣后遇有必须应时正经公务,听候该县令传唤,峒长谕令查办,倘有不法书役借称官差,擅入黎,勒取贡香料等物,索扰黎民,许该峒峒长、黎民捆获解赴。
本府只凭严行察究,该峒长仍得所颁口示勒石,永远遵照,毋得有违,自干重咎,特示。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峒长谢根村遵立碑起)①
该警示碑的核心内容在于防止有司官吏对黎族进行骚扰,不得以各种名目在黎族地区搜刮财产,凡有公务必须与峒长协商办理,如果有官吏私自骚扰黎民,则黎族民众可以在峒长的带领下将该官吏抓获送交官府处理。
又如:
严禁碑[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代理昌化县事儋州正堂随带加二级记录三次记大功二次李为严禁私挖,照得县属亚玉山坐落黎地,土产石碌向有不法民人,潜入该山偷采,业经前县林封禁在案,未及立碑。
本府奉委代理昌篆,于四月二十日到任,合行勒石,永远封禁,所有县属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勿违,特示。②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一立
这一警示碑的内容在于勒石封山,禁止官民到亚玉山私自偷采和挖掘石碌矿藏,并且强调,所有军民人等都必须遵守,以避免驻军和官员侵害属地黎人利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奉道宪严禁碑”也是保存至今的禁示碑之一。该碑记琼州抚黎总局在黎区分布行政条例事,佚名抄刻:“记述清光绪年间琼州抚黎总局为安定黎区,杜绝滋事,针对当时黎区出现的一些问题而颁布的六条行政条例。”③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收集的碑刻中,类似具有规范性管理措施的碑文还有多例。
第二节 外部规范与内部习惯法共构的秩序
自宋将黎族地区统一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以后,在黎族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由黎族土官负责基层管理的自治型社会,形成了由外部规范和内部习惯法共同构成的社会秩序和法律体系。外部规范即中央政府在黎族地区实行的国家法律规范,内部规范即黎族自身的传统习俗与习惯。两种规范虽然效力范围不同,却共同维护着黎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推动着黎族社会的发展,并且随着中央政权的逐渐深入,外部规范吸收了内部规范的有益部分,使黎族习惯法成为国家法的一部分,嵌入中华法系的主流之中,中华法律也因此进一步成为一个由多民族习惯法共同构成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大一统法律。
一 统一法律秩序下的黎族自治
上述中央统一法律秩序的建立,将黎区纳入了全国统一的管理体系中。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虽然是在中央统一秩序管理之下,黎区却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国家统一法和黎区习惯法共同构成了黎区的法律体系。
中央所谓黎族自治,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在黎族地区的管理政策,即循其俗,施其政,以黎治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任用黎人为官,二是由黎人因俗治理。任用黎头为官,这本是唐的羁縻政策,宋代在对海南实行统一管理时则继续采用这一政策。“周仁浚《长编》云:‘初平岭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知琼州,以儋、崖、振、万安四州属焉。上谓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别命正官,且令仁浚择伪官,因其俗而治之。开宝五年,仁浚列上骆崇琛等四人。上曰:各授检校官,俾知州事,徐观其效可也。”①《续资治通鉴》卷七也记载了这件事。宋初平定岭南后,宋太祖赵匡胤任命内廷亲信、太子宫官员周仁浚“权知军州事”,他与宰相赵普谈道,岭南是偏远蛮荒烟瘴之地,不需要另派官员,只要在当地选拔一些官员因俗治理即可。宋统治者治理海南的思路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用羁縻政策,选择当地黎人授予其官职,以黎治黎。自宋之后,各朝代对被征剿后的黎族地区,均采用以黎治黎的自治政策,至清乾隆时,该政策深入到黎族的中心地带,对生黎也采用。
统治者所任命的黎族地方官员,基本上都是在黎民中有一定威信的公众领袖,如黎头、峒首之类。直到1949年以前,黎族群众一般称总管、团董、乡长等类人物为“奥雅”,“奥雅”在黎语中即“老人”的意思。这一称呼一方面说明了原始社会的长者观念仍存在于民众思想意识之中,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央政府对黎族地区实行的仍然是“以黎治黎”的自治政策。“熟黎多纳官粮,然其中地颇荒阔不可以弓丈计,唯岁纳粮若干而已。生黎则各食其土不入版籍,止设有黎练、峒长之类统辖之,遇有事峒长黎练以竹箭传唤,无不至者,其信而畏法如此。黎头辖一峒者为总管,辖一村或数村者为哨官,大抵父死子代,世世相传,或间有无子而妻代之及弟代之者,为众心所归而公立之也。凡小事听哨官处断,大事则投诸总管,总管不能处始出而控告州县。”①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黎族长老在黎族人民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他在处理黎族内部事务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首肯与认同。
黎族自治,因俗治理主要是通过土官来实现的。根据中央政府的任命,土官获得了管理黎族地区的职权与职能,土官运用黎族习惯、习俗来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解决黎民之间的纠纷。土官的行为获得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保障,黎族习惯、习俗也因此成为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习惯法。
日本人冈田谦、尾高邦雄于1942年对原乐东县重合盆地所作的调查称:“村落内部的事情,一般由各户的家长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议处理。但在家长中也有几名年长者,他们经验丰富、明晓事理且行事公正,很受人们的尊重……无论家庭琐事还是村落大事,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且大多会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另外,长老对外还可以代表村落处理公务。峒的事情便由代表各个村落的长老们组成的长老会来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黎族的村落和峒是由长老们统治的。现在,各黎族村都设有村长,村长对外可以代表村落处理公务。但由于这种制度是中国政府为统治黎族而制定的,所以虽然村长表面上是村子的负责人,但在村落内部他们事无巨细都要与长老们商议决定。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汉化程度较高的村子里,村长的权威在逐渐强化,在经济方面他们也变得愈加富有。即使在那些至今仍维持着古老的组织形式的村落,人们也倾向于从那些经济富裕且能力突出的长老中推举村长。然而,归根结底,黎族固有的统治者并不是村长而是长老,这一点不容置疑。”①
自宋以降,随着中央政府剿黎军队向中部山区的不断挺进,中央政权在黎族地区逐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法制权威在黎族地区日益显现。然而因其俗施其政的少数民族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使黎族人民保持了自己的传统习惯,黎族传统习惯法也在中央权威下具有了国家强制力,它的遵守已不完全是依据黎族人民的内心信念,中央权威从外部发挥了推动与强制作用。
二 共构秩序下的法律体系
随着中央权威在黎族地区的逐步确立,在以黎治黎的政策指引下,中央政府实现了对黎族地区的有效统治,建立起由国家制定法与地方习惯法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实现了外部规范和内部习惯法的有机统一,外部规范和内部习惯法共同承担了黎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
共构秩序下的黎族地区法律体系,主要由适用于全国的国家法、地方基层政府针对黎族地区管理而制定的规章、告示和经中央政权确认或认可的习惯法构成。
1.中央政权制定的国家法
由封建中央政权制定的、适用于全国的国家法,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中国的法律特色。自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开始,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典的制定,强调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将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国家法的管辖之下。海南岛虽然孤悬海外,岛上居民虽然被中原统治者认为是不知礼仪的蛮人,却从未被排除在中央政权管辖之外,大一统的法律也从未将海南作为例外而不适用。不论是《宋刑统》的“化外人相犯条”,还是《明律》、《清律》中关于化外人的规定,都将黎人包括其中,“凡化外人相犯”均依律处断。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国政府法律,更是毫无区别地适用于整个海南岛。与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相适应,海南郡县的行政建制及其官员任免,海南地区的城防与经济建设,海南黎汉各民族的刑事犯罪,等等,都是依律而设,依律而断。律以外的诸如令、例、敕等其他形式的法律,同样在黎族地区有效,是黎族地区国家法的重要渊源。明朝将黎族土官纳入地方官体制进行统一管理,君主为表仁爱之心对黎族赋税实行减免,都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而做出的。
国家法在黎族地区适用,这是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统治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不论是宋、明王朝的汉人统治,还是元、清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民族团结、法制统一、国家稳定,是统治者的共同愿望。正如清入关后雍正所言:“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是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①统一的国家法是封建国家的基本法,也是黎族地区的基本法。根据它的原则规定,黎族地方管理者制定了专门的地方法,与之不相冲突的黎族地区传统习惯得以确认和保留,并被赋予了国家强制力,黎族土官无法处理的族内纠纷最终由州县来解决,从而保证了国家司法权的统一。
2.适用于黎族地区的专门法
在黎族社会,除了封建国家制定的统一法典外,还有专门为黎族社会管理而制定的特别法、专门法。
皇帝的诏敕。诏敕是皇帝以敕的形式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册封、宣战、用兵、媾和的旨令。封建中央政权自从对黎族人民实行剿抚政策以后,对归附的黎族头人封官赐财。如宋“乾道二年,从广西经略转运司议,诏海南诸郡倅、守慰抚黎人,示以朝廷恩信,俾归我省地,与之更始。其在乾道元年以前租赋之逋负者尽免之,能来归者复其租五年。守倅能慰安黎人及收复省地者视功大小为赏有差,失地及民者有重罚”。“淳熙八年,诏三十六峒都统领王氏女封宜人。初,王氏居化外,累世立功边陲,皆受封爵。绍兴间,琼山民许益为乱,王母黄氏抚谕诸峒无敢从乱者,以功封宜人。至是,黄氏年老无子,请以女袭封,诏从之。嘉定九年,诏宜人女吴氏袭封,统领三十六峒。”②再如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招抚黎人敕谕:“皇帝敕谕琼山县南岐村黎首陈忠等:恁每都是好百姓,比先只为军卫有司官吏不才,苦害恁上头,恁每害怕了,不肯出来。如今听得朝廷差人来诏谕,便都一心向化,出来朝见,都赏赐了回去。今后恁村峒人民都不要供应差拨,从便安心乐业,享太平的福。但是军卫有司官吏军民人等非法生事,扰害恁的,便将着这敕谕直到京城来说,我将大法度治他。故谕。”①明初为惩治贪官污吏,曾设有民拿害民官制度,永乐时虽然已不允许百姓直接拿掳官吏赴京,但仍允许直接告诉皇帝。永乐年间的这道敕谕,实际上就是将中原地区实行的重典治吏政策适用到海南黎族地区。
地方官为黎族社会管理制定的规章告示。为防止黎乱,实现对黎族地区的有效治理,自明以降,大臣纷纷上奏,献计献策,其中既有关心海南的海南籍官员如海瑞,也有身处黎区担任管理者的现任官员。特别是后者,其所奏之措施大都已付诸实施,成为专门适用于海南黎族地区的专门法。如杨理在《上欧阳郡守四事》中针对黎族结怨仇杀之习惯,建议“如有冤枉,即为伸理;如有混包霸占他人村峒诡避差役者改正,无令群奸欺诳”。②参将俞大猷图说:“其各州县印官,务将管下黎人严禁,童女不得如前涅面纹身,男人务着衣衫,不得如前赤身露腿;其首各要加帽,不得如前簪髻倒颠。各村黎童之幼小者,设社学以教之,使其能言识字。每一年之间,守巡官查考各州县官变化各熟黎几村,招抚过生黎为熟者几村,具呈抚按衙门以为殿最。”③如果说上书奏议还只停留在建议层面,那么,基层政府衙门的所颁发张贴的告示,则是十分具体的在民身边的行为规范,如崖州协镇府、崖州正堂、都关府联合颁发的《除积弊安黎示二则》、《悬赏严拿黎匪谕》、《立章训黎示二则》、《饬汛弁传集各峒黎目受抚札》、《劝释黎民械斗示二则》、《严禁汉奸抢夺黎物抵债示》等告示,对黎民行为的约束规范作用十分明确具体,且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据不完全统计,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刻本的《广东琼州汉黎舆情营伍练兵稿抄》中,类似的具有约束力的告示就有二十一条之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朝廷官员关于海南黎族的治理的奏疏,还是基层政府为管理而颁发的告示,从形式上看,更似治理措施或政策,而非出自中央权威的法律。但是,正是这些治理政策或措施,规范约束了黎民的行为和思想,纠正了黎族陋俗,限制了土官对黎民的滋扰、欺诈与剥削,防范了汉人对黎民的欺骗与侵害,达到了维护黎区治安和发展黎区经济的目的。而且这些措施与政策是由权力机关颁发,多有相应的处罚与奖赏,其权威性、拘束性、指导性十分明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管理法规。
清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冯子材剿定黎乱后,与之拟定《抚黎章程十二条》,并上书光绪皇帝。为了对黎区实行有效治理,冯子材在海南着手实施《抚黎章程十二条》。该《抚黎章程十二条》是为被剿平之黎区进行善后管理的专门抚黎政策,虽然如开路等经济措施未及实施,但在黎人的文化教育与旧习改革方面得到了落实并取得了明显效果。《抚黎章程十二条》虽然不是专门的地方法规,却发挥了地方法规的作用,其实乃黎族地区专门法的典型代表。
禁示碑。如果说黎区专门法尚带有黎族治理的政策措施或建议性质,那么,黎族地方官府刻立的禁示碑则是典型的地方性规范。因为禁示碑是根据黎族地区经常发生的纠纷而刻立的,通过禁示碑的警示功能,达到防止该类纠纷或冲突的再次发生。上文中关于禁示碑已有例举,此处现举一例以说明之。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立,“奉宪永禁扰索示碑”,佚名抄刻。碑文记叙从清嘉庆年间到道光年初,再到道光十四年,官员民丁对当地黎人百姓敲诈勒索越来越严重,多次激起民变,为了调和民族矛盾,加强清政府的统治,特立此碑,严禁地方官员与兵丁扰民,革除弊端、安抚黎人百姓要安心守法。碑文还注明该碑是由官方、多港刘峒长、德霞、抱由及众村总管、哨官、头家、村老等同立,意在禁止文武衙门一切扰黎陋规,以安黎人民众。①有些禁示碑虽然由黎民自行刻立,但基本上都是经过官府认同,仍具有地方立法性质。如:
凭示勒碑[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署昌化县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凌为准自行投纳事,今于抱上都摘出水头村、坡威村、居索村、居新村、落洒村、哥霸村黎粮一十六户,共应纳地丁征银九两,大钱五分四厘正,遇闰每两加银四分六厘五毫,准该黎户符那横等,每年限定三月初十日着落哨官游马传符养外兴老大、老二、万方等六名自行来县投纳清楚,以免粮差下村加征,滋扰黎户。每两定折收纳铜钱二千三百二十文算,共应折铜钱二十乙千四百三十二文,该黎户不得违误,过限致干并究,特示。
符登葵代[请峒长绅士林开甲进官讨示]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吉日众黎户建立。①
3.习惯法
在黎族传统社会里,指导村峒部落成员行为的主要是习惯、习俗。这些习惯习俗是黎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婚姻家庭和经济关系中逐渐形成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中央政权对黎族地区实行管辖,国家法在黎区生效后,那些与国家法不相冲突的习惯习俗被中央政权所确认或认可,赋予国家强制力,成为习惯法,对黎族群众继续发挥着规范调整作用。黎族习惯法内容广泛,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的还与宗教规范、道德规范难以区分。总体来说,黎族习惯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禁星。作为一项原始的习惯法规则,黎族的插星在上一章中已有具体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此处需要强调的是,由于黎族没有文字,对于民间出示广告、启事、禁令、订契之类,都使用插星的符号来表示。每逢生小孩、猪下崽、家中有人生病或播种、酿酒时,黎人都在自家门口挂树叶,禁止外人进屋。除宗教性质外,插星仍然主要用于财产占有、停止侵害等财产所有权和民事交往方面,大到山地、鱼塘、果木,小到茅草、蜂窝,即使是一时不能利用,黎民如果意欲占有,便用插棍结草或划“×”型符号等形式,做上记号以保护下来,表示此物已有主人了。具有告示和警示功能的插星,在中央政权对黎区实行有效统治时期,仍然是黎族人人都需自觉遵守的习惯,如违反了,违者不仅将被众人谴责为不道义,将来有困难时得不到众人的帮助,而且还可能被认定为盗窃罪,受到同胞的追究和官府的制裁。
(2)刻木为契。刻木为契是初民社会应用比较广泛的交易立信方式,黎族没有文字,深居深山,日常交易,以物换物,各得所需。但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田、地、牲畜可以买卖抵押时始出现刻契交易。“山地的批租,银钱的借贷,往来货物的订购,承揽其彼此的契约,都以竹箭代之。其法以竹管一段,用刀刻纹标志记号。刻毕了后,自竹管正中破分为二,彼此例如执,以为凭据。”①在《黎族三峒调查》中称这种记录借贷的借据或票据为“对牌”②。依据该刻契,无论过了多久,子孙都可持契据前来讨债,如果借方偿还了部分,则双方都要将契据的相应部分切掉,债务全部还清后,则双方都废弃契据。契据的制作要在长老的监督下进行,大家一起喝酒。与刻木为契相类似,反映黎族人民在民事交往中记事、守信的做法还有结绳记事和砍箭为信。③
刻木为契不仅在黎族民间交往中盛行,而且还被官府所认可,用来处理政府与黎民的关系。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参将何斌臣会同知州曾邦泰,差官兼里排,招抚儋州黎岐、恶来、催顶等八十村,刻箭承认粮税编册”。④这是黎族刻木为契的具体体现,官员与黎民一起刻箭确定粮税编册,这不仅说明中央政权承认了黎族刻木为契的习惯规则,而且还将其适用到社会管理中来。
(3)峒组织习惯法。直到1949年前,峒仍然是黎族地区县以下的主要基层组织,虽然峒是“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但该地域内的居民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峒内各血缘集团还保留着各自的公共墓地和共同的祖先崇拜。正是基于这种血缘上的联系,峒组织内部有为峒内成员共同自觉遵守的习惯、习俗。这种习惯习俗在自然法秩序时即已存在,在中央权威的统一管理下,峒组织习惯得到了国家政权的确认与维护,成为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习惯法。峒组织习惯法不同于禁忌的意识控制,它是黎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世代相传的一种行为准则。峒组织习惯法包括:
对峒疆界和财产的保卫责任。黎族每个峒都有固定的地域,峒与峒之间一般以山川河流为界,当一峒通过插星宣布自己的区域范围以后,其他峒则不得侵犯,也不得越界活动。峒辖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峒管辖的土地、山林、河流等属于全峒人共同所有,未经许可外人不能越界砍山、开荒、采摘、伐木、打猎、捕鱼和居住。若需越界须经本峒许可,还要上缴一定数量的物产给峒长,上缴多少视行为和内容而定。打猎、捕鱼需上缴猎肉和鱼,砍山开荒、居住,则需上缴猪、牛等物品。峒内成员有保卫本峒疆界和共同财产的责任,当外人侵犯了本峒利益而发生械斗时,全峒人都要参加战斗,共同负担战斗所需费用。
峒内成员相互援助和保护的义务。峒内成员不仅要保护峒的公共利益与疆界,而且彼此之间还要相互援助和相互保护,全峒人也有保护峒内成员的私有财产不受他人侵害的责任。特别是本峒人受到外峒人欺侮时,必须帮助他复仇。
械斗是解决峒村矛盾的主要手段,参加械斗、共同负担械斗时向外请援兵的费用,则因此成为黎族人民为峒村利益而必须承担的责任。
响应信传召唤的义务。黎族人民居住在山区,峒内各村都有一定的距离,每个村人口比较少,耕地也比较分散,因此,在需要结集村民或峒内黎民时,黎族人民有几种传统的传信方式。一是击鼓传约,“头家或族长家内,常备有大鼓一面,有事时击以为号。或遇盗,或办公差,或议事,击法不同,村人则闻而知之。鼓声响处,村人毕集听命”。①即在村长家门口悬挂一面独木大皮鼓,每当村里有急事需通知大家时,村长便击鼓传约,村民根据鼓点的节奏、轻重缓急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如果是械斗村民会很快拿武器到村长家集合待命。二是鸣枪传约,主要用于人死亡时的通知,当村里有人死亡时,几把猎枪同时朝天鸣放,附近村峒的人就知道那个村子有人死亡了,有亲戚关系的人就会去奔丧。三是断箭传信,即用斩断的箭头去联络各村寨(各地区)的群众,主要用于黎族人民起义时或起义过程中的联络,或受到外敌入侵时向异地村寨求援,受箭的村峒村民依约到指定地点集合,及时前往支援受侵的村寨抵制外侵。①四是鸡毛信,即用一根雄鸡毛加一对辣椒送给友方,友方就知道对方有战事,会快速击鼓鸣锣集合去支援对方。
虽然上述几种传信方式较之今天十分原始,在黎族地区却是普遍适用、十分有号召力和强制力的通知或通告方式。为了村峒的集体利益或村峒成员利益,积极响应信传,及时救援,是黎族内部严格的族规之一,是黎族人民必须遵守的公共秩序。清张庆长的《黎岐纪闻》就记载了这一传信规则:“遇有事,峒长黎练以竹箭传唤,无不至者,其信而畏法如此。”“头目有事传呼,截竹缚藤,以次相传,谓之传箭,群黎见而趋赴,若奉符信,无敢后者。”②击鼓传约、断箭传信,黎民对之的认同与遵守,犹如禁忌中对神灵鬼符的信仰,十分虔诚与自觉,究其原因,一是来自黎族人民朴素的族群意识,二是来自峒长黎头的权威。
(4)神明裁判。神明裁判是原始宗教的产物。当人们对某事物缺乏识别能力和不能以确凿证据判断某事物解决争端时,就通过神明的指点,来判断事情真伪并给予嫌疑人以处罚。海南黎族如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也用神明裁判来维护族内社会秩序的稳定。海南黎族的神明裁判主要是鬼神判和雷公判,这与海南黎族原始时期对鬼神、雷公的崇拜是密切相关的。
神鬼判主要用于对通奸、盗窃等行为的裁定。对通奸的审判主要采用火判,如果丈夫怀疑妻子与人通奸,但又没有抓住把柄时,就采用令妻子踩过燃烧的木炭或火灰,眼睛是否变瞎来判断是非。③眼睛变瞎,在当时的黎族社会,意味着丧失劳动能力,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让其眼睛变瞎,是鬼神对犯事者十分严重的处罚。雷神判主要用于盗窃时的审判。如某个人的财物被盗窃,但又没有抓住盗贼,只是怀疑某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被偷的一方还是被怀疑的一方,都可以以理亏遭雷劈的誓言或咒语,来证明自己的判断或清白。人们相信,雷公会劈死做亏心事的人。①神鬼判、雷神判是黎族维护和执行本民族习惯法的一种辅助而又具有强大威慑力的手段。黎族人民信仰原始宗教和巫术,十分相信神鬼判的效应,因为对鬼神的禁忌而产生了心理约束力,因此,神鬼判、雷神判这种神明裁判本身也成为黎族习惯法的一种,是一种解决纠纷的习惯法。神明裁判的结果不仅对当事人双方产生约束力,对其他人也产生心理畏惧和行为约束的警示效果。
(5)血族复仇。在汉人眼里,黎人善射好斗,积世之仇,也要记报,对此,古代文献多有记载:“重报仇,有杀其父祖及乡人者,易世必复。”②
《海槎余录》:“黎人善射好斗,积世之仇必报,每会聚亲朋,各席地而坐,饮酣,顾梁上弓矢,遂奋报仇之志,而众论称焉。其弓矢盖其祖先有几次斗败之耻,则尅箭几次,射于梁上以记之。”③《琼州海黎图·械斗图》:“黎性重仇杀,轻生死,与滇黔苗倮同,挟器惟标枪弓矢,健者则衣著吉贝,头缠红布,乘牛驰骋,以示夸耀云。”《黎岐纪闻》:“一语不合,辄持弓矢标枪相向,势不可挡,有妇人从中间之,即立解。”④中共广东省委1928年4月26日在琼字第二号《致琼崖特委信》中也说:“黎民运动在琼崖暴动愈加发展而愈严重,他们头脑简单,且贪鄙好斗,据C.Y.报告上说很易受酋长之骗。”保亭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张应勇在《奇特的骨片——黎族氏族恩仇报答标志实录》一文中记录了什聘村人恩仇必报的故事,展示了黎族的民族性格特点。他认为,这件事情很有民俗价值和历史意义。他说,什聘人对于家族的恩仇信息采取刻骨铭记的方式世世代代进行传递,记仇是在动物骨片上刻一只箭头,记恩是在动物骨片上刻一片榕树的叶子。
三 国家法与黎族习惯法共构的法律秩序
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权威下,中央统一法律、地方规章制度与黎族习惯法分工协助,各司其职,共同构建了黎区的法律秩序。
一般说来,在调整范围上,中央统一制定的法律以及基层地方政府制定的管理规章主要适用于涉及国家统一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的领域,地方政府的建置及官员的任免、考核,总管、哨长等土官的任命与授权,国家税赋徭役的征收与分派,暴乱、械斗抢劫、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黎族习惯法则主要调整黎族人民的婚姻家庭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事宜,如结婚仪式、离婚调停、土地买卖、财产转让、祭祀驱鬼、偷盗等。在主体方面,与中央政权相适应,地方政府衙门既是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他们代表国家来适用法律,但在具体事务上,多由中央政府任命的黎族土官来负责,峒长、哨官、头家负责案件裁决,“凡小事听哨官处断,大事则报诸总管,总管不能处断,始出而控告州县”。①土官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多依黎族习惯法处断。如偷窃,如果偷窃的是合亩内的共有财产,偷窃者则会被抓送到总管、团董或乡长那里去判处,一般是加两三倍的罚款,一份给失主,另两份作为合亩内的公共财产,另偷窃者还需拿出米酒宰牛宴请。如果偷窃私人物品,则处罚方法同上,但不另加罚给失者的家族。如果惯偷屡教不改,则可以判处杀死,如果被偷的是黎族土官,则偷窃者会被他们杀死。②
总体说来,在中央统一权威下,黎族社会虽然直接由国家法律来统一调整,但是,受国家法律影响较大的是基层政治组织及其官员。对普通的黎族民众来说,本民族的传统习惯才是他们需要自觉遵行的规范。氏族长老在生产生活中传承了习惯法,黎族土官将传统习惯法与中央法律有机结合起来的,使习惯法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有了更高的权威。如果说国家法是外部规范,习惯法是内部法的话,那么,自宋以后,由外部规范和内部习惯法组成的法律体系,十分有效地构建了黎族社会所特有的法律秩序,保障和推动了黎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第三节 土官制度及其传统权威的变化
土官制度是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土官,就是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居住区封赐的能独霸一方的世袭统治者或官员。土官制度是在唐羁縻州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中央政府认命民族首领为世袭官员,统治其所在的少数民族。清雍正年间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终结了土官在本区域的独霸地位,加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与实际控制。
一 土官制度的基本情况
北宋开宝年间“初平岭南”后,“命太子中允周仁浚知琼州”,同时也确立了“因其俗治之”的管理政策。在被征服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招抚黎族头人归降,并对归附之峒首授官封爵,正式拉开了海南黎族土官制度的序幕,以黎族峒首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土官制度逐渐发展为定制。封建王朝在海南黎族地区实行的土官制度,对黎族社会传统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将黎族传统习惯上升为国家确认的习惯法的过程中,土官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虽然自宋代开始,中央政权就注重对海南黎族地区实行统一管理,但其羁縻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海南黎族地区的土官制度,在宋代多为虚职,且品级低下,如:宣人,为县君之封,承信郎、承节郎、进义校尉等均为品级低下的散官衔。元代土官乃始为实职且拥有实权,官职品级也高,最高至正三品。元世祖至元二十八至三十一年(1291~1294年),海南岛统治当局对黎族人民进行大规模军事镇压,连续用兵3年,得峒600、户口23827户,之后,设立“黎兵万户府”和“屯田万户府”,黎兵屯田万户府与黎峒千百户的头目皆为黎族酋领担任,世袭为之,管辖当地军事和民政,官给土、牛、种、农器,免其差徭。黎族土官势力的壮大,使“以黎治黎”政策得到了有力的推行,中央政府在黎区的统治势力也因此得到了较大的加强。
明代的黎族土官制度发展得相当成熟,达到其鼎盛时期。明代初年州县官不用土人,废除元朝所设黎兵万户府,曾有一部分黎族土官不愿出官附籍,甚至据峒抵抗和反叛。于是明朝便加强军事统治,在海南设军事卫、所,立屯田22处,每一处有田20顷以上,实行兵农合一。洪武五年(1372年)设1卫、1 1千户所、额设旗军15927名,马160匹。又在交通要道与通往黎区的路上设巡检司22处,从黎人中点签弓兵450名。另从民户(汉族为主)中抽选“机兵”(又称“机快”),民户30丁选“机兵”1名,共约2195名。
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黎族地区实行“土官、土舍”制度,授以黎族峒首各种土官职衔。永乐二年(1404年)琼州府文昌县林彬招抚黎峒30余村,被授土官典史,可世袭;崖州监生潘隆自愿请求招黎归顺,被授予知县职名。有明一代,黎族地区的土官制度共有两种模式。
1.“土舍、土官”制度
明代从永乐年间起,在海南建立土舍制度,这是在卫所之下设立的地方武装,有土舍41所,辖黎兵2704名(后有变动)。土舍是由当地有势力的黎族峒首担任,专管黎兵。黎兵叫做“峒丁”,遇有调发随军出征,平常则派守各营地。但后来土舍的权力膨胀,土舍恃其掌握的黎兵武装,与州县官勾结,包揽征税和诉讼,鱼肉黎民,“征徭任其科算尽入私囊”,操纵了黎区基层实权。明朝还实行了“以峒管黎”的办法,凡遇公差、纳秋粮,有司俱凭峒首催办,官军征捕,亦凭峒首指引。永乐年间曾招谕许多黎族峒首“赴朝受职”,根据他们招抚“生黎”的户口数,明朝分别授给州同知、知县、县丞、主簿、巡检等土官。土官实行朝贡制度化,每三年峒首必须向朝廷进贡一次,以示对朝廷的忠诚。土官管政,土舍管军,军政分离,明朝的黎族土官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设立土官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归顺的“生黎”就有1670峒,3万余户。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琼州府又设置“抚黎”通判,专管黎事。但至明代后期,由于人民不断反抗土舍、土官的横征暴敛,以及“扶黎诸官夺州县权”等弊端,遂于正统五年(1440年)后相继革除土官制及“抚黎”流官,又逐渐限制土舍行令,更换土舍为粮长,对其所管黎人纳入编户,划归“甲首”管辖。
2.“黎都黎图”制度
这是熟黎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明朝将归附已久,所谓“熟黎”的黎峒统一编入行政区划,即在基层设“黎图”,若干个“黎图”为“黎都”,若干个“黎都”为一乡,乡为流官隶属州县。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使“熟黎”与编户的汉人一样编入都、图,载进鱼鳞册、黄册,要纳粮录差。综合地方文献,海南岛“熟黎”被编入黎都黎图者凡28都、75图,包括155峒,它们以岛的北部与沿海地带居多,岛的南部及山区较少。如琼山县有5都9图,包括9峒;澄迈县有5都60图,包括137个村峒;定安县有3都4图,包括7个峒;陵水县不设都,有2图;儋县有5都,不设图,“黎居良民五分之一”;感恩黎“附版籍者什九,不附者什一”;唯南部“崖州黎其地多于州境,其人十倍之”。至明末清初的发展趋势则是,“则古之书村峒者,今皆为都为图矣”。黎都黎图制的推广,促进了“熟黎”封建化的完成,使“黎地渐归豪民,黎人归化最久,与齐民等”。特别是在岛的北部与东部,如定安、会同建制以来,黎峒大都入籍,琼山县南歧峒等黎、文昌县斩脚峒等黎,悉输赋听役,与“省地”百姓无异。①
清朝沿袭明朝的行政建置,琼州府下辖3州、10县,除文昌、会同2县之外,其余8县皆有黎族人。“清王朝在沿袭明代黎族土官制基础上,进一步削弱了黎族土官的权力,州、县一级官府已不设黎族土官的职位。清代建立的黎族土官制,主要是在黎族峒的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峒’下设峒首、黎总、哨管等职,‘村’则设黎甲或黎首,黎族土官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所属村峒的日常事务,和遇黎人造反时,承担协助清军作战与招降之责。”②雍正九年(1731年)起,便在黎族地区推行“总管”制度,即在州县之下各黎峒上层首领被委为“总管”(辖一峒或数峒)、“哨官”(辖一村或数村)、“头家”(每村一名)等土官。有的地区(如陵水、保亭)称村峒为“弓”,每五“弓”设一“总管”。各峒还有“峒长”(亦称“总头”),是从氏族的“奥雅”(长老)中产生的,“峒长”协助总管处理行政事务,总管因事外出峒长可代理其职务。总管与哨官皆是世袭的,但要报封建官府委派,赐以印牌及官服。“凡小事听哨官处断,大事则报总管,总管不能处始出报告州县。”③如在黎族众多的崖州分东西两界,东路黎族村峒独多,广袤300余里,向设总管6人、哨官13人、峒长6人进行管理;西路村峒纵横200余里,向设峒长6人,总管3人。
而在“熟黎”与汉族杂居区,则将“黎都黎图制”逐步改为“里甲制”。如澄迈县虽有黎都之名而无黎人之实。据统计,自明嘉靖到清道光不到三百年时间里黎村峒减少了30%,清代统治力量深入到黎族大部分地区。
民国初年,海南岛的行政建置仍沿袭清制,置琼崖道,共辖13县。民国十年(1921年)废道制,由粤军旅长兼领琼崖善后处处长,掌军民两政。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广东省政府辖下设琼崖行政委员会,并从琼山县划出海口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抚黎局”为“抚黎专员公署”,并改“总管”为“团董”,加强对黎族地区的统治。接着又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黎、苗聚居的五指山区新设白沙、保亭、乐东县,推行乡、保、甲长制,至此,基层官员已完全纳入中央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中,土官之概念逐渐模糊淡化。
海瑞《上兵部条议七事》第七条称:“黎岐归化,当编其峒首村首为里长,所属之黎为甲首,出入不许仍持弓矢,原耕田地听从其便。其山林可开垦者并绝黎田地,宜招方外无业民耕作,结为里社,与黎岐错居。”
参将黎国耀《条议二事》建议道:“一编保甲。琼州等县原设有牌门乡盟兵,择其豪者为乡勇、哨官或保长以领之。村落大至百余人,小亦不下数十人,闻警息即听有司调集,协同营兵防御,以故寇多不敢犯。近因宦家买置庄田,名曰‘宦庄’,一切佃丁、乡盟人等概获优免,既有警叫调不应。甚者又有豪奴悍佃,窝匿逃亡奸盗,莫可究诘。而各宦庄亦瓜分,势寡不能自卫,遂至束手无措。顷者定安光螺岭上下之事可鉴已。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今督抚令抚黎官亲履各地方,核其户口,稽其生业,无论势宦,一概佃丁、厮役、乡邻,尽籍其壮者为兵。其中有行能者佥为乡勇、哨官,次为保长,分领其众。除农隙讲武外,无事不许辄行差遣。遇有黎岐出没,集众防守,悉听有司营官调发。”①
二 土官权威的变化
峒的组织是黎族社会独具特色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封建王朝中央政权统治之前,它是维持黎族社会内部正常秩序和推动黎族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自治组织,其峒首是黎之头领,“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大抵父死子代,世世相传,或间有无子而妻代之及弟代之者,为众心所归而公立之也。”①熟黎,“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今仅择豪强者充之”。②村头、黎首乃由原始血缘氏族长老演变而来。原始血缘氏族的长老,通常都是本氏族辈分最高、经验最丰富、威望最高的人。他们能说会道,办事能力强,有威信,明事理,讲公道。在黎族社会,这些人通常都是老人,被称为奥雅。鉴于他们的权威与能力,以及氏族成员的血缘关系,黎族长老们被推选为本村峒的管理者或头人。
中央政府在黎区实行土官制以后,过去村峒的黎首被任命为朝廷命官,成为地方的一级行政官吏。基于其原本的黎头身份,这些土官仍拥有在本村本峒的权威和势力,成为兼具黎头和基层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和职能。后一种身份对他们来说,更具吸引力,渐渐地完全成为中央政府在黎区的行政管理者、法律政策的执行者、地方治安的维护者、赋役税收的征办者。
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法秩序之下,黎族土官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身份变化。由原来村峒内部的选举形成和世袭,变成了由中央政府委任与授权,成为政府官员,代表中央政府管理黎族地区,为政府办事,土官开始步入封建统治集团的行列。其次是权力来源的变化。虽然是由黎头演变而来,但其权力来源却已不再是基于氏族长老权威,或是氏族成员的推举,而是中央政府的授予,其背后是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与保障。再次是,权力范围扩大。虽然宋时黎族土官仅仅是个虚职,但其所拥有的官职与官衔,已足以让其在黎族百姓中拥有更大的权威。元朝的黎族土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权威已发展到顶峰。明朝虽将土官的军权与政权拆分,但并未影响到土官所拥有的统治权。有了政权或军权,成为封建政府在册官员,土官较之原本的纯粹黎族头人,其权力范围得到了极大地扩张。最后权力变化产生了人格变化。在取得中央政府授予的权力以后,黎族土官逐渐脱离了原本平等的黎族血缘团体,开始享受各种特权,依据自身在黎区的威信和手中的政府权力,开始豪夺巧取黎民财物,强行占有村峒的共有土地、山林,成为剥削阶级,盘剥百姓,欺骗国家。正是由于土官身份能带来好处,招来了一些汉人冒充黎头充任土官,如《道光琼州府志》记载:崖州东西二路黎村,“熟黎向归里长管辖,生黎及生熟各半黎旧设有峒长、哨官等名,由黎人自行保充。后有不肖绅民假名混保,快其所私,以致黎众不服,因而滋事,今已革除”。①
部分黎族土官在黎族地区的欺上瞒下、挟乱自重,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引起黎族人民反抗,因此,至清末土官制度逐渐被削弱,有的甚至被革除。如崖州东黎境内,过去共设有峒长、总管各六人,哨长十三人,到光绪年间,则只剩下总管之职,而且还没有定额,各村则由自己设立头目一人。实行保甲以后,黎族土官制完全被保甲制所取代,黎头之身份在保甲制之下不再得以体现或享有特权。
黎族土官及其权威的变化,究其原因,一是中央权威在黎族地区发生了效力,中央政权的进入,统一法律秩序的建立,打破了黎族传统的血缘氏族结构,直接导致了黎族社会的分化;二是黎人思想变化的结果,在与汉人相处后,黎族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汉族官员所享有的特权与待遇,令黎族土官向往与羡慕;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黎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与外界民商事交往的频繁,黎族人民的财产私有观念得以加强,随之而来的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黎族土官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仗势敛财乃成为必然。当然在这些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中央政权的进入,导致了黎族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央政府发展经济的举措,导致了黎族土官财富观念的变化,中央政府将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输入与推广,引起了黎族人民思想的变化。
第四节 习惯法秩序的变化与传承
随着中央政权进入海南黎族地区以及统一法律秩序的建立,黎族人民在固守自己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的同时,也享受着外面世界的新鲜气息。学习接受中原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学习汉语,接受中原文化教育,在与汉族人民的接触交往过程中,思想认识、文化水平、经济观念、文明意识等等,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他们改变了自己,改变了千年固守的习惯习俗。在黎族习惯法秩序方面,不论是婚姻家庭、民事交往,还是血缘族内的公共秩序与规则,都在传承中有所提高与改进。
一 婚姻家庭习惯法秩序的变化
(一)婚姻
婚姻是维持人类自身繁衍的一种手段,也是一定社会秩序的体现。丰富多彩的婚恋习俗能够集中展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同时,这些习俗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根据对古籍资料和20世纪前叶社会调查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宋以后,黎族实行的仍然是嫁娶婚,且为氏族外婚,其婚姻成立的过程与方式仍与古代保持一致。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观念的增强,黎族人民与汉民族交往的增多,黎族的婚姻习惯法秩序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婚姻成立的整个过程中。
1.恋爱方式
对歌、“玩隆闺”是黎族传统的恋爱方式,这种自由恋爱方式到了近代,依然盛行,现今黎族传统的节日“三月三”①与对歌不无联系。据史料对黎族青年男女春夏之交聚会的记载,可以推测这是对“三月三”节日的描写。如《民国儋县志》记载:“春则秋千会,邻峒男女妆饰来游,携手并肩,欢歌互答,名曰‘作剧’。有乘时为合婚者,父母率从无禁。”②可见,这一时期黎族男女通过这一大型的集会恋爱是很普遍的,而且从集会的时间上来推测,这些大型的集会便是黎族的传统节日“三月三”。
黎族传统的通过“隆闺”恋爱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依然存在。《海南岛志》记载:“一般女子年纪长大,父母必为之别营居室,听其自由交际。男子之未娶者,入夜辄出游于此类之女子私室中。”③《海南岛新志》记载:“女子及笄,即自由营私室,以与男子交际,待情投意合时,经父母同意,即可结婚。”①而且,在“隆闺”中谈恋爱的不仅是单身女子,已经订婚的女子和结婚未落夫家的女子也有自由在“隆闺”中恋爱。《海南岛志》记载:“其既与人结婚而返居私室之女子,常易与他男子发生恋爱。”②
除对歌与玩“隆闺”外,通过媒人的说合而建立恋爱关系也逐渐增多起来,许多青年男女通过媒人说合后建立了恋爱关系。俗话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说媒是传统婚姻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行为,即男女双方一般都要经人从中说合,才能成为比翼鸟,结为连理枝。这种方式叫“说媒”。这在史料中也有记载:“西部如崖、昌、感、儋、临等县,女子10岁前,凭媒说合,男家备具酒肉、月饼送女家,谓之‘讨真命’。”③“父母常常按汉族的风俗经媒人介绍将女儿嫁给汉族。”④《海南岛志》记载:“黎人婚俗,多取自由择配;亦有凭媒说合者。”⑤在父母托人说媒的婚姻中,偶也传出包办的声音,如黎族传统民歌《叫我怎么办》:“命运真惨,婚姻母包办,红颜配白发,叫我怎么办!”⑥
2.订婚与结婚
古代黎族就有订婚的习俗,女方同意结亲后,男方即选定吉日订婚。订婚要有一定的信物为凭。订婚信物通常有两类:
一是以“箭”为订婚的信物。如《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中提道:“婚姻折箭为定。”⑦《康熙广东通志·琼州府》:“定婚折箭。”⑧在黎族的传统民歌中也有“定婚折箭”的记述,如《我求了又求》:“(男方)亲家母(呀),如果我早认识你家姑娘,亲家母(呀),那我早就带箭来,到你家屋梁下。亲家母(呀),那我早(呀)就整装来到你家楼梯旁。我十天求了又求,我求好像是盼望了六年等稻谷进仓。亲家母(呀),你千万别让我失望。”①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古代黎族有“定婚折箭”的习俗。
二是以“槟榔”。槟榔为订婚中不可缺少的聘礼。这在黎族传统民歌中有记载,如《同吃槟榔来订婚》:“一口槟榔分两份,同吃槟榔来订婚,劝妹要学槟榔树,从头到尾一条心。”②黎族有句俗语:“一口槟榔大如天。”如果女方吃了男方送来的槟榔,就证明女子同意了这门亲事。据《光绪崖州志》记载,黎族订婚时:“俗重槟榔。宾至,必先以敬主,主亦出以礼宾。婚礼纳采,用锡盒盛槟榔,送至女家。尊者先开盒,即为定礼,谓之出槟榔。凡女受聘者,谓之吃某氏槟榔。此俗,琼郡略同,延及闽广,非独崖也。”③
不论是订婚还是结婚,男方都要给女方家一定的聘礼。古代黎族一般以牛、槟榔、吉贝、黎布等作为聘礼。这在黎族的资料中有所记载:“以牛马多寡为婚礼厚薄。”④《琼州志》记载:“男女相悦后,男随托媒持绒线至女门,女亲受之,谓之结绳。又以槟榔、耕牛、吉贝、黎布等聘之。”⑤民国时期,聘礼有所改变,增加了聘金、酒、米等。“一头猪,一缸酒和一只鸡。女子的父母接受这些礼物,便算正式订婚。”⑥再如《海南岛新志》记载:“结婚聘金,以牛、酒为之。”⑦《民国感恩县志》记载:“迎婚聘礼,取生牛两头、猪肉六十斤、米二石、酒一缸。”⑧聘礼的品种向实用化转变。
除了一如既往的以实物为聘礼外,货币开始成为聘礼的一种,据《光绪崖州志》记载:“纳币,书男女命于笺,赍金币礼物,送至女家,谓之押命”。①当男方家不能提供牛这个聘礼时,可以将牛折算成光洋缴交。②
在婚礼仪式方面,古时,据史料记载黎族的婚礼仪式基本上包括:“送礼、送亲、伴眠、屋造、同居。”③“吉日,男家送绣花桶为礼,女家亲戚凡年幼未婚者竞送钗带等物,亲送女至夫家,夫家幼女小儿伴新妇眠二十余日,俟造屋毕,斯成亲同居焉。”④到了近代这些仪式基本保持但稍有变化。
据《光绪崖州志》记载黎族结婚时:“女家有婚嫁事,东里则聚内外眷属,艳妆往贺。女家饰其女,奉槟榔出见。各赍首饰金银为彩,谓之出新妇。西里无之。择吉请期,送聘礼,谓之送日子。冠不三加,娶必亲迎。入门谒祖,谓之拜堂。次日拜谒尊嫜,谓之出拜。三日女婿旋车,谓之回门。大抵礼俗,东西相去不远。惟近日富家竞斗奢靡,贫者每援为例,亦有终身不能娶者。”⑤
民国时期黎族一些地区的婚礼仪式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包括:送亲、迎亲、摆宴席、对歌、逗娘、回门。
送亲。《琼崖志略》记载:“举行婚礼时,九代亲属男女各持牛猪鸡酒前来庆贺,女家亦遣陪嫁者数十人送新妇过门。”⑥
在结婚条件方面,黎族仍然保持了各种婚姻禁忌,禁忌血缘婚,婚姻在不同的氏族间和不同的方言间缔结。根据《黎族三峒调查》显示,黎族“重合老村村民的范围,大多局限于本村本峒之内,与盆地外同一方言的人通婚非常少”。⑦这说明黎族人的通婚范围实际上很小,通婚对于同一方言间黎人的意义不大,却对加强村落的凝聚力十分有利。另外不同方言间不得通婚的禁忌偶也有被打破的现现象存在,这从《黎族三峒调查》第25页注释2中可以看出。
一夫一妻制是黎族自始以来实行的婚姻制度,并且也切实遵守了这个习惯法秩序。但是近代以来,黎族社会中出现了纳妾现象。根据《黎族社会调查》上下两册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黎族中很多乡村在新中国成立前有纳妾现象的出现,纳妾者大部分限于村长及其他一些有钱有势者。同时有的是因年老无子而纳妾,有的已有儿子,但因家庭缺乏劳动力经妻子同意,并由妻子去征求某女子愿做妾的。新中国成立前,还有有钱有势的人,抢夺穷人的女子做妾的。《黎族三峒调查》中也谈到了黎族的纳妾现象:“在黎族中,纳妾者虽然数量极少但却是存在的,这或许是受了汉族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只限于村长及其他有钱有势者。在本次调查的调查地,龙眼村的村长便纳了妾。”①
实际上,原始黎族社会是不存在纳妾制度的,它是随着汉民族文化的逐步传播而得以形成的。可以说,黎族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最终形成是封建制文化的结果。
3.婚姻关系
新媳妇在结婚后两三天内即回娘家,住在原来的隆闺里,过着与婚前一样的单身生活,这种“不落夫家”的婚姻现象到了近代仍然存在,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婚后即回夫家常住。陈铭枢在《海南岛志》中详细记述了近代黎族婚姻关系的微妙变化:“结婚后在男家宿一宵仍回私室,迨生育后始回男家;或从定婚直至生儿后始回男家者亦有之。近来此风稍变,婚后即回夫家长住矣。结婚前,由男家送牛酒食物至妇家设宴。宴后,女子步行至男家,或由新郎邀朋友数人至女家接带,亦有由女家择伶俐妇女数人送新娘至男家者。女家富而男家贫者,男或先在女家做工,至若干年月,由女家赠送牛只、田地,使之成家。亦有先同居数年,待有积钱再举行婚礼者。其既与人结婚而返居私室之女子,常易与他男子发生恋爱。然其事若为其夫所闻,则往往持刀枪寻仇斗杀。青年男女以此伤其生者,不可胜计。故有此种既婚女子私室之村,夜必闭户,盖虑因女室酿祸而波及也。女在私室生儿后,抱归男家。所生之儿未必即为本夫所出,例不之责,惟此类之儿多不得为家主,如无第二儿则属例外。女子居私室时,其动止甚自由,迨既入夫家,则一切惟夫所命。黎俗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制裁极严厉。女子既嫁,不喜落家,此殆其一因也。”①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黎族婚姻关系的几点变化。一是夫妻之间的忠贞在近代得到了黎族夫妻的重视,不落夫家的女子性自由习惯因此受到了挑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发生,女子婚后宁愿选择落入夫家居住;二是财产在婚姻缔结中的地位提高了,男家如果贫穷,不能举行婚礼,则可以先同居待有钱后再举行结婚仪式,如男家不能为新婚夫妻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则男方需要为女方家提供一定期间的劳役,然后由女方家提供牛只、田地;三是开始重视子女血缘的纯正,虽然女子婚后生育的第一个儿子仍能被夫家接受,但是该子的家庭地位受到了限制,他不能成为未来的家主。很显然,黎族婚姻关系的这些变化,使得黎族的婚姻越来越与汉族接近,其婚姻受汉族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4.离婚
黎族人在离婚方面,没有太多的要求与限制。黎族长期坚持离婚自由原则即协议离婚的自由,夫妻感情不和,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离婚的要求,并且所有的合乎情理的离婚要求,都会得到众人的理解和社会的支持。
男女双方若协议提出解除夫妻关系,一般要经过如下过程:“首先各自要向父母报告,然后由男家请来村中有威信的奥雅(即老人)主持离婚仪式。男家杀猪摆酒,男女两家亲属代表各一边就座,并请村里乡亲参加。在奥雅主持下,申明离婚的理由,双方父母表明态度,众亲评议,如果一致同意离婚,就举行离婚仪式:在酒席中间,放三个碗,一个碗盛满酒,两个是空碗,并用一块黑布铺盖碗口,离婚者相对就座。奥雅把黑布从中央撕开分成两块,离婚当事人各取一块,作为脱离关系的凭据,之后奥雅把盛满的一个碗酒倒入两个空碗中,离婚者各把半碗酒饮干,俗称‘喝半碗分手酒’。”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离婚的仪式越简单,一般就以离婚双方撕开一块黑布为凭证。在此过程中,离婚当事人最终决定离婚与否,其他人只作为见证人和调解人。也就是说,在黎族社会,夫妻关系破裂并不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社会承认的只是认可个人对于结束共居状态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由男女双方自己做出的。
好吃懒做、酗酒,劝说不听,也是导致夫妻离婚、家庭破裂的一个原因。黎族谚语说:“不种田吃好米,没有老婆得好妻。”流行于保亭、琼中一带的《割茅歌》中唱道:“老婆滚地猛哭喊,骂老公太惰……全村老少来取笑,碰上这老公猪一样懒!”而保亭县加茂镇毛林村的村规民约中也规定:“反对酗酒闹事,一旦发现,派出所就将其留制,直到酒醒承认错误。”已婚者偷窃,将会成为夫妻离婚的一个原因。
夫妻任何一方死亡的直接后果就是婚姻关系的解除,而双方离婚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一般不需要办什么手续。
总结来说,黎族在有关婚姻制度方面,得益于汉民族文化在黎族地区的逐渐渗入,黎族对汉民族文化的吸收以及黎族地区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使得黎族地区的婚姻制度逐步完善,并逐渐趋于汉族化。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是民族文化进步的一种表现。
(二)妇女地位
黎族婚姻家庭习惯法孕育和根植于这些民族特色之下,具有高度的地方化色彩。与汉族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不同的是,在黎族传统婚姻家庭习惯法中,黎族女性一直处于崇高且受人尊敬的地位。
黎族主要崇拜的始祖神黎母就是女性。海南儋州黎母庙,“在县西黎晓山顶,在巨石岩岩,乡人以祀黎母。灵甚,岁时祭享,祈祷有应”。①即使接触到汉文化时,黎族的许多生活习俗也体现了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现象。到宋代,黎族的部落首领仍有由妇女担任的,“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②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蛮夷》卷四,黎人条载:“峒各有主,父死子继,夫亡妻及。”清代《黎岐纪闻》写道:“其俗贱男贵女,有事则女为政”、“遇有事妇人主之,男不敢预也。”③男子打架,女子相劝一定要停止,“黎性悍而质直,间有同类一语不合,则操戈矢相向,得妇人架中一劝,随亦解释”。①如果峒与峒之间发生械斗,要发出“通牒”,送“通牒”的使者必是妇女,械斗停息,双方各派出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传统的和解仪式“蕊岔”。②
从宋代史籍《岭外问答》记载的“王二娘主政”到清代《黎岐纪闻》记载的“遇有事妇人主之,男不敢预也”,我们可以看到其持续时间之长久。虽然后来在封建化的黎族外围地区,已改变了妇女主政的情况,但妇女依然受到黎人的尊重,如峒主见到妇女、老人也要下马。直到今天,走路时,男子见了女性和老人还要让路。家庭中,妻子有过错,要报告女方娘家处理,女子受了夫家欺负,娘家常兴师动众来论理。③夜游和不落夫家等习俗也都表示着母系社会女性地位崇高观念的遗留,由此引申出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结婚自主等理念甚至影响到今天。
以上情况说明,黎族女性一直处于被人尊敬的地位,但是女性的地位在细微之处还是随着婚姻习惯的变迁而变化的。一夫一妻制时期,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显现,为了氏族的和谐,女性进一步让渡自己的性自由权利,如女性婚后即使不落夫家,性行为也会受到一定道德上的限制。此时期,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上平等。在黎族人的观念中,男女双方分属不同的祖先,也因此女性得以在婚姻中保持自己个体的独立性,男女双方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体现在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上就是男女完全平等与自由。双方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男女之间体现了相互尊重人权、互不干涉强制,只要一方不同意,婚姻家庭关系即建立不起来。结合自愿、离婚自由,男女双方以爱为基础,当事人自己掌握婚姻的主导权,真正实现了以感情为基础的美满自主的婚姻。
总结来说,在黎族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很明显的。随着黎族传统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婚姻习惯的逐步变迁,女性不断地让渡自己的权利,黎族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步降低并逐步与男性社会地位趋于平等。
实际上也只有双方或者多方的权利逐步趋于平衡,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得到实现。
(三)家族
血缘共耕与互助逐步减少。“合亩”制是黎族特有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它应该是黎族最早的一种社会制度,是黎族社会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社会形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来看,“合亩”制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一种生产方式。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合母内成员共同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具有原始社会的色彩。由于合亩制以男长辈为“亩头”,使得黎族的合亩制性质应是原始社会父系家长制或家族的共耕公社。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外部文化尤其是封建地主经济文化的不断浸透,原来单纯的合亩制已变得纷繁复杂。一方面,“合亩”原本都是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组成的,随着合亩的演变,有些合亩已吸收了非血缘关系的外来户,以致非血缘关系合亩的户数、人数越来越多,血缘共耕由此减少。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家族以至家族内各户所私有,社会关系已不是血缘的关系,而是地域和经济的结合。特别是外围地区,随着阶级分化的明显,加上社会成员间的迁徙杂居,这种代替了亲属结合的地域性或邻近间与政治的结合越加稳固了。宋时,羁縻黎峒的生产方式,田土由“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初无文记”。①它与残存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合亩制”略同。不过前者是以“峒”为单位,范围很大;后者公有制和共耕分收制的范围已经缩小得多了。而随着黎族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加深,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元明清时期,黎族公有制和共耕分收制逐步减少。到了民国时期,据了解,在外围地区,本地与外地来户,同姓与外姓界限逐渐消失,全村性的互助无偿减少了,借贷计时计息了,帮工不换工不给报酬受到所谓“社会舆论的制裁”了。如东方县第二区水头乡老村,在帮工互助上,姓氏的感情,并不比同村同一方言来得浓厚。②
二 民事习惯法秩序的变化
宋代以后,黎族由先民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本民族内部没有“私有”的概念,没有交易、交换,慢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以及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迁入岛内,促使了私有财产交易的频繁化,形成了简单的商品经济。黎族的民事交往也由此步入了发展时期。
(一)民事活动范围的扩大
黎族在贸易交换的对象上有了很大的变化,黎族合亩之间的交换,演变成后来的黎汉贸易加强,苗族的迁入使得黎苗贸易出现,民国时期则有了和日本军阀的贸易。据《黎族三峒调查》,1942年末日本人付给石碌矿山的劳工每天的工资是40钱军票,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地方为日本窒素株式会社经营的作业场商店。在此期间黎族和日本人的交易基本代替了黎汉交易。
在贸易物品上,由原来的简单生产资料交换演变成用土特产、粮食交换劳动生产工具,如一包衣针换1斤鸡,或换5斤玉米,1副犁尖换5斗谷子,1支单发粉枪换1头水牛或黄牛等。不难看出汉族文明的传入使得黎族的生产经济有了很大提高,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
(二)民事交往的形式
1.墟市
黎汉之间的贸易由宋朝时期主要在汉族的集市中进行,①转变为以黎族地区开设的墟市为主,②以汉族地区集市交易为辅,而且墟市的范围不断扩大。《明神宗实录》卷363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统治者平定居碌、居林、沙湾三峒黎族起义后,于其中心地带永蕉村“立墟市以通贸易”。清朝黎汉贸易往来进一步深化,墟市不断增多。据《正德琼台志》记载:“全岛兵有一百二十一个较大的墟市;其中琼山三十九个,汀迈二十个,临高十四个,定安八个,文昌九个,会同六个,乐会三个,昌化1个,万州六个,崖州二个,儋州十个,唯独感恩,陵水只左城中设市。”①
随着黎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黎汉往来的频繁化,黎汉通过商业沟通,互通有无,日益融为一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2.典押
黎族习惯法中有一些关于典押的规定。典押最初在当事人双方之间直接发生,后来才出现了中间人,中间人按田地典押或牛的数量来收取报酬。黎族典押经常没有具体的时限,多在两年后才可赎回典押物。有时父亲出典的东西,到儿子时才赎回。根据习惯法的内容,典押关系成立后,双方还要剖竹为凭:用一寸宽、五寸长的竹片一块,把典押价格用刻划于其上,再将竹片一劈为二,由出典人和受典人各执一半为据。日后赎典时,便以此为凭。如果出典人归还典价后,就收回出典物,并当场焚毁竹片,典押关系即结束。
典押也可演变为买卖,如出典人在出典期间,要把出典物卖断,经征得受典人同意后,双方协商,由受典人再给卖主一些牛或钱,土地所有权就属于受典人的了。②
3.借贷
黎族习惯法中借贷的情形发生甚少,外部借贷也不多,所以对此虽有规定但也很少,主要是遵循传统的习俗进行互相帮助。借贷分为两种:
对内无偿借贷。此种借贷是指在同一合亩内的直系血亲间,或者不管是在合亩内借贷还是在合亩外借贷只要是黎族人之间借钱都不付利息。也有些合亩内的非直系血亲归还成本就可以不用偿还利息,同时对偿还期限也无苛刻要求。
对外有偿借贷。此种借贷主要指合亩外,对粮食的借贷都是要计算利息的,要还一倍的利息。即借一还二。在盖章村王老捆做亩头时,合亩内的王老陆向堂侄王老识借稻谷一对,同年还稻谷两对,如果当年不还则要利上加利。①因为在黎族人看来钱不会生长出钱来,可粮食会,所以对粮食的对外借贷一定要双倍偿还。
4.租赁
黎族习惯法中牛和土地是他们主要的财富,也是赖以生存的劳动生产工具,所以在对这两种财物的租赁上有比较细致的规定。
首先,在合亩租牛时,由亩头代表合亩去租,租金由合亩出。而个人租牛时,由个人联系,也有的村还需亩头去交涉。租金一般是固定的。
其次,租赁人在租赁耕牛期间必须合理使用耕牛,并认真对耕牛进行看护。如果牛老死或因过劳致死,租牛者必须以牛进行实物赔偿,死牛归租牛者;如果牛被盗,租牛者要承担赔偿责任,如牛在夜晚被偷,按原数偿还,反之则加倍偿还;如果牛遭遇瘟疫而死,租牛者虽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必须及时通知牛主。牛主需要将牛颈、牛腿等给租牛者。牛主如不要肉,可由租牛者所在的合亩分食,另以1口猪及相应的钱送给牛主。如在牛瘟死后,租牛者未及时通知牛主,而被牛主知道,则租牛者受罚。
再次,关于孳息的问题:租牛所生的小牛归牛主,如被人偷去小牛,租牛者要赔偿1口猪。②
关于田租,在黎语中被称为“同寅田”,即基于平等和合作、因兄弟情谊而互相帮助耕田的意思。③租赁的对象一般是私产田地,主要是水田、旱田和部分山林。公田不允许出租。
在田地租赁方面形成的习惯法内容主要有:
(1)租赁契约达成需要一定的仪式性程序
土地的租佃关系一般发生在同村的合亩与合亩之间或合亩与别村合亩个人之间。在进行租田契约时,农户自己去找田主联系,当然在个别情况下,也有村头出面联系。联系好便要举行仪式,杀鸡、猪、牛与田主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宰杀牲畜的种类和数量往往代表了租赁契约的具体内容。①
(2)以租种土地的部分收成来折抵租金
在租赁的土地开始收割前,租田者要通知田主来分稻谷,田主本人或者派人来对收割过程进行监督。收割后,租田者应先留出种子以及田主及其随从饮酒、吃饭所需的谷子,再将收成分为两份,双方各取一份;有的由田主根据收成的好坏来决定田租的多少。
(3)违约责任以赔偿牲畜或谷物为主
如果租田关系还未到期,田主提出中止租田关系,则根据剩余租田期限的多少对租田者进行赔偿。如9年的租期第6年时田主提出收回田地,田主要给租田者一口猪或价值相当于一口猪的稻谷。②如果是租田者提出提前解除租田关系,田主则不对租田者进行赔偿。
(4)中间人制度
在黎族习惯法中,田地租赁契约的出现较晚,起初只限于出租者和承租者双方,后来为便于协议的履行,出现了保人也就是中间人。据说中间人一般为男性,其主要义务就是在宴会上把双方的权利义务说清楚,并监督双方履行。此外中间人还要负责解决租田双方纠纷。在习惯法中,不论租种田地的面积大小、期限长短、土质好坏,中间人获得的报酬是相同的,但是他对双方当事人违约行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三)民事交往内容的变化
1.书面契约更加规范化
宋代黎人虽无文字,但能通过结绳记事、刻木为契进行交流。宋·苏过《论海南黎事书》记载:黎人“无文书符契之用,刻木结绳而已”。此法在黎区沿用至清代。《广东新语·人语》卷七所记:“黎长不以文字要约。有所借贷,以绳作一结为左券。或不能偿,虽百十年,子若孙皆可持结绳而问之,负者子孙莫敢诿。力能偿,偿之;否则,为之服役。贸易山田亦如是。”①
黎族传统的契约,又称为对牌。对牌由借方和贷方各持一半,如果借方欠债不还,贷方可以向其出示对牌,催促其偿还债务,如果借方偿还了部分债务,双方都要将对牌的相应部分切掉,债务全部还清后,双方均废弃对牌。“出卖或出典田地,都要刻竹为契,即用一节竹筒,将典卖的田地的价值、数量,用刀刻在竹上来表示。如一头牛和五块光洋,可刻成‘x1x11111x’的形状,其中‘x’表示间隔,仅‘1’才表示数量。刻竹以后,将竹筒从当中剖为两片,双方各取一片以后每交一头牛,一块光洋,便将刀痕逐次削去,等削完了,就得两片竹片对证一下,认为没有问题,就当场烧去,表示手续完结。”光绪《定安县志·黎岐》卷九记黎俗,“黎人贸易称贷,截竹有一指之长,千浅刻一痕,剖开各执一为合同”。②
典田竹契1支。清光绪四年(1878年)佚名制。记清代海南乐东千家地区黎族社会民间典田之事。以竹片制成,内侧题有黑色行书“光绪四年出典掃逢田种二×”十二字,并有两道“|”样刻痕;竹契外面自上而下刻有代表契值的纹痕“>| | | | | |>”。为海南乐东千家地区黎族民间典田契约。对研究海南黎族社会民间典当关系与“刻木记事”文化有参考价值,保存完好。③
张亚本断卖田契1纸。清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张大利代笔撰写。三亚崖城地区黎族民族间买卖土地地契。记载抱雷村张亚本因粮债负累将祖父遗下分田多处出卖与本村韦亚临事宜。棉纸,楷书,黑色。代笔人画押,签书人、同见人手模。第三行上部、中间下部、左上部有残缺。④
从上述《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两份田契不仅在材质上不同,在地区上也有差异。笔者认为黎族的文明程度不仅和汉族的入住有关系,而且和地理位置也有很大的关系。乐东位于中部靠西,崖城位于南部靠海,相对于乐东更有利于发展经济,同时文明的进化程度也要高于居于中部的乐东。
上述两份纸质契约不论在内容表述上还是在格式形式上,都已与中原汉族契约十分接近。在使用中原汉族契约形式的问题上,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中我们还发现,在乐东黎族地区,黎族人民不仅使用了纸质的契约,同时还立有竹契,一个民事借贷行为同时有两个形式的契约存在,这说明黎族人民在接受汉族法制文明时的小心谨慎。
2.存在剥削与不对等
在交易过程中,黎族人民恪守传统的交易习惯,诚实信用。《昌化县志·原黎》卷3载:“与人贸易,甚有信。商人信则相与,而至亲借贷不吝。或负约,见其同乡人擒之以为质,枷以横木,必负债者来偿还始释。”但随着交易的频繁,汉商对黎族人民的不平等交易现象出现。《崖州志·黎防一·黎情》卷13所载:“与人贸易,不欺,亦不受人欺。相信,则视如至亲,借贷不吝。或负约,见其村人,即擒为质,枷以横木。负者来偿,始释。负线一缗,偿谷一秤。岁加一倍,无有底止。”此后,明朝和清朝政府都对这一不平等交易现象予以法律规制,以此缓解黎族汉族矛盾。据《明神宗实录》卷534,“万历四十三年七月乙丑”条载:“以后,闽、广各商止许于交界互市,有酬价不登或不偿值者,许黎人告理。”据《清史稿·杨廷璋传》卷323载:“各地方官各于附近州县城外汛防地界,设立墟场一二处或二三处,按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定以墟期,俾源源赴墟,彼此交易。黎货既已流通,物价又复公平。每属墟期,责成该汛巡检弓兵督同黎头保甲赴墟弹压稽察。”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所立《奉道宪严禁碑》称:“议客黎买卖货物,斗秤须要公平,彼此交易,有信有从,不得强牵牛马及儿女抵债,违者送官究治。”
三 中央权威对某些传统禁忌和宗教的限制
在黎族传统习惯习俗中,有一部分是与公共秩序有关的宗教与禁忌。基于对神灵与鬼神的崇拜,在黎族社会产生了众多的禁忌,对于这些禁忌的触犯,会惹来杀身之祸,导致全族恐惧。而各路神灵的惩罚通常是通过族内神职人员(如道公、禁公、禁母等)来体现,该禁忌本身十分愚昧与落后,其后果则十分残酷。故,在中央政权的统一法律秩序下,这些对黎族社会及黎民人身带来恐惧、不安和无辜伤害的禁忌与宗教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一)禁忌:禁公、禁母等巫蛊杀人、伤人
黎族原始宗教的活动,除咒语外主要是原始巫术。所谓原始巫术,是指用一种简单的联想和独特的类比,祈求人世间的幸福,消除社会上的灾难。从上述可见,黎族的原始巫术已浸融在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各个方面,它在原始宗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禁术则是另一种家喻户晓而影响又极坏的巫术形式。由此,在各个时期,各中央王朝政府对黎族有关传统禁忌和宗教都有些否定性规定。
黎族有关“禁”习惯法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盛极一时,但从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府对海南黎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区实施有效控制以后,国家法开始在黎族地区实施,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如清朝光绪年间在黎族地区所立的《奉道宪严禁碑》中第一条规定,“一查造魔克符咒诅杀人并下毒药害人,按律照依谋杀论”。①民国时期,也采取了以国家法制裁黎族“禁”这一传统习惯。
(二)族殴、仇杀
族殴、仇杀这两种情况对黎族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群居生活的种族来说,并不是很陌生。在黎族地区,由于生产力以及宗教信仰等等各方面的原因,族殴、仇杀现象时有发生。故意杀人一般要看是杀外村峒(族)之人,还是本村峒(族)之人。杀死外村峒(族)之人,双方便在两村峒(族)长的主持下,会同两村峒奥雅或全体成员协商,和解成功,便由杀人者支付“赎命价”。若协商不成,往往会先引起村峒之间械斗和血亲复仇,连累无辜,牺牲更多的性命和造成更大的损失,抓到凶手便以命偿命;当抓不到凶手,便会引起两村峒(族)之间冤冤相报不止,直至两村峒(族)再进行谈判协商,最终以凶犯家钱财赎罪了事。故意杀死本村峒(族)之人,须以命抵命,但也有例外。
黎族传统习惯有关族殴、仇杀的解决方法很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情况的出现,不利于中央政府对黎族地区的统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朝中央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对有关族殴、仇杀等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崖州官坊村黎人发生了民黎冲突,时黎人纠集抱碟、粪洗、只酉等村黎人执刀,放火掠杀民人。据《琼州府志》载其因,“岁饥,汉奸放债盘剥,黎人苦之,出掠乡村”。①乾隆皇帝对此也尤为生气,下谕旨说:“黎人敢于纠集人众,抢掠村庄,杀害民人,实属不法,即使该处村民平时或有欺压黎人之事,以致受侮不甘,亦当向地方官控告办理,何得擅自仇杀,此等野性难驯之匪徒,不可不从严究办。”②即体现出清政府对黎人文化的直接干预。这种干预在清末表现得较为强烈,因清末开始转变过去消极治理黎族的政策。
光绪年间,聂缉庆记叙了他在临高当县令时以行政命令干预黎人习俗的事例:“临俗固陋,士入市不衣冠,盖其地极边,中州礼让之风未尝睹也。余至,多方劝勉,莫能移易。最后察士之有仍习者,辄罚金少许为修学费。诸生重财甚于他罚,不一月,衣冠济济,非复从前科跣景象。独齐民无表称,冒其妇里居姓氏为名字。与夫婚同姓,及妇失偶,群恶少争投榔肉,甚至三、五家争娶者。往往至期攘夺,后为强有力者得之,则盈庭聚讼。凡此蔑亲叛义,尤恶之甚者也。愚到任之后,严行饬禁,两载来亦知勉强遵守,略有通都文物之盛矣。”③
聂缉庆主要对临高士人不衣冠之陋习及黎人抢婚致讼进行了改变和禁止,而鲍灿则干预得更多,此处仅择两例。他在《劝释黎民械斗示二则》中云:“照得怀衅斗殴实为地方之害,为此示谕特劝尔等黎民,前经州堂协同本府招抚安绥,自后各安耕凿,严戒子弟,不准藉端生事,保守境界,虽有前仇宿恨,一概永销……如有不遵者,本府定派兵勇按罪剿办,决不宽恕。”④
喜仇杀械斗是黎人的风俗和习性所致,而鲍灿对此进行禁止和劝谕,以使黎人的行为合乎内地的“伦纪”,“风化”,显然是把内地的风俗强加在黎人头上。
(三)盗窃的新形式
盗窃,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众或他人钱财的行为,如偷牛、偷铜锣;另外,采摘、砍伐被人已作标记的果实、树木的也按盗窃罪论处。①黎族“刑事”习惯法视偷牛、偷铜锣为最严重的盗窃行为,被捉拿的盗窃者被苛以成倍惩罚。“一般的情况是‘偷一赔十’。失主将罚得的牛只杀掉两头宴请乡亲们;若偷盗者无法即时赔偿,则责令其‘刻木为契’,日后陆续还清;若罪犯无力赔偿,亲族又不愿意帮助的,被盗者可以将罪犯杀死。”②另外,偷牛、偷铜锣的被抓现行,倘若当场打死,也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黎族地区传统“刑事”习惯法的实施,虽然解决了盗窃案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容易引起重大社会矛盾的发生,尤其有关可以将罪犯杀死的规定将会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不利于中央政府对黎族地区的统治。为此,中央政府对于盗窃现象给予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二十日阎峒屯图同立禁碑。
总体来说,自宋代开始,随着中央政府对海南黎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区实施有效控制以后,为进一步加强对黎族地区的统治,各朝国家法开始在黎族地区实施,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这些具体措施的具体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黎族地区的统治。同时,由于在实施国家法的过程中具体结合了黎族地区的传统法,使得对黎具体治理措施得到实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央政府对黎族地区统治及加强当地封建化进程的目的。可以说,中央王朝国家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黎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汉文化在黎族地区的传播,有利于黎族文明的发展。
第一节 黎族地区被中央政府纳入统一法律秩序之中
一 中央政府对黎族人民的剿抚政策
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全面统治,黎族地区被中央政府纳入统一法律秩序之中,是在中央政权对黎区的征服、对黎人的剿抚中逐步完成的。自汉代建制始,中央政府对海南的管理基本上是放任的,只有在发生黎人暴动时才出兵清剿,甚至曾一度取消了建制,至宋代,封建政府明显加强了对黎民的治理。承袭唐之少数民族羁縻政策,宋一方面对犯乱之黎人进行讨剿,另一方面又招降黎人,奖赏对政府统治有功之黎人,奖惩分明,以达到分化黎人、维护地方安定之目的。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安抚使王祖道经广西到海南岛“抚定”黎峒907峒,丁口6.4万人,开通道路200余里。在被征服地区,宋王朝采取了“羁縻政策”,对黎族上层“首领”委以官禄,通过他们来统治黎族人民,并通过他们来吸引更多的黎族头人归降。“宣和间,儋人陈大功招抚符元亨等三十余峒黎入贡,补元亨等承信郎,诰令其子孙各以官名承袭,世为峒首。大功亦补丁班,只应官至融州巡辖。”②“乾道九年八月,乐会黎贼劫省民,焚县治。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陈颜招降之。琼管安抚司上其功,借补承节郎,诏许子孙袭职。”③宋“元祐三年正月,诏广南西路珠崖军开示恩信,许生黎悔过自新”。①宋之所以在被征服黎区推行羁縻政策,与当时宋王朝对黎人的认识不无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如苏过的《论海南黎事书》:“仆以为以力胜者,兵罢而复塞;以利啖者,贼贪而不叛也。朝廷若捐数官以数人,则贤用于师矣。……使赍金帛入喻诸黎,晓以利害,惧以祸福,若能开复故道,使行旅无壅,则籍其众所畏服者,请诸朝,假以一命,而岁与其禄,不过总十余人,岁绢千缗耳。今朱崖屯师千人,岁不下万缗,若取十一以为黎人之禄,可以罢千师之屯矣。”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宋王朝开始大量任用黎族峒首为黎区地方官。在剿抚黎民的同时,宋还将海南作为官员贬谪②、罪犯流放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文化得以随被贬谪之人深入海岛人民的生产生活之中,黎族人民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步伐因此而加快,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封建政府对海南统治方法的改变,即由过去单纯的武力镇压,改变为剿抚结合,并辅以文化影响,以促进海岛及其居民的文明进化和思想改造。
在唐宋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元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即对归附的少数民族及其首领假以爵禄,宠之名号,使之仍按旧俗管理其原辖地区,民族和部落首领服从中央王朝的统治,并承担一定的赋税及军事义务等。在海南,元统治者对黎族人民的政策重在剿上,但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则在海南岛专门设立“黎兵万户符”,下辖千户所,千户所下又辖百户所,在黎族地区实行土官制度,万户以下一般都任用“归降”的黎族上层为“峒首”,统治者给他们封以官爵,付以实权,世袭其职,统管地方上的军事和民政。
明清时期,虽然大多黎峒已编入版图,居户编入里甲,黎人与汉民杂处现象较普遍,但五指山区仍不断有黎为乱,对此,中央政府采取了以抚黎防黎为主,以剿黎平黎为辅的治黎政策。明朝,由于汉、黎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大多黎峒已编入版图,居户编入里甲,在这些地区,黎人与汉民一样,受地方官管辖,受中央政府法律的统一调整。“在一些开发较早的熟黎地区,明初曾实行‘都图’制度,当地官府对他们采取直接治理的方式,他们与汉人一样纳粮当差,到了嘉靖年间,文昌、乐会、琼山等多个黎峒的黎族已和当地汉族一样编入都图,载入黄册与鱼鳞册,其中不少人‘习书句、能正语’,有些土官子弟入县学、大学读书,到明代后期,部分熟黎民族特点日趋减少,逐渐与汉族同化,已不再被视为黎族了。”①在已顺化的熟黎地区则实行以黎治黎的土官政策,选择有能之熟黎峒首,授以官职,管理黎区;对尚未归顺并仍犯乱之生黎实行剿杀,剿杀之后实行善后抚化政策,开通道路。“洪武初,尽革元人之弊:土酋主都者,元帅陈乾富以降免罪,徙为广西平乐通判;州县各另除官,不用土人;兵屯子孙尽革为民,以峒管黎。二十九年,革除广东公差。大理寺丞彭与民等奏言:琼州府所属,周围俱大海,内包黎峒,民少黎多。其熟黎虽是顺化,上纳秋粮各项差役俱系民当。其生黎时常出没劫掠,连年出镇征剿,为害不息。今询访各处熟黎俱有峒首,凡遇公差役,征纳秋粮,有司俱凭峒首催办,官军征捕亦能凭峒首指引。今所属各有防黎及备倭巡检司,如将各处峒首,选其素能抚服黎人者,授以巡检司职事,其弓兵就于黎人内签点应当,令其镇抚熟黎当差,招抚生黎向化,如此则黎民贴服,军民安息矣。诏如所请。明年五月十一日,琼州府宁远县藤桥巡检司添设副巡检黄旗,通远巡检司添设副巡检黎让,十月十一日万宁县莲塘巡检司添设副巡检王钱,陵水县苗山巡检司添设副巡检符森。”②从此,土人被任命为官协助管理黎区被广泛运用,对被招抚之黎头适用,对有功有能之黎人也适用。如宜伦县熟黎峒首王贤祐。中央政府对黎人,“各验其招抚多寡受赏,除官有差,专一抚黎,不预他事”。③土官的任命使用,在黎族地区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已授禄之黎首,主动请缨招黎受降。
清朝对黎族人民的统治仍然沿袭明代的一套办法,剿抚结合。“雍正八年正月,崖州黎峒三十九村生黎王那诚、向荣等,定安县潮村等处十四村生黎王天贵等,琼山县番否等处十八村生黎符天福等,陵水县生黎那萃等,共二千九百四十六人输诚向化,愿入版图,每丁岁纳银二分二厘以供赋役。三月,总督郝玉麟等奏闻,奉旨:‘生黎诚心向化,愿附版图,朕念其无田可耕,本不忍收其赋税,但既倾心依向,若将丁银全行豁免,恐无以达其输诚纳贡之悃忱,将递年每名输纳丁银二分二厘之数,减去一分二厘,止收一分,以作徭赋。地方文武大臣,时时训饬,所属有司员弁等加意抚绥,悉心教养,务令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以副朕胞与地方之至意。’恩诏既颁,黎民感泣,自是琼属诸黎悉化为良民矣。”①朝廷的抚绥政策,显然有利于减轻生活困难的黎民负担。但清代在对待土官的政策上,则有别于明代,采取逐步削弱土官权力之策。清代的黎族土官职低官小,仅在黎族村峒设“峒长、总管、哨官、黎首、黎练、粮长”等类土官。清代后期(1886年)冯子材率兵入琼镇压黎族人民起义,他深入五指山腹地,在黎族地区设立专门管理黎族事务的“抚黎局”,实行一整套维护封建统治的治黎措施:抚黎局下设黎团总长,统辖县属黎境,黎团总长下设总管,统辖所属全峒之事,峒内设哨官,统管一村或若干村,村内的黎户十家为一排,三排为一甲,三甲为一保。所有的排长、甲长、保长、哨官、总管等职均由黎族担任,黎团总长则为黎族头人或汉族地主担任,抚黎局局长由上级委派汉族封建官吏担任。除了加强基层建设、任用黎首外,冯子材还在征服之黎区,修路设寨,设置招商局,发展贸易,号召黎民学习汉文,薙发改装,除弊化俗。此时在海南岛依然有“生黎、熟黎”之说,但已无生黎、熟黎之分,黎族地区完全置于清王朝有效的统治之下。
二 黎族社会的分化
在封建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下,黎族社会发生了分化。
1.黎民被区分为生黎熟黎
将黎民区分为生黎熟黎,是中央政府等外界所为。生黎熟黎的区别是:“熟黎多纳官粮……生黎则各食其土,不入版籍,止设有黎练峒长之类统辖之……”②可见,是否入籍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是否纳粮缴赋,是区分生黎熟黎的标准。随着封建王朝不断征黎、剿黎,中央政权逐步向黎区纵深扩张,黎族人民的生活范围逐步由沿海向中部山区集中,在这个过程中黎民内部发生了分化。按其与汉族同化的程度,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已与汉族融为一体的黎民、熟黎、半熟半生黎和生黎。
与汉族融为一体的黎民,是熟黎的一种,受中央政权管辖较早,与汉族长期杂居,已基本脱离黎之习性,如同汉人,完全汉化,徒有黎称。“澄迈黎南曰南黎,今为一都二都,西曰西黎,今为中正都,澄迈县诸黎村峒凡一百三十有七……县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旧系黎峒,明永乐间抚黎知府刘铭奏以抚黎官王朝冠等招抚生黎,概免徭差,正统间革归有司,弘治十七年副使王继复援前例以黎图仍归土舍,止令防黎,纳粮免差,其后黎地渐归豪民,黎人归化既久与齐民等。现查其地为西黎中正二都,南黎正一二等都,每都编为十图,虽有黎都之名实无黎人之实。……文昌黎曰斩脚峒,治平已久,田地丈入版图,故有文昌无黎之说。”①这一部分黎人长期与汉人混居,如同汉人,已完全汉化,徒有黎称。《道光琼州府志》也有同样的记载:澄迈“县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旧系黎峒,明永乐间,抚黎知府刘铭奏以抚黎官王朝冠等招抚生黎,概免徭差。正统间,革归有司。弘治十七年,副使王继复援前例,以黎图仍归土舍,止令防黎,纳粮免差。其后,黎地渐归豪民。黎人归化既久,与齐民等。现查其地为西黎中正二都,南黎正一、二等都,每都编为十图,虽有黎都之名,实无黎人之实”。②之所以澄迈、文昌已徒有黎称,其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位于海南岛的北部或东北部沿海,中央政府的军队上岛后最先占领的就是这些沿海地区,并在府城、定安、澄迈等地建立了地方政府衙门,原居民黎人有的逐步向中部山区后退,有的则坚持下来,在与汉人长期的杂居生活中,逐步接受了汉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方式,最终与汉人无异。
除了上述已与汉民齐的黎民外,《治黎辑要》还将崖州黎分为三种,生黎、熟黎和生熟各半黎。熟黎系居住在黎区外围,与汉民接壤,归化既久之黎,“生黎者即乾脚歧之类也,裸体兽性穴居鲜食,环居五指山下,与民人隔绝,不为人害。熟黎者归化既久之黎也,饮食衣服与民人同,惟束发于顶,其俗未改,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其户口编入图甲,有司得治之,故亦不为人害。生熟各半者谓可生可熟之黎也,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其中亦分两种,曰大襜小檐,大抵富有者为大襜,贫者为小襜,平时耕田纳赋听官约束与熟黎同,然性嗜酒好斗……”①清人钟元棣创修,张嶲等纂修的《光绪崖州志》亦将黎区分为熟、生、生熟各半三种,“大抵熟黎习俗与生黎同。近民居者,饮食衣服亦与齐民同。惟宅心险恶,常以蛊毒、禁魇杀人。好斗乐乱,不能久安,动欲寻衅开叛,愈抚愈骄。大创一次,可静十年。其杂处生熟黎中者,为半生半熟黎。平时耕田纳赋,与熟黎同。但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常挟火器自卫,杀人与刈草。一有宿怨,辄手刃之。甚则屠牛走箭,负嵎思逞,引生黎以为州患”。②半熟半生黎,也有称为“三星黎”、“四星黎”的,所谓三星、四星,即三分生、四分生,还没有熟透,他们“开险阻,置村峒”,“好斗乐乱”,“不能久安”。显然,生黎、熟黎、半生半熟黎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接受中央政权统治和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的程度,接受汉族的东西越多,其自身原有的特色则失去的越多。
海南岛生黎、熟黎的划分,始自宋代。宋代同中原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一样,将国之四边的少数民族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称之为夷、狄、蛮等,将苗、壮、黎等少数民族分为“生户、熟户”,其中被纳入政府户籍,由地方管辖以及承担封建赋税和徭役的,或是邻近汉区,与汉人较为接近的,称之为熟户,“居深山避远,横过寇略者之生户”。③也就是从宋开始,黎民被区分为生黎和熟黎两种。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在介绍海南时描述道,“四郡十一县,悉隶广南。西路环供黎母山,黎獠蟠踞其中,有生黎、熟黎之别……熟黎峒落稀少,距城五、七里许外,即生黎所居,不啻数百峒,时有侵扰之害”。④宋王象之之《舆地纪胜》对此有所记载:“诸蛮环居号黎人,其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号生黎,耕作省地者号熟黎……”从封建统治阶级的角度看,谁接受其统治谁就是开化的、熟的、与民同的,反之就是生的、不化的。所谓生黎即嚣顽无知,质直犷悍、不服王化、不供赋税。熟黎就是“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识字者”,“近民居者,饮食衣服亦与齐民同,供赋役于官府”。据宋人乐史纂《太平寰宇记》记载:“有黎人,无城郭,殊异居,非译语难辨其言。不知礼仪,须以威服。号曰生黎,巢居洞深。”对于生黎,推行“以蛮夷治蛮夷”的羁縻政策,加以笼络。统治者对黎人的统治重点在于熟黎,因为他们认为“生黎嚣顽无知,伏居深山,质直犷悍,不服王化,不供赋役,亦不出为民患,惟与其类自相仇斗。间有患及居民者,则熟黎导之也。……生黎虽犷悍,不服王化,亦不出为民害。为民害者,惟熟黎与半熟黎”。①
随着中央政权在黎区的深入,黎民的变化进一步加剧,到了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对所谓的“生黎”已感到非常的遥远与陌生,半生半熟黎则分布最广,人数最多,熟黎也在变化,基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完全汉化的黎,一是由半生半熟黎发展而来,在明代中叶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基于生黎与熟黎的划分,中央政权对黎区实行的政治制度与管理方式有较大的不同。②
2.黎头变化为朝廷命官
自恢复黎区建置以后,中央政府不断完善对海南岛的统治措施,一方面继续对抗命扰民之黎进行清剿,另一方面则通过抚黎政策,改造、分化黎民。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黎族社会发生了政治分化,原来的黎头成为朝廷命官。
据史籍记载:“生黎不属官,亦各有主。”③在明、清以前,黎族社会本身并没有出现过统一的政治人物,但各地黎民却有着自己地域内的政治组织机构,如合亩制地区的亩头承担本亩内的管理事务,峒首则是若干黎族村峒的领导者与管理者,“……置村峒。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④宋代黎峒归顺中央王朝不断扩大,中央王朝对黎族的控制大为加强,开始实行土官制度,委任上层黎首为黎族土官,但这些土官大都为虚衔,且品级低下,如宜人、承信郎、校尉等。元朝起,在征剿后对与汉族接邻的边沿地区的黎族同胞进行招抚,“编入图籍,与齐民无异”,起用“归降”的黎族上层为峒首,封以官爵,付以实权,世袭其职,统管地方上的军事和民政。他们当中有任万户、千户、总管、知州、县尹等要职的。明代在黎族地区仍实行土官制度,鉴于元代“黎兵万户府”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封建王朝构成了威胁,遂废除了这种土官制度,实行另一套比较完备的土官制度,即军政分开,自州以下设土官同知、判官、知县、县丞,任用黎族土官或当地有势力的黎族峒首为土舍,专门管理黎兵。清代仍设土官,管辖黎区。清代黎区基层组织为村峒,以峒辖村,在各村峒设峒长、哨官、黎总。据《道光琼州府志》记载,中央政权在黎族地区的基层组织已基本设立,各县下辖黎区均设村峒,设峒长、哨官、黎总管辖生黎、熟黎,乐会县南北两峒皆系熟黎,北峒各村设黎甲一名,南峒分上、中、下三峒,上峒设黎长一名,中峒设黎甲一名,下峒设峒长一名。至清康熙时,开始注意经营中心腹地,开十字道路通至各州县,在汉黎交错处,如琼山设水尾营、陵水设保亭营等军事机构。光绪十三年(1887年),冯子材率兵“平黎”后,除在中心地区增设镇板营、巡亲营、大坡营、番阳营之外,曾设立“抚黎局”,作为统一管辖黎区的最高机构,下设总管(即黎总)、哨官、头家等官职。任用黎族内部原来的公众领袖,通过他们层层统治黎族人民,以达其“以黎制黎”的目的。1932年陈光汉任“抚黎专员”时,改“抚黎局”为“黎务局”,易总管为团董,日本人登陆海南岛,国民党退守黎区,又将团董改为乡长,下设保长、甲长。①
总管、哨官、头家的授受有一定的仪式。总管由“抚黎局”委派,并给委任书、印章、铜牌、衣履、布鼎等物;哨官由总管委派,也有委任书、印章、铜牌、衣履、布鼎等物;头家为哨官口头指派。总管、哨官均为世袭制,头家多由群众推举,但也有少数是世袭的。各人的职责视其所辖范围大小而定,总管一般是管一峒或数峒,哨官管数村,头家管一村。总管、哨官的职责是每年替“官府”催收钱粮,平时根据传统习惯处理峒内事务,维护社会秩序。经过任命和委任,过去的黎头、峒首成为中央政府的命官,传统权威与中央权力合而为一。《元史·刑法志》说:“诸内郡官仕云南,有罪依常律;土官有罪,罪而不废。”尽量保持土官在当地的世袭权力与地位,以便利用这些蛮夷之官传统的地方势力与影响来统治各族人民。
3.基层经济与社会组织发生变化
(1)合亩制的变化。大亩变小亩,甚至出现了个体小农户。合亩制是部分黎族农民从事集体生产、个别消费的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央政权进入黎族地区以后,合亩制发生了变化。根据调查资料显示:这种变化一是合亩组织由大变小,并分化出个体小农户;二是在边沿地带,合亩制分化为个体小农户。“白沙县第二区毛栈乡什够村,在5代以前只有一个‘亩’,40年前也只发展到4个,其中有一个‘亩’最大,由15户组成,但在约15年前,便分化为8个‘亩’,并有一户从‘合亩’内分化出去单干。又如保亭县第三区通什乡福关和毛利两个表(相当于行政村,由一个大的或两个以上小的自然村组成),在10~20年前,各有4个‘亩’,但是现在福关表有11个‘亩’,毛利表有7个‘亩’。”①“如白沙县第二区红星乡番响村一带,据该乡文书王高定(50多岁)说,在清朝乾隆以前当地是以‘合亩’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到乾隆以后便逐渐分解,现在全部是个体小农户了。”②以上合亩制变化的原因,既有内部原因,如人口增长,耕地面积有限,生产产品不能满足亩内人丁生活,不得不分开各自谋生;亩内田多劳动力多的各户在自身具备单干条件后,宁愿单干而不受平均分配产品原则的限制。也有外力影响所致,如边沿地区受汉族地主的欺压比中心地区严重,往往一人得罪了地主,便被罚大量田产和耕牛,牵连到整个合亩,将祖遗田产分给各户是避免牵连的最好办法。③
(2)原始的黎族村峒成为封建王朝的基层组织。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开始在海南设立珠崖郡、儋耳郡,这两个郡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直接隶属于中央封建王朝,从此中央的封建王朝正式在海南行使它的行政管理权。但是珠崖、儋耳仅是郡一级行政建制,中央政权并没有因此到达社会基层,特别是黎族地区的底层,仍然处在原始的以峒为界的氏族部落状态下。汉代两郡的设置只存在了60多年,60多年后,因为黎族多次起义,汉元帝的时候把这两个郡撤销了。之后的500多年间海南又处于无行政建制的状态,但在名义上海南岛仍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到了南朝梁大同年间,高凉郡俚族首领冼夫人奏请朝廷重新设置崖州之后,海南的行政建制再也没有间断过,而且不断改善。“越人俗好攻击,夫人兄南梁周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旁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峒。”①南梁大同冼夫人向朝廷请命置崖州,从此,中央王朝通过“南越首领”冼夫人,与黎族社会组织峒建立了间接联系。隋唐时期不断有黎峒归附于封建中央朝廷。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开始逐步向黎族社会的基层渗透,将已经归化的熟黎纳入到地方建制中,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实行统一的管理,从而进一步紧密了峒组织与中央政权的结合。明朝建立以后,朝廷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海南的行政治理和加快海南的开发。明太祖建朝以后,在海南设立了琼州府,作为全岛最高的行政机关,结束了海南岛的行政机构互不相干、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将海南由广西管辖改为广东管辖;对黎族进一步实行安抚政策,将封建政权深入黎峒,大多数黎峒被编入封建王朝的基层组织——黎图中。明在基层设“黎图”,若干个“黎图”为“黎都”,若干个“黎都”为一乡,乡为流官隶属州县,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使“熟黎”与编户的汉人一样编入都、图,载进鱼鳞册、黄册,要纳粮录差。综合地方文献,海南岛“熟黎”居多,岛的南部被编入黎都黎图者凡28都、75图,包括155峒,它们以岛的北部与沿海地带居多,岛的南部及山区较少。②清代基本承袭明朝在黎族地区的政策不改,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立了专管黎人的机构——抚黎局。广西提督冯子材在平定黎乱后,大行改革原黎族组织,设立抚黎局,抚黎局下设黎团总长,统辖所属黎境,黎团总长下设总管,统辖全峒,峒内黎户十家为排,三排为甲,三甲为保。至此,中央政权基本覆盖了黎族全境,深入到每一户黎族人家,峒成为清政府在黎区的一个行政单位。
峒,原意是“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区域”,黎族的峒组织自宋代以后文献多有记载。在宋代,黎族社会组织称峒,每一宗姓为一峒,全岛黎峒林立,但规模较小,苏轼有诗云,“四州环一岛,百峒蟠其中”。①黎族的峒是一个封闭的集团,它具有一定的区域,每一个峒由若干村落组成,每一个村由若干个父系氏族即“合亩”血缘家庭构成,每一个氏族(“合亩”)由若干个家庭组成,合亩是峒组织的基础。峒内事务及峒与峒之间的事情由峒内各村的长老参加的长老会议处理,村落的内外事务由长老处理。②峒与峒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相属。
从峒的构成我们可以看出,峒是黎族社会的带有血缘联系的原始氏族部落,在封建中央进入黎族地区以后,黎峒成了中央政府在黎族地区的一级行政单位,原由家庭为基础构成的氏族和村落,在中央政权的统治下,变成了以户为单位的都图、保甲编制,黎族社会原始的血缘氏族的村峒划分被彻底打破,黎族社会从此与中原汉族地区一样,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法律秩序之中。
4.形成贫富对立
黎族喜血缘群居,峒首、黎头原本是本氏族选出的有威信的长老,是黎族人民尊重的公众领袖“奥雅”。因履职需要,他们理所当然地占有较多的氏族财富,职位的世袭,黎众的尊敬,使他们逐渐成为黎民中的富人。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这些富裕家族的氏族长老,取得了部落首领的地位,在所管辖的领域内掌握了政治、军事大权,占有了更多的田地、山林、耕牛等氏族资源和财富。中央政权在黎区实行土官制度后,他们的首领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在本氏族拥有了中央赋予的地方政治与军事大权,世袭制又使得其势力不断扩大,权威不断提高,财富不断积累。当与中央政权结合,峒成为中央政府的基层组织以后,黎头峒首则将原有氏族残余的家长制势力与手中政府权力结合起来,侵吞公有土地、山林,通过放贷强占黎胞田地,处理辖区内事务时,除接受宴请外,还收取黎民酬物,暴发起来,成为剥削阶级,对黎族群众进行压迫与剥削,黎族社会中产生了阶级对立。“如保亭县四区加茂乡毛淋村地主黄朝辉父亲和本人都曾任哨官、团董等伪职,处理偷牛、偷米等大小案件,除要鸡、酒外,还要10至100元光洋,如处理人命案,则任意要多少得给多少,否则便按年复利计息,逼得群众用田、牛或人工来抵债。”①除了财产侵占外,这些黎头、峒首还“学会了一套封建性的统治剥削方式,如勒石示禁、私设监牢等,形成一种‘家长制的农村生活的东方野蛮制度’的独特的统治阶级。而且越到近代,封建剥削的成分越重,虽然名为‘奥雅’,但传统的原始色彩已渐趁消失,并逐渐蜕化为封建性的地主恶霸”。②
土官峒首成为普通黎民之害,还可从官员奏议中得到证实。如明弘治时琼山主事韩俊在《革土舍峒首立州县议》中奏道:“为今之计,莫若革去土舍峒首,立以州、县、屯、所,量拨在外军民,杂处于中防引……今土舍峒首皆仗货利肥家,逢迎府县,闻欲立州、县、屯、所,彼愀然不乐……”③明代杨理在《上欧阳郡守四事》中第一事就是,“申明奸弊事。各峒首土舍欲据黎为利本,峒首乘盛饱餍其欲,受害者积恨,异己者互相侵伐仇杀,而祸害相寻于地方”。④与中央政权相结合,政治上有权、经济上有势的这些黎族土舍、峒首的强取豪夺,危害地方,也应是清中央政府改土归流的原因之一。
三 中央权威下的统一法律秩序
自宋中央政权进入黎族地区,逐步加强对黎族的管理以后,黎族地区形成了中央权威下的“以黎治黎”的统一法律秩序。
所谓中央权威,就是中央政府将黎族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之下,实行与中原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中央权威在黎族地区的统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黎族地区的各级管理者,都是经过中央政府的任命,是经中央授权且世袭的在册官员。如“宋朝宣和年间,陈大功招抚符元亨等三十余峒入贡,补元亨等承信郎,诰令其子孙各以官名承袭,世为峒首”。①宋朝对招抚归顺的黎头授予官衔,虽然多为虚职,却是经过任命、为朝廷效命、联结朝廷与黎人、享有世袭爵位的官员。元朝不仅承袭了宋的羁縻政策,继续任用黎人为官,而且还大幅度提高了黎官的品级,掌管军政大权,担任千户、万户的常常有之。明代的黎官任用制度较元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达到了鼎盛阶段,“明永乐六年春二月,琼州府抚黎知府刘铭率生黎峒首王贤祐、王惠、王存礼等来朝,贡马。命贤祐为儋州同知,惠、存礼为万宁主簿,赐冠带、币钞,俾专抚黎人”。②明朝统治者不仅继续任命归顺之黎头为官,而且将黎官管理纳入了国家统一的官吏管理制度中,同时还将黎官区分为军政两类,从而避免了因手中权力过大而造成对朝廷的不利影响。黎官的广泛使用,使封建政府关于黎区管理的政策得以通畅。鉴于“以流官治黎”使政令推行效果不佳,更使黎人未易信从,明统治者采取“以黎治黎”政策,“宣德四年,以黎峒多侵挠,革去抚黎流官”。③元朝的土官制度对明清两代西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施政与立法影响很大,明朝土司制度更在元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将土司官职完全纳入地方官体制之内。清代“改土归流”之前,基本上沿袭了明代旧制,很多原则与具体措施也来自元朝。
清代抚黎之土官政策一直延续到清末始有较大变化,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现了专管黎人的机构——抚黎局。广西提督冯子材在平定黎乱后,大行改革原黎族组织,设立抚黎局,抚黎局下设有黎团总长,统辖所属黎境,黎团总长下有总管,统辖全峒,峒内黎户十家为排,三排为甲,三甲为保,所有排长、保长、总管均由黎人担任,抚黎总长则由黎首或汉族地主充当。抚黎局的业务在于负责处理诉讼、缉拿盗匪、修路垦田、设墟招商、任免村峒土官等事务。有清一代,虽然也实行以黎治黎的政策,但是,黎族土官远没有元、明时期的地位与权限,中央政府对他们及普通黎民实行了比较严密的监督与管理,土官只能是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一个基层代表而已。严密的保甲制度,打破了黎人村峒的血缘划分,转而成为依地缘而分的地方性组织或团体,黎民彼此之间的相互帮助义务因血缘疏远而逐渐消失了。
其次,封建国家的法律对黎族地区统一适用。《宋刑统》是宋朝的基本法典。其“化外人相犯条”就是对宋朝以外的各民族、各国家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宋朝皇帝的诏敕是最有效力的法律形式之一。北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针对一些地方有人杀人祭鬼的现象下诏:“禁川陕、南岭、湖南杀人祭鬼。”①明朝将土官纳入了化外人的范畴,强调国家法律的管辖权,一律适用明律。《大明律集解附例》:“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明正德年间的《大明律集解》中称“凡土官、土吏、化外夷人有犯,与中国一例拟断”。明朝不仅将国朝法律统一适用于黎区,而且还对黎区实行礼仪教化。明初实行重典治国,强调要“明刑弼教”,即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贯彻礼教纲常。朱元璋认为:“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②他又说:“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顽,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遣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③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高度统一和发展的鼎盛时期,祖国的统一比汉唐宋明各朝代更加巩固,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管辖更加深入,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从国家大一统的原则出发,顺治三年(1646年)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化外人有犯”条明确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并注明“化外人既来归服,即是王民,有罪并依律断,所以示无外也”。所谓化外人,包括满汉民族以外蒙古族等所有已经归附清朝的少数民族,这就从根本上明确了国家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少数民族发挥效力,保证了国家法制的统一。
民国时期的保甲条例,不分黎汉,统一实行保甲管理制度。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东政治分会将广东全省划分为四善后区,南区善后公署设于琼山。为加强管理,专门制定了《保甲施行准则》,其中包括《广东南区保甲条例》、《南区各县市长员办理保甲须知》、《团董须知》、《甲长之职务》、《保长之职务》和《家长之职务》。琼、崖属于南区善后公署的管辖范围。《广东南区保甲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各城市墟镇乡村住户,每10家编为一保,置保长一人;10保为甲,置甲长一人;10甲以上为团,置团董若干人。”第三条规定:“保长甲长由该保甲内公举,经甲长、团董之审查,呈由市县地方长官委充之。”该《保甲施行准则》没有区分黎人、汉民,只按自然城市墟镇乡村编入保甲,实行规范化统一管理,中央政府的统一法律制度在黎族地区已然完全建立。
再次,适用于黎族地区管理的特别法。封建中央政府除了为征剿叛乱、招降黎首、抚恤黎民而颁布一些谕旨外,没有专门为黎族地区的管理制定法律。维持黎族地方秩序和地区稳定的,基本上是黎区管理者制定颁布的带有规范性作用的政策、治理措施等,它多以告示形式出现。这些告示内容主要涉及几个方面:一是禁止各峒黎目总管哨长等对黎民勒索苛派;二是悬赏严拿黎匪;三是严禁汉人进入黎区对黎人欺诈抢夺;四是改造、限制或废止黎民陋俗。①黎区这些特别法有的张贴到黎区成为安民告示,有的被刻勒成碑成为禁示碑,有的张贴于府衙,成为布告。这些公布于众的告示、谕旨、禁示碑等,对黎族地区社会治安和百姓生活,都起到了很好的维护与保护作用。此外国家明确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的黎族习惯法,也是管理黎族地区的特别法。
两广总督张之洞与冯子材拟定的《抚黎章程十二条》,是一部比较典型的专门适用于黎族地区的地方特别法:“(1)官军此举专为剿除黎乱、招抚良黎,开通十字大路,以期黎汉永远相安,其良黎秋毫不挠,毋庸畏惧。(2)从前为匪黎人投诚者免,抗拒者诛擒斩,来献者重赏。(3)投诚诸黎无论生熟,一律䕌(ti)发改装。(4)投诚黎首开送户口册,捆献匪徒缴呈枪械。(5)投诚黎众随大军伐木开山前趋响导,仍按计里数酌给赏犒。(6)将来开通生黎大道后,选择要地设官抚治安营,弹压各村黎长,助剿开路有功者授为土目,就中酌设总土目数人,目给顶带,总目授土职,自为约束,仍听地方官选黜,略仿滇黔各省土司之例,不令吏胥索挠。(7)开通后黎人仍安生理有主之田,断不强夺,惟抗拒者籍产入官,充官军屯田之用。(8)开通后田业三年内不收赋税,三年之外务从轻,则起征断不苛敛。(9)开通后黎境有矿,各山由官商开采者,给钱租赁,绝不强行占据,黎汉均享其利。(10)开路通后,人民盐布百货与黎地牛、木、粮、药等物,在各峒口设场集市,来往畅通,公平交易,严禁汉民讹赖盘剥,总令于黎人有益。(1 1)设立土目之后,应各具永远不敢杀掠、抗官、藏匿匪徒切结存案,所属有犯,责成设归该土目拏(na,同‘拿’)送到官按律惩办。(12)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延请塾师,习学汉语汉文宣讲圣谕广训,所需经费就地筹办。”①该章程虽然是关于黎族地区管理与治理的措施与政策,但其中不少条款具有维护一方治安与秩序、对黎民行为具有调整约束作用的法律规范性质。
该《抚黎章程十二条》中,既有对为乱之黎的惩办与招降政策,也有对剿后黎区政治生活、经济生产、商品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规定与要求,既有对黎民百姓的要求,也有对黎族头目的约束,明确了国家法律在黎区的效力。显然它是一个专门针对黎族地区的特别法,该特别法对于被平定之黎区的生产发展、社会治安和人民生活无疑是有重要的规范作用的。
在消除黎族积弊、维护地方安宁方面,黎区地方政府往往联合几个部门共同颁布安民告示,以劝告黎人安分守己:“崖州协政府黄、持授崖州正堂萧、持授都关府鲍:为晓谕各黎峒事照得黎人生于边鄙居近海滨荷……奈近年来人心日坏,抢劫频仍,执铳持枪杀人放火,日肆猖獗,罪不容诛……本州、协、府爱民如子好生为心,固不忍不教而诛,又何肯养奸姑息。兹当春令伊始,即应亲临该乡察看,尔等近来能否安分守法照章给赏……其有从前误为匪徒者概不追究,倘有顽抗不愿就抚,许各峒内人等面禀缉拏,断不干连株累……晓谕为此示,仰尔黎总管哨长及各峒男妇老幼人等知悉,嗣后务宜各安本分各安生业,父诫其子兄勉其弟,毋籍端滋事,毋寻仇报复,毋结党横行……贫者种作耕田,富者读书向学……严刑劝办,勿谓言之不早也,各宜凛遵毋违特示。一发告示一百六十张,安抚西中等处各泛黎峒晓谕崖州正堂、陆路都司会商,会印:州堂协镇光绪十年二月初八日。”①这段安民告示,意图十分明显,安分守法者赏,违法作乱者惩办,总管哨长、男女老幼都有自我约束和劝导他人的责任。在黎区由各基层政权组织颁发的类似安民告示为数不少,其内容不外是对黎人劝诫,对土官约束。这些安民告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法律规范作用。
历代统治阶级虽然对黎族地区的统治没有颁发系统的成文法,但在明清以后,除上述地方基层政府颁发张贴的安民告示外,还有针对某些具体事务而刻的“禁示碑”,立于村头要道,晓谕官民以为警戒,以进一步加强黎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在黎区常有因某一方面的事情而引起纠纷,或两村械斗,或因官员假借官府之名摊派各种劳役,引起民愤而告官、闹事,为此,官府统治者便通过凿刻立碑的方式公布禁示令,禁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奉府道禁碑”:“告示民众严禁外来商民、兵士进入黎村侵挠黎民、索诈黎民,如有违者应告官治罪。”②再如:
奉宪口口口(口为缺字)[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碑:
特受琼州府正堂随带加三级记录五次肖
为严行申禁事,照得衙门官吏、书役人等,入黎索扰久奉明禁。
本府自莅琼南,叠经申明禁令,遵行示晓谕在案。今据昌化县属大员峒、大村峒黎民符那休持呈称,该处从前奉颁示禁,日久无口,以至骚扰复萌,或借官司名色,或借差役横眉饬取贡香、珠料、花梨、大枝渡船木料、豹皮、棉花、黎峒藤、竹、鹿茸鞭、熊胆、花竹、苏木等货,奔走无期,犹索脚步陋规,膏脂尽竭。乞再给示勒碑,永垂严禁。凡遇应时公务,着落峒长办理,毋许书役擅入黎地,借端索扰,至于峒长遵照,无故不得更,以俾得黎民安堵,共享舜日尧天等情,前来当批准,给示严禁并行县遵照。嗣后倘有书役入黎,借端索扰等,捆获送究在案,除行该县遵照外,合行严禁,为此示谕告该黎峒峒长、黎民人等知悉,嗣后遇有必须应时正经公务,听候该县令传唤,峒长谕令查办,倘有不法书役借称官差,擅入黎,勒取贡香料等物,索扰黎民,许该峒峒长、黎民捆获解赴。
本府只凭严行察究,该峒长仍得所颁口示勒石,永远遵照,毋得有违,自干重咎,特示。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峒长谢根村遵立碑起)①
该警示碑的核心内容在于防止有司官吏对黎族进行骚扰,不得以各种名目在黎族地区搜刮财产,凡有公务必须与峒长协商办理,如果有官吏私自骚扰黎民,则黎族民众可以在峒长的带领下将该官吏抓获送交官府处理。
又如:
严禁碑[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代理昌化县事儋州正堂随带加二级记录三次记大功二次李为严禁私挖,照得县属亚玉山坐落黎地,土产石碌向有不法民人,潜入该山偷采,业经前县林封禁在案,未及立碑。
本府奉委代理昌篆,于四月二十日到任,合行勒石,永远封禁,所有县属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勿违,特示。②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一立
这一警示碑的内容在于勒石封山,禁止官民到亚玉山私自偷采和挖掘石碌矿藏,并且强调,所有军民人等都必须遵守,以避免驻军和官员侵害属地黎人利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奉道宪严禁碑”也是保存至今的禁示碑之一。该碑记琼州抚黎总局在黎区分布行政条例事,佚名抄刻:“记述清光绪年间琼州抚黎总局为安定黎区,杜绝滋事,针对当时黎区出现的一些问题而颁布的六条行政条例。”③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收集的碑刻中,类似具有规范性管理措施的碑文还有多例。
第二节 外部规范与内部习惯法共构的秩序
自宋将黎族地区统一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以后,在黎族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由黎族土官负责基层管理的自治型社会,形成了由外部规范和内部习惯法共同构成的社会秩序和法律体系。外部规范即中央政府在黎族地区实行的国家法律规范,内部规范即黎族自身的传统习俗与习惯。两种规范虽然效力范围不同,却共同维护着黎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推动着黎族社会的发展,并且随着中央政权的逐渐深入,外部规范吸收了内部规范的有益部分,使黎族习惯法成为国家法的一部分,嵌入中华法系的主流之中,中华法律也因此进一步成为一个由多民族习惯法共同构成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大一统法律。
一 统一法律秩序下的黎族自治
上述中央统一法律秩序的建立,将黎区纳入了全国统一的管理体系中。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虽然是在中央统一秩序管理之下,黎区却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国家统一法和黎区习惯法共同构成了黎区的法律体系。
中央所谓黎族自治,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在黎族地区的管理政策,即循其俗,施其政,以黎治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任用黎人为官,二是由黎人因俗治理。任用黎头为官,这本是唐的羁縻政策,宋代在对海南实行统一管理时则继续采用这一政策。“周仁浚《长编》云:‘初平岭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知琼州,以儋、崖、振、万安四州属焉。上谓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别命正官,且令仁浚择伪官,因其俗而治之。开宝五年,仁浚列上骆崇琛等四人。上曰:各授检校官,俾知州事,徐观其效可也。”①《续资治通鉴》卷七也记载了这件事。宋初平定岭南后,宋太祖赵匡胤任命内廷亲信、太子宫官员周仁浚“权知军州事”,他与宰相赵普谈道,岭南是偏远蛮荒烟瘴之地,不需要另派官员,只要在当地选拔一些官员因俗治理即可。宋统治者治理海南的思路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用羁縻政策,选择当地黎人授予其官职,以黎治黎。自宋之后,各朝代对被征剿后的黎族地区,均采用以黎治黎的自治政策,至清乾隆时,该政策深入到黎族的中心地带,对生黎也采用。
统治者所任命的黎族地方官员,基本上都是在黎民中有一定威信的公众领袖,如黎头、峒首之类。直到1949年以前,黎族群众一般称总管、团董、乡长等类人物为“奥雅”,“奥雅”在黎语中即“老人”的意思。这一称呼一方面说明了原始社会的长者观念仍存在于民众思想意识之中,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央政府对黎族地区实行的仍然是“以黎治黎”的自治政策。“熟黎多纳官粮,然其中地颇荒阔不可以弓丈计,唯岁纳粮若干而已。生黎则各食其土不入版籍,止设有黎练、峒长之类统辖之,遇有事峒长黎练以竹箭传唤,无不至者,其信而畏法如此。黎头辖一峒者为总管,辖一村或数村者为哨官,大抵父死子代,世世相传,或间有无子而妻代之及弟代之者,为众心所归而公立之也。凡小事听哨官处断,大事则投诸总管,总管不能处始出而控告州县。”①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黎族长老在黎族人民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他在处理黎族内部事务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首肯与认同。
黎族自治,因俗治理主要是通过土官来实现的。根据中央政府的任命,土官获得了管理黎族地区的职权与职能,土官运用黎族习惯、习俗来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解决黎民之间的纠纷。土官的行为获得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保障,黎族习惯、习俗也因此成为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习惯法。
日本人冈田谦、尾高邦雄于1942年对原乐东县重合盆地所作的调查称:“村落内部的事情,一般由各户的家长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议处理。但在家长中也有几名年长者,他们经验丰富、明晓事理且行事公正,很受人们的尊重……无论家庭琐事还是村落大事,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且大多会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做,另外,长老对外还可以代表村落处理公务。峒的事情便由代表各个村落的长老们组成的长老会来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黎族的村落和峒是由长老们统治的。现在,各黎族村都设有村长,村长对外可以代表村落处理公务。但由于这种制度是中国政府为统治黎族而制定的,所以虽然村长表面上是村子的负责人,但在村落内部他们事无巨细都要与长老们商议决定。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汉化程度较高的村子里,村长的权威在逐渐强化,在经济方面他们也变得愈加富有。即使在那些至今仍维持着古老的组织形式的村落,人们也倾向于从那些经济富裕且能力突出的长老中推举村长。然而,归根结底,黎族固有的统治者并不是村长而是长老,这一点不容置疑。”①
自宋以降,随着中央政府剿黎军队向中部山区的不断挺进,中央政权在黎族地区逐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法制权威在黎族地区日益显现。然而因其俗施其政的少数民族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使黎族人民保持了自己的传统习惯,黎族传统习惯法也在中央权威下具有了国家强制力,它的遵守已不完全是依据黎族人民的内心信念,中央权威从外部发挥了推动与强制作用。
二 共构秩序下的法律体系
随着中央权威在黎族地区的逐步确立,在以黎治黎的政策指引下,中央政府实现了对黎族地区的有效统治,建立起由国家制定法与地方习惯法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实现了外部规范和内部习惯法的有机统一,外部规范和内部习惯法共同承担了黎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
共构秩序下的黎族地区法律体系,主要由适用于全国的国家法、地方基层政府针对黎族地区管理而制定的规章、告示和经中央政权确认或认可的习惯法构成。
1.中央政权制定的国家法
由封建中央政权制定的、适用于全国的国家法,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中国的法律特色。自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开始,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典的制定,强调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将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国家法的管辖之下。海南岛虽然孤悬海外,岛上居民虽然被中原统治者认为是不知礼仪的蛮人,却从未被排除在中央政权管辖之外,大一统的法律也从未将海南作为例外而不适用。不论是《宋刑统》的“化外人相犯条”,还是《明律》、《清律》中关于化外人的规定,都将黎人包括其中,“凡化外人相犯”均依律处断。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国政府法律,更是毫无区别地适用于整个海南岛。与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相适应,海南郡县的行政建制及其官员任免,海南地区的城防与经济建设,海南黎汉各民族的刑事犯罪,等等,都是依律而设,依律而断。律以外的诸如令、例、敕等其他形式的法律,同样在黎族地区有效,是黎族地区国家法的重要渊源。明朝将黎族土官纳入地方官体制进行统一管理,君主为表仁爱之心对黎族赋税实行减免,都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而做出的。
国家法在黎族地区适用,这是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统治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不论是宋、明王朝的汉人统治,还是元、清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民族团结、法制统一、国家稳定,是统治者的共同愿望。正如清入关后雍正所言:“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是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①统一的国家法是封建国家的基本法,也是黎族地区的基本法。根据它的原则规定,黎族地方管理者制定了专门的地方法,与之不相冲突的黎族地区传统习惯得以确认和保留,并被赋予了国家强制力,黎族土官无法处理的族内纠纷最终由州县来解决,从而保证了国家司法权的统一。
2.适用于黎族地区的专门法
在黎族社会,除了封建国家制定的统一法典外,还有专门为黎族社会管理而制定的特别法、专门法。
皇帝的诏敕。诏敕是皇帝以敕的形式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册封、宣战、用兵、媾和的旨令。封建中央政权自从对黎族人民实行剿抚政策以后,对归附的黎族头人封官赐财。如宋“乾道二年,从广西经略转运司议,诏海南诸郡倅、守慰抚黎人,示以朝廷恩信,俾归我省地,与之更始。其在乾道元年以前租赋之逋负者尽免之,能来归者复其租五年。守倅能慰安黎人及收复省地者视功大小为赏有差,失地及民者有重罚”。“淳熙八年,诏三十六峒都统领王氏女封宜人。初,王氏居化外,累世立功边陲,皆受封爵。绍兴间,琼山民许益为乱,王母黄氏抚谕诸峒无敢从乱者,以功封宜人。至是,黄氏年老无子,请以女袭封,诏从之。嘉定九年,诏宜人女吴氏袭封,统领三十六峒。”②再如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招抚黎人敕谕:“皇帝敕谕琼山县南岐村黎首陈忠等:恁每都是好百姓,比先只为军卫有司官吏不才,苦害恁上头,恁每害怕了,不肯出来。如今听得朝廷差人来诏谕,便都一心向化,出来朝见,都赏赐了回去。今后恁村峒人民都不要供应差拨,从便安心乐业,享太平的福。但是军卫有司官吏军民人等非法生事,扰害恁的,便将着这敕谕直到京城来说,我将大法度治他。故谕。”①明初为惩治贪官污吏,曾设有民拿害民官制度,永乐时虽然已不允许百姓直接拿掳官吏赴京,但仍允许直接告诉皇帝。永乐年间的这道敕谕,实际上就是将中原地区实行的重典治吏政策适用到海南黎族地区。
地方官为黎族社会管理制定的规章告示。为防止黎乱,实现对黎族地区的有效治理,自明以降,大臣纷纷上奏,献计献策,其中既有关心海南的海南籍官员如海瑞,也有身处黎区担任管理者的现任官员。特别是后者,其所奏之措施大都已付诸实施,成为专门适用于海南黎族地区的专门法。如杨理在《上欧阳郡守四事》中针对黎族结怨仇杀之习惯,建议“如有冤枉,即为伸理;如有混包霸占他人村峒诡避差役者改正,无令群奸欺诳”。②参将俞大猷图说:“其各州县印官,务将管下黎人严禁,童女不得如前涅面纹身,男人务着衣衫,不得如前赤身露腿;其首各要加帽,不得如前簪髻倒颠。各村黎童之幼小者,设社学以教之,使其能言识字。每一年之间,守巡官查考各州县官变化各熟黎几村,招抚过生黎为熟者几村,具呈抚按衙门以为殿最。”③如果说上书奏议还只停留在建议层面,那么,基层政府衙门的所颁发张贴的告示,则是十分具体的在民身边的行为规范,如崖州协镇府、崖州正堂、都关府联合颁发的《除积弊安黎示二则》、《悬赏严拿黎匪谕》、《立章训黎示二则》、《饬汛弁传集各峒黎目受抚札》、《劝释黎民械斗示二则》、《严禁汉奸抢夺黎物抵债示》等告示,对黎民行为的约束规范作用十分明确具体,且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据不完全统计,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刻本的《广东琼州汉黎舆情营伍练兵稿抄》中,类似的具有约束力的告示就有二十一条之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朝廷官员关于海南黎族的治理的奏疏,还是基层政府为管理而颁发的告示,从形式上看,更似治理措施或政策,而非出自中央权威的法律。但是,正是这些治理政策或措施,规范约束了黎民的行为和思想,纠正了黎族陋俗,限制了土官对黎民的滋扰、欺诈与剥削,防范了汉人对黎民的欺骗与侵害,达到了维护黎区治安和发展黎区经济的目的。而且这些措施与政策是由权力机关颁发,多有相应的处罚与奖赏,其权威性、拘束性、指导性十分明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管理法规。
清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冯子材剿定黎乱后,与之拟定《抚黎章程十二条》,并上书光绪皇帝。为了对黎区实行有效治理,冯子材在海南着手实施《抚黎章程十二条》。该《抚黎章程十二条》是为被剿平之黎区进行善后管理的专门抚黎政策,虽然如开路等经济措施未及实施,但在黎人的文化教育与旧习改革方面得到了落实并取得了明显效果。《抚黎章程十二条》虽然不是专门的地方法规,却发挥了地方法规的作用,其实乃黎族地区专门法的典型代表。
禁示碑。如果说黎区专门法尚带有黎族治理的政策措施或建议性质,那么,黎族地方官府刻立的禁示碑则是典型的地方性规范。因为禁示碑是根据黎族地区经常发生的纠纷而刻立的,通过禁示碑的警示功能,达到防止该类纠纷或冲突的再次发生。上文中关于禁示碑已有例举,此处现举一例以说明之。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立,“奉宪永禁扰索示碑”,佚名抄刻。碑文记叙从清嘉庆年间到道光年初,再到道光十四年,官员民丁对当地黎人百姓敲诈勒索越来越严重,多次激起民变,为了调和民族矛盾,加强清政府的统治,特立此碑,严禁地方官员与兵丁扰民,革除弊端、安抚黎人百姓要安心守法。碑文还注明该碑是由官方、多港刘峒长、德霞、抱由及众村总管、哨官、头家、村老等同立,意在禁止文武衙门一切扰黎陋规,以安黎人民众。①有些禁示碑虽然由黎民自行刻立,但基本上都是经过官府认同,仍具有地方立法性质。如:
凭示勒碑[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署昌化县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凌为准自行投纳事,今于抱上都摘出水头村、坡威村、居索村、居新村、落洒村、哥霸村黎粮一十六户,共应纳地丁征银九两,大钱五分四厘正,遇闰每两加银四分六厘五毫,准该黎户符那横等,每年限定三月初十日着落哨官游马传符养外兴老大、老二、万方等六名自行来县投纳清楚,以免粮差下村加征,滋扰黎户。每两定折收纳铜钱二千三百二十文算,共应折铜钱二十乙千四百三十二文,该黎户不得违误,过限致干并究,特示。
符登葵代[请峒长绅士林开甲进官讨示]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吉日众黎户建立。①
3.习惯法
在黎族传统社会里,指导村峒部落成员行为的主要是习惯、习俗。这些习惯习俗是黎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婚姻家庭和经济关系中逐渐形成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中央政权对黎族地区实行管辖,国家法在黎区生效后,那些与国家法不相冲突的习惯习俗被中央政权所确认或认可,赋予国家强制力,成为习惯法,对黎族群众继续发挥着规范调整作用。黎族习惯法内容广泛,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的还与宗教规范、道德规范难以区分。总体来说,黎族习惯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禁星。作为一项原始的习惯法规则,黎族的插星在上一章中已有具体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此处需要强调的是,由于黎族没有文字,对于民间出示广告、启事、禁令、订契之类,都使用插星的符号来表示。每逢生小孩、猪下崽、家中有人生病或播种、酿酒时,黎人都在自家门口挂树叶,禁止外人进屋。除宗教性质外,插星仍然主要用于财产占有、停止侵害等财产所有权和民事交往方面,大到山地、鱼塘、果木,小到茅草、蜂窝,即使是一时不能利用,黎民如果意欲占有,便用插棍结草或划“×”型符号等形式,做上记号以保护下来,表示此物已有主人了。具有告示和警示功能的插星,在中央政权对黎区实行有效统治时期,仍然是黎族人人都需自觉遵守的习惯,如违反了,违者不仅将被众人谴责为不道义,将来有困难时得不到众人的帮助,而且还可能被认定为盗窃罪,受到同胞的追究和官府的制裁。
(2)刻木为契。刻木为契是初民社会应用比较广泛的交易立信方式,黎族没有文字,深居深山,日常交易,以物换物,各得所需。但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田、地、牲畜可以买卖抵押时始出现刻契交易。“山地的批租,银钱的借贷,往来货物的订购,承揽其彼此的契约,都以竹箭代之。其法以竹管一段,用刀刻纹标志记号。刻毕了后,自竹管正中破分为二,彼此例如执,以为凭据。”①在《黎族三峒调查》中称这种记录借贷的借据或票据为“对牌”②。依据该刻契,无论过了多久,子孙都可持契据前来讨债,如果借方偿还了部分,则双方都要将契据的相应部分切掉,债务全部还清后,则双方都废弃契据。契据的制作要在长老的监督下进行,大家一起喝酒。与刻木为契相类似,反映黎族人民在民事交往中记事、守信的做法还有结绳记事和砍箭为信。③
刻木为契不仅在黎族民间交往中盛行,而且还被官府所认可,用来处理政府与黎民的关系。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参将何斌臣会同知州曾邦泰,差官兼里排,招抚儋州黎岐、恶来、催顶等八十村,刻箭承认粮税编册”。④这是黎族刻木为契的具体体现,官员与黎民一起刻箭确定粮税编册,这不仅说明中央政权承认了黎族刻木为契的习惯规则,而且还将其适用到社会管理中来。
(3)峒组织习惯法。直到1949年前,峒仍然是黎族地区县以下的主要基层组织,虽然峒是“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但该地域内的居民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峒内各血缘集团还保留着各自的公共墓地和共同的祖先崇拜。正是基于这种血缘上的联系,峒组织内部有为峒内成员共同自觉遵守的习惯、习俗。这种习惯习俗在自然法秩序时即已存在,在中央权威的统一管理下,峒组织习惯得到了国家政权的确认与维护,成为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习惯法。峒组织习惯法不同于禁忌的意识控制,它是黎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世代相传的一种行为准则。峒组织习惯法包括:
对峒疆界和财产的保卫责任。黎族每个峒都有固定的地域,峒与峒之间一般以山川河流为界,当一峒通过插星宣布自己的区域范围以后,其他峒则不得侵犯,也不得越界活动。峒辖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峒管辖的土地、山林、河流等属于全峒人共同所有,未经许可外人不能越界砍山、开荒、采摘、伐木、打猎、捕鱼和居住。若需越界须经本峒许可,还要上缴一定数量的物产给峒长,上缴多少视行为和内容而定。打猎、捕鱼需上缴猎肉和鱼,砍山开荒、居住,则需上缴猪、牛等物品。峒内成员有保卫本峒疆界和共同财产的责任,当外人侵犯了本峒利益而发生械斗时,全峒人都要参加战斗,共同负担战斗所需费用。
峒内成员相互援助和保护的义务。峒内成员不仅要保护峒的公共利益与疆界,而且彼此之间还要相互援助和相互保护,全峒人也有保护峒内成员的私有财产不受他人侵害的责任。特别是本峒人受到外峒人欺侮时,必须帮助他复仇。
械斗是解决峒村矛盾的主要手段,参加械斗、共同负担械斗时向外请援兵的费用,则因此成为黎族人民为峒村利益而必须承担的责任。
响应信传召唤的义务。黎族人民居住在山区,峒内各村都有一定的距离,每个村人口比较少,耕地也比较分散,因此,在需要结集村民或峒内黎民时,黎族人民有几种传统的传信方式。一是击鼓传约,“头家或族长家内,常备有大鼓一面,有事时击以为号。或遇盗,或办公差,或议事,击法不同,村人则闻而知之。鼓声响处,村人毕集听命”。①即在村长家门口悬挂一面独木大皮鼓,每当村里有急事需通知大家时,村长便击鼓传约,村民根据鼓点的节奏、轻重缓急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如果是械斗村民会很快拿武器到村长家集合待命。二是鸣枪传约,主要用于人死亡时的通知,当村里有人死亡时,几把猎枪同时朝天鸣放,附近村峒的人就知道那个村子有人死亡了,有亲戚关系的人就会去奔丧。三是断箭传信,即用斩断的箭头去联络各村寨(各地区)的群众,主要用于黎族人民起义时或起义过程中的联络,或受到外敌入侵时向异地村寨求援,受箭的村峒村民依约到指定地点集合,及时前往支援受侵的村寨抵制外侵。①四是鸡毛信,即用一根雄鸡毛加一对辣椒送给友方,友方就知道对方有战事,会快速击鼓鸣锣集合去支援对方。
虽然上述几种传信方式较之今天十分原始,在黎族地区却是普遍适用、十分有号召力和强制力的通知或通告方式。为了村峒的集体利益或村峒成员利益,积极响应信传,及时救援,是黎族内部严格的族规之一,是黎族人民必须遵守的公共秩序。清张庆长的《黎岐纪闻》就记载了这一传信规则:“遇有事,峒长黎练以竹箭传唤,无不至者,其信而畏法如此。”“头目有事传呼,截竹缚藤,以次相传,谓之传箭,群黎见而趋赴,若奉符信,无敢后者。”②击鼓传约、断箭传信,黎民对之的认同与遵守,犹如禁忌中对神灵鬼符的信仰,十分虔诚与自觉,究其原因,一是来自黎族人民朴素的族群意识,二是来自峒长黎头的权威。
(4)神明裁判。神明裁判是原始宗教的产物。当人们对某事物缺乏识别能力和不能以确凿证据判断某事物解决争端时,就通过神明的指点,来判断事情真伪并给予嫌疑人以处罚。海南黎族如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也用神明裁判来维护族内社会秩序的稳定。海南黎族的神明裁判主要是鬼神判和雷公判,这与海南黎族原始时期对鬼神、雷公的崇拜是密切相关的。
神鬼判主要用于对通奸、盗窃等行为的裁定。对通奸的审判主要采用火判,如果丈夫怀疑妻子与人通奸,但又没有抓住把柄时,就采用令妻子踩过燃烧的木炭或火灰,眼睛是否变瞎来判断是非。③眼睛变瞎,在当时的黎族社会,意味着丧失劳动能力,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让其眼睛变瞎,是鬼神对犯事者十分严重的处罚。雷神判主要用于盗窃时的审判。如某个人的财物被盗窃,但又没有抓住盗贼,只是怀疑某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被偷的一方还是被怀疑的一方,都可以以理亏遭雷劈的誓言或咒语,来证明自己的判断或清白。人们相信,雷公会劈死做亏心事的人。①神鬼判、雷神判是黎族维护和执行本民族习惯法的一种辅助而又具有强大威慑力的手段。黎族人民信仰原始宗教和巫术,十分相信神鬼判的效应,因为对鬼神的禁忌而产生了心理约束力,因此,神鬼判、雷神判这种神明裁判本身也成为黎族习惯法的一种,是一种解决纠纷的习惯法。神明裁判的结果不仅对当事人双方产生约束力,对其他人也产生心理畏惧和行为约束的警示效果。
(5)血族复仇。在汉人眼里,黎人善射好斗,积世之仇,也要记报,对此,古代文献多有记载:“重报仇,有杀其父祖及乡人者,易世必复。”②
《海槎余录》:“黎人善射好斗,积世之仇必报,每会聚亲朋,各席地而坐,饮酣,顾梁上弓矢,遂奋报仇之志,而众论称焉。其弓矢盖其祖先有几次斗败之耻,则尅箭几次,射于梁上以记之。”③《琼州海黎图·械斗图》:“黎性重仇杀,轻生死,与滇黔苗倮同,挟器惟标枪弓矢,健者则衣著吉贝,头缠红布,乘牛驰骋,以示夸耀云。”《黎岐纪闻》:“一语不合,辄持弓矢标枪相向,势不可挡,有妇人从中间之,即立解。”④中共广东省委1928年4月26日在琼字第二号《致琼崖特委信》中也说:“黎民运动在琼崖暴动愈加发展而愈严重,他们头脑简单,且贪鄙好斗,据C.Y.报告上说很易受酋长之骗。”保亭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张应勇在《奇特的骨片——黎族氏族恩仇报答标志实录》一文中记录了什聘村人恩仇必报的故事,展示了黎族的民族性格特点。他认为,这件事情很有民俗价值和历史意义。他说,什聘人对于家族的恩仇信息采取刻骨铭记的方式世世代代进行传递,记仇是在动物骨片上刻一只箭头,记恩是在动物骨片上刻一片榕树的叶子。
三 国家法与黎族习惯法共构的法律秩序
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权威下,中央统一法律、地方规章制度与黎族习惯法分工协助,各司其职,共同构建了黎区的法律秩序。
一般说来,在调整范围上,中央统一制定的法律以及基层地方政府制定的管理规章主要适用于涉及国家统一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的领域,地方政府的建置及官员的任免、考核,总管、哨长等土官的任命与授权,国家税赋徭役的征收与分派,暴乱、械斗抢劫、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黎族习惯法则主要调整黎族人民的婚姻家庭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事宜,如结婚仪式、离婚调停、土地买卖、财产转让、祭祀驱鬼、偷盗等。在主体方面,与中央政权相适应,地方政府衙门既是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他们代表国家来适用法律,但在具体事务上,多由中央政府任命的黎族土官来负责,峒长、哨官、头家负责案件裁决,“凡小事听哨官处断,大事则报诸总管,总管不能处断,始出而控告州县”。①土官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多依黎族习惯法处断。如偷窃,如果偷窃的是合亩内的共有财产,偷窃者则会被抓送到总管、团董或乡长那里去判处,一般是加两三倍的罚款,一份给失主,另两份作为合亩内的公共财产,另偷窃者还需拿出米酒宰牛宴请。如果偷窃私人物品,则处罚方法同上,但不另加罚给失者的家族。如果惯偷屡教不改,则可以判处杀死,如果被偷的是黎族土官,则偷窃者会被他们杀死。②
总体说来,在中央统一权威下,黎族社会虽然直接由国家法律来统一调整,但是,受国家法律影响较大的是基层政治组织及其官员。对普通的黎族民众来说,本民族的传统习惯才是他们需要自觉遵行的规范。氏族长老在生产生活中传承了习惯法,黎族土官将传统习惯法与中央法律有机结合起来的,使习惯法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有了更高的权威。如果说国家法是外部规范,习惯法是内部法的话,那么,自宋以后,由外部规范和内部习惯法组成的法律体系,十分有效地构建了黎族社会所特有的法律秩序,保障和推动了黎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第三节 土官制度及其传统权威的变化
土官制度是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土官,就是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居住区封赐的能独霸一方的世袭统治者或官员。土官制度是在唐羁縻州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中央政府认命民族首领为世袭官员,统治其所在的少数民族。清雍正年间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终结了土官在本区域的独霸地位,加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与实际控制。
一 土官制度的基本情况
北宋开宝年间“初平岭南”后,“命太子中允周仁浚知琼州”,同时也确立了“因其俗治之”的管理政策。在被征服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招抚黎族头人归降,并对归附之峒首授官封爵,正式拉开了海南黎族土官制度的序幕,以黎族峒首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土官制度逐渐发展为定制。封建王朝在海南黎族地区实行的土官制度,对黎族社会传统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将黎族传统习惯上升为国家确认的习惯法的过程中,土官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虽然自宋代开始,中央政权就注重对海南黎族地区实行统一管理,但其羁縻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海南黎族地区的土官制度,在宋代多为虚职,且品级低下,如:宣人,为县君之封,承信郎、承节郎、进义校尉等均为品级低下的散官衔。元代土官乃始为实职且拥有实权,官职品级也高,最高至正三品。元世祖至元二十八至三十一年(1291~1294年),海南岛统治当局对黎族人民进行大规模军事镇压,连续用兵3年,得峒600、户口23827户,之后,设立“黎兵万户府”和“屯田万户府”,黎兵屯田万户府与黎峒千百户的头目皆为黎族酋领担任,世袭为之,管辖当地军事和民政,官给土、牛、种、农器,免其差徭。黎族土官势力的壮大,使“以黎治黎”政策得到了有力的推行,中央政府在黎区的统治势力也因此得到了较大的加强。
明代的黎族土官制度发展得相当成熟,达到其鼎盛时期。明代初年州县官不用土人,废除元朝所设黎兵万户府,曾有一部分黎族土官不愿出官附籍,甚至据峒抵抗和反叛。于是明朝便加强军事统治,在海南设军事卫、所,立屯田22处,每一处有田20顷以上,实行兵农合一。洪武五年(1372年)设1卫、1 1千户所、额设旗军15927名,马160匹。又在交通要道与通往黎区的路上设巡检司22处,从黎人中点签弓兵450名。另从民户(汉族为主)中抽选“机兵”(又称“机快”),民户30丁选“机兵”1名,共约2195名。
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黎族地区实行“土官、土舍”制度,授以黎族峒首各种土官职衔。永乐二年(1404年)琼州府文昌县林彬招抚黎峒30余村,被授土官典史,可世袭;崖州监生潘隆自愿请求招黎归顺,被授予知县职名。有明一代,黎族地区的土官制度共有两种模式。
1.“土舍、土官”制度
明代从永乐年间起,在海南建立土舍制度,这是在卫所之下设立的地方武装,有土舍41所,辖黎兵2704名(后有变动)。土舍是由当地有势力的黎族峒首担任,专管黎兵。黎兵叫做“峒丁”,遇有调发随军出征,平常则派守各营地。但后来土舍的权力膨胀,土舍恃其掌握的黎兵武装,与州县官勾结,包揽征税和诉讼,鱼肉黎民,“征徭任其科算尽入私囊”,操纵了黎区基层实权。明朝还实行了“以峒管黎”的办法,凡遇公差、纳秋粮,有司俱凭峒首催办,官军征捕,亦凭峒首指引。永乐年间曾招谕许多黎族峒首“赴朝受职”,根据他们招抚“生黎”的户口数,明朝分别授给州同知、知县、县丞、主簿、巡检等土官。土官实行朝贡制度化,每三年峒首必须向朝廷进贡一次,以示对朝廷的忠诚。土官管政,土舍管军,军政分离,明朝的黎族土官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设立土官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归顺的“生黎”就有1670峒,3万余户。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琼州府又设置“抚黎”通判,专管黎事。但至明代后期,由于人民不断反抗土舍、土官的横征暴敛,以及“扶黎诸官夺州县权”等弊端,遂于正统五年(1440年)后相继革除土官制及“抚黎”流官,又逐渐限制土舍行令,更换土舍为粮长,对其所管黎人纳入编户,划归“甲首”管辖。
2.“黎都黎图”制度
这是熟黎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明朝将归附已久,所谓“熟黎”的黎峒统一编入行政区划,即在基层设“黎图”,若干个“黎图”为“黎都”,若干个“黎都”为一乡,乡为流官隶属州县。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使“熟黎”与编户的汉人一样编入都、图,载进鱼鳞册、黄册,要纳粮录差。综合地方文献,海南岛“熟黎”被编入黎都黎图者凡28都、75图,包括155峒,它们以岛的北部与沿海地带居多,岛的南部及山区较少。如琼山县有5都9图,包括9峒;澄迈县有5都60图,包括137个村峒;定安县有3都4图,包括7个峒;陵水县不设都,有2图;儋县有5都,不设图,“黎居良民五分之一”;感恩黎“附版籍者什九,不附者什一”;唯南部“崖州黎其地多于州境,其人十倍之”。至明末清初的发展趋势则是,“则古之书村峒者,今皆为都为图矣”。黎都黎图制的推广,促进了“熟黎”封建化的完成,使“黎地渐归豪民,黎人归化最久,与齐民等”。特别是在岛的北部与东部,如定安、会同建制以来,黎峒大都入籍,琼山县南歧峒等黎、文昌县斩脚峒等黎,悉输赋听役,与“省地”百姓无异。①
清朝沿袭明朝的行政建置,琼州府下辖3州、10县,除文昌、会同2县之外,其余8县皆有黎族人。“清王朝在沿袭明代黎族土官制基础上,进一步削弱了黎族土官的权力,州、县一级官府已不设黎族土官的职位。清代建立的黎族土官制,主要是在黎族峒的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峒’下设峒首、黎总、哨管等职,‘村’则设黎甲或黎首,黎族土官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所属村峒的日常事务,和遇黎人造反时,承担协助清军作战与招降之责。”②雍正九年(1731年)起,便在黎族地区推行“总管”制度,即在州县之下各黎峒上层首领被委为“总管”(辖一峒或数峒)、“哨官”(辖一村或数村)、“头家”(每村一名)等土官。有的地区(如陵水、保亭)称村峒为“弓”,每五“弓”设一“总管”。各峒还有“峒长”(亦称“总头”),是从氏族的“奥雅”(长老)中产生的,“峒长”协助总管处理行政事务,总管因事外出峒长可代理其职务。总管与哨官皆是世袭的,但要报封建官府委派,赐以印牌及官服。“凡小事听哨官处断,大事则报总管,总管不能处始出报告州县。”③如在黎族众多的崖州分东西两界,东路黎族村峒独多,广袤300余里,向设总管6人、哨官13人、峒长6人进行管理;西路村峒纵横200余里,向设峒长6人,总管3人。
而在“熟黎”与汉族杂居区,则将“黎都黎图制”逐步改为“里甲制”。如澄迈县虽有黎都之名而无黎人之实。据统计,自明嘉靖到清道光不到三百年时间里黎村峒减少了30%,清代统治力量深入到黎族大部分地区。
民国初年,海南岛的行政建置仍沿袭清制,置琼崖道,共辖13县。民国十年(1921年)废道制,由粤军旅长兼领琼崖善后处处长,掌军民两政。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广东省政府辖下设琼崖行政委员会,并从琼山县划出海口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抚黎局”为“抚黎专员公署”,并改“总管”为“团董”,加强对黎族地区的统治。接着又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黎、苗聚居的五指山区新设白沙、保亭、乐东县,推行乡、保、甲长制,至此,基层官员已完全纳入中央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中,土官之概念逐渐模糊淡化。
海瑞《上兵部条议七事》第七条称:“黎岐归化,当编其峒首村首为里长,所属之黎为甲首,出入不许仍持弓矢,原耕田地听从其便。其山林可开垦者并绝黎田地,宜招方外无业民耕作,结为里社,与黎岐错居。”
参将黎国耀《条议二事》建议道:“一编保甲。琼州等县原设有牌门乡盟兵,择其豪者为乡勇、哨官或保长以领之。村落大至百余人,小亦不下数十人,闻警息即听有司调集,协同营兵防御,以故寇多不敢犯。近因宦家买置庄田,名曰‘宦庄’,一切佃丁、乡盟人等概获优免,既有警叫调不应。甚者又有豪奴悍佃,窝匿逃亡奸盗,莫可究诘。而各宦庄亦瓜分,势寡不能自卫,遂至束手无措。顷者定安光螺岭上下之事可鉴已。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今督抚令抚黎官亲履各地方,核其户口,稽其生业,无论势宦,一概佃丁、厮役、乡邻,尽籍其壮者为兵。其中有行能者佥为乡勇、哨官,次为保长,分领其众。除农隙讲武外,无事不许辄行差遣。遇有黎岐出没,集众防守,悉听有司营官调发。”①
二 土官权威的变化
峒的组织是黎族社会独具特色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封建王朝中央政权统治之前,它是维持黎族社会内部正常秩序和推动黎族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自治组织,其峒首是黎之头领,“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大抵父死子代,世世相传,或间有无子而妻代之及弟代之者,为众心所归而公立之也。”①熟黎,“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今仅择豪强者充之”。②村头、黎首乃由原始血缘氏族长老演变而来。原始血缘氏族的长老,通常都是本氏族辈分最高、经验最丰富、威望最高的人。他们能说会道,办事能力强,有威信,明事理,讲公道。在黎族社会,这些人通常都是老人,被称为奥雅。鉴于他们的权威与能力,以及氏族成员的血缘关系,黎族长老们被推选为本村峒的管理者或头人。
中央政府在黎区实行土官制以后,过去村峒的黎首被任命为朝廷命官,成为地方的一级行政官吏。基于其原本的黎头身份,这些土官仍拥有在本村本峒的权威和势力,成为兼具黎头和基层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和职能。后一种身份对他们来说,更具吸引力,渐渐地完全成为中央政府在黎区的行政管理者、法律政策的执行者、地方治安的维护者、赋役税收的征办者。
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法秩序之下,黎族土官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身份变化。由原来村峒内部的选举形成和世袭,变成了由中央政府委任与授权,成为政府官员,代表中央政府管理黎族地区,为政府办事,土官开始步入封建统治集团的行列。其次是权力来源的变化。虽然是由黎头演变而来,但其权力来源却已不再是基于氏族长老权威,或是氏族成员的推举,而是中央政府的授予,其背后是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与保障。再次是,权力范围扩大。虽然宋时黎族土官仅仅是个虚职,但其所拥有的官职与官衔,已足以让其在黎族百姓中拥有更大的权威。元朝的黎族土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权威已发展到顶峰。明朝虽将土官的军权与政权拆分,但并未影响到土官所拥有的统治权。有了政权或军权,成为封建政府在册官员,土官较之原本的纯粹黎族头人,其权力范围得到了极大地扩张。最后权力变化产生了人格变化。在取得中央政府授予的权力以后,黎族土官逐渐脱离了原本平等的黎族血缘团体,开始享受各种特权,依据自身在黎区的威信和手中的政府权力,开始豪夺巧取黎民财物,强行占有村峒的共有土地、山林,成为剥削阶级,盘剥百姓,欺骗国家。正是由于土官身份能带来好处,招来了一些汉人冒充黎头充任土官,如《道光琼州府志》记载:崖州东西二路黎村,“熟黎向归里长管辖,生黎及生熟各半黎旧设有峒长、哨官等名,由黎人自行保充。后有不肖绅民假名混保,快其所私,以致黎众不服,因而滋事,今已革除”。①
部分黎族土官在黎族地区的欺上瞒下、挟乱自重,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引起黎族人民反抗,因此,至清末土官制度逐渐被削弱,有的甚至被革除。如崖州东黎境内,过去共设有峒长、总管各六人,哨长十三人,到光绪年间,则只剩下总管之职,而且还没有定额,各村则由自己设立头目一人。实行保甲以后,黎族土官制完全被保甲制所取代,黎头之身份在保甲制之下不再得以体现或享有特权。
黎族土官及其权威的变化,究其原因,一是中央权威在黎族地区发生了效力,中央政权的进入,统一法律秩序的建立,打破了黎族传统的血缘氏族结构,直接导致了黎族社会的分化;二是黎人思想变化的结果,在与汉人相处后,黎族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汉族官员所享有的特权与待遇,令黎族土官向往与羡慕;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黎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与外界民商事交往的频繁,黎族人民的财产私有观念得以加强,随之而来的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黎族土官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仗势敛财乃成为必然。当然在这些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中央政权的进入,导致了黎族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央政府发展经济的举措,导致了黎族土官财富观念的变化,中央政府将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输入与推广,引起了黎族人民思想的变化。
第四节 习惯法秩序的变化与传承
随着中央政权进入海南黎族地区以及统一法律秩序的建立,黎族人民在固守自己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的同时,也享受着外面世界的新鲜气息。学习接受中原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学习汉语,接受中原文化教育,在与汉族人民的接触交往过程中,思想认识、文化水平、经济观念、文明意识等等,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他们改变了自己,改变了千年固守的习惯习俗。在黎族习惯法秩序方面,不论是婚姻家庭、民事交往,还是血缘族内的公共秩序与规则,都在传承中有所提高与改进。
一 婚姻家庭习惯法秩序的变化
(一)婚姻
婚姻是维持人类自身繁衍的一种手段,也是一定社会秩序的体现。丰富多彩的婚恋习俗能够集中展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同时,这些习俗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根据对古籍资料和20世纪前叶社会调查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宋以后,黎族实行的仍然是嫁娶婚,且为氏族外婚,其婚姻成立的过程与方式仍与古代保持一致。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观念的增强,黎族人民与汉民族交往的增多,黎族的婚姻习惯法秩序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婚姻成立的整个过程中。
1.恋爱方式
对歌、“玩隆闺”是黎族传统的恋爱方式,这种自由恋爱方式到了近代,依然盛行,现今黎族传统的节日“三月三”①与对歌不无联系。据史料对黎族青年男女春夏之交聚会的记载,可以推测这是对“三月三”节日的描写。如《民国儋县志》记载:“春则秋千会,邻峒男女妆饰来游,携手并肩,欢歌互答,名曰‘作剧’。有乘时为合婚者,父母率从无禁。”②可见,这一时期黎族男女通过这一大型的集会恋爱是很普遍的,而且从集会的时间上来推测,这些大型的集会便是黎族的传统节日“三月三”。
黎族传统的通过“隆闺”恋爱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依然存在。《海南岛志》记载:“一般女子年纪长大,父母必为之别营居室,听其自由交际。男子之未娶者,入夜辄出游于此类之女子私室中。”③《海南岛新志》记载:“女子及笄,即自由营私室,以与男子交际,待情投意合时,经父母同意,即可结婚。”①而且,在“隆闺”中谈恋爱的不仅是单身女子,已经订婚的女子和结婚未落夫家的女子也有自由在“隆闺”中恋爱。《海南岛志》记载:“其既与人结婚而返居私室之女子,常易与他男子发生恋爱。”②
除对歌与玩“隆闺”外,通过媒人的说合而建立恋爱关系也逐渐增多起来,许多青年男女通过媒人说合后建立了恋爱关系。俗话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说媒是传统婚姻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行为,即男女双方一般都要经人从中说合,才能成为比翼鸟,结为连理枝。这种方式叫“说媒”。这在史料中也有记载:“西部如崖、昌、感、儋、临等县,女子10岁前,凭媒说合,男家备具酒肉、月饼送女家,谓之‘讨真命’。”③“父母常常按汉族的风俗经媒人介绍将女儿嫁给汉族。”④《海南岛志》记载:“黎人婚俗,多取自由择配;亦有凭媒说合者。”⑤在父母托人说媒的婚姻中,偶也传出包办的声音,如黎族传统民歌《叫我怎么办》:“命运真惨,婚姻母包办,红颜配白发,叫我怎么办!”⑥
2.订婚与结婚
古代黎族就有订婚的习俗,女方同意结亲后,男方即选定吉日订婚。订婚要有一定的信物为凭。订婚信物通常有两类:
一是以“箭”为订婚的信物。如《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中提道:“婚姻折箭为定。”⑦《康熙广东通志·琼州府》:“定婚折箭。”⑧在黎族的传统民歌中也有“定婚折箭”的记述,如《我求了又求》:“(男方)亲家母(呀),如果我早认识你家姑娘,亲家母(呀),那我早就带箭来,到你家屋梁下。亲家母(呀),那我早(呀)就整装来到你家楼梯旁。我十天求了又求,我求好像是盼望了六年等稻谷进仓。亲家母(呀),你千万别让我失望。”①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古代黎族有“定婚折箭”的习俗。
二是以“槟榔”。槟榔为订婚中不可缺少的聘礼。这在黎族传统民歌中有记载,如《同吃槟榔来订婚》:“一口槟榔分两份,同吃槟榔来订婚,劝妹要学槟榔树,从头到尾一条心。”②黎族有句俗语:“一口槟榔大如天。”如果女方吃了男方送来的槟榔,就证明女子同意了这门亲事。据《光绪崖州志》记载,黎族订婚时:“俗重槟榔。宾至,必先以敬主,主亦出以礼宾。婚礼纳采,用锡盒盛槟榔,送至女家。尊者先开盒,即为定礼,谓之出槟榔。凡女受聘者,谓之吃某氏槟榔。此俗,琼郡略同,延及闽广,非独崖也。”③
不论是订婚还是结婚,男方都要给女方家一定的聘礼。古代黎族一般以牛、槟榔、吉贝、黎布等作为聘礼。这在黎族的资料中有所记载:“以牛马多寡为婚礼厚薄。”④《琼州志》记载:“男女相悦后,男随托媒持绒线至女门,女亲受之,谓之结绳。又以槟榔、耕牛、吉贝、黎布等聘之。”⑤民国时期,聘礼有所改变,增加了聘金、酒、米等。“一头猪,一缸酒和一只鸡。女子的父母接受这些礼物,便算正式订婚。”⑥再如《海南岛新志》记载:“结婚聘金,以牛、酒为之。”⑦《民国感恩县志》记载:“迎婚聘礼,取生牛两头、猪肉六十斤、米二石、酒一缸。”⑧聘礼的品种向实用化转变。
除了一如既往的以实物为聘礼外,货币开始成为聘礼的一种,据《光绪崖州志》记载:“纳币,书男女命于笺,赍金币礼物,送至女家,谓之押命”。①当男方家不能提供牛这个聘礼时,可以将牛折算成光洋缴交。②
在婚礼仪式方面,古时,据史料记载黎族的婚礼仪式基本上包括:“送礼、送亲、伴眠、屋造、同居。”③“吉日,男家送绣花桶为礼,女家亲戚凡年幼未婚者竞送钗带等物,亲送女至夫家,夫家幼女小儿伴新妇眠二十余日,俟造屋毕,斯成亲同居焉。”④到了近代这些仪式基本保持但稍有变化。
据《光绪崖州志》记载黎族结婚时:“女家有婚嫁事,东里则聚内外眷属,艳妆往贺。女家饰其女,奉槟榔出见。各赍首饰金银为彩,谓之出新妇。西里无之。择吉请期,送聘礼,谓之送日子。冠不三加,娶必亲迎。入门谒祖,谓之拜堂。次日拜谒尊嫜,谓之出拜。三日女婿旋车,谓之回门。大抵礼俗,东西相去不远。惟近日富家竞斗奢靡,贫者每援为例,亦有终身不能娶者。”⑤
民国时期黎族一些地区的婚礼仪式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包括:送亲、迎亲、摆宴席、对歌、逗娘、回门。
送亲。《琼崖志略》记载:“举行婚礼时,九代亲属男女各持牛猪鸡酒前来庆贺,女家亦遣陪嫁者数十人送新妇过门。”⑥
在结婚条件方面,黎族仍然保持了各种婚姻禁忌,禁忌血缘婚,婚姻在不同的氏族间和不同的方言间缔结。根据《黎族三峒调查》显示,黎族“重合老村村民的范围,大多局限于本村本峒之内,与盆地外同一方言的人通婚非常少”。⑦这说明黎族人的通婚范围实际上很小,通婚对于同一方言间黎人的意义不大,却对加强村落的凝聚力十分有利。另外不同方言间不得通婚的禁忌偶也有被打破的现现象存在,这从《黎族三峒调查》第25页注释2中可以看出。
一夫一妻制是黎族自始以来实行的婚姻制度,并且也切实遵守了这个习惯法秩序。但是近代以来,黎族社会中出现了纳妾现象。根据《黎族社会调查》上下两册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黎族中很多乡村在新中国成立前有纳妾现象的出现,纳妾者大部分限于村长及其他一些有钱有势者。同时有的是因年老无子而纳妾,有的已有儿子,但因家庭缺乏劳动力经妻子同意,并由妻子去征求某女子愿做妾的。新中国成立前,还有有钱有势的人,抢夺穷人的女子做妾的。《黎族三峒调查》中也谈到了黎族的纳妾现象:“在黎族中,纳妾者虽然数量极少但却是存在的,这或许是受了汉族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只限于村长及其他有钱有势者。在本次调查的调查地,龙眼村的村长便纳了妾。”①
实际上,原始黎族社会是不存在纳妾制度的,它是随着汉民族文化的逐步传播而得以形成的。可以说,黎族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最终形成是封建制文化的结果。
3.婚姻关系
新媳妇在结婚后两三天内即回娘家,住在原来的隆闺里,过着与婚前一样的单身生活,这种“不落夫家”的婚姻现象到了近代仍然存在,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婚后即回夫家常住。陈铭枢在《海南岛志》中详细记述了近代黎族婚姻关系的微妙变化:“结婚后在男家宿一宵仍回私室,迨生育后始回男家;或从定婚直至生儿后始回男家者亦有之。近来此风稍变,婚后即回夫家长住矣。结婚前,由男家送牛酒食物至妇家设宴。宴后,女子步行至男家,或由新郎邀朋友数人至女家接带,亦有由女家择伶俐妇女数人送新娘至男家者。女家富而男家贫者,男或先在女家做工,至若干年月,由女家赠送牛只、田地,使之成家。亦有先同居数年,待有积钱再举行婚礼者。其既与人结婚而返居私室之女子,常易与他男子发生恋爱。然其事若为其夫所闻,则往往持刀枪寻仇斗杀。青年男女以此伤其生者,不可胜计。故有此种既婚女子私室之村,夜必闭户,盖虑因女室酿祸而波及也。女在私室生儿后,抱归男家。所生之儿未必即为本夫所出,例不之责,惟此类之儿多不得为家主,如无第二儿则属例外。女子居私室时,其动止甚自由,迨既入夫家,则一切惟夫所命。黎俗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制裁极严厉。女子既嫁,不喜落家,此殆其一因也。”①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黎族婚姻关系的几点变化。一是夫妻之间的忠贞在近代得到了黎族夫妻的重视,不落夫家的女子性自由习惯因此受到了挑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发生,女子婚后宁愿选择落入夫家居住;二是财产在婚姻缔结中的地位提高了,男家如果贫穷,不能举行婚礼,则可以先同居待有钱后再举行结婚仪式,如男家不能为新婚夫妻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则男方需要为女方家提供一定期间的劳役,然后由女方家提供牛只、田地;三是开始重视子女血缘的纯正,虽然女子婚后生育的第一个儿子仍能被夫家接受,但是该子的家庭地位受到了限制,他不能成为未来的家主。很显然,黎族婚姻关系的这些变化,使得黎族的婚姻越来越与汉族接近,其婚姻受汉族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4.离婚
黎族人在离婚方面,没有太多的要求与限制。黎族长期坚持离婚自由原则即协议离婚的自由,夫妻感情不和,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离婚的要求,并且所有的合乎情理的离婚要求,都会得到众人的理解和社会的支持。
男女双方若协议提出解除夫妻关系,一般要经过如下过程:“首先各自要向父母报告,然后由男家请来村中有威信的奥雅(即老人)主持离婚仪式。男家杀猪摆酒,男女两家亲属代表各一边就座,并请村里乡亲参加。在奥雅主持下,申明离婚的理由,双方父母表明态度,众亲评议,如果一致同意离婚,就举行离婚仪式:在酒席中间,放三个碗,一个碗盛满酒,两个是空碗,并用一块黑布铺盖碗口,离婚者相对就座。奥雅把黑布从中央撕开分成两块,离婚当事人各取一块,作为脱离关系的凭据,之后奥雅把盛满的一个碗酒倒入两个空碗中,离婚者各把半碗酒饮干,俗称‘喝半碗分手酒’。”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离婚的仪式越简单,一般就以离婚双方撕开一块黑布为凭证。在此过程中,离婚当事人最终决定离婚与否,其他人只作为见证人和调解人。也就是说,在黎族社会,夫妻关系破裂并不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社会承认的只是认可个人对于结束共居状态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由男女双方自己做出的。
好吃懒做、酗酒,劝说不听,也是导致夫妻离婚、家庭破裂的一个原因。黎族谚语说:“不种田吃好米,没有老婆得好妻。”流行于保亭、琼中一带的《割茅歌》中唱道:“老婆滚地猛哭喊,骂老公太惰……全村老少来取笑,碰上这老公猪一样懒!”而保亭县加茂镇毛林村的村规民约中也规定:“反对酗酒闹事,一旦发现,派出所就将其留制,直到酒醒承认错误。”已婚者偷窃,将会成为夫妻离婚的一个原因。
夫妻任何一方死亡的直接后果就是婚姻关系的解除,而双方离婚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一般不需要办什么手续。
总结来说,黎族在有关婚姻制度方面,得益于汉民族文化在黎族地区的逐渐渗入,黎族对汉民族文化的吸收以及黎族地区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使得黎族地区的婚姻制度逐步完善,并逐渐趋于汉族化。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是民族文化进步的一种表现。
(二)妇女地位
黎族婚姻家庭习惯法孕育和根植于这些民族特色之下,具有高度的地方化色彩。与汉族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不同的是,在黎族传统婚姻家庭习惯法中,黎族女性一直处于崇高且受人尊敬的地位。
黎族主要崇拜的始祖神黎母就是女性。海南儋州黎母庙,“在县西黎晓山顶,在巨石岩岩,乡人以祀黎母。灵甚,岁时祭享,祈祷有应”。①即使接触到汉文化时,黎族的许多生活习俗也体现了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现象。到宋代,黎族的部落首领仍有由妇女担任的,“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②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蛮夷》卷四,黎人条载:“峒各有主,父死子继,夫亡妻及。”清代《黎岐纪闻》写道:“其俗贱男贵女,有事则女为政”、“遇有事妇人主之,男不敢预也。”③男子打架,女子相劝一定要停止,“黎性悍而质直,间有同类一语不合,则操戈矢相向,得妇人架中一劝,随亦解释”。①如果峒与峒之间发生械斗,要发出“通牒”,送“通牒”的使者必是妇女,械斗停息,双方各派出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传统的和解仪式“蕊岔”。②
从宋代史籍《岭外问答》记载的“王二娘主政”到清代《黎岐纪闻》记载的“遇有事妇人主之,男不敢预也”,我们可以看到其持续时间之长久。虽然后来在封建化的黎族外围地区,已改变了妇女主政的情况,但妇女依然受到黎人的尊重,如峒主见到妇女、老人也要下马。直到今天,走路时,男子见了女性和老人还要让路。家庭中,妻子有过错,要报告女方娘家处理,女子受了夫家欺负,娘家常兴师动众来论理。③夜游和不落夫家等习俗也都表示着母系社会女性地位崇高观念的遗留,由此引申出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结婚自主等理念甚至影响到今天。
以上情况说明,黎族女性一直处于被人尊敬的地位,但是女性的地位在细微之处还是随着婚姻习惯的变迁而变化的。一夫一妻制时期,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显现,为了氏族的和谐,女性进一步让渡自己的性自由权利,如女性婚后即使不落夫家,性行为也会受到一定道德上的限制。此时期,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上平等。在黎族人的观念中,男女双方分属不同的祖先,也因此女性得以在婚姻中保持自己个体的独立性,男女双方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体现在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上就是男女完全平等与自由。双方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男女之间体现了相互尊重人权、互不干涉强制,只要一方不同意,婚姻家庭关系即建立不起来。结合自愿、离婚自由,男女双方以爱为基础,当事人自己掌握婚姻的主导权,真正实现了以感情为基础的美满自主的婚姻。
总结来说,在黎族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很明显的。随着黎族传统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婚姻习惯的逐步变迁,女性不断地让渡自己的权利,黎族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步降低并逐步与男性社会地位趋于平等。
实际上也只有双方或者多方的权利逐步趋于平衡,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得到实现。
(三)家族
血缘共耕与互助逐步减少。“合亩”制是黎族特有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它应该是黎族最早的一种社会制度,是黎族社会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社会形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来看,“合亩”制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一种生产方式。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合母内成员共同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具有原始社会的色彩。由于合亩制以男长辈为“亩头”,使得黎族的合亩制性质应是原始社会父系家长制或家族的共耕公社。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外部文化尤其是封建地主经济文化的不断浸透,原来单纯的合亩制已变得纷繁复杂。一方面,“合亩”原本都是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组成的,随着合亩的演变,有些合亩已吸收了非血缘关系的外来户,以致非血缘关系合亩的户数、人数越来越多,血缘共耕由此减少。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家族以至家族内各户所私有,社会关系已不是血缘的关系,而是地域和经济的结合。特别是外围地区,随着阶级分化的明显,加上社会成员间的迁徙杂居,这种代替了亲属结合的地域性或邻近间与政治的结合越加稳固了。宋时,羁縻黎峒的生产方式,田土由“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初无文记”。①它与残存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合亩制”略同。不过前者是以“峒”为单位,范围很大;后者公有制和共耕分收制的范围已经缩小得多了。而随着黎族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加深,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元明清时期,黎族公有制和共耕分收制逐步减少。到了民国时期,据了解,在外围地区,本地与外地来户,同姓与外姓界限逐渐消失,全村性的互助无偿减少了,借贷计时计息了,帮工不换工不给报酬受到所谓“社会舆论的制裁”了。如东方县第二区水头乡老村,在帮工互助上,姓氏的感情,并不比同村同一方言来得浓厚。②
二 民事习惯法秩序的变化
宋代以后,黎族由先民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本民族内部没有“私有”的概念,没有交易、交换,慢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以及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迁入岛内,促使了私有财产交易的频繁化,形成了简单的商品经济。黎族的民事交往也由此步入了发展时期。
(一)民事活动范围的扩大
黎族在贸易交换的对象上有了很大的变化,黎族合亩之间的交换,演变成后来的黎汉贸易加强,苗族的迁入使得黎苗贸易出现,民国时期则有了和日本军阀的贸易。据《黎族三峒调查》,1942年末日本人付给石碌矿山的劳工每天的工资是40钱军票,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地方为日本窒素株式会社经营的作业场商店。在此期间黎族和日本人的交易基本代替了黎汉交易。
在贸易物品上,由原来的简单生产资料交换演变成用土特产、粮食交换劳动生产工具,如一包衣针换1斤鸡,或换5斤玉米,1副犁尖换5斗谷子,1支单发粉枪换1头水牛或黄牛等。不难看出汉族文明的传入使得黎族的生产经济有了很大提高,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
(二)民事交往的形式
1.墟市
黎汉之间的贸易由宋朝时期主要在汉族的集市中进行,①转变为以黎族地区开设的墟市为主,②以汉族地区集市交易为辅,而且墟市的范围不断扩大。《明神宗实录》卷363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统治者平定居碌、居林、沙湾三峒黎族起义后,于其中心地带永蕉村“立墟市以通贸易”。清朝黎汉贸易往来进一步深化,墟市不断增多。据《正德琼台志》记载:“全岛兵有一百二十一个较大的墟市;其中琼山三十九个,汀迈二十个,临高十四个,定安八个,文昌九个,会同六个,乐会三个,昌化1个,万州六个,崖州二个,儋州十个,唯独感恩,陵水只左城中设市。”①
随着黎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黎汉往来的频繁化,黎汉通过商业沟通,互通有无,日益融为一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2.典押
黎族习惯法中有一些关于典押的规定。典押最初在当事人双方之间直接发生,后来才出现了中间人,中间人按田地典押或牛的数量来收取报酬。黎族典押经常没有具体的时限,多在两年后才可赎回典押物。有时父亲出典的东西,到儿子时才赎回。根据习惯法的内容,典押关系成立后,双方还要剖竹为凭:用一寸宽、五寸长的竹片一块,把典押价格用刻划于其上,再将竹片一劈为二,由出典人和受典人各执一半为据。日后赎典时,便以此为凭。如果出典人归还典价后,就收回出典物,并当场焚毁竹片,典押关系即结束。
典押也可演变为买卖,如出典人在出典期间,要把出典物卖断,经征得受典人同意后,双方协商,由受典人再给卖主一些牛或钱,土地所有权就属于受典人的了。②
3.借贷
黎族习惯法中借贷的情形发生甚少,外部借贷也不多,所以对此虽有规定但也很少,主要是遵循传统的习俗进行互相帮助。借贷分为两种:
对内无偿借贷。此种借贷是指在同一合亩内的直系血亲间,或者不管是在合亩内借贷还是在合亩外借贷只要是黎族人之间借钱都不付利息。也有些合亩内的非直系血亲归还成本就可以不用偿还利息,同时对偿还期限也无苛刻要求。
对外有偿借贷。此种借贷主要指合亩外,对粮食的借贷都是要计算利息的,要还一倍的利息。即借一还二。在盖章村王老捆做亩头时,合亩内的王老陆向堂侄王老识借稻谷一对,同年还稻谷两对,如果当年不还则要利上加利。①因为在黎族人看来钱不会生长出钱来,可粮食会,所以对粮食的对外借贷一定要双倍偿还。
4.租赁
黎族习惯法中牛和土地是他们主要的财富,也是赖以生存的劳动生产工具,所以在对这两种财物的租赁上有比较细致的规定。
首先,在合亩租牛时,由亩头代表合亩去租,租金由合亩出。而个人租牛时,由个人联系,也有的村还需亩头去交涉。租金一般是固定的。
其次,租赁人在租赁耕牛期间必须合理使用耕牛,并认真对耕牛进行看护。如果牛老死或因过劳致死,租牛者必须以牛进行实物赔偿,死牛归租牛者;如果牛被盗,租牛者要承担赔偿责任,如牛在夜晚被偷,按原数偿还,反之则加倍偿还;如果牛遭遇瘟疫而死,租牛者虽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必须及时通知牛主。牛主需要将牛颈、牛腿等给租牛者。牛主如不要肉,可由租牛者所在的合亩分食,另以1口猪及相应的钱送给牛主。如在牛瘟死后,租牛者未及时通知牛主,而被牛主知道,则租牛者受罚。
再次,关于孳息的问题:租牛所生的小牛归牛主,如被人偷去小牛,租牛者要赔偿1口猪。②
关于田租,在黎语中被称为“同寅田”,即基于平等和合作、因兄弟情谊而互相帮助耕田的意思。③租赁的对象一般是私产田地,主要是水田、旱田和部分山林。公田不允许出租。
在田地租赁方面形成的习惯法内容主要有:
(1)租赁契约达成需要一定的仪式性程序
土地的租佃关系一般发生在同村的合亩与合亩之间或合亩与别村合亩个人之间。在进行租田契约时,农户自己去找田主联系,当然在个别情况下,也有村头出面联系。联系好便要举行仪式,杀鸡、猪、牛与田主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宰杀牲畜的种类和数量往往代表了租赁契约的具体内容。①
(2)以租种土地的部分收成来折抵租金
在租赁的土地开始收割前,租田者要通知田主来分稻谷,田主本人或者派人来对收割过程进行监督。收割后,租田者应先留出种子以及田主及其随从饮酒、吃饭所需的谷子,再将收成分为两份,双方各取一份;有的由田主根据收成的好坏来决定田租的多少。
(3)违约责任以赔偿牲畜或谷物为主
如果租田关系还未到期,田主提出中止租田关系,则根据剩余租田期限的多少对租田者进行赔偿。如9年的租期第6年时田主提出收回田地,田主要给租田者一口猪或价值相当于一口猪的稻谷。②如果是租田者提出提前解除租田关系,田主则不对租田者进行赔偿。
(4)中间人制度
在黎族习惯法中,田地租赁契约的出现较晚,起初只限于出租者和承租者双方,后来为便于协议的履行,出现了保人也就是中间人。据说中间人一般为男性,其主要义务就是在宴会上把双方的权利义务说清楚,并监督双方履行。此外中间人还要负责解决租田双方纠纷。在习惯法中,不论租种田地的面积大小、期限长短、土质好坏,中间人获得的报酬是相同的,但是他对双方当事人违约行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三)民事交往内容的变化
1.书面契约更加规范化
宋代黎人虽无文字,但能通过结绳记事、刻木为契进行交流。宋·苏过《论海南黎事书》记载:黎人“无文书符契之用,刻木结绳而已”。此法在黎区沿用至清代。《广东新语·人语》卷七所记:“黎长不以文字要约。有所借贷,以绳作一结为左券。或不能偿,虽百十年,子若孙皆可持结绳而问之,负者子孙莫敢诿。力能偿,偿之;否则,为之服役。贸易山田亦如是。”①
黎族传统的契约,又称为对牌。对牌由借方和贷方各持一半,如果借方欠债不还,贷方可以向其出示对牌,催促其偿还债务,如果借方偿还了部分债务,双方都要将对牌的相应部分切掉,债务全部还清后,双方均废弃对牌。“出卖或出典田地,都要刻竹为契,即用一节竹筒,将典卖的田地的价值、数量,用刀刻在竹上来表示。如一头牛和五块光洋,可刻成‘x1x11111x’的形状,其中‘x’表示间隔,仅‘1’才表示数量。刻竹以后,将竹筒从当中剖为两片,双方各取一片以后每交一头牛,一块光洋,便将刀痕逐次削去,等削完了,就得两片竹片对证一下,认为没有问题,就当场烧去,表示手续完结。”光绪《定安县志·黎岐》卷九记黎俗,“黎人贸易称贷,截竹有一指之长,千浅刻一痕,剖开各执一为合同”。②
典田竹契1支。清光绪四年(1878年)佚名制。记清代海南乐东千家地区黎族社会民间典田之事。以竹片制成,内侧题有黑色行书“光绪四年出典掃逢田种二×”十二字,并有两道“|”样刻痕;竹契外面自上而下刻有代表契值的纹痕“>| | | | | |>”。为海南乐东千家地区黎族民间典田契约。对研究海南黎族社会民间典当关系与“刻木记事”文化有参考价值,保存完好。③
张亚本断卖田契1纸。清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张大利代笔撰写。三亚崖城地区黎族民族间买卖土地地契。记载抱雷村张亚本因粮债负累将祖父遗下分田多处出卖与本村韦亚临事宜。棉纸,楷书,黑色。代笔人画押,签书人、同见人手模。第三行上部、中间下部、左上部有残缺。④
从上述《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两份田契不仅在材质上不同,在地区上也有差异。笔者认为黎族的文明程度不仅和汉族的入住有关系,而且和地理位置也有很大的关系。乐东位于中部靠西,崖城位于南部靠海,相对于乐东更有利于发展经济,同时文明的进化程度也要高于居于中部的乐东。
上述两份纸质契约不论在内容表述上还是在格式形式上,都已与中原汉族契约十分接近。在使用中原汉族契约形式的问题上,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中我们还发现,在乐东黎族地区,黎族人民不仅使用了纸质的契约,同时还立有竹契,一个民事借贷行为同时有两个形式的契约存在,这说明黎族人民在接受汉族法制文明时的小心谨慎。
2.存在剥削与不对等
在交易过程中,黎族人民恪守传统的交易习惯,诚实信用。《昌化县志·原黎》卷3载:“与人贸易,甚有信。商人信则相与,而至亲借贷不吝。或负约,见其同乡人擒之以为质,枷以横木,必负债者来偿还始释。”但随着交易的频繁,汉商对黎族人民的不平等交易现象出现。《崖州志·黎防一·黎情》卷13所载:“与人贸易,不欺,亦不受人欺。相信,则视如至亲,借贷不吝。或负约,见其村人,即擒为质,枷以横木。负者来偿,始释。负线一缗,偿谷一秤。岁加一倍,无有底止。”此后,明朝和清朝政府都对这一不平等交易现象予以法律规制,以此缓解黎族汉族矛盾。据《明神宗实录》卷534,“万历四十三年七月乙丑”条载:“以后,闽、广各商止许于交界互市,有酬价不登或不偿值者,许黎人告理。”据《清史稿·杨廷璋传》卷323载:“各地方官各于附近州县城外汛防地界,设立墟场一二处或二三处,按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定以墟期,俾源源赴墟,彼此交易。黎货既已流通,物价又复公平。每属墟期,责成该汛巡检弓兵督同黎头保甲赴墟弹压稽察。”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所立《奉道宪严禁碑》称:“议客黎买卖货物,斗秤须要公平,彼此交易,有信有从,不得强牵牛马及儿女抵债,违者送官究治。”
三 中央权威对某些传统禁忌和宗教的限制
在黎族传统习惯习俗中,有一部分是与公共秩序有关的宗教与禁忌。基于对神灵与鬼神的崇拜,在黎族社会产生了众多的禁忌,对于这些禁忌的触犯,会惹来杀身之祸,导致全族恐惧。而各路神灵的惩罚通常是通过族内神职人员(如道公、禁公、禁母等)来体现,该禁忌本身十分愚昧与落后,其后果则十分残酷。故,在中央政权的统一法律秩序下,这些对黎族社会及黎民人身带来恐惧、不安和无辜伤害的禁忌与宗教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一)禁忌:禁公、禁母等巫蛊杀人、伤人
黎族原始宗教的活动,除咒语外主要是原始巫术。所谓原始巫术,是指用一种简单的联想和独特的类比,祈求人世间的幸福,消除社会上的灾难。从上述可见,黎族的原始巫术已浸融在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各个方面,它在原始宗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禁术则是另一种家喻户晓而影响又极坏的巫术形式。由此,在各个时期,各中央王朝政府对黎族有关传统禁忌和宗教都有些否定性规定。
黎族有关“禁”习惯法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盛极一时,但从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府对海南黎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区实施有效控制以后,国家法开始在黎族地区实施,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如清朝光绪年间在黎族地区所立的《奉道宪严禁碑》中第一条规定,“一查造魔克符咒诅杀人并下毒药害人,按律照依谋杀论”。①民国时期,也采取了以国家法制裁黎族“禁”这一传统习惯。
(二)族殴、仇杀
族殴、仇杀这两种情况对黎族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群居生活的种族来说,并不是很陌生。在黎族地区,由于生产力以及宗教信仰等等各方面的原因,族殴、仇杀现象时有发生。故意杀人一般要看是杀外村峒(族)之人,还是本村峒(族)之人。杀死外村峒(族)之人,双方便在两村峒(族)长的主持下,会同两村峒奥雅或全体成员协商,和解成功,便由杀人者支付“赎命价”。若协商不成,往往会先引起村峒之间械斗和血亲复仇,连累无辜,牺牲更多的性命和造成更大的损失,抓到凶手便以命偿命;当抓不到凶手,便会引起两村峒(族)之间冤冤相报不止,直至两村峒(族)再进行谈判协商,最终以凶犯家钱财赎罪了事。故意杀死本村峒(族)之人,须以命抵命,但也有例外。
黎族传统习惯有关族殴、仇杀的解决方法很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情况的出现,不利于中央政府对黎族地区的统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朝中央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对有关族殴、仇杀等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崖州官坊村黎人发生了民黎冲突,时黎人纠集抱碟、粪洗、只酉等村黎人执刀,放火掠杀民人。据《琼州府志》载其因,“岁饥,汉奸放债盘剥,黎人苦之,出掠乡村”。①乾隆皇帝对此也尤为生气,下谕旨说:“黎人敢于纠集人众,抢掠村庄,杀害民人,实属不法,即使该处村民平时或有欺压黎人之事,以致受侮不甘,亦当向地方官控告办理,何得擅自仇杀,此等野性难驯之匪徒,不可不从严究办。”②即体现出清政府对黎人文化的直接干预。这种干预在清末表现得较为强烈,因清末开始转变过去消极治理黎族的政策。
光绪年间,聂缉庆记叙了他在临高当县令时以行政命令干预黎人习俗的事例:“临俗固陋,士入市不衣冠,盖其地极边,中州礼让之风未尝睹也。余至,多方劝勉,莫能移易。最后察士之有仍习者,辄罚金少许为修学费。诸生重财甚于他罚,不一月,衣冠济济,非复从前科跣景象。独齐民无表称,冒其妇里居姓氏为名字。与夫婚同姓,及妇失偶,群恶少争投榔肉,甚至三、五家争娶者。往往至期攘夺,后为强有力者得之,则盈庭聚讼。凡此蔑亲叛义,尤恶之甚者也。愚到任之后,严行饬禁,两载来亦知勉强遵守,略有通都文物之盛矣。”③
聂缉庆主要对临高士人不衣冠之陋习及黎人抢婚致讼进行了改变和禁止,而鲍灿则干预得更多,此处仅择两例。他在《劝释黎民械斗示二则》中云:“照得怀衅斗殴实为地方之害,为此示谕特劝尔等黎民,前经州堂协同本府招抚安绥,自后各安耕凿,严戒子弟,不准藉端生事,保守境界,虽有前仇宿恨,一概永销……如有不遵者,本府定派兵勇按罪剿办,决不宽恕。”④
喜仇杀械斗是黎人的风俗和习性所致,而鲍灿对此进行禁止和劝谕,以使黎人的行为合乎内地的“伦纪”,“风化”,显然是把内地的风俗强加在黎人头上。
(三)盗窃的新形式
盗窃,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众或他人钱财的行为,如偷牛、偷铜锣;另外,采摘、砍伐被人已作标记的果实、树木的也按盗窃罪论处。①黎族“刑事”习惯法视偷牛、偷铜锣为最严重的盗窃行为,被捉拿的盗窃者被苛以成倍惩罚。“一般的情况是‘偷一赔十’。失主将罚得的牛只杀掉两头宴请乡亲们;若偷盗者无法即时赔偿,则责令其‘刻木为契’,日后陆续还清;若罪犯无力赔偿,亲族又不愿意帮助的,被盗者可以将罪犯杀死。”②另外,偷牛、偷铜锣的被抓现行,倘若当场打死,也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黎族地区传统“刑事”习惯法的实施,虽然解决了盗窃案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容易引起重大社会矛盾的发生,尤其有关可以将罪犯杀死的规定将会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不利于中央政府对黎族地区的统治。为此,中央政府对于盗窃现象给予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二十日阎峒屯图同立禁碑。
总体来说,自宋代开始,随着中央政府对海南黎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区实施有效控制以后,为进一步加强对黎族地区的统治,各朝国家法开始在黎族地区实施,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这些具体措施的具体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黎族地区的统治。同时,由于在实施国家法的过程中具体结合了黎族地区的传统法,使得对黎具体治理措施得到实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央政府对黎族地区统治及加强当地封建化进程的目的。可以说,中央王朝国家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黎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汉文化在黎族地区的传播,有利于黎族文明的发展。
附注
①据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序言介绍,迁移到岛上的汉人既有戍守边疆的士兵和封建官吏,也有普通的劳动者和商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① (民国)陈植编著《海南岛新志》,海南出版社,2003,第13~14页。
②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防黎》,海南出版社,2006,第886页。
③ (明)戴熺、欧阳灿总裁,(明)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上册)卷八《海黎志·抚黎》,海南出版社,2003,第415页。
① (清)钟元棣创修,张嶲等纂修《光绪崖州志》(下册)卷十四《黎防志·黎防志三·抚黎》,海南出版社,2006,第360页。
②宋太宗宰相卢多逊,真宗宰相丁谓,大学士苏轼,抗金大将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均先后被贬谪海南。中原贬官的到来,无疑为海南的文化荒漠注入了甘霖,他们推动了海南的教育,传播了中原文化。
① 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序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②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防黎》,海南出版社,2006,第888~889页。
③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防黎》,海南出版社,2006,第890~891页。
①(清)阮元总裁,陈昌齐总纂《道光广东通志·琼州府》(下册)之《岭蛮》,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第878页。
② (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① (清)陈坤撰《治黎辑要》,光绪庚寅年刻本。
②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十《海黎志六·村峒》。
① (清)陈坤撰《治黎辑要》,光绪庚寅年刻本。
②(清)钟元棣创修,张嶲等纂修《光绪崖州志》(上册)卷十三《黎防志·黎防志一·黎情》,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第330页。
③ 《宋史·宋琪传》。
④ (宋)赵汝适:《诸蕃志·海南》(卷下)。
①(清)钟元棣创修,张嶲等纂修《光绪崖州志》(上册)卷十三《黎防志·黎防志一·黎情》,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第328页。
②参见高泽强《论黎族历史上政治制度和职官制度的特征》,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五指山脚下的耕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第86~92页。
③ (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④(清)钟元棣创修,张嶲纂修《光绪崖州志》(上册)卷十三《黎防志·黎防志一·黎情》,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第329页。
① 参见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02页。
① 参见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40页。
② 参见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41页。
③参见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40~41页。说明:本次调查是在1954年7月至1955年1月间完成,当时黎族地区正进行民主改革,受访者所回忆的基本上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黎族状况,而这些都是在封建中央政府对海南进行统一管理后所发生的。
① (唐)魏徵、长孙无忌等撰《隋书·谯国夫人传》,同治十年,淮南书局刻版。
② 参见苏英博、韦经照、梁定基、符泽辉、邢植朝主编《中国黎族大辞典》,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第428页。
① (宋)苏轼:《戏作》,《东坡全集》卷二四。
② 参见〔日〕冈田谦、尾高邦雄著《黎族三峒调查》,金山等译,民族出版社,2009,第7~8页。
① 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62页。
② 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写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81~82页。
③(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海黎志九·黎议》,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第917~918页。
④(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海黎志九·黎议》,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第928~929页。
①(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海黎志八·防黎》,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第886页。
② (明)郭棐纂修《万历广东通志·琼州府》,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第214页。
③(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海黎志八·防黎》,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第892页。
① 《宋史·太宗本纪》。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零二。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
①从《广东琼州汉黎舆情营伍练兵稿抄》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类告示,如《除积弊安黎示二则》、《悬赏严拿黎匪谕》、《立章训黎示二则》、《饬汛弁传集各峒黎目受抚札》、《劝释黎民械斗示二则》、《严禁汉奸抢夺黎物抵债示》等等。每一个告示或谕都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和规范要求,它对于黎区的秩序维护和社会管理发挥了法律强制性作用。该《抄》由崖州协镇府、崖州正堂、都关府合编,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刻本,《<黎族藏书>古籍资料汇编》卷三。
① 《冯公保军牍》(拍照版),海南省民族学会编印《<黎族藏书>古籍资料汇编》第五卷第一部分《冯公保军牍》,2006。
①崖州协镇府、崖州正堂、都关府合编《<黎族藏书>古籍资料汇编》卷三第一部分《广东琼州汉黎舆情营伍练兵稿抄》之“除积弊安黎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刻本。
② 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第18页。
① 转引自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13页。
② 转引自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13页。
③ 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第23页。
① (宋)王象之编著《舆地纪胜》,《<黎族藏书>古籍资料汇编》第六卷第九部分。
① (清)张庆长编著《黎歧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① 〔日〕冈田谦、尾高邦雄著《黎族三峒调查》,金山等译,民族出版社, 2009,第50~51页。
① (清)雍正《大义觉述录》,光绪末年仁社书局铅印本。
②(明)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第415页。
①(明)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第419页。
②(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海黎志九·黎议》,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第929页。
③(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海黎志九·黎议》,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第928页。
① 参见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第19页。
①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14页。
① (民国)陈献荣编《琼崖》,《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第384页。
② 参见〔日〕冈田谦、尾高邦雄著《黎族三峒调查》,金山等译,民族出版社,2009,第211~213页。
③根据《海南史志网·地方志书·海南省志·民族志》第一章记载:黎族人习惯在竹子上(带有竹节的圆竹)刻各种纹痕来记典当、借贷中的数目,一般称为“押”或“契竹”,它主要有三种,“指长押”(用一根中指长度的小圆竹刻纹)、“掌长押”(用从中指端至腕跟长度的小圆竹刻纹)和“肘长押”(用从中指端至肘跟长度的小圆竹刻纹)。黎族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定是:凡契值在30元(光洋,下同)以下的,用“指长押”,每刻纹代表1元;契值在40元至100元的,用“掌长押”,每刻纹代表5元;百元以上用“肘长押”,每刻纹代表10元……黎族社会中的各种借贷、典当、买卖等都会用到牛只,在竹契中有特定的纹痕表示,它往往用较粗黑的横纹表示,一条粗黑横纹代表1头牛……
④(明)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第420页。
① (民国)陈铭枢纂,曾蹇主编《海南岛志》,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4,第138页。
①明弘治十四年儋州七方峒黎王南蛇起义,是一起典型的断箭传信之例:“刻箭传递,三州十县诸黎峒各皆领箭,闻风响应。”“环海州县峒黎皆应之。”起义爆发后,声势十分浩大。参见海南史志网,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09/05/42/02/。
② (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③ 具体方法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三、对通奸的处罚”,此处不赘述。
① 参见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14页。
②(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广东黎人岐人部汇考一》,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地理志·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第484页。
③ (明)顾岕编著《海槎余录·黎人考》,《<黎族藏书>古籍资料汇编》第六卷。
④ (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① (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② 参见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写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228页。
① 参见苏英博、韦经照、梁定基、符泽辉、邢植朝主编《中国黎族大辞典》,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第428页。
② 高和曦:《黎族峒的组织及其历史作用》,载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海南民族研究(二)——越过山顶的铜锣声》,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第121~122页。
③ (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①周文海重修,卢宗堂、唐之莹纂修《民国感恩县志》,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4,第295、297、298页。
① (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②(清)钟元棣创修《光绪崖州志》(外一种)(上),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第329页。
① (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琼州府志》,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第862页。
①“三月三”是黎族传统的节日,其起源并无文字记载,民间关于三月三的传说却有诸多版本。尽管如此,三月三这天,黎家老少从四面八方汇集一起载歌载舞,青年男女通过对歌寻觅理想对象却是共同的说法。
②彭元藻、曾友文修,王国宪总纂《民国儋县志》卷八,转引自海南省民族学会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三),海南出版社,2009,第223页。
③ (民国)陈铭枢总纂,曾蹇主编《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4,第151页。
① (民国)陈植编著《海南岛新志》,海南出版社,2004,第97页。
② (民国)陈铭枢总纂,曾蹇主编《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4,第151页。
③ (民国)陈铭枢总纂,曾蹇主编《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4,第129、130页。
④ 〔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1964,第99页。
⑤ (民国)陈铭枢总纂,曾蹇主编《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4,第151页。
⑥ 符桂花主编《黎族传统民歌三千首》,海南出版社,2008,第165页。
⑦ (明)戴璟修,张岳等纂,黄佐纂修《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二种),海南出版社,2006,第159页。
⑧ (清)金光祖纂修《康熙广东通志·琼州府》,海南出版社,2006,第283页。
① 符桂花主编《黎族传统民歌三千首》,海南出版社,2008,第549、550页。
② 符桂花主编《黎族传统民歌三千首》,海南出版社,2008,第82页。
③ (清)钟元棣创修,张嵩等纂修《光绪崖州志》(上册),海南出版社,2006,第50页。
④(清)毛奇龄:《蛮司合志》卷一五《两广四》,转引自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下册),1964,第663页。
⑤ 佚名:《琼州志》,转引自海南省民族学会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海南出版社,2009,第686、687页。
⑥ 〔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1964,第96页。
⑦ (民国)陈植编著《海南岛新志》,海南出版社,2004,第97页。
⑧ 周文海重修,卢宗棠、唐之莹纂修《民国感恩县志》,海南出版社,2004,第274页。
① (清)钟元棣创修,张嵩等纂修《光绪崖州志》(上册),海南出版社,2006,第50页。
② 参见高泽强《海南黎族历史研究》,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第224页。
③(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转引自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下册),1964,第722页。
④(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转引自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下册),1964,第722页。
⑤ (清)钟元棣创修,张嵩等纂修《光绪崖州志》(上册),海南出版社,2006,第50页。
⑥ 许崇灏编著《琼崖志略》(第四章),转引自海南省民族学会编《黎族藏书·方志部》卷一,海南出版社,2009,第697页。
⑦ (日)冈田谦、尾高邦雄著《黎族三峒调查》,金山等译,民族出版社,2009,第17页。
① (日)冈田谦、尾高邦雄著《黎族三峒调查》,金山等译,民族出版社,2009,第12页。
① 转引自(日)冈田谦、尾高邦雄著《黎族三峒调查》,金山等译,民族出版社,2009,第34页注9。
②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200页。
① (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六,海南出版社,2006。
②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条,周伟民、唐玲玲辑纂点校《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第19页。
③(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条,周伟民、唐玲玲辑纂点校《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第19页。(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① 李露露:《清代黎族风俗的画卷——<琼州海黎图>》,《东南文化》2001年第4期,第15页。
② 陈立浩、陈兰、陈小蓓著《从原始时代走向现代文明——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变迁历程》,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第8~9页。
③ 王月圣:《黎族创世歌》,海南出版社,1994,第12页。
①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三一零《元丰三年朱初平等言》。
② 参见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465~467页。
①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熟黎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墟市,日晚鸣角,结队而归。”
② 据明《海槎余录》记载:“黎村贸易处,近城则日市场,在乡则日圩场,又日集场,每三日早晚二次会集物货,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
① 杨德春:《海南岛古代简史》,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教师进修学院,1982,第137页。
② 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156页。
① 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122页。
② 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158页。
③ 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157页。
①按习惯杀l头牛租9年,杀1口猪租3年,杀鸡或杀小猪租1、2年;不论土地面积的大小、种类或肥瘠程度,都以它们表示年限。如果租田期满而双方同意续租的话,便要另杀牲畜来决定年限。
② 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158页。
① 吴永章:《黎族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431页。
② 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137页。
③ 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第45页。
④ 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第45页。
① 谭爱萍:《<奉道宪严禁碑>与清代黎族地区的民族关系》,载刘明哲《越过山顶的铜锣声》,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第183~184页。
①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二《防黎》,海南出版社,2006,第916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六,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三月戊寅条。
③ 《光绪临高县志》卷四《疆域民俗》。
④ 《汉黎典情》卷一。
①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11页。
② 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