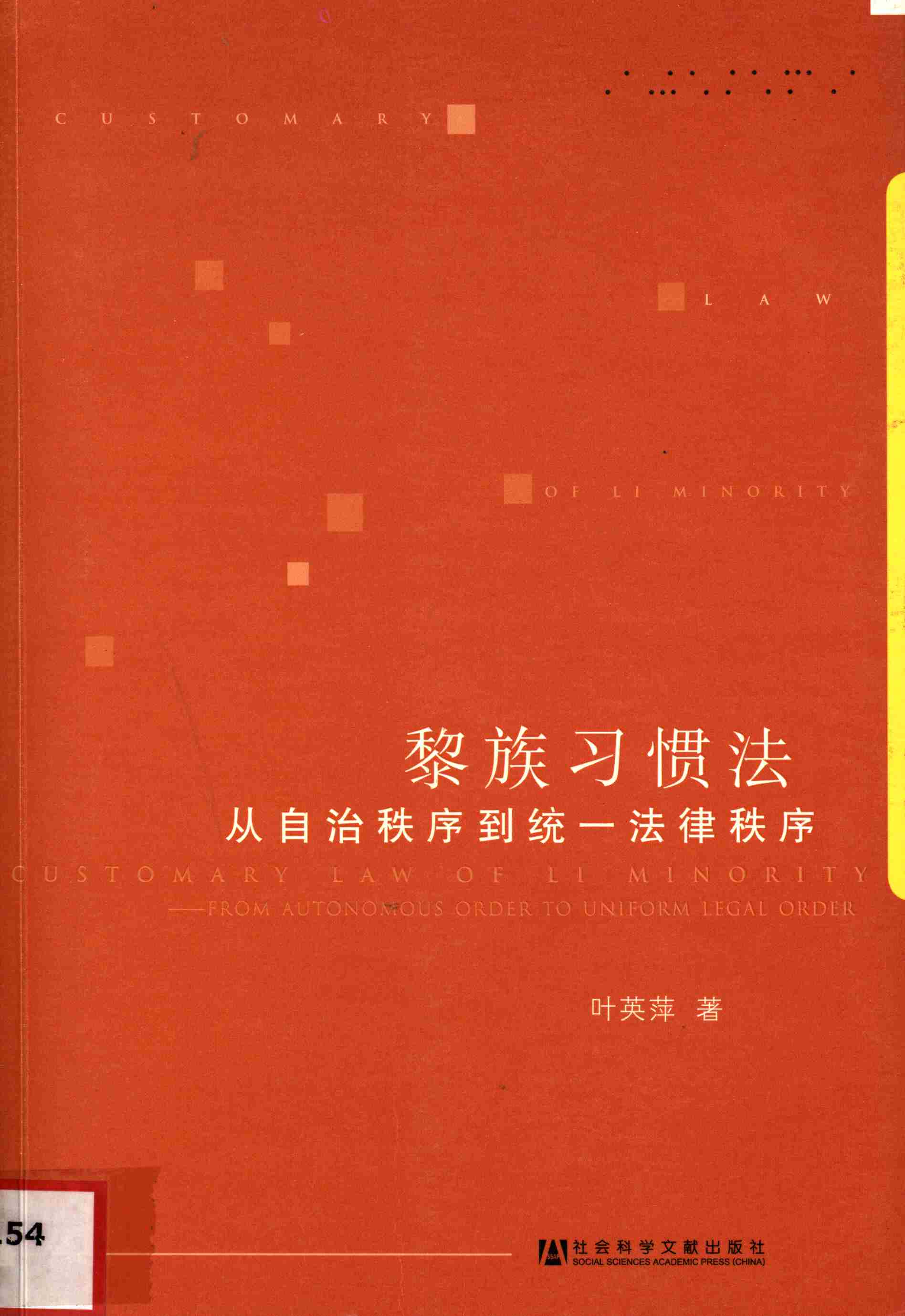内容
与黎族社会公共秩序相对应,在黎族社会里,存在着人们普遍遵守的规则、规范,这些规则、规范,有的表现在黎人精神意识的信仰上,有的则表现在黎人的具体行为上。即使是精神意识方面的信仰,在传统的黎族社会里,最终也落实到黎人具体的生产生活上来,从而对他们的行为产生约束。上述四个类型的黎族社会公共秩序,在黎人的具体行为中,在黎人的日常生活里,表现为涉及族内公共利益及每一个族人利益的“宗教禁忌”,具警示作用和公告作用的“插星”,以及表现为黎人自觉的不偷不盗的习俗习惯和对具体违规行为的处罚的规则等。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规则都是黎人世代相传的、在峒组织内自觉遵守的规则,它没有外力的强制,它完全是一种自然秩序下的习惯法规则。
1.宗教禁忌
从第一章的论述中我们可知,黎族人民有神灵崇拜,自然神、动植物图腾、祖先鬼等,都是黎族人民崇拜的对象。由于崇拜而生敬畏,因敬畏而生行为禁忌,在敬畏与禁忌中,产生了习俗与习惯,成为控制人们的精神意识,约束人们的行为的习惯法规则。
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形成了对自我行为的约束,这是自然秩序下最原始状态的习惯法规则。由于自然界的万物皆有灵,能左右人的生老病死,能决定庄稼的歉与丰,能保佑猎者捕到猎物,因而则必然产生对它们的崇拜,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崇拜,崇拜的方法就是祭祀。人们怀着一种敬畏的、虔诚的心情,约束着自己的行为,小心翼翼地祭拜,祈求平安顺利,祛病消灾。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与祭祀,成为黎族人民共同的生活习俗,维护着族内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生命财产安全。对祖先动植物图腾的崇拜,使人们产生了对祖先图腾的保护意识与习惯,形成氏族成员需要遵守的第二个公共秩序规则,对图腾不敬,不仅会招来祖先的惩罚,也会被氏族成员谴责。对祖先鬼崇拜的方式是“敬而远之”,即平时禁止说出祖先的名字,否则会招回祖先鬼,危害家庭生命健康。因此,关于祖先鬼,不仅自己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也不允许别人说出他们的名字。显然,对祖先鬼的崇拜与禁忌,是氏族成员内部所要极力维护的另一个公共秩序。
基于对神灵鬼魂的崇拜与敬畏,在黎族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有诸多具体禁忌存在,这些禁忌涉及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每一个个体和行为产生约束与规范作用。在这些禁忌规范中,多数是为自己家人的家口平安、生产顺利而对自己行为的一种约束,但也有一些禁忌涉及外人,要求外人不得为某些行为,或为了外人自己不得为某些行为。黎族人民通过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或对他人行为的要求,来实现平安、幸福,这些禁忌已成为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生产规范。例如,“砍山栏时,带饭到山栏边,到吃饭时不能一人先吃,必须共吃”,否则先食者会使后食者掉下树或被砍伤。“未吃过新谷饭,忌向别人借新稻谷”,否则影响别人生产。“死人埋葬时,忌埋棺于别人家坟前”,否则遮盖别人家坟,会使别家不祥。“宅门上置青树叶”,意即室内有病人,外人不得进入。“盖好新房时忌人进入该房哭泣”,否则主人生病,生产不顺。“亩头犁田时,不准别人进家”,否则会使稻子长不好。①
以上禁忌,前三条是对自身行为的要求与约束,后三条则是对别人行为的要求与警示,其效力均源自黎人内心的宗教信仰。正如前文所述,海南黎族的宗教信仰尚处于“万物有灵”阶段,处于生产力非常低下对自然现象缺少科学认识阶段的黎族先民,当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时,往往将其归咎于自身,认为是自身的行为亵渎了神灵而招致了惩罚,因此,为避免这些灾难的降临,必须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久而久之,其日常生活生产中的禁忌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多。
弗洛伊德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禁忌就是人类最古老的无形法律,是由民间约定俗成共同遵守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契约,与国家法不同的是,当人们违反了禁忌受到的不是外在强制力的制裁,而是独自承受的来自内心的恐惧、痛苦与煎熬。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离不开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从法律角度说就是一个稳定和谐的公共社会秩序,禁忌就是这个秩序的缔造者和维护者,它以吉凶征兆的可预测性,对人们产生警示作用,进而达到对社会的控制。
自然神、动植物图腾及祖先鬼,涉及的是黎族氏族社会的整体,在自然法秩序中,它是黎族人民的公共秩序,它需要合亩内、村内、峒内每一个成员来共同维护与遵守。为了不给自己、本家、本亩、本村,甚至本峒招来不幸,每一个人都必须自觉遵守对神灵的禁忌,神灵的神秘力量是公共秩序遵守与维护的力量源泉。诸多的生产生活禁忌,是黎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黎人最基本的习惯规则,它构成了黎族社会第二个层次的公共秩序。
不论是宗教禁忌,还是生产生活禁忌,在人们行为中体现为禳解,其表现形式一是事前的设防,另一是事后的补救,前者达到的是预防作用,后者实现的是心灵的解脱和秩序的恢复。在海南黎族社会中,对神灵等禁忌的禳解方法,视神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影响农业生产和丰收的自然神,打猎出征前的山神,导致生病死亡的鬼神,等等,其中有的可由黎民家庭独自自主进行,有的则需由亩头带领亩众集体进行,有的则由奥雅带领全村人进行,有的是由宗教职业者“道公”、“娘母”、“老人”①等专业祭祀人员进行。原始的宗教信仰,自觉的禁忌行为,神秘的祭祀活动,实现了自然法状态下黎族公共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2.“插星”
“插星”,也叫“打青”、“打星”、“打草标”,也被称为“禁星”,是一种事前设防的标志。“插星”用一种特定的草插在门上或某一特定物体上,或在某特定物体上刻上某种符号,表示祈求意愿或告示该物体已有主人。关于“插星”,宋《清波杂志》卷十二载:广南黎峒家有祀事,即以青叶标门禁往来。这是史料中对海南黎族“插星”习俗的明确记载,是指黎族群众进行宗教祭祀活动后在家门上挂青树叶以驱邪的祀事“插星”,它有避邪与禁止生人入内的作用。黎族社会中,“插星”的种类繁多,除宗教活动“插星”外,还有生产生活“插星”,生育、开山种地、水稻种植、收割庄稼、某物占有、煮酒、封村、警示等都会出现“插星”。在黎民中,“插星”的定义与作用至少有三种:一是财产取得的方式方法,如上节论述的黎族财产取得制度中,“插星”就是一种财产先占的表示方式;二是驱邪保平安,如上文中提到的“宅门上置青树叶”禁忌就属此类;三是具有广而告之的通告与警示功能,这种具广而告之的通告与警示功能的“插星”,就是黎族社会中用途十分广泛的禁止性习惯规则。
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标志,不同的场合,“插星”公告或警示的内容各有不同。如:在村口的树桩上挂树叶或芒秆,则表示该村正在发生瘟疫,禁止外地人进入本村。在地头塘边出现插有一根绑有青草的棍子,则表示这块田地、这口水塘已经有了主人,他人不得再去占有。在某一棵树或小树苗的树干上如有茅草打的结,或刻有“×”符号,则表明该树已有主人,将来该树或长大成材,或开花结果,均归插星者所有,他人不得砍伐、采摘。在本村的公有土地上,如有人想砍山种山栏,则需确定开荒的面积,然后用茅草在树干上打结或刻上“×”符号,以标明砍山的范围,别人看见插星标志,则自觉地另辟他处。总之,在黎族人民的生产实践与生活里,凡是人们看好的山地、树木、果树、牧场、草地、鱼塘、蜂窝等,一时不能利用又要说明物已有主的,就以插棍结草或划“×”符号作插星标记,别人不得占用。
带有警示作用的插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方面。当农作物遭受损害,如禾苗被牛吃了,或菜园被猪或鸡鸭践踏毁坏,其主人会在被破坏之处插上草结,或将被损坏的庄稼带回村边,捆好并插上草结,悬挂于村旁,让村民知道,以警告肇事者不要再搞破坏,或是看管好自家的家禽家畜,假如经“插星”后仍然有破坏现象发生,则查明后进行处罚。为避免别人从自家的田地里放水,或放水到刚施过肥的田里,黎人便在适合放水的自家田埂上插上草结,以警示别人不要放水。①
“插星”是黎族社会通用的一种无言通告,它受到了黎族人民的一致认同。如果说禁忌是一种精神控制的话,那么,“插星”则是一种行为约束,它告诫人们不能为之事。不仅如此,“插星”还有宗教禁忌所没有的现实的、具体的外在强制力,因为触碰了“插星”之物,或拿走了“插星”之物,不仅会产生精神恐惧,而且还会被认定为盗窃罪受到惩处。“采摘、砍伐被人已作标记的果实、树木,按盗窃论处。”①“插星”是黎族社会里人们必须遵守的习惯,黎族人民认同插星,并自觉地遵守“插星”所表达的规范要求,“插星”实现了对黎族社会公共秩序,特别是财产所有权秩序的具体、有效维护。
3.不偷不贪
黎族人民朴实善良,恪守信誉,廉洁自爱。不贪心、不偷盗是每个黎族人信奉的基本生活准则和处事交往原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黎族地区的基本社会风貌。不偷不贪是黎族地区的古老族规,是黎族地区在公共财产利益和个体财产利益方面的普遍行为准则,同时它也是上述插星规则在人们行为中的效力显现。
不偷不盗是黎族社会基本的行为准则。《方舆胜览·卷四三·万安军》条引《图经》之语道:黎人“其俗质野而畏法,不喜为盗,牛羊被野,而无敢冒认”。牛羊被野,不会丢失,这是黎族社会和谐安宁生活环境的生动描述,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景象,主要是黎人不喜为盗,在黎人心目中有自己的法则,这一法则指引人们不去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即使是遗失物,发现者也不会占为己有,而是将其拾起放到显眼之处,以便失主寻找。
不容偷盗是黎族人民维护财产利益的基本理念,其惩罚性规则是重罚。黎人不偷,也不受偷,对于偷盗行为绝不容忍。盗贼夜晚行窃不仅可以被打死,其家人还要被罚赔偿牛、谷等,罚来的物资供全村人共同享用。②对偷盗粮食的处罚是:偷1斗粮食,赔偿牛10头,其中一部分牛会被用来宰杀请客。③
4.参加劳动与互助
劳动是黎族生存的最根本手段,它不仅是黎人获取生存资料的权利,也是个体黎人向家庭、合亩必须履行的义务。在合亩地区,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亩为单位的共同劳动。在亩头的带领下,全体亩众共同劳动,参加亩内集体劳动是合亩制的基本行为准则和获得生活资料的前提。如果不参与劳动,将会受到亩内相应的惩罚,最严重的就是被开除出族群。在实施合亩制度的地区,“有极个别好吃懒做的亩众,屡教不改,便勒令其退亩,成为单干户”。①在黎族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水平下,被退亩后的个体生活将面临极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被间接宣判了死刑。
参加亩内劳动是一种带有无形强制力的强制行为,而亩内成员的互助则是一种自觉行为,不请自帮,有请必帮是自然秩序下黎族人民的一种自觉行为,而且世代相传。“亩内不论哪家哪户结婚、丧葬或有其他之事,大伙都会前来帮忙。如每当某个合亩成员的妻子要归来定居立户时,其他成员都来协助建新房,事后主人请大家吃饭饮酒,表示谢意。”②这种一家有事,众人出力,彼此相助的无偿行为,表面上看是黎族人民纯朴民风的体现,实际上它也是黎族社会的一种公共道德准则,它是不偷不贪的反面,是黎族社会公共秩序的另一种规则,它同不偷不贪一起共同构筑了和谐安宁的公共秩序。
自治秩序下的黎族习惯法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在追求合理秩序的过程中,以自我形成和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合理的秩序对于黎族人民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黎族生产力水平始终处于低下、简单状态,而且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对抗外界的力量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以合作为基础的分工是必要的,从事不同工作的人需要相互配合,从最初的生产到最终完成消费,一切行为都必须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安排,本族生命的延续和种族的繁衍必须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社会规则。这种规则按现代法律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规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怎样行为,而另一种则是行之有效的社会关系协调、处理机制。一方面,稳定的行为规则追求使团体形成一种可以信赖的秩序,并且保证种族生活的规则底线不被侵犯,在这种秩序的控制下,每个族人的行为和其获得的结果都将是可以被预知的;另一方面,纠纷、争议的协调和处理可以使本族人发生纠纷和矛盾时能够尽快化解,而不会激化成冲突,同时尽快恢复以往正常的秩序。
通过研究黎族自然秩序中的习惯法,我们认为,习惯法在财产制度方面,对个体权利成分的规定相对有限,更多时候,一个家、一个村或者在合亩制度下的峒才是习惯法关注和调整的对象。习惯法的直接目的指向的是全族的共同秩序而不是个体权益的实现,个体的满足是通过群体的满足实现的。在多年与自然界抗争的过程中,黎人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个体力量的不足,只有让渡一部分利益给群体,并且接受公共秩序的约束,才有可能在危难时得到全体族人的帮助,获取生存和繁衍的机会。因此,广大黎族人民愿意生活在这种习惯法的规制和影响下,黎族习惯法中保留了大量的共有制度和平均分配的原则。
从现有资料的分析来看,自然秩序中的黎族习惯法存在以下价值取向:
首先,强调生产、繁衍。这是黎族自治秩序追求的,也是黎族习惯法所反映的最重要目标。如同求生是一个人的本能一般,血脉的延续是一个种族的本能要求。而黎族的地理位置远离发达的中原文明,在生产水平、医疗技术等方面较中原落后十分明显,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确保种族的繁衍就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做法,而这些做法的核心要件一个是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另一个就是创造更多的生育机会。经过时间的变迁,能够取得明显效果的做法被予以保留,成为习惯法,并进而巩固社会秩序,这也就解释了偶婚制的社会起源。这一点在婚姻、家庭制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子孙血缘的纯粹在黎族习惯法中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只要一个黎族孩子能够为整个种族的延续贡献力量,那么他就是被认可的。许多学者认为黎族有尊重妇女的优良传统,但严格说来,被尊重的不是妇女,而是妇女的生育功能,离婚妇女和寡妇带子再嫁之所以不被歧视,这是因为和他们共同到来的是血脉相继的可能性和相对高效的劳动力。
其次,强调人性关怀的同时追求秩序的维持。由于对生命的重要性有着出于本能的深刻认知,黎族习惯法比较强调对生命的保护。在其习惯法中能发现不少颇有人文关怀的内容,比如在遇到灾荒年时,向同村、同峒的人借粮度日是不用归还的,只要承诺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即可;此外在财产分配制度上,“合亩”组织保留一部分财产,在遇到荒灾年份时向本峒居民发放,已经具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性质。这些自发形成的习惯法内容,彰显了自治秩序中最原始的人本观念,为黎族习惯法乃至整个中华法系都增添了积极的内容和靓丽的色彩。当然,任何秩序都不是牢不可破的,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是不可避免的,纠纷一旦产生,原有的秩序就会存在被打破的威胁。为此,黎族人民非常重视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整,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社会秩序良好有序的目的。以禁忌和插星为主要形式的黎族习惯法中凝结着黎族人民所特有的秩序观念和法律智慧。
最后,黎族习惯法中有诸多仪式,这些仪式意义重大,它们说明黎族习惯法并非真的无形,只是不具备法律稳定的文字表述而已,那些庄重而神秘的仪式正是黎族习惯法存在的强有力证据和系统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证人将手按在圣经上宣誓证词真是一种法律文化的话,那么各类黎族仪式同样也是习惯法中的法律文化,也许两者在内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上存有差异,但在性质上高度趋同。
1.宗教禁忌
从第一章的论述中我们可知,黎族人民有神灵崇拜,自然神、动植物图腾、祖先鬼等,都是黎族人民崇拜的对象。由于崇拜而生敬畏,因敬畏而生行为禁忌,在敬畏与禁忌中,产生了习俗与习惯,成为控制人们的精神意识,约束人们的行为的习惯法规则。
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形成了对自我行为的约束,这是自然秩序下最原始状态的习惯法规则。由于自然界的万物皆有灵,能左右人的生老病死,能决定庄稼的歉与丰,能保佑猎者捕到猎物,因而则必然产生对它们的崇拜,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崇拜,崇拜的方法就是祭祀。人们怀着一种敬畏的、虔诚的心情,约束着自己的行为,小心翼翼地祭拜,祈求平安顺利,祛病消灾。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与祭祀,成为黎族人民共同的生活习俗,维护着族内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生命财产安全。对祖先动植物图腾的崇拜,使人们产生了对祖先图腾的保护意识与习惯,形成氏族成员需要遵守的第二个公共秩序规则,对图腾不敬,不仅会招来祖先的惩罚,也会被氏族成员谴责。对祖先鬼崇拜的方式是“敬而远之”,即平时禁止说出祖先的名字,否则会招回祖先鬼,危害家庭生命健康。因此,关于祖先鬼,不仅自己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也不允许别人说出他们的名字。显然,对祖先鬼的崇拜与禁忌,是氏族成员内部所要极力维护的另一个公共秩序。
基于对神灵鬼魂的崇拜与敬畏,在黎族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有诸多具体禁忌存在,这些禁忌涉及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每一个个体和行为产生约束与规范作用。在这些禁忌规范中,多数是为自己家人的家口平安、生产顺利而对自己行为的一种约束,但也有一些禁忌涉及外人,要求外人不得为某些行为,或为了外人自己不得为某些行为。黎族人民通过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或对他人行为的要求,来实现平安、幸福,这些禁忌已成为黎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生产规范。例如,“砍山栏时,带饭到山栏边,到吃饭时不能一人先吃,必须共吃”,否则先食者会使后食者掉下树或被砍伤。“未吃过新谷饭,忌向别人借新稻谷”,否则影响别人生产。“死人埋葬时,忌埋棺于别人家坟前”,否则遮盖别人家坟,会使别家不祥。“宅门上置青树叶”,意即室内有病人,外人不得进入。“盖好新房时忌人进入该房哭泣”,否则主人生病,生产不顺。“亩头犁田时,不准别人进家”,否则会使稻子长不好。①
以上禁忌,前三条是对自身行为的要求与约束,后三条则是对别人行为的要求与警示,其效力均源自黎人内心的宗教信仰。正如前文所述,海南黎族的宗教信仰尚处于“万物有灵”阶段,处于生产力非常低下对自然现象缺少科学认识阶段的黎族先民,当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时,往往将其归咎于自身,认为是自身的行为亵渎了神灵而招致了惩罚,因此,为避免这些灾难的降临,必须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久而久之,其日常生活生产中的禁忌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多。
弗洛伊德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禁忌就是人类最古老的无形法律,是由民间约定俗成共同遵守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契约,与国家法不同的是,当人们违反了禁忌受到的不是外在强制力的制裁,而是独自承受的来自内心的恐惧、痛苦与煎熬。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离不开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从法律角度说就是一个稳定和谐的公共社会秩序,禁忌就是这个秩序的缔造者和维护者,它以吉凶征兆的可预测性,对人们产生警示作用,进而达到对社会的控制。
自然神、动植物图腾及祖先鬼,涉及的是黎族氏族社会的整体,在自然法秩序中,它是黎族人民的公共秩序,它需要合亩内、村内、峒内每一个成员来共同维护与遵守。为了不给自己、本家、本亩、本村,甚至本峒招来不幸,每一个人都必须自觉遵守对神灵的禁忌,神灵的神秘力量是公共秩序遵守与维护的力量源泉。诸多的生产生活禁忌,是黎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黎人最基本的习惯规则,它构成了黎族社会第二个层次的公共秩序。
不论是宗教禁忌,还是生产生活禁忌,在人们行为中体现为禳解,其表现形式一是事前的设防,另一是事后的补救,前者达到的是预防作用,后者实现的是心灵的解脱和秩序的恢复。在海南黎族社会中,对神灵等禁忌的禳解方法,视神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影响农业生产和丰收的自然神,打猎出征前的山神,导致生病死亡的鬼神,等等,其中有的可由黎民家庭独自自主进行,有的则需由亩头带领亩众集体进行,有的则由奥雅带领全村人进行,有的是由宗教职业者“道公”、“娘母”、“老人”①等专业祭祀人员进行。原始的宗教信仰,自觉的禁忌行为,神秘的祭祀活动,实现了自然法状态下黎族公共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2.“插星”
“插星”,也叫“打青”、“打星”、“打草标”,也被称为“禁星”,是一种事前设防的标志。“插星”用一种特定的草插在门上或某一特定物体上,或在某特定物体上刻上某种符号,表示祈求意愿或告示该物体已有主人。关于“插星”,宋《清波杂志》卷十二载:广南黎峒家有祀事,即以青叶标门禁往来。这是史料中对海南黎族“插星”习俗的明确记载,是指黎族群众进行宗教祭祀活动后在家门上挂青树叶以驱邪的祀事“插星”,它有避邪与禁止生人入内的作用。黎族社会中,“插星”的种类繁多,除宗教活动“插星”外,还有生产生活“插星”,生育、开山种地、水稻种植、收割庄稼、某物占有、煮酒、封村、警示等都会出现“插星”。在黎民中,“插星”的定义与作用至少有三种:一是财产取得的方式方法,如上节论述的黎族财产取得制度中,“插星”就是一种财产先占的表示方式;二是驱邪保平安,如上文中提到的“宅门上置青树叶”禁忌就属此类;三是具有广而告之的通告与警示功能,这种具广而告之的通告与警示功能的“插星”,就是黎族社会中用途十分广泛的禁止性习惯规则。
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标志,不同的场合,“插星”公告或警示的内容各有不同。如:在村口的树桩上挂树叶或芒秆,则表示该村正在发生瘟疫,禁止外地人进入本村。在地头塘边出现插有一根绑有青草的棍子,则表示这块田地、这口水塘已经有了主人,他人不得再去占有。在某一棵树或小树苗的树干上如有茅草打的结,或刻有“×”符号,则表明该树已有主人,将来该树或长大成材,或开花结果,均归插星者所有,他人不得砍伐、采摘。在本村的公有土地上,如有人想砍山种山栏,则需确定开荒的面积,然后用茅草在树干上打结或刻上“×”符号,以标明砍山的范围,别人看见插星标志,则自觉地另辟他处。总之,在黎族人民的生产实践与生活里,凡是人们看好的山地、树木、果树、牧场、草地、鱼塘、蜂窝等,一时不能利用又要说明物已有主的,就以插棍结草或划“×”符号作插星标记,别人不得占用。
带有警示作用的插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方面。当农作物遭受损害,如禾苗被牛吃了,或菜园被猪或鸡鸭践踏毁坏,其主人会在被破坏之处插上草结,或将被损坏的庄稼带回村边,捆好并插上草结,悬挂于村旁,让村民知道,以警告肇事者不要再搞破坏,或是看管好自家的家禽家畜,假如经“插星”后仍然有破坏现象发生,则查明后进行处罚。为避免别人从自家的田地里放水,或放水到刚施过肥的田里,黎人便在适合放水的自家田埂上插上草结,以警示别人不要放水。①
“插星”是黎族社会通用的一种无言通告,它受到了黎族人民的一致认同。如果说禁忌是一种精神控制的话,那么,“插星”则是一种行为约束,它告诫人们不能为之事。不仅如此,“插星”还有宗教禁忌所没有的现实的、具体的外在强制力,因为触碰了“插星”之物,或拿走了“插星”之物,不仅会产生精神恐惧,而且还会被认定为盗窃罪受到惩处。“采摘、砍伐被人已作标记的果实、树木,按盗窃论处。”①“插星”是黎族社会里人们必须遵守的习惯,黎族人民认同插星,并自觉地遵守“插星”所表达的规范要求,“插星”实现了对黎族社会公共秩序,特别是财产所有权秩序的具体、有效维护。
3.不偷不贪
黎族人民朴实善良,恪守信誉,廉洁自爱。不贪心、不偷盗是每个黎族人信奉的基本生活准则和处事交往原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黎族地区的基本社会风貌。不偷不贪是黎族地区的古老族规,是黎族地区在公共财产利益和个体财产利益方面的普遍行为准则,同时它也是上述插星规则在人们行为中的效力显现。
不偷不盗是黎族社会基本的行为准则。《方舆胜览·卷四三·万安军》条引《图经》之语道:黎人“其俗质野而畏法,不喜为盗,牛羊被野,而无敢冒认”。牛羊被野,不会丢失,这是黎族社会和谐安宁生活环境的生动描述,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景象,主要是黎人不喜为盗,在黎人心目中有自己的法则,这一法则指引人们不去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即使是遗失物,发现者也不会占为己有,而是将其拾起放到显眼之处,以便失主寻找。
不容偷盗是黎族人民维护财产利益的基本理念,其惩罚性规则是重罚。黎人不偷,也不受偷,对于偷盗行为绝不容忍。盗贼夜晚行窃不仅可以被打死,其家人还要被罚赔偿牛、谷等,罚来的物资供全村人共同享用。②对偷盗粮食的处罚是:偷1斗粮食,赔偿牛10头,其中一部分牛会被用来宰杀请客。③
4.参加劳动与互助
劳动是黎族生存的最根本手段,它不仅是黎人获取生存资料的权利,也是个体黎人向家庭、合亩必须履行的义务。在合亩地区,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亩为单位的共同劳动。在亩头的带领下,全体亩众共同劳动,参加亩内集体劳动是合亩制的基本行为准则和获得生活资料的前提。如果不参与劳动,将会受到亩内相应的惩罚,最严重的就是被开除出族群。在实施合亩制度的地区,“有极个别好吃懒做的亩众,屡教不改,便勒令其退亩,成为单干户”。①在黎族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水平下,被退亩后的个体生活将面临极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被间接宣判了死刑。
参加亩内劳动是一种带有无形强制力的强制行为,而亩内成员的互助则是一种自觉行为,不请自帮,有请必帮是自然秩序下黎族人民的一种自觉行为,而且世代相传。“亩内不论哪家哪户结婚、丧葬或有其他之事,大伙都会前来帮忙。如每当某个合亩成员的妻子要归来定居立户时,其他成员都来协助建新房,事后主人请大家吃饭饮酒,表示谢意。”②这种一家有事,众人出力,彼此相助的无偿行为,表面上看是黎族人民纯朴民风的体现,实际上它也是黎族社会的一种公共道德准则,它是不偷不贪的反面,是黎族社会公共秩序的另一种规则,它同不偷不贪一起共同构筑了和谐安宁的公共秩序。
自治秩序下的黎族习惯法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在追求合理秩序的过程中,以自我形成和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合理的秩序对于黎族人民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黎族生产力水平始终处于低下、简单状态,而且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对抗外界的力量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以合作为基础的分工是必要的,从事不同工作的人需要相互配合,从最初的生产到最终完成消费,一切行为都必须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安排,本族生命的延续和种族的繁衍必须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社会规则。这种规则按现代法律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规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怎样行为,而另一种则是行之有效的社会关系协调、处理机制。一方面,稳定的行为规则追求使团体形成一种可以信赖的秩序,并且保证种族生活的规则底线不被侵犯,在这种秩序的控制下,每个族人的行为和其获得的结果都将是可以被预知的;另一方面,纠纷、争议的协调和处理可以使本族人发生纠纷和矛盾时能够尽快化解,而不会激化成冲突,同时尽快恢复以往正常的秩序。
通过研究黎族自然秩序中的习惯法,我们认为,习惯法在财产制度方面,对个体权利成分的规定相对有限,更多时候,一个家、一个村或者在合亩制度下的峒才是习惯法关注和调整的对象。习惯法的直接目的指向的是全族的共同秩序而不是个体权益的实现,个体的满足是通过群体的满足实现的。在多年与自然界抗争的过程中,黎人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个体力量的不足,只有让渡一部分利益给群体,并且接受公共秩序的约束,才有可能在危难时得到全体族人的帮助,获取生存和繁衍的机会。因此,广大黎族人民愿意生活在这种习惯法的规制和影响下,黎族习惯法中保留了大量的共有制度和平均分配的原则。
从现有资料的分析来看,自然秩序中的黎族习惯法存在以下价值取向:
首先,强调生产、繁衍。这是黎族自治秩序追求的,也是黎族习惯法所反映的最重要目标。如同求生是一个人的本能一般,血脉的延续是一个种族的本能要求。而黎族的地理位置远离发达的中原文明,在生产水平、医疗技术等方面较中原落后十分明显,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确保种族的繁衍就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做法,而这些做法的核心要件一个是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另一个就是创造更多的生育机会。经过时间的变迁,能够取得明显效果的做法被予以保留,成为习惯法,并进而巩固社会秩序,这也就解释了偶婚制的社会起源。这一点在婚姻、家庭制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子孙血缘的纯粹在黎族习惯法中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只要一个黎族孩子能够为整个种族的延续贡献力量,那么他就是被认可的。许多学者认为黎族有尊重妇女的优良传统,但严格说来,被尊重的不是妇女,而是妇女的生育功能,离婚妇女和寡妇带子再嫁之所以不被歧视,这是因为和他们共同到来的是血脉相继的可能性和相对高效的劳动力。
其次,强调人性关怀的同时追求秩序的维持。由于对生命的重要性有着出于本能的深刻认知,黎族习惯法比较强调对生命的保护。在其习惯法中能发现不少颇有人文关怀的内容,比如在遇到灾荒年时,向同村、同峒的人借粮度日是不用归还的,只要承诺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即可;此外在财产分配制度上,“合亩”组织保留一部分财产,在遇到荒灾年份时向本峒居民发放,已经具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性质。这些自发形成的习惯法内容,彰显了自治秩序中最原始的人本观念,为黎族习惯法乃至整个中华法系都增添了积极的内容和靓丽的色彩。当然,任何秩序都不是牢不可破的,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是不可避免的,纠纷一旦产生,原有的秩序就会存在被打破的威胁。为此,黎族人民非常重视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整,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社会秩序良好有序的目的。以禁忌和插星为主要形式的黎族习惯法中凝结着黎族人民所特有的秩序观念和法律智慧。
最后,黎族习惯法中有诸多仪式,这些仪式意义重大,它们说明黎族习惯法并非真的无形,只是不具备法律稳定的文字表述而已,那些庄重而神秘的仪式正是黎族习惯法存在的强有力证据和系统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证人将手按在圣经上宣誓证词真是一种法律文化的话,那么各类黎族仪式同样也是习惯法中的法律文化,也许两者在内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上存有差异,但在性质上高度趋同。
附注
①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75~176页;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高泽强、潘先锷著《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第174~178页。
①道公、娘母、老人均非专业宗教人士,只是具有某一祭祀方面的技能或功能而已,他们都不脱离劳动,靠自己的生产劳动生活。道公,民间称之为“三伯公”,因病学道,查鬼看病,有的地区有文武道公之分,世袭,父传子,不授徒不外传。娘母,专门从事民间祭祀活动的人,原先为女性,后也有男性加入,称之为“娘公”,以查疾病、作祖先鬼法事为特色,实质为巫师,传女(或媳妇)不外传。老人,也称“鬼老人”,“专门念诵祖先鬼名之人”,是黎族各家族中能沟通祖先鬼的中介人,职责是用黎语念已故直系家族祖先鬼的名字祭鬼,多为世袭。道公、娘母、老人祭祀人员很受黎族人民的尊敬。参见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73~175页;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高泽强、潘先锷著《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第1~22页。
①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11页,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海南民族研究(一)——五指下山的耕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第169页;高泽强、潘先锷著《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第86~87页。
①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11页。
②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11页。
③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侗、水、毛南、黎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511页。
① 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36页。
② 陈立浩、陈兰、陈小蓓著《从原始时代走向现代文明——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变迁历程》,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