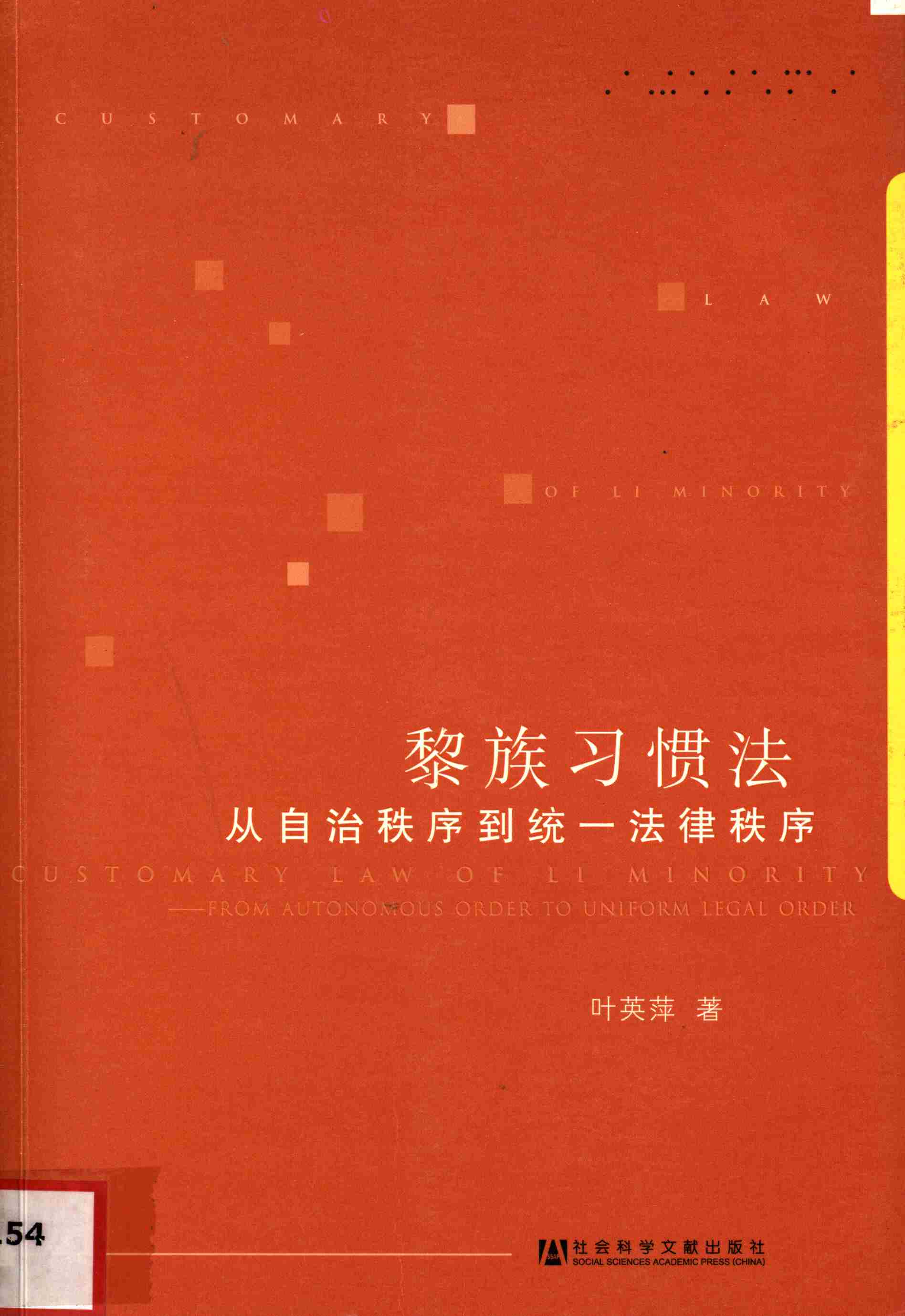内容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百万的为数不多,黎族就是其中之一。据海南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截至2010年11月1日0时海南的黎族人口为1277359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4.73%,①黎族是海南的第一大少数民族。“黎”是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黎族普遍自称为“赛”,依据分布地区、方言及服饰等差异,黎族内部又分为“哈”、“杞”、“美孚”、“润”、“赛”等五个方言区。海南黎族主要分布在海南岛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相对集中在海南岛的三亚市、五指山市、东方市、琼中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等9个市县。
大约一万年前,华南大陆或马来半岛上的原始人类在四处寻觅食物的过程中,发现并登上了海南岛,从此海南岛上有了人类的繁衍生息迹象,尽管目前尚不能确定他们是否为黎人。海南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设置郡县开始的,之前的历史称作海南史前时期。②据现有史料记载,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在海南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③是海南岛上较早的居民。尽管新中国对黎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有半个多世纪,黎族也受到海南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感受了现代化的生活,但是,黎族人民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本民族的习惯和传统,信守着本民族特有的禁忌和崇拜。这些禁忌和崇拜早在原始先民时就已产生,历经上千年的演变形成了黎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秩序。海南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环境,限制了黎族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同时也塑造了独特的黎族社会文化,形成了以崇拜与禁忌为观念基础和力量源泉的黎族习惯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黎族社会组织和习惯法律秩序。
第一节 自然秩序状态下的黎族社会
一 宋之前的黎族社会建制
黎族在秦朝之前,即定居于海南岛,在此后一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一直是海南的主要居民。关于黎族族源在史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海南黎族来源于南洋群岛的一些古老民族。例如德国人史图博在其《海南岛民族志》一书中,认为黎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与印度尼西亚的古代马来人、印度支那大陆各族有着显著的类似,刘咸教授在《海南岛黎族起源之初探》(《西南研究》1940年第一卷第一号)中,根据黎族的文身、妇女服饰、口琴、织绣物品等表现的特点,推断黎族的文化系属于“太平洋四个文化区中的印度尼西亚区”,“与南洋群岛各民族所有者大同小异”。另一种观点认为黎族由古代百越族发展而来。中国学者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大多认为黎族是从古代“百越”族发展而来,与“百越”中的“骆越”支关系尤密。①民族学者还从考古学、语言学、地名学以及民族学等多个方面论证了黎族与古代骆越人的关系。①认为黎族源于古代“百越”族的“骆越”一支,是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共同观点。
秦朝至隋唐五代时期,汉族移民不断进入海南岛,中央政府也不断设置地方机构,管理、垦殖海南地区,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和汉民居住区域始终较为有限。
汉朝在武帝时期以强大的军队攻略海南,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设立珠崖、儋耳两郡,隶属于交趾刺史统辖。但汉朝政府在设置郡县后,驻守海南的官吏、军队以及外来移民欺侮当地黎民,掠夺地方财富,黎民不堪忍受,“故率数岁一反”。在黎民不断起义反抗之下,至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汉中央政府将儋耳郡并入珠崖郡。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又下诏放弃珠崖郡,在海南仅保留了朱卢县建制。②汉王朝在海南的统治已经仅保存在交通便利的极为有限的区域。西汉以后,中央政府多次征伐海南,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建立长久稳固的统治,位于海南本地的政府管理机构时建时废,或在广东大陆的官署遥领海岛治理。
在南梁大同(公元535~546年)年间,当时的儋耳归附的俚僚首领冼夫人③率领一千多峒黎人归附南梁政府。冼夫人还请命于朝,置崖州。冼夫人在政府的授权下,实现了又一次较为统一的黎族人的自治,以归附朝廷的方式达成了汉人政权与黎人的和平。在南北朝以前,大体上是“汉在北,黎在南”;隋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有所扩大,汉族移民的居住区域向南有所扩展,形成了“汉在外,黎在内”的分布格局。居住在海南中南部的黎族人民,在宋朝以前,大多数历史时期是处在与外界交往很少的原始状态,其社会生产、文化观念都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很少受到汉民的影响,其社会组织与秩序,大体保持了村、峒的内部自治,治理的规则主要是遵循传统习惯。
二 封闭的海岛与优越的自然环境
海南四面环海,琼州海峡将之与祖国大陆隔开,在古人看来,海南无疑就是天边。虽只一水之隔,却减低了黎族与中原的联系密度。黎族所居之海南,“海中洲居,广袤千里。(《汉书·贾捐之传》)周回二千里,径度八百里。(郦道元《水经注》)四州各占岛一隅。外环大海,中盘黎峒”。“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数千里,历代安天下之君必遣勇者戍守。”①交通技术的落后和交通方式的简陋,使得海南与中原之间的往来成为艰难之事,中央政权欲对海南实行有效管理,也是一件十分艰难之事,只有勇敢者才能胜任。也正是大海的天然阻隔,使得汉初虽在海南建立珠崖、儋耳两郡,却并没有实行有效统治。路途遥远固然是原因之一,海岛的封闭落后也是封建中央统治者不重视海南的另一原因。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至宋,封建中国的生产力已有很大提高,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大海的天然屏障,却阻挡了中原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进入,整个海岛仍然处在较低层次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尤其是黎族居住地区,大山环绕,林深叶茂,与海岛上的汉族居民相比,海南的黎族则处于更加封闭与落后状态。他们主要集中在五指山地区,大山既是保护他们的天然屏障,同时也阻隔了他们与外界的交往。黎民不仅无缘广泛接触中原文化,而且与岛内的汉族和沿海居民也少有往来,他们仍然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生活在具有浓厚血缘联系的相对封闭的村峒里。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在中央政权对黎族地区实行有效统治之前,对黎族人民影响甚微。
虽然远离中原,与大陆隔绝,同大陆甚至是海岛的汉民族交往稀少,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黎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优越的热带自然环境为黎族人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丰富的物质资源养育了世代黎族人民。海南的黎族主要分布在海岛的中部和南部,这些地区多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以暖湿为气候的主要基调,全年都阳光充足,雨量丰富,而且土壤肥沃,动植物资源丰富,更兼“中部高耸,四维低洼”的地形,使得河流纵横,编织了天然的灌溉网络,在这样优良的自然环境下,水稻在南部地区可以达到一年三熟,而玉米、番薯等主要粮食作物甚至可以终年种植,可以说黎族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刀耕火种的低层次生产劳动,维持温饱的低质量生活水平,近乎原始的落后生活方式,再加上中央政府无求海岛赋税,岛上居民少了中原地区居民缴纳赋税的生产压力。封闭的海岛生活,没有外力压迫的生产生活,使得岛上黎族人民比较满足于现状,如有反抗斗争通常也只是在黎汉之间或黎人内部,对封建中央政权难以产生大的影响和危害。正是这种封闭的海岛环境、大山阻隔和优越的自然资源,以及只需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使得黎族发展缓慢,其生产力水平长期处于极为低下的原始状态。正是在这种缓慢的发展过程中,黎族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与禁忌,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治秩序。
三 原始的生产力水平
四面环海的海岛,与大陆存有天然屏障,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海峡凭借人力难以逾越,使得海岛环境的封闭性与其自然环境的优越性同样突出,因此黎族的科学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发展缓慢。黎族的社会生产直到近现代都处在落后的原始状态,并且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关于黎族的农业生产记载道:“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①在生产领域中,种植农业是唯一独立的生产部门,狩猎、手工制作都是辅助性的补充。
黎民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极为原始简陋,其主要器具为木器、竹器和石器,铁制工具到了宋朝以后才通过汉民少量输入,从事黎族历史研究的学者认为:到了新中国成立前200年,黎族人民才较大范围地利用通过汉民输入的铁制器具。①即使如此,铁制器具也没有完全取代传统工具,经常和木犁、竹耙共同使用。黎民的生产耕作分为山栏耕作、旱地耕作,少数地区有水田耕作,山栏和旱地耕作的生产方法主要以原始的“砍山栏”、“收山栏”②为主,属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集体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土壤的肥力和天然降水来实现作物的生长,农作物的单位产出比率很低。至明代,在汉民帮助下,农具、生产方法已有很大改进,仍未改变粗放式耕作方法,时人顾岕在《海槎余录》中记述道:“黎俗四月晴霁时,必集众斫山木,大小相错,更需五、七日,聕洌则纵火,自上而下,大小烧尽成灰,不但根干无遗,土下尺余亦且熟透矣。徐徐锄转,种棉花,又曰贝花,又种旱稻,曰山禾,禾粒大而香可食。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另择地,所用前法别治。”“迁徙不常,村落聚散无定,所耕田在是即居于是,日久地瘠则去而之他,故村峒土名,数年间数迁数易,其地不可考也。”③正是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简单,农业耕作靠天收,才导致黎族村峒的经常性迁徙,当一块土地肥力丧失不再适合耕作时,黎民便整村开始迁移,寻找新的适合生存的土地。黎族最先进的旱田耕作就是采用“牛踩田”,即由人驱赶牛群在田地里来回走动,把泥土踩碎,然后再以竹、木器具插穴、投种。
水田的耕作要比山栏、旱田的耕作更有效率,但其耕作技术仍然十分落后。最先进的水田耕作就是采用牛犁,一般劳动力组合十分原始,犁地效率很低。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牛犁仍然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上:“在一块2亩左右的田上,驱赶着24头水牛拉犁,造成牛碰牛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犁田的效率。”①加之,当时普遍使用的犁是竹制或是木制的,②比铁制犁的效率要低50%以上,且耕牛的数量也较少,还没有田间除草、施肥等精耕技术,总体生产效率还处在极低的水平。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黎族的农业生产已经历了诸多改进,普遍采用了铁制器具,但仍然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稻谷的产量是很低的,水田每亩产稻谷百余斤,旱田几十斤”。稻谷纵然有每年两熟或三熟,在正常年景下,“每亩年产量仅达120斤左右”。③
除了粮食作物外,黎族也利用优越的自然资源进行副业生产,但是同样受限于生产力的束缚,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其种类主要包括:纺织业,狩猎和捕鱼,饲养禽畜,种植热带、亚热带水果等。
在自然环境优良但是生产水平有限的背景下,黎族族群的生存一方面依赖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主要依靠群体的协同合作,因此,群体主义是黎族社会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族群得以存续和繁衍的保障。
黎族的自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黎族习惯法的形态与内容:海岛封闭的状态为习惯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成环境,使得黎族习惯法保持了高度的原生状态,对黎族居民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脱离海岛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去研究黎族习惯法将必然缺乏实证意义;而黎族居民生产力水平的局限性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也决定了其习惯法所确立的秩序目的和价值追求。
第二节 黎族的神灵崇拜与禁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点,神灵的本质是原始人将支配其生活的自然力量进行人格化,是这种伟大力量在人类意识中的虚幻反映。海南黎族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黎族居民对能够左右其生死温饱的自然力量无法进行科学解释,自然将其视为神灵,为了族群的生存繁衍和粮食丰收,各地黎民普遍有着不同的神灵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为避免灾祸,黎民敬畏鬼神,恪守祖先传承下来的各种禁忌。神灵崇拜和传统禁忌,反映了黎民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是法律秩序的观念基础,也是习惯有效性的文化基础,对神灵的崇拜与禁忌是黎民自觉遵守习惯的力量源泉。
一 频发的自然灾害
黎族居住在亚热带、热带地区,此地雨量丰富,气候湿热,大海环绕。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一方面造成剧烈的自然灾害多发,另一方面使位居深山的黎族人民生活条件比较恶劣。“周岁多东风,秋夏间飓风,或一岁累发,或累岁一发……发在秋夏,有云物之先驱,非青华为起。未几率然凌寻,飘忽怒号,极万籁之变,屋瓦皆飞,坤轴欲转,人物震慑,沆澥湃奔,幨帱倏吼,海鸟翔,天脚晕若半虹,则飓风。”①《方舆志》:“周岁皆东风,秋夏飓风。”台风是海南破坏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给人们带来恐惧的常见灾难。“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汉书·贾捐之传》)病无药饵,但烹犬牛祀神。(乐史《太平寰宇记》)”(②)关于海南的气候与自然条件,《康熙昌化县志》卷一《舆图志》“风土”中有如下描述:“一日之内,一身之间,冷热互见,是以人体疲倦,脚气之患不时有也。有蝇则无蚊,有蜈蚣则无蝎螫,此定数也。而海南诸种皆备,蝇无四时皆有。蚊有二种,有小而黑者,昼不避人,咿唔左右,闻为可厌;夜间流毒者,诸方所有也。……东坡云:海南风俗,食无肉,出无兴,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惟夏无蝇蚊则可喜也。”“地居炎方,多热少寒,时忽瘴云埋树,若非仁人君子,岂得而寿耶。”③在原始黎族社会里,影响其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因素:一是湿热气候及毒草虫蛇,使黎族人民生命健康时刻受到威胁,面对疾病,无医可诊无药可治,他们只能从自身找原因,求助于神灵保佑;二是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兽灾是最为常见的自然灾害,黎民辛勤耕种的粮食作物,经常在一夜之间就被山猪、猴子等野兽啃食破坏。水、旱灾害,台风也是每年多发的灾害,因为海南总体降雨量大(大多数地区年均降雨量在1800毫米至2000毫米),但降雨分布不均匀:降雨多集中在八九月间,容易发生水灾;二、三、四月则是旱季,多发生旱灾。对于病、虫灾,黎民多束手无策,只能以其原始的超自然的方式来解释。黎族没有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然没有改变靠天收的局面。例如,在1953年黎族聚居的乐东县遭受旱灾,其中包谷60%未有收获;1954年,自治区7县从6月至8月初又普遍受旱,其中乐东、东方受灾更为严重,大面积稻田无法插秧。①各种自然灾害,也是黎民生产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人的生老病死等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黎民无法以其自身的知识进行解释,也无法以自身的力量来避免。因而,黎民求助于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用神灵意志来解释这一切,并通过各种神灵崇拜和禁忌规则,试图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避免自然力的无情伤害。
二 神灵崇拜
局限于认识水平和知识的贫乏,以及原始社会末期极其低下的生产力,黎族人民较早地形成了原始的宗教神灵崇拜,各地自然环境不同,所崇拜的神灵也有很大的差异,既包括自然神灵崇拜,也包括动植物图腾崇拜,还有祖先崇拜。
就自然神灵崇拜而言,有的黎民崇拜天,有的崇拜地,有的崇拜水,有的崇拜山,②还有崇拜火、日、月、风、树木的。③自然界的天、地、日、月、山、水、火、石、风、树、鬼魂等现象,在黎民看来都是能左右自己且不可冒犯的鬼魂。①“天鬼”。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天体有云雾、风雨、雷电等现象发生,它伴随着人们的生活。然而海南黎族人民认为,这些现象是一种不灭的神灵,它能使庄稼旱死涝死,受病虫侵害,也可使庄稼丰收,还能使人头痛发烧生病,直至死亡,因而人们十分惧怕这些“天鬼”。②“地鬼”。黎族先人认为农作物丰收是“地鬼”的恩赐,祭祀地鬼以表示期望和感谢。③“水鬼”。它在诸神中位于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主宰田地不受旱涝灾害。④“石”。黎族认为石头神能促进生育,能驱赶破坏庄稼的鸟兽,“有石之细润者,黎人谓之石精,大如枣栗,五色皆有之,黎中珍而藏之以宝,谓可镇家,猎者藏储身边,获禽兽独多”。①⑤“山鬼”。合亩地区的黎族人认为,山中的一切飞禽走兽都受“山鬼”管辖,人们上山打猎必须经过山鬼的同意才行。⑥“雷公”,在黎族人的传统观念里,是代天执法和行刑之神,它能窥见一切人间事,谁做好事谁做坏事,谁有涵养谁没有涵养,它都一目了然。凡是没有道德和做坏事的人都要受到雷公的惩罚。此外,诸如火、日月、风、树、牛、兽、鼓、锣等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灵气,能给人们带来吉与凶,善良的人因此而有神福运,作恶的人因此而产生凶魂,遭到厄运。
就图腾崇拜而言,黎族有动物图腾崇拜,也有植物图腾崇拜。在动物方面,以蛇、鱼、鸟、狗、蛙、牛、猫等为崇拜对象,在植物方面,则以葫芦瓜、水稻、榕树、木棉、竹为主。既有崇拜龙(鱼)图腾的,有崇拜鸟图腾的,有崇拜牛图腾、狗图腾的等,②还有崇拜葫芦瓜、木棉、竹子等植物的。黎族每个氏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图腾,认为自己的氏族起源于它,这些图腾有动物、植物或其他生物。由于相信自己氏族起源于它,此物也就因此成为该氏族的祖先或保护神,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图腾加以崇仰。以动植物为主的黎族图腾崇拜,“其特点是认为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植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③对于自己氏族的图腾,黎族人民一方面将它视为保护神,以一定的形式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如姓、氏族集团的称号等,另一方面,给动物图腾以一种特殊的礼遇,如农历三月初八为牛节,在这一天不能杀牛,不能用牛耕地,“保亭毛道黎族视猫为自己的祖先,禁止杀猫吃肉”。①
就祖先崇拜而言,有崇拜祖先鬼的。黎族的祖先崇拜是建立在鬼魂观念基础上的。黎族将祖先称为祖先鬼,他们认为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氏族普系,都有自己的祖先鬼。有的氏族还自认为本部族由某种神灵繁衍而来,把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结合为一体。祖先鬼是恶鬼、凶鬼,②它支配着人们的生存与幸福。对祖先鬼崇拜的方式是“敬而远之”,即平时禁止说出祖先的名字,否则会招回祖先鬼,危害家庭生命健康。
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黎民社会虽经过了两千余年的演变和与周围民族的融合,但他们仍然保持着普遍的神灵崇拜。这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调查资料中发现:“在调查的22个点中目前仍以祖先崇拜为主的有8个点,以信奉自然的天鬼(雷公鬼)为主的有4个点,英雄崇拜(峒主公)的有3个点,其余便是因接受道教以后改奉‘神’的。”③祖先崇拜是黎民中较普遍的一种崇拜,而每一地区的黎民无一例外地都有神灵崇拜,神灵在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无处不在。这说明黎民在应对自然现象上,神灵崇拜是比较普遍的文化特征。
自然神、动植物图腾、祖先鬼,都是黎族先民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对世界万物、社会常态的一种朴素的认识与思考,其核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灵魂意识,它根源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黎族先民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汉时的郡县建制,尚处在母系社会的繁荣时期,郡县建制后海南岛的母系氏族开始向父系社会过渡,人们建立了相对固定的生活村落。为了繁衍后代,黎族先民开山劈岭,刀耕火种,狩猎捕捞采集,但在当时的生产力之下,生产工具粗糙、简单,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面对不能左右的族人的生、老、病、残、死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人们对这些大自然的现象产生了恐怖、敬畏,祈祷免受其害,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产生了对各路神灵的禁忌。这种原始宗教崇拜,在人类社会,几乎每个民族都曾经历过,黎族当然也不例外。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是,由于文化知识的贫乏,生活空间的封闭,黎族人民的这种宗教禁忌观念,直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仍然存在,对神灵的崇拜与禁忌,仍然普遍盛行。
出于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黎人也注重祭祀。负责主持祭祀的人员都声称自己具有和鬼神直接进行沟通的能力,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使鬼神附于其身上,并借自己的口传达鬼神的意志,黎人对此也深信不疑。通常情况下,主持对自然鬼神祭祀的被称为“娘母”,而负责祭祀祖先鬼的被称为“鬼公”。“娘母”、“鬼公”是专门的“神职人员”,但神事不是其唯一的工作。总之,“海南黎族人民过去仅有一些虚幻的、超自然的观念,以及某些巫术和神话传说,没有系统的神话理论,还未设立神堂和统一固定的崇拜偶像,也没有产生专职神职人员阶层,黎族宗教尚停留在原始宗教阶段”。①
三 禁忌与占卜
禁忌,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犯忌讳的话或行动”,在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中称为“塔布”,意为“忌讳、戒律”。禁忌是一种社会心理层面的信仰习俗,在民间禁忌无处不在。在海南黎族社会中,禁忌广泛存在于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控制着人们的精神意识,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为了不触怒神灵,保佑家口平安、生产顺利,黎民在生活、生产等各种活动中有诸多禁忌。黎民的禁忌主要分为八类,以下仅举保亭加茂地区的禁忌来说明:①生活禁忌(“睡在床上,头忌向门口”等十八项);②生产禁忌(“过旧历年节未过完初四,忌搞生产,否则天旱”等十项);③生育禁忌(“妇女生产未满月,外人忌进宅,否则会致婴儿多病”等四项);④婚姻禁忌(“新娘入宅时若未经火堆和打破鸡蛋,不得入宅,否则鬼会随新娘入宅作祟,致人生病”等四项);⑤丧葬禁忌(“丧宅在未埋葬死人之前,忌入别人宅内,否则使别人不祥”等三项);⑥行猎禁忌(“未过旧历年初四,妇女忌与男子同桌一起吃饭,否则行猎难获猎物”等两项);此外还有节日禁忌、宗教禁忌。②黎人生活在神灵崇拜与禁忌的网络中,对于生活、生产问题,或是面对自然灾害时,他们多希望得到神灵的指导与启示,通过自己的虔诚得到神灵眷顾,并能够在现实中完成与神灵的对接,而巫术和占卜就是黎人完成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他们既是黎人与神灵沟通的主要方式,也是最基本的习惯规则。
黎人多信巫术,尤以采取合亩制的地区为甚。①在对自然界认识受限的情况下,黎人常常通过进行充满神秘感的各种行为以实现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治疗疾病。黎人认为疾病主要是由鬼神附体作祟导致,所以在有人患病时,通常采用巫术,将导致疾病的鬼神找出,并使其离开患者,以实现治病的目的。
占卜是黎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自然界不确定性的畏惧,黎人在进行捕猎、打渔、婚嫁、丧葬等活动之前都要进行占卜,以确定吉凶,只有占得吉象,方进行活动。②
对神灵的祭祀、对禁忌的遵守,以及占卜活动,一般由黎人中的尊长率领族众来共同进行,这也是黎人最重要的团体活动。频繁的祭祀、诸多的禁忌、重要活动的占卜,凝聚了黎人的团体意识,这些活动也传承着黎人的文化,支持着传统习惯规则的遵守。
四 习惯与习惯法
不考虑其内容的科学性,神灵崇拜、占卜和禁忌等活动对于黎族习惯法的形成意义重大,在深刻理解这些活动的寓意后,结合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我们能够大致勾勒出一幅习惯法形成的可能性图景:受限于原始状态的生产力水平,黎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预测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面对自然界各种神奇的现象和巨大的能量,黎人只能将其归结为神灵的意志,由此他们对神灵、图腾和祖先产生了无限崇拜,出于这种崇拜和忌惮,就必然在生活中小心谨慎,会考虑每个行为与神灵可能产生的关系,为了实现趋利避害的目的,会刻意地对一些言行加以限制,如果为不该为的行为,或说不当说的言语,会导致神灵的不悦,进而招来灾祸,这对于黎族人来说是最终极的惩罚。而这种限制经过世代传习,形成稳定的规矩也就是禁忌。这种禁忌已经具有法律的雏形。
但是禁忌距离实际的习惯法尚有距离:首先,禁忌调整的事实上是人和神的关系,它很难直接应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其次,禁忌是一种消极性的规范,它只能指引人们不去做什么,但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情况下需要有规范来指引人们怎样去做,这个问题靠禁忌是无法解决的;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禁忌的禁止性规范是笼统的,而生活中的各种情形是具体的,主观意图上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程度上的严重或者轻微,以笼统的禁忌去规范具体的行为,很有可能会造成显著的不公平,所以为了更进一步、更细化地指导生活和行为,习惯逐渐产生。
习惯是对禁忌的一种主动选择和生活化。在面对共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时,如何行为能够产生最佳的效果是黎人必须思考的问题。远古留下的禁忌经历了时间的考量后,有些被保留,有些被弱化,有些被淘汰。根据被保留下来的禁忌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黎人开始总结生活中的各类与禁忌相冲突和不相冲突的惯常做法。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由模糊的观念变得清晰、具体,并进而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成为稳定的习惯。
从习惯到习惯法则是另一个漫长过程。习惯法即“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习惯最初产生于小范围的群体,随着该习惯的不断推广,适用的区域到达了一定的范围,同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趋于成为整个民族共同承认并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被遵守与认同后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黎族人彼此之间在进行交往时根据这种习惯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进而得到黎族社会的公认,如果违背了这种关系,将会对行为人产生不可避免的消极后果。当人们的行为有意无意地被习惯约束,违反习惯时受到内心自责和社会公众谴责并承担不利后果时,习惯法就已经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得到了确立。
所谓黎族习惯法,就是黎族同胞在其长期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为大家所公认和遵循的风俗习惯、惯例和通行做法等行为规范。
第三节 黎族的紧密型社会组织与权威
群(团)体主义是黎民生活的最基本特征,群体主义也是黎族习惯法贯彻的指导思想和倡导的价值取向,“以维护群体的利益为标准”在黎族习惯法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它首先体现在黎族紧密型的社会组织上,具有血缘关系的户组成的合亩,由合亩构成的村,由村联成的峒,是黎族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
一 家庭与“合亩”
为了克服各种不利的自然因素,确保族群的生活安全和生产有序,黎人选择了一种紧密联系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地域分布上尽可能稠密,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共同参加劳动,平均进行分配,通过满足群体的方式实现个体成员的利益最大化,这类生活方式的典型就是合亩制度。
合亩的基础是户。基于婚姻而形成的家庭,是黎民的社会消费单位——户。户掌握一定的生产工具和资料,而黎民在家庭的基础上,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合亩。①合亩是基本的生产组织、生活组织,是几个家庭合伙占有土地进行合作耕种的形式。家庭是合亩组织的细胞。合亩的组织基础是血缘关系。合亩组织大小不等,既有2户到3户的兄弟亩、父子亩,也有多达30多户的大亩,不过这类大亩非常少见,通常情况是2~6户的亩居多。①在合亩地区内,一般是共同生产,平均分配。亩头是合亩组织内生产、劳动与产品分配等事务的指挥者和组织者,在黎语中的含义是“带头犁田的老人”。②亩头对本亩的成员实施家长式的领导,由本亩内的男性长辈担任,最初亩头是被推选产生,之后由本亩内的男性长辈依次担任。③
黎族合亩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组织、促进生产,亩内的所有成员只要到达一定年龄都需要参加劳动,除了个体可以单独进行的渔、猎等劳动活动外,所有成员的主要任务是参与集体劳动。在集体劳动中,亩内成员同出同归,共同劳动,不将劳动任务分配到个人,也没有更为详细的劳动计划,而是亩众一起动手完成某一项任务。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平均主义劳动方式。④
在合亩组织内,劳动工具一般属于私有,牛、土地等生产资料虽然归由各家看管,但不属于私有,而是合亩成员的共有财产,由合亩统一调拨使用,且没有报酬。
对于劳动产品的分配,合亩制采取的方式是按户平均分配,对于人数多寡,男女、年龄比例等因素都不加以考虑,并且在分配之前还要留出一定的公共粮食以备用,在出现饥荒时,动用这些储备粮帮各户渡过难关,这部分的具体内容在第二章还有详细的介绍。
二 村、峒
村和峒都是地域性社会组织,在未被封建王朝统治之前,它是维持黎族社会内部正常秩序和推动黎族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组织。黎族古代社会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村落或行政组织:村、弓、峒,其中弓、峒是具有鲜明黎族特色的社会政治组织,是黎族一种古老的氏族部落或村落组织。①“山凡数十重,每过一重,稍有平坦之处,黎人即编茅居之,或数十家、数百家相聚为一村,亦名一弓。有众至千余人者为大村,其小者仅止数家。”②从组织上说,即数个合亩组成一村,每个自然村有一个村头,在一些地区被称为“亚雄”,③其职能是处理本村的内部事务。若干个村组成一个峒,作为黎族最大的社会团体单位。“黎地多以峒名,峒内散处各村,并附一峒,明所属也。惟崖州曰村,陵水曰弓,其散处各村并附于一村一弓,亦如峒制。”④民国时《海南岛志》也记载:“黎人择地而居,自谋生活……峒之大者十村八村,小者三村五村。”⑤峒的原意即“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的地域”。⑥峒有大小之分,且规模并无定数,小峒可能只包含两三个村落,而大峒则可能由十几个村组成。总之,黎族峒组织是由具有血缘纽带的黎人共同构成的、峒内有完整行为准则的共同的居住区域。黎族峒组织,文献早有记载,尤以宋元后为多。宋时,黎族的每一宗姓为一峒,海南全岛族峒颇多,⑦且规模均小,峒与峒之间的联系较少,各自独立。⑧到明代,黎族地区仍以峒为主要的社会组织。据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记载,各州县黎峒数量为琼山126澄迈137……明代海南岛12个州县中,共有黎峒1260个。⑨至清代,黎族地区开始设立土官制,主要是在黎族村峒设峒长、总管、哨官、黎甲、黎长、黎首等职。由于大批村峒划入政府直接管辖的领域,峒的数量大大减少,只有42峒,822村了。①峒组织的存在,使得黎民的社会组织从原本单纯的血缘组织发展为血缘和地缘的结合,并将血缘中的亲密关系带入了地缘组织中,形成了千百年来一直左右黎族人民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基础——“同峒皆兄弟”的意识。②峒内成员在彼此有困难时要互相帮助,并且本峒内成员之间享有财产购买的优先权。
各峒领域之间多以山、河为界,而且要通过立碑、种树的方式予以明确。峒界的划定始于何时,目前尚未确定,但是近代的划界常常需要进行一定的仪式,由一峒的峒长杀牛一只,制成肉串,送给邻峒各个峒长,接到肉串的峒长把肉串悬挂于门前,并告知本峒成员,不要侵犯对方峒界。③在黎族观念中,峒界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一峒成员要越过峒界到另一峒进行种植、砍伐、捕猎、打渔必须要提前向该峒声明,并进献一定的礼物。对方的峒长对于此类事件也不可独断专行,而是必须经过全体峒成员的同意,方能授权,而且授权是有期限的,多为一年,一年后必须重新经过上述程序以确定是否继续。如果硬闯入他人峒界,则极有可能造成冲突甚至械斗。④
三 黎族社会的权威
在黎族社会,权威是不可或缺的。权威就是使人信服的力量或者人、物。他们对一个组织、社会的稳定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黎族社会同样如此,而且黎族权威对于黎族习惯法的形成和适用也有重大意义。
黎族社会的权威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祭祀活动中的神灵权威。另一类则是各个级别的社会组织首领,如亩头、村头、峒长等等。
新中国成立前夕,黎族的民间信仰意识大部分仍停留在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祭祀活动中的神灵权威也一直享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得到普遍的尊重与认可,发挥着传达神意和反馈民声的双重功效,实际上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人化。在黎族社会,母娘、娘公、道公、拜公、老人等都是受人信奉的神灵权威。他们的作用虽然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包括:主持祭祀自然鬼神和祖先鬼神的各种仪式,利用巫术治疗急症病人,向神灵祷告、祈福,并就具体事宜向黎民下达具体指示。而这些权威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带有神秘色彩,一般都是在大病后,突然神灵附体,获得了某种超能力,便取得了代言鬼神的资格。在一些仪式上,他们经常会突然失去知觉,躯体成为鬼神暂寄的居所,直接以神鬼的身份发号施令,然后再回复原来的个人意识。黎人对此极度尊崇,并深信不疑。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有伪科学的成分,但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神灵权威的身份和法术都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所有的神灵权威在进行各种仪式时都告诫黎民为善,尚未发现有鼓动作恶的情况,而且也有关于这些权威通过法术成功治愈疾病的记录,①客观上也带来了一定帮助。此外,神灵权威的最大意义仍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持了黎族内部稳定。神灵权威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仍是围绕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鬼神代言人。作为同一个祖先的后裔,和平共处才是祖先的心愿。于是围绕着神灵,存在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黎族群体产生了强大凝聚力,内部和谐并一致对外,这种矛盾、斗争、合作共存的社会状态,伴随着黎族的进化,也见证了习惯法的产生与成熟。
在黎族村峒中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一个大塘,必有一条大鱼;一片山林必有一只‘谷姑’;一片村庄,必有一个‘土地公’;一个地方,必有一个‘头人’”。②这正好映衬了黎人对社会团体内权威的尊重和服从。史书上有记载,“(黎人)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③在现实黎族社会,亩头是最基础的领袖和权威,是一亩之长,在本亩内具有绝对权威,亩众必须服从。其权力行使的范围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兼具行政管理与司法调解的性质。他要全面领导进行农业生产,负责生产之前的各种祈祷活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亲自从事劳动,起带头和模范作用,以激励全亩的生产热情。亩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都要由亩头过问或者直接办理,比如亩众买卖田产、房屋、耕牛等只有在全亩同意的情况下由亩头代理买卖,而盖房子、娶亲这类事情也都要征求亩头的意见。当亩众内部出现纠纷时,亩头要出面进行协调,对轻微违反习惯法的人,要予以训诫。亩头并非当然终身制,而是始终处于亩众的监督之下,一旦德行不端,或者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则很有可能被亩众问责,遭到罢免和撤换。
峒长是地域性的团体领袖,峒长的产生除首任外一般也并非选举,而是按照父死子替、兄终弟及的方式罔替。清人所著《黎岐纪闻》中也记载:峒首,“大抵父死子代,世世相传,间有无子而妻及弟代之者”。①妇女在一定情况下也有成为峒长的资格,《万历琼州府志·海黎志》记载:“熟黎……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父死子继,夫亡妇主。”②“宜人王氏年老无子,嘉定九年五月,诏宜人王氏女姜氏袭封,统领三十六峒。”③“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④
在宋代之前,峒长的选任不需要中央政府的授权,后来随着中央势力向岛内的渗透,峒长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但是任命一般是形式化的,只是对黎族自行产生的峒长予以法律上的承认。峒长负责管理一峒的公共事务,就重大事项召开村长会议,研究讨论对策,并代表本峒处理与外峒事宜。⑤“遇有事,峒长、黎练以竹箭传唤,无不至者,其信而畏法如此。”“头目有事传呼,截竹缚藤,以次相传,谓之传箭,群黎见而趋赴,若奉符信,无敢后者。”⑥《琼州黎民图》则以图画加配诗的形式生动描述了黎族峒长的社会组织权威:“峒长传将箭若符,黎男黎妇子来趋,蛮荒万里无威咫,部怕官衔两笔诛。”其旁边的注文对此解释说:“黎内无文字,其峒长有事传呼,则截缚藤,谓之传箭,以次相传,群黎见之即趋赴不怠,若奉符信然。”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亩头、峒长,尤其是后者,他们是黎族习惯法的维护者,也是黎族习惯法的守法者,他们既要以身作则,自觉遵守习惯法的规定,又要对本峒违反习惯法的重大案件进行处分。他既需要协调黎民的关系,还要维持社会环境的有序、稳定。当然对于峒长的充任资格,习惯法上也有要求,其需要一定的辈分,并且具备一定的德行和能力。虽然具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峒长在参加劳动和产品分配及其他方面,并不具有特权,峒长还需要接受黎族群众的监督,如果群众都认为某峒长不能胜任,则可能将其罢黜,换选新的峒长。
此外,在黎族还有一些老人,虽然不直接掌管行政事务,但也被群众尊重、信任,是一种世俗领袖,即“奥雅”。“奥雅”是黎语,指有经验、有威信的老人。在合亩制地区,那些被公认为领域的长者方能被称为“奥雅”。奥雅作为经验的传授者,受到本亩居民的尊重和爱戴,虽然不是亩头,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比如调解家庭内部矛盾,处理轻微违法行为,收取龙仔等。
由于奥雅掌握了一定的特权,其作用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在合亩地区,奥雅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使得本亩内的生产资料分配极不平衡,出现了原始的剥削。②在清代,奥雅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一定的特权,清政府委任的总管、哨官以及国民党政府委任的团董、保甲中,多有奥雅充任。③此时,奥雅就已经不再如从前那般被广大的黎族居民信任与尊重了。④
权威对于黎族习惯法意义重大。在习惯法形成的过程中,得到大多数黎人的支持和主动遵守是最核心的要件。黎族社会习惯法形成的过程中,生产力始终处于原始社会水平,人们对自然界认识有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必然受到环境因素的限制,“迷信”、“从众”是必然存在的心理状态。而黎族权威由于其身份的特殊和相对丰富的经验,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利用其威信,可以影响广大黎民对于习惯法的态度。作为祭祀中的权威,娘母、鬼公这类人被认为具有沟通神灵与人间的能力,他们的指示即是神灵的意志,这是黎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因此在禁忌、祭祀、占卜等方面形成的习惯法具有很强的效力,几乎没有人敢于违反。当这些内容向更现实的生活渗透时,也更加容易被接受。比如男女之间的禁忌发展到田间劳动中“男不做女活,女不做男活”的规定,就被严格遵守,进而成为有稳固效力的习惯法。而作为社会组织的亩头、村长、峒长认为可以为某些行为,那么大多数组织成员会按照其指示行事,同样的,如果首领认为不可行,成员也不会违反禁令。各级组织成员围绕在首领周围,平时以户为单位遵循自然规律进行生产,在进行交往时按照既有的规矩和首领的指示进行,通过这样的过程,行为和习惯相互印证,有效的、合理的习惯被保留,最终形成习惯法,而习惯法通过肯定首领的权威,为习惯法本身的进化创造理想的条件。
此外,权威也是习惯法效力的保障。如果习惯不被遵守,习惯就不能向习惯法转变。在黎族特有的社会背景下,欲要使习惯具有强制力,必须存在具备很强公信力的社会权威,当有人违反习惯做法时对其进行指责和惩罚。黎族的神灵权威和组织首领都具有这样的职能,以确保黎族生活的有序性,使禁忌不被违反,习惯不被破坏。“遇有事,峒长、黎练以竹箭传唤,无不至者,其信而畏法如此。”“头目有事传呼,截竹缚藤,以次相传,谓之传箭,群黎见而趋赴,若奉符信,无敢后者。”①张庆长的这一描述就证明了这点。在黎族习惯法形成和发挥功能的漫长岁月里,黎族的社会权威起到了维持秩序、稳定人心的重要作用。也因为如此,自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对黎族领袖加以册封,维护其地位和权力,并允许其以朝廷的名义,对辖区进行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黎族社会组织在运转中所体现出的民主因素。虽然亩头、奥雅和峒长在一定组织范围内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这并不代表其可以肆意妄为。在做出重大决策前,峒长必须召集各村负责人进行商议。此外,峒长等世俗领袖需要自觉接受黎族群众的监督,亩头在收成连续若干年不好时就会被撤换。①虽然峒长的选任实施世袭制度,但是在必须进行换选时,也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考验,只有获得了本峒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才能够当选。峒长虽然是终身制的,也并不代表其可以无所顾忌。当本峒大多数成员认为峒长不能为其利益考虑时,可以一起推举新的头人,原来的峒长自然失去权力。②由此可知,即使是黎族原始社会中的权威,也需要保持与普通黎族群众的紧密联系,并且为他们谋取实际的利益,才可以维护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总之,黎族独特的社会环境为习惯法的形成和发挥实效创造了条件。原始的生产力水平使黎民人与人之间的共处与合作成为必然,并导致社会各个层次的组织单位都有以血缘和地缘为媒介进行合并的趋向,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工具,以及抵抗自然灾害和外族侵犯的能力,最终实现大集团、多单位的和谐相处。家庭、合亩、村、峒构成了一个紧密型的社会,这种紧密体现在组织中的个体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担负一定的劳动、生产义务,并相应地享有获取物质资料的权利,通过共同劳动,实现共同温饱。黎人的生产、生活、宗教活动都由本族权威来主导,围绕着权威,依据最初的禁忌和神灵信仰,黎族人民在生活中创造了稳定的自治性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习惯法逐渐形成,并使得原有的社会秩序更加稳定,黎人根据习惯法安排自己的行动,构建属于本民族的理想生活状态。
大约一万年前,华南大陆或马来半岛上的原始人类在四处寻觅食物的过程中,发现并登上了海南岛,从此海南岛上有了人类的繁衍生息迹象,尽管目前尚不能确定他们是否为黎人。海南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设置郡县开始的,之前的历史称作海南史前时期。②据现有史料记载,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在海南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③是海南岛上较早的居民。尽管新中国对黎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有半个多世纪,黎族也受到海南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感受了现代化的生活,但是,黎族人民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本民族的习惯和传统,信守着本民族特有的禁忌和崇拜。这些禁忌和崇拜早在原始先民时就已产生,历经上千年的演变形成了黎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秩序。海南独特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环境,限制了黎族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同时也塑造了独特的黎族社会文化,形成了以崇拜与禁忌为观念基础和力量源泉的黎族习惯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黎族社会组织和习惯法律秩序。
第一节 自然秩序状态下的黎族社会
一 宋之前的黎族社会建制
黎族在秦朝之前,即定居于海南岛,在此后一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一直是海南的主要居民。关于黎族族源在史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海南黎族来源于南洋群岛的一些古老民族。例如德国人史图博在其《海南岛民族志》一书中,认为黎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与印度尼西亚的古代马来人、印度支那大陆各族有着显著的类似,刘咸教授在《海南岛黎族起源之初探》(《西南研究》1940年第一卷第一号)中,根据黎族的文身、妇女服饰、口琴、织绣物品等表现的特点,推断黎族的文化系属于“太平洋四个文化区中的印度尼西亚区”,“与南洋群岛各民族所有者大同小异”。另一种观点认为黎族由古代百越族发展而来。中国学者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大多认为黎族是从古代“百越”族发展而来,与“百越”中的“骆越”支关系尤密。①民族学者还从考古学、语言学、地名学以及民族学等多个方面论证了黎族与古代骆越人的关系。①认为黎族源于古代“百越”族的“骆越”一支,是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共同观点。
秦朝至隋唐五代时期,汉族移民不断进入海南岛,中央政府也不断设置地方机构,管理、垦殖海南地区,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和汉民居住区域始终较为有限。
汉朝在武帝时期以强大的军队攻略海南,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设立珠崖、儋耳两郡,隶属于交趾刺史统辖。但汉朝政府在设置郡县后,驻守海南的官吏、军队以及外来移民欺侮当地黎民,掠夺地方财富,黎民不堪忍受,“故率数岁一反”。在黎民不断起义反抗之下,至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汉中央政府将儋耳郡并入珠崖郡。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又下诏放弃珠崖郡,在海南仅保留了朱卢县建制。②汉王朝在海南的统治已经仅保存在交通便利的极为有限的区域。西汉以后,中央政府多次征伐海南,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建立长久稳固的统治,位于海南本地的政府管理机构时建时废,或在广东大陆的官署遥领海岛治理。
在南梁大同(公元535~546年)年间,当时的儋耳归附的俚僚首领冼夫人③率领一千多峒黎人归附南梁政府。冼夫人还请命于朝,置崖州。冼夫人在政府的授权下,实现了又一次较为统一的黎族人的自治,以归附朝廷的方式达成了汉人政权与黎人的和平。在南北朝以前,大体上是“汉在北,黎在南”;隋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有所扩大,汉族移民的居住区域向南有所扩展,形成了“汉在外,黎在内”的分布格局。居住在海南中南部的黎族人民,在宋朝以前,大多数历史时期是处在与外界交往很少的原始状态,其社会生产、文化观念都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很少受到汉民的影响,其社会组织与秩序,大体保持了村、峒的内部自治,治理的规则主要是遵循传统习惯。
二 封闭的海岛与优越的自然环境
海南四面环海,琼州海峡将之与祖国大陆隔开,在古人看来,海南无疑就是天边。虽只一水之隔,却减低了黎族与中原的联系密度。黎族所居之海南,“海中洲居,广袤千里。(《汉书·贾捐之传》)周回二千里,径度八百里。(郦道元《水经注》)四州各占岛一隅。外环大海,中盘黎峒”。“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数千里,历代安天下之君必遣勇者戍守。”①交通技术的落后和交通方式的简陋,使得海南与中原之间的往来成为艰难之事,中央政权欲对海南实行有效管理,也是一件十分艰难之事,只有勇敢者才能胜任。也正是大海的天然阻隔,使得汉初虽在海南建立珠崖、儋耳两郡,却并没有实行有效统治。路途遥远固然是原因之一,海岛的封闭落后也是封建中央统治者不重视海南的另一原因。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至宋,封建中国的生产力已有很大提高,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大海的天然屏障,却阻挡了中原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进入,整个海岛仍然处在较低层次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尤其是黎族居住地区,大山环绕,林深叶茂,与海岛上的汉族居民相比,海南的黎族则处于更加封闭与落后状态。他们主要集中在五指山地区,大山既是保护他们的天然屏障,同时也阻隔了他们与外界的交往。黎民不仅无缘广泛接触中原文化,而且与岛内的汉族和沿海居民也少有往来,他们仍然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生活在具有浓厚血缘联系的相对封闭的村峒里。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在中央政权对黎族地区实行有效统治之前,对黎族人民影响甚微。
虽然远离中原,与大陆隔绝,同大陆甚至是海岛的汉民族交往稀少,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黎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优越的热带自然环境为黎族人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丰富的物质资源养育了世代黎族人民。海南的黎族主要分布在海岛的中部和南部,这些地区多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以暖湿为气候的主要基调,全年都阳光充足,雨量丰富,而且土壤肥沃,动植物资源丰富,更兼“中部高耸,四维低洼”的地形,使得河流纵横,编织了天然的灌溉网络,在这样优良的自然环境下,水稻在南部地区可以达到一年三熟,而玉米、番薯等主要粮食作物甚至可以终年种植,可以说黎族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刀耕火种的低层次生产劳动,维持温饱的低质量生活水平,近乎原始的落后生活方式,再加上中央政府无求海岛赋税,岛上居民少了中原地区居民缴纳赋税的生产压力。封闭的海岛生活,没有外力压迫的生产生活,使得岛上黎族人民比较满足于现状,如有反抗斗争通常也只是在黎汉之间或黎人内部,对封建中央政权难以产生大的影响和危害。正是这种封闭的海岛环境、大山阻隔和优越的自然资源,以及只需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使得黎族发展缓慢,其生产力水平长期处于极为低下的原始状态。正是在这种缓慢的发展过程中,黎族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与禁忌,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治秩序。
三 原始的生产力水平
四面环海的海岛,与大陆存有天然屏障,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海峡凭借人力难以逾越,使得海岛环境的封闭性与其自然环境的优越性同样突出,因此黎族的科学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发展缓慢。黎族的社会生产直到近现代都处在落后的原始状态,并且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关于黎族的农业生产记载道:“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①在生产领域中,种植农业是唯一独立的生产部门,狩猎、手工制作都是辅助性的补充。
黎民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极为原始简陋,其主要器具为木器、竹器和石器,铁制工具到了宋朝以后才通过汉民少量输入,从事黎族历史研究的学者认为:到了新中国成立前200年,黎族人民才较大范围地利用通过汉民输入的铁制器具。①即使如此,铁制器具也没有完全取代传统工具,经常和木犁、竹耙共同使用。黎民的生产耕作分为山栏耕作、旱地耕作,少数地区有水田耕作,山栏和旱地耕作的生产方法主要以原始的“砍山栏”、“收山栏”②为主,属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集体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土壤的肥力和天然降水来实现作物的生长,农作物的单位产出比率很低。至明代,在汉民帮助下,农具、生产方法已有很大改进,仍未改变粗放式耕作方法,时人顾岕在《海槎余录》中记述道:“黎俗四月晴霁时,必集众斫山木,大小相错,更需五、七日,聕洌则纵火,自上而下,大小烧尽成灰,不但根干无遗,土下尺余亦且熟透矣。徐徐锄转,种棉花,又曰贝花,又种旱稻,曰山禾,禾粒大而香可食。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另择地,所用前法别治。”“迁徙不常,村落聚散无定,所耕田在是即居于是,日久地瘠则去而之他,故村峒土名,数年间数迁数易,其地不可考也。”③正是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简单,农业耕作靠天收,才导致黎族村峒的经常性迁徙,当一块土地肥力丧失不再适合耕作时,黎民便整村开始迁移,寻找新的适合生存的土地。黎族最先进的旱田耕作就是采用“牛踩田”,即由人驱赶牛群在田地里来回走动,把泥土踩碎,然后再以竹、木器具插穴、投种。
水田的耕作要比山栏、旱田的耕作更有效率,但其耕作技术仍然十分落后。最先进的水田耕作就是采用牛犁,一般劳动力组合十分原始,犁地效率很低。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牛犁仍然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上:“在一块2亩左右的田上,驱赶着24头水牛拉犁,造成牛碰牛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犁田的效率。”①加之,当时普遍使用的犁是竹制或是木制的,②比铁制犁的效率要低50%以上,且耕牛的数量也较少,还没有田间除草、施肥等精耕技术,总体生产效率还处在极低的水平。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黎族的农业生产已经历了诸多改进,普遍采用了铁制器具,但仍然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稻谷的产量是很低的,水田每亩产稻谷百余斤,旱田几十斤”。稻谷纵然有每年两熟或三熟,在正常年景下,“每亩年产量仅达120斤左右”。③
除了粮食作物外,黎族也利用优越的自然资源进行副业生产,但是同样受限于生产力的束缚,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其种类主要包括:纺织业,狩猎和捕鱼,饲养禽畜,种植热带、亚热带水果等。
在自然环境优良但是生产水平有限的背景下,黎族族群的生存一方面依赖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主要依靠群体的协同合作,因此,群体主义是黎族社会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族群得以存续和繁衍的保障。
黎族的自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黎族习惯法的形态与内容:海岛封闭的状态为习惯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成环境,使得黎族习惯法保持了高度的原生状态,对黎族居民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脱离海岛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去研究黎族习惯法将必然缺乏实证意义;而黎族居民生产力水平的局限性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也决定了其习惯法所确立的秩序目的和价值追求。
第二节 黎族的神灵崇拜与禁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点,神灵的本质是原始人将支配其生活的自然力量进行人格化,是这种伟大力量在人类意识中的虚幻反映。海南黎族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黎族居民对能够左右其生死温饱的自然力量无法进行科学解释,自然将其视为神灵,为了族群的生存繁衍和粮食丰收,各地黎民普遍有着不同的神灵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为避免灾祸,黎民敬畏鬼神,恪守祖先传承下来的各种禁忌。神灵崇拜和传统禁忌,反映了黎民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是法律秩序的观念基础,也是习惯有效性的文化基础,对神灵的崇拜与禁忌是黎民自觉遵守习惯的力量源泉。
一 频发的自然灾害
黎族居住在亚热带、热带地区,此地雨量丰富,气候湿热,大海环绕。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一方面造成剧烈的自然灾害多发,另一方面使位居深山的黎族人民生活条件比较恶劣。“周岁多东风,秋夏间飓风,或一岁累发,或累岁一发……发在秋夏,有云物之先驱,非青华为起。未几率然凌寻,飘忽怒号,极万籁之变,屋瓦皆飞,坤轴欲转,人物震慑,沆澥湃奔,幨帱倏吼,海鸟翔,天脚晕若半虹,则飓风。”①《方舆志》:“周岁皆东风,秋夏飓风。”台风是海南破坏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给人们带来恐惧的常见灾难。“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汉书·贾捐之传》)病无药饵,但烹犬牛祀神。(乐史《太平寰宇记》)”(②)关于海南的气候与自然条件,《康熙昌化县志》卷一《舆图志》“风土”中有如下描述:“一日之内,一身之间,冷热互见,是以人体疲倦,脚气之患不时有也。有蝇则无蚊,有蜈蚣则无蝎螫,此定数也。而海南诸种皆备,蝇无四时皆有。蚊有二种,有小而黑者,昼不避人,咿唔左右,闻为可厌;夜间流毒者,诸方所有也。……东坡云:海南风俗,食无肉,出无兴,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惟夏无蝇蚊则可喜也。”“地居炎方,多热少寒,时忽瘴云埋树,若非仁人君子,岂得而寿耶。”③在原始黎族社会里,影响其生产和生活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因素:一是湿热气候及毒草虫蛇,使黎族人民生命健康时刻受到威胁,面对疾病,无医可诊无药可治,他们只能从自身找原因,求助于神灵保佑;二是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兽灾是最为常见的自然灾害,黎民辛勤耕种的粮食作物,经常在一夜之间就被山猪、猴子等野兽啃食破坏。水、旱灾害,台风也是每年多发的灾害,因为海南总体降雨量大(大多数地区年均降雨量在1800毫米至2000毫米),但降雨分布不均匀:降雨多集中在八九月间,容易发生水灾;二、三、四月则是旱季,多发生旱灾。对于病、虫灾,黎民多束手无策,只能以其原始的超自然的方式来解释。黎族没有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然没有改变靠天收的局面。例如,在1953年黎族聚居的乐东县遭受旱灾,其中包谷60%未有收获;1954年,自治区7县从6月至8月初又普遍受旱,其中乐东、东方受灾更为严重,大面积稻田无法插秧。①各种自然灾害,也是黎民生产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人的生老病死等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黎民无法以其自身的知识进行解释,也无法以自身的力量来避免。因而,黎民求助于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用神灵意志来解释这一切,并通过各种神灵崇拜和禁忌规则,试图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避免自然力的无情伤害。
二 神灵崇拜
局限于认识水平和知识的贫乏,以及原始社会末期极其低下的生产力,黎族人民较早地形成了原始的宗教神灵崇拜,各地自然环境不同,所崇拜的神灵也有很大的差异,既包括自然神灵崇拜,也包括动植物图腾崇拜,还有祖先崇拜。
就自然神灵崇拜而言,有的黎民崇拜天,有的崇拜地,有的崇拜水,有的崇拜山,②还有崇拜火、日、月、风、树木的。③自然界的天、地、日、月、山、水、火、石、风、树、鬼魂等现象,在黎民看来都是能左右自己且不可冒犯的鬼魂。①“天鬼”。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天体有云雾、风雨、雷电等现象发生,它伴随着人们的生活。然而海南黎族人民认为,这些现象是一种不灭的神灵,它能使庄稼旱死涝死,受病虫侵害,也可使庄稼丰收,还能使人头痛发烧生病,直至死亡,因而人们十分惧怕这些“天鬼”。②“地鬼”。黎族先人认为农作物丰收是“地鬼”的恩赐,祭祀地鬼以表示期望和感谢。③“水鬼”。它在诸神中位于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主宰田地不受旱涝灾害。④“石”。黎族认为石头神能促进生育,能驱赶破坏庄稼的鸟兽,“有石之细润者,黎人谓之石精,大如枣栗,五色皆有之,黎中珍而藏之以宝,谓可镇家,猎者藏储身边,获禽兽独多”。①⑤“山鬼”。合亩地区的黎族人认为,山中的一切飞禽走兽都受“山鬼”管辖,人们上山打猎必须经过山鬼的同意才行。⑥“雷公”,在黎族人的传统观念里,是代天执法和行刑之神,它能窥见一切人间事,谁做好事谁做坏事,谁有涵养谁没有涵养,它都一目了然。凡是没有道德和做坏事的人都要受到雷公的惩罚。此外,诸如火、日月、风、树、牛、兽、鼓、锣等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灵气,能给人们带来吉与凶,善良的人因此而有神福运,作恶的人因此而产生凶魂,遭到厄运。
就图腾崇拜而言,黎族有动物图腾崇拜,也有植物图腾崇拜。在动物方面,以蛇、鱼、鸟、狗、蛙、牛、猫等为崇拜对象,在植物方面,则以葫芦瓜、水稻、榕树、木棉、竹为主。既有崇拜龙(鱼)图腾的,有崇拜鸟图腾的,有崇拜牛图腾、狗图腾的等,②还有崇拜葫芦瓜、木棉、竹子等植物的。黎族每个氏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图腾,认为自己的氏族起源于它,这些图腾有动物、植物或其他生物。由于相信自己氏族起源于它,此物也就因此成为该氏族的祖先或保护神,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图腾加以崇仰。以动植物为主的黎族图腾崇拜,“其特点是认为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植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③对于自己氏族的图腾,黎族人民一方面将它视为保护神,以一定的形式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如姓、氏族集团的称号等,另一方面,给动物图腾以一种特殊的礼遇,如农历三月初八为牛节,在这一天不能杀牛,不能用牛耕地,“保亭毛道黎族视猫为自己的祖先,禁止杀猫吃肉”。①
就祖先崇拜而言,有崇拜祖先鬼的。黎族的祖先崇拜是建立在鬼魂观念基础上的。黎族将祖先称为祖先鬼,他们认为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氏族普系,都有自己的祖先鬼。有的氏族还自认为本部族由某种神灵繁衍而来,把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结合为一体。祖先鬼是恶鬼、凶鬼,②它支配着人们的生存与幸福。对祖先鬼崇拜的方式是“敬而远之”,即平时禁止说出祖先的名字,否则会招回祖先鬼,危害家庭生命健康。
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黎民社会虽经过了两千余年的演变和与周围民族的融合,但他们仍然保持着普遍的神灵崇拜。这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调查资料中发现:“在调查的22个点中目前仍以祖先崇拜为主的有8个点,以信奉自然的天鬼(雷公鬼)为主的有4个点,英雄崇拜(峒主公)的有3个点,其余便是因接受道教以后改奉‘神’的。”③祖先崇拜是黎民中较普遍的一种崇拜,而每一地区的黎民无一例外地都有神灵崇拜,神灵在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无处不在。这说明黎民在应对自然现象上,神灵崇拜是比较普遍的文化特征。
自然神、动植物图腾、祖先鬼,都是黎族先民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对世界万物、社会常态的一种朴素的认识与思考,其核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灵魂意识,它根源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黎族先民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汉时的郡县建制,尚处在母系社会的繁荣时期,郡县建制后海南岛的母系氏族开始向父系社会过渡,人们建立了相对固定的生活村落。为了繁衍后代,黎族先民开山劈岭,刀耕火种,狩猎捕捞采集,但在当时的生产力之下,生产工具粗糙、简单,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面对不能左右的族人的生、老、病、残、死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人们对这些大自然的现象产生了恐怖、敬畏,祈祷免受其害,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产生了对各路神灵的禁忌。这种原始宗教崇拜,在人类社会,几乎每个民族都曾经历过,黎族当然也不例外。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是,由于文化知识的贫乏,生活空间的封闭,黎族人民的这种宗教禁忌观念,直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仍然存在,对神灵的崇拜与禁忌,仍然普遍盛行。
出于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黎人也注重祭祀。负责主持祭祀的人员都声称自己具有和鬼神直接进行沟通的能力,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使鬼神附于其身上,并借自己的口传达鬼神的意志,黎人对此也深信不疑。通常情况下,主持对自然鬼神祭祀的被称为“娘母”,而负责祭祀祖先鬼的被称为“鬼公”。“娘母”、“鬼公”是专门的“神职人员”,但神事不是其唯一的工作。总之,“海南黎族人民过去仅有一些虚幻的、超自然的观念,以及某些巫术和神话传说,没有系统的神话理论,还未设立神堂和统一固定的崇拜偶像,也没有产生专职神职人员阶层,黎族宗教尚停留在原始宗教阶段”。①
三 禁忌与占卜
禁忌,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犯忌讳的话或行动”,在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中称为“塔布”,意为“忌讳、戒律”。禁忌是一种社会心理层面的信仰习俗,在民间禁忌无处不在。在海南黎族社会中,禁忌广泛存在于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控制着人们的精神意识,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为了不触怒神灵,保佑家口平安、生产顺利,黎民在生活、生产等各种活动中有诸多禁忌。黎民的禁忌主要分为八类,以下仅举保亭加茂地区的禁忌来说明:①生活禁忌(“睡在床上,头忌向门口”等十八项);②生产禁忌(“过旧历年节未过完初四,忌搞生产,否则天旱”等十项);③生育禁忌(“妇女生产未满月,外人忌进宅,否则会致婴儿多病”等四项);④婚姻禁忌(“新娘入宅时若未经火堆和打破鸡蛋,不得入宅,否则鬼会随新娘入宅作祟,致人生病”等四项);⑤丧葬禁忌(“丧宅在未埋葬死人之前,忌入别人宅内,否则使别人不祥”等三项);⑥行猎禁忌(“未过旧历年初四,妇女忌与男子同桌一起吃饭,否则行猎难获猎物”等两项);此外还有节日禁忌、宗教禁忌。②黎人生活在神灵崇拜与禁忌的网络中,对于生活、生产问题,或是面对自然灾害时,他们多希望得到神灵的指导与启示,通过自己的虔诚得到神灵眷顾,并能够在现实中完成与神灵的对接,而巫术和占卜就是黎人完成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他们既是黎人与神灵沟通的主要方式,也是最基本的习惯规则。
黎人多信巫术,尤以采取合亩制的地区为甚。①在对自然界认识受限的情况下,黎人常常通过进行充满神秘感的各种行为以实现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治疗疾病。黎人认为疾病主要是由鬼神附体作祟导致,所以在有人患病时,通常采用巫术,将导致疾病的鬼神找出,并使其离开患者,以实现治病的目的。
占卜是黎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自然界不确定性的畏惧,黎人在进行捕猎、打渔、婚嫁、丧葬等活动之前都要进行占卜,以确定吉凶,只有占得吉象,方进行活动。②
对神灵的祭祀、对禁忌的遵守,以及占卜活动,一般由黎人中的尊长率领族众来共同进行,这也是黎人最重要的团体活动。频繁的祭祀、诸多的禁忌、重要活动的占卜,凝聚了黎人的团体意识,这些活动也传承着黎人的文化,支持着传统习惯规则的遵守。
四 习惯与习惯法
不考虑其内容的科学性,神灵崇拜、占卜和禁忌等活动对于黎族习惯法的形成意义重大,在深刻理解这些活动的寓意后,结合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我们能够大致勾勒出一幅习惯法形成的可能性图景:受限于原始状态的生产力水平,黎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预测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面对自然界各种神奇的现象和巨大的能量,黎人只能将其归结为神灵的意志,由此他们对神灵、图腾和祖先产生了无限崇拜,出于这种崇拜和忌惮,就必然在生活中小心谨慎,会考虑每个行为与神灵可能产生的关系,为了实现趋利避害的目的,会刻意地对一些言行加以限制,如果为不该为的行为,或说不当说的言语,会导致神灵的不悦,进而招来灾祸,这对于黎族人来说是最终极的惩罚。而这种限制经过世代传习,形成稳定的规矩也就是禁忌。这种禁忌已经具有法律的雏形。
但是禁忌距离实际的习惯法尚有距离:首先,禁忌调整的事实上是人和神的关系,它很难直接应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其次,禁忌是一种消极性的规范,它只能指引人们不去做什么,但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情况下需要有规范来指引人们怎样去做,这个问题靠禁忌是无法解决的;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禁忌的禁止性规范是笼统的,而生活中的各种情形是具体的,主观意图上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程度上的严重或者轻微,以笼统的禁忌去规范具体的行为,很有可能会造成显著的不公平,所以为了更进一步、更细化地指导生活和行为,习惯逐渐产生。
习惯是对禁忌的一种主动选择和生活化。在面对共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时,如何行为能够产生最佳的效果是黎人必须思考的问题。远古留下的禁忌经历了时间的考量后,有些被保留,有些被弱化,有些被淘汰。根据被保留下来的禁忌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黎人开始总结生活中的各类与禁忌相冲突和不相冲突的惯常做法。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由模糊的观念变得清晰、具体,并进而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成为稳定的习惯。
从习惯到习惯法则是另一个漫长过程。习惯法即“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习惯最初产生于小范围的群体,随着该习惯的不断推广,适用的区域到达了一定的范围,同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趋于成为整个民族共同承认并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被遵守与认同后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黎族人彼此之间在进行交往时根据这种习惯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进而得到黎族社会的公认,如果违背了这种关系,将会对行为人产生不可避免的消极后果。当人们的行为有意无意地被习惯约束,违反习惯时受到内心自责和社会公众谴责并承担不利后果时,习惯法就已经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得到了确立。
所谓黎族习惯法,就是黎族同胞在其长期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为大家所公认和遵循的风俗习惯、惯例和通行做法等行为规范。
第三节 黎族的紧密型社会组织与权威
群(团)体主义是黎民生活的最基本特征,群体主义也是黎族习惯法贯彻的指导思想和倡导的价值取向,“以维护群体的利益为标准”在黎族习惯法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它首先体现在黎族紧密型的社会组织上,具有血缘关系的户组成的合亩,由合亩构成的村,由村联成的峒,是黎族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
一 家庭与“合亩”
为了克服各种不利的自然因素,确保族群的生活安全和生产有序,黎人选择了一种紧密联系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地域分布上尽可能稠密,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共同参加劳动,平均进行分配,通过满足群体的方式实现个体成员的利益最大化,这类生活方式的典型就是合亩制度。
合亩的基础是户。基于婚姻而形成的家庭,是黎民的社会消费单位——户。户掌握一定的生产工具和资料,而黎民在家庭的基础上,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合亩。①合亩是基本的生产组织、生活组织,是几个家庭合伙占有土地进行合作耕种的形式。家庭是合亩组织的细胞。合亩的组织基础是血缘关系。合亩组织大小不等,既有2户到3户的兄弟亩、父子亩,也有多达30多户的大亩,不过这类大亩非常少见,通常情况是2~6户的亩居多。①在合亩地区内,一般是共同生产,平均分配。亩头是合亩组织内生产、劳动与产品分配等事务的指挥者和组织者,在黎语中的含义是“带头犁田的老人”。②亩头对本亩的成员实施家长式的领导,由本亩内的男性长辈担任,最初亩头是被推选产生,之后由本亩内的男性长辈依次担任。③
黎族合亩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组织、促进生产,亩内的所有成员只要到达一定年龄都需要参加劳动,除了个体可以单独进行的渔、猎等劳动活动外,所有成员的主要任务是参与集体劳动。在集体劳动中,亩内成员同出同归,共同劳动,不将劳动任务分配到个人,也没有更为详细的劳动计划,而是亩众一起动手完成某一项任务。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平均主义劳动方式。④
在合亩组织内,劳动工具一般属于私有,牛、土地等生产资料虽然归由各家看管,但不属于私有,而是合亩成员的共有财产,由合亩统一调拨使用,且没有报酬。
对于劳动产品的分配,合亩制采取的方式是按户平均分配,对于人数多寡,男女、年龄比例等因素都不加以考虑,并且在分配之前还要留出一定的公共粮食以备用,在出现饥荒时,动用这些储备粮帮各户渡过难关,这部分的具体内容在第二章还有详细的介绍。
二 村、峒
村和峒都是地域性社会组织,在未被封建王朝统治之前,它是维持黎族社会内部正常秩序和推动黎族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组织。黎族古代社会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村落或行政组织:村、弓、峒,其中弓、峒是具有鲜明黎族特色的社会政治组织,是黎族一种古老的氏族部落或村落组织。①“山凡数十重,每过一重,稍有平坦之处,黎人即编茅居之,或数十家、数百家相聚为一村,亦名一弓。有众至千余人者为大村,其小者仅止数家。”②从组织上说,即数个合亩组成一村,每个自然村有一个村头,在一些地区被称为“亚雄”,③其职能是处理本村的内部事务。若干个村组成一个峒,作为黎族最大的社会团体单位。“黎地多以峒名,峒内散处各村,并附一峒,明所属也。惟崖州曰村,陵水曰弓,其散处各村并附于一村一弓,亦如峒制。”④民国时《海南岛志》也记载:“黎人择地而居,自谋生活……峒之大者十村八村,小者三村五村。”⑤峒的原意即“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的地域”。⑥峒有大小之分,且规模并无定数,小峒可能只包含两三个村落,而大峒则可能由十几个村组成。总之,黎族峒组织是由具有血缘纽带的黎人共同构成的、峒内有完整行为准则的共同的居住区域。黎族峒组织,文献早有记载,尤以宋元后为多。宋时,黎族的每一宗姓为一峒,海南全岛族峒颇多,⑦且规模均小,峒与峒之间的联系较少,各自独立。⑧到明代,黎族地区仍以峒为主要的社会组织。据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记载,各州县黎峒数量为琼山126澄迈137……明代海南岛12个州县中,共有黎峒1260个。⑨至清代,黎族地区开始设立土官制,主要是在黎族村峒设峒长、总管、哨官、黎甲、黎长、黎首等职。由于大批村峒划入政府直接管辖的领域,峒的数量大大减少,只有42峒,822村了。①峒组织的存在,使得黎民的社会组织从原本单纯的血缘组织发展为血缘和地缘的结合,并将血缘中的亲密关系带入了地缘组织中,形成了千百年来一直左右黎族人民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基础——“同峒皆兄弟”的意识。②峒内成员在彼此有困难时要互相帮助,并且本峒内成员之间享有财产购买的优先权。
各峒领域之间多以山、河为界,而且要通过立碑、种树的方式予以明确。峒界的划定始于何时,目前尚未确定,但是近代的划界常常需要进行一定的仪式,由一峒的峒长杀牛一只,制成肉串,送给邻峒各个峒长,接到肉串的峒长把肉串悬挂于门前,并告知本峒成员,不要侵犯对方峒界。③在黎族观念中,峒界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一峒成员要越过峒界到另一峒进行种植、砍伐、捕猎、打渔必须要提前向该峒声明,并进献一定的礼物。对方的峒长对于此类事件也不可独断专行,而是必须经过全体峒成员的同意,方能授权,而且授权是有期限的,多为一年,一年后必须重新经过上述程序以确定是否继续。如果硬闯入他人峒界,则极有可能造成冲突甚至械斗。④
三 黎族社会的权威
在黎族社会,权威是不可或缺的。权威就是使人信服的力量或者人、物。他们对一个组织、社会的稳定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黎族社会同样如此,而且黎族权威对于黎族习惯法的形成和适用也有重大意义。
黎族社会的权威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祭祀活动中的神灵权威。另一类则是各个级别的社会组织首领,如亩头、村头、峒长等等。
新中国成立前夕,黎族的民间信仰意识大部分仍停留在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祭祀活动中的神灵权威也一直享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得到普遍的尊重与认可,发挥着传达神意和反馈民声的双重功效,实际上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人化。在黎族社会,母娘、娘公、道公、拜公、老人等都是受人信奉的神灵权威。他们的作用虽然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包括:主持祭祀自然鬼神和祖先鬼神的各种仪式,利用巫术治疗急症病人,向神灵祷告、祈福,并就具体事宜向黎民下达具体指示。而这些权威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带有神秘色彩,一般都是在大病后,突然神灵附体,获得了某种超能力,便取得了代言鬼神的资格。在一些仪式上,他们经常会突然失去知觉,躯体成为鬼神暂寄的居所,直接以神鬼的身份发号施令,然后再回复原来的个人意识。黎人对此极度尊崇,并深信不疑。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有伪科学的成分,但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神灵权威的身份和法术都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所有的神灵权威在进行各种仪式时都告诫黎民为善,尚未发现有鼓动作恶的情况,而且也有关于这些权威通过法术成功治愈疾病的记录,①客观上也带来了一定帮助。此外,神灵权威的最大意义仍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持了黎族内部稳定。神灵权威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仍是围绕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鬼神代言人。作为同一个祖先的后裔,和平共处才是祖先的心愿。于是围绕着神灵,存在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黎族群体产生了强大凝聚力,内部和谐并一致对外,这种矛盾、斗争、合作共存的社会状态,伴随着黎族的进化,也见证了习惯法的产生与成熟。
在黎族村峒中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一个大塘,必有一条大鱼;一片山林必有一只‘谷姑’;一片村庄,必有一个‘土地公’;一个地方,必有一个‘头人’”。②这正好映衬了黎人对社会团体内权威的尊重和服从。史书上有记载,“(黎人)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③在现实黎族社会,亩头是最基础的领袖和权威,是一亩之长,在本亩内具有绝对权威,亩众必须服从。其权力行使的范围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兼具行政管理与司法调解的性质。他要全面领导进行农业生产,负责生产之前的各种祈祷活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亲自从事劳动,起带头和模范作用,以激励全亩的生产热情。亩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都要由亩头过问或者直接办理,比如亩众买卖田产、房屋、耕牛等只有在全亩同意的情况下由亩头代理买卖,而盖房子、娶亲这类事情也都要征求亩头的意见。当亩众内部出现纠纷时,亩头要出面进行协调,对轻微违反习惯法的人,要予以训诫。亩头并非当然终身制,而是始终处于亩众的监督之下,一旦德行不端,或者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则很有可能被亩众问责,遭到罢免和撤换。
峒长是地域性的团体领袖,峒长的产生除首任外一般也并非选举,而是按照父死子替、兄终弟及的方式罔替。清人所著《黎岐纪闻》中也记载:峒首,“大抵父死子代,世世相传,间有无子而妻及弟代之者”。①妇女在一定情况下也有成为峒长的资格,《万历琼州府志·海黎志》记载:“熟黎……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父死子继,夫亡妇主。”②“宜人王氏年老无子,嘉定九年五月,诏宜人王氏女姜氏袭封,统领三十六峒。”③“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④
在宋代之前,峒长的选任不需要中央政府的授权,后来随着中央势力向岛内的渗透,峒长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但是任命一般是形式化的,只是对黎族自行产生的峒长予以法律上的承认。峒长负责管理一峒的公共事务,就重大事项召开村长会议,研究讨论对策,并代表本峒处理与外峒事宜。⑤“遇有事,峒长、黎练以竹箭传唤,无不至者,其信而畏法如此。”“头目有事传呼,截竹缚藤,以次相传,谓之传箭,群黎见而趋赴,若奉符信,无敢后者。”⑥《琼州黎民图》则以图画加配诗的形式生动描述了黎族峒长的社会组织权威:“峒长传将箭若符,黎男黎妇子来趋,蛮荒万里无威咫,部怕官衔两笔诛。”其旁边的注文对此解释说:“黎内无文字,其峒长有事传呼,则截缚藤,谓之传箭,以次相传,群黎见之即趋赴不怠,若奉符信然。”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亩头、峒长,尤其是后者,他们是黎族习惯法的维护者,也是黎族习惯法的守法者,他们既要以身作则,自觉遵守习惯法的规定,又要对本峒违反习惯法的重大案件进行处分。他既需要协调黎民的关系,还要维持社会环境的有序、稳定。当然对于峒长的充任资格,习惯法上也有要求,其需要一定的辈分,并且具备一定的德行和能力。虽然具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峒长在参加劳动和产品分配及其他方面,并不具有特权,峒长还需要接受黎族群众的监督,如果群众都认为某峒长不能胜任,则可能将其罢黜,换选新的峒长。
此外,在黎族还有一些老人,虽然不直接掌管行政事务,但也被群众尊重、信任,是一种世俗领袖,即“奥雅”。“奥雅”是黎语,指有经验、有威信的老人。在合亩制地区,那些被公认为领域的长者方能被称为“奥雅”。奥雅作为经验的传授者,受到本亩居民的尊重和爱戴,虽然不是亩头,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比如调解家庭内部矛盾,处理轻微违法行为,收取龙仔等。
由于奥雅掌握了一定的特权,其作用和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在合亩地区,奥雅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使得本亩内的生产资料分配极不平衡,出现了原始的剥削。②在清代,奥雅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一定的特权,清政府委任的总管、哨官以及国民党政府委任的团董、保甲中,多有奥雅充任。③此时,奥雅就已经不再如从前那般被广大的黎族居民信任与尊重了。④
权威对于黎族习惯法意义重大。在习惯法形成的过程中,得到大多数黎人的支持和主动遵守是最核心的要件。黎族社会习惯法形成的过程中,生产力始终处于原始社会水平,人们对自然界认识有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必然受到环境因素的限制,“迷信”、“从众”是必然存在的心理状态。而黎族权威由于其身份的特殊和相对丰富的经验,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利用其威信,可以影响广大黎民对于习惯法的态度。作为祭祀中的权威,娘母、鬼公这类人被认为具有沟通神灵与人间的能力,他们的指示即是神灵的意志,这是黎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因此在禁忌、祭祀、占卜等方面形成的习惯法具有很强的效力,几乎没有人敢于违反。当这些内容向更现实的生活渗透时,也更加容易被接受。比如男女之间的禁忌发展到田间劳动中“男不做女活,女不做男活”的规定,就被严格遵守,进而成为有稳固效力的习惯法。而作为社会组织的亩头、村长、峒长认为可以为某些行为,那么大多数组织成员会按照其指示行事,同样的,如果首领认为不可行,成员也不会违反禁令。各级组织成员围绕在首领周围,平时以户为单位遵循自然规律进行生产,在进行交往时按照既有的规矩和首领的指示进行,通过这样的过程,行为和习惯相互印证,有效的、合理的习惯被保留,最终形成习惯法,而习惯法通过肯定首领的权威,为习惯法本身的进化创造理想的条件。
此外,权威也是习惯法效力的保障。如果习惯不被遵守,习惯就不能向习惯法转变。在黎族特有的社会背景下,欲要使习惯具有强制力,必须存在具备很强公信力的社会权威,当有人违反习惯做法时对其进行指责和惩罚。黎族的神灵权威和组织首领都具有这样的职能,以确保黎族生活的有序性,使禁忌不被违反,习惯不被破坏。“遇有事,峒长、黎练以竹箭传唤,无不至者,其信而畏法如此。”“头目有事传呼,截竹缚藤,以次相传,谓之传箭,群黎见而趋赴,若奉符信,无敢后者。”①张庆长的这一描述就证明了这点。在黎族习惯法形成和发挥功能的漫长岁月里,黎族的社会权威起到了维持秩序、稳定人心的重要作用。也因为如此,自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对黎族领袖加以册封,维护其地位和权力,并允许其以朝廷的名义,对辖区进行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黎族社会组织在运转中所体现出的民主因素。虽然亩头、奥雅和峒长在一定组织范围内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这并不代表其可以肆意妄为。在做出重大决策前,峒长必须召集各村负责人进行商议。此外,峒长等世俗领袖需要自觉接受黎族群众的监督,亩头在收成连续若干年不好时就会被撤换。①虽然峒长的选任实施世袭制度,但是在必须进行换选时,也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考验,只有获得了本峒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才能够当选。峒长虽然是终身制的,也并不代表其可以无所顾忌。当本峒大多数成员认为峒长不能为其利益考虑时,可以一起推举新的头人,原来的峒长自然失去权力。②由此可知,即使是黎族原始社会中的权威,也需要保持与普通黎族群众的紧密联系,并且为他们谋取实际的利益,才可以维护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总之,黎族独特的社会环境为习惯法的形成和发挥实效创造了条件。原始的生产力水平使黎民人与人之间的共处与合作成为必然,并导致社会各个层次的组织单位都有以血缘和地缘为媒介进行合并的趋向,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工具,以及抵抗自然灾害和外族侵犯的能力,最终实现大集团、多单位的和谐相处。家庭、合亩、村、峒构成了一个紧密型的社会,这种紧密体现在组织中的个体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担负一定的劳动、生产义务,并相应地享有获取物质资料的权利,通过共同劳动,实现共同温饱。黎人的生产、生活、宗教活动都由本族权威来主导,围绕着权威,依据最初的禁忌和神灵信仰,黎族人民在生活中创造了稳定的自治性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习惯法逐渐形成,并使得原有的社会秩序更加稳定,黎人根据习惯法安排自己的行动,构建属于本民族的理想生活状态。
附注
① 《海南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2011年5月11日《海南日报》。
② 赵全鹏:《海南社会结构问题研究》,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第1页。
③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2页。
①《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有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其中南海、桂林、象三郡,即为现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所谓“九郡”,据《通志》载,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兵征讨南越王相吕嘉,“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珠崖、儋耳二郡在海南岛,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越人故地开置九郡,海南岛自然是越地的一部分。《汉书·贾捐之传》曾记载海南岛的居民为“骆越之人”。《汉书·地理志》(卷二八下)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汉)武帝元封元年略以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六畜,山多塵。兵则矛、盾、刀、木工弩、竹矢,或骨为镞。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该“大洲”,即今天的海南岛,“民”,即土著的骆越人。
①参见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2~6页。在考古方面,海南岛出土的石器与我国两广沿海地区发现的器物同属一个文化类型;在语言方面,黎族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与壮语、布依语、傣语、佩语联系紧密;在地名以及民族学上,黎族与百越诸族也有共同之处,如称河流为南,称村庄为抱、包、蕃等;在生活习惯上有断发文身、契臂为盟、善铸铜器等特征。
②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一一六。
③冼夫人,又称冼太夫人,岭南圣母,原名冼英(公元512~590年),南朝广东高凉人,俚族,后嫁于当时的高凉太守冯宝。冼夫人善于结识英雄豪杰,公元550年,在参与平定侯景叛乱中结识后来的陈朝先主陈霸先,并认定他是平定乱世之人。551年,冼夫人协助陈霸先擒杀李迁仕。梁朝论平叛功,册封冼夫人为“保护侯夫人”。公元557年,陈霸先称帝,陈朝立。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冯宝卒,岭南大乱,冼夫人平定乱局,被册封为石龙郡太夫人。隋朝建立,岭南数郡共举冼太夫人为主,尊为“圣母”。后冼夫人率领岭南民众归附,隋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加封谯国夫人,去世后追谥“诚敬夫人”。
① (清)李有益纂修《光绪昌化县志》卷十《人物志》“艺文”,海南出版社,2004,第314页。
①转引自陈立浩、陈兰、陈小蓓著《从原始时代走向现代文明: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变迁历程》,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第70页。
① 陈立浩、陈兰、陈小蓓著《从原始时代走向现代文明——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变迁历程》,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第19页、第26页。
②参见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288~289页。砍山栏是与落后生产力相伴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较为原始,种植地离住所较远,在将山砍为耕地后,用木棒等工具在地表戳出浅穴,即开始耕种,不翻土,不施肥,纯粹靠自然积肥,种一至三年便丢弃十至二十年,再进行耕种;另一种方式在技术上有所进步,砍山种植一年后,便进行翻土,将收获后的稻秆压在土下以为天然肥料,并挖坑种植番薯,来年春季借挖出番薯之机松土,再种上稻子,以此往复循环直到收成锐减后抛荒,待10~20年后,重新砍树种植。
③ 《道光琼州府志》卷十二《海黎志》,海南出版社,2004。
① 广东省编辑组:《毛枝乡调查》,《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84页。
②根据考古发现,早期黎族的主要生产工具包括:石斧、石铲、石锄、木棒、木锄等,石质工具虽然坚硬,但是系打磨而成,非常粗糙,劳动效率低下,而木质工具虽然便于使用,但是容易损害,使用寿命也较短。
③ 陈立浩、陈兰、陈小蓓著《从原始时代走向现代文明——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变迁历程》,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第25页、第6页。
① (清)方岱修,璩之璨校正《康熙昌化县志》卷一《舆图志》“风土”。
② (清)和珅等纂修《乾隆续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
③ (清)李有益纂修《光绪昌化县志》卷十《艺文志》。
① 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写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21页。
②以拜山神为例,由于狩猎是黎族居民获取食物来源的最初方式之一,而狩猎又必须潜入深山进行,所以一些地区的黎族居民对山神非常尊崇,认为是他们生存下去的保障,在出猎前,大家要进行祷告,祈求山神保佑能够捕获到猎物。
③自然崇拜的共同规律是被崇拜的对象都与农业生产和族群生活密切相关,天气日月循环往复,从不间断,这是黎族人所无法解释的伟大现象,只能认为是神明的安排,而至于水、火更是与生活密切相关。
① (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②在图腾崇拜中,还有崇拜猴子和蛇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猴子和蛇是其农产品和家畜的主要侵袭者,故对这两种动物的崇拜一方面说明黎族人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低下,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其较为原始和传统的万物和谐的共处观念。
③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64页。
①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65页。
② 据高泽强、潘先锷在《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中记载,在润方言黎族,其祖先已经变成善鬼,它不仅不招人生病,还有保护家人平安、牲畜繁殖、庄稼丰收的超自然力量。参见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高泽强、潘先锷著《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第201页。
③ 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写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97页。
①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60页。
②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75~176页。
① 巫术是通过幻想,依靠特定主观行动来支配或影响客观事物的现象,是已知人类意识活动的最早形态之一。
②黎族合亩地区狩猎者在出发前进行占卜,只有出现吉光方意味着山神允许他们出猎。参见陈立浩、陈兰、陈小蓓著《从原始时代走向现代文明: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变迁历程》,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第74页。
①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修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第3页。关于习惯法的界定还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习惯法反映国家认可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习惯并不具有法的性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第87页。有关两种界定意见的区别也可以参见张文显《我们需要怎样的习惯法研究?——评高其才著<瑶族习惯法>》,《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11年第3期(总第99期),第156页。
①最初的合亩在黎语中被称为“纹茂”,即血缘近亲组成的家族之意,可见合亩最初在于强调血缘的整合作用,但实际上“合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共同生产,因此合亩在黎语中的称呼最后变为“翁堂沃公”,就是大家一起来做工的意思。
①按照组成成分的不同,合亩又可以分为亲属组织和混合组织。亲属组织即组成合亩的户皆为血缘关系,父子、兄弟、叔侄、岳父母与女婿、舅父与外甥等等,这种组织形式约占合亩总数的七成。混合组织则是在血缘组织的基础上加入了龙仔或工仔。这一比例也再次验证了合亩组织以血缘为基础的论断。
② 陈立浩、陈兰、陈小蓓著《从原始时代走向现代文明: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变迁历程》,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第68页。
③实际情况中,有些合亩也采用亩众推选的方式,而且担任亩头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乐东县番阳县就要求亩头有一定的辈分,已婚,有生产经验,并懂得一定的宗教仪式等。参见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145页。
④合亩的劳动生产有着严格的性别分工,男子负责犁田、赶牛踩田、挑担、砍山栏等重体力劳动,妇女负责拔秧、插秧、收割等,男女间的工作范围已经成为习惯,男女互不相帮。
① 弓、峒意思一致,只是使用的区域不同而已,称为弓的多出现在现今的保亭黎族自治县与陵水黎族自治县的交界处,其他黎地均称为峒。
②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二十“海黎志”,成文出版社,1961,第450页。
③ 陈立浩、陈兰、陈小蓓著《从原始时代走向现代文明: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变迁历程》,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第55页。
④ (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⑤ (民国)陈铭枢总纂《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3,第138页。
⑥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01页。
⑦ 据当时文献统计,宋代黎峒最多时计有907个之多。
⑧宋代诸黎峒之间也产生过一定的松散同盟,产生了比较有统治力的联盟首领,典型者有王二娘、王仲期等人。王二娘曾为36峒统领,而王仲期曾经统治80峒,从那时起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开始向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转化。
⑨ 参见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02页。
①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02页。
② 高泽强、文珍:《海南黎族研究》,海南出版社,2008,第79页。
③ 陈立浩、陈兰、陈小蓓著《从原始时代走向现代文明: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变迁历程》,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第54页。
④原保亭县毛枝乡的毛枝峒和牙冲峒曾为一个山岭的归属进行了长期的对峙,直至20世纪30年代还在互相推倒界碑,并为此事进行了火并恶斗,最终通过谈判才解决了此事,在争议过程中,两峒正常的交往和通婚全部中断。
①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高泽强,潘先锷著《祭祀与辟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第10页、第16~17页。一些邪症,比如突然的昏厥、胡语等,通过正常的医疗手段无法治愈,而利用巫术却可以加以控制,此类事件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记载。
② 民族民校公共哲学课教材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资料选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第1版。
③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
①(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② (明)戴焯(戴熄)、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海南出版社,2003,第409~411页。
③ (元)脱脱等撰《宋史·蛮夷三》卷四九五。
④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条,周伟民、唐玲玲辑纂点校《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第19页。
⑤ 峒长的具体职能包括:调解本峒纠纷,维持秩序;负责收集本峒的公粮;负责招待上级过往官员;召集全峒首领的会议。
⑥ (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① (明)邓廷宣:《琼州黎民图》,参见谭晶《明代<琼州黎民图>》,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拂拭历史尘埃——黎族古籍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第109页。
② 陈立浩、陈兰、陈小蓓著《从原始时代走向现代文明: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变迁历程》,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第64页。
③这类在政治上有权势的奥雅,黎族群众还称之为“奥雅买”。参见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写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144页。
④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时至今日,在黎族地区,有威信、有经验的老人在村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黎民的家庭事务、结婚、生子取黎名等都会听取其意见,甚至是村中集体事务,村领导也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奥雅的精神领袖地位与权威影响力显而易见。
① (清)张庆长编著《黎岐纪闻》,光绪三年刻本。
① 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183页。
② 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下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