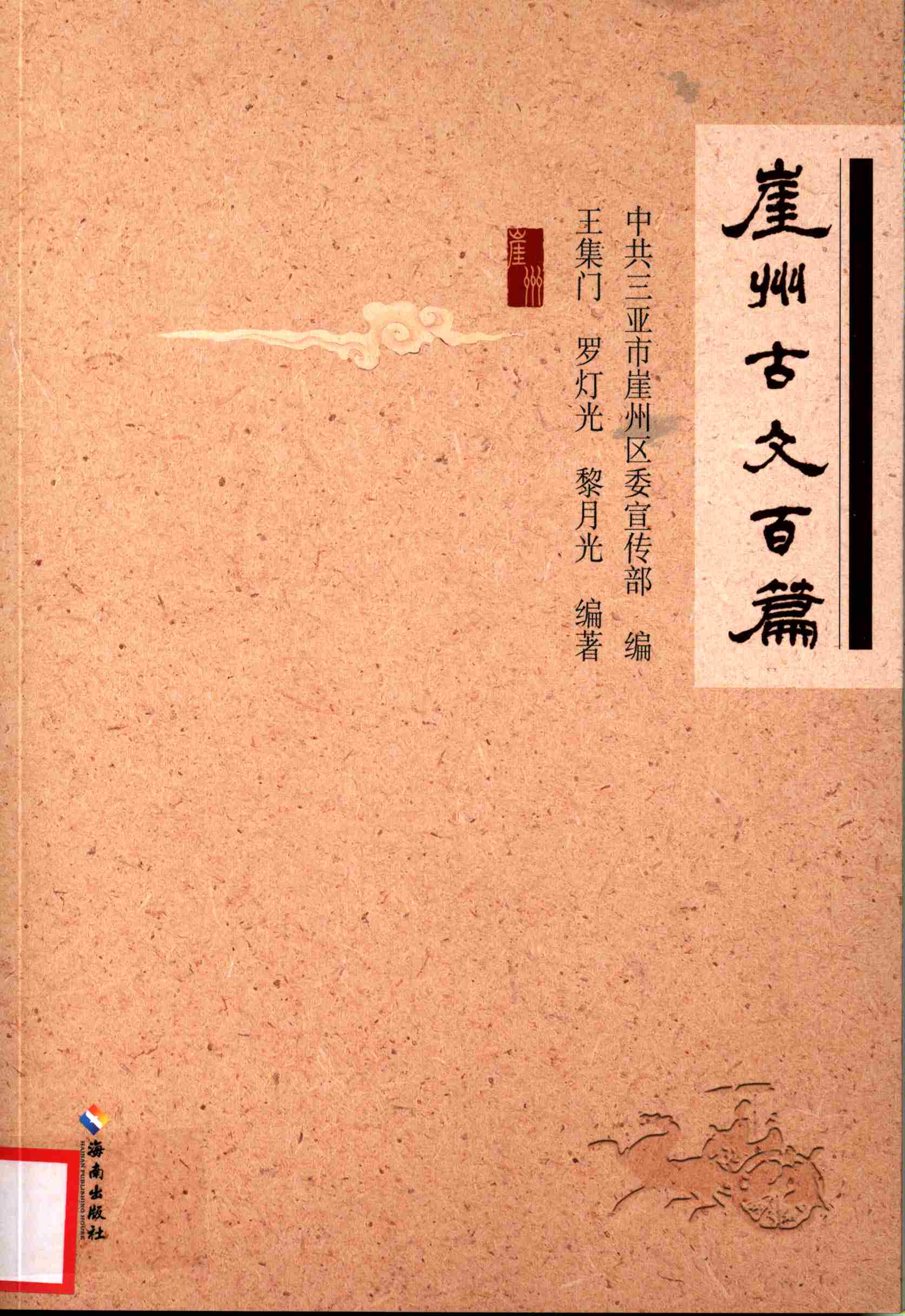内容
或曰:士尚志,尚志者以圣人为的,是故言必曰孔子,而汉以下诸儒不足言也。曰:德盛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辞。子之言志也,志则诚,言则欺,诚者不言也。故曰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公孙弘以周公自许,取诮当世,言而有孚难哉!
或曰:学贵自得,濂洛关闽之言,其刍狗乎?曰:理一而已。谷粟之味,啖之者知之,啖同则味同,味同则不言而契矣。若曰彼之啖者非谷粟也,而求奇以胜之,是将以酮酪为谷粟乎?侮圣言以恣臆说,而启人君慢士之心,曰孔孟以后无真儒,而概乎其夷之也,斯言启之矣。
夫理有常经,而无定在。经者人道之大闲,历千圣而不可变。若夫盘错之会,变通之宜,是非得失毫厘之辨,如观山者随步异形,岂有方体可执泥哉!
赜矣,夫天下之言也。奇则谲,浅则俚,角新竞胜,不根于理,盖其构意惟主于辞,而中无定执也。
或曰:气即有理,阴有阴之理,阳有阳之理,如曲直木之理,从革金之理。朱子认理气为二,非也。曰:理气混于一,而理为本。理则一,气则万殊。气有刚柔清浊,美恶不齐,而性因之以殊。故圣人立教,变异而归同,以本然之性无不同尔。诚若子言,则是人各为性,其本不同矣。本既不同,圣人岂能强而一之。或曰:理不能为气主,如何?曰:乾以君之,大德之敦化也,四时错行,小德之川流也。
而主宰在其中矣。气偏,用事者贱,圣人不能化,则有法以制之。
董仲舒为公孙弘所抑,退以著书为业,曰吾不仕故成业,不动故无悔,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五行志》载其对曰:汉当亡秦大敝之后,多兄弟亲戚骨肉,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故天灾,若语陛下非以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其后淮南衡山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皆以罪轻重受诛,二狱死者数万人。
按:此章欲诛内外宗室,惨酷过于暴秦,与仲舒策对任德不任刑者大戾,绝非仲舒所为,意者出于亲厚以稿就正,既获罪,有难显言而直受之欤。抑偃奸凶酿成之也。即使仲舒忧国,岂无善图,而不仁若此之甚。或拟议未定,而偃讦之,罪在偃矣。是故仲舒令终,昌延于后,而偃族诛,偃固有馀辜哉。
汉武帝元封六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说者谓为历元,非也。按历元者,历之所始,岁月日时皆甲子,而冬至在子夜,方为历元。是年特月朔甲子耳,而冬至又在旦,非历元也。是年丙子,而儿宽以为上元甲子,亦诡顺之词耳。
萧望之云:“虽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望之亦贤相也,然受少史贿润,廉声不闻。左迁太傅,腼颜在位,于守身之义何有?徒言而不能行,岂曰儒哉!
风俗之厚自士夫倡之。汉徐稚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稚徒步负粮到江夏,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张曲江称其感义,有补衰世。及郑玄卒,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衰绖赴会千馀人,盖闻稚之风而兴者。柳子曰:“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非人也。”其有感也夫。侯芭受《太玄》《法言》于扬雄,雄卒,芭为起坟,丧之三年。荀淑高行博学,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淑卒时,膺为尚书,自表师丧。淑子爽为硕儒,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当时往往化以成俗。盖自前汉夏侯胜为孝昭皇后授经,胜卒,后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汉风俗之厚有自来矣。及王莽杀吴章,欲禁锢其子弟门人,多更名他师。而平陵云敞幼儒为大司徒掾,独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棺敛归之,当时高其义,以比栾布。而敞竟以是名后世,与朱云相上下。方正学为之赞曰:“此可以为弟子事师遭变故者之法。”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自管仲有是言,而知己之恩殆与父母同也。
传称汉辕固、黄生争辨汤武革命。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桀纣荒乱,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桀纣虽失道,君也,汤武虽圣,臣也,乃因过而诛之,非杀而何?”东坡罪汤武,谓当时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
按:苏子言与黄生合,虽违经,而果于自信,守臣职之常者也。经言顺天应人以奉时义,达天下之变者也。权时之变而道济天下,非圣人孰敢任之。后世以汤武为口实,而莽操接迹于世,二子之说,其惭德遗意与!
孔子将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惠氏骄奢,逾境而徙,鲁之鬻牛马者不豫贾。然则孔子必任刑乎,是申韩之政也,不任刑乎,则沈犹等奚为畏之若是?曰:刑威圣人所不废,然有不令而行者存焉。子产为政,而桃李巷垂者莫援,则非徒惠焉耳。
士莫贵乎知人,达莫要于荐贤。赵文子立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而举士于白屋下者四十六人,公家甚赖之。文子死,四十六人皆就宾位,是无私德也。相晋,天下无兵革者九年,用贤之效也。
明主任计不任怒,是故齐桓用雠,晋文用盗,然去九官十二牧远矣。
齐攻鲁求岑鼎,欲以柳下惠之言为信。下惠对鲁君曰:“欲岑鼎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臣所难也。”噫!古人一诺重于丘山,岂不然哉!然或真足以存国,则亦可以权变而渝乎?曰:死之可也。信不可渝也,惠固已言之矣。
晋李离为大理,过杀不辜,君再令无死,而必于死。其言曰:“信文墨不察是非,听他辞不精事实,则离之罪误也,非故也。”君赦之可以无死,而必死,古人重义轻生盖如此。虽然误而皆死,为理者亦难矣。
周监二代,曲为之制,事为之防,其究也文烦而俗敝。汉除秦苛法,未遑礼乐,几于易简,而或讥其为苟且之治。伊川曰:“先王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噫!徒法非法也。善其事之谓法,善其事而无私焉之谓道。无法可守,于道何有?
古之教者使人安其所乐,而不强其所不乐。安其所乐,诗书礼乐是也。虽有美质,不长于文,而责之以文,强其所不乐也。科目所取,大率皆文学之士。司马光十科荐士之法,盖以佐科目之所不及,然行之匪人,反以滋弊,不如科目拔十得五为至公也。或曰:文能得士,何也?曰:临下在知,官人者将使之临下也。《易》曰:“知临,大君之宜。”试之文,所以观其知也。
古者天子颁朔,说者谓夏小正之属。今按《月令》一篇,帝王颁朔大概已可想见。所谓时正令善,此其遗意耶?汉惟丙魏数人知谨于此。今之所存者,惟冬至前行刑一事耳。而用兵尤刑之大者,则每以六月兴师,五月渡泸为比。噫!彼岂得已哉!得已而不已,以干天和,召疫疠,仁者弗为也。
东晋贱名检,以法理为俗吏,而目之曰兰熏之器。望白署空者皆名重海内,目为台衡。此王衍所以祸晋,而世道所以不竞也。玄虚与吾儒虚静最相似,吾儒虚而有,异端虚而无,不可不辨。
夫道穷则变,管仲营霸而圣门羞之,何耶?曰:穷则变以从道也,非以济其私也。伯术私也,君子宁无九合之功,而不可为诡遇之获。曰:卑管仲,谓其无本也。使能正身致主,则有本矣。于是变齐为富强,以建功于天下,奚为不可?曰:齐之不正,非特无本。其作内政以寄军令,以诈成功,人心蛊坏,至夫子时益甚矣。子未知天职乎?人君代天立极,必因民恒性而牗之,自二帝三王以来,未之有改也。管氏则反其性而导之以夸诈,纵其欲而诱之以功利,其民欢然趋之,相渐成俗,而性命之大闲决矣。故尊主攘夷,其功固大,而饰巧诈以开万世利欲之源,其害尤大。夫子谓一变乃能至鲁,盖必尽濯旧习而后王道可几也。有志于道者,其无以功利为心哉!
或曰:道尚变,鲁两生不为汉出,仲尼乃彷徨列国,奚不知变欤?曰:时有变,而道不可变。夫道犹川也,川无壅,则滔滔而赴海。春秋之世壅吾道者多矣,是故功利急则欲心炽,夸诈用则信义亏,詝言昌则正俗败,吞并起则王制隳,庶孽宠则国本摇,私门强则公室弱,凡此皆壅斯道而势所必变者也。夫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变非夫子不能,而潜移默化,固有不令而行者。然积习颓敝,群情便之。而势家大族以为不便,则嫉而挠之者至矣。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其曰人乃在位当权者也。季氏柄鲁已久,与之相倚,归而受之,皆臣为主也。臣为主而用舍进退制于其手,夫子虽至圣,其若之何哉!
汉光武以张佚不难正朕,故用为子傅。唐太宗谓李绩不遗李密,故托绩以孤幼。盖忠谅笃厚,乃胜大任,自修者不可不谨于微!
天下之水因山而行,非出于一山也,记者举最先发者以名。其源若江曰岷山,淮曰桐柏山,皆是也。江淮之水实聚众流而后大。汉张骞穷河源,与元所谓星宿之海不同,盖各有所指尔,未可遽以张骞为非。
宋神宗愿治之君也,用安石而乱天下,何耶?曰:神宗功利之心急,而安石中其欲,安石刚愎之气盛,而神宗溺其偏。又曰:神宗徇名而不求实用,安石溺古而不达时宜。
四则饮齐视冬时,注云饮寒也。近世名医谓酒宜冷饮,不为无据。
或曰:更世既远,可以复姓乎?曰:古之人或因官为姓,因族为姓,即所居为姓,其本无二也。智果避智伯之难,易姓辅氏,非得已也。鲁襄公时莒以子为鄫后,《春秋》书曰“莒人灭鄫”,其为训严矣。马世荣避乱姓叶,至其孙晋而复姓马。晋牛金之子避患改为牢,又改为寮,寮氏名默者,乃请于朝而复姓牛。虞伯生曰:“昔人别氏于族者有之,蒙他人姓者无也。”心所未安,则复之,何言乎远哉!
日乌月兔,先儒谓乌尾翘,钟阳之精,兔唇缺,禀阴之精,故假二物以象日月,非也。日生于东,映在酉,为鸡,月生于西,映在卯,为兔,故各以光之所映者象焉。酉有毕月鸟,卯有房口兔。若谓尾翘为阳,则岂特乌为然哉?
秦焚天下之书以愚黔首,而掌在博士者自若也。萧何收秦图籍,不能并收,及项羽烧秦宫室,而先王典籍荡然无馀矣。故汉有口授之艰,唐有手抄之勤。及五代刻印既便,以至宋之中叶,真儒辈出,继者衍绎益繁,汗牛充栋,遂致学子耗精敝神,而忘其本真,此象山陆氏所以有助于程朱,有功于正学也。善学者取其所长可也。朱子答何叔京书曰:“若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不少。”又答刘子澄书云:“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误人亦不少。”此皆为杂博者言耳。要之修德讲学,岂可偏废。
孔明自比管乐,喜申韩,以至祁山之役忧恚呕血,皆陈寿以私怨加诬,不可信也。
孔明八阵在新都沔阳金鱼复,四头八尾,隅落钩连,队陈相容,触处为首,寓先天心法之妙,至今尚存。
宋初未有学,天下惟书院。今则舍儒学而建书院。
明道为御史,不欲掇拾臣下短长,伊川则欲立检察士人行检法。盖掇拾短长,则吹毛求疵,有伤大体。全无检察,则规防荡废,易于纵恣。
今之好功名者,皆喜为萧何,不善为曹参,谓参守旧无能。然每一更张,吏胥乘之为奸,民受其弊。后来者又求奇而更之,弊愈甚矣。必也新其旧而上下兼利,虽变而民不知变,斯善变者乎。
白沙先生养气说,赠信丰俞通“至大至刚以直”为句,似主程子。谓朱说与程抵牾,非特句读文义之差而已。按朱说固为有据,程说亦自无害,而工夫至要全在集义,此固白沙之意也。今乃多嗜欲而谈义道,远矣。
董仲舒云:“性者生之质。”如义以为质之质,非资质也。又云:“质朴之谓性,人欲之谓情。”如孟子云:“五者之欲,性也”,“形色,天性也”,皆兼气质言。又曰:“明于天性,然后知自贵于物。”此犹孟子言性善,盖各有所指耳。其心术高明,卓然有见处,非诸儒所及,未可以博物洽闻例看。世乱则畏诛戮而名位轻,治久则尚门第而名位重,自唐歆科目以来,竞尚名位久矣。虽颜鲁公之贤,犹自叙世族官爵之荣,见于颜秘书碑刻,可考也。而或犹祖老庄遗意,谓名位不足荣,谬哉!然有命焉,积学而顺受其正,斯善矣。周子一部《通书》贯彻首尾,只是“无欲”二字为主,故以此始,以此终。
庄子曰:“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呜呼!一夷跖,齐名利,此庄老欺世之言,儒者不言也。先正云:“好名则有不为,好利则无所不为矣。”旨哉!
不为名而为善,愈于畏名而为善。为名而为善,愈于不为名而不为善。为善而不为名,求自慊也。为名而保名者,必畏义,畏义则不敢为不善。为名而希禄利者必伪,伪则无不至矣。
地天偶也,而尊天。月日匹也,而主日。五岳宗岱,百川宗海。是故两大不并隆。
势均则敌,欲交炽也。声同则应,理相感也。
毋暴怒,毋忮害,毋訾毁,毋自文。自饰其清,反显其浊。欲笃其交,反致其疏。好辨而不入,屡变而求胜,皆诚意不足而其言枝也。
智者知多而所守者简,故明。愚者智少而所务者烦,故昏。
兵二。法制之师,太公、管乐、诸葛是也。法不足而用谋,谋不足而用诈,孙吴是也。
秦之力不足以敌诸侯,故利于割地,不利于战,而示天下以好战之形,阴使说士道之以和。诸侯之力足以敌秦,而轻于割地,重于战,示秦以怯斗之情,此其所以亡也。
曹参为相,日饮醇酒,不事事。王导辅佐三世,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馀。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当思我。”谢安石不存小察,经远无竞。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赵韩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寘二大瓮,满则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陈一切报罢,云以此报国。此六七君子真名世英宰也。
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张说、源乾矅三故相官,帝赋三杰诗自写以赐,其意盖以比萧张等也。说与乾曜,岂璟比哉?明皇可谓不知臣矣。廉颇老而能饭,披甲上马,自示可用,而卒困于郭开之口。汉武帝大击匈奴,李广已老,数自请行,而卒有东道失军之罪。宣帝伐先零,赵充国年七十馀,自任可将,即驰至金城图上方略,虽全师制胜,而祸及其子印。光武讨五溪蛮,马援年老请行,披甲据鞍以示可用,而卒致壶头之尤。李靖因吐谷浑寇边,即往见房乔,自任为将,既平其国,而有高甄生诬罔之事,几于不免。郭子仪年八十馀,犹为关内副元帅、河中节度,不求退身,德宗册罢。诸公皆人杰,而犹不免此,可哀也已。
或曰礼从宜。礼之不可变者三纲五常,万世无弊,其可变者文质,异宜者耳。然繁缨也,隧也,朱干也,两观也,八佾也,皆末节耳,而君子谨之,不敢毫发僭差。至于纲常大伦,乃或轻变以济其私,废君则曰行权,拒父则曰尊祖,崇妾母曰夫人,刃同气曰定乱,居丧纳币曰用礼,如此之类不可殚纪。岂所谓变以从道者,固将不计是非,而一以从俗为宜耶?
鲍叔牙清廉正直,而闻人之过,终身不忘,隘也。隰朋丑不若黄帝,而哀弗己若者,弘也。
阴阳相荡,各以其渐。邵子曰:“春为阳始,夏为阳极,秋为阴始,冬为阴极。”四月乾卦,纯乎阳矣,然必至五月一阴生,六月二阴生,而暑乃盛。十月坤卦,纯乎阴矣,然必至十一月一阳生,十二月二阳生,而寒乃极。故岐伯曰:“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春夏秋冬,各差其分。”
吉凶悔吝生乎动,吉一而已。惩忿窒欲,改过迁善,善一而已。
去谗远色,贱货贵德,徳一而已。是以君子乐善,必谨其防。
居暗则能照明,居明则不能见暗。故君子静以检身,晦以藏智。
心无物而后能烛物,加之意则多事,今之法家,申韩之馀习也。
关尹子曰:“情生于心,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佛氏云明心见性,盖佛老之教皆以性为本体,心为知觉,情为发见处。其言道则窈冥昏默,不可知不可见,犹吾儒言太极也。但言心生于性,则性无顿处。
司马光谓静虑以养神,潜心以实下。盖神为主,神驰则气上升,故静虑使神安于内,则气下降,而根本实矣。杨子所谓“潜心于渊,美厥灵根”是也。
阴阳不测之谓神,天地之神也。在人则心为神,阴阳之会也,生理具乎此矣。
偶阅历天道南行、东行等说,因思其义盖取月建三合,旺月取摹,馀月取旺也。
杨文懿公守陈,天庭有黑子七,宛类北斗。宋文公及陈白沙皆面有七黑子。相书谓面无善黡,岂足据耶?
昔宋儒陈同甫于宋淳熙戊戌春上孝宗书有云:“丙午丁未岁,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明年艺祖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真宗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极盛之时。又六十年而神宗即位,国家之事于是一变。又六十年遂为靖康之祸。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天道六十年一变,可不有以应其变乎?”盖劝孝宗乘丙午丁未以恢复有为也。其于戊申又上书云:“乙巳丙午之间,虏人非无变乱。”故又云:“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验,而再冒万死以自陈,实以宗庙社稷之大计,不得不决于斯时也。”
愚按:人臣告君,惟当匡之以义,不当眩之以天数也。
古今文体不同,同归于实。理,实理也,事,实事也,载之以辞则至文也。岂必曰韩欧不足学,吾其班马,班马不足学,吾其左氏、《檀弓》,左氏、《檀弓》又不足学,吾其简奥如《易》,聱牙如《盘庚》。体制拘而识趣寡也,误哉!且著述与应酬不同,著述尚宏深,发明大道,不为徒作,应酬惟取达意斯已矣。或乃殚心力,效古书篇为之,情实何有?
元帝为太子,谏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怒谓汉道杂王霸,奈何纯任德教。此盖以德教为王,刑名为霸,非惟不知王,亦不知霸也。王者性仁义,霸则假之以济其私。虽尧舜之圣,不能弛刑,刑者义之用,所以辅仁德者。仁之施,所以行义,非王偏任德,霸偏任刑也。宣帝深刻寡恩,似义非义而害仁,下于霸者也。元帝优柔不断,似仁非仁而害义,则嬖幸用事,斨贼忠贤,无可言矣。乃徒以数赦为煦煦之仁,曾谓儒者之用如是哉!
门人记明道之言,要须察识。如云天地中无物不有,何尝有心拣别善恶,一切涵容覆载。若善者亲之,不善者远之,则物不与者多,安得为天地?按此言君子存心公恕,兼包并蓄则可,若当事任,进贤退不肖,或和如春,或肃如秋,时乃天道,恶恶不严,则好善不笃。明道告君欲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正是此意。后人不知,乃倡为调停之说,正邪并用,而正人卒受其害,可叹也。
传称孔子厄于陈蔡,七日藜羹不糁,而弦歌鼓舞不绝。子路讥其无耻,孔子解之,更瑟而弦。此不知君子者也。君子于琴瑟以动荡其和平之音,虽困极不易,固有之矣,而其所以乐者不在是也。如以瑟为乐,舍瑟将何乐乎?在厄难而逾乎其素,则不情,虞从者之疑而强焉以宁众,则近诬。是皆动乎内者也,夫子不为也。或曰:孟氏门人不闻以礼乐器自随,何也?曰:有之,无因故不及。
或问:《宋史》如何?曰陋。自唐以来竞尚润笔,以扬亲之美为孝,修《元史》者皆登之,事无奇特,则杂鬼卜妖妄以骇听闻,皆可删也。《唐书》经欧、宋二公手笔,故事增于日,文省于前,此作史要法。脱脱等不知此义,故《宋史》冗而陋。然则有善不书可乎?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则书,关名贤名臣言行则书,自馀泛泛,略之可也。
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壮伟,其失骋,汉之文华瞻,其失缓,东汉而下无取焉。
文学之用微矣。搜遗抉隐,组绘葩丽,琢字句,炫故实者,其华也。质任坦素,黜巧不事,镇重如崇岳,瀞深如巨汇,如车徒数万,董以渠帅,部分整峻,望之神慑而意阻者,其大体也。中和内融,包钜烛微,探贤圣之秘,启天地之藏,〓濆盈旁溢,而不可御者,其精实也。上士务实,大体从之,下士务华,实斯病焉。《易》《书》《诗》《礼》《春秋》之文,实宏而体备,足乎内而盎乎其外者也。
水阴也,阴宜静,而水体则动。火阳也,阳宜动,而火体则伏。火以气为用,微之显也。水以质为用,静之动也。故君子柔贵能行,刚贵藏用。宋之盛时,居台谏者为人所疏,其后台谏之门挥汗成雨,一徙它局,可张爵罗,风俗媮薄甚矣。
文内多缀古人姓名,自昔讥为点鬼簿。然孟子称王豹绵驹华周杞梁,太史公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撰《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此类甚多,岂足为訾?文之要有四,曰理也,气骨也,典也,实也。若夫为奇为怪,为藻为丽,文多而用寡,特组缋之小巧耳。
或曰:先祖,人鬼也,鬼则不神,外神威灵,故民媚而畏之,是不然。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祇人鬼皆阴阳之灵,吾之精诚随感而应,内外一也。夫孝,百行之首也。能孝必能敬身,能敬身则能事人,能事人则能处物我而无间,处物我而无间,则能与神明合矣。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此理之至微者也,非仁人孰能知之?或曰:古者祭祀不祈,祸福自我,神何预焉。曰:祀者致吾诚而已,徼福妄也,淫祀谄也。《礼》曰百顺之谓福,致吾所祀,顺之至也,而冀鬼神我私,惑也。天道福善祸淫,能敬必有福。曰:福固可祈乎?曰:礼有六祈,周公祈代武王之死,何暇论理之有无?若弃人道而委命于巫祝,则谬矣。
声音与政通,风淳则语多浑朴,虽文彩未足,不害为真率。若《击壤》之歌,《康衢》之谣是已。风漓则语多雕刻,譬之剪彩镂冰,徒炫姿媚,若徐庾温李之类是已。况才有工拙,德有浅深,感有顺逆,酌文质之中,适节奏之宜,以不失乎性情之正,则存乎其人焉。
师保之任,在于辅养君德,镇躁消邪。故《卷阿》称君德曰“岂弟”,称其得贤曰“冯翼孝德”,老成重厚之风,可想见矣。萧望之谓张敞材轻,非辅导之器,真知言哉。
礼乐,由心生者也。性情之德,情之中和也。礼以道中,神明生焉,乐以导和,协气流焉。验诸身心日用之间,而礼乐之全体可知矣。中也者,敬以直,内之体乎?和也者,义以方,外之用乎?
吴临川元仁宗时进司业,乃损益程文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为教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于《易》《书》《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可谓勤矣。然在今世,书籍议论满天下,不患不知,患不能行,诚不如象山之学得曾子三贵遗意。
荆公《洪范传》论五行一段,言五行于物,水为精,火为神,木为魂,金为魄,土为意。又曰:“神从志从,意志致一之谓精,唯天下之至精,为能合天下之至神,精与神一不离,则变化在我而已。”此虽出于通玄修真等书,而与持志养气之说相表里,小用之则生气运行,大用之则制天下之务,皆此志也。
杨文懿公传云:“圣门之学,以精思力践为要,博文强记,辅此而已。”真名言哉。
韩柳文。按韩文篇篇气象广大,不为私小偏徇之言,皆关天下之故,最得《春秋》之旨。柳则精矣,而伤于刻削,其气象大不如韩。近世惟王守溪得韩文宗旨。
昔人云天下之美不得两兼,实美者无好花,花艳者无佳实。故富于文辞者,其家必贫,富于赀货者,其子必不肖,天也,亦人也。然工文辞则志有所专而利轻,故贫,饶货财则心有所恃而过多,故不肖。虽然贫者所以成之,恃者所以败之,莫非天也。
皋陶明刑弼教,成天下之大业,六蓼乃其后也,为楚所灭,时适然尔,岂足议刑官无后哉!子羔卒免于难,于公庆延于世,厚德之报固如此,欧阳子泷冈阡之文祖之。
杨慈湖云:“董仲舒告其君曰愿设诚于内,而致行之。谓诚岂可设,设则非诚,仲舒尚不明己之心,何以启君之心。”愚按,仲舒正谊明道之言,卓然非诸儒所及。设之一字,恐非本文,疑是致字之误,其致行“致”字衍文耳。
东莱云:“孟子深斥杨墨,以其似仁义也。”同时如唐勒景差辈,浮词丽语,未尝一与之辨,道不同故也。讲正学而务辞章,岂曰儒哉!
圣人之心湛然与神明通,学者洗心,日进乎高明,神其几矣。诗曰:“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言神之体物,可畏如此。祭以交神,特暂时事,君子因之以日澡其德,故尤谨乎致齐。
黄庭坚《道院赋》谓江西惟筠州独不嚚讼,然与南康、庐陵、宜春三郡并蒙恶声。是宜春旧以嚚讼闻,今则惟庐陵为甚。是在长民者化之有要,上喜讼则讼愈多。追摄不体,株连蔓引,乃申于上曰某到官问囚几何,军犯几何,死刑几何,追赃罚几何,积谷几何。以简静为无能,计多寡为殿最,深刻者为公道,惨暴者为风力,上以是求,下以是应,孰知以无讼为贵哉?昔黄霸在颍川,八年无重囚,史称其务在成就全安之。霸设心如是,宜其无重囚也。今欲追龚黄之治,而不变申韩之习,难哉!
曾子固请令长贰自举属官一札,诚为有见,中间未必无私厚,然公论自在也。
《余襄公集》谓罗浮有五色雀,各被方色,非时不见。若士大夫将游是山,则先日群翔,寺僧以是为候。嘉靖乙酉有鸟五色集于徐闻山巅,百鸟从之,人争视以为凤,意者即此雀乎?
或曰:学贵自得,濂洛关闽之言,其刍狗乎?曰:理一而已。谷粟之味,啖之者知之,啖同则味同,味同则不言而契矣。若曰彼之啖者非谷粟也,而求奇以胜之,是将以酮酪为谷粟乎?侮圣言以恣臆说,而启人君慢士之心,曰孔孟以后无真儒,而概乎其夷之也,斯言启之矣。
夫理有常经,而无定在。经者人道之大闲,历千圣而不可变。若夫盘错之会,变通之宜,是非得失毫厘之辨,如观山者随步异形,岂有方体可执泥哉!
赜矣,夫天下之言也。奇则谲,浅则俚,角新竞胜,不根于理,盖其构意惟主于辞,而中无定执也。
或曰:气即有理,阴有阴之理,阳有阳之理,如曲直木之理,从革金之理。朱子认理气为二,非也。曰:理气混于一,而理为本。理则一,气则万殊。气有刚柔清浊,美恶不齐,而性因之以殊。故圣人立教,变异而归同,以本然之性无不同尔。诚若子言,则是人各为性,其本不同矣。本既不同,圣人岂能强而一之。或曰:理不能为气主,如何?曰:乾以君之,大德之敦化也,四时错行,小德之川流也。
而主宰在其中矣。气偏,用事者贱,圣人不能化,则有法以制之。
董仲舒为公孙弘所抑,退以著书为业,曰吾不仕故成业,不动故无悔,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五行志》载其对曰:汉当亡秦大敝之后,多兄弟亲戚骨肉,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故天灾,若语陛下非以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其后淮南衡山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皆以罪轻重受诛,二狱死者数万人。
按:此章欲诛内外宗室,惨酷过于暴秦,与仲舒策对任德不任刑者大戾,绝非仲舒所为,意者出于亲厚以稿就正,既获罪,有难显言而直受之欤。抑偃奸凶酿成之也。即使仲舒忧国,岂无善图,而不仁若此之甚。或拟议未定,而偃讦之,罪在偃矣。是故仲舒令终,昌延于后,而偃族诛,偃固有馀辜哉。
汉武帝元封六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说者谓为历元,非也。按历元者,历之所始,岁月日时皆甲子,而冬至在子夜,方为历元。是年特月朔甲子耳,而冬至又在旦,非历元也。是年丙子,而儿宽以为上元甲子,亦诡顺之词耳。
萧望之云:“虽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望之亦贤相也,然受少史贿润,廉声不闻。左迁太傅,腼颜在位,于守身之义何有?徒言而不能行,岂曰儒哉!
风俗之厚自士夫倡之。汉徐稚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稚徒步负粮到江夏,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张曲江称其感义,有补衰世。及郑玄卒,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衰绖赴会千馀人,盖闻稚之风而兴者。柳子曰:“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非人也。”其有感也夫。侯芭受《太玄》《法言》于扬雄,雄卒,芭为起坟,丧之三年。荀淑高行博学,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淑卒时,膺为尚书,自表师丧。淑子爽为硕儒,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当时往往化以成俗。盖自前汉夏侯胜为孝昭皇后授经,胜卒,后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汉风俗之厚有自来矣。及王莽杀吴章,欲禁锢其子弟门人,多更名他师。而平陵云敞幼儒为大司徒掾,独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棺敛归之,当时高其义,以比栾布。而敞竟以是名后世,与朱云相上下。方正学为之赞曰:“此可以为弟子事师遭变故者之法。”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自管仲有是言,而知己之恩殆与父母同也。
传称汉辕固、黄生争辨汤武革命。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桀纣荒乱,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桀纣虽失道,君也,汤武虽圣,臣也,乃因过而诛之,非杀而何?”东坡罪汤武,谓当时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
按:苏子言与黄生合,虽违经,而果于自信,守臣职之常者也。经言顺天应人以奉时义,达天下之变者也。权时之变而道济天下,非圣人孰敢任之。后世以汤武为口实,而莽操接迹于世,二子之说,其惭德遗意与!
孔子将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惠氏骄奢,逾境而徙,鲁之鬻牛马者不豫贾。然则孔子必任刑乎,是申韩之政也,不任刑乎,则沈犹等奚为畏之若是?曰:刑威圣人所不废,然有不令而行者存焉。子产为政,而桃李巷垂者莫援,则非徒惠焉耳。
士莫贵乎知人,达莫要于荐贤。赵文子立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而举士于白屋下者四十六人,公家甚赖之。文子死,四十六人皆就宾位,是无私德也。相晋,天下无兵革者九年,用贤之效也。
明主任计不任怒,是故齐桓用雠,晋文用盗,然去九官十二牧远矣。
齐攻鲁求岑鼎,欲以柳下惠之言为信。下惠对鲁君曰:“欲岑鼎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臣所难也。”噫!古人一诺重于丘山,岂不然哉!然或真足以存国,则亦可以权变而渝乎?曰:死之可也。信不可渝也,惠固已言之矣。
晋李离为大理,过杀不辜,君再令无死,而必于死。其言曰:“信文墨不察是非,听他辞不精事实,则离之罪误也,非故也。”君赦之可以无死,而必死,古人重义轻生盖如此。虽然误而皆死,为理者亦难矣。
周监二代,曲为之制,事为之防,其究也文烦而俗敝。汉除秦苛法,未遑礼乐,几于易简,而或讥其为苟且之治。伊川曰:“先王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噫!徒法非法也。善其事之谓法,善其事而无私焉之谓道。无法可守,于道何有?
古之教者使人安其所乐,而不强其所不乐。安其所乐,诗书礼乐是也。虽有美质,不长于文,而责之以文,强其所不乐也。科目所取,大率皆文学之士。司马光十科荐士之法,盖以佐科目之所不及,然行之匪人,反以滋弊,不如科目拔十得五为至公也。或曰:文能得士,何也?曰:临下在知,官人者将使之临下也。《易》曰:“知临,大君之宜。”试之文,所以观其知也。
古者天子颁朔,说者谓夏小正之属。今按《月令》一篇,帝王颁朔大概已可想见。所谓时正令善,此其遗意耶?汉惟丙魏数人知谨于此。今之所存者,惟冬至前行刑一事耳。而用兵尤刑之大者,则每以六月兴师,五月渡泸为比。噫!彼岂得已哉!得已而不已,以干天和,召疫疠,仁者弗为也。
东晋贱名检,以法理为俗吏,而目之曰兰熏之器。望白署空者皆名重海内,目为台衡。此王衍所以祸晋,而世道所以不竞也。玄虚与吾儒虚静最相似,吾儒虚而有,异端虚而无,不可不辨。
夫道穷则变,管仲营霸而圣门羞之,何耶?曰:穷则变以从道也,非以济其私也。伯术私也,君子宁无九合之功,而不可为诡遇之获。曰:卑管仲,谓其无本也。使能正身致主,则有本矣。于是变齐为富强,以建功于天下,奚为不可?曰:齐之不正,非特无本。其作内政以寄军令,以诈成功,人心蛊坏,至夫子时益甚矣。子未知天职乎?人君代天立极,必因民恒性而牗之,自二帝三王以来,未之有改也。管氏则反其性而导之以夸诈,纵其欲而诱之以功利,其民欢然趋之,相渐成俗,而性命之大闲决矣。故尊主攘夷,其功固大,而饰巧诈以开万世利欲之源,其害尤大。夫子谓一变乃能至鲁,盖必尽濯旧习而后王道可几也。有志于道者,其无以功利为心哉!
或曰:道尚变,鲁两生不为汉出,仲尼乃彷徨列国,奚不知变欤?曰:时有变,而道不可变。夫道犹川也,川无壅,则滔滔而赴海。春秋之世壅吾道者多矣,是故功利急则欲心炽,夸诈用则信义亏,詝言昌则正俗败,吞并起则王制隳,庶孽宠则国本摇,私门强则公室弱,凡此皆壅斯道而势所必变者也。夫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变非夫子不能,而潜移默化,固有不令而行者。然积习颓敝,群情便之。而势家大族以为不便,则嫉而挠之者至矣。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其曰人乃在位当权者也。季氏柄鲁已久,与之相倚,归而受之,皆臣为主也。臣为主而用舍进退制于其手,夫子虽至圣,其若之何哉!
汉光武以张佚不难正朕,故用为子傅。唐太宗谓李绩不遗李密,故托绩以孤幼。盖忠谅笃厚,乃胜大任,自修者不可不谨于微!
天下之水因山而行,非出于一山也,记者举最先发者以名。其源若江曰岷山,淮曰桐柏山,皆是也。江淮之水实聚众流而后大。汉张骞穷河源,与元所谓星宿之海不同,盖各有所指尔,未可遽以张骞为非。
宋神宗愿治之君也,用安石而乱天下,何耶?曰:神宗功利之心急,而安石中其欲,安石刚愎之气盛,而神宗溺其偏。又曰:神宗徇名而不求实用,安石溺古而不达时宜。
四则饮齐视冬时,注云饮寒也。近世名医谓酒宜冷饮,不为无据。
或曰:更世既远,可以复姓乎?曰:古之人或因官为姓,因族为姓,即所居为姓,其本无二也。智果避智伯之难,易姓辅氏,非得已也。鲁襄公时莒以子为鄫后,《春秋》书曰“莒人灭鄫”,其为训严矣。马世荣避乱姓叶,至其孙晋而复姓马。晋牛金之子避患改为牢,又改为寮,寮氏名默者,乃请于朝而复姓牛。虞伯生曰:“昔人别氏于族者有之,蒙他人姓者无也。”心所未安,则复之,何言乎远哉!
日乌月兔,先儒谓乌尾翘,钟阳之精,兔唇缺,禀阴之精,故假二物以象日月,非也。日生于东,映在酉,为鸡,月生于西,映在卯,为兔,故各以光之所映者象焉。酉有毕月鸟,卯有房口兔。若谓尾翘为阳,则岂特乌为然哉?
秦焚天下之书以愚黔首,而掌在博士者自若也。萧何收秦图籍,不能并收,及项羽烧秦宫室,而先王典籍荡然无馀矣。故汉有口授之艰,唐有手抄之勤。及五代刻印既便,以至宋之中叶,真儒辈出,继者衍绎益繁,汗牛充栋,遂致学子耗精敝神,而忘其本真,此象山陆氏所以有助于程朱,有功于正学也。善学者取其所长可也。朱子答何叔京书曰:“若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不少。”又答刘子澄书云:“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误人亦不少。”此皆为杂博者言耳。要之修德讲学,岂可偏废。
孔明自比管乐,喜申韩,以至祁山之役忧恚呕血,皆陈寿以私怨加诬,不可信也。
孔明八阵在新都沔阳金鱼复,四头八尾,隅落钩连,队陈相容,触处为首,寓先天心法之妙,至今尚存。
宋初未有学,天下惟书院。今则舍儒学而建书院。
明道为御史,不欲掇拾臣下短长,伊川则欲立检察士人行检法。盖掇拾短长,则吹毛求疵,有伤大体。全无检察,则规防荡废,易于纵恣。
今之好功名者,皆喜为萧何,不善为曹参,谓参守旧无能。然每一更张,吏胥乘之为奸,民受其弊。后来者又求奇而更之,弊愈甚矣。必也新其旧而上下兼利,虽变而民不知变,斯善变者乎。
白沙先生养气说,赠信丰俞通“至大至刚以直”为句,似主程子。谓朱说与程抵牾,非特句读文义之差而已。按朱说固为有据,程说亦自无害,而工夫至要全在集义,此固白沙之意也。今乃多嗜欲而谈义道,远矣。
董仲舒云:“性者生之质。”如义以为质之质,非资质也。又云:“质朴之谓性,人欲之谓情。”如孟子云:“五者之欲,性也”,“形色,天性也”,皆兼气质言。又曰:“明于天性,然后知自贵于物。”此犹孟子言性善,盖各有所指耳。其心术高明,卓然有见处,非诸儒所及,未可以博物洽闻例看。世乱则畏诛戮而名位轻,治久则尚门第而名位重,自唐歆科目以来,竞尚名位久矣。虽颜鲁公之贤,犹自叙世族官爵之荣,见于颜秘书碑刻,可考也。而或犹祖老庄遗意,谓名位不足荣,谬哉!然有命焉,积学而顺受其正,斯善矣。周子一部《通书》贯彻首尾,只是“无欲”二字为主,故以此始,以此终。
庄子曰:“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呜呼!一夷跖,齐名利,此庄老欺世之言,儒者不言也。先正云:“好名则有不为,好利则无所不为矣。”旨哉!
不为名而为善,愈于畏名而为善。为名而为善,愈于不为名而不为善。为善而不为名,求自慊也。为名而保名者,必畏义,畏义则不敢为不善。为名而希禄利者必伪,伪则无不至矣。
地天偶也,而尊天。月日匹也,而主日。五岳宗岱,百川宗海。是故两大不并隆。
势均则敌,欲交炽也。声同则应,理相感也。
毋暴怒,毋忮害,毋訾毁,毋自文。自饰其清,反显其浊。欲笃其交,反致其疏。好辨而不入,屡变而求胜,皆诚意不足而其言枝也。
智者知多而所守者简,故明。愚者智少而所务者烦,故昏。
兵二。法制之师,太公、管乐、诸葛是也。法不足而用谋,谋不足而用诈,孙吴是也。
秦之力不足以敌诸侯,故利于割地,不利于战,而示天下以好战之形,阴使说士道之以和。诸侯之力足以敌秦,而轻于割地,重于战,示秦以怯斗之情,此其所以亡也。
曹参为相,日饮醇酒,不事事。王导辅佐三世,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馀。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当思我。”谢安石不存小察,经远无竞。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赵韩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寘二大瓮,满则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陈一切报罢,云以此报国。此六七君子真名世英宰也。
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张说、源乾矅三故相官,帝赋三杰诗自写以赐,其意盖以比萧张等也。说与乾曜,岂璟比哉?明皇可谓不知臣矣。廉颇老而能饭,披甲上马,自示可用,而卒困于郭开之口。汉武帝大击匈奴,李广已老,数自请行,而卒有东道失军之罪。宣帝伐先零,赵充国年七十馀,自任可将,即驰至金城图上方略,虽全师制胜,而祸及其子印。光武讨五溪蛮,马援年老请行,披甲据鞍以示可用,而卒致壶头之尤。李靖因吐谷浑寇边,即往见房乔,自任为将,既平其国,而有高甄生诬罔之事,几于不免。郭子仪年八十馀,犹为关内副元帅、河中节度,不求退身,德宗册罢。诸公皆人杰,而犹不免此,可哀也已。
或曰礼从宜。礼之不可变者三纲五常,万世无弊,其可变者文质,异宜者耳。然繁缨也,隧也,朱干也,两观也,八佾也,皆末节耳,而君子谨之,不敢毫发僭差。至于纲常大伦,乃或轻变以济其私,废君则曰行权,拒父则曰尊祖,崇妾母曰夫人,刃同气曰定乱,居丧纳币曰用礼,如此之类不可殚纪。岂所谓变以从道者,固将不计是非,而一以从俗为宜耶?
鲍叔牙清廉正直,而闻人之过,终身不忘,隘也。隰朋丑不若黄帝,而哀弗己若者,弘也。
阴阳相荡,各以其渐。邵子曰:“春为阳始,夏为阳极,秋为阴始,冬为阴极。”四月乾卦,纯乎阳矣,然必至五月一阴生,六月二阴生,而暑乃盛。十月坤卦,纯乎阴矣,然必至十一月一阳生,十二月二阳生,而寒乃极。故岐伯曰:“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春夏秋冬,各差其分。”
吉凶悔吝生乎动,吉一而已。惩忿窒欲,改过迁善,善一而已。
去谗远色,贱货贵德,徳一而已。是以君子乐善,必谨其防。
居暗则能照明,居明则不能见暗。故君子静以检身,晦以藏智。
心无物而后能烛物,加之意则多事,今之法家,申韩之馀习也。
关尹子曰:“情生于心,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佛氏云明心见性,盖佛老之教皆以性为本体,心为知觉,情为发见处。其言道则窈冥昏默,不可知不可见,犹吾儒言太极也。但言心生于性,则性无顿处。
司马光谓静虑以养神,潜心以实下。盖神为主,神驰则气上升,故静虑使神安于内,则气下降,而根本实矣。杨子所谓“潜心于渊,美厥灵根”是也。
阴阳不测之谓神,天地之神也。在人则心为神,阴阳之会也,生理具乎此矣。
偶阅历天道南行、东行等说,因思其义盖取月建三合,旺月取摹,馀月取旺也。
杨文懿公守陈,天庭有黑子七,宛类北斗。宋文公及陈白沙皆面有七黑子。相书谓面无善黡,岂足据耶?
昔宋儒陈同甫于宋淳熙戊戌春上孝宗书有云:“丙午丁未岁,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明年艺祖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真宗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极盛之时。又六十年而神宗即位,国家之事于是一变。又六十年遂为靖康之祸。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天道六十年一变,可不有以应其变乎?”盖劝孝宗乘丙午丁未以恢复有为也。其于戊申又上书云:“乙巳丙午之间,虏人非无变乱。”故又云:“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验,而再冒万死以自陈,实以宗庙社稷之大计,不得不决于斯时也。”
愚按:人臣告君,惟当匡之以义,不当眩之以天数也。
古今文体不同,同归于实。理,实理也,事,实事也,载之以辞则至文也。岂必曰韩欧不足学,吾其班马,班马不足学,吾其左氏、《檀弓》,左氏、《檀弓》又不足学,吾其简奥如《易》,聱牙如《盘庚》。体制拘而识趣寡也,误哉!且著述与应酬不同,著述尚宏深,发明大道,不为徒作,应酬惟取达意斯已矣。或乃殚心力,效古书篇为之,情实何有?
元帝为太子,谏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怒谓汉道杂王霸,奈何纯任德教。此盖以德教为王,刑名为霸,非惟不知王,亦不知霸也。王者性仁义,霸则假之以济其私。虽尧舜之圣,不能弛刑,刑者义之用,所以辅仁德者。仁之施,所以行义,非王偏任德,霸偏任刑也。宣帝深刻寡恩,似义非义而害仁,下于霸者也。元帝优柔不断,似仁非仁而害义,则嬖幸用事,斨贼忠贤,无可言矣。乃徒以数赦为煦煦之仁,曾谓儒者之用如是哉!
门人记明道之言,要须察识。如云天地中无物不有,何尝有心拣别善恶,一切涵容覆载。若善者亲之,不善者远之,则物不与者多,安得为天地?按此言君子存心公恕,兼包并蓄则可,若当事任,进贤退不肖,或和如春,或肃如秋,时乃天道,恶恶不严,则好善不笃。明道告君欲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正是此意。后人不知,乃倡为调停之说,正邪并用,而正人卒受其害,可叹也。
传称孔子厄于陈蔡,七日藜羹不糁,而弦歌鼓舞不绝。子路讥其无耻,孔子解之,更瑟而弦。此不知君子者也。君子于琴瑟以动荡其和平之音,虽困极不易,固有之矣,而其所以乐者不在是也。如以瑟为乐,舍瑟将何乐乎?在厄难而逾乎其素,则不情,虞从者之疑而强焉以宁众,则近诬。是皆动乎内者也,夫子不为也。或曰:孟氏门人不闻以礼乐器自随,何也?曰:有之,无因故不及。
或问:《宋史》如何?曰陋。自唐以来竞尚润笔,以扬亲之美为孝,修《元史》者皆登之,事无奇特,则杂鬼卜妖妄以骇听闻,皆可删也。《唐书》经欧、宋二公手笔,故事增于日,文省于前,此作史要法。脱脱等不知此义,故《宋史》冗而陋。然则有善不书可乎?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则书,关名贤名臣言行则书,自馀泛泛,略之可也。
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壮伟,其失骋,汉之文华瞻,其失缓,东汉而下无取焉。
文学之用微矣。搜遗抉隐,组绘葩丽,琢字句,炫故实者,其华也。质任坦素,黜巧不事,镇重如崇岳,瀞深如巨汇,如车徒数万,董以渠帅,部分整峻,望之神慑而意阻者,其大体也。中和内融,包钜烛微,探贤圣之秘,启天地之藏,〓濆盈旁溢,而不可御者,其精实也。上士务实,大体从之,下士务华,实斯病焉。《易》《书》《诗》《礼》《春秋》之文,实宏而体备,足乎内而盎乎其外者也。
水阴也,阴宜静,而水体则动。火阳也,阳宜动,而火体则伏。火以气为用,微之显也。水以质为用,静之动也。故君子柔贵能行,刚贵藏用。宋之盛时,居台谏者为人所疏,其后台谏之门挥汗成雨,一徙它局,可张爵罗,风俗媮薄甚矣。
文内多缀古人姓名,自昔讥为点鬼簿。然孟子称王豹绵驹华周杞梁,太史公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撰《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此类甚多,岂足为訾?文之要有四,曰理也,气骨也,典也,实也。若夫为奇为怪,为藻为丽,文多而用寡,特组缋之小巧耳。
或曰:先祖,人鬼也,鬼则不神,外神威灵,故民媚而畏之,是不然。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祇人鬼皆阴阳之灵,吾之精诚随感而应,内外一也。夫孝,百行之首也。能孝必能敬身,能敬身则能事人,能事人则能处物我而无间,处物我而无间,则能与神明合矣。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此理之至微者也,非仁人孰能知之?或曰:古者祭祀不祈,祸福自我,神何预焉。曰:祀者致吾诚而已,徼福妄也,淫祀谄也。《礼》曰百顺之谓福,致吾所祀,顺之至也,而冀鬼神我私,惑也。天道福善祸淫,能敬必有福。曰:福固可祈乎?曰:礼有六祈,周公祈代武王之死,何暇论理之有无?若弃人道而委命于巫祝,则谬矣。
声音与政通,风淳则语多浑朴,虽文彩未足,不害为真率。若《击壤》之歌,《康衢》之谣是已。风漓则语多雕刻,譬之剪彩镂冰,徒炫姿媚,若徐庾温李之类是已。况才有工拙,德有浅深,感有顺逆,酌文质之中,适节奏之宜,以不失乎性情之正,则存乎其人焉。
师保之任,在于辅养君德,镇躁消邪。故《卷阿》称君德曰“岂弟”,称其得贤曰“冯翼孝德”,老成重厚之风,可想见矣。萧望之谓张敞材轻,非辅导之器,真知言哉。
礼乐,由心生者也。性情之德,情之中和也。礼以道中,神明生焉,乐以导和,协气流焉。验诸身心日用之间,而礼乐之全体可知矣。中也者,敬以直,内之体乎?和也者,义以方,外之用乎?
吴临川元仁宗时进司业,乃损益程文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为教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于《易》《书》《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可谓勤矣。然在今世,书籍议论满天下,不患不知,患不能行,诚不如象山之学得曾子三贵遗意。
荆公《洪范传》论五行一段,言五行于物,水为精,火为神,木为魂,金为魄,土为意。又曰:“神从志从,意志致一之谓精,唯天下之至精,为能合天下之至神,精与神一不离,则变化在我而已。”此虽出于通玄修真等书,而与持志养气之说相表里,小用之则生气运行,大用之则制天下之务,皆此志也。
杨文懿公传云:“圣门之学,以精思力践为要,博文强记,辅此而已。”真名言哉。
韩柳文。按韩文篇篇气象广大,不为私小偏徇之言,皆关天下之故,最得《春秋》之旨。柳则精矣,而伤于刻削,其气象大不如韩。近世惟王守溪得韩文宗旨。
昔人云天下之美不得两兼,实美者无好花,花艳者无佳实。故富于文辞者,其家必贫,富于赀货者,其子必不肖,天也,亦人也。然工文辞则志有所专而利轻,故贫,饶货财则心有所恃而过多,故不肖。虽然贫者所以成之,恃者所以败之,莫非天也。
皋陶明刑弼教,成天下之大业,六蓼乃其后也,为楚所灭,时适然尔,岂足议刑官无后哉!子羔卒免于难,于公庆延于世,厚德之报固如此,欧阳子泷冈阡之文祖之。
杨慈湖云:“董仲舒告其君曰愿设诚于内,而致行之。谓诚岂可设,设则非诚,仲舒尚不明己之心,何以启君之心。”愚按,仲舒正谊明道之言,卓然非诸儒所及。设之一字,恐非本文,疑是致字之误,其致行“致”字衍文耳。
东莱云:“孟子深斥杨墨,以其似仁义也。”同时如唐勒景差辈,浮词丽语,未尝一与之辨,道不同故也。讲正学而务辞章,岂曰儒哉!
圣人之心湛然与神明通,学者洗心,日进乎高明,神其几矣。诗曰:“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言神之体物,可畏如此。祭以交神,特暂时事,君子因之以日澡其德,故尤谨乎致齐。
黄庭坚《道院赋》谓江西惟筠州独不嚚讼,然与南康、庐陵、宜春三郡并蒙恶声。是宜春旧以嚚讼闻,今则惟庐陵为甚。是在长民者化之有要,上喜讼则讼愈多。追摄不体,株连蔓引,乃申于上曰某到官问囚几何,军犯几何,死刑几何,追赃罚几何,积谷几何。以简静为无能,计多寡为殿最,深刻者为公道,惨暴者为风力,上以是求,下以是应,孰知以无讼为贵哉?昔黄霸在颍川,八年无重囚,史称其务在成就全安之。霸设心如是,宜其无重囚也。今欲追龚黄之治,而不变申韩之习,难哉!
曾子固请令长贰自举属官一札,诚为有见,中间未必无私厚,然公论自在也。
《余襄公集》谓罗浮有五色雀,各被方色,非时不见。若士大夫将游是山,则先日群翔,寺僧以是为候。嘉靖乙酉有鸟五色集于徐闻山巅,百鸟从之,人争视以为凤,意者即此雀乎?
相关人物
钟芳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