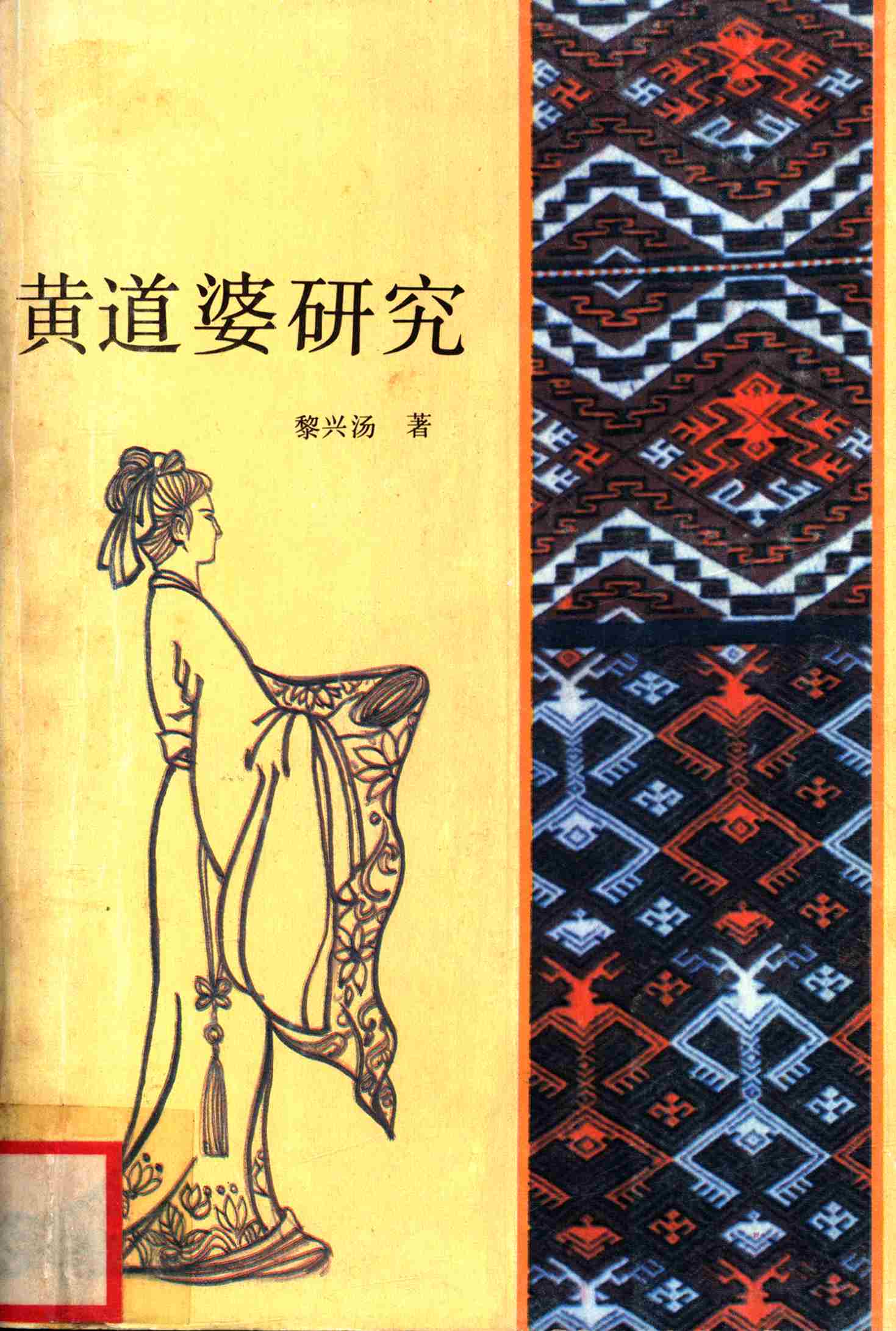内容
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她究竟向谁学艺?30多年来,史学界一直沿袭冯家昇先生的“从当地黎人学艺”说。1982年,笔者在大学毕业论文《黄道婆研究》中,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无独有偶,1990年,梁敏先生也撰文,发表了同样的见解,否定冯老先生的“从当地黎人学艺”说。然而,黄道婆不是从当地黎人学艺,而是向谁学艺呢?在这个问题上,梁敏先生与我却有分歧,他提出了黄道婆向“临高人学艺”的新观点。
说“临高人”是黄道婆学艺的师傅,梁敏先生在文中提出了如下的依据:
第一,梁敏先生认为,“临高人”是仅次于黎族的海南岛上最早居民,另一支越族的子孙;汉武帝设立儋耳、珠崖郡时《汉书》所记“民皆服布,如被单,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女子桑蚕织绩,无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猄,兵则矛盾刀木弓矢竹,或骨为镞”。这是对临高先民的记述,而不是对黎族的记述;早在汉代,临高人已能织广幅布,因珠崖太守孙幸横征暴敛,曾群起而攻郡杀幸。又据《临高县志》所记:“临高妇女业蚕桑,习纺织,……。可见,临高人织具精良,织技高明,又经过一千多年到了宋末元初,临高人的织具及其技术更高一筹了。所以,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她不是从当地织具落后且迁徙不定的黎人学艺,而是拜临高人为习艺的师傅。
笔者认为,梁先生的这些论据是值得商榷的。按梁先生所说临高人既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那么,也就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了。然则,今日还聚居在海南岛上临高、琼山、澄迈、儋县和海口市等县市的几十万的临高人,应该改为少数民族了?然而,这一观点却不为上述临高人所自认,政府也不予以承认。因而,在解放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中,上述地区的临高人均自报为“汉族”,政府也予以肯定。这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梁敏先生把史学界中没有定论的推测来作为界定严格的“民族”的依据,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据查,临高县立于隋大业三年(即公元607年),离汉武帝在海南岛立儋耳、珠崖郡时要迟717年。换言之,“临高人”的概念,于汉武帝在岛上立郡后的717年才产生。因此,不知梁敏先生何以把汉武帝在岛上立郡之时,《汉书》所记“民皆服布,如被单……”,说成是对临高先民的记述?笔者认为梁先生所说这段文字不是对海南岛上的少数民族——黎族的记述,这是对的。但也不是同梁先生所说是对汉族以外的“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的记述,而是对早在立郡前到岛上的汉族居民的记述,其理由有二:
一是从称谓上看,在我国历代的史籍中,对海南岛上除汉族以外的原住居民(少数民族),西汉时称为“骆越”(《汉书贾捐之传》),东汉时称为“里”、“蛮”(《后汉书,南蛮传》),隋代则“俚”、“僚”并称(《隋书谯国夫人传》),唐代亦普遍沿袭这种称呼。因此,梁先生所说的“临高人”果真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也就是“熟黎”的话,上述《汉书》所记岛上居民,为何不记是“骆越”,而记为“民人”?可见,梁先生所说的“临高人”不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事实上,汉族史籍中所记之“民”或“民人”,一般是指“汉民”或“汉人”,或是归顺于汉王朝的“人民”。上述称谓,是相对于不为汉朝统属的“骆越”等少数民族而言的。这点在梁先生引用的《明府志》卷二十,海黎志,村峒条就可找到例证:
“崖州黎分三种,曰生黎,曰熟黎,曰生熟各半黎。生黎者,即乾脚歧之类也……环居五指山下,与人民隔绝,不为人害。熟黎者归化既久之黎也,饮食衣服,与人民同,维束发于顶,其俗未改,日往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其户口编入图甲……。生熟各半者谓可生熟黎也,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崖州黎人如此者十居其七,且与民杂处,黎峒中有民人,民村中有黎人,不能分其畛域,约计三种黎人其众多于民人一倍。”从这段历史记载,显然看出史籍所载的“民”、“民人”、“人民”、“民村”、是指“汉民”、“汉人”、“汉村”、“汉族人民”。所以上述《汉书》所记之“民”当不是梁先生所说的汉族以外的“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而是指早在汉武帝在岛上立儋耳、珠崖两郡之前,已到达了海南岛上的汉族居民。
其二,从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史来看,《汉书》地理志所记之“民”,早在西汉,即公元前110年之前,已经有了先进的农业、畜牧业、纺织业和铁器铸造业。他们“种禾稻苧麻,女子蚕桑织绩”,“民皆服布,如被单”且养有“五畜”,“男子耕农”,还能制造“矛盾刀弓”等兵器。可见,其生产力是极为发达的。从历史上来看,能有这么进步的生产力,在西汉时代的海南岛上,除了汉族以外,其它少数民族(黎族或算是另一支越族的子孙——“临高人”)是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的。比如黎族暂从古之分(“生黎”“熟黎”“生熟各半黎”),在宋元时代,除极少部分的“熟黎”之外,绝大部分的黎族尚处于落后的原始社会形态之中,过着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生活,直到解放初期,在五指山腹地还停留着原始合亩制的社会组织,刀耕火种,生产力极为原始落后。因此,怎么能说,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或早在西汉)时代的岛上的黎人或“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即“熟黎”,能有上述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呢?所以,《汉书》的这段记述是指早在汉武帝在岛上立郡州之时,已到达了海南的汉族先民。
又,梁先生引用《临高县志》有关临高“妇女业蚕桑,习纺织……”的条文和运用汉代珠崖太守孙幸横征暴敛广幅布,激起“临高人”攻郡杀幸一事,作为证明此时崖州“临高人”,“织具精良,织技高明”的依据,这也是不妥的。其原因很简单:
第一,《临高县志》所记“业蚕桑,习纺织”之妇女是居住在海南岛西北部临高县等地真正的临高汉人。梁先生所要论证的是在海南岛南部崖州的所谓“临高人”即“熟黎”。试问,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何以相提并论?这不是在逻辑上变换了概念?再说,梁先生在大作的开头就叙述了自己亲眼所见以及史书和外国人、古人笔下的黎族妇女们“不事蚕桑”,使用极为简单、原始的纺织工具,已断定黄道婆不是向工具落后且迁徙不定的黎人学艺,为什么后来又说黄道婆是向织具精良的“临高人”即“熟黎”学艺呢?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纺织史话》考证,汉武帝末年,珠崖太守横征暴敛广幅布,激起民愤攻郡杀幸一事,是在海南南部的崖城。然而,梁敏先生却认为是在海南北部的琼山县东潭村(不说此地离临高县有多远),然则,离海南南部的崖州有几百里之遥,即使是那里的“临高人”会织广幅布,但史书记载“黄道婆少沦落崖州”,而不是“少沦落琼州”,她怎么会跑到琼山县向那里的“临高人”学习呢?这岂不有悖于历史记载?
第二,梁先生借以立论的依据是,他还以为“临高人”除秦以前已大量迁入海南岛外,还有一些可能是后来陆续迁往的,隋高祖赐冼夫人以临振县汤沫邑1500户是在今崖县;(唐)振州(今崖县)的主要居民都是“临高人”的先民;“熟黎”并不是真正的黎族,除少部分从征至此的两广人和亡命的闽广人外,可能大多数都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即“临高人”;“由于过去人们都认为海南岛‘非汉即黎’,故把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也当作黎族,称之为‘熟黎’以讹传讹,黄道婆从黎人学艺就这样流传下来。”
那么,梁先生借以立论的上述论据真实性如何?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去看看。
关于“临高人”是不是崖州的“主要居民”。
梁先生把隋高祖赐给冼夫人的临振县汤沫邑1500户说是在今崖县即唐时振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理由有四:一是从建置看,据清·张巂主编的《崖州志》,崖州历史沿革表载“梁陈时,大同中置崖州于废儋耳地(按:可见地域与过去儋耳一样广大)属扬州,司刺史,六年折西南地置临振郡,领县五,其二延德、宁远即今(清)崖州地”,这里方志十分清楚地记载,梁大同六年把崖州西南地方立一个临振郡,管辖五个县,其中延德和宁远两县即今崖县地。可见终隋之际,海南岛南部崖城地没属临振县。而属延德宁远两县旧地。当然,临振县汤沫邑1500户也就不在隋时延德,宁远两县境内,也就不在唐时振州,或宋时崖州境内。二是从户籍来看,《崖州志》卷七经政志二,户口条记“唐振州,旧领县四,户819,口2821。”依梁先生所说隋高祖所赐临振县汤沫邑1500户是在临振县(今崖县)境内,那么,不算外地迁入和自然出生人口,光隋时所赐1500户到了唐代那680户怎不见了呢?能说得过去吗?三是从《辞源》所记来看,“汤沫邑”是天子赐给诸侯的封邑,邑内收入供诸侯做汤沫(即沫浴)之用。汤沫邑又叫朝宿邑,是朝见时食宿之处。礼王制,记“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沫邑在天子之县内。”可见,“汤沫邑”是在“天子之县内”的“朝宿邑”。所以说隋高祖赐洗夫人汤沫邑1500户不是在唐时振州或宋时崖州境内。因而这1500户即使是“临高人”,也不会是宋时崖州的主要居民。四是从崖州的居民和语言来看,据清人张巂沿革宋以前的方志《吉阳军图经》等《旧志》编纂而成的《崖州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条记:“崖州习礼仪之教,有邹鲁之风。泰泉《通志》崖语有六种,曰军语,即官语,正音,城内外三坊言之。其初本内地人仕官从军来崖因家焉,故其语尚存,而以军名。曰迈语,音与广州语相似,附城四厢及正三亚里、椰根里言之。曰客语,与闽音相似,永宁里,临川里、保平里及西六里言之(为数众多)与郡语同。曰番语,所三里言之,即回语。曰儋语,儋人隶者言之,与迈语相似。日黎语,东西黎言之,互有异同。参《旧志》”这里方志所记,崖州清代以前的主要居民有六种人:一是军人;二是迈人;三是客人;四是番(回)人;五是儋人;六是黎人。其中以操与闽音相似的客人即福建移民最多,也就是讲海南话的汉民最多。其语言,永宁、临川、保平和西六里共九里通讲,且与郡语相同。可见操这一与闽音相似的客人即福建汉族移民,在崖州六种居民中为数最多分布最广。(这一福建汉族移民,在宋元之时,棉纺织业在国内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因为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初居水南郡治所在地,再移居崖城、后出家到城西广度寺中修道。居崖30多年,主要是在崖州汉族福建广东等地移民中生活的,应该说,她主要是向这些汉族移民学习。)崖州六种居民中,唯独没有操“临高话”的“临高人”。“临高人”的概念早在隋代已形成,为何清代崖州主要居民中却没有记载?这岂不是古人故意与梁先生唱反调?不,历史就是历史,事实不是随意编造而成的。崖州历史和现实中都没有这么一种主要居民——“临高人”,这是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何以说他们是黄道婆少沦落崖州时习艺的师傅呢?岂非咄咄怪事?梁先生又做何种解释呢?对借以立论的主要证据的缺乏,他说:“熟黎,并不是真正的黎族,除少部分从征至此的两广人和亡命的闽广人外,可能大多数都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即临高人。由于在明朝中叶以后,海南岛的汉族大增,势力强盛,到处大兴修谱之风,民族歧视压迫的现象也日益增加,于是语言相通汉化程度较深的‘熟黎’(即临高人)都纷纷改为汉族”。这就是现在崖县、文昌等地没有或很少‘临高人’的缘故。这种解释能使人信服吗?
崖州历史上,不,整个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由于汉族势力的强盛,强迫少数民族同化的事也时有发生。但是,做为一个民族的形成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是多方考验的。民族一经形成,它有相当强大的自身凝聚力,并非容易拆散灭绝。一个民族大兴修谱之风,只能增强本民族意识而对于另一民族来说很难并吞,相反,只能把民族界限和同一血缘更明确地固定下来。再说,崖州汉族大兴族谱,断然不会跑到远离汉民村庄的黎峒中,到异族中,到不同的血缘和姓别的黎人中去扩大自己的亲属队伍,而只是把同一血缘亲属关系的成员登记在册罢了,古今如此。即使有熟黎想加入汉族某一姓氏的族谱之中,也应遵循其是否同一血缘姓氏原则。不说一个民族(熟黎)整个儿加入另一个民族(汉族)中去,就是汉族中的一个姓氏,企图加入汉族的另一个姓氏中去,也是不允许和不易做到的。当然,历史上曾发生过同化现象。有一些同汉人同姓又同居一处的黎人,天长日久,有可能改族而被同化。但这仅是个别在自愿的前提下发生的自然同化现象,要把“临高人”即“熟黎”整个儿从黎族中并吞过来,列入汉族若干姓氏的族谱中去,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也是绝对无法实现的。历史上,汉族统治阶级曾对少数民族有过歧视和压迫,但多次激起他们的反抗,难以达到目的。充其量只能迫使他们迁离汉族远一些,并没有整个民族屈服而汉化的事实发生过。否则,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除了有一个汉族之外,还有50多个少数民族,有的民族人数仅有几千甚至几百人,却没有被同化,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要是说,明代中叶以后,海南大汉族主义严重,那么汉人聚居且开发较早的岛西、北部的儋州、琼州等地,即今临高、琼山、澄迈、儋县、海口等县市汉区,比之岛南的崖州即今乐东三亚等黎族自治县市、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为什么居住在岛西、北部的汉人聚居之地的少数临高人,所谓“熟黎”,却没有被汉化过去呢?以致今日临高人数量之多,和临高语仍然流行?相反,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崖州,做为“主要居民”的“临高人”所谓“熟黎”,为什么却被这少数的汉人“统统汉化”过去了呢?这能说得通吗?
照梁先生说来,“临高人即熟黎”,是在明朝中叶以后才都纷纷改为汉族的了,那么自此而后,崖州本地应没有“临高人”,也就没有“熟黎”了吗?然则,在梁先生引用的《明府志》卷二十,海黎志,村峒条却有:
“崖州黎分三种,曰生黎,曰熟黎,曰生熟各半黎”。这其中的“熟黎”既是“临高人”,为何还不改为汉族?事实上,直到清人纂写的文献上,有关“黎分生熟,生熟各半”的记载,比比皆是,为什么明清以后“熟黎”还继续在方志中出现呢?可见“熟黎”并非即“临高人”,也并非在明中叶后就都改为汉人。只有到了解放后,人民政府尊重黎族,才改变了过去封建统治阶级对黎族的这一蔑称。
要是说,明中叶以后,“临高人即熟黎”,才都改为汉族,那么在明中叶以前,在黄道婆宋末元初沦落崖州之时吧,“临高人”当是没有改为汉族的了。那么,明中叶以前的宋末元初之时,为何崖州方志却不见“临高人”是崖州主要居民或黄道婆向“临高人”学艺的历史记载?可见,梁先生的推断“熟黎并不是真正的黎族——可能大多数都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和“熟黎即临高人”的论点和论据都是不符合崖州的历史事实的。
关于“临高人”是不是“熟黎”的问题。
梁敏先生说汉化程度较深的“熟黎”即“临高人”。这一说法和论据对吗?请看史籍如何记载:
“崖州黎分三种:曰生黎,曰熟黎,曰生熟各半黎……熟者归化既久之黎也,饮食衣服,与民人同,惟束发于顶,其俗未改……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
——《明府志》卷二十,海黎志
“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黎,海南四郡〓土蛮也。〓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傍,号黎人,内为生黎,外为熟黎……闽裔值风水荡去其货,多入黎地耕种不归……熟黎之地,始是州县。”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熟黎,旧传其先本南恩藤梧高化州人,多王符两姓,言语皆彼处乡音,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迫掠土黎,深入荒僻,占食其地,长子育孙……外连居民,慕化服役,固名熟黎。”
——明·嘉清·载璟《广东通志》初稿
“熟黎峒落稀少,踞城五七里许,外即生黎所居,不啻数百峒”
——宋·赵汝适《诸藩志》卷下
“黎,今儋崖琼万岛上蛮也。岛之上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傍,号黎人。内为生黎,外为熟黎,熟黎分隶诸州,耕作省地,供税役,生黎所居绝远,外人不能迹,不供税役;熟黎贪狡,两广福建之奸人亡命逃居其间……”
——明章汉《图书编》
“熟黎之乡,半为湖广福建奸民亡命及南恩藤梧高化之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名称酋长。”
——清·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一十九,列传二百0七广西土司三,广东琼州府附。
“黎母山,高大而隆,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兽居其中,熟黎环之,熟黎能汉语,尝入州县贸易,暮则呜角结队而归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熟黎,其先本南恩藤梧高化诸州人,多王符二姓,言语犹仍其旧,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迫掠土黎,深入荒僻,占据其地,人多从之,以故闽楚之亡命,视为逋逃薮”。
——清雍正郝玉麟《广东通志》
卷五十七,岭蛮志,俚户
“崖州居民……熟黎多李赞皇之裔,有宰相阁,中塑赞皇象,峨冠博带,犹存唐时宰相之衣冠。”
——清·刘世馨《粤屑》
从上述史籍记载来看,封建文人把“黎”分“生”、“熟”“生熟各半”三种,其成因:一是以居住在五指山、黎母山、七指岭内外;汉化程度深浅;离州郡远近;是否隶属于州郡等为划分的依据。这是黎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是因民族发展的差异而形成的。二是除了从“生黎”逐渐开化演变过来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族早到黎地而被黎化过来的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个体,包含有“值风水荡去其货的闽商;”“南恩藤梧高化州之征夫”;“福建亡命之奸民”;“闽楚逋逃”之人;崖州贬臣“李赞皇之后裔”等等,大多数为汉裔黎籍的崖州较早居民。
但这些以汉裔为主的外族黎籍之居民,笔者估计,他们早在宋元以前就已经流落到黎地,他们没能把早在宋元时代,闽广已优先于全国发展起来的棉纺织技术带入黎地,所以,熟黎纺织业与本地土黎一样简陋和原始,远远没有《临高县志》所记之临高人的纺织业发达。这也是“熟黎”并非即“临高人”的又一个例证。大量的史籍表明,梁先生借以立论的依据“临高人即熟黎”,也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综上所述,“临高人”既不是“熟黎”,更不是“崖州的主要居民”。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她习艺的师傅不是“临高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
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她既不是如冯家昇先生所说“从当地黎人学艺”,又不是依梁敏先生之见“拜临高人为师”。那么,她究竟向谁学艺?我的回答是,她主要向宋末元初纺织业优先于全国发展起来的崖州福建汉族移民学习。笔者在《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居处新证》、《黄道婆为什么能成为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少沦落崖州究竟向谁学艺》等篇章中均有系列的论述。
1991年6月28日于乐城
说“临高人”是黄道婆学艺的师傅,梁敏先生在文中提出了如下的依据:
第一,梁敏先生认为,“临高人”是仅次于黎族的海南岛上最早居民,另一支越族的子孙;汉武帝设立儋耳、珠崖郡时《汉书》所记“民皆服布,如被单,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女子桑蚕织绩,无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猄,兵则矛盾刀木弓矢竹,或骨为镞”。这是对临高先民的记述,而不是对黎族的记述;早在汉代,临高人已能织广幅布,因珠崖太守孙幸横征暴敛,曾群起而攻郡杀幸。又据《临高县志》所记:“临高妇女业蚕桑,习纺织,……。可见,临高人织具精良,织技高明,又经过一千多年到了宋末元初,临高人的织具及其技术更高一筹了。所以,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她不是从当地织具落后且迁徙不定的黎人学艺,而是拜临高人为习艺的师傅。
笔者认为,梁先生的这些论据是值得商榷的。按梁先生所说临高人既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那么,也就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了。然则,今日还聚居在海南岛上临高、琼山、澄迈、儋县和海口市等县市的几十万的临高人,应该改为少数民族了?然而,这一观点却不为上述临高人所自认,政府也不予以承认。因而,在解放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中,上述地区的临高人均自报为“汉族”,政府也予以肯定。这又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梁敏先生把史学界中没有定论的推测来作为界定严格的“民族”的依据,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据查,临高县立于隋大业三年(即公元607年),离汉武帝在海南岛立儋耳、珠崖郡时要迟717年。换言之,“临高人”的概念,于汉武帝在岛上立郡后的717年才产生。因此,不知梁敏先生何以把汉武帝在岛上立郡之时,《汉书》所记“民皆服布,如被单……”,说成是对临高先民的记述?笔者认为梁先生所说这段文字不是对海南岛上的少数民族——黎族的记述,这是对的。但也不是同梁先生所说是对汉族以外的“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的记述,而是对早在立郡前到岛上的汉族居民的记述,其理由有二:
一是从称谓上看,在我国历代的史籍中,对海南岛上除汉族以外的原住居民(少数民族),西汉时称为“骆越”(《汉书贾捐之传》),东汉时称为“里”、“蛮”(《后汉书,南蛮传》),隋代则“俚”、“僚”并称(《隋书谯国夫人传》),唐代亦普遍沿袭这种称呼。因此,梁先生所说的“临高人”果真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也就是“熟黎”的话,上述《汉书》所记岛上居民,为何不记是“骆越”,而记为“民人”?可见,梁先生所说的“临高人”不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事实上,汉族史籍中所记之“民”或“民人”,一般是指“汉民”或“汉人”,或是归顺于汉王朝的“人民”。上述称谓,是相对于不为汉朝统属的“骆越”等少数民族而言的。这点在梁先生引用的《明府志》卷二十,海黎志,村峒条就可找到例证:
“崖州黎分三种,曰生黎,曰熟黎,曰生熟各半黎。生黎者,即乾脚歧之类也……环居五指山下,与人民隔绝,不为人害。熟黎者归化既久之黎也,饮食衣服,与人民同,维束发于顶,其俗未改,日往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其户口编入图甲……。生熟各半者谓可生熟黎也,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崖州黎人如此者十居其七,且与民杂处,黎峒中有民人,民村中有黎人,不能分其畛域,约计三种黎人其众多于民人一倍。”从这段历史记载,显然看出史籍所载的“民”、“民人”、“人民”、“民村”、是指“汉民”、“汉人”、“汉村”、“汉族人民”。所以上述《汉书》所记之“民”当不是梁先生所说的汉族以外的“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而是指早在汉武帝在岛上立儋耳、珠崖两郡之前,已到达了海南岛上的汉族居民。
其二,从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史来看,《汉书》地理志所记之“民”,早在西汉,即公元前110年之前,已经有了先进的农业、畜牧业、纺织业和铁器铸造业。他们“种禾稻苧麻,女子蚕桑织绩”,“民皆服布,如被单”且养有“五畜”,“男子耕农”,还能制造“矛盾刀弓”等兵器。可见,其生产力是极为发达的。从历史上来看,能有这么进步的生产力,在西汉时代的海南岛上,除了汉族以外,其它少数民族(黎族或算是另一支越族的子孙——“临高人”)是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的。比如黎族暂从古之分(“生黎”“熟黎”“生熟各半黎”),在宋元时代,除极少部分的“熟黎”之外,绝大部分的黎族尚处于落后的原始社会形态之中,过着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生活,直到解放初期,在五指山腹地还停留着原始合亩制的社会组织,刀耕火种,生产力极为原始落后。因此,怎么能说,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或早在西汉)时代的岛上的黎人或“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即“熟黎”,能有上述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呢?所以,《汉书》的这段记述是指早在汉武帝在岛上立郡州之时,已到达了海南的汉族先民。
又,梁先生引用《临高县志》有关临高“妇女业蚕桑,习纺织……”的条文和运用汉代珠崖太守孙幸横征暴敛广幅布,激起“临高人”攻郡杀幸一事,作为证明此时崖州“临高人”,“织具精良,织技高明”的依据,这也是不妥的。其原因很简单:
第一,《临高县志》所记“业蚕桑,习纺织”之妇女是居住在海南岛西北部临高县等地真正的临高汉人。梁先生所要论证的是在海南岛南部崖州的所谓“临高人”即“熟黎”。试问,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何以相提并论?这不是在逻辑上变换了概念?再说,梁先生在大作的开头就叙述了自己亲眼所见以及史书和外国人、古人笔下的黎族妇女们“不事蚕桑”,使用极为简单、原始的纺织工具,已断定黄道婆不是向工具落后且迁徙不定的黎人学艺,为什么后来又说黄道婆是向织具精良的“临高人”即“熟黎”学艺呢?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纺织史话》考证,汉武帝末年,珠崖太守横征暴敛广幅布,激起民愤攻郡杀幸一事,是在海南南部的崖城。然而,梁敏先生却认为是在海南北部的琼山县东潭村(不说此地离临高县有多远),然则,离海南南部的崖州有几百里之遥,即使是那里的“临高人”会织广幅布,但史书记载“黄道婆少沦落崖州”,而不是“少沦落琼州”,她怎么会跑到琼山县向那里的“临高人”学习呢?这岂不有悖于历史记载?
第二,梁先生借以立论的依据是,他还以为“临高人”除秦以前已大量迁入海南岛外,还有一些可能是后来陆续迁往的,隋高祖赐冼夫人以临振县汤沫邑1500户是在今崖县;(唐)振州(今崖县)的主要居民都是“临高人”的先民;“熟黎”并不是真正的黎族,除少部分从征至此的两广人和亡命的闽广人外,可能大多数都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即“临高人”;“由于过去人们都认为海南岛‘非汉即黎’,故把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也当作黎族,称之为‘熟黎’以讹传讹,黄道婆从黎人学艺就这样流传下来。”
那么,梁先生借以立论的上述论据真实性如何?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去看看。
关于“临高人”是不是崖州的“主要居民”。
梁先生把隋高祖赐给冼夫人的临振县汤沫邑1500户说是在今崖县即唐时振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理由有四:一是从建置看,据清·张巂主编的《崖州志》,崖州历史沿革表载“梁陈时,大同中置崖州于废儋耳地(按:可见地域与过去儋耳一样广大)属扬州,司刺史,六年折西南地置临振郡,领县五,其二延德、宁远即今(清)崖州地”,这里方志十分清楚地记载,梁大同六年把崖州西南地方立一个临振郡,管辖五个县,其中延德和宁远两县即今崖县地。可见终隋之际,海南岛南部崖城地没属临振县。而属延德宁远两县旧地。当然,临振县汤沫邑1500户也就不在隋时延德,宁远两县境内,也就不在唐时振州,或宋时崖州境内。二是从户籍来看,《崖州志》卷七经政志二,户口条记“唐振州,旧领县四,户819,口2821。”依梁先生所说隋高祖所赐临振县汤沫邑1500户是在临振县(今崖县)境内,那么,不算外地迁入和自然出生人口,光隋时所赐1500户到了唐代那680户怎不见了呢?能说得过去吗?三是从《辞源》所记来看,“汤沫邑”是天子赐给诸侯的封邑,邑内收入供诸侯做汤沫(即沫浴)之用。汤沫邑又叫朝宿邑,是朝见时食宿之处。礼王制,记“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沫邑在天子之县内。”可见,“汤沫邑”是在“天子之县内”的“朝宿邑”。所以说隋高祖赐洗夫人汤沫邑1500户不是在唐时振州或宋时崖州境内。因而这1500户即使是“临高人”,也不会是宋时崖州的主要居民。四是从崖州的居民和语言来看,据清人张巂沿革宋以前的方志《吉阳军图经》等《旧志》编纂而成的《崖州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条记:“崖州习礼仪之教,有邹鲁之风。泰泉《通志》崖语有六种,曰军语,即官语,正音,城内外三坊言之。其初本内地人仕官从军来崖因家焉,故其语尚存,而以军名。曰迈语,音与广州语相似,附城四厢及正三亚里、椰根里言之。曰客语,与闽音相似,永宁里,临川里、保平里及西六里言之(为数众多)与郡语同。曰番语,所三里言之,即回语。曰儋语,儋人隶者言之,与迈语相似。日黎语,东西黎言之,互有异同。参《旧志》”这里方志所记,崖州清代以前的主要居民有六种人:一是军人;二是迈人;三是客人;四是番(回)人;五是儋人;六是黎人。其中以操与闽音相似的客人即福建移民最多,也就是讲海南话的汉民最多。其语言,永宁、临川、保平和西六里共九里通讲,且与郡语相同。可见操这一与闽音相似的客人即福建汉族移民,在崖州六种居民中为数最多分布最广。(这一福建汉族移民,在宋元之时,棉纺织业在国内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因为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初居水南郡治所在地,再移居崖城、后出家到城西广度寺中修道。居崖30多年,主要是在崖州汉族福建广东等地移民中生活的,应该说,她主要是向这些汉族移民学习。)崖州六种居民中,唯独没有操“临高话”的“临高人”。“临高人”的概念早在隋代已形成,为何清代崖州主要居民中却没有记载?这岂不是古人故意与梁先生唱反调?不,历史就是历史,事实不是随意编造而成的。崖州历史和现实中都没有这么一种主要居民——“临高人”,这是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何以说他们是黄道婆少沦落崖州时习艺的师傅呢?岂非咄咄怪事?梁先生又做何种解释呢?对借以立论的主要证据的缺乏,他说:“熟黎,并不是真正的黎族,除少部分从征至此的两广人和亡命的闽广人外,可能大多数都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即临高人。由于在明朝中叶以后,海南岛的汉族大增,势力强盛,到处大兴修谱之风,民族歧视压迫的现象也日益增加,于是语言相通汉化程度较深的‘熟黎’(即临高人)都纷纷改为汉族”。这就是现在崖县、文昌等地没有或很少‘临高人’的缘故。这种解释能使人信服吗?
崖州历史上,不,整个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由于汉族势力的强盛,强迫少数民族同化的事也时有发生。但是,做为一个民族的形成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是多方考验的。民族一经形成,它有相当强大的自身凝聚力,并非容易拆散灭绝。一个民族大兴修谱之风,只能增强本民族意识而对于另一民族来说很难并吞,相反,只能把民族界限和同一血缘更明确地固定下来。再说,崖州汉族大兴族谱,断然不会跑到远离汉民村庄的黎峒中,到异族中,到不同的血缘和姓别的黎人中去扩大自己的亲属队伍,而只是把同一血缘亲属关系的成员登记在册罢了,古今如此。即使有熟黎想加入汉族某一姓氏的族谱之中,也应遵循其是否同一血缘姓氏原则。不说一个民族(熟黎)整个儿加入另一个民族(汉族)中去,就是汉族中的一个姓氏,企图加入汉族的另一个姓氏中去,也是不允许和不易做到的。当然,历史上曾发生过同化现象。有一些同汉人同姓又同居一处的黎人,天长日久,有可能改族而被同化。但这仅是个别在自愿的前提下发生的自然同化现象,要把“临高人”即“熟黎”整个儿从黎族中并吞过来,列入汉族若干姓氏的族谱中去,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也是绝对无法实现的。历史上,汉族统治阶级曾对少数民族有过歧视和压迫,但多次激起他们的反抗,难以达到目的。充其量只能迫使他们迁离汉族远一些,并没有整个民族屈服而汉化的事实发生过。否则,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除了有一个汉族之外,还有50多个少数民族,有的民族人数仅有几千甚至几百人,却没有被同化,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要是说,明代中叶以后,海南大汉族主义严重,那么汉人聚居且开发较早的岛西、北部的儋州、琼州等地,即今临高、琼山、澄迈、儋县、海口等县市汉区,比之岛南的崖州即今乐东三亚等黎族自治县市、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为什么居住在岛西、北部的汉人聚居之地的少数临高人,所谓“熟黎”,却没有被汉化过去呢?以致今日临高人数量之多,和临高语仍然流行?相反,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崖州,做为“主要居民”的“临高人”所谓“熟黎”,为什么却被这少数的汉人“统统汉化”过去了呢?这能说得通吗?
照梁先生说来,“临高人即熟黎”,是在明朝中叶以后才都纷纷改为汉族的了,那么自此而后,崖州本地应没有“临高人”,也就没有“熟黎”了吗?然则,在梁先生引用的《明府志》卷二十,海黎志,村峒条却有:
“崖州黎分三种,曰生黎,曰熟黎,曰生熟各半黎”。这其中的“熟黎”既是“临高人”,为何还不改为汉族?事实上,直到清人纂写的文献上,有关“黎分生熟,生熟各半”的记载,比比皆是,为什么明清以后“熟黎”还继续在方志中出现呢?可见“熟黎”并非即“临高人”,也并非在明中叶后就都改为汉人。只有到了解放后,人民政府尊重黎族,才改变了过去封建统治阶级对黎族的这一蔑称。
要是说,明中叶以后,“临高人即熟黎”,才都改为汉族,那么在明中叶以前,在黄道婆宋末元初沦落崖州之时吧,“临高人”当是没有改为汉族的了。那么,明中叶以前的宋末元初之时,为何崖州方志却不见“临高人”是崖州主要居民或黄道婆向“临高人”学艺的历史记载?可见,梁先生的推断“熟黎并不是真正的黎族——可能大多数都是另一支越人的子孙——临高人”和“熟黎即临高人”的论点和论据都是不符合崖州的历史事实的。
关于“临高人”是不是“熟黎”的问题。
梁敏先生说汉化程度较深的“熟黎”即“临高人”。这一说法和论据对吗?请看史籍如何记载:
“崖州黎分三种:曰生黎,曰熟黎,曰生熟各半黎……熟者归化既久之黎也,饮食衣服,与民人同,惟束发于顶,其俗未改……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
——《明府志》卷二十,海黎志
“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黎,海南四郡〓土蛮也。〓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傍,号黎人,内为生黎,外为熟黎……闽裔值风水荡去其货,多入黎地耕种不归……熟黎之地,始是州县。”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熟黎,旧传其先本南恩藤梧高化州人,多王符两姓,言语皆彼处乡音,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迫掠土黎,深入荒僻,占食其地,长子育孙……外连居民,慕化服役,固名熟黎。”
——明·嘉清·载璟《广东通志》初稿
“熟黎峒落稀少,踞城五七里许,外即生黎所居,不啻数百峒”
——宋·赵汝适《诸藩志》卷下
“黎,今儋崖琼万岛上蛮也。岛之上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傍,号黎人。内为生黎,外为熟黎,熟黎分隶诸州,耕作省地,供税役,生黎所居绝远,外人不能迹,不供税役;熟黎贪狡,两广福建之奸人亡命逃居其间……”
——明章汉《图书编》
“熟黎之乡,半为湖广福建奸民亡命及南恩藤梧高化之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名称酋长。”
——清·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一十九,列传二百0七广西土司三,广东琼州府附。
“黎母山,高大而隆,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兽居其中,熟黎环之,熟黎能汉语,尝入州县贸易,暮则呜角结队而归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熟黎,其先本南恩藤梧高化诸州人,多王符二姓,言语犹仍其旧,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迫掠土黎,深入荒僻,占据其地,人多从之,以故闽楚之亡命,视为逋逃薮”。
——清雍正郝玉麟《广东通志》
卷五十七,岭蛮志,俚户
“崖州居民……熟黎多李赞皇之裔,有宰相阁,中塑赞皇象,峨冠博带,犹存唐时宰相之衣冠。”
——清·刘世馨《粤屑》
从上述史籍记载来看,封建文人把“黎”分“生”、“熟”“生熟各半”三种,其成因:一是以居住在五指山、黎母山、七指岭内外;汉化程度深浅;离州郡远近;是否隶属于州郡等为划分的依据。这是黎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是因民族发展的差异而形成的。二是除了从“生黎”逐渐开化演变过来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族早到黎地而被黎化过来的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个体,包含有“值风水荡去其货的闽商;”“南恩藤梧高化州之征夫”;“福建亡命之奸民”;“闽楚逋逃”之人;崖州贬臣“李赞皇之后裔”等等,大多数为汉裔黎籍的崖州较早居民。
但这些以汉裔为主的外族黎籍之居民,笔者估计,他们早在宋元以前就已经流落到黎地,他们没能把早在宋元时代,闽广已优先于全国发展起来的棉纺织技术带入黎地,所以,熟黎纺织业与本地土黎一样简陋和原始,远远没有《临高县志》所记之临高人的纺织业发达。这也是“熟黎”并非即“临高人”的又一个例证。大量的史籍表明,梁先生借以立论的依据“临高人即熟黎”,也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综上所述,“临高人”既不是“熟黎”,更不是“崖州的主要居民”。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她习艺的师傅不是“临高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
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她既不是如冯家昇先生所说“从当地黎人学艺”,又不是依梁敏先生之见“拜临高人为师”。那么,她究竟向谁学艺?我的回答是,她主要向宋末元初纺织业优先于全国发展起来的崖州福建汉族移民学习。笔者在《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居处新证》、《黄道婆为什么能成为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少沦落崖州究竟向谁学艺》等篇章中均有系列的论述。
1991年6月28日于乐城
附注
①上海黄式搅车图1
见王祯《农书》卷二十一。
相关人物
黄道婆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