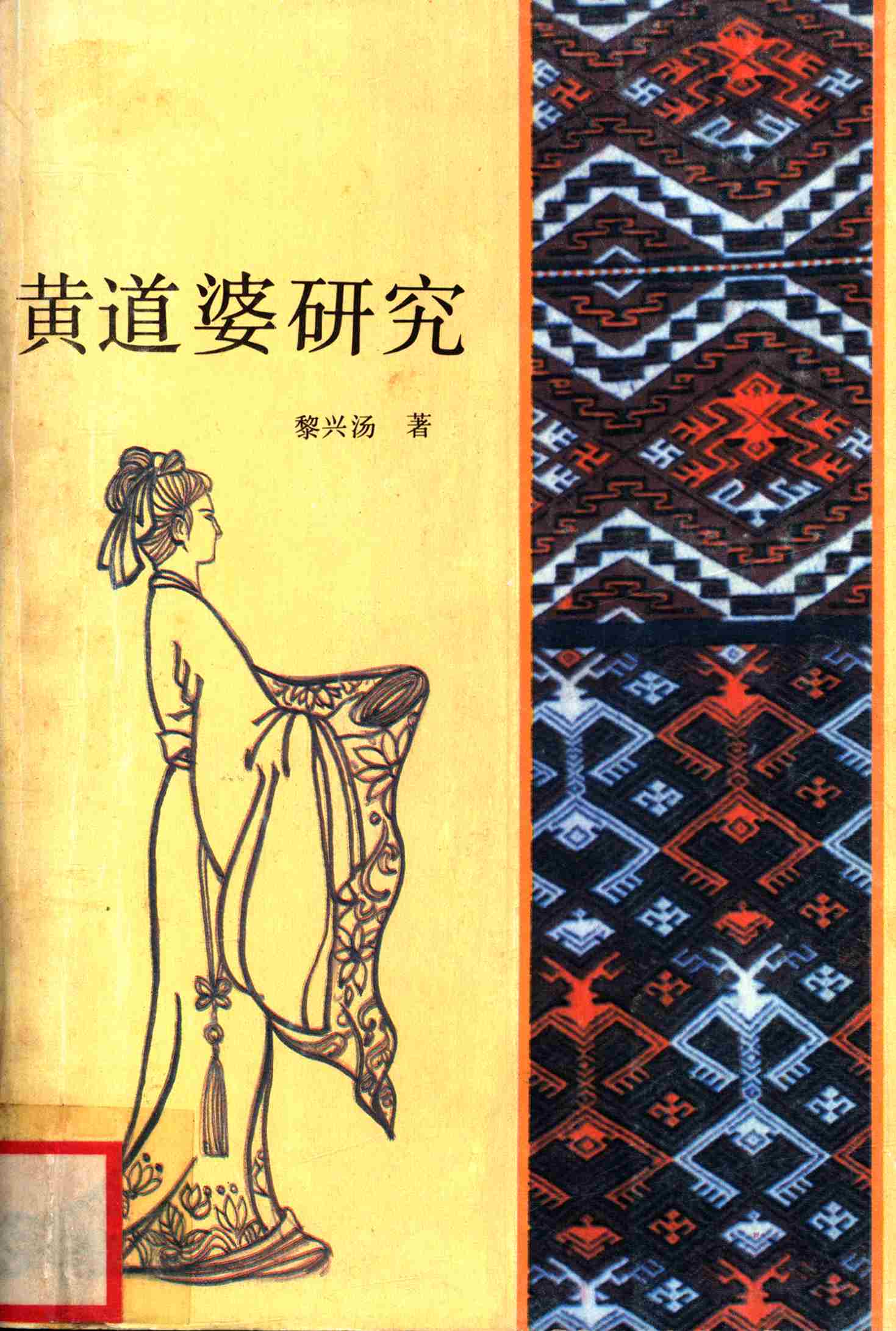内容
黄道婆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这是史学界早已定论的历史人物,难得的一位女科学家。然而,1989年9月上海召开的黄道婆专题学术讨论会,收到了联邦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研究所研究员库恩博士撰写的《关于13世纪的黄道婆的传说——从纺织能手到种艺英雄》的论文,他却提出了“黄道婆或许不是做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的重大怀疑。
库恩博士认为,“黄道婆或许不是做了改进的纺织专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性的看法,”但他已向人们,从本质上重新评价黄道婆的历史功勋,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他从根本上否定史学界对黄道婆已经定论的评价。
笔者对史学猎涉不深,唯独对崖州的历史人物黄道婆、李德裕颇感兴趣。1980年我还在大学二年级之时,已开始了对黄道婆的研究,先后走遍崖州、上海,到黄道婆当年可能生活过的地方实地调查,还走访了广州、北京、上海等地研究黄道婆的专家、学者们,并搜集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年来,我在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黄道婆的生平(即黄道婆的真实姓名和生卒年月;黄道婆的籍贯和族属;黄道婆少年沦落崖州的原因;黄道婆在崖州的居处;黄道婆为什么能成为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在崖州向谁学艺;黄道婆为什么晚年从崖州返回松江等方面)撰写了九篇专论,力图对黄道婆的生平作一个系统而翔实的论述。黄道婆的历史贡献是伟大的,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也是应该永久地得到肯定和褒奖的。如果对黄道婆“做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的这一重大问题,还有疑问,那么黄道婆将被蒙上历史的尘埃,她的形象也难再熠熠生辉,光照千秋。中国人民将失去一位长期受人敬仰、爱戴的女科学家。黄道婆的名字也将退出历史的科学的殿堂,从教科书上消逝。那么,一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尤其是棉纺织技术史,又如何去写呢?为了有益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让黄道婆的光辉形象永放光芒,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扬光大黄道婆的改革创新精神,因是,我写下这篇文章,想就库恩博士的怀疑问题,同他本人商榷,请教于库恩博士和其他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以求对黄道婆获得公正而一致的历史评价。
库恩博士提出了“黄道婆或许不是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的怀疑之后,他推测“称黄道婆是纺织专家的中国传说是怎样形成的?”他列举出两个原因(一个是松江府地区的实际起因;另一个是类似中国“第一个养蚕家”螺祖传说的后期起因),披露了他对黄道婆的怀疑,有具体如下三点:
一是,怀疑“黄道婆的祖籍在松江府地区”。他认为,黄道婆回到的“祖籍松江府地区”只是“想象中”的,不是事实上的。
二是,怀疑黄道婆少年沦落崖州学艺,晚年返回松江传艺的生平经历。他认为这是来自“据说是”和“想象中”的“祖籍松江府地区”的“中国传说。”被尊为“先棉”的黄道婆传说,类似被奉为“先蚕”的螺祖传说的后期起因一样,也“有可能从未存在过。”
三是,怀疑“黄道婆是棉纺织专家”。认为“黄道婆乃是一位普通妇女”,对她的“创造发明能力”和在松江传授的“新技术”,特别加上双引号。这也就从根本上对黄道婆的历史功绩产生了怀疑。
那么,库恩博士上述三点怀疑是否有足够的依据,言之成理呢?让我们逐个去推敲和斟酌。
一、关于黄道婆的祖籍。对黄道婆祖籍在松江的怀疑,不是自库恩博士而始。早在1985年,崖州的周振东同志就提出了“黄道婆崖州人也”①的新观点,他更超过了库恩博士的怀疑,到了完全否定黄道婆祖籍在松江的地步。
周振东同志借以立论的主要史文依据是陶宗仪《辍耕录》的记述:“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鸟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人造捍、弹、纺、织、之具”。周振东同志认为,陶宗仪所记“黄道婆自崖州来”,祖籍只能在崖州。②
然则,王逢《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有序”却明确记载:“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这又如何解释呢?笔者已就黄道婆的祖籍问题写了一篇专论,与周振东同志商榷,这里暂且不赘。仅就两个方面阐明我的看法:
其一,从语言文学的角度看,周振东同志以陶宗仪所记“黄道婆自崖州来”作为怀疑黄道婆祖籍松江进而得出“黄道婆崖州人也”的结论,这是不对的。请看:
《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即“过去我出征的时候,杨柳摇拽,现在我回家的时候,飞雪稠密。”这里,出征“离家”用“往矣”,退役“回家”用“来思”为辞。
《乐府诗集·孤儿行》:“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这里,孤儿所说到“回家”,都用“来归”为辞。
《金瓶梅·词话》第八回《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伙计道:“大官人(西门庆)吃了一日酒,到晚拉众朋友往院里去了。一夜通没来家。你往那里寻他去。”这里,(西门庆)“来家”,当做“回家”用,这“来”与“往”方向相对,是当“回”用。
从这些实例可以见出,古代汉语的“来”和现代汉语的“来”是有显著变化的。其实,只要你留心一下《说文解字注》、《辞海》、《辞源》以及古代的文学作品,对“来”字的本义、引申义及用法就十分明确:“来”,本义为“麦”,后引申为“行来之来”,“凡来之属皆称为来”。“来”作由彼至此,由远至近的趋向动词,与“去”、“往”相对,常当做“回”、“还”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来”在古汉语中有特指和通用:特指,即古代诸候之女回娘家省亲用“来”,又妇女因被丈夫遗弃或夫亡而返回娘家用“来归”为辞;通称,即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对男女老幼从外地“回家”都通称为“来家”。可见,陶宗仪记述“黄道婆自崖州来”,恰好历史地、真实地记述了黄道婆在晚年失去丈夫之后,从崖州道观——广度寺返回娘家——祖籍松江府的特殊身世。由此看来,陶宗仪用词十分讲究,既符合古汉语的规范用法,又切合黄道婆的特殊身世。而王逢所记“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就显得平白些。因此,从“黄道婆自崖州来”而怀疑黄道婆的祖籍在松江府地区,甚至得出“黄道婆崖州人也”的结论,这在语言、文字学上是讲不通的。
其二,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看。对黄道婆祖籍在松江府地区持怀疑态度,甚至把黄道婆说成是“崖州人也”是不对的。库恩博士认为,黄道婆只是回到“想象中的祖籍松江府地区”,那么,黄道婆“现实中的祖籍”又是在哪里呢?我想,库恩博士也是说不上来的。假如说,黄道婆祖籍在崖州,那么《崖州志》、《正德琼台志》、《琼州府志》等方志或史书,为什么没有记载?既然说,“黄道婆崖州人也”,那么,她究竟是崖州何处人氏?为何连周振东同志至今也未说出确切的城镇或乡村?更未拿出文物、古迹作为佐证?
然而,“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不但王逢在《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有序”中记载,而且《松江府志》、《上海县志》、《龙华志》等史书和方志中都有历史记载。此外,松江府地区有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镇,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县龙华乡东湾村。这里,还有黄道婆安息的陵墓和十多处黄道婆祠屋。上述的历史记载和文物古迹足以雄辩地证明:“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这是勿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二、关于黄道婆的历史传说。笔者十年来搜集到的黄道婆的历史传说总共有18篇,大多数属于上海和崖州古代历史人物传说。但也有一两篇出自崖州文人之手的新编故事(这当然不属于本篇讨论的问题)。
库恩博士把黄道婆的历史传说,即作为上海第一个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先棉”的传说与“可能从未有过”的“第一位养蚕家”——“先蚕”螺祖的传说相类比,从而得出“黄道婆或许不是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的怀疑。这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呢?
严格说来,螺祖作为“先蚕”的故事应属于神话,而不是传说。黄道婆作为“先棉”的故事,则属于历史人物传说。两者有质的区别。螺祖的神话产生于远古年代,这是远古人用想象和借助想象,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经过远古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加工过的自然社会形式本身。①因此,历史学家向来认为神话是对当时历史的记录。由此观之,“先蚕”螺祖的神话是中国古代人民对当时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记录,并非是胡编乱造的,黄帝的元妃螺祖即“先蚕”也可能存在。这是其一。其二,黄道婆的传说产生于元朝以后,仅有600多年,“先棉”黄道婆的传说不属于神话,而属于历史人物传说更比“先蚕”的神话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作为社会学科的门类之一的民间文学告诉我们,民间传说是劳动人民创作的,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系的故事。传说的主人翁大都有名有姓,而且不少是历史人物。这类历史传说往往和历史的实有的事物相联系,因此,比神话具有历史的真实性。黄道婆传说,就属于这类历史传说。黄道婆传说有她真名即黄四娘;有她出生地是松江乌泥泾镇,有她的第二故乡是海南岛崖州,而黄道婆少沦落崖州,晚年回归松江,向那里人民传授改革棉纺织工具和技术的历史事实,均见诸于元人王逢《梧溪集》和陶宗仪《辍耕录》等史书和《松江府志》、《上海县志》、《崖州志》等方志上。上海龙华乡东湾村,即古之乌泥泾地,有黄道婆安葬的坟墓,有纪念黄道婆的祠屋十多处,还有以黄道婆命名的村庄——黄婆庙村。在崖州城(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西二里的城西小学内)有黄道婆.在这里修道、学艺30多年的广度寺遗址及完好保存的“黄道婆塔”(塔原名迎望塔,因塔为广度寺附属建筑物而易名)。崖州和上海民间俗重纺织,至今不但两地还保留着黄道婆改革后的制棉工具,而且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海南民族博物馆,均陈列着黄道婆的塑像和她改革过的棉纺织工具及其织物。上述有关黄道婆的文物、古迹、习俗、历史事件,都包含了某种历史的实在因素,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点。从广义上说,一切文学作品,包括神话在内,都由于这样或那样地反映了某一时期的社会现实,而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但是,历史人物传说,除了具有一般文学作品广义的历史性外,还有和历史更为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界、史学界都认为,民间历史传说,可以说是劳动人民“口传的历史”。①当然,黄道婆的历史传说,也可以说是上海和崖州人民对黄道婆的“口传的历史”。但是,由于历史人物传说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又具有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和变异性。历史传说在根据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实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时,是经过了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幻想等艺术加工的,因此,历史传说又不完全等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今人为了某种需要,对历史人物编造了一些新的故事,比如《崖州织女黄道婆》,这就不是黄道婆的历史传说,而是黄道婆故事新编了,要严格区分于大量流传于民间和少数被收入《纺织史话》、《上海风物志》等作品中的黄道婆的历史传说。这是在研究黄道婆的生平事迹时所必须注意区分和扬弃的。因为,此类“新编故事”远离了历史的真实,带有文人的主观随意性。当然,作为真正的历史人物传说,也因为是一种口传的文学,所以,它的语言和细节也是经常变动的。关于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物,常有不同的说法,比如一些黄道婆的故事,往往把想象因素和实际生活现象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把它当作历史资料使用时,必须加以鉴别,否则也会妨碍它在历史科学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当然,不能因为黄道婆历史传说中有这些成份,从而否定它们在历史学(如黄道婆研究)中的作用和价值,更不能因此而把这些历史传说与“可能从未存在过”的“螺祖传说的后期起因”相提并论,从而产生出“黄道婆或许不是做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的怀疑。
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曾说过:“如果不知道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从远古时代起,民间创作就不断地伴随着历史。”①黄道婆做为棉纺织技术革新家的历史传说,也是伴随着崖州、上海乃至中国的棉纺织史而独特地存在、沿流至今的。通过这些黄道婆传说,我们可以了解崖州、上海乃至中国棉纺织史上的一些生动内容和发展趋势。因而,那些真正的黄道婆历史传说,是可以当做信史来读的。也就是当做劳动人民的“口传的历史”来读的。
为什么人们,包括库恩博士,对黄道婆做为棉纺织技术革新家会产生一些疑问呢?我想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古代中国的官修史书(二十四史),没有或少有记载,仅见于《辍耕录》和《梧溪集》呢。然而,黄道婆在宋末元初,她只不过是一个初为流人后为道人,出身贫苦的平民百姓,也就是库恩博士所说的一位“普通妇女”罢了。她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生时所干的纺织事业亦非轰轰烈烈,只有到了死后,人们对她从崖州学习带回传授革新的棉纺织工具及其织技、织物,才慢慢认识到它们的作用和价值。至于她改进的三纺车,在当时世界上属于最先进的纺纱工具。这只有放在若大的世界和历史长河中进行比较,才发现黄道婆的“创造发明能力”和她的伟大历史功绩。而当这些贡献为后人所确认之后,她作为一位不可多得的女棉纺织技术革新家,才在人们的心目中渐渐形成。由于她生前地位的低微,仅是一位“普通妇女”或“纺织能手”,所以,官修史书没有或极少记载,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不能以此做为怀疑乃至否定黄道婆是棉纺织技术革新家的依据。相反,由于官修史书没有或极少记载黄道婆的事迹,这就使上海和崖州人民群众世代口碑相传的民间传说,显得更加珍贵了。因为,这是那里的群众对黄道婆的“口传的历史”。
做为中国的考古学家、文学家的郭沫若同志曾说过:“民间文学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学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①
马克思主义者对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历史人物、事件、传说的历史价值,给予高度的评价。郭老甚至提高到“最正确、最可贵”的程度。虽然笔者不尽有这么高的看法,但从马克思、恩格斯、高尔基、郭沫若等人对民间文艺的评价来看,把黄道婆做为“先棉”的传说,与螺祖做为“先蚕”的(神话)传说类比,从而产生怀疑,认为“黄道婆或许不是做了改进的纺织专家”,这从做为社会学科之一的民间文学的历史传说与历史关系的角度来看,是说不通的。(当然,我这里用来观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的观点,对于身居西方不同思想体系的库恩博士来说,也不必强求一致,问题不在于谁手中拿着什么样的“武器”——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而在于谁对历史事实的发现。)
三、关于黄道婆的历史功勋
黄道婆是否“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这要看她在棉纺织业方面有何历史功勋。要回答这一问题,既要了解崖州和松江当时棉纺织业的情况,更要从比较中看黄道婆从崖州学习、带回并革新过的棉纺织工具、织技、织物对松江,乃至中国人民的纺织业和生活有何作用和影响。这得让事实来说话。
闽广地区的棉纺织业:
黄道婆所处的宋末元初,闽广地区的棉纺织情况怎样?史稿:
“木棉绽出如绵。土人以铁杖碾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绵,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①
这条资料告诉我们,这时闽广之治棉技术高于长江流域(更凌驾于关陕之上)。“丽”者,就是说棉布外表美观好看,“密”者就是棉布质地经纬交织紧密而又坚实。当时能织出“丽密”的布匹来,可见其织具织技比较精良。而“闽广来者,尤为丽密”,就标志着闽广的治棉工具和技术比松江先进。
崖州地区的棉纺织业:
据《纺织史话》所载,崖州气候土壤适宜棉花种植,是国内最早的棉产区。崖州居民有六种:军人、迈人、闽人、番人、儋人、黎人。其中以居住在州治所在地——水南村、崖州城及沿海一带的“闽人”为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其次是音与广州话相似的来自南海、惠阳等地的粤人即广人;再次是从军仕官而由内地来到崖州的军人;还有从外域波斯等地来的番人,即回人;从儋州移居的儋人;以及早期来到黎地的“值风水荡去其货的闽商”、“南恩藤梧高化州之征夫”、“福建亡命之奸民”、“闽楚逋逃之人”、崖州谪臣“李赞皇之后裔”等这些汉裔黎籍的“熟黎”。这些“崖州居民,习礼义之教,有邹鲁之风。(泰泉《通志》)妇女不事蚕桑只织贝,家自耕织,士多业儒,人重廉耻。”“妇女织吉贝为斜纹花布等形”(《旧志》参《府志》)。
崖州沿海一带福建汉族移民中,至今存有大量的〓屋布,就单布、双布、高丽布、斜纹花布,美丽而坚实,又存藏有用于红、白大事的崖州绣被、大帐、小帐、桌裙(食单)等。
从以下民歌、民谣更可以反映崖州纺织业的情况:
种吉贝①
上岭劈园种吉贝,力力松头等它大;
现在寒天将要到,做衣留防冬天寒。
纺纱①
月公出来光落落,眼看庭前纺车装;
纺纱的时623,挑纱的时326。
男纺②
天上起虹弯弯弓,人拾斜纹双压双;
脚踏纺车叫嗌嗌,公爹做成妇女人。
织双布③
天上起云鹧鸪班,双布织成四支椫;
椫味四支综八付,散纱一条都艰难。
织斜纹花布④
天上起虹弯弯弓,人拾斜纹双压双;
头毛梳妆绞紧紧,屋上盖茅层压层。
又,崖州古歌——《织女叹》⑤,通过一个福建汉族移民女子之口,把崖州先进的棉纺织业的情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织女叹》第一,唱出了妇女以纺织为业的社会分工:“早起四邻鸡声乱,放脚快行近布机,机喂最亲就是侬与你,终昼终夜坐相陪,……”第二,唱出了崖州纺织的悠久历史:“初更城楼更鼓乱,把灯添油迎灯光。”崖州城初建于唐代,“城楼更鼓”反映了崖州纺织史的悠久。又从歌中所唱:先织“绫罗绸缎光见影”后见“人织斜纹依亦学”,可知当时是中国纺织史上从织丝转到织棉的这一唐宋交接时期。第三,崖州纺织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若是爹丰母亦足,不用侬劳苦日夜。”“叹侬家贫钱债紧,债主一来侬心寒。”“单双织成匹到匹,织青织红人剪衣,”“手巾织千百对,以包槟榔讨深闺。”这些歌词唱出了崖州妇女为了生计,解除家庭的贫穷,还债裁衣婚嫁之用,不得不日夜纺织,可见地位之重要。第四,崖州棉织品种类之多,技艺之高:“单布”、“双布”、“绫罗绸缎”、“斜纹花布”、“手巾”、“被面”等品类繁多,有的如“鹧鸪斑”,有的如天上彩虹,总之“织巧织奇机上装”,织物“光光平平满面花”。目前,崖州60岁以上的汉族福建移民妇女都工于纺织,有的今天还存有一套旧时的先进手工纺织工具,还织造“单布”、“双布”、“斜纹花布”、“高丽布”、“葫椒粒花布”、“指甲花布”、“柳条花布”等。崖州这些织具和织物跟黄道婆家乡松江上海地区的织具和织物极其相似,早在唐代振州延德郡(即宋时的崖州),就以“斑布”和“食单”做为献给皇帝的贡品。可见在黄道婆沦落崖州之前,海南岛崖州的植棉及棉纺织技术是走在全国前头的。因而,库恩博士怀疑黄道婆从崖州学到了植棉及制棉的“先进技术”,带回松江传授,这恐怕是出于对崖州历史情况不太了解的原因吧?仰或是,库恩博士也认为“崖州是黎族人民聚居之地”,而黎族从古至今都使用原始的纺锤和踞织机,没有黄道婆式的先进的棉纺织工具的原故呢?史学界过去把黄道婆说成是“从当地黎人学艺,”并带回“黎族先进的纺织工具”在松江传授。这一结论,因与崖州黎族的纺织情况不符,的确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库恩博士也不例外。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她究竟向谁学艺,是向崖州织具简单而原始的黎族学习,还是向织具先进的汉族移民学习?我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元初松江纺织业情况。
晚年客居松江的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名日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案即闽广),初不踏车椎弓之制,卒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
文献所记元初黄道婆返回松江之前,这里的制棉工具只有“线弦竹弧”,连较为简单的轧棉工具——铁轴或铁杖都没有。因此,去籽只有用十指摘除。而棉籽都藏在棉英内部,包裹层层,为数又多,光凭十指之力很难把棉籽摘除。因手指摘籽极易疲劳,故功效很低。可见,此时松江制棉工具和方法很原始,远远地落在崖州的后边。
黄道婆从崖州带回松江传授并改进的棉纺织工具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史学界一向认为是王祯《农书》中所记的元代制棉工具。但是,库恩博士在分析了王祯的《农书》中对轧花机改进和弹弓描写后提出,这两种工具定已在王祯生活的时代普遍地使用了。由此推测“黄道婆或许不是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这种看法是否妥当呢?据查,黄道婆生于1245年,约卒于1306年前。①王祯生于1271年,卒于1368年。他们仅是相差26岁左右的同时代人。黄道婆于元贞间(1295—1297)年返回松江;王祯《农书》也是在元贞间即1296年开始着手准备,直至1314年才写成。也就是说,王祯《农书》是在黄道婆返回松江传授和改进纺织技术和纺织工具之后的第18年才完成。《农书》全书37卷,13.6万多字,插图306幅,全书分为《农桑通决》、《百谷谱》、《农器图谱》,其中《农器图谱》主要介绍元代及以前的包括纺织工具在内的农业生产工具。它将百余种器械绘成图谱并附有说明。这是一部图文并茂,集农器图谱之大成的农业科技书籍。因而,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应囊括元初松江的织具,也就是应把黄道婆带回和革新过的纺织工具收录进去。所以,中国史学界一向认为黄道婆带回松江的制棉工具,即陶宗仪所说的“捍、弹、纺、织之具”,在王祯《农书》中得到了记载。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外,笔者于1988年10月在上海搜集到的上海博物馆丛书之一的徐蔚南撰写的《上海棉布·纺织工具》一书,对黄道婆传授、改革后的上海织具,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兹以上述两书为黄道婆改革后的上海织具(简称上海黄式),与崖州汉族福建移民之织具(简称崖州汉式)进行比较,让我们从中看看黄道婆是否做了“改进的纺织专家”:
据《农书》所载,“捍”,即搅车,这是去籽的制棉工具。《上海棉布·纺织工具》介绍。“搅车用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轴端俱作掉拐,轴末柱窍,不透,两人掉拐,一人喂上棉英,二轴相轧,则籽落于内,棉出于外”。
这种搅车,形状结构、原理、使用方法与崖州沿海汉族福建移民使用的碾籽机基本相同。但崖州汉式底部是用一整块阔木板作底,二方柱只在左边柱上通一轴,右边柱上通一碾手(即掉拐)。只能供一至二人同时操作,而上海黄式则可供二至三人同时操作。说明上海黄式是在崖州汉式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的。这种搅车比过去“用手剖去籽”,要“功利数倍”。上海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二人可当八人。这种搅车,比美国人维特尼发明的轧棉机早了500多年。这是黄道婆的一项革新的成果,要是没有“创造发明力”,能做得到吗?
“弹”即弹弓和弹椎,这是用来弹松棉花的制棉工具。
上海黄式弹弓,《上海棉布·纺织工具》载:“以竹为之,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控以线弦,用弹棉英,如弹毛之法,务使结者开,实者虚,假其功用,非弓不可”。
上海黄式弹椎,《上海棉布·纺织工具》记:“弹花椎,圆木,长六、七寸,经二、六寸,两端大而中间略细,弹者手握细处,褚谱置花衣中,以椎击弦作音,则花衣〓散如雪,成熟花衣”。
崖州汉式弹弓弹椎,基本上与上海黄式相同。所不同点,崖州汉式弹弓用木作,其头宽些,接触棉絮就少些,而上海黄式用竹作,接触棉絮就多些。
原松江地区弹棉用的是“线弦竹弧”没有指出有弹弓,而是“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可见黄道婆从崖州返回松江之前,松江府地区,“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弹棉是多么艰难,靠“线弦竹弧”,“振掸成剂”。只有黄道婆从崖州带回并改进了弹弓、弹椎之后,在上海棉纺织工具中,才出现了类同崖州汉式的弹弓和弹椎。这是黄道婆的又一贡献。
“纺”即纺车。这是纺纱用的制棉工具。崖州汉式使用的是单脚踏纺车。上海纺车则是三脚踏纺车。王祯《农书》记载:“木棉纺车,其制比麻纺车颇小,夫轮动弦转,莩随之,纺人左手握棉筒,不过二三,绩於莩,牵引渐长,右手均,俱成紧缕,就绕上。……此即纺车之
用”。
《上海棉布·纺织工具》对纺车作了如下描述:“以木为,有背有足,别刻木附于背上为插椗之颈,凿三孔焉,以受椗,而设轮于背之中,以熟牛皮一条,俗乎皮弦者,环绕轮上,复以横木,名踏条(崖州汉式叫脚踏横担)尖其端,以贯轮之窍,以一端置车之足(崖州汉式脚踏横担不着地,置在足竖柱上)纺者将两足布踏条上,抑扬运之。左手持条子三条,(崖州持一条棉筒)粘椗捎而牵引焉,右手持一短竹,俗呼押纱棒,将纱附于椗”。这就是黄道婆改进的脚踏三纺车。其构造,形状,原理、完全与崖州汉式相同,所不同的是崖州汉式脚踏纺车只能纺单,而上海黄式纺车能纺三。这是黄道婆的一大改革成果。三纺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比英、美、德早四五百年。马克思曾在谈及18世纪的德国时说到,要找到一手能纺双纱的工人,如同找一个双头人一样不易。①然而,在德国18世纪做不到的事情,在中国13世纪已由黄道婆做到了,并且教会了1000多名妇女。从单纺车改进为三纺车,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这不就是黄道婆的一大发明吗?黄道婆不愧为“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王祯《农书》写成于黄道婆返回松江后的第18年,记载了“国初时”没有踏车之制,而此时已出现的“三纺车”,徐蔚南《上海棉布·纺织工具》,在推崇黄道婆之后,也记载了她改进三纺车。这二部史籍,连同《辍耕录》和《梧溪集》一起,是黄道婆“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的历史依据。由于三纺车的出现,促使松江地区纺纱率大大地提高,棉纺织业突飞猛进,使该地区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一伟大历史功绩是为世人所瞩目的,岂能视而不见?“黄道婆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是来不得半点怀疑的。
织布工具主要有织机,包括梭子、子、布扣,综等织具。
上海黄式的梭子、子、布机、和综。据《上海棉布·纺织工具》所记如下:
梭子腹扁阔,中空,钻窍于两端,削细竹茎为心,镶以牛角,便利穿掷”。子,即绕上线的莩筵,用于装梭织布。
布扣,“削篾编成,以薄而匀密为佳”。
综,“综头,棉纱线染绛为之,或二页或四页”。
崖州汉式和上海黄式的子、布扣、综,其名称、形状、构造,功用和使用方法都是完全相同的。说明黄道婆从崖州带回的这些织具,至今还原原本本地保留着。
布刀,崖州的打纬织布工具。木作,长60CM,一边形似斧背,背厚3.5CM,长20CM,在中间凿槽长17CM,深2CM,以装子,另一边平直斜刃如刀,因名布刀。布刀正中靠刀刃2.5CM处钻一孔,把线从子上抽出布刀旁。织布时脚踏椫木,织口张开,就把布刀穿入,同时从子上拉出线,用扣框拉近织口,再用布刀把纬线打实。崖州汉式布刀和上海黄式梭子,虽然叫法不同,形状也有扁长之分,但梭子和布刀的构造,原理都相同,同样内装一个子,同时具有来回穿线打纬的功用,使用方法都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它们是同一种类,有着历史的接承和发展关系。
“织”主要是指织机。上海黄式织机和崖州汉式织机,都是脚踏提综高架斜织机。《上海棉布·纺织工具》记载:
上海织机,“四足如床,前低后高,支片木于首,织者坐焉,名坐机板。次立两耳,以八棱木横贯之,可旋转以盘布,曰布轴。次有扣门,空其中,以装布扣。扣门左右,各设木焉,厥形如股,可屈可伸。外悬综头,以棉纱染绛为之,或二页或四页,立木于综头两旁,上设机焉,形如廿字,名鸦鹊,垂四绳于鸦鹊,以下分属于综头。又于综头之下设两木板,阔仅容足,坎地置之,名踏脚。系两绳于踏脚上,以分属于综头,织者左右足选踏,鹊鸦为之一府一仰,而综头之页,选随升降,布经之穿综头者,遂逐页分开,可容梭织矣。后足上设横木焉,以卷布经于中间,两头穿木为枝格状,如行马者,俗名滴花,总谓之布机。”
上海黄式布机与崖州汉式布机同属于脚踏提综高架斜织机。形状相似,构造、原理相同,使用方法一样。有些部件的名称相同:如布轴、坐板、扣门、布扣、综头、踏脚等主要部件的名称都原原本本地保留着。这说明黄道婆改革后的上海织机和崖州汉式现在还保存的布机是基本相同的,有着接承和发展的历史亲缘关系。
使用上海织机,上海织妇一般每天可织布一匹。古时以宽二尺二寸、长二丈为一匹,那么,上海妇女使用上海织机一日能织出二丈多的布匹。而崖州汉族织妇一日能织半脚布,①即一日能织一丈八尺。稍比上海妇女每天织布量少二尺左右,而却比崖州黎族妇女使用踞织机日织布量三尺,高达六倍以上!
通过上述比较,可见黄道婆从崖州带回并革新过的纺织工具的情形:她使松江从“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到有了“捍弹纺织之具”。这在技术交流方面,黄道婆立下了一个不小的功劳。她把崖州的单纺车改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三脚踏纺车。这不论对松江,还是整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纺纱技术,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是一项很了不起的科技发明!这是黄道婆在改进纺纱工具方面的伟大的历史功绩。
元初的松江,黄道婆传入和改进崖州的织具,相应地也传入和改进崖州的织技。然而,陶宗仪只记“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得其法”,其具体工序和流程怎样?史籍未载,后人也没深入考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何谓“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笔者参阅辞书,对照纺织流程,认为应包括如下内容:
“错纱”:“错”,有“塗饰”、“杂乱”、“相互交错”、“更色”之意。总起来说,“错纱”,包括①把素纱染成各样(杂)的色调。②把色纱互相交错或更迭地进行整经上架。③把有色的纬线(染色或原色)织入或镶嵌进经线中,使经线与纬线组成美丽的花纹图案。“错纱”是染纱、牵经、织纬中都涉及到的常用纺织技术。
“配色”:“配”,有“匹对”、“媲美”、“分发”、“分派”之意。“配色”,就是把已有色的线,“分发”,使之“匹对”而“媲美”。这是织造花布时所必须考虑和运用的技术,在牵经和织纬时,要依照预定织造的花布种类或图案进行配备各种色纱叫配色。
“综线”:丝缕经线与纬线交织曰“综”。“综”,又有“总集”、“聚合”、“治理”之意。“综线”即治理经纬,把经线和纬线交织,使用脚踏提综和用手穿纬织布的方法。
“挚花”:“挚”,有“悬持”、“提起”、“缺”、“绝”、“刻”的意思。“挚花”应有二种:①用手在花机上提花,或用脚踏布椫,使鸦鹊俯仰带动综头,从而提起经线,再按所织布匹种类花纹穿织纬线的织造花布的技术。②印花或括花。印花即在木板上刻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再蒙在素布上,用七彩擦印之。另一种为括花,即先以蜡染花纹,再把布浸入染缸中过色,再括去蜡就成括印花。
——上述“错纱、配色、综线、挚花”的技术,在崖州汉式和上海黄式的织造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应用,而崖州汉式和上海黄式织物又具体而形象地体现这种技术。
那么,上海黄式和崖州汉式的织物是怎样的?上海黄式织物,陶宗仪只记“被、褥、带、帨,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再没有具体的记载。而王祯《农书》也没记录,幸好徐蔚南的《上海棉布》一书详细地描述了。
至于崖州汉式织物,王逢只记“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灿花草”。笔者因是崖州人,对崖州的织物目睹耳闻,不但在上述崖州民歌中有历史的记载,而且在崖州沿海的汉族村民中,60岁以上的妇女,50年代还大批地纺纱织布,甚至去年笔者还在黄流镇抱本村,看到了一位叫黄六娘的妇女,在织造崖州花布。至今那些精致的“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的崖州布被、大帐、小帐、食单、斑布,在沿海一带汉族福建移民中存藏很多。兹把徐蔚南《上海棉布》的种类与笔者收集到的崖州棉布进行比较。从中看看黄道婆到底做了哪些历史性的贡献。
上海棉布织物有四大类:扣布、标布、稀布、高丽布。扣布和标布又叫小布和大布。它们与崖州汉式的单布和双布(也叫小布和大布)是一个样的。何谓扣布?扣即布扣,也叫布蔻,是捎簿竹蔑纵向排列,以长方木框镶嵌而成的织具,用于整经时控制经线的疏密,织布时把纬线拉近织口。这是上海黄式和崖州汉式脚踏提综斜织机上的主要部件之一。布扣有长短之分,当然织物也有宽狭、大小之分。初时,通常用布扣织出的布匹称为扣布,也叫小布。上海稀布也同崖州的双布一样称为大布,甚至长宽和价钱都差不多。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上海黄式有一大布种——“高丽布”。它的名称、织法,规格完全和崖州的“高丽布”一个样。这说明道婆把崖州的高丽布、织具和织技原原本本地传入松江。高丽布源出于朝鲜。崖州是古城,梁陈时已立郡,唐代较兴盛,海上交通发达,与高丽接触频繁,有人员和贸易往来。因此高丽的纺织技术也传入崖州。元初间再由黄道婆带回松江,成为那里的布种之一。这也是黄道婆的一大历史贡献。
此外,上海黄式织物的花布品种绝大部分与崖州汉式的花布相同。比如,上海黄式和崖州汉式花布中,都有花纹呈辫状,斜向排列成一条条纹路的斜纹花布;有经纬蓝白纱间格织成如芦扉形的芦纹布;有分别用蓝纱和白纱间格织成的蓝白柳条花布;有经纬如方胜者,即方形的彩胜,由二个斜方形部分迭合而成的斗纹花布,又称象眼布或指甲花布。尤其是,上海黄式织物中,有一种经过加工的花布叫药斑布的,崖州汉式叫斑布或盘斑布的,其制作的方法是一个样的。这种药斑布或斑布有两种制法;一种叫做括印花,乃以灰粉渗胶,涂作花样,随意染何色而去其粉者即成。另一种叫刷印花,就以木板刻作花卉人物等,也即“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等形,再以布蒙板而用五色刷之,就成华彩如画的花布。这种斑布,早在唐代振州的延德郡(也就是宋时的崖州西南沿海汉族移民集居地)已全国闻名,为皇帝所青睐,被做为贡品入朝。因此黄道婆元初得以学习并带回松江去传授。
由于纺织工具的改进,织技的提高,织物的增多,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首先乌泥泾人织成的“被褥带帨,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元代已称“布,松江者佳”。①到了明代成化间,乌泥泾的布匹流传到皇宫中,为宫女们所喜爱。乌泥泾人又织皇家御用衣袍,上有龙凤、斗牛等花纹,用大红、真紫、赭黄等染色。皇室购买这种衣料,加上官吏中饱糜费,一匹甚至有贵达白银一百两的。②正德年间,松江的“线绫、三棱布两物衣被天下。”……最好的布称“尖”,有“龙华尖”(龙华即黄道婆家乡),还有“松江大布”。又明万历时以丝作经而以棉纱作纬的云布,制品极精,花样既新,色亦娇媚,每匹价至三金,四方争购之。又府城所制漆纱布,大佳,贩鬻邻郡,号称松江方巾。③到了清初(公元1644—1911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所出产的棉布,市场遍及全国。这时,松江各地“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④。
由于棉纺织业的发达,上海成为棉花布匹的贸易地,北方各县在此设局,专门收购,名曰“坐庄”。广东、福建等地的大商人,在二三月间,载着糖霜来到上海出卖,到了秋天就在上海买好花衣布匹运回去。当时“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每晨到午,小东门外为市,负贩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焉。”①当时松江出产的布匹,还销到欧洲各国,其中最大的买主要算英国。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初,更扩大到十多万匹。英国商人指定只要苏松一带出产的紫花布。这种紫花布作成的裤子,和杭绸做成的衬衣,曾成为英国绅士风行一时的时髦服装。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土布穿暖了他们的祖先。
上述资料表明,由于黄道婆的热心提倡,不倦传授,大胆革新,使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产品远销国内外。可见,黄道婆的影响之广,作用之大,难怪她去世六七百年,人们还一直纪念着她,缅怀她的丰功伟绩。
黄道婆作为“改进的棉纺织专家”,除了陶宗仪《辍耕录·黄道婆》和王逢《梧溪集·黄道婆祠有序》这两篇历史文献有所记载之外,清·包世臣撰写的《上海黄道婆祠》的碑志,是一篇绝好的史料。兹摘录于下以资佐证:
“黄婆(黄道婆别称),自崖州附海舶到吾沪乌泥泾,教民纺织,棉始为布(这是黄道婆被尊为“先棉”的原因),化行若神,法流松太(纺织方法之先进,传播之神速),近世秦(陕西中部、甘肃东部)、陇(甘肃一带)、幽(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并山西太原一带),转传治法,在悉产棉布(可见黄道婆传授的纺织方法,在国内传播之广,影响之大)。然松太(松江、太仓地区)所产,卒为天下甲,而吾沪所产,又甲于松太。山梯海航,贸迁南北(即越山过海产品畅销南北)。黄婆之殁(去世)也,乡里醵(聚钱)葬而祠之,递迁递毁。乐利于人。肸蠁无所,有功则祀之,谓何常用为恧。(肸蠁,即分布。恧,惭愧。黄道婆乐意为人民谋利益,分布无所不到,有功则被人民纪念,有什么惭愧呢?)今兹幸以沙船运漕,懋著成绩,而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沙船,即一种平板货船,遇沙不搁。漕,从水路运送粮。懋著,即成绩显著)。海壖产布,厥本黄婆(即松江上海地区棉初为布源在黄道婆)。饮水思源,不仅生养吾民人己也(黄道婆的恩泽很广,不仅松江上海人获利,还波及全国,乃至国外)。
夫以棉布之利,百蚕丝而无主祀之神,异日秩及无文,举先棉之祀,舍黄婆其谁与归(秩,俸禄。举,推举。祀,祭祀。舍,捨,不要。归,归到一处。也就是说,棉布给人的利益有百倍于蚕丝,却没有主祀之神,今后要推举“先棉”纪念,除了黄道婆,谁能称得上呢?可见黄道婆为“先棉”的传说,是建立在她的伟大历史功勋之上的,并非虚说)。诸君子推本海运,归美黄婆,固非无说(许多道德高尚的人、把海运的兴起归结到黄道婆带来的好处上,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然国家承平二百年,徒以河事多故,偶举海运著绩也扰暂。至于松太两属,方壤不过二百里,岁供编银百余万两,额漕六十余万石,而因缘耗羡,以求利者称是。其地土高水下,风潮日至,沙松不保泽。虽得木棉,种于闽广,差宜土性,而车弓未作,莫利民用,农不偿本,久必罢废(虽然从福建广东得木棉种于松江,但由于土性不太适宜,而又没有轧车、纺车、弹弓等,便利于人们的纺织工具,生产成本得不偿失,长久以往必然废止了)。追呼急迫,驯致流亡则虑财赋之邦,鞠为瓯脱矣(追,回溯,急,紧急。迫,逼迫。邦,国家。鞠,养育。瓯脱,国土完整。虑,担扰。这就是说,回溯紧急严重的关头,顺服善良的人民,也不得不逃亡出外,即担扰国家的财政难以养育)。而今数百年来,红粟(富足的粮食)运入太仓者几当岁会十二,朱提(银子)输司农者(即主管钱粮的部门)。当岁会亦且二十而一。而土民仍得各安生业,称东南乐土(乐土,即安乐之地),其以宦游至者,又皆絜驾齿肥(那些作官或游览到此地的人,又都因为这里富饶而并列在此居住),长育子孙,凡所取给,悉出机杼(凡是取得的丰足,全部出自纺织业),以此程黄婆之功(用这些计算黄道婆的功劳),其仰关国计盈虚者(这是上关系到国家大计的满和空的问题),较之海运,奚啻什佰而已哉(与海运比较黄道婆的功劳,那里仅仅是百分之十而已呢)!……故为之铭,其辞曰:
天怜沪人(上海人),乃遣黄婆,浮海来臻(到)。沪非谷土(谷地喻绝境),不得治法,棉种空树(因为不掌握制棉的方法,棉花才空长在树上),惟婆先知,制为奇器,教民治之(只有黄道婆最先掌握制棉的知识,制造出先进的棉纺织工具,教给上海人民制棉的方法)。踏车去核,继以椎弓,花葺条滑(就用搅车去除棉籽,接着用弹椎和弹弓弹松棉花,再把棉花制成平滑的棉筒)。乃引纺车,以足助手,一引三纱(于是运用纺车,用脚踩动纺轮,使之轮动弦转,腾出手来、使一手能纺出三)。错纱为织,粲如文奇,风行郡国(把纱染色,并把有色的经纬线交接成鲜明得就象有花纹的丝织品一样美丽,象风一样地传遍国内)。昔苦讥寒,今乐腹果,租赋早完(过去苦以讥寒交迫,现在丰衣足食租赋早已完成)。昔苦逋负,今乐盈止,以安子妇(过去因为负债太重而逃亡在外,今天由于富足而可以安居乐业,使孩子和媳妇们都安稳地过好日子)。我衣我食,五百年所,远矣明德(500多年来,我沪人穿的吃的,都是黄道婆带来的,多么长远的恩德啊)!
综上所述,黄道婆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她的历史功绩,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黄道婆回到松江,传播和革新了崖州先进的制棉工具。她使松江“初不踏车椎弓之制”,到有了“捍、弹、纺、织之具”。她在崖州先进纺织工具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搅车,比美国人维特尼发明的轧车早500年;她在崖州单脚踏棉纺车的基础上,又研制出三脚踏棉纺车。这二种工具,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去籽和纺纱的工具。这是黄道婆的伟大发明创造,不朽的历史功绩。
二是,黄道婆返回松江传授并革新崖州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使松江地区的人民,从“棉种空树,不得治法”,到去籽,弹花,纺纱、整经、织布,都有了一套先进的工艺流程。又经过她潜心研究,大胆改造,使原先崖州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各得其法”,能织造出“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的织物。这种新技术、新方法“化若神行,风靡郡国”。黄道婆在制棉技术的革新和传播方面又立下一大历史功绩。
三是,黄道婆对棉纺织工具和技术的革新,对元清两代,松江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为社会增加了财富,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社会的向前发展。
因为织具、织技的改革,生产力大大提高。既使松江地区从原先“昔苦讥寒,农不偿本”,“近呼急迫,驯致流亡”到日织万匹,大量的粮食、白银输入松江地区,人民“生活富足”,“岁既就殷”,“今乐腹果”,500多年来,成为丰衣足食的“东南乐土。”这不啻于救活了原先水深火热要外出逃荒的千千万万的子民百姓!
同时,由于织具、织技的改革,产品的增多,使松江地区从“半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中,挣脱困境。不仅能自给自足,而且有了大量的花衣、棉纱和布匹销往外地。元初以后,松江地区家家户户从事专业性的手工纺织业。出现了从事棉纺织生产的专职纺织工人,专门的棉染织工坊,和专门收购出售转运花衣、棉纱和棉布的标局布行,形成棉布市镇和棉纺织中心。这就说明了早在元代的松江地区,就已出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的萌芽,新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四是,黄道婆生于忧患,她坎坷的人生,造就了她勤劳的习惯,叛逆的个性,顽强的意志,改革的精神,爱民的品德。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人民大众都起了或正在起着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她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对中国和世界的棉纺织业的无私奉献的一生。她身上闪光的时代精神和优良品德,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是中国人民学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黄道婆为棉纺织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不会忘记她的伟大历史功勋的,更不会对她“作为改进的纺织专家”产生怀疑。伟大的女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
1991年5月1日于乐城
库恩博士认为,“黄道婆或许不是做了改进的纺织专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性的看法,”但他已向人们,从本质上重新评价黄道婆的历史功勋,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他从根本上否定史学界对黄道婆已经定论的评价。
笔者对史学猎涉不深,唯独对崖州的历史人物黄道婆、李德裕颇感兴趣。1980年我还在大学二年级之时,已开始了对黄道婆的研究,先后走遍崖州、上海,到黄道婆当年可能生活过的地方实地调查,还走访了广州、北京、上海等地研究黄道婆的专家、学者们,并搜集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年来,我在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黄道婆的生平(即黄道婆的真实姓名和生卒年月;黄道婆的籍贯和族属;黄道婆少年沦落崖州的原因;黄道婆在崖州的居处;黄道婆为什么能成为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在崖州向谁学艺;黄道婆为什么晚年从崖州返回松江等方面)撰写了九篇专论,力图对黄道婆的生平作一个系统而翔实的论述。黄道婆的历史贡献是伟大的,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也是应该永久地得到肯定和褒奖的。如果对黄道婆“做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的这一重大问题,还有疑问,那么黄道婆将被蒙上历史的尘埃,她的形象也难再熠熠生辉,光照千秋。中国人民将失去一位长期受人敬仰、爱戴的女科学家。黄道婆的名字也将退出历史的科学的殿堂,从教科书上消逝。那么,一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尤其是棉纺织技术史,又如何去写呢?为了有益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让黄道婆的光辉形象永放光芒,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扬光大黄道婆的改革创新精神,因是,我写下这篇文章,想就库恩博士的怀疑问题,同他本人商榷,请教于库恩博士和其他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以求对黄道婆获得公正而一致的历史评价。
库恩博士提出了“黄道婆或许不是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的怀疑之后,他推测“称黄道婆是纺织专家的中国传说是怎样形成的?”他列举出两个原因(一个是松江府地区的实际起因;另一个是类似中国“第一个养蚕家”螺祖传说的后期起因),披露了他对黄道婆的怀疑,有具体如下三点:
一是,怀疑“黄道婆的祖籍在松江府地区”。他认为,黄道婆回到的“祖籍松江府地区”只是“想象中”的,不是事实上的。
二是,怀疑黄道婆少年沦落崖州学艺,晚年返回松江传艺的生平经历。他认为这是来自“据说是”和“想象中”的“祖籍松江府地区”的“中国传说。”被尊为“先棉”的黄道婆传说,类似被奉为“先蚕”的螺祖传说的后期起因一样,也“有可能从未存在过。”
三是,怀疑“黄道婆是棉纺织专家”。认为“黄道婆乃是一位普通妇女”,对她的“创造发明能力”和在松江传授的“新技术”,特别加上双引号。这也就从根本上对黄道婆的历史功绩产生了怀疑。
那么,库恩博士上述三点怀疑是否有足够的依据,言之成理呢?让我们逐个去推敲和斟酌。
一、关于黄道婆的祖籍。对黄道婆祖籍在松江的怀疑,不是自库恩博士而始。早在1985年,崖州的周振东同志就提出了“黄道婆崖州人也”①的新观点,他更超过了库恩博士的怀疑,到了完全否定黄道婆祖籍在松江的地步。
周振东同志借以立论的主要史文依据是陶宗仪《辍耕录》的记述:“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鸟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人造捍、弹、纺、织、之具”。周振东同志认为,陶宗仪所记“黄道婆自崖州来”,祖籍只能在崖州。②
然则,王逢《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有序”却明确记载:“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这又如何解释呢?笔者已就黄道婆的祖籍问题写了一篇专论,与周振东同志商榷,这里暂且不赘。仅就两个方面阐明我的看法:
其一,从语言文学的角度看,周振东同志以陶宗仪所记“黄道婆自崖州来”作为怀疑黄道婆祖籍松江进而得出“黄道婆崖州人也”的结论,这是不对的。请看:
《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即“过去我出征的时候,杨柳摇拽,现在我回家的时候,飞雪稠密。”这里,出征“离家”用“往矣”,退役“回家”用“来思”为辞。
《乐府诗集·孤儿行》:“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这里,孤儿所说到“回家”,都用“来归”为辞。
《金瓶梅·词话》第八回《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伙计道:“大官人(西门庆)吃了一日酒,到晚拉众朋友往院里去了。一夜通没来家。你往那里寻他去。”这里,(西门庆)“来家”,当做“回家”用,这“来”与“往”方向相对,是当“回”用。
从这些实例可以见出,古代汉语的“来”和现代汉语的“来”是有显著变化的。其实,只要你留心一下《说文解字注》、《辞海》、《辞源》以及古代的文学作品,对“来”字的本义、引申义及用法就十分明确:“来”,本义为“麦”,后引申为“行来之来”,“凡来之属皆称为来”。“来”作由彼至此,由远至近的趋向动词,与“去”、“往”相对,常当做“回”、“还”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来”在古汉语中有特指和通用:特指,即古代诸候之女回娘家省亲用“来”,又妇女因被丈夫遗弃或夫亡而返回娘家用“来归”为辞;通称,即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对男女老幼从外地“回家”都通称为“来家”。可见,陶宗仪记述“黄道婆自崖州来”,恰好历史地、真实地记述了黄道婆在晚年失去丈夫之后,从崖州道观——广度寺返回娘家——祖籍松江府的特殊身世。由此看来,陶宗仪用词十分讲究,既符合古汉语的规范用法,又切合黄道婆的特殊身世。而王逢所记“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就显得平白些。因此,从“黄道婆自崖州来”而怀疑黄道婆的祖籍在松江府地区,甚至得出“黄道婆崖州人也”的结论,这在语言、文字学上是讲不通的。
其二,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看。对黄道婆祖籍在松江府地区持怀疑态度,甚至把黄道婆说成是“崖州人也”是不对的。库恩博士认为,黄道婆只是回到“想象中的祖籍松江府地区”,那么,黄道婆“现实中的祖籍”又是在哪里呢?我想,库恩博士也是说不上来的。假如说,黄道婆祖籍在崖州,那么《崖州志》、《正德琼台志》、《琼州府志》等方志或史书,为什么没有记载?既然说,“黄道婆崖州人也”,那么,她究竟是崖州何处人氏?为何连周振东同志至今也未说出确切的城镇或乡村?更未拿出文物、古迹作为佐证?
然而,“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不但王逢在《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有序”中记载,而且《松江府志》、《上海县志》、《龙华志》等史书和方志中都有历史记载。此外,松江府地区有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镇,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县龙华乡东湾村。这里,还有黄道婆安息的陵墓和十多处黄道婆祠屋。上述的历史记载和文物古迹足以雄辩地证明:“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这是勿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二、关于黄道婆的历史传说。笔者十年来搜集到的黄道婆的历史传说总共有18篇,大多数属于上海和崖州古代历史人物传说。但也有一两篇出自崖州文人之手的新编故事(这当然不属于本篇讨论的问题)。
库恩博士把黄道婆的历史传说,即作为上海第一个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先棉”的传说与“可能从未有过”的“第一位养蚕家”——“先蚕”螺祖的传说相类比,从而得出“黄道婆或许不是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的怀疑。这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呢?
严格说来,螺祖作为“先蚕”的故事应属于神话,而不是传说。黄道婆作为“先棉”的故事,则属于历史人物传说。两者有质的区别。螺祖的神话产生于远古年代,这是远古人用想象和借助想象,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经过远古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加工过的自然社会形式本身。①因此,历史学家向来认为神话是对当时历史的记录。由此观之,“先蚕”螺祖的神话是中国古代人民对当时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记录,并非是胡编乱造的,黄帝的元妃螺祖即“先蚕”也可能存在。这是其一。其二,黄道婆的传说产生于元朝以后,仅有600多年,“先棉”黄道婆的传说不属于神话,而属于历史人物传说更比“先蚕”的神话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作为社会学科的门类之一的民间文学告诉我们,民间传说是劳动人民创作的,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系的故事。传说的主人翁大都有名有姓,而且不少是历史人物。这类历史传说往往和历史的实有的事物相联系,因此,比神话具有历史的真实性。黄道婆传说,就属于这类历史传说。黄道婆传说有她真名即黄四娘;有她出生地是松江乌泥泾镇,有她的第二故乡是海南岛崖州,而黄道婆少沦落崖州,晚年回归松江,向那里人民传授改革棉纺织工具和技术的历史事实,均见诸于元人王逢《梧溪集》和陶宗仪《辍耕录》等史书和《松江府志》、《上海县志》、《崖州志》等方志上。上海龙华乡东湾村,即古之乌泥泾地,有黄道婆安葬的坟墓,有纪念黄道婆的祠屋十多处,还有以黄道婆命名的村庄——黄婆庙村。在崖州城(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西二里的城西小学内)有黄道婆.在这里修道、学艺30多年的广度寺遗址及完好保存的“黄道婆塔”(塔原名迎望塔,因塔为广度寺附属建筑物而易名)。崖州和上海民间俗重纺织,至今不但两地还保留着黄道婆改革后的制棉工具,而且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海南民族博物馆,均陈列着黄道婆的塑像和她改革过的棉纺织工具及其织物。上述有关黄道婆的文物、古迹、习俗、历史事件,都包含了某种历史的实在因素,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点。从广义上说,一切文学作品,包括神话在内,都由于这样或那样地反映了某一时期的社会现实,而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但是,历史人物传说,除了具有一般文学作品广义的历史性外,还有和历史更为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界、史学界都认为,民间历史传说,可以说是劳动人民“口传的历史”。①当然,黄道婆的历史传说,也可以说是上海和崖州人民对黄道婆的“口传的历史”。但是,由于历史人物传说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又具有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和变异性。历史传说在根据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实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时,是经过了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幻想等艺术加工的,因此,历史传说又不完全等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今人为了某种需要,对历史人物编造了一些新的故事,比如《崖州织女黄道婆》,这就不是黄道婆的历史传说,而是黄道婆故事新编了,要严格区分于大量流传于民间和少数被收入《纺织史话》、《上海风物志》等作品中的黄道婆的历史传说。这是在研究黄道婆的生平事迹时所必须注意区分和扬弃的。因为,此类“新编故事”远离了历史的真实,带有文人的主观随意性。当然,作为真正的历史人物传说,也因为是一种口传的文学,所以,它的语言和细节也是经常变动的。关于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物,常有不同的说法,比如一些黄道婆的故事,往往把想象因素和实际生活现象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把它当作历史资料使用时,必须加以鉴别,否则也会妨碍它在历史科学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当然,不能因为黄道婆历史传说中有这些成份,从而否定它们在历史学(如黄道婆研究)中的作用和价值,更不能因此而把这些历史传说与“可能从未存在过”的“螺祖传说的后期起因”相提并论,从而产生出“黄道婆或许不是做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的怀疑。
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曾说过:“如果不知道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从远古时代起,民间创作就不断地伴随着历史。”①黄道婆做为棉纺织技术革新家的历史传说,也是伴随着崖州、上海乃至中国的棉纺织史而独特地存在、沿流至今的。通过这些黄道婆传说,我们可以了解崖州、上海乃至中国棉纺织史上的一些生动内容和发展趋势。因而,那些真正的黄道婆历史传说,是可以当做信史来读的。也就是当做劳动人民的“口传的历史”来读的。
为什么人们,包括库恩博士,对黄道婆做为棉纺织技术革新家会产生一些疑问呢?我想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古代中国的官修史书(二十四史),没有或少有记载,仅见于《辍耕录》和《梧溪集》呢。然而,黄道婆在宋末元初,她只不过是一个初为流人后为道人,出身贫苦的平民百姓,也就是库恩博士所说的一位“普通妇女”罢了。她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生时所干的纺织事业亦非轰轰烈烈,只有到了死后,人们对她从崖州学习带回传授革新的棉纺织工具及其织技、织物,才慢慢认识到它们的作用和价值。至于她改进的三纺车,在当时世界上属于最先进的纺纱工具。这只有放在若大的世界和历史长河中进行比较,才发现黄道婆的“创造发明能力”和她的伟大历史功绩。而当这些贡献为后人所确认之后,她作为一位不可多得的女棉纺织技术革新家,才在人们的心目中渐渐形成。由于她生前地位的低微,仅是一位“普通妇女”或“纺织能手”,所以,官修史书没有或极少记载,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不能以此做为怀疑乃至否定黄道婆是棉纺织技术革新家的依据。相反,由于官修史书没有或极少记载黄道婆的事迹,这就使上海和崖州人民群众世代口碑相传的民间传说,显得更加珍贵了。因为,这是那里的群众对黄道婆的“口传的历史”。
做为中国的考古学家、文学家的郭沫若同志曾说过:“民间文学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学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①
马克思主义者对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历史人物、事件、传说的历史价值,给予高度的评价。郭老甚至提高到“最正确、最可贵”的程度。虽然笔者不尽有这么高的看法,但从马克思、恩格斯、高尔基、郭沫若等人对民间文艺的评价来看,把黄道婆做为“先棉”的传说,与螺祖做为“先蚕”的(神话)传说类比,从而产生怀疑,认为“黄道婆或许不是做了改进的纺织专家”,这从做为社会学科之一的民间文学的历史传说与历史关系的角度来看,是说不通的。(当然,我这里用来观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的观点,对于身居西方不同思想体系的库恩博士来说,也不必强求一致,问题不在于谁手中拿着什么样的“武器”——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而在于谁对历史事实的发现。)
三、关于黄道婆的历史功勋
黄道婆是否“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这要看她在棉纺织业方面有何历史功勋。要回答这一问题,既要了解崖州和松江当时棉纺织业的情况,更要从比较中看黄道婆从崖州学习、带回并革新过的棉纺织工具、织技、织物对松江,乃至中国人民的纺织业和生活有何作用和影响。这得让事实来说话。
闽广地区的棉纺织业:
黄道婆所处的宋末元初,闽广地区的棉纺织情况怎样?史稿:
“木棉绽出如绵。土人以铁杖碾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绵,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①
这条资料告诉我们,这时闽广之治棉技术高于长江流域(更凌驾于关陕之上)。“丽”者,就是说棉布外表美观好看,“密”者就是棉布质地经纬交织紧密而又坚实。当时能织出“丽密”的布匹来,可见其织具织技比较精良。而“闽广来者,尤为丽密”,就标志着闽广的治棉工具和技术比松江先进。
崖州地区的棉纺织业:
据《纺织史话》所载,崖州气候土壤适宜棉花种植,是国内最早的棉产区。崖州居民有六种:军人、迈人、闽人、番人、儋人、黎人。其中以居住在州治所在地——水南村、崖州城及沿海一带的“闽人”为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其次是音与广州话相似的来自南海、惠阳等地的粤人即广人;再次是从军仕官而由内地来到崖州的军人;还有从外域波斯等地来的番人,即回人;从儋州移居的儋人;以及早期来到黎地的“值风水荡去其货的闽商”、“南恩藤梧高化州之征夫”、“福建亡命之奸民”、“闽楚逋逃之人”、崖州谪臣“李赞皇之后裔”等这些汉裔黎籍的“熟黎”。这些“崖州居民,习礼义之教,有邹鲁之风。(泰泉《通志》)妇女不事蚕桑只织贝,家自耕织,士多业儒,人重廉耻。”“妇女织吉贝为斜纹花布等形”(《旧志》参《府志》)。
崖州沿海一带福建汉族移民中,至今存有大量的〓屋布,就单布、双布、高丽布、斜纹花布,美丽而坚实,又存藏有用于红、白大事的崖州绣被、大帐、小帐、桌裙(食单)等。
从以下民歌、民谣更可以反映崖州纺织业的情况:
种吉贝①
上岭劈园种吉贝,力力松头等它大;
现在寒天将要到,做衣留防冬天寒。
纺纱①
月公出来光落落,眼看庭前纺车装;
纺纱的时623,挑纱的时326。
男纺②
天上起虹弯弯弓,人拾斜纹双压双;
脚踏纺车叫嗌嗌,公爹做成妇女人。
织双布③
天上起云鹧鸪班,双布织成四支椫;
椫味四支综八付,散纱一条都艰难。
织斜纹花布④
天上起虹弯弯弓,人拾斜纹双压双;
头毛梳妆绞紧紧,屋上盖茅层压层。
又,崖州古歌——《织女叹》⑤,通过一个福建汉族移民女子之口,把崖州先进的棉纺织业的情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织女叹》第一,唱出了妇女以纺织为业的社会分工:“早起四邻鸡声乱,放脚快行近布机,机喂最亲就是侬与你,终昼终夜坐相陪,……”第二,唱出了崖州纺织的悠久历史:“初更城楼更鼓乱,把灯添油迎灯光。”崖州城初建于唐代,“城楼更鼓”反映了崖州纺织史的悠久。又从歌中所唱:先织“绫罗绸缎光见影”后见“人织斜纹依亦学”,可知当时是中国纺织史上从织丝转到织棉的这一唐宋交接时期。第三,崖州纺织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若是爹丰母亦足,不用侬劳苦日夜。”“叹侬家贫钱债紧,债主一来侬心寒。”“单双织成匹到匹,织青织红人剪衣,”“手巾织千百对,以包槟榔讨深闺。”这些歌词唱出了崖州妇女为了生计,解除家庭的贫穷,还债裁衣婚嫁之用,不得不日夜纺织,可见地位之重要。第四,崖州棉织品种类之多,技艺之高:“单布”、“双布”、“绫罗绸缎”、“斜纹花布”、“手巾”、“被面”等品类繁多,有的如“鹧鸪斑”,有的如天上彩虹,总之“织巧织奇机上装”,织物“光光平平满面花”。目前,崖州60岁以上的汉族福建移民妇女都工于纺织,有的今天还存有一套旧时的先进手工纺织工具,还织造“单布”、“双布”、“斜纹花布”、“高丽布”、“葫椒粒花布”、“指甲花布”、“柳条花布”等。崖州这些织具和织物跟黄道婆家乡松江上海地区的织具和织物极其相似,早在唐代振州延德郡(即宋时的崖州),就以“斑布”和“食单”做为献给皇帝的贡品。可见在黄道婆沦落崖州之前,海南岛崖州的植棉及棉纺织技术是走在全国前头的。因而,库恩博士怀疑黄道婆从崖州学到了植棉及制棉的“先进技术”,带回松江传授,这恐怕是出于对崖州历史情况不太了解的原因吧?仰或是,库恩博士也认为“崖州是黎族人民聚居之地”,而黎族从古至今都使用原始的纺锤和踞织机,没有黄道婆式的先进的棉纺织工具的原故呢?史学界过去把黄道婆说成是“从当地黎人学艺,”并带回“黎族先进的纺织工具”在松江传授。这一结论,因与崖州黎族的纺织情况不符,的确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库恩博士也不例外。黄道婆“少沦落崖州”,她究竟向谁学艺,是向崖州织具简单而原始的黎族学习,还是向织具先进的汉族移民学习?我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元初松江纺织业情况。
晚年客居松江的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名日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案即闽广),初不踏车椎弓之制,卒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
文献所记元初黄道婆返回松江之前,这里的制棉工具只有“线弦竹弧”,连较为简单的轧棉工具——铁轴或铁杖都没有。因此,去籽只有用十指摘除。而棉籽都藏在棉英内部,包裹层层,为数又多,光凭十指之力很难把棉籽摘除。因手指摘籽极易疲劳,故功效很低。可见,此时松江制棉工具和方法很原始,远远地落在崖州的后边。
黄道婆从崖州带回松江传授并改进的棉纺织工具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史学界一向认为是王祯《农书》中所记的元代制棉工具。但是,库恩博士在分析了王祯的《农书》中对轧花机改进和弹弓描写后提出,这两种工具定已在王祯生活的时代普遍地使用了。由此推测“黄道婆或许不是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这种看法是否妥当呢?据查,黄道婆生于1245年,约卒于1306年前。①王祯生于1271年,卒于1368年。他们仅是相差26岁左右的同时代人。黄道婆于元贞间(1295—1297)年返回松江;王祯《农书》也是在元贞间即1296年开始着手准备,直至1314年才写成。也就是说,王祯《农书》是在黄道婆返回松江传授和改进纺织技术和纺织工具之后的第18年才完成。《农书》全书37卷,13.6万多字,插图306幅,全书分为《农桑通决》、《百谷谱》、《农器图谱》,其中《农器图谱》主要介绍元代及以前的包括纺织工具在内的农业生产工具。它将百余种器械绘成图谱并附有说明。这是一部图文并茂,集农器图谱之大成的农业科技书籍。因而,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应囊括元初松江的织具,也就是应把黄道婆带回和革新过的纺织工具收录进去。所以,中国史学界一向认为黄道婆带回松江的制棉工具,即陶宗仪所说的“捍、弹、纺、织之具”,在王祯《农书》中得到了记载。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外,笔者于1988年10月在上海搜集到的上海博物馆丛书之一的徐蔚南撰写的《上海棉布·纺织工具》一书,对黄道婆传授、改革后的上海织具,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兹以上述两书为黄道婆改革后的上海织具(简称上海黄式),与崖州汉族福建移民之织具(简称崖州汉式)进行比较,让我们从中看看黄道婆是否做了“改进的纺织专家”:
据《农书》所载,“捍”,即搅车,这是去籽的制棉工具。《上海棉布·纺织工具》介绍。“搅车用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轴端俱作掉拐,轴末柱窍,不透,两人掉拐,一人喂上棉英,二轴相轧,则籽落于内,棉出于外”。
这种搅车,形状结构、原理、使用方法与崖州沿海汉族福建移民使用的碾籽机基本相同。但崖州汉式底部是用一整块阔木板作底,二方柱只在左边柱上通一轴,右边柱上通一碾手(即掉拐)。只能供一至二人同时操作,而上海黄式则可供二至三人同时操作。说明上海黄式是在崖州汉式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的。这种搅车比过去“用手剖去籽”,要“功利数倍”。上海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二人可当八人。这种搅车,比美国人维特尼发明的轧棉机早了500多年。这是黄道婆的一项革新的成果,要是没有“创造发明力”,能做得到吗?
“弹”即弹弓和弹椎,这是用来弹松棉花的制棉工具。
上海黄式弹弓,《上海棉布·纺织工具》载:“以竹为之,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控以线弦,用弹棉英,如弹毛之法,务使结者开,实者虚,假其功用,非弓不可”。
上海黄式弹椎,《上海棉布·纺织工具》记:“弹花椎,圆木,长六、七寸,经二、六寸,两端大而中间略细,弹者手握细处,褚谱置花衣中,以椎击弦作音,则花衣〓散如雪,成熟花衣”。
崖州汉式弹弓弹椎,基本上与上海黄式相同。所不同点,崖州汉式弹弓用木作,其头宽些,接触棉絮就少些,而上海黄式用竹作,接触棉絮就多些。
原松江地区弹棉用的是“线弦竹弧”没有指出有弹弓,而是“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可见黄道婆从崖州返回松江之前,松江府地区,“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弹棉是多么艰难,靠“线弦竹弧”,“振掸成剂”。只有黄道婆从崖州带回并改进了弹弓、弹椎之后,在上海棉纺织工具中,才出现了类同崖州汉式的弹弓和弹椎。这是黄道婆的又一贡献。
“纺”即纺车。这是纺纱用的制棉工具。崖州汉式使用的是单脚踏纺车。上海纺车则是三脚踏纺车。王祯《农书》记载:“木棉纺车,其制比麻纺车颇小,夫轮动弦转,莩随之,纺人左手握棉筒,不过二三,绩於莩,牵引渐长,右手均,俱成紧缕,就绕上。……此即纺车之
用”。
《上海棉布·纺织工具》对纺车作了如下描述:“以木为,有背有足,别刻木附于背上为插椗之颈,凿三孔焉,以受椗,而设轮于背之中,以熟牛皮一条,俗乎皮弦者,环绕轮上,复以横木,名踏条(崖州汉式叫脚踏横担)尖其端,以贯轮之窍,以一端置车之足(崖州汉式脚踏横担不着地,置在足竖柱上)纺者将两足布踏条上,抑扬运之。左手持条子三条,(崖州持一条棉筒)粘椗捎而牵引焉,右手持一短竹,俗呼押纱棒,将纱附于椗”。这就是黄道婆改进的脚踏三纺车。其构造,形状,原理、完全与崖州汉式相同,所不同的是崖州汉式脚踏纺车只能纺单,而上海黄式纺车能纺三。这是黄道婆的一大改革成果。三纺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比英、美、德早四五百年。马克思曾在谈及18世纪的德国时说到,要找到一手能纺双纱的工人,如同找一个双头人一样不易。①然而,在德国18世纪做不到的事情,在中国13世纪已由黄道婆做到了,并且教会了1000多名妇女。从单纺车改进为三纺车,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这不就是黄道婆的一大发明吗?黄道婆不愧为“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王祯《农书》写成于黄道婆返回松江后的第18年,记载了“国初时”没有踏车之制,而此时已出现的“三纺车”,徐蔚南《上海棉布·纺织工具》,在推崇黄道婆之后,也记载了她改进三纺车。这二部史籍,连同《辍耕录》和《梧溪集》一起,是黄道婆“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的历史依据。由于三纺车的出现,促使松江地区纺纱率大大地提高,棉纺织业突飞猛进,使该地区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一伟大历史功绩是为世人所瞩目的,岂能视而不见?“黄道婆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是来不得半点怀疑的。
织布工具主要有织机,包括梭子、子、布扣,综等织具。
上海黄式的梭子、子、布机、和综。据《上海棉布·纺织工具》所记如下:
梭子腹扁阔,中空,钻窍于两端,削细竹茎为心,镶以牛角,便利穿掷”。子,即绕上线的莩筵,用于装梭织布。
布扣,“削篾编成,以薄而匀密为佳”。
综,“综头,棉纱线染绛为之,或二页或四页”。
崖州汉式和上海黄式的子、布扣、综,其名称、形状、构造,功用和使用方法都是完全相同的。说明黄道婆从崖州带回的这些织具,至今还原原本本地保留着。
布刀,崖州的打纬织布工具。木作,长60CM,一边形似斧背,背厚3.5CM,长20CM,在中间凿槽长17CM,深2CM,以装子,另一边平直斜刃如刀,因名布刀。布刀正中靠刀刃2.5CM处钻一孔,把线从子上抽出布刀旁。织布时脚踏椫木,织口张开,就把布刀穿入,同时从子上拉出线,用扣框拉近织口,再用布刀把纬线打实。崖州汉式布刀和上海黄式梭子,虽然叫法不同,形状也有扁长之分,但梭子和布刀的构造,原理都相同,同样内装一个子,同时具有来回穿线打纬的功用,使用方法都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它们是同一种类,有着历史的接承和发展关系。
“织”主要是指织机。上海黄式织机和崖州汉式织机,都是脚踏提综高架斜织机。《上海棉布·纺织工具》记载:
上海织机,“四足如床,前低后高,支片木于首,织者坐焉,名坐机板。次立两耳,以八棱木横贯之,可旋转以盘布,曰布轴。次有扣门,空其中,以装布扣。扣门左右,各设木焉,厥形如股,可屈可伸。外悬综头,以棉纱染绛为之,或二页或四页,立木于综头两旁,上设机焉,形如廿字,名鸦鹊,垂四绳于鸦鹊,以下分属于综头。又于综头之下设两木板,阔仅容足,坎地置之,名踏脚。系两绳于踏脚上,以分属于综头,织者左右足选踏,鹊鸦为之一府一仰,而综头之页,选随升降,布经之穿综头者,遂逐页分开,可容梭织矣。后足上设横木焉,以卷布经于中间,两头穿木为枝格状,如行马者,俗名滴花,总谓之布机。”
上海黄式布机与崖州汉式布机同属于脚踏提综高架斜织机。形状相似,构造、原理相同,使用方法一样。有些部件的名称相同:如布轴、坐板、扣门、布扣、综头、踏脚等主要部件的名称都原原本本地保留着。这说明黄道婆改革后的上海织机和崖州汉式现在还保存的布机是基本相同的,有着接承和发展的历史亲缘关系。
使用上海织机,上海织妇一般每天可织布一匹。古时以宽二尺二寸、长二丈为一匹,那么,上海妇女使用上海织机一日能织出二丈多的布匹。而崖州汉族织妇一日能织半脚布,①即一日能织一丈八尺。稍比上海妇女每天织布量少二尺左右,而却比崖州黎族妇女使用踞织机日织布量三尺,高达六倍以上!
通过上述比较,可见黄道婆从崖州带回并革新过的纺织工具的情形:她使松江从“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到有了“捍弹纺织之具”。这在技术交流方面,黄道婆立下了一个不小的功劳。她把崖州的单纺车改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三脚踏纺车。这不论对松江,还是整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纺纱技术,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是一项很了不起的科技发明!这是黄道婆在改进纺纱工具方面的伟大的历史功绩。
元初的松江,黄道婆传入和改进崖州的织具,相应地也传入和改进崖州的织技。然而,陶宗仪只记“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得其法”,其具体工序和流程怎样?史籍未载,后人也没深入考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何谓“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笔者参阅辞书,对照纺织流程,认为应包括如下内容:
“错纱”:“错”,有“塗饰”、“杂乱”、“相互交错”、“更色”之意。总起来说,“错纱”,包括①把素纱染成各样(杂)的色调。②把色纱互相交错或更迭地进行整经上架。③把有色的纬线(染色或原色)织入或镶嵌进经线中,使经线与纬线组成美丽的花纹图案。“错纱”是染纱、牵经、织纬中都涉及到的常用纺织技术。
“配色”:“配”,有“匹对”、“媲美”、“分发”、“分派”之意。“配色”,就是把已有色的线,“分发”,使之“匹对”而“媲美”。这是织造花布时所必须考虑和运用的技术,在牵经和织纬时,要依照预定织造的花布种类或图案进行配备各种色纱叫配色。
“综线”:丝缕经线与纬线交织曰“综”。“综”,又有“总集”、“聚合”、“治理”之意。“综线”即治理经纬,把经线和纬线交织,使用脚踏提综和用手穿纬织布的方法。
“挚花”:“挚”,有“悬持”、“提起”、“缺”、“绝”、“刻”的意思。“挚花”应有二种:①用手在花机上提花,或用脚踏布椫,使鸦鹊俯仰带动综头,从而提起经线,再按所织布匹种类花纹穿织纬线的织造花布的技术。②印花或括花。印花即在木板上刻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再蒙在素布上,用七彩擦印之。另一种为括花,即先以蜡染花纹,再把布浸入染缸中过色,再括去蜡就成括印花。
——上述“错纱、配色、综线、挚花”的技术,在崖州汉式和上海黄式的织造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应用,而崖州汉式和上海黄式织物又具体而形象地体现这种技术。
那么,上海黄式和崖州汉式的织物是怎样的?上海黄式织物,陶宗仪只记“被、褥、带、帨,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再没有具体的记载。而王祯《农书》也没记录,幸好徐蔚南的《上海棉布》一书详细地描述了。
至于崖州汉式织物,王逢只记“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灿花草”。笔者因是崖州人,对崖州的织物目睹耳闻,不但在上述崖州民歌中有历史的记载,而且在崖州沿海的汉族村民中,60岁以上的妇女,50年代还大批地纺纱织布,甚至去年笔者还在黄流镇抱本村,看到了一位叫黄六娘的妇女,在织造崖州花布。至今那些精致的“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的崖州布被、大帐、小帐、食单、斑布,在沿海一带汉族福建移民中存藏很多。兹把徐蔚南《上海棉布》的种类与笔者收集到的崖州棉布进行比较。从中看看黄道婆到底做了哪些历史性的贡献。
上海棉布织物有四大类:扣布、标布、稀布、高丽布。扣布和标布又叫小布和大布。它们与崖州汉式的单布和双布(也叫小布和大布)是一个样的。何谓扣布?扣即布扣,也叫布蔻,是捎簿竹蔑纵向排列,以长方木框镶嵌而成的织具,用于整经时控制经线的疏密,织布时把纬线拉近织口。这是上海黄式和崖州汉式脚踏提综斜织机上的主要部件之一。布扣有长短之分,当然织物也有宽狭、大小之分。初时,通常用布扣织出的布匹称为扣布,也叫小布。上海稀布也同崖州的双布一样称为大布,甚至长宽和价钱都差不多。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上海黄式有一大布种——“高丽布”。它的名称、织法,规格完全和崖州的“高丽布”一个样。这说明道婆把崖州的高丽布、织具和织技原原本本地传入松江。高丽布源出于朝鲜。崖州是古城,梁陈时已立郡,唐代较兴盛,海上交通发达,与高丽接触频繁,有人员和贸易往来。因此高丽的纺织技术也传入崖州。元初间再由黄道婆带回松江,成为那里的布种之一。这也是黄道婆的一大历史贡献。
此外,上海黄式织物的花布品种绝大部分与崖州汉式的花布相同。比如,上海黄式和崖州汉式花布中,都有花纹呈辫状,斜向排列成一条条纹路的斜纹花布;有经纬蓝白纱间格织成如芦扉形的芦纹布;有分别用蓝纱和白纱间格织成的蓝白柳条花布;有经纬如方胜者,即方形的彩胜,由二个斜方形部分迭合而成的斗纹花布,又称象眼布或指甲花布。尤其是,上海黄式织物中,有一种经过加工的花布叫药斑布的,崖州汉式叫斑布或盘斑布的,其制作的方法是一个样的。这种药斑布或斑布有两种制法;一种叫做括印花,乃以灰粉渗胶,涂作花样,随意染何色而去其粉者即成。另一种叫刷印花,就以木板刻作花卉人物等,也即“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等形,再以布蒙板而用五色刷之,就成华彩如画的花布。这种斑布,早在唐代振州的延德郡(也就是宋时的崖州西南沿海汉族移民集居地)已全国闻名,为皇帝所青睐,被做为贡品入朝。因此黄道婆元初得以学习并带回松江去传授。
由于纺织工具的改进,织技的提高,织物的增多,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首先乌泥泾人织成的“被褥带帨,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元代已称“布,松江者佳”。①到了明代成化间,乌泥泾的布匹流传到皇宫中,为宫女们所喜爱。乌泥泾人又织皇家御用衣袍,上有龙凤、斗牛等花纹,用大红、真紫、赭黄等染色。皇室购买这种衣料,加上官吏中饱糜费,一匹甚至有贵达白银一百两的。②正德年间,松江的“线绫、三棱布两物衣被天下。”……最好的布称“尖”,有“龙华尖”(龙华即黄道婆家乡),还有“松江大布”。又明万历时以丝作经而以棉纱作纬的云布,制品极精,花样既新,色亦娇媚,每匹价至三金,四方争购之。又府城所制漆纱布,大佳,贩鬻邻郡,号称松江方巾。③到了清初(公元1644—1911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所出产的棉布,市场遍及全国。这时,松江各地“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④。
由于棉纺织业的发达,上海成为棉花布匹的贸易地,北方各县在此设局,专门收购,名曰“坐庄”。广东、福建等地的大商人,在二三月间,载着糖霜来到上海出卖,到了秋天就在上海买好花衣布匹运回去。当时“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每晨到午,小东门外为市,负贩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焉。”①当时松江出产的布匹,还销到欧洲各国,其中最大的买主要算英国。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初,更扩大到十多万匹。英国商人指定只要苏松一带出产的紫花布。这种紫花布作成的裤子,和杭绸做成的衬衣,曾成为英国绅士风行一时的时髦服装。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土布穿暖了他们的祖先。
上述资料表明,由于黄道婆的热心提倡,不倦传授,大胆革新,使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产品远销国内外。可见,黄道婆的影响之广,作用之大,难怪她去世六七百年,人们还一直纪念着她,缅怀她的丰功伟绩。
黄道婆作为“改进的棉纺织专家”,除了陶宗仪《辍耕录·黄道婆》和王逢《梧溪集·黄道婆祠有序》这两篇历史文献有所记载之外,清·包世臣撰写的《上海黄道婆祠》的碑志,是一篇绝好的史料。兹摘录于下以资佐证:
“黄婆(黄道婆别称),自崖州附海舶到吾沪乌泥泾,教民纺织,棉始为布(这是黄道婆被尊为“先棉”的原因),化行若神,法流松太(纺织方法之先进,传播之神速),近世秦(陕西中部、甘肃东部)、陇(甘肃一带)、幽(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并山西太原一带),转传治法,在悉产棉布(可见黄道婆传授的纺织方法,在国内传播之广,影响之大)。然松太(松江、太仓地区)所产,卒为天下甲,而吾沪所产,又甲于松太。山梯海航,贸迁南北(即越山过海产品畅销南北)。黄婆之殁(去世)也,乡里醵(聚钱)葬而祠之,递迁递毁。乐利于人。肸蠁无所,有功则祀之,谓何常用为恧。(肸蠁,即分布。恧,惭愧。黄道婆乐意为人民谋利益,分布无所不到,有功则被人民纪念,有什么惭愧呢?)今兹幸以沙船运漕,懋著成绩,而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沙船,即一种平板货船,遇沙不搁。漕,从水路运送粮。懋著,即成绩显著)。海壖产布,厥本黄婆(即松江上海地区棉初为布源在黄道婆)。饮水思源,不仅生养吾民人己也(黄道婆的恩泽很广,不仅松江上海人获利,还波及全国,乃至国外)。
夫以棉布之利,百蚕丝而无主祀之神,异日秩及无文,举先棉之祀,舍黄婆其谁与归(秩,俸禄。举,推举。祀,祭祀。舍,捨,不要。归,归到一处。也就是说,棉布给人的利益有百倍于蚕丝,却没有主祀之神,今后要推举“先棉”纪念,除了黄道婆,谁能称得上呢?可见黄道婆为“先棉”的传说,是建立在她的伟大历史功勋之上的,并非虚说)。诸君子推本海运,归美黄婆,固非无说(许多道德高尚的人、把海运的兴起归结到黄道婆带来的好处上,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然国家承平二百年,徒以河事多故,偶举海运著绩也扰暂。至于松太两属,方壤不过二百里,岁供编银百余万两,额漕六十余万石,而因缘耗羡,以求利者称是。其地土高水下,风潮日至,沙松不保泽。虽得木棉,种于闽广,差宜土性,而车弓未作,莫利民用,农不偿本,久必罢废(虽然从福建广东得木棉种于松江,但由于土性不太适宜,而又没有轧车、纺车、弹弓等,便利于人们的纺织工具,生产成本得不偿失,长久以往必然废止了)。追呼急迫,驯致流亡则虑财赋之邦,鞠为瓯脱矣(追,回溯,急,紧急。迫,逼迫。邦,国家。鞠,养育。瓯脱,国土完整。虑,担扰。这就是说,回溯紧急严重的关头,顺服善良的人民,也不得不逃亡出外,即担扰国家的财政难以养育)。而今数百年来,红粟(富足的粮食)运入太仓者几当岁会十二,朱提(银子)输司农者(即主管钱粮的部门)。当岁会亦且二十而一。而土民仍得各安生业,称东南乐土(乐土,即安乐之地),其以宦游至者,又皆絜驾齿肥(那些作官或游览到此地的人,又都因为这里富饶而并列在此居住),长育子孙,凡所取给,悉出机杼(凡是取得的丰足,全部出自纺织业),以此程黄婆之功(用这些计算黄道婆的功劳),其仰关国计盈虚者(这是上关系到国家大计的满和空的问题),较之海运,奚啻什佰而已哉(与海运比较黄道婆的功劳,那里仅仅是百分之十而已呢)!……故为之铭,其辞曰:
天怜沪人(上海人),乃遣黄婆,浮海来臻(到)。沪非谷土(谷地喻绝境),不得治法,棉种空树(因为不掌握制棉的方法,棉花才空长在树上),惟婆先知,制为奇器,教民治之(只有黄道婆最先掌握制棉的知识,制造出先进的棉纺织工具,教给上海人民制棉的方法)。踏车去核,继以椎弓,花葺条滑(就用搅车去除棉籽,接着用弹椎和弹弓弹松棉花,再把棉花制成平滑的棉筒)。乃引纺车,以足助手,一引三纱(于是运用纺车,用脚踩动纺轮,使之轮动弦转,腾出手来、使一手能纺出三)。错纱为织,粲如文奇,风行郡国(把纱染色,并把有色的经纬线交接成鲜明得就象有花纹的丝织品一样美丽,象风一样地传遍国内)。昔苦讥寒,今乐腹果,租赋早完(过去苦以讥寒交迫,现在丰衣足食租赋早已完成)。昔苦逋负,今乐盈止,以安子妇(过去因为负债太重而逃亡在外,今天由于富足而可以安居乐业,使孩子和媳妇们都安稳地过好日子)。我衣我食,五百年所,远矣明德(500多年来,我沪人穿的吃的,都是黄道婆带来的,多么长远的恩德啊)!
综上所述,黄道婆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她的历史功绩,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黄道婆回到松江,传播和革新了崖州先进的制棉工具。她使松江“初不踏车椎弓之制”,到有了“捍、弹、纺、织之具”。她在崖州先进纺织工具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搅车,比美国人维特尼发明的轧车早500年;她在崖州单脚踏棉纺车的基础上,又研制出三脚踏棉纺车。这二种工具,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去籽和纺纱的工具。这是黄道婆的伟大发明创造,不朽的历史功绩。
二是,黄道婆返回松江传授并革新崖州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使松江地区的人民,从“棉种空树,不得治法”,到去籽,弹花,纺纱、整经、织布,都有了一套先进的工艺流程。又经过她潜心研究,大胆改造,使原先崖州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各得其法”,能织造出“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的织物。这种新技术、新方法“化若神行,风靡郡国”。黄道婆在制棉技术的革新和传播方面又立下一大历史功绩。
三是,黄道婆对棉纺织工具和技术的革新,对元清两代,松江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为社会增加了财富,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社会的向前发展。
因为织具、织技的改革,生产力大大提高。既使松江地区从原先“昔苦讥寒,农不偿本”,“近呼急迫,驯致流亡”到日织万匹,大量的粮食、白银输入松江地区,人民“生活富足”,“岁既就殷”,“今乐腹果”,500多年来,成为丰衣足食的“东南乐土。”这不啻于救活了原先水深火热要外出逃荒的千千万万的子民百姓!
同时,由于织具、织技的改革,产品的增多,使松江地区从“半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中,挣脱困境。不仅能自给自足,而且有了大量的花衣、棉纱和布匹销往外地。元初以后,松江地区家家户户从事专业性的手工纺织业。出现了从事棉纺织生产的专职纺织工人,专门的棉染织工坊,和专门收购出售转运花衣、棉纱和棉布的标局布行,形成棉布市镇和棉纺织中心。这就说明了早在元代的松江地区,就已出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的萌芽,新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四是,黄道婆生于忧患,她坎坷的人生,造就了她勤劳的习惯,叛逆的个性,顽强的意志,改革的精神,爱民的品德。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人民大众都起了或正在起着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她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对中国和世界的棉纺织业的无私奉献的一生。她身上闪光的时代精神和优良品德,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是中国人民学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黄道婆为棉纺织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不会忘记她的伟大历史功勋的,更不会对她“作为改进的纺织专家”产生怀疑。伟大的女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
1991年5月1日于乐城
附注
①②见1985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第1期和1987年第1期《广东民族论丛》载周振东《黄道婆籍贯考辩》。
①马克思《政治经治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
①见钟敬文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学概论》。
①高尔基《苏联的文学》、《论文学》,第112、113页。
①见《中国民间文学论丛》,郭沫若《我们学习民间文艺的目的》。
①《资治通鉴》卷一,159页胡三省注文。
①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乐东卷》。
①②③④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乐东卷》。
⑤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广东分会出版的《天南》,1980年第1期。
①详见拙作《黄道婆真实姓名和生卒年月考》。
①见《资本论》卷一,397页
①崖州汉族福建移民织布量以“脚”计算,也许取意于脚踏提综织布,一脚布长三丈六尺。
①元《松江府志》。
②③杜黎《明代松江府在棉纺织工业中的地位》。
④《康熙松江府志》卷五。
①渚华《木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