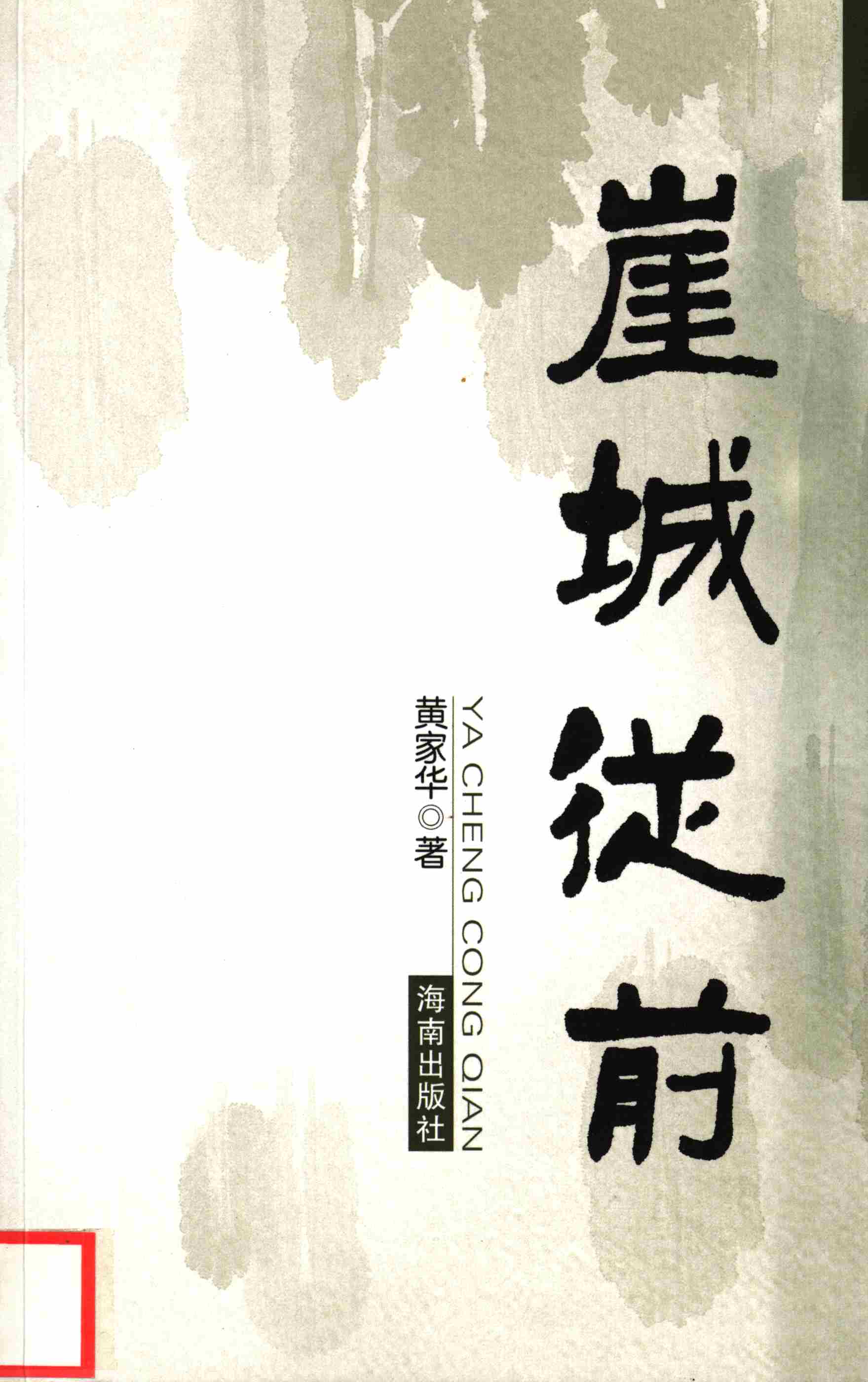水南古村
内容
水南村之“古”,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千一百多年以前。根据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海南岛上置儋耳珠崖二郡,其中珠崖郡所辖的五县之一临振县,县衙便在水南村。
古代按地域幅员来设置郡县,百姓以生存便利择地而居,郡县之设与居民户口是参酌相适合的。可想而知,作为琼南方圆几百公里历史上第一个行政建置所在地,水南村固然有其地缘优势,自然应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聚居。
水南村最早的村民从何而来,何时来到,这已无从查考。《正德琼台志》载:“越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则秦时有至者矣。”海南岛在“越”之属。这么说,早在秦时就可能有中原商贾来到海南岛上。又根据《琼州府志》:“琼州数尚六。禾六束曰一把,钱六百孔曰一贯,物六十觔曰一担。”这种六进制的度量衡,乃“实存秦时旧制”,或许是秦时中原来客的一个证据。至于秦人是否来到琼南水南村?不无可能。《汉书·贾捐之传》载,汉武帝开郡时,海南岛上在籍人口已有二万三千余户。珠崖郡临振县水南村村民户口当然也应包括在其中。
诚如丘浚所言,“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托处”。海南人口与日俱增。据《海南岛志》(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南宋时全岛来自大陆的移民已约有十万。而其时琼南的吉阳军(领辖二县),“境内止三百八户”(见周〓家书)。虽然近乎同时起步,岛南的开发却远远落后于岛北。自西汉至北宋千余年,此间的开发仍然主要局限在水南一方。或许是水土情缘吧,隋朝的临振郡,唐朝的振州及宁远县,北宋的崖州或吉阳军,其治所代代相因,一直盘桓在水南一村。所谓“琼南第一村”,因此成名。然而切莫以今例古,以为州军衙署驻地便会是多么繁华。古之州军行政区,虽说就相当于今之“地市级”,其实却与今之“地市级”相去甚远。丁谓在《到崖州见市井萧条赋诗》中写道:“户口都无二百家”,“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这应是可信的。直到南宋淳熙年间,吉阳军署才迁到宁远水北对岸,即今天之古州城遗址。因此可以说,先有水南村,后有崖州城;如同北京人说的,“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一样。
从考古发掘报告和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常常可以看到,无论是上古的部族聚落遗址,还是中古的村落,大多位于河畔水边的阶地或平缓的坡地上,一般河水暴涨不致受淹,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且适宜耕作。这既是方便生活的居息场所,又是利于农耕的生产基地。水南村的选址,与此不谋而合:安踞宁远河入海口,面山傍河,土地平旷,东北群山拱卫,西南天空海阔。两千年前的先民如何多方勘察然后才择定这处“阳基”来安身立命,我们已不得而知。说风水这边独好,不无偏颇;说什么“钟灵毓秀”也未免空泛。不用讳言的是,这一方水土也真有能容之量,竟让人们偏安于斯千余年,生聚繁衍,养精蓄锐,之后,终于北渡筑城,开拓西进。琼南基业,自此肇开。
当初,水南村与各地古村一样,依乡土社会惯例,聚族而居,各据一方。但随后移民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而来,于是各姓人等也就混居于一村了。而水南村中较为源远流长且于史可稽的家族,大概应该以卢、裴、黎、容四姓为其最。
卢氏一族尊卢多逊为“移崖始祖”。卢多逊原籍河南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县),五代时进士及第。因参与在陈桥驿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政变,以拥立之功任宋太祖一朝宰相。曾与薛居正等人共同编纂《旧五代史》。宋太祖朝任中书侍郎平章事,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加任兵部尚书。三年后,即公元982年,以“包藏奸宄,窥伺君亲,指斥乘舆,交结藩邸”的“大逆不道”之罪下狱。同年,全家亲属一并发配流放崖州。公元985年病逝于水南村,时年52岁。
卢多逊在水南村算来不满三年,但千余年后仍然为人所念及,这便是所谓“人以文传”的缘故。卢以幸免一死的戴罪之身,已不可能为民请命或造福一方而遗爱千秋,人们至今称道他,乃因为他是作诗为水南村写照的第一人。他的七律诗二首是吟咏水南村的开山之作,堪称绝妙好辞。
水南村
为黎伯淳题
其一
珠崖风景水南村,
山下人家林下门。
鹦鹉巢时椰结子,
鹧鸪啼处竹生孙。
鱼盐家给无墟市,
禾黍年登有酒樽。
远客杖藜来往熟,
却疑身世在桃源。
其二
一簇晴岚接海霞,
水南风景最堪夸。
上篱薯蓣春添蔓,
绕屋槟榔夏放花。
狞犬入山多豕鹿,
小舟横港足鱼虾。
谁知绝岛穷荒处,
犹有幽人学士家。
钱钟书先生曾批评宋诗有“爱讲道理,发议论”之弊,而卢多逊的《水南村》则可谓超脱流俗,一尘不染。他以清新朴实的笔触,全方位多侧面地描绘了北宋初年水南村风姿绰约的倩影。全诗宛然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长卷,把水南村的自然风貌描绘得历历在目。
你看那山水风光多么旖旎瑰丽:晴岚悠悠出岫,海霞斑斓似锦,仿佛仙乡幻境。你看那时令风物四季纷呈:鹦鹉筑巢栖息,鹧鸪啼唱不倦;椰树结子累累,翠竹生孙绵绵;薯蓣爬上篱笆,槟榔绕屋开花;狞犬猎获豕鹿,小舟载满鱼虾。虽无墟市而油盐自足,五谷丰登而家酿盈樽。逸士幽居修行,远客杖藜往来……诗中既极力铺叙了古村的物阜民康,又着意渲染古人的风俗淳朴。颇富情趣的传神之笔时而出之,如“竹生孙”句,似乎只是信手拈来,实则可见诗人体察人情物理的细致入微。苏东坡亦有诗云:“不用长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自注:“海南勒竹每节生枝如竹竿大,盖竹孙也”。其注似非。明人笔记云:“竹丈始枝,笋大始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按:竹根横行为鞭,鞭末端又派生小竹,名为竹孙)”当以此说为是。
卢诗标题下注:“为黎伯淳题”。《崖州志·人物志二》“隐逸”篇载:“黎伯淳,水南人。卢多逊称为幽人逸士。”卢诗(其一)首联所云之“林下”,即隐者逸士居处之谓也。其二尾联却刊作“幽人学士”。何“学”之有?隐逸而已。“学士”当是“逸士”之误也。还有(其二)尾联“却疑身世在桃源”,文理不通。“身世”如何能“在桃源”?应为“却疑身是在桃源”。“世”“是”同音而讹也。时人不察,以讹传讹,亦可叹矣。
其实“逸士”也未必逊于“学士”。在古代社会,有的士人为了保持人格尊严或保存一片心灵的净土,于经世致用的正途外,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优游林下,寄情烟霞泉石,以诗酒翰墨自娱,是为隐逸之士。当然,隐逸也有品类不一之分。一般士大夫以清高相推许,故作飘逸放达之态,实则对宦海中的浮沉荣辱耿耿于怀,诸如此辈者姑且不论。有的士人生不逢时,于乱世之际为避祸保身计,不得已暂时隐之以待机而出,这也不必说。也有的士人“志存高远”,以退为进,待价而沽。如此之“隐”即所谓“养望”,略同今之“作秀”耳。而“少无适俗韵”,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守拙归园田”的五柳先生,则无疑真隐者也。那么。水南村的“幽人逸士”黎伯淳,当属何许品类?关于这位水南村黎姓一族的“移崖始祖”,《崖州志》的记载只见上文所引的十五字。其人其事之得以流传,全系卢多逊一诗。仅此而已,其余皆不得其详。或许其中有一个古朴苍凉的故事不为人知?具体情节,尽可见仁见智。但我想,故事的主人公黎伯淳也许真是一位甘当布衣百姓终老山林的逸民。他隐居水南村,也许是“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所以选择远离尘嚣,以享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自在。不知黎氏后人以为然否?
水南裴姓是一方望族,其先祖裴瑑原籍河东郡(今山西省)闻喜县,乃唐朝晋国公裴度的十四世孙。北宋末年(政和年间?)由雷州太守改知吉阳军,后来安家水南村。其子裴闻义南宋初年(绍兴年间)因乃父之功勋而推恩得赐官爵,即所谓“荫补”,知昌化军。皇恩浩荡,裴闻义之子裴嘉瑞“亦以荫补官”。赵鼎胡铨贬谪到崖城时,曾先后居住在水南村裴闻义之宅。胡铨感其大义大德,名其宅堂曰“盛德堂”。裴嘉瑞之孙裴豫,号守素居士,遁世隐居,不事蒙元。及至明朝,裴氏后人出类拔萃者有裴士龙、裴盛、裴崇礼祖孙三代。裴士龙于明永乐年间以岁贡升送京师国子监肄业,时值明成祖诏命编纂《永乐大典》。裴士龙以其才学卓越,得以参与这部我国古代最大类书的编辑工作。编书完成后,被授以承事郎知县之职。士龙之子裴盛,于宣德元年中举。裴盛当年赴省城应试途中经琼台,旅舍旁有位八旬老和尚托他把八十余两白银带给肇庆天宁寺某位僧人,说已有二十几年不通音信了。裴盛把银子如数送达时,僧人诧异道:“我与他分别已久,以为他已去世,况且他又怎么知道我还活着?这些银子你本来可以不用交给我的。”裴盛说:“受人之托,安可负之?”僧人取半数银两酬谢他,他执意不收受。其子裴崇礼,景泰元年中举,“积学能诗,文古有趣”。
南宋初年,水南村慕容居中受朝廷“征辟”,先后委以承事郎、本军佥判、宾州劝农使等职。所谓“征辟”,就是朝廷以特别征取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有德望且学有所长的学者,或委以政事,或备顾问。慕容居中受此殊荣自是不凡。他卸任回乡后,设立书舍兴办教育造福乡里。《崖州志》以“卓行”纪之。前些年水南村有位老兄将其“容”姓改作“慕容”,且有慕容居中乃水南容姓先祖之说,不知所据者何。考“慕容”本为胡族姓氏,是胡语的译音。公元五世纪末,北魏孝文帝拓跋珪推行汉化运动,将其姓“拓跋”改为汉族“元”姓,其他鲜卑复姓也一律改为单音汉姓,如鲜卑族之一的“慕容”氏便改为汉姓“容”。后来,有些崇古怀祖痴心不改之士又恢复了原先的复姓。如果水南容氏与慕容居中的历史渊源属实,则亦可谓源远流长矣。
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功名身份的绅士是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同时也维系着道德教化的责任。绅士的威信建立在他的家世、功名、知识、家产、资历尤其是道德感召力上。诸如裴氏家族的绅士阶层,曾经维持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生态平衡,他们对古代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水南村之“古”,从这种人文历史传统中亦可略见一斑。
近代以来地覆天翻,水南村传统结构的社会生态早已不复存在,自然生态也已经几乎面目全非。公元1329年(元天历二年)贬谪到崖城的王仕熙曾选出“崖州八景”并赋诗一组,其中之一就是“水南暮雨”:
千树槟榔养素封,
城南篱落暮云重。
稻田流水鸦濡翅,
石峒浮烟鹿养茸。
明日买山栽薯蓣,
早春荷锸剪芙蓉。
客来疍浦寻蓑笠,
黄蔑穿鱼酒正浓。
《史记正义》说:“古之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水南村广种槟榔今盛于昔,恐怕这是唯一尚存的旧景观了,但如今种槟榔已没有古代的“素封”之利。宋代诗人黄山谷有“槲叶风微鹿养茸”句,王诗之“鹿养茸”可能由此点化而来,但是化得极是贴切。此间古时多坡鹿,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还时有鹿闯入村进民屋的事,现在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了。“客来疍浦”则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进入水南村的空间路径和方式,曾经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我们从东入村,是明清时开辟陆路驿道之后才开始通行的。汉唐宋元时,进入水南村的主要通道是水路。客从海上来,大船就停泊在宁远河口港湾里。“疍浦”,即宋元时疍家人所聚居的宁远河港湾之谓也。人们入村一般是换乘小舟沿河溯流而上,自西而东,一路停靠各自的码头,然后走到各自的去处。当年人们就是这样进出水南村,也就是这样进出临振县、振州、崖州、吉阳军的。
清康熙年间任崖州学正的郑懋昌也写了一首七绝“水南暮雨”:
水浒村南隐暮鸦,
近溪茅屋傍渔家。
夜来雨过疏藤响,
滴落槟榔半树花。
一条大河碧波滚滚西流而去,水南沿岸竹树掩映,槟榔椰子等棕榈科高挑卓立,一间间茅屋,三五成群,疏疏落落,散布其间。就如清乾隆年间的《琼州府志》所云,“琼郡枕山籍海,多海溢飓风之虞,故公私宫室,不得为高敞,远僻州县,多用茅茨,即公署间有茅屋。”可知,水南古村与徽州古村“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的景观也迥然不同。水南古村丰厚的文化底蕴并不附丽在什么古建筑上。
以“水南暮雨”为“崖州八景”之一并赋诗的,还有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任崖州知州的嵇震。其诗似乎平淡了些,不知是诗才使然,还是风景失色了。
野涵疍雨霏霏急,
山杂蛮烟漠漠遮。
牵犊竖归原上草。
荷蓑人立渡头沙。
小溪绕郭二三里,
短竹编篱四五家。
若把丹青图作画,
此中应着武陵花。
这是最后一首写水南村的古诗了。公元1857年(咸丰元年)中举的崖州才子吉大文和公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任崖州知州的钟元棣再选崖州八景并赋诗时,都遗弃了水南村。莫非水南苍古的遗风已异化了?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的田园牧歌已消失了?
古代按地域幅员来设置郡县,百姓以生存便利择地而居,郡县之设与居民户口是参酌相适合的。可想而知,作为琼南方圆几百公里历史上第一个行政建置所在地,水南村固然有其地缘优势,自然应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聚居。
水南村最早的村民从何而来,何时来到,这已无从查考。《正德琼台志》载:“越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则秦时有至者矣。”海南岛在“越”之属。这么说,早在秦时就可能有中原商贾来到海南岛上。又根据《琼州府志》:“琼州数尚六。禾六束曰一把,钱六百孔曰一贯,物六十觔曰一担。”这种六进制的度量衡,乃“实存秦时旧制”,或许是秦时中原来客的一个证据。至于秦人是否来到琼南水南村?不无可能。《汉书·贾捐之传》载,汉武帝开郡时,海南岛上在籍人口已有二万三千余户。珠崖郡临振县水南村村民户口当然也应包括在其中。
诚如丘浚所言,“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托处”。海南人口与日俱增。据《海南岛志》(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南宋时全岛来自大陆的移民已约有十万。而其时琼南的吉阳军(领辖二县),“境内止三百八户”(见周〓家书)。虽然近乎同时起步,岛南的开发却远远落后于岛北。自西汉至北宋千余年,此间的开发仍然主要局限在水南一方。或许是水土情缘吧,隋朝的临振郡,唐朝的振州及宁远县,北宋的崖州或吉阳军,其治所代代相因,一直盘桓在水南一村。所谓“琼南第一村”,因此成名。然而切莫以今例古,以为州军衙署驻地便会是多么繁华。古之州军行政区,虽说就相当于今之“地市级”,其实却与今之“地市级”相去甚远。丁谓在《到崖州见市井萧条赋诗》中写道:“户口都无二百家”,“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这应是可信的。直到南宋淳熙年间,吉阳军署才迁到宁远水北对岸,即今天之古州城遗址。因此可以说,先有水南村,后有崖州城;如同北京人说的,“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一样。
从考古发掘报告和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常常可以看到,无论是上古的部族聚落遗址,还是中古的村落,大多位于河畔水边的阶地或平缓的坡地上,一般河水暴涨不致受淹,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且适宜耕作。这既是方便生活的居息场所,又是利于农耕的生产基地。水南村的选址,与此不谋而合:安踞宁远河入海口,面山傍河,土地平旷,东北群山拱卫,西南天空海阔。两千年前的先民如何多方勘察然后才择定这处“阳基”来安身立命,我们已不得而知。说风水这边独好,不无偏颇;说什么“钟灵毓秀”也未免空泛。不用讳言的是,这一方水土也真有能容之量,竟让人们偏安于斯千余年,生聚繁衍,养精蓄锐,之后,终于北渡筑城,开拓西进。琼南基业,自此肇开。
当初,水南村与各地古村一样,依乡土社会惯例,聚族而居,各据一方。但随后移民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而来,于是各姓人等也就混居于一村了。而水南村中较为源远流长且于史可稽的家族,大概应该以卢、裴、黎、容四姓为其最。
卢氏一族尊卢多逊为“移崖始祖”。卢多逊原籍河南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县),五代时进士及第。因参与在陈桥驿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政变,以拥立之功任宋太祖一朝宰相。曾与薛居正等人共同编纂《旧五代史》。宋太祖朝任中书侍郎平章事,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加任兵部尚书。三年后,即公元982年,以“包藏奸宄,窥伺君亲,指斥乘舆,交结藩邸”的“大逆不道”之罪下狱。同年,全家亲属一并发配流放崖州。公元985年病逝于水南村,时年52岁。
卢多逊在水南村算来不满三年,但千余年后仍然为人所念及,这便是所谓“人以文传”的缘故。卢以幸免一死的戴罪之身,已不可能为民请命或造福一方而遗爱千秋,人们至今称道他,乃因为他是作诗为水南村写照的第一人。他的七律诗二首是吟咏水南村的开山之作,堪称绝妙好辞。
水南村
为黎伯淳题
其一
珠崖风景水南村,
山下人家林下门。
鹦鹉巢时椰结子,
鹧鸪啼处竹生孙。
鱼盐家给无墟市,
禾黍年登有酒樽。
远客杖藜来往熟,
却疑身世在桃源。
其二
一簇晴岚接海霞,
水南风景最堪夸。
上篱薯蓣春添蔓,
绕屋槟榔夏放花。
狞犬入山多豕鹿,
小舟横港足鱼虾。
谁知绝岛穷荒处,
犹有幽人学士家。
钱钟书先生曾批评宋诗有“爱讲道理,发议论”之弊,而卢多逊的《水南村》则可谓超脱流俗,一尘不染。他以清新朴实的笔触,全方位多侧面地描绘了北宋初年水南村风姿绰约的倩影。全诗宛然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长卷,把水南村的自然风貌描绘得历历在目。
你看那山水风光多么旖旎瑰丽:晴岚悠悠出岫,海霞斑斓似锦,仿佛仙乡幻境。你看那时令风物四季纷呈:鹦鹉筑巢栖息,鹧鸪啼唱不倦;椰树结子累累,翠竹生孙绵绵;薯蓣爬上篱笆,槟榔绕屋开花;狞犬猎获豕鹿,小舟载满鱼虾。虽无墟市而油盐自足,五谷丰登而家酿盈樽。逸士幽居修行,远客杖藜往来……诗中既极力铺叙了古村的物阜民康,又着意渲染古人的风俗淳朴。颇富情趣的传神之笔时而出之,如“竹生孙”句,似乎只是信手拈来,实则可见诗人体察人情物理的细致入微。苏东坡亦有诗云:“不用长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自注:“海南勒竹每节生枝如竹竿大,盖竹孙也”。其注似非。明人笔记云:“竹丈始枝,笋大始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按:竹根横行为鞭,鞭末端又派生小竹,名为竹孙)”当以此说为是。
卢诗标题下注:“为黎伯淳题”。《崖州志·人物志二》“隐逸”篇载:“黎伯淳,水南人。卢多逊称为幽人逸士。”卢诗(其一)首联所云之“林下”,即隐者逸士居处之谓也。其二尾联却刊作“幽人学士”。何“学”之有?隐逸而已。“学士”当是“逸士”之误也。还有(其二)尾联“却疑身世在桃源”,文理不通。“身世”如何能“在桃源”?应为“却疑身是在桃源”。“世”“是”同音而讹也。时人不察,以讹传讹,亦可叹矣。
其实“逸士”也未必逊于“学士”。在古代社会,有的士人为了保持人格尊严或保存一片心灵的净土,于经世致用的正途外,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优游林下,寄情烟霞泉石,以诗酒翰墨自娱,是为隐逸之士。当然,隐逸也有品类不一之分。一般士大夫以清高相推许,故作飘逸放达之态,实则对宦海中的浮沉荣辱耿耿于怀,诸如此辈者姑且不论。有的士人生不逢时,于乱世之际为避祸保身计,不得已暂时隐之以待机而出,这也不必说。也有的士人“志存高远”,以退为进,待价而沽。如此之“隐”即所谓“养望”,略同今之“作秀”耳。而“少无适俗韵”,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守拙归园田”的五柳先生,则无疑真隐者也。那么。水南村的“幽人逸士”黎伯淳,当属何许品类?关于这位水南村黎姓一族的“移崖始祖”,《崖州志》的记载只见上文所引的十五字。其人其事之得以流传,全系卢多逊一诗。仅此而已,其余皆不得其详。或许其中有一个古朴苍凉的故事不为人知?具体情节,尽可见仁见智。但我想,故事的主人公黎伯淳也许真是一位甘当布衣百姓终老山林的逸民。他隐居水南村,也许是“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所以选择远离尘嚣,以享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自在。不知黎氏后人以为然否?
水南裴姓是一方望族,其先祖裴瑑原籍河东郡(今山西省)闻喜县,乃唐朝晋国公裴度的十四世孙。北宋末年(政和年间?)由雷州太守改知吉阳军,后来安家水南村。其子裴闻义南宋初年(绍兴年间)因乃父之功勋而推恩得赐官爵,即所谓“荫补”,知昌化军。皇恩浩荡,裴闻义之子裴嘉瑞“亦以荫补官”。赵鼎胡铨贬谪到崖城时,曾先后居住在水南村裴闻义之宅。胡铨感其大义大德,名其宅堂曰“盛德堂”。裴嘉瑞之孙裴豫,号守素居士,遁世隐居,不事蒙元。及至明朝,裴氏后人出类拔萃者有裴士龙、裴盛、裴崇礼祖孙三代。裴士龙于明永乐年间以岁贡升送京师国子监肄业,时值明成祖诏命编纂《永乐大典》。裴士龙以其才学卓越,得以参与这部我国古代最大类书的编辑工作。编书完成后,被授以承事郎知县之职。士龙之子裴盛,于宣德元年中举。裴盛当年赴省城应试途中经琼台,旅舍旁有位八旬老和尚托他把八十余两白银带给肇庆天宁寺某位僧人,说已有二十几年不通音信了。裴盛把银子如数送达时,僧人诧异道:“我与他分别已久,以为他已去世,况且他又怎么知道我还活着?这些银子你本来可以不用交给我的。”裴盛说:“受人之托,安可负之?”僧人取半数银两酬谢他,他执意不收受。其子裴崇礼,景泰元年中举,“积学能诗,文古有趣”。
南宋初年,水南村慕容居中受朝廷“征辟”,先后委以承事郎、本军佥判、宾州劝农使等职。所谓“征辟”,就是朝廷以特别征取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有德望且学有所长的学者,或委以政事,或备顾问。慕容居中受此殊荣自是不凡。他卸任回乡后,设立书舍兴办教育造福乡里。《崖州志》以“卓行”纪之。前些年水南村有位老兄将其“容”姓改作“慕容”,且有慕容居中乃水南容姓先祖之说,不知所据者何。考“慕容”本为胡族姓氏,是胡语的译音。公元五世纪末,北魏孝文帝拓跋珪推行汉化运动,将其姓“拓跋”改为汉族“元”姓,其他鲜卑复姓也一律改为单音汉姓,如鲜卑族之一的“慕容”氏便改为汉姓“容”。后来,有些崇古怀祖痴心不改之士又恢复了原先的复姓。如果水南容氏与慕容居中的历史渊源属实,则亦可谓源远流长矣。
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功名身份的绅士是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同时也维系着道德教化的责任。绅士的威信建立在他的家世、功名、知识、家产、资历尤其是道德感召力上。诸如裴氏家族的绅士阶层,曾经维持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生态平衡,他们对古代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水南村之“古”,从这种人文历史传统中亦可略见一斑。
近代以来地覆天翻,水南村传统结构的社会生态早已不复存在,自然生态也已经几乎面目全非。公元1329年(元天历二年)贬谪到崖城的王仕熙曾选出“崖州八景”并赋诗一组,其中之一就是“水南暮雨”:
千树槟榔养素封,
城南篱落暮云重。
稻田流水鸦濡翅,
石峒浮烟鹿养茸。
明日买山栽薯蓣,
早春荷锸剪芙蓉。
客来疍浦寻蓑笠,
黄蔑穿鱼酒正浓。
《史记正义》说:“古之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水南村广种槟榔今盛于昔,恐怕这是唯一尚存的旧景观了,但如今种槟榔已没有古代的“素封”之利。宋代诗人黄山谷有“槲叶风微鹿养茸”句,王诗之“鹿养茸”可能由此点化而来,但是化得极是贴切。此间古时多坡鹿,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还时有鹿闯入村进民屋的事,现在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了。“客来疍浦”则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进入水南村的空间路径和方式,曾经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我们从东入村,是明清时开辟陆路驿道之后才开始通行的。汉唐宋元时,进入水南村的主要通道是水路。客从海上来,大船就停泊在宁远河口港湾里。“疍浦”,即宋元时疍家人所聚居的宁远河港湾之谓也。人们入村一般是换乘小舟沿河溯流而上,自西而东,一路停靠各自的码头,然后走到各自的去处。当年人们就是这样进出水南村,也就是这样进出临振县、振州、崖州、吉阳军的。
清康熙年间任崖州学正的郑懋昌也写了一首七绝“水南暮雨”:
水浒村南隐暮鸦,
近溪茅屋傍渔家。
夜来雨过疏藤响,
滴落槟榔半树花。
一条大河碧波滚滚西流而去,水南沿岸竹树掩映,槟榔椰子等棕榈科高挑卓立,一间间茅屋,三五成群,疏疏落落,散布其间。就如清乾隆年间的《琼州府志》所云,“琼郡枕山籍海,多海溢飓风之虞,故公私宫室,不得为高敞,远僻州县,多用茅茨,即公署间有茅屋。”可知,水南古村与徽州古村“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的景观也迥然不同。水南古村丰厚的文化底蕴并不附丽在什么古建筑上。
以“水南暮雨”为“崖州八景”之一并赋诗的,还有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任崖州知州的嵇震。其诗似乎平淡了些,不知是诗才使然,还是风景失色了。
野涵疍雨霏霏急,
山杂蛮烟漠漠遮。
牵犊竖归原上草。
荷蓑人立渡头沙。
小溪绕郭二三里,
短竹编篱四五家。
若把丹青图作画,
此中应着武陵花。
这是最后一首写水南村的古诗了。公元1857年(咸丰元年)中举的崖州才子吉大文和公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任崖州知州的钟元棣再选崖州八景并赋诗时,都遗弃了水南村。莫非水南苍古的遗风已异化了?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的田园牧歌已消失了?
相关地名
水南村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