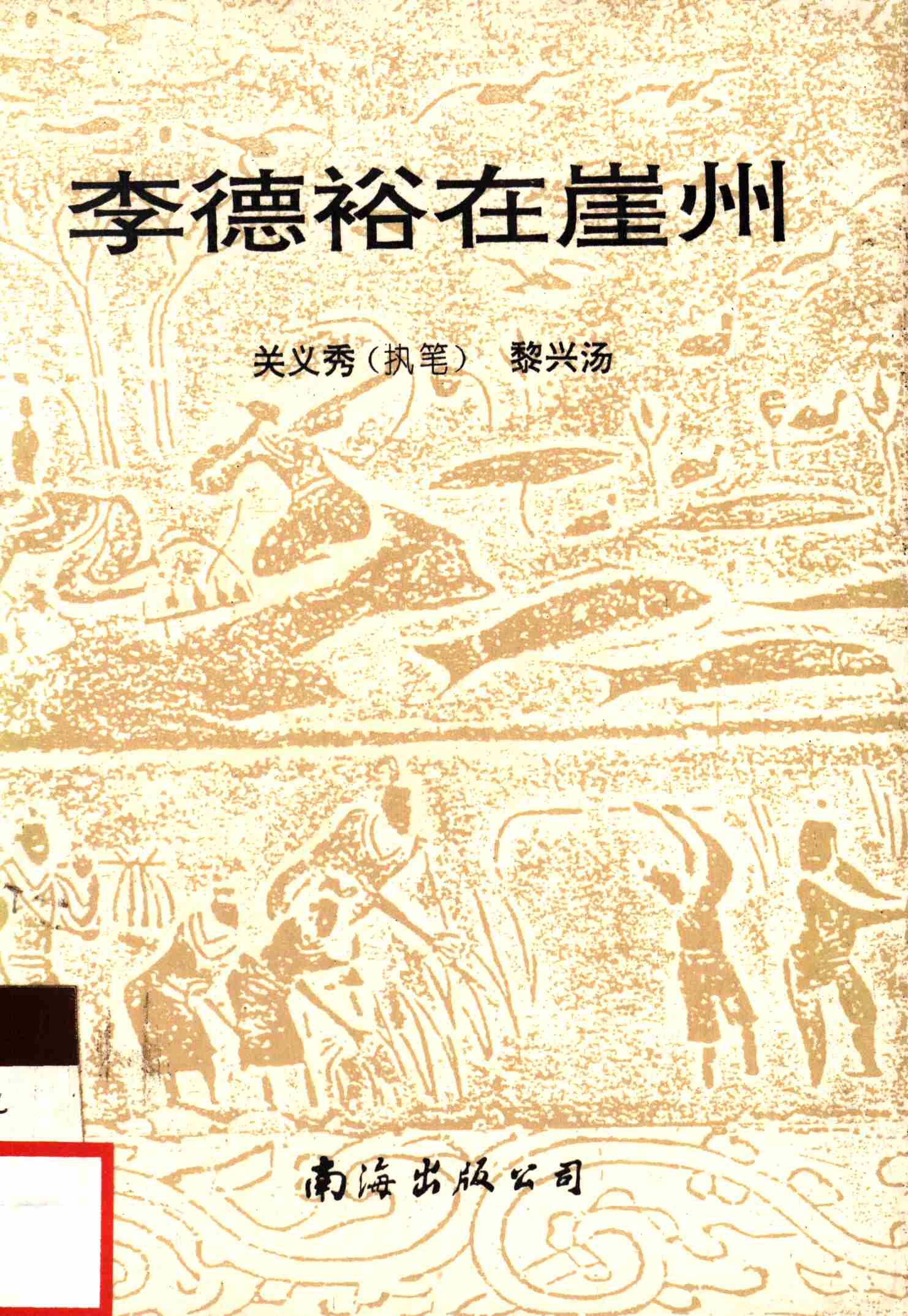内容
远处的山,近处的岭,笼罩在雨幕中,起先是一片迷濛,渐次便分出浓浓淡淡。这边的树,那儿的藤蔓、茅舍,被雨点敲打着,最初是潇潇飒飒,而后便剩下淅淅沥沥。风吹着,雾散着,从那稀薄的地方,慢慢露出了光亮,露出了青黛,露出了山寨雨后的丽日阳天。
多港峒抱班寨里的黎胞也是这样。一场劫难过去了,他们把悲哀埋到心底,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一片废墟上,盖起了一间间崭新的船形屋。寨前那一块盆地,原先是野鼠出没、杂草丛生的野地,黎胞们破天荒在那里开出一丘一丘稻田。此刻,刚刚泛青的秧苗被七月的一场雨水洗过,晶莹着嫩茸茸的绿,把一缕缕油然而生的喜悦沁进黎胞们的心里。
茅舍外面,李德裕踏着雨后的泥地,踱来踱去。叆叇的白云,啁啾叫着飞出林子的小鸟,追逐在田垅上的狗,争先恐后撞入他的眼帘,也撞进他的心中,连那脚板下“咯吱咯吱”的响声也是一种美妙的音韵。李德裕的嘴边,浮上久违了的笑容。他一高兴,亲昵地把李通拉到怀里,得意地念起一首唐诗:
吏舍踢终年,出郊清旷曙。
杨柳散和风,青山淡吾虑。
依丛还自憩,缘涧还复去。
李通很少见到父亲这样高兴的样子,一边跟着念,一边逗着父亲朗声大笑。可他却把“缘涧还复去”念成“缘涧水来急”。
“哟,通儿,你小小年纪,耳朵就有毛病?”李德裕满以为儿子听错了呢。
“父亲,是你眼睛花了,”李通即景生情改了诗句,指手划脚的说,“你看山坡那边——”
李德裕循着儿子手指的方向望去,一股股山水正活蹦乱窜地冲下,把山坡冲成一道道山涧,把那浑浊的泥水卷入寨前那块盆地,卷进那一丘丘稻田。霎时,李德裕脸上罩上阴云,失声喊了起来,“快,快堵住山水,救救稻苗!”
一丛丛新绿,可是李德裕用心血浇灌的啊。他磨破了嘴皮,才说服黎胞们干那从没干过的事情:用石片磨成石锄,用铁片弯成铁锄,一点一点地刨,才刨出这一小丘一小丘的田。然后,又冒了多大风险到外面城里换回谷种,点播,插秧,才换来现在这个样子。黎胞们刨掉了的不仅是草根,更是千百年留下来的习惯,他们播下的也不仅是谷种,更是崭新的信念和热辣辣的期待和憧憬。从此,他们会知道,他们不光会烧山,还会种田,汉族同胞能做到的事他们也会做。李德裕想的就是这,难怪一见山水冲进稻田他就慌了。
大伙听到他的喊声,手拿锄头、石块,堵的堵,挖的挖,终于把山水引向稻田远处的低洼之地。
“峒长,神还真向着咱们哪!你看,咱们开荒造田,神让稻苗长得怪喜人的。咱们一堵山水,神马上让它乖乖跑了,”李德裕想一会,挽住帕威的手说,“帼长,咱们再在神蛙岭下筑起一条堤坝,挡住山洪,把水引入盆地里,神也会依咱。峒长,只要对咱有利的事,神哪一桩不依着咱?胡思进才跟咱作死对头哪。大伙,你们说是不是这回事?”
李德裕趁热打铁,打得正是时候。人们经过官兵一阵折腾之后,再面对此情此景,自然信服李德裕。于是,大伙都拍手叫好,“就听李大人的!”
“峒长,你说呢?”李德裕望着帕威笑。
“大人,话都让你说了,咱还说啥?”帕威倒象一个腼腆的大孩子,“不过,这可是一件大事呀!咱们得祭山神,才破土动工!”
“好!还要选个良辰吉日呢!”李德裕爽快地说。
开山祭选定七月初十龙日举行,以求得龙的庇佑,家事安宁,人畜兴旺。
太阳刚刚爬过山头,神蛙岭下就人声鼎沸。人群中有抱班寨的黎胞,也有多港峒里别的寨子、德霞峒几个寨子赶来的黎胞。抱班寨里男女老少那份得意的劲儿就甭提了。姑娘们身着美丽的桶裙,头插缤纷多采的山花,逢人不语先自笑,不答俚话只答歌。小伙子扎头巾,捆腰带,身挎弓箭多孔武,摇来摆去耍威风。外面来的黎胞一样兴奋不已。他们挑酒提肉,赶山路,赶月亮,赶到了抱班寨,就是要亲眼看看开山祭的场面,睹一睹被弟兄们称为“帅公”的李德裕的威仪,给他敬一碗山兰酒,敬一筒香米饭。
辰末巳初时分,帕威、李德裕相随着,走到祭桌面前。帕威还是赶墟时的一身穿戴,不过那头巾、那麻衣,都是成亲时的,今天他还着意在颈上挂一个用兽牙编成的圆圈。这圆圈让人想起他搏击野兽时的雄姿,使他显得十分慓悍、英武。李德裕一身平民打扮,粗布衣,麻布鞋。山民们望着他,七嘴八舌的谈论着。外人失望了。他们眼中的“帅公”应是个头上长角,身上生剌的人物啊,可是他连一点架子都没 有。可是抱班寨的黎胞立刻振振有词:“他不是帅公,谁是?狗官听到他的名字就吓破胆,山贼在梦里都向他悔过,连那神明都让他三分……”于是,别的寨子的黎胞都点头称是,“难得,难得!帅公神通广大,竟象咱自家人似的不装腔作势,是咱的帅公,咱的帅公!”
祭台排好了,一只生猪、一只生羊、一只肥鸡,十碗米饭,五杯酒、三杯茶,挤满了拼凑起来的两张祭桌。黎家人大事小事都要祭神祭鬼,可祭物这样齐全却还是头一次。烟袅袅升起来了。帕威亲自拿起粉枪,对空鸣了三响。道公身穿长袍,头戴高道帽,手持一把有摇铃的神剑,神色虔诚地立在祭桌旁边。他是新道公,名叫帕侬。帕扣或许良心发现,无颜再见乡亲父老,逃到别的黎峒去了。帕侬双膝微弓,两手一拱,依次敬请神明享用祭品,如此反复三次,又挥舞长剑,表示镇压八方邪魔。然后,他大声喊道,“一拜天地,二拜山神,三拜仙石!”于是,帕威、李德裕和所有在 场的人们,一个个屏声息气,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礼毕,李德裕代帕侬念了祭文:
崖州抱班寨百姓略具薄礼,择七月初十良辰吉日诚心祭祀天地神明、镇村仙石。念我生民辛苦劳作,不得果腹,故欲引水上山,使地尽其利,人尽其力。不惟求一日三餐之温饱,亦欲为百世子孙造福,决非妄自尊大,亵渎神明。此心可察,此情实衷,皇天后土明鉴,祈望大展神威,助我厥日完工,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幸甚,幸甚。
念过祭文,帕威命众人散开。一个“娘母”和一个汉子便粉墨登场,跳起祭祀舞。“娘母”头顶瓷碗,右手拿一根筷子,首先对着祭桌起舞。只见她右脚向前落地,左脚抬起,右手向前,手心正对下方,从上而下不停地摆动。当右手向上时,筷子便拍击头顶上的瓷碗,发出“铿锵铿锵”的响声。那个汉子则敲着铜锣,“哐哐”的锣声奏出和谐的旋律 伴着“娘母”的舞步。于是,“娘母”便从案桌前面开始,向左、向右、向后面跳动。“娘母”始终念着咒语,敬请诸神祝福,保佑村寨平安。
祭祀仪式结束了。
突然,帕威抓过一只大红公鸡,当着众人把它剐了,捧起半碗鸡血。大伙一愣,帕威早已捧着鸡血叩拜了天地,然后,深情环顾四周,对李德裕投去炽热的目光,把碗举到头顶发誓,“苍生有眼,今后咱再对李大人见外,就让山熊咬,让蟒蛇吞!此生此世,咱做牛做马,也听李大人的!”
“专听李大人的!”黎胞们雀跃不已,迸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喊声。
李德裕眼睛润湿了。他曾为宰相,亲临过多少祭祀的场面,多么气派,多么隆重的场面。但它对于李德裕而言,一半是真心的祈祷,一半是礼节性的敷衍。而现在,这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却给他献上一个民族的赤诚。于是,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朝茂光一字一顿地喊,“捧鸡血来!”
“峒长,黎胞们,你们把心掏给了我,情深义重,何以相报?我李德裕只有一句话,只要身在黎山,吾跟你们风雨同舟,共建家园,共谋大业,造福苍生,造福子孙。现在我也歃血为誓,喝了这鸡血,我的心头永远都是热的!”李德裕接过鸡血,一样对天地叩拜,才当着众人一饮而尽。
“好!好!”黎胞们吆喝着。有谁敲起牛皮鼓,接着,唢呐吹起来了,漫山遍野男女老幼跳起舞蹈,唱起山歌,直闹到日过响午,兴犹未尽。
笫二天天刚放亮,神蛙岭上不再是那样神秘、沉寂。人们扛锄抬筐,先先后后上山去了。他们一路拨云踏雾,一路亮开歌喉:
上山罗,上山罗,
鸟儿寻食要出窝罗,
田蟹吃虾要张螫罗,
咱上山来修大坝哟,
你挑土来他打夯哟,
众人同心土成山哟,
汗珠滴下汇成河哟,
千年的黄连要刨根罗,
黎家的日子要甜过糖罗!
上山的人越来越多,歌声也越唱越大,李德裕忙着打地桩,帕威东奔西跑,又是挖土,又是抬筐,又是打夯,忙的不亦乐乎,他们顾不上唱,心里却比唱的还甜蜜。黎胞们唱歌卖力,干活更卖劲。百来斤重的土筐抬着,不够劲,一个人干跪独霸土筐,提着它,用腹皮也贴上,来回快走如飞。那搭挡的失了业。一时找不到工具。只好抱大土块、搬石头垒坝基。挖土的用力过猛,手掌上冒起血泡,才不吭一声呢。他们暗暗咬紧牙,一锄一锄地挖,生怕露了底,被缴了械,那就不妙了。这样,歌声一阵高过一阵,筑坝的高潮也一浪高过一浪。不到一个上午,土坝的底层有模有样了。
可是,人群中却少了一双动情的眼睛,少了一个亭亭玉立的身影……
此刻,她正倚在门边遥望神蛙岭,无奈却又好奇地听着那儿飞来的歌声、笑声、号子声。望着望着,一双本来很黑很亮的眼珠透射出炽烈的光亮,驱散蒙在脸上面的哀伤,使人想到,那迷雾下面还闪动着亮晶晶的星星,冰凉的表层下面依然躁动着一股暖流。她禁不住前方的诱惑,埋怨帕威好狠心把她搁下不管,就缓缓走到外面。其实,是她让帕威去忙大伙的事情,别来伺候她。那边的热火朝天偏使她受了冷遇,使她冤了她的阿爹。秋玉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猛然间又回过头来,跄跄踉踉,扑进她的小屋。她才不相信阿光哥 会绝情地抛下她。多少天过去了,她还是痴痴地坐在床上。她觉得,阿光就坐在她的身旁,目不转眼地望着她,似乎怕她走了似的,弄得她发窘,害羞地低下头来。然而,她果真伸过手去,却再也抚摸不到阿光那结实的、温馨的手,摸不到自己赠给他的那只精致的腰篓。她脸色惨白,绝望地痛 哭,“阿光哥,你在哪里?你怎不回答我呀,侬喊你多少遍啦?”秋玉一次又一次呼喊,泪流干了,嗓子喊哑了,她还在喊。她傻呼呼地想,“阿光哥不会不管咱,他说过,咱们要厮守一辈子,白头到老……”多少回,一听到风吹竹叶,秋玉便以为阿光吹着鼻哨来了;多少遍,一看到屋外花影摇动, 秋玉便以为阿光故意〓〓蹭蹭的不进屋。但是,她一次又一次失望。寨子里的父老姐妹苦口婆心地劝她想开些,李德裕安慰她,“孩子,阿光是个好后生,谁舍得他走啊!可是天底下没有不落的月亮。月总是圆了缺,缺了再圆啊!”直到这个时候,秋玉才真地相信黄泉路无情,阿光哥在那一头,她却在这一头,中间横隔着一道铁门,一道永远不开的铁门。秋玉不由得轻轻喊道:“阿光哥,咱们……咱们来生来世再见!”她早知道,她应该去开始新的生活了,可是真的要离开 这播下爱情种子的寮房时,她却恋恋不舍地回头,情意缠绵地轻轻念着,“阿光哥,陪侬去吧!你啥时候都为咱寨子好,如今,寨里要干大事,干好事,侬也不能当闲人了。你就伴侬去吧!”
于是,秋玉走向神蛙岭,来到了父老姐妹们的中间。大伙见到她,一齐投过十分关切十分同情的眼光。虽然谁也不同她长谈,只是亲切地喊了她一声。可是秋玉觉得这已经足够了,那一声招呼里包含了她所需要的一切。她点一点头,默默地挑起土来。于是,大伙干得更欢了。挖土的、抬土挑土的、打夯的,加速了节奏,加强了力度。那劳动的场面,仿佛一张浓墨云彩的油画,线条粗犷、浑厚,意境开阔、深远,也如一道“哗哗”流泻的山溪,冲刷着一切情感的沉滓,翻滚着忘我的浪花。很快,秋玉那惆怅,那心底的哀伤,象死寂的潭水融进山泉,象潮湿的山岚消失于斑灿的朝霞面前。
秋玉挑得满满的,来回小跑着,脸上沁出了汗水。李德裕默默地望着她的背影,怜爱、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如此可爱可敬的姑娘,恶运竟一次又一次向她袭击,真不知道她怎样承受得了?李德裕忽然觉得,他是风雨飘摇中的破舟,而她就是冰雪覆盖下的小树。人,秉赋不同,地位不同,学识不同,命运有时却惊人地相似。然而,他挺过来了,她也挺过来了,这些日子来,她一直关怀着李德裕,此刻,李德裕却找不到合适的话安慰同病相怜的姑娘。望着她那瘦削的脸蛋儿,他的心都快憋死了。
秋玉又挑着黄土到了坝基上。李德裕望了她一眼,招了招手,“孩子,快来,帮帮个忙!”
秋玉倒下土,三步两步奔过来,李德裕却说声“孩子,先歇歇”,便去拉拉线,打打桩。秋玉急了,便要挑土去。李德裕这才示意她等一等,慢慢走过来,慢条斯理地说,“孩子,你瘦多了!先歇一会嘛!堤坝也不是一天、二天能筑成的!”李德裕说着,又慢腾腾地抬起右脚,笑一笑,“秋玉,帅公的鞋开了窗,土坷粒、石碎什么的,都来欺负我的脚板。你能不能帮个忙哪?”
“大人,咱有空再给你做双新的。”秋玉苦涩地笑。
“那可不行。这不是要累坏了你?”李德裕想了想,掏出一块麻布,“来,缝缝补补就行了。岐,你可不能蛮干啊。太累了,身子也会开窗开洞的,病邪真会欺负你呐!”
说了老半天,秋玉恍然大悟,李德裕处处为她好,心里也就热呼呼的。她麻利地缝好破洞,才低声说,“谢大人。大人,你也得保重!”
“嘿嘿,我老啦,老了的姜虫不吃,”李德裕强装笑容,“年轻人,身体才最要紧!”
“大人,你还不老,不老……”秋玉喃喃自语,默默挑起粪箕,却回过头,投来关切的目光。
七月的太阳,悄悄爬上南仇岭上那最高的山峰,向着天顶挪动。
李德裕笑着对帕威说,“该让大伙歇歇工了,不然,肚子会告状的!”
“说得是!”帕威跳上一个高土墩上,两手凑成喇叭,“大伙儿歇歇工,不歇工的,瞧咱不敲断你的腿!”
人们放下工具,跑到一株大榕树下,里三层,外三层,围住李德裕和帕威,说着,笑个不停。
可附近几个火堆旁,早忙坏了几个姑娘。她们先挖好一个个土坑,在坑里生起火来。等到木柴都烧成炭,她们才把炭火搞平,在上面盖上一层薄土,再在泥土上面匀匀地放好山莳,然后,又把泥土盖过,再在泥土上面生起大火。火焰上窜下跳的,伸着长舌。突然,帕威说声,“差点忘了大 事!”便离开大伙,跳到火堆旁边。他从腰篓里取出一个叶包,掰开葫芦瓜叶,拿出几块鹿母,串在木叉上,扒出炭火,认真的烤起肉来,他烤肉也有一手。不多久,鹿肉既不生也不焦,恰到火候,冒出香喷喷的味儿,早让几个馋嘴鬼流口涎水。
还愣住做啥?开饭,开饭罗!爱吃粥的吃粥,爱吃山莳的扒山莳!山莳好吃好吃的,别让大吃鬼占了便宜!”帕威一头嚷着,一头却把烤肉藏到背后,活象一个几岁的小孩。
大伙一窝蜂去扒山莳,帕威却乘机走到李德裕身旁,啧啧嘴说,山莳好吃,叫人嘴里吃着,眼里想着,就便宜了他们吧。粥不香,可老人吃得消,几个肉片就凑合凑合啦。
“峒长,你几时学会圆谎啦?还真有两下。幸亏你那眼神泄密,不然,我还真会上当呢!”李德裕“嘿嘿”笑着,“好,你的情我领了。不过,我可吃不消啊。拿几片给秋玉,那孩子瘦多了。峒长,你去吧!”
帕威看到李德裕那个不容违抗的样子,也只好乖乖从命了。
帕威挪近女儿身边,望了她一眼,就低下头。果然她瘦多了。这些日子光顾忙大伙的事,似乎把她忘了。如今瞧她这个样子,帕威心里如扎上针,异常难受。但话到唇边又哽住。他眼圈儿湿了,把鹿肉往秋玉手里一塞,才喃喃地说,“孩子……你吃了吧,身子最要紧!”
“阿爹,你怎啦!女儿好好的!鹿肉拿回去,你吃,给李大人吃!”秋玉死活不肯要。
“孩子,生我的气了?阿爹只顾忙大伙的事,关心你不够,该死!”帕威咒起自己来了。
“阿爹,别说了。你若整天陪住我,就不是好阿爹,寨子里的事要紧,女儿还恨自己呢……”秋玉说着,已是泪光点点。
“我的好女儿!”咱威一把拉过女儿,无限深情地抚摸着她的脸颊,到底悄悄放下鹿肉。
“黎胞们,山里有珍禽异兽,有良材好药,地下埋着金银,藏着珠宝。咱却吃粥,吃山莳,吃野菜,盐巴也难得不断顿。这太不公平了!”李德裕一边吃着粥,一边走到大伙中间。这些天来,他时刻想着的是如何使地尽其财,使人尽其力,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太难了。但怕难,什么也就完了。今天,他就要好好地讲一讲,目下所做的,就是砸开那不公平的枷锁的第一步。有了第一,便有第二、第三……还愁枷锁砸不开吗?
李德裕说着,用黎胞们能听得懂、能接受得了的方式说着。山里人你看我,我看你,那眼神是在说,原来山那边,还有一个天地。而咱正是向那边走去。有人乐开了,几个人用手搭成一座轿,抬起李德裕,乐呵呵地沿着坝基来回蹦着。
“别闹了,别闹了,累坏了李大人,看我不打断你的手!”帕威又高兴又生气的嚷着。
不想,几个调皮鬼却眨一眨眼,跑过来抬起帕威蹦蹦跳跳的,把他甩到半空,乐得大伙都笑了。
日子在黎家人的苦干中一天天过去,神蛙岭下的堤坝一天天加高了。
眼看堤坝快要峻工,李德裕心里好不高兴,每天,他和帕威留在后头,瞧这瞧那,聊起来没完没了。
一天傍晚,他突然拉住帕威,怪神秘地说,“峒长,你听,什么在喊呢?”
“还不是鸟喊,野兽叫?”帕威随口说。
“还有青蛙鸣喊的声音。你听,你听!”李德裕一把拉住帕威。
“大人,这坝一筑成,你都变成小孩子,来逗我了。哪里有青蛙叫?”帕威说。
“峒长,这坝一筑成,挡住山洪,咱们再引水上山,面前是一片田洋,十里稻花香。这神蛙石灵,所以,它喜不自禁地喊了,给咱报个信儿。你真地听不出来?咦?”李德裕笑盈盈,解开帕威的闷葫芦。
“哟,原来是这样!我也听见,听见!”帕威这一回惟恐落后了。
然而,才过一天,李德裕却皱起眉头。
刚才,帕威告诉他,山里蜜蜂做窝都飞到高高的树枝、竹枝上做,他还漫不经心地说,“蜜蜂喜欢哪里就飞到哪里,这不关咱的事!”
“大人,你不知道,蜜蜂搬到高枝上做窝,今年肯定会发大水!”帕威说。
“这是真的?”李德裕脸色一沉。
“假不了,咱们山里人见多罗!“帕威那语气不容有争辩的余地。
“峒长,要真发了大水,”李德裕倒抽一口凉气,眼前恍然出现一幅可怕的画面:滔滔的山洪,象从九天滚滚泻来,浊流千里,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他不禁吃惊地河,“咱这堤坝该怎么办?”
“怕啥?兵来将挡。水来土填!”帕威说。
李德裕不作声,只顾默默地绕着堤坝走,环顾了四周,突然拉起帕威走。
“峒长,让大伙干着,咱们走走,乘山洪没来之前,先给它找出路!”李德裕见帕威还在发愣,再用力一拉。
他们沿着堤坝向北走去。他们走过山岗,走过山丘。那山丘和山丘毗邻的地方露出了缺口。然而,李德裕一望面前有山丘,有平地,摇了摇头,便向前走去。
前面是一个峡谷。山坳露出了嶙峋的山石,石上布满青苔,看来很少有人到过。峡谷自然形式一条溪涧。石缝间淅淅沥沥淌下水珠,汇成汩汩细流,淌入涧底光滑的鹅卵石,发出细碎的叮叮咚咚的声音。
李德裕眼前一亮,攀援着石头、树根,走下峡谷。
“大人,你也要小心,小心!”帕威身不由己,跟着他走。
“峒长,你也要小心!李德裕答应着,望着溪涧的坡度,又折断木棍来比比划划,估量着水的落差。末了,他还不放心似的,攀缘着岸边的树木,沿着溪涧,向下走了好远。
“大人,你这是要走到昌化溪去啦?”帕威紧迫不舍,不解地问。
“溪涧通向昌化溪?”李德裕惊喜地问。
“还不是!”帕威说。
“好,好,”李德裕转回身,“我不走啦,别让峒长跟我受累。”
李德裕果真折回头来。可他不时还问着帕威在那里猎过多少野味,还要帕威带他去打猎,他要给帕威“头弓肉”。
“咱们现在就去!”帕威可上瘾了。
“不,不,”李德裕笑着,“说着开开心罢,望梅止渴嘛。现在咱们有正经事!”
上得岸来,李德裕歇了歇气,捧几口泉水漱洗漱洗,清了清脑儿,提了神儿,这才冲着帕威说,“峒长,我昨夜做了个梦。”
”是梦见遇上沉香格木吧?”帕威问道。黎胞们梦见遇上沉香格,是得了好兆。
“不,恐怕比遇上沉香格要好”。李德裕停了一停,才告诉帕威,他梦见大伙就在峡谷上面修了一道滚水石坝,又从堤坝那边挖了沟渠直通到石坝那里。山洪到来时,水都流来,沿着溪涧跑掉。水位低时,堤坝里的蓄水自然排不出去,只灌溉田洋。
“大人,你又编派我了。这哪里是梦?不过,你想的好!”帕威拍拍脑门,“咱就笨,就不想到这上头!”
“还不好!咱们还要挖沟,把昌化溪引上山来。那样,咱们准能过上好日子!你说是不是这样?”李德裕太兴奋了,握住帕威的手问。
“是,是,”帕威连连点头,“堤坝一完工,咱们就干!”
“先修石坝,再引水上山!”李裕补充了一句。
多港峒抱班寨里的黎胞也是这样。一场劫难过去了,他们把悲哀埋到心底,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一片废墟上,盖起了一间间崭新的船形屋。寨前那一块盆地,原先是野鼠出没、杂草丛生的野地,黎胞们破天荒在那里开出一丘一丘稻田。此刻,刚刚泛青的秧苗被七月的一场雨水洗过,晶莹着嫩茸茸的绿,把一缕缕油然而生的喜悦沁进黎胞们的心里。
茅舍外面,李德裕踏着雨后的泥地,踱来踱去。叆叇的白云,啁啾叫着飞出林子的小鸟,追逐在田垅上的狗,争先恐后撞入他的眼帘,也撞进他的心中,连那脚板下“咯吱咯吱”的响声也是一种美妙的音韵。李德裕的嘴边,浮上久违了的笑容。他一高兴,亲昵地把李通拉到怀里,得意地念起一首唐诗:
吏舍踢终年,出郊清旷曙。
杨柳散和风,青山淡吾虑。
依丛还自憩,缘涧还复去。
李通很少见到父亲这样高兴的样子,一边跟着念,一边逗着父亲朗声大笑。可他却把“缘涧还复去”念成“缘涧水来急”。
“哟,通儿,你小小年纪,耳朵就有毛病?”李德裕满以为儿子听错了呢。
“父亲,是你眼睛花了,”李通即景生情改了诗句,指手划脚的说,“你看山坡那边——”
李德裕循着儿子手指的方向望去,一股股山水正活蹦乱窜地冲下,把山坡冲成一道道山涧,把那浑浊的泥水卷入寨前那块盆地,卷进那一丘丘稻田。霎时,李德裕脸上罩上阴云,失声喊了起来,“快,快堵住山水,救救稻苗!”
一丛丛新绿,可是李德裕用心血浇灌的啊。他磨破了嘴皮,才说服黎胞们干那从没干过的事情:用石片磨成石锄,用铁片弯成铁锄,一点一点地刨,才刨出这一小丘一小丘的田。然后,又冒了多大风险到外面城里换回谷种,点播,插秧,才换来现在这个样子。黎胞们刨掉了的不仅是草根,更是千百年留下来的习惯,他们播下的也不仅是谷种,更是崭新的信念和热辣辣的期待和憧憬。从此,他们会知道,他们不光会烧山,还会种田,汉族同胞能做到的事他们也会做。李德裕想的就是这,难怪一见山水冲进稻田他就慌了。
大伙听到他的喊声,手拿锄头、石块,堵的堵,挖的挖,终于把山水引向稻田远处的低洼之地。
“峒长,神还真向着咱们哪!你看,咱们开荒造田,神让稻苗长得怪喜人的。咱们一堵山水,神马上让它乖乖跑了,”李德裕想一会,挽住帕威的手说,“帼长,咱们再在神蛙岭下筑起一条堤坝,挡住山洪,把水引入盆地里,神也会依咱。峒长,只要对咱有利的事,神哪一桩不依着咱?胡思进才跟咱作死对头哪。大伙,你们说是不是这回事?”
李德裕趁热打铁,打得正是时候。人们经过官兵一阵折腾之后,再面对此情此景,自然信服李德裕。于是,大伙都拍手叫好,“就听李大人的!”
“峒长,你说呢?”李德裕望着帕威笑。
“大人,话都让你说了,咱还说啥?”帕威倒象一个腼腆的大孩子,“不过,这可是一件大事呀!咱们得祭山神,才破土动工!”
“好!还要选个良辰吉日呢!”李德裕爽快地说。
开山祭选定七月初十龙日举行,以求得龙的庇佑,家事安宁,人畜兴旺。
太阳刚刚爬过山头,神蛙岭下就人声鼎沸。人群中有抱班寨的黎胞,也有多港峒里别的寨子、德霞峒几个寨子赶来的黎胞。抱班寨里男女老少那份得意的劲儿就甭提了。姑娘们身着美丽的桶裙,头插缤纷多采的山花,逢人不语先自笑,不答俚话只答歌。小伙子扎头巾,捆腰带,身挎弓箭多孔武,摇来摆去耍威风。外面来的黎胞一样兴奋不已。他们挑酒提肉,赶山路,赶月亮,赶到了抱班寨,就是要亲眼看看开山祭的场面,睹一睹被弟兄们称为“帅公”的李德裕的威仪,给他敬一碗山兰酒,敬一筒香米饭。
辰末巳初时分,帕威、李德裕相随着,走到祭桌面前。帕威还是赶墟时的一身穿戴,不过那头巾、那麻衣,都是成亲时的,今天他还着意在颈上挂一个用兽牙编成的圆圈。这圆圈让人想起他搏击野兽时的雄姿,使他显得十分慓悍、英武。李德裕一身平民打扮,粗布衣,麻布鞋。山民们望着他,七嘴八舌的谈论着。外人失望了。他们眼中的“帅公”应是个头上长角,身上生剌的人物啊,可是他连一点架子都没 有。可是抱班寨的黎胞立刻振振有词:“他不是帅公,谁是?狗官听到他的名字就吓破胆,山贼在梦里都向他悔过,连那神明都让他三分……”于是,别的寨子的黎胞都点头称是,“难得,难得!帅公神通广大,竟象咱自家人似的不装腔作势,是咱的帅公,咱的帅公!”
祭台排好了,一只生猪、一只生羊、一只肥鸡,十碗米饭,五杯酒、三杯茶,挤满了拼凑起来的两张祭桌。黎家人大事小事都要祭神祭鬼,可祭物这样齐全却还是头一次。烟袅袅升起来了。帕威亲自拿起粉枪,对空鸣了三响。道公身穿长袍,头戴高道帽,手持一把有摇铃的神剑,神色虔诚地立在祭桌旁边。他是新道公,名叫帕侬。帕扣或许良心发现,无颜再见乡亲父老,逃到别的黎峒去了。帕侬双膝微弓,两手一拱,依次敬请神明享用祭品,如此反复三次,又挥舞长剑,表示镇压八方邪魔。然后,他大声喊道,“一拜天地,二拜山神,三拜仙石!”于是,帕威、李德裕和所有在 场的人们,一个个屏声息气,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礼毕,李德裕代帕侬念了祭文:
崖州抱班寨百姓略具薄礼,择七月初十良辰吉日诚心祭祀天地神明、镇村仙石。念我生民辛苦劳作,不得果腹,故欲引水上山,使地尽其利,人尽其力。不惟求一日三餐之温饱,亦欲为百世子孙造福,决非妄自尊大,亵渎神明。此心可察,此情实衷,皇天后土明鉴,祈望大展神威,助我厥日完工,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幸甚,幸甚。
念过祭文,帕威命众人散开。一个“娘母”和一个汉子便粉墨登场,跳起祭祀舞。“娘母”头顶瓷碗,右手拿一根筷子,首先对着祭桌起舞。只见她右脚向前落地,左脚抬起,右手向前,手心正对下方,从上而下不停地摆动。当右手向上时,筷子便拍击头顶上的瓷碗,发出“铿锵铿锵”的响声。那个汉子则敲着铜锣,“哐哐”的锣声奏出和谐的旋律 伴着“娘母”的舞步。于是,“娘母”便从案桌前面开始,向左、向右、向后面跳动。“娘母”始终念着咒语,敬请诸神祝福,保佑村寨平安。
祭祀仪式结束了。
突然,帕威抓过一只大红公鸡,当着众人把它剐了,捧起半碗鸡血。大伙一愣,帕威早已捧着鸡血叩拜了天地,然后,深情环顾四周,对李德裕投去炽热的目光,把碗举到头顶发誓,“苍生有眼,今后咱再对李大人见外,就让山熊咬,让蟒蛇吞!此生此世,咱做牛做马,也听李大人的!”
“专听李大人的!”黎胞们雀跃不已,迸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喊声。
李德裕眼睛润湿了。他曾为宰相,亲临过多少祭祀的场面,多么气派,多么隆重的场面。但它对于李德裕而言,一半是真心的祈祷,一半是礼节性的敷衍。而现在,这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却给他献上一个民族的赤诚。于是,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朝茂光一字一顿地喊,“捧鸡血来!”
“峒长,黎胞们,你们把心掏给了我,情深义重,何以相报?我李德裕只有一句话,只要身在黎山,吾跟你们风雨同舟,共建家园,共谋大业,造福苍生,造福子孙。现在我也歃血为誓,喝了这鸡血,我的心头永远都是热的!”李德裕接过鸡血,一样对天地叩拜,才当着众人一饮而尽。
“好!好!”黎胞们吆喝着。有谁敲起牛皮鼓,接着,唢呐吹起来了,漫山遍野男女老幼跳起舞蹈,唱起山歌,直闹到日过响午,兴犹未尽。
笫二天天刚放亮,神蛙岭上不再是那样神秘、沉寂。人们扛锄抬筐,先先后后上山去了。他们一路拨云踏雾,一路亮开歌喉:
上山罗,上山罗,
鸟儿寻食要出窝罗,
田蟹吃虾要张螫罗,
咱上山来修大坝哟,
你挑土来他打夯哟,
众人同心土成山哟,
汗珠滴下汇成河哟,
千年的黄连要刨根罗,
黎家的日子要甜过糖罗!
上山的人越来越多,歌声也越唱越大,李德裕忙着打地桩,帕威东奔西跑,又是挖土,又是抬筐,又是打夯,忙的不亦乐乎,他们顾不上唱,心里却比唱的还甜蜜。黎胞们唱歌卖力,干活更卖劲。百来斤重的土筐抬着,不够劲,一个人干跪独霸土筐,提着它,用腹皮也贴上,来回快走如飞。那搭挡的失了业。一时找不到工具。只好抱大土块、搬石头垒坝基。挖土的用力过猛,手掌上冒起血泡,才不吭一声呢。他们暗暗咬紧牙,一锄一锄地挖,生怕露了底,被缴了械,那就不妙了。这样,歌声一阵高过一阵,筑坝的高潮也一浪高过一浪。不到一个上午,土坝的底层有模有样了。
可是,人群中却少了一双动情的眼睛,少了一个亭亭玉立的身影……
此刻,她正倚在门边遥望神蛙岭,无奈却又好奇地听着那儿飞来的歌声、笑声、号子声。望着望着,一双本来很黑很亮的眼珠透射出炽烈的光亮,驱散蒙在脸上面的哀伤,使人想到,那迷雾下面还闪动着亮晶晶的星星,冰凉的表层下面依然躁动着一股暖流。她禁不住前方的诱惑,埋怨帕威好狠心把她搁下不管,就缓缓走到外面。其实,是她让帕威去忙大伙的事情,别来伺候她。那边的热火朝天偏使她受了冷遇,使她冤了她的阿爹。秋玉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猛然间又回过头来,跄跄踉踉,扑进她的小屋。她才不相信阿光哥 会绝情地抛下她。多少天过去了,她还是痴痴地坐在床上。她觉得,阿光就坐在她的身旁,目不转眼地望着她,似乎怕她走了似的,弄得她发窘,害羞地低下头来。然而,她果真伸过手去,却再也抚摸不到阿光那结实的、温馨的手,摸不到自己赠给他的那只精致的腰篓。她脸色惨白,绝望地痛 哭,“阿光哥,你在哪里?你怎不回答我呀,侬喊你多少遍啦?”秋玉一次又一次呼喊,泪流干了,嗓子喊哑了,她还在喊。她傻呼呼地想,“阿光哥不会不管咱,他说过,咱们要厮守一辈子,白头到老……”多少回,一听到风吹竹叶,秋玉便以为阿光吹着鼻哨来了;多少遍,一看到屋外花影摇动, 秋玉便以为阿光故意〓〓蹭蹭的不进屋。但是,她一次又一次失望。寨子里的父老姐妹苦口婆心地劝她想开些,李德裕安慰她,“孩子,阿光是个好后生,谁舍得他走啊!可是天底下没有不落的月亮。月总是圆了缺,缺了再圆啊!”直到这个时候,秋玉才真地相信黄泉路无情,阿光哥在那一头,她却在这一头,中间横隔着一道铁门,一道永远不开的铁门。秋玉不由得轻轻喊道:“阿光哥,咱们……咱们来生来世再见!”她早知道,她应该去开始新的生活了,可是真的要离开 这播下爱情种子的寮房时,她却恋恋不舍地回头,情意缠绵地轻轻念着,“阿光哥,陪侬去吧!你啥时候都为咱寨子好,如今,寨里要干大事,干好事,侬也不能当闲人了。你就伴侬去吧!”
于是,秋玉走向神蛙岭,来到了父老姐妹们的中间。大伙见到她,一齐投过十分关切十分同情的眼光。虽然谁也不同她长谈,只是亲切地喊了她一声。可是秋玉觉得这已经足够了,那一声招呼里包含了她所需要的一切。她点一点头,默默地挑起土来。于是,大伙干得更欢了。挖土的、抬土挑土的、打夯的,加速了节奏,加强了力度。那劳动的场面,仿佛一张浓墨云彩的油画,线条粗犷、浑厚,意境开阔、深远,也如一道“哗哗”流泻的山溪,冲刷着一切情感的沉滓,翻滚着忘我的浪花。很快,秋玉那惆怅,那心底的哀伤,象死寂的潭水融进山泉,象潮湿的山岚消失于斑灿的朝霞面前。
秋玉挑得满满的,来回小跑着,脸上沁出了汗水。李德裕默默地望着她的背影,怜爱、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如此可爱可敬的姑娘,恶运竟一次又一次向她袭击,真不知道她怎样承受得了?李德裕忽然觉得,他是风雨飘摇中的破舟,而她就是冰雪覆盖下的小树。人,秉赋不同,地位不同,学识不同,命运有时却惊人地相似。然而,他挺过来了,她也挺过来了,这些日子来,她一直关怀着李德裕,此刻,李德裕却找不到合适的话安慰同病相怜的姑娘。望着她那瘦削的脸蛋儿,他的心都快憋死了。
秋玉又挑着黄土到了坝基上。李德裕望了她一眼,招了招手,“孩子,快来,帮帮个忙!”
秋玉倒下土,三步两步奔过来,李德裕却说声“孩子,先歇歇”,便去拉拉线,打打桩。秋玉急了,便要挑土去。李德裕这才示意她等一等,慢慢走过来,慢条斯理地说,“孩子,你瘦多了!先歇一会嘛!堤坝也不是一天、二天能筑成的!”李德裕说着,又慢腾腾地抬起右脚,笑一笑,“秋玉,帅公的鞋开了窗,土坷粒、石碎什么的,都来欺负我的脚板。你能不能帮个忙哪?”
“大人,咱有空再给你做双新的。”秋玉苦涩地笑。
“那可不行。这不是要累坏了你?”李德裕想了想,掏出一块麻布,“来,缝缝补补就行了。岐,你可不能蛮干啊。太累了,身子也会开窗开洞的,病邪真会欺负你呐!”
说了老半天,秋玉恍然大悟,李德裕处处为她好,心里也就热呼呼的。她麻利地缝好破洞,才低声说,“谢大人。大人,你也得保重!”
“嘿嘿,我老啦,老了的姜虫不吃,”李德裕强装笑容,“年轻人,身体才最要紧!”
“大人,你还不老,不老……”秋玉喃喃自语,默默挑起粪箕,却回过头,投来关切的目光。
七月的太阳,悄悄爬上南仇岭上那最高的山峰,向着天顶挪动。
李德裕笑着对帕威说,“该让大伙歇歇工了,不然,肚子会告状的!”
“说得是!”帕威跳上一个高土墩上,两手凑成喇叭,“大伙儿歇歇工,不歇工的,瞧咱不敲断你的腿!”
人们放下工具,跑到一株大榕树下,里三层,外三层,围住李德裕和帕威,说着,笑个不停。
可附近几个火堆旁,早忙坏了几个姑娘。她们先挖好一个个土坑,在坑里生起火来。等到木柴都烧成炭,她们才把炭火搞平,在上面盖上一层薄土,再在泥土上面匀匀地放好山莳,然后,又把泥土盖过,再在泥土上面生起大火。火焰上窜下跳的,伸着长舌。突然,帕威说声,“差点忘了大 事!”便离开大伙,跳到火堆旁边。他从腰篓里取出一个叶包,掰开葫芦瓜叶,拿出几块鹿母,串在木叉上,扒出炭火,认真的烤起肉来,他烤肉也有一手。不多久,鹿肉既不生也不焦,恰到火候,冒出香喷喷的味儿,早让几个馋嘴鬼流口涎水。
还愣住做啥?开饭,开饭罗!爱吃粥的吃粥,爱吃山莳的扒山莳!山莳好吃好吃的,别让大吃鬼占了便宜!”帕威一头嚷着,一头却把烤肉藏到背后,活象一个几岁的小孩。
大伙一窝蜂去扒山莳,帕威却乘机走到李德裕身旁,啧啧嘴说,山莳好吃,叫人嘴里吃着,眼里想着,就便宜了他们吧。粥不香,可老人吃得消,几个肉片就凑合凑合啦。
“峒长,你几时学会圆谎啦?还真有两下。幸亏你那眼神泄密,不然,我还真会上当呢!”李德裕“嘿嘿”笑着,“好,你的情我领了。不过,我可吃不消啊。拿几片给秋玉,那孩子瘦多了。峒长,你去吧!”
帕威看到李德裕那个不容违抗的样子,也只好乖乖从命了。
帕威挪近女儿身边,望了她一眼,就低下头。果然她瘦多了。这些日子光顾忙大伙的事,似乎把她忘了。如今瞧她这个样子,帕威心里如扎上针,异常难受。但话到唇边又哽住。他眼圈儿湿了,把鹿肉往秋玉手里一塞,才喃喃地说,“孩子……你吃了吧,身子最要紧!”
“阿爹,你怎啦!女儿好好的!鹿肉拿回去,你吃,给李大人吃!”秋玉死活不肯要。
“孩子,生我的气了?阿爹只顾忙大伙的事,关心你不够,该死!”帕威咒起自己来了。
“阿爹,别说了。你若整天陪住我,就不是好阿爹,寨子里的事要紧,女儿还恨自己呢……”秋玉说着,已是泪光点点。
“我的好女儿!”咱威一把拉过女儿,无限深情地抚摸着她的脸颊,到底悄悄放下鹿肉。
“黎胞们,山里有珍禽异兽,有良材好药,地下埋着金银,藏着珠宝。咱却吃粥,吃山莳,吃野菜,盐巴也难得不断顿。这太不公平了!”李德裕一边吃着粥,一边走到大伙中间。这些天来,他时刻想着的是如何使地尽其财,使人尽其力,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太难了。但怕难,什么也就完了。今天,他就要好好地讲一讲,目下所做的,就是砸开那不公平的枷锁的第一步。有了第一,便有第二、第三……还愁枷锁砸不开吗?
李德裕说着,用黎胞们能听得懂、能接受得了的方式说着。山里人你看我,我看你,那眼神是在说,原来山那边,还有一个天地。而咱正是向那边走去。有人乐开了,几个人用手搭成一座轿,抬起李德裕,乐呵呵地沿着坝基来回蹦着。
“别闹了,别闹了,累坏了李大人,看我不打断你的手!”帕威又高兴又生气的嚷着。
不想,几个调皮鬼却眨一眨眼,跑过来抬起帕威蹦蹦跳跳的,把他甩到半空,乐得大伙都笑了。
日子在黎家人的苦干中一天天过去,神蛙岭下的堤坝一天天加高了。
眼看堤坝快要峻工,李德裕心里好不高兴,每天,他和帕威留在后头,瞧这瞧那,聊起来没完没了。
一天傍晚,他突然拉住帕威,怪神秘地说,“峒长,你听,什么在喊呢?”
“还不是鸟喊,野兽叫?”帕威随口说。
“还有青蛙鸣喊的声音。你听,你听!”李德裕一把拉住帕威。
“大人,这坝一筑成,你都变成小孩子,来逗我了。哪里有青蛙叫?”帕威说。
“峒长,这坝一筑成,挡住山洪,咱们再引水上山,面前是一片田洋,十里稻花香。这神蛙石灵,所以,它喜不自禁地喊了,给咱报个信儿。你真地听不出来?咦?”李德裕笑盈盈,解开帕威的闷葫芦。
“哟,原来是这样!我也听见,听见!”帕威这一回惟恐落后了。
然而,才过一天,李德裕却皱起眉头。
刚才,帕威告诉他,山里蜜蜂做窝都飞到高高的树枝、竹枝上做,他还漫不经心地说,“蜜蜂喜欢哪里就飞到哪里,这不关咱的事!”
“大人,你不知道,蜜蜂搬到高枝上做窝,今年肯定会发大水!”帕威说。
“这是真的?”李德裕脸色一沉。
“假不了,咱们山里人见多罗!“帕威那语气不容有争辩的余地。
“峒长,要真发了大水,”李德裕倒抽一口凉气,眼前恍然出现一幅可怕的画面:滔滔的山洪,象从九天滚滚泻来,浊流千里,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他不禁吃惊地河,“咱这堤坝该怎么办?”
“怕啥?兵来将挡。水来土填!”帕威说。
李德裕不作声,只顾默默地绕着堤坝走,环顾了四周,突然拉起帕威走。
“峒长,让大伙干着,咱们走走,乘山洪没来之前,先给它找出路!”李德裕见帕威还在发愣,再用力一拉。
他们沿着堤坝向北走去。他们走过山岗,走过山丘。那山丘和山丘毗邻的地方露出了缺口。然而,李德裕一望面前有山丘,有平地,摇了摇头,便向前走去。
前面是一个峡谷。山坳露出了嶙峋的山石,石上布满青苔,看来很少有人到过。峡谷自然形式一条溪涧。石缝间淅淅沥沥淌下水珠,汇成汩汩细流,淌入涧底光滑的鹅卵石,发出细碎的叮叮咚咚的声音。
李德裕眼前一亮,攀援着石头、树根,走下峡谷。
“大人,你也要小心,小心!”帕威身不由己,跟着他走。
“峒长,你也要小心!李德裕答应着,望着溪涧的坡度,又折断木棍来比比划划,估量着水的落差。末了,他还不放心似的,攀缘着岸边的树木,沿着溪涧,向下走了好远。
“大人,你这是要走到昌化溪去啦?”帕威紧迫不舍,不解地问。
“溪涧通向昌化溪?”李德裕惊喜地问。
“还不是!”帕威说。
“好,好,”李德裕转回身,“我不走啦,别让峒长跟我受累。”
李德裕果真折回头来。可他不时还问着帕威在那里猎过多少野味,还要帕威带他去打猎,他要给帕威“头弓肉”。
“咱们现在就去!”帕威可上瘾了。
“不,不,”李德裕笑着,“说着开开心罢,望梅止渴嘛。现在咱们有正经事!”
上得岸来,李德裕歇了歇气,捧几口泉水漱洗漱洗,清了清脑儿,提了神儿,这才冲着帕威说,“峒长,我昨夜做了个梦。”
”是梦见遇上沉香格木吧?”帕威问道。黎胞们梦见遇上沉香格,是得了好兆。
“不,恐怕比遇上沉香格要好”。李德裕停了一停,才告诉帕威,他梦见大伙就在峡谷上面修了一道滚水石坝,又从堤坝那边挖了沟渠直通到石坝那里。山洪到来时,水都流来,沿着溪涧跑掉。水位低时,堤坝里的蓄水自然排不出去,只灌溉田洋。
“大人,你又编派我了。这哪里是梦?不过,你想的好!”帕威拍拍脑门,“咱就笨,就不想到这上头!”
“还不好!咱们还要挖沟,把昌化溪引上山来。那样,咱们准能过上好日子!你说是不是这样?”李德裕太兴奋了,握住帕威的手问。
“是,是,”帕威连连点头,“堤坝一完工,咱们就干!”
“先修石坝,再引水上山!”李裕补充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