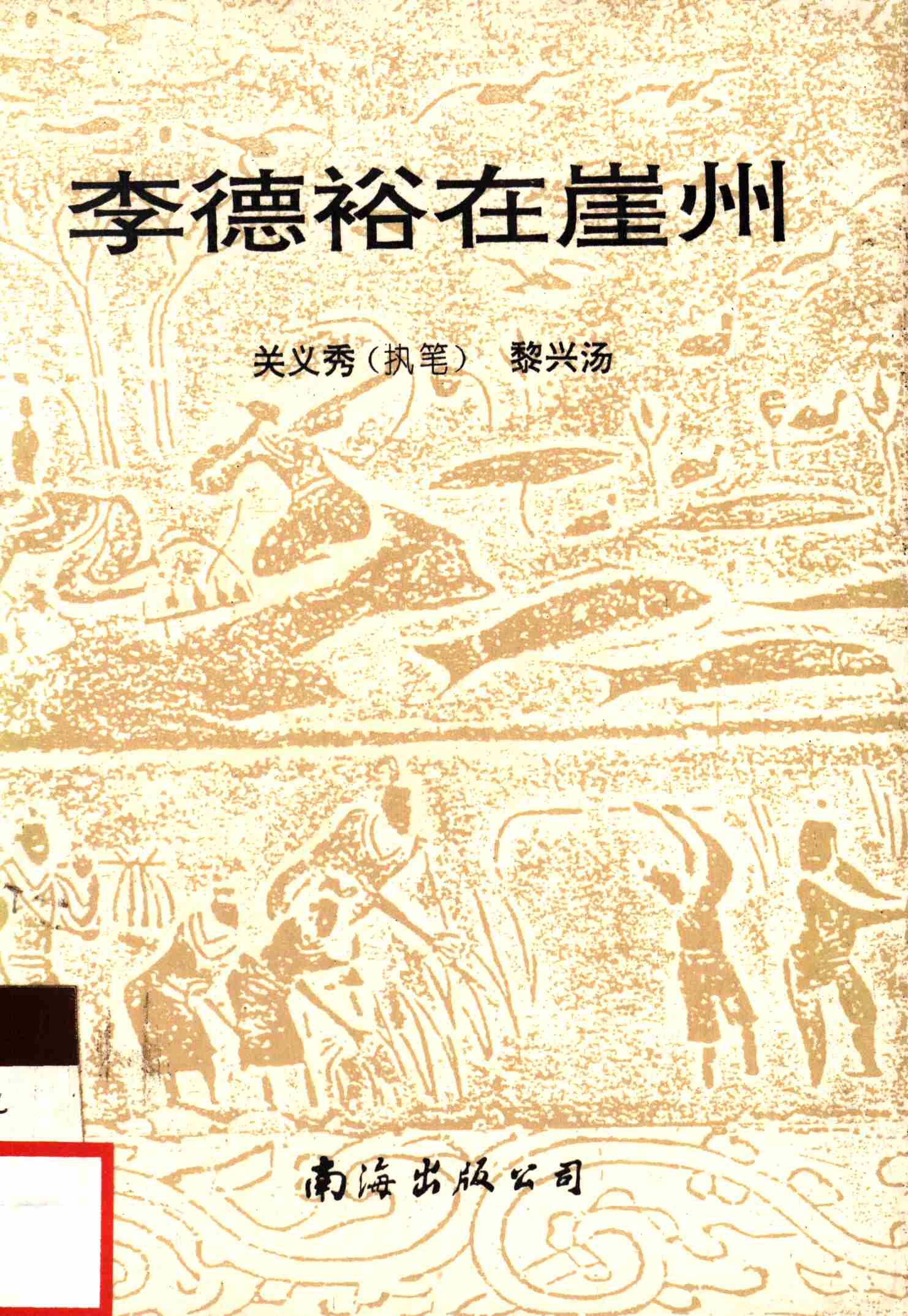内容
秋玉也罢,阿光也好,终究不能说动帕威。二寸大的钉头,容易弯的?李德裕眼见时机不成熟,只好瞧一段再说。南仇岭上山也砍了,园也烧了,人们正忙着播种。也不用犁翻,也不用耙耙,男子赶着雨后表土湿透松软,用削尖的木棍戳穴。脚步是尺,眼光是寸,穴戳得又匀又直。男人在前面戳穴,女人在后面跟着。一手播下种子,双脚便朝穴里埋土。她们种山兰、玉米、木豆,也种蕃薯、木薯。有谁唱起来了:
五月来到好播种,
播下种子心宽松。
咱命今年要变好,
朱满园来谷满笼。
一人唱,百人和,半园人影一园歌。这也难怪,不管是苦,是乐,黎胞们都借歌抒怀,与歌结下无解之缘。
歌声也有停歇的时候。一天响午,大伙在树底下歇着, 要李德裕给他们摆龙门阵。李德裕天天上山,握一根削得尖利的木棍戳穴,天天要应付热心听众,号令古往今来的人物粉墨登场,也算是手下有兵,口中有权的人物了。他本沉默寡言,只因为黎胞殷勤,舌头特别来了劲儿。这一天,他讲的是中原人的饮食穿着,人情掌故。讲者虽是拉家常,娓娓道来,听者却是心花怒放,躁动不宁,飘飘然,徘徊于一个神秘、陌生的天地。
“峒长,不好啦,”突然,一个壮年汉子跌跌撞撞跑上山,一直跑到帕威身边。
“别打岔!不好个屁!”来人冲撞了帕威,他撒野来了。
“峒长,官军来啦!”来人焦急地说。
“官军来了?来得好,咱正要找他呢!李大人,你讲完,咱听了个过瘾,再慢慢收拾他!”帕威嚷着,可一点也不慌忙。
“峒长,官军快到鬼门关了。咱刚才采药见到他们在鬼门关下埋伏,就赶回来向你报告!”
“哟,来得这么快?李大人,下一回再听你讲!先去会会狗官,甭说咱不客气。”帕威冷笑着,拿起山刀,“咣当”两下砍倒一株树,“趁这刀利,把那狗官砍了!”
“对,把狗官砍了!”突如其来的消息象一把火,点燃了人们心头愤怒的火种,个个眼睛冒起血丝,磨拳擦掌,爆发出震撼山崖的吼声。
李德裕默不作声,扫视着崖州城方向,冷峻的目光,象是要穿过层峦叠嶂,骤起的眉峰,正如思绪掀起的浪涛。胡思进,胡思进!你带兵深入黎峒,是奉朝庭之命平黎,还是冲我李德裕而来?难道你利令智昏,才轻举妄动,贸然深入这险绝之地?难道你有机可乘,才倾巢而动?对了,胡思进狡猾之辈不来则罢,一来便有恃无恐。李德裕想着,不禁连想到近日发生的事情。他察觉出,帕威同他一度闹僵,说不定有人从中作祟。虽说这几天已经风平浪静,可一有风吹草动,难保他不受人挑拨,意外情况不可不虑。万一落到成了孤家寡人的地步,自家几个人怎能应战?胡思进的阴谋不就得逞了么?李德裕想着,觉得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心情异常沉重。即使问题不那么复杂,他也宁可把事情看得严重些,以便寻想应变之策,从狭缝中走出一条路来。不管来者是何用意,反正自己跟黎胞是同上一条船了,是同在一道生死线上。自己要考虑周密,绝不让黎胞中了胡思进的奸计。
“峒长,是否再派人探个明白?”李德裕提醒帕威。
帕威说声“是”,立即唤过两个精明汉子,李德裕细细嘱附他们一番。
“官兵来了,不知峒长如何迎敌?”李德裕试探着问。
“咱有的是弓,有的是箭!咱又不是不摸过他的屁股,怕啥?”帕威轻蔑地笑。
“桐长,前一回你们打进州衙,这一回却是他们送货上门。咱们要布下天罗地网,让他打咱打不中,咱一打就打他头破血流!”李德裕说。
“大人,你好好摆布摆布,咱专听大人吩咐!”帕威说完,同众人回到寨里,果然照李德裕的话做,派人到多港峒其它寨子联系,让黎胞都到抱班寨迎战官兵。他还派人去德霞峒,请峒长也来助战。
众人分头行动,帕威正扎好绑带,拿起牛角,准备鸣号出动,突然,帕扣进屋里,鬼鬼祟祟把帕威拉倒一旁,“峒长,我有话对你说。”
“说话?你就不看个时候!”帕威嚷着,“你好好祈求神灵佑护咱们寨子!”
“峒长,咱得了神灵明示,才来禀告于你!”帕扣说得异常神秘。
“哟?那你快说!”
”峒长,只怕说出来,你——”
“别婆婆妈妈的!叫你说,叫你快说!咱没闲跟你磨牙!”帕威瞪大眼睛,那样子,是要下逐客令了。
“峒长,神明示咱,官兵是为为……为李大人而来的!”帕扣说了一句,瞧了帕威的神色,便合上双掌,似乎对天祷告似的说下去,“神明示咱,要交出李大人,寨子才得安全。峒长,李大人对咱这般好。可是神却不容他。这……这该怎么办?”
帕威直盯帕扣,想从脸上找出破绽,识破其中的谎言。但帕威失望了,他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帕扣对神明谟拜,对李德裕无比同情,那令人惊异又不能不信的同情。一时间,帕威如五雷炸顶,脸上失去了血色,眼前昏花一片,恍然现出一个大窟窿,而他自己却把李德裕往那窟窿里推。他猛地擂了擂胸膛,痛苦地喊,“咱又要保住寨子,又要不难为李大人,该怎办,该怎办?”他嚷着,拿到酒埕,仰开埕盖就喝,喝着喝着,又把酒埕往地上一碰,“去你的吧!”吓得帕扣趁机溜了。
李德裕进屋时,帕威还傻呼呼地坐着。
“峒长,你怎么啦?探子回来了,胡思进到鬼门关了!兄弟们在等着你!”李德裕以为帕威贪杯,摇了摇他。
“大人,你不——知——道——”帕威欲言又止,叹了长气。
“峒长,情况危急,有话你就直说!”李德裕觉察事有蹊跷,可还是沉着地催促帕威。
“大人,神让……交出你……寨子……安全……咱怎怎办……”帕威颤抖着,语声断断续续。
李德裕沉思瞬时,凭着他的机敏、果断,已经把断续的地方补充,把明沟暗阱看个十有八九。他猜测得出,狡滑的胡思进已经买通了谁借神的名义蛊惑人心,逼得帕威把人交出。那时,官军便会得寸进尺,攻下寨子。好阴险的毒计啊!他想跟帕威申辩,揭穿胡思进的诡计,可是帕威会听他的吗?帕威会违抗神的意旨吗?不,不可能!如今火已烧到眉毛,跟帕威理论下去,只会贻误战机,惹他反感,最终会众叛亲离,有害无益。李德裕迅速地权衡利害得失,毅然作决定,挺身而出,把天大的担子都挑起来,只要保得寨子安全就行。看胡思进要怎样治罪!谅他也没有那个狗胆。如果他把我李德裕押送上朝庭,我也可据理陈词,洗刷蒙受的不白之冤。纵然皇上不听忠言,我李德裕在九泉之下,也会听到后世人的公论。李德裕神色极为痛苦,语调却极为坚决,“峒长,别害了全寨子的父老兄弟。你就放我出去,看胡思进有何话说!”
“大人,咱又不是黑了心肝,烂了脾肺,让你去去……”帕威揪心裂肺似的嚎叫,底下的话他说不出口。这时,外面的黎胞已荷弓挎箭,磨拳擦掌的等待帕威带他们出击。帕威情急智生,忽然下跪,“事到如今,也不是咱无情啊。就请你到白石洞里一避。你一离开寨子,便是把你交出去了。等咱杀了官军。再请大人回来!”
李德裕扶起帕威,动情地说,“峒长,难为了你。可这怎么行?放我出去,我一个人死了,也不足惜!况且,我李德裕才不傻,让胡思进白白占了便宜!”冷不防,帕威“嗖”地拔出尖刀,凶声凶气地说,“大人不听我的,咱就一死罢了,别争来争去!”
李德裕一时愕然,说不出话来,痴痴地听着帕威吹起牛角。帕威率领一群兄弟出发了,临走前又回过头,望着李德裕。李德裕这才如梦初醒,匆匆说了一句,“峒长,要拖住、困住官兵,再狠狠打他!切勿跟他硬拼!”说完,他就奔出外面,饱含着无限关切,无限忧虑的深情,眼送着黎胞远去,消失在山路之中。然后,李德裕回到家里,把一切家物都收拾好,才带着家人跟着引路的黎胞,到白石洞里安下身来。
快到鬼门关口,帕威停下来,威严地注视着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弟兄们,狗官送上门来了,跟他拼个白对白,红对红!谁怕死,祖宗不饶他!谁杀死那个胡狗官,咱让他当峒长!”这时已是申牌时分。胡思进带着百余兵卒,埋伏在鬼门关下一会了。他一直按兵不动,直到脚步声越来越近,才狞笑着对兵丁说,“你们都不准乱动,专听我的指挥!”
帕威已近在眼前了。胡思进让一个官兵喊道,“黎峒兄弟听住!这次官兵进寨,是奉朝庭之命,专来擒拿李德裕归案。只要把他献出来,剌史大人会重重地封赏你们峒长,封赏你们诸位兄弟!”
“闭上你的臭嘴!”帕威手起箭飞,险些射中喊话的兵丁。眼看头箭落空,帕威一挥手,利箭如飞蝗,呼啸着向鬼门关上射去。胡思进躲在一个大石头后面,朝官兵一指,探出头来的官兵便纷纷卧倒。胡思进暗暗命几个兵丁专射帕威,阿光赶忙拉帕威伏下,待胡思进再探出头,他〓个真切,连发两支毒箭,却被胡思进躲过。帕威左右寻思,不能得手,情急智生,蹬蹬两下爬上树权,居高临下放出箭来。黎胞们也竞相仿效,爬上大树,凭绿枝作盾牌,伺机放箭。刹那间,弓弦响如爆豆,彼落此起,利箭从天而落,防不胜防。胡思进见了这般情景,将令旗一指,前队改作后队、后队改作前队撤退,所有的亲兵都护住他。官兵边打边撤,还把盐包抛在路上,引诱黎胞们上当,得以一个个逃掉。
帕威眼看官兵逃窜了,不禁得意得很,一刀砍在大树上,“亏那狗官两条腿长,不然,咱倒要瞧他脑壳硬还是树头硬!”黎胞们也跟着臭骂官兵。可是,他们一等再等,再见不到胡思进人影。眼看林里渐渐黑了,帕威不解恨地收兵回寨。
黎胞回到半路,帕扣早恭候在路边。他老远就嚷着,“峒长,你打胜了,好,好!你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咱得好好慰劳慰劳你们。咱在寨子里一直求神保佑,神明真灵验,真灵验!”帕扣瞧了帕威那个得意劲儿,一路给他灌迷魂汤,帕威真以为官军都吓破了胆,不敢再犯寨子。刚进家门,帕扣指着一堤山兰酒,一把拉帕威、阿光他们坐下,“峒长,没啥孝敬弟兄们,咱的老本都掏出来了。峒长可得赏个面子!”
于是,他们席地而下,酒到话来。喝着,喝着,帕威掣出尖刀,跳了起来。几个转身斜剌,几回单脚飞旋,寒光闪,人影动,不减当年本色。惹得几个陪酒的黎胞也拿出尖刀,对刺起来。他们跳了喝,喝了跳。秋玉和阿光劝了帕威几次,帕威喝到兴头上,哪里听得进去?他拍一拍桌子,“怕啥?酒是力!咱们喝个痛快,跳个痛快,明天狗官来的话,再杀它个痛快!”帕扣为了凑趣,也扭着屁股跟帕威对刺几下。可他妆神弄鬼惯了,刚摆动几下子,手也哆嗦,脚也哆嗦。帕威有意逗个笑,把尖刀对帕扣胸口直戳过去,帕扣一惊,手一松,尖刀“咣啷”一声落地。于是,笑的捧腹,闹的尽兴。这一夜,山寨里的灯火醉了,星儿醉了,连那平常清凉的空气也是醉醺醺的。
夜深了。黎胞们伴着醉意进入梦乡,只有一堆堆篝火不知疲倦地跳荡。突然,一溜黑影窜入抱班寨,乘着神不知鬼不觉四处点火,才窜出寨外。顷刻间,火舌乱窜,烈焰腾空,一间间低矮的船形屋,形同三月野火吞噬下的小山头,被烧了个焦头烂额。人们听到噼啪噼啪的响声滚起来时,匆匆忙忙收拾身边的东西逃出了火海,却喊天不应,眼睁睁望着自己的坑席变为焦土。
帕威听到喊声,一骨碌滚起来,望到大火仿佛从天而降,一下子怔住了。他来不及查明失火的原因,便奔入嚣张的火海之中。他身不由己,只要听到呼救的声音,就扑进去。直到确信弟兄们都逃出来了,帕威就吹响牛角,让寨子里的老老小小集到一块。这时,人们惊魂不定,寨子外面又传来脚步声。帕威大喊一声:“不好了!”他立刻叫阿光、秋玉带着老人孩子向李德裕藏身的石洞方向逃命,而他自己则带着一群精壮的小伙子殿后。一话刚完,官兵早从黑暗中冲出,见人就砍、就刺。帕威大吼一声,“孩子们、弟兄们,别怕,跟我来! ”帕威四下里一望,哪里官兵多,他就往哪里冲过去。几个官兵瞧他来势凶猛,悄悄闪到一旁。帕威故意大声叫嚷,“狗官听住,咱帕威在此!你来一个,咱杀你一个!你来两个,咱杀你一双!”他拼死拼活,总算掩护阿光他们突围。可是,帕威他们毕竟人少,幸亏黎胞地熟、官军人生,才得以死里逃生。
帕威拖往官军,阿光扶老携幼向白石洞投奔李德裕。他们走在黑暗的山路里,却不时回头遥望寨子,个个唉声叹气,忽然,前面传来了喊声。阿光一顿脚,再有官兵袭击过来,他如何保得住老的小的?万一有个闪失,他宁愿跳入谷里去,然而,来人不是官兵,而是李德浴他们。阿光竟象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伤心地哭了,“大人,官兵烧了寨子……咱们对不住你……”
“孩子,别难过了!”黑喑中,李德裕似乎看到一个个无家可归的人眼巴巴望着自己,投过来殷切的、恳求的目光,他的抱怨早飞到九霄云外,“吾来晚了,让胡思进得逞了!”
“大人,你半夜三更,怎的……”阿光诧异,李德裕怎的知道了一切?
“阿光,李大人身不在,心可放不下寨子呐。他让我潜伏在附近,观察动静。我看到峒长喝得稀巴烂,大伙都喝得大醉,知道其中有诈,就连夜回来报告大人。一切果然不出大人之所料!”说话的是李茂光。
“大人真是神!”
“你们都神,刚去过白石洞,却能在夜里通行无阻!”
山民们惊异之余,不由赞叹说。
“哈哈,你们可不知道,我跟李大人察看地形,去过白石洞两回了。要不,我还能摸黑回到这?”李茂光解释着。
“阿光,你带着大伙到洞里暂时安身,我等几个去接应峒长!”李德裕不容拖延,吩咐大伙分头行动。
“大人,让秋玉去就行了!”阿光思忖一会,恳求李德裕,“让咱跟你们去!就是死,咱也咬那狗官一口,不让他便宜!”
“还不闭上你的臭嘴!”秋玉伸过手去,抿住阿光的嘴巴,嗔怒地说,“你快去快回,捉住那个狗官来给大人叩头,让咱寨子老老小小骂个痛快,打个痛快,再让他做牛做马,还咱的血,还咱的屋!”
说话间,脚步声越来越近。李德裕握住剑,谛听着动静。阿光惊喜道,“大人,峒长来了,大伙来了!”
来人果然是帕威。他寡不敌众,只好趁黑突围,带着弟兄们赶了上来。如今,见到李德裕就在眼前,惭愧、悔恨蓦然而生,“卟咚”一声跪下,声泪皆下地说,“大人,咱委屈了你,咱毁了寨子,咱怎有面目见你?你打我、骂我,好让我减轻罪孽吧……”
李德裕深情地抚摸着他的头、脸,抚摸着他那血迹斑斑的双手,就象一个慈祥的父亲面对着刚从沙场上血战归来的儿子一样。那里面有理解,有赞许,有安慰,有勉励,有宽恕。人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机械重复的动作里面,往往包涵着最复杂的感情,最能表达思想的语言。静默,静默,谁都保持静默。只有善解人意的夜风轻轻吹来,带走沉痛,穿过山路,进入深山老林……
当帕威从那一场感情的风暴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记起什么来了,便呼喊着,“帕扣,帕扣!”可是没人回答,只有深谷那边荡来回音。帕威心里疑团顿生:为啥官军逃窜了,却又半夜里偷偷回来,放火烧了寨子?看来咱一行一动,官兵都知道,可是他怎么这般神通?这不明摆着有人通风报讯?为啥帕扣昨夜卖力地劝酒,现在却逃得无影无踪?为啥寨子里男女老幼都对李大人好,帕扣却眼高眼低的看他?为啥帕扣说官军专来捉李大人,说寨子里容不得李大人?难道帕扣真这么神通?帕威越想,越知道这里面的瓜葛太多了,他受骗上当了。他勃然大怒,“哼,好一个道公!他跑到哪里去了?咱要问问他,神怎不告诉他,官兵要火烧寨子?哼,看他跑到哪里去?”
“峒长,咱们好好计议,怎样打败官兵,怎样反败为胜。其余的事,以后再好好商议嘛!反正,我李德裕是跟大伙同生共死,跟寨子共存亡!”李德裕语气很坚决、果断。
“大人,你就吩咐吧!”帕威流着泪,“咱再说半个不字,咱就是猪狗!”
“峒长,你言重了!”李德裕百般抚慰帕威,这才对帕威、阿光、刘松等,说了他的计策,大家一齐喊好。
一行人摸黑到了白石洞栖身。第二天,一个汉子去德霞峒联系,请他们火速派人到洞里会合,在洞里的忙着制造弓箭,擦亮尖刀,设法弄多一点火药。第三天,德霞峒三十多名精壮汉子到了。李德裕细细嘱咐帕威、阿光,让他们挑选精强的人马,亲自率领队伍到多港间道上雷公嘴那里埋伏,专候胡思进窜回崖州城时陷入罗网。他还派人到各处扬言:“李德裕带领黎人抄新开的山路打到崖州城去了。”调拨停 当,秋玉逗笑着说,“大人,你还恼着阿爹吧?怎么不给自己派个差使干?”李德裕笑了,“我留在这保卫后方,该也是个差使吧?再说,我还是朝庭的命官呢。我还得赏给胡思进一个面子吧!这一回有劳大伙吧!”
胡思进火烧抱班寨,一时未免得意,可是两天来见不到一个人影,不能大功告成,心里又焦躁起来。突然,崖州城来人报告,说李德裕已率领儿个黎峒的人马要打到州衙去。一开始,胡思进还摇摇头,他才不相信李德裕会真的谋反,与官府与朝庭分庭抗礼。可是一寻思,李德裕不这样干,才真是傻瓜呢。他打回崖州城去,为官一方,有何不可?天高皇帝远,朝庭鞭长莫及,也奈何他不得。胡思进轻轻喊一声,“中计,中计!”便派人四处寻找帕扣,却找不到他的影子。原来帕扣已经被胡思进暗暗收买了。连日来,帕扣无孔不入,趁机挑拨离间,其实事出有因。李德裕要引水上山,帕扣钻了一个空子,造成帕威跟李德裕不和,使胡思进贸然带兵深入黎寨。前几夜,胡思进也是接到帕扣的密报,才敢定计纵火烧了抱班寨。可是,帕扣如今到哪里去了?胡思进臭骂奴才一回,无计可施,传令撤军火速奔回崖州城。
一路上胡思进如惊弓之鸟,匆匆逃过鬼门关,才稍稍放下心来。但是,雷公嘴这险阻的关隘现在面前,他的心弦倏地绷紧。山路到了这里又狭窄,又低洼,成了U形的一条细线。两岸的山崖老长老长的伸了出来,上面的怪石、或赤、或朱、或黑,如犬牙,如利剑,如钩,如战,如妖,如魔,人侧身从山崖下面而过,就仿佛挣扎在血盆大嘴里。胡思进惊魂未定,可一听四周并不动静,突然哂笑起来,“李德裕啊李德裕,你曾为统帅,却不谙用兵之道!你若在这里伏一支人马,哼……”胡思进得意起来,便令士兵继续前进。眼着大部分人马都掉进了那“U”字形的底部,刹那间一声传来:“狗官,你跑不了!”接着,号角“呜呜”,山石如骤雨,利箭似飞蝗,直奔官军而去。
胡思进大喊一声,“不好!”先找个地方躲着,才命令士兵射击。可两岸大树遮阴蔽日,怪石丛然成堆,哪里见到一个人影?士兵们只得胡乱朝天放箭。胡思进急了,命几个士兵簇拥着他,企图夺路而逃。然而,那一支支利箭,似乎都长着眼睛,朝胡思进奔去。胡思进突然抢过一个士兵的帽子给自己戴上,让那士兵戴他的帽子。就这样,胡思进混在 人群里,猫着腰,向对面路口爬去。
胡思进眼看要爬上路口,不料想,阿光俨然一位天神从天而下,挡住他的去路,“狗官,哪里去?乖乖跟咱回去!”胡思进假意点头哈腰,却回过身朝两个士兵挥手。阿光脸无惧色,一心一意要把胡思进生擒,好给寨里乡亲消气,好给李德裕解脱罪名。不然,胡思进早死在他的手下。想不到,两个心腹冒死上前死缠住阿光,胡思进乘机溜上路口。阿光一急,挣脱那两个兵丁,同追上来的帕威等人,合力追寻胡思进。他们以为胡思进一定沿着山路走了,就拼命地追,可追过了一段山路,四下里一望还是不见胡思进的影子。帕威几个就在附近寻找,乘机堵住兵丁的归路。阿光心急,独自折了回来,朝山路上边搜寻。果然,狡猾的胡思进并不沿着山路跑去,此刻,他正躲在一株大榕树后,等待官兵赶到。阿光目疾,瞥见了鬼鬼祟祟的胡思进,心里一喜,却并不作声,蹑手蹑脚的绕到他背后。胡思进也见了阿光,拔出长剑,步步逼去,要直刺阿光的心窝。阿光倒退三步,拈上毒箭,猛喝一声,“你不住手,我这毒箭可不留情!”
胡思进望着山路,连声喊,“好,好,我住手,我住手!”阿光掣出尖刀,砍了一根长藤,套了一个圈,便要将胡思进生擒。不料这时,那两个闻声赶到的兵丁举起长枪,向阿光背后刺去,好一个阿光,连中两枪,吃力地撑住身子,咬紧牙关,朝胡思进射出了最后的一箭,才摇晃着身子,倒在殷红的血泊里。
这一仗,官兵伤亡惨重,胡思进却拾得一条命,逃窜回崖州城去。
等到帕威赶回来时,一切都晚了,阿光已安静地闭上眼睛,嘴角边噙住一个遗憾的微笑。帕威猛扒到他的身边,摇着他的双手。帕威不相信阿光会这么狠心地离他而去,离秋玉而去。阿光还有许多事要做,他们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孩子,你快醒来,快醒来呀!但是,帕威再也不能把阿光摇醒了,只有那张英俊的脸面对着青天,只有那殷红的血染红了 山崖,从那青枝绿叶间淌下去……
帕威还是跪在阿光的身边,他嚎啕多少遍了,声音都嘶哑了。他喊不出声来,失神地望着阿光,想起了他们相濡以染的许多往事。突然,他的眼神放亮了:石头上那一株株淡黄色的、只有两个单叶的小草,染了鲜红的血,刹那间叶片全变得殷红、透亮,就是那不曾染血的这种小草,也一样殷红、透亮,就象那鲜活的琥珀薄片。帕威喃喃自语,“孩 子,你显灵了,显灵了!”
这小草后来得了个名字:真金草。真金草永远是那样血红、透亮,在石缝里生,在树底下长,点缀了青翠的山崖。
五月来到好播种,
播下种子心宽松。
咱命今年要变好,
朱满园来谷满笼。
一人唱,百人和,半园人影一园歌。这也难怪,不管是苦,是乐,黎胞们都借歌抒怀,与歌结下无解之缘。
歌声也有停歇的时候。一天响午,大伙在树底下歇着, 要李德裕给他们摆龙门阵。李德裕天天上山,握一根削得尖利的木棍戳穴,天天要应付热心听众,号令古往今来的人物粉墨登场,也算是手下有兵,口中有权的人物了。他本沉默寡言,只因为黎胞殷勤,舌头特别来了劲儿。这一天,他讲的是中原人的饮食穿着,人情掌故。讲者虽是拉家常,娓娓道来,听者却是心花怒放,躁动不宁,飘飘然,徘徊于一个神秘、陌生的天地。
“峒长,不好啦,”突然,一个壮年汉子跌跌撞撞跑上山,一直跑到帕威身边。
“别打岔!不好个屁!”来人冲撞了帕威,他撒野来了。
“峒长,官军来啦!”来人焦急地说。
“官军来了?来得好,咱正要找他呢!李大人,你讲完,咱听了个过瘾,再慢慢收拾他!”帕威嚷着,可一点也不慌忙。
“峒长,官军快到鬼门关了。咱刚才采药见到他们在鬼门关下埋伏,就赶回来向你报告!”
“哟,来得这么快?李大人,下一回再听你讲!先去会会狗官,甭说咱不客气。”帕威冷笑着,拿起山刀,“咣当”两下砍倒一株树,“趁这刀利,把那狗官砍了!”
“对,把狗官砍了!”突如其来的消息象一把火,点燃了人们心头愤怒的火种,个个眼睛冒起血丝,磨拳擦掌,爆发出震撼山崖的吼声。
李德裕默不作声,扫视着崖州城方向,冷峻的目光,象是要穿过层峦叠嶂,骤起的眉峰,正如思绪掀起的浪涛。胡思进,胡思进!你带兵深入黎峒,是奉朝庭之命平黎,还是冲我李德裕而来?难道你利令智昏,才轻举妄动,贸然深入这险绝之地?难道你有机可乘,才倾巢而动?对了,胡思进狡猾之辈不来则罢,一来便有恃无恐。李德裕想着,不禁连想到近日发生的事情。他察觉出,帕威同他一度闹僵,说不定有人从中作祟。虽说这几天已经风平浪静,可一有风吹草动,难保他不受人挑拨,意外情况不可不虑。万一落到成了孤家寡人的地步,自家几个人怎能应战?胡思进的阴谋不就得逞了么?李德裕想着,觉得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心情异常沉重。即使问题不那么复杂,他也宁可把事情看得严重些,以便寻想应变之策,从狭缝中走出一条路来。不管来者是何用意,反正自己跟黎胞是同上一条船了,是同在一道生死线上。自己要考虑周密,绝不让黎胞中了胡思进的奸计。
“峒长,是否再派人探个明白?”李德裕提醒帕威。
帕威说声“是”,立即唤过两个精明汉子,李德裕细细嘱附他们一番。
“官兵来了,不知峒长如何迎敌?”李德裕试探着问。
“咱有的是弓,有的是箭!咱又不是不摸过他的屁股,怕啥?”帕威轻蔑地笑。
“桐长,前一回你们打进州衙,这一回却是他们送货上门。咱们要布下天罗地网,让他打咱打不中,咱一打就打他头破血流!”李德裕说。
“大人,你好好摆布摆布,咱专听大人吩咐!”帕威说完,同众人回到寨里,果然照李德裕的话做,派人到多港峒其它寨子联系,让黎胞都到抱班寨迎战官兵。他还派人去德霞峒,请峒长也来助战。
众人分头行动,帕威正扎好绑带,拿起牛角,准备鸣号出动,突然,帕扣进屋里,鬼鬼祟祟把帕威拉倒一旁,“峒长,我有话对你说。”
“说话?你就不看个时候!”帕威嚷着,“你好好祈求神灵佑护咱们寨子!”
“峒长,咱得了神灵明示,才来禀告于你!”帕扣说得异常神秘。
“哟?那你快说!”
”峒长,只怕说出来,你——”
“别婆婆妈妈的!叫你说,叫你快说!咱没闲跟你磨牙!”帕威瞪大眼睛,那样子,是要下逐客令了。
“峒长,神明示咱,官兵是为为……为李大人而来的!”帕扣说了一句,瞧了帕威的神色,便合上双掌,似乎对天祷告似的说下去,“神明示咱,要交出李大人,寨子才得安全。峒长,李大人对咱这般好。可是神却不容他。这……这该怎么办?”
帕威直盯帕扣,想从脸上找出破绽,识破其中的谎言。但帕威失望了,他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帕扣对神明谟拜,对李德裕无比同情,那令人惊异又不能不信的同情。一时间,帕威如五雷炸顶,脸上失去了血色,眼前昏花一片,恍然现出一个大窟窿,而他自己却把李德裕往那窟窿里推。他猛地擂了擂胸膛,痛苦地喊,“咱又要保住寨子,又要不难为李大人,该怎办,该怎办?”他嚷着,拿到酒埕,仰开埕盖就喝,喝着喝着,又把酒埕往地上一碰,“去你的吧!”吓得帕扣趁机溜了。
李德裕进屋时,帕威还傻呼呼地坐着。
“峒长,你怎么啦?探子回来了,胡思进到鬼门关了!兄弟们在等着你!”李德裕以为帕威贪杯,摇了摇他。
“大人,你不——知——道——”帕威欲言又止,叹了长气。
“峒长,情况危急,有话你就直说!”李德裕觉察事有蹊跷,可还是沉着地催促帕威。
“大人,神让……交出你……寨子……安全……咱怎怎办……”帕威颤抖着,语声断断续续。
李德裕沉思瞬时,凭着他的机敏、果断,已经把断续的地方补充,把明沟暗阱看个十有八九。他猜测得出,狡滑的胡思进已经买通了谁借神的名义蛊惑人心,逼得帕威把人交出。那时,官军便会得寸进尺,攻下寨子。好阴险的毒计啊!他想跟帕威申辩,揭穿胡思进的诡计,可是帕威会听他的吗?帕威会违抗神的意旨吗?不,不可能!如今火已烧到眉毛,跟帕威理论下去,只会贻误战机,惹他反感,最终会众叛亲离,有害无益。李德裕迅速地权衡利害得失,毅然作决定,挺身而出,把天大的担子都挑起来,只要保得寨子安全就行。看胡思进要怎样治罪!谅他也没有那个狗胆。如果他把我李德裕押送上朝庭,我也可据理陈词,洗刷蒙受的不白之冤。纵然皇上不听忠言,我李德裕在九泉之下,也会听到后世人的公论。李德裕神色极为痛苦,语调却极为坚决,“峒长,别害了全寨子的父老兄弟。你就放我出去,看胡思进有何话说!”
“大人,咱又不是黑了心肝,烂了脾肺,让你去去……”帕威揪心裂肺似的嚎叫,底下的话他说不出口。这时,外面的黎胞已荷弓挎箭,磨拳擦掌的等待帕威带他们出击。帕威情急智生,忽然下跪,“事到如今,也不是咱无情啊。就请你到白石洞里一避。你一离开寨子,便是把你交出去了。等咱杀了官军。再请大人回来!”
李德裕扶起帕威,动情地说,“峒长,难为了你。可这怎么行?放我出去,我一个人死了,也不足惜!况且,我李德裕才不傻,让胡思进白白占了便宜!”冷不防,帕威“嗖”地拔出尖刀,凶声凶气地说,“大人不听我的,咱就一死罢了,别争来争去!”
李德裕一时愕然,说不出话来,痴痴地听着帕威吹起牛角。帕威率领一群兄弟出发了,临走前又回过头,望着李德裕。李德裕这才如梦初醒,匆匆说了一句,“峒长,要拖住、困住官兵,再狠狠打他!切勿跟他硬拼!”说完,他就奔出外面,饱含着无限关切,无限忧虑的深情,眼送着黎胞远去,消失在山路之中。然后,李德裕回到家里,把一切家物都收拾好,才带着家人跟着引路的黎胞,到白石洞里安下身来。
快到鬼门关口,帕威停下来,威严地注视着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弟兄们,狗官送上门来了,跟他拼个白对白,红对红!谁怕死,祖宗不饶他!谁杀死那个胡狗官,咱让他当峒长!”这时已是申牌时分。胡思进带着百余兵卒,埋伏在鬼门关下一会了。他一直按兵不动,直到脚步声越来越近,才狞笑着对兵丁说,“你们都不准乱动,专听我的指挥!”
帕威已近在眼前了。胡思进让一个官兵喊道,“黎峒兄弟听住!这次官兵进寨,是奉朝庭之命,专来擒拿李德裕归案。只要把他献出来,剌史大人会重重地封赏你们峒长,封赏你们诸位兄弟!”
“闭上你的臭嘴!”帕威手起箭飞,险些射中喊话的兵丁。眼看头箭落空,帕威一挥手,利箭如飞蝗,呼啸着向鬼门关上射去。胡思进躲在一个大石头后面,朝官兵一指,探出头来的官兵便纷纷卧倒。胡思进暗暗命几个兵丁专射帕威,阿光赶忙拉帕威伏下,待胡思进再探出头,他〓个真切,连发两支毒箭,却被胡思进躲过。帕威左右寻思,不能得手,情急智生,蹬蹬两下爬上树权,居高临下放出箭来。黎胞们也竞相仿效,爬上大树,凭绿枝作盾牌,伺机放箭。刹那间,弓弦响如爆豆,彼落此起,利箭从天而落,防不胜防。胡思进见了这般情景,将令旗一指,前队改作后队、后队改作前队撤退,所有的亲兵都护住他。官兵边打边撤,还把盐包抛在路上,引诱黎胞们上当,得以一个个逃掉。
帕威眼看官兵逃窜了,不禁得意得很,一刀砍在大树上,“亏那狗官两条腿长,不然,咱倒要瞧他脑壳硬还是树头硬!”黎胞们也跟着臭骂官兵。可是,他们一等再等,再见不到胡思进人影。眼看林里渐渐黑了,帕威不解恨地收兵回寨。
黎胞回到半路,帕扣早恭候在路边。他老远就嚷着,“峒长,你打胜了,好,好!你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咱得好好慰劳慰劳你们。咱在寨子里一直求神保佑,神明真灵验,真灵验!”帕扣瞧了帕威那个得意劲儿,一路给他灌迷魂汤,帕威真以为官军都吓破了胆,不敢再犯寨子。刚进家门,帕扣指着一堤山兰酒,一把拉帕威、阿光他们坐下,“峒长,没啥孝敬弟兄们,咱的老本都掏出来了。峒长可得赏个面子!”
于是,他们席地而下,酒到话来。喝着,喝着,帕威掣出尖刀,跳了起来。几个转身斜剌,几回单脚飞旋,寒光闪,人影动,不减当年本色。惹得几个陪酒的黎胞也拿出尖刀,对刺起来。他们跳了喝,喝了跳。秋玉和阿光劝了帕威几次,帕威喝到兴头上,哪里听得进去?他拍一拍桌子,“怕啥?酒是力!咱们喝个痛快,跳个痛快,明天狗官来的话,再杀它个痛快!”帕扣为了凑趣,也扭着屁股跟帕威对刺几下。可他妆神弄鬼惯了,刚摆动几下子,手也哆嗦,脚也哆嗦。帕威有意逗个笑,把尖刀对帕扣胸口直戳过去,帕扣一惊,手一松,尖刀“咣啷”一声落地。于是,笑的捧腹,闹的尽兴。这一夜,山寨里的灯火醉了,星儿醉了,连那平常清凉的空气也是醉醺醺的。
夜深了。黎胞们伴着醉意进入梦乡,只有一堆堆篝火不知疲倦地跳荡。突然,一溜黑影窜入抱班寨,乘着神不知鬼不觉四处点火,才窜出寨外。顷刻间,火舌乱窜,烈焰腾空,一间间低矮的船形屋,形同三月野火吞噬下的小山头,被烧了个焦头烂额。人们听到噼啪噼啪的响声滚起来时,匆匆忙忙收拾身边的东西逃出了火海,却喊天不应,眼睁睁望着自己的坑席变为焦土。
帕威听到喊声,一骨碌滚起来,望到大火仿佛从天而降,一下子怔住了。他来不及查明失火的原因,便奔入嚣张的火海之中。他身不由己,只要听到呼救的声音,就扑进去。直到确信弟兄们都逃出来了,帕威就吹响牛角,让寨子里的老老小小集到一块。这时,人们惊魂不定,寨子外面又传来脚步声。帕威大喊一声:“不好了!”他立刻叫阿光、秋玉带着老人孩子向李德裕藏身的石洞方向逃命,而他自己则带着一群精壮的小伙子殿后。一话刚完,官兵早从黑暗中冲出,见人就砍、就刺。帕威大吼一声,“孩子们、弟兄们,别怕,跟我来! ”帕威四下里一望,哪里官兵多,他就往哪里冲过去。几个官兵瞧他来势凶猛,悄悄闪到一旁。帕威故意大声叫嚷,“狗官听住,咱帕威在此!你来一个,咱杀你一个!你来两个,咱杀你一双!”他拼死拼活,总算掩护阿光他们突围。可是,帕威他们毕竟人少,幸亏黎胞地熟、官军人生,才得以死里逃生。
帕威拖往官军,阿光扶老携幼向白石洞投奔李德裕。他们走在黑暗的山路里,却不时回头遥望寨子,个个唉声叹气,忽然,前面传来了喊声。阿光一顿脚,再有官兵袭击过来,他如何保得住老的小的?万一有个闪失,他宁愿跳入谷里去,然而,来人不是官兵,而是李德浴他们。阿光竟象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伤心地哭了,“大人,官兵烧了寨子……咱们对不住你……”
“孩子,别难过了!”黑喑中,李德裕似乎看到一个个无家可归的人眼巴巴望着自己,投过来殷切的、恳求的目光,他的抱怨早飞到九霄云外,“吾来晚了,让胡思进得逞了!”
“大人,你半夜三更,怎的……”阿光诧异,李德裕怎的知道了一切?
“阿光,李大人身不在,心可放不下寨子呐。他让我潜伏在附近,观察动静。我看到峒长喝得稀巴烂,大伙都喝得大醉,知道其中有诈,就连夜回来报告大人。一切果然不出大人之所料!”说话的是李茂光。
“大人真是神!”
“你们都神,刚去过白石洞,却能在夜里通行无阻!”
山民们惊异之余,不由赞叹说。
“哈哈,你们可不知道,我跟李大人察看地形,去过白石洞两回了。要不,我还能摸黑回到这?”李茂光解释着。
“阿光,你带着大伙到洞里暂时安身,我等几个去接应峒长!”李德裕不容拖延,吩咐大伙分头行动。
“大人,让秋玉去就行了!”阿光思忖一会,恳求李德裕,“让咱跟你们去!就是死,咱也咬那狗官一口,不让他便宜!”
“还不闭上你的臭嘴!”秋玉伸过手去,抿住阿光的嘴巴,嗔怒地说,“你快去快回,捉住那个狗官来给大人叩头,让咱寨子老老小小骂个痛快,打个痛快,再让他做牛做马,还咱的血,还咱的屋!”
说话间,脚步声越来越近。李德裕握住剑,谛听着动静。阿光惊喜道,“大人,峒长来了,大伙来了!”
来人果然是帕威。他寡不敌众,只好趁黑突围,带着弟兄们赶了上来。如今,见到李德裕就在眼前,惭愧、悔恨蓦然而生,“卟咚”一声跪下,声泪皆下地说,“大人,咱委屈了你,咱毁了寨子,咱怎有面目见你?你打我、骂我,好让我减轻罪孽吧……”
李德裕深情地抚摸着他的头、脸,抚摸着他那血迹斑斑的双手,就象一个慈祥的父亲面对着刚从沙场上血战归来的儿子一样。那里面有理解,有赞许,有安慰,有勉励,有宽恕。人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机械重复的动作里面,往往包涵着最复杂的感情,最能表达思想的语言。静默,静默,谁都保持静默。只有善解人意的夜风轻轻吹来,带走沉痛,穿过山路,进入深山老林……
当帕威从那一场感情的风暴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记起什么来了,便呼喊着,“帕扣,帕扣!”可是没人回答,只有深谷那边荡来回音。帕威心里疑团顿生:为啥官军逃窜了,却又半夜里偷偷回来,放火烧了寨子?看来咱一行一动,官兵都知道,可是他怎么这般神通?这不明摆着有人通风报讯?为啥帕扣昨夜卖力地劝酒,现在却逃得无影无踪?为啥寨子里男女老幼都对李大人好,帕扣却眼高眼低的看他?为啥帕扣说官军专来捉李大人,说寨子里容不得李大人?难道帕扣真这么神通?帕威越想,越知道这里面的瓜葛太多了,他受骗上当了。他勃然大怒,“哼,好一个道公!他跑到哪里去了?咱要问问他,神怎不告诉他,官兵要火烧寨子?哼,看他跑到哪里去?”
“峒长,咱们好好计议,怎样打败官兵,怎样反败为胜。其余的事,以后再好好商议嘛!反正,我李德裕是跟大伙同生共死,跟寨子共存亡!”李德裕语气很坚决、果断。
“大人,你就吩咐吧!”帕威流着泪,“咱再说半个不字,咱就是猪狗!”
“峒长,你言重了!”李德裕百般抚慰帕威,这才对帕威、阿光、刘松等,说了他的计策,大家一齐喊好。
一行人摸黑到了白石洞栖身。第二天,一个汉子去德霞峒联系,请他们火速派人到洞里会合,在洞里的忙着制造弓箭,擦亮尖刀,设法弄多一点火药。第三天,德霞峒三十多名精壮汉子到了。李德裕细细嘱咐帕威、阿光,让他们挑选精强的人马,亲自率领队伍到多港间道上雷公嘴那里埋伏,专候胡思进窜回崖州城时陷入罗网。他还派人到各处扬言:“李德裕带领黎人抄新开的山路打到崖州城去了。”调拨停 当,秋玉逗笑着说,“大人,你还恼着阿爹吧?怎么不给自己派个差使干?”李德裕笑了,“我留在这保卫后方,该也是个差使吧?再说,我还是朝庭的命官呢。我还得赏给胡思进一个面子吧!这一回有劳大伙吧!”
胡思进火烧抱班寨,一时未免得意,可是两天来见不到一个人影,不能大功告成,心里又焦躁起来。突然,崖州城来人报告,说李德裕已率领儿个黎峒的人马要打到州衙去。一开始,胡思进还摇摇头,他才不相信李德裕会真的谋反,与官府与朝庭分庭抗礼。可是一寻思,李德裕不这样干,才真是傻瓜呢。他打回崖州城去,为官一方,有何不可?天高皇帝远,朝庭鞭长莫及,也奈何他不得。胡思进轻轻喊一声,“中计,中计!”便派人四处寻找帕扣,却找不到他的影子。原来帕扣已经被胡思进暗暗收买了。连日来,帕扣无孔不入,趁机挑拨离间,其实事出有因。李德裕要引水上山,帕扣钻了一个空子,造成帕威跟李德裕不和,使胡思进贸然带兵深入黎寨。前几夜,胡思进也是接到帕扣的密报,才敢定计纵火烧了抱班寨。可是,帕扣如今到哪里去了?胡思进臭骂奴才一回,无计可施,传令撤军火速奔回崖州城。
一路上胡思进如惊弓之鸟,匆匆逃过鬼门关,才稍稍放下心来。但是,雷公嘴这险阻的关隘现在面前,他的心弦倏地绷紧。山路到了这里又狭窄,又低洼,成了U形的一条细线。两岸的山崖老长老长的伸了出来,上面的怪石、或赤、或朱、或黑,如犬牙,如利剑,如钩,如战,如妖,如魔,人侧身从山崖下面而过,就仿佛挣扎在血盆大嘴里。胡思进惊魂未定,可一听四周并不动静,突然哂笑起来,“李德裕啊李德裕,你曾为统帅,却不谙用兵之道!你若在这里伏一支人马,哼……”胡思进得意起来,便令士兵继续前进。眼着大部分人马都掉进了那“U”字形的底部,刹那间一声传来:“狗官,你跑不了!”接着,号角“呜呜”,山石如骤雨,利箭似飞蝗,直奔官军而去。
胡思进大喊一声,“不好!”先找个地方躲着,才命令士兵射击。可两岸大树遮阴蔽日,怪石丛然成堆,哪里见到一个人影?士兵们只得胡乱朝天放箭。胡思进急了,命几个士兵簇拥着他,企图夺路而逃。然而,那一支支利箭,似乎都长着眼睛,朝胡思进奔去。胡思进突然抢过一个士兵的帽子给自己戴上,让那士兵戴他的帽子。就这样,胡思进混在 人群里,猫着腰,向对面路口爬去。
胡思进眼看要爬上路口,不料想,阿光俨然一位天神从天而下,挡住他的去路,“狗官,哪里去?乖乖跟咱回去!”胡思进假意点头哈腰,却回过身朝两个士兵挥手。阿光脸无惧色,一心一意要把胡思进生擒,好给寨里乡亲消气,好给李德裕解脱罪名。不然,胡思进早死在他的手下。想不到,两个心腹冒死上前死缠住阿光,胡思进乘机溜上路口。阿光一急,挣脱那两个兵丁,同追上来的帕威等人,合力追寻胡思进。他们以为胡思进一定沿着山路走了,就拼命地追,可追过了一段山路,四下里一望还是不见胡思进的影子。帕威几个就在附近寻找,乘机堵住兵丁的归路。阿光心急,独自折了回来,朝山路上边搜寻。果然,狡猾的胡思进并不沿着山路跑去,此刻,他正躲在一株大榕树后,等待官兵赶到。阿光目疾,瞥见了鬼鬼祟祟的胡思进,心里一喜,却并不作声,蹑手蹑脚的绕到他背后。胡思进也见了阿光,拔出长剑,步步逼去,要直刺阿光的心窝。阿光倒退三步,拈上毒箭,猛喝一声,“你不住手,我这毒箭可不留情!”
胡思进望着山路,连声喊,“好,好,我住手,我住手!”阿光掣出尖刀,砍了一根长藤,套了一个圈,便要将胡思进生擒。不料这时,那两个闻声赶到的兵丁举起长枪,向阿光背后刺去,好一个阿光,连中两枪,吃力地撑住身子,咬紧牙关,朝胡思进射出了最后的一箭,才摇晃着身子,倒在殷红的血泊里。
这一仗,官兵伤亡惨重,胡思进却拾得一条命,逃窜回崖州城去。
等到帕威赶回来时,一切都晚了,阿光已安静地闭上眼睛,嘴角边噙住一个遗憾的微笑。帕威猛扒到他的身边,摇着他的双手。帕威不相信阿光会这么狠心地离他而去,离秋玉而去。阿光还有许多事要做,他们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孩子,你快醒来,快醒来呀!但是,帕威再也不能把阿光摇醒了,只有那张英俊的脸面对着青天,只有那殷红的血染红了 山崖,从那青枝绿叶间淌下去……
帕威还是跪在阿光的身边,他嚎啕多少遍了,声音都嘶哑了。他喊不出声来,失神地望着阿光,想起了他们相濡以染的许多往事。突然,他的眼神放亮了:石头上那一株株淡黄色的、只有两个单叶的小草,染了鲜红的血,刹那间叶片全变得殷红、透亮,就是那不曾染血的这种小草,也一样殷红、透亮,就象那鲜活的琥珀薄片。帕威喃喃自语,“孩 子,你显灵了,显灵了!”
这小草后来得了个名字:真金草。真金草永远是那样血红、透亮,在石缝里生,在树底下长,点缀了青翠的山崖。
相关人物
李德裕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