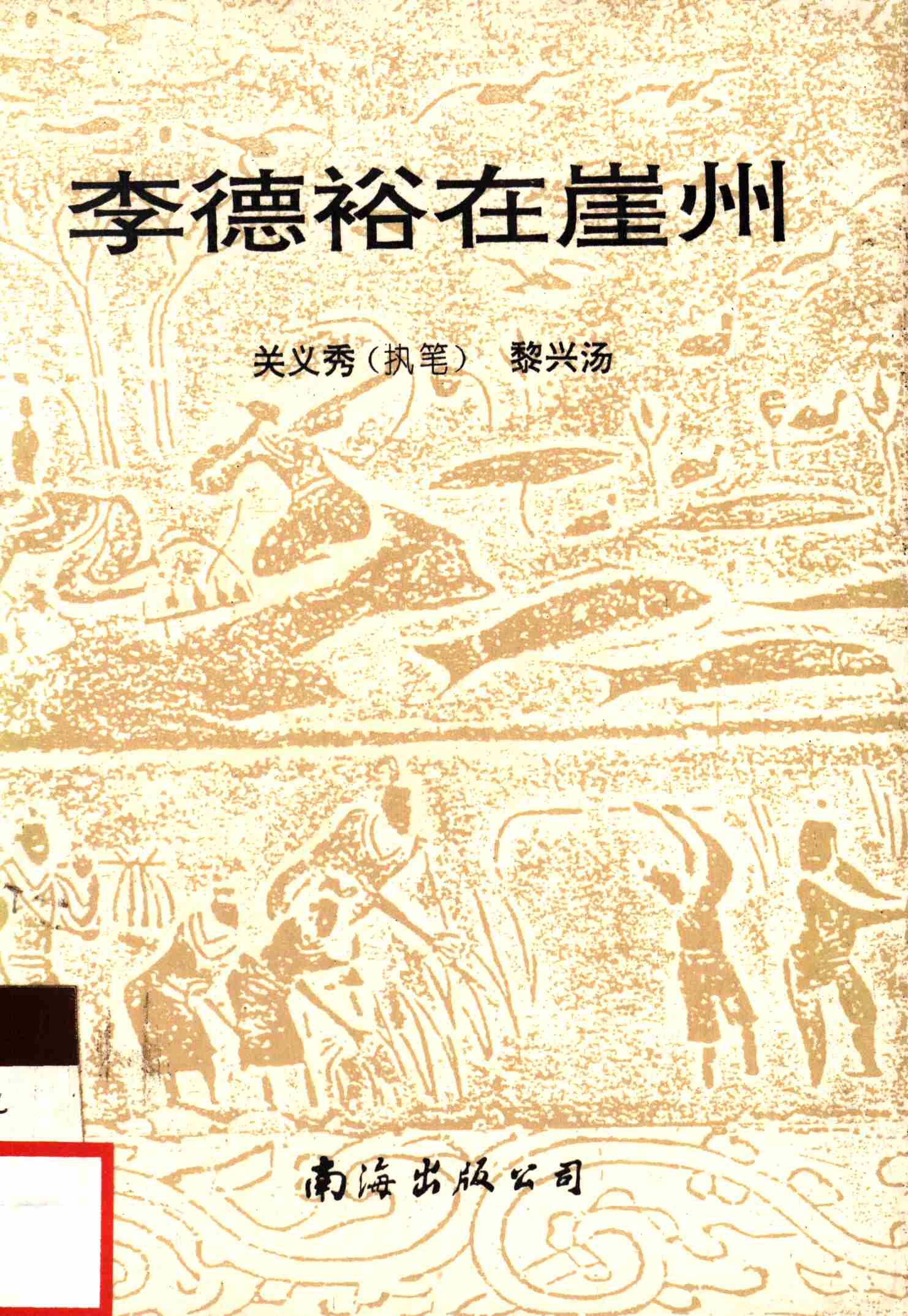内容
砍倒树一片,
再放火烧山。
种下包麦种,
还要种山兰。
日日不得闲,
三顿断两餐。
怨天不公道,
咱们多愁烦。
……
粗犷、高亢、悠婉的歌声,倾吐着怨艾、悲愤,伴着叮叮咚咚的砍伐声,从树顶上飘出去,从杂枝间飘出去,在南仇岭半山腰、低谷间迥荡着,迥荡着。五月的骄阳烤得石头上直冒青烟,烤得黎家人酱赯色的背脊流油。他们把蓝天当帽,把树枝当帽,把笠大的葵叶当帽。肚子饿了,胡乱塞进些山莳、野菜,汗流干了,捧口泉水就喝。可是,歌是从心里掏出来的,却掏也掏个不完,伴着砍伐声惊跑林间野兽, 惊飞丛中鸟儿。
帕威砍山来了,秋玉也砍山来了。帕威还真心疼女儿嫩葱葱的皮肉,死活要她呆在家里,秋玉哪里肯依?黎家男子砍山时,女人得停下手中针线。据说不这样,男人爬树便要碍住手脚,摔个半死半活的,可就难说了。再说,大伙都上山来,自己呆在家里,不就往闷葫芦里钻?秋玉宁愿晒成个火炭人儿,也要跟大伙累在一块,笑在一块。帕威拗不过她,只好依了。秋玉不能象阿爹那样爬在树上,砍倒这株, 又攀上那株。她砍杂枝,砍小树,也忙得手不停,脚不歇。当然,她也有放下活儿,驻足侧耳的时候。这不是别的,是那诱惑的歌声飞过来了:
不砍大树砍小树,
只砍旁枝留树冠。
让鸟儿做窝,
让鸟儿成双。
让千年老藤,
一直往上窜!
心上人儿哟,
你也快来攀。
秋玉顺着声音望去,眼睛放亮了。这不是阿光哥吗?他象一个猴子骑在一株黑格树上,一边砍倒树枝,一边探出头来,卖力地唱着。秋玉心里“呸”了一声,你就是眼睛尖利,瞧见咱在这儿,故意唱给咱听!才两天不见面了,心肝都给猫抓得发痒!近来,秋玉恨他,可怜他,也越发爱他。李夫人都过七了,阿光才空着双手回来,秋玉真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寨子里的人也似乎怨他,阿光竟果真躲了起来, 说是没面目见人。这一回,秋玉又恨起自己来了。那仙水是阿妈的阿妈说的,谁知道真有还是假有?就真有仙水潭,谁见到?这不是到海里去捞针吗?阿光哥肉都掉了十斤,脚板都磨破两层皮才回来,他是要找到仙水啊。秋玉这一想,千怪万怪,只怪自己心眼儿偏,便向阿光赔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是。然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秋玉又恨阿光来了。她想不通,李大人够难受的了,咱恨不能跟他分些痛苦。咱多给他问安,多给他打些柴火,也是合人情道理的嘛。也不碍谁的手,碍谁的脚。阿光哥你也是愿李大人好,帮不了他忙,你为啥对咱斜着眼睛?你心眼儿就是大不过针眼儿。恨归恨了,秋玉细细寻思,阿光这全是为了她,向着她呀。一想到这,秋玉气都消了,要罚罚他的念头也消了,只可怜他青梅树不成坡垒格,只爱他如自家的疮疤自己疼一样。因此,这会儿听到阿光的歌声,秋玉踮起脚尖,脸朝阿光那边唱起来了:
鱼儿爱深潭,
鹿儿爱青山,
兔儿爱嫩草,
雀儿爱山兰。
峰高有云缭,
树大有藤攀,
石厚有崖恋,
哥好有姝跟。
别做龙眼树大生小籽,
别做鸡不吹箫嘴巴尖,
别做木棉皮青肚内白,
别做椰子生肉不生仁……
“唱得好,阿玉。”李德裕悄悄站在秋玉背后听了一会,夸了秋玉,又对同来的帕威说,“峒长,阿玉手巧心诚,好,好!你有福气呀!”
“李大人……你……你怎的也上山来?这不苦了你嘛!”秋玉羞红了脸,到底关切地问。
“苦,苦,大伙都苦得,我却苦不得,这还象个理吗?阿玉,你也别小嘘人啰!”李德裕爽朗地笑道。
“大人,你就是不听咱的。咱是握惯了山刀把,可你,你是捏惯笔头的呀!有我帕威吃的,就有大人喝的。大人在家唸诗作对,咱来供养你,心里才舒服!”帕威蛮不服气的。
“峒长,在家人都憋出病,还能念出诗来!你看,我一上山就拾到好诗,”李德裕说着,念起来了:
别做龙眼树大生小籽
别做鸡不吹箫嘴巴尖
“大人,你,你又瞎编人!”秋玉娇嗔地笑。
“不是瞎编,咱们是说正经的。你们都叫我‘大人’, 我就要成大人的样子。不然,就是龙眼树了。你们说,是不是呀?”李德裕摊了摊手。
说话之间,周围的黎胞都放下手中活计,阿光早从树上跳下来,围在李德裕身旁。这时,一个黎胞调皮地说,“大人,从今天起,咱们砍山,你就包烧山,好吧?”
“这容易,容易,东风随我意,一把火烧山!我要把大伙吃的穿的,全给包了!”李德裕故作神秘地说。
“大人,还会说笑话儿呢。”有人乐了,直拍拍手掌。
“哟,你们是说我瞎吹?嘿,别看我老了,早年可学过法术,神通广大的法术。如今这法术可派上大用场了!”李德裕说得一本正经的。
“哟,大人还真神呢!”
“可不,李大人治那山贼,就凭着那法术呢。怪不得歹徒不敢作孽!”
“嘿,大人,你也别葫芦里卖膏药呀!什么法术,也得说来见识见识,让大伙高兴高兴!”
大伙还真是七嘴八舌的。
“不过,大伙都得听我的,这法术才灵验。”李德裕望着一张张兴奋的脸,便绘声绘影地说了:他一招手,山神就俯首听命,传令给各路大土神、小土神,一个个要恭候两旁,给河神鸣锣开道,接驾引路;二招手,河神也乖乖听话,吩咐昌化溪里的虾兵蟹将,大大小小一群水族,拥着水珠,摇着浪花,大摇大摆从南木岭里峰拥而上……说着,说着,李德裕忽然停下。
“大人,你果真有这天大本事?那你快说,接下说呀!”黎胞们听到过瘾处,自然急于知个分晓。
“哎哟,大伙这一打岔,河神跟我讨价还价来啦!”李德裕捋一捋胡须,笑咪咪地说,“这一回,可得请大伙帮个忙啰!”
“这还用说!咱让帕扣唸经,杀三头牛、六头猪祭他!”帕威挺认真的。
“不行呀!”李德裕煞有其事地说。
“咱再供他香米饭、山兰酒,哪位神仙不吃耙!”有人说。
“还不行!”李德裕依然摇头。
“那……那咱织一幅黎锦,请他坐在上面,八个阿哥抬他,还抬不动他吗?”秋玉已有点急不可耐了。
“阿玉,算你说得还差不多。其实,河神也不要咱抬他。他一帮人马,要走得体面些,求咱给修条大路,”李德裕一边说,一边用两手比比划划,”他一来到咱家门呀,多港峒里年年风调雨顺,南仇岭上种下的玉米啦、山兰啦,也犯不上怕毒日晒,坡头坡尾全都种上庄稼。到那时,咱们一日三餐醉,餐餐醉山兰。大伙,你们说,修修路可值得吧?”
大伙心头热呼呼,入了神,谁都不答腔。
“大人,你这一比一划的,不就是要修条沟吗?”阿光沉思着,琢磨出了条条道道,”“你是说,让咱把昌化溪水都引上山来,是吧?”
“哎,阿光说得对呀。对,对,修沟就修沟,只要修来个肚子饱,就行!”黎胞们人呼雀跃的嚷。
“阿光,你还真聪明哩。这一回,就看你们后生哥抖出个威风来啰!”李德裕拍拍阿光的肩膀,“后生哥,你说呢?”
“咱是专听李大人的。修沟的事,咱……”阿光跃跃欲试的,突然话塞。
大伙一楞:帕威正拉下脸来,默默的不说话。一个个也就象蔫了的瓜秧,提不起神来。这也难怪。俗话说,过水看头人。多港峒里,帕威的话比圣旨还灵着呢。帕威不吭声,谁还敢放气?
李德裕心里喊一声;糟了,多港峒里破天荒的大事,自己也不先跟峒长通通气,乘着兴头捅了出来,可要惹来麻烦。错就将错就错。自己从来不吃后悔药。树尾先动,树头就不动?于是,他就对着帕威说,“峒长,我光动嘴皮儿罢了。这力气,得大伙出。大伙正等着峒长的吩咐呢。”
帕威不答腔,只顾狠狠捏碎土坷粒。
“阿爹,你说话呀,快说话呀!”秋玉轻轻拂拭着帕威手上的尘土,“李大人还不是为了咱们好?”
“这事儿,是件大事呀,峒里没有过的大事!”帕威怔怔地望着地面,自言自语。
“是呀,是峒里没有过的大事!”众人一齐附和着。
李德裕不再说了,只顾默默地望着那一张张酱赯色的脸,望着那一双双渴望的,却又是困惑的眼睛。他想从那里寻找理解,寻找支持。他觉得什么都寻到了,什么又都失去。他明白,黎家人在这片土地上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些人习惯了,仿佛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就象太阳从东边出来又从西边落下去一样的天经地义。有些人想冲出去,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却怕绊了跟头,摔伤了胳膊,折断了腿。帕威犯了什么禁忌,李德裕心中也拿不准。但他知道,让黎家人开沟挖河,并不比上几道奏章容易。然而,他不能无动于衷,坐视百姓在一潭死水中度日。他从政多年,一生以救济天下苍生为职责,如今身居黎山,体味到百姓如何在贫困、饥饿中挣扎,才知道自己的政治抱负只是半句空话,“皇恩播九州”这一句话,实在只是大臣们冠冕堂皇的颂辞罢了。而在日子的艰难中,黎胞们却伸出了慷慨的、无私的手。他们饿着肚子,也要把吃的、用的掏出来,塞到李德裕的手里。当他含着泪花接过一块黄猄肉、接过一碗玉米粥、接过一担木柴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在颤抖地呼喊:我李德裕欠了黎胞一笔债呀!以前他信奉孔老夫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现在很清楚,等到“在其位”再来“谋其政”,恐怕来不及了。为着报效皇上,报效天下苍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李德裕这些日子一直在想,他该给黎胞们做点什么。他隐隐觉得生命的灯火快要熄灭了,但越是意识到这,就越产生强烈的欲望,要积聚最后的力量,放出夺目的光辉。有了这个念头,一切偷生的、息事宁人的想法,都从胸臆中逍遁,一切畏难的情绪都退避三舍,一切坏的结果都考虑到了。因此,李德裕沉思一会,便笑着对帕威说,“峒长,这天大的事情咱们再好好商量嘛。来,我来砍山!”于是,大伙也慢慢散了。
李德裕瞄住一株黄槐树,捲一捲袖口,站了个弓步,挥起山勾刀就要向树茎底部砍去。可是,刀落下时,刀勾划了划树皮便弹了回到面前。在一旁砍树的帕威走过来,嗡声嗡气地说,“大人,这不是闹着玩的。你歇着吧!”李德裕解嘲似的笑着,“这山刀还不如长枪好使!”其实,他是心疼,一株大树好端端的,要当作柴火烧了,才砍个歪着。但他不肯说出来,怕惹大伙笑话。他暗暗发誓,一定要砍倒大树,不然,他就要矮人三寸的。李德裕谢过帕威,又砍起树来。他站着砍,蹲着砍,往上砍,往下砍,左砍右砍,虎口震得起了几个血泡,终于砍倒了大树。阿光眼尖,望见李德裕砍倒了大树,吆喝几声,使劲唱起来:
砍哟,砍哟,
砍倒千年老树哟嗬咳,
砍倒万丈古藤呦嗬咳,
砍出一条新道哟嗬咳。
往年黎家自己砍,
今年风光大不同。
李大人跟咱砍山呦嗬咳,
七月包谷堆成岭呦嗬咳……
阿光一唱,小伙子跟着唱,姑娘跟着唱,帕威也跟着唱,唱了个山谷来风,群情振奋……
然而,一回到家,秋玉问起修沟的事,帕威却白了她一眼,不耐烦地嚷,“问个啥?你懂什么?”一连几晚,他总独自喝着闷酒。
一天晚上,帕扣来了,帕威低着头,似乎不把他的到来当一回事。
“怎啦,峒长,一个人喝着?”帕扣弯腰低头,挤眉弄眼地踅到桌旁。那样子是说,你便不请我,我也自己来。帕扣给帕威添满一碗,再给自己倒满一碗,摆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峒长,你吃了豹子胆,托大啦?连我进来,也给一张冷凳。”可是帕威依然不理他。帕扣讨了个无趣,便挟起一块山鸡肉,吞进嘴里又吐了出来,津津有味地折腾,无话找话说,“好吃,好吃!峒长就是好手段。哦,峒长今儿不高兴,该是让一只坡鹿逃了?要不,咱兄弟俩就喝喝到星儿落下碗里。”
“喝,喝,你就知道喝!”帕威干脆把自己的酒碗都推到他面前。
“哟,峒长,好大的火气!”帕扣捂捂鼻子,表示他的愤慨,两只三角眼同时也在帕威脸上搜寻什么。突然,他恍然大悟似的直点头,“怪不得……峒长你……我看出来“你看出啥?”帕威有点急不可捺。
“嗨,不说也罢……”帕扣摇了摇手。
“你不说?你敢不说?快说,叫你说,你就快说!”帕威汹汹然地嚷。
“好,我说,我说!”帕扣润了润喉咙 半昧住眼睛,嘴皮一张一闭的,半响才吭出声来:“峒长,你你气色不好,凶星缠上你啊!峒长,你是一峒之长,只怕你灾星不脱,咱峒里也要有血光之灾呀。”
“你说,凶星怎来的?”
“这……这几天我不在寨子里,寨子里出了什么事,我也说不准。幸而灾星缠身不久,峒长你你啥事都留点神,我再给你求福,会消灾脱难的,”帕扣说着说着,扳了扳指头,诡秘地朝帕威眯了眯眼,”峒长,咱黎家的规矩一条一条都犯不得,咱黎家的山头一个一个都动不得,南仇岭上的神蛙石千万动不得啊!它可是多港峒,是咱抱班寨的命脉啊!”
“这是真的?这都是真的?”帕威脸色由红转青,由青转白,声音也微微发抖。
“桐长,咱啥时候不是为你好,为寨子好,谁存心骗你?谁骗你,谁就是——”帕扣一话未完,帕威伸过手掌猛然捂住他的嘴巴,“谁让你咒了自己?”
这一夜帕威躺在床上不曾合眼。
他走一山看一山似的一路想起帕扣,想起帕扣今晚说的话来。帕扣倒是护着咱呢。十几岁那年,帕威挑一担玉米过溪。刹那间,岭顶上炸了几个响雷,乌云盖过山头,山雨噼噼拍拍来了,山水滚滚而下。冷不防,已过溪中央的帕威被卷进旋涡里。他偏舍不得甩掉担子,在浊浪里死死挣扎,眼看就要被大水吞没。幸好帕扣也从对岸的小路赶到总路口,一见这情景,二话不说,只身跳入激流,把帕威连人和担子推上岸边。这些年来,帕扣开口不离神,闭口不离鬼,可他是道公啊,也难怪他。帕扣酒是贪喝,有几回还跟晒经坡墟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的混,大概是混碗酒喝,没啥。帕威想来想去,还是认准帕扣真心为他好,不由寻思黎家一条条规矩。族有族规,有奸情的,奸夫不是毙命,也要罚酒罚猪,当众认罪。家有家法,竹都分个上节下节,长幼之间的礼节,乱来不得。可帕威细细想来,族规、家规大的小的,他从来不触犯。谁敢说他半句不公道?对了,一定是李大人要修沟的事,让上天知道了,要降罪下来了。李大人呀,你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得咱黎家的规矩。山神、河神,谁敢动得他一根毫毛?放火烧山种山兰,自古至今有谁种出啥来?种出稻米,祖宗也不认你。那天咱不吭声,是碍住一层脸皮,别让你大人难为情。可你那天比比划划,比出了沟沿,不就比出来一条长蛇,冲犯了神蛙石,那还了得?李大人呀,咱也不是冤了你,道公分明也这么说。你可叫我怎办?
清晨,乳白色的雾气从山林、深谷、寨子那边滚滚升腾,那绿树,那小室,浮动在这流动的浆液里,若隐若现。而神蛙岭这边低矮,多是小山丘,雾气就淡些,就薄些。在一个小山丘半腰,一堆丈把高的石头拔地而出,凝神细看,它纤毫不爽,酷似一个巨大的青蛙。那青蛙昂头蹲着,嘴巴半张,宛然对着寨子翘首待鸣。在田园诗人的笔下,雾气下的山谷、村寨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田洋,而这青蛙,就是来自田洋里的使者,预报着丰收的喜讯。帕威身披白雾踏着露珠来了,来到大石跟前,脚步放得很轻很轻,眼里贮满不容亵渎的异样的光彩。他突然“卟咚”一声跪下,两掌齐放胸前,虔诚地轻声念着,“神灵保佑,神灵保佑。”他一直跪着,谛听神灵发出什么训谕。可四周静悄悄的,神蛙石不说话,连飞鸟也不来报个讯儿。他就一动也不动地跪着,跪到太阳爬过山头好高好高。这样,雾淡了,散了,千树万树披 上金色的流苏。神蛙石在阳光的照耀下,也仿佛身披那金色的流苏。帕威眼冒金花,心里惊喊,“这可是灵光?一道一道的灵光!神蛙石真灵啊!”他连忙拜了九拜,让赶来的大伙也跟着跪拜。
帕威跪拜完毕,连饭也顾不上吃,就跑到山兰园里去了。他挨个走到黎胞身旁,汹声汹气的就是一句话:“从今天起,谁也不准提开沟的事!”
一句话,却象严冬里一声闷雷在寨子里炸裂,人人惶恐,不安,郁闷,困惑。从上午到下午,从傍晚到黄昏……
月亮从山脊上爬上来了。溶溶山月,把寨子泡在轻柔的世界。要是平时,缠绵绵的乐器声、对歌声,早同月光把寨子泡得酥软酥软。可是今天晚上,寨子里却静静的,静得令人透不过气。
秋玉三扒两扒吃过晚饭,就到寮房呆着。她心里都烦死,却不见阿光来。不一会儿阿光来了,她劈头就问,“你到哪里死去了,今儿才转生?你难道害了笑病,一点正经事儿也不管一管?”
阿光知道她骂啥,对不了她爹,就来骂他,正是对不得坡上鹿却来管栏里猪。阿光心里才急呢。李大人好心不得好报,阿爹他……唉,帕扣不该来装弄神鬼,来添油添火!他那张阴阳脸看起就叫人恶心,那扭扭捏捏的样子,就会让人长鸡皮疙瘩。可是阿光也没办法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嘛。阿光正是找秋玉商量商量,不想一进门就挨骂。但他明知道秋玉是一片好心,并不计较她,却故意逗她,“骂吧,骂我遭瘟,谁来陪你?”
“你坏,你坏,都啥时候了,还闹着玩?”秋玉刮了阿光一下嘴巴。
“谁闹着玩?咱不是想出个办法来了吗?只要治得帕扣,阿爹就……阿光凑到秋玉耳朵旁,嘀嘀咕咕一阵。
明天阿光要到德霞峒那边打猎。他打得坡鹿,一定送“头弓”给帕扣,不过,得悄悄对他说,那只鹿是养在“插星”岭里的,养给天神享用的,看看帕扣这只猫还吃不吃腥。这样……
“好,好,要是帕扣露了馅,阿爹就不会被他迷住!”秋玉一高兴,竟象一个孩子似的跳起来。
“这是正经事吧?”阿光有意讨好恋人。
“还有正经事,咱们去看看李大人,别让他给闷住!”秋玉恳求起阿光来啦。
“我不听你的!”阿光说完,却拉着秋玉走出了寮房。
李德裕的屋子就在眼前了。灯光透出来,桔黄色的灯光虽然不那么明亮,可是它照出了一尊浮雕式的身影。他面对着一盏海棠油灯,面对着一张草图,兀然端坐,使人想起山峰在月色下勾勒着庄严,勾勒着凝重,阿光和秋玉想见到他,又怕见到他,一步一步椰近窗前。他们瞥见了,那草图上面画着——那一堆一堆的,不就是山岭吗?那弯弯的,从山里穿过的不就是溪吗?对了,那是寨子,那象盆一样凹下去的,不就是寨子前面那一块盆地么?对了,李大人想什么,全在纸上画出来了。两人心里一热,李大人在琢磨着挖沟的事儿!突然,李德裕叹息一声,捧着那张草图,“把你烧了!”
“大人,烧它不得.烧它不得!”阿光和秋玉奔进屋子,不约而同地喊。
李德裕一望深夜这不速之客,惊喜地喊,“哟,阿光,秋玉,来,坐,坐!”
“大人,可委屈了你,都怪咱阿爹不好……”秋玉难为情地说。
“傻孩子,说到哪里去了?峒长怎的不好?峒长不好,能容得我住下?因为我念着峒长好,才想出点力,来报答峒长,报答大伙。喝了寨子的水,吃了百家饭,也要给你们留点什么,让大伙,让后人都说我不白到过这里。我只盼着我能有这一天!”李德裕说着,说着,真的动情了。
“大人,阿爹一时糊涂,你可别怪他!”阿光陪了笑脸。
“孩子,这不叫糊涂。走路惯了,就有马骑,也怕摔下来,得一瞧再瞧。你们送我茶,又甜又香又补身子,我开始还真不敢尝尝。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东西 难怪峒长一时转不过弯来。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李德裕说。
“哎,是呀,大人看透了咱的心事。只是,咱总觉得李大人为咱好,大人要咱怎办,咱就要跟着办,”秋玉想了想,撒起娇来,“阿爹,他会想通的。你不该要把它把它毁掉!”
“生我的气啦,秋玉?”李德裕笑着问。为了这张草图,李德裕悄悄察看昌化江,走遍了南仇岭大山头小山头,名为观赏风光,吟诗作对,实际是一步一步考虑如何把江水引上山来。他哪里肯把心血付之东流?刚才,他一时心烦,说了一句丧气的话,却被秋玉听见。当下,他认错似的对两人说,“我赔个不是,好吧?你们,峒里的父老兄弟孩子,都可得帮我一把!”
“大人,咱啥时候不听你的?阿爹他……咱要说他……”秋玉边说边望李德裕。
于是,李德裕捻大灯蕊,摊开草图,对着这一对年轻人描绘那将出现的情景,二人听得如痴如醉,不觉月影西斜……
再放火烧山。
种下包麦种,
还要种山兰。
日日不得闲,
三顿断两餐。
怨天不公道,
咱们多愁烦。
……
粗犷、高亢、悠婉的歌声,倾吐着怨艾、悲愤,伴着叮叮咚咚的砍伐声,从树顶上飘出去,从杂枝间飘出去,在南仇岭半山腰、低谷间迥荡着,迥荡着。五月的骄阳烤得石头上直冒青烟,烤得黎家人酱赯色的背脊流油。他们把蓝天当帽,把树枝当帽,把笠大的葵叶当帽。肚子饿了,胡乱塞进些山莳、野菜,汗流干了,捧口泉水就喝。可是,歌是从心里掏出来的,却掏也掏个不完,伴着砍伐声惊跑林间野兽, 惊飞丛中鸟儿。
帕威砍山来了,秋玉也砍山来了。帕威还真心疼女儿嫩葱葱的皮肉,死活要她呆在家里,秋玉哪里肯依?黎家男子砍山时,女人得停下手中针线。据说不这样,男人爬树便要碍住手脚,摔个半死半活的,可就难说了。再说,大伙都上山来,自己呆在家里,不就往闷葫芦里钻?秋玉宁愿晒成个火炭人儿,也要跟大伙累在一块,笑在一块。帕威拗不过她,只好依了。秋玉不能象阿爹那样爬在树上,砍倒这株, 又攀上那株。她砍杂枝,砍小树,也忙得手不停,脚不歇。当然,她也有放下活儿,驻足侧耳的时候。这不是别的,是那诱惑的歌声飞过来了:
不砍大树砍小树,
只砍旁枝留树冠。
让鸟儿做窝,
让鸟儿成双。
让千年老藤,
一直往上窜!
心上人儿哟,
你也快来攀。
秋玉顺着声音望去,眼睛放亮了。这不是阿光哥吗?他象一个猴子骑在一株黑格树上,一边砍倒树枝,一边探出头来,卖力地唱着。秋玉心里“呸”了一声,你就是眼睛尖利,瞧见咱在这儿,故意唱给咱听!才两天不见面了,心肝都给猫抓得发痒!近来,秋玉恨他,可怜他,也越发爱他。李夫人都过七了,阿光才空着双手回来,秋玉真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寨子里的人也似乎怨他,阿光竟果真躲了起来, 说是没面目见人。这一回,秋玉又恨起自己来了。那仙水是阿妈的阿妈说的,谁知道真有还是假有?就真有仙水潭,谁见到?这不是到海里去捞针吗?阿光哥肉都掉了十斤,脚板都磨破两层皮才回来,他是要找到仙水啊。秋玉这一想,千怪万怪,只怪自己心眼儿偏,便向阿光赔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是。然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秋玉又恨阿光来了。她想不通,李大人够难受的了,咱恨不能跟他分些痛苦。咱多给他问安,多给他打些柴火,也是合人情道理的嘛。也不碍谁的手,碍谁的脚。阿光哥你也是愿李大人好,帮不了他忙,你为啥对咱斜着眼睛?你心眼儿就是大不过针眼儿。恨归恨了,秋玉细细寻思,阿光这全是为了她,向着她呀。一想到这,秋玉气都消了,要罚罚他的念头也消了,只可怜他青梅树不成坡垒格,只爱他如自家的疮疤自己疼一样。因此,这会儿听到阿光的歌声,秋玉踮起脚尖,脸朝阿光那边唱起来了:
鱼儿爱深潭,
鹿儿爱青山,
兔儿爱嫩草,
雀儿爱山兰。
峰高有云缭,
树大有藤攀,
石厚有崖恋,
哥好有姝跟。
别做龙眼树大生小籽,
别做鸡不吹箫嘴巴尖,
别做木棉皮青肚内白,
别做椰子生肉不生仁……
“唱得好,阿玉。”李德裕悄悄站在秋玉背后听了一会,夸了秋玉,又对同来的帕威说,“峒长,阿玉手巧心诚,好,好!你有福气呀!”
“李大人……你……你怎的也上山来?这不苦了你嘛!”秋玉羞红了脸,到底关切地问。
“苦,苦,大伙都苦得,我却苦不得,这还象个理吗?阿玉,你也别小嘘人啰!”李德裕爽朗地笑道。
“大人,你就是不听咱的。咱是握惯了山刀把,可你,你是捏惯笔头的呀!有我帕威吃的,就有大人喝的。大人在家唸诗作对,咱来供养你,心里才舒服!”帕威蛮不服气的。
“峒长,在家人都憋出病,还能念出诗来!你看,我一上山就拾到好诗,”李德裕说着,念起来了:
别做龙眼树大生小籽
别做鸡不吹箫嘴巴尖
“大人,你,你又瞎编人!”秋玉娇嗔地笑。
“不是瞎编,咱们是说正经的。你们都叫我‘大人’, 我就要成大人的样子。不然,就是龙眼树了。你们说,是不是呀?”李德裕摊了摊手。
说话之间,周围的黎胞都放下手中活计,阿光早从树上跳下来,围在李德裕身旁。这时,一个黎胞调皮地说,“大人,从今天起,咱们砍山,你就包烧山,好吧?”
“这容易,容易,东风随我意,一把火烧山!我要把大伙吃的穿的,全给包了!”李德裕故作神秘地说。
“大人,还会说笑话儿呢。”有人乐了,直拍拍手掌。
“哟,你们是说我瞎吹?嘿,别看我老了,早年可学过法术,神通广大的法术。如今这法术可派上大用场了!”李德裕说得一本正经的。
“哟,大人还真神呢!”
“可不,李大人治那山贼,就凭着那法术呢。怪不得歹徒不敢作孽!”
“嘿,大人,你也别葫芦里卖膏药呀!什么法术,也得说来见识见识,让大伙高兴高兴!”
大伙还真是七嘴八舌的。
“不过,大伙都得听我的,这法术才灵验。”李德裕望着一张张兴奋的脸,便绘声绘影地说了:他一招手,山神就俯首听命,传令给各路大土神、小土神,一个个要恭候两旁,给河神鸣锣开道,接驾引路;二招手,河神也乖乖听话,吩咐昌化溪里的虾兵蟹将,大大小小一群水族,拥着水珠,摇着浪花,大摇大摆从南木岭里峰拥而上……说着,说着,李德裕忽然停下。
“大人,你果真有这天大本事?那你快说,接下说呀!”黎胞们听到过瘾处,自然急于知个分晓。
“哎哟,大伙这一打岔,河神跟我讨价还价来啦!”李德裕捋一捋胡须,笑咪咪地说,“这一回,可得请大伙帮个忙啰!”
“这还用说!咱让帕扣唸经,杀三头牛、六头猪祭他!”帕威挺认真的。
“不行呀!”李德裕煞有其事地说。
“咱再供他香米饭、山兰酒,哪位神仙不吃耙!”有人说。
“还不行!”李德裕依然摇头。
“那……那咱织一幅黎锦,请他坐在上面,八个阿哥抬他,还抬不动他吗?”秋玉已有点急不可耐了。
“阿玉,算你说得还差不多。其实,河神也不要咱抬他。他一帮人马,要走得体面些,求咱给修条大路,”李德裕一边说,一边用两手比比划划,”他一来到咱家门呀,多港峒里年年风调雨顺,南仇岭上种下的玉米啦、山兰啦,也犯不上怕毒日晒,坡头坡尾全都种上庄稼。到那时,咱们一日三餐醉,餐餐醉山兰。大伙,你们说,修修路可值得吧?”
大伙心头热呼呼,入了神,谁都不答腔。
“大人,你这一比一划的,不就是要修条沟吗?”阿光沉思着,琢磨出了条条道道,”“你是说,让咱把昌化溪水都引上山来,是吧?”
“哎,阿光说得对呀。对,对,修沟就修沟,只要修来个肚子饱,就行!”黎胞们人呼雀跃的嚷。
“阿光,你还真聪明哩。这一回,就看你们后生哥抖出个威风来啰!”李德裕拍拍阿光的肩膀,“后生哥,你说呢?”
“咱是专听李大人的。修沟的事,咱……”阿光跃跃欲试的,突然话塞。
大伙一楞:帕威正拉下脸来,默默的不说话。一个个也就象蔫了的瓜秧,提不起神来。这也难怪。俗话说,过水看头人。多港峒里,帕威的话比圣旨还灵着呢。帕威不吭声,谁还敢放气?
李德裕心里喊一声;糟了,多港峒里破天荒的大事,自己也不先跟峒长通通气,乘着兴头捅了出来,可要惹来麻烦。错就将错就错。自己从来不吃后悔药。树尾先动,树头就不动?于是,他就对着帕威说,“峒长,我光动嘴皮儿罢了。这力气,得大伙出。大伙正等着峒长的吩咐呢。”
帕威不答腔,只顾狠狠捏碎土坷粒。
“阿爹,你说话呀,快说话呀!”秋玉轻轻拂拭着帕威手上的尘土,“李大人还不是为了咱们好?”
“这事儿,是件大事呀,峒里没有过的大事!”帕威怔怔地望着地面,自言自语。
“是呀,是峒里没有过的大事!”众人一齐附和着。
李德裕不再说了,只顾默默地望着那一张张酱赯色的脸,望着那一双双渴望的,却又是困惑的眼睛。他想从那里寻找理解,寻找支持。他觉得什么都寻到了,什么又都失去。他明白,黎家人在这片土地上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些人习惯了,仿佛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就象太阳从东边出来又从西边落下去一样的天经地义。有些人想冲出去,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却怕绊了跟头,摔伤了胳膊,折断了腿。帕威犯了什么禁忌,李德裕心中也拿不准。但他知道,让黎家人开沟挖河,并不比上几道奏章容易。然而,他不能无动于衷,坐视百姓在一潭死水中度日。他从政多年,一生以救济天下苍生为职责,如今身居黎山,体味到百姓如何在贫困、饥饿中挣扎,才知道自己的政治抱负只是半句空话,“皇恩播九州”这一句话,实在只是大臣们冠冕堂皇的颂辞罢了。而在日子的艰难中,黎胞们却伸出了慷慨的、无私的手。他们饿着肚子,也要把吃的、用的掏出来,塞到李德裕的手里。当他含着泪花接过一块黄猄肉、接过一碗玉米粥、接过一担木柴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在颤抖地呼喊:我李德裕欠了黎胞一笔债呀!以前他信奉孔老夫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现在很清楚,等到“在其位”再来“谋其政”,恐怕来不及了。为着报效皇上,报效天下苍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李德裕这些日子一直在想,他该给黎胞们做点什么。他隐隐觉得生命的灯火快要熄灭了,但越是意识到这,就越产生强烈的欲望,要积聚最后的力量,放出夺目的光辉。有了这个念头,一切偷生的、息事宁人的想法,都从胸臆中逍遁,一切畏难的情绪都退避三舍,一切坏的结果都考虑到了。因此,李德裕沉思一会,便笑着对帕威说,“峒长,这天大的事情咱们再好好商量嘛。来,我来砍山!”于是,大伙也慢慢散了。
李德裕瞄住一株黄槐树,捲一捲袖口,站了个弓步,挥起山勾刀就要向树茎底部砍去。可是,刀落下时,刀勾划了划树皮便弹了回到面前。在一旁砍树的帕威走过来,嗡声嗡气地说,“大人,这不是闹着玩的。你歇着吧!”李德裕解嘲似的笑着,“这山刀还不如长枪好使!”其实,他是心疼,一株大树好端端的,要当作柴火烧了,才砍个歪着。但他不肯说出来,怕惹大伙笑话。他暗暗发誓,一定要砍倒大树,不然,他就要矮人三寸的。李德裕谢过帕威,又砍起树来。他站着砍,蹲着砍,往上砍,往下砍,左砍右砍,虎口震得起了几个血泡,终于砍倒了大树。阿光眼尖,望见李德裕砍倒了大树,吆喝几声,使劲唱起来:
砍哟,砍哟,
砍倒千年老树哟嗬咳,
砍倒万丈古藤呦嗬咳,
砍出一条新道哟嗬咳。
往年黎家自己砍,
今年风光大不同。
李大人跟咱砍山呦嗬咳,
七月包谷堆成岭呦嗬咳……
阿光一唱,小伙子跟着唱,姑娘跟着唱,帕威也跟着唱,唱了个山谷来风,群情振奋……
然而,一回到家,秋玉问起修沟的事,帕威却白了她一眼,不耐烦地嚷,“问个啥?你懂什么?”一连几晚,他总独自喝着闷酒。
一天晚上,帕扣来了,帕威低着头,似乎不把他的到来当一回事。
“怎啦,峒长,一个人喝着?”帕扣弯腰低头,挤眉弄眼地踅到桌旁。那样子是说,你便不请我,我也自己来。帕扣给帕威添满一碗,再给自己倒满一碗,摆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峒长,你吃了豹子胆,托大啦?连我进来,也给一张冷凳。”可是帕威依然不理他。帕扣讨了个无趣,便挟起一块山鸡肉,吞进嘴里又吐了出来,津津有味地折腾,无话找话说,“好吃,好吃!峒长就是好手段。哦,峒长今儿不高兴,该是让一只坡鹿逃了?要不,咱兄弟俩就喝喝到星儿落下碗里。”
“喝,喝,你就知道喝!”帕威干脆把自己的酒碗都推到他面前。
“哟,峒长,好大的火气!”帕扣捂捂鼻子,表示他的愤慨,两只三角眼同时也在帕威脸上搜寻什么。突然,他恍然大悟似的直点头,“怪不得……峒长你……我看出来“你看出啥?”帕威有点急不可捺。
“嗨,不说也罢……”帕扣摇了摇手。
“你不说?你敢不说?快说,叫你说,你就快说!”帕威汹汹然地嚷。
“好,我说,我说!”帕扣润了润喉咙 半昧住眼睛,嘴皮一张一闭的,半响才吭出声来:“峒长,你你气色不好,凶星缠上你啊!峒长,你是一峒之长,只怕你灾星不脱,咱峒里也要有血光之灾呀。”
“你说,凶星怎来的?”
“这……这几天我不在寨子里,寨子里出了什么事,我也说不准。幸而灾星缠身不久,峒长你你啥事都留点神,我再给你求福,会消灾脱难的,”帕扣说着说着,扳了扳指头,诡秘地朝帕威眯了眯眼,”峒长,咱黎家的规矩一条一条都犯不得,咱黎家的山头一个一个都动不得,南仇岭上的神蛙石千万动不得啊!它可是多港峒,是咱抱班寨的命脉啊!”
“这是真的?这都是真的?”帕威脸色由红转青,由青转白,声音也微微发抖。
“桐长,咱啥时候不是为你好,为寨子好,谁存心骗你?谁骗你,谁就是——”帕扣一话未完,帕威伸过手掌猛然捂住他的嘴巴,“谁让你咒了自己?”
这一夜帕威躺在床上不曾合眼。
他走一山看一山似的一路想起帕扣,想起帕扣今晚说的话来。帕扣倒是护着咱呢。十几岁那年,帕威挑一担玉米过溪。刹那间,岭顶上炸了几个响雷,乌云盖过山头,山雨噼噼拍拍来了,山水滚滚而下。冷不防,已过溪中央的帕威被卷进旋涡里。他偏舍不得甩掉担子,在浊浪里死死挣扎,眼看就要被大水吞没。幸好帕扣也从对岸的小路赶到总路口,一见这情景,二话不说,只身跳入激流,把帕威连人和担子推上岸边。这些年来,帕扣开口不离神,闭口不离鬼,可他是道公啊,也难怪他。帕扣酒是贪喝,有几回还跟晒经坡墟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的混,大概是混碗酒喝,没啥。帕威想来想去,还是认准帕扣真心为他好,不由寻思黎家一条条规矩。族有族规,有奸情的,奸夫不是毙命,也要罚酒罚猪,当众认罪。家有家法,竹都分个上节下节,长幼之间的礼节,乱来不得。可帕威细细想来,族规、家规大的小的,他从来不触犯。谁敢说他半句不公道?对了,一定是李大人要修沟的事,让上天知道了,要降罪下来了。李大人呀,你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得咱黎家的规矩。山神、河神,谁敢动得他一根毫毛?放火烧山种山兰,自古至今有谁种出啥来?种出稻米,祖宗也不认你。那天咱不吭声,是碍住一层脸皮,别让你大人难为情。可你那天比比划划,比出了沟沿,不就比出来一条长蛇,冲犯了神蛙石,那还了得?李大人呀,咱也不是冤了你,道公分明也这么说。你可叫我怎办?
清晨,乳白色的雾气从山林、深谷、寨子那边滚滚升腾,那绿树,那小室,浮动在这流动的浆液里,若隐若现。而神蛙岭这边低矮,多是小山丘,雾气就淡些,就薄些。在一个小山丘半腰,一堆丈把高的石头拔地而出,凝神细看,它纤毫不爽,酷似一个巨大的青蛙。那青蛙昂头蹲着,嘴巴半张,宛然对着寨子翘首待鸣。在田园诗人的笔下,雾气下的山谷、村寨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田洋,而这青蛙,就是来自田洋里的使者,预报着丰收的喜讯。帕威身披白雾踏着露珠来了,来到大石跟前,脚步放得很轻很轻,眼里贮满不容亵渎的异样的光彩。他突然“卟咚”一声跪下,两掌齐放胸前,虔诚地轻声念着,“神灵保佑,神灵保佑。”他一直跪着,谛听神灵发出什么训谕。可四周静悄悄的,神蛙石不说话,连飞鸟也不来报个讯儿。他就一动也不动地跪着,跪到太阳爬过山头好高好高。这样,雾淡了,散了,千树万树披 上金色的流苏。神蛙石在阳光的照耀下,也仿佛身披那金色的流苏。帕威眼冒金花,心里惊喊,“这可是灵光?一道一道的灵光!神蛙石真灵啊!”他连忙拜了九拜,让赶来的大伙也跟着跪拜。
帕威跪拜完毕,连饭也顾不上吃,就跑到山兰园里去了。他挨个走到黎胞身旁,汹声汹气的就是一句话:“从今天起,谁也不准提开沟的事!”
一句话,却象严冬里一声闷雷在寨子里炸裂,人人惶恐,不安,郁闷,困惑。从上午到下午,从傍晚到黄昏……
月亮从山脊上爬上来了。溶溶山月,把寨子泡在轻柔的世界。要是平时,缠绵绵的乐器声、对歌声,早同月光把寨子泡得酥软酥软。可是今天晚上,寨子里却静静的,静得令人透不过气。
秋玉三扒两扒吃过晚饭,就到寮房呆着。她心里都烦死,却不见阿光来。不一会儿阿光来了,她劈头就问,“你到哪里死去了,今儿才转生?你难道害了笑病,一点正经事儿也不管一管?”
阿光知道她骂啥,对不了她爹,就来骂他,正是对不得坡上鹿却来管栏里猪。阿光心里才急呢。李大人好心不得好报,阿爹他……唉,帕扣不该来装弄神鬼,来添油添火!他那张阴阳脸看起就叫人恶心,那扭扭捏捏的样子,就会让人长鸡皮疙瘩。可是阿光也没办法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嘛。阿光正是找秋玉商量商量,不想一进门就挨骂。但他明知道秋玉是一片好心,并不计较她,却故意逗她,“骂吧,骂我遭瘟,谁来陪你?”
“你坏,你坏,都啥时候了,还闹着玩?”秋玉刮了阿光一下嘴巴。
“谁闹着玩?咱不是想出个办法来了吗?只要治得帕扣,阿爹就……阿光凑到秋玉耳朵旁,嘀嘀咕咕一阵。
明天阿光要到德霞峒那边打猎。他打得坡鹿,一定送“头弓”给帕扣,不过,得悄悄对他说,那只鹿是养在“插星”岭里的,养给天神享用的,看看帕扣这只猫还吃不吃腥。这样……
“好,好,要是帕扣露了馅,阿爹就不会被他迷住!”秋玉一高兴,竟象一个孩子似的跳起来。
“这是正经事吧?”阿光有意讨好恋人。
“还有正经事,咱们去看看李大人,别让他给闷住!”秋玉恳求起阿光来啦。
“我不听你的!”阿光说完,却拉着秋玉走出了寮房。
李德裕的屋子就在眼前了。灯光透出来,桔黄色的灯光虽然不那么明亮,可是它照出了一尊浮雕式的身影。他面对着一盏海棠油灯,面对着一张草图,兀然端坐,使人想起山峰在月色下勾勒着庄严,勾勒着凝重,阿光和秋玉想见到他,又怕见到他,一步一步椰近窗前。他们瞥见了,那草图上面画着——那一堆一堆的,不就是山岭吗?那弯弯的,从山里穿过的不就是溪吗?对了,那是寨子,那象盆一样凹下去的,不就是寨子前面那一块盆地么?对了,李大人想什么,全在纸上画出来了。两人心里一热,李大人在琢磨着挖沟的事儿!突然,李德裕叹息一声,捧着那张草图,“把你烧了!”
“大人,烧它不得.烧它不得!”阿光和秋玉奔进屋子,不约而同地喊。
李德裕一望深夜这不速之客,惊喜地喊,“哟,阿光,秋玉,来,坐,坐!”
“大人,可委屈了你,都怪咱阿爹不好……”秋玉难为情地说。
“傻孩子,说到哪里去了?峒长怎的不好?峒长不好,能容得我住下?因为我念着峒长好,才想出点力,来报答峒长,报答大伙。喝了寨子的水,吃了百家饭,也要给你们留点什么,让大伙,让后人都说我不白到过这里。我只盼着我能有这一天!”李德裕说着,说着,真的动情了。
“大人,阿爹一时糊涂,你可别怪他!”阿光陪了笑脸。
“孩子,这不叫糊涂。走路惯了,就有马骑,也怕摔下来,得一瞧再瞧。你们送我茶,又甜又香又补身子,我开始还真不敢尝尝。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东西 难怪峒长一时转不过弯来。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李德裕说。
“哎,是呀,大人看透了咱的心事。只是,咱总觉得李大人为咱好,大人要咱怎办,咱就要跟着办,”秋玉想了想,撒起娇来,“阿爹,他会想通的。你不该要把它把它毁掉!”
“生我的气啦,秋玉?”李德裕笑着问。为了这张草图,李德裕悄悄察看昌化江,走遍了南仇岭大山头小山头,名为观赏风光,吟诗作对,实际是一步一步考虑如何把江水引上山来。他哪里肯把心血付之东流?刚才,他一时心烦,说了一句丧气的话,却被秋玉听见。当下,他认错似的对两人说,“我赔个不是,好吧?你们,峒里的父老兄弟孩子,都可得帮我一把!”
“大人,咱啥时候不听你的?阿爹他……咱要说他……”秋玉边说边望李德裕。
于是,李德裕捻大灯蕊,摊开草图,对着这一对年轻人描绘那将出现的情景,二人听得如痴如醉,不觉月影西斜……
相关人物
秋玉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