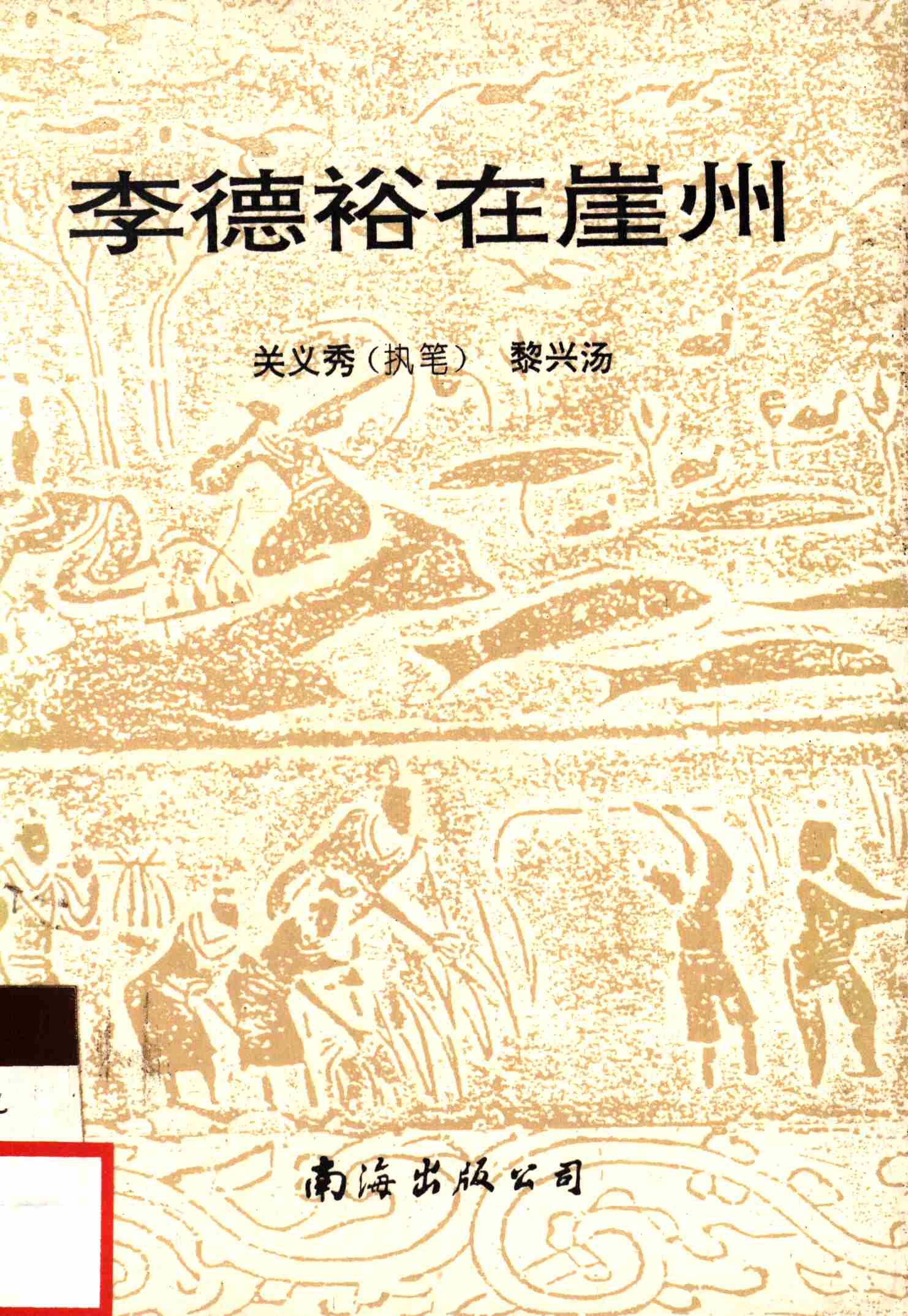内容
回风岭还裹在苍茫的曙色里。
天空里,灰暗、幽蓝揉合成迟滞的、厚重的色块,东天送来些微亮色,才抹上一缕一缕桔黄的花边。
在这色块下面,一个个山头就像铁铸的巨兽,凝重,但还不崭现生气。低垂的雾霭,步履沉重地、执着地,从这个山头捱过那个山头,甩出一柱一柱轻烟,升腾入苍茫深处。
崖州城里鸡又叫过一遍,这里却是静悄悄的。只有露珠,从青梅、竹叶松,绿楠、毛丹的叶尖上,从杜鹃、山茶、桐剌、金银花的花瓣上,一滴一滴,轻无声息地洒落。春天里的深山将近拂晓,还是冰冷冰冷的。枝丫间、草丛里的斑鸩、山鸡、山雀、长尾猿,一个个睁开了眼,又懒洋洋地闭上。贪吃的野猪呼噜呼噜拱了拱窝里的野草,又翻过身子打起鼾声。更不用说穿山甲了,此刻它正在土洞里做着美梦呢。
可是这个时候,血战了一夜的黎胞们正踏上回风岭的山路。尽管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心头还笼罩着悲哀,但黎家人一旦投进大山的怀抱,便觉着是鱼儿跳出了火锅,游进了大海。况且,他们还杀死了官军,救出了秋玉。他们走着,似乎笫一次发觉深山拂晓的空气这么清爽。一个个呼吸着凉气,撩开麻衣,让冲出云雾的下弦月光洒进胸膛,让它洗涤一场血战留在心上的伤痕。
帕威也跟兄弟们一样,享受了片刻的快意。但他走着,走着,只觉心往下沉,往下沉,沉到那深幽幽的谷底。刚才阿光到哂经坡墟去,帕威背着李夫人走一段路了。他本是多港峒里的呱呱叫的壮汉。百把斤重的山猪扛在肩膀上,他一蹦就蹦过山涧,连气也不喘一喘。有一次,他打猎一整天,米粒不沾一口,舀几口溪水就充饥。回家的路上,一只大熊突然从旁边扑来。他一闪,一跳,跳到一棵大槐树上。 山熊正在树底吼叫,两支利箭几乎同时飞来,射中眼睛,不能动弹。帕威跳下树来,再打几拳,大熊断了气。眼看四下无人,帕威背起死熊就走,一口气走了三里多山路,回到了寨子。可是这一回他背着李夫人走,心地沉重,脚步也就格外沉重。
帕威走三步两步,便回过头,焦躁地叫起来,“阿光怎的还不回来?夫人等着药呀!”身旁有人应道,“峒长,他们刚走一会!”帕威还是嚷着,“这是什么时候?他们就不焦急!”
当然,帕威是枪筒着火,一着就冒烟。其实,阿光一样心急呢,他带了两个兄弟赶到晒经坡墟,先找了李三。原来李三带阿光进城,王得利只抓住一鳞半爪便去报官,添油加醋的乱说一通。李三因此遭了官军毒打,养伤在床。阿光来不及细说,只说李夫人受了重伤,请李三想想办法。李三一再叹气,不能两肋插刀杀进城去,冤了好人,又在阿光耳边低声说了什么。阿光边听边点头,辞别李三,带着兄弟们走了。
阿光寻到王得利家,操着官腔,敲了敲王得利的房门,“快起,快起!半夜黎人打进州衙,官军伤亡不轻。胡大人命我来取上等伤药,还有人参、熊胆!”王得利睡眼惺忪闪开房门,一看来头不妙。猛地要把门关上。阿光目疾,早抢在前面闯进房里,亮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对准王得利的心口。
“自家人,好说,好说!兄弟别动肝火,我取就是,我取就是!”王得利捣蒜般直叩头,两只眼睛却贼溜溜转,突然撸起一拳,朝阿光阴部猛击。想不到阿光乘势一跃,骑住他的脖子,两手揪住头发,将头往墙上碰。王得利吓得象挨刀的猪嚎叫,求饶不止。阿光放了他,王得利只得乖乖取出药物。阿光把药物包好,却回过身来,让同行的弟兄把王得利捆了。“把他杀了!”两个黎胞掣出尖刀。阿光皱一皱眉,喝问王得利,“是死是活,由你挑!”王得利早认出阿光他们,吓得魂消魄散,此刻只有浑身打抖的功夫了,“饶了小人……一条狗命!”阿光冷笑道,“杀你三遍,也是罪有应得!可你是条狗,杀了你,腥我的刀!咱放了你,看谁还敢说黎人无法无天?你听着,再动李三哥一根毫毛,就让狼来扒你的肝,撕你的肺!”阿光说完,那两个兄弟往王得利嘴里塞进一团破布,大笑着,“叫你去报官!”
阿光三人六腿生风,一口气赶到歇脚寮,同帕威他们相遇。
歇脚寮是黎胞们赶墟时往返歇息的一间草屋。几根木柱搭起了架子,上面盖上茅草。也就是了,简陋就是简陋,可春夏秋冬,它送往迎来,倒是热热闹闹的。这里地势平坦低洼,旁边大树枝丫交错,门前清泉四季流淌,叮叮咚咚,清泉洗刷得山石莹润光洁,三个一堆,五个一簇。此去晒经坡墟不远,黎胞们跑了好长山路,自然要在这里松松口气。这时,老年人放下担子,便拢来干枝枯叶,来个钻木取火,吧哒吧哒抽起烟来。年轻小伙子则抹了抹脸,喝一口泉水,扎一扎腰带,嘴巴一咧开,哼起情意绵绵的黎歌,要不就吹起鼻箫、唎咧。年轻的姑娘最爱采山花一朵、两朵往头上斜插,坐在山石上,也情不自禁扭动腰肢,同小伙子传情达意。进山时,歇脚寮成了集合地点。先到的等候后来的,我帮他,他帮你,大伙整好担子。牛角号一响,黎胞们才一起动身。
“得了?”帕威见到阿光,连忙问道。
“嗯。”阿光轻声应道,走进歇脚寮里扶住还在昏迷的李夫人。
帕威紧蹙的眉头稍为舒张。他小心挪开身子,让阿光扶好夫人,自己把伤药再给夫人上了。秋玉把人参切成小片,轻轻捣烂,轻轻放进夫人嘴里。帕威望了夫人身上的箭,闷声不响,拔出尖刀放在火上炆着。
一双双眼睛投向跳动的火苗,仿佛那刚烧起来的篝火里在燃烧着希望……
“老天,饶恕咱的罪孽,救救咱黎家的大恩人吧!”帕威蹲在篝火旁,双手按住胸口,虔诚地念着,然后,才拿出烙红的尖刀,仔细端详着它的火候。他拿起刀,走到李夫人身旁又“扑咚”跪下,又一次念道,“夫人,你受惊了!老天,救救咱的大恩人吧!”说完,他双手颤抖把刀贴近夫人伤口,闭住眼睛,狠心把刀往上面一按,牙齿“格登”一响,猛地一拔,拔出了那支利箭。这一切是在瞬间完成的,众人都惊呆了,山头的轻岚也凝然不动。
“见鬼去!”帕威把箭折了,掷进深谷,深深地吐一口气,一个个心里,也似落下一块大石头。
黎胞又犯难了。帕威怔怔地望着夫人和大伙。他们心中嘀咕,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是回头无路,只得把夫人背上山,把她救活再说。
又一次给李夫人喂药、熬药,又一次给她裹好衣服,黎胞们才上路。
今天的山路好长好长,今天的山岚好浓好浓。黎胞们跋涉过一个山头,便向山下了望,看看是不是快到家了。虽然谁都知道这段山路有多少个山头,有多少个岔口,闭上眼睛也懂得还有多少路程。然而,当寨子里的牛叫声、狗吠声传来时,人们悲喜交织着的心里,仿佛又添上了什么,不觉把脚步放慢。
“阿光,你先走回寨子,叫父老们把什么都免了!”帕威闷声闷气地说。
平时,每逢围猎丰盈时节,弟兄们反击官军征剿胜利归来,寨子里沉浸在纵歌狂欢里。分不清谁喜迎亲人,分不清谁凯旋而归,你挥动尖刀,我飞舞利刃,一对一对剌杀,洋溢着内心的喜悦。遍坡满路,人影跃动。或当面进攻,或背后袭击,或旁敲,或斜剌,迅猛如山雨骤来,轻捷如蜻蜓点水;人如老虎下山,如山猪坐地,如壮猴舒臂,刀光似白鲫过江,似金蛇狂舞,似银鹤掠翅。年老的,年幼的,在一旁 敲着牛皮鼓,吹着唎咧、唢呐,拍着手掌,助威助兴。胜利归来,不跳起狩猎舞,便如菜里少了盐,席间缺了酒,用十八丈长的藤片也提不起劲头。帕威打猎、跳舞,样样出色。老峒长因此看上他,大伙也因此而选举他接了峒长。哪一次不是他首先迈开矫健的步子?可是今天背着李夫人,他一点儿兴味都没了。
父老们捧着山兰酒,捧着香米饭站在路边,可是帕威只是点了点头,便走过去,大伙也默默地走过去了。一个个获胜归来的黎胞,就这样进了抱班寨,进了自己的家。
第一天李夫人醒过来,又昏过去了。秋玉一整天都侍候在她身边。这里是她的寮房,还是新盖好的,屋顶的葵叶还散着淡淡的清香。床上铺着的,也是她不久前织好的簇新的锦被。虽说秋玉的手艺无人不夸,可是让她自己满意的,才有这一张锦被。每一根纱线都是精心纺成的,每一个图案都是精心织好的。它还织进秋玉灼灼动人的眼神儿,织进秋玉那不肯告诉别人,只留在心底的梦。难怪它那么鲜亮,那么温馨。几回回,秋玉只要闭上眼皮,这张锦被就变成一朵彩霞,让她和阿光坐着,飞到一个人迹罕至,异常新奇的地方。那里,石头上长出山兰,千年的铁树挂了果,金钱豹同山羊一起拉军,彩虹给深谷架桥,常春藤缠着青松,金鹿儿唱起动听的歌……床上原来铺着一张半新的黎锦,秋玉望着,迟疑着,突然狠下心抱来这一张簇新的锦被。她阿妈见了,小声地骂,“你疯了?”便一把抢过被子。秋玉勃然生气,猛然抢回被子,跪下哭了,“妈,要不是夫人……咱可见不了你……可你……”原来,黎家人有条规矩,结婚要用的东西,过门时才能破新,否则会损了一生福气。阿妈见女儿这般,无可奈何,兀自叹息。
李夫人昏迷过去,又醒了过来,醒了过来,又昏迷过去。她随丈夫南下,一路上折腾,早已心力交瘁,完全是撑住,打发日子。到了崖州,她水土不服,病邪缠身。虚弱的身子,又怎受得严重的箭伤,挨得一夜的餐风饮露?
昏迷中,李夫人多少次模糊不清地唤着李通的乳名,唤着“大人,大人”。远在毕兰村的亲人,可曾听到她的呼唤?黎胞是听到了,每听到一次,心里就仿佛多射进一支利箭,酱赯色的面孔上颤栗着无比的哀伤、痛楚。可是他们,这些围在四周的黎胞,却无法让李夫人脱离苦海。
秋玉坐在身旁,含着泪给李夫人喂米汤。夫人呻吟着,“喝……喝……”秋玉把汤匙轻轻送到唇边。夫人哪里咽得下去?米汤一点一滴溢了出来,秋玉轻轻拭着,又一点一滴送进夫人嘴里,不喂汤时,秋玉就怔怔地想。她想起来了,仙水能治百病,使人起死回生。她听阿妈的阿妈说过的,仙水就在仙水潭里。于是,她眼前恍然现出一汪水潭。水潭四周石头儿可怪了,什么样子的都有。你想得出什么,它就象什么。四周的鲜花可奇了,红、黄、蓝、绿、紫,一年四季就在青枝上挂着。毒日晒时,一朵一朵,全都水灵灵的开着,风吹雨淋时,小朵张大成了大朵,大朵干脆爆了一枝繁花,潭里的仙水最神了。它象水不是水,象乳不是乳,象山兰酒不是山兰酒。渴了时,喝下它,只觉甜凉凉的,一直透到耳根;全身发冷时,只要闻到它的味儿,五脏六腑立刻暖烘烘的,年老的也来了劲儿。秋玉这般美美地想着,心里顿时惊喊,“夫人得救了,得救了!”于是,她立即打发阿光去讨回仙水。
“我该到哪儿去找呢?”阿光高兴是高兴,可为难了。
“这……”秋玉也为难了,阿妈的阿妈并不告诉她仙女潭在什么地方,“到尖峰岭去找吧。那里有仙人草,也会有仙水嘛!再不然,就到抱告岭、石门岭、南山岭去吧,反正,这仙水非找回来不可!”
阿光动身出发了。他明知道,这是上天摘星斗,但没路也得寻路上。
李夫人昏昏沉沉,又发起高烧来了。
第二天,帕威叫人杀三头牛,亲自请道公帕扣给夫人求神除病。
桌上摆满猪肉等祭品,燃上沉香做的香,香味扑鼻,香烟缭绕。帕扣一身打扮,对天、对地、对香案,连连叩了九叩。接着,他把一只公鸡剐了,扔在地上,站立在香案旁边,往桌上不停的拍击木卜,半闭着眼,嘴中念着:“嗽……嗽嗽……”他这样做是查一查阴鬼,询查是哪一种凶鬼的作崇。不料,那只公鸡扑打着翅膀死去时,头颅却朝向大门之外。帕扣猛摇脑袋,怕是要摇断了脖子,“大事不好,大事不好!病人犯了天规,神要惩治她!”
帕威一直在旁边看着,一听帕扣说,脸色涨红转青,慢慢煞白,嘴唇也微微哆嗦,“求求你禀告,神要惩治,就惩治我吧!”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帕扣又晃了晃脑袋,“嗽嗽嗽……峒长,一人做孽一人当,谁也替不得呀!嗽……嗽……嗽……”
突然,帕威两眼炯炯发光,伸过铁钳般的手捏住帕扣不放,“你说说,她有什么罪过?我要让她活,天哪,我的大恩人哪!”
“嗽嗽……嗽……”帕扣念念有词,“这是天意,天意!峒长,谁能跟天做对?”
“道公,请你再对天祷告,对神明祷告,求求你呀!”帕威苦苦哀求,简直要下跪了。
“峒长,神明只显灵一次。咱还敢再惹神明吗?嗽嗽嗽……”帕扣摆了摆手。
帕威垂头丧气,进了秋玉屋子。大伙见到他这个模样,话都憋住了。
李夫人时停时续的说胡话。傍晚时分,她一只手指了指外面,又指了指胸口,如此重复着这个动作。
一时,大伙都捉摸不着夫人为何这般动作,帕威急得直抓头皮。
“阿爹,夫人这不是要见李大人吗?”秋玉两手比划着,恍然大悟对帕威说,“阿爹,快告诉李大人呀!”
“对,咱为啥这傻?”帕威也恍然大悟,拍了拍脑壳,“咱怎不想到这层?砍了脑袋,也得请李大人上山!”
帕威又犯愁了:空口无凭,李大人会相信自己吗?秋玉看出他的难处,望着屋里四周,眼光慢慢落到李夫人那枝漂亮的头簪上,兀地放亮了,“阿爹,头簪——行吗?”
“对,头簪,对,头簪,爹这就去!”帕威破涕为笑了。
帕威嘱咐老伴利女儿一番,望着李夫人,合起双掌,“夫人,你好好歇着,大人会来的,会来的!”说完,他接过秋玉递过来的头簪,带着一个懂汉话的兄弟,马不停蹄星夜赶到了毕兰村。
时已二更。还是黑沉沉的夜,还是那盏孤灯。可上一回是李夫人苦苦着丈夫速归,这一回却是丈夫惦挂着妻子生死未卜。那天早上李德裕回家,见不到夫人,只见一滩血,一条红头巾,不禁大声哭喊,“夫人,你好苦哇!”夫人啊,你一生贤慧,半生忧愁,风烛残年,你难道惨遭不测?
李德裕认出那红头巾了,帕威在眼前恍然一闪而过。是他下了毒手?不可能。我李德裕问心无愧,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们绝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难道说,是胡思进嫁罪于他?李李德裕摇了摇头,要是这样,事情就更复杂了。李德裕左思右想,觉着事情凶多吉少,暗暗叫苦,“夫人啊,吾到哪里找你?”过了一个时辰,李三来了。李三哭着,把李夫人中箭受伤的前前后后都说了。李德裕听罢,勃然大怒,“胡思进,还吾夫人来,还吾夫人来!”两天内他找了胡思进三 次,次次都吃闭门羹。李德裕想要进山去找夫人,又怕被胡思进反诬一口,说他私通黎贼,一时委决不下,不禁仰天长叹,“想不到吾一个重臣,遭小人作弄到这地步!夫人危在旦夕,吾却眼睁睁坐视不救!”当时,李德裕坐在灯下,思绪奔涌,悲愤不已。不远处偏传来猫头鹰“咕,咕,咕”三下喊声,他兀地站起来,默默望着窗外。
这时,帕威早等在外面片刻,心急如火烧,却不敢惊动李德裕,直到他被鸟声惊扰,帕威才悄悄进了屋子,跪在李德裕背后。
“你们是谁?”李德裕转过身,瞥见来人,便大声喝问。
“大人,咱们该死,该死!”两人还是跪在地下。
“你们来此何干?”李德裕面对这不速之客,一表威严,厉声喝问,“快说,快说!”
帕威这才抬起头,嘴唇一张一闭的,颤抖着双手,献上李夫人的头簪。
这不是他吗?借着灯光,李德裕认出了帕威。但他不说话,迟疑着,突然一把抓过头簪,紧紧攥在手里,眼泪夺眶而出,“夫人,她,她怎么啦?你们快说,快说呀!”
“夫人,咱害了夫……夫人……她她重……重伤……在床……”帕威哭诉着。
李德裕猛然抬起手来,挥到半空,似乎要发作的样子,那手却伴着一声长叹,重重地落到他的大腿上,“嗨,你们干的好事……”
“大人,你就杀了我吧!”帕威哭个不止,“可你,一定要去见夫人!她想你呀……”
李德裕心如刀绞,恨不得立刻飞到夫人身边。可他一想起胡思进,又恨又怕,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大人,见夫人要紧!什么王法不王法?如今天高皇帝远,咱管王法,王法却不管咱!这窝囊气还要受多久?”刘松、李茂光一齐劝主人赶快动身。
李德裕沉吟半响,又叹了一口气,才匆匆草就一封书信——
胡刺史钩鉴:
卑职李德裕贱妾前夜遭官军箭伤,现已身陷黎峒,生命危在旦夕。吾两天内三次禀见大人,未尝面遇,以致一误再误。伏念夫妻一场,患难与共,安能见死不救?吾出于无奈,星夜携几奔赴黎峒,见妇一面,以尽为夫之道,达于人伦之义。吾皇向以礼义治国,大人幸勿见 怪。卑职自往自回,勿念。
李德裕把书信摺好,交与茂光,嘱他第二天早晨交胡思进,便带着李通,随着帕威直奔抱班寨而去。
下弦月还藏在浓云里。走在回风岭那幽深崎岖的山路上,黑魆魆的山头从两旁、从前面,不断地压来,压来,李德裕忽然觉得自己钻入了黑幽幽的无底洞。四周静极了,静到让人心寒,要不是偶尔有一声狼嗥,有一声鸟叫,还会以为一切都死灭了。李德裕何曾不在夜间走过山路?但那时他是一军之主,百骑千骑簇拥着他,气贯如虹,就是地狱,也敢去闯一闯的。而现在,他孤身陷进黑暗的无底洞,心灵也陷进悲伤的无底洞。今非昔比,完全是天壤之别。因此,李德裕走着,走着,只觉得恐怖从四面八方都压过来。好几回,他微微战栗,把害怕得透不过气来的李通紧紧搂在怀里,只有当他想起夫人还在山那边等着他,似乎听到了夫人深情的、虽然是那么微弱的呼唤,这个时候,心里才猛然一惊,提起精神,纵起马缰绳来。枣红色的龙驹马,似乎懂得主人的心思,平稳地小步跑了起来。“的的笃笃”的马蹄声,清越、欢快,惊破了黑夜的死寂。李德裕在那绝望之中,又听到了当年进军的鼓点……
天快亮时,抱班寨里彻夜跳动的篝火,一双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盼来了李德裕。
李德裕老远就下马,一下子扑到妻子身旁。这是相濡以染的妻子吗?怎么,怎么啦?才隔几天,就仿佛隔着了几年、几十年!李德裕握紧妻子的手,一次又一次呼唤着妻子的小名,喊声那样轻,却饱含着悲恸,颤抖着惋惜和抗争。夫人,你怎不回答丈夫,怎不拭一拭他的泪滴?哪怕是回答一声,拭一滴泪滴也好!还有,你也该亲一亲可爱的孩子,别让他泪流满面!夫人,你还应说一声,你根本不触犯什么天规!可是,你什么也不说,只顾昏昏沉沉地躺着……
李德裕把随身带的中药煮了,一汤匙一汤匙喂给夫人。 药汁,慢慢润湿她的嘴唇,渗入她的喉中。李德裕越发苍老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李夫人忽然缓缓睁开眼睛,呆滞的眼光在李德裕身上停留,久久的,才翕动嘴唇,轻轻喊出声来,“老爷——通儿——”
“夫人!”
“娘!”
爷儿俩几乎同时喊出声来。
李夫人把丈夫的手吃力地缓缓拉过来,按住自己的胸口,眼角浮上凄然的笑,“老爷——妾跟你这些年——怕是——”
“夫人,你要撑住,你能撑住呀!”李德裕哽咽着,“你说过,三年五载——咱们回城去——回京城去啊!”
夫人轻轻摇了摇头,吁了一口长气,苍白的脸上浮起一丝异常得意的笑容,“妾——可知足了。”
“夫人,你要撑住,阿光哥快回来,仙水——”秋玉呆痴痴地说。
“好姑娘——我——我”夫人说着,说着,突然断了气。
那一双美丽的眼睛就这样闭上了,永远地闭上了,再也见不到她的亲人了。也许,她活得太烦恼、太累、太沉重,要带着深深的爱到一个幽静的地方慢慢消受。
李德裕正想把夫人遗体运回崖州城安葬,不料茂光他们都上山来。原来,胡思进接了李德裕书信,竟诬谄他串通黎人谋反,要申报朝廷,治李德裕的罪。茂光他们走投无路,只好上山报讯。
“竖子,你欺人太甚!”面对接踵而来的沉重打击,李德裕招架不住了,大喝一声,就昏了过去。
事到如今,只好暂时把夫人在抱班寨安葬了。
多港峒十几个寨子遇上百年大哀。
李德裕入乡随俗,丧事由帕威按黎族风俗办了。
报丧时,十几个黎胞举起粉枪,对天空鸣枪三发。然后,才换下夫人衣服,给她换上新衣。祭奠仪式是从祭灵头饭开始。黎胞们在夫人头顶供放米饭、米汤等祭品,并用木棉花醮米汤滴入她的嘴里,给她“喂饭”。入殡前,帕扣和一位道公,把一只祭猪吊在屋檐下,将一个簸箕供放灵头饭祭了夫人,又拿着一支龙眼枝醮了清水,浇潄于夫人遗体上,给她“洗浴”,再用剪刀剪了她头上一缕青丝,表示对 夫人挽留的情意。入殓时,秋玉哭得死去活来,把自己织的锦被都放在棺木里,把自己那只玉镯子放在枕头底下。入殓盖棺后,黎胞再对空鸣枪三发。一个个哭得愁云惨惨,悲风呼呼,哭得青山低下头,哭得流水也呜咽。停尸七天期间,黎胞敲锣,打鼓,吹唢呐,昼夜给夫人奏了哀乐,道公们跳起五风舞,又一次为亡灵追祭。出殡择一个良辰吉日。道公们念经超度亡灵,德裕、李通、帕威、秋玉等人,跪在灵柩前嚎啕大哭。峒里一个个黎胞,全都披麻戴孝,抚棺而哭。送殡队缓缓而行,伴着唢呐声幽幽怨怨,伴着送葬歌悲悲恻恻,缠绵着山路弯弯……
坟地在后达岭上,是一块向阳坡地,李德裕亲自选定的。帕威按黎俗以蛋掷地,选定了墓穴。招魂之后,棺材下葬了。
李德裕痛哭祷告,“夫人,吾不能让你归返乡里,只能让你安息山林,遥望家园。吾有愧于你,宽恕我吧,宽恕我吧!”
帕威接着把停灵时放在灵柩旁的两株芭蕉树种在坟墓两侧。黎胞们痛惜夫人生前不能跟他们同欢共乐,只好盼望她的魂灵在黎乡创家立业。
微风吹来,芭蕉树摇曳几枝翠叶……
天空里,灰暗、幽蓝揉合成迟滞的、厚重的色块,东天送来些微亮色,才抹上一缕一缕桔黄的花边。
在这色块下面,一个个山头就像铁铸的巨兽,凝重,但还不崭现生气。低垂的雾霭,步履沉重地、执着地,从这个山头捱过那个山头,甩出一柱一柱轻烟,升腾入苍茫深处。
崖州城里鸡又叫过一遍,这里却是静悄悄的。只有露珠,从青梅、竹叶松,绿楠、毛丹的叶尖上,从杜鹃、山茶、桐剌、金银花的花瓣上,一滴一滴,轻无声息地洒落。春天里的深山将近拂晓,还是冰冷冰冷的。枝丫间、草丛里的斑鸩、山鸡、山雀、长尾猿,一个个睁开了眼,又懒洋洋地闭上。贪吃的野猪呼噜呼噜拱了拱窝里的野草,又翻过身子打起鼾声。更不用说穿山甲了,此刻它正在土洞里做着美梦呢。
可是这个时候,血战了一夜的黎胞们正踏上回风岭的山路。尽管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心头还笼罩着悲哀,但黎家人一旦投进大山的怀抱,便觉着是鱼儿跳出了火锅,游进了大海。况且,他们还杀死了官军,救出了秋玉。他们走着,似乎笫一次发觉深山拂晓的空气这么清爽。一个个呼吸着凉气,撩开麻衣,让冲出云雾的下弦月光洒进胸膛,让它洗涤一场血战留在心上的伤痕。
帕威也跟兄弟们一样,享受了片刻的快意。但他走着,走着,只觉心往下沉,往下沉,沉到那深幽幽的谷底。刚才阿光到哂经坡墟去,帕威背着李夫人走一段路了。他本是多港峒里的呱呱叫的壮汉。百把斤重的山猪扛在肩膀上,他一蹦就蹦过山涧,连气也不喘一喘。有一次,他打猎一整天,米粒不沾一口,舀几口溪水就充饥。回家的路上,一只大熊突然从旁边扑来。他一闪,一跳,跳到一棵大槐树上。 山熊正在树底吼叫,两支利箭几乎同时飞来,射中眼睛,不能动弹。帕威跳下树来,再打几拳,大熊断了气。眼看四下无人,帕威背起死熊就走,一口气走了三里多山路,回到了寨子。可是这一回他背着李夫人走,心地沉重,脚步也就格外沉重。
帕威走三步两步,便回过头,焦躁地叫起来,“阿光怎的还不回来?夫人等着药呀!”身旁有人应道,“峒长,他们刚走一会!”帕威还是嚷着,“这是什么时候?他们就不焦急!”
当然,帕威是枪筒着火,一着就冒烟。其实,阿光一样心急呢,他带了两个兄弟赶到晒经坡墟,先找了李三。原来李三带阿光进城,王得利只抓住一鳞半爪便去报官,添油加醋的乱说一通。李三因此遭了官军毒打,养伤在床。阿光来不及细说,只说李夫人受了重伤,请李三想想办法。李三一再叹气,不能两肋插刀杀进城去,冤了好人,又在阿光耳边低声说了什么。阿光边听边点头,辞别李三,带着兄弟们走了。
阿光寻到王得利家,操着官腔,敲了敲王得利的房门,“快起,快起!半夜黎人打进州衙,官军伤亡不轻。胡大人命我来取上等伤药,还有人参、熊胆!”王得利睡眼惺忪闪开房门,一看来头不妙。猛地要把门关上。阿光目疾,早抢在前面闯进房里,亮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对准王得利的心口。
“自家人,好说,好说!兄弟别动肝火,我取就是,我取就是!”王得利捣蒜般直叩头,两只眼睛却贼溜溜转,突然撸起一拳,朝阿光阴部猛击。想不到阿光乘势一跃,骑住他的脖子,两手揪住头发,将头往墙上碰。王得利吓得象挨刀的猪嚎叫,求饶不止。阿光放了他,王得利只得乖乖取出药物。阿光把药物包好,却回过身来,让同行的弟兄把王得利捆了。“把他杀了!”两个黎胞掣出尖刀。阿光皱一皱眉,喝问王得利,“是死是活,由你挑!”王得利早认出阿光他们,吓得魂消魄散,此刻只有浑身打抖的功夫了,“饶了小人……一条狗命!”阿光冷笑道,“杀你三遍,也是罪有应得!可你是条狗,杀了你,腥我的刀!咱放了你,看谁还敢说黎人无法无天?你听着,再动李三哥一根毫毛,就让狼来扒你的肝,撕你的肺!”阿光说完,那两个兄弟往王得利嘴里塞进一团破布,大笑着,“叫你去报官!”
阿光三人六腿生风,一口气赶到歇脚寮,同帕威他们相遇。
歇脚寮是黎胞们赶墟时往返歇息的一间草屋。几根木柱搭起了架子,上面盖上茅草。也就是了,简陋就是简陋,可春夏秋冬,它送往迎来,倒是热热闹闹的。这里地势平坦低洼,旁边大树枝丫交错,门前清泉四季流淌,叮叮咚咚,清泉洗刷得山石莹润光洁,三个一堆,五个一簇。此去晒经坡墟不远,黎胞们跑了好长山路,自然要在这里松松口气。这时,老年人放下担子,便拢来干枝枯叶,来个钻木取火,吧哒吧哒抽起烟来。年轻小伙子则抹了抹脸,喝一口泉水,扎一扎腰带,嘴巴一咧开,哼起情意绵绵的黎歌,要不就吹起鼻箫、唎咧。年轻的姑娘最爱采山花一朵、两朵往头上斜插,坐在山石上,也情不自禁扭动腰肢,同小伙子传情达意。进山时,歇脚寮成了集合地点。先到的等候后来的,我帮他,他帮你,大伙整好担子。牛角号一响,黎胞们才一起动身。
“得了?”帕威见到阿光,连忙问道。
“嗯。”阿光轻声应道,走进歇脚寮里扶住还在昏迷的李夫人。
帕威紧蹙的眉头稍为舒张。他小心挪开身子,让阿光扶好夫人,自己把伤药再给夫人上了。秋玉把人参切成小片,轻轻捣烂,轻轻放进夫人嘴里。帕威望了夫人身上的箭,闷声不响,拔出尖刀放在火上炆着。
一双双眼睛投向跳动的火苗,仿佛那刚烧起来的篝火里在燃烧着希望……
“老天,饶恕咱的罪孽,救救咱黎家的大恩人吧!”帕威蹲在篝火旁,双手按住胸口,虔诚地念着,然后,才拿出烙红的尖刀,仔细端详着它的火候。他拿起刀,走到李夫人身旁又“扑咚”跪下,又一次念道,“夫人,你受惊了!老天,救救咱的大恩人吧!”说完,他双手颤抖把刀贴近夫人伤口,闭住眼睛,狠心把刀往上面一按,牙齿“格登”一响,猛地一拔,拔出了那支利箭。这一切是在瞬间完成的,众人都惊呆了,山头的轻岚也凝然不动。
“见鬼去!”帕威把箭折了,掷进深谷,深深地吐一口气,一个个心里,也似落下一块大石头。
黎胞又犯难了。帕威怔怔地望着夫人和大伙。他们心中嘀咕,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是回头无路,只得把夫人背上山,把她救活再说。
又一次给李夫人喂药、熬药,又一次给她裹好衣服,黎胞们才上路。
今天的山路好长好长,今天的山岚好浓好浓。黎胞们跋涉过一个山头,便向山下了望,看看是不是快到家了。虽然谁都知道这段山路有多少个山头,有多少个岔口,闭上眼睛也懂得还有多少路程。然而,当寨子里的牛叫声、狗吠声传来时,人们悲喜交织着的心里,仿佛又添上了什么,不觉把脚步放慢。
“阿光,你先走回寨子,叫父老们把什么都免了!”帕威闷声闷气地说。
平时,每逢围猎丰盈时节,弟兄们反击官军征剿胜利归来,寨子里沉浸在纵歌狂欢里。分不清谁喜迎亲人,分不清谁凯旋而归,你挥动尖刀,我飞舞利刃,一对一对剌杀,洋溢着内心的喜悦。遍坡满路,人影跃动。或当面进攻,或背后袭击,或旁敲,或斜剌,迅猛如山雨骤来,轻捷如蜻蜓点水;人如老虎下山,如山猪坐地,如壮猴舒臂,刀光似白鲫过江,似金蛇狂舞,似银鹤掠翅。年老的,年幼的,在一旁 敲着牛皮鼓,吹着唎咧、唢呐,拍着手掌,助威助兴。胜利归来,不跳起狩猎舞,便如菜里少了盐,席间缺了酒,用十八丈长的藤片也提不起劲头。帕威打猎、跳舞,样样出色。老峒长因此看上他,大伙也因此而选举他接了峒长。哪一次不是他首先迈开矫健的步子?可是今天背着李夫人,他一点儿兴味都没了。
父老们捧着山兰酒,捧着香米饭站在路边,可是帕威只是点了点头,便走过去,大伙也默默地走过去了。一个个获胜归来的黎胞,就这样进了抱班寨,进了自己的家。
第一天李夫人醒过来,又昏过去了。秋玉一整天都侍候在她身边。这里是她的寮房,还是新盖好的,屋顶的葵叶还散着淡淡的清香。床上铺着的,也是她不久前织好的簇新的锦被。虽说秋玉的手艺无人不夸,可是让她自己满意的,才有这一张锦被。每一根纱线都是精心纺成的,每一个图案都是精心织好的。它还织进秋玉灼灼动人的眼神儿,织进秋玉那不肯告诉别人,只留在心底的梦。难怪它那么鲜亮,那么温馨。几回回,秋玉只要闭上眼皮,这张锦被就变成一朵彩霞,让她和阿光坐着,飞到一个人迹罕至,异常新奇的地方。那里,石头上长出山兰,千年的铁树挂了果,金钱豹同山羊一起拉军,彩虹给深谷架桥,常春藤缠着青松,金鹿儿唱起动听的歌……床上原来铺着一张半新的黎锦,秋玉望着,迟疑着,突然狠下心抱来这一张簇新的锦被。她阿妈见了,小声地骂,“你疯了?”便一把抢过被子。秋玉勃然生气,猛然抢回被子,跪下哭了,“妈,要不是夫人……咱可见不了你……可你……”原来,黎家人有条规矩,结婚要用的东西,过门时才能破新,否则会损了一生福气。阿妈见女儿这般,无可奈何,兀自叹息。
李夫人昏迷过去,又醒了过来,醒了过来,又昏迷过去。她随丈夫南下,一路上折腾,早已心力交瘁,完全是撑住,打发日子。到了崖州,她水土不服,病邪缠身。虚弱的身子,又怎受得严重的箭伤,挨得一夜的餐风饮露?
昏迷中,李夫人多少次模糊不清地唤着李通的乳名,唤着“大人,大人”。远在毕兰村的亲人,可曾听到她的呼唤?黎胞是听到了,每听到一次,心里就仿佛多射进一支利箭,酱赯色的面孔上颤栗着无比的哀伤、痛楚。可是他们,这些围在四周的黎胞,却无法让李夫人脱离苦海。
秋玉坐在身旁,含着泪给李夫人喂米汤。夫人呻吟着,“喝……喝……”秋玉把汤匙轻轻送到唇边。夫人哪里咽得下去?米汤一点一滴溢了出来,秋玉轻轻拭着,又一点一滴送进夫人嘴里,不喂汤时,秋玉就怔怔地想。她想起来了,仙水能治百病,使人起死回生。她听阿妈的阿妈说过的,仙水就在仙水潭里。于是,她眼前恍然现出一汪水潭。水潭四周石头儿可怪了,什么样子的都有。你想得出什么,它就象什么。四周的鲜花可奇了,红、黄、蓝、绿、紫,一年四季就在青枝上挂着。毒日晒时,一朵一朵,全都水灵灵的开着,风吹雨淋时,小朵张大成了大朵,大朵干脆爆了一枝繁花,潭里的仙水最神了。它象水不是水,象乳不是乳,象山兰酒不是山兰酒。渴了时,喝下它,只觉甜凉凉的,一直透到耳根;全身发冷时,只要闻到它的味儿,五脏六腑立刻暖烘烘的,年老的也来了劲儿。秋玉这般美美地想着,心里顿时惊喊,“夫人得救了,得救了!”于是,她立即打发阿光去讨回仙水。
“我该到哪儿去找呢?”阿光高兴是高兴,可为难了。
“这……”秋玉也为难了,阿妈的阿妈并不告诉她仙女潭在什么地方,“到尖峰岭去找吧。那里有仙人草,也会有仙水嘛!再不然,就到抱告岭、石门岭、南山岭去吧,反正,这仙水非找回来不可!”
阿光动身出发了。他明知道,这是上天摘星斗,但没路也得寻路上。
李夫人昏昏沉沉,又发起高烧来了。
第二天,帕威叫人杀三头牛,亲自请道公帕扣给夫人求神除病。
桌上摆满猪肉等祭品,燃上沉香做的香,香味扑鼻,香烟缭绕。帕扣一身打扮,对天、对地、对香案,连连叩了九叩。接着,他把一只公鸡剐了,扔在地上,站立在香案旁边,往桌上不停的拍击木卜,半闭着眼,嘴中念着:“嗽……嗽嗽……”他这样做是查一查阴鬼,询查是哪一种凶鬼的作崇。不料,那只公鸡扑打着翅膀死去时,头颅却朝向大门之外。帕扣猛摇脑袋,怕是要摇断了脖子,“大事不好,大事不好!病人犯了天规,神要惩治她!”
帕威一直在旁边看着,一听帕扣说,脸色涨红转青,慢慢煞白,嘴唇也微微哆嗦,“求求你禀告,神要惩治,就惩治我吧!”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帕扣又晃了晃脑袋,“嗽嗽嗽……峒长,一人做孽一人当,谁也替不得呀!嗽……嗽……嗽……”
突然,帕威两眼炯炯发光,伸过铁钳般的手捏住帕扣不放,“你说说,她有什么罪过?我要让她活,天哪,我的大恩人哪!”
“嗽嗽……嗽……”帕扣念念有词,“这是天意,天意!峒长,谁能跟天做对?”
“道公,请你再对天祷告,对神明祷告,求求你呀!”帕威苦苦哀求,简直要下跪了。
“峒长,神明只显灵一次。咱还敢再惹神明吗?嗽嗽嗽……”帕扣摆了摆手。
帕威垂头丧气,进了秋玉屋子。大伙见到他这个模样,话都憋住了。
李夫人时停时续的说胡话。傍晚时分,她一只手指了指外面,又指了指胸口,如此重复着这个动作。
一时,大伙都捉摸不着夫人为何这般动作,帕威急得直抓头皮。
“阿爹,夫人这不是要见李大人吗?”秋玉两手比划着,恍然大悟对帕威说,“阿爹,快告诉李大人呀!”
“对,咱为啥这傻?”帕威也恍然大悟,拍了拍脑壳,“咱怎不想到这层?砍了脑袋,也得请李大人上山!”
帕威又犯愁了:空口无凭,李大人会相信自己吗?秋玉看出他的难处,望着屋里四周,眼光慢慢落到李夫人那枝漂亮的头簪上,兀地放亮了,“阿爹,头簪——行吗?”
“对,头簪,对,头簪,爹这就去!”帕威破涕为笑了。
帕威嘱咐老伴利女儿一番,望着李夫人,合起双掌,“夫人,你好好歇着,大人会来的,会来的!”说完,他接过秋玉递过来的头簪,带着一个懂汉话的兄弟,马不停蹄星夜赶到了毕兰村。
时已二更。还是黑沉沉的夜,还是那盏孤灯。可上一回是李夫人苦苦着丈夫速归,这一回却是丈夫惦挂着妻子生死未卜。那天早上李德裕回家,见不到夫人,只见一滩血,一条红头巾,不禁大声哭喊,“夫人,你好苦哇!”夫人啊,你一生贤慧,半生忧愁,风烛残年,你难道惨遭不测?
李德裕认出那红头巾了,帕威在眼前恍然一闪而过。是他下了毒手?不可能。我李德裕问心无愧,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们绝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难道说,是胡思进嫁罪于他?李李德裕摇了摇头,要是这样,事情就更复杂了。李德裕左思右想,觉着事情凶多吉少,暗暗叫苦,“夫人啊,吾到哪里找你?”过了一个时辰,李三来了。李三哭着,把李夫人中箭受伤的前前后后都说了。李德裕听罢,勃然大怒,“胡思进,还吾夫人来,还吾夫人来!”两天内他找了胡思进三 次,次次都吃闭门羹。李德裕想要进山去找夫人,又怕被胡思进反诬一口,说他私通黎贼,一时委决不下,不禁仰天长叹,“想不到吾一个重臣,遭小人作弄到这地步!夫人危在旦夕,吾却眼睁睁坐视不救!”当时,李德裕坐在灯下,思绪奔涌,悲愤不已。不远处偏传来猫头鹰“咕,咕,咕”三下喊声,他兀地站起来,默默望着窗外。
这时,帕威早等在外面片刻,心急如火烧,却不敢惊动李德裕,直到他被鸟声惊扰,帕威才悄悄进了屋子,跪在李德裕背后。
“你们是谁?”李德裕转过身,瞥见来人,便大声喝问。
“大人,咱们该死,该死!”两人还是跪在地下。
“你们来此何干?”李德裕面对这不速之客,一表威严,厉声喝问,“快说,快说!”
帕威这才抬起头,嘴唇一张一闭的,颤抖着双手,献上李夫人的头簪。
这不是他吗?借着灯光,李德裕认出了帕威。但他不说话,迟疑着,突然一把抓过头簪,紧紧攥在手里,眼泪夺眶而出,“夫人,她,她怎么啦?你们快说,快说呀!”
“夫人,咱害了夫……夫人……她她重……重伤……在床……”帕威哭诉着。
李德裕猛然抬起手来,挥到半空,似乎要发作的样子,那手却伴着一声长叹,重重地落到他的大腿上,“嗨,你们干的好事……”
“大人,你就杀了我吧!”帕威哭个不止,“可你,一定要去见夫人!她想你呀……”
李德裕心如刀绞,恨不得立刻飞到夫人身边。可他一想起胡思进,又恨又怕,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大人,见夫人要紧!什么王法不王法?如今天高皇帝远,咱管王法,王法却不管咱!这窝囊气还要受多久?”刘松、李茂光一齐劝主人赶快动身。
李德裕沉吟半响,又叹了一口气,才匆匆草就一封书信——
胡刺史钩鉴:
卑职李德裕贱妾前夜遭官军箭伤,现已身陷黎峒,生命危在旦夕。吾两天内三次禀见大人,未尝面遇,以致一误再误。伏念夫妻一场,患难与共,安能见死不救?吾出于无奈,星夜携几奔赴黎峒,见妇一面,以尽为夫之道,达于人伦之义。吾皇向以礼义治国,大人幸勿见 怪。卑职自往自回,勿念。
李德裕把书信摺好,交与茂光,嘱他第二天早晨交胡思进,便带着李通,随着帕威直奔抱班寨而去。
下弦月还藏在浓云里。走在回风岭那幽深崎岖的山路上,黑魆魆的山头从两旁、从前面,不断地压来,压来,李德裕忽然觉得自己钻入了黑幽幽的无底洞。四周静极了,静到让人心寒,要不是偶尔有一声狼嗥,有一声鸟叫,还会以为一切都死灭了。李德裕何曾不在夜间走过山路?但那时他是一军之主,百骑千骑簇拥着他,气贯如虹,就是地狱,也敢去闯一闯的。而现在,他孤身陷进黑暗的无底洞,心灵也陷进悲伤的无底洞。今非昔比,完全是天壤之别。因此,李德裕走着,走着,只觉得恐怖从四面八方都压过来。好几回,他微微战栗,把害怕得透不过气来的李通紧紧搂在怀里,只有当他想起夫人还在山那边等着他,似乎听到了夫人深情的、虽然是那么微弱的呼唤,这个时候,心里才猛然一惊,提起精神,纵起马缰绳来。枣红色的龙驹马,似乎懂得主人的心思,平稳地小步跑了起来。“的的笃笃”的马蹄声,清越、欢快,惊破了黑夜的死寂。李德裕在那绝望之中,又听到了当年进军的鼓点……
天快亮时,抱班寨里彻夜跳动的篝火,一双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盼来了李德裕。
李德裕老远就下马,一下子扑到妻子身旁。这是相濡以染的妻子吗?怎么,怎么啦?才隔几天,就仿佛隔着了几年、几十年!李德裕握紧妻子的手,一次又一次呼唤着妻子的小名,喊声那样轻,却饱含着悲恸,颤抖着惋惜和抗争。夫人,你怎不回答丈夫,怎不拭一拭他的泪滴?哪怕是回答一声,拭一滴泪滴也好!还有,你也该亲一亲可爱的孩子,别让他泪流满面!夫人,你还应说一声,你根本不触犯什么天规!可是,你什么也不说,只顾昏昏沉沉地躺着……
李德裕把随身带的中药煮了,一汤匙一汤匙喂给夫人。 药汁,慢慢润湿她的嘴唇,渗入她的喉中。李德裕越发苍老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李夫人忽然缓缓睁开眼睛,呆滞的眼光在李德裕身上停留,久久的,才翕动嘴唇,轻轻喊出声来,“老爷——通儿——”
“夫人!”
“娘!”
爷儿俩几乎同时喊出声来。
李夫人把丈夫的手吃力地缓缓拉过来,按住自己的胸口,眼角浮上凄然的笑,“老爷——妾跟你这些年——怕是——”
“夫人,你要撑住,你能撑住呀!”李德裕哽咽着,“你说过,三年五载——咱们回城去——回京城去啊!”
夫人轻轻摇了摇头,吁了一口长气,苍白的脸上浮起一丝异常得意的笑容,“妾——可知足了。”
“夫人,你要撑住,阿光哥快回来,仙水——”秋玉呆痴痴地说。
“好姑娘——我——我”夫人说着,说着,突然断了气。
那一双美丽的眼睛就这样闭上了,永远地闭上了,再也见不到她的亲人了。也许,她活得太烦恼、太累、太沉重,要带着深深的爱到一个幽静的地方慢慢消受。
李德裕正想把夫人遗体运回崖州城安葬,不料茂光他们都上山来。原来,胡思进接了李德裕书信,竟诬谄他串通黎人谋反,要申报朝廷,治李德裕的罪。茂光他们走投无路,只好上山报讯。
“竖子,你欺人太甚!”面对接踵而来的沉重打击,李德裕招架不住了,大喝一声,就昏了过去。
事到如今,只好暂时把夫人在抱班寨安葬了。
多港峒十几个寨子遇上百年大哀。
李德裕入乡随俗,丧事由帕威按黎族风俗办了。
报丧时,十几个黎胞举起粉枪,对天空鸣枪三发。然后,才换下夫人衣服,给她换上新衣。祭奠仪式是从祭灵头饭开始。黎胞们在夫人头顶供放米饭、米汤等祭品,并用木棉花醮米汤滴入她的嘴里,给她“喂饭”。入殡前,帕扣和一位道公,把一只祭猪吊在屋檐下,将一个簸箕供放灵头饭祭了夫人,又拿着一支龙眼枝醮了清水,浇潄于夫人遗体上,给她“洗浴”,再用剪刀剪了她头上一缕青丝,表示对 夫人挽留的情意。入殓时,秋玉哭得死去活来,把自己织的锦被都放在棺木里,把自己那只玉镯子放在枕头底下。入殓盖棺后,黎胞再对空鸣枪三发。一个个哭得愁云惨惨,悲风呼呼,哭得青山低下头,哭得流水也呜咽。停尸七天期间,黎胞敲锣,打鼓,吹唢呐,昼夜给夫人奏了哀乐,道公们跳起五风舞,又一次为亡灵追祭。出殡择一个良辰吉日。道公们念经超度亡灵,德裕、李通、帕威、秋玉等人,跪在灵柩前嚎啕大哭。峒里一个个黎胞,全都披麻戴孝,抚棺而哭。送殡队缓缓而行,伴着唢呐声幽幽怨怨,伴着送葬歌悲悲恻恻,缠绵着山路弯弯……
坟地在后达岭上,是一块向阳坡地,李德裕亲自选定的。帕威按黎俗以蛋掷地,选定了墓穴。招魂之后,棺材下葬了。
李德裕痛哭祷告,“夫人,吾不能让你归返乡里,只能让你安息山林,遥望家园。吾有愧于你,宽恕我吧,宽恕我吧!”
帕威接着把停灵时放在灵柩旁的两株芭蕉树种在坟墓两侧。黎胞们痛惜夫人生前不能跟他们同欢共乐,只好盼望她的魂灵在黎乡创家立业。
微风吹来,芭蕉树摇曳几枝翠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