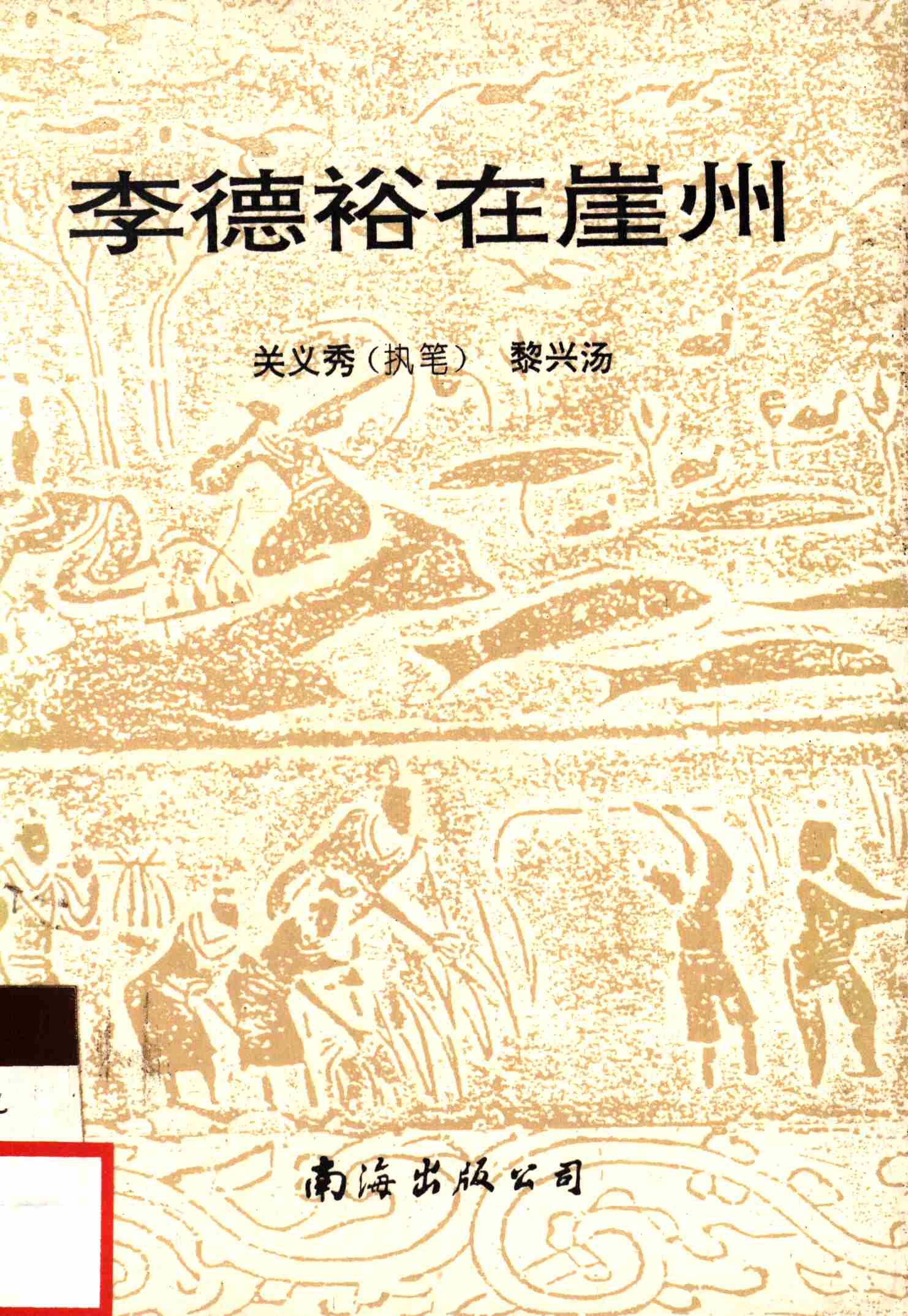内容
夜,张开一只黑洞洞的巨嘴,吞噬一穹湛蓝湛蓝,吞噬漫天星光,吞噬崖州城里家家灯火,只留下无边的黑暗。州衙内不时有几点萤火虫飞来飞去,仿佛鬼影在游荡。这并不给黑夜亮些生气,反而点缀着它的阴森。四周静悄悄的,州衙内偶尔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使人觉得那隐在黑夜里,俨然蒙面怪兽的牒楼、屋宇,正在摆布阵势。一阵闷热之后,一记闪电突然划过长空,宛如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口,横七竖 八,在夜幕上划过。接着,呼啸的海风穿过城外黑黝黝的椰林,穿过密密匝匝的槟榔丛,一直刮进城里。州衙内蜷伏在墙角的狗,发狂似地吠起来,惊醒了暮春三月的沉寂。然而,这只是风雨到来的前夕。天幕划过了,又合拢来,依然是使人透不过气来的穹窿……
三更时分,一个个黑影从城北荔枝林里,鱼贯着跃出。听不到说话声,听不到脚步响。黑影猫着腰,匍匐着前进,那么敏捷,那么自如,就像鱼儿在水里游着。黑影在大路口聚拢,依然没有人说话。只有一只手掌轻轻按着另一只手掌,一只只挨次按着。显然知道人都到齐了,有人轻轻吹一声口哨。黑影便分二路,人不知鬼不觉地踅到城北墙根底下埋伏。
两个黑影站起来,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听不到城里有一点动静,不约而同,爬过低矮的土墙。他们凝神片刻,还故意朝草丛里甩了一个石头。的确四周还是没有响声,除了刚才那一声石响,他们这才轻轻打开城北大门。
几十个黑影潮水般涌进了崖州城里。
那两个黑影走在前头,领着同伙一个紧挨一个,穿过大路小巷,穿过鳞次栉比的瓦屋房舍,一直来到州衙后面。
打头的两个黑影让同伙伏下,捱到州衙门口。轻轻一推,小门“咿”地开了,原来它只虚掩着。
“阿爹,难道狗官有了准备?”说话人原来是阿光,他凑近同来的人帕威耳朵旁低话,“难道有人走漏了风声?”
“怕什么!”帕威轻声应道。
“阿爹,这一回救不出秋玉,以后就更难了!咱们还是小心为好。你们先呆着,咱进去探个明白,再作打算!”
“也好,你快去快回!要不,咱爷儿俩一起去,咱憋得要死啦!”
“不,阿爹,你要领着大伙!”阿光说完,扭头走了。
四天前,秋玉被李德裕放走,又被胡思进抓回关在牢房里。帕威、李三他们等候在外面,一瞧不见人,二瞧不见影,知道事情糟了。刚好阿光从多港峒里赶了出来。李三探明情况,带着扮作汉人的阿光混进城里,摸清全部底细,事到如今,已别无道路可走,他们决定趁着黑夜打入州府,把秋玉救出。今夜,多港峒里的精壮人马都出动了。阿光只身探路,深感责任重大,一步闪失不得。他进了州府,蹑手蹑脚踏过一个个台阶,踩过一块块草坪,拐到墙角便躲着,故意弄些声响。然而,越走近牢房,他越按不住心里的躁动。黑糊糊的牢房隐隐现在眼前。他觉得那是火坑,那是要把他的好妹子烧糊、烧焦的火坑,可恶的火舌正四处乱窜。阿光差点忘了自己只身闯入虎口,要喊出声来,“好妹子,阿哥救你来了,你要挺住!”然而,阿光终于不喊,也不莽撞地走近牢房。在离牢房一二十步远的地方,他冷静下来。万一……他想起什么来了,摸出了鼻箫,轻轻吹了起来。鼻箫声再轻、再低,阿妹也会听到的,也会听得出是阿哥吹的。
阿光吹第二遍的时候,秋玉醒了。
几天来,她被关在牢房里给胡思进织黎锦。一拿起梭子,心儿便飞回胡多港峒。她仿佛见到阿光就在身旁,嘻皮笑脸,“阿玉,别光织花呀、鸟呀的,再织一个男娃娃和一个女娃娃。男的像我,女的像你。好不好?”她嗔怒地白了阿光一眼,“你贫嘴,你贫嘴!”却又任恋人爱抚着发烫的脸颊。逝去的一幕现在眼前,秋玉呆头呆脑,对着窗外出神。她恨不得身生双翅,飞回到姐妹们中间。今天上午刘松趁家丁不在,偷偷给她报讯,她一下子高兴得昏了。直到兵丁来了,她才卖力地织起来。这一天她织得快、织得好,让谁都以为她驯服了。夜来了,秋玉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谛听着外面的动静。她高兴,她埋怨,她担心,她咒骂。单调的打更声唤起她的难熬、盼望,唤起她的恩恩怨怨。可是她太累了,眼皮老爱打架。尽管她不时用织布的横棍捶打大腿,但捶着,捶着,却睡去了……
秋玉刚合眼便醒过来,一惊,那是什么声音,轻轻,袅袅,却饱含绵绵的、厚厚的情意?秋玉一骨碌滚起来,把头伸出窗去。她哭了,“阿光哥,你们可来了!”她发疯似地扑到门口,用力推房门。门却关得紧,推也推不开。秋玉一惊,门上了大锁,锁匙一定在胡狗官手里。“阿光哥呀,千万别遇上贼狗官!万一半夜三更他来……”秋玉心里叫起苦来。昨天胡思进又来过。他挑剔了一番,说贡品马虎不得,又满口夸奖秋玉,然后,把一只手镯塞进秋玉手里,便趁势靠到她的身上。秋玉倒退两步,挖苦他,“大人,别脏了你的身子!”胡思进一点也不尴尬,反倒一本正经似的,“也是,也是!只是鱼有鱼味,肉有肉味!”此刻,秋玉已做好准备,胡思进果真来尝鱼味,就陪上一条命给他。怕就怕胡思进识破大伙的行动,可就麻烦了。秋玉按捺住焦急,贴近窗口,学着鹦鹉喊了几声。她同阿光玩耍时,常常学着野猪叫、学着鸟叫、学着男子汉猎到野味时的嘻笑声,以此来取乐,却无形中露出温柔、文静中的豪爽,洒脱。
“秋玉,秋玉!”阿光急促地,轻声地喊着,摸黑挪到窗前。
“阿玉!”
“阿光哥!”
两人几乎同时叫出声来,两双手紧攥看不放。
“门锁了?”
“贼狗官比狐狸还精!”秋玉声音压得很低,但压不住心头的怒火。
“我扒瓦片,把你救出!”小心的阿光已忘掉了一切恨不得身长三头六臂。
突然,不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
“阿光哥,你听,怕是……快走,先别管我!快去找大伙再说……”秋玉怕有意外,狠心对阿光说,“快去,妹子等着你!”
阿光回头出了衙门外面,把情况都说了,听不到新的声响,便领着大伙闪入州衙。
突然三声鼓响,州衙里高处低处明处暗处全亮起火把。火把发出呼呼的燃烧声,吐着血红的火舌,喷出团团烟焰。刹那间,火起风来,风逞火威,惊动暮春那一个黑夜。
火光里胡思进站在牒楼挡身处。他见帕威他们进入埋伏圈,只是微微一笑,“顽黎,吾等候你多时了!”说罢,又亲自擂起鼓来。鼓声刚起,牒楼、厢房、正房里,一支支箭从垛口、窗棂、墙眼里飞出,一直飞向阵脚不稳的黎胞。
“不好了!”慌乱间,帕威大喊一声。他料不到,奸滑、刁钻的王得利早把李三、阿光暗地里跟踪,并把一切报告给胡思进。他更料不到胡思进已秘密布下天罗地网。
“弟兄们,散开,趴下!”帕威已回过神来,指挥一时手足无措的同伴,他自己则像一尊铁柱立在那里,两只手一左一右的挥舞大弓,把射来的箭打落在地。众兵丁不觉呆住。帕威不说话,乘空搭上一箭,专朝胡思进射去。弓弦响处,才猛喝一声,“中!”
胡思进一侧身,躲过呼啸而来的箭,勃然大怒,“射死他,射死这黎头的重赏!”
箭呼呼而来,帕威全无惧色,且战且退,带着同伴往暗处走,往旯旮儿躲,何机而动。可是处处都躲藏着兵丁,个个都想领功受赏。鼓声一起,呐喊声不绝于耳,箭镞也长了眼睛似的,专找人去。帕威只得东奔西窜。
“李大人,本官请你来看这出好戏,可有看头?”胡思进掩饰住内心的得意,对着身旁的李德裕故意问道。但一想到眼前这位不同心又难制服的同僚,竟被玩弄于手掌之中——他今晚要灭黎,杀鸡给猴看,看你李德裕再敢偏袒黎头黎妞!——就不免沾沾自喜,“李大人堂堂重臣,自然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不信顽黎无法无天,一味与官府做对。今夜之事,眼见为实了吧!”
此刻,李德裕心潮难平。他好悔恨,那天把秋玉送出城外,就免了今晚这场大祸。但这只能怪自己?好一个胡思进,把人往陷井里推,还要给人罪名。他做得绝了,调兵遣将,竟瞒过自己。临到今晚才把自己叫来,又是为了什么?无非要给自己一点颜色看看,即使官兵输了,也要把责任推给自己。气愤、恼恨、同情,一齐涌来。李德裕觉得心里沉沉的。他要发泄心中的郁积。在犹豫、徘徊中,他拿定了主 意,再也不能一误再误了。于是,他明为赞许暗实嘲弄地说:“胡大人,你棋高一筹呀!”
“大人过奖了,”胡思进指指前面,“其实,胡某完全为大人着想。将来平黎有功,李大人官复原职,重操权柄,胡某担当些干系,也是值得,值得!”
两人说话时,帕威却带着一帮兄弟,赶到牢房附近,跟早到那里的阿光会合。无奈胡思进已在那里埋伏人马。刚才阿光只身探牢时,他们想来个一网打尽,才按兵不动。等到阿光带伙伴们赶到,兵丁们一个个躲在草丛里就放起箭来。阿光几次舍身扑上牢房,都被乱箭射回。等到帕威赶来,黎胞合伙,直往牢门冲去。兵丁急了,又自恃人多势众,跃出拦截。双方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战。一方是激怒的火牛,眼里生火,全身着火,蹄下生风,角上长劲,面前是山,是石,都要把它烧个痛快,掀个痛快。另一方是贪婪的狼,仗着凶残,仗着狡猾,面前是骨,是肉,都要张开血盆大嘴吞食。于是,双方混战一场,刀光闪闪,剑影幢幢,阴云四起。
厮杀声阵阵传来,李德裕一直望着牢房那边。渐渐地,黎胞的呐喊声小了。李德裕暗暗吃惊,突然心生一计,便拱手对胡思进说:“胡大人,如今双方混战,恐怕胜负难卜。依吾之见,群黎夜袭州衙,实为劫出那个女子。只要黎女在押,官军就能诱其上钩,终能稳操胜券,就怕黎女被劫走,坏了大人功名!”
“李大人过虑了,”胡思进摸摸下颔,自信十足,“吾早在那里埋伏数十名训练有方之卒,头目又极为精干。群黎充其量五六十人,不谙兵法,唯恃膂力而已。不出多久,吾军定能把他们斩绝杀尽!”
“大人深谋远虑,佩服,佩服!只是智者千虑,恐有一失。吾曾闻群黎极为凶悍,视死为儿戏,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更兼夜战乃吾军之短,群黎之长。怕就怕狗急跳墙,群黎以死相搏,劫走黎女!”李德裕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
“吾调集兵力,围而歼之!”
“此言恐有不当。别处兵力一撤,势必空虚。万一群黎铤而走险,直捣公堂,毁我大印,打入房内掠走尊夫人,那后果作何设想?大人可不能唐突!”
“也是,也是,依李大人之计——”
“依吾之计,不如派武艺高强的几个精兵,趁着双方混战之际,悄悄带走黎女,把她押到楼上,一来可防她走失, 二来也可吸引群黎过来。大人便可发号施令!”
“此计甚好,”胡思进要寻出其中破绽,以防李德裕别有用心也无懈可击,不由叫好。但他又沉思起来,疑而发问,“只伯黎女被劫,岂不坏了大事?”
“大人所虑亦是。只是官兵在暗处,群黎如何便知?我那刘松胆大心细,武艺超群。大人多派几个人,吾再派他助一臂之力,如何?”李德裕从容道来,并无强加于人之意。
胡思进私下怀疑,却鸡蛋里挑不出骨头,便唤过身边四个亲兵和一个头目,嘱咐一番。李德裕则唤过刘松,“千万小心,莫让黎女跑了!”
刘松跟随李德裕多年,摸准了主人的脾性。此刻,他听李德裕把一个“跑”字念得有一点带劲,便明白主人话中有话。作为回报,他响亮地回了一声,“是!”
小头目领路,几个人绕到牢房后面。小头目趁无人,掏出胡思进刚给的钥匙开了后门,把秋玉捆了,往她嘴里塞进一团麻纱。秋玉拳动不得,嘴动不得,眼睁睁任兵丁把自己押走,直向牒楼方向而去。走了好几步远,阿光借着火光看见秋玉被押走了,大叫:“救秋玉!”不顾死活冲了上前,却被闻声而到的官兵困在中央。他左冲右突,却冲不出重围,眼看秋玉走到一个墙角。他又大声呐喊,帕威几个也从后面掩杀过来,眼看赶上秋玉。头目连忙把秋玉押进墙角黑暗里。这时,刘松瞅了个空,从背后甩出一个飞镖,猛地将小头目击倒,又故意喊起来,“伏倒,黎人箭射来了!”同来的兵丁不辨真假,一时走了神,秋玉乘机逃走。刘松这才故意抱起小头目来大喊:“不好了,官军中了箭,黎妞跑了!”
刘松这一喊,既掩护自己,又给帕威报了讯。果然,帕威听到秋玉走脱了,便死死缠住官军,不让他们搜捕女儿。崖州州衙里,又展开一场恶战。阿光瞅了个空儿,朝城北走,寻找秋玉去了。
秋玉一走脱,便往黑暗处、人声疏落处跑,一脚高一脚低,捱到一座假山后面。两只膝盖一软,瘫倒在一个大石上。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背着手,往那有梭角的地方就是搓。但那麻绳捆得紧,越搓,手越痛。也不知咬紧牙关多少回,也不知出了多少冷汗,仿佛死去了,又活过来,原来手上的绳竟搓断了。厮杀声就在不远处,秋玉忽然觉得胆怯。刚才在牢房里,心上系住同胞的安危,把自己给忘了。现在独自逃生,便似失群的小羊羔,被抛在深山荒岭之中。她二只手紧紧按住胸口,狠狠压迫那怦怦的心跳。天色渐渐变白,浓云里透出点点星光。天气虽还闷热,秋玉可透出一口气,她觉得自己是多峒港里最好命的人,叔伯哥弟都疼她,为她拼命,便笑了。这时,秋玉觉得毛孔里都长了力气,呼地一下站起来。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冲出去,要冲出去!这样才能对得起阿爹,对得住阿光哥,对得住峒里的兄弟姐妹们!
秋玉犯难了。四处是人,四处都是火光,该往哪儿走,才能逃出官军的魔掌?她想起来了,自己那天织布时,不是看见一条排水沟?那排水沟就在木栅附近,绿树、乱草掩映着,从崖州城百姓住区穿过州衙,一直通出城南门外。对了,只好爬水沟了,顺着排水沟往北走,就可逃出虎口。
秋玉摸到排水沟,半走半爬地前进。喊杀声逼近了,她顾不得满沟泥水,马上扑倒。蚊子成群结队在头上嘤嘤嗡嗡地盘旋,恶臭味一阵袭来,她全不理会,只顾爬。有两回,头碰上岸边石头,碰出了鲜血,她以为脸上的泥水,抹一抹,又爬。喊杀声远了,疏疏落落。她一阵惊喜,自己果真逃出州衙了?她挺起身子,环顾四周,证实自己逃出了虎口,不由深深吸了一口空气。可转瞬间,她又难过极了。阿爹,阿光哥,你们在哪里?你们快逃呀,快逃出州衙。我可撇下你们,自个儿逃出来了。你们一个个平安无事,我才得安生呀。你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为什么要活下去?秋玉怔怔地想,忽然咒骂起自己来了:瞧你愣头愣脑的,净长瞎心眼。咱阿爹行得方,走得正,摔在石头上也不会碰破皮,踩在刀尖上也不会出血,最是命大福大!那狗官黑心肠,天容不得他,骨头里都会生虫,不得好报。可是,李大人可不这样……今夜咱被押走,那凶神恶煞般的兵丁突然倒了,咱才脱得身,肯定是李大人的关照!
后来,秋玉爬上了水沟,别的都不想了,只是想万一阿爹还不出来,怎样给他们报个信儿。崖州城里人人都知道今晚出了大事,家家户户把门关紧。只有狗听到远处的声响,不时狂吠。秋玉想着,要是窜出阿爹那条猎狗来,该有多好。然而,哪里有它的影子?秋玉死了心眼,悄悄绕过一间间低矮的瓦房,到了崖州城北门附近。“嘭嘭嘭”的脚步声由远渐近,片刻间,一溜黑影出了城外。“阿光哥,你们等一等!”秋玉差点喊出声来。但她转念一想,万一是官兵追了出来,岂不送肉上钩?于是,她急忙躲到树丛后。脚步声远去了,她又后悔起来。她想他们一定是自己人,白白错过机会,便壮着胆子跑出城外。
秋玉慌不择路,见有小路可走,就尽力的跑。后面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秋玉胆子大了,趴在路边,想从脚步声中判断来人是谁。她失望了。突然,她的眼晴放亮了:路东不远的地方,亮着一盏灯光。那灯光在苍茫的夜色中显得异常孤独,却又异常亲切。秋玉眼前恍然闪现篝火的灰烬中残存的一点火炭,闪过姐妹们在篝火边取暖逗乐的情景。受一种下意识的驱使,秋玉身不由己向灯光方向挪去。近了,面前的一切都看得出来。这是一幢屋子。屋里一个女人陪灯而坐,轻声地叹息。咦,她好面熟?咱在哪里见过她?秋玉一想,想起来了:咱在牢房里织锦的时候,她陪李大人来过两次。她拿起黎锦啧啧口,又抚摸咱的手掌。她不说话,可咱看得出,她十分心疼咱,十分怜惜咱。对了,她就是李夫人。不知什么缘故,此刻秋玉见到她,就象见到自己的母亲,真想 扑进她的怀里,诉说心中的苦楚、惊喜和激动。
但秋玉还流着泪,喃喃自语,欲动不动的站住。过了会,她才鼓起勇气,走到屋子前面敲门。也就在这时,黑暗里有人喊一声,“秋玉!”秋玉一惊,好熟悉的声音,猛地转过身来,惊喜地喊,“阿光哥,是你!”便一头扑在他肩上,哭了——一对恋人,巧遇了。
“咿呀”一声,门开了。屋里的女人迟疑片刻,走出外面。
女人正是李夫人。当晚撑灯时分李德裕被胡思进喊进州衙,只剩她和李通留在毕兰村。她待娇儿睡了,便眼睁睁坐着,等待丈夫归来。丈夫一夜未归,她担惊受怕,近二日又偶感风寒,不觉心力交瘁。但她偏不能入睡,尽力的撑住。听到声音,她以为丈夫回来了,后来却察觉不是,但还是开门而出。
“夫人,打扰你了!”秋玉一步一颤,激动着走上前去。
“嗬,是你,孩子!”李夫人借着灯光,认出了秋玉,“你怎么走到这?哟,你出来了?好,好孩子,出来就好!”说完,她一把拉过了秋玉。
阿光还愣住。李夫人喊着,“孩子,快进屋里!”
“好哇,原来在这,你们跑不了!”黑暗里有人狂喊。原来,追出城外的官军发现了搜寻的目标。
“谁敢如此放肆?”李夫人怒不可遏,一甩袖子,朝黑暗里喝道,“这是李参军的家!还不给我走开!”
什么李参军张参军?老子只听得胡大人的吩咐。你如果识趣,交出黎男黎女,便可立功受赏!如若不然,便是私通黎犯,吃罪不起!”黑暗里那喊声越喊越凶。
“谁有胆的站出来,看你还懂不懂王法,随便抓人?”李夫人神不慌,心不跳,怒斥对手。
一瞬沉默。
突然,箭,一支、两支,冷啸啸地,朝阿光飞来。
阿光挥舞长弓,奋力把箭打落在地,便闪身出去,同在黑暗里的官军厮打。可是,还有暗箭射来,李夫人把秋玉拉住,不让她出去跟官军拼命。就在这时,另一支箭眼看射中秋玉,李夫人急忙把她推过一旁,无情的箭镞却穿进自己的背部。秋玉惊得连话也说不出,咬紧牙,把李夫人抱进屋里……
当时,阿光孤身一人同数个官军苦战,寡不敌众。幸有夜色掩护,更喜他在夜间常常出猎,练了一身本事,因此能同官军巧妙周旋,东击西闪、幸免于难。但他毕竟独力难支了。正在这时,帕威领着一群黎胞赶到。原来,帕威在州衙里听人喊“黎妞跑了”,便知秋玉走脱,拼死同官军干了一场,以掩护秋玉突围。后来,他四处寻不到秋玉,稍后又寻不到阿光,便知他们已走出州衙。于是,他便带着兄弟们突围。出了州衙,他们在城里也打听不到秋玉的下落,又见官兵追出城去,这才跟踪出了城外。数名官军眼见黎胞人多势众,早已不战而逃了。
虽然救出了秋玉,但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李夫人又中了箭,帕威分不清是悲,是喜,石头似的汉子捶胸大喊,“咱该死,咱该死!”
“阿爹,事到如今,只好火速进山!要不然,官军白天还会——”阿光不再说下去了。
“进山,进山,夫人该怎么办?”秋玉抱着昏过去的李夫人嚎啕大哭。
“恩人,恩人呀!”帕威、阿光跟着痛哭,大伙也跟着哭了。
留也不得,去也不得,大伙面面相面面相〓。
“可恨的狗官,”帕威大吼一声,“逼得咱们好苦哇!”
“咱们再杀回州衙去!”有人不解恨地说。
“阿爹,咱们现在是救人要紧呀,”阿光沉思片刻,
“咱们是不是把夫人背出城外,救了她,再作商量?”
“这箭,这背上的箭,该怎么办?”帕威直跺脚。
“这箭,现在还动不得!哦,有了!”阿光一边说,一边掏出草药水给夫人喂了。原来,这是他随身带的治疗金枪箭伤的药水。刚才心急,把什么都忘了。
东天渐渐发白。
“峒长,夫人大概不碍事了,咱们快走!”有人催促道。
“不行!谁知道李大人什么时候才回来?他不回来,医治夫人的伤口,她可就要……要……”阿光指着夫人出血的伤口说。
“阿爹,咱背上夫人走吧!她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秋玉泣不成声。
“走!”帕威铁青着脸说,“背起夫人走!救命要紧!”
阿光一声不吭,两腿一蹭,轻轻背起李夫人,秋玉在后面扶住她。
“慢!咱们先给她祭一祭祖先鬼!”帕威想起来了,挥手说。
可哪里请来的娘母?哪里弄得到祭物?帕威情急智生,叫过一个兄弟充当娘母,一边念动咒语:“哎……唎!哎……唎!……”一边给李夫人、他自己以及秋玉和阿光的颈项、双手各系上一条棉线。按照黎族的习惯,这表示他们三人是李夫人的亲属,棉线已经锁住病者,祖先鬼只好悄然离去。当然,这只是他们的善良愿望罢了。若说鬼,并不是祖先鬼,应该是官鬼。
祭祀完毕,阿光背起李夫人走了。
帕威望了屋里屋外,又记起什么来了,突然解下身上的红头巾放在桌子上。这头巾,正是他遇见李德裕时扎的。当然,他是想让李德裕知道,是他带走了李夫人。
这时,鸡刚刚喊了三遍。浓云散了,一弯下弦月挂在树梢,照着一群步履沉重的黎胞,向山路走去……
三更时分,一个个黑影从城北荔枝林里,鱼贯着跃出。听不到说话声,听不到脚步响。黑影猫着腰,匍匐着前进,那么敏捷,那么自如,就像鱼儿在水里游着。黑影在大路口聚拢,依然没有人说话。只有一只手掌轻轻按着另一只手掌,一只只挨次按着。显然知道人都到齐了,有人轻轻吹一声口哨。黑影便分二路,人不知鬼不觉地踅到城北墙根底下埋伏。
两个黑影站起来,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听不到城里有一点动静,不约而同,爬过低矮的土墙。他们凝神片刻,还故意朝草丛里甩了一个石头。的确四周还是没有响声,除了刚才那一声石响,他们这才轻轻打开城北大门。
几十个黑影潮水般涌进了崖州城里。
那两个黑影走在前头,领着同伙一个紧挨一个,穿过大路小巷,穿过鳞次栉比的瓦屋房舍,一直来到州衙后面。
打头的两个黑影让同伙伏下,捱到州衙门口。轻轻一推,小门“咿”地开了,原来它只虚掩着。
“阿爹,难道狗官有了准备?”说话人原来是阿光,他凑近同来的人帕威耳朵旁低话,“难道有人走漏了风声?”
“怕什么!”帕威轻声应道。
“阿爹,这一回救不出秋玉,以后就更难了!咱们还是小心为好。你们先呆着,咱进去探个明白,再作打算!”
“也好,你快去快回!要不,咱爷儿俩一起去,咱憋得要死啦!”
“不,阿爹,你要领着大伙!”阿光说完,扭头走了。
四天前,秋玉被李德裕放走,又被胡思进抓回关在牢房里。帕威、李三他们等候在外面,一瞧不见人,二瞧不见影,知道事情糟了。刚好阿光从多港峒里赶了出来。李三探明情况,带着扮作汉人的阿光混进城里,摸清全部底细,事到如今,已别无道路可走,他们决定趁着黑夜打入州府,把秋玉救出。今夜,多港峒里的精壮人马都出动了。阿光只身探路,深感责任重大,一步闪失不得。他进了州府,蹑手蹑脚踏过一个个台阶,踩过一块块草坪,拐到墙角便躲着,故意弄些声响。然而,越走近牢房,他越按不住心里的躁动。黑糊糊的牢房隐隐现在眼前。他觉得那是火坑,那是要把他的好妹子烧糊、烧焦的火坑,可恶的火舌正四处乱窜。阿光差点忘了自己只身闯入虎口,要喊出声来,“好妹子,阿哥救你来了,你要挺住!”然而,阿光终于不喊,也不莽撞地走近牢房。在离牢房一二十步远的地方,他冷静下来。万一……他想起什么来了,摸出了鼻箫,轻轻吹了起来。鼻箫声再轻、再低,阿妹也会听到的,也会听得出是阿哥吹的。
阿光吹第二遍的时候,秋玉醒了。
几天来,她被关在牢房里给胡思进织黎锦。一拿起梭子,心儿便飞回胡多港峒。她仿佛见到阿光就在身旁,嘻皮笑脸,“阿玉,别光织花呀、鸟呀的,再织一个男娃娃和一个女娃娃。男的像我,女的像你。好不好?”她嗔怒地白了阿光一眼,“你贫嘴,你贫嘴!”却又任恋人爱抚着发烫的脸颊。逝去的一幕现在眼前,秋玉呆头呆脑,对着窗外出神。她恨不得身生双翅,飞回到姐妹们中间。今天上午刘松趁家丁不在,偷偷给她报讯,她一下子高兴得昏了。直到兵丁来了,她才卖力地织起来。这一天她织得快、织得好,让谁都以为她驯服了。夜来了,秋玉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谛听着外面的动静。她高兴,她埋怨,她担心,她咒骂。单调的打更声唤起她的难熬、盼望,唤起她的恩恩怨怨。可是她太累了,眼皮老爱打架。尽管她不时用织布的横棍捶打大腿,但捶着,捶着,却睡去了……
秋玉刚合眼便醒过来,一惊,那是什么声音,轻轻,袅袅,却饱含绵绵的、厚厚的情意?秋玉一骨碌滚起来,把头伸出窗去。她哭了,“阿光哥,你们可来了!”她发疯似地扑到门口,用力推房门。门却关得紧,推也推不开。秋玉一惊,门上了大锁,锁匙一定在胡狗官手里。“阿光哥呀,千万别遇上贼狗官!万一半夜三更他来……”秋玉心里叫起苦来。昨天胡思进又来过。他挑剔了一番,说贡品马虎不得,又满口夸奖秋玉,然后,把一只手镯塞进秋玉手里,便趁势靠到她的身上。秋玉倒退两步,挖苦他,“大人,别脏了你的身子!”胡思进一点也不尴尬,反倒一本正经似的,“也是,也是!只是鱼有鱼味,肉有肉味!”此刻,秋玉已做好准备,胡思进果真来尝鱼味,就陪上一条命给他。怕就怕胡思进识破大伙的行动,可就麻烦了。秋玉按捺住焦急,贴近窗口,学着鹦鹉喊了几声。她同阿光玩耍时,常常学着野猪叫、学着鸟叫、学着男子汉猎到野味时的嘻笑声,以此来取乐,却无形中露出温柔、文静中的豪爽,洒脱。
“秋玉,秋玉!”阿光急促地,轻声地喊着,摸黑挪到窗前。
“阿玉!”
“阿光哥!”
两人几乎同时叫出声来,两双手紧攥看不放。
“门锁了?”
“贼狗官比狐狸还精!”秋玉声音压得很低,但压不住心头的怒火。
“我扒瓦片,把你救出!”小心的阿光已忘掉了一切恨不得身长三头六臂。
突然,不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
“阿光哥,你听,怕是……快走,先别管我!快去找大伙再说……”秋玉怕有意外,狠心对阿光说,“快去,妹子等着你!”
阿光回头出了衙门外面,把情况都说了,听不到新的声响,便领着大伙闪入州衙。
突然三声鼓响,州衙里高处低处明处暗处全亮起火把。火把发出呼呼的燃烧声,吐着血红的火舌,喷出团团烟焰。刹那间,火起风来,风逞火威,惊动暮春那一个黑夜。
火光里胡思进站在牒楼挡身处。他见帕威他们进入埋伏圈,只是微微一笑,“顽黎,吾等候你多时了!”说罢,又亲自擂起鼓来。鼓声刚起,牒楼、厢房、正房里,一支支箭从垛口、窗棂、墙眼里飞出,一直飞向阵脚不稳的黎胞。
“不好了!”慌乱间,帕威大喊一声。他料不到,奸滑、刁钻的王得利早把李三、阿光暗地里跟踪,并把一切报告给胡思进。他更料不到胡思进已秘密布下天罗地网。
“弟兄们,散开,趴下!”帕威已回过神来,指挥一时手足无措的同伴,他自己则像一尊铁柱立在那里,两只手一左一右的挥舞大弓,把射来的箭打落在地。众兵丁不觉呆住。帕威不说话,乘空搭上一箭,专朝胡思进射去。弓弦响处,才猛喝一声,“中!”
胡思进一侧身,躲过呼啸而来的箭,勃然大怒,“射死他,射死这黎头的重赏!”
箭呼呼而来,帕威全无惧色,且战且退,带着同伴往暗处走,往旯旮儿躲,何机而动。可是处处都躲藏着兵丁,个个都想领功受赏。鼓声一起,呐喊声不绝于耳,箭镞也长了眼睛似的,专找人去。帕威只得东奔西窜。
“李大人,本官请你来看这出好戏,可有看头?”胡思进掩饰住内心的得意,对着身旁的李德裕故意问道。但一想到眼前这位不同心又难制服的同僚,竟被玩弄于手掌之中——他今晚要灭黎,杀鸡给猴看,看你李德裕再敢偏袒黎头黎妞!——就不免沾沾自喜,“李大人堂堂重臣,自然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不信顽黎无法无天,一味与官府做对。今夜之事,眼见为实了吧!”
此刻,李德裕心潮难平。他好悔恨,那天把秋玉送出城外,就免了今晚这场大祸。但这只能怪自己?好一个胡思进,把人往陷井里推,还要给人罪名。他做得绝了,调兵遣将,竟瞒过自己。临到今晚才把自己叫来,又是为了什么?无非要给自己一点颜色看看,即使官兵输了,也要把责任推给自己。气愤、恼恨、同情,一齐涌来。李德裕觉得心里沉沉的。他要发泄心中的郁积。在犹豫、徘徊中,他拿定了主 意,再也不能一误再误了。于是,他明为赞许暗实嘲弄地说:“胡大人,你棋高一筹呀!”
“大人过奖了,”胡思进指指前面,“其实,胡某完全为大人着想。将来平黎有功,李大人官复原职,重操权柄,胡某担当些干系,也是值得,值得!”
两人说话时,帕威却带着一帮兄弟,赶到牢房附近,跟早到那里的阿光会合。无奈胡思进已在那里埋伏人马。刚才阿光只身探牢时,他们想来个一网打尽,才按兵不动。等到阿光带伙伴们赶到,兵丁们一个个躲在草丛里就放起箭来。阿光几次舍身扑上牢房,都被乱箭射回。等到帕威赶来,黎胞合伙,直往牢门冲去。兵丁急了,又自恃人多势众,跃出拦截。双方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战。一方是激怒的火牛,眼里生火,全身着火,蹄下生风,角上长劲,面前是山,是石,都要把它烧个痛快,掀个痛快。另一方是贪婪的狼,仗着凶残,仗着狡猾,面前是骨,是肉,都要张开血盆大嘴吞食。于是,双方混战一场,刀光闪闪,剑影幢幢,阴云四起。
厮杀声阵阵传来,李德裕一直望着牢房那边。渐渐地,黎胞的呐喊声小了。李德裕暗暗吃惊,突然心生一计,便拱手对胡思进说:“胡大人,如今双方混战,恐怕胜负难卜。依吾之见,群黎夜袭州衙,实为劫出那个女子。只要黎女在押,官军就能诱其上钩,终能稳操胜券,就怕黎女被劫走,坏了大人功名!”
“李大人过虑了,”胡思进摸摸下颔,自信十足,“吾早在那里埋伏数十名训练有方之卒,头目又极为精干。群黎充其量五六十人,不谙兵法,唯恃膂力而已。不出多久,吾军定能把他们斩绝杀尽!”
“大人深谋远虑,佩服,佩服!只是智者千虑,恐有一失。吾曾闻群黎极为凶悍,视死为儿戏,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更兼夜战乃吾军之短,群黎之长。怕就怕狗急跳墙,群黎以死相搏,劫走黎女!”李德裕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
“吾调集兵力,围而歼之!”
“此言恐有不当。别处兵力一撤,势必空虚。万一群黎铤而走险,直捣公堂,毁我大印,打入房内掠走尊夫人,那后果作何设想?大人可不能唐突!”
“也是,也是,依李大人之计——”
“依吾之计,不如派武艺高强的几个精兵,趁着双方混战之际,悄悄带走黎女,把她押到楼上,一来可防她走失, 二来也可吸引群黎过来。大人便可发号施令!”
“此计甚好,”胡思进要寻出其中破绽,以防李德裕别有用心也无懈可击,不由叫好。但他又沉思起来,疑而发问,“只伯黎女被劫,岂不坏了大事?”
“大人所虑亦是。只是官兵在暗处,群黎如何便知?我那刘松胆大心细,武艺超群。大人多派几个人,吾再派他助一臂之力,如何?”李德裕从容道来,并无强加于人之意。
胡思进私下怀疑,却鸡蛋里挑不出骨头,便唤过身边四个亲兵和一个头目,嘱咐一番。李德裕则唤过刘松,“千万小心,莫让黎女跑了!”
刘松跟随李德裕多年,摸准了主人的脾性。此刻,他听李德裕把一个“跑”字念得有一点带劲,便明白主人话中有话。作为回报,他响亮地回了一声,“是!”
小头目领路,几个人绕到牢房后面。小头目趁无人,掏出胡思进刚给的钥匙开了后门,把秋玉捆了,往她嘴里塞进一团麻纱。秋玉拳动不得,嘴动不得,眼睁睁任兵丁把自己押走,直向牒楼方向而去。走了好几步远,阿光借着火光看见秋玉被押走了,大叫:“救秋玉!”不顾死活冲了上前,却被闻声而到的官兵困在中央。他左冲右突,却冲不出重围,眼看秋玉走到一个墙角。他又大声呐喊,帕威几个也从后面掩杀过来,眼看赶上秋玉。头目连忙把秋玉押进墙角黑暗里。这时,刘松瞅了个空,从背后甩出一个飞镖,猛地将小头目击倒,又故意喊起来,“伏倒,黎人箭射来了!”同来的兵丁不辨真假,一时走了神,秋玉乘机逃走。刘松这才故意抱起小头目来大喊:“不好了,官军中了箭,黎妞跑了!”
刘松这一喊,既掩护自己,又给帕威报了讯。果然,帕威听到秋玉走脱了,便死死缠住官军,不让他们搜捕女儿。崖州州衙里,又展开一场恶战。阿光瞅了个空儿,朝城北走,寻找秋玉去了。
秋玉一走脱,便往黑暗处、人声疏落处跑,一脚高一脚低,捱到一座假山后面。两只膝盖一软,瘫倒在一个大石上。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背着手,往那有梭角的地方就是搓。但那麻绳捆得紧,越搓,手越痛。也不知咬紧牙关多少回,也不知出了多少冷汗,仿佛死去了,又活过来,原来手上的绳竟搓断了。厮杀声就在不远处,秋玉忽然觉得胆怯。刚才在牢房里,心上系住同胞的安危,把自己给忘了。现在独自逃生,便似失群的小羊羔,被抛在深山荒岭之中。她二只手紧紧按住胸口,狠狠压迫那怦怦的心跳。天色渐渐变白,浓云里透出点点星光。天气虽还闷热,秋玉可透出一口气,她觉得自己是多峒港里最好命的人,叔伯哥弟都疼她,为她拼命,便笑了。这时,秋玉觉得毛孔里都长了力气,呼地一下站起来。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冲出去,要冲出去!这样才能对得起阿爹,对得住阿光哥,对得住峒里的兄弟姐妹们!
秋玉犯难了。四处是人,四处都是火光,该往哪儿走,才能逃出官军的魔掌?她想起来了,自己那天织布时,不是看见一条排水沟?那排水沟就在木栅附近,绿树、乱草掩映着,从崖州城百姓住区穿过州衙,一直通出城南门外。对了,只好爬水沟了,顺着排水沟往北走,就可逃出虎口。
秋玉摸到排水沟,半走半爬地前进。喊杀声逼近了,她顾不得满沟泥水,马上扑倒。蚊子成群结队在头上嘤嘤嗡嗡地盘旋,恶臭味一阵袭来,她全不理会,只顾爬。有两回,头碰上岸边石头,碰出了鲜血,她以为脸上的泥水,抹一抹,又爬。喊杀声远了,疏疏落落。她一阵惊喜,自己果真逃出州衙了?她挺起身子,环顾四周,证实自己逃出了虎口,不由深深吸了一口空气。可转瞬间,她又难过极了。阿爹,阿光哥,你们在哪里?你们快逃呀,快逃出州衙。我可撇下你们,自个儿逃出来了。你们一个个平安无事,我才得安生呀。你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为什么要活下去?秋玉怔怔地想,忽然咒骂起自己来了:瞧你愣头愣脑的,净长瞎心眼。咱阿爹行得方,走得正,摔在石头上也不会碰破皮,踩在刀尖上也不会出血,最是命大福大!那狗官黑心肠,天容不得他,骨头里都会生虫,不得好报。可是,李大人可不这样……今夜咱被押走,那凶神恶煞般的兵丁突然倒了,咱才脱得身,肯定是李大人的关照!
后来,秋玉爬上了水沟,别的都不想了,只是想万一阿爹还不出来,怎样给他们报个信儿。崖州城里人人都知道今晚出了大事,家家户户把门关紧。只有狗听到远处的声响,不时狂吠。秋玉想着,要是窜出阿爹那条猎狗来,该有多好。然而,哪里有它的影子?秋玉死了心眼,悄悄绕过一间间低矮的瓦房,到了崖州城北门附近。“嘭嘭嘭”的脚步声由远渐近,片刻间,一溜黑影出了城外。“阿光哥,你们等一等!”秋玉差点喊出声来。但她转念一想,万一是官兵追了出来,岂不送肉上钩?于是,她急忙躲到树丛后。脚步声远去了,她又后悔起来。她想他们一定是自己人,白白错过机会,便壮着胆子跑出城外。
秋玉慌不择路,见有小路可走,就尽力的跑。后面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秋玉胆子大了,趴在路边,想从脚步声中判断来人是谁。她失望了。突然,她的眼晴放亮了:路东不远的地方,亮着一盏灯光。那灯光在苍茫的夜色中显得异常孤独,却又异常亲切。秋玉眼前恍然闪现篝火的灰烬中残存的一点火炭,闪过姐妹们在篝火边取暖逗乐的情景。受一种下意识的驱使,秋玉身不由己向灯光方向挪去。近了,面前的一切都看得出来。这是一幢屋子。屋里一个女人陪灯而坐,轻声地叹息。咦,她好面熟?咱在哪里见过她?秋玉一想,想起来了:咱在牢房里织锦的时候,她陪李大人来过两次。她拿起黎锦啧啧口,又抚摸咱的手掌。她不说话,可咱看得出,她十分心疼咱,十分怜惜咱。对了,她就是李夫人。不知什么缘故,此刻秋玉见到她,就象见到自己的母亲,真想 扑进她的怀里,诉说心中的苦楚、惊喜和激动。
但秋玉还流着泪,喃喃自语,欲动不动的站住。过了会,她才鼓起勇气,走到屋子前面敲门。也就在这时,黑暗里有人喊一声,“秋玉!”秋玉一惊,好熟悉的声音,猛地转过身来,惊喜地喊,“阿光哥,是你!”便一头扑在他肩上,哭了——一对恋人,巧遇了。
“咿呀”一声,门开了。屋里的女人迟疑片刻,走出外面。
女人正是李夫人。当晚撑灯时分李德裕被胡思进喊进州衙,只剩她和李通留在毕兰村。她待娇儿睡了,便眼睁睁坐着,等待丈夫归来。丈夫一夜未归,她担惊受怕,近二日又偶感风寒,不觉心力交瘁。但她偏不能入睡,尽力的撑住。听到声音,她以为丈夫回来了,后来却察觉不是,但还是开门而出。
“夫人,打扰你了!”秋玉一步一颤,激动着走上前去。
“嗬,是你,孩子!”李夫人借着灯光,认出了秋玉,“你怎么走到这?哟,你出来了?好,好孩子,出来就好!”说完,她一把拉过了秋玉。
阿光还愣住。李夫人喊着,“孩子,快进屋里!”
“好哇,原来在这,你们跑不了!”黑暗里有人狂喊。原来,追出城外的官军发现了搜寻的目标。
“谁敢如此放肆?”李夫人怒不可遏,一甩袖子,朝黑暗里喝道,“这是李参军的家!还不给我走开!”
什么李参军张参军?老子只听得胡大人的吩咐。你如果识趣,交出黎男黎女,便可立功受赏!如若不然,便是私通黎犯,吃罪不起!”黑暗里那喊声越喊越凶。
“谁有胆的站出来,看你还懂不懂王法,随便抓人?”李夫人神不慌,心不跳,怒斥对手。
一瞬沉默。
突然,箭,一支、两支,冷啸啸地,朝阿光飞来。
阿光挥舞长弓,奋力把箭打落在地,便闪身出去,同在黑暗里的官军厮打。可是,还有暗箭射来,李夫人把秋玉拉住,不让她出去跟官军拼命。就在这时,另一支箭眼看射中秋玉,李夫人急忙把她推过一旁,无情的箭镞却穿进自己的背部。秋玉惊得连话也说不出,咬紧牙,把李夫人抱进屋里……
当时,阿光孤身一人同数个官军苦战,寡不敌众。幸有夜色掩护,更喜他在夜间常常出猎,练了一身本事,因此能同官军巧妙周旋,东击西闪、幸免于难。但他毕竟独力难支了。正在这时,帕威领着一群黎胞赶到。原来,帕威在州衙里听人喊“黎妞跑了”,便知秋玉走脱,拼死同官军干了一场,以掩护秋玉突围。后来,他四处寻不到秋玉,稍后又寻不到阿光,便知他们已走出州衙。于是,他便带着兄弟们突围。出了州衙,他们在城里也打听不到秋玉的下落,又见官兵追出城去,这才跟踪出了城外。数名官军眼见黎胞人多势众,早已不战而逃了。
虽然救出了秋玉,但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李夫人又中了箭,帕威分不清是悲,是喜,石头似的汉子捶胸大喊,“咱该死,咱该死!”
“阿爹,事到如今,只好火速进山!要不然,官军白天还会——”阿光不再说下去了。
“进山,进山,夫人该怎么办?”秋玉抱着昏过去的李夫人嚎啕大哭。
“恩人,恩人呀!”帕威、阿光跟着痛哭,大伙也跟着哭了。
留也不得,去也不得,大伙面面相面面相〓。
“可恨的狗官,”帕威大吼一声,“逼得咱们好苦哇!”
“咱们再杀回州衙去!”有人不解恨地说。
“阿爹,咱们现在是救人要紧呀,”阿光沉思片刻,
“咱们是不是把夫人背出城外,救了她,再作商量?”
“这箭,这背上的箭,该怎么办?”帕威直跺脚。
“这箭,现在还动不得!哦,有了!”阿光一边说,一边掏出草药水给夫人喂了。原来,这是他随身带的治疗金枪箭伤的药水。刚才心急,把什么都忘了。
东天渐渐发白。
“峒长,夫人大概不碍事了,咱们快走!”有人催促道。
“不行!谁知道李大人什么时候才回来?他不回来,医治夫人的伤口,她可就要……要……”阿光指着夫人出血的伤口说。
“阿爹,咱背上夫人走吧!她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秋玉泣不成声。
“走!”帕威铁青着脸说,“背起夫人走!救命要紧!”
阿光一声不吭,两腿一蹭,轻轻背起李夫人,秋玉在后面扶住她。
“慢!咱们先给她祭一祭祖先鬼!”帕威想起来了,挥手说。
可哪里请来的娘母?哪里弄得到祭物?帕威情急智生,叫过一个兄弟充当娘母,一边念动咒语:“哎……唎!哎……唎!……”一边给李夫人、他自己以及秋玉和阿光的颈项、双手各系上一条棉线。按照黎族的习惯,这表示他们三人是李夫人的亲属,棉线已经锁住病者,祖先鬼只好悄然离去。当然,这只是他们的善良愿望罢了。若说鬼,并不是祖先鬼,应该是官鬼。
祭祀完毕,阿光背起李夫人走了。
帕威望了屋里屋外,又记起什么来了,突然解下身上的红头巾放在桌子上。这头巾,正是他遇见李德裕时扎的。当然,他是想让李德裕知道,是他带走了李夫人。
这时,鸡刚刚喊了三遍。浓云散了,一弯下弦月挂在树梢,照着一群步履沉重的黎胞,向山路走去……
相关人物
秋玉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