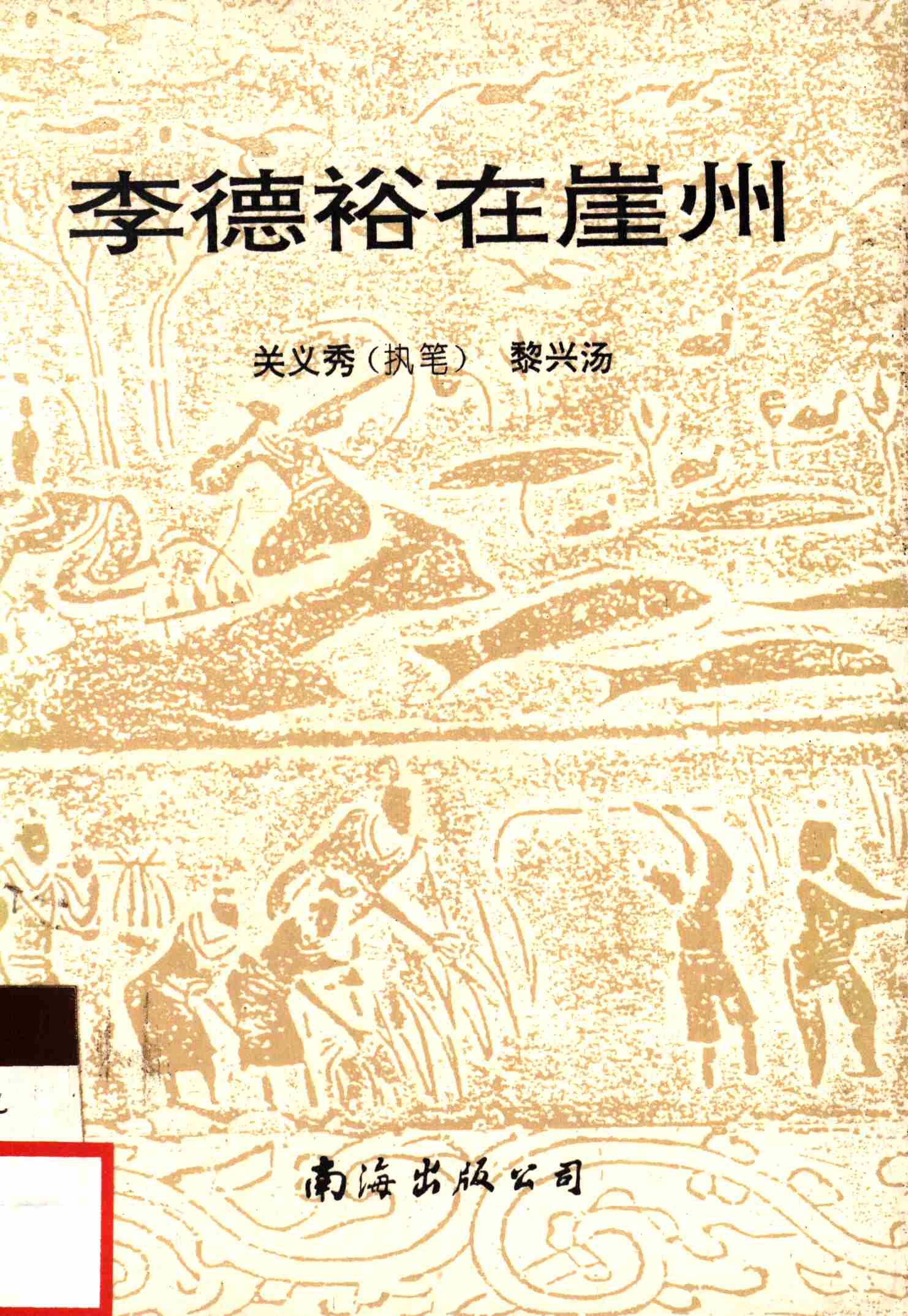内容
时光就是这样:它常常像蜜蜂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生活的艰辛中给你酿造蜜,使你尝到苦中有甜,滋长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可是它有时则像狂风,肆意掀翻原先苦心经营的巢,抖落花粉和蜂蜜。
这种情形,如今正应在秋玉的身上。十几年来,伴着日子的磨练,她走过孩童的天真无邪,走进少女的朦胧和初恋,走向那幸福的分娩。然而,她被抓来了,才经过短暂的一夜,无情的时光已把她的美梦撕得支离破碎,只留给她痛苦,留给她愤怒,留给她满脸泪痕。
“你们,都疯了!无缘无故抓我!放我出去!我要……回家!”秋玉被抓进牢时,一遍一遍地喊,此刻被关在州衙大厅里,依然一遍一遍地喊。声音可变了。原先那甜美、清脆、动情,虽然未丧失殆尽,但已分明掺进几分粗裂,几分凶狠,几分凄厉。
大厅里的听众,她连名儿都喊不上的大鼓、太师椅、题有“明镜高悬”几个赫然在眼的大字的匾,旋转着面孔,瞪大眼睛,对她报以热烈的响应。大厅里再无别人,却像有谁在丑陋地学着她的腔调。
秋玉感到受了奚落,受了嘲弄,索性闭上眼睛,朦胧中,一个高大的身影,吹着鼻哨,走进月光浸白了的寮房。他坐在铺着黎锦的床上,慢慢挪近低着头的妹子。哨声停了,忽然,他使劲咬了咬那浸白了的芒果下巴。“你坏,你坏!”妹子两只粉拳擂着男子的胸脯。“再使劲,我才更过瘾!”男子反倒给她加油。”你不得好死!”妹子加把劲擂,突然发觉说走了火,抽回手来抿住自己嘴巴。“我不得好死,你也不得好活!”男子不怕咸,不怕辣的,还是哈哈地笑。“别闹了,咱们出去走走,谈谈正经事!”还是男子先讲和了。于是,他们一前一后,踏着月色,走进那飘香的槟榔园……
“黎妞,胡大人要来看你!”一个兵士进了大厅,嗡里嗡气的声音惊破那一片温馨,那一片宁谧,那如火如蜜的初恋。
“你为什么要嚷?你为什么要嚷?”秋玉挣开眼睛,见兵丁在面前斜眼歪嘴直喊,便撒野似地照着。最难得,昔日的情景再现在眼前。
“哎哟,这个黎妞,好大的架子!”兵丁轻蔑也耸耸肩膀,突然一大步跨到秋玉身旁,弯下腰来,拧一拧秋玉的脸颊。
“你手指生疮!”秋玉狠狠白了他一眼,背过脸去。
不想,兵丁嘻皮笑脸又伸过手去,秋玉想用手一挡,却动不了。她都忘了,一双手早被捆了个严严实实,上面深一道、浅一道血痕斑斑……
兵丁讨了个没趣,只好讪讪地走开,秋玉可忍不住掉泪。
这双手,曾是那么自在,那么惬意地编织着一个黎家少女的五彩花环。它在山溪里洗濯,十指灵活地曲伸,仿佛异常鲜活的山蝦;它在园里拔草,拔出了杂草,也拔个玉米杆儿丝丝地往上冒高;它在山峦间轻盈地一抬,漾起和风,漾起绿浪,五色雀儿翩翩而来。它任阿光的手指扣着、掌心贴着,传给他回味无穷的感觉:它是那么温柔,如鸭绒飞到嫩草坪上,又是那么炽烈,如跳荡的篝火,燃红饱含活力的脸孔。
秋玉狠狠地瞪住手上的麻绳。突然,麻绳翻滚起来,变成一条大蟒蛇……
10岁那年,秋玉在山里采野艾。她边采边唱,好不得意。突然,一阵风骤然刮过来。猛抬头,一条大蟒蛇扫倒坡上小树,高昂着头,张开血盆大嘴,扑到了身旁。她猛然昏蹶过去,瘫倒在地。蟒蛇用尾巴捲紧她的脚踝,膝盖、腰、腹,眼看就要捲到胳肢窝。捲过胳肢窝,蟒蛇就会从头到脚,把秋玉囵囫吞下去,就像吞一只山羊羔一样。刹那间,秋玉觉得全身发痛,兀地甦醒过来。眼看蟒蛇正要捲过胳肢窝,一阵惊骇,冒了全身冷汗。可也就在这一瞬间,她猛地拔出身上插的绣花针,手起针落,刚好刺中蟒蛇的眼珠……
大蟒蛇恍惚间又变成手上的麻绳。秋玉又瞪了它一眼,忽然看到那张大桌子四支腿有棱有角的,便挪近桌去,反绑着的手靠近一支桌腿,狠狠搓了起来。越搓,手上的伤口越发疼不可忍,五脏六腑也仿佛被搓个鲜红淋漓。可怕的大蟒蛇,一支绣花针就对付过来。手上的麻绳却搓也搓不断,越搓越痛苦。然而,秋玉还是忍住痛,不停地搓。此刻,她只想着:拼死,也要逃出去!
“哟,火气还挺大!”秋玉听到说话声,连忙移开,来人应声而进。
秋玉不由偷偷瞥了来人一眼。他头上戴的是帽子吧,为啥两旁还长着两只牛耳朵?身上穿的是什么怪衣服?上面绣着怪东西,说鹰不是鹰,说兔不是兔。脸皮倒也白净,模样像个男人,偏偏挺胸凸肚,似个孕妇。孕妇却不会如此般托大,一提脚,衣袖扇得噼啪响。那一双眼睛,一眨眼皮寒,一眨眼皮热,一眨眼皮刮风,一眨眼皮闪电,难道说,自己清天白日见了装神弄鬼的道公?
“还愣住干啥?快给姑娘松绑!”秋玉还理不出头绪时,来人已命令跟进来的兵丁。
双手轻松了。难道这是真的?为啥无缘无故给抓来,又无缘无故给放了?秋玉怔怔地想,疑团一个解不开,又增加一个。
“姑娘,一场误会,”来人摸摸下巴,显出一个姿态,那等待秋玉对他的恩赐表示感激的姿态,然后谄媚一笑,“你是山中凤凰,可惜屈在深山,无人识货!本官胡思进请你来,无非让你见见世面。手下人照顾不周之处,姑娘可别见怪就是!”
“请我?”秋玉越发糊涂了。人,是这样请的?况且,自己跟这人无亲无故的,他怎么瞧得起咱呢?
“姑娘,你就多住几天,帮帮我织黎锦。本官决不会亏待你,朝庭还会重重的赏你!”胡思进慢悠悠地说。
秋玉当然不晓得其中的原委。起初,王得利使人报告,胡思进听了只是想,反正能抓到黎人就好。他不造反,我叫他造反,罪名也逃脱不了。日后功劳簿上自然加上这笔新帐。然而,兵丁抓来了秋玉,抢来了秋玉的两袋东西。一旦间,他解开麻袋,里面的黎锦闪亮闪亮,叫他看了心花怒放。可再偷偷看了织锦人,织锦人更比黎锦光彩。由不得他心驰神往,魂儿荡荡……
“大人,这……这……”秋玉一时慌了,想不出合适的话来。
“有什么难为情的?”胡思进喜滋滋地说,更是喜不自禁地想:女人都是这样,嘴里吃着,手里推着,假正经。但胡思进绝不得浮荡之徒,眼见心想,心想手动。那样岂不会失去州官的尊严!他要让鱼儿自动上钩,要让鸟儿入巢,要让鱼蝦把腥臊给猫,还得感谢猫。于是,他接着说,“姑娘,别难为情。我重用你,你便识抬举嘛。这叫做两厢情愿!”
两句话,惹得秋玉心里头扑腾扑腾一把大火烧起来。你别错看了人。老猴精,也捞不得溪中月。有什么情愿不情愿?咱前辈子不欠你的,这辈子不欠你的,为啥要给你织布?多港峒里大村小寨,多少阿哥阿弟求咱,一个个发誓当咱的牛,做咱的马,只想沾上咱这双手,咱都没法子答应。你好大的口气。你不知道,再轮上十辈子,也轮不上你。咱这一双手,已经许给了阿光哥……那一天,阿爹进房来,憨憨 地笑,显出极为关切的样子,“阿玉,你长大了,你的事……也该定了!”叫我怎么说呢?我心中早有了人,又怕把事情说穿了,伤了那么多阿哥的心。咱只得想想办法,让谁都过得去。咱让阿爹说明白,谁给采来了神仙草,咱就是他的人。毛头小伙听了,都咂咂嘴,不认输也得认输,“咱没有这个福气!”只有阿光哥说,“别人怕,咱不怕采不到神仙草”。好啦,咱就等他这句话。可咱还要考考他,“神仙一不扛锄,又不赶犁,哪来个神仙草”?阿光哥说,“尖峰岭顶上有两株灵芝,火烧不死,雷劈不动。这是神仙给咱种下的,咱一人一株。”阿光哥心中有了咱,弓箭上有胆,脚板下有路,爬过九十九座大山,蹚过九十九道青溪,闯过九十九个鬼门关。阿光哥终于采摘回两株灵芝草。此生此世,咱就是阿光哥的人了。谁要让咱离开阿光哥,除非他也能让太阳从西边出来!
秋玉一扭头,便向厅外走去。
却有两个兵丁挡住去路。
“你就走吧,走不快,再插翅给你飞!”胡思进只是狡黠地笑,“你别回来就是!”
秋玉吃了一惊,可是她奋不顾身推开士兵,头回也不回,汹声汹气地嚷,“放我走,我不会织布,我要回家!”
“你要回家?好说,好说!“本官不会白养着你!你依了我,织到鸡毛沉下水,织到本官不长胡子,”胡思进也说,边捋一捋几根山羊胡,嘿嘿地笑,“本官就用大轿抬你回去!”
胡思进一话落地,兵丁四只手便来光顾,把秋玉往后推,推了个树倒墙塌。
秋玉被推倒地,屁股仿佛挨刀砍,挨斧劈,疼痛万分。可她心里才更痛苦。一个17岁的黎家少女,过惯了天真烂漫的生活,未曾体味到人生的屈辱,看惯了鲜花,香草,未曾见过魑魅魍魉,享受了人际的纯真、友爱。未尝领略卑鄙、恫吓、虚伪、奸诈,这一回,她什么都享受了。她感到茫然、恐怖,似乎身临悬崖绝壁,下面是万丈深渊,有豺狼张着如剑的利牙,有山鬼洞开血盆大嘴。她惊骇过去,又苏醒过来。她突然想到死,好留得一个自自在在,清清白白。只见她头一抬高,猛地向发霉的青砖地板碰去——
“哎哟,年纪轻轻的就寻死?”胡思进一把拉起秋玉,却若无其事地说。
秋玉呆呆地站住。
“你好糊涂呀,只要织个三五天,我就放你回家!”胡思进依然那样若无其事,口气却软和多了。
糊涂?是呀!咱才是含苞的花儿,学飞的鸟儿,怎能撇下黎家的山,黎家的水,怎能撇下黎家的阿爹阿妈、姐姐妹妹?对了,自己要活下去!秋玉忽然清醒过来,转动着脑瓜儿。俗话说,逼子成才,这一回却是逼得秋玉说起谎话。她心头卜通卜通猛跳,却极力显出自然、煞有其事的样子,“大人,咱得谢你。可是空手不能打虎,没刀不能砍柴。没有梭子,咱怎能织呀?”
“我当是缺什么,梭子有的是!”胡思进以为秋玉回转心意,免不了高兴几分秋玉“演技”出色竟一时日过胡思进。
“咱要的是神梭。没有神梭,咱实在织不好黎锦!”秋玉十分为难。
“哪来神梭”胡思进着急地问。
“大人信得过,咱就回家拿来。这是祖上传下宝贝。多亏它,帮了咱的大忙。”秋玉说得不慌不忙。
“你家里果真有神梭?”胡思进目不转睛地盯住秋玉。
“是!”秋玉极力显出镇静。
“神梭哪里来的?难道神仙去过你家里不成?”胡思进声色俱厉。
“祖上……传下来的。”秋玉声音有点低怯。
“抬起头来看我!”胡思进走到公案前,拍了拍惊堂木,“你在骗本官!”
“不…骗!不骗!”秋玉竭力辩白。
“哼,一个黎妞也敢来捉弄本官,狗胆包天,可恨,可恶!”胡思进狂笑不止,“本官要被一个黎妞骗过,岂不是枉为州官,白吃朝庭俸禄!来人,给她撑嘴,教她学精!”
门口两个兵丁应声而进,刮了她一巴掌,又把她双手反绑。
“胡大人,吾来迟了!”外面传来一声宏亮的声音。
谁敢如此放肆?胡思进刚要发作,一看来人,一种神色,那么不可捉摸,那么难以言状的神色,不易察觉地一掠而过,这才冲着进来的人答礼,“李大人,你—”
来人正是李德裕。他默默地望了秋玉一眼,对胡思进说:“胡大人,李某迟来,深感渎职,还望大人海涵!”
“李大人,你说到哪里去啦?你言重了!”胡思进还在捉摸什么,听见李德裕道歉之辞,连忙拱手应答。
“崖州出了作奸犯科之徒,李某身为司户参军,缉捕不力,反让胡大人代劳,岂不是卑职过错?”李德裕说。
一时,胡思进沉吟不语。他派人把秋玉抓来,当时忘了州衙内新来的同僚。面前这个同僚,不是庸常之辈。自古来,宰相腹里能撑船。他撑哪家子管船,是否跟自己同一条水路,实在讳莫如深。不管怎么说,凡事都得多长几个心眼,多留几条活路。但想来想去,活路并不多条。要么就说,这个黎妞,她的父亲,都是贼,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也可让李德裕相信,黎山十八峒,个个青面獠牙,无法无天。日后胡某剿黎、平黎,他也不敢来饶舌,也得跟自己卖命。就怕李德裕弄个水落石出,抓了把柄,告胡某草官民命。要么就说,这黎妞手巧,特意让她来织锦,上贡朝庭,这对谁都有好处。对了,以朝庭的名义说话,谅李德裕也不敢多嘴。于是,胡思进忽然笑道,“大人此言差矣。这姑娘并非作奸犯料之徒,实乃本州要上贡黎锦于朝庭,故而把她唤来!”
“你说谎!兵丁抓咱们父女,抢咱们东西,是为了让咱来织锦?”秋玉指着胡思进责问。
“李大人,你亲眼见了,黎妞就是不识抬举。她不但不来州府,反而伙同她贼父,在墟市上为非作歹。兵丁们一气之下,还不把她抓来? ”胡思进狠狠白了秋玉一眼,转身对里德裕叹息,“崖州出了此等事,吾深为遗憾!为了一州百姓之安宁,吾只好严惩此等狂徒!”
胡思进或许不知道,他说得越动听,掩盖得越巧妙,就越遭李德裕的耻笑,越引起他的愤慨,使李德裕还存有的好感、期待,化为乌有……
出事的当天下午,李三回船了。不知怎的,他心里似挂碍什么,就加把劲赶路,顺风船便提前抵港。帕威赶到晒经坡墟,王得利却躲起来了。帕威一气之下,赶到海边找同伴。同伴找到了,又遇上李三,帕威“哇”地一声哭了。
“同年,你有什么伤心事?快说!,快说!”李三不由得焦急。
帕威哭着,把一切都告诉李三。
同伴们嗷嗷喊起来,“先收拾王得利那小子!”
李三脸色变得异常冷峻“先救出妹子要紧!那小子,慢慢再收拾!”
几个同伴又嚷起来“咱打进州衙去!救出孩子,再把狗官一刀剐了,岂不痛快?”
“鲁莽不得!”李三直摆手。
“那可怎么办?”大伙面面相〓家。
“如今只好找李大人看看!”“李三思忖半晌,叹了一口气。众人犹豫不定,眼看无路可走,只得照办。
一行人乘着夜色,赶到了毕兰村。同伴都稍候在村外,李三、帕威两人悄悄进入村里。
李德裕正在灯下看书,忽听有人喊一声:“李大人!”回头看时,却见两人跪在地上,不禁动问,“尔等是何人?胆敢闯进官员私室?”
“李大人,咱这小小舵工,你还可曾记得?”李三不请自起,站在一旁哂笑。
帕威不觉跟着站起。猛抬头,心中一阵惊喜:他不是墟市上遇到的老先生吗?咱请他写过一张状子!可他又换上这套官服,难道他——
李德裕认出了来人,失声叫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二位!请坐,请坐!” 一边让了坐,一边问李三,“这回没遭到海盗了吧?”
“托大人的福,不曾遇到海盗!你一治,几个草民都怕了!可是,崖州城里却出了官盗。不晓得大人是否知道?李三拱手说。
“哟,州城里出了官盗?”李德裕沉思着,忽然记起什么,便向帕威,“你那孩子呢?”
“她命苦哇,老先生!”帕威伤心透了。
“她被抢啦,被官府人抢走了!”李三无不愤慨地说,转身对帕威,“他不是老先生,是官府里的好人!咱得请李大人给咱作主!”
“李大人,官府的人不把咱黎人当人看哟!”帕威声声是血,是泪,是有力的控诉!
“大人,崖州的百姓眼巴巴的望着,你给不给汉人、黎人,都作个主呀!”李三跪下了,帕威也跪下了……
“你们都起来,起来!我想想办法!”李德裕说。
“难为胡大人了!”李德裕把一切都埋到心底,蒙在鼓里似的恭维胡思进。其实,他已明白,胡思进是主谋。他明不争,暗要斗,要把主动权抓在手里,才好救出秋玉,于是,显出为胡思进效命的样子,”吾蒙胡大人器重,却不建尺寸之动。大人理当让李某审理此案,以报效于大人万……”
“如此小案一桩,何敢惊动大人,“胡思进颇为彬彬有礼,然后,诡秘一笑,“敢情李大人信不过胡某?”
“岂敢,岂敢!”李德裕欠身答礼,“只是李某既为司户参军,便不该虚在其位。虽然老朽不才,理应出力才是!”
“李大人,好——吧!今日之事拜托大人了!”胡思进面露愠色,拂袖而起。
秋玉本是被告,现在反倒成了看客。她认出李德裕原来就是那位老先生。一些话她听不懂,但从两人的表情中,她隐隐察觉出其中的阴差阳错、她不由暗暗地感激李德裕。胡思进拂袖而起时,她竟为李德裕捏着一把汗,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了。
“胡大人,请慢走,”李德裕拿定主意,让胡思进留下,免得他以后反诬一口,“今日之事,还仰仗大人鼎力相助!”胡思进说声“好吧”,翘起二郎腿坐了。
李茂光擂罢三通鼓,李德裕龙行虎步,威风凛凛,坐镇公堂,三拍惊堂木,“被告现押在此,再传原告上堂!”
李茂光领签欲走,胡思进却在一旁讪笑,“黎家父女打劫,崖州人谁不知晓?要找原告,全城人都是原告,大人如何发落?既有犯人在押,定罪便了,大人何必节外生枝?”
“胡大人,请别过虑,李某自有道理。量刑绳法,一丝不苟,吾岂能马虎?”李德裕说罢,递了个眼色,李茂光抬腿便走。
眨眼间,李茂光已把王得利押上公堂。
原来,李德裕早命刘松几个,以崖州司户参军相邀为名,把王得利领进州衙。听李茂光说参军有请,王得利乐呵呵地疾走如飞。及到进了州衙,发觉气氛森严,才生疑云。然而,他看到胡思进在,便得意忘形,上前弯腰作辑。
“来人可是原告,还不跪下!”李德裕目光炯炯,扫视王得利,拍了拍惊堂木,“公堂之上,别忘了规矩!”
“什么原告?”王得利如堕五里雾中,瞠目结舌,扑通一声下跪。
“你仔细看看,旁边跪着的是谁?”李德裕喝了一声,“你可认得她?”
王得利这才发现秋玉也跪在堂上,满面怒容。他又是慌乱,又是得意,不由嘘了一声,“认得,认得!”
“本官谅你也会认得。你既是原告,便把这女子如何打劫,都说个青红皂白!倘若有半句不实之词,可别怪本官不客气!”李德裕有板有眼的说。
王得利眼看李德裕仪表威严,心里发怵,“咚咚”直打鼓,骨碌骨碌转悠着眼神。无形中,他瞥见胡思进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不以为然的目光,腰杆子一下变硬,嘴巴也转得灵。谁听了都会相信秋玉父女真是十恶不赦的强盗。
“大人,他,贼喊捉贼,含血喷人!”秋玉被激怒,忍无可忍。
“静,静!”李德裕喝一声,又问王得利,“你说的可是实话?”
“半句是假,舌头立刻烂掉!”王得利说。
“抬起头看!你可认得本官?”李德裕一笑。
刚才匆促之间不曾看清,这回认出李德裕来了,王得利脑里“嗡地一声,似乎当头挨了一捧。天哪,他……他不是墟市上那个先生么?
“你可曾见过本官?”王得利张着嘴唇不说话时,李德裕又笑了笑。
“大人,咱做小买卖的,怎能有眼福呢?”刹那间,王得利已回过神儿,摇了摇头。
“茂光、刘松,你们跟我同行的,认一认他,该不是本官眼花了吧?”李德裕示意二人。
“禀大人,此人正是墟市上为非作歹、顶撞你的奸诈之徒!他烧成了灰,在下也会认得!”刘松、茂光不约而同地说。
“如此说来,你就是欺诈黎家父女,反倒诬蔑好人,谋财害命的恶棍。王得利,你该当何罪?”李德裕狠狠拍了拍惊堂木。
“大人,你们三人该……该不是认错了人吧?”王得利声音有点发抖,却还抵赖着。
“李大人,果真如此,恶棍该重重的法办。只是瞧他那个模样……李大人,你们会不会一时认错人来呢?”胡思进连骂带帮地说。
“你们都看,”李德裕忽然从衣袖中取出王得利写的那张字条,“你们都看清楚,白纸黑字,本官该不是诬蔑好人吧!”
胡思进一瞧,心里叫苦不迭,然而,眨眼间又亮出新招,朝着王得利喝道,“你这刁滑小民,也胆敢欺骗本官!要不念你初犯,非打断你的狗骨不可!还不给李大人谢恩,还不快快滚开!”
王得利似乎得到救命稻草,捣蒜似地磕头,便要溜走。
“且慢!”李德裕喝一声,又回头向胡思进说,“今日之事,非同儿戏!只怕让奸人逍遥法外,有伤崖州风化,世风日下,民无宁日。胡大人须慎重为之!”
“李大人深谋远虑,胡某佩服,佩服!只是李大人初到崖州,风俗民情略有不察之处。崖州滋事惹祸之最烈者,莫过于顽黎。他们聚众于山林之下,茹毛饮血,不服王化,或打家劫舍,或敢城略地,防不胜防,实为吾心腹大患。区区小民,何足挂齿?”胡思进慷慨激昂,说出一番话来。
“胡大人,贤者治国,赏罚分明,恩威并加,黎民自然感化。昔日诸葛南抚百越,终成大业。黎人果若如此凶顽,依吾看来,更应攻心为上!”李德裕一样慷憾激昂。
“可惜诸葛亮孔明已不一一复生!”胡思进拖长猫腔,忽然以攻为守,“李大人,你对黎人如此偏爱,该不是沾亲带故?”
“吾初到崖州,便沾亲带故,胡大人久治崖州,何不沾亲带故?”李德裕从容应答,“吾所念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九州之民,莫非王臣,对治下百胜一视同仁,才不辜负皇上之恩!”
胡思进时语塞。于是,李德裕叫刘松解开秋玉手上麻绳,王得利却乘机溜了,胡思进也悻悼地走了。
秋玉眼里淌着滚滚的热泪,对着李德裕下脆,一连叩了几个响头。李德裕安慰她一番,嘱她出城去,外面自然有人接应她。
仿佛一只挣脱囚笼的小鸟,秋玉急急忙忙跑出大厅,跑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朝李德裕远去的背影一再叩头,然后,飞也似地跑到崖州城门口。又要见到乡亲们了,又要像自在的鸟儿一样,秋玉快活极了,差点喊出声来。城外接应的亲人,也在深情望着。突然,城门提早关了。冷不防,三支长枪伸了过来,一齐对准秋玉的胸口……
她“呸”了一声,转身回时,却见胡思进在对面狞笑,“哈哈,在崖州究竟谁说了算?”
“当然是大人,当然是大人!”胡思进背后的王得利点头哈腰。看上去,真像帕威出猎时那条花狗。
这种情形,如今正应在秋玉的身上。十几年来,伴着日子的磨练,她走过孩童的天真无邪,走进少女的朦胧和初恋,走向那幸福的分娩。然而,她被抓来了,才经过短暂的一夜,无情的时光已把她的美梦撕得支离破碎,只留给她痛苦,留给她愤怒,留给她满脸泪痕。
“你们,都疯了!无缘无故抓我!放我出去!我要……回家!”秋玉被抓进牢时,一遍一遍地喊,此刻被关在州衙大厅里,依然一遍一遍地喊。声音可变了。原先那甜美、清脆、动情,虽然未丧失殆尽,但已分明掺进几分粗裂,几分凶狠,几分凄厉。
大厅里的听众,她连名儿都喊不上的大鼓、太师椅、题有“明镜高悬”几个赫然在眼的大字的匾,旋转着面孔,瞪大眼睛,对她报以热烈的响应。大厅里再无别人,却像有谁在丑陋地学着她的腔调。
秋玉感到受了奚落,受了嘲弄,索性闭上眼睛,朦胧中,一个高大的身影,吹着鼻哨,走进月光浸白了的寮房。他坐在铺着黎锦的床上,慢慢挪近低着头的妹子。哨声停了,忽然,他使劲咬了咬那浸白了的芒果下巴。“你坏,你坏!”妹子两只粉拳擂着男子的胸脯。“再使劲,我才更过瘾!”男子反倒给她加油。”你不得好死!”妹子加把劲擂,突然发觉说走了火,抽回手来抿住自己嘴巴。“我不得好死,你也不得好活!”男子不怕咸,不怕辣的,还是哈哈地笑。“别闹了,咱们出去走走,谈谈正经事!”还是男子先讲和了。于是,他们一前一后,踏着月色,走进那飘香的槟榔园……
“黎妞,胡大人要来看你!”一个兵士进了大厅,嗡里嗡气的声音惊破那一片温馨,那一片宁谧,那如火如蜜的初恋。
“你为什么要嚷?你为什么要嚷?”秋玉挣开眼睛,见兵丁在面前斜眼歪嘴直喊,便撒野似地照着。最难得,昔日的情景再现在眼前。
“哎哟,这个黎妞,好大的架子!”兵丁轻蔑也耸耸肩膀,突然一大步跨到秋玉身旁,弯下腰来,拧一拧秋玉的脸颊。
“你手指生疮!”秋玉狠狠白了他一眼,背过脸去。
不想,兵丁嘻皮笑脸又伸过手去,秋玉想用手一挡,却动不了。她都忘了,一双手早被捆了个严严实实,上面深一道、浅一道血痕斑斑……
兵丁讨了个没趣,只好讪讪地走开,秋玉可忍不住掉泪。
这双手,曾是那么自在,那么惬意地编织着一个黎家少女的五彩花环。它在山溪里洗濯,十指灵活地曲伸,仿佛异常鲜活的山蝦;它在园里拔草,拔出了杂草,也拔个玉米杆儿丝丝地往上冒高;它在山峦间轻盈地一抬,漾起和风,漾起绿浪,五色雀儿翩翩而来。它任阿光的手指扣着、掌心贴着,传给他回味无穷的感觉:它是那么温柔,如鸭绒飞到嫩草坪上,又是那么炽烈,如跳荡的篝火,燃红饱含活力的脸孔。
秋玉狠狠地瞪住手上的麻绳。突然,麻绳翻滚起来,变成一条大蟒蛇……
10岁那年,秋玉在山里采野艾。她边采边唱,好不得意。突然,一阵风骤然刮过来。猛抬头,一条大蟒蛇扫倒坡上小树,高昂着头,张开血盆大嘴,扑到了身旁。她猛然昏蹶过去,瘫倒在地。蟒蛇用尾巴捲紧她的脚踝,膝盖、腰、腹,眼看就要捲到胳肢窝。捲过胳肢窝,蟒蛇就会从头到脚,把秋玉囵囫吞下去,就像吞一只山羊羔一样。刹那间,秋玉觉得全身发痛,兀地甦醒过来。眼看蟒蛇正要捲过胳肢窝,一阵惊骇,冒了全身冷汗。可也就在这一瞬间,她猛地拔出身上插的绣花针,手起针落,刚好刺中蟒蛇的眼珠……
大蟒蛇恍惚间又变成手上的麻绳。秋玉又瞪了它一眼,忽然看到那张大桌子四支腿有棱有角的,便挪近桌去,反绑着的手靠近一支桌腿,狠狠搓了起来。越搓,手上的伤口越发疼不可忍,五脏六腑也仿佛被搓个鲜红淋漓。可怕的大蟒蛇,一支绣花针就对付过来。手上的麻绳却搓也搓不断,越搓越痛苦。然而,秋玉还是忍住痛,不停地搓。此刻,她只想着:拼死,也要逃出去!
“哟,火气还挺大!”秋玉听到说话声,连忙移开,来人应声而进。
秋玉不由偷偷瞥了来人一眼。他头上戴的是帽子吧,为啥两旁还长着两只牛耳朵?身上穿的是什么怪衣服?上面绣着怪东西,说鹰不是鹰,说兔不是兔。脸皮倒也白净,模样像个男人,偏偏挺胸凸肚,似个孕妇。孕妇却不会如此般托大,一提脚,衣袖扇得噼啪响。那一双眼睛,一眨眼皮寒,一眨眼皮热,一眨眼皮刮风,一眨眼皮闪电,难道说,自己清天白日见了装神弄鬼的道公?
“还愣住干啥?快给姑娘松绑!”秋玉还理不出头绪时,来人已命令跟进来的兵丁。
双手轻松了。难道这是真的?为啥无缘无故给抓来,又无缘无故给放了?秋玉怔怔地想,疑团一个解不开,又增加一个。
“姑娘,一场误会,”来人摸摸下巴,显出一个姿态,那等待秋玉对他的恩赐表示感激的姿态,然后谄媚一笑,“你是山中凤凰,可惜屈在深山,无人识货!本官胡思进请你来,无非让你见见世面。手下人照顾不周之处,姑娘可别见怪就是!”
“请我?”秋玉越发糊涂了。人,是这样请的?况且,自己跟这人无亲无故的,他怎么瞧得起咱呢?
“姑娘,你就多住几天,帮帮我织黎锦。本官决不会亏待你,朝庭还会重重的赏你!”胡思进慢悠悠地说。
秋玉当然不晓得其中的原委。起初,王得利使人报告,胡思进听了只是想,反正能抓到黎人就好。他不造反,我叫他造反,罪名也逃脱不了。日后功劳簿上自然加上这笔新帐。然而,兵丁抓来了秋玉,抢来了秋玉的两袋东西。一旦间,他解开麻袋,里面的黎锦闪亮闪亮,叫他看了心花怒放。可再偷偷看了织锦人,织锦人更比黎锦光彩。由不得他心驰神往,魂儿荡荡……
“大人,这……这……”秋玉一时慌了,想不出合适的话来。
“有什么难为情的?”胡思进喜滋滋地说,更是喜不自禁地想:女人都是这样,嘴里吃着,手里推着,假正经。但胡思进绝不得浮荡之徒,眼见心想,心想手动。那样岂不会失去州官的尊严!他要让鱼儿自动上钩,要让鸟儿入巢,要让鱼蝦把腥臊给猫,还得感谢猫。于是,他接着说,“姑娘,别难为情。我重用你,你便识抬举嘛。这叫做两厢情愿!”
两句话,惹得秋玉心里头扑腾扑腾一把大火烧起来。你别错看了人。老猴精,也捞不得溪中月。有什么情愿不情愿?咱前辈子不欠你的,这辈子不欠你的,为啥要给你织布?多港峒里大村小寨,多少阿哥阿弟求咱,一个个发誓当咱的牛,做咱的马,只想沾上咱这双手,咱都没法子答应。你好大的口气。你不知道,再轮上十辈子,也轮不上你。咱这一双手,已经许给了阿光哥……那一天,阿爹进房来,憨憨 地笑,显出极为关切的样子,“阿玉,你长大了,你的事……也该定了!”叫我怎么说呢?我心中早有了人,又怕把事情说穿了,伤了那么多阿哥的心。咱只得想想办法,让谁都过得去。咱让阿爹说明白,谁给采来了神仙草,咱就是他的人。毛头小伙听了,都咂咂嘴,不认输也得认输,“咱没有这个福气!”只有阿光哥说,“别人怕,咱不怕采不到神仙草”。好啦,咱就等他这句话。可咱还要考考他,“神仙一不扛锄,又不赶犁,哪来个神仙草”?阿光哥说,“尖峰岭顶上有两株灵芝,火烧不死,雷劈不动。这是神仙给咱种下的,咱一人一株。”阿光哥心中有了咱,弓箭上有胆,脚板下有路,爬过九十九座大山,蹚过九十九道青溪,闯过九十九个鬼门关。阿光哥终于采摘回两株灵芝草。此生此世,咱就是阿光哥的人了。谁要让咱离开阿光哥,除非他也能让太阳从西边出来!
秋玉一扭头,便向厅外走去。
却有两个兵丁挡住去路。
“你就走吧,走不快,再插翅给你飞!”胡思进只是狡黠地笑,“你别回来就是!”
秋玉吃了一惊,可是她奋不顾身推开士兵,头回也不回,汹声汹气地嚷,“放我走,我不会织布,我要回家!”
“你要回家?好说,好说!“本官不会白养着你!你依了我,织到鸡毛沉下水,织到本官不长胡子,”胡思进也说,边捋一捋几根山羊胡,嘿嘿地笑,“本官就用大轿抬你回去!”
胡思进一话落地,兵丁四只手便来光顾,把秋玉往后推,推了个树倒墙塌。
秋玉被推倒地,屁股仿佛挨刀砍,挨斧劈,疼痛万分。可她心里才更痛苦。一个17岁的黎家少女,过惯了天真烂漫的生活,未曾体味到人生的屈辱,看惯了鲜花,香草,未曾见过魑魅魍魉,享受了人际的纯真、友爱。未尝领略卑鄙、恫吓、虚伪、奸诈,这一回,她什么都享受了。她感到茫然、恐怖,似乎身临悬崖绝壁,下面是万丈深渊,有豺狼张着如剑的利牙,有山鬼洞开血盆大嘴。她惊骇过去,又苏醒过来。她突然想到死,好留得一个自自在在,清清白白。只见她头一抬高,猛地向发霉的青砖地板碰去——
“哎哟,年纪轻轻的就寻死?”胡思进一把拉起秋玉,却若无其事地说。
秋玉呆呆地站住。
“你好糊涂呀,只要织个三五天,我就放你回家!”胡思进依然那样若无其事,口气却软和多了。
糊涂?是呀!咱才是含苞的花儿,学飞的鸟儿,怎能撇下黎家的山,黎家的水,怎能撇下黎家的阿爹阿妈、姐姐妹妹?对了,自己要活下去!秋玉忽然清醒过来,转动着脑瓜儿。俗话说,逼子成才,这一回却是逼得秋玉说起谎话。她心头卜通卜通猛跳,却极力显出自然、煞有其事的样子,“大人,咱得谢你。可是空手不能打虎,没刀不能砍柴。没有梭子,咱怎能织呀?”
“我当是缺什么,梭子有的是!”胡思进以为秋玉回转心意,免不了高兴几分秋玉“演技”出色竟一时日过胡思进。
“咱要的是神梭。没有神梭,咱实在织不好黎锦!”秋玉十分为难。
“哪来神梭”胡思进着急地问。
“大人信得过,咱就回家拿来。这是祖上传下宝贝。多亏它,帮了咱的大忙。”秋玉说得不慌不忙。
“你家里果真有神梭?”胡思进目不转睛地盯住秋玉。
“是!”秋玉极力显出镇静。
“神梭哪里来的?难道神仙去过你家里不成?”胡思进声色俱厉。
“祖上……传下来的。”秋玉声音有点低怯。
“抬起头来看我!”胡思进走到公案前,拍了拍惊堂木,“你在骗本官!”
“不…骗!不骗!”秋玉竭力辩白。
“哼,一个黎妞也敢来捉弄本官,狗胆包天,可恨,可恶!”胡思进狂笑不止,“本官要被一个黎妞骗过,岂不是枉为州官,白吃朝庭俸禄!来人,给她撑嘴,教她学精!”
门口两个兵丁应声而进,刮了她一巴掌,又把她双手反绑。
“胡大人,吾来迟了!”外面传来一声宏亮的声音。
谁敢如此放肆?胡思进刚要发作,一看来人,一种神色,那么不可捉摸,那么难以言状的神色,不易察觉地一掠而过,这才冲着进来的人答礼,“李大人,你—”
来人正是李德裕。他默默地望了秋玉一眼,对胡思进说:“胡大人,李某迟来,深感渎职,还望大人海涵!”
“李大人,你说到哪里去啦?你言重了!”胡思进还在捉摸什么,听见李德裕道歉之辞,连忙拱手应答。
“崖州出了作奸犯科之徒,李某身为司户参军,缉捕不力,反让胡大人代劳,岂不是卑职过错?”李德裕说。
一时,胡思进沉吟不语。他派人把秋玉抓来,当时忘了州衙内新来的同僚。面前这个同僚,不是庸常之辈。自古来,宰相腹里能撑船。他撑哪家子管船,是否跟自己同一条水路,实在讳莫如深。不管怎么说,凡事都得多长几个心眼,多留几条活路。但想来想去,活路并不多条。要么就说,这个黎妞,她的父亲,都是贼,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也可让李德裕相信,黎山十八峒,个个青面獠牙,无法无天。日后胡某剿黎、平黎,他也不敢来饶舌,也得跟自己卖命。就怕李德裕弄个水落石出,抓了把柄,告胡某草官民命。要么就说,这黎妞手巧,特意让她来织锦,上贡朝庭,这对谁都有好处。对了,以朝庭的名义说话,谅李德裕也不敢多嘴。于是,胡思进忽然笑道,“大人此言差矣。这姑娘并非作奸犯料之徒,实乃本州要上贡黎锦于朝庭,故而把她唤来!”
“你说谎!兵丁抓咱们父女,抢咱们东西,是为了让咱来织锦?”秋玉指着胡思进责问。
“李大人,你亲眼见了,黎妞就是不识抬举。她不但不来州府,反而伙同她贼父,在墟市上为非作歹。兵丁们一气之下,还不把她抓来? ”胡思进狠狠白了秋玉一眼,转身对里德裕叹息,“崖州出了此等事,吾深为遗憾!为了一州百姓之安宁,吾只好严惩此等狂徒!”
胡思进或许不知道,他说得越动听,掩盖得越巧妙,就越遭李德裕的耻笑,越引起他的愤慨,使李德裕还存有的好感、期待,化为乌有……
出事的当天下午,李三回船了。不知怎的,他心里似挂碍什么,就加把劲赶路,顺风船便提前抵港。帕威赶到晒经坡墟,王得利却躲起来了。帕威一气之下,赶到海边找同伴。同伴找到了,又遇上李三,帕威“哇”地一声哭了。
“同年,你有什么伤心事?快说!,快说!”李三不由得焦急。
帕威哭着,把一切都告诉李三。
同伴们嗷嗷喊起来,“先收拾王得利那小子!”
李三脸色变得异常冷峻“先救出妹子要紧!那小子,慢慢再收拾!”
几个同伴又嚷起来“咱打进州衙去!救出孩子,再把狗官一刀剐了,岂不痛快?”
“鲁莽不得!”李三直摆手。
“那可怎么办?”大伙面面相〓家。
“如今只好找李大人看看!”“李三思忖半晌,叹了一口气。众人犹豫不定,眼看无路可走,只得照办。
一行人乘着夜色,赶到了毕兰村。同伴都稍候在村外,李三、帕威两人悄悄进入村里。
李德裕正在灯下看书,忽听有人喊一声:“李大人!”回头看时,却见两人跪在地上,不禁动问,“尔等是何人?胆敢闯进官员私室?”
“李大人,咱这小小舵工,你还可曾记得?”李三不请自起,站在一旁哂笑。
帕威不觉跟着站起。猛抬头,心中一阵惊喜:他不是墟市上遇到的老先生吗?咱请他写过一张状子!可他又换上这套官服,难道他——
李德裕认出了来人,失声叫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二位!请坐,请坐!” 一边让了坐,一边问李三,“这回没遭到海盗了吧?”
“托大人的福,不曾遇到海盗!你一治,几个草民都怕了!可是,崖州城里却出了官盗。不晓得大人是否知道?李三拱手说。
“哟,州城里出了官盗?”李德裕沉思着,忽然记起什么,便向帕威,“你那孩子呢?”
“她命苦哇,老先生!”帕威伤心透了。
“她被抢啦,被官府人抢走了!”李三无不愤慨地说,转身对帕威,“他不是老先生,是官府里的好人!咱得请李大人给咱作主!”
“李大人,官府的人不把咱黎人当人看哟!”帕威声声是血,是泪,是有力的控诉!
“大人,崖州的百姓眼巴巴的望着,你给不给汉人、黎人,都作个主呀!”李三跪下了,帕威也跪下了……
“你们都起来,起来!我想想办法!”李德裕说。
“难为胡大人了!”李德裕把一切都埋到心底,蒙在鼓里似的恭维胡思进。其实,他已明白,胡思进是主谋。他明不争,暗要斗,要把主动权抓在手里,才好救出秋玉,于是,显出为胡思进效命的样子,”吾蒙胡大人器重,却不建尺寸之动。大人理当让李某审理此案,以报效于大人万……”
“如此小案一桩,何敢惊动大人,“胡思进颇为彬彬有礼,然后,诡秘一笑,“敢情李大人信不过胡某?”
“岂敢,岂敢!”李德裕欠身答礼,“只是李某既为司户参军,便不该虚在其位。虽然老朽不才,理应出力才是!”
“李大人,好——吧!今日之事拜托大人了!”胡思进面露愠色,拂袖而起。
秋玉本是被告,现在反倒成了看客。她认出李德裕原来就是那位老先生。一些话她听不懂,但从两人的表情中,她隐隐察觉出其中的阴差阳错、她不由暗暗地感激李德裕。胡思进拂袖而起时,她竟为李德裕捏着一把汗,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了。
“胡大人,请慢走,”李德裕拿定主意,让胡思进留下,免得他以后反诬一口,“今日之事,还仰仗大人鼎力相助!”胡思进说声“好吧”,翘起二郎腿坐了。
李茂光擂罢三通鼓,李德裕龙行虎步,威风凛凛,坐镇公堂,三拍惊堂木,“被告现押在此,再传原告上堂!”
李茂光领签欲走,胡思进却在一旁讪笑,“黎家父女打劫,崖州人谁不知晓?要找原告,全城人都是原告,大人如何发落?既有犯人在押,定罪便了,大人何必节外生枝?”
“胡大人,请别过虑,李某自有道理。量刑绳法,一丝不苟,吾岂能马虎?”李德裕说罢,递了个眼色,李茂光抬腿便走。
眨眼间,李茂光已把王得利押上公堂。
原来,李德裕早命刘松几个,以崖州司户参军相邀为名,把王得利领进州衙。听李茂光说参军有请,王得利乐呵呵地疾走如飞。及到进了州衙,发觉气氛森严,才生疑云。然而,他看到胡思进在,便得意忘形,上前弯腰作辑。
“来人可是原告,还不跪下!”李德裕目光炯炯,扫视王得利,拍了拍惊堂木,“公堂之上,别忘了规矩!”
“什么原告?”王得利如堕五里雾中,瞠目结舌,扑通一声下跪。
“你仔细看看,旁边跪着的是谁?”李德裕喝了一声,“你可认得她?”
王得利这才发现秋玉也跪在堂上,满面怒容。他又是慌乱,又是得意,不由嘘了一声,“认得,认得!”
“本官谅你也会认得。你既是原告,便把这女子如何打劫,都说个青红皂白!倘若有半句不实之词,可别怪本官不客气!”李德裕有板有眼的说。
王得利眼看李德裕仪表威严,心里发怵,“咚咚”直打鼓,骨碌骨碌转悠着眼神。无形中,他瞥见胡思进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不以为然的目光,腰杆子一下变硬,嘴巴也转得灵。谁听了都会相信秋玉父女真是十恶不赦的强盗。
“大人,他,贼喊捉贼,含血喷人!”秋玉被激怒,忍无可忍。
“静,静!”李德裕喝一声,又问王得利,“你说的可是实话?”
“半句是假,舌头立刻烂掉!”王得利说。
“抬起头看!你可认得本官?”李德裕一笑。
刚才匆促之间不曾看清,这回认出李德裕来了,王得利脑里“嗡地一声,似乎当头挨了一捧。天哪,他……他不是墟市上那个先生么?
“你可曾见过本官?”王得利张着嘴唇不说话时,李德裕又笑了笑。
“大人,咱做小买卖的,怎能有眼福呢?”刹那间,王得利已回过神儿,摇了摇头。
“茂光、刘松,你们跟我同行的,认一认他,该不是本官眼花了吧?”李德裕示意二人。
“禀大人,此人正是墟市上为非作歹、顶撞你的奸诈之徒!他烧成了灰,在下也会认得!”刘松、茂光不约而同地说。
“如此说来,你就是欺诈黎家父女,反倒诬蔑好人,谋财害命的恶棍。王得利,你该当何罪?”李德裕狠狠拍了拍惊堂木。
“大人,你们三人该……该不是认错了人吧?”王得利声音有点发抖,却还抵赖着。
“李大人,果真如此,恶棍该重重的法办。只是瞧他那个模样……李大人,你们会不会一时认错人来呢?”胡思进连骂带帮地说。
“你们都看,”李德裕忽然从衣袖中取出王得利写的那张字条,“你们都看清楚,白纸黑字,本官该不是诬蔑好人吧!”
胡思进一瞧,心里叫苦不迭,然而,眨眼间又亮出新招,朝着王得利喝道,“你这刁滑小民,也胆敢欺骗本官!要不念你初犯,非打断你的狗骨不可!还不给李大人谢恩,还不快快滚开!”
王得利似乎得到救命稻草,捣蒜似地磕头,便要溜走。
“且慢!”李德裕喝一声,又回头向胡思进说,“今日之事,非同儿戏!只怕让奸人逍遥法外,有伤崖州风化,世风日下,民无宁日。胡大人须慎重为之!”
“李大人深谋远虑,胡某佩服,佩服!只是李大人初到崖州,风俗民情略有不察之处。崖州滋事惹祸之最烈者,莫过于顽黎。他们聚众于山林之下,茹毛饮血,不服王化,或打家劫舍,或敢城略地,防不胜防,实为吾心腹大患。区区小民,何足挂齿?”胡思进慷慨激昂,说出一番话来。
“胡大人,贤者治国,赏罚分明,恩威并加,黎民自然感化。昔日诸葛南抚百越,终成大业。黎人果若如此凶顽,依吾看来,更应攻心为上!”李德裕一样慷憾激昂。
“可惜诸葛亮孔明已不一一复生!”胡思进拖长猫腔,忽然以攻为守,“李大人,你对黎人如此偏爱,该不是沾亲带故?”
“吾初到崖州,便沾亲带故,胡大人久治崖州,何不沾亲带故?”李德裕从容应答,“吾所念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九州之民,莫非王臣,对治下百胜一视同仁,才不辜负皇上之恩!”
胡思进时语塞。于是,李德裕叫刘松解开秋玉手上麻绳,王得利却乘机溜了,胡思进也悻悼地走了。
秋玉眼里淌着滚滚的热泪,对着李德裕下脆,一连叩了几个响头。李德裕安慰她一番,嘱她出城去,外面自然有人接应她。
仿佛一只挣脱囚笼的小鸟,秋玉急急忙忙跑出大厅,跑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朝李德裕远去的背影一再叩头,然后,飞也似地跑到崖州城门口。又要见到乡亲们了,又要像自在的鸟儿一样,秋玉快活极了,差点喊出声来。城外接应的亲人,也在深情望着。突然,城门提早关了。冷不防,三支长枪伸了过来,一齐对准秋玉的胸口……
她“呸”了一声,转身回时,却见胡思进在对面狞笑,“哈哈,在崖州究竟谁说了算?”
“当然是大人,当然是大人!”胡思进背后的王得利点头哈腰。看上去,真像帕威出猎时那条花狗。
相关人物
秋玉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