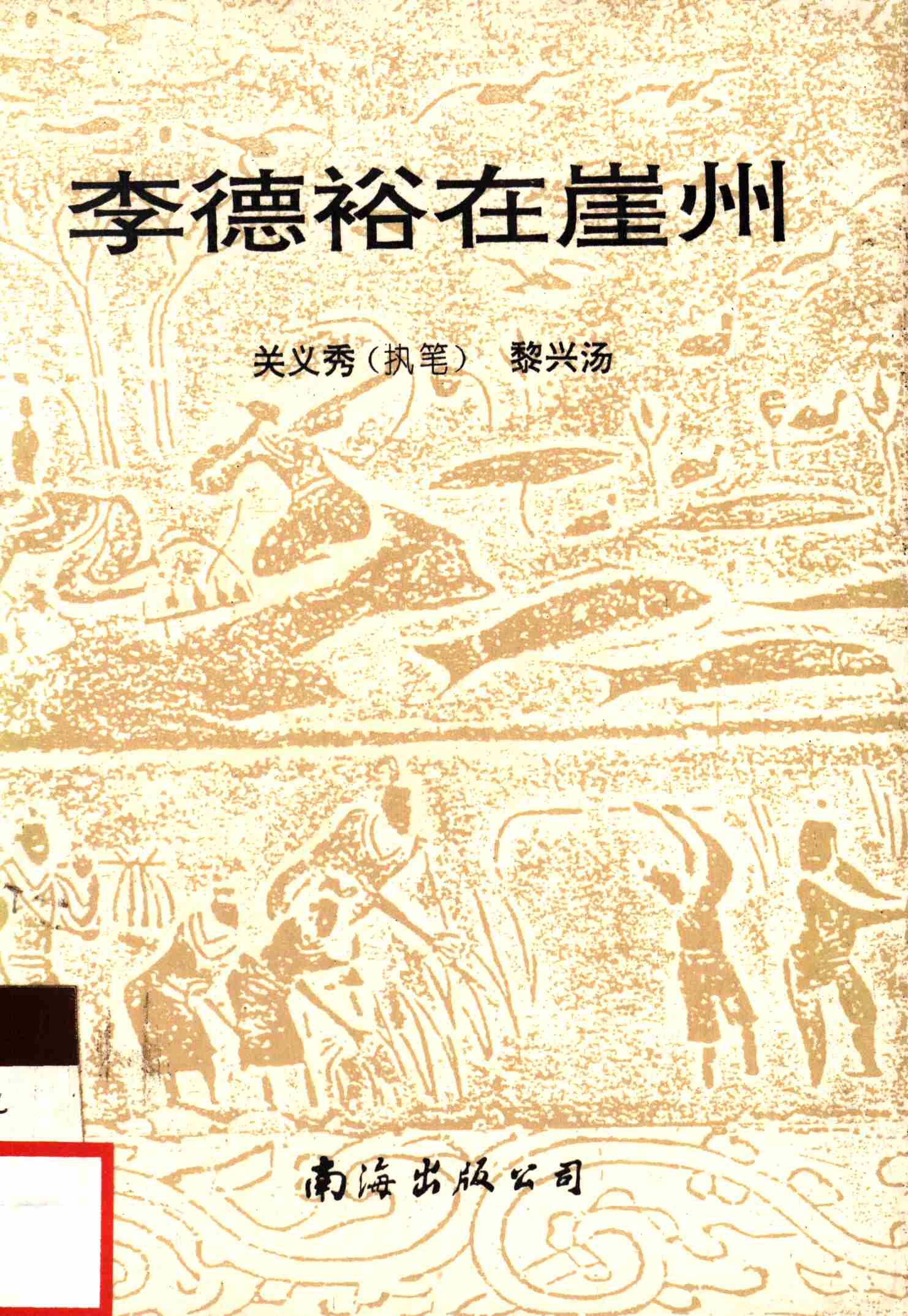内容
二月廿五。
天气转暖了。晒经坡上,乍暖还寒时节,红黄斑驳,风疏雨斜。眨眼儿,绿丛间、枝梢头,忙坏了山雀、鹧鸪,一大早就扑闪扑闪翅儿,转悠着觅食。邻近的崖州城里,荷锄的、肩挑的,待不得东天鱼肚白,就离开家门,赶了个早儿;大蛋港口,撒网的、掌舵的,鸡叫二遍就忙开了,赶了个趟儿。晒经坡下的晒经坡墟,地处大蛋港和崖州城中间,位置得天独厚的交通枢纽,成了南北交往的一个驿站。由这 里,崖州土产源源不断地输出,中原百货络绎不绝地运进。而进进出出之间,晒经坡墟自然是一个交汇点。鲜鱼新米,吉贝铁器,以物易物,以货易物,应有尽有。或三天两天,或七八成群,肩挑手提,品长论短,便完成一桩桩交易。交易之间多是公平互惠,心气平和,却也有油头滑脑的,或串通外商,或勾结官府,多说几句昧心话,多赚几把血汗钱。天气转好了,晒经坡墟自然热闹繁忙。这一天日上三竿,来往之人长袖短裤,文身裸体。一个个东瞧西望,手摸目掂,大头大户人家简直门庭若市。军话、迈话、黎话、闽南话,南腔北调,不绝于耳。
人群中一男一女先后走着,一步不离。
男的大约40来岁。你看他一身打扮:扎的是红头巾,披的是麻布衣,双腿打紧麻绑带,脚板踏着牛皮做的千里鞋,腰间缠严一条皂色腰带。头巾上还插两枝五色雀羽毛,腰带上别一个精致的编着图案的白藤腰篓,篓里插一把三尖两刃刀,左肩上挎弓箭,右肩上背一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他就是多港峒峒长帕威。不用说,他是赶墟来了。
帕威“蹚蹚蹚”地走着,两腿生风。帕威走到哪里,哪里便投去惊讶的,羡慕的,乃至馋诞欲滴的眼光。他是典型的黎族汉子,一表慓悍孔武。古铜色的长方脸上,一对突出的,像用雕刀雕塑的眉弓下面,闪烁着两只炯炯有神的虎眼。鼻的山根稍为凹陷,却挺起丰满的准头。他的四肢也是古铜色的,肌肉仿佛一道道凸起的山梁,整个身躯就是脱了白的坡垒格桩,显示着阳刚和力度。年轻时,帕威有如南仇 岭的主峰,追逐他的黎家姑娘就如山头的彩霞。如今,他早淡漠了儿女情长,但一见到那笑容、那馋劲,心里头却如灌进蜜。
原来他知道,那目光,全冲着女儿来的。
人们指指划划,“瞧,她来了,她来了!”听到声音,喝汤的放下碗,挑货的放下担,小娃娃跟不上时拍拍手往前跳,老公公走得远了扭转头朝后面跑。一个个赞叹她一身华丽的桶裙:那上面的五色雀,就真地扑闪扑闪飞过来啦,那上面的日月星辰,夜里白天一样发亮。老太婆争个不休,她长得这样标致,父母是不是描着模样生她?她脾性这么惹人喜欢,是不是十代八代的造化?她也曾生气,也曾发火, 可的越是发火,人越喜欢?这个问,那个答,惹得她鹅蛋脸儿飞红霞,惹得那水灵灵的眸子格外动人,抬起来,便是亮晶晶的星星;放低去,却如清幽幽的山月。
父女俩跟七八个黎胞赶了半夜山路来到晒经坡墟,一点也不疲倦。帕威让同伴分散行动,换货的换货,访亲的访亲,傍晚再鸣号结伴进山。帕威一要换货,二要访亲,因此父女相伴而行,离开同来的黎胞。
这天逢大墟。州衙内无事,李德裕扮了个私塾先生,李茂光扮成家人,刘松扮老童生,相伴出外走走。
近来,胡思进并不节外生枝,惹事生端,对李德裕也颇看重似的,然而,李德裕终究郁闷日多,开怀时少。因此,也曾乔装打扮,走港口,上墟市,看燕子南来,望云帆北去跟外来客商聊聊中原掌故,跟崖州人学一学军话、俚话、凑一凑南腔北调。
一天,他登上望阙亭,扶住雕花栏杆,抬头北望。四周的马鞍山、香岭、回风岭,层峦叠嶂,奔腾起伏,仿佛一个个波涛,涌向遥远的天际。他却无端地觉得,那波涛一个接一个,前伏后起,从遥远的地方逼过来,逼过来,四下里没有立身之地。他失神地,发痴地望着天空。高空里,一只老鹰搏动双翅,似拖下一条丝线,拖着自己那颗心一起飞腾。然而,却飞不出关山重重,浓云漫漫,飞不出那片幽深,那片寂寥。仿佛一场梦醒,李德裕来回踱着,发出回肠荡气的咏叹:
独上江亭望帝京,
鸟飞犹用半年程。
江山只恐人归去,
百匝千回绕郡城。
二月廿五这天,风和日丽,李德裕三人出了毕兰村不觉神清气爽,信步走到古树参天的大云寺里。当年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经,海上遇飓风,飘到崖州,在崖州晒了经卷,还给百姓诵经。如今崖州百姓建造大云寺、晒经亭纪念他,晒经坡、晒经坡墟也因此而得名。李德裕缓缓登上晒经亭,想起斯人虽逝,音容犹在,一时触动心事,不禁对二人笑,“咱们去当和尚好啰!”刘松也笑着,“我使枪弄棍惯了,怎的敲得木鱼?”李茂光皱了皱眉,“我专吃斋,肚里头便敲锣打鼓!”三人说说笑笑,到庙里进了香,才缓步而出。
李德裕到了晒经坡墟一条路,恰好,帕威父女也逛到那里。天底下少了“凑巧”两字,可要少了看头呢。
大家一打照脸,好脸熟,似在哪里见过的,可谁都愕着,一时答不上腔。
李德裕也曾见过黎胞,瞧帕威那模样,那打扮,不由赞叹一番,“好一个黎族壮汉!”可是帕威的女儿,却让李德裕犯了疑团。黎家姑娘怎生得如此文雅可掬,如此丰采照人?她跟想象中的黎家姑娘,相差何其天地迥异。一个是天上月,一个是屋里灯;一个似凤,一个如鸡。那娇态,那丰韵,也不比当年李夫人差。李德裕荡了魂儿。但他愧从心起,暗地里咒骂自己,“吾岂是好色之徙,怎么能想入非 非?”
帕威也端详着李德裕。一表人材,肚里盛半溪墨水。眉目最和善,嘴巴虽不张开,倒像要跟咱拉一拉家常话,夏天种山兰,冬日打黄猄。帕威差一点喊出声来,“教书老先生, 好,好!”但他到底暗自发笑,“你怎的见得,怎的知晓?人家跟你又没啥瓜葛!”
“同年,赶墟来啦!”李德裕先打招呼,黎话、闽南话一齐来,都一样半生不熟。闽南话是崖州人通用的方言,黎人也能听懂。
“是,是!”帕威光顾笑嘻嘻。
“同年跑得好远,跑得好累!”李德裕说着,指了指大山方向,比比自己的脚板。
“不远……远……没啥,咱惯了,老先生!”帕威似乎语无伦次。
“同年,有眼力。他就是老先生!”李茂光举起大拇指说。
帕威朝女儿一笑,神气得很:我没猜错吧!他心里更乐不可支。老先生这么好,说不定有一天也请他来,教女儿认几个字,教山里人认几个字。咱女儿哪样比不上有钱人家的女孩!她再认得字,脸儿光亮肚里也光亮。帕威一高兴,忽然解开布袋,把一块鹿茸塞给李德裕,还朝身子划一个大圆圈,“老先生,交个同年。这,补补身子!”
“这怎么使得?”李德裕为难极了,推辞着。
“老先生,你不肯收下,就是瞧不起咱,不肯交同年!”帕威满脸不高兴,噘起嘴巴,仿佛一个大孩子受了委屈。
“好,我收下。”李德裕摸了摸身上,摸不到可以回敬之物,只好作罢,“同年,我就住在毕兰村里。”
“好,好。我叫帕威,住在多港峒里,”帕威破涕为笑,指着女儿说,”她叫秋玉,老先生,以后咱们山里不见墟上见!”
秋玉默默不语。可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里,朦胧和清澈交融着,拘束和热情交织着,汇成一个黎家少女单纯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同李德裕分手,帕威父女往墟南李三家去。李三没在,他女人赔礼说:“同年来得不凑巧。孩子他爸出海去了,少说几天才回来。”
帕威送了东西,怏怏不乐走了。
父女俩走过一家门口,听到喊声:“同年,抽筒烟啰!”一瞧,一张猴脸皮笑肉不笑的朝他喊,帕威不听见喊声则罢,听见了反倒大步流星朝前走。
“同年,慢走!”猴脸跑出来,拦住父女,“咱给你留下一批新货!”
还跟这号人做买卖?去年一天,帕威和几个兄弟上晒经坡墟,准备换回铜片、铁钉,钉一个铜鼓。正是这张猴脸,嘴甜过蜜地说,“同年,咱有好货!”帕威他们两话不说,爽爽快快解下布袋。“同年,咱这铜片、铁钉钉的大鼓,咚咚咚响,熊听见了吓破胆,”猴脸拿出几块铜片,一撮铁钉,“包你管用,包你够用!只是同年怎不多带一点山货?这样吧,先给你们东西,山货咱也收下。下次同年再给点就 是。”帕威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几麻袋山货还不够”?他心里嘀咕着,却不吭声,还赔了情,才招呼兄弟们走。猴脸忽然拖长猫腔,“黎剥皮,敢欺负我王得利来了!”帕威见王得利破口骂人,火了:“谁敢剥皮?”王得利自恃围观的几个杀狗兄弟护住他,越发跳得凶:“黎剥皮,钉铜鼓岂不是要造反?官府不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才怪!”冷不防,人群中闪出一个汉子,脱下粗布衣往旁边一个兄弟身上掷去,露出一起一伏的胸脯。一个箭步跻到王得利跟前,右手朝肚皮上一按,“王得利,好种的,你就朝这上面剥!”王得利睁眼看清汉子,看看周围几个向着他的兄弟,脸上紫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结结巴巴地说,“他是……是你的什么人?你你你护着他!”汉子嘻皮笑脸地反问,“官府派你查户口来啦?好,我告诉你,他是我的同年!”一场闹戏风平浪静。帕威到了汉子家里,千声万声,感激这同他素不相识的汉子。汉子笑了笑,“别谢来谢去的,怪不好受!那年我到山里买长板给船家,半路上发痧倒下。要不是一个同年搭救,我早见阎王爷了。你谢我,我该谢谁呢?”
帕威想起往事,还感到可气,但王得利一再叫喊,让他心软,不觉停住脚步。
“同年,咱自家人不说两样话。这一回,天上有的,皇宫里摆的,咱一件不少!同年坐下来,挑个清楚。”王得利边说,边搬过一张凳子,边打量着秋玉,“哟,同年,有福气!阿〓真靓,再打扮,天下的汉子都想你!”
秋玉白了他一眼,”呸,不正经!再说,嘴上生恶疮,你不得好死!”
“阿〓生靓,不打扮,也就算了!”王得利改口说。
“少啰嗦,拿货来看!”帕威可要发火。
“同年,想换什么,说啰。”王得利陪笑脸。
帕威朝女儿啧上嘴巴,“阿玉,你一件一件说给他,让他拿来”!
秋玉扳扳指头。针可少不了啦,峒里几个姐妹都嘱咐的。盐巴也少不得,咸香淡臭,好儿家都喝清汤了。铁片更要紧,阿爹早晚都用上它。那面铜镜子也锈了,该换了,自己梦过好几回。还有,尖刀也是顶管用的,阿光哥不说,也得送一把新的给他……秋玉想着,想着,心儿醉了,脸儿也醉了。
秋玉思量好了。她本想一五一十说出来,转念一想,这不白白便宜了这老贼精,一件一件编个谜语说了,让他想破脑壳。于是,阿玉一口气编了五道谜语。“拴条长绳穿过岭,”她刚念完最后一句,王得利嚷了起来,“哎哟,这不是牛吗?哎哟,百担沉香才得换得一头牛,别提,别提!”
秋玉抿住嘴儿笑了。帕威可急了,“咱换的是铁片、镜子、盐巴、尖刀和针,不是牛!”
“哎哟,同年眼睛穿过布,好利!哪样东西宝贵,你就提那样!也罢,都是自家人,就依了你。反正肥水不过别人田。”王得利说完,到屋里拿出来五支针、二升盐巴、一张小铁片和一面铜镜子。
“没啦?”帕威问。
“同年,你还嫌少?你,可是要刨我的命根啦!”王得利虽这么说,眼晴却直盯住一大两小三个麻袋——两个小麻袋秋玉挑着。那里面的吉贝布、沉香、鹿茸,一件件,都是上等货色。好几回,王得利想要鸡蛋里挑石头,却说得牛头不对马嘴。
“再给一把尖刀!”帕威不再想跟他磨牙,再讨得一把尖刀给那好后生,也就得了。
“同年,我已赔本了。”王得利丧着脸,果真像猴子闻鸡屎,但转头缠住秋玉时,哭脸又变了笑脸,“阿〓,今天运气了你。你不晓得,这针才有来头呢。当年它们是五杆神铁,过路的仙人帮我磨了,还给吹了孔。要不得我疼你,我才舍不得!”
王得利越说越玄,也不理会帕威父女脸色勃然变了,还兀自喋喋不休地说,唾星儿四处飞溅。反正他想,谁会骗人,谁才会做买卖。
帕威不再吭声,闷声闷气的,背起麻袋就走。
王得利䀹了䀹眼,两条汉子跳出去,挡住帕威去路。
“让开!咱不白吃你的,白穿你的!大路长在脚板下,咱兴往哪走,就往哪走!”帕威瞪起两只虎眼。
王得利用军话骂,“千刀万剐的黎剥皮,学假精”!说着,奔上前去,拉住帕威,“同年,人要有个良心!东西让你弄掉了毛,谁还肯要”?
“你,你,你又要欺负咱!”帕威眼眦涨红了,脖子上暴起一道一道青筋。
“你想赖账?没这么容易!我的东西掉了毛,你不给装好,就别想走!”王得利冷笑不止。
帕威动怒了,眼里冒出阵阵火星,粗气呼呼而出,牙齿咬得嘣嘣响。
秋玉却轻轻推开父亲,斜睨王得利一眼,故作惊讶地说:“你何不早一点说?快把掉了的毛捡回来。我给你一根一根装好!”
王得利一听,脸色刹地变白。可是,他竟不理秋玉,走上大路中央,扯开嗓门大喊,“黎头反了,黎头反了!”
一时间,周围的人都跑了过去,想看个究竟,围了个水泄不通。
李德裕同帕威分手后,到大蛋港走走,便转回毕兰村,路过晒经坡墟听人传扬黎人造反,连忙奔往出事地点。平日里他听胡思进说过,崖州欲得安宁,便须剿灭顽黎。但他就不相信,黎、汉百姓同居一方土,同饮一江水,世代相往来,黎民却如此凶顽!今天他初遇帕威父女,黎胞如此通情达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使他不疑自己平日所见。但身为司户参军,他深感责任重大,绝不可拿王法当儿戏,绝不可凭意气用事。果真有顽黎聚众造反,打家劫舍,便当绳之以法,以张扬大唐律典之尊严,以矫正百姓之视听。民风谆朴,人心思治,崖州始得安宁。
李德裕挤进人群,不觉大吃一惊。帕威父女被王得利一帮人围住,帕威像一头被网网住的野猪,左冲右突,要找王得利算帐。可是父女俩寡不敌众,怎能脱得身来。李德裕认出帕威,私下叹息,“不想他不懂王法!该我治罪时,我不能徇情枉法!”但他转生念头,凡事得弄个水落石出,万不可冤枉好人。李德裕悄悄问几个老人,有的说,“王得利要吸黎人髓”,有的把经过一五一十说了。李德裕再看帕威,他样子是凶,脸上却露出委屈的神色。而王得利一副模样,外 表三分可怜,骨子里七分得意。李德明白了一切,心中一把火扑腾扑腾地窜起。这刁钻之徒太可恶了,不把他拿下,再让他胡作非为? 一个方步,李德裕奔王得利而去,忽然觉得有人拽住衣袖,猛地想起自己乔装出访,不宜贸然从事,不如略施小计,救出父女再说。
李德裕一边佯装不认识帕威,一边显出关切的样子走近王得利身旁,“出事啦?”
“可不!可恶的黎头,要打家劫舍!”王得利更加神气。
“这还了得?咱平生爱帮人打官司,你拿出笔砚来,一条一条说与我,我帮你告他一状,如何?”李德裕郑重其事地说。
“好,好,好!”王得利不知是计,忙叫家人拿出纸笔。
“他如何反了,你要说个明明白白,才能一告通天!”李德裕端的提起笔。
“他……他谋财害命!”王得利振振有词。
“乃是在青天白日之下花言巧语,欺诈勒索,敲骨吸髓,大耍无赖,反诬一口,含血喷人吗?”李德裕佯作奋笔疾书之状。
“滚开,谁让你胡说八道!”王得利忽然省悟过来,李德裕在挖苦他,不禁恼羞成怒。
“哈哈,你喊我滚,我偏不滚。你不让我写,我就请你写,赏个光吧!”李德裕举着毛笔发笑。
“你滚开!谁让你来管闲事?”王得利习惯地拖长了猫腔。
“你呀!”李德裕说。
“你胡说!”王得利性起,伸开两指直指李德裕,不提防被刘松一只大手扼着手腕,吓得面如土色,连连求饶。他那几个杀狗兄弟一瞧来头不妙,也不敢动手动脚。
“好,就饶了你!你马上立下字据,以后不再胡作妄为!”李德裕说完,放下笔来。
王得利伸长脖子往前望,叹了气,像瘪了的皮球,蹦不起来。原来,他刚才使人去了州府,却不见救兵赶到。他使尽平生力气,拿起笔,如抱大树般吃劲,眼晴忙碌了一阵儿,写下一行字来:
我欺压黎人惹事端半斤八两今后不得再犯王得利立此字据
李德裕看了字条,暗笑道,“好一个刁钻之徒!”便拿笔过来加上标点,去了4个字,大声说,“我念一念,你有何话说”?说罢,当众念了:
我欺压黎人惹事端,今后不得再犯。王得利立此字据。
王得利班门弄不得钝斧,默默走开。李德裕藏好字条走了。
帕威父女脱身后,悄悄跟着李德裕,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老先生,救命恩人!救命恩人,老先生!”帕威“卜通”一声跪下。
秋玉不说话,满腹子要说的话,饱含在那一双深情的眸子里。
“起来,起来,让你委屈了!”李德裕弯腰扶起帕威。
父女还要送东西,李德裕哪里再肯收下?他一再嘱咐父女俩,便回毕兰村去了。
帕威赶往大蛋港,准备召集同来的伴伴,提早进山。刚才他们不在,害得父女势单力薄。帕威怕他们也遇到麻烦,事情可糟了。天塌下来,大伙在一块,也有个照应。
帕威拜别李德裕三人,和秋玉折回大路来,突然,拐角里闪出七八个兵丁,王得利也跑在中间,边跑边喊,“就是他,就是他!”帕威一看事情不妙,一转身,踅回一棵大树底下,一边招呼秋玉快走,一边回头唬着来人。怎奈秋玉是个女子,肩挑布袋,所以落后几步。
“贼剥皮,“王得利嚎喊着,“谅你插翅也飞不了!”
原来,王得利早跟胡思进明来暗往。王得利使唤的人进了州衙,见过胡思进,便谎报晒经墟上两个黎头造反。胡想进本来就巴不得逮住兔子作老虎,以便向上邀功,因此也不问个真假,便派兵丁赶来。
8个士兵分开两路,一半扑向帕威,一半扑向秋玉。
帕威站在大树底下,眼看四个兵丁包抄过去,切断了父女间的联系,奋不顾身,像过涧的老虎扑向兵丁,想把他们全都吸引过来。那边4个兵丁不为所动,这边4个兵丁却乘势包围上来。眼看一时讨不了便宜,只得退回大树下。4个兵丁分四方站定,指弓搭箭,全瞄准帕威这个靶心。帕威全无惧色,大喊;“谁先动手,谁死!”吓得兵丁楞住,谁也不敢抢先放箭。
“射呀,射死这个黎头!”王得利张牙舞爪地喊,“胡大人赏你们头功!”
这一喊还奏效,有谁首先放箭。箭,如飞蝗呼呼而出,接着,兵丁们全都放箭。帕威不慌不忙,凭借大树掩护,东躲西闪,逃过一个个箭镞,兵丁们再拈弓搭箭时,帕威早猫身来,瞄得真切,一支利箭应声而出,专向王得利的嘴巴下飞去,亏他装死装得快,嚎喊一声倒地,竟躲过了箭镞。
兵丁见王得利应弦而倒,一时手软,不曾放箭。帕威趁这空隙,三步两步,拐到一个墙角蹲定。兵丁紧追不舍,步步向帕威逼近。双方再次对射,你来我往。一边人多势众,一边气贯长虹,分不出胜负。帕威双眼闪着血光,两道浓眉拧紧,当那眉毛即将撞到一起时,喝了一声:“放!”弯腰搭弓,却虚晃一下,箭不曾出手。一边小头目受王得利怂恿,以为帕威把箭射光了,便想领个头功,从侧面绕了上去。帕威早〓得准,不声不响,拈上利箭。不曾听到弓弦响,利箭已射中小头目胸口。兵丁喊一声,“不好”!背起受伤的同伴走了。
帕威脱得身,心急火燎般寻找女儿时,秋玉已不知去向……
刚才,4个兵丁扑过来,秋玉呼天不答,呼地不应,脚膝盖都瘫软。她恍然听见一个声音,“跑,拼命跑,绝不能落到贼子手里!”她咬一咬牙龈,脚下似乎长了双翅。她看见一条小路,一头通进茂密的林子,就往小路跑去。她跑呀跑,心儿都仿佛飞出胸膛去了,可有一股风在推她,一个个声音在呼唤她。对了,寨子里的人在山那边等待她,阿光哥在那边等待她,越过这道山坡就见到亲人。她好几次要跌倒了,步子一抬,又朝前奔去。肩上的两个袋,越走越沉。她真想撂下麻袋,好跑得飞快。转瞬间,她又狠狠骂自己,“怕死鬼,软骨虫!袋里的是乡亲们的血汗,是寨子的命根子!撂给贼子,不是白让他便宜!就是死,也得把东西交回乡亲们手里!”秋玉想着,跑着,最后干脆什么都不去想,光顾拼命的跑……
秋玉当然没有想到,这条路不是南仇岭上的山路,只是通往崖州州城的一条小径。她人生地疏,慌不择路,最终跑不出虎口。两个兵丁紧迫不舍,堵住她的后路,另外两个早绕了弯,等候在岔路口。当她一口气跑出路口时,突然被一根拦路的绳子拌倒,两个兵丁凶神恶煞般扑上来了……
帕威当然不知道这一切 但他左右打听,都没弄清女儿的下落。突然,他放声哭了。刚才,面对敌人,他有的是复仇的火焰,是拼死到底的决心,刀劈下头颅也决不掉泪。这一回,他却伤心地哭了。他隐隐知道,女儿是落进了虎口。可怜的女儿呀,爹对不住你!乡亲们呀,咱对不住你们!帕威哭着,突然挥起青梅格般结实的拳头,对着自己的胸捶。他捶呀,捶呀,拳头都麻了,泪也干了。他兀地骂自己傻,傻!为什么白白伤了自己,不找贼子算账去?要让他们还我女儿,绝不让她伤损一根毫毛。若有半个“不”字,便以一换十,拼了个鱼死网破!
帕威浑身是火,扑向王得利家去了——
天气转暖了。晒经坡上,乍暖还寒时节,红黄斑驳,风疏雨斜。眨眼儿,绿丛间、枝梢头,忙坏了山雀、鹧鸪,一大早就扑闪扑闪翅儿,转悠着觅食。邻近的崖州城里,荷锄的、肩挑的,待不得东天鱼肚白,就离开家门,赶了个早儿;大蛋港口,撒网的、掌舵的,鸡叫二遍就忙开了,赶了个趟儿。晒经坡下的晒经坡墟,地处大蛋港和崖州城中间,位置得天独厚的交通枢纽,成了南北交往的一个驿站。由这 里,崖州土产源源不断地输出,中原百货络绎不绝地运进。而进进出出之间,晒经坡墟自然是一个交汇点。鲜鱼新米,吉贝铁器,以物易物,以货易物,应有尽有。或三天两天,或七八成群,肩挑手提,品长论短,便完成一桩桩交易。交易之间多是公平互惠,心气平和,却也有油头滑脑的,或串通外商,或勾结官府,多说几句昧心话,多赚几把血汗钱。天气转好了,晒经坡墟自然热闹繁忙。这一天日上三竿,来往之人长袖短裤,文身裸体。一个个东瞧西望,手摸目掂,大头大户人家简直门庭若市。军话、迈话、黎话、闽南话,南腔北调,不绝于耳。
人群中一男一女先后走着,一步不离。
男的大约40来岁。你看他一身打扮:扎的是红头巾,披的是麻布衣,双腿打紧麻绑带,脚板踏着牛皮做的千里鞋,腰间缠严一条皂色腰带。头巾上还插两枝五色雀羽毛,腰带上别一个精致的编着图案的白藤腰篓,篓里插一把三尖两刃刀,左肩上挎弓箭,右肩上背一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他就是多港峒峒长帕威。不用说,他是赶墟来了。
帕威“蹚蹚蹚”地走着,两腿生风。帕威走到哪里,哪里便投去惊讶的,羡慕的,乃至馋诞欲滴的眼光。他是典型的黎族汉子,一表慓悍孔武。古铜色的长方脸上,一对突出的,像用雕刀雕塑的眉弓下面,闪烁着两只炯炯有神的虎眼。鼻的山根稍为凹陷,却挺起丰满的准头。他的四肢也是古铜色的,肌肉仿佛一道道凸起的山梁,整个身躯就是脱了白的坡垒格桩,显示着阳刚和力度。年轻时,帕威有如南仇 岭的主峰,追逐他的黎家姑娘就如山头的彩霞。如今,他早淡漠了儿女情长,但一见到那笑容、那馋劲,心里头却如灌进蜜。
原来他知道,那目光,全冲着女儿来的。
人们指指划划,“瞧,她来了,她来了!”听到声音,喝汤的放下碗,挑货的放下担,小娃娃跟不上时拍拍手往前跳,老公公走得远了扭转头朝后面跑。一个个赞叹她一身华丽的桶裙:那上面的五色雀,就真地扑闪扑闪飞过来啦,那上面的日月星辰,夜里白天一样发亮。老太婆争个不休,她长得这样标致,父母是不是描着模样生她?她脾性这么惹人喜欢,是不是十代八代的造化?她也曾生气,也曾发火, 可的越是发火,人越喜欢?这个问,那个答,惹得她鹅蛋脸儿飞红霞,惹得那水灵灵的眸子格外动人,抬起来,便是亮晶晶的星星;放低去,却如清幽幽的山月。
父女俩跟七八个黎胞赶了半夜山路来到晒经坡墟,一点也不疲倦。帕威让同伴分散行动,换货的换货,访亲的访亲,傍晚再鸣号结伴进山。帕威一要换货,二要访亲,因此父女相伴而行,离开同来的黎胞。
这天逢大墟。州衙内无事,李德裕扮了个私塾先生,李茂光扮成家人,刘松扮老童生,相伴出外走走。
近来,胡思进并不节外生枝,惹事生端,对李德裕也颇看重似的,然而,李德裕终究郁闷日多,开怀时少。因此,也曾乔装打扮,走港口,上墟市,看燕子南来,望云帆北去跟外来客商聊聊中原掌故,跟崖州人学一学军话、俚话、凑一凑南腔北调。
一天,他登上望阙亭,扶住雕花栏杆,抬头北望。四周的马鞍山、香岭、回风岭,层峦叠嶂,奔腾起伏,仿佛一个个波涛,涌向遥远的天际。他却无端地觉得,那波涛一个接一个,前伏后起,从遥远的地方逼过来,逼过来,四下里没有立身之地。他失神地,发痴地望着天空。高空里,一只老鹰搏动双翅,似拖下一条丝线,拖着自己那颗心一起飞腾。然而,却飞不出关山重重,浓云漫漫,飞不出那片幽深,那片寂寥。仿佛一场梦醒,李德裕来回踱着,发出回肠荡气的咏叹:
独上江亭望帝京,
鸟飞犹用半年程。
江山只恐人归去,
百匝千回绕郡城。
二月廿五这天,风和日丽,李德裕三人出了毕兰村不觉神清气爽,信步走到古树参天的大云寺里。当年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经,海上遇飓风,飘到崖州,在崖州晒了经卷,还给百姓诵经。如今崖州百姓建造大云寺、晒经亭纪念他,晒经坡、晒经坡墟也因此而得名。李德裕缓缓登上晒经亭,想起斯人虽逝,音容犹在,一时触动心事,不禁对二人笑,“咱们去当和尚好啰!”刘松也笑着,“我使枪弄棍惯了,怎的敲得木鱼?”李茂光皱了皱眉,“我专吃斋,肚里头便敲锣打鼓!”三人说说笑笑,到庙里进了香,才缓步而出。
李德裕到了晒经坡墟一条路,恰好,帕威父女也逛到那里。天底下少了“凑巧”两字,可要少了看头呢。
大家一打照脸,好脸熟,似在哪里见过的,可谁都愕着,一时答不上腔。
李德裕也曾见过黎胞,瞧帕威那模样,那打扮,不由赞叹一番,“好一个黎族壮汉!”可是帕威的女儿,却让李德裕犯了疑团。黎家姑娘怎生得如此文雅可掬,如此丰采照人?她跟想象中的黎家姑娘,相差何其天地迥异。一个是天上月,一个是屋里灯;一个似凤,一个如鸡。那娇态,那丰韵,也不比当年李夫人差。李德裕荡了魂儿。但他愧从心起,暗地里咒骂自己,“吾岂是好色之徙,怎么能想入非 非?”
帕威也端详着李德裕。一表人材,肚里盛半溪墨水。眉目最和善,嘴巴虽不张开,倒像要跟咱拉一拉家常话,夏天种山兰,冬日打黄猄。帕威差一点喊出声来,“教书老先生, 好,好!”但他到底暗自发笑,“你怎的见得,怎的知晓?人家跟你又没啥瓜葛!”
“同年,赶墟来啦!”李德裕先打招呼,黎话、闽南话一齐来,都一样半生不熟。闽南话是崖州人通用的方言,黎人也能听懂。
“是,是!”帕威光顾笑嘻嘻。
“同年跑得好远,跑得好累!”李德裕说着,指了指大山方向,比比自己的脚板。
“不远……远……没啥,咱惯了,老先生!”帕威似乎语无伦次。
“同年,有眼力。他就是老先生!”李茂光举起大拇指说。
帕威朝女儿一笑,神气得很:我没猜错吧!他心里更乐不可支。老先生这么好,说不定有一天也请他来,教女儿认几个字,教山里人认几个字。咱女儿哪样比不上有钱人家的女孩!她再认得字,脸儿光亮肚里也光亮。帕威一高兴,忽然解开布袋,把一块鹿茸塞给李德裕,还朝身子划一个大圆圈,“老先生,交个同年。这,补补身子!”
“这怎么使得?”李德裕为难极了,推辞着。
“老先生,你不肯收下,就是瞧不起咱,不肯交同年!”帕威满脸不高兴,噘起嘴巴,仿佛一个大孩子受了委屈。
“好,我收下。”李德裕摸了摸身上,摸不到可以回敬之物,只好作罢,“同年,我就住在毕兰村里。”
“好,好。我叫帕威,住在多港峒里,”帕威破涕为笑,指着女儿说,”她叫秋玉,老先生,以后咱们山里不见墟上见!”
秋玉默默不语。可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里,朦胧和清澈交融着,拘束和热情交织着,汇成一个黎家少女单纯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同李德裕分手,帕威父女往墟南李三家去。李三没在,他女人赔礼说:“同年来得不凑巧。孩子他爸出海去了,少说几天才回来。”
帕威送了东西,怏怏不乐走了。
父女俩走过一家门口,听到喊声:“同年,抽筒烟啰!”一瞧,一张猴脸皮笑肉不笑的朝他喊,帕威不听见喊声则罢,听见了反倒大步流星朝前走。
“同年,慢走!”猴脸跑出来,拦住父女,“咱给你留下一批新货!”
还跟这号人做买卖?去年一天,帕威和几个兄弟上晒经坡墟,准备换回铜片、铁钉,钉一个铜鼓。正是这张猴脸,嘴甜过蜜地说,“同年,咱有好货!”帕威他们两话不说,爽爽快快解下布袋。“同年,咱这铜片、铁钉钉的大鼓,咚咚咚响,熊听见了吓破胆,”猴脸拿出几块铜片,一撮铁钉,“包你管用,包你够用!只是同年怎不多带一点山货?这样吧,先给你们东西,山货咱也收下。下次同年再给点就 是。”帕威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几麻袋山货还不够”?他心里嘀咕着,却不吭声,还赔了情,才招呼兄弟们走。猴脸忽然拖长猫腔,“黎剥皮,敢欺负我王得利来了!”帕威见王得利破口骂人,火了:“谁敢剥皮?”王得利自恃围观的几个杀狗兄弟护住他,越发跳得凶:“黎剥皮,钉铜鼓岂不是要造反?官府不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才怪!”冷不防,人群中闪出一个汉子,脱下粗布衣往旁边一个兄弟身上掷去,露出一起一伏的胸脯。一个箭步跻到王得利跟前,右手朝肚皮上一按,“王得利,好种的,你就朝这上面剥!”王得利睁眼看清汉子,看看周围几个向着他的兄弟,脸上紫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结结巴巴地说,“他是……是你的什么人?你你你护着他!”汉子嘻皮笑脸地反问,“官府派你查户口来啦?好,我告诉你,他是我的同年!”一场闹戏风平浪静。帕威到了汉子家里,千声万声,感激这同他素不相识的汉子。汉子笑了笑,“别谢来谢去的,怪不好受!那年我到山里买长板给船家,半路上发痧倒下。要不是一个同年搭救,我早见阎王爷了。你谢我,我该谢谁呢?”
帕威想起往事,还感到可气,但王得利一再叫喊,让他心软,不觉停住脚步。
“同年,咱自家人不说两样话。这一回,天上有的,皇宫里摆的,咱一件不少!同年坐下来,挑个清楚。”王得利边说,边搬过一张凳子,边打量着秋玉,“哟,同年,有福气!阿〓真靓,再打扮,天下的汉子都想你!”
秋玉白了他一眼,”呸,不正经!再说,嘴上生恶疮,你不得好死!”
“阿〓生靓,不打扮,也就算了!”王得利改口说。
“少啰嗦,拿货来看!”帕威可要发火。
“同年,想换什么,说啰。”王得利陪笑脸。
帕威朝女儿啧上嘴巴,“阿玉,你一件一件说给他,让他拿来”!
秋玉扳扳指头。针可少不了啦,峒里几个姐妹都嘱咐的。盐巴也少不得,咸香淡臭,好儿家都喝清汤了。铁片更要紧,阿爹早晚都用上它。那面铜镜子也锈了,该换了,自己梦过好几回。还有,尖刀也是顶管用的,阿光哥不说,也得送一把新的给他……秋玉想着,想着,心儿醉了,脸儿也醉了。
秋玉思量好了。她本想一五一十说出来,转念一想,这不白白便宜了这老贼精,一件一件编个谜语说了,让他想破脑壳。于是,阿玉一口气编了五道谜语。“拴条长绳穿过岭,”她刚念完最后一句,王得利嚷了起来,“哎哟,这不是牛吗?哎哟,百担沉香才得换得一头牛,别提,别提!”
秋玉抿住嘴儿笑了。帕威可急了,“咱换的是铁片、镜子、盐巴、尖刀和针,不是牛!”
“哎哟,同年眼睛穿过布,好利!哪样东西宝贵,你就提那样!也罢,都是自家人,就依了你。反正肥水不过别人田。”王得利说完,到屋里拿出来五支针、二升盐巴、一张小铁片和一面铜镜子。
“没啦?”帕威问。
“同年,你还嫌少?你,可是要刨我的命根啦!”王得利虽这么说,眼晴却直盯住一大两小三个麻袋——两个小麻袋秋玉挑着。那里面的吉贝布、沉香、鹿茸,一件件,都是上等货色。好几回,王得利想要鸡蛋里挑石头,却说得牛头不对马嘴。
“再给一把尖刀!”帕威不再想跟他磨牙,再讨得一把尖刀给那好后生,也就得了。
“同年,我已赔本了。”王得利丧着脸,果真像猴子闻鸡屎,但转头缠住秋玉时,哭脸又变了笑脸,“阿〓,今天运气了你。你不晓得,这针才有来头呢。当年它们是五杆神铁,过路的仙人帮我磨了,还给吹了孔。要不得我疼你,我才舍不得!”
王得利越说越玄,也不理会帕威父女脸色勃然变了,还兀自喋喋不休地说,唾星儿四处飞溅。反正他想,谁会骗人,谁才会做买卖。
帕威不再吭声,闷声闷气的,背起麻袋就走。
王得利䀹了䀹眼,两条汉子跳出去,挡住帕威去路。
“让开!咱不白吃你的,白穿你的!大路长在脚板下,咱兴往哪走,就往哪走!”帕威瞪起两只虎眼。
王得利用军话骂,“千刀万剐的黎剥皮,学假精”!说着,奔上前去,拉住帕威,“同年,人要有个良心!东西让你弄掉了毛,谁还肯要”?
“你,你,你又要欺负咱!”帕威眼眦涨红了,脖子上暴起一道一道青筋。
“你想赖账?没这么容易!我的东西掉了毛,你不给装好,就别想走!”王得利冷笑不止。
帕威动怒了,眼里冒出阵阵火星,粗气呼呼而出,牙齿咬得嘣嘣响。
秋玉却轻轻推开父亲,斜睨王得利一眼,故作惊讶地说:“你何不早一点说?快把掉了的毛捡回来。我给你一根一根装好!”
王得利一听,脸色刹地变白。可是,他竟不理秋玉,走上大路中央,扯开嗓门大喊,“黎头反了,黎头反了!”
一时间,周围的人都跑了过去,想看个究竟,围了个水泄不通。
李德裕同帕威分手后,到大蛋港走走,便转回毕兰村,路过晒经坡墟听人传扬黎人造反,连忙奔往出事地点。平日里他听胡思进说过,崖州欲得安宁,便须剿灭顽黎。但他就不相信,黎、汉百姓同居一方土,同饮一江水,世代相往来,黎民却如此凶顽!今天他初遇帕威父女,黎胞如此通情达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使他不疑自己平日所见。但身为司户参军,他深感责任重大,绝不可拿王法当儿戏,绝不可凭意气用事。果真有顽黎聚众造反,打家劫舍,便当绳之以法,以张扬大唐律典之尊严,以矫正百姓之视听。民风谆朴,人心思治,崖州始得安宁。
李德裕挤进人群,不觉大吃一惊。帕威父女被王得利一帮人围住,帕威像一头被网网住的野猪,左冲右突,要找王得利算帐。可是父女俩寡不敌众,怎能脱得身来。李德裕认出帕威,私下叹息,“不想他不懂王法!该我治罪时,我不能徇情枉法!”但他转生念头,凡事得弄个水落石出,万不可冤枉好人。李德裕悄悄问几个老人,有的说,“王得利要吸黎人髓”,有的把经过一五一十说了。李德裕再看帕威,他样子是凶,脸上却露出委屈的神色。而王得利一副模样,外 表三分可怜,骨子里七分得意。李德明白了一切,心中一把火扑腾扑腾地窜起。这刁钻之徒太可恶了,不把他拿下,再让他胡作非为? 一个方步,李德裕奔王得利而去,忽然觉得有人拽住衣袖,猛地想起自己乔装出访,不宜贸然从事,不如略施小计,救出父女再说。
李德裕一边佯装不认识帕威,一边显出关切的样子走近王得利身旁,“出事啦?”
“可不!可恶的黎头,要打家劫舍!”王得利更加神气。
“这还了得?咱平生爱帮人打官司,你拿出笔砚来,一条一条说与我,我帮你告他一状,如何?”李德裕郑重其事地说。
“好,好,好!”王得利不知是计,忙叫家人拿出纸笔。
“他如何反了,你要说个明明白白,才能一告通天!”李德裕端的提起笔。
“他……他谋财害命!”王得利振振有词。
“乃是在青天白日之下花言巧语,欺诈勒索,敲骨吸髓,大耍无赖,反诬一口,含血喷人吗?”李德裕佯作奋笔疾书之状。
“滚开,谁让你胡说八道!”王得利忽然省悟过来,李德裕在挖苦他,不禁恼羞成怒。
“哈哈,你喊我滚,我偏不滚。你不让我写,我就请你写,赏个光吧!”李德裕举着毛笔发笑。
“你滚开!谁让你来管闲事?”王得利习惯地拖长了猫腔。
“你呀!”李德裕说。
“你胡说!”王得利性起,伸开两指直指李德裕,不提防被刘松一只大手扼着手腕,吓得面如土色,连连求饶。他那几个杀狗兄弟一瞧来头不妙,也不敢动手动脚。
“好,就饶了你!你马上立下字据,以后不再胡作妄为!”李德裕说完,放下笔来。
王得利伸长脖子往前望,叹了气,像瘪了的皮球,蹦不起来。原来,他刚才使人去了州府,却不见救兵赶到。他使尽平生力气,拿起笔,如抱大树般吃劲,眼晴忙碌了一阵儿,写下一行字来:
我欺压黎人惹事端半斤八两今后不得再犯王得利立此字据
李德裕看了字条,暗笑道,“好一个刁钻之徒!”便拿笔过来加上标点,去了4个字,大声说,“我念一念,你有何话说”?说罢,当众念了:
我欺压黎人惹事端,今后不得再犯。王得利立此字据。
王得利班门弄不得钝斧,默默走开。李德裕藏好字条走了。
帕威父女脱身后,悄悄跟着李德裕,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老先生,救命恩人!救命恩人,老先生!”帕威“卜通”一声跪下。
秋玉不说话,满腹子要说的话,饱含在那一双深情的眸子里。
“起来,起来,让你委屈了!”李德裕弯腰扶起帕威。
父女还要送东西,李德裕哪里再肯收下?他一再嘱咐父女俩,便回毕兰村去了。
帕威赶往大蛋港,准备召集同来的伴伴,提早进山。刚才他们不在,害得父女势单力薄。帕威怕他们也遇到麻烦,事情可糟了。天塌下来,大伙在一块,也有个照应。
帕威拜别李德裕三人,和秋玉折回大路来,突然,拐角里闪出七八个兵丁,王得利也跑在中间,边跑边喊,“就是他,就是他!”帕威一看事情不妙,一转身,踅回一棵大树底下,一边招呼秋玉快走,一边回头唬着来人。怎奈秋玉是个女子,肩挑布袋,所以落后几步。
“贼剥皮,“王得利嚎喊着,“谅你插翅也飞不了!”
原来,王得利早跟胡思进明来暗往。王得利使唤的人进了州衙,见过胡思进,便谎报晒经墟上两个黎头造反。胡想进本来就巴不得逮住兔子作老虎,以便向上邀功,因此也不问个真假,便派兵丁赶来。
8个士兵分开两路,一半扑向帕威,一半扑向秋玉。
帕威站在大树底下,眼看四个兵丁包抄过去,切断了父女间的联系,奋不顾身,像过涧的老虎扑向兵丁,想把他们全都吸引过来。那边4个兵丁不为所动,这边4个兵丁却乘势包围上来。眼看一时讨不了便宜,只得退回大树下。4个兵丁分四方站定,指弓搭箭,全瞄准帕威这个靶心。帕威全无惧色,大喊;“谁先动手,谁死!”吓得兵丁楞住,谁也不敢抢先放箭。
“射呀,射死这个黎头!”王得利张牙舞爪地喊,“胡大人赏你们头功!”
这一喊还奏效,有谁首先放箭。箭,如飞蝗呼呼而出,接着,兵丁们全都放箭。帕威不慌不忙,凭借大树掩护,东躲西闪,逃过一个个箭镞,兵丁们再拈弓搭箭时,帕威早猫身来,瞄得真切,一支利箭应声而出,专向王得利的嘴巴下飞去,亏他装死装得快,嚎喊一声倒地,竟躲过了箭镞。
兵丁见王得利应弦而倒,一时手软,不曾放箭。帕威趁这空隙,三步两步,拐到一个墙角蹲定。兵丁紧追不舍,步步向帕威逼近。双方再次对射,你来我往。一边人多势众,一边气贯长虹,分不出胜负。帕威双眼闪着血光,两道浓眉拧紧,当那眉毛即将撞到一起时,喝了一声:“放!”弯腰搭弓,却虚晃一下,箭不曾出手。一边小头目受王得利怂恿,以为帕威把箭射光了,便想领个头功,从侧面绕了上去。帕威早〓得准,不声不响,拈上利箭。不曾听到弓弦响,利箭已射中小头目胸口。兵丁喊一声,“不好”!背起受伤的同伴走了。
帕威脱得身,心急火燎般寻找女儿时,秋玉已不知去向……
刚才,4个兵丁扑过来,秋玉呼天不答,呼地不应,脚膝盖都瘫软。她恍然听见一个声音,“跑,拼命跑,绝不能落到贼子手里!”她咬一咬牙龈,脚下似乎长了双翅。她看见一条小路,一头通进茂密的林子,就往小路跑去。她跑呀跑,心儿都仿佛飞出胸膛去了,可有一股风在推她,一个个声音在呼唤她。对了,寨子里的人在山那边等待她,阿光哥在那边等待她,越过这道山坡就见到亲人。她好几次要跌倒了,步子一抬,又朝前奔去。肩上的两个袋,越走越沉。她真想撂下麻袋,好跑得飞快。转瞬间,她又狠狠骂自己,“怕死鬼,软骨虫!袋里的是乡亲们的血汗,是寨子的命根子!撂给贼子,不是白让他便宜!就是死,也得把东西交回乡亲们手里!”秋玉想着,跑着,最后干脆什么都不去想,光顾拼命的跑……
秋玉当然没有想到,这条路不是南仇岭上的山路,只是通往崖州州城的一条小径。她人生地疏,慌不择路,最终跑不出虎口。两个兵丁紧迫不舍,堵住她的后路,另外两个早绕了弯,等候在岔路口。当她一口气跑出路口时,突然被一根拦路的绳子拌倒,两个兵丁凶神恶煞般扑上来了……
帕威当然不知道这一切 但他左右打听,都没弄清女儿的下落。突然,他放声哭了。刚才,面对敌人,他有的是复仇的火焰,是拼死到底的决心,刀劈下头颅也决不掉泪。这一回,他却伤心地哭了。他隐隐知道,女儿是落进了虎口。可怜的女儿呀,爹对不住你!乡亲们呀,咱对不住你们!帕威哭着,突然挥起青梅格般结实的拳头,对着自己的胸捶。他捶呀,捶呀,拳头都麻了,泪也干了。他兀地骂自己傻,傻!为什么白白伤了自己,不找贼子算账去?要让他们还我女儿,绝不让她伤损一根毫毛。若有半个“不”字,便以一换十,拼了个鱼死网破!
帕威浑身是火,扑向王得利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