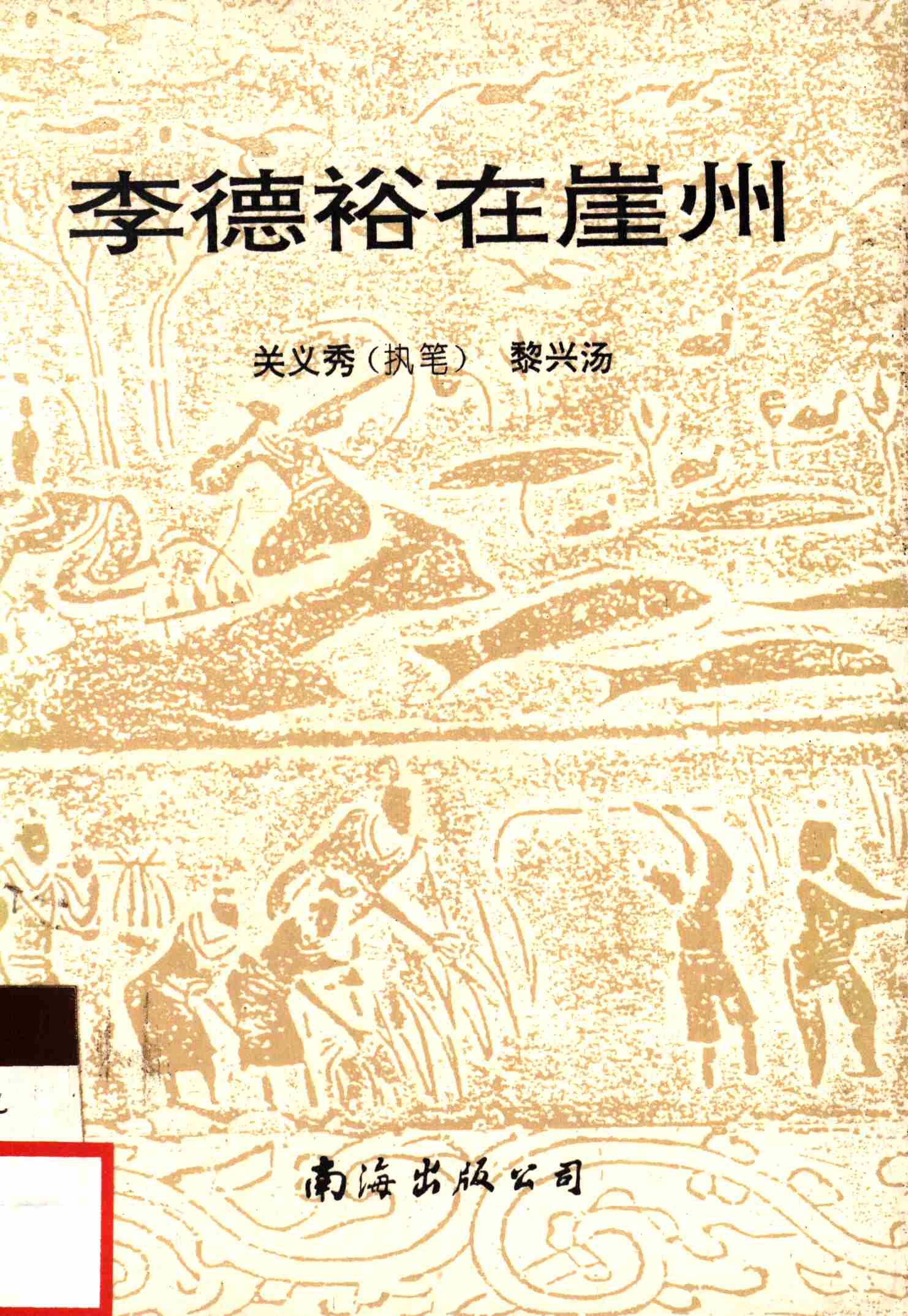内容
笫二天中午,大船抵达大蛋港。港口虽然不大,倒有大船横泊,小舟穿梭。李德裕下了船,放眼四望,并不见崖州州衙一个人影,不觉感叹一番。舵工也不辞而别。一行人只得怏怏上路。走了一程,忽听后面有人大声叫喊。回头看时,舵工气急败坏地赶来了。原来刚才他跟主人交差,匆促之间来不及打个招呼。这时,他才告诉李德裕,他叫李三。原本不想说的,怕玷辱一个“李”字。想来想去还是说了,日后也好有个照应。他就住在晒经坡墟。李三一再嘱咐大家小心,崖州城并不是个避风港。他一直把众人送到崖州州衙门外,跪拜了李德裕,才洒泪离去。
李德裕一行人在毕兰村住下了。
过了3天,李德裕上州衙当差。他万万没有想到,剌史胡思进会在外面恭迎。他平生见过不少州官,一个个不失缙绅的风度。但温柔之乡的父母官,理当如此。而今在这蛮荒之地遇上这一个顶头上司,李德裕就不能不称奇了。胡思进一直低着头,把李德裕迎进大厅。寒喧应酬之间,一派温文尔雅,一举手一投足,都异常得体。白晰的脸盘上,嘴角堆上笑容,眉梢传情达意,配合得天籁自成。美中不足的是,一只鼻子凸出极高的驼峰,鼻准头又弯成一个鹰嘴,显得有点累赘,无论如何也使端正的五官有失和谐。然而,他张口恰到好处的忠孝礼义,把这外表上的暇疵全遮掩了。李德裕阅人无数,还满以为他是翰林院里的人物,绝不想到他是靠征剿黎胞发迹的乡间举子。
“大人光临敝州之日,卑职适因公务外出,有失远迎!幸亏大人不计小人过,”胡思进学着中原腔调,“此是大人不幸胡某有幸。不过,委屈了大人,卑职于心实在不忍”!
“大人过谦了。下官载罪在身,赖朝庭洪恩,蒙大人错爱,实是感激不尽。吾初到崖州,人生地疏,还仰大人明示,以免渎职。”李德裕谦恭地说。
“大人刚到,安歇三月五月,又有何妨?恕吾妄言,本州虽非文明礼仪之邦,也断无作奸犯科之徒。大人回去歇息就是。改日吾再设薄宴为大人洗尘!”胡思进极为诚恳地说。
李德裕是个重义气之人。一席话,他仿佛他乡遇故知。心头似乎搬掉了一块大石。
李德裕闲着没事干,白天就教李通念书。几天来他心情好多了,便把《论语》教给孩子。
读了几页,李通却吵起来:“我不要读,我不读!”
“不读,将来你怎么治国平天下?”李德裕板起脸训斥孩子。
“我不要治国平天下。治国治国,治到头来,都治不了墙壁的窟窿!”李通并不服气。
李德裕不禁抬起头,环顾了一家人的住屋。这是一间陈旧的瓦房。由于年久失修,屋顶开了“天窗”,料峭的寒风从破墙洞里进进出出。
“孩子,好好念书才好回家去!”李德裕哄着孩子。
“真的?什么时候?”李通破涕为笑地嚷。
“不出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李德裕低声说,慢慢闭上眼睛。眼前,闪过金碧辉煌的九重宫阙,闪过那八角飞檐的精思亭,闪过那一张威风凛凛的太师椅。他在亭里计议过多少国事,草就过多少封诏诰册命,写下多少篇锦绣文章。更那堪,别时容易见时难。此刻,只能在幻觉中同它们相会。
李通知道父亲在想家,不再吵了。他毕竟懂一点事了。
夜。
吃过晚饭,一家人聚在房里,闲话崖州人情风物。李通依偎在母亲身边,歪着头,出神地听着。
“通儿,过来,”李德裕指着桌上的《论语》对李通说,“父亲考考你!子日何者为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李通倒背如流,却赖在李夫人身边。
“过来!吾再考你:君子欲讷者何,欲敏者何?”李德裕有意为难孩子——这还不曾教呢。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李通依然倒背如流。
“这孩子,10年后又是一个翰林!”李茂光赞叹着。
“孩子,咱李家可不兴翘尾巴的规矩。在崖州更得事事留心,切莫让人道个三长两短!”李夫人把孩子搂到跟前,理了理他的衣服,才让他到父亲面前。
李通独自读起《论语》。
“痒呀!痒呀!”忽然李通嚷道。
“不好好读,嚷什么?”李德裕一话刚完,也低声叫,“哎,奇怪!吾也发痒!”
仿佛一场瘟疫流行,你传染我,我传染他,屋里头喊“痒”之声彼落此起。
“莫非咱初到崖州不服水土,犯了皮肤病?”李茂光压低嗓门说。
李德裕刚要说什么,一个人已进屋里。他想到不李三突然来了,手里挎着一个竹篮子。一个大大咧咧的汉子,腼腆,怪难为情地说:“大人,没好衣物孝敬你!托你的福,一个同年送给我几块鹿肉干。我知道你爱尝它,咱就来打扰你了!”
“兄弟,谁得你有这片好心,如何谢你?”李夫人千般感激。
“谢什么?要谢,就谢我的同年!反正,鹿肉干不是我的!”李三摊开两手说。
李德裕不禁想起,朝中大臣都曾经说过崖州人长尾巴,个个青面獠牙。他们岂不是闭着眼睛说梦话?眼前一个船夫,开口并非三纲五常,闭口殊少治国安邦良策。可是他同自己不过萍水相逢,却这般情深义重。比起那些口是心非、落石下井之流来,他强过多少!而他,正是崖州人,并非出身诗书簪缨之族。顿时,一腔热血直冲头顶,李德裕吩咐夫人收下鹿肉,郑重地说:“君子报恩,三年不晚嘛。容日后再酬谢兄弟。”
这会儿,李通放下书,也来凑凑热闹,忽然又嚷“痒,痒”不停。
“兄弟,崖州可有郎中?不知怎样,今晚咱们都犯了痒病。”李茂光问李三道。
人不答话,李三也叫“痒”不止。他一伸手,从衣服里抓出来什么,嚷一声,“掐死你这个贼”。“嚓”一响,果然结果了小东西生命。他又把手伸进衣服下面,恍然大悟地说,“你们都是这般痒的吧?那是什么病,是这贼作怪!”说完,他抓出来一只虫子,掐死,放在掌心给大家看。
“咱怎么没见过这虫子?”李通大惑不解。
“孩子,你怎么能见过?”李三指手划脚的,“这是跳蚤。咱给它编了歌:跳蚤跳蚤本领大,一个跟头三丈高。躲在身上吸人血,胃也撑来肚也饱。”
李三边唱边跳,大家直乐。
“大人,毕兰村是有名的跳蚤村。村里的跳蚤,比苍蝇还要大!”李三说说笑笑,忽然沉下脸来,“好一个胡鹰鼻!他啄到大人头上来了!他让你住在这,不是要把你折腾苦么?”
“兄弟,哪一个胡鹰鼻?”李德裕不解地问。
“还不是堂堂的剌史大人!”李三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
“你又编派父母官了!”李夫人笑着。
“崖州人谁不说他好?”李三反唇相讥。
“兄弟,剌史大人有他的难处!”李德裕压低了声音。
“什么难处?难,也不该难到大人头上来。亏他还到处征粮派饷,说是要好好款待你。款待,款待,跳蚤肝跳蚤肺,真够好吃!”李三数落个不停。
大家都不说话。李德裕想起来了,胡思进是说过要给他接风洗尘。也许,人家真心实意的。不过,事情也真有蹊跷。海上有海盗拦路打劫,胡思进却一本正经,说崖州没有作奸犯科之徒。事情还真难分子日诗云。李德裕越想,心越往下沉,心越往下沉,偏往好方面想……
胡思进倒是说到做到。
正月十八这一天,崖州州衙里大摆酒席,盛况空前。红灯从大厅,三五步一个,一直挂到大门口,门前的石人、石马,也披红着绿,天刚亮,四名衙役就在门口轮番敲打铜鼓。鼓槌飞舞得煞得好看,急骤时赛纺车疾转,舒缓处似鲫鱼过江。鼓声飞进府州门前奔腾的宁远河水,飞进深山老林里的百姓人家,伴着一片寒喧得体的官腔,飞进不甘寂寞的杯盏……
胡思进踱着八字步,那样从容,潇洒。他极力显出心平气和,却不时瞻前顾后,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大厅里摆了五张酒桌,主席正好在大厅正中。他信步向着主桌走去,却一再谦让,要推李德裕坐了主位。
李德裕脸上掠过一丝凄楚,哪里肯就座?他择东边一个次位坐了。
“这可折杀胡某了,”胡思进再次推辞,毕竟坐了主位。其实,主位上端然摆放的,就是他平日坐的太师椅。
“李大人曾贵为宰辅,”胡思进首先举起酒杯致辞,不知什么缘故,说到“宰辅”两字时,似乎噎住,压低声音,“此次光临崖州,实乃百姓洪福。诸位,咱先敬李大人一杯!”
李德裕举杯答礼,然后离开座位,走到每张酒桌面前,挨次给各同僚敬酒,才回到座位致辞,“多蒙胡大人错爱,多蒙各位错爱。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诸位义重如山,何况崖州百姓有恩于我。我李某,当肝脑涂地以相报!”
“难得李大人这般看重义气,吾辈越发钦佩,钦佩!”
胡思进一边说,一边环顾众人。
“钦佩,钦佩!”附和之声不绝于耳。
“来,诸位喝呀。君子动口又动手嘛!”胡思进边说,边大动筷子。诸官员便一齐仿效。于是,杯筹觥错之声回荡在崖州州衙大厅。
李德裕文绉绉的,象征性地尝了一点菜。
“咦,李大人!文明归文明,大丈夫干起杯来,得有君临天下的勇气。对吗?”胡思进指着菜肴,颇为得意,“崖州之珍禽怪兽全在面前。吃掉它们。不然,咱怎能成为一州之主呢?”
“胡大人高见,高见。”一个花白胡子幕僚连忙扳起大拇指。
胡思进似乎不满意这廉价的恭维,看也不看花白胡子,双手抓起一只大螃蟹。一折,一瓣,一剥,三下两下,嫩生生的蟹肉露了出来。“好鲜,好鲜,”胡思进仿佛美食家,大谈吃蟹经,“螃蟹可白煮,可伴炒。白煮的佐料不同,酸、甜、苦、辣、咸,应有尽有,虽是一样蘸着蟹吃,却能吃出不同味道。至于伴炒,也是花样翻新……”胡思进说着,说着,馋劲倒真的来了。他顾不得许多,张开十只手指,把蟹肉连撕连扯,一起塞进嘴里。只剩下黄澄澄的蟹油,东一撮西一撮在下巴上发光。
“崖州风味,够味,够味,”幕僚们又一次仿效,又一次喝彩。
“李大人,你这慢条斯理的,可不够气派,”胡思进又一次献殷勤,“哟,大人怕两只螯张牙舞爪的,是不是?螃蟹活着时也够神气的,它如今已是盘中之物!李大人,请!”
但李德裕始终气派不起来。他亲临过多少宴会,如今宾主互位,心里自有难言的苦衷。他本来就是应酬而赴宴的。况且,他文惯了,这粗,这野,自然要使他大倒口胃。对于胡思进的盛情,只好报以彬彬有礼的敷衍。然而,当胡思进请他尝尝“全牛汤”的时候,这敷衍便达到了极限。
全牛汤其实是胡思进的创造。无非取牛的一点五脏六腑,熬成汤,再加一点生姜之类配料而已。用料并不稀贵,味道也属寻常。可是胡思进居然命人熬了全牛汤,特意请李德裕品尝,颇为幸灾乐祸地摇头晃脑,“牛怪可怜的,为人拉车、套犁,终为碗中之羹其实人牛又有何异?”李德裕感到诧异,胡思进为何扯个天南地北?莫非他借题发挥?难道他……李德裕是个机敏之人,顿时萌生一个念头,何不试探胡思进一下,便若无其事地说,“还得有劳大人赏李子下酒!”
“咱崖州何来李子?再说,崖州官民未尝用果子下酒呢!”胡思进尴尬一笑。
其实,这一笑后面大有文章呢。十天八天来,李德裕的贬崖似乎一块石头,在胡思进心湖中激起层层波澜。一想到一代名相,将是他治下一介参军,将要听从他的调遣,禁不住心花怒放。如果说,他以前只是尝够土皇帝的滋味,那未,这一回他要好好享用享用真命天子的尊贵了。因为在他看来,李德裕是宰相,而自己凌驾在他之上,岂不成了货真价实的大唐皇帝?但伴君如伴虎。李德裕虽不是君,却位极人 臣,自己能制服得他吗?别说自己一个小小刺史,就是朝庭中一个个文韬武略的重臣,也曾败在李德裕的手下。一想到这,胡思进不免畏了三分,真有点惶惶然不可终日了。但胡思进很快就心地释然了。自古以来,谁被贬,谁就是囚徒。何况在崖州,天高皇帝远。李德裕纵有三头六臂,也只是笼中的饿老虎罢了。更何况,上面早来了密令,叫他严加监管李德裕。胡思进捧着那张文书,胜过捧着皇帝的圣旨,腰板子铁硬了五分,呼出来的气粗了六分。但他转念一想,铁树都有开花时。万一圣驾崩了,新皇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德裕重新得宠,那怎么办?因此,胡思进心里头,轻的、重的都掂过了,甜的、苦的都尝过了,明的、暗的都盘算过了。他既要耍一耍威风,又要表一表敬意,既要摊一摊牌,又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翻遍了史书典籍,想着自己官运亨通的来历,专来对付一个李德裕。最后,他得出5个字:抬、压、哄、抓、告。几天来,他抬举、恭维过了,得压一压老头子,别让他翘尾巴。至于哄骗啦,抓把柄、抓人啦,密告他于朝庭啦,日子还长着呢。胡思进知道牛僧孺、李德裕长期不和,故此借全牛汤影射:姓牛的没有好下场,既欲套出李的话来,又想杀一杀他的余威!李德裕不露声色试探一问,弦外之音在于告诉胡思进:谅你也不敢把吾怎样!胡思进对此心照不宣,急忙掩饰,露出一点尴尬之色也就不足怪了。这一回合,胡思进倒自讨个没趣。
众人已喝到酒酣耳热,胡思进占不到便宜,似乎骨梗于喉,咽不下一口气。他摸摸下巴,朝座上两个幕僚䀹一䀹眼,又对李德裕笑了笑,“李大人,崖州天偏地僻,席间无丝竹管弦助兴,实是一大憾事。不妨猜拳行令以凑热闹。李大人才高北斗,吾辈借光了。”两个幕僚不约而同张嘴举拳,“胡大人之言,正合下官心意。”李德裕捋捋胡子,微微一笑:“胡大人雅量高致,吾敢不奉陪?只是猜拳行乐,谁答不上来,该罚一碗,以增乐趣才是!”胡思进又朝两个幕僚䀹一䀹眼,“好!咱先来个颠倒令。我先念上句,李大人接下句。谁答不上来,甘心受罚!”李大人怕丈夫有个闪失,在众人面前露馅,连连对他使眼色。李德裕却当没看见,满口答应了。
虽是行令,胡思迎却要把气往上出,压得李德裕抬不起头。两只眼睛骨碌一转,心中有了,便润了润喉咙,高声念道,“大也小,傍山落日哀垂暮。”那意思是,你李德裕哪怕是个庞然大物,如今也变“小”了,真正是日薄西山,危在旦夕。李德裕瞧他那个得意劲儿,明白他又含沙射影,怒气勃然而生。你要朝李某头上拉屎,吾岂饶你?大丈夫死则死矣,绝不受此窝囊气。不过,他绝无弩拔弓张之态,只是在对答里寸步不让:“小似大,草间蟋蟀鸣破天。”你胡某一个小小蟋蟀也要自鸣得意,太不自量了!
一个幕僚眼看胡思进托住下巴,连忙念,“有似无,仙子飘游太空处。”李德裕略加思索念道,“无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
另一个幕僚不甘落后,抢着念,“易似难,执手临分话别间”。李德裕一拱手,“嗖”地站起,“难似易,一腔热血酬知己。”
瘦马拉车牛帮力。两个幕僚帮了忙,唱了几个回合,到底赢不了李德裕。只好停了颠倒令。刘松斟了满满一碗,径直递到胡思进面前。胡思进本来要出李德裕的丑,不想屎却拉到头上来,真是哑子吃黄连。可他颇有腹量,接过酒碗还笑道,“李大人瞧得起胡某!多谢李大人!”说罢,一饮而尽。
“李大人,再来花鸟虫鱼令。吾先念一句令名,大人就说出崖州一件物名。请吧!”胡思进挟起熊掌往嘴里送,边吃边说。
“吾初到崖州,不谙人情风物。胡大人,你岂不让李某出丑?”李德裕佯作推辞的样子。
“哎,李大人博学多才,区区酒令何足挂齿?”胡思进也不管李德裕是否答应,便念了一句令名:“花开百日不见红。”
“是百里红吧。”李德裕带着拿不准的口气。
“花到老来越妖烧!”胡思进接声而起,不让李德裕喘过气来。
“老来红!”李德裕也脱口而出。
“摇摇摆摆过山来”眼看胡思进卡壳,花白胡子幕僚连忙接应。
“过山龙!”李德裕思讨一会。
“周甲子开花!”花白胡子以为李德裕江郎才尽,又喊了一句令名。
李德裕猜了几件物名,都没有猜中。
“是铁树!李大人,你也该输一回,礼尚往来嘛!”胡思进颇为得意,李德裕甘心罚了
其实,这一回李德裕故意装糊涂。一来,输了免得胡思进耿耿于怀;二来,也免得众人生疑;李德裕乍来崖州,怎会对崖州一切了如指掌?这还了得!
胡思进被瞒过了。他正暗自得意,忽见手下人进来,在身边嘀咕什么,这才出到大厅外面。
“大人,吉阳县送来的礼单!”来人毕敬毕恭地递上一张红帖。
胡思进两话不说,接过红帖便看,上面一项一项写着:
白米十石 鱿鱼二百斤
牛 十头 猪二十头
槟榔三千只 椰子一千个
胡思进把礼单掷在地上,扬长口气,“吉阳县令,你好大的胆子!”
“来人说,县令择日再把其余礼物送来!”手下人小心翼翼的样子。
“我还以为他长两颗恼袋呢!”胡思进愤愤不平,“他误了日期,又打了折扣,这不是要让李参军喝海水?你去对来人说,黎锦、鹿茸限3天内送来,一尺不能短,一两不能少!”
胡思进余怒未消,回到大厅时,还掩饰不住内心的不悦。
“大人,咱们哼几句崖州土歌,聊庆今日之喜,如何?”花白胡子幕僚讨好地问。
“好嘛,好嘛!”胡思进心不在焉地应道。
花白胡子清清嗓子,唱了起来:
今旦逢光辉盛景,
州府里集众官绅。
全仰刺史大人福,
日丽风和颂太平。
花白胡子用黄流话唱,李德裕听不懂,却饶有兴味地品味那咿咿呀呀的腔调。胡思进忽然借花献佛,一边学唱,一边给李德裕解释,“李大人,崖州百胜仰望你有如百川归海,痛骂奸人天理难容!”
听到“百姓”两字,李德裕动情了。他依稀见到阴风呼呼,长安城街道上石人石马也冷着面孔。他孤家寡人般的走在大街。旧时三千门客哪里去了?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语,只有那沉重的靴声,在朔风中叩打着揪心的凄楚。然而,在长安城外,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携儿带女,荷箪端浆,跪在道路两旁,为他送行,为他祈福:一声声保重,一声声地平安……李德裕哭了,一个堂堂的大唐丞相哭了,哭得热泪盈眶,哭个悔恨不止:“我李德裕有何功德,值得百姓同情?天呀!我枉为百姓父母官呀!”这一场景恍然现在眼前,李德裕眼眶润湿,颤抖地捧起酒碗,对着众人,对着上下四方,”皇天在上:我李德裕敬百姓一杯,敬崖州百姓一杯!”
“胡某代崖州百姓领了大人美意,饮了这碗酒吧!”胡思进伸过手去,捧着碗一饮而尽。
李德裕刚好坐下,胡思进突然又捧起酒杯,“李大人,胡思进代崖州百姓敬你一杯!”
李德裕本不胜酒量,可胡思进一而再再而三地敬酒,幕僚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摇唇鼓舌,尽管李大人、李茂光、刘松一齐挡驾,也无济于事。本来,李德裕亲临过无数官庭宴会,仙泉玉液何尝不品味个够?然而,当此“四十年来车马客,无人相送到崖州”的落魄之时,李德裕正需要那水火相融的液体,来把胸中郁积的压抑、愤懑,化作清风,散为轻烟,好乐得一身自在。更何况,胡思进嘴里“百姓”两个 字,万般诱惑着他。因此,他不禁贪欲了几杯。
猛然,李德裕只觉得一股热腾腾的气流,仿佛脱缰的野马,在心里横冲直撞,在天灵盖上闹了个晴天霹雳。面前的大厅、酒席、人,都搅混在一起。自己也迷迷糊糊的,随着搅混了的一切旋转。
胡思进本有海量,就是泡在酒缸里,他也清清爽爽。可是,李德裕喝醉时,他也“啪”地摔了酒杯,踉踉跄跄离开开座位,三步趔趄,五步栽葱,手舞足蹈地嚷,“我没一醉,再干——三百杯,谁欺——欺负——李大人,我—我—决不—饶—饶他!”
一句话,火上添油。刹那间,李德裕双眼闪烁电光,闪出漫天烈火,发抖的双手如掣剑,往四面八方劈,“谁—敢敢欺欺负我?老夫—就就劈谁!江山都运—运在咱掌心里, 白—白敏中—好大胆—在皇上耳边—吹吹风—老夫—劈—劈—”说罢,,大笑不止。
“佩服,佩—佩服!”胡思进仰头大笑,“胡大人—天上—文曲星—快拿笔—李大人一题诗—”
李夫人扶住丈夫坐定,用清水擦了擦他。李德裕酒醒了。乘着酒兴,他龙飞蛇舞题下一首五绝,抒发内心的感慨:
一去一万里,
千之千不还。
崖州在何处?
生度鬼门关。
“领教,领教了!”胡思进那样子也醒酒了,其实,他根本没醉。他边说,边拿过诗稿。嘿,好一个“生度鬼门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治下的崖州,竟是鬼门关!死罪临头,你这不知死罪的李德裕!胡思进心里狂笑不止,可他脸上堆满笑容,眯住眼睛赞不绝口,“李大人,好诗!诗以言志嘛”。
一个喜不自禁,另一个却懊恼不已。虽说酒后失言,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吐出来倒也痛快,自己是死是活也不要紧。但连累一家老小,白白坏了一世功名,便宜了那帮小人,这岂不冤哉枉也?李德裕越想,越坐立不安,不觉对胡思进及众官绅拱手谢罪,“刚才老夫贪杯,一时妄言,诸位可别见怪。吾载罪于身,蒙朝庭大恩大德,授予司户参军之职,一定效犬马之劳。臣作牛作马,以报答皇上荡荡圣恩”!
此时,胡思进袖袍里揣着李德裕诗稿,仿佛揣着一张催命符,哪里听得进李德裕的一番话?大肠小肠里虽填饱了膏油,胡思进还是挟起盘里一只虎蟹。虎蟹满身虎斑,乃蟹中大王。它虽然成了盘中之物,两只大的螯张着,还虎虎有生气。胡思进把螫狠狠折了,狂笑不止,“看你还神气不神气”?
“胡大人,吾告辞了!”李德裕拱手道谢,“诸位,吾告辞了”!
“恕不远送!”胡思进欠身说。比起开宴时,他的热度大大降温了。
时已中午。锣鼓手早撤兵了,太阳躲在乌云里,懒懒散散,不肯露面。一阵冷风刮来,撩起李德裕的袍角。他不由说:好大的风!
李德裕一行人在毕兰村住下了。
过了3天,李德裕上州衙当差。他万万没有想到,剌史胡思进会在外面恭迎。他平生见过不少州官,一个个不失缙绅的风度。但温柔之乡的父母官,理当如此。而今在这蛮荒之地遇上这一个顶头上司,李德裕就不能不称奇了。胡思进一直低着头,把李德裕迎进大厅。寒喧应酬之间,一派温文尔雅,一举手一投足,都异常得体。白晰的脸盘上,嘴角堆上笑容,眉梢传情达意,配合得天籁自成。美中不足的是,一只鼻子凸出极高的驼峰,鼻准头又弯成一个鹰嘴,显得有点累赘,无论如何也使端正的五官有失和谐。然而,他张口恰到好处的忠孝礼义,把这外表上的暇疵全遮掩了。李德裕阅人无数,还满以为他是翰林院里的人物,绝不想到他是靠征剿黎胞发迹的乡间举子。
“大人光临敝州之日,卑职适因公务外出,有失远迎!幸亏大人不计小人过,”胡思进学着中原腔调,“此是大人不幸胡某有幸。不过,委屈了大人,卑职于心实在不忍”!
“大人过谦了。下官载罪在身,赖朝庭洪恩,蒙大人错爱,实是感激不尽。吾初到崖州,人生地疏,还仰大人明示,以免渎职。”李德裕谦恭地说。
“大人刚到,安歇三月五月,又有何妨?恕吾妄言,本州虽非文明礼仪之邦,也断无作奸犯科之徒。大人回去歇息就是。改日吾再设薄宴为大人洗尘!”胡思进极为诚恳地说。
李德裕是个重义气之人。一席话,他仿佛他乡遇故知。心头似乎搬掉了一块大石。
李德裕闲着没事干,白天就教李通念书。几天来他心情好多了,便把《论语》教给孩子。
读了几页,李通却吵起来:“我不要读,我不读!”
“不读,将来你怎么治国平天下?”李德裕板起脸训斥孩子。
“我不要治国平天下。治国治国,治到头来,都治不了墙壁的窟窿!”李通并不服气。
李德裕不禁抬起头,环顾了一家人的住屋。这是一间陈旧的瓦房。由于年久失修,屋顶开了“天窗”,料峭的寒风从破墙洞里进进出出。
“孩子,好好念书才好回家去!”李德裕哄着孩子。
“真的?什么时候?”李通破涕为笑地嚷。
“不出一年,二年,三年,五年……”李德裕低声说,慢慢闭上眼睛。眼前,闪过金碧辉煌的九重宫阙,闪过那八角飞檐的精思亭,闪过那一张威风凛凛的太师椅。他在亭里计议过多少国事,草就过多少封诏诰册命,写下多少篇锦绣文章。更那堪,别时容易见时难。此刻,只能在幻觉中同它们相会。
李通知道父亲在想家,不再吵了。他毕竟懂一点事了。
夜。
吃过晚饭,一家人聚在房里,闲话崖州人情风物。李通依偎在母亲身边,歪着头,出神地听着。
“通儿,过来,”李德裕指着桌上的《论语》对李通说,“父亲考考你!子日何者为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李通倒背如流,却赖在李夫人身边。
“过来!吾再考你:君子欲讷者何,欲敏者何?”李德裕有意为难孩子——这还不曾教呢。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李通依然倒背如流。
“这孩子,10年后又是一个翰林!”李茂光赞叹着。
“孩子,咱李家可不兴翘尾巴的规矩。在崖州更得事事留心,切莫让人道个三长两短!”李夫人把孩子搂到跟前,理了理他的衣服,才让他到父亲面前。
李通独自读起《论语》。
“痒呀!痒呀!”忽然李通嚷道。
“不好好读,嚷什么?”李德裕一话刚完,也低声叫,“哎,奇怪!吾也发痒!”
仿佛一场瘟疫流行,你传染我,我传染他,屋里头喊“痒”之声彼落此起。
“莫非咱初到崖州不服水土,犯了皮肤病?”李茂光压低嗓门说。
李德裕刚要说什么,一个人已进屋里。他想到不李三突然来了,手里挎着一个竹篮子。一个大大咧咧的汉子,腼腆,怪难为情地说:“大人,没好衣物孝敬你!托你的福,一个同年送给我几块鹿肉干。我知道你爱尝它,咱就来打扰你了!”
“兄弟,谁得你有这片好心,如何谢你?”李夫人千般感激。
“谢什么?要谢,就谢我的同年!反正,鹿肉干不是我的!”李三摊开两手说。
李德裕不禁想起,朝中大臣都曾经说过崖州人长尾巴,个个青面獠牙。他们岂不是闭着眼睛说梦话?眼前一个船夫,开口并非三纲五常,闭口殊少治国安邦良策。可是他同自己不过萍水相逢,却这般情深义重。比起那些口是心非、落石下井之流来,他强过多少!而他,正是崖州人,并非出身诗书簪缨之族。顿时,一腔热血直冲头顶,李德裕吩咐夫人收下鹿肉,郑重地说:“君子报恩,三年不晚嘛。容日后再酬谢兄弟。”
这会儿,李通放下书,也来凑凑热闹,忽然又嚷“痒,痒”不停。
“兄弟,崖州可有郎中?不知怎样,今晚咱们都犯了痒病。”李茂光问李三道。
人不答话,李三也叫“痒”不止。他一伸手,从衣服里抓出来什么,嚷一声,“掐死你这个贼”。“嚓”一响,果然结果了小东西生命。他又把手伸进衣服下面,恍然大悟地说,“你们都是这般痒的吧?那是什么病,是这贼作怪!”说完,他抓出来一只虫子,掐死,放在掌心给大家看。
“咱怎么没见过这虫子?”李通大惑不解。
“孩子,你怎么能见过?”李三指手划脚的,“这是跳蚤。咱给它编了歌:跳蚤跳蚤本领大,一个跟头三丈高。躲在身上吸人血,胃也撑来肚也饱。”
李三边唱边跳,大家直乐。
“大人,毕兰村是有名的跳蚤村。村里的跳蚤,比苍蝇还要大!”李三说说笑笑,忽然沉下脸来,“好一个胡鹰鼻!他啄到大人头上来了!他让你住在这,不是要把你折腾苦么?”
“兄弟,哪一个胡鹰鼻?”李德裕不解地问。
“还不是堂堂的剌史大人!”李三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
“你又编派父母官了!”李夫人笑着。
“崖州人谁不说他好?”李三反唇相讥。
“兄弟,剌史大人有他的难处!”李德裕压低了声音。
“什么难处?难,也不该难到大人头上来。亏他还到处征粮派饷,说是要好好款待你。款待,款待,跳蚤肝跳蚤肺,真够好吃!”李三数落个不停。
大家都不说话。李德裕想起来了,胡思进是说过要给他接风洗尘。也许,人家真心实意的。不过,事情也真有蹊跷。海上有海盗拦路打劫,胡思进却一本正经,说崖州没有作奸犯科之徒。事情还真难分子日诗云。李德裕越想,心越往下沉,心越往下沉,偏往好方面想……
胡思进倒是说到做到。
正月十八这一天,崖州州衙里大摆酒席,盛况空前。红灯从大厅,三五步一个,一直挂到大门口,门前的石人、石马,也披红着绿,天刚亮,四名衙役就在门口轮番敲打铜鼓。鼓槌飞舞得煞得好看,急骤时赛纺车疾转,舒缓处似鲫鱼过江。鼓声飞进府州门前奔腾的宁远河水,飞进深山老林里的百姓人家,伴着一片寒喧得体的官腔,飞进不甘寂寞的杯盏……
胡思进踱着八字步,那样从容,潇洒。他极力显出心平气和,却不时瞻前顾后,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大厅里摆了五张酒桌,主席正好在大厅正中。他信步向着主桌走去,却一再谦让,要推李德裕坐了主位。
李德裕脸上掠过一丝凄楚,哪里肯就座?他择东边一个次位坐了。
“这可折杀胡某了,”胡思进再次推辞,毕竟坐了主位。其实,主位上端然摆放的,就是他平日坐的太师椅。
“李大人曾贵为宰辅,”胡思进首先举起酒杯致辞,不知什么缘故,说到“宰辅”两字时,似乎噎住,压低声音,“此次光临崖州,实乃百姓洪福。诸位,咱先敬李大人一杯!”
李德裕举杯答礼,然后离开座位,走到每张酒桌面前,挨次给各同僚敬酒,才回到座位致辞,“多蒙胡大人错爱,多蒙各位错爱。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诸位义重如山,何况崖州百姓有恩于我。我李某,当肝脑涂地以相报!”
“难得李大人这般看重义气,吾辈越发钦佩,钦佩!”
胡思进一边说,一边环顾众人。
“钦佩,钦佩!”附和之声不绝于耳。
“来,诸位喝呀。君子动口又动手嘛!”胡思进边说,边大动筷子。诸官员便一齐仿效。于是,杯筹觥错之声回荡在崖州州衙大厅。
李德裕文绉绉的,象征性地尝了一点菜。
“咦,李大人!文明归文明,大丈夫干起杯来,得有君临天下的勇气。对吗?”胡思进指着菜肴,颇为得意,“崖州之珍禽怪兽全在面前。吃掉它们。不然,咱怎能成为一州之主呢?”
“胡大人高见,高见。”一个花白胡子幕僚连忙扳起大拇指。
胡思进似乎不满意这廉价的恭维,看也不看花白胡子,双手抓起一只大螃蟹。一折,一瓣,一剥,三下两下,嫩生生的蟹肉露了出来。“好鲜,好鲜,”胡思进仿佛美食家,大谈吃蟹经,“螃蟹可白煮,可伴炒。白煮的佐料不同,酸、甜、苦、辣、咸,应有尽有,虽是一样蘸着蟹吃,却能吃出不同味道。至于伴炒,也是花样翻新……”胡思进说着,说着,馋劲倒真的来了。他顾不得许多,张开十只手指,把蟹肉连撕连扯,一起塞进嘴里。只剩下黄澄澄的蟹油,东一撮西一撮在下巴上发光。
“崖州风味,够味,够味,”幕僚们又一次仿效,又一次喝彩。
“李大人,你这慢条斯理的,可不够气派,”胡思进又一次献殷勤,“哟,大人怕两只螯张牙舞爪的,是不是?螃蟹活着时也够神气的,它如今已是盘中之物!李大人,请!”
但李德裕始终气派不起来。他亲临过多少宴会,如今宾主互位,心里自有难言的苦衷。他本来就是应酬而赴宴的。况且,他文惯了,这粗,这野,自然要使他大倒口胃。对于胡思进的盛情,只好报以彬彬有礼的敷衍。然而,当胡思进请他尝尝“全牛汤”的时候,这敷衍便达到了极限。
全牛汤其实是胡思进的创造。无非取牛的一点五脏六腑,熬成汤,再加一点生姜之类配料而已。用料并不稀贵,味道也属寻常。可是胡思进居然命人熬了全牛汤,特意请李德裕品尝,颇为幸灾乐祸地摇头晃脑,“牛怪可怜的,为人拉车、套犁,终为碗中之羹其实人牛又有何异?”李德裕感到诧异,胡思进为何扯个天南地北?莫非他借题发挥?难道他……李德裕是个机敏之人,顿时萌生一个念头,何不试探胡思进一下,便若无其事地说,“还得有劳大人赏李子下酒!”
“咱崖州何来李子?再说,崖州官民未尝用果子下酒呢!”胡思进尴尬一笑。
其实,这一笑后面大有文章呢。十天八天来,李德裕的贬崖似乎一块石头,在胡思进心湖中激起层层波澜。一想到一代名相,将是他治下一介参军,将要听从他的调遣,禁不住心花怒放。如果说,他以前只是尝够土皇帝的滋味,那未,这一回他要好好享用享用真命天子的尊贵了。因为在他看来,李德裕是宰相,而自己凌驾在他之上,岂不成了货真价实的大唐皇帝?但伴君如伴虎。李德裕虽不是君,却位极人 臣,自己能制服得他吗?别说自己一个小小刺史,就是朝庭中一个个文韬武略的重臣,也曾败在李德裕的手下。一想到这,胡思进不免畏了三分,真有点惶惶然不可终日了。但胡思进很快就心地释然了。自古以来,谁被贬,谁就是囚徒。何况在崖州,天高皇帝远。李德裕纵有三头六臂,也只是笼中的饿老虎罢了。更何况,上面早来了密令,叫他严加监管李德裕。胡思进捧着那张文书,胜过捧着皇帝的圣旨,腰板子铁硬了五分,呼出来的气粗了六分。但他转念一想,铁树都有开花时。万一圣驾崩了,新皇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德裕重新得宠,那怎么办?因此,胡思进心里头,轻的、重的都掂过了,甜的、苦的都尝过了,明的、暗的都盘算过了。他既要耍一耍威风,又要表一表敬意,既要摊一摊牌,又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翻遍了史书典籍,想着自己官运亨通的来历,专来对付一个李德裕。最后,他得出5个字:抬、压、哄、抓、告。几天来,他抬举、恭维过了,得压一压老头子,别让他翘尾巴。至于哄骗啦,抓把柄、抓人啦,密告他于朝庭啦,日子还长着呢。胡思进知道牛僧孺、李德裕长期不和,故此借全牛汤影射:姓牛的没有好下场,既欲套出李的话来,又想杀一杀他的余威!李德裕不露声色试探一问,弦外之音在于告诉胡思进:谅你也不敢把吾怎样!胡思进对此心照不宣,急忙掩饰,露出一点尴尬之色也就不足怪了。这一回合,胡思进倒自讨个没趣。
众人已喝到酒酣耳热,胡思进占不到便宜,似乎骨梗于喉,咽不下一口气。他摸摸下巴,朝座上两个幕僚䀹一䀹眼,又对李德裕笑了笑,“李大人,崖州天偏地僻,席间无丝竹管弦助兴,实是一大憾事。不妨猜拳行令以凑热闹。李大人才高北斗,吾辈借光了。”两个幕僚不约而同张嘴举拳,“胡大人之言,正合下官心意。”李德裕捋捋胡子,微微一笑:“胡大人雅量高致,吾敢不奉陪?只是猜拳行乐,谁答不上来,该罚一碗,以增乐趣才是!”胡思进又朝两个幕僚䀹一䀹眼,“好!咱先来个颠倒令。我先念上句,李大人接下句。谁答不上来,甘心受罚!”李大人怕丈夫有个闪失,在众人面前露馅,连连对他使眼色。李德裕却当没看见,满口答应了。
虽是行令,胡思迎却要把气往上出,压得李德裕抬不起头。两只眼睛骨碌一转,心中有了,便润了润喉咙,高声念道,“大也小,傍山落日哀垂暮。”那意思是,你李德裕哪怕是个庞然大物,如今也变“小”了,真正是日薄西山,危在旦夕。李德裕瞧他那个得意劲儿,明白他又含沙射影,怒气勃然而生。你要朝李某头上拉屎,吾岂饶你?大丈夫死则死矣,绝不受此窝囊气。不过,他绝无弩拔弓张之态,只是在对答里寸步不让:“小似大,草间蟋蟀鸣破天。”你胡某一个小小蟋蟀也要自鸣得意,太不自量了!
一个幕僚眼看胡思进托住下巴,连忙念,“有似无,仙子飘游太空处。”李德裕略加思索念道,“无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
另一个幕僚不甘落后,抢着念,“易似难,执手临分话别间”。李德裕一拱手,“嗖”地站起,“难似易,一腔热血酬知己。”
瘦马拉车牛帮力。两个幕僚帮了忙,唱了几个回合,到底赢不了李德裕。只好停了颠倒令。刘松斟了满满一碗,径直递到胡思进面前。胡思进本来要出李德裕的丑,不想屎却拉到头上来,真是哑子吃黄连。可他颇有腹量,接过酒碗还笑道,“李大人瞧得起胡某!多谢李大人!”说罢,一饮而尽。
“李大人,再来花鸟虫鱼令。吾先念一句令名,大人就说出崖州一件物名。请吧!”胡思进挟起熊掌往嘴里送,边吃边说。
“吾初到崖州,不谙人情风物。胡大人,你岂不让李某出丑?”李德裕佯作推辞的样子。
“哎,李大人博学多才,区区酒令何足挂齿?”胡思进也不管李德裕是否答应,便念了一句令名:“花开百日不见红。”
“是百里红吧。”李德裕带着拿不准的口气。
“花到老来越妖烧!”胡思进接声而起,不让李德裕喘过气来。
“老来红!”李德裕也脱口而出。
“摇摇摆摆过山来”眼看胡思进卡壳,花白胡子幕僚连忙接应。
“过山龙!”李德裕思讨一会。
“周甲子开花!”花白胡子以为李德裕江郎才尽,又喊了一句令名。
李德裕猜了几件物名,都没有猜中。
“是铁树!李大人,你也该输一回,礼尚往来嘛!”胡思进颇为得意,李德裕甘心罚了
其实,这一回李德裕故意装糊涂。一来,输了免得胡思进耿耿于怀;二来,也免得众人生疑;李德裕乍来崖州,怎会对崖州一切了如指掌?这还了得!
胡思进被瞒过了。他正暗自得意,忽见手下人进来,在身边嘀咕什么,这才出到大厅外面。
“大人,吉阳县送来的礼单!”来人毕敬毕恭地递上一张红帖。
胡思进两话不说,接过红帖便看,上面一项一项写着:
白米十石 鱿鱼二百斤
牛 十头 猪二十头
槟榔三千只 椰子一千个
胡思进把礼单掷在地上,扬长口气,“吉阳县令,你好大的胆子!”
“来人说,县令择日再把其余礼物送来!”手下人小心翼翼的样子。
“我还以为他长两颗恼袋呢!”胡思进愤愤不平,“他误了日期,又打了折扣,这不是要让李参军喝海水?你去对来人说,黎锦、鹿茸限3天内送来,一尺不能短,一两不能少!”
胡思进余怒未消,回到大厅时,还掩饰不住内心的不悦。
“大人,咱们哼几句崖州土歌,聊庆今日之喜,如何?”花白胡子幕僚讨好地问。
“好嘛,好嘛!”胡思进心不在焉地应道。
花白胡子清清嗓子,唱了起来:
今旦逢光辉盛景,
州府里集众官绅。
全仰刺史大人福,
日丽风和颂太平。
花白胡子用黄流话唱,李德裕听不懂,却饶有兴味地品味那咿咿呀呀的腔调。胡思进忽然借花献佛,一边学唱,一边给李德裕解释,“李大人,崖州百胜仰望你有如百川归海,痛骂奸人天理难容!”
听到“百姓”两字,李德裕动情了。他依稀见到阴风呼呼,长安城街道上石人石马也冷着面孔。他孤家寡人般的走在大街。旧时三千门客哪里去了?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语,只有那沉重的靴声,在朔风中叩打着揪心的凄楚。然而,在长安城外,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携儿带女,荷箪端浆,跪在道路两旁,为他送行,为他祈福:一声声保重,一声声地平安……李德裕哭了,一个堂堂的大唐丞相哭了,哭得热泪盈眶,哭个悔恨不止:“我李德裕有何功德,值得百姓同情?天呀!我枉为百姓父母官呀!”这一场景恍然现在眼前,李德裕眼眶润湿,颤抖地捧起酒碗,对着众人,对着上下四方,”皇天在上:我李德裕敬百姓一杯,敬崖州百姓一杯!”
“胡某代崖州百姓领了大人美意,饮了这碗酒吧!”胡思进伸过手去,捧着碗一饮而尽。
李德裕刚好坐下,胡思进突然又捧起酒杯,“李大人,胡思进代崖州百姓敬你一杯!”
李德裕本不胜酒量,可胡思进一而再再而三地敬酒,幕僚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摇唇鼓舌,尽管李大人、李茂光、刘松一齐挡驾,也无济于事。本来,李德裕亲临过无数官庭宴会,仙泉玉液何尝不品味个够?然而,当此“四十年来车马客,无人相送到崖州”的落魄之时,李德裕正需要那水火相融的液体,来把胸中郁积的压抑、愤懑,化作清风,散为轻烟,好乐得一身自在。更何况,胡思进嘴里“百姓”两个 字,万般诱惑着他。因此,他不禁贪欲了几杯。
猛然,李德裕只觉得一股热腾腾的气流,仿佛脱缰的野马,在心里横冲直撞,在天灵盖上闹了个晴天霹雳。面前的大厅、酒席、人,都搅混在一起。自己也迷迷糊糊的,随着搅混了的一切旋转。
胡思进本有海量,就是泡在酒缸里,他也清清爽爽。可是,李德裕喝醉时,他也“啪”地摔了酒杯,踉踉跄跄离开开座位,三步趔趄,五步栽葱,手舞足蹈地嚷,“我没一醉,再干——三百杯,谁欺——欺负——李大人,我—我—决不—饶—饶他!”
一句话,火上添油。刹那间,李德裕双眼闪烁电光,闪出漫天烈火,发抖的双手如掣剑,往四面八方劈,“谁—敢敢欺欺负我?老夫—就就劈谁!江山都运—运在咱掌心里, 白—白敏中—好大胆—在皇上耳边—吹吹风—老夫—劈—劈—”说罢,,大笑不止。
“佩服,佩—佩服!”胡思进仰头大笑,“胡大人—天上—文曲星—快拿笔—李大人一题诗—”
李夫人扶住丈夫坐定,用清水擦了擦他。李德裕酒醒了。乘着酒兴,他龙飞蛇舞题下一首五绝,抒发内心的感慨:
一去一万里,
千之千不还。
崖州在何处?
生度鬼门关。
“领教,领教了!”胡思进那样子也醒酒了,其实,他根本没醉。他边说,边拿过诗稿。嘿,好一个“生度鬼门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治下的崖州,竟是鬼门关!死罪临头,你这不知死罪的李德裕!胡思进心里狂笑不止,可他脸上堆满笑容,眯住眼睛赞不绝口,“李大人,好诗!诗以言志嘛”。
一个喜不自禁,另一个却懊恼不已。虽说酒后失言,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吐出来倒也痛快,自己是死是活也不要紧。但连累一家老小,白白坏了一世功名,便宜了那帮小人,这岂不冤哉枉也?李德裕越想,越坐立不安,不觉对胡思进及众官绅拱手谢罪,“刚才老夫贪杯,一时妄言,诸位可别见怪。吾载罪于身,蒙朝庭大恩大德,授予司户参军之职,一定效犬马之劳。臣作牛作马,以报答皇上荡荡圣恩”!
此时,胡思进袖袍里揣着李德裕诗稿,仿佛揣着一张催命符,哪里听得进李德裕的一番话?大肠小肠里虽填饱了膏油,胡思进还是挟起盘里一只虎蟹。虎蟹满身虎斑,乃蟹中大王。它虽然成了盘中之物,两只大的螯张着,还虎虎有生气。胡思进把螫狠狠折了,狂笑不止,“看你还神气不神气”?
“胡大人,吾告辞了!”李德裕拱手道谢,“诸位,吾告辞了”!
“恕不远送!”胡思进欠身说。比起开宴时,他的热度大大降温了。
时已中午。锣鼓手早撤兵了,太阳躲在乌云里,懒懒散散,不肯露面。一阵冷风刮来,撩起李德裕的袍角。他不由说:好大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