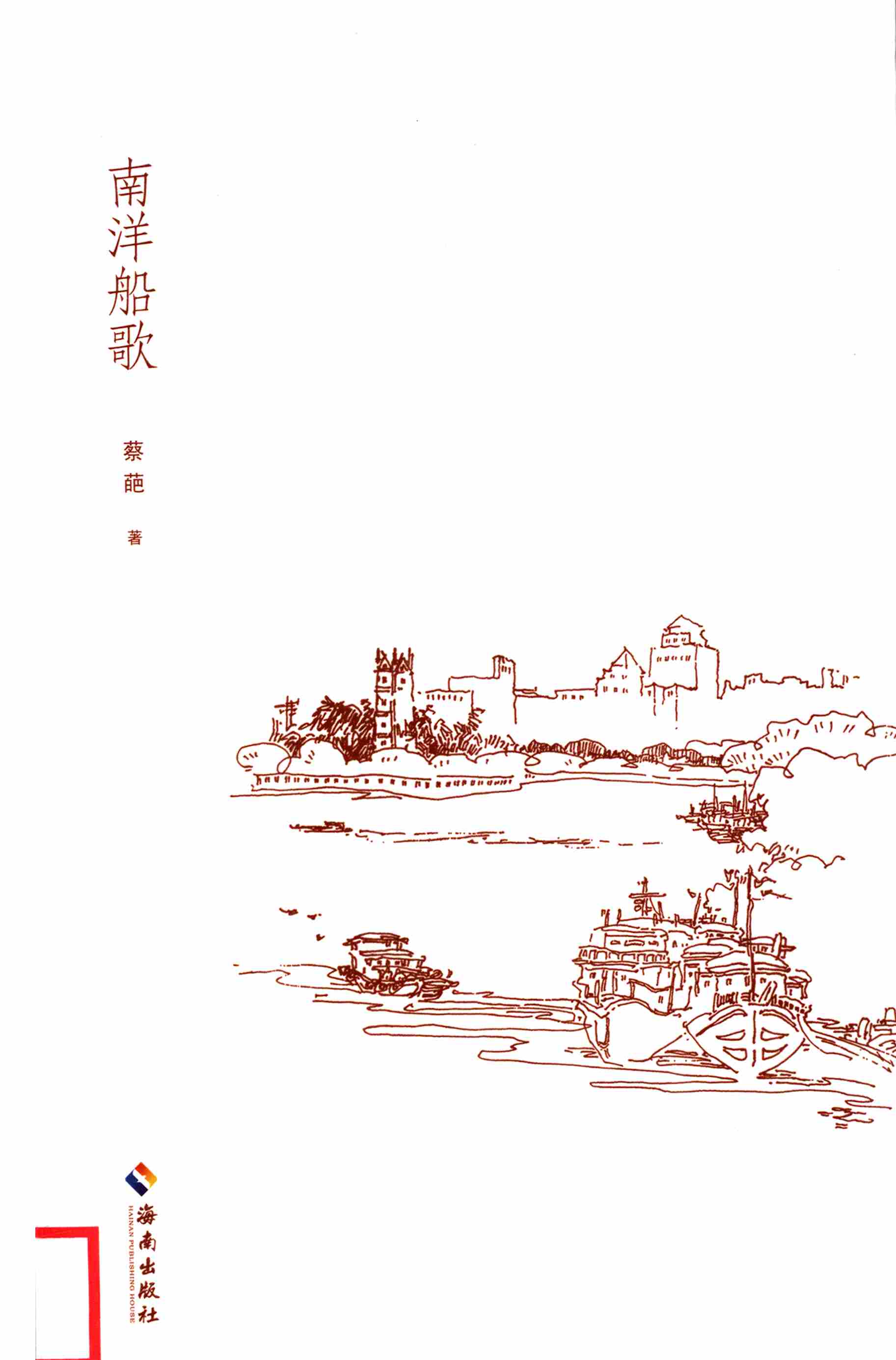1947,归去来兮
| 内容出处: | 《南洋船歌》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2256 |
| 颗粒名称: | 1947,归去来兮 |
| 分类号: | K820.8 |
| 页数: | 18 |
| 页码: | 283-30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抗战爆发之际韩步青将军与抗日名将孙立人等人的合影。寻觅到这张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时,相片中的文昌籍将军韩步青已经离世半个多世纪。照片中的他们正当青春年华,年轻的脸庞上坚毅的表情,果敢的目光,在那个随时可能会战死沙场的硝烟弥漫的时代显得如此无所畏惧,义无反顾。2015年底,韩步青将军的亲人从香港、广州等地回到老家文昌,为将军远去的灵魂祈祷平安。笔者经林鸿顺先生(“末代格格”恒容的儿子)的引荐,结识了韩步青之子韩传雄、韩传俊兄弟。韩氏兄弟均已年逾八十高龄,手足情深。他们饱含感情的叙述和书写的手记让我久久深陷其中,就此开始了一段令人感慨唏嘘的口述实录。 |
| 关键词: | 1947 归去来兮 合影 |
内容
这是抗战爆发之际韩步青将军与抗日名将孙立人等人的合影。寻觅到这张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时,相片中的文昌籍将军韩步青已经离世半个多世纪。照片中的他们正当青春年华,年轻的脸庞上坚毅的表情、果敢的目光,在那个随时可能会战死沙场的硝烟弥漫的时代显得如此无所畏惧、义无反顾。2015年底,韩步青将军的亲人从香港、广州等地回到老家文昌,为将军远去的灵魂祈祷平安。笔者经林鸿顺先生(“末代格格”恒容的儿子)的引荐,结识了韩步青之子韩传雄、韩传俊兄弟。韩氏兄弟均已年逾八旬,手足情深。他们饱含感情的叙述和书写的手记让我久久深陷其中,就此开始了一段令人感慨唏嘘的口述实录。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方面声称将采取自卫手段保护日侨利益。1932年1月28日,日军海军陆战队的2300人在坦克的掩护下,沿上海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终于爆发。
时任国民党税警团团长的韩步青(原名韩源、韩坚)参加了这次战争。将军的二儿子韩传雄讲述:“由于税警团驻地靠近海港,因此成为击退日寇从海上抢滩登陆的最前沿阵地。税警团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缉私,并没有炮兵和高射炮等设备。因此日寇的飞机和排炮的狂轰滥炸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然而,他们一直坚守阵地,直至接到转移阵地的命令时才撤出。在反击日寇的抢滩登陆中,日寇大量伤亡,尸横遍野。”
在淞沪抗战中,韩步青团长身上多处受伤,仍坚持领导作战。战争中有一颗子弹,打中了他靠近心脏的位置,他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然而竟没有伤着,这简直是奇迹!对此,将军三子韩传俊说,这其中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淞沪抗战爆发几天前,父亲在上海街头遇见一个身穿破烂衣服的老妇,她手中拿着一块光洋,哭着、骂着,说是买米时有人把她骗了,把她的真银元换成了这个假银元,她的全家人无法活下去了……手头并不阔绰的父亲停下脚步,对她说:“大嫂,莫哭,让我看看!”
父亲迅即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真银元给她,说:“莫哭,莫哭!这可是真的呢!”
老妇人并没发觉父亲的“调包”,他把那枚假银元放进左边的衣袋中。没想到,几天后在激烈的战场上,正是这一枚假银元救了父亲的命!
“那一枚假银元,被日寇的子弹打得全凹了,它正好护住了父亲的胸膛,让父亲躲过了一劫!这件事成为军中的佳话。当人们问起这件事,父亲总是腼腆地说,他在中山先生身边任警卫连长时,常听中山先生‘与人为善’‘好心得好报’的教导,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验证而已。”由于韩步青团长英勇作战,身先士卒,表现突出,上级为表彰他的战功,在战后将他擢升为少将参谋长,威名一时。
1892年韩步青出生于文昌市昌洒镇昌述村,少时在家乡读书,17岁毕业于广东省六师(即琼台师范)。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年代,刚从六师毕业的韩步青负笈赴滇,考取了云南省陆军讲武堂,学习三年后毕业。风华正茂的韩步青毕业后回到广州粤军中服役,由于文武双全,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先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团排长、连长,追随孙中山革命(见《文昌文史》)。1932年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已经是财政部税警团团长了。
1939年,广东战云密布,日寇侵占了广东大部分的县,剩下的10余个山区县也岌岌可危。为了抗击日寇,保卫国土,保障军队供给,韩步青临危受命,先后到南雄、广宁当了5年县长。特别是在广宁的4年中,他积极动员、训练、调遣县保安团和民众武装扼守进入广宁的陆路和水道的多个防守要点,几年来多次击退日寇和伪武装的进攻,保卫了广宁,保障抗日部队的粮食供给,直至抗战胜利。
据韩步青的三儿子韩传俊回忆,广宁是一个山区县,处处崇山峻岭,山多田少。当地的竹子多,竹子产量冠全省,俗语有云:“广宁竹,怀集木。”全县大部分农民将出产的竹子,一船一船运往广州售卖,再从广州运回粮食。自从日寇入侵广州后,竹子运不出去,没有粮食,广宁很快就出现了全县性粮荒。身为县长的父亲当机立断,发动、组织农民开荒种粮,将部分竹山改为粮山,农民们出尽了力气,把那些生长了多年盘根错节的竹丛一个个挖起,种上了木茨,这才解决了全县性的粮荒问题,还有力支持了抗战前方。
在广宁县,至今仍传诵着韩步青施粥济民的故事。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大量饥民涌入广宁县城。那段日子,韩步青组织发动各个商家和团体,给一批批流落街头的饥民施粥,调集粮食,整个县城都沸腾了。韩将军的夫人廖宝珍也亲身参与县妇救会的施粥活动。粮荒解除了,老百姓的口粮和军粮不足的问题随之解决,韩将军的美名不胫而走,在岭南地区影响一时。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宣告胜利!那举国欢腾、盼望过上安定日子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经过多年战乱,每一个幸存者最基本的要求不过是有一处休养生息的地方。那一年,韩家从广宁县的山旮旯出来了。他们一家人分乘几艘小船摇摇晃晃地来到了西江之畔的四会县。那是一座热闹的城市,抗战胜利之后,人们压抑很久的情绪得到释放,连鱼市里的叫卖声也是久违的喧嚣和响亮。抗战胜利了,多少人做着回归田园、回归平静生活的美梦。韩传俊回忆道:“我记得那时有一个叫作陈乡长的来过家里。他一来,就拉着我们一家子到附近的一间大酒楼吃饭,席间一再感谢父亲的提携,滔滔不绝地介绍说在四会县城附近有好大一片橄榄树林,主人要到广州经商,打算卖掉这一片林子。他说:‘这可是一片收入可观的林子呢!’最使妈妈感兴趣的,就是那片林子的主人竟然是陈乡长的表哥!妈妈想着那片林子的价钱可以压得低一些。”
“打从那天以后,爸爸和妈妈都变了。妈妈整天乐滋滋的,期望着几天后去看一看那一片林子,那是一个可以结束10多年漂泊、可以使一家人安居乐业的地方!而爸爸却变得沉默寡言,整天若有所思的样子。这天下午,爸爸带着我们三兄弟到滨河路散步,走着走着,爸爸会突然停下来,望着那滚滚东去的西江水,好像在思索什么。忽然我听到爸爸口中念念有词,而且反复地念着,经过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爸爸当时念的是王维的《送别》诗: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他矛盾、彷徨,想到过归隐故乡海南。但是,他戎马半生,一生得意,官至少将,做了多年的县长,他能放得下吗?
“几天后,陈乡长又来了。爸妈带着我们三兄弟,跟着陈乡长到码头上了船。这是一艘有篷的小船,一个壮汉摇着橹,咿咿呀呀,摇摇晃晃的,约莫半个钟头光景,我们便渡过了洪流滚滚的西江,上岸后,再步行约半个钟头,便到了陈乡长所说的那一片橄榄林了。
“偌大的一片树林,一望无际,每棵树都很大,一个大人刚好可以合抱得过。树林郁郁葱葱,树叶遮天蔽日。走了一阵,到了树林中间,竟然出现一大片碧绿碧绿的青草地,一下子令人豁然开朗。草地开满了许多紫色的、黄色的小花,草地的缓缓斜坡下,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溪底下有一些漂亮的卵石。溪水潺潺,流向奔腾不息的西江。树上飞鸟在歌唱,秋虫在雨后吱吱和鸣。哎呀,好一幅世外桃源的光景啊!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我们,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震住了。
“我和二哥一下子便认出那开着五瓣紫花的是酢浆草,那草根下面都藏着一个小小的萝苩,甜甜的,很好吃,我们在学校的草地里就挖来吃过。于是,我和二哥迫不及待地找了一根木棍挖了起来。这时,大概是上午11点了吧,十月的太阳也蛮炙热的,我们挖了一阵,就已经汗流浃背了。我们将那些比小指头还要小的萝苩,拿到小河里去洗。我数了一下,我一共挖了11个,而二哥挖了18个。他把其中比较大的10颗给了我,我们吃着觉得甜极了。我拿了几颗给大哥,他笑了笑,说不吃,拿给妈,妈也不吃。妈和大哥都在专注地听着陈乡长对那片橄榄林果子产量和产值的预测,生怕漏掉一个字,哪里顾得上吃东西!妈妈兴奋极了,她指着小河边的一块平地说:‘这是建屋的好地方!晒场、仓库、菜地、鸡场、水井……’她喜不自胜地描画着,一切都似乎胸有成竹。妈妈是出身贫苦的人,她厌倦了这10多年来不断搬迁的生活,从上海到江西,到江苏海州,广西南宁,广东南雄、广宁、四会再到即将要去的广州。其实她并不祈求大富大贵,只是希望能够安居乐业,将孩子抚养长大罢了。
“父亲一言不发。他在想着什么呢?他有时看着妈妈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样子,也会笑一笑,但还是能从他眼中看出忧虑。
“到了12点钟的时候,我们才再次乘上来时搭乘的摇船,咿咿呀呀,摇摇晃晃地摇回了四会。
“一连几天,爸爸和妈妈总在争论着什么,有时还听见妈妈低声地啜泣。有一晚,我听见爸爸大声地说道:‘你知道这世间有多险恶吗?你能应付得了那一帮一帮的恶霸地痞流氓吗?陈乡长在广宁当乡长,他的手能有多长呢?虽说他能保护我们一时,又能保护我们一世吗?算了,我们还是走吧!’爸爸身经百战,深知‘来龙不及地虎,来路汉不及地头蛇’的道理。他的果敢和判断,不容置疑。我的妈妈,也只能收回她的梦想了。那一片绿油油的橄榄林,就永远留我们的梦里。
“我知道,我们又要走了。晚上,我梦见那一片美丽的树林和草地,我还梦见那潺潺小溪忽然变大了,我和二哥竟然可以在那里游来游去……
“我1935年出生,那一年我才10岁,尽管67年过去了,这些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回想起来,感慨万千!那是一个容不得你有梦想的时代。过了两年,我们只能选择回乡了。
“我们知道,爸爸是个有故乡的人,而我们没有。我们在异乡的战火中诞生,一路跟随爸爸行军作战,四海为家已经是我们的常态了。1947年秋天,爸爸带着我们回到他阔别多年的家乡海南,首站是热带风情浓郁的海口。那是一座南国的滨海之城,在靠近海的地方,有一条得胜沙路,那是海外归客云集的地方。那儿有一座白色的海关大楼,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建筑物算得上是宏伟、气派的了。我所怀念的并不是这一座古老的建筑,而是它后面那一片绿茵茵的草地,那草地上有几棵很大的凤凰树,一到夏天树冠总会开满红彤彤的鲜花,像火海一样。几十年了,每当我经过那个地方,那青草地,那高大的凤凰树,总能勾起我一丝淡淡的记忆……
“1947年对于我们全家而言,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年份。这一年,我读到一位名叫天尔的海南人写的一篇《琼崖散忆》,他说了好多个爱海口的理由,现在读来依然叫我怦然心动。他说:‘我爱海口,就是因为它的城野不分明。说它是乡村,其实是海南岛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说它是城市,却随处可以看见青青的田野,绿绿的树林。如果我要调剂一下太紧张的生活,也有公园、泳场、戏院、音乐等场所,由我去优游娱乐;如果我要发奋,尽管闭户读书,也不会有什么外来的干扰。’
“抗战胜利后两年了,海口街面有了一种平和寂静的气氛。街上已经没有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军,见到更多的是来自各地的国民党接收部队和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的男生女生。没有回到海口之前,听人们说海南文化落后,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海口全市面积不过方圆五六里,战后人口不过6万,却有书店8家,报馆3家,印刷局7家,咖啡馆多家。街上男子西装革履,女子裙装飘逸,戴墨镜的女子竟开化到用黛绿染眼眶的地步。但因为私塾学校随处都有,最繁华的马路上尚行走着‘不改旧时装’的赤足女子。这是一个新旧混杂、土洋交互的年代。《琼崖散忆》这样记叙:
夕阳斜照时,衔着烟卷在马路上看‘新’‘旧’混杂的人物;更深人静后,独自在海口公园的木桥上踏着幽凉的月色漫步;空暇无事的星期日,偕三五朋友在海边河畔钓鱼;都是最富诗情画意的事,可以启发我的文思。何况海口的附近,还有五公祠,浮粟泉,东坡读书处,丘濬墓,海瑞墓……许多古迹,足供我去凭吊流连。
然而我爱海口还不止这些。海口的咖啡店,咖啡弄得很好,是广州、香港、上海、北平不及的,我每天都在那里流连约两个钟头,并且成为我谈笑和会客之所。又如乐园的‘加积鸭’和‘米粉’,奇珍的‘炸水饺’,大丰利咖啡店的‘夹心面包’,味道之甘美,是大家承认的,我当然不能例外。最使我口馋的,尤其是宵夜店的‘便炉’,中华餐室的‘夜粥’,富南楼的‘乳猪’,琼南酒店的‘汤面’和‘蛋散’。可惜‘乳猪’的价格昂贵,非三五元不得一尝其味,穷光蛋只好‘涎向肚里吞’了。
“夏季的海口,每天下午常来急雨,我们叫作‘对时雨’,几乎每天同一时刻会来那么一场,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带着凉爽的尾巴走了。即使是盛夏,有时热到使人不能呼吸,但忽来一阵急雨后,气候便像清爽的初秋一样。所以,传说中的海口因位居热带,气候炎热和实际情形是不相符的。我在内地城市饱受夏日的酷热,晚上热到无法入眠,街市上尽是纳凉的人们。回到海口,才感受到热带海岛的凉意。
“爸爸带我们回乡的那一年,我11岁,入读匹谨中学(即华美中学)初一。那时,我们家住在海口市振东街58号后面的小洋楼里。那座小洋楼坐落在小花园里,与前面的四进古老旧屋相比,显得鹤立鸡群。这些房子,是海口富商符森记的产业。此时的海南,历经7年抗战之后,商业不兴,正在慢慢恢复着元气。海南各界精英力图建设新海南而内外呼应,倾力合作,一时间,海南出现了一股南洋客回乡的热潮。1947年11月开学的私立海南大学,给海口带来了一股久违的朝气。从全国各地而来的学生,都以自己是海大学子为荣,尤其是在私立海南大学附中,那些从南洋各地回来的华人华侨子弟与当地学生汇聚一堂,吹拉弹唱,给战后的海南带来一股青春的气息。学生们无论仪表、言谈、行为都很讲究,他们的精神风貌,像一束强烈的阳光,一扫抗战以来的晦气。他们因为是被耽误了的一代,许多学生年龄超了,倍感时光的珍贵,因而勤奋读书,互相学习,爱师爱校,这便成了海大当年的风气。在私立海南大学设立的附属中学,也接纳了来自南洋与内地的学子。自小喜欢音乐与歌唱的我,1949年9月,便从匹谨中学转学到私立海南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三。置身于椰子岛的滨海校园,天天有读不完的书,唱不完的歌儿。那些从南洋归来的少年,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乐器,各种各样的南洋歌儿。年少的我怎知,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更迭将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怎样的命运?
“1950年5月,一个很普通的夜晚。街上好像听不见什么枪炮声,也听不见嘈杂的声音,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一觉醒来,打开大门一看,只见海口街上的骑楼里,东一堆、西一堆地站着或者坐着许许多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他们见了人,会微微地笑着。但,世界一下子改变了。
“那一天是5月1日。海口,解放了!
“这两天,我大着胆子,回到学校——私立海南大学附属中学,可校园的氛围已然不同。
“连日来,南京解放军文工团的团员来学校教学生们扭秧歌,跳腰鼓舞,还教学生唱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歌。很快,我学会了跳秧歌舞,那些新的歌,也会唱了。但是,我的心境并不欢快,我是矛盾的,父亲毕竟是国民党阵营的人物,在这样的历史变迁时刻,他的命运会如何呢?”
韩成俊陷入了深深的回忆。1950年4月,本可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韩步青连夜从三亚榆林港赶回文昌老家与妻儿相聚。就在家人祈祷他千万别回老家时,他却突然出现在村头。他许诺给妻儿一个田园梦,岂可抛弃他们独自离去?他撕掉了赴台的船票,连夜从三亚榆林港赶回,300多里路,跌跌撞撞,躲躲藏藏,回来见到妻儿,已经累得说不出一句话。
时间到了1950年底,韩步青得到共和国将军张云逸的口信,希望他到广西参事室当一名参事(见《文昌文史》),韩步青却坚持与家人待在海南,他认为自己的一生都在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参加过淞沪抗日战争,后来担任税警团团长、广东广宁县县长,官声颇好,是一个文官,对民众没有“血债”,他相信他是不会受到新时代“法办”的。回想1947年,他辞官回乡,携带妻儿回到故乡海南,原本是为了一个田园梦而回来的,他不想再远离故乡到他乡,因而婉拒了张云逸将军的邀请,决定与妻儿回到文昌老家,寄望终老家乡。与韩步青同为文昌籍的张云逸将军,深知韩步青的个人史,他清楚共产党对民主革命先驱者的历史尊重,他力主他到广西,为新政权服务。可是,韩步青执意要跟家人在一起,他无法预料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的猛烈。当他最后一次回望海口老街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那是他跟这个世界最后的道别……
60多年过去了,韩步青所做的田园梦,已经由他的孩子们替他实现了。他们在老家文昌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园。那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如今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者,岁月在他们心中,已经翻过沉重的一页。他的子孙与新中国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最终成为对新中国有贡献的人。二儿子韩传雄曾是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海南省委原副主委兼秘书长;三儿子韩传俊历经磨难之后成了海南省林业战线上的一名领导者。回望不是怀旧,而是寻找,寻找那个“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战火年代,人的家国情怀与在艰难时势下的命运,是那样的纷繁复杂、欲说还休……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方面声称将采取自卫手段保护日侨利益。1932年1月28日,日军海军陆战队的2300人在坦克的掩护下,沿上海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终于爆发。
时任国民党税警团团长的韩步青(原名韩源、韩坚)参加了这次战争。将军的二儿子韩传雄讲述:“由于税警团驻地靠近海港,因此成为击退日寇从海上抢滩登陆的最前沿阵地。税警团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缉私,并没有炮兵和高射炮等设备。因此日寇的飞机和排炮的狂轰滥炸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然而,他们一直坚守阵地,直至接到转移阵地的命令时才撤出。在反击日寇的抢滩登陆中,日寇大量伤亡,尸横遍野。”
在淞沪抗战中,韩步青团长身上多处受伤,仍坚持领导作战。战争中有一颗子弹,打中了他靠近心脏的位置,他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然而竟没有伤着,这简直是奇迹!对此,将军三子韩传俊说,这其中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淞沪抗战爆发几天前,父亲在上海街头遇见一个身穿破烂衣服的老妇,她手中拿着一块光洋,哭着、骂着,说是买米时有人把她骗了,把她的真银元换成了这个假银元,她的全家人无法活下去了……手头并不阔绰的父亲停下脚步,对她说:“大嫂,莫哭,让我看看!”
父亲迅即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真银元给她,说:“莫哭,莫哭!这可是真的呢!”
老妇人并没发觉父亲的“调包”,他把那枚假银元放进左边的衣袋中。没想到,几天后在激烈的战场上,正是这一枚假银元救了父亲的命!
“那一枚假银元,被日寇的子弹打得全凹了,它正好护住了父亲的胸膛,让父亲躲过了一劫!这件事成为军中的佳话。当人们问起这件事,父亲总是腼腆地说,他在中山先生身边任警卫连长时,常听中山先生‘与人为善’‘好心得好报’的教导,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验证而已。”由于韩步青团长英勇作战,身先士卒,表现突出,上级为表彰他的战功,在战后将他擢升为少将参谋长,威名一时。
1892年韩步青出生于文昌市昌洒镇昌述村,少时在家乡读书,17岁毕业于广东省六师(即琼台师范)。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年代,刚从六师毕业的韩步青负笈赴滇,考取了云南省陆军讲武堂,学习三年后毕业。风华正茂的韩步青毕业后回到广州粤军中服役,由于文武双全,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先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团排长、连长,追随孙中山革命(见《文昌文史》)。1932年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已经是财政部税警团团长了。
1939年,广东战云密布,日寇侵占了广东大部分的县,剩下的10余个山区县也岌岌可危。为了抗击日寇,保卫国土,保障军队供给,韩步青临危受命,先后到南雄、广宁当了5年县长。特别是在广宁的4年中,他积极动员、训练、调遣县保安团和民众武装扼守进入广宁的陆路和水道的多个防守要点,几年来多次击退日寇和伪武装的进攻,保卫了广宁,保障抗日部队的粮食供给,直至抗战胜利。
据韩步青的三儿子韩传俊回忆,广宁是一个山区县,处处崇山峻岭,山多田少。当地的竹子多,竹子产量冠全省,俗语有云:“广宁竹,怀集木。”全县大部分农民将出产的竹子,一船一船运往广州售卖,再从广州运回粮食。自从日寇入侵广州后,竹子运不出去,没有粮食,广宁很快就出现了全县性粮荒。身为县长的父亲当机立断,发动、组织农民开荒种粮,将部分竹山改为粮山,农民们出尽了力气,把那些生长了多年盘根错节的竹丛一个个挖起,种上了木茨,这才解决了全县性的粮荒问题,还有力支持了抗战前方。
在广宁县,至今仍传诵着韩步青施粥济民的故事。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大量饥民涌入广宁县城。那段日子,韩步青组织发动各个商家和团体,给一批批流落街头的饥民施粥,调集粮食,整个县城都沸腾了。韩将军的夫人廖宝珍也亲身参与县妇救会的施粥活动。粮荒解除了,老百姓的口粮和军粮不足的问题随之解决,韩将军的美名不胫而走,在岭南地区影响一时。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宣告胜利!那举国欢腾、盼望过上安定日子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经过多年战乱,每一个幸存者最基本的要求不过是有一处休养生息的地方。那一年,韩家从广宁县的山旮旯出来了。他们一家人分乘几艘小船摇摇晃晃地来到了西江之畔的四会县。那是一座热闹的城市,抗战胜利之后,人们压抑很久的情绪得到释放,连鱼市里的叫卖声也是久违的喧嚣和响亮。抗战胜利了,多少人做着回归田园、回归平静生活的美梦。韩传俊回忆道:“我记得那时有一个叫作陈乡长的来过家里。他一来,就拉着我们一家子到附近的一间大酒楼吃饭,席间一再感谢父亲的提携,滔滔不绝地介绍说在四会县城附近有好大一片橄榄树林,主人要到广州经商,打算卖掉这一片林子。他说:‘这可是一片收入可观的林子呢!’最使妈妈感兴趣的,就是那片林子的主人竟然是陈乡长的表哥!妈妈想着那片林子的价钱可以压得低一些。”
“打从那天以后,爸爸和妈妈都变了。妈妈整天乐滋滋的,期望着几天后去看一看那一片林子,那是一个可以结束10多年漂泊、可以使一家人安居乐业的地方!而爸爸却变得沉默寡言,整天若有所思的样子。这天下午,爸爸带着我们三兄弟到滨河路散步,走着走着,爸爸会突然停下来,望着那滚滚东去的西江水,好像在思索什么。忽然我听到爸爸口中念念有词,而且反复地念着,经过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爸爸当时念的是王维的《送别》诗: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他矛盾、彷徨,想到过归隐故乡海南。但是,他戎马半生,一生得意,官至少将,做了多年的县长,他能放得下吗?
“几天后,陈乡长又来了。爸妈带着我们三兄弟,跟着陈乡长到码头上了船。这是一艘有篷的小船,一个壮汉摇着橹,咿咿呀呀,摇摇晃晃的,约莫半个钟头光景,我们便渡过了洪流滚滚的西江,上岸后,再步行约半个钟头,便到了陈乡长所说的那一片橄榄林了。
“偌大的一片树林,一望无际,每棵树都很大,一个大人刚好可以合抱得过。树林郁郁葱葱,树叶遮天蔽日。走了一阵,到了树林中间,竟然出现一大片碧绿碧绿的青草地,一下子令人豁然开朗。草地开满了许多紫色的、黄色的小花,草地的缓缓斜坡下,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溪底下有一些漂亮的卵石。溪水潺潺,流向奔腾不息的西江。树上飞鸟在歌唱,秋虫在雨后吱吱和鸣。哎呀,好一幅世外桃源的光景啊!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我们,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震住了。
“我和二哥一下子便认出那开着五瓣紫花的是酢浆草,那草根下面都藏着一个小小的萝苩,甜甜的,很好吃,我们在学校的草地里就挖来吃过。于是,我和二哥迫不及待地找了一根木棍挖了起来。这时,大概是上午11点了吧,十月的太阳也蛮炙热的,我们挖了一阵,就已经汗流浃背了。我们将那些比小指头还要小的萝苩,拿到小河里去洗。我数了一下,我一共挖了11个,而二哥挖了18个。他把其中比较大的10颗给了我,我们吃着觉得甜极了。我拿了几颗给大哥,他笑了笑,说不吃,拿给妈,妈也不吃。妈和大哥都在专注地听着陈乡长对那片橄榄林果子产量和产值的预测,生怕漏掉一个字,哪里顾得上吃东西!妈妈兴奋极了,她指着小河边的一块平地说:‘这是建屋的好地方!晒场、仓库、菜地、鸡场、水井……’她喜不自胜地描画着,一切都似乎胸有成竹。妈妈是出身贫苦的人,她厌倦了这10多年来不断搬迁的生活,从上海到江西,到江苏海州,广西南宁,广东南雄、广宁、四会再到即将要去的广州。其实她并不祈求大富大贵,只是希望能够安居乐业,将孩子抚养长大罢了。
“父亲一言不发。他在想着什么呢?他有时看着妈妈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样子,也会笑一笑,但还是能从他眼中看出忧虑。
“到了12点钟的时候,我们才再次乘上来时搭乘的摇船,咿咿呀呀,摇摇晃晃地摇回了四会。
“一连几天,爸爸和妈妈总在争论着什么,有时还听见妈妈低声地啜泣。有一晚,我听见爸爸大声地说道:‘你知道这世间有多险恶吗?你能应付得了那一帮一帮的恶霸地痞流氓吗?陈乡长在广宁当乡长,他的手能有多长呢?虽说他能保护我们一时,又能保护我们一世吗?算了,我们还是走吧!’爸爸身经百战,深知‘来龙不及地虎,来路汉不及地头蛇’的道理。他的果敢和判断,不容置疑。我的妈妈,也只能收回她的梦想了。那一片绿油油的橄榄林,就永远留我们的梦里。
“我知道,我们又要走了。晚上,我梦见那一片美丽的树林和草地,我还梦见那潺潺小溪忽然变大了,我和二哥竟然可以在那里游来游去……
“我1935年出生,那一年我才10岁,尽管67年过去了,这些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回想起来,感慨万千!那是一个容不得你有梦想的时代。过了两年,我们只能选择回乡了。
“我们知道,爸爸是个有故乡的人,而我们没有。我们在异乡的战火中诞生,一路跟随爸爸行军作战,四海为家已经是我们的常态了。1947年秋天,爸爸带着我们回到他阔别多年的家乡海南,首站是热带风情浓郁的海口。那是一座南国的滨海之城,在靠近海的地方,有一条得胜沙路,那是海外归客云集的地方。那儿有一座白色的海关大楼,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建筑物算得上是宏伟、气派的了。我所怀念的并不是这一座古老的建筑,而是它后面那一片绿茵茵的草地,那草地上有几棵很大的凤凰树,一到夏天树冠总会开满红彤彤的鲜花,像火海一样。几十年了,每当我经过那个地方,那青草地,那高大的凤凰树,总能勾起我一丝淡淡的记忆……
“1947年对于我们全家而言,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年份。这一年,我读到一位名叫天尔的海南人写的一篇《琼崖散忆》,他说了好多个爱海口的理由,现在读来依然叫我怦然心动。他说:‘我爱海口,就是因为它的城野不分明。说它是乡村,其实是海南岛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说它是城市,却随处可以看见青青的田野,绿绿的树林。如果我要调剂一下太紧张的生活,也有公园、泳场、戏院、音乐等场所,由我去优游娱乐;如果我要发奋,尽管闭户读书,也不会有什么外来的干扰。’
“抗战胜利后两年了,海口街面有了一种平和寂静的气氛。街上已经没有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军,见到更多的是来自各地的国民党接收部队和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的男生女生。没有回到海口之前,听人们说海南文化落后,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海口全市面积不过方圆五六里,战后人口不过6万,却有书店8家,报馆3家,印刷局7家,咖啡馆多家。街上男子西装革履,女子裙装飘逸,戴墨镜的女子竟开化到用黛绿染眼眶的地步。但因为私塾学校随处都有,最繁华的马路上尚行走着‘不改旧时装’的赤足女子。这是一个新旧混杂、土洋交互的年代。《琼崖散忆》这样记叙:
夕阳斜照时,衔着烟卷在马路上看‘新’‘旧’混杂的人物;更深人静后,独自在海口公园的木桥上踏着幽凉的月色漫步;空暇无事的星期日,偕三五朋友在海边河畔钓鱼;都是最富诗情画意的事,可以启发我的文思。何况海口的附近,还有五公祠,浮粟泉,东坡读书处,丘濬墓,海瑞墓……许多古迹,足供我去凭吊流连。
然而我爱海口还不止这些。海口的咖啡店,咖啡弄得很好,是广州、香港、上海、北平不及的,我每天都在那里流连约两个钟头,并且成为我谈笑和会客之所。又如乐园的‘加积鸭’和‘米粉’,奇珍的‘炸水饺’,大丰利咖啡店的‘夹心面包’,味道之甘美,是大家承认的,我当然不能例外。最使我口馋的,尤其是宵夜店的‘便炉’,中华餐室的‘夜粥’,富南楼的‘乳猪’,琼南酒店的‘汤面’和‘蛋散’。可惜‘乳猪’的价格昂贵,非三五元不得一尝其味,穷光蛋只好‘涎向肚里吞’了。
“夏季的海口,每天下午常来急雨,我们叫作‘对时雨’,几乎每天同一时刻会来那么一场,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带着凉爽的尾巴走了。即使是盛夏,有时热到使人不能呼吸,但忽来一阵急雨后,气候便像清爽的初秋一样。所以,传说中的海口因位居热带,气候炎热和实际情形是不相符的。我在内地城市饱受夏日的酷热,晚上热到无法入眠,街市上尽是纳凉的人们。回到海口,才感受到热带海岛的凉意。
“爸爸带我们回乡的那一年,我11岁,入读匹谨中学(即华美中学)初一。那时,我们家住在海口市振东街58号后面的小洋楼里。那座小洋楼坐落在小花园里,与前面的四进古老旧屋相比,显得鹤立鸡群。这些房子,是海口富商符森记的产业。此时的海南,历经7年抗战之后,商业不兴,正在慢慢恢复着元气。海南各界精英力图建设新海南而内外呼应,倾力合作,一时间,海南出现了一股南洋客回乡的热潮。1947年11月开学的私立海南大学,给海口带来了一股久违的朝气。从全国各地而来的学生,都以自己是海大学子为荣,尤其是在私立海南大学附中,那些从南洋各地回来的华人华侨子弟与当地学生汇聚一堂,吹拉弹唱,给战后的海南带来一股青春的气息。学生们无论仪表、言谈、行为都很讲究,他们的精神风貌,像一束强烈的阳光,一扫抗战以来的晦气。他们因为是被耽误了的一代,许多学生年龄超了,倍感时光的珍贵,因而勤奋读书,互相学习,爱师爱校,这便成了海大当年的风气。在私立海南大学设立的附属中学,也接纳了来自南洋与内地的学子。自小喜欢音乐与歌唱的我,1949年9月,便从匹谨中学转学到私立海南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三。置身于椰子岛的滨海校园,天天有读不完的书,唱不完的歌儿。那些从南洋归来的少年,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乐器,各种各样的南洋歌儿。年少的我怎知,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更迭将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怎样的命运?
“1950年5月,一个很普通的夜晚。街上好像听不见什么枪炮声,也听不见嘈杂的声音,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一觉醒来,打开大门一看,只见海口街上的骑楼里,东一堆、西一堆地站着或者坐着许许多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他们见了人,会微微地笑着。但,世界一下子改变了。
“那一天是5月1日。海口,解放了!
“这两天,我大着胆子,回到学校——私立海南大学附属中学,可校园的氛围已然不同。
“连日来,南京解放军文工团的团员来学校教学生们扭秧歌,跳腰鼓舞,还教学生唱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歌。很快,我学会了跳秧歌舞,那些新的歌,也会唱了。但是,我的心境并不欢快,我是矛盾的,父亲毕竟是国民党阵营的人物,在这样的历史变迁时刻,他的命运会如何呢?”
韩成俊陷入了深深的回忆。1950年4月,本可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韩步青连夜从三亚榆林港赶回文昌老家与妻儿相聚。就在家人祈祷他千万别回老家时,他却突然出现在村头。他许诺给妻儿一个田园梦,岂可抛弃他们独自离去?他撕掉了赴台的船票,连夜从三亚榆林港赶回,300多里路,跌跌撞撞,躲躲藏藏,回来见到妻儿,已经累得说不出一句话。
时间到了1950年底,韩步青得到共和国将军张云逸的口信,希望他到广西参事室当一名参事(见《文昌文史》),韩步青却坚持与家人待在海南,他认为自己的一生都在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参加过淞沪抗日战争,后来担任税警团团长、广东广宁县县长,官声颇好,是一个文官,对民众没有“血债”,他相信他是不会受到新时代“法办”的。回想1947年,他辞官回乡,携带妻儿回到故乡海南,原本是为了一个田园梦而回来的,他不想再远离故乡到他乡,因而婉拒了张云逸将军的邀请,决定与妻儿回到文昌老家,寄望终老家乡。与韩步青同为文昌籍的张云逸将军,深知韩步青的个人史,他清楚共产党对民主革命先驱者的历史尊重,他力主他到广西,为新政权服务。可是,韩步青执意要跟家人在一起,他无法预料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的猛烈。当他最后一次回望海口老街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那是他跟这个世界最后的道别……
60多年过去了,韩步青所做的田园梦,已经由他的孩子们替他实现了。他们在老家文昌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园。那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如今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者,岁月在他们心中,已经翻过沉重的一页。他的子孙与新中国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最终成为对新中国有贡献的人。二儿子韩传雄曾是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海南省委原副主委兼秘书长;三儿子韩传俊历经磨难之后成了海南省林业战线上的一名领导者。回望不是怀旧,而是寻找,寻找那个“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战火年代,人的家国情怀与在艰难时势下的命运,是那样的纷繁复杂、欲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