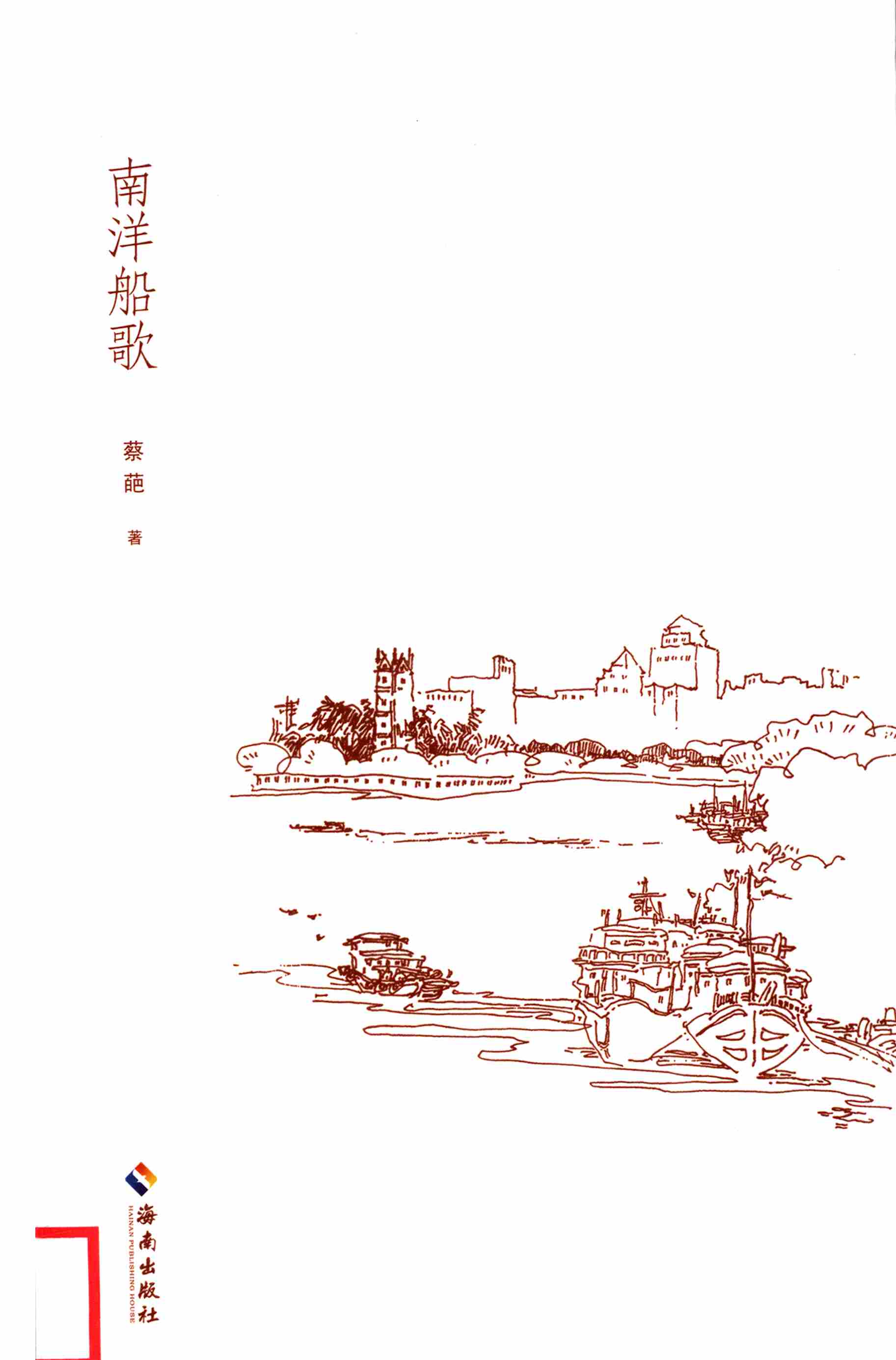内容
1998年11月3日,西安交通大学原副书记兼副校长的琼籍学者林施均在古城西安度过他的80岁寿辰。这天,他接到一份情义深长的电报:“尊敬的林施均书记:正值您八十大寿的大喜日子,海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特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海南大学,这块您曾辛勤耕耘和播种过的热土,‘过去是大海,现在是海大’,在昔日荒凉的滩涂上,已矗立起一所完备的综合性大学。作为学校的第一任党委书记,您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为海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您的光辉业绩、卓越智慧和艰苦奋斗的风范永远是海大开拓进取的精神财富……”
在儿孙和亲朋好友的簇拥中度过生日的林老对着刚来的电报,神情喜悦,心里为之大感快慰。是啊,这可是他晚年最值得书写的一笔了。林老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抗大,中间只有1950年间回过老家文昌,此外的日子都在内地任职,直到1983年海南大学创办,他才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当年,海南行政区在全国范围内物色合适的人选担当起创办海大这个历史重任。筹备小组在全国考察一圈后,林施均终于以其深厚的资力、丰富的办学经验和敢于开拓事业的精神,尤其是为故乡奉献才智的雄心,成为创办海大的首要人选。这一年,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1918年11月3日,林施均出生在海南文昌。他出生时,父亲已在广西北海、越南一带做生意,家境富裕。兄妹四人,他排行老二。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出生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注定着要过一种动荡的充满着艰难选择的生活。1933年,林施均随父亲来到广西,在北海中学(原合浦一中)读书。这是林施均初到北海时在相馆里的留影(见P218左下图)。他眉目清秀,紧抿着嘴唇,梳妆齐整地面对镜头。也许这张照片带给他从未有过的感动,这位聪敏的少年学着当时时髦的做法,在相片后面留下了一首自题诗:“昨天是我兮,今天是我兮,明天还是我兮,永远是我的形态兮。”如果这算是一个少年人因出于对生命、对时光有朦胧感悟而写成的诗句的话,那么,这位曾在中国诗坛活跃过的诗人,从那个时候起,就喜欢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直至用诗歌来当作武器,就该有些年头了。
2003年11月,海南大学举行建校20周年庆典,林施均作为该校的开创者之一,被海大请回参加庆典活动。我有幸在海口见到这位依旧风度翩然、气质优雅的老诗人、老革命家,他的身旁,是那位在革命队伍中有才女之名的夫人段克强女士。现在,战争的岁月已然远去,这位曾充满豪情的老革命家身上透出的更多是诗人的儒雅和敏感,他与老友谈得更多的还是他挚爱了一辈子的诗歌。他送给我一本他新近出版的诗集叫《岁月情深》,他的诗歌不仅流溢出壮怀激烈的豪情,也有活力四射、温情脉脉的情愫在荡漾。比如那首《今年的夏天》,清淡的几笔,似是信手拈来,读来却是情意浓郁,让人涌起一种莫名的乡愁:“今年的夏天/岛上的菠罗蜜/熟得很早/其中有一个属于我//今年夏天/林中的养鸡场/发展很多/其中有一个/属于我的亲人。”而他在70多岁高龄写的那首《《五月的家园》更是婉约清丽,看不出诗的作者已经是一名年逾古稀的老人:“流动与闪烁的/五月的家园/颜色随意/勾画潇洒线条//抑扬与顿挫的/五月的家园/跃动枝头/一只会唱的画眉……”
诗集里还有很多韵律优美且充满着生命活力的诗句,有一些是他早期充满着激情、同情底层的诗篇。1936年秋林施均到广州读高中,那正是抗日运动的高潮期,凡有血性的青年都不会苟全性命,躲在时代的洪流后面。林施均参加了“广州艺术界抗敌协会”诗歌组活动,接受新诗歌大众化的进步思想,是《广州诗坛》的第一批参加者。1937年2月,他写了一首有关清洁工人的诗《倒马桶之歌》以及一系列反映社会生活内容的诗,在广州诗坛有了自己的声誉。然而,那不是一个能够以优美的诗歌来愉悦自己、试图留下文名的时代。1938年林施均20岁,抗日救亡的歌曲在呼唤着他,青纱帐、甘蔗林在召唤着他,他已顾不得父亲为他做的继续求学的安排,他就读于中山大学的大哥也希望自己这位悟性很高的弟弟能够完成大学学业,但是,看起来很文雅、性格温和甚至有些柔弱的弟弟,去意竟如此的决绝。从广州到延安,这一路上该如何走,父亲和哥哥难以设想,以为那一走几乎是生死离别,父亲对这位充满救世情怀的孩子投以眷恋而绝望的目光,默默送其远走。
这位南国诗坛的活跃分子带着他的诗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与他结伴的是几位热血青年。沿途的艰难与危险不言而喻,但他们终于在4月到达了延安。这位斯文温润、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诗人,被安排进“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学习,期满结束,他学业优秀,被留校当教员。当年在延安的有几位海南老乡,而林施均以标准的普通话、较高的理论水平而备受老乡和战友们的尊敬。在后来的日子里,谦逊的林施均从来不会跟别人炫耀他的这些经历。他在延河边驰骋,在宝塔山下操练,聆听第一代领袖们的宣言和演讲。亲历了延安时期主要的运动,他看到了壮烈,也看到斗争的残酷,但,他从未放弃对美好理想信念的追求。
1938年几乎同一个时间,在河南滑县城关西门里,一位叫段克强的女孩被迫离开家园,参加抗日救国宣传队工作。她开明的父亲让她读当地的女子师范学校,这在当时当地可是稀奇事。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让她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家园,她的求学理想和一个女孩子的美好梦想全部化为乌有。
在遇见林施均之前,队伍中曾有女友问她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人,耿直而浪漫的段克强不加思索地冲口而出:“不漂亮的我可不要!”当时引来姐妹们的哄然大笑。说这话时她没有想到远方真有一位潇洒的男子在等着她,也没有想到日后她会随着他来到海南岛,将人生最后漂亮的一笔写在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上。
1983年5月,阔别家乡30多年的林施均和老伴段克强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受到海南区党委的热情欢迎。时任西安交通大学副书记兼副校长的林施均,以儒雅又干练的行事作风给人们留下最初的印象。与此同时,另一位在中国科学界颇有影响的植物学家、时任江西大学副校长的海南琼籍学者林英也被海南行政区隆重请回,共同创办备受瞩目的海南大学。
在故乡走了一遭之后,8月,广东省委来函西安交大,商调林施均到海南。已经年过六十的一对老人,选择离开早已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三个业已成人的孩子,回到久违的故乡开创一番事业,如果没有对故土的深切情感以及诗人般的浪漫情怀,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战胜多少人性的弱点,舍弃多少既得的利益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育有二男一女,名字分别叫作海南、海方和海莉,林施均说,三个孩子名字都有个“海”字,就是为了让孩子们不要忘了自己是海南人。随后,他们在花甲之年来到百废待兴的海南大学校址,望着一片汪洋与滩涂,决意要将那一片“大海”变成“海大”。
新建的海南大学要把原来的海南师专、海南医专、海南农学院和海南水产学校合在一起变成一所综合性大学。但是,这四所学校都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地方,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每个学校都交织着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将这四股力量拧在一起,是具有丰富办学经验的林施均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新海大号称有3000亩地,但除了海南水产学校有400亩熟地和一些简陋的房子外,其余都是填海造地。那2000多亩地也几乎是海水,最深处有两三米,一般是深一米。有人来参观问海大建在哪里,我们用手一指,就说是建在海水里。”20年后的林施均这样对笔者说。
建校首先是要搞基建,这些工作由主管全面的林施均来抓。当时区党委考虑到这对老人的身体状况,特别安排他们住在区党委招待所,可这对老革命家却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硬要跟教职工住在一起,方便指挥日夜不能停息的基建工作。
那是海南水产学校留下来的一间破旧教学楼,共3层、12间教室。一对饱经风霜的老者就住在楼下东边的一间教室里。段克强老人回忆说,这教室已是年久失修,门窗不严,漏风。来后不久,他们遭遇了海南的台风季节。从未经历过台风洗礼的段老,眼看着疾风带着大雨泼进窗来却无计可施。台风肆虐的那个夜晚让她此生难忘,并想起了陆游的诗句:“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屋漏不可支,窗户俱有声。”台风总会过去,尤其让人心里发毛的是从门口到大路这一段十几米的土路,长着一米多高的杂草,怕就怕里面有蛇!于是,人们常见晚饭之后,堂堂的海大党委书记和他的老伴拿着镰刀,坐在小板凳上,一点一点地往前边挪边割草,草一片片地倒下,路一点点地露了出来。这对资深的老革命家、老知识分子硬是从杂草丛中开出一条路来。他们有些苍老的背影让人感慨,当年海大创办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海南历史上曾存在过一所私立海南大学,它是由当年的海南籍精英汇聚各方力量办起来的,校址在海口得胜沙路尾的椰子园内,即今海军424医院所在地。它于1947年开始招生,1950年5月海南解放后就关闭了,直到1983年,当大多数的人们早已忘记那所私立海大时,新海大的建立已经变得迫在眉睫了。林老回忆说,1983年10月10日左右,一个台风过后的日子,工地上还在热火朝天地施工中,海南大学就招了第一期学生,正式开学了。海大开学前一天,宣布海大成立的大会却不在海大校园里召开,而将会场设在区党委大会堂里,那种隆重和庄严的气氛,给人一种奋进的力量。海大师生员工1000人左右参加大会,广东省委常委杨应彬、广州军区副司令庄田、香港海南商会会长黄坚也都来了,并在会上庆贺海南解放以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所综合性大学,黄坚会长还代表海南籍港商周成泰、吴多泰给海大捐助建设资金300万港币,当消息宣布时,会场忽然爆发出惊喜的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天,那串特制的特长鞭炮燃烧着鸣叫着,持续将近半个小时,那情那景,让海大学子喉头发紧,有些人是含着泪水离开会场的。
现在,限于篇幅,我们无法细说海大当年建设的艰难了。林英校长已乘鹤归去,只留下空中的足音,令人怀想;林施均先生也于2006年8月突发疾病离我们远去。彼时,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已经买好第二天回海南的机票,应约参加在海南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我们正等待着接机,与他叙谈。他还有很多计划未及实施,上天却终止了他的生命。回望海大30多年的校史,似乎挺短,可是,海大的建立,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历史内涵,承载着上一代人太多的浓厚的理想主义精神。
遥想1948年12月19日,当那位一心想嫁给一位漂亮男子的段克强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英俊潇洒的林施均的夫人、海南人的媳妇时,这从未到过海南的河南女子,却在几十年之后以年迈而病弱之身,帮助着丈夫在他的故乡开创一番富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业。那柔情四溢、书卷气浓郁的丈夫,当白日的喧嚣褪去后,仍像在战争年月一样,在黑夜里还原为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因此,在海南短短的两年间,林施均除了处理海大繁忙的事务,他还热情满怀地组织海南的诗友,成立海南诗社,并亲任第一任社长。此外,还创办《诗书画》和《诗文学报》,组织出版海南诗人诗集等,在20世纪80年代曾让诗歌与诗人风光了起来。至今,海南诗社仍香火延续,维系着诗人间的心神交融。林施均晚年擅长画竹,因秉承着中国文人以竹寄喻高洁情操的传统精神而为世人所称道。而今他留下来的墨宝,只能让人睹物思人,追思他远去的魂灵了。
2003年11月,当这对已度过金婚的老人重返海南大学时,他们信步来到当年自己的海大故居,自感时光流逝的匆忙!离乡多年的诗人看到故居早已物是人非,只有那些当年亲手栽培的花草仍在年年凋谢、年年复苏,默默诉说着生命生生不息而又周而复始的故事!于是,不老的诗人凝思片刻,在故居的前面赋诗一首:
新绿藤萝蔓碧窗,
小楼近处砌花墙。
冬去中庭斑竹翠,
秋来斜槛菊花黄。
芭蕉雨足结肥果,
茉莉风轻散郁香。
多谢花公敷锦绣,
客心岂愿泊他乡。
耐人寻味的是最后一句,既然不愿意离乡为什么又要客居他乡?难道生活在别处真的是诗人的命运?但以诗人的达观和对世界的爱,以及爱侣的陪伴,想必他乡即是故乡……
1987年,诗人林施均在家学画山水画
1985年林施均在海南大学
在儿孙和亲朋好友的簇拥中度过生日的林老对着刚来的电报,神情喜悦,心里为之大感快慰。是啊,这可是他晚年最值得书写的一笔了。林老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抗大,中间只有1950年间回过老家文昌,此外的日子都在内地任职,直到1983年海南大学创办,他才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当年,海南行政区在全国范围内物色合适的人选担当起创办海大这个历史重任。筹备小组在全国考察一圈后,林施均终于以其深厚的资力、丰富的办学经验和敢于开拓事业的精神,尤其是为故乡奉献才智的雄心,成为创办海大的首要人选。这一年,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
1918年11月3日,林施均出生在海南文昌。他出生时,父亲已在广西北海、越南一带做生意,家境富裕。兄妹四人,他排行老二。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出生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注定着要过一种动荡的充满着艰难选择的生活。1933年,林施均随父亲来到广西,在北海中学(原合浦一中)读书。这是林施均初到北海时在相馆里的留影(见P218左下图)。他眉目清秀,紧抿着嘴唇,梳妆齐整地面对镜头。也许这张照片带给他从未有过的感动,这位聪敏的少年学着当时时髦的做法,在相片后面留下了一首自题诗:“昨天是我兮,今天是我兮,明天还是我兮,永远是我的形态兮。”如果这算是一个少年人因出于对生命、对时光有朦胧感悟而写成的诗句的话,那么,这位曾在中国诗坛活跃过的诗人,从那个时候起,就喜欢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直至用诗歌来当作武器,就该有些年头了。
2003年11月,海南大学举行建校20周年庆典,林施均作为该校的开创者之一,被海大请回参加庆典活动。我有幸在海口见到这位依旧风度翩然、气质优雅的老诗人、老革命家,他的身旁,是那位在革命队伍中有才女之名的夫人段克强女士。现在,战争的岁月已然远去,这位曾充满豪情的老革命家身上透出的更多是诗人的儒雅和敏感,他与老友谈得更多的还是他挚爱了一辈子的诗歌。他送给我一本他新近出版的诗集叫《岁月情深》,他的诗歌不仅流溢出壮怀激烈的豪情,也有活力四射、温情脉脉的情愫在荡漾。比如那首《今年的夏天》,清淡的几笔,似是信手拈来,读来却是情意浓郁,让人涌起一种莫名的乡愁:“今年的夏天/岛上的菠罗蜜/熟得很早/其中有一个属于我//今年夏天/林中的养鸡场/发展很多/其中有一个/属于我的亲人。”而他在70多岁高龄写的那首《《五月的家园》更是婉约清丽,看不出诗的作者已经是一名年逾古稀的老人:“流动与闪烁的/五月的家园/颜色随意/勾画潇洒线条//抑扬与顿挫的/五月的家园/跃动枝头/一只会唱的画眉……”
诗集里还有很多韵律优美且充满着生命活力的诗句,有一些是他早期充满着激情、同情底层的诗篇。1936年秋林施均到广州读高中,那正是抗日运动的高潮期,凡有血性的青年都不会苟全性命,躲在时代的洪流后面。林施均参加了“广州艺术界抗敌协会”诗歌组活动,接受新诗歌大众化的进步思想,是《广州诗坛》的第一批参加者。1937年2月,他写了一首有关清洁工人的诗《倒马桶之歌》以及一系列反映社会生活内容的诗,在广州诗坛有了自己的声誉。然而,那不是一个能够以优美的诗歌来愉悦自己、试图留下文名的时代。1938年林施均20岁,抗日救亡的歌曲在呼唤着他,青纱帐、甘蔗林在召唤着他,他已顾不得父亲为他做的继续求学的安排,他就读于中山大学的大哥也希望自己这位悟性很高的弟弟能够完成大学学业,但是,看起来很文雅、性格温和甚至有些柔弱的弟弟,去意竟如此的决绝。从广州到延安,这一路上该如何走,父亲和哥哥难以设想,以为那一走几乎是生死离别,父亲对这位充满救世情怀的孩子投以眷恋而绝望的目光,默默送其远走。
这位南国诗坛的活跃分子带着他的诗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与他结伴的是几位热血青年。沿途的艰难与危险不言而喻,但他们终于在4月到达了延安。这位斯文温润、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诗人,被安排进“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学习,期满结束,他学业优秀,被留校当教员。当年在延安的有几位海南老乡,而林施均以标准的普通话、较高的理论水平而备受老乡和战友们的尊敬。在后来的日子里,谦逊的林施均从来不会跟别人炫耀他的这些经历。他在延河边驰骋,在宝塔山下操练,聆听第一代领袖们的宣言和演讲。亲历了延安时期主要的运动,他看到了壮烈,也看到斗争的残酷,但,他从未放弃对美好理想信念的追求。
1938年几乎同一个时间,在河南滑县城关西门里,一位叫段克强的女孩被迫离开家园,参加抗日救国宣传队工作。她开明的父亲让她读当地的女子师范学校,这在当时当地可是稀奇事。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让她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家园,她的求学理想和一个女孩子的美好梦想全部化为乌有。
在遇见林施均之前,队伍中曾有女友问她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人,耿直而浪漫的段克强不加思索地冲口而出:“不漂亮的我可不要!”当时引来姐妹们的哄然大笑。说这话时她没有想到远方真有一位潇洒的男子在等着她,也没有想到日后她会随着他来到海南岛,将人生最后漂亮的一笔写在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上。
1983年5月,阔别家乡30多年的林施均和老伴段克强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受到海南区党委的热情欢迎。时任西安交通大学副书记兼副校长的林施均,以儒雅又干练的行事作风给人们留下最初的印象。与此同时,另一位在中国科学界颇有影响的植物学家、时任江西大学副校长的海南琼籍学者林英也被海南行政区隆重请回,共同创办备受瞩目的海南大学。
在故乡走了一遭之后,8月,广东省委来函西安交大,商调林施均到海南。已经年过六十的一对老人,选择离开早已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三个业已成人的孩子,回到久违的故乡开创一番事业,如果没有对故土的深切情感以及诗人般的浪漫情怀,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战胜多少人性的弱点,舍弃多少既得的利益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育有二男一女,名字分别叫作海南、海方和海莉,林施均说,三个孩子名字都有个“海”字,就是为了让孩子们不要忘了自己是海南人。随后,他们在花甲之年来到百废待兴的海南大学校址,望着一片汪洋与滩涂,决意要将那一片“大海”变成“海大”。
新建的海南大学要把原来的海南师专、海南医专、海南农学院和海南水产学校合在一起变成一所综合性大学。但是,这四所学校都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地方,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每个学校都交织着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将这四股力量拧在一起,是具有丰富办学经验的林施均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新海大号称有3000亩地,但除了海南水产学校有400亩熟地和一些简陋的房子外,其余都是填海造地。那2000多亩地也几乎是海水,最深处有两三米,一般是深一米。有人来参观问海大建在哪里,我们用手一指,就说是建在海水里。”20年后的林施均这样对笔者说。
建校首先是要搞基建,这些工作由主管全面的林施均来抓。当时区党委考虑到这对老人的身体状况,特别安排他们住在区党委招待所,可这对老革命家却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硬要跟教职工住在一起,方便指挥日夜不能停息的基建工作。
那是海南水产学校留下来的一间破旧教学楼,共3层、12间教室。一对饱经风霜的老者就住在楼下东边的一间教室里。段克强老人回忆说,这教室已是年久失修,门窗不严,漏风。来后不久,他们遭遇了海南的台风季节。从未经历过台风洗礼的段老,眼看着疾风带着大雨泼进窗来却无计可施。台风肆虐的那个夜晚让她此生难忘,并想起了陆游的诗句:“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屋漏不可支,窗户俱有声。”台风总会过去,尤其让人心里发毛的是从门口到大路这一段十几米的土路,长着一米多高的杂草,怕就怕里面有蛇!于是,人们常见晚饭之后,堂堂的海大党委书记和他的老伴拿着镰刀,坐在小板凳上,一点一点地往前边挪边割草,草一片片地倒下,路一点点地露了出来。这对资深的老革命家、老知识分子硬是从杂草丛中开出一条路来。他们有些苍老的背影让人感慨,当年海大创办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海南历史上曾存在过一所私立海南大学,它是由当年的海南籍精英汇聚各方力量办起来的,校址在海口得胜沙路尾的椰子园内,即今海军424医院所在地。它于1947年开始招生,1950年5月海南解放后就关闭了,直到1983年,当大多数的人们早已忘记那所私立海大时,新海大的建立已经变得迫在眉睫了。林老回忆说,1983年10月10日左右,一个台风过后的日子,工地上还在热火朝天地施工中,海南大学就招了第一期学生,正式开学了。海大开学前一天,宣布海大成立的大会却不在海大校园里召开,而将会场设在区党委大会堂里,那种隆重和庄严的气氛,给人一种奋进的力量。海大师生员工1000人左右参加大会,广东省委常委杨应彬、广州军区副司令庄田、香港海南商会会长黄坚也都来了,并在会上庆贺海南解放以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所综合性大学,黄坚会长还代表海南籍港商周成泰、吴多泰给海大捐助建设资金300万港币,当消息宣布时,会场忽然爆发出惊喜的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天,那串特制的特长鞭炮燃烧着鸣叫着,持续将近半个小时,那情那景,让海大学子喉头发紧,有些人是含着泪水离开会场的。
现在,限于篇幅,我们无法细说海大当年建设的艰难了。林英校长已乘鹤归去,只留下空中的足音,令人怀想;林施均先生也于2006年8月突发疾病离我们远去。彼时,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已经买好第二天回海南的机票,应约参加在海南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我们正等待着接机,与他叙谈。他还有很多计划未及实施,上天却终止了他的生命。回望海大30多年的校史,似乎挺短,可是,海大的建立,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历史内涵,承载着上一代人太多的浓厚的理想主义精神。
遥想1948年12月19日,当那位一心想嫁给一位漂亮男子的段克强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英俊潇洒的林施均的夫人、海南人的媳妇时,这从未到过海南的河南女子,却在几十年之后以年迈而病弱之身,帮助着丈夫在他的故乡开创一番富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业。那柔情四溢、书卷气浓郁的丈夫,当白日的喧嚣褪去后,仍像在战争年月一样,在黑夜里还原为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因此,在海南短短的两年间,林施均除了处理海大繁忙的事务,他还热情满怀地组织海南的诗友,成立海南诗社,并亲任第一任社长。此外,还创办《诗书画》和《诗文学报》,组织出版海南诗人诗集等,在20世纪80年代曾让诗歌与诗人风光了起来。至今,海南诗社仍香火延续,维系着诗人间的心神交融。林施均晚年擅长画竹,因秉承着中国文人以竹寄喻高洁情操的传统精神而为世人所称道。而今他留下来的墨宝,只能让人睹物思人,追思他远去的魂灵了。
2003年11月,当这对已度过金婚的老人重返海南大学时,他们信步来到当年自己的海大故居,自感时光流逝的匆忙!离乡多年的诗人看到故居早已物是人非,只有那些当年亲手栽培的花草仍在年年凋谢、年年复苏,默默诉说着生命生生不息而又周而复始的故事!于是,不老的诗人凝思片刻,在故居的前面赋诗一首:
新绿藤萝蔓碧窗,
小楼近处砌花墙。
冬去中庭斑竹翠,
秋来斜槛菊花黄。
芭蕉雨足结肥果,
茉莉风轻散郁香。
多谢花公敷锦绣,
客心岂愿泊他乡。
耐人寻味的是最后一句,既然不愿意离乡为什么又要客居他乡?难道生活在别处真的是诗人的命运?但以诗人的达观和对世界的爱,以及爱侣的陪伴,想必他乡即是故乡……
1987年,诗人林施均在家学画山水画
1985年林施均在海南大学
相关人物
林施均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