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和大学梦
| 内容出处: |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下册》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1731 |
| 颗粒名称: | 知青往事和大学梦 |
| 分类号: | F323.6 |
| 页数: | 8 |
| 页码: | 171-178 |
| 摘要: | 本文描述了作者于1968年下山下乡,到海南崖县南田农场参加劳动的经历。首先描述了生产队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包括分房,工具,劳保等。然后描述了1969年原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农场的改编情况以及兵团的半军事化管理。最后描述了橡胶树的种植和采集流程。 |
| 关键词: | 下乡 南田农场 橡胶树 |
内容
我1964年从文昌中学考入海南中学就读高中,1968年11月上山下乡到位于海南崖县的南田农场(兵团时期为三师八团),直至1973年上学,经历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知青岁月。
1968年11月16日,海口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发之日,我随学校的统一安排,下到国营南田农场。当天一同下乡的还有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杨泽江的儿子杨永春、杨永庆兄弟俩和副书记林树兰的儿子林红光等14人。
我们被分到各分场前,每人预领1个月工资。永春、永庆、红光等6个人去了爱国分场,我和谢丽玲、林万里、云昌山等8人到长田分场,何明芳到响水分场。长田分场有6个生产队、1个加工厂、1个试验站、1间卫生所、2间学校,还有邮政代办点和商店。全分场除了其中一个以山东、河南籍职工为主的长岭队外,通用的语言都是“白话”(即粤语)。我很快也就融入“白话”这个语言环境中。因为生产队与分场在一起,大部分房屋是瓦房。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生产队特意把几个单身职工调到茅屋,腾出瓦房安排我们住下。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摆了3张单人木床,床是新的,房子中间有1张用两段苦楝树桩钉上木板的小平台。每人领到一大一小两个铝质胶桶、一根扁担、一把胶刀、一个胶灯、一把锄头、一把砍刀和磨胶刀用的粗、细油石各一块,这是每个胶工的标配。胶灯是将手电筒中间装电池的筒身部分剪掉把电筒后盖和灯头焊接在一起,再焊上一块插片改装而成。劳保方面,两年一双中筒水鞋、每年一件工作服,要上衣还是要裤子,到分场缝纫组量身时登记说明。工作服的布料是深蓝色的坚固呢,即当今的牛仔布。
第二天就让我们学习割胶。用来练刀的是埋在地里的半人多高的苦楝树树桩,树皮很硬。上岗第一天,班长禤福洪就教我看胶树的割面。班长告诉我,橡胶树的树皮结构,由外往里,分别是表皮、沙皮、青皮、胶囊和水皮。割胶时,下刀要准,行刀要平稳,收口要整齐,要尽量多切断些胶囊才有利于多排胶乳,但又不能割穿水皮,否则伤到木质的部位会长成木瘤,影响再生皮第二次利用。班长又指给我看:再生皮长得均匀、平滑,基本看不到伤疤的割面是“文革”前的,而“文革”开始以后的割面伤痕累累,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
1969年4月1日,原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我所在的南田农场改建制为三师八团,所在的长田分场长征队随之改编为五营25连。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和后勤、生产处处长都是现役军人,只有生产处云庆荣副处长是原南田农场副场长。兵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内部的战备气氛趋于紧张。团部有1个武装连,还有1个警通班。原农场的车辆改按兵团番号顺序重新编排号牌,车牌号以“兵”字开头,接着第一位数字代表师,后面二、三、四位数字是各个团的车辆号。三师的车号是“兵3XXX”。三师辖区包括通什镇(现五指山市)和琼中、保亭、崖县、乐东等县,从地方农垦一下子成为准军事编制的兵团,改挂兵团车辆车牌号,农场司机们就牛了,部队牌号的车,地方司机一般都不敢惹。
兵团成立后,生产任务更重了。有一位干部在做报告时说:一棵橡胶树20年的产胶量,最好1年就全部拿下来。为了多产胶水,经常是不下雨也割双树位,甚至为了刺激胶水长流,还要在胶树树头埋下电石块。我们连队的橡胶林基本上是实生苗长成的老树,产胶量不均匀,有的高产树每次出胶量可达200毫升,但低产树只有几十毫升。在电石的刺激下,有些低产树的胶乳很快就被排干了,成为死皮树。入夏后,胶林异常闷热,蚊子又多,脖子和脸上布满了蚊子咬过的红点。沾满胶水的裤子变得像牛皮又厚又硬,汗水顺着大腿往水鞋流。被汗水浸透的工服在太阳烘晒下,结出一圈圈白色的盐晶,好像穿着的是花衣服。夏季,割胶时经常会遇到雷阵雨。胶水如果被雨水淋过就会变质,像豆腐渣一样,不能再使用。雨一下,不管有没有割完,都要将已经排出的胶乳抢收回来,并且要马上注入氨水防止胶水凝固。有时候,胶水是收了,人却成了“落汤鸡”。每逢下雨,伙房都会熬上一锅姜糖水,给大家驱寒,预防感冒。
橡胶树是落叶乔木,冬天落叶春天抽芽。每年春天,在对橡胶林做物候观测的同时,还要喷洒硫黄粉,防治橡胶白粉病。橡胶树的物候分为萌动、古铜、淡绿、老化四个阶段,根据林段胶树新叶达到老化程度的比例确定新年度的开割时间。我被连长选为测报员,跟着24连的老测报员彭宗辉见习一天,就单独上岗了。为了提高测报精度,天没亮我就得起床提前去林段,太阳一出就蹚着露水开始观测,争取在上午之前就将全部观测点都记录完毕。为了增强白粉病的防治效果,要等下半夜胶叶沾上露水后才进行喷粉。两个人一组抬着沉重的喷粉机在刺鼻的硫黄味与喷粉机的马达声交织在一起的胶林中穿梭,那种感觉就像扛着机枪在打仗。
第二年冬季停割后,连队组织突击队参加团部组织的开荒大会战,在山坡上安营扎寨,砍岜、清防火带、烧岜、定标、挖穴,连续干了一个多月。我们连的突击队队员是清一色的“壮丁”。砍岜时,大伙呈带状散开,抡着砍刀从山脚下向山顶进攻。砍岜比割胶辛苦得多。藤缠树、树撑藤,一刀砍下去,藤不仅没有被砍断,刀反而给弹开了。有一种野藤比脖子还粗,又长又韧,砍下一段再劈成小条就可以当绳子用。没过多久,双手就磨出了血泡,连刀把都握不住,索性脱下背心缠在刀把上,咬着牙坚持干下去。烧岜前,必须先清好防火带,还要有人看守,然后再逐块点火。定标,是用脚宽2米的大三脚架从山顶开始,一边测定挖“环山行”(梯田)的等高线,一边量出株距并插上挖穴标志。穴标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挖一个长、宽、深各80厘米的标准胶穴,位置不能随意改动。遇到岩石挖不动,就用炸药爆破。我自告奋勇当爆破手,细心地装填炸药,沉着地点燃导火线,一盒雷管用完,一次哑炮也没有出现过。我们站在山头,手握砍刀,被太阳晒黑的脸上淌着汗珠,夕阳下阵风夹着烧山的余热迎面扑来,放眼望去,四周没有烧尽的树木七零八落,有的还冒着青烟,正在清岜的工人好像是在打扫战场,那些挖橡胶穴的工人好像在构筑工事,还有拴着钢丝绳穿梭在工地上拔大树头的拖拉机以及远处正在开路的推土机,看上去极似推进中的坦克,那种情景如同在许多战争影片中看过的战斗场面一样,非常壮观。
我到农场不久,谢丽玲的几个同辈亲戚从北京过来投靠她,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对姐妹。北方人向往大海。一个休息日,应他们邀请,我们几个年轻人,采来芭蕉叶包了几个粽子,骑了约12公里自行车去看海。次日,分场的兽医黄良能悄悄告诉我:小杨,有人说你昨天带了干粮去看地形,在调查呢。后来才知道,因为我父亲是“走资派”这一特殊的家庭背景,我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待遇。
所幸淳朴的老职工默默地给了我许多关爱和帮助。禤福洪班长一割完胶,就拎着小桶过来同我一起磨刀,唠家常,讲老工人垦荒的故事。禤班长还把他珍藏多年的一把胶刀送给我。这种胶刀是早期农场到东北的工厂定制的,比发给我们的胶刀长些、粗些。刀身用优质钢材锻压成型,涂上黄漆的刀把材质很硬,尾端还镶着一个钢套。这种刀开口后很锋利又不容易卷刃,我非常喜欢。好马配好鞍,好战士要好武装。工人们装胶刀用的是粗糙的竹篓,装电池用的是竹筒。为了和靓刀匹配,我用铁线编了一个胶篓,又请后勤班的李子谭师傅用木板做了一个电池盒,割胶时就别在皮腰带上,这样的装束形象在割胶时精神都爽一些。没多久,长田队分出一个长征队,我、林万里、谢丽玲、云昌山、冯玉梅等5人分到了长征队。林万里的父亲一复出就来看他,他立马就被借调到团部当了报道员。虽然父亲还不能来看我,但通过书信,一再叮咛我:越是艰难困苦越能磨炼意志,要像自己的名字一样,勇敢地面对一切,好好锻炼。我暗下决心在艰难困苦中默默地磨炼自己,无论何时何地干什么都不可以甘居人后,做什么都要力争做到最好。连队新宿舍建成,我们从24连搬过去时还没有通电,我用在学校学过的知识,带领两个广州知青为每家都装上了一盏电灯照明。
有一次台风过后,要将被台风刮倒的橡胶树扶正复位。有一棵胶树因为一条侧枝卡在另一棵胶树的树丫中,没有完全倒地。工友陈益怡就爬上去砍其他没有被卡住的分枝,我和陈卓珍挖去树头周边泥土清完侧根后,主干还是没有倒下来。陈益怡再次爬上去打算多砍几条细枝,可是刚砍完一条,就听到“啪”的一声,那条侧枝突然折断了,他赶忙扔掉砍刀两手紧抱树干,我一个箭步冲过去用肩膀顶住正在下坠的树干。匆忙中我一只脚滑进了树沟,感到腰椎被狠狠地挫了一下,但还是死死扛着,陈卓珍和另一个工人赶忙过来一起撑着,直到陈益怡安全下到地面。因为这个台风带来的大雨,山洪冲毁了连队的菜地,我们过了一段相当长时间靠红豆汤和绿豆汤送饭的日子。
我们拿的工资是农业工人级别标准,农业工人工资比林业工人工资低一些。几年后,兵团职工工资调整,并且按林业工人工资的级别标准进行套改。干部在宣释有关调资文件精神时特别传达了兵团首长的指示:兵团职工从今往后是正式的林业工人了,待遇提高了。
在一个休息日傍晚,从三营那边传来工友陈益怡下河摸鱼不幸溺水的消息,不等连长发话,我和云昌山、王延康(广州知青)等几人向老工人借了自行车就往三营一阵狂奔,赶到落水地点,尸体已经被捞上岸。我们折回附近的爱国队要了两根竹竿和两条麻袋,做成一副担架,王延康在前我在后,把尸体抬到大路边,等待拉棺材的汽车。抬死人感觉比抬活人沉重许多,穿过麻袋的竹竿也不够长,死者的脚时不时会蹭到王延康的脖子,为了避开死者的头发,我要把头往后仰,抬着摇摇晃晃的“担架”在夜幕中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往前走。回到下葬地点,家里的职工已经挖好墓穴,问过死者妻子,云昌山为棺木盖板钉上了第一枚钉子。在胶灯的光线下回填好墓穴,工人们都将手中的锄头往火堆里烤过再离开。陈益怡走了,留下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第二天去打饭遇见陈益怡的妻子,她指着怀里的孩子对我说:“你看,他这么小就没有了爸爸,多可怜呀!”
1971年初,团里以营为单位组织文艺汇演,我被抽调到营部当领队兼编导。舞导是23连的海口知青王良戴和陈卓珍的妻子陈池英。一名从26连抽选的女演员是农场职工子女,姓孙,家庭出身不大好,但有文艺功底。参演的节目有一个由我编写的有忆苦思甜内容的演唱剧本。汇演结束,又有人质疑为何让她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演忆苦思甜的节目。尔后,我留在营部当报道员,还兼做统计,每天将各个连队当天的胶水产量汇总上报给团生产处。
1972年4月,我从营部调到五营第一中心小学当教师。校长符学芳是本地黎族干部。指导员(党支部书记)黄鉴是当年带领民工挑着粮食长途跋涉,从广东高鹤走到南田农场的老同志。这时,陆续有知青通过各种途径离开兵团回城,有的人父母门路更广,还去了部队当兵。海南区党委、行署大院下到三师八团(南田农场)的15名干部子弟,也先后走了13人,留下的只有我和何明芳,那时她已经和1名场职工子弟结婚了。父亲复出后还兼海南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父亲要我以平常心对待别人回城,路要靠自己走出来。有一天,学校指导员要我写一篇安心扎根兵团的心得体会,还说是团里交代的。后来,符学芳校长和黄鉴指导员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从小时候起,父亲对我的要求就很严格,教育我好好读书、立志做人。我的读书习惯,就是从读父亲书架上的《星火燎原》《红旗飘飘》和《在烈火中永生》等革命书籍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我几乎都读过,包括《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青年近卫军》等,但是影响最深、最受教育的是《红岩》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父亲送给我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这三本。后来,与我同班的林天儒同学不知从哪儿弄来几本《国际问题研究》期刊,我读后就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心中的目标又多了一个:要么参军,要么考上与国际问题有关的大学。
下农场后没多久,“读书无用论”泛起,接着又批判师道尊严。北京出了一个反潮流的黄帅,中原某省又冒出一起学生因抵制考试、不堪老师批评而投河自杀的“马镇湖中学”事件。一位团领导在传达“马镇湖事件”有关文件时,念到动情之处,甚至还掏出手帕来擦眼泪。我很纠结,也很疑惑。我们在校期间,中国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三钱”(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和华罗庚等科学领域泰斗,都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偶像。钱学森历尽曲折艰辛才从美国回到祖国的经历,就像神话故事一样广为传颂。陈毅元帅说过:一个飞行员,虽然立场坚定但是没有过硬的技术,一上天就会被敌人打下来;尽管徒有技术但是立场不坚定,上了天就可能把飞机开到敌人那边去。我反复思考,大学停招,中学生一毕业就上山下乡,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依靠谁来建设现代化?在众多知青中,渴望继续读书的不乏其人。坚持读书学习,逐渐成了我工余时间主要的消遣方式。
1971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知青下乡满两年才有资格报名,头两批上学的都是老职工子女。我们营24连老工人许英林的儿子许志勇,从部队退伍回来留在团部警通班没多久,就幸运地被保送上了清华。大学恢复招生,让我看到了曙光和希望。当了营报道员后,我经常向团报道员王公棉(潮汕知青,后在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工作,副巡视员)请教新闻报道的写作方法。还向武装连的报道员吴耀南借了一本《报道员手册》研习不同体裁的写作技巧。后来当了教师,我获得了一个宽松的自学环境。我教授小学四、五年级语文和初中常识,虽然不怎么费力,但仍不敢怠慢,每一课都要阅读教学参考资料,认真准备教案,需要板书的内容也一一标注清楚。星期天炊事员休息,一杯藕粉加几块饼干权当午饭。从一位老大学生那儿借到一本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著的《修辞学发凡》,爱不释手,认真拜读了好几遍。全团教师业务培训班搞语文基础知识测试,其中有一道句子分析题目,我的答案漂亮,被负责评卷的团中学周涛老师在小结时特意抽出来作范例。每到寒、暑假,我就有更多时间读书了。我通读了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就开始啃于光远写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和李达主编的《哲学》等理论书籍。后来工资调整,月工资从28.6元一下子涨到36.5元。作为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了钱就买书并订阅《红旗》《国际问题研究》《解放军文艺》等杂志。每个月在这方面的花销差不多占工资的1/4。“文革”前,父亲经常下乡,不能及时看到报纸,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花了差不多1个月的工资买了1部南京生产的熊猫牌7管半导体收音机。我回家休假,父亲将它送给我带回学校。
1973年3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国务院教科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已经实施两年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查”的内容。这年7月,我被推荐上大学。全师的被推荐生集中在我们八团参加文化考试。录取名额和考试人数的比例是1:8。到团部报到时,我遇到团中学参加改卷的李德义老师。他对我说:“你不用考了,肯定可以上,你的底子谁都知道。”他接着透露,团政治处冯副主任几天前在团中学应届毕业典礼上讲话中提到我,并表示团里已经确定批准我上大学。
开考前,由一位女青年作辅导报告。当时高校招生遵循“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语文科的作文题目是《深刻的一课》,我写的是那次受伤的经历和感受。考数学科时,我在解答一道已知井绳缠在轱辘上的圈数和轱辘内环直径求水井深度的题目时,监考的青年老师站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快步走上讲台,敲着黑板请大家注意:“第X题给出的条件是轱辘内环的直径而不是半径,别搞错了。”我一看卷,自己也是这种情况。
面试时有两位考官,一个是那位数学监考老师,另一个就是那位作辅导报告的女青年。轮到我面试,时间只有几分钟。男考官先问我半导体三管收音机的电路原理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女考官接着问我报的是什么专业,并问如果改为体育学院我去不去。我如实回答我的腰和脚都受过伤,不合适读体育专业。结果,这位女考官给我写下的鉴定结论是“读大学目的不明确,向党讨价还价”。当天傍晚,整个团部考场都传开了。有的人对我说:“明知道不过是试探,说一句坚决服从分配不就行了!你干吗那么老实?”
这一年的9月,海南遭到“7314号”超强台风袭击,琼海县(现琼海市)损失最严重,嘉积镇汽车站几十吨重的水塔都被强大的龙卷风摧毁,塔身滚到几十米开外。中央派了医疗工作队到海南参与救灾。工作结束后,父亲陪同工作队到三亚基地参观,途中顺道拐进来看望我。父亲留给我一句话:唯求真知,不图虚名。
第二年推荐大学生的做法与上一年不同。团里将一个招生名额分配到营,由营里决定谁可以上大学。学校早早就把我向营部挂了号。到了开会评选大学生那天,我们学校的欧副指导员却因其他事而迟到,而营里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教导员却偏偏又因病住院,改为毫不知情的副营长主持会议。在会上,27连副指导员翻出前一年的老账,说我对专业挑挑拣拣,思想有问题。另一位与会的21连副指导员是潮汕知青,恰恰其本人也是被评议的对象。欧副指导员赶到营部没多久会议就结束了。结果是那位潮汕知青捷足先登,1个月后读大学去了。
意想不到的是,10月份广东省外贸学校海关专业来招生。全师只有1个名额,学制3年,要求笔试、面试,有点专向特招性质(毕业后学员都回到本人入学前所在地区)。虽然只是中专,离我的大学梦有一定距离,但一心求学的我毫不迟疑地报了名。学校自主招生,人为的阻碍因素自然减少了很多。我按要求提交了一篇文章后,很快就接到通知去三亚面试,随后就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入学报到时,海南去的新生有我,还有儋县(现儋州市)那大、昌江县石禄铁矿各1人以及海口海关的2名保送生,共5人。这也是该校在全国恢复高考前招收的唯一一个海关专业班。
按当时的有关政策,工龄满5年就可以带薪上学。可是到了广州后,农场就是不给我发工资。开弓没有回头箭,此后将近3年时间,大妹每月从她微薄的工资中抽出15块钱资助我,支持我完成学业。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在东方的八所海关。
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在外地出差时从早上的新闻广播中获知的消息,同在1973年听到“白卷英雄”的新闻时的感受截然相反,非常激动,立马赶回单位向领导报告要报名参加高考。可是海关王副关长不同意,说我已经读过了,而且在海关当了干部,不必再读了。他不同意,我便自己跑去县招生办报名。
在等待考试的那些日子里,我无从获取任何有关高考的复习资料,甚至连一本高中的教材都找不到。当时能做到的,是拟出了几个语文作文题目。押题的依据源自与父亲的一次谈话受到的启迪。有一天我看到父亲在审阅一份海南省人民医院新址平面图,我问父亲海南省人民医院为什么要搬迁。父亲说,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国家百废待兴,方方面面都要有新的举措新的作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他要做两件事: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从海南一级医疗单位被下放到基层的医疗技术人员,统统都要调回来;二是将海南省人民医院从海口市区迁往秀英,扩大院区容积,加强技术力量,提升医疗水平,促进海南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因此,我猜题的范围,一是批判“读书无用论”,坚持走红专结合的道路;二是记叙周边发生的有意义的人和事,因为对在兵团参加上大学文化考试时的作文题目《深刻的一课》还有很深的印象。
八所中学也开设了辅导班,但每间课室都人满为患,连走廊都站满了听课的人。我因为要当班值勤,无法去听辅导课,只是有一天晚上和卫检所的小蔡向八所中学的文老师请教了一些数学方面的问题。
12月11日至13日开考,并且是先填志愿后考试。开考时,考场周围用绳子拉起警戒线,并有扛枪的民兵站岗。虽然是开卷考试,但是一无资料二没时间,每一科都凭自己原有的基础应考。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史地(文科)或理化(理科),报外语专业要加考英语,但不记入总分。语文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写的是记叙一次港口装载工人进行劳动技能竞赛的场景,内容深度不是很够,但在结尾以一句“在初秋金色阳光的照耀下,发电厂高大挺拔的烟囱上‘抓纲治国’四个白色的大字格外的醒目”扣题。
考完试后的一天晚上,我与小蔡去八所中学找文老师聊天,刚好遇到从广州来负责相关招生工作的两位老师。当我说到我报的志愿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时,其中一位从广东邮电学校来的青年教师说复旦这个专业全省只有6个名额,我敢报复旦胃口真大。尔后无意中说到我妹妹也参加了高考,这位青年教师认为我们兄妹有互相通水串题之嫌,并且写了一张纸条放进我的卷宗袋中。另一位华南农学院的老师认为不可凭猜疑就轻率行事,又把那张纸条给抽了出来。非常感谢那位华农的老师,如果不是他,我就可能重蹈在兵团的覆辙,这一辈子就与大学失之交臂了。县招生办一位同志告诉我,我的卷宗袋封面上注有一个“英”字,表示英语科考的分数比较高。
高考放榜,我幸运地被复旦大学袁稚辉老师录招,并如愿就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圆了大学梦。
1968年11月16日,海口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发之日,我随学校的统一安排,下到国营南田农场。当天一同下乡的还有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杨泽江的儿子杨永春、杨永庆兄弟俩和副书记林树兰的儿子林红光等14人。
我们被分到各分场前,每人预领1个月工资。永春、永庆、红光等6个人去了爱国分场,我和谢丽玲、林万里、云昌山等8人到长田分场,何明芳到响水分场。长田分场有6个生产队、1个加工厂、1个试验站、1间卫生所、2间学校,还有邮政代办点和商店。全分场除了其中一个以山东、河南籍职工为主的长岭队外,通用的语言都是“白话”(即粤语)。我很快也就融入“白话”这个语言环境中。因为生产队与分场在一起,大部分房屋是瓦房。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生产队特意把几个单身职工调到茅屋,腾出瓦房安排我们住下。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摆了3张单人木床,床是新的,房子中间有1张用两段苦楝树桩钉上木板的小平台。每人领到一大一小两个铝质胶桶、一根扁担、一把胶刀、一个胶灯、一把锄头、一把砍刀和磨胶刀用的粗、细油石各一块,这是每个胶工的标配。胶灯是将手电筒中间装电池的筒身部分剪掉把电筒后盖和灯头焊接在一起,再焊上一块插片改装而成。劳保方面,两年一双中筒水鞋、每年一件工作服,要上衣还是要裤子,到分场缝纫组量身时登记说明。工作服的布料是深蓝色的坚固呢,即当今的牛仔布。
第二天就让我们学习割胶。用来练刀的是埋在地里的半人多高的苦楝树树桩,树皮很硬。上岗第一天,班长禤福洪就教我看胶树的割面。班长告诉我,橡胶树的树皮结构,由外往里,分别是表皮、沙皮、青皮、胶囊和水皮。割胶时,下刀要准,行刀要平稳,收口要整齐,要尽量多切断些胶囊才有利于多排胶乳,但又不能割穿水皮,否则伤到木质的部位会长成木瘤,影响再生皮第二次利用。班长又指给我看:再生皮长得均匀、平滑,基本看不到伤疤的割面是“文革”前的,而“文革”开始以后的割面伤痕累累,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
1969年4月1日,原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我所在的南田农场改建制为三师八团,所在的长田分场长征队随之改编为五营25连。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和后勤、生产处处长都是现役军人,只有生产处云庆荣副处长是原南田农场副场长。兵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内部的战备气氛趋于紧张。团部有1个武装连,还有1个警通班。原农场的车辆改按兵团番号顺序重新编排号牌,车牌号以“兵”字开头,接着第一位数字代表师,后面二、三、四位数字是各个团的车辆号。三师的车号是“兵3XXX”。三师辖区包括通什镇(现五指山市)和琼中、保亭、崖县、乐东等县,从地方农垦一下子成为准军事编制的兵团,改挂兵团车辆车牌号,农场司机们就牛了,部队牌号的车,地方司机一般都不敢惹。
兵团成立后,生产任务更重了。有一位干部在做报告时说:一棵橡胶树20年的产胶量,最好1年就全部拿下来。为了多产胶水,经常是不下雨也割双树位,甚至为了刺激胶水长流,还要在胶树树头埋下电石块。我们连队的橡胶林基本上是实生苗长成的老树,产胶量不均匀,有的高产树每次出胶量可达200毫升,但低产树只有几十毫升。在电石的刺激下,有些低产树的胶乳很快就被排干了,成为死皮树。入夏后,胶林异常闷热,蚊子又多,脖子和脸上布满了蚊子咬过的红点。沾满胶水的裤子变得像牛皮又厚又硬,汗水顺着大腿往水鞋流。被汗水浸透的工服在太阳烘晒下,结出一圈圈白色的盐晶,好像穿着的是花衣服。夏季,割胶时经常会遇到雷阵雨。胶水如果被雨水淋过就会变质,像豆腐渣一样,不能再使用。雨一下,不管有没有割完,都要将已经排出的胶乳抢收回来,并且要马上注入氨水防止胶水凝固。有时候,胶水是收了,人却成了“落汤鸡”。每逢下雨,伙房都会熬上一锅姜糖水,给大家驱寒,预防感冒。
橡胶树是落叶乔木,冬天落叶春天抽芽。每年春天,在对橡胶林做物候观测的同时,还要喷洒硫黄粉,防治橡胶白粉病。橡胶树的物候分为萌动、古铜、淡绿、老化四个阶段,根据林段胶树新叶达到老化程度的比例确定新年度的开割时间。我被连长选为测报员,跟着24连的老测报员彭宗辉见习一天,就单独上岗了。为了提高测报精度,天没亮我就得起床提前去林段,太阳一出就蹚着露水开始观测,争取在上午之前就将全部观测点都记录完毕。为了增强白粉病的防治效果,要等下半夜胶叶沾上露水后才进行喷粉。两个人一组抬着沉重的喷粉机在刺鼻的硫黄味与喷粉机的马达声交织在一起的胶林中穿梭,那种感觉就像扛着机枪在打仗。
第二年冬季停割后,连队组织突击队参加团部组织的开荒大会战,在山坡上安营扎寨,砍岜、清防火带、烧岜、定标、挖穴,连续干了一个多月。我们连的突击队队员是清一色的“壮丁”。砍岜时,大伙呈带状散开,抡着砍刀从山脚下向山顶进攻。砍岜比割胶辛苦得多。藤缠树、树撑藤,一刀砍下去,藤不仅没有被砍断,刀反而给弹开了。有一种野藤比脖子还粗,又长又韧,砍下一段再劈成小条就可以当绳子用。没过多久,双手就磨出了血泡,连刀把都握不住,索性脱下背心缠在刀把上,咬着牙坚持干下去。烧岜前,必须先清好防火带,还要有人看守,然后再逐块点火。定标,是用脚宽2米的大三脚架从山顶开始,一边测定挖“环山行”(梯田)的等高线,一边量出株距并插上挖穴标志。穴标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挖一个长、宽、深各80厘米的标准胶穴,位置不能随意改动。遇到岩石挖不动,就用炸药爆破。我自告奋勇当爆破手,细心地装填炸药,沉着地点燃导火线,一盒雷管用完,一次哑炮也没有出现过。我们站在山头,手握砍刀,被太阳晒黑的脸上淌着汗珠,夕阳下阵风夹着烧山的余热迎面扑来,放眼望去,四周没有烧尽的树木七零八落,有的还冒着青烟,正在清岜的工人好像是在打扫战场,那些挖橡胶穴的工人好像在构筑工事,还有拴着钢丝绳穿梭在工地上拔大树头的拖拉机以及远处正在开路的推土机,看上去极似推进中的坦克,那种情景如同在许多战争影片中看过的战斗场面一样,非常壮观。
我到农场不久,谢丽玲的几个同辈亲戚从北京过来投靠她,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对姐妹。北方人向往大海。一个休息日,应他们邀请,我们几个年轻人,采来芭蕉叶包了几个粽子,骑了约12公里自行车去看海。次日,分场的兽医黄良能悄悄告诉我:小杨,有人说你昨天带了干粮去看地形,在调查呢。后来才知道,因为我父亲是“走资派”这一特殊的家庭背景,我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待遇。
所幸淳朴的老职工默默地给了我许多关爱和帮助。禤福洪班长一割完胶,就拎着小桶过来同我一起磨刀,唠家常,讲老工人垦荒的故事。禤班长还把他珍藏多年的一把胶刀送给我。这种胶刀是早期农场到东北的工厂定制的,比发给我们的胶刀长些、粗些。刀身用优质钢材锻压成型,涂上黄漆的刀把材质很硬,尾端还镶着一个钢套。这种刀开口后很锋利又不容易卷刃,我非常喜欢。好马配好鞍,好战士要好武装。工人们装胶刀用的是粗糙的竹篓,装电池用的是竹筒。为了和靓刀匹配,我用铁线编了一个胶篓,又请后勤班的李子谭师傅用木板做了一个电池盒,割胶时就别在皮腰带上,这样的装束形象在割胶时精神都爽一些。没多久,长田队分出一个长征队,我、林万里、谢丽玲、云昌山、冯玉梅等5人分到了长征队。林万里的父亲一复出就来看他,他立马就被借调到团部当了报道员。虽然父亲还不能来看我,但通过书信,一再叮咛我:越是艰难困苦越能磨炼意志,要像自己的名字一样,勇敢地面对一切,好好锻炼。我暗下决心在艰难困苦中默默地磨炼自己,无论何时何地干什么都不可以甘居人后,做什么都要力争做到最好。连队新宿舍建成,我们从24连搬过去时还没有通电,我用在学校学过的知识,带领两个广州知青为每家都装上了一盏电灯照明。
有一次台风过后,要将被台风刮倒的橡胶树扶正复位。有一棵胶树因为一条侧枝卡在另一棵胶树的树丫中,没有完全倒地。工友陈益怡就爬上去砍其他没有被卡住的分枝,我和陈卓珍挖去树头周边泥土清完侧根后,主干还是没有倒下来。陈益怡再次爬上去打算多砍几条细枝,可是刚砍完一条,就听到“啪”的一声,那条侧枝突然折断了,他赶忙扔掉砍刀两手紧抱树干,我一个箭步冲过去用肩膀顶住正在下坠的树干。匆忙中我一只脚滑进了树沟,感到腰椎被狠狠地挫了一下,但还是死死扛着,陈卓珍和另一个工人赶忙过来一起撑着,直到陈益怡安全下到地面。因为这个台风带来的大雨,山洪冲毁了连队的菜地,我们过了一段相当长时间靠红豆汤和绿豆汤送饭的日子。
我们拿的工资是农业工人级别标准,农业工人工资比林业工人工资低一些。几年后,兵团职工工资调整,并且按林业工人工资的级别标准进行套改。干部在宣释有关调资文件精神时特别传达了兵团首长的指示:兵团职工从今往后是正式的林业工人了,待遇提高了。
在一个休息日傍晚,从三营那边传来工友陈益怡下河摸鱼不幸溺水的消息,不等连长发话,我和云昌山、王延康(广州知青)等几人向老工人借了自行车就往三营一阵狂奔,赶到落水地点,尸体已经被捞上岸。我们折回附近的爱国队要了两根竹竿和两条麻袋,做成一副担架,王延康在前我在后,把尸体抬到大路边,等待拉棺材的汽车。抬死人感觉比抬活人沉重许多,穿过麻袋的竹竿也不够长,死者的脚时不时会蹭到王延康的脖子,为了避开死者的头发,我要把头往后仰,抬着摇摇晃晃的“担架”在夜幕中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往前走。回到下葬地点,家里的职工已经挖好墓穴,问过死者妻子,云昌山为棺木盖板钉上了第一枚钉子。在胶灯的光线下回填好墓穴,工人们都将手中的锄头往火堆里烤过再离开。陈益怡走了,留下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第二天去打饭遇见陈益怡的妻子,她指着怀里的孩子对我说:“你看,他这么小就没有了爸爸,多可怜呀!”
1971年初,团里以营为单位组织文艺汇演,我被抽调到营部当领队兼编导。舞导是23连的海口知青王良戴和陈卓珍的妻子陈池英。一名从26连抽选的女演员是农场职工子女,姓孙,家庭出身不大好,但有文艺功底。参演的节目有一个由我编写的有忆苦思甜内容的演唱剧本。汇演结束,又有人质疑为何让她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演忆苦思甜的节目。尔后,我留在营部当报道员,还兼做统计,每天将各个连队当天的胶水产量汇总上报给团生产处。
1972年4月,我从营部调到五营第一中心小学当教师。校长符学芳是本地黎族干部。指导员(党支部书记)黄鉴是当年带领民工挑着粮食长途跋涉,从广东高鹤走到南田农场的老同志。这时,陆续有知青通过各种途径离开兵团回城,有的人父母门路更广,还去了部队当兵。海南区党委、行署大院下到三师八团(南田农场)的15名干部子弟,也先后走了13人,留下的只有我和何明芳,那时她已经和1名场职工子弟结婚了。父亲复出后还兼海南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父亲要我以平常心对待别人回城,路要靠自己走出来。有一天,学校指导员要我写一篇安心扎根兵团的心得体会,还说是团里交代的。后来,符学芳校长和黄鉴指导员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从小时候起,父亲对我的要求就很严格,教育我好好读书、立志做人。我的读书习惯,就是从读父亲书架上的《星火燎原》《红旗飘飘》和《在烈火中永生》等革命书籍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我几乎都读过,包括《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青年近卫军》等,但是影响最深、最受教育的是《红岩》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父亲送给我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这三本。后来,与我同班的林天儒同学不知从哪儿弄来几本《国际问题研究》期刊,我读后就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心中的目标又多了一个:要么参军,要么考上与国际问题有关的大学。
下农场后没多久,“读书无用论”泛起,接着又批判师道尊严。北京出了一个反潮流的黄帅,中原某省又冒出一起学生因抵制考试、不堪老师批评而投河自杀的“马镇湖中学”事件。一位团领导在传达“马镇湖事件”有关文件时,念到动情之处,甚至还掏出手帕来擦眼泪。我很纠结,也很疑惑。我们在校期间,中国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三钱”(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和华罗庚等科学领域泰斗,都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偶像。钱学森历尽曲折艰辛才从美国回到祖国的经历,就像神话故事一样广为传颂。陈毅元帅说过:一个飞行员,虽然立场坚定但是没有过硬的技术,一上天就会被敌人打下来;尽管徒有技术但是立场不坚定,上了天就可能把飞机开到敌人那边去。我反复思考,大学停招,中学生一毕业就上山下乡,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依靠谁来建设现代化?在众多知青中,渴望继续读书的不乏其人。坚持读书学习,逐渐成了我工余时间主要的消遣方式。
1971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知青下乡满两年才有资格报名,头两批上学的都是老职工子女。我们营24连老工人许英林的儿子许志勇,从部队退伍回来留在团部警通班没多久,就幸运地被保送上了清华。大学恢复招生,让我看到了曙光和希望。当了营报道员后,我经常向团报道员王公棉(潮汕知青,后在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工作,副巡视员)请教新闻报道的写作方法。还向武装连的报道员吴耀南借了一本《报道员手册》研习不同体裁的写作技巧。后来当了教师,我获得了一个宽松的自学环境。我教授小学四、五年级语文和初中常识,虽然不怎么费力,但仍不敢怠慢,每一课都要阅读教学参考资料,认真准备教案,需要板书的内容也一一标注清楚。星期天炊事员休息,一杯藕粉加几块饼干权当午饭。从一位老大学生那儿借到一本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著的《修辞学发凡》,爱不释手,认真拜读了好几遍。全团教师业务培训班搞语文基础知识测试,其中有一道句子分析题目,我的答案漂亮,被负责评卷的团中学周涛老师在小结时特意抽出来作范例。每到寒、暑假,我就有更多时间读书了。我通读了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就开始啃于光远写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和李达主编的《哲学》等理论书籍。后来工资调整,月工资从28.6元一下子涨到36.5元。作为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了钱就买书并订阅《红旗》《国际问题研究》《解放军文艺》等杂志。每个月在这方面的花销差不多占工资的1/4。“文革”前,父亲经常下乡,不能及时看到报纸,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花了差不多1个月的工资买了1部南京生产的熊猫牌7管半导体收音机。我回家休假,父亲将它送给我带回学校。
1973年3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国务院教科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已经实施两年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查”的内容。这年7月,我被推荐上大学。全师的被推荐生集中在我们八团参加文化考试。录取名额和考试人数的比例是1:8。到团部报到时,我遇到团中学参加改卷的李德义老师。他对我说:“你不用考了,肯定可以上,你的底子谁都知道。”他接着透露,团政治处冯副主任几天前在团中学应届毕业典礼上讲话中提到我,并表示团里已经确定批准我上大学。
开考前,由一位女青年作辅导报告。当时高校招生遵循“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语文科的作文题目是《深刻的一课》,我写的是那次受伤的经历和感受。考数学科时,我在解答一道已知井绳缠在轱辘上的圈数和轱辘内环直径求水井深度的题目时,监考的青年老师站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快步走上讲台,敲着黑板请大家注意:“第X题给出的条件是轱辘内环的直径而不是半径,别搞错了。”我一看卷,自己也是这种情况。
面试时有两位考官,一个是那位数学监考老师,另一个就是那位作辅导报告的女青年。轮到我面试,时间只有几分钟。男考官先问我半导体三管收音机的电路原理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女考官接着问我报的是什么专业,并问如果改为体育学院我去不去。我如实回答我的腰和脚都受过伤,不合适读体育专业。结果,这位女考官给我写下的鉴定结论是“读大学目的不明确,向党讨价还价”。当天傍晚,整个团部考场都传开了。有的人对我说:“明知道不过是试探,说一句坚决服从分配不就行了!你干吗那么老实?”
这一年的9月,海南遭到“7314号”超强台风袭击,琼海县(现琼海市)损失最严重,嘉积镇汽车站几十吨重的水塔都被强大的龙卷风摧毁,塔身滚到几十米开外。中央派了医疗工作队到海南参与救灾。工作结束后,父亲陪同工作队到三亚基地参观,途中顺道拐进来看望我。父亲留给我一句话:唯求真知,不图虚名。
第二年推荐大学生的做法与上一年不同。团里将一个招生名额分配到营,由营里决定谁可以上大学。学校早早就把我向营部挂了号。到了开会评选大学生那天,我们学校的欧副指导员却因其他事而迟到,而营里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教导员却偏偏又因病住院,改为毫不知情的副营长主持会议。在会上,27连副指导员翻出前一年的老账,说我对专业挑挑拣拣,思想有问题。另一位与会的21连副指导员是潮汕知青,恰恰其本人也是被评议的对象。欧副指导员赶到营部没多久会议就结束了。结果是那位潮汕知青捷足先登,1个月后读大学去了。
意想不到的是,10月份广东省外贸学校海关专业来招生。全师只有1个名额,学制3年,要求笔试、面试,有点专向特招性质(毕业后学员都回到本人入学前所在地区)。虽然只是中专,离我的大学梦有一定距离,但一心求学的我毫不迟疑地报了名。学校自主招生,人为的阻碍因素自然减少了很多。我按要求提交了一篇文章后,很快就接到通知去三亚面试,随后就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入学报到时,海南去的新生有我,还有儋县(现儋州市)那大、昌江县石禄铁矿各1人以及海口海关的2名保送生,共5人。这也是该校在全国恢复高考前招收的唯一一个海关专业班。
按当时的有关政策,工龄满5年就可以带薪上学。可是到了广州后,农场就是不给我发工资。开弓没有回头箭,此后将近3年时间,大妹每月从她微薄的工资中抽出15块钱资助我,支持我完成学业。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在东方的八所海关。
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在外地出差时从早上的新闻广播中获知的消息,同在1973年听到“白卷英雄”的新闻时的感受截然相反,非常激动,立马赶回单位向领导报告要报名参加高考。可是海关王副关长不同意,说我已经读过了,而且在海关当了干部,不必再读了。他不同意,我便自己跑去县招生办报名。
在等待考试的那些日子里,我无从获取任何有关高考的复习资料,甚至连一本高中的教材都找不到。当时能做到的,是拟出了几个语文作文题目。押题的依据源自与父亲的一次谈话受到的启迪。有一天我看到父亲在审阅一份海南省人民医院新址平面图,我问父亲海南省人民医院为什么要搬迁。父亲说,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国家百废待兴,方方面面都要有新的举措新的作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他要做两件事: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从海南一级医疗单位被下放到基层的医疗技术人员,统统都要调回来;二是将海南省人民医院从海口市区迁往秀英,扩大院区容积,加强技术力量,提升医疗水平,促进海南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因此,我猜题的范围,一是批判“读书无用论”,坚持走红专结合的道路;二是记叙周边发生的有意义的人和事,因为对在兵团参加上大学文化考试时的作文题目《深刻的一课》还有很深的印象。
八所中学也开设了辅导班,但每间课室都人满为患,连走廊都站满了听课的人。我因为要当班值勤,无法去听辅导课,只是有一天晚上和卫检所的小蔡向八所中学的文老师请教了一些数学方面的问题。
12月11日至13日开考,并且是先填志愿后考试。开考时,考场周围用绳子拉起警戒线,并有扛枪的民兵站岗。虽然是开卷考试,但是一无资料二没时间,每一科都凭自己原有的基础应考。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史地(文科)或理化(理科),报外语专业要加考英语,但不记入总分。语文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写的是记叙一次港口装载工人进行劳动技能竞赛的场景,内容深度不是很够,但在结尾以一句“在初秋金色阳光的照耀下,发电厂高大挺拔的烟囱上‘抓纲治国’四个白色的大字格外的醒目”扣题。
考完试后的一天晚上,我与小蔡去八所中学找文老师聊天,刚好遇到从广州来负责相关招生工作的两位老师。当我说到我报的志愿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时,其中一位从广东邮电学校来的青年教师说复旦这个专业全省只有6个名额,我敢报复旦胃口真大。尔后无意中说到我妹妹也参加了高考,这位青年教师认为我们兄妹有互相通水串题之嫌,并且写了一张纸条放进我的卷宗袋中。另一位华南农学院的老师认为不可凭猜疑就轻率行事,又把那张纸条给抽了出来。非常感谢那位华农的老师,如果不是他,我就可能重蹈在兵团的覆辙,这一辈子就与大学失之交臂了。县招生办一位同志告诉我,我的卷宗袋封面上注有一个“英”字,表示英语科考的分数比较高。
高考放榜,我幸运地被复旦大学袁稚辉老师录招,并如愿就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圆了大学梦。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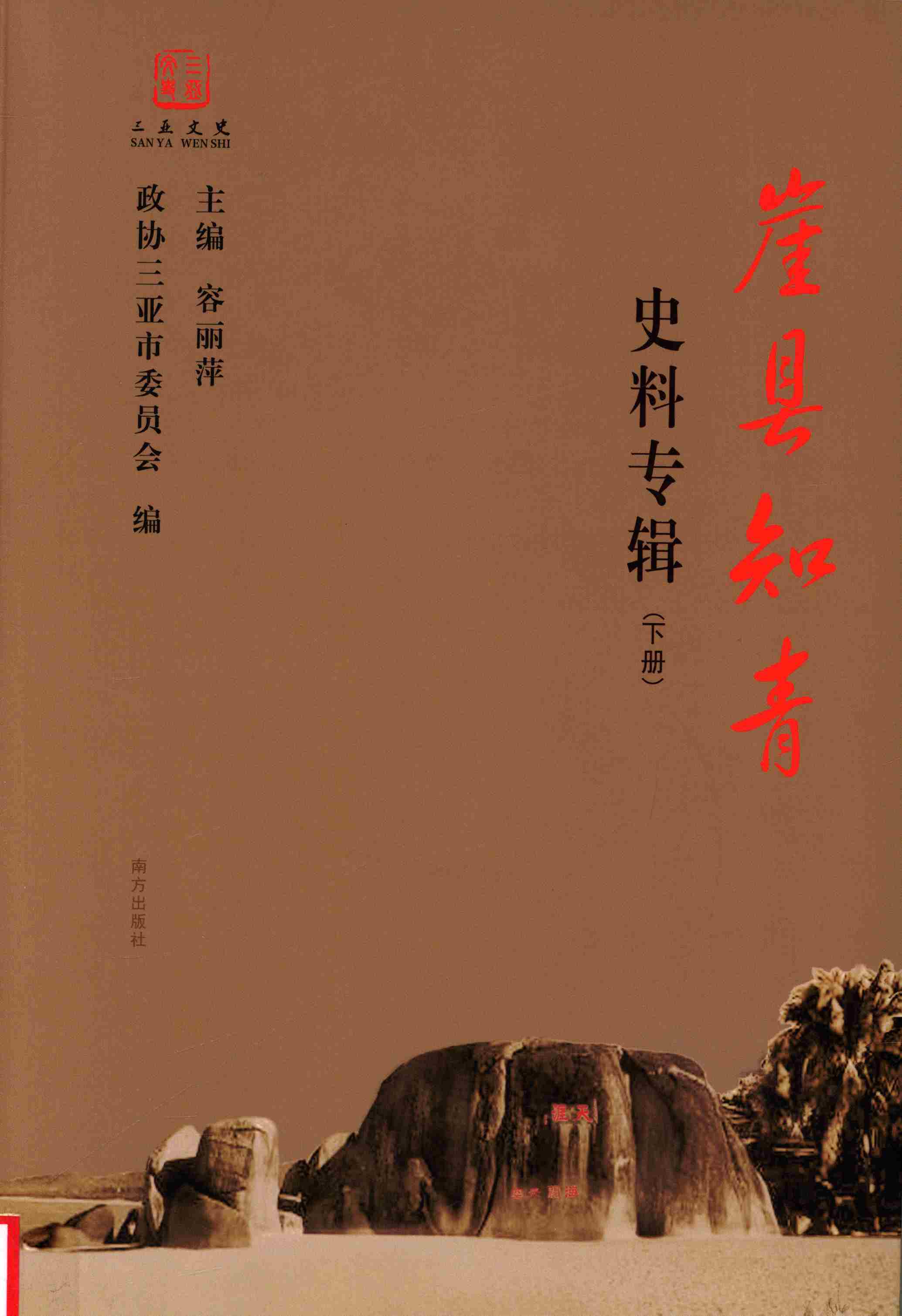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下册》
出版者:南方出版社
本书共有79篇文稿:港西(4篇)公社、梅山公社(7篇)、其他(2篇)3处安置点13篇知青回忆录;垦区南田(32篇)、南新(3篇)、南岛(11篇)、立才(5篇)、南滨(15篇)5个农场66篇知青回忆录。
阅读
相关人物
杨勇军
责任者
相关机构
南田农场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崖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