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开始的地方
| 内容出处: |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下册》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1716 |
| 颗粒名称: | 梦开始的地方 |
| 分类号: | F592.99 |
| 页数: | 10 |
| 页码: | 97-106 |
| 摘要: | 文章讲述了作者赴海南南田农场下乡的经历,以及在该地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文章描绘了乡村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以及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和向往。最后谈到了连队生活和准备战备的情况。 |
| 关键词: | 海南 下乡 连队生活 |
内容
小路的遐想
这条小路,多是人走和牛车过,也能通一辆汽车,一遇下雨天,泥泞又坑洼。一处聚居地,人们相互依存,无论叫什么(生产队或连队),都实则是一个村庄。这条长长的小路,是我当知青时落户的村庄往外走唯一的通途。当年,我曾赶着发出“吱吱呀呀”声响的牛车,一次又一次走在这条小路上,把生产队(连队)汇集的乳白胶水送到东风分场(一营)制胶厂。我也曾打着手电筒,从这小路摸黑赶着去四五公里外的赤田驻军部队看电影。也是这条小路,我踏着它松软的脊梁,回到我曾离开的地方……五十一年过去了,今天,我依然缱绻这条长长的小路,带着我的思念回到那魂牵梦萦的村庄。
1968年12月20日,我和同是广州第十四中学的饶建礼、陈干之、刘国培、吴伟湛、杨志彬、王美美、吴秀娴等人上山下乡来到海南岛,分在南田农场东风分场黄继光生产队,走进了农垦工人的行列。此时,农场总人口过万,职工人数五千多人,橡胶产量在海南农垦系统引人注目,下辖东风、黎场、爱国、红旗、长田、响水六个分场,我所在的东风分场是各分场之首,下面有丰收、东风、前线、前哨、前进队、黄继光六个生产队。
我们广州十四中学的100多名知青和广州二十中学的若干名知青,在场部集训了三天后,我与20多名同校同学(知青)登上农场一部“解放”牌汽车。行驶速度不太快的汽车,越过了藤桥河大桥,向东风分场奔去,一路上颠簸不止。汽车先是在丰收队停下,分到这里的知青陆续下车,因为东风、前线都没有分配知青,黄继光队在路途最末端,汽车搭载我们8人继续前行。
下了车,迎接我们的是支部书记杨传华、生产队长李干州。杨书记是退伍军人,好像是河北人,可能是长年劳累所致,显得有点病恹恹的,身体似乎不太硬实。李队长是广东电白人,他的外貌及动作,给人的印象就像他的名字,精干,风风火火。
我们住在茅草房,细条的茅草夹成片盖了屋顶,黄泥裹稻草糊成墙壁,木桩竹板加上干燥的禾秆就是睡床。从秀英港下船踏上海南的红土壤,曾经设想过农场的种种艰苦,也有了思想准备,毕竟大家都抱着一颗红心干革命,哪里艰苦哪里去的决心。可当我们放下行李,走进散发出潮湿腐霉气味的茅草房时,这种生活环境还是大大超出我的预想,接近黄昏,环顾生产队四周,一个令人烦心的现实是,因为偏远,这地方是东风分场唯一没有电力供应的生产队。
夜幕低垂,这个倚傍着山峦而建的小村庄(生产队),开始进入梦乡。我的睡床旁,黄泥墙壁开了一个两书本大小的窟窿,算是窗户吧。往外看过去,皎洁的月光给潺潺的溪水,笼上白玉般的轻纱。溪水的上方,黝黑的橡胶树环山行,折叠而上,萤火虫拽着不停闪烁的尾巴,在树林中飞舞穿梭。偶尔,树林的深处,传来鹧鸪的呜呜几声,短暂撕碎了寂静,不一会,又是万籁俱寂。在朦朦胧胧中,我度过了来生产队后的第一个夜晚。
1969年4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一并统辖广东湛江、徐闻和海南所有的垦区农场。南田农场改称三师八团,农场下辖的六个分场,分别为一至六营,我所在的黄继光队成了一营四连。当时连队宣读此命令时,知青无不激情澎湃,光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行列中的一员,这是那时革命青年梦寐以求的向往。而连队里的老职工和退伍兵对建设兵团的成立,却是处之泰然。
成立兵团当晚,在茅草房微弱的油灯光下,我给家里人写信,叮嘱他们以后回邮的地址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八团一营四连,并请求他们寄几套旧军装给我。
连队的生活
兵团成立之初,知青在闲暇时谈论最多的是,一旦与隔海相望的越南交战,我们这些屯垦戍边的热血青年,必定会手握钢枪,上阵杀敌,要时刻准备着。在连队橡胶林的某林段,有一座修建多年的战备山洞,能通过汽车。如果发生战事,走海榆东线公路的汽车可在八团改道,经过此处驶往中线公路的保亭、通什(现五指山),不用从崖县田独公社墟市绕弯,能节省不少时间。超强台风“玛琪”于1973年9月14日凌晨从琼海县登陆,波及全岛大部分地区,崖县境内也有狂风暴雨。13日中午接到团部通知后,我们连队除了干部和骨干,其他人员都在傍晚时进入了山洞躲避台风,一夜安然无事。
1974年1月,南海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我们满心欢喜,天真地认为,奔赴战场的时机来了。可是兴奋没几天,团部一纸命令下到连队,要在几天内紧急动员,收集木柴支援前线。大家对这道命令感到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四连地处山林,可连队大伙房日供三餐,每天消耗不少柴火,并没有多少存量。军令如山,连长只好抓紧动员,大伙房的大部分木柴、老职工房前屋后的木柴都贡献了出来。知青们则组成突击队,带上砍刀和钢锯到胶林里,砍伐已经死皮出不了胶水的橡胶树。没几天,连队的球场就垒起几大堆木柴,团部派来汽车运走了。就这样,我们知青的参战愿望没实现,倒是当了几天伐木工。
改制为兵团不久,本应是“秋雨绵绵无绝期”的时节,我们连队却遭遇了严重旱灾。都说海南岛的气候是四季皆夏、一雨成秋,可从4月开始直到11月,基本上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很少下雨。干旱导致地表蒸发加强,地下水源逐渐枯竭,而吸水性较强的大片橡胶林、防风林桉树又吸去大量地表水分,使得旱情更加严重。有一条小河围绕我们连队驻地,平日流水潺潺,奔流不息。老职工说从他们来到这里垦荒时起,这条小河未曾断流,这时却断流干涸了,裸露出龟裂的河床。
连队的两口水井都倚傍着小河,相隔没多远,紧靠大伙房的食用大水井有十多米深,山坡边上的洗浴小水井只有几米深。小水井很快就滴水无存,全连用水都只能依靠大水井,而附近村庄的黎族群众这时也跑过来打水。井底涌泉越来越小,水位一天天降低,眼看快要见底了。于是,连长命令几个懂爆破的退伍兵,在干涸的小水井底下埋放炸药,想看爆炸后的水井能出多少水,可引爆后掏了几米深,还只是流出小孩子尿水般大的细流。连长无奈,只好拨通上级电话紧急求援,于是团部从那天起,每天派汽车运送饮用水到连队。至于洗澡洗衣服,要到一公里外的大河边去。这种缺水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那段日子,种菜班的职工最辛苦,每天好几趟赶牛车装上大铁桶,到大河边运水浇菜地。
1973年夏季,我调去后勤班放牛,不用凌晨三四点钟起来割胶了。我每天都欢天喜地跟着放牛老职工,吆喝着20多头大大小小的水牛,把它们往山沟、林段、坡地驱赶。哪里水草丰盛,牛儿就往哪里钻,并不用牛倌多费心。不过,连队四周都有黎胞的水稻田,那是牛群万万不能进入的禁区。
看似惬意轻松的工作,不知不觉就干了半年。有一天下午放牛回来,我发现右膝盖擦伤了,而且红肿发胀,心想大概是放牛时穿着短裤,给野草树枝碰剐的,晚上到卫生所涂抹点红汞水就可以消炎了。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去放牛,感觉患处还是隐隐作痛,仗着自己年轻,不当一回事。可是到了晚上,头部开始裂痛,整个人仿佛掉进火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凌晨四点多时,连队提醒职工割早胶的钟敲响了,卫生员也到各个点巡查,看有没有因伤病不能割胶的。他来到我们宿舍,我说发烧了很难受,他没细问,给了一包止痛退热散就走了。
天亮后,割完胶回来的知青帮我从伙房端来面条,我才勉强坐起来。他见我身上到处是红斑很惊讶,我说大概是吃了退烧药的缘故。我想下床来走动,见膝盖患处已肿起一个大疱,疼痛难忍。到了下午,高烧依然不退,身上的红斑点越来越多。一个平时交情不错的老职工来到宿舍,看到我当时的情况,忙建议去团部卫生队治疗。卫生员可能是认为问题不大,还是不够重视,没有任何表示。我一看不对头,不顾自己头有点昏昏沉沉,赶紧坐上了老职工的单车尾座直奔团部。
到了团部卫生队,因为发高烧,我很快就陷入昏迷状态,所有住院手续都是老职工帮我办理。我不知道是怎么就躺在病床上了,迷迷糊糊感觉身边人来人往,大概是在住院部的走廊。不知过了多久,有些光亮刺激我沉重的眼帘,一幅幅洁白的轻纱在我面前飘动。这时,一个温柔的女声在我耳边响起:“你哪里不舒服啊?”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用手指了一下膝盖。接下来,她们说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了。在朦胧中,感觉臀部被扎了一针,膝盖被捣鼓了好一会儿。那天晚上,头昏沉沉的,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睡醒过来,头部的沉重和疼痛减少了,膝盖患处也好了一点。我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惊讶地发现,病床和地上有许多从患处流出的脓液。给我换药的护士说是细菌感染,引起血液中毒,积聚多了散发不出来,导致高烧不退。她还说,你好在遇上陈护士长给你治疗,不然昨晚小命不保,她的医术比有的医生还厉害呢。后来我听说了,陈护士长原是彭德怀元帅的护士,因政治原因,被下放到了改制前的南田农场医院。
那时年轻,住院部的医疗条件比较好,治疗也算及时,不到十天就出院了。回到连队,连长大概是怕派我去放牛又出状况,改安排我去收胶站当收胶员,那可是一个不错的工种。
一张乒乓球桌
1973年上半年,我们连队迎来第三任连长张万德(后兼任指导员),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连队的各项工作以及生活环境大为改观。张连长负责全面,唐捷副连长分管后勤,杨绪林副指导员分管政治思想工作及知青工作。
唐捷副连长是从团部汽车队调来的,管后勤生活很有一套。为了养好原有的存栏猪,她增派了一个有饲养经验的电白职工。她又要求看守木薯山的职工饲养几只黑山羊和一大群鸡,还在鱼塘投放了大量的罗非鱼。大伙房虽然不是顿顿有鱼肉,可比以前好多了。特别是蔬菜,就算是台风暴雨季节,连队新鲜蔬菜一时供应不上时,仓库储备的冬瓜、南瓜,也够吃上一段日子。
杨副指导员是退伍兵,文化水平不高,但待人和蔼细心。他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像是一位大哥哥。他做思想政治工作很有一套,总是联系实际、对症下药,注意工作方法,不讲空头政治,不搞形式宣教。对于知青工作,他侧重于思想状况、生活层面、合理要求,认真倾听知青的呼声,尽量关心爱护。比如,我们建议开辟排球场,他很快就带领大家搞义务劳动,将篮球场上方的土坡平整成平台,埋下两根树桩,又弄来排球网和排球,使知青的工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一天下午,我路过连部,看到杨副指导员一个人在看报纸,就向他建议制作一张乒乓球台,他与连里木工商量后就答复了我,但要求我提供大致图纸及具体尺寸。想来木工平时多是修理工具、用具,制作乒乓球台的确有难度。我马上给家里写信,叫家人去广州的文体商店测量乒乓球台尺寸,很快就把图纸尺寸交到木匠的手里。两个星期过去了,木工棚仍然没有打造球台的迹象,我以为是修理工作太忙。又过了两个星期,还是没有动静,这时候我真的有点急了,去连部找到杨副指导员问情况。
杨副指导员也急了起来,就去找木工了解情况和催促尽快动工,一问才知道是做球台的铁钉不够用。虽说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总不至于连几斤铁钉都解决不了吧,我请杨副指导员写了张证明,自己抽空去买。我在第二天下午把连队的胶水送到营部制胶厂后,就走路直奔团部商店,谁知去到那里,售货员告知铁钉是供销社统销产品,要我去藤桥公社供销社看看。于是我又折返到藤桥供销社,递上购买铁钉证明,终于买了几斤宝贝般的铁钉回到连队。
在杨副指导员的得力支持下,乒乓球台很快做好了,连队又购置了两副球拍和球网。这下,爱打乒乓球的知青们可热闹了,一有时间就兴致勃勃地玩起来,几乎个个都踊跃参加乒乓球擂台比赛。后来,有个普宁知青因为球打得好,被营部选上去参加团部的比赛,还得了第三名呢,可把大家乐坏了。
“童子尿”
1969年底至1970年初的一天,连里一位海口女知青完成割胶任务,磨好割胶刀后,开始提着胶桶收集胶水。没走几个环山行,突然从草丛中窜出一条大狗,后面还跟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这位女知青负责的林段,在最偏僻的一个山坳下。虽说她没听说这地方有女生被侵害的事情发生,但在这荒山野岭,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突然站在面前,吓得她三魂五魄不见了,愣了一下后,回过神来转身就跑。可山坳处的林段,环山行宽度太窄,没留神一脚踏空,接连在环山行斜坡翻了几个滚,手上提着的胶桶把持不住,粘糊糊、白花花的胶水全都泼洒出来,有好多弄到了她的头发、脸庞和身子上。
那位黎族男子也被吓着了,原来他是连队附近村庄的村民,带着猎狗上山捕猎正好路过,并没有不良企图。他操着黎族方言嘟哝了几句,女知青也不知他说些什么,只是蜷缩在斜坡的草丛中发抖。直到那男人带着狗走远后,惊魂未定的她才挣扎着从斜坡爬上环山行。
这时,女知青才想起有一位海口男知青在隔壁林段割胶,就连声呼喊,惊动了那位男知青,他跑过来后看到女知青浑身上下沾满了胶水,一时不知所措。如不赶快清洗,粘在头发的胶水很快就会凝固,这就不好办了。可现在胶林里没有水源,磨胶刀的脏水也倒掉了。怎么办?女知青低声向男知青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请求,就是在胶杯里撒一泡尿,好用尿水洗掉头发上的胶水,男知青万分为难,最后婉言拒绝了。他答应女知青帮忙把余下林段的胶水收完,催促她赶快回连队去想办法。
女知青一路小跑回连队,在路上碰到了铁姑娘班的徐班长。徐班长是农场老职工,处理这些麻烦事有经验,知道水不能溶化风干的胶水,但气味难闻的煤油可以。就把女知青带到自家的小伙房,用点灯的煤油帮她反复搓洗粘满胶水的头发。不一会儿,头发上的胶水就全部被洗干净了。这个秘密一直到我们最近建立连队微信群,当事人才讲给大家听。当成笑话。
大山里的动物
上山下乡之前,我们除了逛动物园,没有别的机会看到或接触动物。来到这里后,见到圈养的猪、放牧的黄牛、放养的黑山羊,还有鱼塘里的鱼,觉得很兴奋。当时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我也曾受邀到老职工的小伙房,吃过豪猪(箭猪)和狐狸肉,野味真的好吃,难得一享口福。附近村庄黎胞捕猎有收获时,有时会在连部门口摆卖野猪肉、坡鹿肉等猎物肉类。黎胞曾经抬了一条四五米长活的蟒蛇从连队路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蛇类,啧啧称奇。有一次我去21连(前线队)水库游泳,刚走到水边,突然在草丛中窜出一头野猪,我还没回过神,它就嗖的一下跳到水里,不到十多分钟,就连刨带划游到水库对岸山坡,我十分吃惊,海南的野猪一点都不蠢啊!
说到最恐怖的动物,我觉得非蝎子莫属,本地人称山虾。胶林里潮湿,堆积大量腐叶,是山虾生长最好的地方。林段里每棵胶树上都装有胶杯架,收完胶后胶杯要放回架上,而山虾就最喜欢躲在胶杯里。我们半夜三更来到林段割胶,在天亮之前割完三四百棵树,非常匆忙。如果遇到“大割”,天亮前要割完七八百多棵树,更是万分紧张。割胶时,我们一般都是右手拿胶刀,左手三只手指捏着胶杯边沿,下刀沿着胶树割完表皮之后,就将手中的胶杯轮换挂在胶树上的杯子,盛放缓缓流出的胶水。在昏暗的电石灯下,专心、紧张、麻利地割胶,很难发现蛰伏在胶杯里的山虾。手拿胶杯时一不注意,就会被山虾尾巴毒刺扎到手指,十指连心,钻心的疼痛令人痛苦万分,疼痛一般会在“对时”(12个时辰)后缓解,也有人连续疼痛几天。我在割胶班工作的四年期间,曾经多次被蝎子蜇伤。除了蝎子,偏远处的胶林里还有毒蛇、蜈蚣等动物,树干还有变色龙,悄无声息地隐藏着。
有一段时间,连队不允许个人饲养鸡鸭和种菜,因关系到生活问题,后来又慢慢放开了。大概从1973年下半年起,饲养鸡鸭和种菜的多了起来,主要是自己吃或送人,很少有人往外售卖。一次,当地老乡挑着一箩筐刚出生不久的小鸡到连部卖,看到毛茸茸的小鸡,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掏了一块钱买了十只,回到宿舍把它们放到胶桶里养。当时只是出于好玩,随着小鸡一天天长大,胶桶已经容纳不下,后来一位与我很要好的老职工送来一个用木板钉的鸡笼,我把鸡笼放在宿舍门前的一棵苦楝树下,将十只小鸡放了进去,稍大一些就放养野外了。连队的独特环境是天然养鸡场,每天天一亮,小鸡就叽叽喳喳钻到胶林、草丛、水沟去觅食。到了中午,只要在宿舍门口“咕咕咕”地一呼,它们就会从四面八方飞奔回来,啄食撒在地上的米饭,然后又各奔东西。等到黄昏时,它们又在宿舍门口等候我们撒米饭,吃饱后就乖乖回到笼子里睡觉。一天到晚,完全不用我操心操劳,它们绝不会走错路迷失方向。
有一天,我在鸡群里发现一只麻栗色小母鸡窝在鸡笼里不动,我好奇地往鸡笼看看,过了一会儿,小母鸡“咯咯哒”叫了几声走出来,鸡笼里留下一只洁白的蛋。过了大概半个月时间,有一天,小母鸡又窝在笼里不想出来,原来它要孵小鸡了。我把它生下的鸡蛋全放进笼中用稻草做的孵窝里,大约过了一周,母鸡就带着已孵化的小鸡仔走出了笼子。直到我1975年离开连队回广州,这只麻栗色的小母鸡一茬又一茬地生鸡蛋、孵小鸡,为我们提供了最天然营养品。回城后,我们几个知青相聚时,还会提起那只功勋小母鸡——麻栗色的小母鸡。
有趣的文娱活动
在农场,蜗居在偏僻山沟的我们,刚开始时,每天的生活多是枯燥无味的,连队的篮球场本是“发泄”旺盛精力的好地方,可有时候收工回来(特别是开荒大会战的日子),累得腰酸背痛,剩下的力气都用来上冲凉房洗澡和到伙房打饭去了。我从广州背了一把吉他回农场,偶尔还可以弹弹琴消遣。后来,连队建起排球场,添了一张乒乓球台,知青又多了些娱乐项目。渐渐地,兴起“斗地主”形式打扑克,成了知青们工余时间新的娱乐活动。
不过,最令人向往的就是看电影了。在农场的七个年头,可能是路途太远和位置太偏僻,连队只放过两次电影,一次是场部电影队下连队放的,另一次是连队不知从哪里外请的电影队放的。那天的中午时分,大家把大伙房礼堂的四个窗户用厚棉被遮住,里面黑咕隆咚。外来电影队(只有一个人)放电影时,连张幕布都没有,画面就投影在坑坑洼洼的墙壁上。最搞笑的是,放电影的电源居然是我们连队一个潮州知青踩着单车供应的。也许是那潮州知青踩着踩着就没力了,或是他被电影内容所吸引,车速变慢电力不足,电影里面的声音一下子全部变声走调,电影放了一半,就出现了几次这样的情况。连长见此,马上叫了几个身强力壮的知青,轮流踩单车供电,才算把电影放完。那场电影结束后,大家都像是被“蒸笼”蒸过一般,个个浑身冒汗走出礼堂。不过看电影总比干重活好,回去洗个澡就可以了。
赤田驻军部队离我们连队有四五公里远,我们经常到那里的露天放映场看电影,自己带了凳子过去。最轰动是那一年放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藤桥公社十里八乡的人都涌到赤田,只为看一场源自海南的样板戏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大家都安安静静,沉浸于电影情节中,没有人大声说话,一直到电影放映结束。我们看到了海南的风土人情、黎族姑娘优美的舞蹈,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动。
1973年我探家返回时,带了一台两波段的广州产“珠江”牌半导体收音机回连队。那时国内大陆的娱乐新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收听香港台湾电台是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径之一,却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我那时已经搬到新建的收胶房,那里远离连队,在胶林旁边,而且是我一个人居住。每天晚上,连队的政治学习结束后,我就赶紧跑回收胶房宿舍,关紧门,用棉被捂着收音机,打开旋钮收听香港电台的超短波频道,经常收听的节目是搞笑的《十八楼C座》、专讲鬼故事的《夜半奇谈》。台湾的节目晚上时段基本播放流行歌曲,男歌星青山嗓子浑厚,女歌星尤雅歌喉软润,青山唱的《泪的小雨,寻梦园》,尤雅唱的《往事只能回味》,那时候听到只觉是天籁,余音绕梁。
1969年兵团成立不久,团部组建了宣传队和篮球队,我们连队的海口知青林碧珍(宣传队员)、广州知青吴秀娴(女篮队员)上调团部。记得团部宣传队曾经到我们连队演出,那天晚上,附近黎村不少群众也来观看演出。宣传队当时表演了什么节目已经忘了,只是演出之前,连队前面的大榕树下,竟然有位男队员拨弄一把吉他,我连忙走到他面前,向他请教弹奏吉他的方法,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广州知青,名叫沈文全。
劳动中长见识
当了割胶工才知道,只有完成六七百棵(大割)胶树割胶任务时,下午才可以休息;若平常只割三四百棵胶树时,那天下午是要干农活的。我们从读初中开始,每学期有两周下乡参加农忙活动,那时候最害怕下水田插秧、割水稻。谁知来到海南,连队居然有十多亩水田,种植了番薯、花生、甘蔗,还有糯米稻子。有一天下午,连长安排我们两个班10多人到水田插秧,我挽起裤脚刚下水田,还没插下几株秧苗,就听到邻近几个女知青又叫又喊,还三步并两脚跳上了田埂。原来她们个个细皮嫩肉,在插秧时搅动了水面,近处游弋的蚂蟥迅速赶来,毫不客气叮咬在小腿上。
来海南之前,曾听人说山蚂蟥无处不在,叮咬人于无形,吸饱血就悄悄溜走,只在你皮肤上留下流血不止的小窟窿。奇怪了,让人谈之色变的山蚂蟥,在连队没见过一条,倒是水田蚂蟥的肆虐领教了。我们几个男知青讪笑还没几分钟,就发现自己的小腿后侧不知何时已被蚂蟥吸附,赶紧对准蚂蟥用手拍落。那天插秧结束后,男女知青无人幸免,腿脚上血痕累累。
反观与我们一起插秧的老工人,似有天然排斥力,蚂蟥很少靠近。第二天,连队没有派知青去水田插秧,因为头天知青插下的秧苗大都歪歪扭扭不成行,有些没插实的整株浮在水面上。后来才知道山蚂蟥主要栖身于阴冷潮湿处,开发久的熟地及人居处并不适合它。水里的蚂蟥发现叮咬目标全靠听觉,而老工人插秧时是手动而腿脚站稳,蚂蟥听不到响声就注意不到。
在林段,给橡胶林压青施肥,首先要从连队猪栏牛栏把猪粪牛粪挑到指定的林段。一路上,猪粪牛粪的尿臊味直呛鼻孔,又不能快步走去林段,怕粪肥抛撒在路上。来回几趟挑肥后,要用砍岜刀把林段丛生的飞机草杂草砍下来,连着环山行厚厚的腐叶和堆积的猪牛粪混合沤晒几天,再把混合肥料抛洒到树株之间的一个个小坑里,好让橡胶树充分吸收养料。
只要不是头顶灼热的太阳,收获花生的农活是件既轻松又可以填饱肚子的工作,尽管带队去拔花生的连队干部在花生地里到处吆喝,但还是制止不住大家把刚拔下来的花生偷偷往嘴里送。特别是男知青,在花生地干了几天,嘴巴总是咀嚼不停,却没有一人因此拉肚子,个中原因可能是肚里的油水太少吧。
有时,知青被安排去挖番薯和木薯,连队的职工小孩听到后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一去地里,10多个小孩就跟在后面,我们每挖完一垄地,他们就拿着锄头翻地捡漏,往往会有不少收获。因为知青的挖掘技能太差,田地里遗漏下来确实不少。他们有时挖出完整大个的或有大半截的,就马上藏到草丛中,以免连队干部发现后没收。带队的连干部尽管也驱赶小孩们,但都明白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又是连队职工的孩子,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罢了。近年我们30多名各地知青回访农场的生产队(连队),有位广州知青还用挖木薯的事调侃当年的小孩——现在当了队长的张某某,大家都笑得不亦乐乎。
这条小路,多是人走和牛车过,也能通一辆汽车,一遇下雨天,泥泞又坑洼。一处聚居地,人们相互依存,无论叫什么(生产队或连队),都实则是一个村庄。这条长长的小路,是我当知青时落户的村庄往外走唯一的通途。当年,我曾赶着发出“吱吱呀呀”声响的牛车,一次又一次走在这条小路上,把生产队(连队)汇集的乳白胶水送到东风分场(一营)制胶厂。我也曾打着手电筒,从这小路摸黑赶着去四五公里外的赤田驻军部队看电影。也是这条小路,我踏着它松软的脊梁,回到我曾离开的地方……五十一年过去了,今天,我依然缱绻这条长长的小路,带着我的思念回到那魂牵梦萦的村庄。
1968年12月20日,我和同是广州第十四中学的饶建礼、陈干之、刘国培、吴伟湛、杨志彬、王美美、吴秀娴等人上山下乡来到海南岛,分在南田农场东风分场黄继光生产队,走进了农垦工人的行列。此时,农场总人口过万,职工人数五千多人,橡胶产量在海南农垦系统引人注目,下辖东风、黎场、爱国、红旗、长田、响水六个分场,我所在的东风分场是各分场之首,下面有丰收、东风、前线、前哨、前进队、黄继光六个生产队。
我们广州十四中学的100多名知青和广州二十中学的若干名知青,在场部集训了三天后,我与20多名同校同学(知青)登上农场一部“解放”牌汽车。行驶速度不太快的汽车,越过了藤桥河大桥,向东风分场奔去,一路上颠簸不止。汽车先是在丰收队停下,分到这里的知青陆续下车,因为东风、前线都没有分配知青,黄继光队在路途最末端,汽车搭载我们8人继续前行。
下了车,迎接我们的是支部书记杨传华、生产队长李干州。杨书记是退伍军人,好像是河北人,可能是长年劳累所致,显得有点病恹恹的,身体似乎不太硬实。李队长是广东电白人,他的外貌及动作,给人的印象就像他的名字,精干,风风火火。
我们住在茅草房,细条的茅草夹成片盖了屋顶,黄泥裹稻草糊成墙壁,木桩竹板加上干燥的禾秆就是睡床。从秀英港下船踏上海南的红土壤,曾经设想过农场的种种艰苦,也有了思想准备,毕竟大家都抱着一颗红心干革命,哪里艰苦哪里去的决心。可当我们放下行李,走进散发出潮湿腐霉气味的茅草房时,这种生活环境还是大大超出我的预想,接近黄昏,环顾生产队四周,一个令人烦心的现实是,因为偏远,这地方是东风分场唯一没有电力供应的生产队。
夜幕低垂,这个倚傍着山峦而建的小村庄(生产队),开始进入梦乡。我的睡床旁,黄泥墙壁开了一个两书本大小的窟窿,算是窗户吧。往外看过去,皎洁的月光给潺潺的溪水,笼上白玉般的轻纱。溪水的上方,黝黑的橡胶树环山行,折叠而上,萤火虫拽着不停闪烁的尾巴,在树林中飞舞穿梭。偶尔,树林的深处,传来鹧鸪的呜呜几声,短暂撕碎了寂静,不一会,又是万籁俱寂。在朦朦胧胧中,我度过了来生产队后的第一个夜晚。
1969年4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一并统辖广东湛江、徐闻和海南所有的垦区农场。南田农场改称三师八团,农场下辖的六个分场,分别为一至六营,我所在的黄继光队成了一营四连。当时连队宣读此命令时,知青无不激情澎湃,光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行列中的一员,这是那时革命青年梦寐以求的向往。而连队里的老职工和退伍兵对建设兵团的成立,却是处之泰然。
成立兵团当晚,在茅草房微弱的油灯光下,我给家里人写信,叮嘱他们以后回邮的地址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八团一营四连,并请求他们寄几套旧军装给我。
连队的生活
兵团成立之初,知青在闲暇时谈论最多的是,一旦与隔海相望的越南交战,我们这些屯垦戍边的热血青年,必定会手握钢枪,上阵杀敌,要时刻准备着。在连队橡胶林的某林段,有一座修建多年的战备山洞,能通过汽车。如果发生战事,走海榆东线公路的汽车可在八团改道,经过此处驶往中线公路的保亭、通什(现五指山),不用从崖县田独公社墟市绕弯,能节省不少时间。超强台风“玛琪”于1973年9月14日凌晨从琼海县登陆,波及全岛大部分地区,崖县境内也有狂风暴雨。13日中午接到团部通知后,我们连队除了干部和骨干,其他人员都在傍晚时进入了山洞躲避台风,一夜安然无事。
1974年1月,南海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我们满心欢喜,天真地认为,奔赴战场的时机来了。可是兴奋没几天,团部一纸命令下到连队,要在几天内紧急动员,收集木柴支援前线。大家对这道命令感到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四连地处山林,可连队大伙房日供三餐,每天消耗不少柴火,并没有多少存量。军令如山,连长只好抓紧动员,大伙房的大部分木柴、老职工房前屋后的木柴都贡献了出来。知青们则组成突击队,带上砍刀和钢锯到胶林里,砍伐已经死皮出不了胶水的橡胶树。没几天,连队的球场就垒起几大堆木柴,团部派来汽车运走了。就这样,我们知青的参战愿望没实现,倒是当了几天伐木工。
改制为兵团不久,本应是“秋雨绵绵无绝期”的时节,我们连队却遭遇了严重旱灾。都说海南岛的气候是四季皆夏、一雨成秋,可从4月开始直到11月,基本上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很少下雨。干旱导致地表蒸发加强,地下水源逐渐枯竭,而吸水性较强的大片橡胶林、防风林桉树又吸去大量地表水分,使得旱情更加严重。有一条小河围绕我们连队驻地,平日流水潺潺,奔流不息。老职工说从他们来到这里垦荒时起,这条小河未曾断流,这时却断流干涸了,裸露出龟裂的河床。
连队的两口水井都倚傍着小河,相隔没多远,紧靠大伙房的食用大水井有十多米深,山坡边上的洗浴小水井只有几米深。小水井很快就滴水无存,全连用水都只能依靠大水井,而附近村庄的黎族群众这时也跑过来打水。井底涌泉越来越小,水位一天天降低,眼看快要见底了。于是,连长命令几个懂爆破的退伍兵,在干涸的小水井底下埋放炸药,想看爆炸后的水井能出多少水,可引爆后掏了几米深,还只是流出小孩子尿水般大的细流。连长无奈,只好拨通上级电话紧急求援,于是团部从那天起,每天派汽车运送饮用水到连队。至于洗澡洗衣服,要到一公里外的大河边去。这种缺水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那段日子,种菜班的职工最辛苦,每天好几趟赶牛车装上大铁桶,到大河边运水浇菜地。
1973年夏季,我调去后勤班放牛,不用凌晨三四点钟起来割胶了。我每天都欢天喜地跟着放牛老职工,吆喝着20多头大大小小的水牛,把它们往山沟、林段、坡地驱赶。哪里水草丰盛,牛儿就往哪里钻,并不用牛倌多费心。不过,连队四周都有黎胞的水稻田,那是牛群万万不能进入的禁区。
看似惬意轻松的工作,不知不觉就干了半年。有一天下午放牛回来,我发现右膝盖擦伤了,而且红肿发胀,心想大概是放牛时穿着短裤,给野草树枝碰剐的,晚上到卫生所涂抹点红汞水就可以消炎了。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去放牛,感觉患处还是隐隐作痛,仗着自己年轻,不当一回事。可是到了晚上,头部开始裂痛,整个人仿佛掉进火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凌晨四点多时,连队提醒职工割早胶的钟敲响了,卫生员也到各个点巡查,看有没有因伤病不能割胶的。他来到我们宿舍,我说发烧了很难受,他没细问,给了一包止痛退热散就走了。
天亮后,割完胶回来的知青帮我从伙房端来面条,我才勉强坐起来。他见我身上到处是红斑很惊讶,我说大概是吃了退烧药的缘故。我想下床来走动,见膝盖患处已肿起一个大疱,疼痛难忍。到了下午,高烧依然不退,身上的红斑点越来越多。一个平时交情不错的老职工来到宿舍,看到我当时的情况,忙建议去团部卫生队治疗。卫生员可能是认为问题不大,还是不够重视,没有任何表示。我一看不对头,不顾自己头有点昏昏沉沉,赶紧坐上了老职工的单车尾座直奔团部。
到了团部卫生队,因为发高烧,我很快就陷入昏迷状态,所有住院手续都是老职工帮我办理。我不知道是怎么就躺在病床上了,迷迷糊糊感觉身边人来人往,大概是在住院部的走廊。不知过了多久,有些光亮刺激我沉重的眼帘,一幅幅洁白的轻纱在我面前飘动。这时,一个温柔的女声在我耳边响起:“你哪里不舒服啊?”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用手指了一下膝盖。接下来,她们说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了。在朦胧中,感觉臀部被扎了一针,膝盖被捣鼓了好一会儿。那天晚上,头昏沉沉的,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睡醒过来,头部的沉重和疼痛减少了,膝盖患处也好了一点。我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惊讶地发现,病床和地上有许多从患处流出的脓液。给我换药的护士说是细菌感染,引起血液中毒,积聚多了散发不出来,导致高烧不退。她还说,你好在遇上陈护士长给你治疗,不然昨晚小命不保,她的医术比有的医生还厉害呢。后来我听说了,陈护士长原是彭德怀元帅的护士,因政治原因,被下放到了改制前的南田农场医院。
那时年轻,住院部的医疗条件比较好,治疗也算及时,不到十天就出院了。回到连队,连长大概是怕派我去放牛又出状况,改安排我去收胶站当收胶员,那可是一个不错的工种。
一张乒乓球桌
1973年上半年,我们连队迎来第三任连长张万德(后兼任指导员),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连队的各项工作以及生活环境大为改观。张连长负责全面,唐捷副连长分管后勤,杨绪林副指导员分管政治思想工作及知青工作。
唐捷副连长是从团部汽车队调来的,管后勤生活很有一套。为了养好原有的存栏猪,她增派了一个有饲养经验的电白职工。她又要求看守木薯山的职工饲养几只黑山羊和一大群鸡,还在鱼塘投放了大量的罗非鱼。大伙房虽然不是顿顿有鱼肉,可比以前好多了。特别是蔬菜,就算是台风暴雨季节,连队新鲜蔬菜一时供应不上时,仓库储备的冬瓜、南瓜,也够吃上一段日子。
杨副指导员是退伍兵,文化水平不高,但待人和蔼细心。他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像是一位大哥哥。他做思想政治工作很有一套,总是联系实际、对症下药,注意工作方法,不讲空头政治,不搞形式宣教。对于知青工作,他侧重于思想状况、生活层面、合理要求,认真倾听知青的呼声,尽量关心爱护。比如,我们建议开辟排球场,他很快就带领大家搞义务劳动,将篮球场上方的土坡平整成平台,埋下两根树桩,又弄来排球网和排球,使知青的工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一天下午,我路过连部,看到杨副指导员一个人在看报纸,就向他建议制作一张乒乓球台,他与连里木工商量后就答复了我,但要求我提供大致图纸及具体尺寸。想来木工平时多是修理工具、用具,制作乒乓球台的确有难度。我马上给家里写信,叫家人去广州的文体商店测量乒乓球台尺寸,很快就把图纸尺寸交到木匠的手里。两个星期过去了,木工棚仍然没有打造球台的迹象,我以为是修理工作太忙。又过了两个星期,还是没有动静,这时候我真的有点急了,去连部找到杨副指导员问情况。
杨副指导员也急了起来,就去找木工了解情况和催促尽快动工,一问才知道是做球台的铁钉不够用。虽说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总不至于连几斤铁钉都解决不了吧,我请杨副指导员写了张证明,自己抽空去买。我在第二天下午把连队的胶水送到营部制胶厂后,就走路直奔团部商店,谁知去到那里,售货员告知铁钉是供销社统销产品,要我去藤桥公社供销社看看。于是我又折返到藤桥供销社,递上购买铁钉证明,终于买了几斤宝贝般的铁钉回到连队。
在杨副指导员的得力支持下,乒乓球台很快做好了,连队又购置了两副球拍和球网。这下,爱打乒乓球的知青们可热闹了,一有时间就兴致勃勃地玩起来,几乎个个都踊跃参加乒乓球擂台比赛。后来,有个普宁知青因为球打得好,被营部选上去参加团部的比赛,还得了第三名呢,可把大家乐坏了。
“童子尿”
1969年底至1970年初的一天,连里一位海口女知青完成割胶任务,磨好割胶刀后,开始提着胶桶收集胶水。没走几个环山行,突然从草丛中窜出一条大狗,后面还跟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这位女知青负责的林段,在最偏僻的一个山坳下。虽说她没听说这地方有女生被侵害的事情发生,但在这荒山野岭,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突然站在面前,吓得她三魂五魄不见了,愣了一下后,回过神来转身就跑。可山坳处的林段,环山行宽度太窄,没留神一脚踏空,接连在环山行斜坡翻了几个滚,手上提着的胶桶把持不住,粘糊糊、白花花的胶水全都泼洒出来,有好多弄到了她的头发、脸庞和身子上。
那位黎族男子也被吓着了,原来他是连队附近村庄的村民,带着猎狗上山捕猎正好路过,并没有不良企图。他操着黎族方言嘟哝了几句,女知青也不知他说些什么,只是蜷缩在斜坡的草丛中发抖。直到那男人带着狗走远后,惊魂未定的她才挣扎着从斜坡爬上环山行。
这时,女知青才想起有一位海口男知青在隔壁林段割胶,就连声呼喊,惊动了那位男知青,他跑过来后看到女知青浑身上下沾满了胶水,一时不知所措。如不赶快清洗,粘在头发的胶水很快就会凝固,这就不好办了。可现在胶林里没有水源,磨胶刀的脏水也倒掉了。怎么办?女知青低声向男知青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请求,就是在胶杯里撒一泡尿,好用尿水洗掉头发上的胶水,男知青万分为难,最后婉言拒绝了。他答应女知青帮忙把余下林段的胶水收完,催促她赶快回连队去想办法。
女知青一路小跑回连队,在路上碰到了铁姑娘班的徐班长。徐班长是农场老职工,处理这些麻烦事有经验,知道水不能溶化风干的胶水,但气味难闻的煤油可以。就把女知青带到自家的小伙房,用点灯的煤油帮她反复搓洗粘满胶水的头发。不一会儿,头发上的胶水就全部被洗干净了。这个秘密一直到我们最近建立连队微信群,当事人才讲给大家听。当成笑话。
大山里的动物
上山下乡之前,我们除了逛动物园,没有别的机会看到或接触动物。来到这里后,见到圈养的猪、放牧的黄牛、放养的黑山羊,还有鱼塘里的鱼,觉得很兴奋。当时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我也曾受邀到老职工的小伙房,吃过豪猪(箭猪)和狐狸肉,野味真的好吃,难得一享口福。附近村庄黎胞捕猎有收获时,有时会在连部门口摆卖野猪肉、坡鹿肉等猎物肉类。黎胞曾经抬了一条四五米长活的蟒蛇从连队路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蛇类,啧啧称奇。有一次我去21连(前线队)水库游泳,刚走到水边,突然在草丛中窜出一头野猪,我还没回过神,它就嗖的一下跳到水里,不到十多分钟,就连刨带划游到水库对岸山坡,我十分吃惊,海南的野猪一点都不蠢啊!
说到最恐怖的动物,我觉得非蝎子莫属,本地人称山虾。胶林里潮湿,堆积大量腐叶,是山虾生长最好的地方。林段里每棵胶树上都装有胶杯架,收完胶后胶杯要放回架上,而山虾就最喜欢躲在胶杯里。我们半夜三更来到林段割胶,在天亮之前割完三四百棵树,非常匆忙。如果遇到“大割”,天亮前要割完七八百多棵树,更是万分紧张。割胶时,我们一般都是右手拿胶刀,左手三只手指捏着胶杯边沿,下刀沿着胶树割完表皮之后,就将手中的胶杯轮换挂在胶树上的杯子,盛放缓缓流出的胶水。在昏暗的电石灯下,专心、紧张、麻利地割胶,很难发现蛰伏在胶杯里的山虾。手拿胶杯时一不注意,就会被山虾尾巴毒刺扎到手指,十指连心,钻心的疼痛令人痛苦万分,疼痛一般会在“对时”(12个时辰)后缓解,也有人连续疼痛几天。我在割胶班工作的四年期间,曾经多次被蝎子蜇伤。除了蝎子,偏远处的胶林里还有毒蛇、蜈蚣等动物,树干还有变色龙,悄无声息地隐藏着。
有一段时间,连队不允许个人饲养鸡鸭和种菜,因关系到生活问题,后来又慢慢放开了。大概从1973年下半年起,饲养鸡鸭和种菜的多了起来,主要是自己吃或送人,很少有人往外售卖。一次,当地老乡挑着一箩筐刚出生不久的小鸡到连部卖,看到毛茸茸的小鸡,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掏了一块钱买了十只,回到宿舍把它们放到胶桶里养。当时只是出于好玩,随着小鸡一天天长大,胶桶已经容纳不下,后来一位与我很要好的老职工送来一个用木板钉的鸡笼,我把鸡笼放在宿舍门前的一棵苦楝树下,将十只小鸡放了进去,稍大一些就放养野外了。连队的独特环境是天然养鸡场,每天天一亮,小鸡就叽叽喳喳钻到胶林、草丛、水沟去觅食。到了中午,只要在宿舍门口“咕咕咕”地一呼,它们就会从四面八方飞奔回来,啄食撒在地上的米饭,然后又各奔东西。等到黄昏时,它们又在宿舍门口等候我们撒米饭,吃饱后就乖乖回到笼子里睡觉。一天到晚,完全不用我操心操劳,它们绝不会走错路迷失方向。
有一天,我在鸡群里发现一只麻栗色小母鸡窝在鸡笼里不动,我好奇地往鸡笼看看,过了一会儿,小母鸡“咯咯哒”叫了几声走出来,鸡笼里留下一只洁白的蛋。过了大概半个月时间,有一天,小母鸡又窝在笼里不想出来,原来它要孵小鸡了。我把它生下的鸡蛋全放进笼中用稻草做的孵窝里,大约过了一周,母鸡就带着已孵化的小鸡仔走出了笼子。直到我1975年离开连队回广州,这只麻栗色的小母鸡一茬又一茬地生鸡蛋、孵小鸡,为我们提供了最天然营养品。回城后,我们几个知青相聚时,还会提起那只功勋小母鸡——麻栗色的小母鸡。
有趣的文娱活动
在农场,蜗居在偏僻山沟的我们,刚开始时,每天的生活多是枯燥无味的,连队的篮球场本是“发泄”旺盛精力的好地方,可有时候收工回来(特别是开荒大会战的日子),累得腰酸背痛,剩下的力气都用来上冲凉房洗澡和到伙房打饭去了。我从广州背了一把吉他回农场,偶尔还可以弹弹琴消遣。后来,连队建起排球场,添了一张乒乓球台,知青又多了些娱乐项目。渐渐地,兴起“斗地主”形式打扑克,成了知青们工余时间新的娱乐活动。
不过,最令人向往的就是看电影了。在农场的七个年头,可能是路途太远和位置太偏僻,连队只放过两次电影,一次是场部电影队下连队放的,另一次是连队不知从哪里外请的电影队放的。那天的中午时分,大家把大伙房礼堂的四个窗户用厚棉被遮住,里面黑咕隆咚。外来电影队(只有一个人)放电影时,连张幕布都没有,画面就投影在坑坑洼洼的墙壁上。最搞笑的是,放电影的电源居然是我们连队一个潮州知青踩着单车供应的。也许是那潮州知青踩着踩着就没力了,或是他被电影内容所吸引,车速变慢电力不足,电影里面的声音一下子全部变声走调,电影放了一半,就出现了几次这样的情况。连长见此,马上叫了几个身强力壮的知青,轮流踩单车供电,才算把电影放完。那场电影结束后,大家都像是被“蒸笼”蒸过一般,个个浑身冒汗走出礼堂。不过看电影总比干重活好,回去洗个澡就可以了。
赤田驻军部队离我们连队有四五公里远,我们经常到那里的露天放映场看电影,自己带了凳子过去。最轰动是那一年放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藤桥公社十里八乡的人都涌到赤田,只为看一场源自海南的样板戏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大家都安安静静,沉浸于电影情节中,没有人大声说话,一直到电影放映结束。我们看到了海南的风土人情、黎族姑娘优美的舞蹈,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动。
1973年我探家返回时,带了一台两波段的广州产“珠江”牌半导体收音机回连队。那时国内大陆的娱乐新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收听香港台湾电台是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径之一,却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我那时已经搬到新建的收胶房,那里远离连队,在胶林旁边,而且是我一个人居住。每天晚上,连队的政治学习结束后,我就赶紧跑回收胶房宿舍,关紧门,用棉被捂着收音机,打开旋钮收听香港电台的超短波频道,经常收听的节目是搞笑的《十八楼C座》、专讲鬼故事的《夜半奇谈》。台湾的节目晚上时段基本播放流行歌曲,男歌星青山嗓子浑厚,女歌星尤雅歌喉软润,青山唱的《泪的小雨,寻梦园》,尤雅唱的《往事只能回味》,那时候听到只觉是天籁,余音绕梁。
1969年兵团成立不久,团部组建了宣传队和篮球队,我们连队的海口知青林碧珍(宣传队员)、广州知青吴秀娴(女篮队员)上调团部。记得团部宣传队曾经到我们连队演出,那天晚上,附近黎村不少群众也来观看演出。宣传队当时表演了什么节目已经忘了,只是演出之前,连队前面的大榕树下,竟然有位男队员拨弄一把吉他,我连忙走到他面前,向他请教弹奏吉他的方法,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广州知青,名叫沈文全。
劳动中长见识
当了割胶工才知道,只有完成六七百棵(大割)胶树割胶任务时,下午才可以休息;若平常只割三四百棵胶树时,那天下午是要干农活的。我们从读初中开始,每学期有两周下乡参加农忙活动,那时候最害怕下水田插秧、割水稻。谁知来到海南,连队居然有十多亩水田,种植了番薯、花生、甘蔗,还有糯米稻子。有一天下午,连长安排我们两个班10多人到水田插秧,我挽起裤脚刚下水田,还没插下几株秧苗,就听到邻近几个女知青又叫又喊,还三步并两脚跳上了田埂。原来她们个个细皮嫩肉,在插秧时搅动了水面,近处游弋的蚂蟥迅速赶来,毫不客气叮咬在小腿上。
来海南之前,曾听人说山蚂蟥无处不在,叮咬人于无形,吸饱血就悄悄溜走,只在你皮肤上留下流血不止的小窟窿。奇怪了,让人谈之色变的山蚂蟥,在连队没见过一条,倒是水田蚂蟥的肆虐领教了。我们几个男知青讪笑还没几分钟,就发现自己的小腿后侧不知何时已被蚂蟥吸附,赶紧对准蚂蟥用手拍落。那天插秧结束后,男女知青无人幸免,腿脚上血痕累累。
反观与我们一起插秧的老工人,似有天然排斥力,蚂蟥很少靠近。第二天,连队没有派知青去水田插秧,因为头天知青插下的秧苗大都歪歪扭扭不成行,有些没插实的整株浮在水面上。后来才知道山蚂蟥主要栖身于阴冷潮湿处,开发久的熟地及人居处并不适合它。水里的蚂蟥发现叮咬目标全靠听觉,而老工人插秧时是手动而腿脚站稳,蚂蟥听不到响声就注意不到。
在林段,给橡胶林压青施肥,首先要从连队猪栏牛栏把猪粪牛粪挑到指定的林段。一路上,猪粪牛粪的尿臊味直呛鼻孔,又不能快步走去林段,怕粪肥抛撒在路上。来回几趟挑肥后,要用砍岜刀把林段丛生的飞机草杂草砍下来,连着环山行厚厚的腐叶和堆积的猪牛粪混合沤晒几天,再把混合肥料抛洒到树株之间的一个个小坑里,好让橡胶树充分吸收养料。
只要不是头顶灼热的太阳,收获花生的农活是件既轻松又可以填饱肚子的工作,尽管带队去拔花生的连队干部在花生地里到处吆喝,但还是制止不住大家把刚拔下来的花生偷偷往嘴里送。特别是男知青,在花生地干了几天,嘴巴总是咀嚼不停,却没有一人因此拉肚子,个中原因可能是肚里的油水太少吧。
有时,知青被安排去挖番薯和木薯,连队的职工小孩听到后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一去地里,10多个小孩就跟在后面,我们每挖完一垄地,他们就拿着锄头翻地捡漏,往往会有不少收获。因为知青的挖掘技能太差,田地里遗漏下来确实不少。他们有时挖出完整大个的或有大半截的,就马上藏到草丛中,以免连队干部发现后没收。带队的连干部尽管也驱赶小孩们,但都明白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又是连队职工的孩子,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罢了。近年我们30多名各地知青回访农场的生产队(连队),有位广州知青还用挖木薯的事调侃当年的小孩——现在当了队长的张某某,大家都笑得不亦乐乎。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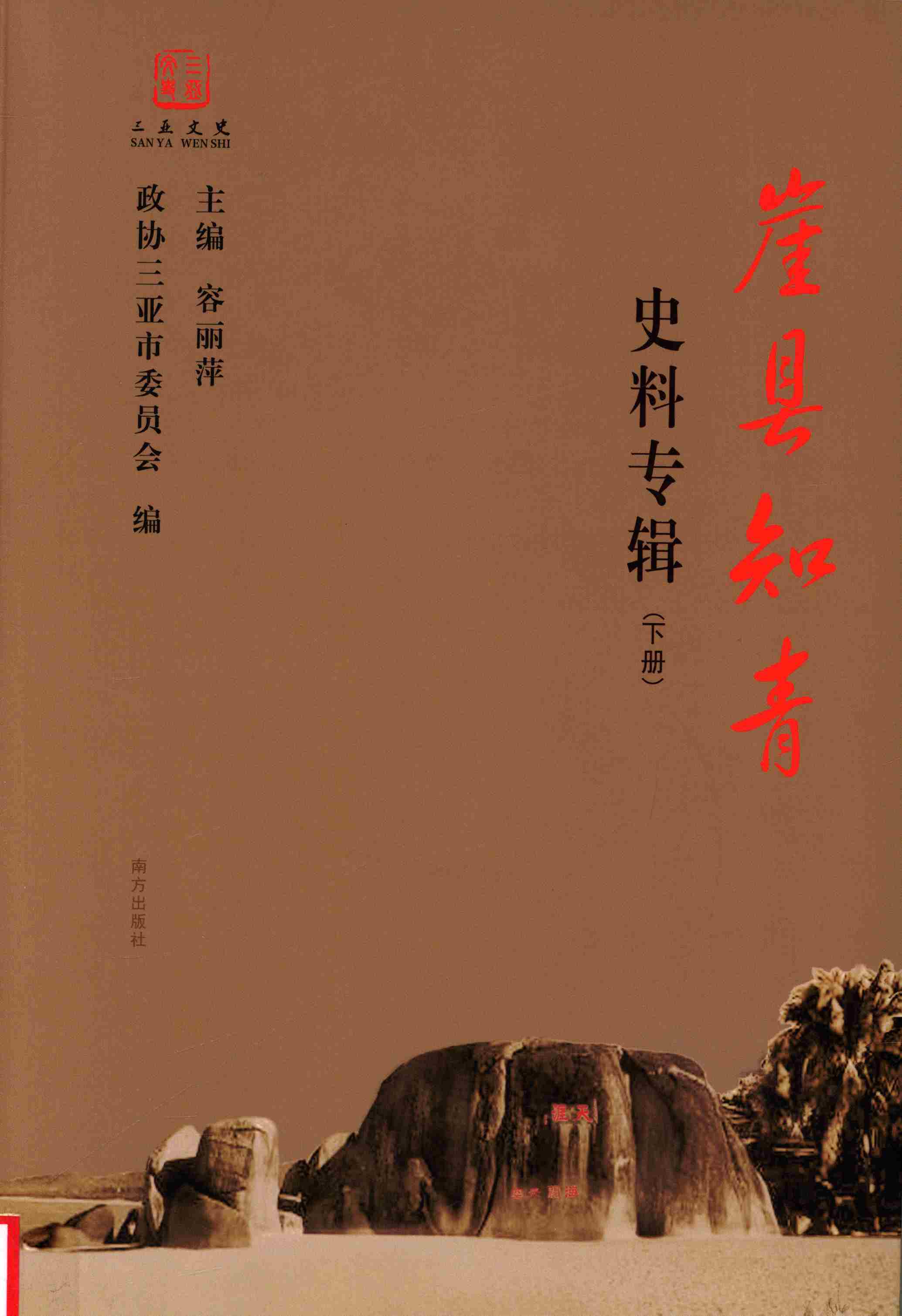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下册》
出版者:南方出版社
本书共有79篇文稿:港西(4篇)公社、梅山公社(7篇)、其他(2篇)3处安置点13篇知青回忆录;垦区南田(32篇)、南新(3篇)、南岛(11篇)、立才(5篇)、南滨(15篇)5个农场66篇知青回忆录。
阅读
相关机构
南田农场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崖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