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田故事
| 内容出处: |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下册》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1714 |
| 颗粒名称: | 南田故事 |
| 分类号: | K262 |
| 页数: | 8 |
| 页码: | 83-90 |
| 摘要: | 本文主要讲述了身为一名知青,刚到农场的艰苦生活,包括在橡胶林里割胶、除草、施肥、种植等农活,还有义务劳动、扛运木柴等体力活。整个环境和生活都十分艰苦,但是革命时期的种种宣传,让作者和许多年轻人充满了热血和使命感,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多做贡献。 |
| 关键词: | 艰苦生活 橡胶林 农场 |
内容
1968年12月底,我只身离开寒冷的武汉,坐火车、乘海船、换汽车,历经五天,终于到达了南田农场前锋队(兵团时期称三师八团21连),开始了崖县知青生活。
初到前锋队
被大片橡胶林所怀抱的前锋队驻地,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平”。
驻地的东、西、南三面是高坡,建有瓦房或茅草房的职工宿舍;中间是一块平地,有食堂、队部、幼儿园;北面的溪流七八米宽,水不深,上游有一条水坝,坝面也是道路,下游有一座独木桥。
宿舍建在斜坡上,房屋地面不平,每间房摆三张床,床脚要用石头垫平,活动空间窄小,连转身都勉强。各人床头贴有一张毛主席像,一张旧课桌放日用品,一张中板凳平常坐,几个胶桶用于洗浴。
南坡是驻地最高处,搭了3米高的木台子当广播站,使用纸质扩音筒广播,这个土喇叭很起作用,是主要的消息来源。队长或书记每天广播工作安排、各种通知、生产情况、好人好事。我们知青每天傍晚,轮流到台子上读报,但报纸往往是过期的。
每家都有三五个孩子,那时能买到的布料只有两三种,缝纫样式也不多。所以大人和小孩穿的衣服颜色单调,样式相似。这里的孩子长得特像爸妈,有人说是女人怀孕时很少见到外人的缘故,如果衣服、发型也相同,想必小孩会是大人的微缩版。说实在的,我在一段时间里,分不清谁是谁、哪家跟哪家,总觉得差别不大。
艰苦的磨练
从大城市到偏远山区,从初中生到农工,这个转换实在太快。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艰难的环境、艰苦的劳动对于我,是脱胎换骨般的磨练,尽管我在学校表现优秀、信心满满,现在要从头做起,心里没有底。
橡胶林已全面开割,我来到队里后,跟着学了个把月,就开始到树位割胶了。割胶工是很辛苦的,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戴上头灯去胶林割胶,一上午要跑十几里地。割夜胶是对我最大的考验,在家时我从来不敢独自走夜路,现在要独自在黑暗的胶林里割胶,几百米范围内只有我一个人,真的好害怕!
我刚到海南岛时水土不服,加上每天穿着塑料凉鞋(当时没有胶鞋卖)在胶林里跑,脚上总被胶籽壳和树枝划伤。夜里胶林里露水大、湿气重,往往上半身被汗水湿透,下半身裤腿被露水打湿,太阳出来后又将湿衣服晒干。这没办法,在新环境里,困难再大也要克服。
胶林同样是不平的,有的在山边,有的在半山腰。胶林里道路崎岖,野草蔓蔓,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窜来窜去。有时在夜晚,队里的牛跑到胶林里,卧在草丛中睡觉,一听见脚步声,就突然站起来,用胶灯照射过去,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像是见到鬼,真是吓死人!
胶林里经常有蝙蝠飞来飞去乱窜,有时趴在树干上,或躲在胶杯里……有一次,有只蝙蝠趴在胶树割口上,想用胶刀把它推开,谁知道它嗖的一下子窜到我眼前,吓得我惊慌失措,乱舞手中胶刀,才把它赶走。但低头一看,胸前衣服上有血迹,还粘着一小块带血的皮肉,我头皮都麻了,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很恶心。我双腿发软无力,瘫坐在地上,一直等到天亮,才站起来继续割完胶。
我有一个树位很远,在本队的边缘地带,紧挨着黎族村庄的番薯地。有一天队里两点钟就出工,割到这里天还没亮,突然听到前方有一阵阵哗啦啦的响声,我顺着响声用头灯照过去,只见一个白影子在晃动,吓得我头发竖了起来,双腿发软,气喘不上,喊不出声来。我连滚带爬跑到隔壁班长的树位,看到了班长的头灯,才稍稍缓过气来……见了班长,我全身发抖,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
班长听我说了,又叫上一个老工人,一起走过去看。这时天已蒙蒙亮,走近刚才哗哗作响的地方,才知道是黎族老乡刚埋新坟,坟头上插满了纸幡儿,在风中摇曳作响……自那以后,许多年里我只要看见白色的飘带,仍会情不自禁地发怵!
在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年代里,我们上午割胶,下午给胶林除草、施肥,还要种木薯、红薯、花生、甘蔗。此外,还有无数的义务劳动。队里养猪,每人要交100斤的胶树果;队里烧砖,每人要交100斤的木柴;有时,要参加建窑烧砖……胶树果很轻,捡好多才够100斤,几乎耗去我所有的休息时间,直到离开前锋队时也没捡够。
烧砖用的木柴要到三四里外的高山密林去扛回,老工人已提前砍好树木,但这活儿也不轻松。那边是原始森林,野草丛生,林木茂密,爬到山顶已气喘吁吁。我找了一截最细的树木,让别人帮我放到肩膀上,顿时双腿打晃,几乎栽倒。我挺了挺腰,勉强站定了,紧紧咬着牙,一步步走下山去。山路崎岖且很陡峭,实在不好走,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扛回驻地。一过秤才58斤,没有完成任务,我怎么也不相信。以后的好多天,我的肩头、手脚、腰背,还隐隐作疼。
当时我们天天听到的宣传,就是天然橡胶是很重要的战备物资,美帝、苏修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每吨橡胶要用20吨大米换,影响了我国的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听了这些话,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精神振奋,决心多生产天然橡胶,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多做贡献。
记得在1970年底,团(场)部组织大会战,全连男女劳力都到大山深处的新连队(黎场分场新队)。我们背着行李,扛着劳动工具,走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这里已完成砍岜烧荒,要在石头多的山坡上,挖出环山行和长、宽、深各80厘米的胶树穴,每人每天定额4个。铁镐挖下闪火花,锄头脱把和卷刃,是常有的事。我在别人的帮助下,第一天勉强完成3个,但双手起了血泡,胳膊也疼痛,端饭碗都困难。晚上睡在露天地里,铺上草席挂上蚊帐,腰背疼得不能翻身。接连干了3天,最后全连终于完成任务。
有苦有乐的知青生活
连队里有专人在水边种空心菜,所以食堂每餐都煮空心菜,大家都吃怕了。种空心菜最简单,不用管就生长茂盛,炊事员在水边连摘带洗,就可以担回来下锅了。这儿的粮食就只有大米,我们天天都在吃,好想念家乡的馒头、包子、面条,但是没办法满足。
每次逢年过节时,营部都在小溪边架起大锅杀猪,各连队都来人领猪肉,每人可分到一斤。这时我们拿着猪肉到老工人家里去加工,简单地炒炒炖炖,没放什么佐料,一碗肉一顿就能吃光,一点也不觉得腻,肚子里没油水,也算是过节了!
我的肝脏有点肿大,医生说要多吃糖,家里就寄来一些水果糖,我每天都含两颗。糖果在那时也算奢侈品,轻易不能得到,后来我发现隔壁家的三岁的小女孩,总在怔怔地看着我吃糖果,实在是于心不忍,就把剩下的糖分给了几个孩子,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每个连队都要有文艺宣传队,21连(前锋队)暂时是空白点。我去了以后,书记就把组队的任务交给我。年轻人总是爱热闹,在一起唱唱跳跳,也能轻松、高兴、欢乐一下,这是件好事。我在学校时是文艺爱好者,也参加过一些宣传演出,好歹能模仿一些应时的节目,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红军不怕远征难》等舞蹈。我们宣传队在春节时拿出几个歌舞节目,得到了分场的好评,被选到总场汇演。书记很高兴,特地表扬了我。
后来书记又交给我新任务,每天晚上教大家跳“忠字舞”,书记自己带头学,以表对毛主席的忠心。多数的工人都很认真跟着做,但总是不习惯、不好意思,动作生硬,缺乏协调性,不得要领地乱舞,有时让人忍俊不禁。真正跳得好的、跳得高兴的,还是队里的孩子们,又不用做作业,唱唱跳跳多好玩啊。倒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白天太劳累,晚上想放松,有敷衍的想法,又不敢不认真。
广州知青没啥事,我却水土不服,身上到处长脓疱,腿上、手臂上长,连腋下、胸前、背后、屁股上这些隐蔽处也长,特别是一条腿上长了二十多个。眼睛还长挑针(麦粒肿),左右眼、上下眼皮轮着来。连里卫生室只有鱼石脂黑膏药、紫药水,我又贴又擦的,旧疱刚好新的又长,没完没了。我眼睛睁不开、手放不下、脚跛着走,跟个残废人似的。真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痛苦不堪,心情糟糕透顶了。
直到全身烂到发高烧,我住进了团部医院,用上了青霉素,情况才有好转。奇怪,我从小都对青霉素过敏,到了这里却不会,或许是身体里热毒太重了吧。
一次地震虚惊
1969年下半年,某天下午正在胶林里分班组学习,我自带一张矮板凳,正架在一块废木板上坐,突然觉得小板凳猛烈摇晃了一下,我以为后面有人踩到木板,回头看却没有,太奇怪了!
连长在晚饭后才开会传达,海南兵团总部发紧急通知,说下午海南岛发生地震,有可能要发生更大的地震和海啸,让各团(场)各连(队)时刻做好防灾工作。连长随后布置,全连的人要做好准备,以鼓声为令,一接到紧急撤离通知,马上往后面的山上撤离。
这偏僻的深山老林,有事情要发生!我想象海啸就是很厉害的海浪吧,便要求加入青年突击队,参加抢险救灾的工作,连长同意了。青年突击队的任务,是在地震和海啸来临时,帮助队里的大人小孩向山上转移,保护队里的财产,抢险救灾等,一切行动听从团(场)部的指挥。
开完会,我们同住的三个知青回到宿舍,简单收拾了一下,把一些必要物品装入书包,盛上刚煮好的稀饭吃了几口,就听到鼓声响起及连长的喊声:“团部来了地震警报,全队立即撤离!……”我感觉到了种种紧张的气氛,又听见连长继续喊话:“大家不要害怕,不要慌乱,带好东西,牵好小孩,有次序地走。青年突击队帮助大家撤离后要回到队里……”
我从撤离人群中,拉起两个正在哭的小孩,牵着他们的手一路小跑上山去。在微弱的月光下,山路沟沟坎坎、扯扯拌拌,很是难走,我一手拉着一个孩子,但一路上比孩子摔跤还要多,后来倒是两个孩子扶着我走。跌跌撞撞走了将近三四十分钟,终于到了山脚下,把孩子交给了他妈,就同其他突击队员一起返回队里。
夜里我们正在巡逻,发现一个宿舍有人“呼哧!呼哧”搬东西,几个男知青迅速追上去,原来是两个连里的工人,从山上回来搬家里的贵重财产,即一部缝纫机、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是很金贵的大件,整个连里没几家拥有,就帮助他们把这些物品艰难地搬上山去。
我们在连部守着手摇电话机,眼睛死死地盯着桌上正反倒扣的胶杯,胶杯里满满装着水,只要有地震,胶杯里的水就会泼出来,是自制的地震仪。
到了后半夜,大家都有点熬不住了,肚子也饿了,想起宿舍里还有没吃完的稀饭,就回宿舍打开门,用头灯往房内一照,禁不住尖叫起来。只见一群大老鼠正在吃锅里、碗里的稀饭,桌上、地上都是饭渣,杯盘狼藉,惨不忍睹。吃的东西没有了,那就睡觉吧,和衣躺在床上很快就入睡了,一觉睡到天亮。
警报还没有解除,山上就有人陆陆续续地回来。食堂工人回来做饭菜,我们中午就往山上送,下午又往山上送水。山上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家在半山腰的杂树林里清理出一块稍平的地方,铺上草席,一家人挤在一个蚊帐里,睡不好,又没有水喝,吃饭只能靠食堂送,根本吃不饱。百把人乱哄哄地扎在一起,没有秩序,大人小孩随地大小便,四周臭烘烘的。
第三天下山的人多了些,回来的人都不想上山了,等着到团部开会的连长。连长回来后还是动员大家上山,说是警报还没有解除。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孩子们要上学。大家都陆续回家了,再没有谁把地震当回事了,说地震不死要被山上的蚊子咬死。
地震就这么不声不响地结束了,人们又回到每天依旧的生活之中。
水坝上的悲剧
21连的北面小溪,平时水不深、流不急,可以蹚水过去。每逢枯水季节,溪沟底下有很多大石头,坐在上面很好玩。如果有台风来,或连续几天下大雨,小溪就会涨水,甚至形成山洪暴泻而下。
就在小溪下游的对岸,有一个黎族同胞居住的村子,属藤桥公社管辖。连里的胶林周围,都是黎族农民的水田,因为溪水关系到21连和黎族村子的生产与生活,所以水坝一直由双方共同管理,大家互有往来,关系不错。谁能知道,后来发生的一件意外事故,竟然打破了原有的祥和与平静……
上游下了几天大雨,小溪水涨得很厉害。半夜里,我们连长叫上对面黎族村庄的黎族队长,两人一起到水坝上去察看水情。他们看见小溪的水位很高了,怕上游会有山洪冲来,两人商量决定要开闸放水。由于天气寒冷,两位领导说好先回去喝点酒,暖和暖和身子,再找几个人来一起干。
等我们连长带了知青过来,看到水闸已经打开,黎族队长却不见了,忙派人到他家去找,但家人说他早就出来了。于是大家四处寻找,还是没找到。后来有人在溪边的草丛里发现了他的衣服和鞋,才感到大事不好了,更多的人在水里、岸上,到处找他。
黎族村子的族人听说后,好多年轻人也参加寻找,整个夜晚都闹哄哄的。我住在山坡上连队的最后一排房子,晚上睡得死,起来时又迷糊,所以对晚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我们上午收工路过水坝时,看见水坝上游的水已经排干,溪底石头都露出来了,还是没有发现队长。又看到我们连的男知青手拉手排成人墙,从下游往水坝方向慢慢地在溪水中摸索,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
直到晌午后,才听说在水坝下游几米远的大石头缝里,找到了这位黎族队长的遗体。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在人们的想象中,黎族队长应是等人等不及,又担心洪水冲垮水坝,所以一人独自开闸放水,以致不幸殁世,真是可悲又可敬,让人备受震撼!
后来,再也没有人管理水坝了。一年以后,暴发的山洪冲垮了水坝……
人生新转折
当知青一年多后,有一天连长通知我去团(场)部。在路上就碰见了24连(长田队)的北京知青陈雁,得知她也接到通知。她告诉我,是团部想调我俩到总机班工作。
我俩刚走进团(场)部,就碰到原来农场武装部的干部老杜。他是“四野”的东北老兵,解放海南岛后就留在这里,为人很豪爽、幽默,很爱跟年轻人交朋友。我刚到农场时见过他,他夸奖我的字写得好。老杜告诉我们,新来的参谋长想增加总机的话务员,他就推荐了我俩,一来我们的口齿清楚、普通话说得好、声音好听,二来说我的字写得规整,以后可以兼做抄写文件之类的工作。老杜带我们见了参谋长,他姓杨,是现役军人,四十多岁,个子不高,胖胖的,笑眯眯的,挺和气的。杨参谋长跟我们说,通讯是战备很重要的工作,所以要调我俩来,加强团部总机班的工作。
几天后团(场)部的调令到了,通知我带上行李,到营部搭运胶水的卡车去团(场)部报到,连长让我坐连里的牛车过去。连队的牛车每天去一趟营部,算是连队的“班车”吧。我把行李放到车上,惬意地坐了上去,开始很新奇,想着就要离开生产队了,心情特别地爽。这牛车不仅走得慢,声音大,而且摇晃得厉害,一会儿就晃得头昏眼花,脖子要断了似的,我赶紧下车步行。
从连队到团(场)部总机班,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不用再每天半夜起床,大部分时间可以睡到自然醒。当时海南的地方通讯十分落后,团(场)部只有一个五十门的手摇式总机,转接电话全靠手摇,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在长田营部还有一个二十门的分机。团(场)部总机连通比较近的四个营部,长田分机连通比较远的两个分场。由于总机的门数少,拉的电话线也少,不够每个连队都有专线,所以,有的一条电话线上串两三个连队,规定铃声响两下是前一个连接,响三下是后一个连接。
全团(场)的电话线是与广播共用的,这是很麻烦的事。每天早上六点钟,晚上七点,我们将双联开关推到广播室的接线,全场所有连队的电话线路的双联开关,也都推到喇叭的接线位置,广播就可以开始了。晚上八点半停广播以后,就是电话最忙的时候,全团(场)布置生产、传达任务都在这个时候。由于线路少,就要充分利用线路的空隙,在最短的时间内接通电话。这时精神高度紧张,要脑子反应快;要眼快,看信号牌;要嘴快,呼叫用户;要手快插线、换线;摇发电机摇到手软。如果碰到连队没有人接电话,或是在串联的电话线上,不该接的连队接了,你还得说服他赶紧放下电话,要继续摇另一个连队的电话,真是费劲。
海南岛雨水多、雷电多、台风多。打雷时,我们就要断开线路,不能转接电话,怕雷电会击毁总机。只要台风一来,我们的总机绝对是到处不通的,本来所用的电线杆、铁丝就很简陋,经不起风吹雨打,每次狂风暴雨过后,总是倒得乱七八糟的。这时我们就跟着老班长翻山越岭去查线,大部分情况老班长心里有数,知道在什么地方杆子会倒,线会断,所以不至于要跑很远,一找一个准。如果是远处的线断了,就辗转通知当地的生产队去接线,但下次台风保准又会断。
1971年“9·13”事件后,全国的形势明显有一些改变,特别是知青政策宽松多了,全国陆续开始接收知青回城,湖北的一些工厂也开始招知青了,我的亲戚、同学都有被招到了城里的工厂,可是海南岛没有任何招工的消息,我的心里很着急。
有一天,我在团(场)部抄文件时,听说凡是有外单位的商调函,兵团司令部都会同意调离,并下调令让下面放人。这真是特好消息,这时我父亲已经从“走资派”解放了,要找一个招工单位,搞一个商调函应该不会很困难,我立即跟家里联系,家里很快就有商调函发到海南,没几天我的调令到了,手续也很快办好。没想到这么顺利,办得这么快,然后我就离开了海南。
在南田农场的3年多时间,是我人生中经历的艰苦磨炼的岁月,也是我生活阅历中的重要部分,我深知这段经历,是我人生历程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是我应该永远珍藏的人生财富!
初到前锋队
被大片橡胶林所怀抱的前锋队驻地,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平”。
驻地的东、西、南三面是高坡,建有瓦房或茅草房的职工宿舍;中间是一块平地,有食堂、队部、幼儿园;北面的溪流七八米宽,水不深,上游有一条水坝,坝面也是道路,下游有一座独木桥。
宿舍建在斜坡上,房屋地面不平,每间房摆三张床,床脚要用石头垫平,活动空间窄小,连转身都勉强。各人床头贴有一张毛主席像,一张旧课桌放日用品,一张中板凳平常坐,几个胶桶用于洗浴。
南坡是驻地最高处,搭了3米高的木台子当广播站,使用纸质扩音筒广播,这个土喇叭很起作用,是主要的消息来源。队长或书记每天广播工作安排、各种通知、生产情况、好人好事。我们知青每天傍晚,轮流到台子上读报,但报纸往往是过期的。
每家都有三五个孩子,那时能买到的布料只有两三种,缝纫样式也不多。所以大人和小孩穿的衣服颜色单调,样式相似。这里的孩子长得特像爸妈,有人说是女人怀孕时很少见到外人的缘故,如果衣服、发型也相同,想必小孩会是大人的微缩版。说实在的,我在一段时间里,分不清谁是谁、哪家跟哪家,总觉得差别不大。
艰苦的磨练
从大城市到偏远山区,从初中生到农工,这个转换实在太快。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艰难的环境、艰苦的劳动对于我,是脱胎换骨般的磨练,尽管我在学校表现优秀、信心满满,现在要从头做起,心里没有底。
橡胶林已全面开割,我来到队里后,跟着学了个把月,就开始到树位割胶了。割胶工是很辛苦的,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戴上头灯去胶林割胶,一上午要跑十几里地。割夜胶是对我最大的考验,在家时我从来不敢独自走夜路,现在要独自在黑暗的胶林里割胶,几百米范围内只有我一个人,真的好害怕!
我刚到海南岛时水土不服,加上每天穿着塑料凉鞋(当时没有胶鞋卖)在胶林里跑,脚上总被胶籽壳和树枝划伤。夜里胶林里露水大、湿气重,往往上半身被汗水湿透,下半身裤腿被露水打湿,太阳出来后又将湿衣服晒干。这没办法,在新环境里,困难再大也要克服。
胶林同样是不平的,有的在山边,有的在半山腰。胶林里道路崎岖,野草蔓蔓,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窜来窜去。有时在夜晚,队里的牛跑到胶林里,卧在草丛中睡觉,一听见脚步声,就突然站起来,用胶灯照射过去,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像是见到鬼,真是吓死人!
胶林里经常有蝙蝠飞来飞去乱窜,有时趴在树干上,或躲在胶杯里……有一次,有只蝙蝠趴在胶树割口上,想用胶刀把它推开,谁知道它嗖的一下子窜到我眼前,吓得我惊慌失措,乱舞手中胶刀,才把它赶走。但低头一看,胸前衣服上有血迹,还粘着一小块带血的皮肉,我头皮都麻了,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很恶心。我双腿发软无力,瘫坐在地上,一直等到天亮,才站起来继续割完胶。
我有一个树位很远,在本队的边缘地带,紧挨着黎族村庄的番薯地。有一天队里两点钟就出工,割到这里天还没亮,突然听到前方有一阵阵哗啦啦的响声,我顺着响声用头灯照过去,只见一个白影子在晃动,吓得我头发竖了起来,双腿发软,气喘不上,喊不出声来。我连滚带爬跑到隔壁班长的树位,看到了班长的头灯,才稍稍缓过气来……见了班长,我全身发抖,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
班长听我说了,又叫上一个老工人,一起走过去看。这时天已蒙蒙亮,走近刚才哗哗作响的地方,才知道是黎族老乡刚埋新坟,坟头上插满了纸幡儿,在风中摇曳作响……自那以后,许多年里我只要看见白色的飘带,仍会情不自禁地发怵!
在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年代里,我们上午割胶,下午给胶林除草、施肥,还要种木薯、红薯、花生、甘蔗。此外,还有无数的义务劳动。队里养猪,每人要交100斤的胶树果;队里烧砖,每人要交100斤的木柴;有时,要参加建窑烧砖……胶树果很轻,捡好多才够100斤,几乎耗去我所有的休息时间,直到离开前锋队时也没捡够。
烧砖用的木柴要到三四里外的高山密林去扛回,老工人已提前砍好树木,但这活儿也不轻松。那边是原始森林,野草丛生,林木茂密,爬到山顶已气喘吁吁。我找了一截最细的树木,让别人帮我放到肩膀上,顿时双腿打晃,几乎栽倒。我挺了挺腰,勉强站定了,紧紧咬着牙,一步步走下山去。山路崎岖且很陡峭,实在不好走,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扛回驻地。一过秤才58斤,没有完成任务,我怎么也不相信。以后的好多天,我的肩头、手脚、腰背,还隐隐作疼。
当时我们天天听到的宣传,就是天然橡胶是很重要的战备物资,美帝、苏修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每吨橡胶要用20吨大米换,影响了我国的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听了这些话,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精神振奋,决心多生产天然橡胶,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多做贡献。
记得在1970年底,团(场)部组织大会战,全连男女劳力都到大山深处的新连队(黎场分场新队)。我们背着行李,扛着劳动工具,走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这里已完成砍岜烧荒,要在石头多的山坡上,挖出环山行和长、宽、深各80厘米的胶树穴,每人每天定额4个。铁镐挖下闪火花,锄头脱把和卷刃,是常有的事。我在别人的帮助下,第一天勉强完成3个,但双手起了血泡,胳膊也疼痛,端饭碗都困难。晚上睡在露天地里,铺上草席挂上蚊帐,腰背疼得不能翻身。接连干了3天,最后全连终于完成任务。
有苦有乐的知青生活
连队里有专人在水边种空心菜,所以食堂每餐都煮空心菜,大家都吃怕了。种空心菜最简单,不用管就生长茂盛,炊事员在水边连摘带洗,就可以担回来下锅了。这儿的粮食就只有大米,我们天天都在吃,好想念家乡的馒头、包子、面条,但是没办法满足。
每次逢年过节时,营部都在小溪边架起大锅杀猪,各连队都来人领猪肉,每人可分到一斤。这时我们拿着猪肉到老工人家里去加工,简单地炒炒炖炖,没放什么佐料,一碗肉一顿就能吃光,一点也不觉得腻,肚子里没油水,也算是过节了!
我的肝脏有点肿大,医生说要多吃糖,家里就寄来一些水果糖,我每天都含两颗。糖果在那时也算奢侈品,轻易不能得到,后来我发现隔壁家的三岁的小女孩,总在怔怔地看着我吃糖果,实在是于心不忍,就把剩下的糖分给了几个孩子,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每个连队都要有文艺宣传队,21连(前锋队)暂时是空白点。我去了以后,书记就把组队的任务交给我。年轻人总是爱热闹,在一起唱唱跳跳,也能轻松、高兴、欢乐一下,这是件好事。我在学校时是文艺爱好者,也参加过一些宣传演出,好歹能模仿一些应时的节目,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红军不怕远征难》等舞蹈。我们宣传队在春节时拿出几个歌舞节目,得到了分场的好评,被选到总场汇演。书记很高兴,特地表扬了我。
后来书记又交给我新任务,每天晚上教大家跳“忠字舞”,书记自己带头学,以表对毛主席的忠心。多数的工人都很认真跟着做,但总是不习惯、不好意思,动作生硬,缺乏协调性,不得要领地乱舞,有时让人忍俊不禁。真正跳得好的、跳得高兴的,还是队里的孩子们,又不用做作业,唱唱跳跳多好玩啊。倒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白天太劳累,晚上想放松,有敷衍的想法,又不敢不认真。
广州知青没啥事,我却水土不服,身上到处长脓疱,腿上、手臂上长,连腋下、胸前、背后、屁股上这些隐蔽处也长,特别是一条腿上长了二十多个。眼睛还长挑针(麦粒肿),左右眼、上下眼皮轮着来。连里卫生室只有鱼石脂黑膏药、紫药水,我又贴又擦的,旧疱刚好新的又长,没完没了。我眼睛睁不开、手放不下、脚跛着走,跟个残废人似的。真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痛苦不堪,心情糟糕透顶了。
直到全身烂到发高烧,我住进了团部医院,用上了青霉素,情况才有好转。奇怪,我从小都对青霉素过敏,到了这里却不会,或许是身体里热毒太重了吧。
一次地震虚惊
1969年下半年,某天下午正在胶林里分班组学习,我自带一张矮板凳,正架在一块废木板上坐,突然觉得小板凳猛烈摇晃了一下,我以为后面有人踩到木板,回头看却没有,太奇怪了!
连长在晚饭后才开会传达,海南兵团总部发紧急通知,说下午海南岛发生地震,有可能要发生更大的地震和海啸,让各团(场)各连(队)时刻做好防灾工作。连长随后布置,全连的人要做好准备,以鼓声为令,一接到紧急撤离通知,马上往后面的山上撤离。
这偏僻的深山老林,有事情要发生!我想象海啸就是很厉害的海浪吧,便要求加入青年突击队,参加抢险救灾的工作,连长同意了。青年突击队的任务,是在地震和海啸来临时,帮助队里的大人小孩向山上转移,保护队里的财产,抢险救灾等,一切行动听从团(场)部的指挥。
开完会,我们同住的三个知青回到宿舍,简单收拾了一下,把一些必要物品装入书包,盛上刚煮好的稀饭吃了几口,就听到鼓声响起及连长的喊声:“团部来了地震警报,全队立即撤离!……”我感觉到了种种紧张的气氛,又听见连长继续喊话:“大家不要害怕,不要慌乱,带好东西,牵好小孩,有次序地走。青年突击队帮助大家撤离后要回到队里……”
我从撤离人群中,拉起两个正在哭的小孩,牵着他们的手一路小跑上山去。在微弱的月光下,山路沟沟坎坎、扯扯拌拌,很是难走,我一手拉着一个孩子,但一路上比孩子摔跤还要多,后来倒是两个孩子扶着我走。跌跌撞撞走了将近三四十分钟,终于到了山脚下,把孩子交给了他妈,就同其他突击队员一起返回队里。
夜里我们正在巡逻,发现一个宿舍有人“呼哧!呼哧”搬东西,几个男知青迅速追上去,原来是两个连里的工人,从山上回来搬家里的贵重财产,即一部缝纫机、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是很金贵的大件,整个连里没几家拥有,就帮助他们把这些物品艰难地搬上山去。
我们在连部守着手摇电话机,眼睛死死地盯着桌上正反倒扣的胶杯,胶杯里满满装着水,只要有地震,胶杯里的水就会泼出来,是自制的地震仪。
到了后半夜,大家都有点熬不住了,肚子也饿了,想起宿舍里还有没吃完的稀饭,就回宿舍打开门,用头灯往房内一照,禁不住尖叫起来。只见一群大老鼠正在吃锅里、碗里的稀饭,桌上、地上都是饭渣,杯盘狼藉,惨不忍睹。吃的东西没有了,那就睡觉吧,和衣躺在床上很快就入睡了,一觉睡到天亮。
警报还没有解除,山上就有人陆陆续续地回来。食堂工人回来做饭菜,我们中午就往山上送,下午又往山上送水。山上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家在半山腰的杂树林里清理出一块稍平的地方,铺上草席,一家人挤在一个蚊帐里,睡不好,又没有水喝,吃饭只能靠食堂送,根本吃不饱。百把人乱哄哄地扎在一起,没有秩序,大人小孩随地大小便,四周臭烘烘的。
第三天下山的人多了些,回来的人都不想上山了,等着到团部开会的连长。连长回来后还是动员大家上山,说是警报还没有解除。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孩子们要上学。大家都陆续回家了,再没有谁把地震当回事了,说地震不死要被山上的蚊子咬死。
地震就这么不声不响地结束了,人们又回到每天依旧的生活之中。
水坝上的悲剧
21连的北面小溪,平时水不深、流不急,可以蹚水过去。每逢枯水季节,溪沟底下有很多大石头,坐在上面很好玩。如果有台风来,或连续几天下大雨,小溪就会涨水,甚至形成山洪暴泻而下。
就在小溪下游的对岸,有一个黎族同胞居住的村子,属藤桥公社管辖。连里的胶林周围,都是黎族农民的水田,因为溪水关系到21连和黎族村子的生产与生活,所以水坝一直由双方共同管理,大家互有往来,关系不错。谁能知道,后来发生的一件意外事故,竟然打破了原有的祥和与平静……
上游下了几天大雨,小溪水涨得很厉害。半夜里,我们连长叫上对面黎族村庄的黎族队长,两人一起到水坝上去察看水情。他们看见小溪的水位很高了,怕上游会有山洪冲来,两人商量决定要开闸放水。由于天气寒冷,两位领导说好先回去喝点酒,暖和暖和身子,再找几个人来一起干。
等我们连长带了知青过来,看到水闸已经打开,黎族队长却不见了,忙派人到他家去找,但家人说他早就出来了。于是大家四处寻找,还是没找到。后来有人在溪边的草丛里发现了他的衣服和鞋,才感到大事不好了,更多的人在水里、岸上,到处找他。
黎族村子的族人听说后,好多年轻人也参加寻找,整个夜晚都闹哄哄的。我住在山坡上连队的最后一排房子,晚上睡得死,起来时又迷糊,所以对晚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我们上午收工路过水坝时,看见水坝上游的水已经排干,溪底石头都露出来了,还是没有发现队长。又看到我们连的男知青手拉手排成人墙,从下游往水坝方向慢慢地在溪水中摸索,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
直到晌午后,才听说在水坝下游几米远的大石头缝里,找到了这位黎族队长的遗体。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在人们的想象中,黎族队长应是等人等不及,又担心洪水冲垮水坝,所以一人独自开闸放水,以致不幸殁世,真是可悲又可敬,让人备受震撼!
后来,再也没有人管理水坝了。一年以后,暴发的山洪冲垮了水坝……
人生新转折
当知青一年多后,有一天连长通知我去团(场)部。在路上就碰见了24连(长田队)的北京知青陈雁,得知她也接到通知。她告诉我,是团部想调我俩到总机班工作。
我俩刚走进团(场)部,就碰到原来农场武装部的干部老杜。他是“四野”的东北老兵,解放海南岛后就留在这里,为人很豪爽、幽默,很爱跟年轻人交朋友。我刚到农场时见过他,他夸奖我的字写得好。老杜告诉我们,新来的参谋长想增加总机的话务员,他就推荐了我俩,一来我们的口齿清楚、普通话说得好、声音好听,二来说我的字写得规整,以后可以兼做抄写文件之类的工作。老杜带我们见了参谋长,他姓杨,是现役军人,四十多岁,个子不高,胖胖的,笑眯眯的,挺和气的。杨参谋长跟我们说,通讯是战备很重要的工作,所以要调我俩来,加强团部总机班的工作。
几天后团(场)部的调令到了,通知我带上行李,到营部搭运胶水的卡车去团(场)部报到,连长让我坐连里的牛车过去。连队的牛车每天去一趟营部,算是连队的“班车”吧。我把行李放到车上,惬意地坐了上去,开始很新奇,想着就要离开生产队了,心情特别地爽。这牛车不仅走得慢,声音大,而且摇晃得厉害,一会儿就晃得头昏眼花,脖子要断了似的,我赶紧下车步行。
从连队到团(场)部总机班,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不用再每天半夜起床,大部分时间可以睡到自然醒。当时海南的地方通讯十分落后,团(场)部只有一个五十门的手摇式总机,转接电话全靠手摇,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在长田营部还有一个二十门的分机。团(场)部总机连通比较近的四个营部,长田分机连通比较远的两个分场。由于总机的门数少,拉的电话线也少,不够每个连队都有专线,所以,有的一条电话线上串两三个连队,规定铃声响两下是前一个连接,响三下是后一个连接。
全团(场)的电话线是与广播共用的,这是很麻烦的事。每天早上六点钟,晚上七点,我们将双联开关推到广播室的接线,全场所有连队的电话线路的双联开关,也都推到喇叭的接线位置,广播就可以开始了。晚上八点半停广播以后,就是电话最忙的时候,全团(场)布置生产、传达任务都在这个时候。由于线路少,就要充分利用线路的空隙,在最短的时间内接通电话。这时精神高度紧张,要脑子反应快;要眼快,看信号牌;要嘴快,呼叫用户;要手快插线、换线;摇发电机摇到手软。如果碰到连队没有人接电话,或是在串联的电话线上,不该接的连队接了,你还得说服他赶紧放下电话,要继续摇另一个连队的电话,真是费劲。
海南岛雨水多、雷电多、台风多。打雷时,我们就要断开线路,不能转接电话,怕雷电会击毁总机。只要台风一来,我们的总机绝对是到处不通的,本来所用的电线杆、铁丝就很简陋,经不起风吹雨打,每次狂风暴雨过后,总是倒得乱七八糟的。这时我们就跟着老班长翻山越岭去查线,大部分情况老班长心里有数,知道在什么地方杆子会倒,线会断,所以不至于要跑很远,一找一个准。如果是远处的线断了,就辗转通知当地的生产队去接线,但下次台风保准又会断。
1971年“9·13”事件后,全国的形势明显有一些改变,特别是知青政策宽松多了,全国陆续开始接收知青回城,湖北的一些工厂也开始招知青了,我的亲戚、同学都有被招到了城里的工厂,可是海南岛没有任何招工的消息,我的心里很着急。
有一天,我在团(场)部抄文件时,听说凡是有外单位的商调函,兵团司令部都会同意调离,并下调令让下面放人。这真是特好消息,这时我父亲已经从“走资派”解放了,要找一个招工单位,搞一个商调函应该不会很困难,我立即跟家里联系,家里很快就有商调函发到海南,没几天我的调令到了,手续也很快办好。没想到这么顺利,办得这么快,然后我就离开了海南。
在南田农场的3年多时间,是我人生中经历的艰苦磨炼的岁月,也是我生活阅历中的重要部分,我深知这段经历,是我人生历程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是我应该永远珍藏的人生财富!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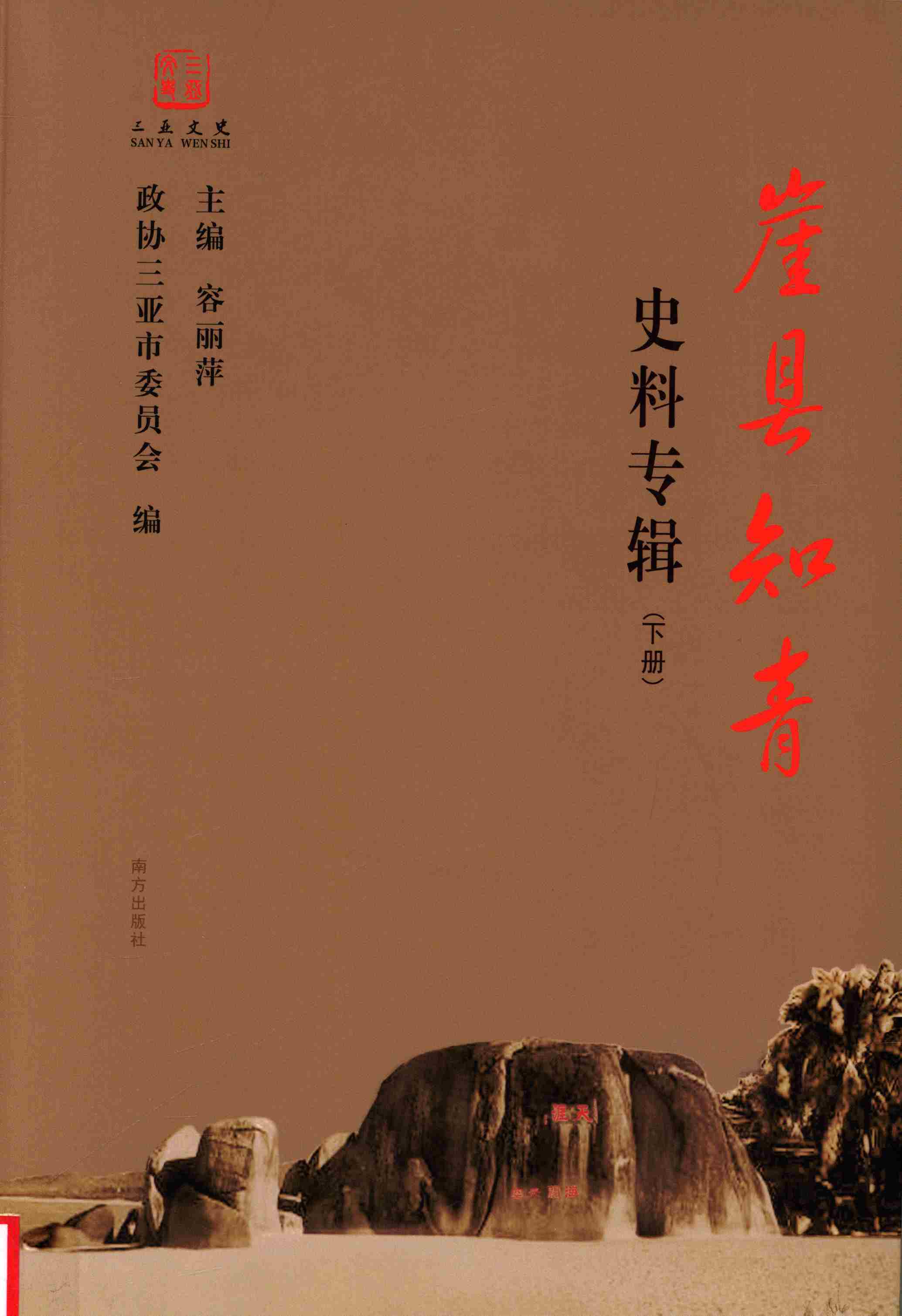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下册》
出版者:南方出版社
本书共有79篇文稿:港西(4篇)公社、梅山公社(7篇)、其他(2篇)3处安置点13篇知青回忆录;垦区南田(32篇)、南新(3篇)、南岛(11篇)、立才(5篇)、南滨(15篇)5个农场66篇知青回忆录。
阅读
相关机构
南田农场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崖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