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难忘
| 内容出处: |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上册》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1561 |
| 颗粒名称: | 知青往事难忘 |
| 分类号: | D432.9 |
| 页数: | 9 |
| 页码: | 180-188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作者在1973年上山下乡到崖县青年农场,并参加了工交战线、路线教育等知青生活的经历。作者在知青生活中通过教人种菜、注意劳动安全、进山伐木等事情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
| 关键词: | 知青 上山下乡 伐木 |
内容
我在崖县(今三亚市)上山下乡当知青两年多,在知青点的时间不长,倒是差不多成了“专职”工作队员。但是对我来说,不管是在知青点劳动还是参加农村路线教育工作队,都是特殊的锻炼和考验,许多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是一段抹不去的人生记忆。
在崖县青年农场
1973年7月我从崖县藤桥中学高中毕业,等到10月份藤桥糖厂开榨,就像往年一样做季节工,挣些钱补贴家用,同时体验当糖厂工人的乐趣。我的同届同学许政平、潘平也在厂里打工,我们平时很要好,经常在一起玩。有一天,许政平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县里要成立一个青年农场,就在羊栏公社水蛟大队的水蛟坡,专门安置工交战线、财贸战线报名上山下乡的职工子弟,他和潘平已经报名。我父母工作在藤桥二轻橡胶制品厂,隶属县二轻系统,我也是工交战线职工子弟。我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心切,于是没有多想,就请他帮我从藤桥糖厂这边报名,好和他们俩一起去。
事如所愿,在当年的12月27日,我正式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知青,和许政平、潘平一起被分到了崖县青年农场(后来改称国营三亚菜场)工交连,而另一个同学刘雁玲分到同场的财贸连。当时崖县工交战线委派的带队干部是周经源、黄瑞鹤两位大叔,分别担任工交连指导员、连长。那时我只有18岁,是共青团员,思想上要求进步,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对即将来临的知青生活很是期待。
我读高中时一直担任班长,多次参加过农村、农场、糖厂的生产劳动,熟悉农村生活,有不少农村朋友。来崖县青年农场后结交的三亚县城的朋友,都叫我们藤桥来的几个为“藤桥仔”。也许是履历表的原因,我在这里受到场领导及带队干部的重视。
到青年农场后,先是安排林海旺和我任工交连二排正、副排长。不久取消排级建制,安排梁生刚和我任第一、第二副连长(林保烈、周玉珠任第一、第二副指导员),我们紧密配合,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我的知青岁月由两部分构成:从上山下乡至1974年7月,我在知青点度过6个多月,连队的各项大事,从安排生活、早造生产,到备料建瓦房,我都一一参加了;从1974年7月至1976年2月,我搞路教一年零七个月,连续三次参加了路教工作队,并在第三次路教期间应征入伍。
在知青点的劳动生活,有几件事值得一谈。
第一件事是教人种菜。1974年元旦放假一天,返回农场后就进入正常工作,当时黄琼木等人正在营房后面平整土地,准备在这里育菜秧,菜种已经买回来了。但我近前一看,觉得情况不妙,原来是他们都从未种过菜,不知道如何播种,往地垄上浇了很多水,并和成稀泥状,打算撒上菜种。这样肯定不行,我立即制止他们。我在家里从小就种菜,吃不完时还送人,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了安排好连队的伙食,我们有必要自己种菜补充。于是我就耐心讲解,教会他们许多基本知识,还现场示范操作方法,使他们懂得了如何整地播种、培育菜秧……他们以后就干得不错了。
第二件事是注意劳动安全。有一次连队组织上山砍柴,大家用过早餐后,带上砍刀就朝山里进发。初次上山砍柴,有人还缺乏经验,不戴草帽也没带水。大家分散开来,相互距离不远,山林中回荡着一阵阵砍柴的声音。临近中午时,太阳火辣辣的,感到口干舌燥,有人向同伴讨水喝,有人不时闪身到树荫下。我砍着砍着,忽闻身后传来“有人晕倒了!”的喊叫声,马上转身跑过去,发现是搬运木柴的女知青韩春荣晕倒在地。我想一定是中暑引起晕厥,就与在场的另外一位女知青,将其抬到就近大树底下阴凉处,让她半坐半躺着。我用右手大拇指按其人中穴位,等她稍有意识后喂几口水,再叫上黄琼木、陈瑞兴等人将其抬回驻地休息。经过这次险情,在连队工作会议上,我提出外出劳动必须自备水壶,要买草帽发给每人一顶,得到大家的赞成。当然,这种事情再也没有发生了。
第三件事是进山伐木。为了建造自己居住的新瓦房,工交连在1974年两次组织人员伐木,我参加了3月份的第一次。梁生刚和我共带了20余人进山,宿营在高峰保扎村晒谷场旁的茅草棚,女知青韩春荣、冯曼南负责后勤。我们主要是砍伐房梁及方木,伐木地点在几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大棚不远处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溪底有大小不一的石头。到了夜晚,流水声哗哗作响,猫头鹰啼叫不停。本来男女在大棚里铺地而睡各在一边,可到了夜深人静时两位女生却害怕得叫嚷起来,吵得大家无法睡。无奈,我只好和邢孔志睡在外围,充当护花使者角色,好让她们俩睡得安稳。
在伐木过程中,伐木工作非常艰苦,危险时有发生。我们当连队干部的,自己每天要完成劳动定额,还经常负责开路、断后、支援,以及组织互帮,充当了组织者、冲锋队、收容队等角色,以确保每天劳动安全、完成定额。我们第一批伐木人员共砍伐了二十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满足了当时建房的需要。就在当年的6月,我被评为崖县知识青年先进个人,与梁生刚、吴开仁等13名场里知青一起,参加了县里召开的首届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
在南山大队什道村
1974年7月,县里决定抽调人员组成第二期“路线教育工作队”,我们农场有4个名额,工交连、财贸连各有2个,说是作为干部苗子选送。我们连我和邢孔志被选中,离场到县里接受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藤桥公社工作队。邢孔志分在附近的汉族村,我被分配到十几公里外黎胞聚居的南山大队什道村,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三同”),但黎族语言听不懂,只能用海南话与他们很吃力的沟通。当时的口号是“大批大斗促大干,抓政治学习促农业生产”。那年我才十九岁,社会经验不足,边干边学习,上头怎么安排,我回村后就怎么落实。
全村有二十几户人家,坐落在农场橡胶园旁的一个小山坡上,村里道路坑洼不平,家家住的都是茅草房,厨房与卧室连在一起,中间隔着一道用细木条当架子、稻草裹黄泥糊的泥土墙。生产队长姓林,我住在他家的饭厅靠墙一侧,白色的蚊帐只挂了一周就被厨房烟火熏得黑黄黑黄的。每天早上吃玉米粥,到了中午还是吃带点酸味的玉米粥,只有晚餐才有一顿干饭吃。只有盐巴和生姜当菜,有时下田劳动时抓一些青蛙、小鱼之类的回来,洗洗就放锅里一煮放点盐,就算是美食了。
村里的水稻产量也就每亩200多斤,杂粮有玉米、红薯。人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男人都抽水烟筒,妇女脸上刺有青色花纹。刚下村时,我经常走家串户、了解民情。通常是白天一起下地劳动、了解生产情况,晚上开会宣讲有关文件、从大队带回的报纸。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基本上掌握了队里各种情况。
每次从大队接受任务回来,都要组织队长、队委,贫协主席开会讨论,工作配合得很好,事事都不落人后。有一次我去公社开三级干部会时,发现镇上有一个生产队制作的打谷桶方便实用,便回村里与队委商量是否也制作一批。大家都说没钱制作,还想将收割的稻谷挑回村里的晒谷场,再用牛群踩踏的老方法脱谷,这样做当然也行,但人与牛都很疲惫,工效也低。我看到使用打谷桶能提高工效,节省劳动力,稻秆放在田间做肥料,把稻谷挑回来即可以了,就坚决要求这样做。
道理讲了一大堆,队长、队委也赞同我的建议,可没钱就是不好办。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想到可以自己筹料加工,这样就能少花钱多办事。第二天我到附近的南田农场爱国队找高中同学,把情况说明清楚,请求支援一些被台风刮倒的橡胶树,然后锯成一块块的木板运回村,又派村民上山砍适用的小木条,叫会计去买回铁钉。我略懂木工活,打过简单家具,正好人尽其才。等一切准备就绪,我就独自一人加工起打谷桶来,结果只用了四天时间及花了几块钱买铁钉,就制作了7个结实耐用的打谷桶。社员们见了都很高兴,尤其是妇女们更加高兴,从此不用连稻秆一起挑回村子了,就留在农田当肥料,也解决了晒谷场每年四周堆满稻草、排水不畅问题。
这7个打谷桶投入使用后,在晚稻收割中效果显著,使生产队的秋收工作走在前头。晚造备耕大积绿肥没白忙,本造单产比往年提高了100多斤,众人皆大欢喜。我在什道村驻队,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一干就是九个月,直到1975年3月才离开。由于工作出色,得到社员们的一致好评,也被藤桥公社工作队评为先进工作队员。第二期路教工作刚结束,我被通知留队,又继续参加了第三期。
在西岛海洋九队(1)
第三期路教工作从4月份开始,我分到南海公社路教工作队西岛工作组,因家里有事,上岛迟了一周。那天是星期五,我搭乘部队登陆艇上岛,就直接到工作组报到,其他队员已驻队,只有胡家魁和钟耀洲等人接待我。初次见面作了自我介绍,他们说起有一名女队员上码头接我,我说不知道。钟耀洲接着解释说,看了名字还以为你是个女的,那位大姐高兴自己有伴了,就到码头接你去。话音刚落,那位大姐已返回,并惊讶地望着我,问我是不是肖家顺?我回答说如假包换,大家听了一阵好笑。
当天下午,工作组成员及大队干部、各生产队长在大队会议室开会,我被安排在海洋九队。九队队长姓麦,个头比我还高,黑铜色的皮肤,满口槟榔色的牙齿,平时话很少,人很老实。麦队长当晚安排我住在曾医生家里,他是大队周书记的妹夫。房间是个单间,收拾得挺干净。女主人热情地沏茶,问这问那,两个小孩有6岁、8岁的样子,挺懂礼貌的。吃饭则安排在不远处的曾医生姐姐家,这家三口人,女儿十五六岁。生活挺不错的,每餐都有鱼有菜拌饭吃。
用过晚饭,我独自在岛上居民区走了一圈,了解一下风土民情。岛上的房子全是用石灰将珊瑚盘石砌成的,房顶是混凝土结构,看来非常牢固,防台风应无问题。水井的井壁、井边、井沿,也是用珊瑚石砌成的,井水有些咸涩,据说含钙偏高,但可以饮用。就是巷子太多,房屋布局有些凌乱。岛上到了夜晚,除了时有狗叫,就是海浪拍打岸边的潮水声。
第二天我便正式开始工作,先找到麦队长,了解队里生产情况及渔民居住位置。生产队有事时,队委都在队长家开会或商量,因渔民住地比较分散,平时很少集中。全队只有5条2.5吨的木帆船和两条小舢板,近两年渔业捕获量在全大队最低,和有机帆船的队更是没法比。全队有渔民35人,每条船配备渔工7人,年纪大的有50多岁,年少的也有20多岁,年龄都比我大。每家都是青壮年男性当渔民,家庭妇女或适龄女孩全在剑麻厂工作。
我随船出海的头一天,上午天气很好,船队驶向南山海域作业,要捕捞炮弹鱼(即鲣鱼)。原以为自小在藤桥海边长大,会游泳水性好,上船捕鱼一定没事,不承想出海不久就晕船了,全身感觉不自在。以后不断呕吐,黄胆水都吐出来了,接着全身发软,人瘫倒在船板上。队长安排一位老渔民负责照顾我,他一会递毛巾一会递水给我喝,还安慰说不要紧的,刚上船都这样,习惯了就没事。下午五点多钟,渔船驶回渔港,海上作业的事,我全然不知,听说只捕获了几百斤。下船后,我勉强走回住所,把女主人煮好的姜汤喝下两大碗,又吃了些米粥,接着回房休息,慢慢才缓过劲来。
以后我坚持跟船出海,抗晕能力一次比一次强。到了第四五次,就差不多习惯了,可以在船上帮助撒网、收网了,也渐渐与渔工打成一片,增进了相互间的感情,了解了作业技能和捕鱼方法。每次回港后,我都向其他驻点工作队员了解各队的捕捞情况,及时向本队队委通报,适当调整捕捞海域,哪里鱼多往哪里去。随着捕捞量明显提高,大家越来越有信心,决心赶超产量高的生产队。
我还每天到岛上水产部门了解各队当天交售数字,了解捕获的鱼类品种及数量,再向工作队队友打听捕捞海域及位置,以便本队灵活转场。后来队友发现我有偷窃“情报”嫌疑,对我有了防范,有些情况就不告诉我了。经过几个月的近海作业,我对各海域的鱼类分布情况有所了解,也算是懂行了,就有资格参与生产决策,为队里的捕捞生产出一把力。
一晃到了八月份,是捕捞鲳鱼的季节。有一天凌晨四点多,五条渔船早早出海,到南山海域时天已大亮,就在海面上展开搜索,有的船长还爬上桅杆瞭望,但整个上午没有动静。有人灰心了,生怕无功而返,但更多是不甘心。因为昨天就在这里,别的队捕捞到数量可观的鲳鱼。中午稍作休息后,又继续巡航搜索。
下午两点多钟,副队长在桅杆顶端突然发现,西北海面的海水颜色时黄时蓝,明显是大鱼群,大家兴奋极了,马上按照事先的分工,五艘船同时调转船头向鱼群方向驶去,快到鱼群位置迅速下网围捕,配合极为默契迅速。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作业,终于将鱼群围住了,我没见过这阵势,既激动又紧张。随着一步步收网拉近,看到鱼儿在水面不停地跳跃,每个人都无比兴奋。这庞大的鲳鱼群,难得被我们一网打尽,装了满满五船舱,足足有一万多斤。
紧张劳作之后,累得筋疲力尽,都在各自船上休息。这时队长过来与我商量,看是否犒劳一下,言下之意是在海上吃一餐鲜鱼宴。按当时规定,渔民只能正常食用但不能拿鱼回家,否则就是侵占公共财产,轻则批评,重则批斗及通报全公社。我当然想到,以鱼当饭有违规嫌疑,但体谅大家辛苦,不想打击积极性,就私下同意了。于是各船都支起大铝锅水煮活鱼,也就是水烧开后,不刮鱼鳞不开肚,就将整条活鱼放入锅中煮,煮熟后捞放在大碗中,夹一块鱼肉沾一下酸豆酱,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肚子饱饱的,我自己也一样,那份满足感自不待言,多年也忘不了。
回到港口上岸后,队长特地开了个小会,要求对鲜鱼宴一事严守私密,不得对外泄漏,大家都会心一笑,然后各自回家。自此以后,我与渔民们更加亲近,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说,他们都亲热地叫我“老肖仔”。若干年后我专程回岛探望他们,大家仍然有说不完的话,关系还是那么亲密。
在西岛海洋九队(2)
就在那年的8月份,西岛大队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一下子就死亡12人,这是西岛大队、南海公社,甚至是整个崖县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意外灾难。西岛工作组的所有队员都参加了救援工作,我也不例外,参加了搜寻、安抚整个过程,数天来的辛苦倒不算什么,只是看到那么多条鲜活生命突然消失,觉得非常可惜和难过。
那时刚刮过一场台风,—西岛的渔民好几天都没出海打鱼,连平时到县城三亚采购物资、接送学生来回的船只也停开好几天了,唯独七队的机帆船“赶风头、追风尾”出海打鱼,早上才回港卸鱼货,还来不及收好网具,只是临时堆放在船头。这时看到天已放晴,是难得的好天气,就直接停靠在大码头上,准备去三亚镇街市采购物资。
而岛上被困了几天的学生、准备去三亚上班的部分人员,一听说有船要去三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搭乘此船去三亚。到了船上后,大部分小孩和大人坐在船头的尼龙渔网上,因为既干净又柔软,坐着挺舒服的,全船总共乘坐了30多号人。机帆船开动后,一路上欢声笑语,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三亚港码头(有8海里)了。可谁也没想到,此时灾难正向他们逼近。
由于刚刮过台风,又下了几天雨,三亚河上游有六罗水、半岭水、汤他水等处水流汇集,并以汹涌之势冲出三亚河出海口,在三亚港外的灯塔处附近,与海水发生交汇,形成了洄旋涡流。当七队的机帆船行驶至此,便被急促而强大的水流冲击,产生激烈颠簸。顷刻之间,船体被打横、船舵失灵,坐在船头网具上的大人和小孩随即落水,接着整条船被掀翻倒扣在海里,撒开的尼龙渔网把落水的人盖得严严实实、动弹不得,情势万分危急。
此时附近码头发现险情,连续鸣笛示警。停靠近处的渔船上的渔民见状,纷纷拿着刀具跳到海中迅速游近,奋力割网救人。结果只救出了20余人。由于水流湍急、救援不及,仍有12人寻找不到,估计已被激流卷入大海。
为了救助幸存者和打捞尸体,我们西岛工作组的全体队员都来到三亚港,和来自各处的渔民一起,在南边海及三亚湾岸边,组成一字人体拉网向浅海区搜寻,还从西岛调来几条船在附近海面展开搜寻,连续不断地寻找了几天。在白天,工作组的一部分人员参与搜找,一部分人做好遗体的善后工作。到了晚上,又要到遇难者家中做安抚工作,每人都疲惫不堪。
到了第三、第四天,失踪的尸体逐渐在海面浮起,有的就在出事点附近,有的漂流到较远的海岸或海面。由于受到长时候的海水浸泡,加上浮出水面后又被烈日高温蒸浴,尸体基本上已浮肿变形,甚至出现残缺、腐烂,真是惨不忍睹。我们只能在海水中先用装盐的草袋从人体两头往中间套,待套好绑着之后,再小心翼翼地抬上船,运回岛上入殓安葬。一时,海潮呜咽,日月无光,亲人痛彻心扉,旁人无不落泪。
那几天,我每天都参与搜寻、安抚工作,别的事都顾不得了。每当吃饭时,很自然想起打捞尸体的种种情景,根本吃不下饭,只能喝点稀粥。晚上又要到遇难者家中安抚作陪,到了深夜才能回三同户家中休息,还不能告诉人家说自己参与打捞尸体了。好在到了第五天,失踪者已全部找到并处理完毕,整个工作才宣告结束。到了这时,渔业生产又转入正常。
在西岛海洋九队(3)
到了九月份,渔业生产转入灯光鱼捕捞季节。这种捕鱼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在近海渔场驶出两只小舢板船,船尾两侧挂上两盏大气灯,利用灯光将附近的鱼儿(有趋光性)吸引到灯光下,其他渔船则在附近预先将尼龙网撒开,等待灯光下的鱼儿聚集多了,小舢板船才慢慢向事先撒好的渔网中划去,将追逐灯光的鱼儿引进大网中。差不多了,再迅速将渔网的四个角拉起收网。直到渔网的四条边拉出水面,小舢板船才驶离网区。这种捕鱼方法是大小鱼通捕,只要不漏网的都被捞入船舱。
一次我们船队到铁炉港海区捕灯光鱼,连续十几天在船上吃住、作业,捕捞的鱼就近交售水产部门。我们白天靠岸休息,晚上出海捕捞,捕获的鱼可不少。那时没有通信设备,只靠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有一天下午,收听到台风即将到来的消息,我和队长、队委经过商量,决定停止捕捞作业,向南返回西岛。收拾完毕就拔锚起航,我与队长所在船只负责带路,其他四条船紧随其后。
经过东洲、西洲、白虎岭、锦母角、虎头岭等处海区时,海上风浪不大,行驶还算顺利。可到了傍晚,船队驶入榆林港外海区,榆林角隐约可见,此时海面一改温驯面孔,风越刮越猛,海面汹涌澎湃,波浪滔天,后面船只不时被海浪遮挡,只见到片片风帆。谁都知道,再向西岛方向行驶,小船很难抵挡风浪,弄不好就船毁人亡。于是,我和队长共同决定驶向红沙港湾,躲避这场台风。
还未到达榆林角,海浪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暴风雨也来了,行船极为危险。就在船队快要进入榆林港时,副队长所在尾船的桅杆被狂风刮断,船上人员乱成一团,幸得他沉着冷静,大声指挥船工割断帆绳、将桅杆及船帆丢弃海中。一边靠人工奋力摇橹,一边靠前面船只抛出的粗绳绑紧船头拖动,继续跟队前行。好在榆林港口已经不远,经过一阵的艰难行驶,船队终于平安进入港区。接着再驶向红沙港湾,最后停泊在驻守红沙墟镇北侧的高炮连营区海域,这时已是夜晚九点多钟。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人又冷又饿,无法生火煮饭,只好蹚水登岸,在靠海边一处未竣工的二层楼房将就歇息,席地而睡。到了下半夜的三四点钟,部队哨兵巡逻时发现,把我们摇醒说这是军事禁区,不能在此过夜,把我和队长带去问话,限别人不准走动,等待进一步处理。到了值班室后,我们讲明了缘由,外面又是夜幕低垂的风雨天,高炮连领导也挺同情。他们经与西岛守备连联系,该连又派人到大队查询,确认我们是海洋九队的,才允许继续住下,但要求不得随便走动,天亮就要撤离。
我和队长返回后,已经没有任何睡意,只好坐等天亮再说。第二天上午,风雨总算消停了,我们再回到船上,开始烧火做饭,才吃上一餐热饭。我和队长接着就到红沙邮电所,打电话给大队报平安,然后率船队驶回西岛,总算有惊无险平安归来。
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同时多商量、想办法,海洋九队的生产形势越来越好,捕捞产量不断上升。到了当年11月份,海洋九队居然高居榜首,成为全大队当年渔业产量最高的一个队。我也因为工作认真、积极肯干、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工作队员,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组织一员。稍有遗憾的是,尽管成绩突出,却因海外背景,故在表决通过时,票数只勉强达到,不过我也知足了。
第三次参加路教及当兵
第三期路教工作在11月底结束,我以为会被招工分配,谁知左等右等不见动静。
我心慌起来,赶紧打听消息,才知原方案是将我安排到县气象站或邮电局工作,但政审时因我父母是归侨,被认为不适合进入敏感单位,就给取消了。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想要求回原知青点当知青,又觉得很没面子,生怕别人笑话,真是心有不甘。
正在苦闷无奈之中,心想不会又当工作队员吧?果不其然,我在12月中旬接到参加第四期路教的通知,安排我到林旺公社工作队青田工作组,临时顶替另外一名队员抓早造备耕。这时我有思想抵触,看来真是条好用的牛,拉重车少不了,又派回黎族村庄了。
领导说好一个月再另做安排,我心里仍然不畅快,但还是踏踏实实地干。1976年1月中旬,公社搞农田大改造,我被调到洪风工作组,驻点风塘村是个汉族村庄。由于有了二次路教工作经验,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干好工作不在话下,一切都很顺利。抓备耕、抓学习、抓生产这些,都是老一套了,我和队长、队委紧密配合,又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安排井井有条。工作队领导时常下来检查工作,既表扬了我也安慰我,我只能答应一定干好工作,请他们放心。
1976年2月中旬,林旺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全体工作队员也参加了。在会议期间,恰好遇上县里春季征兵,我一时心血来潮,就私下报了名。我想得很简单,感觉近几个月身体有些消瘦,会不会有什么病,不如体检一下看看,反正也不要钱的(我每月工资21元,交完伙食费没剩多少)。没想到体检居然合格了,几天后就接到应征入伍通知书,是弄假成真弄巧成拙了,这时进退两难。我好歹已辛苦了两年多,很希望被分配工作,还真的不想去当兵。
我找到工作组领导表明了想法,他当即批评我:“你刚入党不久,又体检合格,不去当兵,想当逃兵,还是个党员吗?当兵多光荣啊!”几句话把我吓得够呛,我只好服从了。于是,我交接工作、收拾行李、辞别众人,回家小住几天,就向父母告别。
当我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崖县青年农场时,与我同为第一批的不少知青已被招工、推荐上学离场,增加了众多陌生面孔,想来应是第二三批到来的。风景依旧,人物时新,我之将离,感慨万端!次日上午,场里组织了欢送大会,敲锣打鼓送我和另一个知青一起去当兵,一直送到了县武装部。由此,我就成了崖县青年农场第一批被招兵的知青,那时我刚满21岁。
在崖县青年农场
1973年7月我从崖县藤桥中学高中毕业,等到10月份藤桥糖厂开榨,就像往年一样做季节工,挣些钱补贴家用,同时体验当糖厂工人的乐趣。我的同届同学许政平、潘平也在厂里打工,我们平时很要好,经常在一起玩。有一天,许政平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县里要成立一个青年农场,就在羊栏公社水蛟大队的水蛟坡,专门安置工交战线、财贸战线报名上山下乡的职工子弟,他和潘平已经报名。我父母工作在藤桥二轻橡胶制品厂,隶属县二轻系统,我也是工交战线职工子弟。我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心切,于是没有多想,就请他帮我从藤桥糖厂这边报名,好和他们俩一起去。
事如所愿,在当年的12月27日,我正式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知青,和许政平、潘平一起被分到了崖县青年农场(后来改称国营三亚菜场)工交连,而另一个同学刘雁玲分到同场的财贸连。当时崖县工交战线委派的带队干部是周经源、黄瑞鹤两位大叔,分别担任工交连指导员、连长。那时我只有18岁,是共青团员,思想上要求进步,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对即将来临的知青生活很是期待。
我读高中时一直担任班长,多次参加过农村、农场、糖厂的生产劳动,熟悉农村生活,有不少农村朋友。来崖县青年农场后结交的三亚县城的朋友,都叫我们藤桥来的几个为“藤桥仔”。也许是履历表的原因,我在这里受到场领导及带队干部的重视。
到青年农场后,先是安排林海旺和我任工交连二排正、副排长。不久取消排级建制,安排梁生刚和我任第一、第二副连长(林保烈、周玉珠任第一、第二副指导员),我们紧密配合,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我的知青岁月由两部分构成:从上山下乡至1974年7月,我在知青点度过6个多月,连队的各项大事,从安排生活、早造生产,到备料建瓦房,我都一一参加了;从1974年7月至1976年2月,我搞路教一年零七个月,连续三次参加了路教工作队,并在第三次路教期间应征入伍。
在知青点的劳动生活,有几件事值得一谈。
第一件事是教人种菜。1974年元旦放假一天,返回农场后就进入正常工作,当时黄琼木等人正在营房后面平整土地,准备在这里育菜秧,菜种已经买回来了。但我近前一看,觉得情况不妙,原来是他们都从未种过菜,不知道如何播种,往地垄上浇了很多水,并和成稀泥状,打算撒上菜种。这样肯定不行,我立即制止他们。我在家里从小就种菜,吃不完时还送人,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了安排好连队的伙食,我们有必要自己种菜补充。于是我就耐心讲解,教会他们许多基本知识,还现场示范操作方法,使他们懂得了如何整地播种、培育菜秧……他们以后就干得不错了。
第二件事是注意劳动安全。有一次连队组织上山砍柴,大家用过早餐后,带上砍刀就朝山里进发。初次上山砍柴,有人还缺乏经验,不戴草帽也没带水。大家分散开来,相互距离不远,山林中回荡着一阵阵砍柴的声音。临近中午时,太阳火辣辣的,感到口干舌燥,有人向同伴讨水喝,有人不时闪身到树荫下。我砍着砍着,忽闻身后传来“有人晕倒了!”的喊叫声,马上转身跑过去,发现是搬运木柴的女知青韩春荣晕倒在地。我想一定是中暑引起晕厥,就与在场的另外一位女知青,将其抬到就近大树底下阴凉处,让她半坐半躺着。我用右手大拇指按其人中穴位,等她稍有意识后喂几口水,再叫上黄琼木、陈瑞兴等人将其抬回驻地休息。经过这次险情,在连队工作会议上,我提出外出劳动必须自备水壶,要买草帽发给每人一顶,得到大家的赞成。当然,这种事情再也没有发生了。
第三件事是进山伐木。为了建造自己居住的新瓦房,工交连在1974年两次组织人员伐木,我参加了3月份的第一次。梁生刚和我共带了20余人进山,宿营在高峰保扎村晒谷场旁的茅草棚,女知青韩春荣、冯曼南负责后勤。我们主要是砍伐房梁及方木,伐木地点在几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大棚不远处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溪底有大小不一的石头。到了夜晚,流水声哗哗作响,猫头鹰啼叫不停。本来男女在大棚里铺地而睡各在一边,可到了夜深人静时两位女生却害怕得叫嚷起来,吵得大家无法睡。无奈,我只好和邢孔志睡在外围,充当护花使者角色,好让她们俩睡得安稳。
在伐木过程中,伐木工作非常艰苦,危险时有发生。我们当连队干部的,自己每天要完成劳动定额,还经常负责开路、断后、支援,以及组织互帮,充当了组织者、冲锋队、收容队等角色,以确保每天劳动安全、完成定额。我们第一批伐木人员共砍伐了二十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满足了当时建房的需要。就在当年的6月,我被评为崖县知识青年先进个人,与梁生刚、吴开仁等13名场里知青一起,参加了县里召开的首届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
在南山大队什道村
1974年7月,县里决定抽调人员组成第二期“路线教育工作队”,我们农场有4个名额,工交连、财贸连各有2个,说是作为干部苗子选送。我们连我和邢孔志被选中,离场到县里接受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藤桥公社工作队。邢孔志分在附近的汉族村,我被分配到十几公里外黎胞聚居的南山大队什道村,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三同”),但黎族语言听不懂,只能用海南话与他们很吃力的沟通。当时的口号是“大批大斗促大干,抓政治学习促农业生产”。那年我才十九岁,社会经验不足,边干边学习,上头怎么安排,我回村后就怎么落实。
全村有二十几户人家,坐落在农场橡胶园旁的一个小山坡上,村里道路坑洼不平,家家住的都是茅草房,厨房与卧室连在一起,中间隔着一道用细木条当架子、稻草裹黄泥糊的泥土墙。生产队长姓林,我住在他家的饭厅靠墙一侧,白色的蚊帐只挂了一周就被厨房烟火熏得黑黄黑黄的。每天早上吃玉米粥,到了中午还是吃带点酸味的玉米粥,只有晚餐才有一顿干饭吃。只有盐巴和生姜当菜,有时下田劳动时抓一些青蛙、小鱼之类的回来,洗洗就放锅里一煮放点盐,就算是美食了。
村里的水稻产量也就每亩200多斤,杂粮有玉米、红薯。人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男人都抽水烟筒,妇女脸上刺有青色花纹。刚下村时,我经常走家串户、了解民情。通常是白天一起下地劳动、了解生产情况,晚上开会宣讲有关文件、从大队带回的报纸。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基本上掌握了队里各种情况。
每次从大队接受任务回来,都要组织队长、队委,贫协主席开会讨论,工作配合得很好,事事都不落人后。有一次我去公社开三级干部会时,发现镇上有一个生产队制作的打谷桶方便实用,便回村里与队委商量是否也制作一批。大家都说没钱制作,还想将收割的稻谷挑回村里的晒谷场,再用牛群踩踏的老方法脱谷,这样做当然也行,但人与牛都很疲惫,工效也低。我看到使用打谷桶能提高工效,节省劳动力,稻秆放在田间做肥料,把稻谷挑回来即可以了,就坚决要求这样做。
道理讲了一大堆,队长、队委也赞同我的建议,可没钱就是不好办。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想到可以自己筹料加工,这样就能少花钱多办事。第二天我到附近的南田农场爱国队找高中同学,把情况说明清楚,请求支援一些被台风刮倒的橡胶树,然后锯成一块块的木板运回村,又派村民上山砍适用的小木条,叫会计去买回铁钉。我略懂木工活,打过简单家具,正好人尽其才。等一切准备就绪,我就独自一人加工起打谷桶来,结果只用了四天时间及花了几块钱买铁钉,就制作了7个结实耐用的打谷桶。社员们见了都很高兴,尤其是妇女们更加高兴,从此不用连稻秆一起挑回村子了,就留在农田当肥料,也解决了晒谷场每年四周堆满稻草、排水不畅问题。
这7个打谷桶投入使用后,在晚稻收割中效果显著,使生产队的秋收工作走在前头。晚造备耕大积绿肥没白忙,本造单产比往年提高了100多斤,众人皆大欢喜。我在什道村驻队,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一干就是九个月,直到1975年3月才离开。由于工作出色,得到社员们的一致好评,也被藤桥公社工作队评为先进工作队员。第二期路教工作刚结束,我被通知留队,又继续参加了第三期。
在西岛海洋九队(1)
第三期路教工作从4月份开始,我分到南海公社路教工作队西岛工作组,因家里有事,上岛迟了一周。那天是星期五,我搭乘部队登陆艇上岛,就直接到工作组报到,其他队员已驻队,只有胡家魁和钟耀洲等人接待我。初次见面作了自我介绍,他们说起有一名女队员上码头接我,我说不知道。钟耀洲接着解释说,看了名字还以为你是个女的,那位大姐高兴自己有伴了,就到码头接你去。话音刚落,那位大姐已返回,并惊讶地望着我,问我是不是肖家顺?我回答说如假包换,大家听了一阵好笑。
当天下午,工作组成员及大队干部、各生产队长在大队会议室开会,我被安排在海洋九队。九队队长姓麦,个头比我还高,黑铜色的皮肤,满口槟榔色的牙齿,平时话很少,人很老实。麦队长当晚安排我住在曾医生家里,他是大队周书记的妹夫。房间是个单间,收拾得挺干净。女主人热情地沏茶,问这问那,两个小孩有6岁、8岁的样子,挺懂礼貌的。吃饭则安排在不远处的曾医生姐姐家,这家三口人,女儿十五六岁。生活挺不错的,每餐都有鱼有菜拌饭吃。
用过晚饭,我独自在岛上居民区走了一圈,了解一下风土民情。岛上的房子全是用石灰将珊瑚盘石砌成的,房顶是混凝土结构,看来非常牢固,防台风应无问题。水井的井壁、井边、井沿,也是用珊瑚石砌成的,井水有些咸涩,据说含钙偏高,但可以饮用。就是巷子太多,房屋布局有些凌乱。岛上到了夜晚,除了时有狗叫,就是海浪拍打岸边的潮水声。
第二天我便正式开始工作,先找到麦队长,了解队里生产情况及渔民居住位置。生产队有事时,队委都在队长家开会或商量,因渔民住地比较分散,平时很少集中。全队只有5条2.5吨的木帆船和两条小舢板,近两年渔业捕获量在全大队最低,和有机帆船的队更是没法比。全队有渔民35人,每条船配备渔工7人,年纪大的有50多岁,年少的也有20多岁,年龄都比我大。每家都是青壮年男性当渔民,家庭妇女或适龄女孩全在剑麻厂工作。
我随船出海的头一天,上午天气很好,船队驶向南山海域作业,要捕捞炮弹鱼(即鲣鱼)。原以为自小在藤桥海边长大,会游泳水性好,上船捕鱼一定没事,不承想出海不久就晕船了,全身感觉不自在。以后不断呕吐,黄胆水都吐出来了,接着全身发软,人瘫倒在船板上。队长安排一位老渔民负责照顾我,他一会递毛巾一会递水给我喝,还安慰说不要紧的,刚上船都这样,习惯了就没事。下午五点多钟,渔船驶回渔港,海上作业的事,我全然不知,听说只捕获了几百斤。下船后,我勉强走回住所,把女主人煮好的姜汤喝下两大碗,又吃了些米粥,接着回房休息,慢慢才缓过劲来。
以后我坚持跟船出海,抗晕能力一次比一次强。到了第四五次,就差不多习惯了,可以在船上帮助撒网、收网了,也渐渐与渔工打成一片,增进了相互间的感情,了解了作业技能和捕鱼方法。每次回港后,我都向其他驻点工作队员了解各队的捕捞情况,及时向本队队委通报,适当调整捕捞海域,哪里鱼多往哪里去。随着捕捞量明显提高,大家越来越有信心,决心赶超产量高的生产队。
我还每天到岛上水产部门了解各队当天交售数字,了解捕获的鱼类品种及数量,再向工作队队友打听捕捞海域及位置,以便本队灵活转场。后来队友发现我有偷窃“情报”嫌疑,对我有了防范,有些情况就不告诉我了。经过几个月的近海作业,我对各海域的鱼类分布情况有所了解,也算是懂行了,就有资格参与生产决策,为队里的捕捞生产出一把力。
一晃到了八月份,是捕捞鲳鱼的季节。有一天凌晨四点多,五条渔船早早出海,到南山海域时天已大亮,就在海面上展开搜索,有的船长还爬上桅杆瞭望,但整个上午没有动静。有人灰心了,生怕无功而返,但更多是不甘心。因为昨天就在这里,别的队捕捞到数量可观的鲳鱼。中午稍作休息后,又继续巡航搜索。
下午两点多钟,副队长在桅杆顶端突然发现,西北海面的海水颜色时黄时蓝,明显是大鱼群,大家兴奋极了,马上按照事先的分工,五艘船同时调转船头向鱼群方向驶去,快到鱼群位置迅速下网围捕,配合极为默契迅速。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作业,终于将鱼群围住了,我没见过这阵势,既激动又紧张。随着一步步收网拉近,看到鱼儿在水面不停地跳跃,每个人都无比兴奋。这庞大的鲳鱼群,难得被我们一网打尽,装了满满五船舱,足足有一万多斤。
紧张劳作之后,累得筋疲力尽,都在各自船上休息。这时队长过来与我商量,看是否犒劳一下,言下之意是在海上吃一餐鲜鱼宴。按当时规定,渔民只能正常食用但不能拿鱼回家,否则就是侵占公共财产,轻则批评,重则批斗及通报全公社。我当然想到,以鱼当饭有违规嫌疑,但体谅大家辛苦,不想打击积极性,就私下同意了。于是各船都支起大铝锅水煮活鱼,也就是水烧开后,不刮鱼鳞不开肚,就将整条活鱼放入锅中煮,煮熟后捞放在大碗中,夹一块鱼肉沾一下酸豆酱,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肚子饱饱的,我自己也一样,那份满足感自不待言,多年也忘不了。
回到港口上岸后,队长特地开了个小会,要求对鲜鱼宴一事严守私密,不得对外泄漏,大家都会心一笑,然后各自回家。自此以后,我与渔民们更加亲近,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说,他们都亲热地叫我“老肖仔”。若干年后我专程回岛探望他们,大家仍然有说不完的话,关系还是那么亲密。
在西岛海洋九队(2)
就在那年的8月份,西岛大队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一下子就死亡12人,这是西岛大队、南海公社,甚至是整个崖县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意外灾难。西岛工作组的所有队员都参加了救援工作,我也不例外,参加了搜寻、安抚整个过程,数天来的辛苦倒不算什么,只是看到那么多条鲜活生命突然消失,觉得非常可惜和难过。
那时刚刮过一场台风,—西岛的渔民好几天都没出海打鱼,连平时到县城三亚采购物资、接送学生来回的船只也停开好几天了,唯独七队的机帆船“赶风头、追风尾”出海打鱼,早上才回港卸鱼货,还来不及收好网具,只是临时堆放在船头。这时看到天已放晴,是难得的好天气,就直接停靠在大码头上,准备去三亚镇街市采购物资。
而岛上被困了几天的学生、准备去三亚上班的部分人员,一听说有船要去三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搭乘此船去三亚。到了船上后,大部分小孩和大人坐在船头的尼龙渔网上,因为既干净又柔软,坐着挺舒服的,全船总共乘坐了30多号人。机帆船开动后,一路上欢声笑语,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三亚港码头(有8海里)了。可谁也没想到,此时灾难正向他们逼近。
由于刚刮过台风,又下了几天雨,三亚河上游有六罗水、半岭水、汤他水等处水流汇集,并以汹涌之势冲出三亚河出海口,在三亚港外的灯塔处附近,与海水发生交汇,形成了洄旋涡流。当七队的机帆船行驶至此,便被急促而强大的水流冲击,产生激烈颠簸。顷刻之间,船体被打横、船舵失灵,坐在船头网具上的大人和小孩随即落水,接着整条船被掀翻倒扣在海里,撒开的尼龙渔网把落水的人盖得严严实实、动弹不得,情势万分危急。
此时附近码头发现险情,连续鸣笛示警。停靠近处的渔船上的渔民见状,纷纷拿着刀具跳到海中迅速游近,奋力割网救人。结果只救出了20余人。由于水流湍急、救援不及,仍有12人寻找不到,估计已被激流卷入大海。
为了救助幸存者和打捞尸体,我们西岛工作组的全体队员都来到三亚港,和来自各处的渔民一起,在南边海及三亚湾岸边,组成一字人体拉网向浅海区搜寻,还从西岛调来几条船在附近海面展开搜寻,连续不断地寻找了几天。在白天,工作组的一部分人员参与搜找,一部分人做好遗体的善后工作。到了晚上,又要到遇难者家中做安抚工作,每人都疲惫不堪。
到了第三、第四天,失踪的尸体逐渐在海面浮起,有的就在出事点附近,有的漂流到较远的海岸或海面。由于受到长时候的海水浸泡,加上浮出水面后又被烈日高温蒸浴,尸体基本上已浮肿变形,甚至出现残缺、腐烂,真是惨不忍睹。我们只能在海水中先用装盐的草袋从人体两头往中间套,待套好绑着之后,再小心翼翼地抬上船,运回岛上入殓安葬。一时,海潮呜咽,日月无光,亲人痛彻心扉,旁人无不落泪。
那几天,我每天都参与搜寻、安抚工作,别的事都顾不得了。每当吃饭时,很自然想起打捞尸体的种种情景,根本吃不下饭,只能喝点稀粥。晚上又要到遇难者家中安抚作陪,到了深夜才能回三同户家中休息,还不能告诉人家说自己参与打捞尸体了。好在到了第五天,失踪者已全部找到并处理完毕,整个工作才宣告结束。到了这时,渔业生产又转入正常。
在西岛海洋九队(3)
到了九月份,渔业生产转入灯光鱼捕捞季节。这种捕鱼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在近海渔场驶出两只小舢板船,船尾两侧挂上两盏大气灯,利用灯光将附近的鱼儿(有趋光性)吸引到灯光下,其他渔船则在附近预先将尼龙网撒开,等待灯光下的鱼儿聚集多了,小舢板船才慢慢向事先撒好的渔网中划去,将追逐灯光的鱼儿引进大网中。差不多了,再迅速将渔网的四个角拉起收网。直到渔网的四条边拉出水面,小舢板船才驶离网区。这种捕鱼方法是大小鱼通捕,只要不漏网的都被捞入船舱。
一次我们船队到铁炉港海区捕灯光鱼,连续十几天在船上吃住、作业,捕捞的鱼就近交售水产部门。我们白天靠岸休息,晚上出海捕捞,捕获的鱼可不少。那时没有通信设备,只靠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有一天下午,收听到台风即将到来的消息,我和队长、队委经过商量,决定停止捕捞作业,向南返回西岛。收拾完毕就拔锚起航,我与队长所在船只负责带路,其他四条船紧随其后。
经过东洲、西洲、白虎岭、锦母角、虎头岭等处海区时,海上风浪不大,行驶还算顺利。可到了傍晚,船队驶入榆林港外海区,榆林角隐约可见,此时海面一改温驯面孔,风越刮越猛,海面汹涌澎湃,波浪滔天,后面船只不时被海浪遮挡,只见到片片风帆。谁都知道,再向西岛方向行驶,小船很难抵挡风浪,弄不好就船毁人亡。于是,我和队长共同决定驶向红沙港湾,躲避这场台风。
还未到达榆林角,海浪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暴风雨也来了,行船极为危险。就在船队快要进入榆林港时,副队长所在尾船的桅杆被狂风刮断,船上人员乱成一团,幸得他沉着冷静,大声指挥船工割断帆绳、将桅杆及船帆丢弃海中。一边靠人工奋力摇橹,一边靠前面船只抛出的粗绳绑紧船头拖动,继续跟队前行。好在榆林港口已经不远,经过一阵的艰难行驶,船队终于平安进入港区。接着再驶向红沙港湾,最后停泊在驻守红沙墟镇北侧的高炮连营区海域,这时已是夜晚九点多钟。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人又冷又饿,无法生火煮饭,只好蹚水登岸,在靠海边一处未竣工的二层楼房将就歇息,席地而睡。到了下半夜的三四点钟,部队哨兵巡逻时发现,把我们摇醒说这是军事禁区,不能在此过夜,把我和队长带去问话,限别人不准走动,等待进一步处理。到了值班室后,我们讲明了缘由,外面又是夜幕低垂的风雨天,高炮连领导也挺同情。他们经与西岛守备连联系,该连又派人到大队查询,确认我们是海洋九队的,才允许继续住下,但要求不得随便走动,天亮就要撤离。
我和队长返回后,已经没有任何睡意,只好坐等天亮再说。第二天上午,风雨总算消停了,我们再回到船上,开始烧火做饭,才吃上一餐热饭。我和队长接着就到红沙邮电所,打电话给大队报平安,然后率船队驶回西岛,总算有惊无险平安归来。
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同时多商量、想办法,海洋九队的生产形势越来越好,捕捞产量不断上升。到了当年11月份,海洋九队居然高居榜首,成为全大队当年渔业产量最高的一个队。我也因为工作认真、积极肯干、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工作队员,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组织一员。稍有遗憾的是,尽管成绩突出,却因海外背景,故在表决通过时,票数只勉强达到,不过我也知足了。
第三次参加路教及当兵
第三期路教工作在11月底结束,我以为会被招工分配,谁知左等右等不见动静。
我心慌起来,赶紧打听消息,才知原方案是将我安排到县气象站或邮电局工作,但政审时因我父母是归侨,被认为不适合进入敏感单位,就给取消了。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想要求回原知青点当知青,又觉得很没面子,生怕别人笑话,真是心有不甘。
正在苦闷无奈之中,心想不会又当工作队员吧?果不其然,我在12月中旬接到参加第四期路教的通知,安排我到林旺公社工作队青田工作组,临时顶替另外一名队员抓早造备耕。这时我有思想抵触,看来真是条好用的牛,拉重车少不了,又派回黎族村庄了。
领导说好一个月再另做安排,我心里仍然不畅快,但还是踏踏实实地干。1976年1月中旬,公社搞农田大改造,我被调到洪风工作组,驻点风塘村是个汉族村庄。由于有了二次路教工作经验,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干好工作不在话下,一切都很顺利。抓备耕、抓学习、抓生产这些,都是老一套了,我和队长、队委紧密配合,又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安排井井有条。工作队领导时常下来检查工作,既表扬了我也安慰我,我只能答应一定干好工作,请他们放心。
1976年2月中旬,林旺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全体工作队员也参加了。在会议期间,恰好遇上县里春季征兵,我一时心血来潮,就私下报了名。我想得很简单,感觉近几个月身体有些消瘦,会不会有什么病,不如体检一下看看,反正也不要钱的(我每月工资21元,交完伙食费没剩多少)。没想到体检居然合格了,几天后就接到应征入伍通知书,是弄假成真弄巧成拙了,这时进退两难。我好歹已辛苦了两年多,很希望被分配工作,还真的不想去当兵。
我找到工作组领导表明了想法,他当即批评我:“你刚入党不久,又体检合格,不去当兵,想当逃兵,还是个党员吗?当兵多光荣啊!”几句话把我吓得够呛,我只好服从了。于是,我交接工作、收拾行李、辞别众人,回家小住几天,就向父母告别。
当我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崖县青年农场时,与我同为第一批的不少知青已被招工、推荐上学离场,增加了众多陌生面孔,想来应是第二三批到来的。风景依旧,人物时新,我之将离,感慨万端!次日上午,场里组织了欢送大会,敲锣打鼓送我和另一个知青一起去当兵,一直送到了县武装部。由此,我就成了崖县青年农场第一批被招兵的知青,那时我刚满21岁。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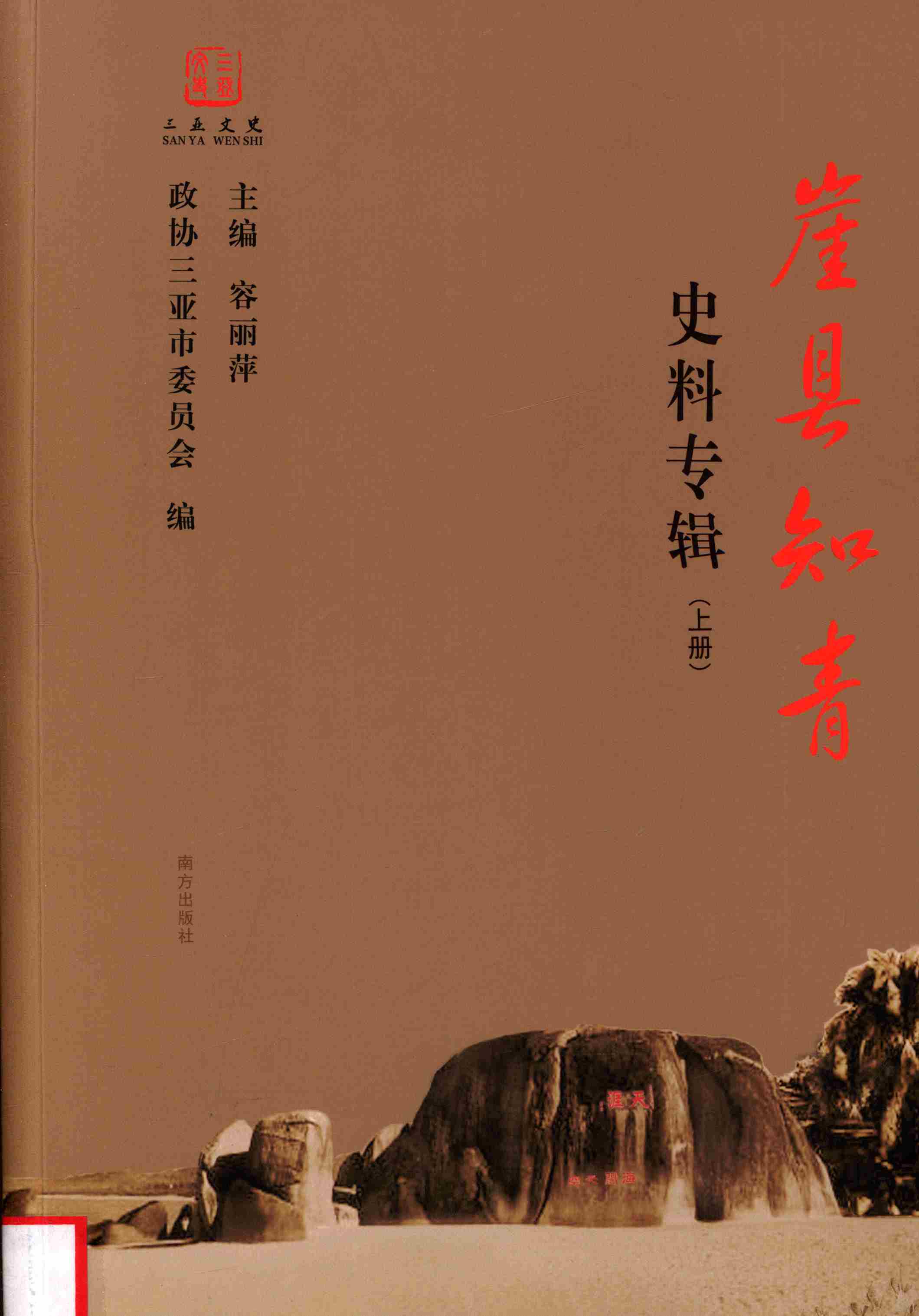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上册》
出版者:南方出版社
本书共有69篇文稿,崖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崖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崖县上山下乡知青安置点简介3篇综述文稿,1956年、 1958年到来崖县的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9篇知青回忆 录,1969年本地知青、潮汕知青12篇知青回忆录,崖县知青场45篇知青回忆录。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