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 内容出处: |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上册》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1549 |
| 颗粒名称: | 我的知青生活 |
| 分类号: | D432.9 |
| 页数: | 5 |
| 页码: | 107-111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一个知青在1969年下乡后的生活经历,包括与当地人的相处、队长及家人对他们的关心、和南繁育种队员一起的生活、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等内容。 |
| 关键词: | 知青 下乡 生活经历 |
内容
下乡第一天
1969年3月8日,18岁的我也成了崖县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的一员,我和6位学友一道被安排在崖县羊栏公社水蛟大队的水蛟、白鸡生产队(以村为队)。
记得那天早上,我们带着行李在当时地处菜市场的停车场等待知青专车,车里是初次离家、彷徨不知前路的年轻人,车外是反复叮咛、不忍离去的家人。有一对医生夫妇来给他们的一对儿女送行,他们特地给孩子们戴上了红花,并充满激情地用革命的豪言壮语来鼓励他们。我的母亲只是一个街道小市民,她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只是流着眼泪和邻家临高伯母在车窗外不断叮嘱我需要注意的生活细节。看着哭啼的母亲与邻家伯母,想到自己未卜的前途,我也心酸落泪。
到了羊栏车站,早有水蛟、白鸡生产队的村民,敲锣打鼓列着队伍到车站来迎接我们。我们跟随着各自的队伍,来到了我们的新家——队里给我们建造的一人一间10平方米的茅房,我是唯一的女生,被安排在中间。当时房子里外都已围满了热情的村民,我一进屋,还未看清楚人们的脸面,就被一位黎族老阿婆紧紧抱在怀里,她嘴里乐呵呵地说:“我要认这个做女儿!我要认这个做女儿!”阿婆的热情使我一时不知所措,但也让我消除了不少陌生感。后来听村里人说,这阿婆没生儿女,抱养的一个儿子现在部队,平时难得回一次家,阿婆感到很寂寞,听说这次村里要来几个知青,就想从中挑一个做女儿。后来我在农村的两年半中,阿婆真的把我当做女儿了,每当蒸糯米饭时,就会叫我去她家一块吃。
围着的村民们热情地和我们聊天,问我们姓名、年龄、家庭情况,还亲切地用他们的习惯叫法称呼我们“老李”“老邢”“老陈”。
热闹了一阵,人们都走了,我们几个人看着陌生的房间,睡在木床上辗转难眠,大家都坐立不安,决定去看望另外那3个知青。谁知走到中途就碰上了同样也准备来看望我们的3个知青,大家诉说着进村后的情景,直到天色将晚,他们才回了自己的村庄。
我们的队长及家人
我们生产队的董队长是个典型的黎族中年汉子,高额头、粗鼻子、厚嘴唇,喜欢仰着头、眯着眼睛,说着不太流利的海南话。他和家人都很关心我们。
他的爱人不大会讲海南话,所以很少与我们交谈,但她经常在我们做饭时一言不发地走过来看我们的菜,一看见我们的菜太差了,就跑回家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椰子肉丝煮山豆子给我们下饭。在水稻、地瓜收获的季节,晒谷子、地瓜片时碰到下雨,他们家就会兵分两路,一队收他们自家的粮食,另一队来帮我们。他的两个女儿总是细心地帮我们把雨布或木板垫在地下,然后将尚未晒干的谷子倒在上面摊开晾干,要是地瓜片还得小心地一片片铺开晾干,才不至于发霉变黑。要不是他们帮忙,一旦把粮食弄坏,那我们下季的口粮都会成大问题。
队长的大女儿是一个善良、勤劳、朴实的女孩,我离开水蛟后,听说她已嫁到三亚临春村。如今,她因到我们街道收集泔水喂猪,我们得以常见面,她还是瘦瘦的,还是那么倔强地为生活苦苦地喂养着8头猪。虽儿女已长大,都能打工了,但她说现在还能劳动,要为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多累点,以后也免拖累儿女。我向我的邻居们介绍我这队长的女儿,讲述她的娘家人,讲述往事……
和南繁育种队员一起的日子
在我们下乡期间,乡下就有湖南、安徽、辽宁、贵州等省份的南繁育种队来到村里来育种,因为我们会说普通话,自然就成了他们和村民之间沟通的翻译。这使我们自然地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今天,我和他们还有联系。
安徽阜阳、涡阳育种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大、中专毕业的农业技术员,文化素质较高,劳动观点又很好,都能吃苦耐劳。在安徽,重体力活都是男子负责,就是砍柴挑水都不让女孩子做,他们看到我们当地的女孩子那么辛苦、那么勤劳,都赞叹不已。他们总督促我们的男生多干重活,让我干轻的。有一天,我收工回家准备做饭,看到水缸里没水了,正要挑起水桶去挑水,这时收工回来的育种队员看到了,都大声质问两位值班做饭的男生为什么让我去挑,弄得两位男生赶紧跑来和我抢水桶。
有时我和他们一起上山砍柴回来,他们看我们的菜较差,就把他们吃的好菜、面食端来硬要我吃,他们那种爱护妇女的习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培育的是玉米种子,需要大面积灌溉时,队长就会安排我们几位知青去帮他们干活,我们一起干到晚上12点才能休息,有时还要连续干十几、二十天才能完成。
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
当时的农村缺乏文化生活,农民最大的文化享受,就是看村里的宣传队唱样板戏。
由于有些文化,我们下乡的7个人中就有4人自然地成为宣传队队员,队长、编导全由我们担任,附近的炮兵营部队是水蛟大队的军民联营单位,经常派战士教我们唱革命样板戏,指导我们排练样板戏小段,我就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小段里扮演小常宝。每天晚上,宣传队员到大队排练节目,排好了就到大队所属的十几个村庄巡回演出。有时也到炮营或个别大队联欢。虽然我们表演水平不高,但也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这样的活动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快活了。
在农村过年
下乡的两个年头中,大年初一我都是在农村和黎族群众一起度过的。
乡下过年,热闹而有真情。通常在大年初一的清晨,我们还未从梦中醒来,村里的大伯、大妈们已经围在我们屋外,等我们一醒,就抢着拉我们到他们家一起过年。我们只好答应他们说,每家的酒我们都会去喝,他们才放心地先回家了。
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孙女都和我们一样大了,为了生活方便,他们自己做饭吃。每到那一天,他们总是最早守在我们房门前,为了让他们高兴,我们去的第一家也总是他们家。在老人家里,我们一起喝着他们自酿的糯米酒,尽管老人家只会把鱼、肉、蛋、菜都合在一起煮一大锅,味道不怎样,我们还是大口大口地吃着,跟他们干杯,祝福他们健康长寿,老人笑得合不拢嘴。我们一家吃一点,一天时间里会一口气吃十几家的年饭,喝十几家的年酒,喝得头昏脑涨。晚上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我还跟姑娘们学了几首黎族山歌,半生半熟地唱给他们听,逗得大家都笑弯了腰,一年的第一天就这样欢欢乐乐地度过了。
参加水利大会战
下乡知青没有不参加水利大会战的,我也参加了两次,一次是西河水利大会战,一次是岭曲水利大会战。两次劳动,使我深深体会到了兴修水利的艰险和苦乐,特别是岭曲水利大会战,更让人终生难忘。
当时(1971年初)到岭曲去没有汽车坐,我和队里同批修水利的村民挑着行李和工具,沿着陡坡山路步行而上,走了两天多山路才到达工地。
羊栏公社的一间间大工棚修建在山脚下,是茅草屋顶,里面是两排用木条临时捆起的床架,绑上竹条铺上草席,就是两排大平铺了。
工地没发伙食费,民工的用餐由队里统一安排,粮食是自带的,菜一般是豆芽(把每个人从家里带来的扁豆用箩筐装着,每天浇点水培育成豆芽。)刚开始,我还吃得下,过了一个多星期就吃腻了,实在难以下咽时只好每餐盛点豆汤就着饭吃。看着村民们每天就这样吃,却没人有怨言,我也不好意思暴露自己的情绪。
修水利是辛苦又危险的强体力劳动。男人和较强壮的女人天天抡大锤打石眼,爆破石头,石头爆炸起来石块满天飞溅,防不胜防。即使躲在认为很安全的地方,也难免会发生事故,工地上不时有人被砸得头破血流。
我的工作是与其他妇女一起修平台,用拖拉板拖土。拖平台看似轻松,但拖了几天,手上打起了血泡,手抓到绳子一拉,就痛得直咬牙。山路崎岖,每天上工要爬着山路,手抓山藤荡到平台上去。年轻人手脚麻利还应付得了,那些身子很重的大妈大婶们(有些已40多岁)就较艰难了,要荡好多次才能成功跃上平台。我这时才感觉到,插秧、割稻、挑肥等农活比起水利工地的劳动,算不了什么。
后来公社指挥部抽调我到指挥部当资料员和广播员,我的苦就算到头了。新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把本公社水利工地的好人好事写成报道,送给县水利总指挥部出工地简报,同时抄写在本工地的黑板报上,并用当时的广播器向本工地广播。我和另一位抽调来的资料员还得把这些好人好事编成“对口词”,到工地上去宣传表演,以激发民工的劳动热情和忘我精神。我在水利工地的表现,得到了公社领导的一致好评。
水利工地的劳动虽然辛苦,却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广阔天地,一到休息时间,年轻人积极串走工棚,物色意中人,黎族青年在山坡上约会时对唱山歌谈情说爱,苦中作乐。
有几个苗族姑娘到我们工棚来玩,那些黎族小伙子热情接待她们,亲密交谈,窃窃私语,其彬彬有礼的举止和语气,和平时简直判若两人,令我忍俊不禁。
后记
1971年6月,我在羊栏公社知青会议上评为本年度公社知青的积极分子。同年9月,县知青办安排我到崖县农机厂工作,还把本年度一个宝贵的学徒指标照顾给我。
9月底,我就和村里的父老乡亲告别,离开了这几年关爱着我的人们,离开了留下我青春足迹的土地。
回忆起这段岁月,我的心是快乐的、感激的,因为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年月里,我得到的是更多的人间真情。
1969年3月8日,18岁的我也成了崖县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的一员,我和6位学友一道被安排在崖县羊栏公社水蛟大队的水蛟、白鸡生产队(以村为队)。
记得那天早上,我们带着行李在当时地处菜市场的停车场等待知青专车,车里是初次离家、彷徨不知前路的年轻人,车外是反复叮咛、不忍离去的家人。有一对医生夫妇来给他们的一对儿女送行,他们特地给孩子们戴上了红花,并充满激情地用革命的豪言壮语来鼓励他们。我的母亲只是一个街道小市民,她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只是流着眼泪和邻家临高伯母在车窗外不断叮嘱我需要注意的生活细节。看着哭啼的母亲与邻家伯母,想到自己未卜的前途,我也心酸落泪。
到了羊栏车站,早有水蛟、白鸡生产队的村民,敲锣打鼓列着队伍到车站来迎接我们。我们跟随着各自的队伍,来到了我们的新家——队里给我们建造的一人一间10平方米的茅房,我是唯一的女生,被安排在中间。当时房子里外都已围满了热情的村民,我一进屋,还未看清楚人们的脸面,就被一位黎族老阿婆紧紧抱在怀里,她嘴里乐呵呵地说:“我要认这个做女儿!我要认这个做女儿!”阿婆的热情使我一时不知所措,但也让我消除了不少陌生感。后来听村里人说,这阿婆没生儿女,抱养的一个儿子现在部队,平时难得回一次家,阿婆感到很寂寞,听说这次村里要来几个知青,就想从中挑一个做女儿。后来我在农村的两年半中,阿婆真的把我当做女儿了,每当蒸糯米饭时,就会叫我去她家一块吃。
围着的村民们热情地和我们聊天,问我们姓名、年龄、家庭情况,还亲切地用他们的习惯叫法称呼我们“老李”“老邢”“老陈”。
热闹了一阵,人们都走了,我们几个人看着陌生的房间,睡在木床上辗转难眠,大家都坐立不安,决定去看望另外那3个知青。谁知走到中途就碰上了同样也准备来看望我们的3个知青,大家诉说着进村后的情景,直到天色将晚,他们才回了自己的村庄。
我们的队长及家人
我们生产队的董队长是个典型的黎族中年汉子,高额头、粗鼻子、厚嘴唇,喜欢仰着头、眯着眼睛,说着不太流利的海南话。他和家人都很关心我们。
他的爱人不大会讲海南话,所以很少与我们交谈,但她经常在我们做饭时一言不发地走过来看我们的菜,一看见我们的菜太差了,就跑回家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椰子肉丝煮山豆子给我们下饭。在水稻、地瓜收获的季节,晒谷子、地瓜片时碰到下雨,他们家就会兵分两路,一队收他们自家的粮食,另一队来帮我们。他的两个女儿总是细心地帮我们把雨布或木板垫在地下,然后将尚未晒干的谷子倒在上面摊开晾干,要是地瓜片还得小心地一片片铺开晾干,才不至于发霉变黑。要不是他们帮忙,一旦把粮食弄坏,那我们下季的口粮都会成大问题。
队长的大女儿是一个善良、勤劳、朴实的女孩,我离开水蛟后,听说她已嫁到三亚临春村。如今,她因到我们街道收集泔水喂猪,我们得以常见面,她还是瘦瘦的,还是那么倔强地为生活苦苦地喂养着8头猪。虽儿女已长大,都能打工了,但她说现在还能劳动,要为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多累点,以后也免拖累儿女。我向我的邻居们介绍我这队长的女儿,讲述她的娘家人,讲述往事……
和南繁育种队员一起的日子
在我们下乡期间,乡下就有湖南、安徽、辽宁、贵州等省份的南繁育种队来到村里来育种,因为我们会说普通话,自然就成了他们和村民之间沟通的翻译。这使我们自然地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今天,我和他们还有联系。
安徽阜阳、涡阳育种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大、中专毕业的农业技术员,文化素质较高,劳动观点又很好,都能吃苦耐劳。在安徽,重体力活都是男子负责,就是砍柴挑水都不让女孩子做,他们看到我们当地的女孩子那么辛苦、那么勤劳,都赞叹不已。他们总督促我们的男生多干重活,让我干轻的。有一天,我收工回家准备做饭,看到水缸里没水了,正要挑起水桶去挑水,这时收工回来的育种队员看到了,都大声质问两位值班做饭的男生为什么让我去挑,弄得两位男生赶紧跑来和我抢水桶。
有时我和他们一起上山砍柴回来,他们看我们的菜较差,就把他们吃的好菜、面食端来硬要我吃,他们那种爱护妇女的习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培育的是玉米种子,需要大面积灌溉时,队长就会安排我们几位知青去帮他们干活,我们一起干到晚上12点才能休息,有时还要连续干十几、二十天才能完成。
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
当时的农村缺乏文化生活,农民最大的文化享受,就是看村里的宣传队唱样板戏。
由于有些文化,我们下乡的7个人中就有4人自然地成为宣传队队员,队长、编导全由我们担任,附近的炮兵营部队是水蛟大队的军民联营单位,经常派战士教我们唱革命样板戏,指导我们排练样板戏小段,我就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小段里扮演小常宝。每天晚上,宣传队员到大队排练节目,排好了就到大队所属的十几个村庄巡回演出。有时也到炮营或个别大队联欢。虽然我们表演水平不高,但也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这样的活动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快活了。
在农村过年
下乡的两个年头中,大年初一我都是在农村和黎族群众一起度过的。
乡下过年,热闹而有真情。通常在大年初一的清晨,我们还未从梦中醒来,村里的大伯、大妈们已经围在我们屋外,等我们一醒,就抢着拉我们到他们家一起过年。我们只好答应他们说,每家的酒我们都会去喝,他们才放心地先回家了。
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孙女都和我们一样大了,为了生活方便,他们自己做饭吃。每到那一天,他们总是最早守在我们房门前,为了让他们高兴,我们去的第一家也总是他们家。在老人家里,我们一起喝着他们自酿的糯米酒,尽管老人家只会把鱼、肉、蛋、菜都合在一起煮一大锅,味道不怎样,我们还是大口大口地吃着,跟他们干杯,祝福他们健康长寿,老人笑得合不拢嘴。我们一家吃一点,一天时间里会一口气吃十几家的年饭,喝十几家的年酒,喝得头昏脑涨。晚上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我还跟姑娘们学了几首黎族山歌,半生半熟地唱给他们听,逗得大家都笑弯了腰,一年的第一天就这样欢欢乐乐地度过了。
参加水利大会战
下乡知青没有不参加水利大会战的,我也参加了两次,一次是西河水利大会战,一次是岭曲水利大会战。两次劳动,使我深深体会到了兴修水利的艰险和苦乐,特别是岭曲水利大会战,更让人终生难忘。
当时(1971年初)到岭曲去没有汽车坐,我和队里同批修水利的村民挑着行李和工具,沿着陡坡山路步行而上,走了两天多山路才到达工地。
羊栏公社的一间间大工棚修建在山脚下,是茅草屋顶,里面是两排用木条临时捆起的床架,绑上竹条铺上草席,就是两排大平铺了。
工地没发伙食费,民工的用餐由队里统一安排,粮食是自带的,菜一般是豆芽(把每个人从家里带来的扁豆用箩筐装着,每天浇点水培育成豆芽。)刚开始,我还吃得下,过了一个多星期就吃腻了,实在难以下咽时只好每餐盛点豆汤就着饭吃。看着村民们每天就这样吃,却没人有怨言,我也不好意思暴露自己的情绪。
修水利是辛苦又危险的强体力劳动。男人和较强壮的女人天天抡大锤打石眼,爆破石头,石头爆炸起来石块满天飞溅,防不胜防。即使躲在认为很安全的地方,也难免会发生事故,工地上不时有人被砸得头破血流。
我的工作是与其他妇女一起修平台,用拖拉板拖土。拖平台看似轻松,但拖了几天,手上打起了血泡,手抓到绳子一拉,就痛得直咬牙。山路崎岖,每天上工要爬着山路,手抓山藤荡到平台上去。年轻人手脚麻利还应付得了,那些身子很重的大妈大婶们(有些已40多岁)就较艰难了,要荡好多次才能成功跃上平台。我这时才感觉到,插秧、割稻、挑肥等农活比起水利工地的劳动,算不了什么。
后来公社指挥部抽调我到指挥部当资料员和广播员,我的苦就算到头了。新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把本公社水利工地的好人好事写成报道,送给县水利总指挥部出工地简报,同时抄写在本工地的黑板报上,并用当时的广播器向本工地广播。我和另一位抽调来的资料员还得把这些好人好事编成“对口词”,到工地上去宣传表演,以激发民工的劳动热情和忘我精神。我在水利工地的表现,得到了公社领导的一致好评。
水利工地的劳动虽然辛苦,却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广阔天地,一到休息时间,年轻人积极串走工棚,物色意中人,黎族青年在山坡上约会时对唱山歌谈情说爱,苦中作乐。
有几个苗族姑娘到我们工棚来玩,那些黎族小伙子热情接待她们,亲密交谈,窃窃私语,其彬彬有礼的举止和语气,和平时简直判若两人,令我忍俊不禁。
后记
1971年6月,我在羊栏公社知青会议上评为本年度公社知青的积极分子。同年9月,县知青办安排我到崖县农机厂工作,还把本年度一个宝贵的学徒指标照顾给我。
9月底,我就和村里的父老乡亲告别,离开了这几年关爱着我的人们,离开了留下我青春足迹的土地。
回忆起这段岁月,我的心是快乐的、感激的,因为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年月里,我得到的是更多的人间真情。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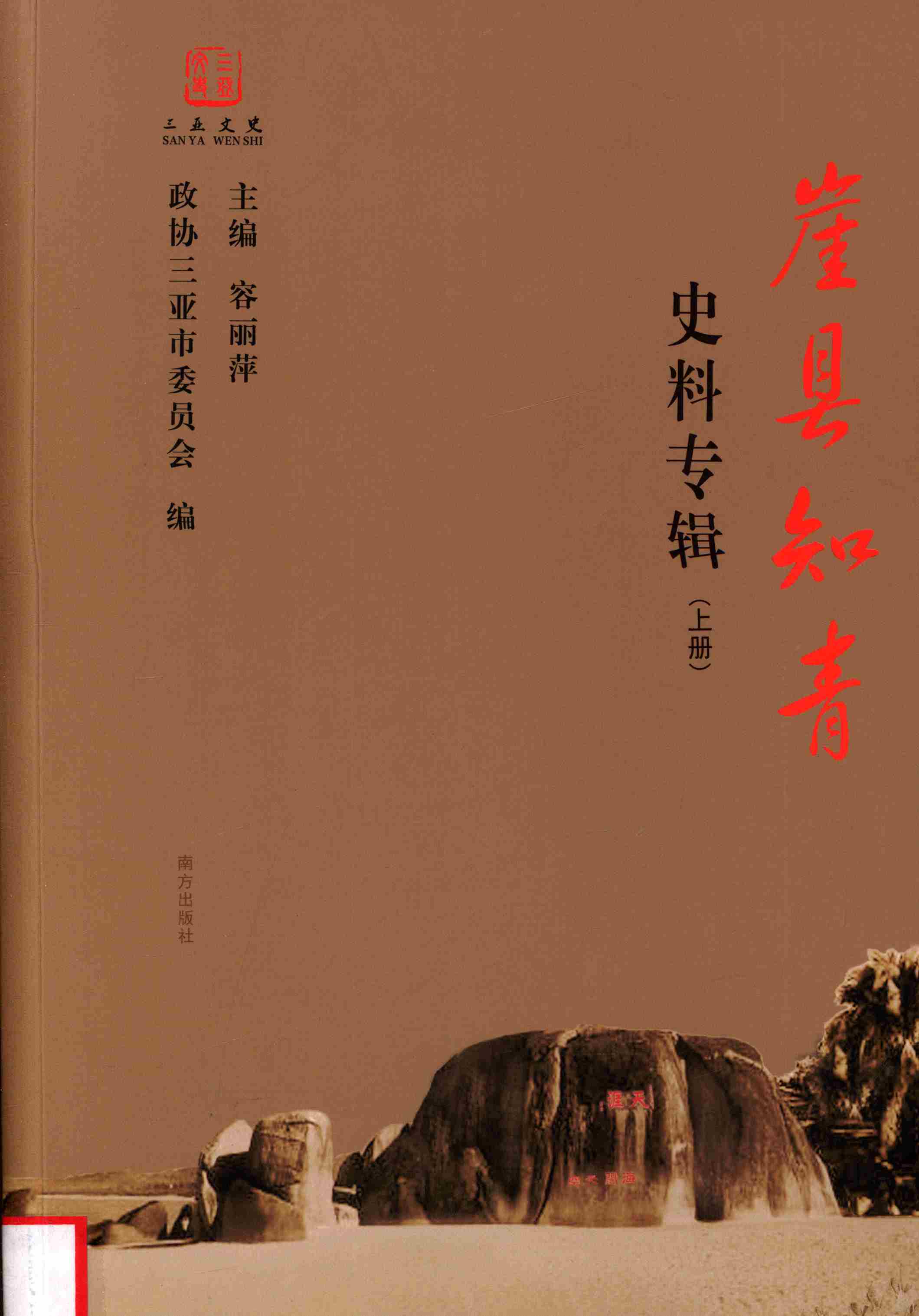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上册》
出版者:南方出版社
本书共有69篇文稿,崖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崖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崖县上山下乡知青安置点简介3篇综述文稿,1956年、 1958年到来崖县的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9篇知青回忆 录,1969年本地知青、潮汕知青12篇知青回忆录,崖县知青场45篇知青回忆录。
阅读
相关地名
崖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