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荒岁月回顾
| 内容出处: |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上册》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1544 |
| 颗粒名称: | 垦荒岁月回顾 |
| 分类号: | K825.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80-90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广州青年马玉良在1950年代末到海南岛崖县垦荒的经历。描述了他乘船到达海南、途中景色、到达前干部学校休整、到达崖县参加垦荒等情况。 |
| 关键词: | 广州青年 崖县 垦荒 |
内容
由广州到崖县
1958年3月21日下午,到码头编队、乘船。等上了船已是晚上。大街上华灯初上,珠江水面倒映着两岸的灯火。我在轮船机器的轰鸣声中睡去。什么时候开的船已经不知道了。醒来时已是早晨。海面上灰蒙蒙的,天水一色,并没有作家们所描写的大海那种瑰丽的色彩。
23日,经雷州半岛时,天气放晴,我们都站在甲板上观赏海景。邱菊秋竟然作起诗来。不过,因为他不是诗人,虽然内心有感,可惜表达不出来,讲的驴唇不对马嘴。我当然也是如此。下午两点多钟,船到海口秀英码头。因水浅,须上小船过渡才能泊岸。上了岸,由伦启良带路(他是驻社干部),走了一段路后,搭公共汽车来到了前干部学校。这是一个空置的地方,学校宿舍有木板床,我们临时在这儿休整。第二天休息一天,我逛了一遍海口。这里马路两旁也有骑楼,和广州的建筑差不多。海南的天气很热,在广州还可以穿单衣,在这儿就只有穿衬衣了。25日早晨6点多钟坐汽车赶赴崖县。我们属今年到崖县的第三批垦荒队,一共80多人,分乘三辆公共汽车。一路上的景色不差,海南岛的春天好像北方的盛夏。汽车经过之处,到处是葱茏茂密的树林。很多树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在别人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菠萝蜜、剑麻、橡胶。中途休息的小镇,大都有香蕉、鸭蛋售卖。一般不论斤两,而以一角钱为单位:香蕉一角钱七只,鸭蛋煮熟的五分钱一个。车到陵水一带,两旁都是高大的椰子树,更显示了热带风光。无怪乎一提到海南岛,往往头脑中浮现出大海、椰子树的画面。晚上,还听到了很动听的苗族民歌。也见到了黎族人,全是穿的黑衣服,女的包头,穿筒裙。汽车经过县城三亚镇,一直驶向驻地——广州青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我们将要在这里落户,参加劳动。对于未来,我考虑的很少,因有朋友,也不觉得孤独。晚上没有床铺,大家都睡在地上,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
次日,根据安排,我们这些新到的垦荒队员(已转换成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社员身份)就开往垦荒的最前线——水源池作业区,投入到雨季到来前紧张的开荒劳动中:砍芭、烧荒、开苗圃、育苗,为大种香茅、油棕作准备。在艰巨的劳作中,流汗流血吃了苦,也强壮了身体,坚定了意志,为今后从事各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生活的熔炉里
生活总是有波澜的,不会那么平顺。1959年7月,我们由水源池作业区来到五工区参加会战。五工区就是原来的广青社所在地,改为农场后,这里变成了第五作业区。这里和周围一大片地方都是平地,也是荒地,只是周围的黎族同胞曾经开荒种过农作物。他们是刀耕火种,一般只种一轮便丢荒了。
我们要在这里种的油棕,是一种木本油料作物,有“世界油王”之称。这里的地属于三级荒地,大都是一人多高的飞机草,还有一些较小的树木。用刀把这些野生作物砍断,断口离地面不能低于三寸。过些天,晒干后,一把火烧掉。然后就是整地,用锄头把地面的茬口锄掉。不要求挖树头,因油棕是挖穴种植,只有在穴位上的树头才要挖去。
这项工作干了好几个月。那时,只要是有月亮的夜晚便要开工。毕竟是夜间,纵使有月光,也不是像灯光那样明亮的。尤其是月亮被云遮住的时候,地面的物体看不清,锄头落下去经常是盲目的,干了半天也不出成绩,我便对旁边的人说,夜晚开工,工效不高。
第二天,我的这句话便出现在宣传栏的漫画上:画中一个人站着,两手拄着锄头,形成“三只脚”,旁白:“马玉良说,夜晚开工工效不高。”“三只脚”是粤语,用来比喻偷懒的人。这幅漫画把我变成了偷懒的人。天哪!只因一句话,就可改变一个人的形象,以往辛辛苦苦的工作全被抹煞了。
我看着漫画,眼里沁出了泪水,无声地扛起锄头往回走。唐志强跟在我后面,小声说:“阿马,想开些啦,现在人心难测,以后不要讲那么多话。”
那幅漫画至今仍深刻在我脑海中。我一样的吃饭,一样的做工,不就是多讲了几句话吗?是我年幼无知,还是我真真正正的错了?
我这样的说话做事没遮没拦,初到荒地不久我就曾吃过亏。记得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号角响遍全国,在这天涯海角的一隅,这个有着二百多名广州青年的地方,也无一例外地引起了躁动。
我刚从学校出来,没有接触过社会,还是张白纸。没人写我的大字报,我也不知别人的事情。但社里动员每个人都要向党交心。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你心里是怎样想的,有什么不符合党的要求的思想,要用书面的形式写出来,交给组织。我是个共青团员,组织上要求我们向党交心,就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心交出来。我的思想极其简单:我是怀着满腔热情和幻想来到海南岛的,但这里的生活太单调了,每天就是出工、吃饭、睡觉三部曲,我觉得很没意思。我把这个想法写了交上去。我原意是批判自己:我们的工作就是开荒、种香茅草,这实际上是对国家做贡献,而觉得没意思这个消极想法是不应该有的。
不料没过几天,驻社干部伦启良就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了我,重复了我的“出工、吃饭、睡觉”三部曲,大加鞭挞了一通。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觉得被人愚弄了。社里经常召开大会,号召向坏人坏事做斗争。这种大会实质是斗争会。在总社,通常是在白天开,我们也会过去参加。在水源池作业区,通常是晚上开。晚上在露天地挂一盏汽灯照明。斗争会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出身不好,有历史污点,有反动言论的坏分子,及怕苦怕累逃跑回广州而在海口码头被截回来的人。开会前夕,一般会先召集党团员、积极分子开个小会,告知大会内容和被批斗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想:我们都是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家别井,来到这蛮荒之地奉献青春,有什么言行不当,用得着这样对待吗?当年年轻,有着天然的乐观情绪,在此后的日子里,还是内心充满阳光和欢乐,相信党会带领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
我当上了工区会计
水源池和红光作业区合并,称为一工区。1960年某月,工区会计余策樱调走了。他是高中生,调走也是预料中的事。因那时已对高中生很重视,纷纷调往场部和县城,留在工区的也只有我们这些初中生了。
余的工作由我来接替,这工作是脱产的,会计兼统计,也兼出纳,即负责发工资、每月去场部取几千元钱回来发工资。那时的工资很低,每人也就30多元,扣除伙食费,实际也就剩20多元了。想起来有些后怕,一个人去场部,场部在荔枝沟,距工区约7公里,步行要两个多小时。有时下午五点多钟往回赶,一个人走夜路。有时碰到略懂广州话的黎族青年主动和我搭话,心中忐忑。幸好那时社会治安好,人心纯朴,倒是未闻抢劫事件发生(除了粮食和农作物之外)。
会计相当于工区的第三把手了。除了主任、副主任之外,只有我一个脱产干部,我自认能胜任这个工作。早在小学六年级时,数学老师就教过我们记账:借方、贷方,收入支出、账目要平衡,幸而有了这些基础知识。其实记账的知识是小学课本没有的,是老师额外教的。
有了基础知识垫底,接过余策樱的账本,很自然地就继续下去了。也因为工区发生的事情少,因而项目简单。工区有蔬菜队、畜牧场、奶牛场,奶牛场也只有二十多头奶牛。奶牛其实也是菜牛,生了牛犊有奶了就挤奶,挤出来的奶交给炼奶员制成炼奶。她用一个大盆子盛奶,下生炭火,不停地用木铲搅拌。要搅拌一整天,才能生产几瓶炼奶。这些炼奶最终要交到县商业局。
至于蔬菜,除了自用外,也可以外卖。派人用牛车拉到县城三亚,当时种菜的人还不多,因而销路很好。有时也有部队的人来买菜。在崖县的大山里驻有一些部队,虽然部队也有自己的农场,但想必不能完全自给。当时的菜价怎样呢?只记得空心菜是两分钱一斤,最贵的是辣椒,要三角六一斤。
会计是脱产干部,常和主任、副主任一起商讨工作,也享受点“特权”。记得有次和麦桢源、陈兴主任到水源池,他们不知在哪搞到一个鱼炮,就是把黑色火药用报纸卷成一个圆筒形,外有引线。水源池有三个水库,最上游的一个是榆林海军于1958年建的,用200毫米供水管向榆林海军基地供水。中间一个也是向榆林供水用,直径100毫米。估计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后来才又建一个。下游还有个水库是土坝,是当地农民为灌溉之用建的,我们叫它“三八池”,因我们工区女同志在那洗澡而取名。
我们就在三八池炸鱼。在未炸之前先抛下一些烂菜叶等饭堂垃圾,过了差不多半小时,估计鱼儿已经集中了,才把炸药抛下去。一声巨响,水柱冲天,鱼儿纷纷翻出水面。看到这个场景,心情振奋,马上跳下水去捞鱼。其实浮上水面的都是些小鱼,大鱼都在水底,也没死,只不过震昏了而已。因不会潜水也只能捞点小鱼了。
这种鱼是真正的山水鱼,我们捞了半筐。鱼的样子有点像鲮鱼,请炊事员煮熟,没有任何调味料,也没有油,只是放点白菜和盐。吃起来无任何腥味,肉质嫩滑,非常好吃。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一次鱼。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吃过无数次的鱼,包括鲈鱼、桂鱼、福寿鱼、扁鱼、塌沙鱼,等等,但都比不上水源池的山水鱼好吃。
我的会计工作转眼已做了半年时间。突然有一天,副场长陈亮坐着解放牌卡车来到了红光作业区,说是要调牛、调羊,场部取这些东西叫“调”,也就是上调的意思。当时是上午九时左右,主任不在,牛羊都放出去了,不知放在哪个方向,我急得团团转,埋怨陈副场长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当时的通信真是落后!工区有一部手摇电话,可以通过“妙林”总机和场部联系。那是一部什么电话啊!这边讲话,用了最大的声音,总机才勉强听到,待转到荔枝沟场部,就什么都听不到了。我方讲话对方听不清,对方讲话我方还可勉强听到。后来才知道,这部电话是送话器坏了,但为什么不修复它呢?这部电话实际上是个摆设。副场长大概也是事情紧急,当然他也无法事先通知了。
事后,场部干部彭国权来到工区,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他先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表示对我的理解和同情,然后宣布要我下放当工人。
其实陈亮副场长是个好领导,他说话温和,待人和气。不过,再好的人也会有脾气,也会有自尊心。我一个小小的会计,竟敢“埋怨”场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我的会计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在畜牧场牧牛
我调到畜牧场,是因为畜牧场的头儿彭志坚看中了我。畜牧场搬迁前,彭想物色几个心中满意的人选。场里有两群牛,大约一百多头,还有四十多只羊。在红光作业区,周围的土地都开垦了,荒地很少,很多是周围黎族农民开垦过、种过水稻的。黎族同胞那时种地不怎么施肥,因此,种过几轮后,就休闲或丢荒了。这种地也没多少草。因此,畜牧场的搬迁势在必行。
新畜牧场选在三亚老飞机场附近。该机场是日军占领时修建的,后已废弃。解放后,有解放军部队驻扎,是搞后勤的。畜牧场就位于飞机场西边。这个地方离海不远,地势平坦,与飞机场持平,相对北边的公路和村庄、农田,这里是一片高地,向南步行15分钟就是海边。海边是几十米宽的沙滩,非常干净。放眼望去,很长很长的沙滩环抱着碧蓝色的海水。隔着海遥望到的是东岛、西岛,风景秀美。
新畜牧场有一口水井留存。我们就利用这口井做水源,在旁边盖起了两间茅屋,住人及煮饭用。又盖了牛栏、羊舍。
这里是沙土地,草长的稀疏,到处是仙人掌。高地以东直到飞机场,有一片湿地,有水和树木,草长势较好,是较为理想的牧场,但面积有限。在高地西北边,绕过农田和儋州村,后方还有一片荒地,面积很大,三亚至八所的铁路穿过其间。我经常宁愿走远点,把牛群赶到那个地方放牧。待牛群安定下来后,爬上铁路桥墩,在桥墩与钢轨的空间休息。桥墩矮,很容易爬上去。在那里甚至可以睡觉。因大群牛是两个人放牧,其中一人睡觉完全可以放心。那个地方有水有草,周围没有农田,牛群根本不会走远。
畜牧场共有九人,我兼职保管员。用草墙隔出一间小房,存放粮食、番薯之类的东西。每餐按开餐人数把米称出来,煮饭是轮流的。除了两群牛、一群羊外,还有两头荷兰牛和一头杂交的小牛仔,由肖亚胜专门放牧。
我们在高地斜坡下靠近儋州村的田地旁开辟了一小块地,呈长条形,种蔬菜。周围也没有卖菜的,想吃就得自己种。我和几个抽烟的还种了点烟叶,成熟时晒干切成烟丝抽。
我们每天早晨九点钟开始放牛,下午四点往回走。牛群边吃边走,回到畜牧场已是五点钟,这是标准的收工时间。收工后,我们通常去海里游泳,回来后,用井水从头淋到脚,浑身清凉,然后才吃饭。我们这小单位,日子过得平静有序,比起出大力、流大汗的开荒一线劳动,轻松多了。
彭志坚场长是马来亚归侨生,为人比较灵活,比较能说会道,对畜牧颇有研究,又注意搞好与周边农民的关系。他想出了以牛粪换番薯,来解决荷兰牛的饲料来源问题。他这是一箭三雕:既解决了荷兰种牛的精饲料来源问题,又可以使放牧人员填饱肚子,还保证了牛栏的清洁卫生。儋州人跟我们交换,一切都由他们动手。他们用牛车拉来番薯,拉走牛粪,为我们清扫了牛舍,什么都搞得妥妥帖帖。
但这个办法遭到了工区麦主任的反对,他说服场部,由场部下命令:牛粪是肥料,农场自用,不能擅自处理。接下来,场部派来了解放牌汽车拉走了牛粪。其实麦的主意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试想,相隔十几公里,用解放牌汽车来拉牛粪,牛粪的价值决不会抵销汽油费和汽车损耗(折旧)费,况且还要人工装卸费,稍有成本意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而且荷兰牛没有精饲料,作为种公牛的价值大打折扣。荷兰牛作为种公牛,光吃草肯定不行。因为这不是外国,像新西兰、澳洲,有优质牧草。我们这里不行,我们的草只适宜本地牛。
事实证明,荷兰牛与本地牛杂交而生的小牛极少,且很多都夭折。当然和草的质量也有关,这片地方虽然大,草还是不够。彭志坚考虑过种植优质牧草或将牧场搬到大山里去,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能实现。
彭志坚以牛粪换番薯的双赢计划虽实行不久就夭折了,但我们和儋州村的关系并没受到什么影响。我们有时应邀到儋州村做客,村民杀狗款待我们。他们的饭很好吃,是用好米煮的,煮得很硬,像是广州人所说的“虾仔饭”。我们喝酒、吃狗肉。旁边有妇女,给我们装饭。如你说不吃了,她们也决不会像大陆人那般客套。她们会端来一碗水给你,不是开水,只是井水,让你饭后漱口。
这里保留着纯朴的民风。村中有青年屋,供青年男女活动。每年春节,青年男女会到空旷的高地聚集,跳舞、唱歌、玩游戏。我们曾被邀请到儋州村参观青年屋,里面有大通铺可以睡觉。有调皮的小青年示意我们找女孩子聊天,他们都是讲白话(粤语)的。倒不是语言的关系,毕竟习俗不同,我们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
彭志坚还和回民打交道。回民住在羊栏圩镇,距离畜牧场不远。因为民族习俗,他们对牛羊牧养较为重视,也就有了交流的基础。因有交流,我们就有机会走进他们的生活。一个晚上,我们向海边出发,去参加回民的捕鱼活动。他们实际上是刮鱼,即用一艘船拖着一条百十米的缆绳,由岸边驶向海中约一百多米,拴好渔网。然后横向行驶约数十米后再折返岸边,使这张渔网横在海中。船在往返中已各拖带了另一条缆绳,这条缆绳很粗,直径约三厘米。这时,已有两条绳子通向岸边,相距数十米,正好是渔网的长度。每条缆绳都有一个绳套。两条缆绳大约有二十人,每边十人左右。把绳套套在后腰上,面向大海,双手拉绳,随着海浪的节拍向后用力,边退边拉绳。当海浪退去的时候,便随着向前走几步。当海浪涌上来时,便借力向后用力拉。全过程约两个多小时。当渔网拉上岸时,网内的鱼儿在扑腾,别有一番丰收的喜悦。
这一网鱼大约一百斤左右。接着是分鱼,他们先把墨鱼拣出来,这是分给头头的。大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高级的鱼类。其余的鱼被分成十几二十份,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也分到了一份鱼。这种鱼叫不出名称,类似青鱼,大部分是这种鱼,还有几条不同品种的,一概不知名。这份鱼大约六七斤。回来后,立即洗来煲鱼粥。食之,无任何腥味,我们也没有任何调料,就是放点盐而已。吃时觉得很美味。海鱼如果是活着宰杀确实不错,从此我知道了鱼还有不腥的。
和周边的群众融洽相处,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孤单烦闷,还可以从中收获欢乐。
记得畜牧场还在红光作业区时,我们也曾到相邻的黎族村寨游玩过一次。那是农历三月初三晚上,我们畜牧场几个年轻人摸黑出发,沿小路走到离我们最近的黎村。我们的出现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照样过他们的“三月三”节。村寨并不大,却热闹非凡。人们大概全都从家里出来了,整个村像是一个墟。小路边有很多卖农副产品的,大多是吃的东西。在路两边,坐着一群群的青年男女,他们在唱歌,每群人有五六个,有的十个八个,男女对面而坐,中间间隔大约也就两米。我们分析这不只是一个村的,而是周边几个村的。
青年男女唱的歌很动听。这和我们平时在舞台银幕上听到的少数民族歌曲不大一样,是原汁原味的黎歌,不是经过汉族音乐家改编的。曲调、旋律都比较简单,听起来有一种原始的感觉。我们虽然听不懂黎话,但从歌唱者的表情可以看出,这无疑是情歌。男孩唱完女孩唱,绝对是对歌的形式。女孩子的年龄也就是十六七岁,很年轻,面带羞涩。唱完一首时往往会掩面浅笑,姊妹拥作一团。据说通过对歌,相互了解了,便可定下婚姻大事。这种风俗应该比汉族以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现时代的“家长干预”更能体现婚姻自由吧!
我们在村里顺着小路,踏着朦胧月色走了一圈,就回驻地去。一路上,黎歌声如影随形跟着我们走了很远很远。
我于1961年到畜牧场,干了一年多,到1962年,大约是夏秋季,接到通知到五工区参加基干民兵集训。我的牧牛生涯从此结束了。
我得了水肿病
1959年春季,海南岛已出现了粮食紧张趋势。农场因不种粮食,除了国家配给的大米外,无其他任何副食品。一开始,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后来逐渐增加了些,到秋季,已经平均每月有28—33斤大米了。但因没有油水,还是填不饱肚子。
1959年夏季时,我得了水肿病。一开始是脚踝、膝盖肿,后肿到面部。那些地方,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小坑,很久都不能复原。除了肿,浑身都没有力气,脚步轻浮。我所在的作业区90多人,大约有十余人得此病。
当时广州也开始有点紧张,但情况还算好些,毕竟是大城市,广州当时还有饼干卖,要凭票供应。于是,很多人收到家里寄来的饼干。我无此福气。我父母早逝,后由大哥抚养。大哥已经有三个孩子,我可不敢开口求援。忍到秋季(那时我的水肿已好了),终于向我的哥哥姐姐们发信求助了。大哥寄来10元钱,二姐也寄过钱,多少已不记得了。三姐寄的最多,一次就寄来15元,还有5斤全国粮票,三哥也寄来3斤粮票,这些粮票后来去三亚时全部用光了。它们满足了我的吃一次饱饭的愿望,不止一次,而是数次。有一次,一餐竟然吃了一斤十二两(十六两秤),每半斤装一个大碗,共三大碗再加一小碗四两,再配一碟咸鱼白菜。太饱了,吃的我出了饭店走不了路,不得不和同伴坐在路边休息,真是饿也痛苦、饱也痛苦。
我的水肿病在八九月时好了。在此之前,上级给每个水肿病人配了一斤米糠、半斤黄豆、一个椰子,还有半斤椰子油。说是米糠要煮水喝,我哪管得了那么多,就这样煮着吃了。那半斤椰子油和黄德胜换了一盒罐头。黄德胜是印尼归侨生,他的家人从海外给他寄来一些罐头。其中有一盒画着北极熊,全部外文,看不懂。他说是熊肉,我打开后,才发现是奶油,于是每餐吃饭,我都挖一勺放在饭里。这也对治愈水肿病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的香烟故事
我原来对香烟根本不感兴趣,记得十二岁时,第一次接触烟。姐夫是抽烟的,每月发工资时,他都买两条,放在家里抽。有一次,我拿了他一支烟,趁他上班不在家,偷偷地抽掉了约半支。一股子苦味,还呛鼻子,剩下半截扔到煤炉里了。
参加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到海南岛崖县,我们也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先是上山砍柴,就是砍树,用木材炼钢。在崖县安游附近,有一条铁路路基。路基很高,我们就从这路基中间挖一条长沟。据说这叫“地炉”,可以炼几百吨钢。在此之前,挖了一整天,晚上也没睡觉,第二天继续干。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觉了。第二天白天,感到听觉出了问题周围的声音都变小了。晚上再挖时,已经没有精神了,那个困呐内!居然可以一边挖一边睡。社里对抽烟的每人发了一包烟,不要钱,据说是记账的,到时扣除。为了抵挡睡意,我也要了一包。可是一包烟抽完了,还是困,根本没起作用。
地炉还没挖完,我们又大兵团转移去秋收了。秋收,就是收割水稻。那时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时代,我们都属公社管辖。三餐饭不要钱,走到哪吃到哪。工作是分到哪就干到哪。行李随身带,走到哪睡到哪。因不可能每天回农场,有时就在村庄的稻草堆睡觉。好在禾秆草多,在地上铺上一层禾秆草,打开行李就睡,在就近的河里冲凉(洗澡)。工作不可能是八小时,起码要干到天黑,甚至干到半夜。那时公社经常开会,一些小会要求干部和党团员都参加。夜晚在一间屋子里开会,吸烟的人很多,整间屋子烟雾弥漫。公社干部都是海南人,讲海南话。我们广州青年听不懂,觉得乏味,就在地上睡觉,有些坐着睡,有的半躺着,或者加入抽烟大军,掏出烟来吞云吐雾。农村屋的地面都是土地面,开会这间房屋挤了三十多人,满满的,凳子也不够用,只有挤在地上了。
会议开到半夜,回到田地时,其他人还在工作。已是下半夜,我们的饭堂煮了糖水送到工地。不干工作还有糖水喝,我觉得内疚。别人干活我们开会,我觉得心里不是味儿。
1959年7月,正是海南岛的雨季,我们广州知青集中在五工区开荒种油棕。那时已是粮食紧张时期。吃不饱,总想找点什么东西吃,但有什么能吃的呢?只有椰子。这椰子,街上是买不到的,只有黎族同胞的村落才有。但那时钱已经大为贬值,椰子由1958年的一角钱一只涨到了一块钱、一块五角钱一只,还不一定买得到。农民不要钱,要物。最可靠的是用烟、酒去换。这时,恰好在场部附近的部队合作社新到了一批烟。农民去买不卖,但我们广州知青可以买。得知这个消息,我们几个人相约一同去买。我们每人都买了一两条。烟很便宜,大约一角五分钱一包,一大条二十包。我买了一大条红炮台牌,是云南烟。原想用这些烟去农村换椰子,一包烟就可以换一只椰子,谁知此后再也没时间去换椰子了。
根据政治形势的要求,农场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大战八九月”的口号。我们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以上,吃饭也不能回工区,而是送饭到工地。最怕是晚上出月亮,一出月亮就一定要开工的。有时一天要干二十个小时。这些香烟已经无法拿去换椰子了。因为从农场步行到山边的农村(那里有大片的椰子林),要走差不多一小时,来回要两个多小时,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只好拿来自己享用。由于工作艰苦,中途抽一支烟,也可缓解一下疲劳。由不会到会,二十包烟抽完,我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烟民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物资奇缺,香烟的来源当然没有保障,买不到怎么办?只有退而求其次,买烟丝、烟叶,再买不到就捡烟头。香烟烟头,还剩下一小截的,我们称为“肉蜢”(广州话),手卷烟丝抽剩下的,我们称它为“棺材钉”,有时烟瘾来了,手头没有烟,就用木瓜叶切丝代替。
那时待人接物,如递上一支烟或接受一支烟,那将大大地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和相互了解。
朋友谭汝荣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自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也交结了一些朋友。到垦荒队后,有一位新交的朋友,在工作上、生活上予我很多帮助,使我至今难忘。
他原是广东的一个农村青年,上学到初中二年级,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很苦,又吃不饱。他听了亲戚的话,跑来海南岛找工作。以投亲靠友的方式,在农场找到了工作,住了下来。他这种情况的人在我们农场不少。
我认识他是在1962年7月份。正是备战的时候,我调来五工区参加基干民兵集训,平常就做机动工。所谓机动工,就是没有固定的工作,可随意变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他也是机动工,因而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晚上放哨也在一起。我发觉他很诚实,工作也肯干,具有农村青年那种纯朴的性格。由于性格相近与工作中经常接触,我们在无形中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工作起来总是老老实实,毫无一点欺骗,质量很好。因自小习惯劳动,显然比我强得多。虽然身体比我瘦小,但在劳动上却是我的先生,他曾在工作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五工区原来住的都是茅草屋。1962年下半年计划盖砖瓦房,为筹集材料,派出30多人前往尖峰岭伐木。我和他都是这支伐木队的成员。
尖峰岭是海南三大原始森林之一,环境险恶。那里有个林场,规模很大。工区领导已和林场取得联系。一开始我们也参加伐木,后出于安全考虑,改为修便道,以工换料。但小的木材还是我们自己砍伐。在尖峰岭工作的两个多月的艰苦日子里,正是他给予我的帮助,使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那时除了每天正常的工作外,还有突击劳动——上山砍树。在一天中,每人的任务是十条三级树(一丈二尺长、三寸头、两寸尾),两人一条一级树(一丈二尺长、五寸头、三寸尾),砍好还要扛回驻地。劳累自不待说,就任务本身来讲,也够繁重的,体力不强就很难完成。我们两人合作,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即使他比我多做了很多,但他从没有只记在自己的账上,而是算我们两个人做的。这种同舟共济的无私精神令我非常感动。
由于工作繁重,体力消耗大,因而每天的饭都吃不饱。往往上午九点多钟肚子就饿了。他又靠外面的同乡关系,买了很多高价米,补充粮食不足。当时全队30多人,每人都是靠在家的亲朋好友买米自己煮来加餐。我没有亲戚,在家也无朋友,幸而他解决了这个难题,不然真不知怎样过呢!
和他相处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却是无比的深厚。分别的时候,我俩内心是很难过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可恶的疾病的影响,我不得不离开农场了。走的时候,他一路相送,帮我挑着行李直到三亚。下午他才搭公共汽车回农场。告别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的眼里瞬时潮润欲泪。晚上,住县城旅店,我在行李里发现了一封信,是他留给我的,信里还夹着五元钱。农场已半年未发工资了,而他居然把仅有的五元钱给了我。
我捏着这五元钱,心里百般滋味。明天,我就要离开三亚,永远告别农场了。从好友谭汝荣又想及其他的农友,想及这几年在垦荒队里、农场里度过的艰苦并快乐的日子。一股暖流充斥心头,久久不能平息。
1958年3月21日下午,到码头编队、乘船。等上了船已是晚上。大街上华灯初上,珠江水面倒映着两岸的灯火。我在轮船机器的轰鸣声中睡去。什么时候开的船已经不知道了。醒来时已是早晨。海面上灰蒙蒙的,天水一色,并没有作家们所描写的大海那种瑰丽的色彩。
23日,经雷州半岛时,天气放晴,我们都站在甲板上观赏海景。邱菊秋竟然作起诗来。不过,因为他不是诗人,虽然内心有感,可惜表达不出来,讲的驴唇不对马嘴。我当然也是如此。下午两点多钟,船到海口秀英码头。因水浅,须上小船过渡才能泊岸。上了岸,由伦启良带路(他是驻社干部),走了一段路后,搭公共汽车来到了前干部学校。这是一个空置的地方,学校宿舍有木板床,我们临时在这儿休整。第二天休息一天,我逛了一遍海口。这里马路两旁也有骑楼,和广州的建筑差不多。海南的天气很热,在广州还可以穿单衣,在这儿就只有穿衬衣了。25日早晨6点多钟坐汽车赶赴崖县。我们属今年到崖县的第三批垦荒队,一共80多人,分乘三辆公共汽车。一路上的景色不差,海南岛的春天好像北方的盛夏。汽车经过之处,到处是葱茏茂密的树林。很多树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在别人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菠萝蜜、剑麻、橡胶。中途休息的小镇,大都有香蕉、鸭蛋售卖。一般不论斤两,而以一角钱为单位:香蕉一角钱七只,鸭蛋煮熟的五分钱一个。车到陵水一带,两旁都是高大的椰子树,更显示了热带风光。无怪乎一提到海南岛,往往头脑中浮现出大海、椰子树的画面。晚上,还听到了很动听的苗族民歌。也见到了黎族人,全是穿的黑衣服,女的包头,穿筒裙。汽车经过县城三亚镇,一直驶向驻地——广州青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我们将要在这里落户,参加劳动。对于未来,我考虑的很少,因有朋友,也不觉得孤独。晚上没有床铺,大家都睡在地上,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
次日,根据安排,我们这些新到的垦荒队员(已转换成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社员身份)就开往垦荒的最前线——水源池作业区,投入到雨季到来前紧张的开荒劳动中:砍芭、烧荒、开苗圃、育苗,为大种香茅、油棕作准备。在艰巨的劳作中,流汗流血吃了苦,也强壮了身体,坚定了意志,为今后从事各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生活的熔炉里
生活总是有波澜的,不会那么平顺。1959年7月,我们由水源池作业区来到五工区参加会战。五工区就是原来的广青社所在地,改为农场后,这里变成了第五作业区。这里和周围一大片地方都是平地,也是荒地,只是周围的黎族同胞曾经开荒种过农作物。他们是刀耕火种,一般只种一轮便丢荒了。
我们要在这里种的油棕,是一种木本油料作物,有“世界油王”之称。这里的地属于三级荒地,大都是一人多高的飞机草,还有一些较小的树木。用刀把这些野生作物砍断,断口离地面不能低于三寸。过些天,晒干后,一把火烧掉。然后就是整地,用锄头把地面的茬口锄掉。不要求挖树头,因油棕是挖穴种植,只有在穴位上的树头才要挖去。
这项工作干了好几个月。那时,只要是有月亮的夜晚便要开工。毕竟是夜间,纵使有月光,也不是像灯光那样明亮的。尤其是月亮被云遮住的时候,地面的物体看不清,锄头落下去经常是盲目的,干了半天也不出成绩,我便对旁边的人说,夜晚开工,工效不高。
第二天,我的这句话便出现在宣传栏的漫画上:画中一个人站着,两手拄着锄头,形成“三只脚”,旁白:“马玉良说,夜晚开工工效不高。”“三只脚”是粤语,用来比喻偷懒的人。这幅漫画把我变成了偷懒的人。天哪!只因一句话,就可改变一个人的形象,以往辛辛苦苦的工作全被抹煞了。
我看着漫画,眼里沁出了泪水,无声地扛起锄头往回走。唐志强跟在我后面,小声说:“阿马,想开些啦,现在人心难测,以后不要讲那么多话。”
那幅漫画至今仍深刻在我脑海中。我一样的吃饭,一样的做工,不就是多讲了几句话吗?是我年幼无知,还是我真真正正的错了?
我这样的说话做事没遮没拦,初到荒地不久我就曾吃过亏。记得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号角响遍全国,在这天涯海角的一隅,这个有着二百多名广州青年的地方,也无一例外地引起了躁动。
我刚从学校出来,没有接触过社会,还是张白纸。没人写我的大字报,我也不知别人的事情。但社里动员每个人都要向党交心。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你心里是怎样想的,有什么不符合党的要求的思想,要用书面的形式写出来,交给组织。我是个共青团员,组织上要求我们向党交心,就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心交出来。我的思想极其简单:我是怀着满腔热情和幻想来到海南岛的,但这里的生活太单调了,每天就是出工、吃饭、睡觉三部曲,我觉得很没意思。我把这个想法写了交上去。我原意是批判自己:我们的工作就是开荒、种香茅草,这实际上是对国家做贡献,而觉得没意思这个消极想法是不应该有的。
不料没过几天,驻社干部伦启良就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了我,重复了我的“出工、吃饭、睡觉”三部曲,大加鞭挞了一通。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觉得被人愚弄了。社里经常召开大会,号召向坏人坏事做斗争。这种大会实质是斗争会。在总社,通常是在白天开,我们也会过去参加。在水源池作业区,通常是晚上开。晚上在露天地挂一盏汽灯照明。斗争会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出身不好,有历史污点,有反动言论的坏分子,及怕苦怕累逃跑回广州而在海口码头被截回来的人。开会前夕,一般会先召集党团员、积极分子开个小会,告知大会内容和被批斗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想:我们都是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家别井,来到这蛮荒之地奉献青春,有什么言行不当,用得着这样对待吗?当年年轻,有着天然的乐观情绪,在此后的日子里,还是内心充满阳光和欢乐,相信党会带领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
我当上了工区会计
水源池和红光作业区合并,称为一工区。1960年某月,工区会计余策樱调走了。他是高中生,调走也是预料中的事。因那时已对高中生很重视,纷纷调往场部和县城,留在工区的也只有我们这些初中生了。
余的工作由我来接替,这工作是脱产的,会计兼统计,也兼出纳,即负责发工资、每月去场部取几千元钱回来发工资。那时的工资很低,每人也就30多元,扣除伙食费,实际也就剩20多元了。想起来有些后怕,一个人去场部,场部在荔枝沟,距工区约7公里,步行要两个多小时。有时下午五点多钟往回赶,一个人走夜路。有时碰到略懂广州话的黎族青年主动和我搭话,心中忐忑。幸好那时社会治安好,人心纯朴,倒是未闻抢劫事件发生(除了粮食和农作物之外)。
会计相当于工区的第三把手了。除了主任、副主任之外,只有我一个脱产干部,我自认能胜任这个工作。早在小学六年级时,数学老师就教过我们记账:借方、贷方,收入支出、账目要平衡,幸而有了这些基础知识。其实记账的知识是小学课本没有的,是老师额外教的。
有了基础知识垫底,接过余策樱的账本,很自然地就继续下去了。也因为工区发生的事情少,因而项目简单。工区有蔬菜队、畜牧场、奶牛场,奶牛场也只有二十多头奶牛。奶牛其实也是菜牛,生了牛犊有奶了就挤奶,挤出来的奶交给炼奶员制成炼奶。她用一个大盆子盛奶,下生炭火,不停地用木铲搅拌。要搅拌一整天,才能生产几瓶炼奶。这些炼奶最终要交到县商业局。
至于蔬菜,除了自用外,也可以外卖。派人用牛车拉到县城三亚,当时种菜的人还不多,因而销路很好。有时也有部队的人来买菜。在崖县的大山里驻有一些部队,虽然部队也有自己的农场,但想必不能完全自给。当时的菜价怎样呢?只记得空心菜是两分钱一斤,最贵的是辣椒,要三角六一斤。
会计是脱产干部,常和主任、副主任一起商讨工作,也享受点“特权”。记得有次和麦桢源、陈兴主任到水源池,他们不知在哪搞到一个鱼炮,就是把黑色火药用报纸卷成一个圆筒形,外有引线。水源池有三个水库,最上游的一个是榆林海军于1958年建的,用200毫米供水管向榆林海军基地供水。中间一个也是向榆林供水用,直径100毫米。估计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后来才又建一个。下游还有个水库是土坝,是当地农民为灌溉之用建的,我们叫它“三八池”,因我们工区女同志在那洗澡而取名。
我们就在三八池炸鱼。在未炸之前先抛下一些烂菜叶等饭堂垃圾,过了差不多半小时,估计鱼儿已经集中了,才把炸药抛下去。一声巨响,水柱冲天,鱼儿纷纷翻出水面。看到这个场景,心情振奋,马上跳下水去捞鱼。其实浮上水面的都是些小鱼,大鱼都在水底,也没死,只不过震昏了而已。因不会潜水也只能捞点小鱼了。
这种鱼是真正的山水鱼,我们捞了半筐。鱼的样子有点像鲮鱼,请炊事员煮熟,没有任何调味料,也没有油,只是放点白菜和盐。吃起来无任何腥味,肉质嫩滑,非常好吃。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一次鱼。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吃过无数次的鱼,包括鲈鱼、桂鱼、福寿鱼、扁鱼、塌沙鱼,等等,但都比不上水源池的山水鱼好吃。
我的会计工作转眼已做了半年时间。突然有一天,副场长陈亮坐着解放牌卡车来到了红光作业区,说是要调牛、调羊,场部取这些东西叫“调”,也就是上调的意思。当时是上午九时左右,主任不在,牛羊都放出去了,不知放在哪个方向,我急得团团转,埋怨陈副场长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当时的通信真是落后!工区有一部手摇电话,可以通过“妙林”总机和场部联系。那是一部什么电话啊!这边讲话,用了最大的声音,总机才勉强听到,待转到荔枝沟场部,就什么都听不到了。我方讲话对方听不清,对方讲话我方还可勉强听到。后来才知道,这部电话是送话器坏了,但为什么不修复它呢?这部电话实际上是个摆设。副场长大概也是事情紧急,当然他也无法事先通知了。
事后,场部干部彭国权来到工区,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他先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表示对我的理解和同情,然后宣布要我下放当工人。
其实陈亮副场长是个好领导,他说话温和,待人和气。不过,再好的人也会有脾气,也会有自尊心。我一个小小的会计,竟敢“埋怨”场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我的会计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在畜牧场牧牛
我调到畜牧场,是因为畜牧场的头儿彭志坚看中了我。畜牧场搬迁前,彭想物色几个心中满意的人选。场里有两群牛,大约一百多头,还有四十多只羊。在红光作业区,周围的土地都开垦了,荒地很少,很多是周围黎族农民开垦过、种过水稻的。黎族同胞那时种地不怎么施肥,因此,种过几轮后,就休闲或丢荒了。这种地也没多少草。因此,畜牧场的搬迁势在必行。
新畜牧场选在三亚老飞机场附近。该机场是日军占领时修建的,后已废弃。解放后,有解放军部队驻扎,是搞后勤的。畜牧场就位于飞机场西边。这个地方离海不远,地势平坦,与飞机场持平,相对北边的公路和村庄、农田,这里是一片高地,向南步行15分钟就是海边。海边是几十米宽的沙滩,非常干净。放眼望去,很长很长的沙滩环抱着碧蓝色的海水。隔着海遥望到的是东岛、西岛,风景秀美。
新畜牧场有一口水井留存。我们就利用这口井做水源,在旁边盖起了两间茅屋,住人及煮饭用。又盖了牛栏、羊舍。
这里是沙土地,草长的稀疏,到处是仙人掌。高地以东直到飞机场,有一片湿地,有水和树木,草长势较好,是较为理想的牧场,但面积有限。在高地西北边,绕过农田和儋州村,后方还有一片荒地,面积很大,三亚至八所的铁路穿过其间。我经常宁愿走远点,把牛群赶到那个地方放牧。待牛群安定下来后,爬上铁路桥墩,在桥墩与钢轨的空间休息。桥墩矮,很容易爬上去。在那里甚至可以睡觉。因大群牛是两个人放牧,其中一人睡觉完全可以放心。那个地方有水有草,周围没有农田,牛群根本不会走远。
畜牧场共有九人,我兼职保管员。用草墙隔出一间小房,存放粮食、番薯之类的东西。每餐按开餐人数把米称出来,煮饭是轮流的。除了两群牛、一群羊外,还有两头荷兰牛和一头杂交的小牛仔,由肖亚胜专门放牧。
我们在高地斜坡下靠近儋州村的田地旁开辟了一小块地,呈长条形,种蔬菜。周围也没有卖菜的,想吃就得自己种。我和几个抽烟的还种了点烟叶,成熟时晒干切成烟丝抽。
我们每天早晨九点钟开始放牛,下午四点往回走。牛群边吃边走,回到畜牧场已是五点钟,这是标准的收工时间。收工后,我们通常去海里游泳,回来后,用井水从头淋到脚,浑身清凉,然后才吃饭。我们这小单位,日子过得平静有序,比起出大力、流大汗的开荒一线劳动,轻松多了。
彭志坚场长是马来亚归侨生,为人比较灵活,比较能说会道,对畜牧颇有研究,又注意搞好与周边农民的关系。他想出了以牛粪换番薯,来解决荷兰牛的饲料来源问题。他这是一箭三雕:既解决了荷兰种牛的精饲料来源问题,又可以使放牧人员填饱肚子,还保证了牛栏的清洁卫生。儋州人跟我们交换,一切都由他们动手。他们用牛车拉来番薯,拉走牛粪,为我们清扫了牛舍,什么都搞得妥妥帖帖。
但这个办法遭到了工区麦主任的反对,他说服场部,由场部下命令:牛粪是肥料,农场自用,不能擅自处理。接下来,场部派来了解放牌汽车拉走了牛粪。其实麦的主意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试想,相隔十几公里,用解放牌汽车来拉牛粪,牛粪的价值决不会抵销汽油费和汽车损耗(折旧)费,况且还要人工装卸费,稍有成本意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而且荷兰牛没有精饲料,作为种公牛的价值大打折扣。荷兰牛作为种公牛,光吃草肯定不行。因为这不是外国,像新西兰、澳洲,有优质牧草。我们这里不行,我们的草只适宜本地牛。
事实证明,荷兰牛与本地牛杂交而生的小牛极少,且很多都夭折。当然和草的质量也有关,这片地方虽然大,草还是不够。彭志坚考虑过种植优质牧草或将牧场搬到大山里去,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能实现。
彭志坚以牛粪换番薯的双赢计划虽实行不久就夭折了,但我们和儋州村的关系并没受到什么影响。我们有时应邀到儋州村做客,村民杀狗款待我们。他们的饭很好吃,是用好米煮的,煮得很硬,像是广州人所说的“虾仔饭”。我们喝酒、吃狗肉。旁边有妇女,给我们装饭。如你说不吃了,她们也决不会像大陆人那般客套。她们会端来一碗水给你,不是开水,只是井水,让你饭后漱口。
这里保留着纯朴的民风。村中有青年屋,供青年男女活动。每年春节,青年男女会到空旷的高地聚集,跳舞、唱歌、玩游戏。我们曾被邀请到儋州村参观青年屋,里面有大通铺可以睡觉。有调皮的小青年示意我们找女孩子聊天,他们都是讲白话(粤语)的。倒不是语言的关系,毕竟习俗不同,我们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
彭志坚还和回民打交道。回民住在羊栏圩镇,距离畜牧场不远。因为民族习俗,他们对牛羊牧养较为重视,也就有了交流的基础。因有交流,我们就有机会走进他们的生活。一个晚上,我们向海边出发,去参加回民的捕鱼活动。他们实际上是刮鱼,即用一艘船拖着一条百十米的缆绳,由岸边驶向海中约一百多米,拴好渔网。然后横向行驶约数十米后再折返岸边,使这张渔网横在海中。船在往返中已各拖带了另一条缆绳,这条缆绳很粗,直径约三厘米。这时,已有两条绳子通向岸边,相距数十米,正好是渔网的长度。每条缆绳都有一个绳套。两条缆绳大约有二十人,每边十人左右。把绳套套在后腰上,面向大海,双手拉绳,随着海浪的节拍向后用力,边退边拉绳。当海浪退去的时候,便随着向前走几步。当海浪涌上来时,便借力向后用力拉。全过程约两个多小时。当渔网拉上岸时,网内的鱼儿在扑腾,别有一番丰收的喜悦。
这一网鱼大约一百斤左右。接着是分鱼,他们先把墨鱼拣出来,这是分给头头的。大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高级的鱼类。其余的鱼被分成十几二十份,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也分到了一份鱼。这种鱼叫不出名称,类似青鱼,大部分是这种鱼,还有几条不同品种的,一概不知名。这份鱼大约六七斤。回来后,立即洗来煲鱼粥。食之,无任何腥味,我们也没有任何调料,就是放点盐而已。吃时觉得很美味。海鱼如果是活着宰杀确实不错,从此我知道了鱼还有不腥的。
和周边的群众融洽相处,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孤单烦闷,还可以从中收获欢乐。
记得畜牧场还在红光作业区时,我们也曾到相邻的黎族村寨游玩过一次。那是农历三月初三晚上,我们畜牧场几个年轻人摸黑出发,沿小路走到离我们最近的黎村。我们的出现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照样过他们的“三月三”节。村寨并不大,却热闹非凡。人们大概全都从家里出来了,整个村像是一个墟。小路边有很多卖农副产品的,大多是吃的东西。在路两边,坐着一群群的青年男女,他们在唱歌,每群人有五六个,有的十个八个,男女对面而坐,中间间隔大约也就两米。我们分析这不只是一个村的,而是周边几个村的。
青年男女唱的歌很动听。这和我们平时在舞台银幕上听到的少数民族歌曲不大一样,是原汁原味的黎歌,不是经过汉族音乐家改编的。曲调、旋律都比较简单,听起来有一种原始的感觉。我们虽然听不懂黎话,但从歌唱者的表情可以看出,这无疑是情歌。男孩唱完女孩唱,绝对是对歌的形式。女孩子的年龄也就是十六七岁,很年轻,面带羞涩。唱完一首时往往会掩面浅笑,姊妹拥作一团。据说通过对歌,相互了解了,便可定下婚姻大事。这种风俗应该比汉族以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现时代的“家长干预”更能体现婚姻自由吧!
我们在村里顺着小路,踏着朦胧月色走了一圈,就回驻地去。一路上,黎歌声如影随形跟着我们走了很远很远。
我于1961年到畜牧场,干了一年多,到1962年,大约是夏秋季,接到通知到五工区参加基干民兵集训。我的牧牛生涯从此结束了。
我得了水肿病
1959年春季,海南岛已出现了粮食紧张趋势。农场因不种粮食,除了国家配给的大米外,无其他任何副食品。一开始,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后来逐渐增加了些,到秋季,已经平均每月有28—33斤大米了。但因没有油水,还是填不饱肚子。
1959年夏季时,我得了水肿病。一开始是脚踝、膝盖肿,后肿到面部。那些地方,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小坑,很久都不能复原。除了肿,浑身都没有力气,脚步轻浮。我所在的作业区90多人,大约有十余人得此病。
当时广州也开始有点紧张,但情况还算好些,毕竟是大城市,广州当时还有饼干卖,要凭票供应。于是,很多人收到家里寄来的饼干。我无此福气。我父母早逝,后由大哥抚养。大哥已经有三个孩子,我可不敢开口求援。忍到秋季(那时我的水肿已好了),终于向我的哥哥姐姐们发信求助了。大哥寄来10元钱,二姐也寄过钱,多少已不记得了。三姐寄的最多,一次就寄来15元,还有5斤全国粮票,三哥也寄来3斤粮票,这些粮票后来去三亚时全部用光了。它们满足了我的吃一次饱饭的愿望,不止一次,而是数次。有一次,一餐竟然吃了一斤十二两(十六两秤),每半斤装一个大碗,共三大碗再加一小碗四两,再配一碟咸鱼白菜。太饱了,吃的我出了饭店走不了路,不得不和同伴坐在路边休息,真是饿也痛苦、饱也痛苦。
我的水肿病在八九月时好了。在此之前,上级给每个水肿病人配了一斤米糠、半斤黄豆、一个椰子,还有半斤椰子油。说是米糠要煮水喝,我哪管得了那么多,就这样煮着吃了。那半斤椰子油和黄德胜换了一盒罐头。黄德胜是印尼归侨生,他的家人从海外给他寄来一些罐头。其中有一盒画着北极熊,全部外文,看不懂。他说是熊肉,我打开后,才发现是奶油,于是每餐吃饭,我都挖一勺放在饭里。这也对治愈水肿病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的香烟故事
我原来对香烟根本不感兴趣,记得十二岁时,第一次接触烟。姐夫是抽烟的,每月发工资时,他都买两条,放在家里抽。有一次,我拿了他一支烟,趁他上班不在家,偷偷地抽掉了约半支。一股子苦味,还呛鼻子,剩下半截扔到煤炉里了。
参加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到海南岛崖县,我们也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先是上山砍柴,就是砍树,用木材炼钢。在崖县安游附近,有一条铁路路基。路基很高,我们就从这路基中间挖一条长沟。据说这叫“地炉”,可以炼几百吨钢。在此之前,挖了一整天,晚上也没睡觉,第二天继续干。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觉了。第二天白天,感到听觉出了问题周围的声音都变小了。晚上再挖时,已经没有精神了,那个困呐内!居然可以一边挖一边睡。社里对抽烟的每人发了一包烟,不要钱,据说是记账的,到时扣除。为了抵挡睡意,我也要了一包。可是一包烟抽完了,还是困,根本没起作用。
地炉还没挖完,我们又大兵团转移去秋收了。秋收,就是收割水稻。那时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时代,我们都属公社管辖。三餐饭不要钱,走到哪吃到哪。工作是分到哪就干到哪。行李随身带,走到哪睡到哪。因不可能每天回农场,有时就在村庄的稻草堆睡觉。好在禾秆草多,在地上铺上一层禾秆草,打开行李就睡,在就近的河里冲凉(洗澡)。工作不可能是八小时,起码要干到天黑,甚至干到半夜。那时公社经常开会,一些小会要求干部和党团员都参加。夜晚在一间屋子里开会,吸烟的人很多,整间屋子烟雾弥漫。公社干部都是海南人,讲海南话。我们广州青年听不懂,觉得乏味,就在地上睡觉,有些坐着睡,有的半躺着,或者加入抽烟大军,掏出烟来吞云吐雾。农村屋的地面都是土地面,开会这间房屋挤了三十多人,满满的,凳子也不够用,只有挤在地上了。
会议开到半夜,回到田地时,其他人还在工作。已是下半夜,我们的饭堂煮了糖水送到工地。不干工作还有糖水喝,我觉得内疚。别人干活我们开会,我觉得心里不是味儿。
1959年7月,正是海南岛的雨季,我们广州知青集中在五工区开荒种油棕。那时已是粮食紧张时期。吃不饱,总想找点什么东西吃,但有什么能吃的呢?只有椰子。这椰子,街上是买不到的,只有黎族同胞的村落才有。但那时钱已经大为贬值,椰子由1958年的一角钱一只涨到了一块钱、一块五角钱一只,还不一定买得到。农民不要钱,要物。最可靠的是用烟、酒去换。这时,恰好在场部附近的部队合作社新到了一批烟。农民去买不卖,但我们广州知青可以买。得知这个消息,我们几个人相约一同去买。我们每人都买了一两条。烟很便宜,大约一角五分钱一包,一大条二十包。我买了一大条红炮台牌,是云南烟。原想用这些烟去农村换椰子,一包烟就可以换一只椰子,谁知此后再也没时间去换椰子了。
根据政治形势的要求,农场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大战八九月”的口号。我们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以上,吃饭也不能回工区,而是送饭到工地。最怕是晚上出月亮,一出月亮就一定要开工的。有时一天要干二十个小时。这些香烟已经无法拿去换椰子了。因为从农场步行到山边的农村(那里有大片的椰子林),要走差不多一小时,来回要两个多小时,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只好拿来自己享用。由于工作艰苦,中途抽一支烟,也可缓解一下疲劳。由不会到会,二十包烟抽完,我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烟民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物资奇缺,香烟的来源当然没有保障,买不到怎么办?只有退而求其次,买烟丝、烟叶,再买不到就捡烟头。香烟烟头,还剩下一小截的,我们称为“肉蜢”(广州话),手卷烟丝抽剩下的,我们称它为“棺材钉”,有时烟瘾来了,手头没有烟,就用木瓜叶切丝代替。
那时待人接物,如递上一支烟或接受一支烟,那将大大地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和相互了解。
朋友谭汝荣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自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也交结了一些朋友。到垦荒队后,有一位新交的朋友,在工作上、生活上予我很多帮助,使我至今难忘。
他原是广东的一个农村青年,上学到初中二年级,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很苦,又吃不饱。他听了亲戚的话,跑来海南岛找工作。以投亲靠友的方式,在农场找到了工作,住了下来。他这种情况的人在我们农场不少。
我认识他是在1962年7月份。正是备战的时候,我调来五工区参加基干民兵集训,平常就做机动工。所谓机动工,就是没有固定的工作,可随意变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他也是机动工,因而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晚上放哨也在一起。我发觉他很诚实,工作也肯干,具有农村青年那种纯朴的性格。由于性格相近与工作中经常接触,我们在无形中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工作起来总是老老实实,毫无一点欺骗,质量很好。因自小习惯劳动,显然比我强得多。虽然身体比我瘦小,但在劳动上却是我的先生,他曾在工作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五工区原来住的都是茅草屋。1962年下半年计划盖砖瓦房,为筹集材料,派出30多人前往尖峰岭伐木。我和他都是这支伐木队的成员。
尖峰岭是海南三大原始森林之一,环境险恶。那里有个林场,规模很大。工区领导已和林场取得联系。一开始我们也参加伐木,后出于安全考虑,改为修便道,以工换料。但小的木材还是我们自己砍伐。在尖峰岭工作的两个多月的艰苦日子里,正是他给予我的帮助,使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那时除了每天正常的工作外,还有突击劳动——上山砍树。在一天中,每人的任务是十条三级树(一丈二尺长、三寸头、两寸尾),两人一条一级树(一丈二尺长、五寸头、三寸尾),砍好还要扛回驻地。劳累自不待说,就任务本身来讲,也够繁重的,体力不强就很难完成。我们两人合作,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即使他比我多做了很多,但他从没有只记在自己的账上,而是算我们两个人做的。这种同舟共济的无私精神令我非常感动。
由于工作繁重,体力消耗大,因而每天的饭都吃不饱。往往上午九点多钟肚子就饿了。他又靠外面的同乡关系,买了很多高价米,补充粮食不足。当时全队30多人,每人都是靠在家的亲朋好友买米自己煮来加餐。我没有亲戚,在家也无朋友,幸而他解决了这个难题,不然真不知怎样过呢!
和他相处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却是无比的深厚。分别的时候,我俩内心是很难过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可恶的疾病的影响,我不得不离开农场了。走的时候,他一路相送,帮我挑着行李直到三亚。下午他才搭公共汽车回农场。告别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的眼里瞬时潮润欲泪。晚上,住县城旅店,我在行李里发现了一封信,是他留给我的,信里还夹着五元钱。农场已半年未发工资了,而他居然把仅有的五元钱给了我。
我捏着这五元钱,心里百般滋味。明天,我就要离开三亚,永远告别农场了。从好友谭汝荣又想及其他的农友,想及这几年在垦荒队里、农场里度过的艰苦并快乐的日子。一股暖流充斥心头,久久不能平息。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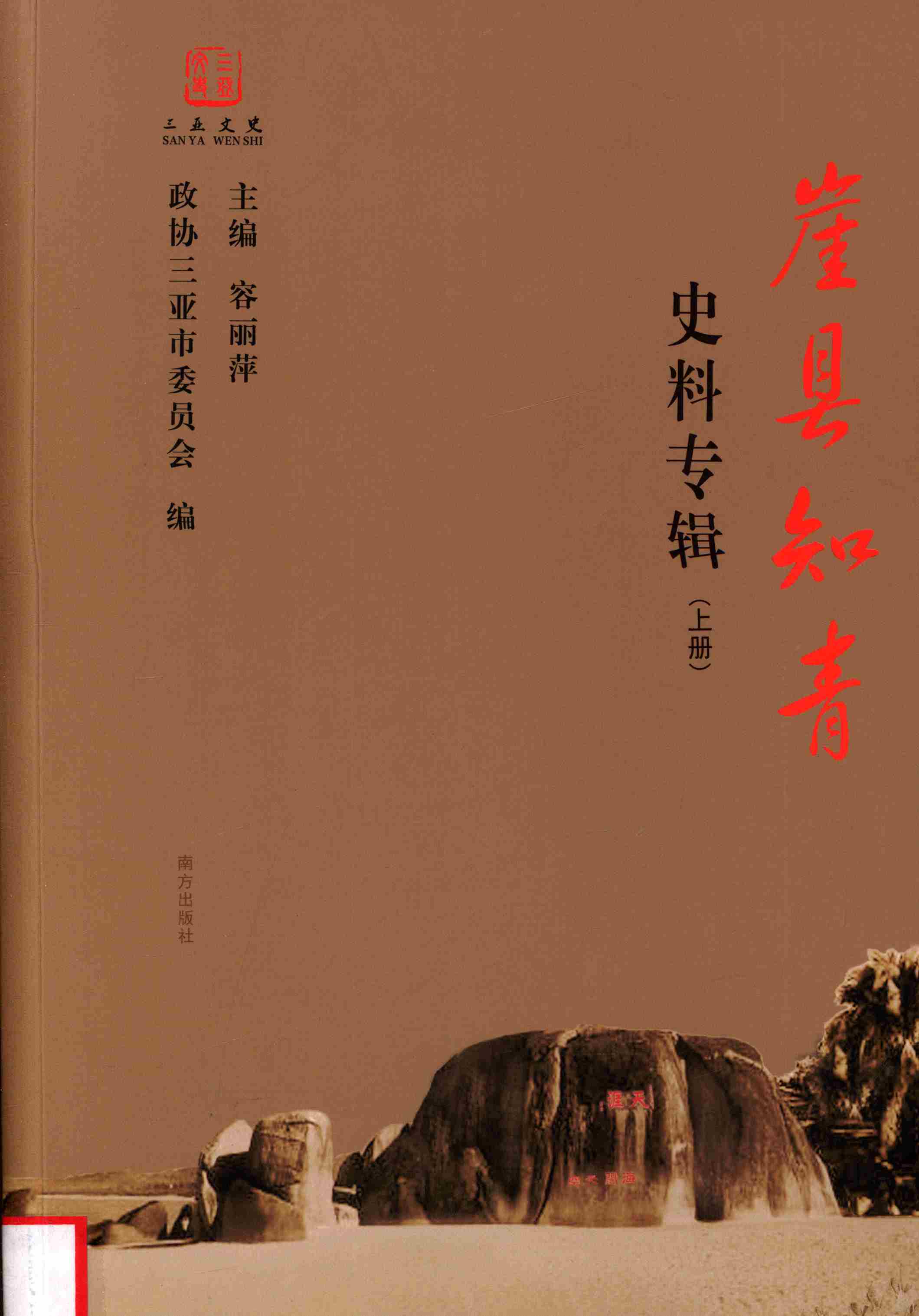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上册》
出版者:南方出版社
本书共有69篇文稿,崖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崖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崖县上山下乡知青安置点简介3篇综述文稿,1956年、 1958年到来崖县的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9篇知青回忆 录,1969年本地知青、潮汕知青12篇知青回忆录,崖县知青场45篇知青回忆录。
阅读
相关地名
崖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