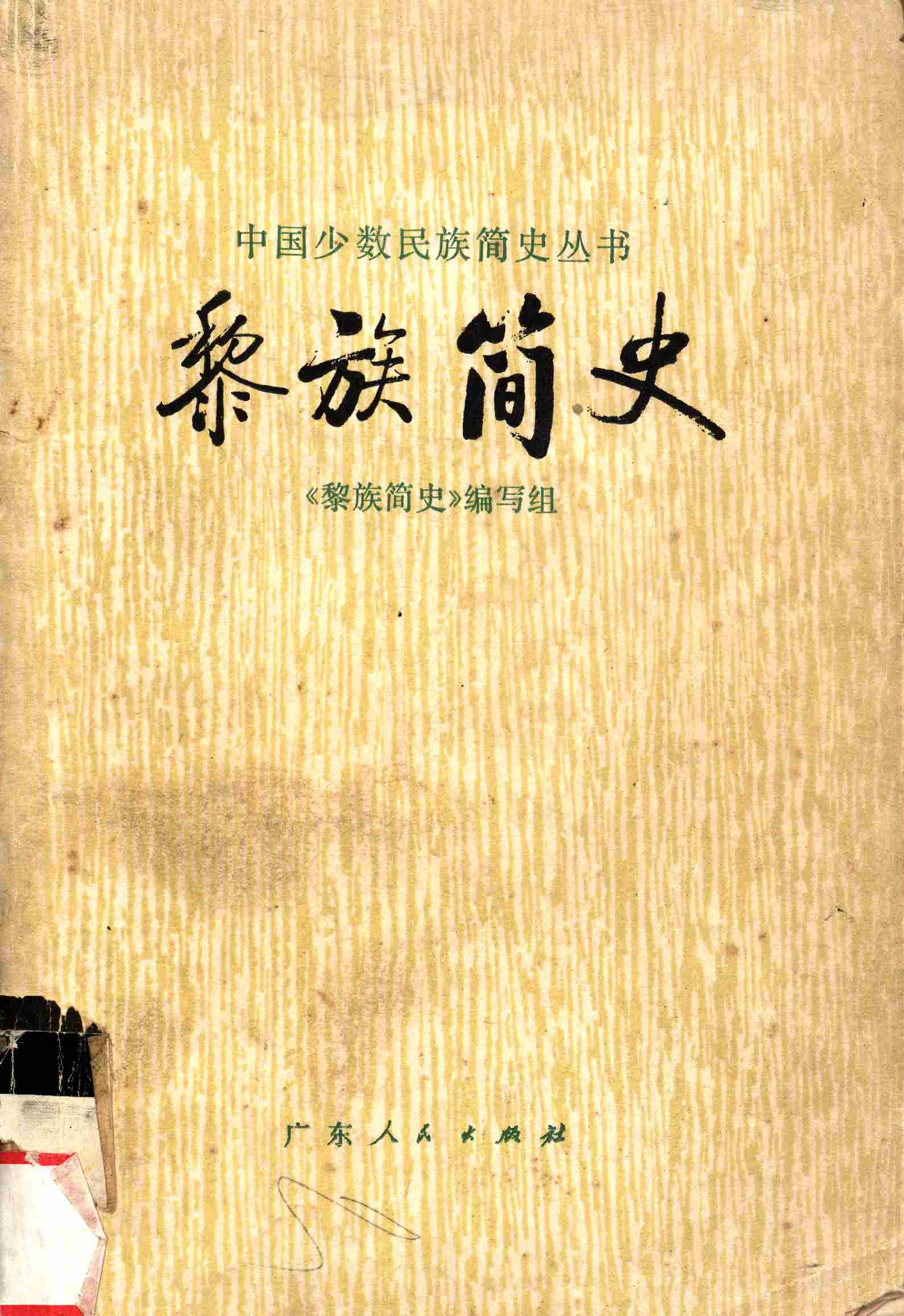内容
在五指山中心地区,即保亭、乐东、琼中三县的毗连地带,直到解放前②,还保存着黎族人民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带有浓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合亩制”。“合亩”是汉语的意译,黎语原称“纹茂”(van mau),意即家族。但一般叫做“翁堂沃工”(uengx tongs vuek gung),意思是“大家一起做工”,或“翁堂打”(uengx tongs dax),意即“大家的田”。一个合亩包括若干个家庭,各个家庭之间有着血缘关系,以后逐渐有非血缘的成员参加;合亩内的主要生产资料如土地、牛只等一般由合亩统一经营,并以合亩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合亩全体成员共同劳动,按户平均分配产品。
据一九五四年的调查,解放前仍然保留合亩制的地区共有二十六个乡,其中包括保亭县第三区的十四个乡(现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直属红旗公社,保亭县毛道公社、畅好公社的全部,南圣公社的一小部分),第五区的毛感、毛岱两个乡(现毛感公社的部分地区),白沙县第二区的七个乡(现琼中县毛阳公社全部,什运公社的部分地区),乐东县第二区的番阳、加艾、毛农三个乡(现乐东县番阳公社的部分地区),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约占黎族地区总面积的8.7%。这二十六个乡共有九百七十一个合亩,三千五百九十一户,一万三千四百一十三人,占当时黎族人口(三十六万人)的3.73%。
这一片地区位于海南岛第二大河流昌化江的河源和上游地带,深入到五指山腹地。河谷两旁高山海拔均在一千米以上。高山上生长着热带季雨林,在河谷和低丘上分布着黎族的村落,这里树木比较稀疏,属稀树灌木丛地带。由于长期以来刀耕火种的结果,天然植被已被破坏,多是萌生林和次生林。从这些自然地貌可以看出人们在合亩地区进行开发活动已有长久的历史。
解放后,在合亩地区多次捡获露出于地表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如一九五六年的一次调查中,在保亭县的毛道、毛枝、雅袁等处就发现有肩石斧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三十九件,可知这些地方在很早的时候已有人类居住。
昌化江上游以东北至西南的流向流经合亩地区。在过去未通公路以前,从海南岛北部平原地区进入五指山,以至南下直达崖县,昌化江是一条天然走廊,是从中部山区南北纵贯海南岛的必经之路。明代海瑞在《平黎图说》中建议开辟的黎山十字大路,以至清代多次拟议的开路方案,都计划采取这条路线。由于地处要冲,自元代以来的历次大举“征黎”,这里也是必到之地。早在明朝正德年间(一五〇六至一五二一年),有些村庄的名称已见于文献记载。如杨理的《上欧阳郡主四事》中,就提到磨岸(毛岸)、磨魁(毛贵)等至今仍然存在的村峒名称。稍后嘉靖年间(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郑廷鹄的《平黎疏》、海瑞的《平黎图说》,万历年间(一五七三至一六二〇年)林如楚的《图说》,提到的村峒名称更多,如凡阳(番阳)、磨羊(毛阳)、磨赞(毛栈)、南恺(南解)、磨敢(毛感)、磨菜(毛赛)等等。海瑞甚至在《上兵部条议七事》中提出“其凡阳、磨栈二村之间,乃东西南北之中,可立一大县”。可见黎族人民在合亩地区建村立寨,最少已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
合亩地区的黎族属于岐黎(即杨理在《上卢兵备书》中所指的“五指之中历代信直不化者为岐”)支系,其中又以服饰风俗等的差别细分为“大鬃黎”、“小鬃黎”、“生铁黎”、“剃头黎”等等,他们都同讲黎语中的岐黎方言。这里隔一鹦哥岭与白沙县的“本地黎”相邻。在乐东县的番阳,则与当地的“侾黎”(“四星黎”)交错杂居。据解放初期的调查,当时除了岐黎这一支系之外,在其他支系的黎族中未发现有合亩制。在岐黎支系中,也只有少部分地区仍保存合亩制。据老人们的回忆,大约在五、六十年前,居住在保亭县第一区毛盖乡、番文乡(今保城公社的部分地区)、琼中县第一区南万乡一带的黎族,仍实行合亩制。更早一些时候,现今琼中县的红毛、什运、五指山三个公社的地方也还存在合亩制。以上地区的黎族也属于岐黎支系。
生产力
农业是合亩地区的主要生产部门,并以合亩为单位进行生产。此外,纺织、编织、制陶、酿酒等手工业只作为副业在农闲时进行,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饲养禽畜、园艺、狩猎、捕鱼等都是家庭副业,而且和手工业一样,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的(狩猎多以村或合亩为单位),采集野生小动物和植物作为食料相当普遍。
农业的生产工具除耕牛外,主要有犁、耙、锄头、铲、钩刀、手捻小刀、四齿手耙、斧头等。耙是木质或竹制工具,其余都是铁质工具。铁质工具都是从汉区输入的。畜力一般不缺乏,主要使用水牛,黄牛少用于耕田,有用于拉车的。
绝大部分的劳动力都投放在农业生产上。劳动力占总人口的60%以上,其中女劳动力稍多于男劳动力。妇女在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生产过程中还保留着比较严格的性别分工和原始的简单协作的残余,加上众多的生产禁忌日①,劳动力的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农业生产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主要是稻谷,其次是番薯、玉米、木薯、高粱等。此外,还种植少量的烟草。稻谷分水稻和早稻,以水稻耕作为主。由于缺乏水利设施,大多数的稻田一年只能种一造,种双造的水田较少。耕作技术比较落后,虽然实行二犁二耙,但全部使用木耙或竹耙,牛踩田代替犁耙田的比较普遍。播种、育秧、移栽的方法和汉区基本相同,但没有选种的习惯。除育秧田施一些肥料外,其他的田都不施肥,尤其不使用人粪尿。田间管理很差,对中耕除草不重视,除驱除鸟兽害外,对防御病虫害则缺少办法。男女性别分工严格,男子负责犁田耙田、浸种播种、灌溉、挑稻、防鸟兽害和砍烧山栏地;妇女负责插秧、除草、收割脱粒和播山栏稻种子。此外,劳动上还存在原始的简单协作的残余,不分工种,不分轻重,大家都在同一时间集中在同一地点做同样的一种工作。收割时以手捻小刀(长三寸宽六分的薄铁片)逐穗割下,割一把稻(净谷重二斤左右)约需十五分钟。收割后把稻穗一把把的挂在竹扎的晒谷架上,任由风吹雨淋,鸟吃鼠耗,浪费很大。
除水稻耕作外,还在坡地和山栏地里种植旱稻。“山栏稻”是一种“刀耕火种”式的耕作方法,即在旱季时把山林砍倒烧光,清除残枝后,等到雨季来临时,由男子以尖木棒戳穴,妇女随后点播种子,经一、二次除草,即等待收获。一般种植两、三年,地力衰竭后就荒弃,另择地烧垦。山栏稻的产量因当年的雨量多寡而相差悬殊。在合亩地区种山栏仍相当盛行,约占当地稻谷总产量的20%左右。
由于耕作粗放,缺乏人工灌溉设备,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薄弱,因而粮食产量很低。一般上等田单造水稻平均亩产只有二百斤左右,最差的只有五十斤左右。
手工业是主要的家庭副业,没有出现专业的手工业者,也没有专门作为商品生产的手工业产品。男子一般都会编织藤箩、藤小凳、刀篓、鱼网,制造木耙、犁架、铁质农具的木柄和简单的纺织工具、织鱼网工具等,有些地区男子还会制造牛车、谷磨。钩刀、凿、小尖铁棒等是主要的手工业工具。妇女一般都会纺纱、织〓、织木棉被和山麻被、织山麻的男子服装、编织露兜叶席、酿酒等,一些地区的妇女还会制造陶器。
纺织工具有木质手摇轧花机和脚踏纺纱机,也有使用比较原始的纺锤,织布是用一块压板和几根横棍坐地围腰而织的原始工具。制陶技术比较落后,都是用手捏和条筑法制成陶坯放在柴堆上烧成。
饲养家畜家禽是一项重要的副业,有牛、猪、狗、鸡、鸭、鹅等。但牛、猪都没有栏圈,特别是牛,一般都是放进山里野牧。由于迷信的风俗,往往杀牲(以牛为主,还有猪和鸡)“做鬼”①,损耗很大。
狩猎、捕鱼也是副业的一种。狩猎主要使用土枪,还有弓箭、镖枪、尖刀等工具。平时以一家一户单独进行,但年终时还保留以村为单位进行狩猎(围猎)的习惯。捕鱼工具有鱼网、鱼笼、鱼栅、弓箭、长短矛、钓钩等,也有使用毒药的,人工养殖极少。渔猎的捕获量很少,都是自给性生产。蔬菜仅有少量种植,副食品还大部分依靠采集野生植物和小动物。
综合以上的情况来看,合亩地区总的生产力水平虽然已远远脱离了原始公社时期的状态,但它的落后面貌仍然严重存在着。如这里的黎族人民不会炼铁,也不会制造铁质农具,只能够把用坏的铁质农具进行简单的加工,制成其他工具,而懂得这种技术的人也很少。由于铁质农具都是从汉区输入,在来源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直接影响到合亩地区生产力的发展,
合亩的规模和类型合亩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标志是以合亩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但合亩规模的大小却各地有所不同。据一九五四年调查,三个县的合亩地区共有九百七十一个合亩,三千五百九十一户,平均每个合亩为三点七户。其中最小的为两户,最大的达到三十一户。从不同地区来看,以乐东县番阳地区三个乡平均每个合亩的户数最多(五点六五户),保亭县毛感、毛岱两个乡的户数最少(二点二三户,不及前者的一半)。又在抽样调查的六十一个合亩中,由二至四户组成的有四十一个合亩(占67.21%),五至九户的有十六个合亩(占26.23%),十至十四户的有四个合亩(占6.56%)。由此可见合亩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大的也不过十来户,二十至三十户的极少。只有保亭县毛道乡的合亩规模较大,平均为七、八户,最多的三十一户,十五至二十户或二十户以上的也不少。据调查,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毛道乡仍然保留较多的几代人从未分亩的“大合亩”。毛道乡的合亩,原始的色彩一般较别处地方为浓厚。
从合亩内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来看,所有的合亩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血缘纽带的基础上,由父系亲属组成;一类是除血缘亲属之外,并有非血缘的外来户参加。这两种类型的合亩所占的比例,在不同的地区,以至不同的村、峒也各不相同。据调查,保亭县通什乡和毛道乡共一百O八个合亩中,全是血缘亲属组成的合亩五十一个,占总合亩数的47.2%,占总户数的35.6%;亲属与非亲属混合组成的合亩五十七个,占总合亩数的52.8%,占总户数的64.4%。但也有一些地区是第一种类型占多数的。在一般情况下,规模较大的合亩多属于混合类型;而规模越小,则纯血缘的类型就越多。有些两三户组成的合亩(这在合亩地区边沿的保亭县毛感、毛岱乡;白沙县的毛贵、毛栈等乡较多见),往往就是一些“父子亩”或“兄弟亩”。如上述的五十一个血缘合亩中,属于“父子亩”和“兄弟亩”的占总数的86.5%。这类小合亩都是从比较大的合亩分化出来的,一旦他们抛弃了合亩的某些传统内容和形式,就和一般的大家庭没有很大的差别。但也有一些血缘合亩规模比较大,超过十户以上,这些都是几代以来从未分过亩的,这在毛道乡比较多见。
根据合亩内外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来划分,合亩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合亩内部没有产生剥削关系,合亩里人们的关系基本上是共耕和互助合作的关系。亩头和亩众以至亩众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这种类型的合亩绝大多数是由血缘亲属组成,渗杂外来户的很少。在毛道乡二十五个合亩中,二十四个属于这一类型。在这类合亩中,有个别的虽然内部没有剥削关系,但亩头(也有个别的亩众)对亩外的人,以及合亩对亩外的人、合亩与合亩之间已产生了剥削关系。
(二)合亩内部和合亩对外都已产生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一些合亩中,剥削关系还十分严重和突出。亩头(龙公)对亩内众多的外来户(龙仔、工仔),以至对其他合亩的人已经是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毛道乡二十五个合亩中,只有王老本一个合亩属于这一类型。又通什乡的王老关合亩,番阳乡的王如清合亩、徐新东父合亩也属于这一类型。这类合亩只是保持了旧的合亩的形式,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的合亩共耕仅仅留下一个躯壳而已。
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
合亩地区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是很复杂的。
首先是耕地的占有。合亩地区的耕地包括水田(指一年可种两造的水稻田)、旱田(一年只能种一造水稻)、山栏地、坡地、园地等五种。从各种耕地所占的比例来看,主要是水田、旱田;其次是山栏地;再次是坡地、园地。如番阳乡空透、什茂、万板三个村共有耕地七一五点九亩,其中水田一〇五点六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4.75%),旱田四四五点七亩(占62.26%),山栏地一四五点七亩(占20.85%),坡地十八点九亩(占2.64%)。
从水田、旱田和坡地的占有情况来看,可分为合亩内各户集体所有,亩内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合亩内各户集体所有(以下简称合亩所有)的耕地,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的水田,主要是所有者用猪、牛或光洋买进的,旱田多是自己开荒得来,也有雇工来开垦的。
至于这三种所有制各占的比例多少,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合亩都各有不同。一般的情况是:没有外来户纯由血缘亲属组成的合亩,大部分的耕地属合亩所有,其次是几户伙有,一户所有的最少。如毛道乡的王老东合亩,六代以来从未分亩,没有外来户,合亩所有的水田占合亩内全部水田总面积的87.9%,旱田则占84.4%。该乡雅袁峒的六个合亩,合亩所有的水田占50.15%,几户伙有的占87.25%,一户所有的占12.6%。在一些规模较小的父子合亩和兄弟合亩中,合亩所有的耕地所占的比例就更高。如保亭县通什乡,合亩所有的耕地共二九一点五
亩,其中八十八亩的所有者是由两户组成的合亩,一三一亩归三户组成的合亩所有,这两种合亩所有的耕地已占全部合亩所有耕地总面积的73.41%。虽然在这些合亩中合亩所有的耕地所占的比例很高,但尚未出现耕地和牛只伙有和私有的合亩仅是个别的。另一方面,在外来户较多(有些甚至占多数)的混合组织的合亩中,耕地大部分为几户伙有(以二至四户伙有的占大多数),其次是一户所有,合亩所有的最少。在个别地主恶霸当亩头的合亩中,耕地全部由亩头一户私有或其兄弟几户伙有,合亩所有的耕地已不存在,大量的外来户(龙仔、工仔)则片土皆无。
在不同的地区,合亩所有的耕地所占比例相差也很悬殊。如毛道乡毛枝大村九个合亩中,除王老对合亩的水旱田全属私有外,其余八个合亩的耕地全属合亩所有,没有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的。又毛道乡除毛枝大村之外的十八个合亩中,合亩所有的耕地所占的比例就小一些,其中水田占总面积的50.14%,旱田占53.18%;几户伙有的,水田占37.25%,旱田占38.1%;一户所有的,水田占12.61%,旱田占8.72%,合亩所有的耕地仍占多数。但在通什乡,合亩所有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0.2%,几户伙有的则为52.4%,一户所有则占37.4%。在乐东县毛农乡毛或村的九个合亩中,合亩所有的耕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12.8%。在白沙县的毛贵乡什盖等七个村,合亩所有的水田占31.88%,旱田占27.9%。但同县的毛路乡,全部的耕地归合亩内各户私有,没有合亩所有和几户伙有。
山林、荒地、河流均属全村或全峒公有,在本村、本峒地域内居住的各合亩成员(包括亩头、亩众、龙仔、工仔)都享有平等的使用权利。开垦山栏地种植旱稻和杂粮,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地段,不受限制。一般都是由合亩内的近亲分别组合,一个合亩分成两个以上的组合进行耕作,也有一家一户单独进行的。只有规模最小,且由血缘亲属组成的合亩,才以合亩为单位进行开垦。晚近时期,有一部分山林、荒地、河流已为地主恶霸所侵占,在这些山林、河流中种山栏、狩猎和捕鱼,事先都要征得所有者的同意,并向其交租或送礼,形成了山租等的特殊剥削方式。
至于屋前屋后的园地,都归开垦者一户私有。
牛只是合亩地区仅次于耕地的重要生产资料。牛只(包括耕牛和非耕牛)的占有也分合亩各户集体所有、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形式,但合亩所有的成分已不占优势,绝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的合亩以一户所有为主,几户伙有次之。如上述毛道乡十八个合亩的牛只中,属合亩所有的仅占牛只总数的10.41%,几户伙有占42.90%,一户所有则占46.69%。又如通什乡,90%以上的牛只归一户所有和几户伙有。牛只的来源以家庭副业产品交换得来为主,其次是出嫁女儿的财礼和媳妇的嫁妆,以及牛只自身的繁殖等等。牛只不仅用作畜力(曳引力),而且是财富的标志和交换的媒介。由于婚丧活动和“做鬼”等都要宰杀大量的牛,因此牛的消耗量很大。
除了耕牛之外,农业(包括园艺、饲养禽畜等)、手工业、捕鱼、狩猎等活动所使用的一切工具,完全属一家一户私有。合亩成员从事合亩的集体生产时,都使用自己的工具,损坏后也由自己负责修补和添置。手工业、副业以至大部分的山栏地耕作,都以户为单位进行,产品归该户所得,已属于家庭私有经济的范畴。
随着土地、牛只等生产资料交换关系的出现,合亩内各户以至合亩之间生产资料的占有日趋贫富不均。如白沙县毛贵乡的王友风合亩,有耕地三十八点八亩,其中亩头王友风一户就占了二十九亩,为耕地总面积的74.7%,他的弟弟和堂兄等共六户仅有九亩(占23.2%),有两户龙仔则完全没有耕地。合亩之间占有的不平衡更为严重,以至贫困的合亩不得不租入土地来耕种。如白沙县毛栈乡番满村六个合亩共有耕地七十五点八八亩,其中王大富一个合亩(其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便占有三十六点六三亩,约占全村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乐东县番阳乡什茂等四个村共十八个合亩,共有耕地七五九点三亩,平均每个合亩占有耕地四十二点一八亩,而徐新东父合亩便占了一〇六点九亩,为平均数的一倍半;王老波父合亩共五户,占有耕地八十二点四亩,平均每户十六点四八亩,而张亚久父合亩共八户,仅占有耕地二十二点一亩,平均每户只有二点七六亩,仅为前者的六分之一。
牛只占有的悬殊也很突出。如毛道乡十五个村十八个合亩共有耕牛二三五头,平均每个合亩有耕牛十三点〇六头。其中占有耕牛不到十头的合亩有十个,占全部合亩数的55.6%,其中王老黄合亩一头耕牛也没有。而王老本合亩和王国才父合亩分别占有耕牛四十三头和四十一头,相当于平均数的三倍多。王老本合亩共十九户,有牛只一一三头,其中耕牛四十三头,非耕牛七十头。亩头王老本一户就占有耕牛二十五头(占耕牛总数的58.14%),非耕牛四十五头(占64.29%),同一合亩的王老对、王老青、王老永等七户则连一头牛也没有。乐东县番
阳乡什茂等四个村共有牛只一四九头,平均每个合亩有八点二八头,其中徐新东父合亩有三十一头,王老波父合亩有二十七头,均相当于平均数的三倍以上,而张亚八合亩和张亚久父合亩则一头牛也没有。
至于犁、耙、锄头、钩刀等生产工具几乎每户都备有,只有极少数农户的农具不齐全。
在一般的情况下,不论何种占有形式的耕地和牛只,所有者均有完全的支配权,可以租佃、抵押和买卖,并按父系继承,也没有出现定期进行重新分配或调整的现象。合亩所有的耕地和牛只如要改变所有权,一般需经合亩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才能作出决定;但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的,则不需征得合亩内其他成员(包括亩头在内)的同意。另一方面,在特殊的情况下,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的耕地和牛只,所有者的支配权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合亩内某一成员遭遇天灾人祸,或被恶霸强罚,该成员把自己的田地和牛只全部卖光仍不足以应付时,他的兄弟私有的以至合亩所有的田地牛只也要拿来出卖抵债,甚至有亲属关系的其他合亩也有义务来帮忙。
无论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耕地和牛只,大部分都交由合亩统一使用,不按交出的耕地、牛只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因此,所有者(主要指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的)在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方面受到了限制,私有制的所有权就未能充分实现。
在合亩内,也有个别富裕户抽回属于自己所有(包括伙有)的一部分耕地牛只来自耕或出租,黎语称为“沃偏”,意思是“做私己”。这种情况并不多,而几户组合或单独一户种山栏地的则比较普遍。
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每一个合亩都有一个“亩头”,亩内的其他成员就是“亩众”。
亩头黎语称“俄布笼”(go plug lug),直译是“大房头”,是“家族长”的意思。又称“畏雅”,意思是“犁第一道犁路的老人”。白沙县合亩地区则称亩头为“禾打”或“头耕”,前者为音译,后者为意译。
亩头由合亩内最高辈分中年事最长的男性担任,亩头死后,由其弟依次继承,如没有弟弟,则由长子继承。由于是血缘世袭,因此外来户通常不能当亩头,但经过“入主”仪式并改姓亩头的姓,承认亩头的祖先是自己的祖先的外来户,如果条件具备,也可以继承亩头的职位。
亩头必须有较丰富的生产经验,能够组织和领导全合亩的生产活动。同时亩头必须和他的妻子一起在生产过程中举行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因此规定亩头必须已婚并与妻子同住;如果已婚但妻子未落夫家,或婚后妻子死了没有续娶,就不能当亩头。
亩头是一亩之长,是合亩集体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有较丰富的生产经验和传统知识,在亩众中有一定的威信。亩头除了与亩众同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外,还要主持一些生产上的宗教仪式,如播种、插秧、放牛上山、收获等等,都要亩头和他的妻子分别带头做一下样子,然后亩众才跟着劳动。吃新谷时,由亩头先吃,妻子一天后才吃,然后亩众跟着吃起来。亩头的妻子在管理妇女的生产活动方面,是亩头的助手。
亩头不仅领导合亩的生产并掌握分配,而且亩内和亩与亩之间的一切重大事情,如处理和保管集体财产,处理亩内外的纠纷,接收外来户(龙仔)等等,都由亩头出面联系、调解和处置,亩众一般都表示服从,但没有强制权力。亩众经过一定的手续可以主动提出分亩或退亩,但分亩时,亩头照例多分得一些田产。
在基本没有剥削关系的合亩内,亩头与亩众,以至亩众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一部分外来户除外)。亩头除了按传统习惯多分配一些农产品外,在其他方面与亩众同处于平等的地位,如平等参加集体劳动,担负共同的费用,共同防卫外来袭击,平等享受各种权利等。此外相互之间,还保留互助合作的传统习惯,不论亩头或亩众,当他在盖屋、婚娶、生病“做鬼”或办丧事时,整个合亩以至全村都来帮忙,事主只要略备酒饭招待,不需任何报酬。亩内有人缺粮或经济困难,较富裕的户就设法帮助,借贷不要利息,甚至无偿援助。此外,如某户被敲诈勒索和处罚,或因“做鬼”花费巨大而本人又无力偿付时,所在合亩就有义务帮助他偿还,必要时经合亩全体成员议决,可以出卖合亩集体所有的土地和牛只。对于抚养鳏寡孤幼,亩众们都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妇女丧夫后回娘家居住,参加生产劳动和分配,丧失劳动力的,合亩内她的亲属成员(主要是亲兄弟)就把她抚养起来。这种互助合作的关系,也存在于合亩与合亩之间,特别在生产活动中比较多见,如插秧、收割和开垦荒地时彼此帮工,事主杀牲招待喝酒以示答谢,不计报酬。
随着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势力不断向合亩地区扩展,以及合亩内部的演化,亩头的地位和性质、亩头与亩众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等与互助合作的关系遭到破坏,代之以压迫和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亩头最初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分配中取得某些特权,把具有宗教性质的和属于公共开支的传统留粮攫为已有,并随意增加留粮的数量,使之变质为剥削,同时以龙仔、工仔等外来户作为剥削对象。特别是那些充当反动统治代表人物的亩头,如保亭县通什乡的王老关,毛道乡的王老本,乐东县番阳乡的王公清、王如清等,他们与反动政府相勾结,出任总管、团董、哨官、乡保长等反动职务,亩众们遭受着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合亩内原来的共耕、按户平均分配产品、互助合作等等传统形式已被这些亩头利用作为统治剥削亩众的手段。这种亩头,实质上已不是原来意义的亩头,而变为合亩地区里的地主恶霸,这种类型的合亩已成为一种残存的躯壳。
在合亩地区,人们在生产过程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中,还有所谓“龙公”和“龙仔”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合亩地区以外的黎族中亦存在,但不及合亩地区那样普遍,形式也有一些差别。
“龙公”、“龙仔”是汉语海南方言的称呼。黎语称“龙仔”为“沃伐”(vuek vat),直译是“做穷人”,也有“做奴”、“做长工”的意思;黎语称“龙公”为“沃凡”(vuek veeng),直译是“做富人”,也有“做主人”的意思。在合亩地区,龙公和龙仔都有个人和集体两种形式。龙公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合亩、几个合亩或一个村为整体,接受来投靠的龙仔;龙仔可以个人或自己一家去投靠,也有一个合亩、几个合亩或一个村为整体,去投靠龙公的。在一个合亩内,龙公绝大多数都是亩头,但亩头也有沦为别人的龙仔的,个别的亩众也可以收纳龙仔。在集体投靠中,由几个合亩公推辈分最高最有威信的亩头作为集体的代表充任龙公;“村头”则作为全村的代表充任龙公。
龙仔之所以投靠龙公,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或自己一家)投靠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如生活贫困破产、无依无靠、负债或被罚巨额钱财而无力偿还等等,也有因受豪强恶霸的欺压,在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去投靠龙公的。但未发现因战争和械斗被俘而沦为龙仔的。集体投靠多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如因械斗等,为求豪强的援助和保护而整个合亩、几个合亩、甚至全村全峒投靠政治上有权有势的龙公,这主要是政治上的依附关系,平时一般不为龙公负担什么经济上的义务。
缔结龙公龙仔关系时,龙仔要给龙公送牛、铜锣①和酒等礼物,龙公设酒席宴请全村的人,并须举行“砍箭为凭”②的仪式。一经砍箭确立关系后,便世代承袭,祖先是龙仔的,他的子孙后代都是龙仔,龙仔如果单方面否认和废除这种关系,会被重罚甚至杀害。
集体投靠的龙仔不必移居到龙公的合亩和村里生活和劳动。个人投靠的龙仔平日在自己家里劳动和生活,但遇农忙或龙公修建房屋时,按例要到龙公家里从事无偿劳动一两次;逢年过节或婚丧、“做鬼”杀牲时,以至猎到野兽,也要送一些肉给龙公;龙公每年有两三次到龙仔家,龙仔要设酒席,送礼物。政治上,龙仔要充当龙公的耳目,为龙公通风报信,发生械斗时要替龙公出力卖命。而龙公则以龙仔的保护人自居,龙仔一旦出了事,龙公就出面为他们进行调解或说情,以减免罚款,但亦有个别龙公乘机勒索巨额报酬的。
有一部分龙仔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迁居到龙公合亩中,参加龙公合亩的生产劳动。这类龙仔以个人投靠为主,只有个别是全家移居到龙公合亩的。这些龙仔初来投靠时,大多数是青年未婚男子,他们对合亩原有的耕地牛只都没有所有权,也没有享受按户平均分配产品的权利,只有在龙公帮助之下结婚成家之后,才另立一户参加合亩的分配,并且通过搞副业、种山栏等积累一些钱财买入少量的耕地和牛只。这些私有财产受到社会的承认,龙公不能随意侵占。这类龙仔除了移居入亩内和参加龙公合亩生产劳动之外,其他应负担的义务与不参加合亩生产的龙仔相同。
在移居投靠的龙仔当中,有些是短期投靠的,一旦还清债务或纠纷已经解决,便可自由离开(退亩),但要交三头牛给龙公作为生活费用(俗称“吃饭费”)的补偿,但离开后龙公龙仔的关系仍然保留着。
有一类移居投靠的龙仔是以身抵债的,他们多数是自幼孤苦伶仃,生活无依无靠,或因重大变故而完全破产的人。这类龙仔在当地又称为工仔,有些自小卖身的称为“出卖龙仔”(有被父亲出卖的,也有自己出卖自己的)。他们属于终身投靠的性质,人身不自由,根本不能离开龙公,他们不仅参加合亩的生产劳动,还要负担龙公的家务劳动。他们在结婚立户以前,一无所有,分配上比上述一般的龙仔更不平等,社会地位也更低。结婚立户后,才能和一般的龙仔一样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在工余时间自己种植山栏、饲养家禽和从事家庭副业。但是工仔的结婚年龄一般都在四十岁左右,并由龙公帮助一点结婚费用。
与“出卖龙仔”性质相类似的就是义子(养子)。所不同的是义父往往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或缺少劳动力,主动付出一定的身价来收养义子。收养义子时也要举行设席请客的仪式。义子必须改姓义父的姓,认义父的祖先为自己的祖先,成为义父家族内的成员,禁止与义父同一血缘集团的妇女结婚或“放寮”①,义父帮助义子娶妻,结婚成家之后便正式成为合亩内的一户,有资格按户平均分得一份谷物。义子可以继承义父的财产,并得充任亩头。若义父死后其亲生儿子年纪尚幼,义子则暂时代理义父的亩头职务,等亲生儿子长大后才让位。
上述各种类型的龙仔,与合亩内不是龙仔的一般亩众,在地位和待遇上存在一定的差别。龙公对龙仔不能毒打、杀害,不能转让、出卖,龙仔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私有财产也受到社会上的承认;但龙仔在人格上不是完全的独立自主,动辄被龙公贱骂为奴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龙仔是被轻视和鄙视的。
至于在某些地区的一些合亩内,那些称为工仔的在劳动和分配上显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特别是个别地主恶霸当亩头的合亩内,如前述的王老关、王老本、王如清合亩,工仔的境况十分恶劣,不仅常常劳动多,分配少,而且龙公更以种种借口处罚工仔,进行超经济掠夺。工仔逃走被抓回即遭痛打,龙公可以打骂以至杀死工仔,并出卖工仔和他的子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工仔从种植山栏、手工业、副业所得来的收入,仍不受龙公的侵占。
此外,因为关系世袭,子孙繁衍的结果,也形成了有些整个合亩甚至整个村都成为某一个合亩或某一个村的龙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龙公、龙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发生变化,不少人既是别人的龙仔,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龙公,兼有双重的身分。有些比较贫穷的亩众也有自己的龙仔。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合亩地区的龙公龙仔关系,在它的原始阶段可能带有氏族收养成员的性质,但随着合亩内部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的现象,这种关系也演变为压迫与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特别到了晚近年代,有些龙公已成为地主恶霸,在他手下有大量的龙仔和工仔,他们已经带有家庭奴隶的性质。而合亩内属于外来户的龙仔、工仔不断增加,血缘纽带逐渐松弛,这也是促使合亩解体的一个因素。
产品分配
合亩地区产品分配方式,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复杂性相适应,也是多种多样的。
合亩内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或几户伙同进行生产所得的产品,出租土地、牛只所得的地租和牛租,以至各种副业等其它收入,均归该户或该几户所得,不归合亩分配。
合亩共耕所得的产品,由亩头主持分配。按传统习惯,在全部产品中,首先要扣除下列的几项稻谷:
(1)种子。
(2)“稻公稻母”(黎语称“麦雄”,意即“五谷的灵魂”),又称“头米”。这些稻谷只有亩头一家人可以吃(群众说:“这些稻公稻母一定要留给亩头吃,否则对来年生产不利。”),不能出卖、转让或赠送,但可以拿来救济亩内的困难户。各个合亩扣除“稻公稻母”的数量不完全相同,一般是按每块田或每次买入的田地(不论块数)收一把至三、四把稻谷,每把净谷重约二斤。
(3)“留新禾”。收割前,亩头的妻子先割回十至十二把稻谷煮饭酿酒,亩头夫妻吃一天后,次日全合亩的人一齐来吃。
(4)“酿酒粮”,或称聚餐粮,约数十斤稻谷,由亩头掌管,用来酿酒,待插秧完毕后全合亩的人一齐共饮;尚有米剩余的则煮饭吃。
(5)“公家粮”,数量不定,由全合亩的成员共同管理,需要动用时由全体成员商量决定。亩头可以用公家粮来招待客人,合亩成员结婚、盖房子有困难时也可以动用,也有用来救济亩内缺粮户的。有些地区还另留“青年粮”(约九十至一百斤稻谷),专门分给未婚青年男子,由他们自己支配或积蓄起来供日后结婚之用。
扣除上述部分之后,余下的全部按户平均分配,连同龙公龙仔在内,没有特殊或例外。当男女青年结婚后,只要盖有房子并单独开伙食,参加合亩内的主要劳动,便可取得作为一户进行分配的权利。如丈夫年幼不能参加主要劳动,但妻子回家参加主要劳动,则仍算作一户。婚后不久妻子死去,丈夫仍能保持分配方面的一户的权利。若婚后丈夫年幼未能参加亩内的主要劳动,而妻子尚住在娘家,丈夫就随他的父母生活,只能算作半户进行分配。如妻子在农忙时偶尔回夫家参加劳动,便由合亩公议分给一些稻谷,娘家对她则不分配。若夫妻双方均死去,分配方面的一户的权利就被取消,年幼的子女由合亩里血缘最亲近的成员负责扶养。
在有些地区如通什乡,则按户并适当照顾人口进行分配。
此外,对合亩内的老人、小孩、残废者分给相当于半个劳动力所得的稻谷。至于丈夫死后回娘家生活的寡妇、随母亲出嫁而来的少年、幼童,均受到抚养而不受歧视。
有一些内部已经出现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合亩,按户平均分配的传统已遭到破坏,亩头(龙公)往往以各种借口多分一些稻谷。如毛道乡王老仁合亩共六户,其中五户是龙仔,全年稻谷总产量二千九百斤,扣除传统留粮约五百斤,实际分配二千四百斤,结果亩头王老仁一户分得四百五十斤,其余五户龙仔各得三百九十斤。特别是一些地主恶霸当亩头(龙公)的,亩内分配更为悬殊。如毛道乡的王老本合亩,亩头王老本一户每年独得稻谷八、九千斤,而龙仔、工仔每户仅得四、五百斤。又如通什乡黄老茅合亩,亩头一户就分得三千斤,黄老茅的儿子和侄儿两户各得一千四百斤,龙仔五户平均每户仅得五百八十斤。
至于合亩和合亩之间,由于耕地牛只占有的不平衡,分配水平也就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如乐东县番阳乡万板村的徐新东父合亩,平均每户分得一千三百一十斤,而同村的徐老磊合亩,平均每户仅得六百五十七点六斤,相当于前者的一半左右。
如上所述,合亩内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手工业、园艺、饲养禽畜、捕鱼、采集野生动植物等活动,所得均归各户所有,由各家独立消费。种植山栏分一户单独进行和几户合伙经营两种方式,前者所得归该户所有,后者所得则由合伙各户平均分配。
狩猎一般以村为单位(也有少数以合亩、或联合两三个合亩为单位)在农闲时(每年的十二月至次年二月)集体进行。猎获物的分配原则是:首先把野兽的头分给领导打猎的人(黎语称“俄巴”,由参加狩猎的人在出猎前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推选出来),一只后腿分给首先打中猎物的人,其余全部兽肉在狩猎单位内多则按人,少则按户平分。个人的狩猎以户为单位,多在每年的四至六月间的晚上进行。所得的猎获物由打猎者先取一只腿,剩下的仍在原来的集体狩猎单位内按户平均分配。
交换关系
合亩地区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很不发达,还没有形成本民族的商人阶层。交换关系主要在黎族人民和汉商之间进行,并以物物交换为主,亦有少数使用汉区通行的货币如光洋、铜钱、铜币等作为交换的媒介物。汉族商贩有座商和货郎担,前者分散住在各个较大的黎族村寨内,合亩地区在解放前还未出现进行集中交换活动的市集。汉商从乐东、崖县、藤桥等地运入各种生产资料(主要是犁头、锄头、钩刀等铁质农具)和生活用品(主要是盐、棉纱、丝线、针、金属饰物等),换取黎族人民的牲畜(猪、狗、鸡)、红白藤、烟草、藤箩、兽皮等土特产。在交换过程中,汉族奸商的剥削相当严重,一支针换一只鸡是通常的事,他们经常把商业剥削和高利贷剥削结合起来,以攫取更多的财富。在一般情况下,黎族人民进行交易具有为买而卖的特点,当人们需要购买农具或其他日用品时,才会把猪、鸡、红白藤等出卖。
合亩地区发生的另一种交换关系是土地的买卖。解放前合亩地区土地买卖的现象相当普遍。如乐东县番阳乡万板村共有耕地一六一点六亩,其中有九十九点二亩发生过买卖关系。白沙县毛贵乡番满峒五个村共有耕地一五〇点六亩,其中有一二一点八亩发生过买卖关系。毛道乡七个村最近四代以来共发生过二十六次土地买卖,其中二十一次是以牛为媒介物。由于土地的所有权存在合亩集体所有、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形式,因此,土地的买卖也分别以合亩、几户和一户为单位进行。合亩集体所有的土地出卖,须得到合亩的同意。几户伙有或一户所有的土地出卖,由几户或一户的所有者自己决定。买入土地的情况也如此,谁买入即归谁所有。在出卖土地时,首先应卖给本合亩的人,如本合亩无力购买,就按血缘关系的亲疏依次卖给同村的其他合亩、同远祖的其他村,最后才卖给无血缘关系的人。因此土地买卖一般不出本村本峒,也有发生于兄弟之间的。晚近以来,有些地主恶霸还从外村外峒买入土地。土地买卖要有中人,并由买者备酒邀请村内的亩头、父老、本合亩的兄弟亲属和卖田者全合亩的男人一起来喝酒,双方当面讲明价格,并砍竹为凭。地价比合亩地区以外的黎族地区低,中等田每亩一般值两头牛和五个光洋,甚至有更低的。在不少情况下,都是卖主因被罚或“做鬼”缺牛而出卖土地换取牛只的,牛成为土地买卖的主要媒介物。至于土地买卖从何时开始出现,据毛道乡的老人回忆,当地在四代以前就发生过土地买卖。在白沙县毛阳乡的什益村,曾发现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间订立的“卖山契”,是用汉文书写的,显然是较后期的事了。
除了土地买卖之外,还存在土地典当的关系。这里的黎语中没有“典当”和“抵押”的词汇,都是使用汉语借词。土地典当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间相当普遍。除双方当事人外还要中间人,双方同意后典当关系便告成立,并刻竹为凭。典价相当于售价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赎典时都是照原典价赎回,不论年限长短,一概无息,因此典当的期限并不严格。租佃、借贷、雇佣关系合亩地区土地租佃关系比其他黎族地区少见,但不同地区以至各村各峒之间的情况也不一样。如番阳乡万板、抱隆、什茂三个村出租的土地分别占该村耕地总面积的40.6%、13.5%和9.43%。毛道乡全乡出租的土地四〇六点一亩,占全乡耕地总面积的15%强,而隔邻的通什乡出租土地只占3.36%。租佃关系有发生于合亩与合亩之间、合亩与个人之间、以至个人之间等三种情况,但尚未出现全靠佃耕的合亩和合亩内的个体佃户。地租是实物地租,分固定租和对半分的活租制两种。固定租一般是三至五亩旱田每年交一拇①谷子。租佃关系的出现,使土地经营越出了本合亩共耕的狭小范围,这是促成合亩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牛只的出租比买卖更普遍。通什乡属于地主性质的亩头共有牛四二三头,其中出租一九〇头,占牛只总数的45%。每头牛的租金不论租期长短,一次过收二至八个光洋,也有每三年付一个光洋的。繁殖的牛犊归牛主。牛主每年来看牛时,租牛户(合亩或个人)要备酒肉款待。
借贷关系也发生于合亩内部和合亩之间。亩内成员之间借粮食绝大多数要利息,年利率百分之百,复利计算,但借钱(光洋)则不要利息。毛道乡雅袁峒的王老陆合亩出现过将借出的光洋折作粮食收息的事例。借牛在三年内归还的不取利息,三年以后,每头牛需付息一拇稻谷。合亩之间以借稻谷的较多,牛只、光洋次之,利率与私人借贷相同。由于合亩地区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借贷通常发生在因病杀猪杀牛“做鬼”而不堪负担,或歉收缺粮的时候,因此上述两种借贷关系并不多见,而且尚未出现以放债为业的寄生者。
雇工剥削在合亩地区是晚近才有的事,多发生于边沿地区,如白沙县的毛贵、毛栈乡等地。长工做两三年可得猪一只、鸡若干只,四、五年可得牛一头。短工工资由双方商定,每月工资光洋一元左右。雇工在合亩内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能享受按户平均分配产品的权利,也不能继承亩头的职位。
综合以上的各种情况,可以归纳为几点:
(1)在生产力状况方面,合亩地区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是直到解放前夕,当地的黎族既不懂炼铁,也不会制造铁质农具,铁质工具全靠从汉区输入,由于来源不够稳定和受到不等价交换的剥削,限制了生产的扩大和发展;加上手工业没有和农业分离,交换关系不发达,人们的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水平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和水平不高是很明显的。但这样的情况在合亩地区以外的黎族地区也是存在的,只是合亩地区更为落后而已。就合亩地区农作物的产量来看,人们劳动所能提供的产品,不仅可以维持人们低水平的生活需要,而且可以提供某些剩余产品,这就为剥削关系的存在提供了物质条件。
(2)在生产关系方面,合亩地区所有制的形式,主要分合亩集体所有、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这三种所有制所占的比例,在不同的合亩以至不同地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合亩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合亩数量较多,其他所有制占优势的合亩较少;反之,在另一些地区,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制占优势的合亩却是多数,合亩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合亩则占少数。这种不同的情况,可以说是合亩向个体经济转化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反映。就整个合亩地区来看,以后一类地区占主导地位。
(3)在上述三种所有制中,一户所有属私有制性质是明确的,虽然这些私有的土地耕牛要交给合亩统一使用,不计报酬,私有权未能充分实现。至于几户伙有和合亩集体所有在所有权
和使用权方面都属于公有的范畴,但联系到合亩地区已存在私有财产的父系继承制度,以至土地占有关系的历史,私有和公有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转化就比较复杂。因为许多几户伙有和合亩集体所有的土地牛只,往往是他们祖先的私人所有物,通过父系继承关系而转归他们共同占有的,这就发生了从私有到公有的转化。
(4)合亩分为内部没有剥削关系和已经产生剥削关系两大类型,不同类型的合亩,反映了合亩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中也可以看到合亩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原始形态的合亩,可能是黎族早期社会的家族公社,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私有制的发生、发展,合亩内公有制残余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矛盾(私人占有和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合亩和个体家庭之间的矛盾(集体劳动与个别消费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私有制的因素不断冲击着原始公社制的藩篱。由于合亩公有的成分逐渐减少,合亩内土地耕牛的私人所有者要求充分实现其所有权,不愿把它们交给合亩共同使用,甚至发展到抽出自己份额的土地自耕(所谓“沃偏”)或出租,加上土地和耕牛的自由买卖,使主要的生产资料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平均分配的原则也开始引起了多数成员的不满,特别是龙仔、工仔和贫苦的亩众们更不堪地主恶霸式的亩头的压迫剥削。为了减少对合亩的依赖而积蓄私有财产的愿望,促使亩众付出更多的个体劳动,并积极关心家庭私有经济的发展。最后,作为合亩内分配和消费单位的小家庭,力求摆脱合亩的支配,把自己的家庭发展成为独立的、完全的生产单位。随着合亩内血缘联系逐渐削弱,地域或比邻关系逐渐增强,大合亩分成小合亩
的现象日益频繁,合亩的规模也越来越小,血缘关系也日渐缩小到最狭窄的范围,合亩成员除了更经常地“沃偏”之外,退亩单干也逐渐增加。这一种发展趋势深刻地反映出家的私有制对亩的公有制的矛盾,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形式。家的私有制侵蚀和动摇了合亩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共耕与平均分配,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为个体经济所代替,合亩瓦解为个体家庭。
(5)解放前的一段时期,合亩正处于自身矛盾发展而趋于瓦解的过程之中,因此合亩地区的经济结构就显得错综复杂。它既早已超越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合亩内私有制已占主导地位并出现了贫富分化和剥削关系,某些合亩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抗;另一方面又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家族公社的残余和家庭奴隶制的某些因素。
(6)直到解放前,在这一片拥有约一万三千多人的地区,合亩还没有为个体经济所代替,而且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残余,甚至在剥削关系十分严重突出的合亩内,诸如简单协作的集体劳动形式,集体生产出来的一部分粮食仍按户平均分配,血缘亲属之间处理“稻公稻母”、“聚餐粮”以及借贷互助等方面仍按传统习惯执行,山栏地仍归公有……等等带有公有制因素的东西仍然保留下来。这都足以说明合亩的瓦解过程是很缓慢的,之所以这样缓慢,显然是与合亩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力水平低下,传统习惯势力约束等等有关。同时,剥削阶级利用合亩作为剥削工具,某些传统习惯有利于维持亩众的最低生活而不致彻底破产,这些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是,合亩地区只是黎族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其他黎族地区特别是汉族地
区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包围,土地买卖、租佃、典当以及借贷、雇工等等经济活动都对合亩制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使合亩地区不可避免地要走其他黎族地区同样的道路。
峒的组织
合亩地区和其他黎族地区一样,直到解放前仍保留着一种具有特色的社会政治组织,黎语称为kom,原意是“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汉语音译为“弓”或“峒”。从峒的原来组织形式和职能来看,可能是黎族的一种古老的氏族部落组织,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而成为一种残存的躯壳,到后来更和封建地方政权的基层组织结合为一体了。
每个峒都有固定的地域,共同地域是峒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峒的地域一般以山岭、河流为界,并且立碑、砌石,有的则种树、栽竹、插木板、埋牛角等等作标志。因此,峒与峒之间有着清楚的界线,而且是自远古的时候就划定了的。峒的地域确定以后,不得随意侵犯,全峒的人都有保卫峒域的职责。倘若要到别峒种山栏、捕鱼、采藤、伐木、狩猎,都必须征得该峒峒头(vau kom)以及全体亩头的同意,并缴纳各种形式的租金或礼物。未经对方同意而逾越峒界开荒或捕鱼、伐术,就被视为对权利的严重侵犯,往往因此而酿成冲突和械斗。
峒有大峒、小峒之分,大峒之下包括几个小峒,各有自己的固定地域。如琼中县的红毛下峒包括毛贵、喃唠、毛兴、毛路、牙开等五个小峒,一个小峒之内往往有两个以上的自然村。峒的疆界原来是比较固定的,大峒辖下小峒的数目亦有一
定。但到了晚近的时候,峒已经和一般的行政区域一样,随政治上的需要有分有合,地缘因素已占主导的地位。如乐东县番阳峒原来包括绸怀、才花、毛农、毛或、雅曼五个小峒,后来将各小峒的疆界略为调整,增加了一个雅开峒,共辖六个小峒。
解放前,峒内各成员之间,经济的和地域的社会联系早已代替了原先的血缘纽带。但是血缘纽带是峒的组织基础这一特征,还可以看到它的痕迹。一个小峒原来可能居住着同一血缘集团的人,他们之间严格禁止通婚。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小峒都已混杂着不同血缘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峒之内开始存在两个以上的、互相通婚的血缘集团。此外,不同血缘的峒与峒之间的通婚是不受限制的。峒内各血缘集团还保留各自的公共墓地和共同的祖先崇拜。峒内许多与原住居民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来户,大多数是来投靠的龙仔、工仔,他们经过两三代之后,也有从龙公的合亩分离出来,单独组成一个合亩或一个村庄的。
凡同住一个峒内的人,都被认为峒的一个成员,他们都以世代祖先的传统习惯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如对峒的疆界的保卫责任;峒内成员间相互援助和保护的义务,特别受到外峒人欺侮时必须帮助复仇;共同负担械斗时向外请援兵的费用;以至村头、峒头的选举、罢免和继承等等,大家都按传统习惯行事。峒内的社会秩序主要靠这些习惯法来维持。
每一个村、峒都有一个至数个“村头”(vau fan)和“峒头”(vaukom),村头和峒头都是汉语的意译。在较早时代,一个村只有一个合亩的,即由亩头充任村头;一个村内有几个合亩的,由各个亩头中最长辈者任村头。除此之外,只要有人能
讲道理,能为村人调解纠纷,在办事时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有了威信,遇事便被邀请参加处理,也就被公认为村头了。这类村头多数是村内的老人,黎语称为“奥雅”(aoya),平时也为人们所尊重。在某些地区,也有由选举产生村头的。一峒之内,从几个村头中推选出辈分最高的任峒头。大峒的峒头又有称为峒长的,大多数由上级(清朝末年时称为总管)所委派。在血缘关系比较单一的村、峒,杂居其中的外来居民一般不能当村头和峒头;反之,当外来居民已占相当的比例时,也可以有自己的村头和峒头。
村头、峒头原来纯粹是村内、峒内的自然领袖,受到群众的尊敬。他们除了为群众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秩序,根据传统习惯处理峒内事务之外,没有什么带强制性的行政权力(甚至在发生械斗时,指挥者或当事人都不一定是村头或峒头),也没有向群众索取报酬。但是,由于合亩内部以及合亩之间的一切纠纷都由峒(通过峒长、峒头、村头、“奥雅”等人物)来解决,峒就成了一定地域内最高的社会政治组织。
峒与峒之间的劳动人民存在着友好往来的关系,最明显的是互通婚姻,结成亲戚;在生活上、生产上互相帮助是常有的事,如遇婚丧、盖房、农忙等,则互相表示关怀和帮助,甚至与别处发生纷争或械斗时,峒与峒之间还有互相支援的情况。
在统治阶级的挑唆下,峒与峒之间也会发生械斗的敌对关系。械斗的起因和目的大多与财产或债务有关系。获胜的一方往往恃势处罚负方巨额的财富(牛只、铜锣、光洋等)。每当发生械斗,一般双方都向别峒拜认龙公,请求出兵支援,龙公在接受所求时乘机索取大量的铜锣、牛只等作代价。龙公不论
直接派人参与械斗或者仅出面调解,都要大量的报酬。因为拜认龙公的关系,往往村与村、峒与峒的战争经常会酿成几个村、几个峒之间的战争。械斗的首领由肇事双方的当事人充任,他们不一定亲自参加战斗,可以出赏雇佣“兵头”带头打仗,完成战争任务后按约给予奖酬。由于挑起械斗的一般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是械斗的核心,由他们决定战争或和解。这些人通过挑拨械斗发财致富,广大劳动人民由于负担沉重的械斗费用而贫困破产。
据毛道乡和毛贵乡的调查,解放前在某些械斗过程中,有这样的情况:械斗之前以猪颈或“鸡毛信”(用一条细小的白藤打一个大圈三个小圈插上一条鸡毛)作为“战争通牒”送给对方,表示要索取指定数量的罚款。若对方拒绝付出罚款,即将通牒退回,从此双方认为进入械斗状态。送通牒由对方嫁来的妇女或请来的外峒人为使者。进攻前必须举行“鸡卜”以占吉凶。对待俘虏一般不加杀害,以便和解后与对方交换或索取赎金,赎金多少按俘虏身分而有所不同。械斗的和解一般请有权有势的峒长、峒头主持,举行“蕊岔”仪式,并由双方当事人杀牛设宴,在宴会上峒长、峒头与械斗双方砍箭为约,达成和解。
村头、峒头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峒这一黎族社会原有的自然组织的情况。但随着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扩展到合亩地区,从此峒的性质以至村头、峒头等的地位和作用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反动统治阶级大力推行反动的“以夷制夷”的政策,以各种官职官衔收买拉拢当地黎族社会内部原有的自然领袖,通过他们对合亩地区的黎族人民进行压迫和统治。特别自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清朝在海南岛设置“抚黎局”以后,合亩地区内也设有总管、峒长、哨官、头家等职衔(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又有团董,乡、保、甲长的名称),委派亩头(龙公)、村头、峒头等上层人物充当。如当时整个合亩地区都受红毛峒(现今琼中县红毛公社)总管王政和所管辖,由他委任峒长(管一大峒,相当于后来团董或乡长所管辖的范围)、哨官(管一小峒,也有管一大峒的)、头家(管一个村或一个小峒)。这些有了世袭职衔的亩头、村头、峒头等等,不仅在政治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在基层的代理人,而且在经济地位上大多数是剥削阶级。他们凭借政治特权侵占峒内的公共土地、山林和河流,勾结反动官府向峒内群众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并从中贪污中饱;征派繁重的劳役,使群众疲于奔命。他们经常在处理民、刑案件纠纷中,肆意敲榨勒索。更严重的是制造纠纷,挑拨械斗,从中渔利;或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害善良,横加重罚,许多地主恶霸就是通过这些手段,掠取了农民大量的土地和牛只。至此,原来的自然领袖已经逐步演变为世袭的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统治人物。至于峒的组织,则已丧失了它原来的社会意义,只是被利用为封建王朝以至国民党反动派的基层政权组织的补充和附属物而已。
据一九五四年的调查,解放前仍然保留合亩制的地区共有二十六个乡,其中包括保亭县第三区的十四个乡(现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直属红旗公社,保亭县毛道公社、畅好公社的全部,南圣公社的一小部分),第五区的毛感、毛岱两个乡(现毛感公社的部分地区),白沙县第二区的七个乡(现琼中县毛阳公社全部,什运公社的部分地区),乐东县第二区的番阳、加艾、毛农三个乡(现乐东县番阳公社的部分地区),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约占黎族地区总面积的8.7%。这二十六个乡共有九百七十一个合亩,三千五百九十一户,一万三千四百一十三人,占当时黎族人口(三十六万人)的3.73%。
这一片地区位于海南岛第二大河流昌化江的河源和上游地带,深入到五指山腹地。河谷两旁高山海拔均在一千米以上。高山上生长着热带季雨林,在河谷和低丘上分布着黎族的村落,这里树木比较稀疏,属稀树灌木丛地带。由于长期以来刀耕火种的结果,天然植被已被破坏,多是萌生林和次生林。从这些自然地貌可以看出人们在合亩地区进行开发活动已有长久的历史。
解放后,在合亩地区多次捡获露出于地表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如一九五六年的一次调查中,在保亭县的毛道、毛枝、雅袁等处就发现有肩石斧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三十九件,可知这些地方在很早的时候已有人类居住。
昌化江上游以东北至西南的流向流经合亩地区。在过去未通公路以前,从海南岛北部平原地区进入五指山,以至南下直达崖县,昌化江是一条天然走廊,是从中部山区南北纵贯海南岛的必经之路。明代海瑞在《平黎图说》中建议开辟的黎山十字大路,以至清代多次拟议的开路方案,都计划采取这条路线。由于地处要冲,自元代以来的历次大举“征黎”,这里也是必到之地。早在明朝正德年间(一五〇六至一五二一年),有些村庄的名称已见于文献记载。如杨理的《上欧阳郡主四事》中,就提到磨岸(毛岸)、磨魁(毛贵)等至今仍然存在的村峒名称。稍后嘉靖年间(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郑廷鹄的《平黎疏》、海瑞的《平黎图说》,万历年间(一五七三至一六二〇年)林如楚的《图说》,提到的村峒名称更多,如凡阳(番阳)、磨羊(毛阳)、磨赞(毛栈)、南恺(南解)、磨敢(毛感)、磨菜(毛赛)等等。海瑞甚至在《上兵部条议七事》中提出“其凡阳、磨栈二村之间,乃东西南北之中,可立一大县”。可见黎族人民在合亩地区建村立寨,最少已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
合亩地区的黎族属于岐黎(即杨理在《上卢兵备书》中所指的“五指之中历代信直不化者为岐”)支系,其中又以服饰风俗等的差别细分为“大鬃黎”、“小鬃黎”、“生铁黎”、“剃头黎”等等,他们都同讲黎语中的岐黎方言。这里隔一鹦哥岭与白沙县的“本地黎”相邻。在乐东县的番阳,则与当地的“侾黎”(“四星黎”)交错杂居。据解放初期的调查,当时除了岐黎这一支系之外,在其他支系的黎族中未发现有合亩制。在岐黎支系中,也只有少部分地区仍保存合亩制。据老人们的回忆,大约在五、六十年前,居住在保亭县第一区毛盖乡、番文乡(今保城公社的部分地区)、琼中县第一区南万乡一带的黎族,仍实行合亩制。更早一些时候,现今琼中县的红毛、什运、五指山三个公社的地方也还存在合亩制。以上地区的黎族也属于岐黎支系。
生产力
农业是合亩地区的主要生产部门,并以合亩为单位进行生产。此外,纺织、编织、制陶、酿酒等手工业只作为副业在农闲时进行,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饲养禽畜、园艺、狩猎、捕鱼等都是家庭副业,而且和手工业一样,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的(狩猎多以村或合亩为单位),采集野生小动物和植物作为食料相当普遍。
农业的生产工具除耕牛外,主要有犁、耙、锄头、铲、钩刀、手捻小刀、四齿手耙、斧头等。耙是木质或竹制工具,其余都是铁质工具。铁质工具都是从汉区输入的。畜力一般不缺乏,主要使用水牛,黄牛少用于耕田,有用于拉车的。
绝大部分的劳动力都投放在农业生产上。劳动力占总人口的60%以上,其中女劳动力稍多于男劳动力。妇女在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生产过程中还保留着比较严格的性别分工和原始的简单协作的残余,加上众多的生产禁忌日①,劳动力的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农业生产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主要是稻谷,其次是番薯、玉米、木薯、高粱等。此外,还种植少量的烟草。稻谷分水稻和早稻,以水稻耕作为主。由于缺乏水利设施,大多数的稻田一年只能种一造,种双造的水田较少。耕作技术比较落后,虽然实行二犁二耙,但全部使用木耙或竹耙,牛踩田代替犁耙田的比较普遍。播种、育秧、移栽的方法和汉区基本相同,但没有选种的习惯。除育秧田施一些肥料外,其他的田都不施肥,尤其不使用人粪尿。田间管理很差,对中耕除草不重视,除驱除鸟兽害外,对防御病虫害则缺少办法。男女性别分工严格,男子负责犁田耙田、浸种播种、灌溉、挑稻、防鸟兽害和砍烧山栏地;妇女负责插秧、除草、收割脱粒和播山栏稻种子。此外,劳动上还存在原始的简单协作的残余,不分工种,不分轻重,大家都在同一时间集中在同一地点做同样的一种工作。收割时以手捻小刀(长三寸宽六分的薄铁片)逐穗割下,割一把稻(净谷重二斤左右)约需十五分钟。收割后把稻穗一把把的挂在竹扎的晒谷架上,任由风吹雨淋,鸟吃鼠耗,浪费很大。
除水稻耕作外,还在坡地和山栏地里种植旱稻。“山栏稻”是一种“刀耕火种”式的耕作方法,即在旱季时把山林砍倒烧光,清除残枝后,等到雨季来临时,由男子以尖木棒戳穴,妇女随后点播种子,经一、二次除草,即等待收获。一般种植两、三年,地力衰竭后就荒弃,另择地烧垦。山栏稻的产量因当年的雨量多寡而相差悬殊。在合亩地区种山栏仍相当盛行,约占当地稻谷总产量的20%左右。
由于耕作粗放,缺乏人工灌溉设备,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薄弱,因而粮食产量很低。一般上等田单造水稻平均亩产只有二百斤左右,最差的只有五十斤左右。
手工业是主要的家庭副业,没有出现专业的手工业者,也没有专门作为商品生产的手工业产品。男子一般都会编织藤箩、藤小凳、刀篓、鱼网,制造木耙、犁架、铁质农具的木柄和简单的纺织工具、织鱼网工具等,有些地区男子还会制造牛车、谷磨。钩刀、凿、小尖铁棒等是主要的手工业工具。妇女一般都会纺纱、织〓、织木棉被和山麻被、织山麻的男子服装、编织露兜叶席、酿酒等,一些地区的妇女还会制造陶器。
纺织工具有木质手摇轧花机和脚踏纺纱机,也有使用比较原始的纺锤,织布是用一块压板和几根横棍坐地围腰而织的原始工具。制陶技术比较落后,都是用手捏和条筑法制成陶坯放在柴堆上烧成。
饲养家畜家禽是一项重要的副业,有牛、猪、狗、鸡、鸭、鹅等。但牛、猪都没有栏圈,特别是牛,一般都是放进山里野牧。由于迷信的风俗,往往杀牲(以牛为主,还有猪和鸡)“做鬼”①,损耗很大。
狩猎、捕鱼也是副业的一种。狩猎主要使用土枪,还有弓箭、镖枪、尖刀等工具。平时以一家一户单独进行,但年终时还保留以村为单位进行狩猎(围猎)的习惯。捕鱼工具有鱼网、鱼笼、鱼栅、弓箭、长短矛、钓钩等,也有使用毒药的,人工养殖极少。渔猎的捕获量很少,都是自给性生产。蔬菜仅有少量种植,副食品还大部分依靠采集野生植物和小动物。
综合以上的情况来看,合亩地区总的生产力水平虽然已远远脱离了原始公社时期的状态,但它的落后面貌仍然严重存在着。如这里的黎族人民不会炼铁,也不会制造铁质农具,只能够把用坏的铁质农具进行简单的加工,制成其他工具,而懂得这种技术的人也很少。由于铁质农具都是从汉区输入,在来源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直接影响到合亩地区生产力的发展,
合亩的规模和类型合亩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标志是以合亩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但合亩规模的大小却各地有所不同。据一九五四年调查,三个县的合亩地区共有九百七十一个合亩,三千五百九十一户,平均每个合亩为三点七户。其中最小的为两户,最大的达到三十一户。从不同地区来看,以乐东县番阳地区三个乡平均每个合亩的户数最多(五点六五户),保亭县毛感、毛岱两个乡的户数最少(二点二三户,不及前者的一半)。又在抽样调查的六十一个合亩中,由二至四户组成的有四十一个合亩(占67.21%),五至九户的有十六个合亩(占26.23%),十至十四户的有四个合亩(占6.56%)。由此可见合亩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大的也不过十来户,二十至三十户的极少。只有保亭县毛道乡的合亩规模较大,平均为七、八户,最多的三十一户,十五至二十户或二十户以上的也不少。据调查,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毛道乡仍然保留较多的几代人从未分亩的“大合亩”。毛道乡的合亩,原始的色彩一般较别处地方为浓厚。
从合亩内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来看,所有的合亩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血缘纽带的基础上,由父系亲属组成;一类是除血缘亲属之外,并有非血缘的外来户参加。这两种类型的合亩所占的比例,在不同的地区,以至不同的村、峒也各不相同。据调查,保亭县通什乡和毛道乡共一百O八个合亩中,全是血缘亲属组成的合亩五十一个,占总合亩数的47.2%,占总户数的35.6%;亲属与非亲属混合组成的合亩五十七个,占总合亩数的52.8%,占总户数的64.4%。但也有一些地区是第一种类型占多数的。在一般情况下,规模较大的合亩多属于混合类型;而规模越小,则纯血缘的类型就越多。有些两三户组成的合亩(这在合亩地区边沿的保亭县毛感、毛岱乡;白沙县的毛贵、毛栈等乡较多见),往往就是一些“父子亩”或“兄弟亩”。如上述的五十一个血缘合亩中,属于“父子亩”和“兄弟亩”的占总数的86.5%。这类小合亩都是从比较大的合亩分化出来的,一旦他们抛弃了合亩的某些传统内容和形式,就和一般的大家庭没有很大的差别。但也有一些血缘合亩规模比较大,超过十户以上,这些都是几代以来从未分过亩的,这在毛道乡比较多见。
根据合亩内外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来划分,合亩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合亩内部没有产生剥削关系,合亩里人们的关系基本上是共耕和互助合作的关系。亩头和亩众以至亩众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这种类型的合亩绝大多数是由血缘亲属组成,渗杂外来户的很少。在毛道乡二十五个合亩中,二十四个属于这一类型。在这类合亩中,有个别的虽然内部没有剥削关系,但亩头(也有个别的亩众)对亩外的人,以及合亩对亩外的人、合亩与合亩之间已产生了剥削关系。
(二)合亩内部和合亩对外都已产生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一些合亩中,剥削关系还十分严重和突出。亩头(龙公)对亩内众多的外来户(龙仔、工仔),以至对其他合亩的人已经是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毛道乡二十五个合亩中,只有王老本一个合亩属于这一类型。又通什乡的王老关合亩,番阳乡的王如清合亩、徐新东父合亩也属于这一类型。这类合亩只是保持了旧的合亩的形式,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的合亩共耕仅仅留下一个躯壳而已。
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
合亩地区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是很复杂的。
首先是耕地的占有。合亩地区的耕地包括水田(指一年可种两造的水稻田)、旱田(一年只能种一造水稻)、山栏地、坡地、园地等五种。从各种耕地所占的比例来看,主要是水田、旱田;其次是山栏地;再次是坡地、园地。如番阳乡空透、什茂、万板三个村共有耕地七一五点九亩,其中水田一〇五点六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4.75%),旱田四四五点七亩(占62.26%),山栏地一四五点七亩(占20.85%),坡地十八点九亩(占2.64%)。
从水田、旱田和坡地的占有情况来看,可分为合亩内各户集体所有,亩内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合亩内各户集体所有(以下简称合亩所有)的耕地,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的水田,主要是所有者用猪、牛或光洋买进的,旱田多是自己开荒得来,也有雇工来开垦的。
至于这三种所有制各占的比例多少,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合亩都各有不同。一般的情况是:没有外来户纯由血缘亲属组成的合亩,大部分的耕地属合亩所有,其次是几户伙有,一户所有的最少。如毛道乡的王老东合亩,六代以来从未分亩,没有外来户,合亩所有的水田占合亩内全部水田总面积的87.9%,旱田则占84.4%。该乡雅袁峒的六个合亩,合亩所有的水田占50.15%,几户伙有的占87.25%,一户所有的占12.6%。在一些规模较小的父子合亩和兄弟合亩中,合亩所有的耕地所占的比例就更高。如保亭县通什乡,合亩所有的耕地共二九一点五
亩,其中八十八亩的所有者是由两户组成的合亩,一三一亩归三户组成的合亩所有,这两种合亩所有的耕地已占全部合亩所有耕地总面积的73.41%。虽然在这些合亩中合亩所有的耕地所占的比例很高,但尚未出现耕地和牛只伙有和私有的合亩仅是个别的。另一方面,在外来户较多(有些甚至占多数)的混合组织的合亩中,耕地大部分为几户伙有(以二至四户伙有的占大多数),其次是一户所有,合亩所有的最少。在个别地主恶霸当亩头的合亩中,耕地全部由亩头一户私有或其兄弟几户伙有,合亩所有的耕地已不存在,大量的外来户(龙仔、工仔)则片土皆无。
在不同的地区,合亩所有的耕地所占比例相差也很悬殊。如毛道乡毛枝大村九个合亩中,除王老对合亩的水旱田全属私有外,其余八个合亩的耕地全属合亩所有,没有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的。又毛道乡除毛枝大村之外的十八个合亩中,合亩所有的耕地所占的比例就小一些,其中水田占总面积的50.14%,旱田占53.18%;几户伙有的,水田占37.25%,旱田占38.1%;一户所有的,水田占12.61%,旱田占8.72%,合亩所有的耕地仍占多数。但在通什乡,合亩所有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0.2%,几户伙有的则为52.4%,一户所有则占37.4%。在乐东县毛农乡毛或村的九个合亩中,合亩所有的耕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12.8%。在白沙县的毛贵乡什盖等七个村,合亩所有的水田占31.88%,旱田占27.9%。但同县的毛路乡,全部的耕地归合亩内各户私有,没有合亩所有和几户伙有。
山林、荒地、河流均属全村或全峒公有,在本村、本峒地域内居住的各合亩成员(包括亩头、亩众、龙仔、工仔)都享有平等的使用权利。开垦山栏地种植旱稻和杂粮,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地段,不受限制。一般都是由合亩内的近亲分别组合,一个合亩分成两个以上的组合进行耕作,也有一家一户单独进行的。只有规模最小,且由血缘亲属组成的合亩,才以合亩为单位进行开垦。晚近时期,有一部分山林、荒地、河流已为地主恶霸所侵占,在这些山林、河流中种山栏、狩猎和捕鱼,事先都要征得所有者的同意,并向其交租或送礼,形成了山租等的特殊剥削方式。
至于屋前屋后的园地,都归开垦者一户私有。
牛只是合亩地区仅次于耕地的重要生产资料。牛只(包括耕牛和非耕牛)的占有也分合亩各户集体所有、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形式,但合亩所有的成分已不占优势,绝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的合亩以一户所有为主,几户伙有次之。如上述毛道乡十八个合亩的牛只中,属合亩所有的仅占牛只总数的10.41%,几户伙有占42.90%,一户所有则占46.69%。又如通什乡,90%以上的牛只归一户所有和几户伙有。牛只的来源以家庭副业产品交换得来为主,其次是出嫁女儿的财礼和媳妇的嫁妆,以及牛只自身的繁殖等等。牛只不仅用作畜力(曳引力),而且是财富的标志和交换的媒介。由于婚丧活动和“做鬼”等都要宰杀大量的牛,因此牛的消耗量很大。
除了耕牛之外,农业(包括园艺、饲养禽畜等)、手工业、捕鱼、狩猎等活动所使用的一切工具,完全属一家一户私有。合亩成员从事合亩的集体生产时,都使用自己的工具,损坏后也由自己负责修补和添置。手工业、副业以至大部分的山栏地耕作,都以户为单位进行,产品归该户所得,已属于家庭私有经济的范畴。
随着土地、牛只等生产资料交换关系的出现,合亩内各户以至合亩之间生产资料的占有日趋贫富不均。如白沙县毛贵乡的王友风合亩,有耕地三十八点八亩,其中亩头王友风一户就占了二十九亩,为耕地总面积的74.7%,他的弟弟和堂兄等共六户仅有九亩(占23.2%),有两户龙仔则完全没有耕地。合亩之间占有的不平衡更为严重,以至贫困的合亩不得不租入土地来耕种。如白沙县毛栈乡番满村六个合亩共有耕地七十五点八八亩,其中王大富一个合亩(其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便占有三十六点六三亩,约占全村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乐东县番阳乡什茂等四个村共十八个合亩,共有耕地七五九点三亩,平均每个合亩占有耕地四十二点一八亩,而徐新东父合亩便占了一〇六点九亩,为平均数的一倍半;王老波父合亩共五户,占有耕地八十二点四亩,平均每户十六点四八亩,而张亚久父合亩共八户,仅占有耕地二十二点一亩,平均每户只有二点七六亩,仅为前者的六分之一。
牛只占有的悬殊也很突出。如毛道乡十五个村十八个合亩共有耕牛二三五头,平均每个合亩有耕牛十三点〇六头。其中占有耕牛不到十头的合亩有十个,占全部合亩数的55.6%,其中王老黄合亩一头耕牛也没有。而王老本合亩和王国才父合亩分别占有耕牛四十三头和四十一头,相当于平均数的三倍多。王老本合亩共十九户,有牛只一一三头,其中耕牛四十三头,非耕牛七十头。亩头王老本一户就占有耕牛二十五头(占耕牛总数的58.14%),非耕牛四十五头(占64.29%),同一合亩的王老对、王老青、王老永等七户则连一头牛也没有。乐东县番
阳乡什茂等四个村共有牛只一四九头,平均每个合亩有八点二八头,其中徐新东父合亩有三十一头,王老波父合亩有二十七头,均相当于平均数的三倍以上,而张亚八合亩和张亚久父合亩则一头牛也没有。
至于犁、耙、锄头、钩刀等生产工具几乎每户都备有,只有极少数农户的农具不齐全。
在一般的情况下,不论何种占有形式的耕地和牛只,所有者均有完全的支配权,可以租佃、抵押和买卖,并按父系继承,也没有出现定期进行重新分配或调整的现象。合亩所有的耕地和牛只如要改变所有权,一般需经合亩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才能作出决定;但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的,则不需征得合亩内其他成员(包括亩头在内)的同意。另一方面,在特殊的情况下,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的耕地和牛只,所有者的支配权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合亩内某一成员遭遇天灾人祸,或被恶霸强罚,该成员把自己的田地和牛只全部卖光仍不足以应付时,他的兄弟私有的以至合亩所有的田地牛只也要拿来出卖抵债,甚至有亲属关系的其他合亩也有义务来帮忙。
无论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耕地和牛只,大部分都交由合亩统一使用,不按交出的耕地、牛只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因此,所有者(主要指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的)在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方面受到了限制,私有制的所有权就未能充分实现。
在合亩内,也有个别富裕户抽回属于自己所有(包括伙有)的一部分耕地牛只来自耕或出租,黎语称为“沃偏”,意思是“做私己”。这种情况并不多,而几户组合或单独一户种山栏地的则比较普遍。
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每一个合亩都有一个“亩头”,亩内的其他成员就是“亩众”。
亩头黎语称“俄布笼”(go plug lug),直译是“大房头”,是“家族长”的意思。又称“畏雅”,意思是“犁第一道犁路的老人”。白沙县合亩地区则称亩头为“禾打”或“头耕”,前者为音译,后者为意译。
亩头由合亩内最高辈分中年事最长的男性担任,亩头死后,由其弟依次继承,如没有弟弟,则由长子继承。由于是血缘世袭,因此外来户通常不能当亩头,但经过“入主”仪式并改姓亩头的姓,承认亩头的祖先是自己的祖先的外来户,如果条件具备,也可以继承亩头的职位。
亩头必须有较丰富的生产经验,能够组织和领导全合亩的生产活动。同时亩头必须和他的妻子一起在生产过程中举行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因此规定亩头必须已婚并与妻子同住;如果已婚但妻子未落夫家,或婚后妻子死了没有续娶,就不能当亩头。
亩头是一亩之长,是合亩集体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有较丰富的生产经验和传统知识,在亩众中有一定的威信。亩头除了与亩众同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外,还要主持一些生产上的宗教仪式,如播种、插秧、放牛上山、收获等等,都要亩头和他的妻子分别带头做一下样子,然后亩众才跟着劳动。吃新谷时,由亩头先吃,妻子一天后才吃,然后亩众跟着吃起来。亩头的妻子在管理妇女的生产活动方面,是亩头的助手。
亩头不仅领导合亩的生产并掌握分配,而且亩内和亩与亩之间的一切重大事情,如处理和保管集体财产,处理亩内外的纠纷,接收外来户(龙仔)等等,都由亩头出面联系、调解和处置,亩众一般都表示服从,但没有强制权力。亩众经过一定的手续可以主动提出分亩或退亩,但分亩时,亩头照例多分得一些田产。
在基本没有剥削关系的合亩内,亩头与亩众,以至亩众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一部分外来户除外)。亩头除了按传统习惯多分配一些农产品外,在其他方面与亩众同处于平等的地位,如平等参加集体劳动,担负共同的费用,共同防卫外来袭击,平等享受各种权利等。此外相互之间,还保留互助合作的传统习惯,不论亩头或亩众,当他在盖屋、婚娶、生病“做鬼”或办丧事时,整个合亩以至全村都来帮忙,事主只要略备酒饭招待,不需任何报酬。亩内有人缺粮或经济困难,较富裕的户就设法帮助,借贷不要利息,甚至无偿援助。此外,如某户被敲诈勒索和处罚,或因“做鬼”花费巨大而本人又无力偿付时,所在合亩就有义务帮助他偿还,必要时经合亩全体成员议决,可以出卖合亩集体所有的土地和牛只。对于抚养鳏寡孤幼,亩众们都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妇女丧夫后回娘家居住,参加生产劳动和分配,丧失劳动力的,合亩内她的亲属成员(主要是亲兄弟)就把她抚养起来。这种互助合作的关系,也存在于合亩与合亩之间,特别在生产活动中比较多见,如插秧、收割和开垦荒地时彼此帮工,事主杀牲招待喝酒以示答谢,不计报酬。
随着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势力不断向合亩地区扩展,以及合亩内部的演化,亩头的地位和性质、亩头与亩众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等与互助合作的关系遭到破坏,代之以压迫和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亩头最初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分配中取得某些特权,把具有宗教性质的和属于公共开支的传统留粮攫为已有,并随意增加留粮的数量,使之变质为剥削,同时以龙仔、工仔等外来户作为剥削对象。特别是那些充当反动统治代表人物的亩头,如保亭县通什乡的王老关,毛道乡的王老本,乐东县番阳乡的王公清、王如清等,他们与反动政府相勾结,出任总管、团董、哨官、乡保长等反动职务,亩众们遭受着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合亩内原来的共耕、按户平均分配产品、互助合作等等传统形式已被这些亩头利用作为统治剥削亩众的手段。这种亩头,实质上已不是原来意义的亩头,而变为合亩地区里的地主恶霸,这种类型的合亩已成为一种残存的躯壳。
在合亩地区,人们在生产过程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中,还有所谓“龙公”和“龙仔”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合亩地区以外的黎族中亦存在,但不及合亩地区那样普遍,形式也有一些差别。
“龙公”、“龙仔”是汉语海南方言的称呼。黎语称“龙仔”为“沃伐”(vuek vat),直译是“做穷人”,也有“做奴”、“做长工”的意思;黎语称“龙公”为“沃凡”(vuek veeng),直译是“做富人”,也有“做主人”的意思。在合亩地区,龙公和龙仔都有个人和集体两种形式。龙公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合亩、几个合亩或一个村为整体,接受来投靠的龙仔;龙仔可以个人或自己一家去投靠,也有一个合亩、几个合亩或一个村为整体,去投靠龙公的。在一个合亩内,龙公绝大多数都是亩头,但亩头也有沦为别人的龙仔的,个别的亩众也可以收纳龙仔。在集体投靠中,由几个合亩公推辈分最高最有威信的亩头作为集体的代表充任龙公;“村头”则作为全村的代表充任龙公。
龙仔之所以投靠龙公,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或自己一家)投靠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如生活贫困破产、无依无靠、负债或被罚巨额钱财而无力偿还等等,也有因受豪强恶霸的欺压,在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去投靠龙公的。但未发现因战争和械斗被俘而沦为龙仔的。集体投靠多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如因械斗等,为求豪强的援助和保护而整个合亩、几个合亩、甚至全村全峒投靠政治上有权有势的龙公,这主要是政治上的依附关系,平时一般不为龙公负担什么经济上的义务。
缔结龙公龙仔关系时,龙仔要给龙公送牛、铜锣①和酒等礼物,龙公设酒席宴请全村的人,并须举行“砍箭为凭”②的仪式。一经砍箭确立关系后,便世代承袭,祖先是龙仔的,他的子孙后代都是龙仔,龙仔如果单方面否认和废除这种关系,会被重罚甚至杀害。
集体投靠的龙仔不必移居到龙公的合亩和村里生活和劳动。个人投靠的龙仔平日在自己家里劳动和生活,但遇农忙或龙公修建房屋时,按例要到龙公家里从事无偿劳动一两次;逢年过节或婚丧、“做鬼”杀牲时,以至猎到野兽,也要送一些肉给龙公;龙公每年有两三次到龙仔家,龙仔要设酒席,送礼物。政治上,龙仔要充当龙公的耳目,为龙公通风报信,发生械斗时要替龙公出力卖命。而龙公则以龙仔的保护人自居,龙仔一旦出了事,龙公就出面为他们进行调解或说情,以减免罚款,但亦有个别龙公乘机勒索巨额报酬的。
有一部分龙仔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迁居到龙公合亩中,参加龙公合亩的生产劳动。这类龙仔以个人投靠为主,只有个别是全家移居到龙公合亩的。这些龙仔初来投靠时,大多数是青年未婚男子,他们对合亩原有的耕地牛只都没有所有权,也没有享受按户平均分配产品的权利,只有在龙公帮助之下结婚成家之后,才另立一户参加合亩的分配,并且通过搞副业、种山栏等积累一些钱财买入少量的耕地和牛只。这些私有财产受到社会的承认,龙公不能随意侵占。这类龙仔除了移居入亩内和参加龙公合亩生产劳动之外,其他应负担的义务与不参加合亩生产的龙仔相同。
在移居投靠的龙仔当中,有些是短期投靠的,一旦还清债务或纠纷已经解决,便可自由离开(退亩),但要交三头牛给龙公作为生活费用(俗称“吃饭费”)的补偿,但离开后龙公龙仔的关系仍然保留着。
有一类移居投靠的龙仔是以身抵债的,他们多数是自幼孤苦伶仃,生活无依无靠,或因重大变故而完全破产的人。这类龙仔在当地又称为工仔,有些自小卖身的称为“出卖龙仔”(有被父亲出卖的,也有自己出卖自己的)。他们属于终身投靠的性质,人身不自由,根本不能离开龙公,他们不仅参加合亩的生产劳动,还要负担龙公的家务劳动。他们在结婚立户以前,一无所有,分配上比上述一般的龙仔更不平等,社会地位也更低。结婚立户后,才能和一般的龙仔一样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在工余时间自己种植山栏、饲养家禽和从事家庭副业。但是工仔的结婚年龄一般都在四十岁左右,并由龙公帮助一点结婚费用。
与“出卖龙仔”性质相类似的就是义子(养子)。所不同的是义父往往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或缺少劳动力,主动付出一定的身价来收养义子。收养义子时也要举行设席请客的仪式。义子必须改姓义父的姓,认义父的祖先为自己的祖先,成为义父家族内的成员,禁止与义父同一血缘集团的妇女结婚或“放寮”①,义父帮助义子娶妻,结婚成家之后便正式成为合亩内的一户,有资格按户平均分得一份谷物。义子可以继承义父的财产,并得充任亩头。若义父死后其亲生儿子年纪尚幼,义子则暂时代理义父的亩头职务,等亲生儿子长大后才让位。
上述各种类型的龙仔,与合亩内不是龙仔的一般亩众,在地位和待遇上存在一定的差别。龙公对龙仔不能毒打、杀害,不能转让、出卖,龙仔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私有财产也受到社会上的承认;但龙仔在人格上不是完全的独立自主,动辄被龙公贱骂为奴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龙仔是被轻视和鄙视的。
至于在某些地区的一些合亩内,那些称为工仔的在劳动和分配上显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特别是个别地主恶霸当亩头的合亩内,如前述的王老关、王老本、王如清合亩,工仔的境况十分恶劣,不仅常常劳动多,分配少,而且龙公更以种种借口处罚工仔,进行超经济掠夺。工仔逃走被抓回即遭痛打,龙公可以打骂以至杀死工仔,并出卖工仔和他的子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工仔从种植山栏、手工业、副业所得来的收入,仍不受龙公的侵占。
此外,因为关系世袭,子孙繁衍的结果,也形成了有些整个合亩甚至整个村都成为某一个合亩或某一个村的龙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龙公、龙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发生变化,不少人既是别人的龙仔,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龙公,兼有双重的身分。有些比较贫穷的亩众也有自己的龙仔。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合亩地区的龙公龙仔关系,在它的原始阶段可能带有氏族收养成员的性质,但随着合亩内部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的现象,这种关系也演变为压迫与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特别到了晚近年代,有些龙公已成为地主恶霸,在他手下有大量的龙仔和工仔,他们已经带有家庭奴隶的性质。而合亩内属于外来户的龙仔、工仔不断增加,血缘纽带逐渐松弛,这也是促使合亩解体的一个因素。
产品分配
合亩地区产品分配方式,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复杂性相适应,也是多种多样的。
合亩内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或几户伙同进行生产所得的产品,出租土地、牛只所得的地租和牛租,以至各种副业等其它收入,均归该户或该几户所得,不归合亩分配。
合亩共耕所得的产品,由亩头主持分配。按传统习惯,在全部产品中,首先要扣除下列的几项稻谷:
(1)种子。
(2)“稻公稻母”(黎语称“麦雄”,意即“五谷的灵魂”),又称“头米”。这些稻谷只有亩头一家人可以吃(群众说:“这些稻公稻母一定要留给亩头吃,否则对来年生产不利。”),不能出卖、转让或赠送,但可以拿来救济亩内的困难户。各个合亩扣除“稻公稻母”的数量不完全相同,一般是按每块田或每次买入的田地(不论块数)收一把至三、四把稻谷,每把净谷重约二斤。
(3)“留新禾”。收割前,亩头的妻子先割回十至十二把稻谷煮饭酿酒,亩头夫妻吃一天后,次日全合亩的人一齐来吃。
(4)“酿酒粮”,或称聚餐粮,约数十斤稻谷,由亩头掌管,用来酿酒,待插秧完毕后全合亩的人一齐共饮;尚有米剩余的则煮饭吃。
(5)“公家粮”,数量不定,由全合亩的成员共同管理,需要动用时由全体成员商量决定。亩头可以用公家粮来招待客人,合亩成员结婚、盖房子有困难时也可以动用,也有用来救济亩内缺粮户的。有些地区还另留“青年粮”(约九十至一百斤稻谷),专门分给未婚青年男子,由他们自己支配或积蓄起来供日后结婚之用。
扣除上述部分之后,余下的全部按户平均分配,连同龙公龙仔在内,没有特殊或例外。当男女青年结婚后,只要盖有房子并单独开伙食,参加合亩内的主要劳动,便可取得作为一户进行分配的权利。如丈夫年幼不能参加主要劳动,但妻子回家参加主要劳动,则仍算作一户。婚后不久妻子死去,丈夫仍能保持分配方面的一户的权利。若婚后丈夫年幼未能参加亩内的主要劳动,而妻子尚住在娘家,丈夫就随他的父母生活,只能算作半户进行分配。如妻子在农忙时偶尔回夫家参加劳动,便由合亩公议分给一些稻谷,娘家对她则不分配。若夫妻双方均死去,分配方面的一户的权利就被取消,年幼的子女由合亩里血缘最亲近的成员负责扶养。
在有些地区如通什乡,则按户并适当照顾人口进行分配。
此外,对合亩内的老人、小孩、残废者分给相当于半个劳动力所得的稻谷。至于丈夫死后回娘家生活的寡妇、随母亲出嫁而来的少年、幼童,均受到抚养而不受歧视。
有一些内部已经出现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合亩,按户平均分配的传统已遭到破坏,亩头(龙公)往往以各种借口多分一些稻谷。如毛道乡王老仁合亩共六户,其中五户是龙仔,全年稻谷总产量二千九百斤,扣除传统留粮约五百斤,实际分配二千四百斤,结果亩头王老仁一户分得四百五十斤,其余五户龙仔各得三百九十斤。特别是一些地主恶霸当亩头(龙公)的,亩内分配更为悬殊。如毛道乡的王老本合亩,亩头王老本一户每年独得稻谷八、九千斤,而龙仔、工仔每户仅得四、五百斤。又如通什乡黄老茅合亩,亩头一户就分得三千斤,黄老茅的儿子和侄儿两户各得一千四百斤,龙仔五户平均每户仅得五百八十斤。
至于合亩和合亩之间,由于耕地牛只占有的不平衡,分配水平也就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如乐东县番阳乡万板村的徐新东父合亩,平均每户分得一千三百一十斤,而同村的徐老磊合亩,平均每户仅得六百五十七点六斤,相当于前者的一半左右。
如上所述,合亩内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手工业、园艺、饲养禽畜、捕鱼、采集野生动植物等活动,所得均归各户所有,由各家独立消费。种植山栏分一户单独进行和几户合伙经营两种方式,前者所得归该户所有,后者所得则由合伙各户平均分配。
狩猎一般以村为单位(也有少数以合亩、或联合两三个合亩为单位)在农闲时(每年的十二月至次年二月)集体进行。猎获物的分配原则是:首先把野兽的头分给领导打猎的人(黎语称“俄巴”,由参加狩猎的人在出猎前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推选出来),一只后腿分给首先打中猎物的人,其余全部兽肉在狩猎单位内多则按人,少则按户平分。个人的狩猎以户为单位,多在每年的四至六月间的晚上进行。所得的猎获物由打猎者先取一只腿,剩下的仍在原来的集体狩猎单位内按户平均分配。
交换关系
合亩地区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很不发达,还没有形成本民族的商人阶层。交换关系主要在黎族人民和汉商之间进行,并以物物交换为主,亦有少数使用汉区通行的货币如光洋、铜钱、铜币等作为交换的媒介物。汉族商贩有座商和货郎担,前者分散住在各个较大的黎族村寨内,合亩地区在解放前还未出现进行集中交换活动的市集。汉商从乐东、崖县、藤桥等地运入各种生产资料(主要是犁头、锄头、钩刀等铁质农具)和生活用品(主要是盐、棉纱、丝线、针、金属饰物等),换取黎族人民的牲畜(猪、狗、鸡)、红白藤、烟草、藤箩、兽皮等土特产。在交换过程中,汉族奸商的剥削相当严重,一支针换一只鸡是通常的事,他们经常把商业剥削和高利贷剥削结合起来,以攫取更多的财富。在一般情况下,黎族人民进行交易具有为买而卖的特点,当人们需要购买农具或其他日用品时,才会把猪、鸡、红白藤等出卖。
合亩地区发生的另一种交换关系是土地的买卖。解放前合亩地区土地买卖的现象相当普遍。如乐东县番阳乡万板村共有耕地一六一点六亩,其中有九十九点二亩发生过买卖关系。白沙县毛贵乡番满峒五个村共有耕地一五〇点六亩,其中有一二一点八亩发生过买卖关系。毛道乡七个村最近四代以来共发生过二十六次土地买卖,其中二十一次是以牛为媒介物。由于土地的所有权存在合亩集体所有、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形式,因此,土地的买卖也分别以合亩、几户和一户为单位进行。合亩集体所有的土地出卖,须得到合亩的同意。几户伙有或一户所有的土地出卖,由几户或一户的所有者自己决定。买入土地的情况也如此,谁买入即归谁所有。在出卖土地时,首先应卖给本合亩的人,如本合亩无力购买,就按血缘关系的亲疏依次卖给同村的其他合亩、同远祖的其他村,最后才卖给无血缘关系的人。因此土地买卖一般不出本村本峒,也有发生于兄弟之间的。晚近以来,有些地主恶霸还从外村外峒买入土地。土地买卖要有中人,并由买者备酒邀请村内的亩头、父老、本合亩的兄弟亲属和卖田者全合亩的男人一起来喝酒,双方当面讲明价格,并砍竹为凭。地价比合亩地区以外的黎族地区低,中等田每亩一般值两头牛和五个光洋,甚至有更低的。在不少情况下,都是卖主因被罚或“做鬼”缺牛而出卖土地换取牛只的,牛成为土地买卖的主要媒介物。至于土地买卖从何时开始出现,据毛道乡的老人回忆,当地在四代以前就发生过土地买卖。在白沙县毛阳乡的什益村,曾发现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间订立的“卖山契”,是用汉文书写的,显然是较后期的事了。
除了土地买卖之外,还存在土地典当的关系。这里的黎语中没有“典当”和“抵押”的词汇,都是使用汉语借词。土地典当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间相当普遍。除双方当事人外还要中间人,双方同意后典当关系便告成立,并刻竹为凭。典价相当于售价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赎典时都是照原典价赎回,不论年限长短,一概无息,因此典当的期限并不严格。租佃、借贷、雇佣关系合亩地区土地租佃关系比其他黎族地区少见,但不同地区以至各村各峒之间的情况也不一样。如番阳乡万板、抱隆、什茂三个村出租的土地分别占该村耕地总面积的40.6%、13.5%和9.43%。毛道乡全乡出租的土地四〇六点一亩,占全乡耕地总面积的15%强,而隔邻的通什乡出租土地只占3.36%。租佃关系有发生于合亩与合亩之间、合亩与个人之间、以至个人之间等三种情况,但尚未出现全靠佃耕的合亩和合亩内的个体佃户。地租是实物地租,分固定租和对半分的活租制两种。固定租一般是三至五亩旱田每年交一拇①谷子。租佃关系的出现,使土地经营越出了本合亩共耕的狭小范围,这是促成合亩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
牛只的出租比买卖更普遍。通什乡属于地主性质的亩头共有牛四二三头,其中出租一九〇头,占牛只总数的45%。每头牛的租金不论租期长短,一次过收二至八个光洋,也有每三年付一个光洋的。繁殖的牛犊归牛主。牛主每年来看牛时,租牛户(合亩或个人)要备酒肉款待。
借贷关系也发生于合亩内部和合亩之间。亩内成员之间借粮食绝大多数要利息,年利率百分之百,复利计算,但借钱(光洋)则不要利息。毛道乡雅袁峒的王老陆合亩出现过将借出的光洋折作粮食收息的事例。借牛在三年内归还的不取利息,三年以后,每头牛需付息一拇稻谷。合亩之间以借稻谷的较多,牛只、光洋次之,利率与私人借贷相同。由于合亩地区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借贷通常发生在因病杀猪杀牛“做鬼”而不堪负担,或歉收缺粮的时候,因此上述两种借贷关系并不多见,而且尚未出现以放债为业的寄生者。
雇工剥削在合亩地区是晚近才有的事,多发生于边沿地区,如白沙县的毛贵、毛栈乡等地。长工做两三年可得猪一只、鸡若干只,四、五年可得牛一头。短工工资由双方商定,每月工资光洋一元左右。雇工在合亩内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能享受按户平均分配产品的权利,也不能继承亩头的职位。
综合以上的各种情况,可以归纳为几点:
(1)在生产力状况方面,合亩地区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是直到解放前夕,当地的黎族既不懂炼铁,也不会制造铁质农具,铁质工具全靠从汉区输入,由于来源不够稳定和受到不等价交换的剥削,限制了生产的扩大和发展;加上手工业没有和农业分离,交换关系不发达,人们的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水平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和水平不高是很明显的。但这样的情况在合亩地区以外的黎族地区也是存在的,只是合亩地区更为落后而已。就合亩地区农作物的产量来看,人们劳动所能提供的产品,不仅可以维持人们低水平的生活需要,而且可以提供某些剩余产品,这就为剥削关系的存在提供了物质条件。
(2)在生产关系方面,合亩地区所有制的形式,主要分合亩集体所有、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三种。这三种所有制所占的比例,在不同的合亩以至不同地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合亩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合亩数量较多,其他所有制占优势的合亩较少;反之,在另一些地区,几户伙有和一户所有制占优势的合亩却是多数,合亩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合亩则占少数。这种不同的情况,可以说是合亩向个体经济转化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反映。就整个合亩地区来看,以后一类地区占主导地位。
(3)在上述三种所有制中,一户所有属私有制性质是明确的,虽然这些私有的土地耕牛要交给合亩统一使用,不计报酬,私有权未能充分实现。至于几户伙有和合亩集体所有在所有权
和使用权方面都属于公有的范畴,但联系到合亩地区已存在私有财产的父系继承制度,以至土地占有关系的历史,私有和公有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转化就比较复杂。因为许多几户伙有和合亩集体所有的土地牛只,往往是他们祖先的私人所有物,通过父系继承关系而转归他们共同占有的,这就发生了从私有到公有的转化。
(4)合亩分为内部没有剥削关系和已经产生剥削关系两大类型,不同类型的合亩,反映了合亩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中也可以看到合亩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原始形态的合亩,可能是黎族早期社会的家族公社,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私有制的发生、发展,合亩内公有制残余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矛盾(私人占有和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合亩和个体家庭之间的矛盾(集体劳动与个别消费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私有制的因素不断冲击着原始公社制的藩篱。由于合亩公有的成分逐渐减少,合亩内土地耕牛的私人所有者要求充分实现其所有权,不愿把它们交给合亩共同使用,甚至发展到抽出自己份额的土地自耕(所谓“沃偏”)或出租,加上土地和耕牛的自由买卖,使主要的生产资料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平均分配的原则也开始引起了多数成员的不满,特别是龙仔、工仔和贫苦的亩众们更不堪地主恶霸式的亩头的压迫剥削。为了减少对合亩的依赖而积蓄私有财产的愿望,促使亩众付出更多的个体劳动,并积极关心家庭私有经济的发展。最后,作为合亩内分配和消费单位的小家庭,力求摆脱合亩的支配,把自己的家庭发展成为独立的、完全的生产单位。随着合亩内血缘联系逐渐削弱,地域或比邻关系逐渐增强,大合亩分成小合亩
的现象日益频繁,合亩的规模也越来越小,血缘关系也日渐缩小到最狭窄的范围,合亩成员除了更经常地“沃偏”之外,退亩单干也逐渐增加。这一种发展趋势深刻地反映出家的私有制对亩的公有制的矛盾,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形式。家的私有制侵蚀和动摇了合亩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共耕与平均分配,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为个体经济所代替,合亩瓦解为个体家庭。
(5)解放前的一段时期,合亩正处于自身矛盾发展而趋于瓦解的过程之中,因此合亩地区的经济结构就显得错综复杂。它既早已超越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合亩内私有制已占主导地位并出现了贫富分化和剥削关系,某些合亩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抗;另一方面又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家族公社的残余和家庭奴隶制的某些因素。
(6)直到解放前,在这一片拥有约一万三千多人的地区,合亩还没有为个体经济所代替,而且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残余,甚至在剥削关系十分严重突出的合亩内,诸如简单协作的集体劳动形式,集体生产出来的一部分粮食仍按户平均分配,血缘亲属之间处理“稻公稻母”、“聚餐粮”以及借贷互助等方面仍按传统习惯执行,山栏地仍归公有……等等带有公有制因素的东西仍然保留下来。这都足以说明合亩的瓦解过程是很缓慢的,之所以这样缓慢,显然是与合亩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力水平低下,传统习惯势力约束等等有关。同时,剥削阶级利用合亩作为剥削工具,某些传统习惯有利于维持亩众的最低生活而不致彻底破产,这些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是,合亩地区只是黎族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其他黎族地区特别是汉族地
区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包围,土地买卖、租佃、典当以及借贷、雇工等等经济活动都对合亩制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使合亩地区不可避免地要走其他黎族地区同样的道路。
峒的组织
合亩地区和其他黎族地区一样,直到解放前仍保留着一种具有特色的社会政治组织,黎语称为kom,原意是“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汉语音译为“弓”或“峒”。从峒的原来组织形式和职能来看,可能是黎族的一种古老的氏族部落组织,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而成为一种残存的躯壳,到后来更和封建地方政权的基层组织结合为一体了。
每个峒都有固定的地域,共同地域是峒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峒的地域一般以山岭、河流为界,并且立碑、砌石,有的则种树、栽竹、插木板、埋牛角等等作标志。因此,峒与峒之间有着清楚的界线,而且是自远古的时候就划定了的。峒的地域确定以后,不得随意侵犯,全峒的人都有保卫峒域的职责。倘若要到别峒种山栏、捕鱼、采藤、伐木、狩猎,都必须征得该峒峒头(vau kom)以及全体亩头的同意,并缴纳各种形式的租金或礼物。未经对方同意而逾越峒界开荒或捕鱼、伐术,就被视为对权利的严重侵犯,往往因此而酿成冲突和械斗。
峒有大峒、小峒之分,大峒之下包括几个小峒,各有自己的固定地域。如琼中县的红毛下峒包括毛贵、喃唠、毛兴、毛路、牙开等五个小峒,一个小峒之内往往有两个以上的自然村。峒的疆界原来是比较固定的,大峒辖下小峒的数目亦有一
定。但到了晚近的时候,峒已经和一般的行政区域一样,随政治上的需要有分有合,地缘因素已占主导的地位。如乐东县番阳峒原来包括绸怀、才花、毛农、毛或、雅曼五个小峒,后来将各小峒的疆界略为调整,增加了一个雅开峒,共辖六个小峒。
解放前,峒内各成员之间,经济的和地域的社会联系早已代替了原先的血缘纽带。但是血缘纽带是峒的组织基础这一特征,还可以看到它的痕迹。一个小峒原来可能居住着同一血缘集团的人,他们之间严格禁止通婚。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小峒都已混杂着不同血缘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峒之内开始存在两个以上的、互相通婚的血缘集团。此外,不同血缘的峒与峒之间的通婚是不受限制的。峒内各血缘集团还保留各自的公共墓地和共同的祖先崇拜。峒内许多与原住居民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来户,大多数是来投靠的龙仔、工仔,他们经过两三代之后,也有从龙公的合亩分离出来,单独组成一个合亩或一个村庄的。
凡同住一个峒内的人,都被认为峒的一个成员,他们都以世代祖先的传统习惯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如对峒的疆界的保卫责任;峒内成员间相互援助和保护的义务,特别受到外峒人欺侮时必须帮助复仇;共同负担械斗时向外请援兵的费用;以至村头、峒头的选举、罢免和继承等等,大家都按传统习惯行事。峒内的社会秩序主要靠这些习惯法来维持。
每一个村、峒都有一个至数个“村头”(vau fan)和“峒头”(vaukom),村头和峒头都是汉语的意译。在较早时代,一个村只有一个合亩的,即由亩头充任村头;一个村内有几个合亩的,由各个亩头中最长辈者任村头。除此之外,只要有人能
讲道理,能为村人调解纠纷,在办事时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有了威信,遇事便被邀请参加处理,也就被公认为村头了。这类村头多数是村内的老人,黎语称为“奥雅”(aoya),平时也为人们所尊重。在某些地区,也有由选举产生村头的。一峒之内,从几个村头中推选出辈分最高的任峒头。大峒的峒头又有称为峒长的,大多数由上级(清朝末年时称为总管)所委派。在血缘关系比较单一的村、峒,杂居其中的外来居民一般不能当村头和峒头;反之,当外来居民已占相当的比例时,也可以有自己的村头和峒头。
村头、峒头原来纯粹是村内、峒内的自然领袖,受到群众的尊敬。他们除了为群众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秩序,根据传统习惯处理峒内事务之外,没有什么带强制性的行政权力(甚至在发生械斗时,指挥者或当事人都不一定是村头或峒头),也没有向群众索取报酬。但是,由于合亩内部以及合亩之间的一切纠纷都由峒(通过峒长、峒头、村头、“奥雅”等人物)来解决,峒就成了一定地域内最高的社会政治组织。
峒与峒之间的劳动人民存在着友好往来的关系,最明显的是互通婚姻,结成亲戚;在生活上、生产上互相帮助是常有的事,如遇婚丧、盖房、农忙等,则互相表示关怀和帮助,甚至与别处发生纷争或械斗时,峒与峒之间还有互相支援的情况。
在统治阶级的挑唆下,峒与峒之间也会发生械斗的敌对关系。械斗的起因和目的大多与财产或债务有关系。获胜的一方往往恃势处罚负方巨额的财富(牛只、铜锣、光洋等)。每当发生械斗,一般双方都向别峒拜认龙公,请求出兵支援,龙公在接受所求时乘机索取大量的铜锣、牛只等作代价。龙公不论
直接派人参与械斗或者仅出面调解,都要大量的报酬。因为拜认龙公的关系,往往村与村、峒与峒的战争经常会酿成几个村、几个峒之间的战争。械斗的首领由肇事双方的当事人充任,他们不一定亲自参加战斗,可以出赏雇佣“兵头”带头打仗,完成战争任务后按约给予奖酬。由于挑起械斗的一般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是械斗的核心,由他们决定战争或和解。这些人通过挑拨械斗发财致富,广大劳动人民由于负担沉重的械斗费用而贫困破产。
据毛道乡和毛贵乡的调查,解放前在某些械斗过程中,有这样的情况:械斗之前以猪颈或“鸡毛信”(用一条细小的白藤打一个大圈三个小圈插上一条鸡毛)作为“战争通牒”送给对方,表示要索取指定数量的罚款。若对方拒绝付出罚款,即将通牒退回,从此双方认为进入械斗状态。送通牒由对方嫁来的妇女或请来的外峒人为使者。进攻前必须举行“鸡卜”以占吉凶。对待俘虏一般不加杀害,以便和解后与对方交换或索取赎金,赎金多少按俘虏身分而有所不同。械斗的和解一般请有权有势的峒长、峒头主持,举行“蕊岔”仪式,并由双方当事人杀牛设宴,在宴会上峒长、峒头与械斗双方砍箭为约,达成和解。
村头、峒头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峒这一黎族社会原有的自然组织的情况。但随着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扩展到合亩地区,从此峒的性质以至村头、峒头等的地位和作用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反动统治阶级大力推行反动的“以夷制夷”的政策,以各种官职官衔收买拉拢当地黎族社会内部原有的自然领袖,通过他们对合亩地区的黎族人民进行压迫和统治。特别自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清朝在海南岛设置“抚黎局”以后,合亩地区内也设有总管、峒长、哨官、头家等职衔(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又有团董,乡、保、甲长的名称),委派亩头(龙公)、村头、峒头等上层人物充当。如当时整个合亩地区都受红毛峒(现今琼中县红毛公社)总管王政和所管辖,由他委任峒长(管一大峒,相当于后来团董或乡长所管辖的范围)、哨官(管一小峒,也有管一大峒的)、头家(管一个村或一个小峒)。这些有了世袭职衔的亩头、村头、峒头等等,不仅在政治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在基层的代理人,而且在经济地位上大多数是剥削阶级。他们凭借政治特权侵占峒内的公共土地、山林和河流,勾结反动官府向峒内群众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并从中贪污中饱;征派繁重的劳役,使群众疲于奔命。他们经常在处理民、刑案件纠纷中,肆意敲榨勒索。更严重的是制造纠纷,挑拨械斗,从中渔利;或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害善良,横加重罚,许多地主恶霸就是通过这些手段,掠取了农民大量的土地和牛只。至此,原来的自然领袖已经逐步演变为世袭的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统治人物。至于峒的组织,则已丧失了它原来的社会意义,只是被利用为封建王朝以至国民党反动派的基层政权组织的补充和附属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