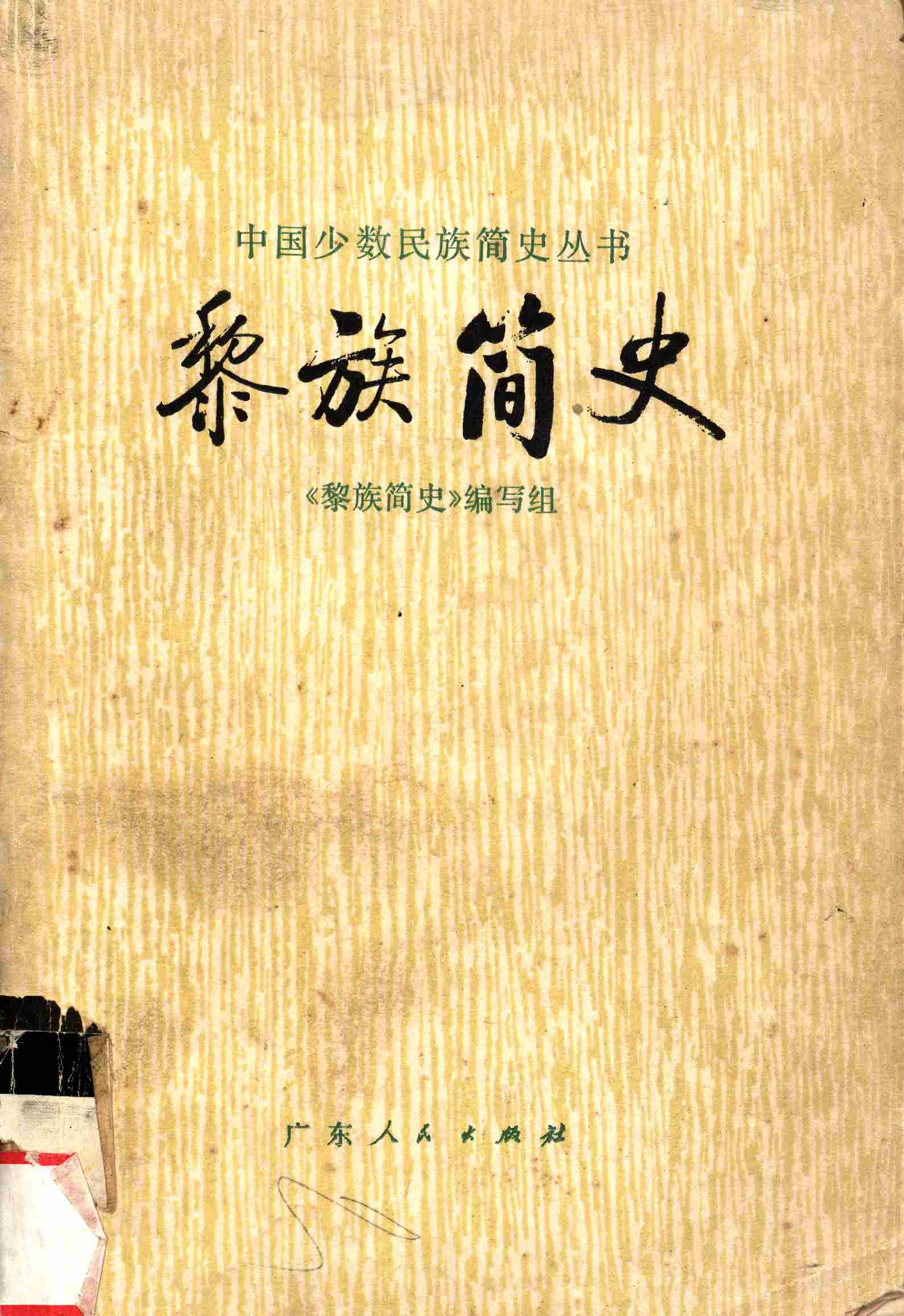内容
第一节 中原封建势力进入海南岛
我国史籍最早有关海南岛的记载,以《汉书·地理志》最为详细,书内记述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在岛上设立珠崖、儋耳两郡,“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并对岛上的物产和土著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作了一般的描述,但对当时汉人在海南岛的情况则没有提及。王佐(明朝海南岛临高县人)在《琼台外纪》中曾明确指出:“武帝置郡之初,已有(善人)三万之数”。这里所谓“善人”,“此皆远近商贾兴贩货利有积业者,及土著受井受廛者”①,由此可见当时岛上的汉人已有一定的数量。其实早在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经略岭南,设立桂林、南海、象三郡之后,就迁徙大批中原的汉人进入各郡,与越人杂居。当时作为象郡的“外徼”的海南岛虽然尚未设立郡县的统治,但从一些事实来看,已有汉人进入海南岛居住了①。到了建立郡县之后,更多的汉人便陆续到达岛上的沿海地区,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黎族的远古祖先在内)进行通商贸易,因之当时海南岛出产的奇珍异宝如珠玑、玳瑁、犀角、广幅布和各种热带果品等已为中原人士所熟知,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掠夺的对象。随着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黎族内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加速了黎族原始社会的解体,一方面又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出现。在郡县建立的过程中,由于使用了武力,使劳动人民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在客观上对于巩固祖国的统一,密切海南岛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黎汉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黎族社会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两汉伏波将军开琼”的各种传说和有关的名胜古迹,一直受到人们的传颂②。
郡县制的建立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个进步,但由于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给黎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引起了黎族人民多次的强烈反抗。据《汉书·贾捐之传》载,从设立珠崖、儋耳郡之后,到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八六年)的二十多年间,大小的反抗斗争有六次之多,以后在神爵三年(公元前五九年)、甘露元年(公元前五三年)、初元元年(公元前四八年)都爆发过反抗斗争。在汉武帝末年(公元前八七年),黎族人民在反抗珠崖太守孙幸强征广幅布时,曾攻破郡城,杀了孙幸①。这些历史现象,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着的复杂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以后封建王朝在海南岛的设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时并,有时废,管辖的地方有时扩大,有时缩小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并没有妨碍黎汉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汉族人民仍然不断迁移到岛上来,汉族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继续在黎族中传播,黎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不断受到汉族的影响。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在汉代我国南方的部分地区,包括海南岛在内,过去是“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自从王莽执政(九至二三年)以后,从中原迁徙了一部分居民“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到了东汉建武十八年(四二年),伏波将军马援曾“往来南海,抚定珠崖,调立城郭,置井邑”③,这是中央封建政权比较认真经营海南岛的开始。稍后,在明帝永平年间(五八至七五年)曾任儋耳太守的僮尹,“还至珠崖,戒勅官吏毋贪珍赂,劝谕其民毋镂面颊,以自别于峒俚,雕题之习,自是日变”④。这些措施对于黎族社会的发展,以至风俗习惯的变革,都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至于从汉代至梁朝以前黎族社会封建化的程度如何,目前尚缺乏充分的史料加以说明,但从当时移居到海南岛的汉族人口还占少数,中央封建集权的措施在岛上的推行也还受到很大的限制等情况来看,这时除了沿海(主要是岛的北部)极小部分地区的黎族由于与汉族接触较早,受到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较深,发展较快,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之外,就当时绝大部分黎族地区的社会情况来说,仍相当落后,封建因素还是很微小的。如三国时吴国孙权曾策划远征海南岛,就受到他的大臣全琮和陆逊的劝谏,认为该地“隔绝瘴海,水土气毒”,而且会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①等等可以见其一二。最后孙权不接纳大臣的劝谏,还是派聂友和陆凯进兵海南岛,结果,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虽然人民的反抗被镇压下去了,但因“士众疾疫者十有八九”,不久就被迫撤军②,只得在现今的雷州半岛上另立行政机构珠崖郡和朱卢、珠官两县,对海南岛只是“遥领”而已。
从南朝的梁朝到唐代(五四〇至九〇五年)三百六十多年间,黎族社会的封建因素逐渐有所增长。梁朝于大同中(五四〇至五四一年)在废儋耳郡的地方设置崖州,这是因为当时该地的俚僚(包括黎族的古代祖先)一千多峒“归附”冼夫人,由她“请命于朝”而置崖州的①。冼夫人“多筹略,能行军用师,劝亲族为善”,“政令有序”,是六世纪我国南方越族的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②。当时广东的西南部地区、雷州半岛和海南岛都在她的统领之下。隋初,冼夫人因率领所属十多个州的地方归附隋朝,又以“抚慰诸俚僚”、“和辑百越”有功,隋文帝赐给她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并封赠她的儿子冯仆为崖州总管③。由于冼夫人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事业,不仅密切了中原地区与海南岛的关系,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同时对于促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她的业绩一直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怀念④。
到了唐代,由于当时国际贸易的频繁,使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与南海海上交通中点的海南岛,开始受到中原地区越来越大的注意,岛上出产的珍珠、玳瑁、香料、梹榔、荔枝、龙眼等珍贵物产,有许多一向要从南海诸国输入国内的,这时也由岛上以“土贡”的方式或由商人贩运到大陆地区⑤,使海南岛与大陆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了。唐代海南岛由于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加而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据《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十三》的记载,开元年间(七一三至七四一年)海南全岛五个州(琼、崖、儋、振、万安)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五户①,其中崖州(包括现今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就有六千六百四十六户,比当时大陆地区开发较早的雷州(四千三百户)、廉州(三千零十二户)的人口还要多。当时岛上汉族居民的分布,也从原来岛北沿海开发较早烟瘴较少的地区,逐步向比较偏远、开发较迟而瘴疠较严重的岛南、岛东南地区扩展。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多与分布地区的日益扩展,在沿海黎汉族杂居的地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有较显著的提高。天宝年间(七四二至七五六年),当鉴真大师漂流到岛南的振州(今崖县)时,就看到当地已经是“一年养蚕八次,收稻两次,十月种田,正月收粟”②了。当时山区出产的高良羌、五色藤、盘班布、金糖香、益智子……等土特产,也有不少作为“贡品”或商品而输入中原地区,在沿海一带还出现了作为经纪的商人阶层③。德宗年间(七八〇至八〇五年),琼山郡守韦公干家里从事奴役性手工业劳动的奴仆已能“织花缣文纱”,制角器,熔锻金银,用珍木造杂具,又驱使木工采伐乌文、呿〓等珍贵木材,造大船两只,饰以金银,以健卒为船员,远航广州④。鉴真在振州和崖州滞留期间,就曾主持重修当地的大云寺和开元寺,可见当时该地的建筑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⑤。至于李德裕诗中的“五月畲田收火米”①,说明在唐代后期(八四八年间),“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在崖州地区还相当普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岛上沿海黎汉族杂居地区的阶级分化也日益明显,出现了“以富为雄,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的局面②,还出现了一些独霸一方的豪强官吏。如前述的琼山郡守韦公干,万安州的大首领冯若芳(两人均非黎族),“掠人为奴婢”,强迫这些奴婢从事奴役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竭夷僚之膏血以自肥”,从中剥削掠夺而成巨富③。冯若芳家里有客来时,一次就燃烧从外国输入的珍贵乳香百余斤,他的屋后苏木(一种名贵染料)堆积如山;“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④鉴真为了在崖州重建开元寺,振州别驾冯崇债“即遣诸奴各令进一椽”,三日之内便把强征的巨木收集完毕⑤。振州的富豪陈武振,“家累万金,犀(角)象(牙)玳瑁仓库数百”,连当时的招讨使也要去巴结他⑥。上述这些豪富们的奴婢,有些是被俘虏的波斯船上的船员,但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各族劳动人民⑦。同时,黎族内部的上层首领也已成为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经常通过战争和掠夺以加强对黎族人民的压榨,使黎族人民痛苦不堪。《新唐书》记载的“中宗时(七〇五至七〇九年),(宋)庆礼为岭南采访使,时崖、振五州首领更相掠,民苦于兵”⑧,即是这一情况的纪实。
唐代海南岛沿海地区封建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和当时中央封建王朝对这些地方的积极经营有关。自贞元五年(七八九年)岭南节度使李复平定海南各种纷乱,“讨平峒蛮”,“恢复”琼州之后,全岛共设立了五州二十二县①,为以后的行政建制奠定了基础。而且当时设立的有些县,如琼山、文昌、澄迈、临高、陵水等,有不少的县名仍沿用至今。至于海南岛后来简称“琼崖”,也是自这时前后设置了琼州和崖州而来的。当时县的设置已不限于原来开发较早的岛北沿海一带,而是扩大到岛南和岛东南沿海,使环岛沿海地区几乎全部纳入了州县的范围。如一向气候卑湿的岛东南的万安州(今万宁县),是在唐高宗龙朔二年(六六二年)才设置的②。从此,汉族和黎族的分布状况已不再是“汉在北,黎在南”,而是“汉在外围,黎在腹地”了(这种状况基本上一直持续到解放前)。但是,州县设立之后,苦于赋税、贡品负担的繁重,以及大小官吏的苛索欺凌,在加剧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的同时,也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唐朝中央政府在海南岛设治的不少困难。早在乾封初年(六六六至六六七年)黎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一次反抗斗争,连琼州都被攻陷了③。懿宗咸通五年(八六四年),在镇压以黎族蒋璘为首的反抗斗争之后,刚设立起来的忠州(今定安县西南部)在兵退之后也被迫撤消④。特别是县的设置,有许多是时立时废,变动很大,建立在山区的,如儋州的洛场县,振州的落屯县,更是如同虚设。这反映出中央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除沿海黎汉杂居区外,直到唐代还未十分稳定,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对黎族社会的影响仍未普遍和深入,尤其是黎族聚居的广大山区所受的影响更少,如当时振州的土著居民还完整地保持着文身、凿齿和吹鼻箫等风俗。虽然到了唐代后期宪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年),有“琼管儋、崖、振、万安等州峒俚来归,进五州六十二峒归降图”①,但受统治的黎族仍占少数。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海南岛的开发有了一定的进展,这从文献上有关海南岛的记载逐渐增多得到反映。如后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晋朝王范的《交广春秋》,都有关于朱崖、儋耳两郡风俗的记载。又晋朝盖泓所写的《朱崖传》一卷,是海南岛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唐德宗时(七八〇至八〇五年)杜佑所撰的《通典》,也有关于海南岛的记述。唐昭宗时(八八九至九〇四年)任广州司马的刘恂所写的《岭表录异》,不仅对海南岛的物产风俗有所描述,而且使用了“夷黎”这一专称来称呼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些情况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海南岛以及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了解逐步加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但尽管如此,直到唐代,海南岛开发的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而且仍远比中原地区落后。当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海南岛仍然是一处“化外之地,瘴疠之区”。封建王朝开始把它作为流放贬谪官员的地方,而被流贬的官吏更视海南岛为畏途,“一经南贬,便同死别”。唐大中二年(八四八年)被流贬为崖州司户的著名政治家、诗①参看嘉靖《广东通志》所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岭南节度使赵昌的事迹。
人李德裕,在诗中曾写道:“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①这些情况也反映了唐代海南岛的沿海地区封建化的区域虽然扩大了,但对整个黎族社会来说,原来的落后状况和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通向封建社会的道路上仍处于十分缓慢的进程中。
第二节 十世纪至十四世纪封建影响的加深
五代(九〇五至九五九年)以后,从宋到元(九六〇至一三六五年),特别是宋代,无论从海南岛开发的程度和黎族社会的封建化来说,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五代时,由于中原战乱频仍,而长江以南地区尚能保持比较安定的局面,大批汉族人口纷纷南移,其中不少迁移到海南岛。据估计,南宋(一一二七至一二七九年)时,移居到海南岛的汉族已从唐代的七万多人增至十万人②。正如明代丘浚的《南溟奇甸赋》所提到的:“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托处。”③当时迁到岛上来的,不仅有商人和官吏,也有戍守边疆的士兵,以及大批的汉族劳动人民,他们与黎族人民一起辛勤垦殖,大大促进了海南岛经济的开发与黎族社会的发展,迅速改变了从汉至唐近千年间开发缓慢的局面。这种情况从宋代大诗人苏轼的亲身见闻中可以得到说明。他在《伏波庙记》中写道:“自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班班然矣。”①
在经济方面,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如农业生产就有显著的发展。宋代从占城传入的稻种,能夏种秋收,增加了产量②,而当地的苎麻,一年可收四次③。苏东坡和他的儿子苏过在海南谪居时咏当地农事活动的诗常有“钽”(锄)、“耜”(起土用的农具)、“耰”(用以平田碎块的农具)、“耦”(两人并耕)、“耕牛”、“良田”、“霜降稻实”等词④,可见北宋后期儋州一带农业生产的工具和技术(如牛耕等),已与中原地区习见的无异。水利的修建也被注意,如开宝八年(九七五年)琼州地方开修渠堰,引峻灵塘水灌溉水田二百多顷⑤。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年),琼州帅守韩璧“教(民)以耕耨灌溉之法”⑥。当时沿海地区与汉族接壤和杂居的黎族的生产情况,大致上和汉族差不多。根据文献记载,宋代隶属州县辖下的黎族人民也和当地汉族一样耕作稻田。如朱熹在《琼州知乐亭记》中提到,淳熙年间(一一七四至一一八九年)“化外黎人闻风感慕,至有愿得供田税比省民者”。《宋史·蛮夷传》也有“乾道二年(一一六六年),慰抚黎人,民无产者,官给田以耕”的记载。至于当时
黎族人民种植的各种薯类,不仅品质优良,“芋魁大盈尺”①,而且成为当地的主要食粮,“海南以薯为粮,几米之十六”②,“薯芋人人送,囷庖日日丰”⑧。此外,采集香料和其他土特产也成为黎族人民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所种秔稌不足于食,故俗以贸香为业”④。黎峒出产的沉香、蓬莱香笺香、槟榔、椰子、吉贝(棉花)、翠羽、黄腊、赤白藤和青桂、花梨等珍贵木材,通过汉族商人贩运至大陆地区销售⑤。
在手工业方面,黎族妇女“工纺织,得中土绮彩拆取色丝,加木棉挑织为单幕;又纯织木棉、吉贝为布。”⑥黎族妇女所织绣的“黎锦”、“黎单”、“黎幕”,“五色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青红间道,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⑦还有被后人誉之为“东粤棉布之最美者”的“白〓”⑧,早在北宋时就已在黎族聚居区出现。可见宋代黎族人民在棉纺织技术和工艺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我国的纺织工艺史增添了光彩。当时这些绚丽多彩、美观实用的棉纺织品,曾远销至广西桂林一带。同时黎族人民用特殊方法酿造的名酒(银皮酒),也深为苏东坡所喜爱⑨。
宋代由于国内市场对香料和产于热带地区的土特产以及奇珍异物的大量需要,刺激了岛上黎、汉族之间频繁的贸易活动。特别是槟榔、吉贝、香料的贸易在当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海南土产……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州)商兴(化)贩大率仰此”①。“槟榔生海南黎峒……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②,“(琼州)非槟榔之利,不能为此一州也”③。对当时贸易的重要性,苏过(苏轼的儿子,与父亲同往海南)在他的《论海南黎事书》④中就曾说过:“濒海郡县所以能鸠民置吏,养兵聚财者,恃商人耳”。如果“绝黎人之欢,商人不来”,贸易一旦断绝,则官府便会遭到“关市之征,岁入不足”,“兵吏廪赐无所从出”,“衣食不足,饥寒从之”等三大困难。而“黎人处不毛之地,盐酪谷帛斤斧器用,悉资之华人,特以沉香、吉贝易之耳”。当时邻近汉区的黎族人民每逢墟日即结队到州县城内的市集进行交易,以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土特产品与汉商交换铁器、瓦器、牛畜、鱼盐、酒米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交易以物物交换为主,如一担香料可以换回一头牛⑤。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黎族社会的封建化程度比过去有所加深,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和复杂。一些富有的上层“首领”还养有家奴。如北宋至和初年(一〇五四至一〇五五年)琼州有一个名叫符护的“首领”,“边吏尝获其奴婢十人”⑥。
南宋淳熙年间(一一七四至一一八九年)成为琼州“三十六峒统领”的黎族妇女王二娘,她的祖先早在北宋皇祐年间(一〇四九至一〇五三年)就接受封建王朝的“封赐”,她自己不仅世袭“宜人”的封号,并且掌握实际的统治权力,封建王朝凡有命令都通过她来执行①。这些经过“加官晋爵”的黎族统治人物的出现,标志着黎族社会的封建化到了十二世纪后期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在沿海黎、汉族杂居的地区,黎族劳动人民的土地大批被封建官府、本民族上层“首领”和汉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霸占了去②。一些汉族奸商还乘机“欺其愚而夺其财”,甚至“市黎人物而不与直”③。至于当时封建统治的黑暗,如“法令之烦苛,调敛之无时,官吏之贪求”,“贪胥猾商肆其奸”④,给黎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加深了黎族社会的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
宋、元两代,随着沿海地区黎族社会封建化的加深,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也日益加强。如北宋崇宁(一一〇二至一一〇六年)中,经略广西安抚使王祖道“抚定”黎人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并开通道路一千二百余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其酋亦有补官”⑤。宋代以前的文献中,有关封建王朝“治黎”政策的记载不多,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宋以前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仍然是相当薄弱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对黎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的开发,还未引起封建王朝足够的注意。到了宋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封建王朝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开始着意寻求一种比较能够“长治久安”的统治黎族的政策。苏过在他的《论海南黎事书》中①,就曾提出一些比较系统和具体的“治黎”措施,如政治上参照统治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办法,对于黎族的上层“首领”以官爵利禄进行收买,实施“羁縻政策”,通过他们来统治黎族人民,所谓“籍其众所畏服者请于朝,假以一命,而岁与其禄”,于是“今朱崖屯师千人,岁不下万缗,若取十一以为黎人之禄,可以罢千师之屯矣”。军事上则利用当地的地主武装以加强镇压,所谓“戍卒可省,民兵可用”,因为“(地主们)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而又习其山川险阻,耐其风土瘴疠,吏若拊循其民,岁有以赏之,则吾藩篱不可窥矣”。最后则“许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内属,法令徭赋,一均吾民”,实行强迫同化。苏过提出的以羁縻笼络为主、武装镇压为辅的“治黎”政策,一直为宋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奉行。宋代受到封建王朝“封爵袭职”的黎族上层“首领”(当时称为“峒首”),最早见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一〇六八至一〇七七年)的记载②。稍后,在宣和年间(一一一九至一一二五年),还有符元享等黎族峒首因接受儋州人陈大功的“招抚”,而被封为“承信郎”,“其子孙各以官名承袭”③。但此类的记载更多的则是在南宋期间的事。除上述的王二娘⑧道光《琼州府志》。
外,还有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年)乐会县的王日存、王承福、陈颜等也因“招降”有功而被封为“承节郎”等职①。宋代除在黎族地区的险隘处设立宝西、西峰、定南、延德等寨派军驻守外②,还征集地方武装以加强对黎族人民的镇压。当时这类地方武装称为乡军、土丁(王安石实行保甲制则称民兵),招募的对象有当地“附籍”的汉族,叫做“寨丁”,还有黎族,即所谓“羁縻州之民”,叫做“峒丁”③。采取正规军与地方地主武装相结合,以及驱使当地的黎、汉族人民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成为宋代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加强对黎族人民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
到了元代(一二八〇至一三六八年),封建统治者一面对黎族人民实行残暴的武力镇压,同时任用“归降”的黎族上层“首领”,封以官爵,付以实权(这与宋代仅给予封爵不同),世袭其职。在元朝九十多年的统治中,大举“征黎”不下十次,武装镇压的规模更是前所未见。如元初至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一二九一至一二九四年)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元军兵马深入黎峒,连偏僻的五指山中心地区都不能幸免,计有琼州清水峒以下的十九峒被“剿平”,“归降”的峒六百二十六,户口二万三千八百二十七,并“招抚”户口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七④。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元朝统治者在海南岛专门设立了“黎兵万户府”,下辖十三翼千户所,分布在全岛各地,每千户④参见《琼州府志》、《儋县志》及邢梦璜的《至元癸巳平黎碑记》。其中提到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春刻石五指山、黎婺岭而还。该石刻现存乐东县尖峰公社。
所又辖百户所八处;自万户以下都任用黎族“峒首”世袭其职,统率属下的“黎兵”,兼管地方上的军事和民政,同时还强占黎族人民的土地设立“屯田”,称为“海南黎蛮屯田万户府”。据《元史》记载,当时琼州路的“屯田”就有二百九十二顷九十八亩。元朝统治者不仅驱使“黎兵”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还征调他们参加远征①。而不少黎族上层“首领”也因参与远征“有功”,被授以更高的官职,得到重用。如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南宁军(统辖宜伦、昌化、感恩三县)的黎族上层“首领”谢有奎由于招降“三十峒首与三千户同时内附”,并率领“黎兵”远征“有功”,而被“授以沿海军民总管,佩金符”②。
宋元两代对黎族施行的统治政策,加速了黎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加深了各方面的矛盾,引起了黎族人民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据文献记载,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年)到元末(一三六八年)近三百年内,黎族农民起义达十八次之多,起义地点不仅遍及封建化较早的岛北、岛东和岛西的琼山、临高、澄迈、文昌、乐会、昌化等县,而且还发展到开发较迟的岛东南的万安军和吉阳军一带。在这些起义中,以南宋嘉定至绍定年间(一二〇八至一二三三年)琼山王居起领导的起义与宋末咸淳年间(一二六五至一二七四年)吉阳军黎族人民响应汉族陈公发、陈明甫的起义,元代至顺元年到元统三年(一三三〇至一三三五年)澄迈县和定安县王马、王六具、王官福等人领导的十九峒黎族起义规模较大①。王居起曾自号“南王”,他率领的义军猛攻临高、澄迈和文昌等地的封建统治据点,声势十分浩大,使“琼州城门尽闭”,离城数十里外尽为义军所控制。王马等人领导的元代后期的黎族农民大起义,一次出动的武装群众达数万人之多,连续攻陷元朝在海南岛的主要军事政治据点南宁军、万安军、吉阳军和会同、乐会、文昌、南建州(定安县)等地,“东西诸黎皆应,仅存琼州”,使大半个海南岛燃遍了起义斗争的烈火。元朝统治者最后调动了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四省的兵力,历时四、五年才把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但“黎乱(反抗斗争)终元之世”不绝②,大大动摇了元朝在海南岛的统治地位。宋元两代的黎族农民起义,虽然大多数表现为民族对抗的形式,但其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很明显的。许多黎族的“首领”充当封建王朝镇压黎族人民起义的帮凶,如前述的宋代王二娘的祖先以及王日存、王承福等,就是因“招降有功”而得到“封官受爵”的。元代由黎族“首领”充当的万户、千户、百户,更是经常率领属下的“黎兵”为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效力,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特权,后来还演变成各自拥兵为雄,僭称官职,互相撕杀,造成了元末各首领之间“狗咬狗”的混乱局面③。至于黎汉族劳动人民之间,在共同的阶级命运的基础上,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则多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的。如宋代吉阳军以陈公发、陈明甫为领导的黎汉族人民联合起义,就是其中较显著的一例。
宋代是黎汉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和团结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时期。自五代以来,汉族人民迁住海南岛的日多,黎汉两族人民交错杂居的情况日益普遍。苏轼在《书上元夜游》中所写的“(儋州)历小巷,民夷杂糅”①。《诸蕃志》记载的“(万安军)民与黎蛋杂居”,“(吉阳军)与黎僚错杂”②,都是这一情况的纪实。苏轼当时居住在临近海边的儋州城,但到了晚上就能听到附近黎族夜猎的狗吠声③。黎汉族人民一向是友好相处,团结互助的。苏轼父子谪居儋州时,黎族人民把自己酿好的酒,腌好的肉酸(当时称为“蛙蛤蚁酱”),种得的薯芋和打猎得来的兽肉,都馈赠给他俩品尝④。在贸易方面则互通有无,发展了生产和改善了生活。当时黎族人民对于有信用的汉族商人十分欢迎,“商人有信,则相与如至亲……岁望其一来,不来,则数数念之”⑤。这种情况不仅在沿海平原地区是如此,在黎族聚居的山区,也有不少汉人迁入,所谓“湖广福建之奸民亡命杂焉”⑥。这些所谓“奸民亡命”者,实际上不少是不堪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指
出的:“琼崖儋万,民既贫苦,仍出役钱,其间大半贫困,不曾输纳,甚者逃入黎峒”①;《诸蕃志》也提到:“省民之负罪者,多逋逃归之(黎峒)”。此外,还有商人,“闽商值风飘荡,貲货陷没,多入黎地”,也有戍守的寨丁、屯兵及其家属留居下来的。他们进入黎区后,与黎族人民融洽地相处,有的定居后“耕种不归”,后来逐渐与黎族自然同化。在沿海和靠近州县城的地方,不少黎族人民已经“半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其为黎)焉”②。据说当时在沿海州县许多姓黎的汉人,都是黎族的后代③。可见黎汉族间自然同化的现象,在历史上早就存在了。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宋末元初杰出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勤学苦练纺织崖州被的方法,创造出当时一套最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我国棉纺织业发展的动人事迹④。黄道婆出生于南宋末年江苏松江府乌泥泾(在上海旧城西南九里的地方,现属上海县龙华公社东湾大队)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她八岁当童养媳,因不堪封建家庭的虐待,被迫离乡别井,乘搭航行于闽、广间的海船,流落到崖州(今崖县)。当时崖州是个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黎族人民十分同情黄道婆的悲惨遭遇,热情地关心和款待她,并向她传授纺织崖州被的技术。她在崖州居住了四十年,到元朝成宗元贞年间(一二九五至一二九六年)返回故乡。黄道婆回到乌泥泾后,把从黎族妇女学来的一套棉纺织工具和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劳动妇女,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对去籽、弹花、纺线和织布的工具和工艺进行了改革和创造,成功地创制出轧棉用的手摇搞车,弹棉用的粗弦大弓,以及三〓脚踏纺车(我国古代的手摇单〓纺车只能纺一根纱,新式的纺车能一手同时纺三根纱,功效提高两三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棉工具)。黄道婆把黎族妇女擅长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工艺,结合祖国传统的优良丝织技术,运用到棉织品上去,织成的褥、带、帨(手巾),有花草、鸟兽、折枝、团凤、棋局等图案花纹,光彩美丽,栩栩如生,灿然如画,甚得当时人们的喜爱,一时松江地区出产的棉织品竟行销全国,过去“民食不给”的乌泥泾,一变成为“家既就殷”的富庶地方。黄道婆对于我国棉纺织技术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是黎汉两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黎汉两族人民兄弟般的亲密友谊的体现。
和唐朝时一样,宋王朝继续把海南岛作为流放官吏的一个重要地方。继唐代的李德裕等人之后,宋代又有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如苏轼、赵鼎、丁谓、胡铨、李光等,先后被贬到海南岛。唐宋两代被贬的官吏在居留期间,曾经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对当地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起着促进的作用。如唐代贞观年间(六二七至六四九年)被贬为吉安(今昌江县境)丞的王义方,曾“开陈经书”,教育黎族子弟,“人人悦服”①。李德裕、苏轼等人在当地“教民读书著文”,或“讲学明道,教化日兴”。胡铨在崖州时,“日以训传经书为事,黎酋闻之,遣子入学”。由于他们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欢迎。苏轼在谪居儋州的三年多时间中,与当地的黎族人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关心黎族人民的生产,因此有《劝农诗》之作;他对黎族人民生活的贫困,也寄予深切的同情,曾写了谴责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黎族人民的诗篇。由于他与热情好客的黎族人民有了深厚的感情,当他被赦回大陆时,竟写出了“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①的诗句,充分流露出诗人对黎族人民依依不舍的怀念之情。
与此同时,汉族封建文化在海南岛也开创出一个新局面。宋仁宗庆历四年(一〇四四年)琼州府儒学首先设立,后来到了北宋末南宋初期,琼山、澄迈、文昌、万州、陵水、崖州、感恩各州县的儒学也相继成立。大观三年(一一〇九年)并出现了海南岛第一个进士(儋州的符确)②。当时为了方便“黎人遣子弟入学”,还在琼州郡学中特别设立了“新学”③。元代则在各千户所设立“黎学”(又称“寨学”)。这些措施虽然都是为了在黎族中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后代,但对于黎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客观上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括上述的情况来看,从十至十四世纪中叶(五代至元)这四百多年间,黎族社会无论哪一方面都比唐代和唐代以前有着明显的变化和发展,但从当时整个海南岛的经济开发程度来看,仍然比中原地区甚至比两广大陆地区落后。宋代的海南岛,仍然被人视为“九死南荒”的“蛮烟之地”。同时地区性发展不平衡仍相当显著,岛东南和岛南这些开发较迟、黎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比岛北、岛东北、岛西这些开发较早、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更落后些。苏轼在《夜卧濯足》诗中描写当时万安军(今万宁县)的情况是:“万安市无井,斗水宽百忧。天低瘴云重,地薄海气浮”①。《桂海虞衡志》则提到:“其余三郡(指昌化、万安、吉阳),强名小垒,实不及江浙间一村落”。丁谓在《到崖州见市井萧条赋诗》中,也慨叹“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二百家。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②。周辉在《清波杂志》中提到当时的吉阳军(今崖县):“抵郡,止茅茨,散处数十家。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峒贸易,顷刻即散。”至于五指山中心地区,苏过形容其为“豺狼魑魅之所凭,水土疾疫之为厉”③,依然是“外人不复有迹之处”。
在这一时期里,黎族内部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比宋代以前更为显著。文献上开始出现“生黎”、“熟黎”的名称,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生黎”的名称最早见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九七六至九八三年)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其后,在南宋淳熙年间(一一七四至一一八九年)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首先应用了“熟黎”这一名称。以后直到清代的文献一直袭用这些名称。所谓“生黎”和“熟黎”,不过是封建统
治阶级对黎族的一种侮辱性的称呼,其划分的界限主要是看他们是否归属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定。但是,这种称呼上的差别,正好反映出了黎族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在宋元时期,黎族内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长期与汉族人民交错杂居的黎族(一般分布在沿海平原和河口地区,特别是靠近州县治所的地方,也有少数居住在城镇上),他们受州县的直接统治,早已编入户册,纳粮当差,和当地的汉族没有什么差别,不少已经逐渐与汉族自然同化而被视为“黎裔汉人”。他们的经济形态和当地的汉族一样,是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
(二)被封建统治者称为“熟黎”的黎族,他们居住在州县统治范围(即所谓“耕种省地”)之内,但离州县治所较远,所谓“熟黎所居已深阻”①,如北宋大观元年(一一〇七年)曾在那里设立过镇州(今东方县东方公社)的就是这类所谓“熟黎”地区②。他们也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渔猎和采集土特产品还占相当的比重(苏过在他的《夜猎行》一诗中,对当时儋州的黎人的狩猎活动有生动的描述),并且通过汉族商人与汉族地区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他们已经普遍使用从汉区输入的铁制生产工具,但生产技术水平则较汉族地区落后。原来的“土地峒内公有”的制度已被破坏,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已经出现,但土地大多为汉族地主、奸商、高利贷者和黎族内部的上层“首领”和富户所侵占①,阶级对立已相当明显。封建王朝通过“峒”的制度和黎族的上层“首领”进行统治。黎族人民受到汉族封建统治者和本民族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负担着繁重的赋税和官吏、豪富们的抽剥苛索②,生活极为困苦,反抗斗争也特别激烈,宋、元两代的黎族农民起义,多是在这类地区爆发。这部分所谓“熟黎”的黎族由于不同地区受到封建王朝统治的时间长短不一,统治势力强弱不等,以及接受汉族经济文化影响深浅不同,表现在封建化程度上也不完全一致,有些地区还继续蓄养家奴③;但从总的来说,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当地的汉族已有着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基本上也属于封建地主经济的范畴,只是在封建化的程度上有着某些差别而已。
(三)居住在距离汉族地区更远的山区中的黎族,当时被封建统治者称为“生黎”,他们不受州县统治,不供赋役,无论在生产和生活上都比上述两类黎族落后。他们也从事农业生产,但捕鱼、狩猎、采集等活动仍占重要的地位,贸易以物物交换为主,基本上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生活上保留原始的东西较多。如普遍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早稻、薯类和其他粮食作物,生产关系方面仍以公有制为主,所谓“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④。各峒有峒首为领导。在生活上,则“弓刀未尝离手,弓以竹为弦”,“巢居洞深,绩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议婚姻折箭为质,聚会椎鼓歌舞,死必杀牛以祭,祭神以牛犬鸡彘”①;氏族血亲复仇的风俗还相当普遍,“其亲人为人所杀,后见仇家人及其峒中种类,即擒取而械之”②。这部分黎族保留原始的东西还很多,从总的情况来看,还处在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中。
上述三种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黎族,他们所占的人口和地区比例的大小,目前还缺乏充分的史料加以具体的说明。但从当时整个海南岛的开发程度来看,属于州县统治范围内的地区和人口还是不多的,正如苏轼所说的“四州环一岛,百峒蟠其中”③,范成大提到的“四郡各占岛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得,亦无路可通”④,都说明了宋代汉族居住的和黎汉杂居的各州县境,仅占环岛沿海地带的一隅而已,其余不入州县统治范围的广大山区则是“峒落日以繁滋,不知其几千百也”⑤。特别是在岛的南部、东南部和腹心地区更是如此,如当时岛南的吉阳军(今崖县境)“距城五七里许”,不受州县统治的黎族就“不啻数百峒之多”⑥。由此可以推断在这一时期里,属于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这一经济类型的黎族,在分布地区和人口方面可能仍占多数。
我国史籍最早有关海南岛的记载,以《汉书·地理志》最为详细,书内记述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在岛上设立珠崖、儋耳两郡,“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并对岛上的物产和土著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作了一般的描述,但对当时汉人在海南岛的情况则没有提及。王佐(明朝海南岛临高县人)在《琼台外纪》中曾明确指出:“武帝置郡之初,已有(善人)三万之数”。这里所谓“善人”,“此皆远近商贾兴贩货利有积业者,及土著受井受廛者”①,由此可见当时岛上的汉人已有一定的数量。其实早在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经略岭南,设立桂林、南海、象三郡之后,就迁徙大批中原的汉人进入各郡,与越人杂居。当时作为象郡的“外徼”的海南岛虽然尚未设立郡县的统治,但从一些事实来看,已有汉人进入海南岛居住了①。到了建立郡县之后,更多的汉人便陆续到达岛上的沿海地区,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黎族的远古祖先在内)进行通商贸易,因之当时海南岛出产的奇珍异宝如珠玑、玳瑁、犀角、广幅布和各种热带果品等已为中原人士所熟知,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掠夺的对象。随着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黎族内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加速了黎族原始社会的解体,一方面又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出现。在郡县建立的过程中,由于使用了武力,使劳动人民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在客观上对于巩固祖国的统一,密切海南岛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黎汉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黎族社会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两汉伏波将军开琼”的各种传说和有关的名胜古迹,一直受到人们的传颂②。
郡县制的建立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个进步,但由于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给黎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引起了黎族人民多次的强烈反抗。据《汉书·贾捐之传》载,从设立珠崖、儋耳郡之后,到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八六年)的二十多年间,大小的反抗斗争有六次之多,以后在神爵三年(公元前五九年)、甘露元年(公元前五三年)、初元元年(公元前四八年)都爆发过反抗斗争。在汉武帝末年(公元前八七年),黎族人民在反抗珠崖太守孙幸强征广幅布时,曾攻破郡城,杀了孙幸①。这些历史现象,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着的复杂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以后封建王朝在海南岛的设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时并,有时废,管辖的地方有时扩大,有时缩小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并没有妨碍黎汉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汉族人民仍然不断迁移到岛上来,汉族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继续在黎族中传播,黎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不断受到汉族的影响。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在汉代我国南方的部分地区,包括海南岛在内,过去是“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自从王莽执政(九至二三年)以后,从中原迁徙了一部分居民“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到了东汉建武十八年(四二年),伏波将军马援曾“往来南海,抚定珠崖,调立城郭,置井邑”③,这是中央封建政权比较认真经营海南岛的开始。稍后,在明帝永平年间(五八至七五年)曾任儋耳太守的僮尹,“还至珠崖,戒勅官吏毋贪珍赂,劝谕其民毋镂面颊,以自别于峒俚,雕题之习,自是日变”④。这些措施对于黎族社会的发展,以至风俗习惯的变革,都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至于从汉代至梁朝以前黎族社会封建化的程度如何,目前尚缺乏充分的史料加以说明,但从当时移居到海南岛的汉族人口还占少数,中央封建集权的措施在岛上的推行也还受到很大的限制等情况来看,这时除了沿海(主要是岛的北部)极小部分地区的黎族由于与汉族接触较早,受到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较深,发展较快,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之外,就当时绝大部分黎族地区的社会情况来说,仍相当落后,封建因素还是很微小的。如三国时吴国孙权曾策划远征海南岛,就受到他的大臣全琮和陆逊的劝谏,认为该地“隔绝瘴海,水土气毒”,而且会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①等等可以见其一二。最后孙权不接纳大臣的劝谏,还是派聂友和陆凯进兵海南岛,结果,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虽然人民的反抗被镇压下去了,但因“士众疾疫者十有八九”,不久就被迫撤军②,只得在现今的雷州半岛上另立行政机构珠崖郡和朱卢、珠官两县,对海南岛只是“遥领”而已。
从南朝的梁朝到唐代(五四〇至九〇五年)三百六十多年间,黎族社会的封建因素逐渐有所增长。梁朝于大同中(五四〇至五四一年)在废儋耳郡的地方设置崖州,这是因为当时该地的俚僚(包括黎族的古代祖先)一千多峒“归附”冼夫人,由她“请命于朝”而置崖州的①。冼夫人“多筹略,能行军用师,劝亲族为善”,“政令有序”,是六世纪我国南方越族的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②。当时广东的西南部地区、雷州半岛和海南岛都在她的统领之下。隋初,冼夫人因率领所属十多个州的地方归附隋朝,又以“抚慰诸俚僚”、“和辑百越”有功,隋文帝赐给她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并封赠她的儿子冯仆为崖州总管③。由于冼夫人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事业,不仅密切了中原地区与海南岛的关系,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同时对于促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她的业绩一直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怀念④。
到了唐代,由于当时国际贸易的频繁,使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与南海海上交通中点的海南岛,开始受到中原地区越来越大的注意,岛上出产的珍珠、玳瑁、香料、梹榔、荔枝、龙眼等珍贵物产,有许多一向要从南海诸国输入国内的,这时也由岛上以“土贡”的方式或由商人贩运到大陆地区⑤,使海南岛与大陆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了。唐代海南岛由于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加而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据《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十三》的记载,开元年间(七一三至七四一年)海南全岛五个州(琼、崖、儋、振、万安)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五户①,其中崖州(包括现今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就有六千六百四十六户,比当时大陆地区开发较早的雷州(四千三百户)、廉州(三千零十二户)的人口还要多。当时岛上汉族居民的分布,也从原来岛北沿海开发较早烟瘴较少的地区,逐步向比较偏远、开发较迟而瘴疠较严重的岛南、岛东南地区扩展。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多与分布地区的日益扩展,在沿海黎汉族杂居的地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有较显著的提高。天宝年间(七四二至七五六年),当鉴真大师漂流到岛南的振州(今崖县)时,就看到当地已经是“一年养蚕八次,收稻两次,十月种田,正月收粟”②了。当时山区出产的高良羌、五色藤、盘班布、金糖香、益智子……等土特产,也有不少作为“贡品”或商品而输入中原地区,在沿海一带还出现了作为经纪的商人阶层③。德宗年间(七八〇至八〇五年),琼山郡守韦公干家里从事奴役性手工业劳动的奴仆已能“织花缣文纱”,制角器,熔锻金银,用珍木造杂具,又驱使木工采伐乌文、呿〓等珍贵木材,造大船两只,饰以金银,以健卒为船员,远航广州④。鉴真在振州和崖州滞留期间,就曾主持重修当地的大云寺和开元寺,可见当时该地的建筑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⑤。至于李德裕诗中的“五月畲田收火米”①,说明在唐代后期(八四八年间),“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在崖州地区还相当普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岛上沿海黎汉族杂居地区的阶级分化也日益明显,出现了“以富为雄,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的局面②,还出现了一些独霸一方的豪强官吏。如前述的琼山郡守韦公干,万安州的大首领冯若芳(两人均非黎族),“掠人为奴婢”,强迫这些奴婢从事奴役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竭夷僚之膏血以自肥”,从中剥削掠夺而成巨富③。冯若芳家里有客来时,一次就燃烧从外国输入的珍贵乳香百余斤,他的屋后苏木(一种名贵染料)堆积如山;“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④鉴真为了在崖州重建开元寺,振州别驾冯崇债“即遣诸奴各令进一椽”,三日之内便把强征的巨木收集完毕⑤。振州的富豪陈武振,“家累万金,犀(角)象(牙)玳瑁仓库数百”,连当时的招讨使也要去巴结他⑥。上述这些豪富们的奴婢,有些是被俘虏的波斯船上的船员,但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各族劳动人民⑦。同时,黎族内部的上层首领也已成为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经常通过战争和掠夺以加强对黎族人民的压榨,使黎族人民痛苦不堪。《新唐书》记载的“中宗时(七〇五至七〇九年),(宋)庆礼为岭南采访使,时崖、振五州首领更相掠,民苦于兵”⑧,即是这一情况的纪实。
唐代海南岛沿海地区封建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和当时中央封建王朝对这些地方的积极经营有关。自贞元五年(七八九年)岭南节度使李复平定海南各种纷乱,“讨平峒蛮”,“恢复”琼州之后,全岛共设立了五州二十二县①,为以后的行政建制奠定了基础。而且当时设立的有些县,如琼山、文昌、澄迈、临高、陵水等,有不少的县名仍沿用至今。至于海南岛后来简称“琼崖”,也是自这时前后设置了琼州和崖州而来的。当时县的设置已不限于原来开发较早的岛北沿海一带,而是扩大到岛南和岛东南沿海,使环岛沿海地区几乎全部纳入了州县的范围。如一向气候卑湿的岛东南的万安州(今万宁县),是在唐高宗龙朔二年(六六二年)才设置的②。从此,汉族和黎族的分布状况已不再是“汉在北,黎在南”,而是“汉在外围,黎在腹地”了(这种状况基本上一直持续到解放前)。但是,州县设立之后,苦于赋税、贡品负担的繁重,以及大小官吏的苛索欺凌,在加剧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的同时,也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唐朝中央政府在海南岛设治的不少困难。早在乾封初年(六六六至六六七年)黎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一次反抗斗争,连琼州都被攻陷了③。懿宗咸通五年(八六四年),在镇压以黎族蒋璘为首的反抗斗争之后,刚设立起来的忠州(今定安县西南部)在兵退之后也被迫撤消④。特别是县的设置,有许多是时立时废,变动很大,建立在山区的,如儋州的洛场县,振州的落屯县,更是如同虚设。这反映出中央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除沿海黎汉杂居区外,直到唐代还未十分稳定,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对黎族社会的影响仍未普遍和深入,尤其是黎族聚居的广大山区所受的影响更少,如当时振州的土著居民还完整地保持着文身、凿齿和吹鼻箫等风俗。虽然到了唐代后期宪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年),有“琼管儋、崖、振、万安等州峒俚来归,进五州六十二峒归降图”①,但受统治的黎族仍占少数。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海南岛的开发有了一定的进展,这从文献上有关海南岛的记载逐渐增多得到反映。如后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晋朝王范的《交广春秋》,都有关于朱崖、儋耳两郡风俗的记载。又晋朝盖泓所写的《朱崖传》一卷,是海南岛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唐德宗时(七八〇至八〇五年)杜佑所撰的《通典》,也有关于海南岛的记述。唐昭宗时(八八九至九〇四年)任广州司马的刘恂所写的《岭表录异》,不仅对海南岛的物产风俗有所描述,而且使用了“夷黎”这一专称来称呼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些情况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海南岛以及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了解逐步加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但尽管如此,直到唐代,海南岛开发的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而且仍远比中原地区落后。当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海南岛仍然是一处“化外之地,瘴疠之区”。封建王朝开始把它作为流放贬谪官员的地方,而被流贬的官吏更视海南岛为畏途,“一经南贬,便同死别”。唐大中二年(八四八年)被流贬为崖州司户的著名政治家、诗①参看嘉靖《广东通志》所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岭南节度使赵昌的事迹。
人李德裕,在诗中曾写道:“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①这些情况也反映了唐代海南岛的沿海地区封建化的区域虽然扩大了,但对整个黎族社会来说,原来的落后状况和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通向封建社会的道路上仍处于十分缓慢的进程中。
第二节 十世纪至十四世纪封建影响的加深
五代(九〇五至九五九年)以后,从宋到元(九六〇至一三六五年),特别是宋代,无论从海南岛开发的程度和黎族社会的封建化来说,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五代时,由于中原战乱频仍,而长江以南地区尚能保持比较安定的局面,大批汉族人口纷纷南移,其中不少迁移到海南岛。据估计,南宋(一一二七至一二七九年)时,移居到海南岛的汉族已从唐代的七万多人增至十万人②。正如明代丘浚的《南溟奇甸赋》所提到的:“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托处。”③当时迁到岛上来的,不仅有商人和官吏,也有戍守边疆的士兵,以及大批的汉族劳动人民,他们与黎族人民一起辛勤垦殖,大大促进了海南岛经济的开发与黎族社会的发展,迅速改变了从汉至唐近千年间开发缓慢的局面。这种情况从宋代大诗人苏轼的亲身见闻中可以得到说明。他在《伏波庙记》中写道:“自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班班然矣。”①
在经济方面,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如农业生产就有显著的发展。宋代从占城传入的稻种,能夏种秋收,增加了产量②,而当地的苎麻,一年可收四次③。苏东坡和他的儿子苏过在海南谪居时咏当地农事活动的诗常有“钽”(锄)、“耜”(起土用的农具)、“耰”(用以平田碎块的农具)、“耦”(两人并耕)、“耕牛”、“良田”、“霜降稻实”等词④,可见北宋后期儋州一带农业生产的工具和技术(如牛耕等),已与中原地区习见的无异。水利的修建也被注意,如开宝八年(九七五年)琼州地方开修渠堰,引峻灵塘水灌溉水田二百多顷⑤。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年),琼州帅守韩璧“教(民)以耕耨灌溉之法”⑥。当时沿海地区与汉族接壤和杂居的黎族的生产情况,大致上和汉族差不多。根据文献记载,宋代隶属州县辖下的黎族人民也和当地汉族一样耕作稻田。如朱熹在《琼州知乐亭记》中提到,淳熙年间(一一七四至一一八九年)“化外黎人闻风感慕,至有愿得供田税比省民者”。《宋史·蛮夷传》也有“乾道二年(一一六六年),慰抚黎人,民无产者,官给田以耕”的记载。至于当时
黎族人民种植的各种薯类,不仅品质优良,“芋魁大盈尺”①,而且成为当地的主要食粮,“海南以薯为粮,几米之十六”②,“薯芋人人送,囷庖日日丰”⑧。此外,采集香料和其他土特产也成为黎族人民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所种秔稌不足于食,故俗以贸香为业”④。黎峒出产的沉香、蓬莱香笺香、槟榔、椰子、吉贝(棉花)、翠羽、黄腊、赤白藤和青桂、花梨等珍贵木材,通过汉族商人贩运至大陆地区销售⑤。
在手工业方面,黎族妇女“工纺织,得中土绮彩拆取色丝,加木棉挑织为单幕;又纯织木棉、吉贝为布。”⑥黎族妇女所织绣的“黎锦”、“黎单”、“黎幕”,“五色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青红间道,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⑦还有被后人誉之为“东粤棉布之最美者”的“白〓”⑧,早在北宋时就已在黎族聚居区出现。可见宋代黎族人民在棉纺织技术和工艺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我国的纺织工艺史增添了光彩。当时这些绚丽多彩、美观实用的棉纺织品,曾远销至广西桂林一带。同时黎族人民用特殊方法酿造的名酒(银皮酒),也深为苏东坡所喜爱⑨。
宋代由于国内市场对香料和产于热带地区的土特产以及奇珍异物的大量需要,刺激了岛上黎、汉族之间频繁的贸易活动。特别是槟榔、吉贝、香料的贸易在当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海南土产……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州)商兴(化)贩大率仰此”①。“槟榔生海南黎峒……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②,“(琼州)非槟榔之利,不能为此一州也”③。对当时贸易的重要性,苏过(苏轼的儿子,与父亲同往海南)在他的《论海南黎事书》④中就曾说过:“濒海郡县所以能鸠民置吏,养兵聚财者,恃商人耳”。如果“绝黎人之欢,商人不来”,贸易一旦断绝,则官府便会遭到“关市之征,岁入不足”,“兵吏廪赐无所从出”,“衣食不足,饥寒从之”等三大困难。而“黎人处不毛之地,盐酪谷帛斤斧器用,悉资之华人,特以沉香、吉贝易之耳”。当时邻近汉区的黎族人民每逢墟日即结队到州县城内的市集进行交易,以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土特产品与汉商交换铁器、瓦器、牛畜、鱼盐、酒米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交易以物物交换为主,如一担香料可以换回一头牛⑤。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黎族社会的封建化程度比过去有所加深,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和复杂。一些富有的上层“首领”还养有家奴。如北宋至和初年(一〇五四至一〇五五年)琼州有一个名叫符护的“首领”,“边吏尝获其奴婢十人”⑥。
南宋淳熙年间(一一七四至一一八九年)成为琼州“三十六峒统领”的黎族妇女王二娘,她的祖先早在北宋皇祐年间(一〇四九至一〇五三年)就接受封建王朝的“封赐”,她自己不仅世袭“宜人”的封号,并且掌握实际的统治权力,封建王朝凡有命令都通过她来执行①。这些经过“加官晋爵”的黎族统治人物的出现,标志着黎族社会的封建化到了十二世纪后期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在沿海黎、汉族杂居的地区,黎族劳动人民的土地大批被封建官府、本民族上层“首领”和汉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霸占了去②。一些汉族奸商还乘机“欺其愚而夺其财”,甚至“市黎人物而不与直”③。至于当时封建统治的黑暗,如“法令之烦苛,调敛之无时,官吏之贪求”,“贪胥猾商肆其奸”④,给黎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加深了黎族社会的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
宋、元两代,随着沿海地区黎族社会封建化的加深,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也日益加强。如北宋崇宁(一一〇二至一一〇六年)中,经略广西安抚使王祖道“抚定”黎人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并开通道路一千二百余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其酋亦有补官”⑤。宋代以前的文献中,有关封建王朝“治黎”政策的记载不多,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宋以前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仍然是相当薄弱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对黎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的开发,还未引起封建王朝足够的注意。到了宋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封建王朝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开始着意寻求一种比较能够“长治久安”的统治黎族的政策。苏过在他的《论海南黎事书》中①,就曾提出一些比较系统和具体的“治黎”措施,如政治上参照统治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办法,对于黎族的上层“首领”以官爵利禄进行收买,实施“羁縻政策”,通过他们来统治黎族人民,所谓“籍其众所畏服者请于朝,假以一命,而岁与其禄”,于是“今朱崖屯师千人,岁不下万缗,若取十一以为黎人之禄,可以罢千师之屯矣”。军事上则利用当地的地主武装以加强镇压,所谓“戍卒可省,民兵可用”,因为“(地主们)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而又习其山川险阻,耐其风土瘴疠,吏若拊循其民,岁有以赏之,则吾藩篱不可窥矣”。最后则“许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内属,法令徭赋,一均吾民”,实行强迫同化。苏过提出的以羁縻笼络为主、武装镇压为辅的“治黎”政策,一直为宋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奉行。宋代受到封建王朝“封爵袭职”的黎族上层“首领”(当时称为“峒首”),最早见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一〇六八至一〇七七年)的记载②。稍后,在宣和年间(一一一九至一一二五年),还有符元享等黎族峒首因接受儋州人陈大功的“招抚”,而被封为“承信郎”,“其子孙各以官名承袭”③。但此类的记载更多的则是在南宋期间的事。除上述的王二娘⑧道光《琼州府志》。
外,还有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年)乐会县的王日存、王承福、陈颜等也因“招降”有功而被封为“承节郎”等职①。宋代除在黎族地区的险隘处设立宝西、西峰、定南、延德等寨派军驻守外②,还征集地方武装以加强对黎族人民的镇压。当时这类地方武装称为乡军、土丁(王安石实行保甲制则称民兵),招募的对象有当地“附籍”的汉族,叫做“寨丁”,还有黎族,即所谓“羁縻州之民”,叫做“峒丁”③。采取正规军与地方地主武装相结合,以及驱使当地的黎、汉族人民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工具,成为宋代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加强对黎族人民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
到了元代(一二八〇至一三六八年),封建统治者一面对黎族人民实行残暴的武力镇压,同时任用“归降”的黎族上层“首领”,封以官爵,付以实权(这与宋代仅给予封爵不同),世袭其职。在元朝九十多年的统治中,大举“征黎”不下十次,武装镇压的规模更是前所未见。如元初至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一二九一至一二九四年)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元军兵马深入黎峒,连偏僻的五指山中心地区都不能幸免,计有琼州清水峒以下的十九峒被“剿平”,“归降”的峒六百二十六,户口二万三千八百二十七,并“招抚”户口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七④。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元朝统治者在海南岛专门设立了“黎兵万户府”,下辖十三翼千户所,分布在全岛各地,每千户④参见《琼州府志》、《儋县志》及邢梦璜的《至元癸巳平黎碑记》。其中提到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春刻石五指山、黎婺岭而还。该石刻现存乐东县尖峰公社。
所又辖百户所八处;自万户以下都任用黎族“峒首”世袭其职,统率属下的“黎兵”,兼管地方上的军事和民政,同时还强占黎族人民的土地设立“屯田”,称为“海南黎蛮屯田万户府”。据《元史》记载,当时琼州路的“屯田”就有二百九十二顷九十八亩。元朝统治者不仅驱使“黎兵”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还征调他们参加远征①。而不少黎族上层“首领”也因参与远征“有功”,被授以更高的官职,得到重用。如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南宁军(统辖宜伦、昌化、感恩三县)的黎族上层“首领”谢有奎由于招降“三十峒首与三千户同时内附”,并率领“黎兵”远征“有功”,而被“授以沿海军民总管,佩金符”②。
宋元两代对黎族施行的统治政策,加速了黎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加深了各方面的矛盾,引起了黎族人民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据文献记载,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年)到元末(一三六八年)近三百年内,黎族农民起义达十八次之多,起义地点不仅遍及封建化较早的岛北、岛东和岛西的琼山、临高、澄迈、文昌、乐会、昌化等县,而且还发展到开发较迟的岛东南的万安军和吉阳军一带。在这些起义中,以南宋嘉定至绍定年间(一二〇八至一二三三年)琼山王居起领导的起义与宋末咸淳年间(一二六五至一二七四年)吉阳军黎族人民响应汉族陈公发、陈明甫的起义,元代至顺元年到元统三年(一三三〇至一三三五年)澄迈县和定安县王马、王六具、王官福等人领导的十九峒黎族起义规模较大①。王居起曾自号“南王”,他率领的义军猛攻临高、澄迈和文昌等地的封建统治据点,声势十分浩大,使“琼州城门尽闭”,离城数十里外尽为义军所控制。王马等人领导的元代后期的黎族农民大起义,一次出动的武装群众达数万人之多,连续攻陷元朝在海南岛的主要军事政治据点南宁军、万安军、吉阳军和会同、乐会、文昌、南建州(定安县)等地,“东西诸黎皆应,仅存琼州”,使大半个海南岛燃遍了起义斗争的烈火。元朝统治者最后调动了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四省的兵力,历时四、五年才把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但“黎乱(反抗斗争)终元之世”不绝②,大大动摇了元朝在海南岛的统治地位。宋元两代的黎族农民起义,虽然大多数表现为民族对抗的形式,但其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很明显的。许多黎族的“首领”充当封建王朝镇压黎族人民起义的帮凶,如前述的宋代王二娘的祖先以及王日存、王承福等,就是因“招降有功”而得到“封官受爵”的。元代由黎族“首领”充当的万户、千户、百户,更是经常率领属下的“黎兵”为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效力,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特权,后来还演变成各自拥兵为雄,僭称官职,互相撕杀,造成了元末各首领之间“狗咬狗”的混乱局面③。至于黎汉族劳动人民之间,在共同的阶级命运的基础上,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则多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的。如宋代吉阳军以陈公发、陈明甫为领导的黎汉族人民联合起义,就是其中较显著的一例。
宋代是黎汉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和团结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时期。自五代以来,汉族人民迁住海南岛的日多,黎汉两族人民交错杂居的情况日益普遍。苏轼在《书上元夜游》中所写的“(儋州)历小巷,民夷杂糅”①。《诸蕃志》记载的“(万安军)民与黎蛋杂居”,“(吉阳军)与黎僚错杂”②,都是这一情况的纪实。苏轼当时居住在临近海边的儋州城,但到了晚上就能听到附近黎族夜猎的狗吠声③。黎汉族人民一向是友好相处,团结互助的。苏轼父子谪居儋州时,黎族人民把自己酿好的酒,腌好的肉酸(当时称为“蛙蛤蚁酱”),种得的薯芋和打猎得来的兽肉,都馈赠给他俩品尝④。在贸易方面则互通有无,发展了生产和改善了生活。当时黎族人民对于有信用的汉族商人十分欢迎,“商人有信,则相与如至亲……岁望其一来,不来,则数数念之”⑤。这种情况不仅在沿海平原地区是如此,在黎族聚居的山区,也有不少汉人迁入,所谓“湖广福建之奸民亡命杂焉”⑥。这些所谓“奸民亡命”者,实际上不少是不堪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指
出的:“琼崖儋万,民既贫苦,仍出役钱,其间大半贫困,不曾输纳,甚者逃入黎峒”①;《诸蕃志》也提到:“省民之负罪者,多逋逃归之(黎峒)”。此外,还有商人,“闽商值风飘荡,貲货陷没,多入黎地”,也有戍守的寨丁、屯兵及其家属留居下来的。他们进入黎区后,与黎族人民融洽地相处,有的定居后“耕种不归”,后来逐渐与黎族自然同化。在沿海和靠近州县城的地方,不少黎族人民已经“半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其为黎)焉”②。据说当时在沿海州县许多姓黎的汉人,都是黎族的后代③。可见黎汉族间自然同化的现象,在历史上早就存在了。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宋末元初杰出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勤学苦练纺织崖州被的方法,创造出当时一套最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我国棉纺织业发展的动人事迹④。黄道婆出生于南宋末年江苏松江府乌泥泾(在上海旧城西南九里的地方,现属上海县龙华公社东湾大队)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她八岁当童养媳,因不堪封建家庭的虐待,被迫离乡别井,乘搭航行于闽、广间的海船,流落到崖州(今崖县)。当时崖州是个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黎族人民十分同情黄道婆的悲惨遭遇,热情地关心和款待她,并向她传授纺织崖州被的技术。她在崖州居住了四十年,到元朝成宗元贞年间(一二九五至一二九六年)返回故乡。黄道婆回到乌泥泾后,把从黎族妇女学来的一套棉纺织工具和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劳动妇女,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对去籽、弹花、纺线和织布的工具和工艺进行了改革和创造,成功地创制出轧棉用的手摇搞车,弹棉用的粗弦大弓,以及三〓脚踏纺车(我国古代的手摇单〓纺车只能纺一根纱,新式的纺车能一手同时纺三根纱,功效提高两三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棉工具)。黄道婆把黎族妇女擅长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工艺,结合祖国传统的优良丝织技术,运用到棉织品上去,织成的褥、带、帨(手巾),有花草、鸟兽、折枝、团凤、棋局等图案花纹,光彩美丽,栩栩如生,灿然如画,甚得当时人们的喜爱,一时松江地区出产的棉织品竟行销全国,过去“民食不给”的乌泥泾,一变成为“家既就殷”的富庶地方。黄道婆对于我国棉纺织技术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是黎汉两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黎汉两族人民兄弟般的亲密友谊的体现。
和唐朝时一样,宋王朝继续把海南岛作为流放官吏的一个重要地方。继唐代的李德裕等人之后,宋代又有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如苏轼、赵鼎、丁谓、胡铨、李光等,先后被贬到海南岛。唐宋两代被贬的官吏在居留期间,曾经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对当地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起着促进的作用。如唐代贞观年间(六二七至六四九年)被贬为吉安(今昌江县境)丞的王义方,曾“开陈经书”,教育黎族子弟,“人人悦服”①。李德裕、苏轼等人在当地“教民读书著文”,或“讲学明道,教化日兴”。胡铨在崖州时,“日以训传经书为事,黎酋闻之,遣子入学”。由于他们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各族人民的欢迎。苏轼在谪居儋州的三年多时间中,与当地的黎族人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关心黎族人民的生产,因此有《劝农诗》之作;他对黎族人民生活的贫困,也寄予深切的同情,曾写了谴责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黎族人民的诗篇。由于他与热情好客的黎族人民有了深厚的感情,当他被赦回大陆时,竟写出了“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①的诗句,充分流露出诗人对黎族人民依依不舍的怀念之情。
与此同时,汉族封建文化在海南岛也开创出一个新局面。宋仁宗庆历四年(一〇四四年)琼州府儒学首先设立,后来到了北宋末南宋初期,琼山、澄迈、文昌、万州、陵水、崖州、感恩各州县的儒学也相继成立。大观三年(一一〇九年)并出现了海南岛第一个进士(儋州的符确)②。当时为了方便“黎人遣子弟入学”,还在琼州郡学中特别设立了“新学”③。元代则在各千户所设立“黎学”(又称“寨学”)。这些措施虽然都是为了在黎族中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后代,但对于黎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客观上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括上述的情况来看,从十至十四世纪中叶(五代至元)这四百多年间,黎族社会无论哪一方面都比唐代和唐代以前有着明显的变化和发展,但从当时整个海南岛的经济开发程度来看,仍然比中原地区甚至比两广大陆地区落后。宋代的海南岛,仍然被人视为“九死南荒”的“蛮烟之地”。同时地区性发展不平衡仍相当显著,岛东南和岛南这些开发较迟、黎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比岛北、岛东北、岛西这些开发较早、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更落后些。苏轼在《夜卧濯足》诗中描写当时万安军(今万宁县)的情况是:“万安市无井,斗水宽百忧。天低瘴云重,地薄海气浮”①。《桂海虞衡志》则提到:“其余三郡(指昌化、万安、吉阳),强名小垒,实不及江浙间一村落”。丁谓在《到崖州见市井萧条赋诗》中,也慨叹“程途何啻一万里,户口都无二百家。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②。周辉在《清波杂志》中提到当时的吉阳军(今崖县):“抵郡,止茅茨,散处数十家。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峒贸易,顷刻即散。”至于五指山中心地区,苏过形容其为“豺狼魑魅之所凭,水土疾疫之为厉”③,依然是“外人不复有迹之处”。
在这一时期里,黎族内部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比宋代以前更为显著。文献上开始出现“生黎”、“熟黎”的名称,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生黎”的名称最早见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九七六至九八三年)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其后,在南宋淳熙年间(一一七四至一一八九年)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首先应用了“熟黎”这一名称。以后直到清代的文献一直袭用这些名称。所谓“生黎”和“熟黎”,不过是封建统
治阶级对黎族的一种侮辱性的称呼,其划分的界限主要是看他们是否归属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定。但是,这种称呼上的差别,正好反映出了黎族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在宋元时期,黎族内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长期与汉族人民交错杂居的黎族(一般分布在沿海平原和河口地区,特别是靠近州县治所的地方,也有少数居住在城镇上),他们受州县的直接统治,早已编入户册,纳粮当差,和当地的汉族没有什么差别,不少已经逐渐与汉族自然同化而被视为“黎裔汉人”。他们的经济形态和当地的汉族一样,是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
(二)被封建统治者称为“熟黎”的黎族,他们居住在州县统治范围(即所谓“耕种省地”)之内,但离州县治所较远,所谓“熟黎所居已深阻”①,如北宋大观元年(一一〇七年)曾在那里设立过镇州(今东方县东方公社)的就是这类所谓“熟黎”地区②。他们也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渔猎和采集土特产品还占相当的比重(苏过在他的《夜猎行》一诗中,对当时儋州的黎人的狩猎活动有生动的描述),并且通过汉族商人与汉族地区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他们已经普遍使用从汉区输入的铁制生产工具,但生产技术水平则较汉族地区落后。原来的“土地峒内公有”的制度已被破坏,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已经出现,但土地大多为汉族地主、奸商、高利贷者和黎族内部的上层“首领”和富户所侵占①,阶级对立已相当明显。封建王朝通过“峒”的制度和黎族的上层“首领”进行统治。黎族人民受到汉族封建统治者和本民族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负担着繁重的赋税和官吏、豪富们的抽剥苛索②,生活极为困苦,反抗斗争也特别激烈,宋、元两代的黎族农民起义,多是在这类地区爆发。这部分所谓“熟黎”的黎族由于不同地区受到封建王朝统治的时间长短不一,统治势力强弱不等,以及接受汉族经济文化影响深浅不同,表现在封建化程度上也不完全一致,有些地区还继续蓄养家奴③;但从总的来说,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当地的汉族已有着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基本上也属于封建地主经济的范畴,只是在封建化的程度上有着某些差别而已。
(三)居住在距离汉族地区更远的山区中的黎族,当时被封建统治者称为“生黎”,他们不受州县统治,不供赋役,无论在生产和生活上都比上述两类黎族落后。他们也从事农业生产,但捕鱼、狩猎、采集等活动仍占重要的地位,贸易以物物交换为主,基本上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生活上保留原始的东西较多。如普遍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早稻、薯类和其他粮食作物,生产关系方面仍以公有制为主,所谓“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④。各峒有峒首为领导。在生活上,则“弓刀未尝离手,弓以竹为弦”,“巢居洞深,绩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议婚姻折箭为质,聚会椎鼓歌舞,死必杀牛以祭,祭神以牛犬鸡彘”①;氏族血亲复仇的风俗还相当普遍,“其亲人为人所杀,后见仇家人及其峒中种类,即擒取而械之”②。这部分黎族保留原始的东西还很多,从总的情况来看,还处在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中。
上述三种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黎族,他们所占的人口和地区比例的大小,目前还缺乏充分的史料加以具体的说明。但从当时整个海南岛的开发程度来看,属于州县统治范围内的地区和人口还是不多的,正如苏轼所说的“四州环一岛,百峒蟠其中”③,范成大提到的“四郡各占岛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得,亦无路可通”④,都说明了宋代汉族居住的和黎汉杂居的各州县境,仅占环岛沿海地带的一隅而已,其余不入州县统治范围的广大山区则是“峒落日以繁滋,不知其几千百也”⑤。特别是在岛的南部、东南部和腹心地区更是如此,如当时岛南的吉阳军(今崖县境)“距城五七里许”,不受州县统治的黎族就“不啻数百峒之多”⑥。由此可以推断在这一时期里,属于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这一经济类型的黎族,在分布地区和人口方面可能仍占多数。
附注
①转引自民国《儋县志》卷一。
①据道光《琼州府志》载,过去海南人的度量衡实行六进制,此“实存秦时旧制”云云,由此推断秦时已有汉人到达海南岛。今天黎族传统的计算法仍是六进制,如稻谷的数量以束为最小单位,六束为一攒,六攒为一对。
② 关于这方面的传说,海南岛各县的地方志均有记载。道光《广东通志》载,儋耳郡的外城,传说是汉武帝时楼船将军杨仆所筑。现今东方县十所村的汉伏波井,儋县白马井镇的马口井,相传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所开凿。至于过去祭祀路博德、马援两伏波将军的庙宇,几乎遍布海南岛各地。
①见《后汉书·南蛮传》。
②自汉武帝初设珠崖、儋耳两郡到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八二年)罢儋耳郡并入珠崖郡,至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四六年)采纳贾捐之的建议撤销珠崖郡,改为一个朱卢县,隶属合浦郡,以后则常有变更。详见道光《琼州府志·历代沿革表》。
③④道光《琼州府志》卷二十九,《官师志·马援传》、《官师志·僮尹传》。
①参看晋·陈寿:《三国志·吴志》卷十三,《陆逊传》;卷十五,《全琮传》。又卷八《薛琮传·慎选长吏疏》云:“………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
②参见《三国志·吴志》卷二,《孙权传》;卷十六,《陆凯传》,嘉靖《广东通志》卷四十四,《列传·名宦·聂友传》。
①乾隆《琼州府志》。
②唐·魏徵:《隋书》卷八十,《列传四十五,冼氏传》。又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一,《列传七十九·谯国夫人冼氏传》。
③见前引《隋书·冼氏传》、《北史·谯国夫人冼氏传》。
④解放前,在广东省湛江地区一带和海南岛,不少地方均有冼夫人庙,有关的传说也很多。如琼山县新坡公社梁沙村就有一座相当规模的冼夫人庙。在临高县和儋县,很多村镇都建有冼夫人庙。
⑤《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三上。又参看《群书类丛》第四辑,卷九十六,《唐太和上东征传》。
①此一人口数字似偏低,因汉朝时海南岛已有户二万三千余。
②见前引《唐太和上东征传》。
③见前引《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三上;又参看前引《唐太和上东征传》。
④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九,《韦公干》条。
⑤见前引《唐太和上东征传》。
①宣统《崖州志》卷二十一,艺文志三,李德裕诗:《贬崖州司户道中》。
②参见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四。
③④⑤⑦参见前引《太平广记》和《唐太和上东征传》。
⑥《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陈武振》条。
⑧《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列传五十五,宋庆礼》。
①参见道光《琼州府志》卷首,《历代沿革表》。
②参见道光《琼州府志》卷首,《历代沿革表》。
③道光《琼州府志》:“乾封二年,洞僚陷琼州,东南诸乡尽没。”
④参见道光《琼州府志》卷首,《历代沿革表》。
①参看嘉靖《广东通志》所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岭南节度使赵昌的事迹。
①引自道光《琼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志,李德裕诗:《贬崖州司户道中》。
②关于从唐以前至元代海南岛汉族人口的增加,据一九三三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海南岛志》记载,唐以前海南岛汉族人口约二万人,到唐代增至七万多人,南宋时增至十万人,及至元朝则达十七万多人。
③丘浚:《丘文庄公集》。
①苏轼:《居儋录》。
②道光《琼州府志》:“自宋播占城禾种,夏种秋收。”
③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四:“土产苎麻,岁四番收采”。
④苏轼:《居儋录》;苏过:《斜川集》。
⑤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五,《广东六》。
⑥宋·朱熹:《琼州知乐亭记》。
①《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五,《广南西路昌化军》转引李光诗:《失题》。
②《居儋录·薯说》。
③《居儋录·已卯冬至儋人携具见饮既罢有怀惠许兄弟》。
④《居儋录·劝农诗序》。
⑤宋·赵汝适:《诸蕃志》。
⑥⑦参见《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诸蕃志》有关海南部分。
⑧清·李调元:《南越笔记》。
⑨《居儋录·己卯冬至儋人携具见饮既罢有怀惠许兄弟》。
①《诸蕃志》,《货物》条。
②《岭外代答》卷八。
③《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四,《琼州》条。
④苏过:《斜川集》。
⑤《桂海虞衡志》。
⑥《宋史·蛮夷传》。
①《桂海虞衡志》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朱初平奏言》:“海北之民乃作请田文字,查其田土,使无所耕种。又或因商贩以少许物资,令虚增钱数,立契买峒民田土,岁久侵占。”
③④苏过:《论海南黎事书》,载《斜川集》。
⑤周去非:《岭外代答》。
①苏过:《论海南黎事书》,载《斜川集》。
②《岭外代答》。
⑧道光《琼州府志》。
①《宋史·蛮夷传》。
②③《岭外代答》卷三《寨丁》条。
④参见《琼州府志》、《儋县志》及邢梦璜的《至元癸巳平黎碑记》。其中提到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春刻石五指山、黎婺岭而还。该石刻现存乐东县尖峰公社。
①《元史·安南传》: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曾征发海外四州黎兵一万五千人参加远征。
②道光《琼州府志》卷四十二。
①参看《广东通志》、《琼州府志》有关记载。
②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八:“元设黎兵万户府,统十三翼,兼管民兵,黎峒万千百户,以土人为之,致黎乱终元之世。”
③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八。
①引自苏轼:《居儋录》。又《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五载苏东坡诗有:“琼崖千里环海中,民夷错居古相蒙”;“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等句。
②《诸蕃志》,《海南》条。
③苏过:《斜川集·夜猎行》。
④参看苏轼:《居儋录》中有关诗篇,如《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已卯冬至儋人携具见饮既罢有怀惠许兄弟》等。又引自苏过:《斜川集》卷一,《用伯充韵赠孙志举》。
⑤⑥《桂海虞衡志》。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朱初平奏言》。
②《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条。
③《桂海虞衡志》:“四郡之人多黎姓,盖其裔族。”
④关于黄道婆的事迹,参见元代陶宗仪所著的《辍耕录》和近人有关她的评著。
①《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二,《列传三十七·王义方》。
①苏轼:《居儋录·和陶田舍始春怀古诗并引》。
②道光《琼州府志》。
③《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四,《琼州·景物上》,《新学》条。
①引自《居儋录》。
②《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七,《广南西路·吉阳军》。
③引自苏过:《论海南黎事书》。
①《桂海虞衡志》,《志蛮》条。
②《宋会要稿》:“徽宗大观元年六月,依提点刑狱王祖道奏请,于黎母山峒置镇州。”
①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朱初平奏言》曾提及当时议禁海北之民及商贩等侵占峒民田土。又议严诫豪富之家高利抽剥,以致贫民抑雇儿女,脱身无期。
③参看《诸蕃志》、《桂海虞衡志》、《宋史·蛮夷传》有关记载。
④见前引《朱初平奏言》。
①引自《太平寰宇记》。
②《桂海虞衡志》。
③引自《居儋录·戏作》。
④《桂海虞衡志》。
⑤⑥《诸蕃志》,《海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