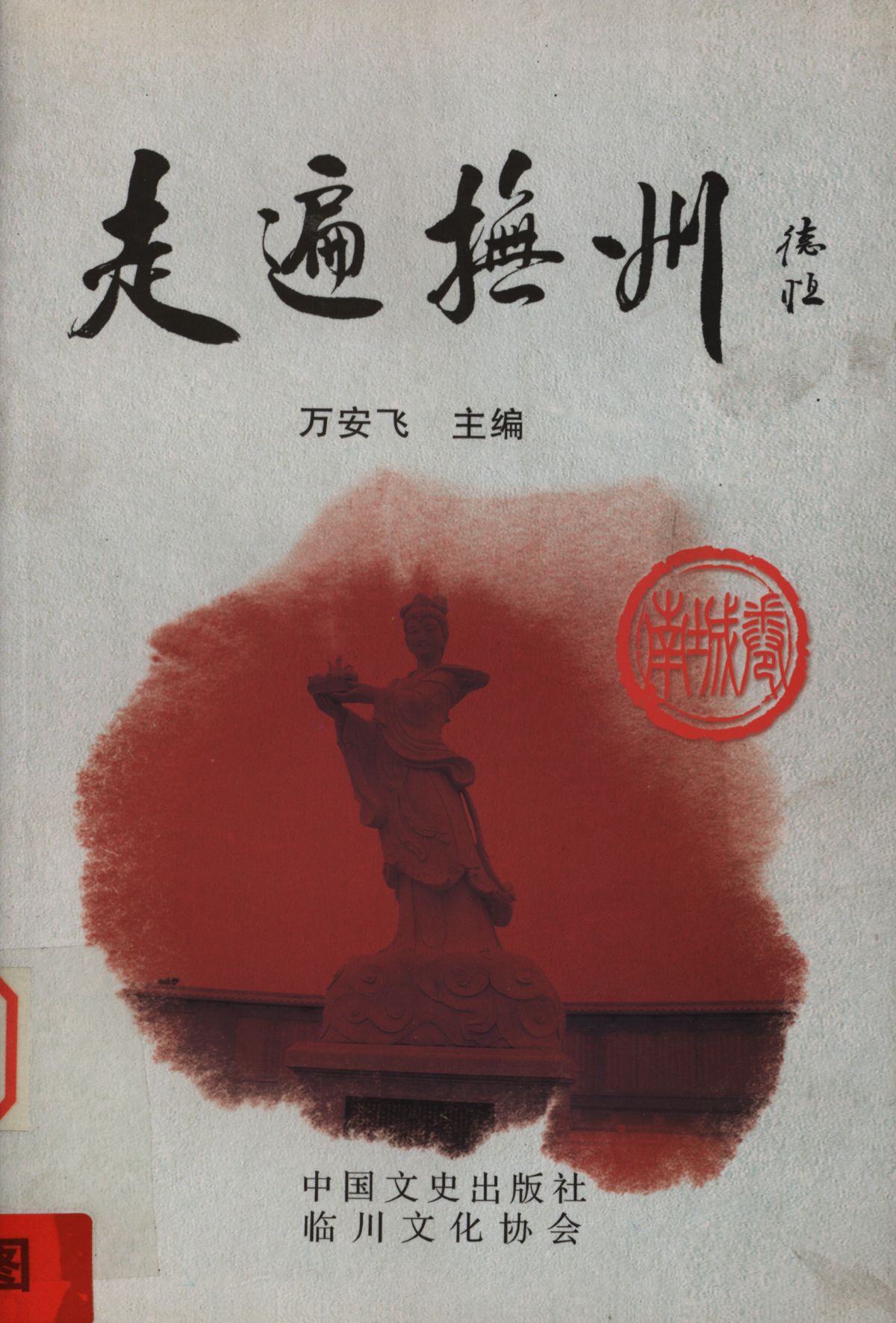内容
1972年1月下旬,江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南城县红湖公社红岭大队外源村北发掘了明代益王朱祐槟夫妇合葬墓,出土二百余件文物,为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一批参考资料,现将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一)墓地外况
外源村位于县之东南,距城十七公里,南至洪门车站一公里。村庄座落在山谷小盆地东南方,村北有一高山,名曰金华山。这里山势高峻,山之南麓有一小丘陵。丘陵南端为一小山包,墓地坐落在呈“交椅”形状的山窝里,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的小山包是他们的陵寝,陵寝周围的山墙长25丈,宽15丈,陵寝正前方远处有一条蜿蜒的小溪。站在现在通往洪门的公路下面,就可以看见其非凡的气势。在山下水田路边,发现许多琉璃瓦片,从遗迹观察,似为亭殿遗址。再往南约一百米处,依次有用红石雕成的文史、武将、马、狮、望柱及汉白玉碑各一对。碑额雕刻双龙抢珠,碑身高522、宽111、厚35厘米。左碑因早年倾倒,风雨侵蚀,不见碑文,右碑刻有嘉靖十八,十九年赐祭朱祐右槟夫妇的“御祭文”。
在上述小丘陵东西两侧各有一支脉向南延伸,形如双手合抱。在两支脉内侧发现了墙基瓦片,应是当年坟地的围墙。围墙范围之内,约有水田六七十亩,这和明代“亲王茔地五十亩”的规定大体相符合。根据《南城县志》记载,这一带原葬有许多民坟,自从朱祐槟圈地造坟之后,就不许老百姓在这里埋葬,也不许进山砍柴,并且圈占1159亩良田作为护坟地。朱祐槟不但生前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就是死后也还要霸占大片山林良田,建坟筑殿。封建统治阶级侵吞土地鱼肉乡民的狰狞面目,由此可见一斑。
(二)墓宫结构
该墓建于石山之中。造墓时,先将石山凿开,用红条石做墙基,然后以38×21.1×8,及43×20×10厘米的素面青砖结砌,墓顶上再填封土,厚达122-200厘米。
墓为券棚式,分前后二室,设二道石门,全长820厘米,平面呈“凸”字形。墓门方向为正东南。墓内墙壁经过磨洗,光滑平整,胶缝石灰细如一线,平直工整,甚为美观。石门和棺台雕刻精工,说明当时造墓工人具有很高的建筑水平。
墓门前有一墓道,长492、宽310厘米自东南向西北倾斜至墓门口,南端比北端高55厘米。地面铺垫一层厚为39—68厘米的黄土。
墓门为券拱形,内空宽162、深112、高212厘米,门上以青砖卷墙砌六层成墙。每两层之间砌横箍一道,合为六卷七箍。七箍之上平铺一层,两边砌眠砖与之相齐成为羽墙。门卷厚122厘米,中塞三道青砖封门墙,墙后即为插扳式石门。以两块宽178、高119、厚9.5厘米红石板插于墓门两边的石槽中,石槽顶上再压一块千斤石。门卷地面及门槛全用红条石铺砌。
石门后为前室,深121、宽162、高212厘米。仰顶为卷棚式,墓底铺以长条红麻石,室内空无一物。
前室后为二门,门之上下左右各以条石构成门框。门为双扉枢轴式。各以宽92、高211厘米的素面红石板构成。铺首以原石凿成17×15×5厘米的狮首,口含铜环。双扉靠轴一边厚12、靠铺首一边厚7厘米。两扉门关闭时不紧合,缝隙宽约2厘米。门缝北面有一长40、宽14厘米的石栓插于门槛后石槽中,与历次发掘的帝王陵墓不同。
开二门为后室,高297、宽362、长520厘米,仰顶亦为卷棚式。墓底铺以32×32厘米的方砖。左右两壁各有一高62、宽80、深38厘米的壁龛,龛内各放有小木箱子4个,已腐朽一空,墓室后壁亦有二壁龛,龛高110、宽102、深30厘米,各放置一副圹志。左右墓壁在第28、29两层砖上各刻画三个卦象。后壁及二门门框上面,在同一水平地方各刻画一个卦象,均填以朱砂。乾卦在西北,巽卦在东南,与墓向一致。后室正中为一红石棺台。高60、宽233、长266厘米。台之四侧有闾柱的须弥座,并雕刻有莲瓣图案。台面铺以方酵,砖上置有垫石三行。左右两行各有五块20×20×7的方石,中间一行为五块44×21×7长方形石块。垫石上捆置两具红漆棺木,左为朱祐槟,右为彭氏。棺台前空地上放置100个陶仪仗俑,分六行排列,上面积满汗土。
棺台东边15厘米处有一石座子,高68,宽54、长54厘米。座上置一红漆木匣,匣上有锁,匣已朽烂;只剩漆皮,保持匣子形状。内置一谥册,册为木质,上有阴文,烫以金粉。因腐蚀严重,仅能辨认个别字句,中有“谥曰端……工部造”等字,故知为朱祐槟死后呈室追悼的谥文。
二具棺柩均已腐朽,只剩一层红漆皮保持棺木外形。彭棺长210、宽03-89、高71厘米。朱棺长210、宽86-92,高93厘米。彭棺棺盖已塌陷,盖上置一肃面铜镜。朱棺盖上写有“大明益端王”五个白字,二尸俱为直肢仰身葬,头向均与墓门方向相反。由于彭氏先死两年,停棺别处再迁葬,因此骸骨腐朽更为严重,棺内器物位置也略有扰动、损失。
(三)出土器物
该墓器物除一对金长簪一副玉带出自朱祐槟棺内,陶俑放在棺台前以外,均出自彭氏棺内。
1、金凤钗一对。凤高10.5、钗脚高12.5厘米,钗脚切面为扁形,上宽下狭,背款“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内造玖成色金贰两外焊贰分”。凤的姿势,一俯一仰,俯者状极虔敬,仰者意态昂然。头部以金叶制成,略如花生形状。以尖部向前,尖端下曲开裂成嘴,似鹦鹉嘴面短,尖部上面以绳状金丝盘曲如嘲蝶结,是为毛冠。脑后有水草形二片高出头顶,以代肉冠。又以绳状全丝缕缕向上下左右回卷如须,以代劲鬣。颈部向后深回,胸部圃鼓。胸前两旁以金丝按螺旋方式绕成一小圆饼,然后以余下的金丝紧密地绕成蛇行曲线的劲羽二片,笔直向上。颈、胸、腹、腿等部分的外表全用细如发丝的金钱割成长鳞形的羽毛,排列整齐。背上二翅羽如刀形,上长下短。翅下另有如西番草的毛羽数茎,圆转流畅及于尾都。尾羽很长,从体后同旋向上面前,及于头部,成为金凤主要部分之一,脚胫用绳状金丝缠绕而成,脚趾有力地抓于上大下小的云形体上,云形体尾尖向后,用大小金丝编组而成,纤纤如缕。云形体下为钗足。钗足上端转为粗圆形金丝,自云形体下穿入其内。全器纤细秀丽,巧夺天工,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它显示了明初我国金银工艺的高度水平。
这对金凤钗和1958年发掘的朱祐槟长子朱厚烨墓中万氏棺内出土的金凤钗完全一样,而且均是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出品,出土时插在凤冠之上。可能是皇宫内作为亲王纳妃采礼之用。有一件凤脚小腿部发现修理过的痕迹,当为生前使用时损坏的缘故。
2、金钿花16件。用绳形金丝绕成六瓣花彤,最宽处为1.7厘米。原为凤冠上饰物,凤冠腐烂只剩下这些金钿花及一些珍珠。
3、金簪3对。一对出于朱祐槟头部,呈圆钉形状,通长7.8厘米。二对出于彭氏头上。一对簪花为梅花形,脚切面为圆形,通长7.6厘米。另一对簪头为伞形,脚切面亦为圆形,通长11.2厘米。脚款:“银作局弘治六年十月内造金五钱。”
4、金挖耳1件。首部为圆勺形,脚部为圆钉形,通长8厘米。
5、金耳环1对。上部以径粗0.2厘米金丝扭成“2”字形,下部以细金丝扭成五边形。五边形顶端用金丝绕一旋形小圆饼两边各饰一朵五瓣花形的绿宝石。下边金丝绕成“X”形,从现象观察,上面应有饰物,但已朽腐,通高9.3厘米。
6、金鬓花1对。正面呈云状纹,背面素平。有一脚向上直伸。云纹正中镶红、蓝宝石一枚,通长13.9厘米。7、金扣花分为三种。(1)大扣花2副,每副由两只蝴蝶组成采花图案。雌的头部饰六瓣花形一朵,每瓣镶一宝石。雄的头部镶宝石一颗,扣合的成为花蕊。蝶身及前后翅膀上共镶宝石五颗。通长7.9、宽3.4厘米。(2)中扣花7副半,呈蝴蝶采菊花图案。雄者头部镶一宝石,蝶身各镶一宝石。通长5、宽2.2厘米。(3)小金扣6副半,亦呈蝶恋花形状,但不镶宝石。长2.3、宽1厘米。另有小金扣一件,呈圆球形,有钮,径0.7厘米。
8、金香囊1件,以金叶二片外锤压成半椭圆球状,有如倒置的心脏,球面楼刻飞凤图案。囊上有钩,钩上刻缠枝纹。通长15.8、宽7.8、厚5厘米。
9、金片4件,形如磐,中镂空呈栏杆形状,为缀带上的饰物,宽4.4,高2.6厘米。
10、玉佩2副,一副为叶形玉片和菱形玉块组成,另一副为玉片和玉珠组成,玉片上阴刻云凤图案,玉珩上有长7.5厘米的金钩,钩内阴刻“银作局弘治六年十月内造金伍钱”等字,复原后,通长74.5厘米。其形制与《明史》及《三才图绘》上诸王冠服图所载近似。
11、玉饰22件。其中玉绶花1件,镂刻宝相花坟,宽7、厚0.3厘米;玉人2件,长6.4、厚1.8厘米;玉羊2件,最宽处7.2,厚0.8厘米;玉鱼2件,长7.1,厚0.7厘米;玉泥鳅1件,长1.2,头高2厘米;玉鸳鸯4件,长3.1、高1.6,厚0.8厘米;小玉鱼4件,长3.1,高12,厚0.8厘米;玉坠珠6件;2件为辣椒形,通高4、径1.5厘米;4件为圆茄形,通高2.8,径1.6厘米。顶部俱缀以金叶。
12、玉带1副,白羊脂玉。素面无纹,出土时环列于朱祐槟腰部,共20块。宽俱为4.8(只有正面中间一块为4.9)厘米,厚均为0.65厘米,长度为6.9(5块)、8(2块)、6(1块)、6.55(2块),2.2(2块),1.95(2块)厘米。心形6块,宽4.6,长4.9厘米。13、玉圭1件,色呈豆青。出于彭氏头部左侧,宽5.1、自尖至底边长15.2,厚0,8厘米,两面均刻五行圆泡,即所谓“以聘女”之谷圭。
14、铜镜1件。径15.6厘米,圆纽,只有六道凸弦绞,出土时置于彭氏棺盖上。
15、铜钱30枚,除4枚为“永乐通宝”外,俱为“宜德通宝”。出土时散置棺台和后室地面。
16、谥册1件,置于后室棺台东边15厘米处的石座上之红漆小木箱里。箱高26.5,宽3.5、长35.7厘米,木质已朽,只剩漆皮保持箱形,箱上加铜锁。箱中另有一涂金小木匣,亦朽烂。匣中藏谥册,册为木质,上阴刻溢文,烫以金粉。因腐朽,仅能辨认:“……者殁必有谥,爵以贵其身,谥以表其行……善循理,早著贤…福寿之兼备…眷念亲……溢曰端…克歆……日工部造”等字。据《南城县志》卷9所载,此溢册全文应为:
“制曰:朕先王之典。生有爵者,殁必有谥。爵以贵其身,谥以表其行。此古不易之常道也。叔父益王,乐善循理,早著贤誉。宜福寿之兼备,以光重于藩邦。乃疾痰庚婴,药石弗效,倏闻长逝,痛闻长逝,痛何可言!眷念亲贤,宜申册命。兹特谥曰:端,灵爽不昧,庶克歆承。日工部造。”
17、圹志2副:皆用皤石制成(朱志略呈青灰色,彭志较白)。每副2块,篆盖,志文各一,相对合并,外套以铁箍二道。朱志每块76.5×76.2×17.5厘米,彭志76.1×76.3×10.7厘米,篆盖,志文四周均无花坟图案。
18、陶仪仗俑110件:用灰色陶土模制加工而成,肩部以下用模子压印成中空的筒状,然后刻划衣纹束带,并乘湿将手弯曲成各种姿态,头部多为手制,再用漆调石灰作黏合剂插在肩上。窑烧后再加彩,脸部涂白粉,再绘以眉须眼目,口唇涂朱,衣服亦多施朱红,出土时多褪蚀。这批仪仗俑分六行排列于棺台前面的地上。按其身份大致可分为骑马乐俑、仪仗俑、吏俑、男女乐队俑,轿夫俑,男女侍俑等六种,
①骑马乐俑10件。通高23厘米,戴尖顶圆帽,穿长衣,束带,着靴。其中六件一手上举平肩,一手搁置大腿上。另两件为一手平肩,一手及于腰部。手上均有所持,因腐朽不明器形,另一件两手置于肚前,似为打小锣者。另一件两手拱于口前,鼓腮努嘴,应为吹唢呐者。
②仪仗俑27件。通高21.1厘米,俱身穿长袍,束带。其中头戴无梁黑冠双手拱于胸前者16件,头戴五梁冠双手拱于胸前者2件,头戴风帽者5件其中2件为一手平胸,一手扶带,其余三件均拱手胸前。头戴老人巾者4件,均一手平胸,一手扶带。以上各俑手中皆有圆洞,原插有本质器具,因俱腐朽,不明器形。推之当为亲王仪仗规定的骨朵、立瓜、旗刀戟之类。
③吏俑14件。通高25.2厘米4件,其余高21.1厘米。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袍,束带,胸背绘有翔风、卧虎等补服图察,袖手拱于胸前。其中有二件面部雕刻五络长须,老态龙钟,似为王府左右长史之职。其余应是王府长史司中的官吏僚属之类。
④男女乐队俑30件,通高20.2厘米。其中女乐俑12件,头梳云髻。身穿短衣,下着长裙。手中乐器多腐蚀,仅能辨认琵琶、三弦、洞萧、拍扳、小鼓数种。男乐俑18件。其中六件为鼓手,头戴红色尖顶圆帽,身穿长衫,束带,四人胸前挂一扁鼓,双手执槌作敲打状。二人一手执小板鼓,一手执鼓槌。鼓上均绘有梅花图案;其余12件,头戴平顶帽,帽前着一花朵,身穿长袍,腰间束带,手执琵琶、洞箫、拍扳等乐器。
⑤轿夫俑16件,通高20.1厘米,头戴风帽。身穿长衣,腰间束带。八人合抬一轿,一手扶杠。一手垂于身侧。另八人一手扶杠,一手扶带。轿系木质,出土时已腐烂。
⑥男女侍俑13件。男侍7件,2件高21.3厘米,头戴乌纱帽,身穿长袍,束带,双手捧水罐。5件高20厘米,戴尖顶圆帽,长衣,束带,双手中执物已佚。女侍6件,云髻,长衣,束带,双手拱于胸前,器物已佚,通高20厘米。
明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镇压人民反抗,用榨取来的人民血汗,豢养了一批仪仗侍卫,走狗爪牙,出门时前呼后拥,一唱百诺,借以壮胆,用以吓人。即所谓“明制度示等威”“慎出入远危疑”。因此亲王和亲王妃的仪仗就多达112人。上述110个陶俑就是朱祐槟生前拥有众多奴仆、炫耀封建淫威的反映,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色厉内荏,虚张声势,害怕人民的纸老虎本质。就艺术价值而言,这批陶俑的主要成就在于人物性格的刻划,雕塑者仅以简单的线条表现了衣纹折痕,但对人物的脸部却是精雕细刻,力求准确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因而110个陶俑或耸肩哈腰,或挺胸凸肚,或温文尔雅,或骄横跋扈,不但老少胖瘦各不相同,神情风貌也是因人而异。刀笔纯熟刚劲,线条简洁流畅,反映了明代雕塑工艺的高度水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个男侍俑形象:上身前倾,下腹微收,右手握拳,左手拂袖,浓眉暴眼,气势汹汹,雕塑者用简炼而又夸张的刀笔把一个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地主走狗的形象,刻划得维妙维肖,不但显示了雕塑者具有高度艺术概括能力和雕塑技巧,而且也表现了饱受朱祐槟蹂躏的雕塑工人对地主阶级强烈的阶级仇恨。
(四)关于墓主
明代,江西境内共有三藩。南昌一带是宁献王朱权系统的势力范围。鄱阳湖一带是淮靖王朱瞻墺系统的势力范围,南城一带则是益端王朱祐槟系统的势力范围,其中益王一系延续到清初才覆灭,统治江西一百四十几年。明代江西人民除了要受当地的官府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外,还要受这三大藩王的直接榨取,苦难格外深重。因此研究三藩在江西的罪恶统治是研究明代江西阶级斗争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益王朱祐槟墓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批资料。
朱祐槟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六代孙,宪宗皇帝第四子,生于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九岁(成化二十三年)被封为益王,十七岁(弘治八年)就国江西建昌府,死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统治建昌府达四十二年之久。
朱祐槟是一个骑在江西人民头上贪婪残暴的统治者。“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朱祐槟仗着皇室淫威,凭借这些封建特权,肆无忌惮地压榨广大贫苦农民。据《南城县志》记载:当时南城一带农民的负担是极为沉重的。他们每年除了缴纳田赋(秋粮、夏税)课程(商税、茶税,盐钞,门摊)等奇捐重税外,还要献纳茶芽、鹇鸡、野鸡、活兔、羽毛、杂皮、蜜饯、冬笋、腌腊、药材、弓箭弦、红铜、黑铅、棕蘑等物,称之为职贡。此外还要服繁重的徭役(正役、均徭、驿传、民兵,谓之四差。)“奸臂猾里,放富差贫,名为均徭,不均实甚。”这些劳动人民的血汗多半是用来满足王府庞大统治机构穷奢极欲的,林俊在《论宁府用琉璃硫》中曾提到:“益府宫殿蚁蠹,益殿下见移东寝……修盖之安,约三万余两。”当时南城县每年的田赋是24719两8钱。也就是说南城县农民一年缴纳的赋还不够益府修一次房子。因此连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江西赋税苛杂、徭役繁重,乃是王府残酷剥削的结果。“江西自弘治以来(朱祐槟就是弘治八年到江西来的)赋役渐繁” 、“三藩盘建江省肆米供繁,此赋额渐加之由也。”、“迨宗藩日盛,而役益增。”以致“江西公私匮竭,人民滋困。”朱祐槟是一个疯狂榨取农民血汗的大地主。按照明代规定,亲王占有土地十万亩,加上郡主的土地以及他们子孙的坟地和护坟地,朱祐槟一家所占的土地总数在十七万亩以上,这些土地的租税全部归益府收入充作禄米。朱祐槟家族对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横征巧取进行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租额之高,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当时官府租税以谷折钱的标准是“每谷五石,作银一两”,但是“江西各王府收受禄米,每石用银一两陆柒钱(较官定标准高八倍)”,并且这样高的租额,在灾荒年月也毫不减免,因此“小民田苦:要行禁冶,……但王府地方司府等官既畏惧而不能阻违,巡抚巡按亦推避而不肯究治”,广大农民在这种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铤而走险,拿起扁担锄头进行武装反抗了。
朱祐槟又是一个残暴屠杀农民、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建昌府的贫苦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仅在朱祐槟盘踞江西四十二年之间,就前仆后继,先后爆发了十一次农民起义,攻打广昌、南丰、南城等县,活捉击毙四个知县,消灭大量反动官兵。“地方震动,亲藩惊恐”,沉重地打击了明代封建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显示了中国人民酷爱自由勇于革命的英雄本色。朱祐槟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调动了大量反动军队,疯狂反扑,残酷地镇压农民,实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政策。仅南城一县,在朱祐槟统治期间,人口就由173782人减少到154465人。
朱祐右槟还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大骗子。他为了掩盖其屠杀人民的血腥罪行,麻痹人民的斗志,搞些小恩小惠,故意装模作样地“每日一素食,以清神思”,“精制丸散,每给赐以活人”,甚至连临死之际也要骗人,假惺惺地“命不藏金玉,嚣用惟陶瓦而已”。于是他儿子朱厚烨就大肆标榜,肉麻地吹捧他“裁省浮费,一遵俭约,禁兵卫毋夺于市,戒校官舞虐于民……居常不事浮夸,巾服浣至再,性不嗜酒,膳不兼昧”。封建史学家也跟着学舌,美化他;“性俭约,巾服瀚至再,日一素食,好书史,爱民重士,无所侵扰。”(《明史·益王传》)。竟然把一个荒淫残暴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乔扮成“爱民重士,无所侵扰”的救世主!现在,朱祐槟墓被打开了,人们发现墓中埋葬的尽是金玉,器用并无陶瓦。朱家设下的历史骗局被揭穿了,被颠倒的历史终于复原过来。
(执笔:陈文华,原题为《江西明益王朱祐檳墓發掘報告》,原载《文物》1973年第三期)
(一)墓地外况
外源村位于县之东南,距城十七公里,南至洪门车站一公里。村庄座落在山谷小盆地东南方,村北有一高山,名曰金华山。这里山势高峻,山之南麓有一小丘陵。丘陵南端为一小山包,墓地坐落在呈“交椅”形状的山窝里,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的小山包是他们的陵寝,陵寝周围的山墙长25丈,宽15丈,陵寝正前方远处有一条蜿蜒的小溪。站在现在通往洪门的公路下面,就可以看见其非凡的气势。在山下水田路边,发现许多琉璃瓦片,从遗迹观察,似为亭殿遗址。再往南约一百米处,依次有用红石雕成的文史、武将、马、狮、望柱及汉白玉碑各一对。碑额雕刻双龙抢珠,碑身高522、宽111、厚35厘米。左碑因早年倾倒,风雨侵蚀,不见碑文,右碑刻有嘉靖十八,十九年赐祭朱祐右槟夫妇的“御祭文”。
在上述小丘陵东西两侧各有一支脉向南延伸,形如双手合抱。在两支脉内侧发现了墙基瓦片,应是当年坟地的围墙。围墙范围之内,约有水田六七十亩,这和明代“亲王茔地五十亩”的规定大体相符合。根据《南城县志》记载,这一带原葬有许多民坟,自从朱祐槟圈地造坟之后,就不许老百姓在这里埋葬,也不许进山砍柴,并且圈占1159亩良田作为护坟地。朱祐槟不但生前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就是死后也还要霸占大片山林良田,建坟筑殿。封建统治阶级侵吞土地鱼肉乡民的狰狞面目,由此可见一斑。
(二)墓宫结构
该墓建于石山之中。造墓时,先将石山凿开,用红条石做墙基,然后以38×21.1×8,及43×20×10厘米的素面青砖结砌,墓顶上再填封土,厚达122-200厘米。
墓为券棚式,分前后二室,设二道石门,全长820厘米,平面呈“凸”字形。墓门方向为正东南。墓内墙壁经过磨洗,光滑平整,胶缝石灰细如一线,平直工整,甚为美观。石门和棺台雕刻精工,说明当时造墓工人具有很高的建筑水平。
墓门前有一墓道,长492、宽310厘米自东南向西北倾斜至墓门口,南端比北端高55厘米。地面铺垫一层厚为39—68厘米的黄土。
墓门为券拱形,内空宽162、深112、高212厘米,门上以青砖卷墙砌六层成墙。每两层之间砌横箍一道,合为六卷七箍。七箍之上平铺一层,两边砌眠砖与之相齐成为羽墙。门卷厚122厘米,中塞三道青砖封门墙,墙后即为插扳式石门。以两块宽178、高119、厚9.5厘米红石板插于墓门两边的石槽中,石槽顶上再压一块千斤石。门卷地面及门槛全用红条石铺砌。
石门后为前室,深121、宽162、高212厘米。仰顶为卷棚式,墓底铺以长条红麻石,室内空无一物。
前室后为二门,门之上下左右各以条石构成门框。门为双扉枢轴式。各以宽92、高211厘米的素面红石板构成。铺首以原石凿成17×15×5厘米的狮首,口含铜环。双扉靠轴一边厚12、靠铺首一边厚7厘米。两扉门关闭时不紧合,缝隙宽约2厘米。门缝北面有一长40、宽14厘米的石栓插于门槛后石槽中,与历次发掘的帝王陵墓不同。
开二门为后室,高297、宽362、长520厘米,仰顶亦为卷棚式。墓底铺以32×32厘米的方砖。左右两壁各有一高62、宽80、深38厘米的壁龛,龛内各放有小木箱子4个,已腐朽一空,墓室后壁亦有二壁龛,龛高110、宽102、深30厘米,各放置一副圹志。左右墓壁在第28、29两层砖上各刻画三个卦象。后壁及二门门框上面,在同一水平地方各刻画一个卦象,均填以朱砂。乾卦在西北,巽卦在东南,与墓向一致。后室正中为一红石棺台。高60、宽233、长266厘米。台之四侧有闾柱的须弥座,并雕刻有莲瓣图案。台面铺以方酵,砖上置有垫石三行。左右两行各有五块20×20×7的方石,中间一行为五块44×21×7长方形石块。垫石上捆置两具红漆棺木,左为朱祐槟,右为彭氏。棺台前空地上放置100个陶仪仗俑,分六行排列,上面积满汗土。
棺台东边15厘米处有一石座子,高68,宽54、长54厘米。座上置一红漆木匣,匣上有锁,匣已朽烂;只剩漆皮,保持匣子形状。内置一谥册,册为木质,上有阴文,烫以金粉。因腐蚀严重,仅能辨认个别字句,中有“谥曰端……工部造”等字,故知为朱祐槟死后呈室追悼的谥文。
二具棺柩均已腐朽,只剩一层红漆皮保持棺木外形。彭棺长210、宽03-89、高71厘米。朱棺长210、宽86-92,高93厘米。彭棺棺盖已塌陷,盖上置一肃面铜镜。朱棺盖上写有“大明益端王”五个白字,二尸俱为直肢仰身葬,头向均与墓门方向相反。由于彭氏先死两年,停棺别处再迁葬,因此骸骨腐朽更为严重,棺内器物位置也略有扰动、损失。
(三)出土器物
该墓器物除一对金长簪一副玉带出自朱祐槟棺内,陶俑放在棺台前以外,均出自彭氏棺内。
1、金凤钗一对。凤高10.5、钗脚高12.5厘米,钗脚切面为扁形,上宽下狭,背款“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内造玖成色金贰两外焊贰分”。凤的姿势,一俯一仰,俯者状极虔敬,仰者意态昂然。头部以金叶制成,略如花生形状。以尖部向前,尖端下曲开裂成嘴,似鹦鹉嘴面短,尖部上面以绳状金丝盘曲如嘲蝶结,是为毛冠。脑后有水草形二片高出头顶,以代肉冠。又以绳状全丝缕缕向上下左右回卷如须,以代劲鬣。颈部向后深回,胸部圃鼓。胸前两旁以金丝按螺旋方式绕成一小圆饼,然后以余下的金丝紧密地绕成蛇行曲线的劲羽二片,笔直向上。颈、胸、腹、腿等部分的外表全用细如发丝的金钱割成长鳞形的羽毛,排列整齐。背上二翅羽如刀形,上长下短。翅下另有如西番草的毛羽数茎,圆转流畅及于尾都。尾羽很长,从体后同旋向上面前,及于头部,成为金凤主要部分之一,脚胫用绳状金丝缠绕而成,脚趾有力地抓于上大下小的云形体上,云形体尾尖向后,用大小金丝编组而成,纤纤如缕。云形体下为钗足。钗足上端转为粗圆形金丝,自云形体下穿入其内。全器纤细秀丽,巧夺天工,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它显示了明初我国金银工艺的高度水平。
这对金凤钗和1958年发掘的朱祐槟长子朱厚烨墓中万氏棺内出土的金凤钗完全一样,而且均是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出品,出土时插在凤冠之上。可能是皇宫内作为亲王纳妃采礼之用。有一件凤脚小腿部发现修理过的痕迹,当为生前使用时损坏的缘故。
2、金钿花16件。用绳形金丝绕成六瓣花彤,最宽处为1.7厘米。原为凤冠上饰物,凤冠腐烂只剩下这些金钿花及一些珍珠。
3、金簪3对。一对出于朱祐槟头部,呈圆钉形状,通长7.8厘米。二对出于彭氏头上。一对簪花为梅花形,脚切面为圆形,通长7.6厘米。另一对簪头为伞形,脚切面亦为圆形,通长11.2厘米。脚款:“银作局弘治六年十月内造金五钱。”
4、金挖耳1件。首部为圆勺形,脚部为圆钉形,通长8厘米。
5、金耳环1对。上部以径粗0.2厘米金丝扭成“2”字形,下部以细金丝扭成五边形。五边形顶端用金丝绕一旋形小圆饼两边各饰一朵五瓣花形的绿宝石。下边金丝绕成“X”形,从现象观察,上面应有饰物,但已朽腐,通高9.3厘米。
6、金鬓花1对。正面呈云状纹,背面素平。有一脚向上直伸。云纹正中镶红、蓝宝石一枚,通长13.9厘米。7、金扣花分为三种。(1)大扣花2副,每副由两只蝴蝶组成采花图案。雌的头部饰六瓣花形一朵,每瓣镶一宝石。雄的头部镶宝石一颗,扣合的成为花蕊。蝶身及前后翅膀上共镶宝石五颗。通长7.9、宽3.4厘米。(2)中扣花7副半,呈蝴蝶采菊花图案。雄者头部镶一宝石,蝶身各镶一宝石。通长5、宽2.2厘米。(3)小金扣6副半,亦呈蝶恋花形状,但不镶宝石。长2.3、宽1厘米。另有小金扣一件,呈圆球形,有钮,径0.7厘米。
8、金香囊1件,以金叶二片外锤压成半椭圆球状,有如倒置的心脏,球面楼刻飞凤图案。囊上有钩,钩上刻缠枝纹。通长15.8、宽7.8、厚5厘米。
9、金片4件,形如磐,中镂空呈栏杆形状,为缀带上的饰物,宽4.4,高2.6厘米。
10、玉佩2副,一副为叶形玉片和菱形玉块组成,另一副为玉片和玉珠组成,玉片上阴刻云凤图案,玉珩上有长7.5厘米的金钩,钩内阴刻“银作局弘治六年十月内造金伍钱”等字,复原后,通长74.5厘米。其形制与《明史》及《三才图绘》上诸王冠服图所载近似。
11、玉饰22件。其中玉绶花1件,镂刻宝相花坟,宽7、厚0.3厘米;玉人2件,长6.4、厚1.8厘米;玉羊2件,最宽处7.2,厚0.8厘米;玉鱼2件,长7.1,厚0.7厘米;玉泥鳅1件,长1.2,头高2厘米;玉鸳鸯4件,长3.1、高1.6,厚0.8厘米;小玉鱼4件,长3.1,高12,厚0.8厘米;玉坠珠6件;2件为辣椒形,通高4、径1.5厘米;4件为圆茄形,通高2.8,径1.6厘米。顶部俱缀以金叶。
12、玉带1副,白羊脂玉。素面无纹,出土时环列于朱祐槟腰部,共20块。宽俱为4.8(只有正面中间一块为4.9)厘米,厚均为0.65厘米,长度为6.9(5块)、8(2块)、6(1块)、6.55(2块),2.2(2块),1.95(2块)厘米。心形6块,宽4.6,长4.9厘米。13、玉圭1件,色呈豆青。出于彭氏头部左侧,宽5.1、自尖至底边长15.2,厚0,8厘米,两面均刻五行圆泡,即所谓“以聘女”之谷圭。
14、铜镜1件。径15.6厘米,圆纽,只有六道凸弦绞,出土时置于彭氏棺盖上。
15、铜钱30枚,除4枚为“永乐通宝”外,俱为“宜德通宝”。出土时散置棺台和后室地面。
16、谥册1件,置于后室棺台东边15厘米处的石座上之红漆小木箱里。箱高26.5,宽3.5、长35.7厘米,木质已朽,只剩漆皮保持箱形,箱上加铜锁。箱中另有一涂金小木匣,亦朽烂。匣中藏谥册,册为木质,上阴刻溢文,烫以金粉。因腐朽,仅能辨认:“……者殁必有谥,爵以贵其身,谥以表其行……善循理,早著贤…福寿之兼备…眷念亲……溢曰端…克歆……日工部造”等字。据《南城县志》卷9所载,此溢册全文应为:
“制曰:朕先王之典。生有爵者,殁必有谥。爵以贵其身,谥以表其行。此古不易之常道也。叔父益王,乐善循理,早著贤誉。宜福寿之兼备,以光重于藩邦。乃疾痰庚婴,药石弗效,倏闻长逝,痛闻长逝,痛何可言!眷念亲贤,宜申册命。兹特谥曰:端,灵爽不昧,庶克歆承。日工部造。”
17、圹志2副:皆用皤石制成(朱志略呈青灰色,彭志较白)。每副2块,篆盖,志文各一,相对合并,外套以铁箍二道。朱志每块76.5×76.2×17.5厘米,彭志76.1×76.3×10.7厘米,篆盖,志文四周均无花坟图案。
18、陶仪仗俑110件:用灰色陶土模制加工而成,肩部以下用模子压印成中空的筒状,然后刻划衣纹束带,并乘湿将手弯曲成各种姿态,头部多为手制,再用漆调石灰作黏合剂插在肩上。窑烧后再加彩,脸部涂白粉,再绘以眉须眼目,口唇涂朱,衣服亦多施朱红,出土时多褪蚀。这批仪仗俑分六行排列于棺台前面的地上。按其身份大致可分为骑马乐俑、仪仗俑、吏俑、男女乐队俑,轿夫俑,男女侍俑等六种,
①骑马乐俑10件。通高23厘米,戴尖顶圆帽,穿长衣,束带,着靴。其中六件一手上举平肩,一手搁置大腿上。另两件为一手平肩,一手及于腰部。手上均有所持,因腐朽不明器形,另一件两手置于肚前,似为打小锣者。另一件两手拱于口前,鼓腮努嘴,应为吹唢呐者。
②仪仗俑27件。通高21.1厘米,俱身穿长袍,束带。其中头戴无梁黑冠双手拱于胸前者16件,头戴五梁冠双手拱于胸前者2件,头戴风帽者5件其中2件为一手平胸,一手扶带,其余三件均拱手胸前。头戴老人巾者4件,均一手平胸,一手扶带。以上各俑手中皆有圆洞,原插有本质器具,因俱腐朽,不明器形。推之当为亲王仪仗规定的骨朵、立瓜、旗刀戟之类。
③吏俑14件。通高25.2厘米4件,其余高21.1厘米。头戴乌纱帽,身穿红袍,束带,胸背绘有翔风、卧虎等补服图察,袖手拱于胸前。其中有二件面部雕刻五络长须,老态龙钟,似为王府左右长史之职。其余应是王府长史司中的官吏僚属之类。
④男女乐队俑30件,通高20.2厘米。其中女乐俑12件,头梳云髻。身穿短衣,下着长裙。手中乐器多腐蚀,仅能辨认琵琶、三弦、洞萧、拍扳、小鼓数种。男乐俑18件。其中六件为鼓手,头戴红色尖顶圆帽,身穿长衫,束带,四人胸前挂一扁鼓,双手执槌作敲打状。二人一手执小板鼓,一手执鼓槌。鼓上均绘有梅花图案;其余12件,头戴平顶帽,帽前着一花朵,身穿长袍,腰间束带,手执琵琶、洞箫、拍扳等乐器。
⑤轿夫俑16件,通高20.1厘米,头戴风帽。身穿长衣,腰间束带。八人合抬一轿,一手扶杠。一手垂于身侧。另八人一手扶杠,一手扶带。轿系木质,出土时已腐烂。
⑥男女侍俑13件。男侍7件,2件高21.3厘米,头戴乌纱帽,身穿长袍,束带,双手捧水罐。5件高20厘米,戴尖顶圆帽,长衣,束带,双手中执物已佚。女侍6件,云髻,长衣,束带,双手拱于胸前,器物已佚,通高20厘米。
明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镇压人民反抗,用榨取来的人民血汗,豢养了一批仪仗侍卫,走狗爪牙,出门时前呼后拥,一唱百诺,借以壮胆,用以吓人。即所谓“明制度示等威”“慎出入远危疑”。因此亲王和亲王妃的仪仗就多达112人。上述110个陶俑就是朱祐槟生前拥有众多奴仆、炫耀封建淫威的反映,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色厉内荏,虚张声势,害怕人民的纸老虎本质。就艺术价值而言,这批陶俑的主要成就在于人物性格的刻划,雕塑者仅以简单的线条表现了衣纹折痕,但对人物的脸部却是精雕细刻,力求准确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因而110个陶俑或耸肩哈腰,或挺胸凸肚,或温文尔雅,或骄横跋扈,不但老少胖瘦各不相同,神情风貌也是因人而异。刀笔纯熟刚劲,线条简洁流畅,反映了明代雕塑工艺的高度水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个男侍俑形象:上身前倾,下腹微收,右手握拳,左手拂袖,浓眉暴眼,气势汹汹,雕塑者用简炼而又夸张的刀笔把一个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地主走狗的形象,刻划得维妙维肖,不但显示了雕塑者具有高度艺术概括能力和雕塑技巧,而且也表现了饱受朱祐槟蹂躏的雕塑工人对地主阶级强烈的阶级仇恨。
(四)关于墓主
明代,江西境内共有三藩。南昌一带是宁献王朱权系统的势力范围。鄱阳湖一带是淮靖王朱瞻墺系统的势力范围,南城一带则是益端王朱祐槟系统的势力范围,其中益王一系延续到清初才覆灭,统治江西一百四十几年。明代江西人民除了要受当地的官府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外,还要受这三大藩王的直接榨取,苦难格外深重。因此研究三藩在江西的罪恶统治是研究明代江西阶级斗争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益王朱祐槟墓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批资料。
朱祐槟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六代孙,宪宗皇帝第四子,生于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九岁(成化二十三年)被封为益王,十七岁(弘治八年)就国江西建昌府,死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统治建昌府达四十二年之久。
朱祐槟是一个骑在江西人民头上贪婪残暴的统治者。“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朱祐槟仗着皇室淫威,凭借这些封建特权,肆无忌惮地压榨广大贫苦农民。据《南城县志》记载:当时南城一带农民的负担是极为沉重的。他们每年除了缴纳田赋(秋粮、夏税)课程(商税、茶税,盐钞,门摊)等奇捐重税外,还要献纳茶芽、鹇鸡、野鸡、活兔、羽毛、杂皮、蜜饯、冬笋、腌腊、药材、弓箭弦、红铜、黑铅、棕蘑等物,称之为职贡。此外还要服繁重的徭役(正役、均徭、驿传、民兵,谓之四差。)“奸臂猾里,放富差贫,名为均徭,不均实甚。”这些劳动人民的血汗多半是用来满足王府庞大统治机构穷奢极欲的,林俊在《论宁府用琉璃硫》中曾提到:“益府宫殿蚁蠹,益殿下见移东寝……修盖之安,约三万余两。”当时南城县每年的田赋是24719两8钱。也就是说南城县农民一年缴纳的赋还不够益府修一次房子。因此连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江西赋税苛杂、徭役繁重,乃是王府残酷剥削的结果。“江西自弘治以来(朱祐槟就是弘治八年到江西来的)赋役渐繁” 、“三藩盘建江省肆米供繁,此赋额渐加之由也。”、“迨宗藩日盛,而役益增。”以致“江西公私匮竭,人民滋困。”朱祐槟是一个疯狂榨取农民血汗的大地主。按照明代规定,亲王占有土地十万亩,加上郡主的土地以及他们子孙的坟地和护坟地,朱祐槟一家所占的土地总数在十七万亩以上,这些土地的租税全部归益府收入充作禄米。朱祐槟家族对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横征巧取进行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租额之高,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当时官府租税以谷折钱的标准是“每谷五石,作银一两”,但是“江西各王府收受禄米,每石用银一两陆柒钱(较官定标准高八倍)”,并且这样高的租额,在灾荒年月也毫不减免,因此“小民田苦:要行禁冶,……但王府地方司府等官既畏惧而不能阻违,巡抚巡按亦推避而不肯究治”,广大农民在这种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铤而走险,拿起扁担锄头进行武装反抗了。
朱祐槟又是一个残暴屠杀农民、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建昌府的贫苦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仅在朱祐槟盘踞江西四十二年之间,就前仆后继,先后爆发了十一次农民起义,攻打广昌、南丰、南城等县,活捉击毙四个知县,消灭大量反动官兵。“地方震动,亲藩惊恐”,沉重地打击了明代封建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显示了中国人民酷爱自由勇于革命的英雄本色。朱祐槟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调动了大量反动军队,疯狂反扑,残酷地镇压农民,实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政策。仅南城一县,在朱祐槟统治期间,人口就由173782人减少到154465人。
朱祐右槟还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大骗子。他为了掩盖其屠杀人民的血腥罪行,麻痹人民的斗志,搞些小恩小惠,故意装模作样地“每日一素食,以清神思”,“精制丸散,每给赐以活人”,甚至连临死之际也要骗人,假惺惺地“命不藏金玉,嚣用惟陶瓦而已”。于是他儿子朱厚烨就大肆标榜,肉麻地吹捧他“裁省浮费,一遵俭约,禁兵卫毋夺于市,戒校官舞虐于民……居常不事浮夸,巾服浣至再,性不嗜酒,膳不兼昧”。封建史学家也跟着学舌,美化他;“性俭约,巾服瀚至再,日一素食,好书史,爱民重士,无所侵扰。”(《明史·益王传》)。竟然把一个荒淫残暴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乔扮成“爱民重士,无所侵扰”的救世主!现在,朱祐槟墓被打开了,人们发现墓中埋葬的尽是金玉,器用并无陶瓦。朱家设下的历史骗局被揭穿了,被颠倒的历史终于复原过来。
(执笔:陈文华,原题为《江西明益王朱祐檳墓發掘報告》,原载《文物》1973年第三期)
相关人物
陈文华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抚州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