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人文综述
| 内容出处: | 《抚州市志:全5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40220020220000016 |
| 颗粒名称: | 抚州人文综述 |
| 分类号: | K290 |
| 页数: | 7 |
| 页码: | 12-18 |
| 摘要: | 抚州自古为江南名区。市境环山面湖、水系如网,腹部平原沃野如膏。唐代时,农业已趋繁荣,殷实之家供子弟读书入仕渐成时尚。宋代,州治所在地临川县因科举连捷而被称为“人才之乡”。至明代,“临川才子金溪书”民谣已在远近传开。其时,域内各县皆文风昌盛、英才迭出,历千年而不衰,抚州因之享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盛誉。 |
| 关键词: | 抚州 人文 |
内容
抚州自古为江南名区。市境环山面湖、水系如网,腹部平原沃野如膏。唐代时,农业已趋繁荣,殷实之家供子弟读书入仕渐成时尚。宋代,州治所在地临川县因科举连捷而被称为“人才之乡”。至明代,“临川才子金溪书”民谣已在远近传开。其时,域内各县皆文风昌盛、英才迭出,历千年而不衰,抚州因之享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盛誉。
一、人才渊薮源远流长 赣抚大地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家给人足,蓄藏无缺”的物质条件为人才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抚州人才渊薮可追溯到南朝,是时海内纷争,诸侯争霸,战事频仍,域内黄法氍、周迪、周敷及周续等豪酋崛起,首次以群体方式登上历史舞台,无不仕至州牧,在南朝梁陈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黄法氍“劲捷有勇力,颇便书疏。”是个孔武有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西晋“永嘉之乱”到唐代“安史之乱”,关中及河南、河北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北方士人纷纷南迁,正如李白所描绘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晚唐黄巢农民大起义后,中国再次进入藩镇割据局面,抚州先后为吴、南唐辖地。相对于北方饱受战乱之苦而言,南方的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加之吴、南唐政权均采取保境息民政策,各于境内劝课农桑,招徕商旅,使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危全讽治理抚州27年,对外结交豪强,招抚流散;对内保境安民、轻徭薄赋、劝励耕织,大行修州衙,筑城池,兴儒学,弘佛教之善举,使临川成为“翳野农桑、俯津阗阌,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的“名区”;南城也是“人繁土沃,桑耕有秋。学富文清,取舍无误。既状周道,兼贯鲁风。万户鱼鳞,实谓名邑。”富庶的经济条件和安宁的政治环境,对北方深受战乱煎熬的士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纷纷落籍抚州。如宋代宰相晏殊远祖为“有姜之裔,齐为晏氏”,曾祖晏延昌“徙其籍于临川”;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氏姒姓,其先鲁人”,高祖曾展成“为南唐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受遣至南丰为县令,始籍南丰”;宰相王安石“其先出太原”,曾祖王永泰“游览山川,慕其地之善,遂徙寓于此,故为临川王氏之祖”;地理学家乐史,其父乐璋原籍河南,因“朱温扰京兆,乃游仕江左,为抚州临川丞,籍居临川”,后因弃官居家,上大华山进香路过宜黄霍源村,见其“风景秀丽,乃举家迁移于此落户”。哲学家李觏,其先祖本系南唐宗室,始封临川,后徙金溪、泸溪(今资溪)、南城。这些家族都是有一定经济、政治实力的望族,本身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文化积累。他们迁徙来的不仅是家庭和人口,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鲜的北方文化空气。先进的北方文化与抚州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交流,推动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迎来了两宋人文荟萃、名贤辈出的空前盛况。
人才的兴起离不开完善的教育体系。《宋书·礼志》记载,早在晋穆帝永和年间(公元345—357)“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可知此前临川郡曾设立过学校。南城县于“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始诏立庙”,表明正式设立官学。落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有赖于有声望、才干、勤政的地方官,唐大历三年(公元768)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临川学子杨志坚家贫如洗却嗜学如命,其妻耐不住贫困生活,提出离婚。杨以《送妻诗》明志:“平生志业在琴诗”,颜真卿欣赏其苦读精神,赠以布匹、粮食,留其在署中任职,对抚州良好学风的形成起了导向作用。唐末五代,危全讽治理抚州期间大兴儒学,于天复二年(公元902)在抚州城设立文宣王庙,置州学,设文学、助教掌教育之职。在此良政鼓舞下,宜黄罗坚于天祐年间(公元904—907)赠田棠阴,建湖山书院,首开抚州创办书院之先河。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战乱,为防止分裂割据局面重演,宋太祖赵匡胤采取轻武功,兴文教的政策。咸平三年(1006)在临川县置儒学,设主学一员管理教育行政。有宋一代,先后掀起过晏殊、范仲淹“庆历兴学”,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大兴学校,及徽宗的“崇宁兴学”3次兴学高潮。同时,把教育与科举紧密联系起来,规定凡应举士子必须接受学校的系统教育,学满300天方准许参加科举考试。于是求学士子趋之若鹜。在朝廷的倡导下,庆历四年(1044)抚州知州马寻在危全讽建立的儒学基础上充实教师队伍,扩大办学规模,定120人掌诸职事。宜黄当时尚未设立官学,学子得跋山涉水到百里之外的抚州就学,皇祐元年(1049),宜黄县令李祥倡议立县学,立即得到县人的热烈响应,“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此后各县纷纷兴办官学,广昌、新城、乐安3县在建县之初即相应设立儒学。元、明、清三代,朝廷在发展官学的同时,扩大民众受教育面,在各地农村设立社学,开展启蒙教育,规定50家为一社,要求“每社设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除官办教育机构外,私人出资创办的各种家塾、义学、蒙馆在域内城乡普遍设立。同时还大量兴办更高级的教育机构——书院。由于宋代皇帝立下不杀读书人的誓言,士人有了言论自由。一些文人学者遵循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箴言,或隐居山林,或回归乡里,一面读书自学,修身养性;一面招徒讲学,著书立说。于是出家资而立学馆,因胜地而建书院,私人创办书院风气兴起。宋代乐史办有慈竹书院、曾巩办有兴鲁书院、李觏办有吁江书院、陆九渊办有槐堂书屋、傅梦泉办有曾潭讲堂、瞿元肃建有华林书堂;元代吴澄创办草庐书院,虞集建有东湖书院;明代吴与弼建有小陂书院,饶秉鉴建有雯峰书院;清代建有青云书院、凤岗书院等。两宋时期,全国有书院400余所,其中江西140余所,而抚州域内见诸史籍的有40多所,足见书院之盛。
朝廷在修建州(府)县学的同时,创立学田制度,不仅诏给诸州学田10顷,还下令将“民间绝户田产俱入学赡士。”除赐田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私人捐赠,对州(府)县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其中,抚州州学学田年收米2488石,绢119匹,钱78.33万文;临川县学学田每年收租米431石,租绢8匹9尺。随着办学机构的完善,州(府)县学对学生入学资格逐渐放宽,教育对象不断扩大,教学内容增设了武学、画学等学科。教育离不开教师。由于私学教师在学行方面都是有威望或在乡里为人所敬仰者,于是上至知州,下至儒生纷纷加入教师队伍。如宋代抚州知州黄震多次在州学和临汝书堂讲学,在其所著的《黄氏日钞》收录了两篇讲义——《抚州辛未冬至讲义》《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临川人陈南仲“以六经授徒于乡”,艾性精通经学,“阖门教授,执经者盈门”;明代徐奋鹏“讲学授徒,四方裹粮问业,履填户外”。
宋代开始扩大开科取士数额,通过教育达成仕进已成为士民的共识,在这一社会主流价值的驱使下,读书识字人数急速增加,形成基层社会的优势群体。于是抚州各地“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昝,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形成“地无城乡,家无贫富,诗书之声,尽室皆然”的社会风尚。不仅男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仕族之家妇女受教育的人也不少。宋代王安石外祖母黄夫人“喜书史,晓大致”,其母吴氏“好学强记,老而不倦”。何师韫著有诗文40卷;南丰曾布之妻魏玩被朱熹称赞为“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李易安二人而已”;明代南城景翩翩“博学能文,工诗善曲,名扬当时”;清代宜黄邹含光“幼时好静喜读书”“日夕诵读经史”。
自宋至清抚州域内登文科进士达2450名,占江西省总数的23%;登武科进士者91人。历代科举中,登三鼎甲者有17人,其中,状元5人,榜眼10人,探花2人。父子同科、五子登科、一门多士者比比皆是。如临川王氏10进士,晏氏9进士,蔡氏、饶氏8进士;宜黄乐氏8进士、涂氏5进士;南城陈氏9进士、黄氏家族6进士;崇仁熊氏7进士、吴氏6进士。其中,南丰曾巩家族出进士29名,乐安董淳逸家族出进士27名。宋明道三年(1034),董其5子同榜及第,“五桂齐芳”佳话一时令朝野轰动、公卿咋舌。两百年后,文天祥《谢恩表》中有“花耀贴金,一门而五董”之典。抚州不但人才众多,而且有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巨星泰斗交相辉映。自五代至明,任宰相者7人,任副相者10人。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恢复高考以后,抚州秉承崇文好学优良传统,各级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基础教育迅猛发展,临川教育集团成为抚州一张熠熠生辉的名片。抚州的优质教育资源吸引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学子前来就读,各级各类学校共向全国高等院校输送38万名优质生源。少年大学生约占全国1/10。解放军中有中将1名,少将3名,学界有两院院士7名。抚州英才领航国内各高端领域,遍布世界各地。真可谓“花光柳色今何限,更有才人胜古人”。
二、人文景观异彩纷呈 初唐大诗人王勃写下“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名句,但当时抚州著名才士尚不多。晚唐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抚州在全国地位上升,“人杰地灵”优势初露端倪。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抚州占有重要位置。仅宋一代,就出现李觏、王安石、陆九渊等一批哲学大师。李觏从“阴阳二气会合”观点出发,说明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认为挽救失误、克服弊端最好办法就是变革;王安石继承和发展李觏哲学思想,树立“万物皆变”观点,倡导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陆九渊汲取儒学和佛教禅宗思想,以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哲学命题,创立影响深远的“心学”体系。元代理学家吴澄糅合程朱理学和心学创立“草庐学派”,是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被誉为“国之名儒”,与许衡并称“南吴北许”。明代吴与弼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主张天理与人道合一,创立“崇仁学派”,从学者数百人。罗汝芳参与创立“泰州学派”,对汤显祖的戏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他们都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引人注目的篇章。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临川之笔”更是熠熠生辉。宋词是中华文学艺术瑰宝,抚州词人则是构筑宋词艺术大厦的顶梁柱。两宋期间,全国共有词人876人,其中抚州籍有44人。晏殊之词“风流蕴藉、一时莫及”。晏殊之子晏几道擅长词中小令,后人评价他“把我国令词推向了顶点”。晏氏父子被公认为宋词“四大开祖”之二。晏殊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同样惊人,仅其汇编成册的诗就有1万多首。在宋代诗坛上,抚州籍谢逸、谢蘧、汪革、饶节均为“江西诗派”首领,领一代风骚而为后世文人所推崇。
唐宋期间,中国有过两次倡导“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这是对先秦以后骈体文的重大革新。在领导古文运动的“唐宋八大家”中,抚州有曾巩、王安石两家。千余年来,曾、王佳作一直被视为文中典范。
元代,中国杂剧步入繁荣,而明代汤显祖则把中国戏曲推上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他创作“临川四梦”声震世界曲坛,与莎士比亚并称为“东西曲坛伟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世界100位文化名人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在书画领域,抚州巨匠辈出。晋代“书圣”王羲之在临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其“以精力自致”的进取精神与其后抚州刺史颜真卿的书法精神一道,滋润着抚州一代代书法英才:宋朝晏殊、王安石、赵崇幡、陈景元、曾纡,元朝程钜夫、吴徵、虞集、饶介,明朝危素、胡布、宋季子、程南云、吴余庆、王英,清朝赵世骏、吴铸、李瑞清,当代“党内一支笔”舒同等,均在中国书苑留下光彩照人的墨宝。
抚州也不乏驰名海内的丹青妙手。宋代临川画家陈容以擅画龙虎著称于世,其传世杰作《九龙图》曾被清朝乾隆皇帝视为奇珍。明代金溪画家吴宏以擅画山水竹石名噪海内,为“金陵八大家”之一,大量作品流传至今。清代乾隆帝亲自命题考画,将乐安袁国栋录为第一,时人称之“画状元”。清末民初李瑞清既是杰出书画家,又是艺术教育拓荒者。他首开国内美术、音乐教育课,并亲自培育出张大千、张善行、胡小石、吕凤子、姜丹书等一大批著名画家。
中国历史文化大厦由史文化、志文化和谱文化三根支柱支撑,抚州历代有不少名儒巨宿参与国史和地方志书编修。乐史是宋代杰出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其编著的《太平寰宇记》200卷是继唐代《元和郡县志》之后的一部采摭繁富的地理总志,时称阅此书可“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曾巩典修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5朝国史,并校定南齐、梁、陈3书。撰修宋、元、明、清4代实录的抚州籍人士有程钜夫、危素、吴当、程南云、何中、李来泰等12人。南宋时崇仁吴曾史作甚多,均为学界所重,其《能改斋漫录》堪与洪迈《容斋随笔》媲美。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虞集,主修《经世大典》880卷;朱思本绘成的《舆地图》“方位不爽毫厘”,是中国制图史上的创造。明代吴溥是世界最早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副总裁;徐奋鹏撰著《古今治统》传至日本,被视为“资治之妙药,兴国之良方”。清代直隶总督、方志大家李绂主编《八旗通志》《广西通志》,自撰《西江志补》《抚州府志》,并创立完整的方志理论体系。南丰籍吴宗慈是近代方志界一颗巨星,以强烈爱国敬业精神,在日本侵略军炮火下编修《江西通志》,为后人留下宝贵精神、文化遗产。抚州素称“文献之邦”。历代乡贤著述汗牛充栋,被选入《四库全书》目录有206种,后人著作更十倍于前。外地文人、作家关于抚州的诗文和著作也很多。台湾至今还有以“临川文献”命名的刊物。在古往今来的抚州文献典籍中,地方志为数不少。域内修志始于南朝荀伯子撰《临川记》,州、县修志至宋始兴。宋、元、明、清4代,抚州共编纂地方志书140余种,共计2000余卷,是一方历史文化的生动记录和重要组成部分。抚州民众历来聚族而居,以绵世系,衍宗支,昭祖训,明嫡庶的族谱家乘编纂,从宋代至今绵延不绝,数量众多。
抚州中医药文化根深叶茂。域内历代多名医,各类史志书籍载有名医200多名。江西历史上十大名医中,抚州籍有7位。这些名医大都有高深文化素养,不少人曾中举人、进士,因不附时俗或仕途坎坷,从而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壮志善愿,或世代传承,发扬家学,或精心钻研,终成一代良医。良医传世不光是起死回生的精湛医术,更宝贵的是高尚医德医风,不附权势,不贪名利,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宋代名医陈自明在其医著中提出“存仁心,通儒道,莫嫉妒,勿重利”等医家要旨,其所著《妇人大全良方》直到清朝仍被视为“妇科圣典”。骨科名医危亦林使用乌头、蔓陀罗为麻醉药,比日本医圣华冈青州早450年,创立悬吊正骨法比英国达维斯(Daris)早600多年。曾被明朝万历皇帝赐为“医林状元”的龚廷贤在治愈鲁王爱妃重病之后,拒收千金之酬,只求将自己的医著刊行于世,以便培养出更多良医。清代名医谢星焕,坐堂看病不收酬金,每年还给家乡百姓赠送“金不换正气丸”以防时疫。在“医药不分家”的中医传统作用下,抚州古代中药业十分繁荣,历史悠久的建昌药帮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樟树帮同扛中华药业大鼎,海内共传“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经建昌不行”。自然科学领域中有不少抚州英才,如北宋水利专家侯叔献、音韵学家陈彭年,明代天文学家吴伯宗,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揭暄等,都是当时科学家中佼佼者。
历代抚州人才中,更有不少见高识广、智勇双全的能臣良吏。晚唐时,南城危全讽任抚州刺史,一面安抚士民,奖励垦荒,发展经济,一面建孑孔庙,兴州学,倡文事,揽人才,延请本寂、匡仁、园照、文偃等禅宗高僧主持寺院,使抚州不仅“人繁土沃,桑耕有秋”,而且“学富文清”“既状周道,兼贯鲁风”,吸引了北方大量人士南迁抚州,为抚州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宋代,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等,更是政绩卓著的一代贤臣。还有屡挫金兵、保境安民的邓州通判饶廷直,元代极力建议朝廷修筑海堤、捍水为田的翰林直讲学士虞集,明代威丧敌胆的抗倭名将谭纶、傅良桥,清代禁烟名臣黄爵兹,外交能臣黄维翰、吴奇,兴修水利、力劝农桑、重教兴学政绩斐然的陇西知县应先烈,治政有方、不畏强权、依法惩办和坤亲属的御史谢阶树,胸怀韬略、屡建战功的民国骁将欧阳琳等,他们超凡的业绩向世人昭示出抚州才子的魅力和风范。
抚州宗教文化得天独厚。南城县麻姑山被誉为“洞天福地兼而有之”的道教圣地,麻姑在此得道成仙、三见沧海化桑田的传说更是妇孺皆知。颜真卿亲撰《麻姑山仙坛记》为此处道教文化增添色彩。宋代曾有5位皇帝颁敕令加封麻姑。乐安华盖山亦是著名道教胜地,宋代4位皇帝封华盖山仙神“真君”尊号。直到清末民初,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信徒从省内及闽、浙、湘、皖前来“朝华”。唐代,南城道士邓紫阳佐玄宗退西戎兵,被称为“神人”;宋代,抚州高道辈出,南丰人王文卿创立“神霄派”,临川人饶洞天创立“天心派”,影响及于朝野。西晋前期,佛教已传入抚州。南朝谢灵运在临川宝应寺设翻经台翻译佛经。唐末五代,宜黄曹山寺本寂禅师创立曹洞宗广传海内,远播日本。南禅五叶有曹洞、法眼、云门3宗源于抚州。法眼宗被称为“汝水之灯”,抚州被称为“天下禅河中心”。域内名寺、高僧众多。明代崇仁人宗泐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南城人行保,被列为“天下高僧十一人”;崇仁人慧经“躬自作务,力田饭僧”40年,拒绝官僚王公布施,保持了寺院经济独立,成为曹洞宗中兴祖师。民国初年,宜黄欧阳竟无、临川李证刚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
新中国成立后,抚州人才不少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蜚声海内外者,有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有被毛泽东称为“红军书法家”,“舒体”创始人舒同,有解放军第一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黄火星。创业于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大有人在:中国物理学“四大名旦”之一饶毓泰,著名文学史专家游国恩、肖涤非,首次提出将激光用于受控热核聚变的丁渝,创立中国高校首个道路工程专业的陈本瑞,首倡成立西北风能研究所并任名誉所长的邓慎康,研制旋转导弹激光导引取得重大成果的物理学家周仕忠,撰著中国首部《土壤学》的著名专家王云森,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筹委会执行主席鲁之俊,等等。
今日抚州人才更广泛地分布在世界各地。改革开放以后,抚州在英、美、日、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人数大增,其中攻读博士、博士后的有500余人。在海外建功立业的著名人士不胜枚举,南城黄天中历任美国数家大学副校长、校长,并且是美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任华人校长。在日本担任原子控制研究员并兼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的中年科学家黄德欢,同时又是名闻世界的纳米技术专家。黎川籍全国著名女歌唱家余珊鸣足迹和歌声遍及整个欧洲。
三、文化积淀丰富深厚 域内现存古迹众多,分布面广。广昌县出土的中生代白垩纪恐龙化石,被央视新闻联播称为“广昌恐龙——中华之最”。临川、乐安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有31处,商周时期遗址在域内各县区均有发现,出土文物众多。人类的文化遗迹不仅出现在陶器、铜器和铁器上,在固态的石体上也有发现。广昌赤水摩岩石刻古文字符号,尚待破译。隋唐开始,域内便有专业生产的瓷窑,全市7个县区19处古代陶瓷窑址仍有不少保存完整。南丰白舍窑生产的青白瓷,以“瓷胎质薄细润,洁白坚滑”,与景德镇窑 、吉州窑、洪州窑、赣州七里镇窑并称为“江西五大名窑”,产品足以与景德镇瓷争价。抚州古墓葬众多,临川抚北镇、广昌甘竹镇汉墓群规模壮观;唐代本寂禅师墓,宋代乐史墓、南丰曾巩墓、金溪陆象山墓,明代南城益王家族墓葬群,临川汤显祖墓、陈际泰墓,宜黄谭纶墓,乐安董裕墓,崇仁吴与弼墓等40余处,至今保存完好。域内现存古寺、古塔、古桥各具特色。临川云山大金山寺,金溪浒湾竦山寺,宜黄曹山寺、石巩寺,南丰县城寿昌寺,广昌龙凤岩清雨古寺,市城区正觉寺等,或寺高殿广、气宇轩昂,或小巧灵珑,选址精妙。南丰地藏菩萨像高6米,为省内最大的石菩萨像。市城区圣约瑟大教堂,为全国三大天主教堂之一。临川石港明代万魁塔、南城聚星塔,宜黄棠阴迎恩塔等,结构独特,造型奇美。唐代临川湖南瑶山双拱桥,五代广昌驿前吁姆桥,明代南城万年桥以及临川文昌桥,是中国古桥建筑的杰作。
各县区古代民居、牌坊、祠堂星罗棋布。乐安流坑村至今依然保持着明代中期格局,街巷纵横交错却井然有序,存有明代建筑19处,清代建筑250处,被称为“中国古代农村文明的典型”“明清建筑艺术博物馆”,石雕、砖雕、木雕、楹联、壁画等艺术品数以千计。此外,金溪竹桥、宜黄棠阴、南城磁圭、广昌驿前、黎川下陈等地古代建筑群落,都凝聚着灿烂的建筑文化。抚州还有众多散落于乡村的巨型建筑——船形屋,如黎川洲湖船屋拥有108间,36个天井,72个地漏,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宜黄县麻坑船屋9间厅堂,18间房间;南城县饶坊船屋有108间,占地10亩;广昌驿前船屋,有大小厅堂、厢房30余间,占地540平方米。这些船形屋的建造初衷,尚待后人破译。
抚州属典型江南农耕文化区,数千年间,人们崇尚世代同堂。宋代金溪陆氏“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爨将二百年”,明代南城吴焕“八世同爨,至二百余人”。各村落以宗族为单元相聚而居,至今仍保存有大量规模宏大的宗祠,人们秉承长幼有序、守信重义、忠孝传家的儒家礼法。为官者多崇尚正义、刚直不阿,热心除暴安良、为民请命。工匠商人大都有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诚信无欺、取财以道的职业道德。在农耕文化浸润下的抚州人尤其热爱家乡、眷恋故土,并由此延伸为浓厚的爱国之情,即使在身陷困境时,也牢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明万历年间临川商人朱均旺被倭寇掳至日本为奴,当他得知日本欲派兵侵犯朝鲜和中国后,3次冒险偷渡回国报信,使明朝政府及时作好准备与朝鲜联合出兵,歼灭来犯侵略军。
抚州民间文化艺术多姿多彩。被称为“中国舞蹈艺术活化石”的傩舞,自汉代陆续传人南丰、乐安、宜黄、黎川、广昌等地,至今仍为群众所喜爱。南丰傩班多次应邀到日本、美国、新加坡演出,该县被文化部命名为“傩舞之乡”。抚州灯彩极为丰富,龙灯、狮灯、跑马灯、罗汉灯、踩高跷等,每于春节期间一展风采。民歌、山歌、船歌、莳田歌、采茶歌、伐木歌风格各异。抚河沿岸,端午节赛龙舟之俗久传不衰。富有地方特色的稻作文化、桔文化、莲文化、夏布文化为抚州农耕文化增添丰富的内涵。
在灯彩、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抚州戏曲艺术历史悠久,北宋时,域内已有“杏楼”“瓦舍”等演出场所。宋末,吁河戏、抚河戏、宜黄戏均已崭露头角。兴起于清代的“三角班”迅速发展成地方特色鲜明的抚州采茶戏,百余年来风靡城乡,在江南艺苑中独树一帜。
抚州革命传统文化尤为珍贵。早在1919年,临川学生就积极声援“五·四”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中央苏区的创建、扩展,广昌、南丰、宜黄、乐安、资溪、黎川、南城、金溪、崇仁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组成部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抚州领导军民开展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进行过第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浴血战斗。很多老人至今还能演唱当年革命歌谣,还保留着红军用过的物品。抚州到处有革命文物和革命故事,与苏区精神一起 ,汇成光前裕后的苏区文化,永远是激励中华儿女爱国爱乡、奋发进取的精神资源。
四、文化创新继往开来 抚州人历来富有创新精神。宋代中期,李觏就曾大胆提出“言利”“言欲”的合理性,反对虚伪道学。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变法图新,成为11世纪中国杰出的政治改革家。陆九渊突破朱熹僵化的“格物”理论,创立肯定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心学”。汤显祖更是针锋相对地向封建儒学和礼教宣战,响亮地喊出“世总为情”的口号,并写出大量“情”战胜“理”的作品。然而,这些先贤的创新精神终因时代局限或社会桎梏而被窒息,或只能成为涓涓细流。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文化创新指明方向并开辟道路。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文化主人,清除剥削阶级腐朽文化,用社会主义占领城乡思想文化阵地。同时,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文化。50年代初,域内各县(市)就普遍兴建文化馆、站,组建专业文艺宣传队伍,崭新的群众性文化空前活跃。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下,传统文化被当作“四旧”破除,大量珍贵文物和文化遗址被摧毁。域内原有的14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7个被毁,其余7个也受到严重破坏,更多的民间文物被糟蹋。民间文化艺术一概被斥为“封、资、修”而禁绝,人们的思想遭到严重禁锢。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整套教育制度被打乱,教师受批斗,考试被取消,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区域文化蒙受巨大灾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迅速拨乱反正,优良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至2011年底,全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452处。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6个,在保护和整修的基础上开发利用。80年代以后,文化建设和创新的速度明显加快,先后兴建王安石纪念馆、曾巩纪念馆、玉茗堂影剧院、舒同书画院、汤显祖纪念馆,修缮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旧居、旧址,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及文化活动场所。
自80年代始,域内教育改革和创新频传佳音:在合理调整教学网点、切实提高教师素质、努力夯实教育基础、发扬民间办学传统的同时,不断加速教育装备和教学方式的现代化,计算机应用已成为城镇中学及部分农村学校的必授课。学校教育科研活动步步深入,开设“家长学校”“3+1”德育实验、中小学“六环节四步迁移教学法”等一系科研成果在教学中普遍推广,成效显著。域内4所普通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绝大部分被社会采纳,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抚州教育质量多年来保持全国先进水平。教育已成为人才和文化的活水之源。
临川文化是以临川古治为中心,辐射而覆盖当今赣东11个县(区)的区域性文化流派。临川古郡东连吴越,西接潇湘,南控闽粤,北襟江湖,横跨吴、越、楚三地,号称“江西大郡”。先秦时期,赣东属百越之地。据《汉书·地理志下》臣瓒注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赣东处于交趾(今越南境内)至会稽(今浙江绍兴)的中段,这里的原住民是古越族的一支,叫“干越”。唐代颜师古注《汉书·货殖列传》曰:“干越,南方越名也。”当代朱维幹编著的《福建史稿》更明确指出:“干越在今天的赣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已进入农业经济阶段的多数越人逐渐与北方南迁的汉人融合,他们筚路蓝缕,共同开发临川的文明源头。在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和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三次人口大迁徙中,赣东地区融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为临川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至两宋时期,临川文化的主体已基本构成。以抚河为纽带,相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形成临川固有的文化特征。赣东区域远古多沼泽、丘陵,草木繁茂,气候湿润,原住民过着“火耕水耨、饭稻羹鱼”游耕生活。北人南迁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水平,初步形成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物质文化结构,表现为有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勤稼穑、重桑艺的耕作文化;诚实守信、弃自守而进取的商业文化;崇实达理,秀而能文,以诗书求闻达的教育文化;重血缘、聚族而居的宗族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礼仪文化。淳朴的民风孕育出充满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进而形成相同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以及虔诚笃信的宗教文化和保留丰富中原古音韵的语言文化等。千百年来,在较高文化水准基础上形成的临川文学、哲学、艺术、科技、宗教等,涌现出一批有世界影响的文化代表人物。文化的开创离不传承,清代临川李绂在《南园答问》一文中说:“晏临川(晏殊)开荆国文公(王安石),李盱江(李觏)传南丰子固(曾巩);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精辟独到地解读了临川思想家们互相启迪、继承和发展的渊源关系。从宋代逐渐形成的临川文化声誉,一直到清代经久不衰,不仅激发了抚州人民对家乡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使外地墨客文人对临川礼仪之邦、才子之乡抱有敬仰之心,为临川文化灿烂的历史和巨大的魅力所吸引。1992年,中共抚州地委和地区行署根据专家和人民群众的共识,将以临川为中心的赣东区域文化正式命名为“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并列为江西两大区域文化,并成立“临川文化”开发领导小组,对“临川文化”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的研究和开发,把发展教育、文化、旅游、经济结合起来。一批研究、开发临川文化的机构和社会团体相继成立。临川文化研究逐步广泛深入,由单纯对名人、名作的研究,扩展到名人、文学、宗教、民俗、革命传统等多种领域。《临川文化史》《临川文学史》《临川近现代文化史》等全面、系统研究抚州历史文化的新成果相继面世,推出了《抚州人物》以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汤显祖等人物传记专著,点校了《王文公文集》《曾巩集》《李觏集》《陆象山全集》《殊玉词》《小山词》《谭纶集》等名人著作。地、县两级新志书的编修,构建成抚州地情资料的宏大宝库。临川文化也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开展深入的研究。国内著名学者徐朔方、漆侠、石凌鹤等出版30余部临川文化研究专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成为王安石的国外研究中心,出版的研究成果颇丰。汤显祖《牡丹亭》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并搬上德国兰心大戏院。台湾作家白先勇编导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内外演出200余场。日本东京大学、神奈川大学、大阪大学专家学者6次到南丰考察傩文化。宜黄曹山寺吸引了日本佛教史迹考察团参拜祭祖,不仅扩大临川文化的影响,还拓宽了临川文化研究的视野。域内在加强市镇建设、美化、净化环境的同时,重点建设名人文化园、拟岘台、大觉山、麻姑山、流坑村、大金山寺等一批旅游景区、景点,增建大量文化体育设施,汤显祖大剧院、抚州市图书馆、博物馆、体育中心等现代化场馆拔地而起,进一步优化了抚州的人文环境。90年代,多种形式的文化市场不断增加,到2011年,域内共有商业性文化经营场所2189家。文化和经济结合,发生能量聚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厚智力资源和强大精神动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抚州人民加速思想观念更新,摈弃听天由命,“求土不求人”,安土重迁、小富即安、怕担风险等陈旧思想和小农意识,不断增强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珍惜时间、讲求效益、互利互惠、重视协作、见义勇为、乐于奉献已成为抚州区域文化的重要内涵。
跨世纪之际,抚州撤地建市,中共抚州市委、抚州市人民政府提出“创文化名城、建经济强市”,合理开发和利用文化资源,加速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大力培植和发展教育、旅游、艺术等文化产业。抚州文化和经济迈上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全面繁荣新里程。
一、人才渊薮源远流长 赣抚大地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家给人足,蓄藏无缺”的物质条件为人才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抚州人才渊薮可追溯到南朝,是时海内纷争,诸侯争霸,战事频仍,域内黄法氍、周迪、周敷及周续等豪酋崛起,首次以群体方式登上历史舞台,无不仕至州牧,在南朝梁陈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黄法氍“劲捷有勇力,颇便书疏。”是个孔武有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西晋“永嘉之乱”到唐代“安史之乱”,关中及河南、河北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北方士人纷纷南迁,正如李白所描绘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晚唐黄巢农民大起义后,中国再次进入藩镇割据局面,抚州先后为吴、南唐辖地。相对于北方饱受战乱之苦而言,南方的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加之吴、南唐政权均采取保境息民政策,各于境内劝课农桑,招徕商旅,使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危全讽治理抚州27年,对外结交豪强,招抚流散;对内保境安民、轻徭薄赋、劝励耕织,大行修州衙,筑城池,兴儒学,弘佛教之善举,使临川成为“翳野农桑、俯津阗阌,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的“名区”;南城也是“人繁土沃,桑耕有秋。学富文清,取舍无误。既状周道,兼贯鲁风。万户鱼鳞,实谓名邑。”富庶的经济条件和安宁的政治环境,对北方深受战乱煎熬的士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纷纷落籍抚州。如宋代宰相晏殊远祖为“有姜之裔,齐为晏氏”,曾祖晏延昌“徙其籍于临川”;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氏姒姓,其先鲁人”,高祖曾展成“为南唐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受遣至南丰为县令,始籍南丰”;宰相王安石“其先出太原”,曾祖王永泰“游览山川,慕其地之善,遂徙寓于此,故为临川王氏之祖”;地理学家乐史,其父乐璋原籍河南,因“朱温扰京兆,乃游仕江左,为抚州临川丞,籍居临川”,后因弃官居家,上大华山进香路过宜黄霍源村,见其“风景秀丽,乃举家迁移于此落户”。哲学家李觏,其先祖本系南唐宗室,始封临川,后徙金溪、泸溪(今资溪)、南城。这些家族都是有一定经济、政治实力的望族,本身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文化积累。他们迁徙来的不仅是家庭和人口,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鲜的北方文化空气。先进的北方文化与抚州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交流,推动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迎来了两宋人文荟萃、名贤辈出的空前盛况。
人才的兴起离不开完善的教育体系。《宋书·礼志》记载,早在晋穆帝永和年间(公元345—357)“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可知此前临川郡曾设立过学校。南城县于“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始诏立庙”,表明正式设立官学。落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有赖于有声望、才干、勤政的地方官,唐大历三年(公元768)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临川学子杨志坚家贫如洗却嗜学如命,其妻耐不住贫困生活,提出离婚。杨以《送妻诗》明志:“平生志业在琴诗”,颜真卿欣赏其苦读精神,赠以布匹、粮食,留其在署中任职,对抚州良好学风的形成起了导向作用。唐末五代,危全讽治理抚州期间大兴儒学,于天复二年(公元902)在抚州城设立文宣王庙,置州学,设文学、助教掌教育之职。在此良政鼓舞下,宜黄罗坚于天祐年间(公元904—907)赠田棠阴,建湖山书院,首开抚州创办书院之先河。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战乱,为防止分裂割据局面重演,宋太祖赵匡胤采取轻武功,兴文教的政策。咸平三年(1006)在临川县置儒学,设主学一员管理教育行政。有宋一代,先后掀起过晏殊、范仲淹“庆历兴学”,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大兴学校,及徽宗的“崇宁兴学”3次兴学高潮。同时,把教育与科举紧密联系起来,规定凡应举士子必须接受学校的系统教育,学满300天方准许参加科举考试。于是求学士子趋之若鹜。在朝廷的倡导下,庆历四年(1044)抚州知州马寻在危全讽建立的儒学基础上充实教师队伍,扩大办学规模,定120人掌诸职事。宜黄当时尚未设立官学,学子得跋山涉水到百里之外的抚州就学,皇祐元年(1049),宜黄县令李祥倡议立县学,立即得到县人的热烈响应,“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此后各县纷纷兴办官学,广昌、新城、乐安3县在建县之初即相应设立儒学。元、明、清三代,朝廷在发展官学的同时,扩大民众受教育面,在各地农村设立社学,开展启蒙教育,规定50家为一社,要求“每社设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除官办教育机构外,私人出资创办的各种家塾、义学、蒙馆在域内城乡普遍设立。同时还大量兴办更高级的教育机构——书院。由于宋代皇帝立下不杀读书人的誓言,士人有了言论自由。一些文人学者遵循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箴言,或隐居山林,或回归乡里,一面读书自学,修身养性;一面招徒讲学,著书立说。于是出家资而立学馆,因胜地而建书院,私人创办书院风气兴起。宋代乐史办有慈竹书院、曾巩办有兴鲁书院、李觏办有吁江书院、陆九渊办有槐堂书屋、傅梦泉办有曾潭讲堂、瞿元肃建有华林书堂;元代吴澄创办草庐书院,虞集建有东湖书院;明代吴与弼建有小陂书院,饶秉鉴建有雯峰书院;清代建有青云书院、凤岗书院等。两宋时期,全国有书院400余所,其中江西140余所,而抚州域内见诸史籍的有40多所,足见书院之盛。
朝廷在修建州(府)县学的同时,创立学田制度,不仅诏给诸州学田10顷,还下令将“民间绝户田产俱入学赡士。”除赐田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私人捐赠,对州(府)县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其中,抚州州学学田年收米2488石,绢119匹,钱78.33万文;临川县学学田每年收租米431石,租绢8匹9尺。随着办学机构的完善,州(府)县学对学生入学资格逐渐放宽,教育对象不断扩大,教学内容增设了武学、画学等学科。教育离不开教师。由于私学教师在学行方面都是有威望或在乡里为人所敬仰者,于是上至知州,下至儒生纷纷加入教师队伍。如宋代抚州知州黄震多次在州学和临汝书堂讲学,在其所著的《黄氏日钞》收录了两篇讲义——《抚州辛未冬至讲义》《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临川人陈南仲“以六经授徒于乡”,艾性精通经学,“阖门教授,执经者盈门”;明代徐奋鹏“讲学授徒,四方裹粮问业,履填户外”。
宋代开始扩大开科取士数额,通过教育达成仕进已成为士民的共识,在这一社会主流价值的驱使下,读书识字人数急速增加,形成基层社会的优势群体。于是抚州各地“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昝,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形成“地无城乡,家无贫富,诗书之声,尽室皆然”的社会风尚。不仅男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仕族之家妇女受教育的人也不少。宋代王安石外祖母黄夫人“喜书史,晓大致”,其母吴氏“好学强记,老而不倦”。何师韫著有诗文40卷;南丰曾布之妻魏玩被朱熹称赞为“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李易安二人而已”;明代南城景翩翩“博学能文,工诗善曲,名扬当时”;清代宜黄邹含光“幼时好静喜读书”“日夕诵读经史”。
自宋至清抚州域内登文科进士达2450名,占江西省总数的23%;登武科进士者91人。历代科举中,登三鼎甲者有17人,其中,状元5人,榜眼10人,探花2人。父子同科、五子登科、一门多士者比比皆是。如临川王氏10进士,晏氏9进士,蔡氏、饶氏8进士;宜黄乐氏8进士、涂氏5进士;南城陈氏9进士、黄氏家族6进士;崇仁熊氏7进士、吴氏6进士。其中,南丰曾巩家族出进士29名,乐安董淳逸家族出进士27名。宋明道三年(1034),董其5子同榜及第,“五桂齐芳”佳话一时令朝野轰动、公卿咋舌。两百年后,文天祥《谢恩表》中有“花耀贴金,一门而五董”之典。抚州不但人才众多,而且有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巨星泰斗交相辉映。自五代至明,任宰相者7人,任副相者10人。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恢复高考以后,抚州秉承崇文好学优良传统,各级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基础教育迅猛发展,临川教育集团成为抚州一张熠熠生辉的名片。抚州的优质教育资源吸引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学子前来就读,各级各类学校共向全国高等院校输送38万名优质生源。少年大学生约占全国1/10。解放军中有中将1名,少将3名,学界有两院院士7名。抚州英才领航国内各高端领域,遍布世界各地。真可谓“花光柳色今何限,更有才人胜古人”。
二、人文景观异彩纷呈 初唐大诗人王勃写下“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名句,但当时抚州著名才士尚不多。晚唐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抚州在全国地位上升,“人杰地灵”优势初露端倪。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抚州占有重要位置。仅宋一代,就出现李觏、王安石、陆九渊等一批哲学大师。李觏从“阴阳二气会合”观点出发,说明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认为挽救失误、克服弊端最好办法就是变革;王安石继承和发展李觏哲学思想,树立“万物皆变”观点,倡导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陆九渊汲取儒学和佛教禅宗思想,以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哲学命题,创立影响深远的“心学”体系。元代理学家吴澄糅合程朱理学和心学创立“草庐学派”,是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被誉为“国之名儒”,与许衡并称“南吴北许”。明代吴与弼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主张天理与人道合一,创立“崇仁学派”,从学者数百人。罗汝芳参与创立“泰州学派”,对汤显祖的戏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他们都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引人注目的篇章。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临川之笔”更是熠熠生辉。宋词是中华文学艺术瑰宝,抚州词人则是构筑宋词艺术大厦的顶梁柱。两宋期间,全国共有词人876人,其中抚州籍有44人。晏殊之词“风流蕴藉、一时莫及”。晏殊之子晏几道擅长词中小令,后人评价他“把我国令词推向了顶点”。晏氏父子被公认为宋词“四大开祖”之二。晏殊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同样惊人,仅其汇编成册的诗就有1万多首。在宋代诗坛上,抚州籍谢逸、谢蘧、汪革、饶节均为“江西诗派”首领,领一代风骚而为后世文人所推崇。
唐宋期间,中国有过两次倡导“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这是对先秦以后骈体文的重大革新。在领导古文运动的“唐宋八大家”中,抚州有曾巩、王安石两家。千余年来,曾、王佳作一直被视为文中典范。
元代,中国杂剧步入繁荣,而明代汤显祖则把中国戏曲推上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他创作“临川四梦”声震世界曲坛,与莎士比亚并称为“东西曲坛伟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世界100位文化名人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在书画领域,抚州巨匠辈出。晋代“书圣”王羲之在临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其“以精力自致”的进取精神与其后抚州刺史颜真卿的书法精神一道,滋润着抚州一代代书法英才:宋朝晏殊、王安石、赵崇幡、陈景元、曾纡,元朝程钜夫、吴徵、虞集、饶介,明朝危素、胡布、宋季子、程南云、吴余庆、王英,清朝赵世骏、吴铸、李瑞清,当代“党内一支笔”舒同等,均在中国书苑留下光彩照人的墨宝。
抚州也不乏驰名海内的丹青妙手。宋代临川画家陈容以擅画龙虎著称于世,其传世杰作《九龙图》曾被清朝乾隆皇帝视为奇珍。明代金溪画家吴宏以擅画山水竹石名噪海内,为“金陵八大家”之一,大量作品流传至今。清代乾隆帝亲自命题考画,将乐安袁国栋录为第一,时人称之“画状元”。清末民初李瑞清既是杰出书画家,又是艺术教育拓荒者。他首开国内美术、音乐教育课,并亲自培育出张大千、张善行、胡小石、吕凤子、姜丹书等一大批著名画家。
中国历史文化大厦由史文化、志文化和谱文化三根支柱支撑,抚州历代有不少名儒巨宿参与国史和地方志书编修。乐史是宋代杰出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其编著的《太平寰宇记》200卷是继唐代《元和郡县志》之后的一部采摭繁富的地理总志,时称阅此书可“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曾巩典修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5朝国史,并校定南齐、梁、陈3书。撰修宋、元、明、清4代实录的抚州籍人士有程钜夫、危素、吴当、程南云、何中、李来泰等12人。南宋时崇仁吴曾史作甚多,均为学界所重,其《能改斋漫录》堪与洪迈《容斋随笔》媲美。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虞集,主修《经世大典》880卷;朱思本绘成的《舆地图》“方位不爽毫厘”,是中国制图史上的创造。明代吴溥是世界最早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副总裁;徐奋鹏撰著《古今治统》传至日本,被视为“资治之妙药,兴国之良方”。清代直隶总督、方志大家李绂主编《八旗通志》《广西通志》,自撰《西江志补》《抚州府志》,并创立完整的方志理论体系。南丰籍吴宗慈是近代方志界一颗巨星,以强烈爱国敬业精神,在日本侵略军炮火下编修《江西通志》,为后人留下宝贵精神、文化遗产。抚州素称“文献之邦”。历代乡贤著述汗牛充栋,被选入《四库全书》目录有206种,后人著作更十倍于前。外地文人、作家关于抚州的诗文和著作也很多。台湾至今还有以“临川文献”命名的刊物。在古往今来的抚州文献典籍中,地方志为数不少。域内修志始于南朝荀伯子撰《临川记》,州、县修志至宋始兴。宋、元、明、清4代,抚州共编纂地方志书140余种,共计2000余卷,是一方历史文化的生动记录和重要组成部分。抚州民众历来聚族而居,以绵世系,衍宗支,昭祖训,明嫡庶的族谱家乘编纂,从宋代至今绵延不绝,数量众多。
抚州中医药文化根深叶茂。域内历代多名医,各类史志书籍载有名医200多名。江西历史上十大名医中,抚州籍有7位。这些名医大都有高深文化素养,不少人曾中举人、进士,因不附时俗或仕途坎坷,从而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壮志善愿,或世代传承,发扬家学,或精心钻研,终成一代良医。良医传世不光是起死回生的精湛医术,更宝贵的是高尚医德医风,不附权势,不贪名利,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宋代名医陈自明在其医著中提出“存仁心,通儒道,莫嫉妒,勿重利”等医家要旨,其所著《妇人大全良方》直到清朝仍被视为“妇科圣典”。骨科名医危亦林使用乌头、蔓陀罗为麻醉药,比日本医圣华冈青州早450年,创立悬吊正骨法比英国达维斯(Daris)早600多年。曾被明朝万历皇帝赐为“医林状元”的龚廷贤在治愈鲁王爱妃重病之后,拒收千金之酬,只求将自己的医著刊行于世,以便培养出更多良医。清代名医谢星焕,坐堂看病不收酬金,每年还给家乡百姓赠送“金不换正气丸”以防时疫。在“医药不分家”的中医传统作用下,抚州古代中药业十分繁荣,历史悠久的建昌药帮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樟树帮同扛中华药业大鼎,海内共传“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经建昌不行”。自然科学领域中有不少抚州英才,如北宋水利专家侯叔献、音韵学家陈彭年,明代天文学家吴伯宗,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揭暄等,都是当时科学家中佼佼者。
历代抚州人才中,更有不少见高识广、智勇双全的能臣良吏。晚唐时,南城危全讽任抚州刺史,一面安抚士民,奖励垦荒,发展经济,一面建孑孔庙,兴州学,倡文事,揽人才,延请本寂、匡仁、园照、文偃等禅宗高僧主持寺院,使抚州不仅“人繁土沃,桑耕有秋”,而且“学富文清”“既状周道,兼贯鲁风”,吸引了北方大量人士南迁抚州,为抚州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宋代,晏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等,更是政绩卓著的一代贤臣。还有屡挫金兵、保境安民的邓州通判饶廷直,元代极力建议朝廷修筑海堤、捍水为田的翰林直讲学士虞集,明代威丧敌胆的抗倭名将谭纶、傅良桥,清代禁烟名臣黄爵兹,外交能臣黄维翰、吴奇,兴修水利、力劝农桑、重教兴学政绩斐然的陇西知县应先烈,治政有方、不畏强权、依法惩办和坤亲属的御史谢阶树,胸怀韬略、屡建战功的民国骁将欧阳琳等,他们超凡的业绩向世人昭示出抚州才子的魅力和风范。
抚州宗教文化得天独厚。南城县麻姑山被誉为“洞天福地兼而有之”的道教圣地,麻姑在此得道成仙、三见沧海化桑田的传说更是妇孺皆知。颜真卿亲撰《麻姑山仙坛记》为此处道教文化增添色彩。宋代曾有5位皇帝颁敕令加封麻姑。乐安华盖山亦是著名道教胜地,宋代4位皇帝封华盖山仙神“真君”尊号。直到清末民初,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信徒从省内及闽、浙、湘、皖前来“朝华”。唐代,南城道士邓紫阳佐玄宗退西戎兵,被称为“神人”;宋代,抚州高道辈出,南丰人王文卿创立“神霄派”,临川人饶洞天创立“天心派”,影响及于朝野。西晋前期,佛教已传入抚州。南朝谢灵运在临川宝应寺设翻经台翻译佛经。唐末五代,宜黄曹山寺本寂禅师创立曹洞宗广传海内,远播日本。南禅五叶有曹洞、法眼、云门3宗源于抚州。法眼宗被称为“汝水之灯”,抚州被称为“天下禅河中心”。域内名寺、高僧众多。明代崇仁人宗泐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南城人行保,被列为“天下高僧十一人”;崇仁人慧经“躬自作务,力田饭僧”40年,拒绝官僚王公布施,保持了寺院经济独立,成为曹洞宗中兴祖师。民国初年,宜黄欧阳竟无、临川李证刚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
新中国成立后,抚州人才不少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蜚声海内外者,有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有被毛泽东称为“红军书法家”,“舒体”创始人舒同,有解放军第一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黄火星。创业于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大有人在:中国物理学“四大名旦”之一饶毓泰,著名文学史专家游国恩、肖涤非,首次提出将激光用于受控热核聚变的丁渝,创立中国高校首个道路工程专业的陈本瑞,首倡成立西北风能研究所并任名誉所长的邓慎康,研制旋转导弹激光导引取得重大成果的物理学家周仕忠,撰著中国首部《土壤学》的著名专家王云森,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筹委会执行主席鲁之俊,等等。
今日抚州人才更广泛地分布在世界各地。改革开放以后,抚州在英、美、日、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人数大增,其中攻读博士、博士后的有500余人。在海外建功立业的著名人士不胜枚举,南城黄天中历任美国数家大学副校长、校长,并且是美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任华人校长。在日本担任原子控制研究员并兼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的中年科学家黄德欢,同时又是名闻世界的纳米技术专家。黎川籍全国著名女歌唱家余珊鸣足迹和歌声遍及整个欧洲。
三、文化积淀丰富深厚 域内现存古迹众多,分布面广。广昌县出土的中生代白垩纪恐龙化石,被央视新闻联播称为“广昌恐龙——中华之最”。临川、乐安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有31处,商周时期遗址在域内各县区均有发现,出土文物众多。人类的文化遗迹不仅出现在陶器、铜器和铁器上,在固态的石体上也有发现。广昌赤水摩岩石刻古文字符号,尚待破译。隋唐开始,域内便有专业生产的瓷窑,全市7个县区19处古代陶瓷窑址仍有不少保存完整。南丰白舍窑生产的青白瓷,以“瓷胎质薄细润,洁白坚滑”,与景德镇窑 、吉州窑、洪州窑、赣州七里镇窑并称为“江西五大名窑”,产品足以与景德镇瓷争价。抚州古墓葬众多,临川抚北镇、广昌甘竹镇汉墓群规模壮观;唐代本寂禅师墓,宋代乐史墓、南丰曾巩墓、金溪陆象山墓,明代南城益王家族墓葬群,临川汤显祖墓、陈际泰墓,宜黄谭纶墓,乐安董裕墓,崇仁吴与弼墓等40余处,至今保存完好。域内现存古寺、古塔、古桥各具特色。临川云山大金山寺,金溪浒湾竦山寺,宜黄曹山寺、石巩寺,南丰县城寿昌寺,广昌龙凤岩清雨古寺,市城区正觉寺等,或寺高殿广、气宇轩昂,或小巧灵珑,选址精妙。南丰地藏菩萨像高6米,为省内最大的石菩萨像。市城区圣约瑟大教堂,为全国三大天主教堂之一。临川石港明代万魁塔、南城聚星塔,宜黄棠阴迎恩塔等,结构独特,造型奇美。唐代临川湖南瑶山双拱桥,五代广昌驿前吁姆桥,明代南城万年桥以及临川文昌桥,是中国古桥建筑的杰作。
各县区古代民居、牌坊、祠堂星罗棋布。乐安流坑村至今依然保持着明代中期格局,街巷纵横交错却井然有序,存有明代建筑19处,清代建筑250处,被称为“中国古代农村文明的典型”“明清建筑艺术博物馆”,石雕、砖雕、木雕、楹联、壁画等艺术品数以千计。此外,金溪竹桥、宜黄棠阴、南城磁圭、广昌驿前、黎川下陈等地古代建筑群落,都凝聚着灿烂的建筑文化。抚州还有众多散落于乡村的巨型建筑——船形屋,如黎川洲湖船屋拥有108间,36个天井,72个地漏,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宜黄县麻坑船屋9间厅堂,18间房间;南城县饶坊船屋有108间,占地10亩;广昌驿前船屋,有大小厅堂、厢房30余间,占地540平方米。这些船形屋的建造初衷,尚待后人破译。
抚州属典型江南农耕文化区,数千年间,人们崇尚世代同堂。宋代金溪陆氏“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爨将二百年”,明代南城吴焕“八世同爨,至二百余人”。各村落以宗族为单元相聚而居,至今仍保存有大量规模宏大的宗祠,人们秉承长幼有序、守信重义、忠孝传家的儒家礼法。为官者多崇尚正义、刚直不阿,热心除暴安良、为民请命。工匠商人大都有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诚信无欺、取财以道的职业道德。在农耕文化浸润下的抚州人尤其热爱家乡、眷恋故土,并由此延伸为浓厚的爱国之情,即使在身陷困境时,也牢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明万历年间临川商人朱均旺被倭寇掳至日本为奴,当他得知日本欲派兵侵犯朝鲜和中国后,3次冒险偷渡回国报信,使明朝政府及时作好准备与朝鲜联合出兵,歼灭来犯侵略军。
抚州民间文化艺术多姿多彩。被称为“中国舞蹈艺术活化石”的傩舞,自汉代陆续传人南丰、乐安、宜黄、黎川、广昌等地,至今仍为群众所喜爱。南丰傩班多次应邀到日本、美国、新加坡演出,该县被文化部命名为“傩舞之乡”。抚州灯彩极为丰富,龙灯、狮灯、跑马灯、罗汉灯、踩高跷等,每于春节期间一展风采。民歌、山歌、船歌、莳田歌、采茶歌、伐木歌风格各异。抚河沿岸,端午节赛龙舟之俗久传不衰。富有地方特色的稻作文化、桔文化、莲文化、夏布文化为抚州农耕文化增添丰富的内涵。
在灯彩、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抚州戏曲艺术历史悠久,北宋时,域内已有“杏楼”“瓦舍”等演出场所。宋末,吁河戏、抚河戏、宜黄戏均已崭露头角。兴起于清代的“三角班”迅速发展成地方特色鲜明的抚州采茶戏,百余年来风靡城乡,在江南艺苑中独树一帜。
抚州革命传统文化尤为珍贵。早在1919年,临川学生就积极声援“五·四”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中央苏区的创建、扩展,广昌、南丰、宜黄、乐安、资溪、黎川、南城、金溪、崇仁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组成部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抚州领导军民开展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进行过第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浴血战斗。很多老人至今还能演唱当年革命歌谣,还保留着红军用过的物品。抚州到处有革命文物和革命故事,与苏区精神一起 ,汇成光前裕后的苏区文化,永远是激励中华儿女爱国爱乡、奋发进取的精神资源。
四、文化创新继往开来 抚州人历来富有创新精神。宋代中期,李觏就曾大胆提出“言利”“言欲”的合理性,反对虚伪道学。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变法图新,成为11世纪中国杰出的政治改革家。陆九渊突破朱熹僵化的“格物”理论,创立肯定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心学”。汤显祖更是针锋相对地向封建儒学和礼教宣战,响亮地喊出“世总为情”的口号,并写出大量“情”战胜“理”的作品。然而,这些先贤的创新精神终因时代局限或社会桎梏而被窒息,或只能成为涓涓细流。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文化创新指明方向并开辟道路。广大劳动人民成为文化主人,清除剥削阶级腐朽文化,用社会主义占领城乡思想文化阵地。同时,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文化。50年代初,域内各县(市)就普遍兴建文化馆、站,组建专业文艺宣传队伍,崭新的群众性文化空前活跃。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下,传统文化被当作“四旧”破除,大量珍贵文物和文化遗址被摧毁。域内原有的14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7个被毁,其余7个也受到严重破坏,更多的民间文物被糟蹋。民间文化艺术一概被斥为“封、资、修”而禁绝,人们的思想遭到严重禁锢。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整套教育制度被打乱,教师受批斗,考试被取消,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区域文化蒙受巨大灾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迅速拨乱反正,优良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至2011年底,全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452处。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6个,在保护和整修的基础上开发利用。80年代以后,文化建设和创新的速度明显加快,先后兴建王安石纪念馆、曾巩纪念馆、玉茗堂影剧院、舒同书画院、汤显祖纪念馆,修缮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旧居、旧址,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及文化活动场所。
自80年代始,域内教育改革和创新频传佳音:在合理调整教学网点、切实提高教师素质、努力夯实教育基础、发扬民间办学传统的同时,不断加速教育装备和教学方式的现代化,计算机应用已成为城镇中学及部分农村学校的必授课。学校教育科研活动步步深入,开设“家长学校”“3+1”德育实验、中小学“六环节四步迁移教学法”等一系科研成果在教学中普遍推广,成效显著。域内4所普通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绝大部分被社会采纳,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抚州教育质量多年来保持全国先进水平。教育已成为人才和文化的活水之源。
临川文化是以临川古治为中心,辐射而覆盖当今赣东11个县(区)的区域性文化流派。临川古郡东连吴越,西接潇湘,南控闽粤,北襟江湖,横跨吴、越、楚三地,号称“江西大郡”。先秦时期,赣东属百越之地。据《汉书·地理志下》臣瓒注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赣东处于交趾(今越南境内)至会稽(今浙江绍兴)的中段,这里的原住民是古越族的一支,叫“干越”。唐代颜师古注《汉书·货殖列传》曰:“干越,南方越名也。”当代朱维幹编著的《福建史稿》更明确指出:“干越在今天的赣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已进入农业经济阶段的多数越人逐渐与北方南迁的汉人融合,他们筚路蓝缕,共同开发临川的文明源头。在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和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三次人口大迁徙中,赣东地区融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为临川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至两宋时期,临川文化的主体已基本构成。以抚河为纽带,相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形成临川固有的文化特征。赣东区域远古多沼泽、丘陵,草木繁茂,气候湿润,原住民过着“火耕水耨、饭稻羹鱼”游耕生活。北人南迁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水平,初步形成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物质文化结构,表现为有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勤稼穑、重桑艺的耕作文化;诚实守信、弃自守而进取的商业文化;崇实达理,秀而能文,以诗书求闻达的教育文化;重血缘、聚族而居的宗族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礼仪文化。淳朴的民风孕育出充满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进而形成相同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以及虔诚笃信的宗教文化和保留丰富中原古音韵的语言文化等。千百年来,在较高文化水准基础上形成的临川文学、哲学、艺术、科技、宗教等,涌现出一批有世界影响的文化代表人物。文化的开创离不传承,清代临川李绂在《南园答问》一文中说:“晏临川(晏殊)开荆国文公(王安石),李盱江(李觏)传南丰子固(曾巩);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精辟独到地解读了临川思想家们互相启迪、继承和发展的渊源关系。从宋代逐渐形成的临川文化声誉,一直到清代经久不衰,不仅激发了抚州人民对家乡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使外地墨客文人对临川礼仪之邦、才子之乡抱有敬仰之心,为临川文化灿烂的历史和巨大的魅力所吸引。1992年,中共抚州地委和地区行署根据专家和人民群众的共识,将以临川为中心的赣东区域文化正式命名为“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并列为江西两大区域文化,并成立“临川文化”开发领导小组,对“临川文化”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的研究和开发,把发展教育、文化、旅游、经济结合起来。一批研究、开发临川文化的机构和社会团体相继成立。临川文化研究逐步广泛深入,由单纯对名人、名作的研究,扩展到名人、文学、宗教、民俗、革命传统等多种领域。《临川文化史》《临川文学史》《临川近现代文化史》等全面、系统研究抚州历史文化的新成果相继面世,推出了《抚州人物》以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汤显祖等人物传记专著,点校了《王文公文集》《曾巩集》《李觏集》《陆象山全集》《殊玉词》《小山词》《谭纶集》等名人著作。地、县两级新志书的编修,构建成抚州地情资料的宏大宝库。临川文化也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开展深入的研究。国内著名学者徐朔方、漆侠、石凌鹤等出版30余部临川文化研究专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成为王安石的国外研究中心,出版的研究成果颇丰。汤显祖《牡丹亭》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并搬上德国兰心大戏院。台湾作家白先勇编导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内外演出200余场。日本东京大学、神奈川大学、大阪大学专家学者6次到南丰考察傩文化。宜黄曹山寺吸引了日本佛教史迹考察团参拜祭祖,不仅扩大临川文化的影响,还拓宽了临川文化研究的视野。域内在加强市镇建设、美化、净化环境的同时,重点建设名人文化园、拟岘台、大觉山、麻姑山、流坑村、大金山寺等一批旅游景区、景点,增建大量文化体育设施,汤显祖大剧院、抚州市图书馆、博物馆、体育中心等现代化场馆拔地而起,进一步优化了抚州的人文环境。90年代,多种形式的文化市场不断增加,到2011年,域内共有商业性文化经营场所2189家。文化和经济结合,发生能量聚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厚智力资源和强大精神动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抚州人民加速思想观念更新,摈弃听天由命,“求土不求人”,安土重迁、小富即安、怕担风险等陈旧思想和小农意识,不断增强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珍惜时间、讲求效益、互利互惠、重视协作、见义勇为、乐于奉献已成为抚州区域文化的重要内涵。
跨世纪之际,抚州撤地建市,中共抚州市委、抚州市人民政府提出“创文化名城、建经济强市”,合理开发和利用文化资源,加速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大力培植和发展教育、旅游、艺术等文化产业。抚州文化和经济迈上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全面繁荣新里程。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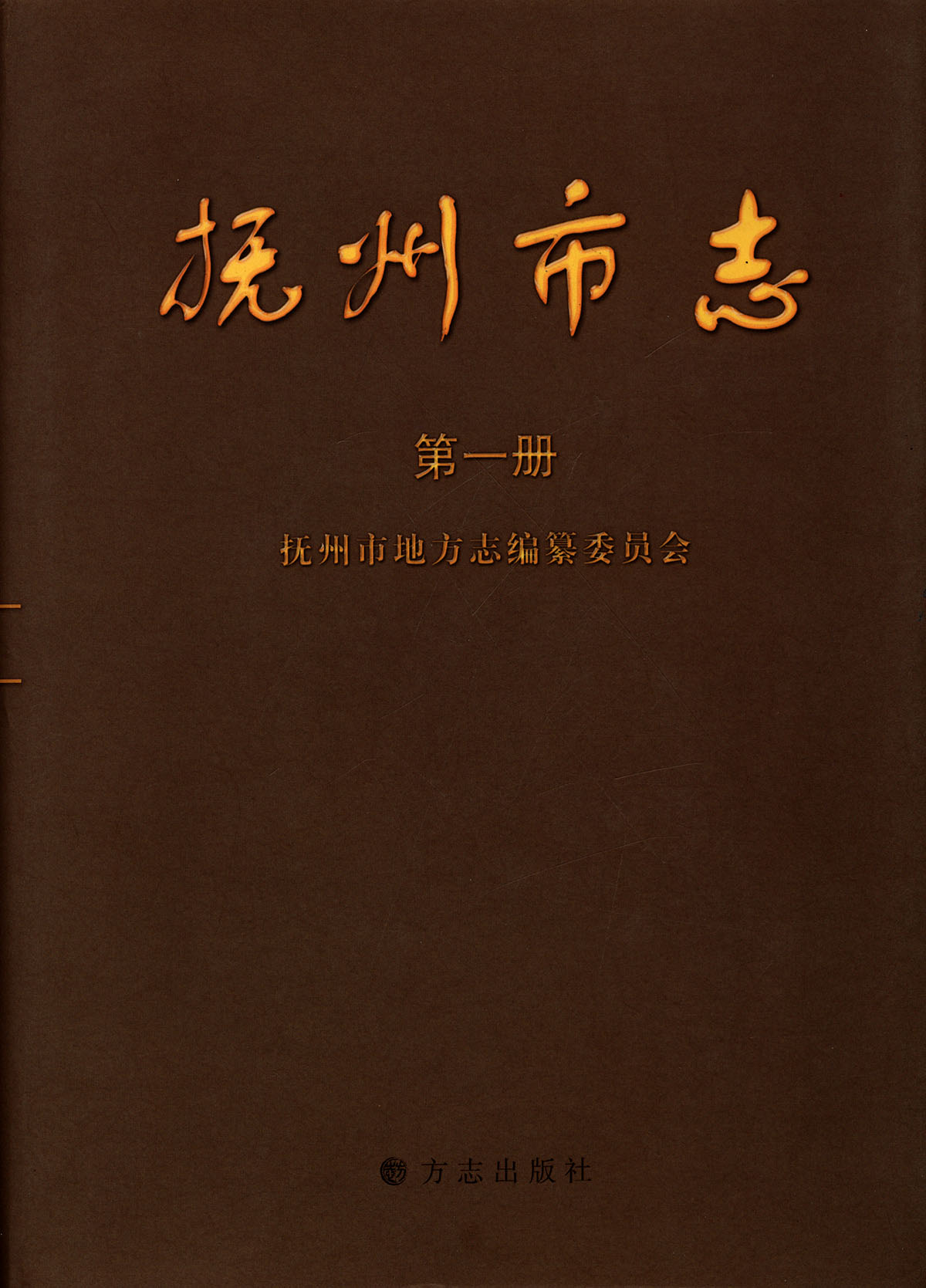
《抚州市志:全5册》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卷首部分包括序言、概述、抚州人文综述、抚州革命斗争纪略、大事记;主体分志设29卷174章,内容包括政区、自然环境、人口居民生活、政党、群众团体、政权、政务、公安司法、军事、经济发展总情、经济管理、财政税务金融、农业、林业垦殖、水利、工业、乡镇企业、名优特产、贸易、交通信息产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化旅游、新闻媒体、方言、宗教民俗传说故事、艺文、人物等栏目介绍了抚州的发展历程。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