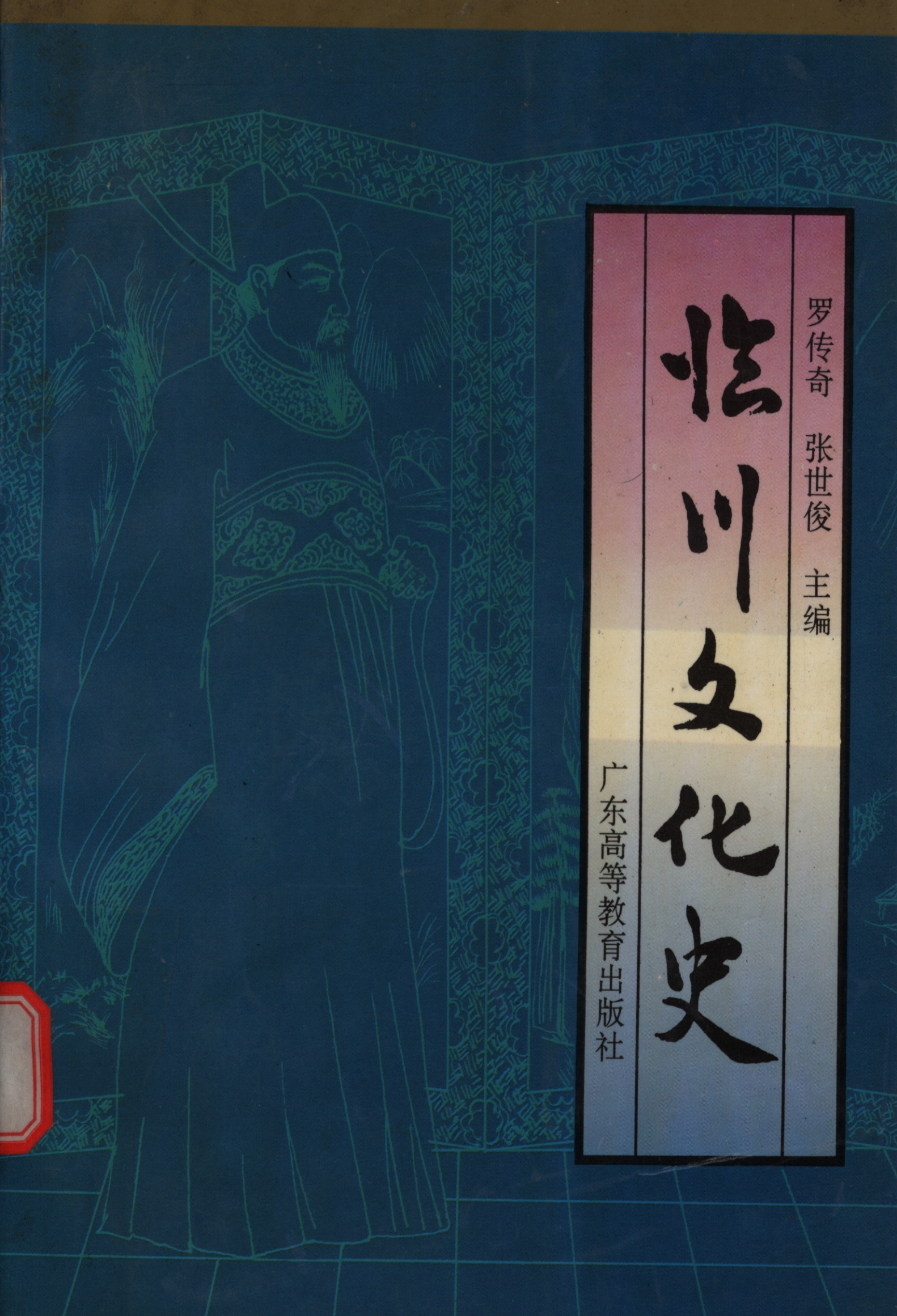临川文化兴盛的原因
内容
首先,中华文化中心的南移和外域文人对本土文化的浸润、浇灌,是临川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临川文化的兴盛自宋而始,究其原因,是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态势所制约、所决定的。宋以后,南方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推动文化中心南移之势最后完成。这个历史变动,对江南、对临川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久远的。
之一,随着宋王朝对南方经济依赖的加强,在政权上进一步实行对南人开放。这就给南方士人参与朝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推动他们进德力学、焕发才华、崭露头角。南方士人在这种现实刺激下,怀抱继圣道,建功业,求闻达的浩然之志,兴学重教,奋发读书,大批人才应运而生,《东乡县志》(新修)收入县邑历代进士87人,其中,北宋6人,南宋们人,元代2人,明代22人,清代17人,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说明。
之二,文化中心南移过程中,直接给南方士子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帮助他们扩大心胸,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公元961年,南唐迁都洪州。这个设教坊、立画院,网罗词客,重视艺术的小邦,深刻影响了江西文艺家的成长。南唐重臣、雅爱词章而成为词坛中心人物之一的冯延已曾在抚州任职3年(948—951),把词的种子撒播在临川的土地上,对临川区域词人影响殊深。晏殊就是承其流响的。
之三,受历史潮流之裹挟,北人南迁,不仅帮助了江南经济的开发,而且带来了士族重视族人子弟教育的传统、风习。抚州士人先辈多系从外地辗转迁徙而来的。他们来此落籍后,普遍重视对子弟的培养,或筑馆以教,或家学以传,无不竭尽全力。如王安石,先世为太原人,曾巩先辈为山东人,陆象山,远祖是北方人等。他们先祖迁到临川区域后,兴起了一代又一代良好文风和学风,影响是很大的。
之四,由于临川区域邻近南昌,魏晋以来特别是唐统一以后,大批文士纷纷来临川供职、讲学、寓居和游览。谢灵运、王羲之、颜真卿、陆游等,这些文人名士在临川区域的种种活动、业绩、著述、佳话,给临川文化以沾溉,以营养,以促进,无疑是临川文化万木峥嵘的春风雨露。
其次,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如第一章所论,临川区域,处于赣东,紧邻南昌,控带瓯越,襟领江湖。境内,山环水贯,地势平广,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既有山林竹木之利,舟楫水利之便,又有渔米、桑麻之养,通商贸易之惠。北方战乱频繁,而临川整个区域,和平而安宁,兴旺而富庶。由于此,四方商贾云集于此,文人雅士常会于斯。这是一块生存的乐土,图强的渊薮,是颇能吸引人们来此落籍生根的,是极利于发展生产、兴办教育、积累文化的。勤劳淳朴,安土乐业的临川区域人民正是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也用自己的灵秀创造了光华灿烂的学术文化。临川区域在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之后,于宋一代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局面,乃势所必然。
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泰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序言和《艺术哲学》等论著中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创作、文学产生和发展的3种力量,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是制约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1个因素。现代学者亦重视从生存环境寻找人类文化的根源。我们在研究临川文化昌隆缘由的时候,是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临川区域特定历史环境及由此决定的交通、经济状况这个母体的。
再次,发达的官学、书院教育和喜诗书、好礼仪的社会风气,是临川人才并肩接踵,成团涌现的基本原因。自古以来,我国一向以士农为骨干,以孝悌力田,敬祖先、睦家族为教化,耕读传家,习以为常。临川区域为江南腹地,环境既开放又封闭。临川人民扬己宜于农桑之长,遵循“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家训,勤耕织以得衣食,喜诗书以求闻达,读书之风极盛。古代临川市井,书坊林立,毛笔生产驰名东南,印刷行业特别发达,到处是浓浓的文化氛围,亦是这种重文风气的一种反映。临川英才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发育、生成的。
临川区域的官学教育成绩显著。由于晏殊的力倡和力行,自仁宗天圣年间起,“天下皆立学”,临川区内亦然,且基础好,起手早,办学多。临川学子和当时他地文人一样,凡所到之处喜欢为州县写“学记”。李靓作《袁州州学记》,王安石作《虔州学记》,曾巩作《宜黄县县学记》等等,反映了当日江西、抚州对教育的重视和兴学的盛况。
临川区域以宋为始,除官学外,书院遍布,名儒巨子,聚徒讲学,四方学子,闻风从游,为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觏,创盱江书院于凤凰岗麓,“门人随镓者干有余人”。
曾巩入仕前曾创兴鲁书院于今抚州市香楠峰(抚州地委大院之地),亲自为之制定学规,远近生徒聚而从之,名人学士济济一时,抚州文风盛、人才多,曾巩实有倡学之功。
“百世大儒”陆九渊1 172年至1 175年登进士第在家候职期间,1186年至1191年离京还里在家闲居,始从教于槐堂书院,继设讲于“象山精舍”,从学之士,四方云集。其弟子有杨简、傅梦泉、邓约礼、彭世昌、黄叔丰、石斗文、傅子云、陈刚、俞廷蝽、李伯敏、詹阜民、包杨等65人。他们簇拥陆氏讲席,组成了陆氏“心学”学派的基本队伍。
罗汝芳于1544年在南城东南郊创从姑山房,接待四方来此讲学之士。16年后,任刑部山东司主事的罗汝芳回南城探亲,求学者踵至,时年13岁的汤显祖亦拜罗为师,学习其“百姓日用即道”的理学体系,对汤氏日后的思想和创作影响深远。
国家之兴,人才为上,人才之道,本在教育。临川区域人才荟萃,广教、重学是一条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
第四,临川区域士人普遍具有的主“通变”、立新说、开拓进取、勇于超越的心理机制和坚持真理、忠于学术、喜欢辩难的文化精神,是临川文化取得很高成就的深层动因。李觏作为哲人是一位勇猛的战士。他在肯定世界的物质性的同时,力主天“道”的变通,认为“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①。尤为可贵的是,在当时理学思想笼罩整个社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存天理、灭人欲”等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把人们禁锢得密不透风的情况下,敢于大发“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言不可言,无乃赋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这样的惊人之论,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言利、言欲的合理性,表现了其对虚伪道学十分可贵的批判精神,体现了临川区域哲人义利统一,情理交错的心理结构。陆九渊不愧是一位走新路、创新猷的大学者。在程朱理学已形成体系之时,另打旗号,立“心即理”的心学一派,虽然其说与程朱之学都属唯心主义阵营,但前者与后者在本体论、性论和方法论诸方面殊异。这就引发了两派在学术上的长期对立和论争。清代金溪蔡上翔费27年之工,撰写了《王荆公年谱考略》,力排俗议,为改革家王安石辩诬,都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临川文人的学术战斗精神和析疑求真,不为旧说所缚,不为俗见所囿的开拓性格。
第五,长辈前贤重视对后辈的奖引、举荐,提携,是临川区域人才大量涌现的重要条件。晏殊才高学广,识见明决,深知治国本末,从35岁入枢府至54岁罢相,十余年如一日,知人善任,求贤若渴,荐贤如流,一代名臣贤士,都出其门。曾巩对王安石乡谊极深,先后于庆历四年、五年,两次致书欧阳修举荐王安石,庆历六年,欧阳修贬知滁州,曾巩亲赴滁州面呈王安石文章。据他的《与王介甫第一书》云,欧公得王文后,颇称其善,“爱叹诵写”,“不胜其勤”,并希望得以一见。10年后,欧公在朝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王调任开封群牧司判官,两位文学家方会晤于京都,高兴之余,互赠诗文,欧公并立即向仁宗推荐王安石,并在后来还向仁宗荐王安石为谏官。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尽管后期政见不尽相同,但个人交谊甚厚。欧阳修死后在众多的祭奠文章中,唯王荆公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写得最为真切感人。王安石亦以人才为务,理论一上多有发挥。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倡导政治变革,而其核心的内容是论述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他还专门写了《材论》一文,起用了包括临川人才在内的许多年轻有识之士,为其改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第六,临川区域士子、地方官都热心于古籍整理和地方文献的考证、编集,是临川文化持续繁荣、发展诸动因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前面说过,抚州是“文献之邦”,历代文人撰著甚丰。这些文献倘任其流散,势必给文化的发展造成莫大的损失。抚州学子、官宦深明此理,普遍重视致力于文集,文章的整理、考据、编辑工作。从刘宋时期临川内史荀伯子修《临川记》6卷(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卷2;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6;李肪《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9;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54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开始,就有宋代抚州教授徐天麟、户部郎中知临川军事家坤翁、明代抚州知府黄显、蔡邦俊修《临川志》《抚州府志》,宋代以下各朝知县、郡守、推官、邑人70余人修纂建昌府志和临川、南城、崇仁、乐安、宜黄、南丰、黎川、资溪、金溪、东乡等各县县志。清刘玉瓒辑选《临川文选》6种。清临川知县胡亦堂辑《临川文献》15种25卷,包括:晏同叔先生集2集、晏叔原先生集1卷、王介甫先生集2卷、章介庵先生文集2卷、陈明水先生集2卷、帅惟审先生集2卷、汤义仍先生集2卷、丘毛伯先生集2卷、章大力先生集1卷、艾千子先生集1卷、罗文止先生集1卷、陈大士先生集1卷、揭蒿庵先生集2卷、游日生先生集2卷、傅平叔先生集2卷。金溪乾隆43年进士王谟,无意仕途,喜好考据之学、才识雄伟,精力过人,雅慕郑樵、马端临二贤(均为考据学家),终日采经摘传,搜罗散失旧闻,以补史书之缺,著有《江西考古录》1卷,《豫章十代文献考略》50卷,编辑《汉魏遗书抄》 500余种。清吕留良辑评《江西五家稿》5种,清冯行辑《黎川文载》24卷。清黎川诗人、学者杨希闵在前人卷轶浩繁的文史著述基础上,先后辑有《水经注汇校》 40卷,《四书改错平》1 4卷,《四朝先贤六家年谱》、《豫章先贤九家年谱》15卷,《绝句诗选》3卷、《诗榷》12卷、《乡诗摭谭》正1 0卷、续1 0卷,仅后者就评述了陶渊明以来江西340多位诗人,是研究江西诗歌发展史极为重要的参考史料。
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思格斯亦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②可以认为,临川文化在发展的途程中,所得到的先辈的遗产是极其丰厚的,“特定的思想资料”这个“前提”是相当充分的。
之一,随着宋王朝对南方经济依赖的加强,在政权上进一步实行对南人开放。这就给南方士人参与朝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推动他们进德力学、焕发才华、崭露头角。南方士人在这种现实刺激下,怀抱继圣道,建功业,求闻达的浩然之志,兴学重教,奋发读书,大批人才应运而生,《东乡县志》(新修)收入县邑历代进士87人,其中,北宋6人,南宋们人,元代2人,明代22人,清代17人,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说明。
之二,文化中心南移过程中,直接给南方士子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帮助他们扩大心胸,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公元961年,南唐迁都洪州。这个设教坊、立画院,网罗词客,重视艺术的小邦,深刻影响了江西文艺家的成长。南唐重臣、雅爱词章而成为词坛中心人物之一的冯延已曾在抚州任职3年(948—951),把词的种子撒播在临川的土地上,对临川区域词人影响殊深。晏殊就是承其流响的。
之三,受历史潮流之裹挟,北人南迁,不仅帮助了江南经济的开发,而且带来了士族重视族人子弟教育的传统、风习。抚州士人先辈多系从外地辗转迁徙而来的。他们来此落籍后,普遍重视对子弟的培养,或筑馆以教,或家学以传,无不竭尽全力。如王安石,先世为太原人,曾巩先辈为山东人,陆象山,远祖是北方人等。他们先祖迁到临川区域后,兴起了一代又一代良好文风和学风,影响是很大的。
之四,由于临川区域邻近南昌,魏晋以来特别是唐统一以后,大批文士纷纷来临川供职、讲学、寓居和游览。谢灵运、王羲之、颜真卿、陆游等,这些文人名士在临川区域的种种活动、业绩、著述、佳话,给临川文化以沾溉,以营养,以促进,无疑是临川文化万木峥嵘的春风雨露。
其次,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如第一章所论,临川区域,处于赣东,紧邻南昌,控带瓯越,襟领江湖。境内,山环水贯,地势平广,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既有山林竹木之利,舟楫水利之便,又有渔米、桑麻之养,通商贸易之惠。北方战乱频繁,而临川整个区域,和平而安宁,兴旺而富庶。由于此,四方商贾云集于此,文人雅士常会于斯。这是一块生存的乐土,图强的渊薮,是颇能吸引人们来此落籍生根的,是极利于发展生产、兴办教育、积累文化的。勤劳淳朴,安土乐业的临川区域人民正是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也用自己的灵秀创造了光华灿烂的学术文化。临川区域在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之后,于宋一代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局面,乃势所必然。
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泰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序言和《艺术哲学》等论著中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创作、文学产生和发展的3种力量,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是制约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1个因素。现代学者亦重视从生存环境寻找人类文化的根源。我们在研究临川文化昌隆缘由的时候,是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临川区域特定历史环境及由此决定的交通、经济状况这个母体的。
再次,发达的官学、书院教育和喜诗书、好礼仪的社会风气,是临川人才并肩接踵,成团涌现的基本原因。自古以来,我国一向以士农为骨干,以孝悌力田,敬祖先、睦家族为教化,耕读传家,习以为常。临川区域为江南腹地,环境既开放又封闭。临川人民扬己宜于农桑之长,遵循“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家训,勤耕织以得衣食,喜诗书以求闻达,读书之风极盛。古代临川市井,书坊林立,毛笔生产驰名东南,印刷行业特别发达,到处是浓浓的文化氛围,亦是这种重文风气的一种反映。临川英才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发育、生成的。
临川区域的官学教育成绩显著。由于晏殊的力倡和力行,自仁宗天圣年间起,“天下皆立学”,临川区内亦然,且基础好,起手早,办学多。临川学子和当时他地文人一样,凡所到之处喜欢为州县写“学记”。李靓作《袁州州学记》,王安石作《虔州学记》,曾巩作《宜黄县县学记》等等,反映了当日江西、抚州对教育的重视和兴学的盛况。
临川区域以宋为始,除官学外,书院遍布,名儒巨子,聚徒讲学,四方学子,闻风从游,为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觏,创盱江书院于凤凰岗麓,“门人随镓者干有余人”。
曾巩入仕前曾创兴鲁书院于今抚州市香楠峰(抚州地委大院之地),亲自为之制定学规,远近生徒聚而从之,名人学士济济一时,抚州文风盛、人才多,曾巩实有倡学之功。
“百世大儒”陆九渊1 172年至1 175年登进士第在家候职期间,1186年至1191年离京还里在家闲居,始从教于槐堂书院,继设讲于“象山精舍”,从学之士,四方云集。其弟子有杨简、傅梦泉、邓约礼、彭世昌、黄叔丰、石斗文、傅子云、陈刚、俞廷蝽、李伯敏、詹阜民、包杨等65人。他们簇拥陆氏讲席,组成了陆氏“心学”学派的基本队伍。
罗汝芳于1544年在南城东南郊创从姑山房,接待四方来此讲学之士。16年后,任刑部山东司主事的罗汝芳回南城探亲,求学者踵至,时年13岁的汤显祖亦拜罗为师,学习其“百姓日用即道”的理学体系,对汤氏日后的思想和创作影响深远。
国家之兴,人才为上,人才之道,本在教育。临川区域人才荟萃,广教、重学是一条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
第四,临川区域士人普遍具有的主“通变”、立新说、开拓进取、勇于超越的心理机制和坚持真理、忠于学术、喜欢辩难的文化精神,是临川文化取得很高成就的深层动因。李觏作为哲人是一位勇猛的战士。他在肯定世界的物质性的同时,力主天“道”的变通,认为“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①。尤为可贵的是,在当时理学思想笼罩整个社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存天理、灭人欲”等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把人们禁锢得密不透风的情况下,敢于大发“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言不可言,无乃赋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这样的惊人之论,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言利、言欲的合理性,表现了其对虚伪道学十分可贵的批判精神,体现了临川区域哲人义利统一,情理交错的心理结构。陆九渊不愧是一位走新路、创新猷的大学者。在程朱理学已形成体系之时,另打旗号,立“心即理”的心学一派,虽然其说与程朱之学都属唯心主义阵营,但前者与后者在本体论、性论和方法论诸方面殊异。这就引发了两派在学术上的长期对立和论争。清代金溪蔡上翔费27年之工,撰写了《王荆公年谱考略》,力排俗议,为改革家王安石辩诬,都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临川文人的学术战斗精神和析疑求真,不为旧说所缚,不为俗见所囿的开拓性格。
第五,长辈前贤重视对后辈的奖引、举荐,提携,是临川区域人才大量涌现的重要条件。晏殊才高学广,识见明决,深知治国本末,从35岁入枢府至54岁罢相,十余年如一日,知人善任,求贤若渴,荐贤如流,一代名臣贤士,都出其门。曾巩对王安石乡谊极深,先后于庆历四年、五年,两次致书欧阳修举荐王安石,庆历六年,欧阳修贬知滁州,曾巩亲赴滁州面呈王安石文章。据他的《与王介甫第一书》云,欧公得王文后,颇称其善,“爱叹诵写”,“不胜其勤”,并希望得以一见。10年后,欧公在朝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王调任开封群牧司判官,两位文学家方会晤于京都,高兴之余,互赠诗文,欧公并立即向仁宗推荐王安石,并在后来还向仁宗荐王安石为谏官。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尽管后期政见不尽相同,但个人交谊甚厚。欧阳修死后在众多的祭奠文章中,唯王荆公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写得最为真切感人。王安石亦以人才为务,理论一上多有发挥。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倡导政治变革,而其核心的内容是论述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他还专门写了《材论》一文,起用了包括临川人才在内的许多年轻有识之士,为其改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第六,临川区域士子、地方官都热心于古籍整理和地方文献的考证、编集,是临川文化持续繁荣、发展诸动因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前面说过,抚州是“文献之邦”,历代文人撰著甚丰。这些文献倘任其流散,势必给文化的发展造成莫大的损失。抚州学子、官宦深明此理,普遍重视致力于文集,文章的整理、考据、编辑工作。从刘宋时期临川内史荀伯子修《临川记》6卷(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卷2;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6;李肪《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9;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54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开始,就有宋代抚州教授徐天麟、户部郎中知临川军事家坤翁、明代抚州知府黄显、蔡邦俊修《临川志》《抚州府志》,宋代以下各朝知县、郡守、推官、邑人70余人修纂建昌府志和临川、南城、崇仁、乐安、宜黄、南丰、黎川、资溪、金溪、东乡等各县县志。清刘玉瓒辑选《临川文选》6种。清临川知县胡亦堂辑《临川文献》15种25卷,包括:晏同叔先生集2集、晏叔原先生集1卷、王介甫先生集2卷、章介庵先生文集2卷、陈明水先生集2卷、帅惟审先生集2卷、汤义仍先生集2卷、丘毛伯先生集2卷、章大力先生集1卷、艾千子先生集1卷、罗文止先生集1卷、陈大士先生集1卷、揭蒿庵先生集2卷、游日生先生集2卷、傅平叔先生集2卷。金溪乾隆43年进士王谟,无意仕途,喜好考据之学、才识雄伟,精力过人,雅慕郑樵、马端临二贤(均为考据学家),终日采经摘传,搜罗散失旧闻,以补史书之缺,著有《江西考古录》1卷,《豫章十代文献考略》50卷,编辑《汉魏遗书抄》 500余种。清吕留良辑评《江西五家稿》5种,清冯行辑《黎川文载》24卷。清黎川诗人、学者杨希闵在前人卷轶浩繁的文史著述基础上,先后辑有《水经注汇校》 40卷,《四书改错平》1 4卷,《四朝先贤六家年谱》、《豫章先贤九家年谱》15卷,《绝句诗选》3卷、《诗榷》12卷、《乡诗摭谭》正1 0卷、续1 0卷,仅后者就评述了陶渊明以来江西340多位诗人,是研究江西诗歌发展史极为重要的参考史料。
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思格斯亦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②可以认为,临川文化在发展的途程中,所得到的先辈的遗产是极其丰厚的,“特定的思想资料”这个“前提”是相当充分的。
附注
① 《李觏集》卷第29《原文》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②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