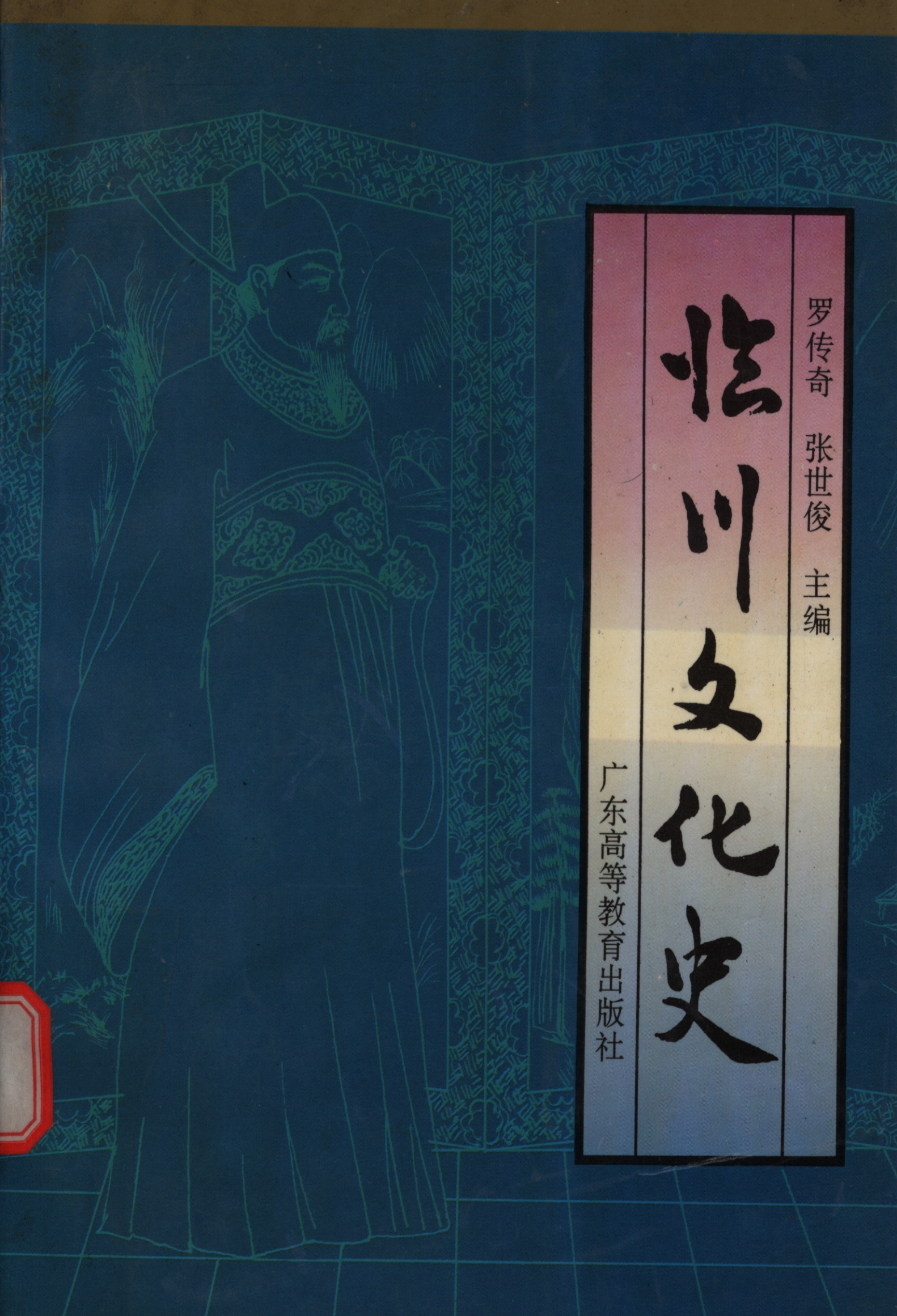第十九章 临川文化兴盛的原因及地位
| 内容出处: | 《临川文化史》 图书 |
| 唯一号: | 140220020210000233 |
| 颗粒名称: | 第十九章 临川文化兴盛的原因及地位 |
| 分类号: | K2 |
| 页数: | 15 |
| 摘要: | 临川区域文化发展史,就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临川才人脱颖而出,争奇比秀,创造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什么原因使临川文化如此繁荣,如此辉煌,而且由宋代至近代,延绵千年而不衰呢?我们以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中华文化中心的南移和外域文人对本土文化的浸润、浇灌,是临川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临川文化的兴盛自宋而始,究其原因,是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态势所制约、所决定的。宋以后,南方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推动文化中心南移之势最后完成。这个历史变动,对江南、对临川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久远的。 |
| 关键词: | 文化史 临川 |
内容
第一节临川文化兴盛的原因如上所述,自魏晋以来,特别是宋代以降,钟灵毓秀、神奇美丽的临川区域,文事昌盛,人才辈出,在哲学、文学、史学、医学、数学、军事学、地理学、语言学、天文学、考据学、方志学和书法、绘画、雕刻、建筑、戏曲、舞蹈等各个领域,一大批文化伟人相继问世,一大批俊杰高士弄潮争雄。他们的天才创造和各自达到的成就,为豫章文化的形成,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光耀史册的贡献;他们的活动、思想、著述、业绩和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构成了品格特异、光华耀眼的“临川文化”现象。
可以说,一部临川区域文化发展史,就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临川才人脱颖而出,争奇比秀,创造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什么原因使临川文化如此繁荣,如此辉煌,而且由宋代至近代,延绵千年而不衰呢?我们以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中华文化中心的南移和外域文人对本土文化的浸润、浇灌,是临川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临川文化的兴盛自宋而始,究其原因,是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态势所制约、所决定的。宋以后,南方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推动文化中心南移之势最后完成。这个历史变动,对江南、对临川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久远的。
之一,随着宋王朝对南方经济依赖的加强,在政权上进一步实行对南人开放。这就给南方士人参与朝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推动他们进德力学、焕发才华、崭露头角。南方士人在这种现实刺激下,怀抱继圣道,建功业,求闻达的浩然之志,兴学重教,奋发读书,大批人才应运而生,《东乡县志》(新修)收入县邑历代进士87人,其中,北宋6人,南宋们人,元代2人,明代22人,清代17人,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说明。
之二,文化中心南移过程中,直接给南方士子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帮助他们扩大心胸,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公元961年,南唐迁都洪州。这个设教坊、立画院,网罗词客,重视艺术的小邦,深刻影响了江西文艺家的成长。南唐重臣、雅爱词章而成为词坛中心人物之一的冯延已曾在抚州任职3年(948—951),把词的种子撒播在临川的土地上,对临川区域词人影响殊深。晏殊就是承其流响的。
之三,受历史潮流之裹挟,北人南迁,不仅帮助了江南经济的开发,而且带来了士族重视族人子弟教育的传统、风习。抚州士人先辈多系从外地辗转迁徙而来的。他们来此落籍后,普遍重视对子弟的培养,或筑馆以教,或家学以传,无不竭尽全力。如王安石,先世为太原人,曾巩先辈为山东人,陆象山,远祖是北方人等。他们先祖迁到临川区域后,兴起了一代又一代良好文风和学风,影响是很大的。
之四,由于临川区域邻近南昌,魏晋以来特别是唐统一以后,大批文士纷纷来临川供职、讲学、寓居和游览。谢灵运、王羲之、颜真卿、陆游等,这些文人名士在临川区域的种种活动、业绩、著述、佳话,给临川文化以沾溉,以营养,以促进,无疑是临川文化万木峥嵘的春风雨露。
其次,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如第一章所论,临川区域,处于赣东,紧邻南昌,控带瓯越,襟领江湖。境内,山环水贯,地势平广,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既有山林竹木之利,舟楫水利之便,又有渔米、桑麻之养,通商贸易之惠。北方战乱频繁,而临川整个区域,和平而安宁,兴旺而富庶。由于此,四方商贾云集于此,文人雅士常会于斯。这是一块生存的乐土,图强的渊薮,是颇能吸引人们来此落籍生根的,是极利于发展生产、兴办教育、积累文化的。勤劳淳朴,安土乐业的临川区域人民正是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也用自己的灵秀创造了光华灿烂的学术文化。临川区域在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之后,于宋一代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局面,乃势所必然。
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泰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序言和《艺术哲学》等论著中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创作、文学产生和发展的3种力量,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是制约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1个因素。现代学者亦重视从生存环境寻找人类文化的根源。我们在研究临川文化昌隆缘由的时候,是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临川区域特定历史环境及由此决定的交通、经济状况这个母体的。
再次,发达的官学、书院教育和喜诗书、好礼仪的社会风气,是临川人才并肩接踵,成团涌现的基本原因。自古以来,我国一向以士农为骨干,以孝悌力田,敬祖先、睦家族为教化,耕读传家,习以为常。临川区域为江南腹地,环境既开放又封闭。临川人民扬己宜于农桑之长,遵循“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家训,勤耕织以得衣食,喜诗书以求闻达,读书之风极盛。古代临川市井,书坊林立,毛笔生产驰名东南,印刷行业特别发达,到处是浓浓的文化氛围,亦是这种重文风气的一种反映。临川英才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发育、生成的。
临川区域的官学教育成绩显著。由于晏殊的力倡和力行,自仁宗天圣年间起,“天下皆立学”,临川区内亦然,且基础好,起手早,办学多。临川学子和当时他地文人一样,凡所到之处喜欢为州县写“学记”。李靓作《袁州州学记》,王安石作《虔州学记》,曾巩作《宜黄县县学记》等等,反映了当日江西、抚州对教育的重视和兴学的盛况。
临川区域以宋为始,除官学外,书院遍布,名儒巨子,聚徒讲学,四方学子,闻风从游,为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觏,创盱江书院于凤凰岗麓,“门人随镓者干有余人”。
曾巩入仕前曾创兴鲁书院于今抚州市香楠峰(抚州地委大院之地),亲自为之制定学规,远近生徒聚而从之,名人学士济济一时,抚州文风盛、人才多,曾巩实有倡学之功。
“百世大儒”陆九渊1 172年至1 175年登进士第在家候职期间,1186年至1191年离京还里在家闲居,始从教于槐堂书院,继设讲于“象山精舍”,从学之士,四方云集。其弟子有杨简、傅梦泉、邓约礼、彭世昌、黄叔丰、石斗文、傅子云、陈刚、俞廷蝽、李伯敏、詹阜民、包杨等65人。他们簇拥陆氏讲席,组成了陆氏“心学”学派的基本队伍。
罗汝芳于1544年在南城东南郊创从姑山房,接待四方来此讲学之士。16年后,任刑部山东司主事的罗汝芳回南城探亲,求学者踵至,时年13岁的汤显祖亦拜罗为师,学习其“百姓日用即道”的理学体系,对汤氏日后的思想和创作影响深远。
国家之兴,人才为上,人才之道,本在教育。临川区域人才荟萃,广教、重学是一条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
第四,临川区域士人普遍具有的主“通变”、立新说、开拓进取、勇于超越的心理机制和坚持真理、忠于学术、喜欢辩难的文化精神,是临川文化取得很高成就的深层动因。李觏作为哲人是一位勇猛的战士。他在肯定世界的物质性的同时,力主天“道”的变通,认为“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①。尤为可贵的是,在当时理学思想笼罩整个社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存天理、灭人欲”等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把人们禁锢得密不透风的情况下,敢于大发“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言不可言,无乃赋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这样的惊人之论,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言利、言欲的合理性,表现了其对虚伪道学十分可贵的批判精神,体现了临川区域哲人义利统一,情理交错的心理结构。陆九渊不愧是一位走新路、创新猷的大学者。在程朱理学已形成体系之时,另打旗号,立“心即理”的心学一派,虽然其说与程朱之学都属唯心主义阵营,但前者与后者在本体论、性论和方法论诸方面殊异。这就引发了两派在学术上的长期对立和论争。清代金溪蔡上翔费27年之工,撰写了《王荆公年谱考略》,力排俗议,为改革家王安石辩诬,都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临川文人的学术战斗精神和析疑求真,不为旧说所缚,不为俗见所囿的开拓性格。
第五,长辈前贤重视对后辈的奖引、举荐,提携,是临川区域人才大量涌现的重要条件。晏殊才高学广,识见明决,深知治国本末,从35岁入枢府至54岁罢相,十余年如一日,知人善任,求贤若渴,荐贤如流,一代名臣贤士,都出其门。曾巩对王安石乡谊极深,先后于庆历四年、五年,两次致书欧阳修举荐王安石,庆历六年,欧阳修贬知滁州,曾巩亲赴滁州面呈王安石文章。据他的《与王介甫第一书》云,欧公得王文后,颇称其善,“爱叹诵写”,“不胜其勤”,并希望得以一见。10年后,欧公在朝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王调任开封群牧司判官,两位文学家方会晤于京都,高兴之余,互赠诗文,欧公并立即向仁宗推荐王安石,并在后来还向仁宗荐王安石为谏官。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尽管后期政见不尽相同,但个人交谊甚厚。欧阳修死后在众多的祭奠文章中,唯王荆公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写得最为真切感人。王安石亦以人才为务,理论一上多有发挥。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倡导政治变革,而其核心的内容是论述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他还专门写了《材论》一文,起用了包括临川人才在内的许多年轻有识之士,为其改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第六,临川区域士子、地方官都热心于古籍整理和地方文献的考证、编集,是临川文化持续繁荣、发展诸动因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前面说过,抚州是“文献之邦”,历代文人撰著甚丰。这些文献倘任其流散,势必给文化的发展造成莫大的损失。抚州学子、官宦深明此理,普遍重视致力于文集,文章的整理、考据、编辑工作。从刘宋时期临川内史荀伯子修《临川记》6卷(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卷2;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6;李肪《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9;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54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开始,就有宋代抚州教授徐天麟、户部郎中知临川军事家坤翁、明代抚州知府黄显、蔡邦俊修《临川志》《抚州府志》,宋代以下各朝知县、郡守、推官、邑人70余人修纂建昌府志和临川、南城、崇仁、乐安、宜黄、南丰、黎川、资溪、金溪、东乡等各县县志。清刘玉瓒辑选《临川文选》6种。清临川知县胡亦堂辑《临川文献》15种25卷,包括:晏同叔先生集2集、晏叔原先生集1卷、王介甫先生集2卷、章介庵先生文集2卷、陈明水先生集2卷、帅惟审先生集2卷、汤义仍先生集2卷、丘毛伯先生集2卷、章大力先生集1卷、艾千子先生集1卷、罗文止先生集1卷、陈大士先生集1卷、揭蒿庵先生集2卷、游日生先生集2卷、傅平叔先生集2卷。金溪乾隆43年进士王谟,无意仕途,喜好考据之学、才识雄伟,精力过人,雅慕郑樵、马端临二贤(均为考据学家),终日采经摘传,搜罗散失旧闻,以补史书之缺,著有《江西考古录》1卷,《豫章十代文献考略》50卷,编辑《汉魏遗书抄》 500余种。清吕留良辑评《江西五家稿》5种,清冯行辑《黎川文载》24卷。清黎川诗人、学者杨希闵在前人卷轶浩繁的文史著述基础上,先后辑有《水经注汇校》 40卷,《四书改错平》1 4卷,《四朝先贤六家年谱》、《豫章先贤九家年谱》15卷,《绝句诗选》3卷、《诗榷》12卷、《乡诗摭谭》正1 0卷、续1 0卷,仅后者就评述了陶渊明以来江西340多位诗人,是研究江西诗歌发展史极为重要的参考史料。
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思格斯亦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②可以认为,临川文化在发展的途程中,所得到的先辈的遗产是极其丰厚的,“特定的思想资料”这个“前提”是相当充分的。
第二节临川文化的地位和影响自宋而清,临川文化郁郁乎如春林竞秀,灿灿然似秋夜长空。在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临川区域的历代文化名人,以自己的卓越才能,为中华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作出了光耀史册的贡献,而其中许多天才大家的思想、著述和业绩,则是华厦文化中最有价值、最为耀眼的一个部分。如果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座辉煌无比的精神大厦,那么,临川区域的诸多文化伟人,则充当了构建这座大厦的某些部分的梁柱。临川文化是属于江西的,亦是属于全民族、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
审视临川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和横向的生存态势及其所发散的价值能量,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无论在当时,抑或于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北宋是个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封建王朝。面对“三冗”严重、积贫积弱的颓危国势,“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发动和领导了以“理财”为中心,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政治改革运动,由于过于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破坏,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收到的促进生产、增加收入、壮大国力的实效是明显的。它表现了临川文化伟人积极进取、变革图新的战斗精神。
临川士子尊师重教,倡学笃行,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江南文化的开发和南北文化的全面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晏殊,早在仁宗天圣年间任应天知府时,即延请范仲淹“以教生徒”,后来升任宰相,更是全面关心各处人才的培养,以至天下洲郡学校大兴,贤才俊士涌流于世,形成江南才子甲于天下,江西才子复冠江南的可喜局面。晏殊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发展史和江南文化开发史上居于先驱者地位。
理学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以伦理为本体,涵泳儒、释、道三教思想之精粹的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哲学体系。北宋以降,江西是理学的发达之地,而安祥、温馨的临川区域,致力于理学探研的人物尤多,大家巨子尤众。南宋以陆象山为代表的象山学派,元代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明代泰州学派的三传弟子罗汝芳和以吴与弼为代表的崇仁学派,清代以谢文存为代表的程山学派,表现了临川区域哲人开宗创派的学术进取精神,展示了临川区域理学的繁荣景象。尤其是陆象山“心学”的创立,作为主观唯心论之一翼,与朱熹的客观唯心论一起,共同构建了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使之更加完整、恢宏、深刻和精致。同时,从抽象方面发掘和强化了人“心”的本原性心理能量,突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超越性。陆象山及其后继者王阳明的“陆王心学”,对元、明、清三代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其“人皆可为圣人”,“百姓日用为道”的命题及其合理内核,则成为李贽、黄宗羲等思想大师诞生的诱发因素。
文学是临川文化最为灿烂的篇章。
在北宋初年荒芜的词坛上,晏殊以自己的天才最先走进词苑,揭开宋词发展的序幕,流风所及,天下景从。他上继南唐、、“花间”之遗绪,下开北宋婉约之词风,在词的发展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为宋词的发展和一代文学的兴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自己的榜样,影响、带动和培育了一大批词人,形成了以他为首,以欧阳修、晏几道、张先为主要成员的“江西词派”,由此,历来受到词家的高度评价。冯熙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左宫右微,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薛砺若的《宋词通论》介绍北宋词坛四大开祖时,把晏殊排在首位。周笃文亦在其《宋词》—著中称:“崛起于词林而成为本期领袖人物的是晏殊和欧阳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宋词,是由他们掀开扉页的。
临川学人皆能为诗。晏殊作诗逾万。王安石的诗在全国是第一流的,后期更臻园熟,绝句尤负盛名,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荆公绝句妙天下”的称誉。“江西诗派”前期25人,临川区域有谢逸、谢莲、汪革和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尧节。李觏、曾巩的诗作,风格别具。陆九渊为以朱熹为首的“理学诗派”的骨干。在斑烂绚丽的中国诗史上,临川才子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以韩愈、柳宗元为首领和以欧阳修为盟主而分别发生在中唐和北宋的两次“古文运动”,实质上是以复古为旗帜的散文革新运动。领导和参加这场运动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等唐宋8大家,在中国散文史上处于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高举改革的旗帜,各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改变了散文的历史面貌,拨正了散文的发展方向,推动了散文的健康发展,使自由活泼、接近口语,更富表现力的新散文,长期占据了散文发展史上的主流地位。他们的功绩在于,重新恢复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夺回了被骈文统治数百年的文坛主导地位,再次确立了现实主义在散文领域的优势,击退了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逆流,完成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历史任务;他们在“文以载道”的前提下,苦心孤诣地追求文章之妙,极大地丰富提高了我国古典散文的艺术水平,为后世散文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在理论方面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成为后人创作的指导思想;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拓宽了散文的题材,丰富了散文的样式,使我国散文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臻完备和成熟。
唐宋8大家,江西为3,临川区域占其2,临川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1 6世纪汤显祖的诞生及其杰出的戏剧创怍成就,是临川文化最可引以自豪和骄傲的部分。
汤显祖是王学左派著名思想家罗汝芳的弟子,李贽的敬仰者,达观的交游者,徐谓的交往者,“三袁”的同道人,在晚明宦官专权、特务横行、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他不仅仗义执言,抨击时政,勤政为民,而且以明确的反叛封建礼教的思想和“自然而然”,反对模拟形似、格律至上的艺术追求,创作了名播四海的戏剧杰作《临川四梦》。汤显祖不愧是一位站在那个时代峰巅的思想巨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戏剧大师。
中国戏曲在发展途中,经历了元杂剧、明传奇、清传奇3座高峰。汤显祖生活在明代晚期。他的戏剧创作是第2座高峰的主要体现。他上继关汉卿等戏剧艺术之传统,下开孔尚任、洪升艺术精神之源流。他的出现,有如满月升起,照亮了整个明代文坛。
他和莎士比亚一起,双星辉映,高悬于人类艺术的天空。
临川区域的文论遗产十分丰富。李觏强调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雕锼以为丽”,同时又不排斥文采的一定重要性,嘲笑泥古,力主创新,肯定文章表现利欲,甚至认为诗可以道“男女之时,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见一国之风”。王安石提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的论断,看取文章的内容,强调文章“以适用为本”,又在这个前提下,给“以刻镂绘画为之容”的形式美以一定的地位。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唯物主义思想家对文学的主张和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和现实的借鉴价值。汤显祖的理论建树甚高。他在晚明极为复杂的思想艺术斗争中,取崇尚真性情而反对假道学的“童心”之说,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一道,抨击复古主义的文学逆流,同以沈臻为代表的“吴江派”的格律至上论展开论辩,对于后来的戏剧艺术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解放意义。艾南英是明末重要的文学批评家。面对当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倾向和片面追求格调、法度、彼此标榜、刻意模仿、盲目附和的形式主义歪风,作为全国三大文学批评学派之一的豫章派的首领,艾南英与当时在文坛负有重名的钱谦益一道,对前后“七子”和“竞陵派”之流,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与钱氏相呼应,痛斥七子和竟陵“骄”、“易”、“昧”、“欺”的批评态度,提出“通经学古”、“转益多师”、“无不学而又无不言”的文学主张,强调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又尊重别人的风格,而不要作兼并古人之想,也不可作抹煞一切之论。崇尚“千古文章独一史迁,史迁而后,千有余年,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的古文标准,抨击秦汉之伪体,六朝之俪体与古文家中尚奇的一派,针对当时批评界业已存在的埧气,编选了《文剿》、《文妖》、《文腐》、《文冕》、《文戏”》5书,以提供古文范本为学习上借鉴。他倡导文章内容与形式技巧的统一,要求语言“简约”,反对艰深晦涩、诘屈聱牙之作。所有这些,都为随后的“桐城派”文论思想开了先河。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对李、王、汤三氏的文学思想作了专节评述: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把艾氏与钱谦益并列,以一节之文,论之甚详。
临川区域素称文献之邦,学术文化十分丰厚。历代学者,或从事于诗词选注,或受命于类书、丛书,工具书的编纂,或潜心于史、地、天文、医术、数学的著述。《宋史》、《辽史》、《金史》、《明史》的编修,耗费了他们的心血、汗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康熙字典》的编纂,显示了他们的才学智慧;《古今治统》、《大宋重修广韵》、《太平寰宇记》、《王荆公年谱考略》、《江西诗征》、《乡诗摭谈》、《妇人大全良方》、《世医得效方》等,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古籍名著。据查,临川区域文人著述被收入《四库全书》目录者为206部①。辉辉煌煌的中华文化史册,永远闪耀着临川区域学者的名字。
临川文化的显赫,既表现于人才的众多和文化成就的重大,也表现于历史文化名人在中央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北宋太祖、太宗以前,将相重臣多是北人,真宗、仁宗时,开始起用南人为相。北宋中叶以后,南人当宰相的渐多。从五代至明代,临川区域先后有11人为相或副相②。这是我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一个外在显现,亦是古代临川区域文化昌盛和强劲的一个政治象征。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临川区域文化都是赣文化、中华文化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倘若缺少了这一部分,民族文化有可能出现某些断层或空白。这也是无须赘言的。
正因为这样,临川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现象,向来为国人所看重。早在宋代就有人研究临川文化(宋·詹太和撰《王荆公年谱四卷》,元大德五年出版),以后临川文化名人及其著述研究者,代有其人。至现、当代、先后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作家评传、作品选注、鉴赏辞典、名人辞典、科技专著,都给临川文化名人及其著述留下了重要地位。它们或列节介绍、或专章评述临川文化大家的生平、业绩及其地位。同时,文化界还整理、出版了临川区域作家、学者的多种著作。
正因为这样,临川文化大家及其成就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特别关注。
南宋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是现存宋人诗注中极富史料价值的一种,为学术界所推重。
李壁(1159—1222),字季章,号雁湖,眉州丹稜(今四川丹棱)人,南宋著名史学家焘第6子,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后兼知枢密院事。开禧三年(1207)至嘉定二年(1209),李氏谪居抚州时写成了《王荆文公诗笺注》一书,是书以注释详备、重视实物资料和辑佚补缺为其特点。
李壁书问世后,元代大德五年(1301),刘辰翁为便于儿侄阅读遂将此书评点、删略,并由门人王常予刊行,从此这个节本便广泛流传于世,而原本几成绝迹。1984年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先生在日本讲学时于名古屋市蓬左文库发现《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朝鲜古活字本),经与现通行本核对研究,发现该本不仅附载有宋人詹太和所撰的《王荆公年谱》,而且注诗较为详细,注文比现通行本竟多出一倍左右,附有“补注”、“庚寅增注”,基本恢复了宋本原貌,是现存版本中的最佳版本,亦是人间的一个孤本。此书对研究王安石诗文作品年代及王安石生平、著述和诗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的发现,是临川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收获,亦是临川文化在国内外影响的一个表证。
日本是国外王安石研究的中心。早在明治维新前,著名学者赖山阳著《读临川集书后》一文,高度评价王安石及其诗文。明治维新后,吉田宇之助撰《王安石》一书,称王氏变法乃“良医治疾”、“良医相国”,“实为富国强兵”,赞王安石“实支那史上空前之大人物”。现、当代以来,王安石研究在东土日本,队伍益壮,著述尤丰,论文如林。东一夫、东村治兵卫、高桥作卫、佐伯富、周藤吉之,都是有名的王荆公研究者。
元代崇仁理学家吴澄,在欧美等国广有影响。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俄亥俄州的大学历史系主任葛德卫教授,专攻元代理学,致力于《吴文正公全集》和“草庐学派”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 1986年,美国一批学者赴崇仁考察了吴澄的有关遗迹和史料。
一代戏曲大师汤显祖及其剧作,更是受到世界人民的称誉。早在20世纪初叶,他的名作就不断地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广泛传播,争相上演。德国汉学家洪德升用德文翻译了《牡丹亭》(至《惊梦》止),并在德国兰心大戏院隆重演出。英国用英文翻译了《牡丹亭》中《春香闹学》 —书,刊登在英国有名的《天下》月刊杂志第8卷4号上。日本学者、戏曲史专家青木正儿从本世纪2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戏曲和汤显祖的研究,其《 中国近世戏曲史》,用大篇幅介评汤氏的生平及剧作,第一次把汤显祖和英国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原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卷四盛赞《牡丹亭》对旧道德的挑战。英、美、日诸国还不断派遣留学生来中国研究中国戏曲和汤氏剧作。
另外,危亦林、李据、龚廷贤诸氏的医著,徐奋鹏的史著,吴嵩梁、李瑞清的书画,亦在国外备享盛誉,广为流传。
值得重视的是,临川文化的强力影响和高能辐射,不但表现在对世界文化历史进程的推动上,而且表现在现、当代本区域人才涌流的激励机制上。仅以临川一县而论,且不说中国物理学“四大名旦”之一的饶毓泰,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波谱学奠基人丁渝,著述宏富、饮誉中外的《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杜甫研究专家肖涤非,蜚声海内外的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著名化学家邓从豪等,都是临川籍人氏,且不说该县在外地学习、工作的副教授、诗人、作家和副师级以上人物计有14 0余人,各学科研究生49人,留学生19人,仅自恢复高考以来的15年中,该县向各大中专学校输送的学生就多达万余人,少年班大学生61人。不少人家,一家数人上大学,读研究生,不少村庄,大学生成团出现,被称为“大学生之家”、“留学生之户”、“大学生之村”。历届全国初、高中(含省、地)各学科竞赛,临川学生获奖者居全省县级首位。
“烟波楼阁春如海,明日临川更绝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乐诗书而好文辞”的临川人民,正在接过先辈点燃的文化火炬,奋然进取,开拓未来,为世人注目的临川文化,必将出现更大的繁荣。
可以说,一部临川区域文化发展史,就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临川才人脱颖而出,争奇比秀,创造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什么原因使临川文化如此繁荣,如此辉煌,而且由宋代至近代,延绵千年而不衰呢?我们以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中华文化中心的南移和外域文人对本土文化的浸润、浇灌,是临川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临川文化的兴盛自宋而始,究其原因,是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态势所制约、所决定的。宋以后,南方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推动文化中心南移之势最后完成。这个历史变动,对江南、对临川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久远的。
之一,随着宋王朝对南方经济依赖的加强,在政权上进一步实行对南人开放。这就给南方士人参与朝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推动他们进德力学、焕发才华、崭露头角。南方士人在这种现实刺激下,怀抱继圣道,建功业,求闻达的浩然之志,兴学重教,奋发读书,大批人才应运而生,《东乡县志》(新修)收入县邑历代进士87人,其中,北宋6人,南宋们人,元代2人,明代22人,清代17人,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说明。
之二,文化中心南移过程中,直接给南方士子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帮助他们扩大心胸,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公元961年,南唐迁都洪州。这个设教坊、立画院,网罗词客,重视艺术的小邦,深刻影响了江西文艺家的成长。南唐重臣、雅爱词章而成为词坛中心人物之一的冯延已曾在抚州任职3年(948—951),把词的种子撒播在临川的土地上,对临川区域词人影响殊深。晏殊就是承其流响的。
之三,受历史潮流之裹挟,北人南迁,不仅帮助了江南经济的开发,而且带来了士族重视族人子弟教育的传统、风习。抚州士人先辈多系从外地辗转迁徙而来的。他们来此落籍后,普遍重视对子弟的培养,或筑馆以教,或家学以传,无不竭尽全力。如王安石,先世为太原人,曾巩先辈为山东人,陆象山,远祖是北方人等。他们先祖迁到临川区域后,兴起了一代又一代良好文风和学风,影响是很大的。
之四,由于临川区域邻近南昌,魏晋以来特别是唐统一以后,大批文士纷纷来临川供职、讲学、寓居和游览。谢灵运、王羲之、颜真卿、陆游等,这些文人名士在临川区域的种种活动、业绩、著述、佳话,给临川文化以沾溉,以营养,以促进,无疑是临川文化万木峥嵘的春风雨露。
其次,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如第一章所论,临川区域,处于赣东,紧邻南昌,控带瓯越,襟领江湖。境内,山环水贯,地势平广,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既有山林竹木之利,舟楫水利之便,又有渔米、桑麻之养,通商贸易之惠。北方战乱频繁,而临川整个区域,和平而安宁,兴旺而富庶。由于此,四方商贾云集于此,文人雅士常会于斯。这是一块生存的乐土,图强的渊薮,是颇能吸引人们来此落籍生根的,是极利于发展生产、兴办教育、积累文化的。勤劳淳朴,安土乐业的临川区域人民正是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也用自己的灵秀创造了光华灿烂的学术文化。临川区域在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之后,于宋一代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局面,乃势所必然。
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泰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序言和《艺术哲学》等论著中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创作、文学产生和发展的3种力量,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是制约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1个因素。现代学者亦重视从生存环境寻找人类文化的根源。我们在研究临川文化昌隆缘由的时候,是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临川区域特定历史环境及由此决定的交通、经济状况这个母体的。
再次,发达的官学、书院教育和喜诗书、好礼仪的社会风气,是临川人才并肩接踵,成团涌现的基本原因。自古以来,我国一向以士农为骨干,以孝悌力田,敬祖先、睦家族为教化,耕读传家,习以为常。临川区域为江南腹地,环境既开放又封闭。临川人民扬己宜于农桑之长,遵循“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家训,勤耕织以得衣食,喜诗书以求闻达,读书之风极盛。古代临川市井,书坊林立,毛笔生产驰名东南,印刷行业特别发达,到处是浓浓的文化氛围,亦是这种重文风气的一种反映。临川英才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发育、生成的。
临川区域的官学教育成绩显著。由于晏殊的力倡和力行,自仁宗天圣年间起,“天下皆立学”,临川区内亦然,且基础好,起手早,办学多。临川学子和当时他地文人一样,凡所到之处喜欢为州县写“学记”。李靓作《袁州州学记》,王安石作《虔州学记》,曾巩作《宜黄县县学记》等等,反映了当日江西、抚州对教育的重视和兴学的盛况。
临川区域以宋为始,除官学外,书院遍布,名儒巨子,聚徒讲学,四方学子,闻风从游,为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觏,创盱江书院于凤凰岗麓,“门人随镓者干有余人”。
曾巩入仕前曾创兴鲁书院于今抚州市香楠峰(抚州地委大院之地),亲自为之制定学规,远近生徒聚而从之,名人学士济济一时,抚州文风盛、人才多,曾巩实有倡学之功。
“百世大儒”陆九渊1 172年至1 175年登进士第在家候职期间,1186年至1191年离京还里在家闲居,始从教于槐堂书院,继设讲于“象山精舍”,从学之士,四方云集。其弟子有杨简、傅梦泉、邓约礼、彭世昌、黄叔丰、石斗文、傅子云、陈刚、俞廷蝽、李伯敏、詹阜民、包杨等65人。他们簇拥陆氏讲席,组成了陆氏“心学”学派的基本队伍。
罗汝芳于1544年在南城东南郊创从姑山房,接待四方来此讲学之士。16年后,任刑部山东司主事的罗汝芳回南城探亲,求学者踵至,时年13岁的汤显祖亦拜罗为师,学习其“百姓日用即道”的理学体系,对汤氏日后的思想和创作影响深远。
国家之兴,人才为上,人才之道,本在教育。临川区域人才荟萃,广教、重学是一条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
第四,临川区域士人普遍具有的主“通变”、立新说、开拓进取、勇于超越的心理机制和坚持真理、忠于学术、喜欢辩难的文化精神,是临川文化取得很高成就的深层动因。李觏作为哲人是一位勇猛的战士。他在肯定世界的物质性的同时,力主天“道”的变通,认为“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①。尤为可贵的是,在当时理学思想笼罩整个社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存天理、灭人欲”等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把人们禁锢得密不透风的情况下,敢于大发“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言不可言,无乃赋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这样的惊人之论,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言利、言欲的合理性,表现了其对虚伪道学十分可贵的批判精神,体现了临川区域哲人义利统一,情理交错的心理结构。陆九渊不愧是一位走新路、创新猷的大学者。在程朱理学已形成体系之时,另打旗号,立“心即理”的心学一派,虽然其说与程朱之学都属唯心主义阵营,但前者与后者在本体论、性论和方法论诸方面殊异。这就引发了两派在学术上的长期对立和论争。清代金溪蔡上翔费27年之工,撰写了《王荆公年谱考略》,力排俗议,为改革家王安石辩诬,都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临川文人的学术战斗精神和析疑求真,不为旧说所缚,不为俗见所囿的开拓性格。
第五,长辈前贤重视对后辈的奖引、举荐,提携,是临川区域人才大量涌现的重要条件。晏殊才高学广,识见明决,深知治国本末,从35岁入枢府至54岁罢相,十余年如一日,知人善任,求贤若渴,荐贤如流,一代名臣贤士,都出其门。曾巩对王安石乡谊极深,先后于庆历四年、五年,两次致书欧阳修举荐王安石,庆历六年,欧阳修贬知滁州,曾巩亲赴滁州面呈王安石文章。据他的《与王介甫第一书》云,欧公得王文后,颇称其善,“爱叹诵写”,“不胜其勤”,并希望得以一见。10年后,欧公在朝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王调任开封群牧司判官,两位文学家方会晤于京都,高兴之余,互赠诗文,欧公并立即向仁宗推荐王安石,并在后来还向仁宗荐王安石为谏官。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尽管后期政见不尽相同,但个人交谊甚厚。欧阳修死后在众多的祭奠文章中,唯王荆公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写得最为真切感人。王安石亦以人才为务,理论一上多有发挥。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倡导政治变革,而其核心的内容是论述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他还专门写了《材论》一文,起用了包括临川人才在内的许多年轻有识之士,为其改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第六,临川区域士子、地方官都热心于古籍整理和地方文献的考证、编集,是临川文化持续繁荣、发展诸动因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前面说过,抚州是“文献之邦”,历代文人撰著甚丰。这些文献倘任其流散,势必给文化的发展造成莫大的损失。抚州学子、官宦深明此理,普遍重视致力于文集,文章的整理、考据、编辑工作。从刘宋时期临川内史荀伯子修《临川记》6卷(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卷2;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6;李肪《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9;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54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开始,就有宋代抚州教授徐天麟、户部郎中知临川军事家坤翁、明代抚州知府黄显、蔡邦俊修《临川志》《抚州府志》,宋代以下各朝知县、郡守、推官、邑人70余人修纂建昌府志和临川、南城、崇仁、乐安、宜黄、南丰、黎川、资溪、金溪、东乡等各县县志。清刘玉瓒辑选《临川文选》6种。清临川知县胡亦堂辑《临川文献》15种25卷,包括:晏同叔先生集2集、晏叔原先生集1卷、王介甫先生集2卷、章介庵先生文集2卷、陈明水先生集2卷、帅惟审先生集2卷、汤义仍先生集2卷、丘毛伯先生集2卷、章大力先生集1卷、艾千子先生集1卷、罗文止先生集1卷、陈大士先生集1卷、揭蒿庵先生集2卷、游日生先生集2卷、傅平叔先生集2卷。金溪乾隆43年进士王谟,无意仕途,喜好考据之学、才识雄伟,精力过人,雅慕郑樵、马端临二贤(均为考据学家),终日采经摘传,搜罗散失旧闻,以补史书之缺,著有《江西考古录》1卷,《豫章十代文献考略》50卷,编辑《汉魏遗书抄》 500余种。清吕留良辑评《江西五家稿》5种,清冯行辑《黎川文载》24卷。清黎川诗人、学者杨希闵在前人卷轶浩繁的文史著述基础上,先后辑有《水经注汇校》 40卷,《四书改错平》1 4卷,《四朝先贤六家年谱》、《豫章先贤九家年谱》15卷,《绝句诗选》3卷、《诗榷》12卷、《乡诗摭谭》正1 0卷、续1 0卷,仅后者就评述了陶渊明以来江西340多位诗人,是研究江西诗歌发展史极为重要的参考史料。
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思格斯亦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②可以认为,临川文化在发展的途程中,所得到的先辈的遗产是极其丰厚的,“特定的思想资料”这个“前提”是相当充分的。
第二节临川文化的地位和影响自宋而清,临川文化郁郁乎如春林竞秀,灿灿然似秋夜长空。在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临川区域的历代文化名人,以自己的卓越才能,为中华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作出了光耀史册的贡献,而其中许多天才大家的思想、著述和业绩,则是华厦文化中最有价值、最为耀眼的一个部分。如果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座辉煌无比的精神大厦,那么,临川区域的诸多文化伟人,则充当了构建这座大厦的某些部分的梁柱。临川文化是属于江西的,亦是属于全民族、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
审视临川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和横向的生存态势及其所发散的价值能量,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无论在当时,抑或于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北宋是个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封建王朝。面对“三冗”严重、积贫积弱的颓危国势,“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发动和领导了以“理财”为中心,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政治改革运动,由于过于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破坏,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收到的促进生产、增加收入、壮大国力的实效是明显的。它表现了临川文化伟人积极进取、变革图新的战斗精神。
临川士子尊师重教,倡学笃行,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江南文化的开发和南北文化的全面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晏殊,早在仁宗天圣年间任应天知府时,即延请范仲淹“以教生徒”,后来升任宰相,更是全面关心各处人才的培养,以至天下洲郡学校大兴,贤才俊士涌流于世,形成江南才子甲于天下,江西才子复冠江南的可喜局面。晏殊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发展史和江南文化开发史上居于先驱者地位。
理学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以伦理为本体,涵泳儒、释、道三教思想之精粹的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哲学体系。北宋以降,江西是理学的发达之地,而安祥、温馨的临川区域,致力于理学探研的人物尤多,大家巨子尤众。南宋以陆象山为代表的象山学派,元代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明代泰州学派的三传弟子罗汝芳和以吴与弼为代表的崇仁学派,清代以谢文存为代表的程山学派,表现了临川区域哲人开宗创派的学术进取精神,展示了临川区域理学的繁荣景象。尤其是陆象山“心学”的创立,作为主观唯心论之一翼,与朱熹的客观唯心论一起,共同构建了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使之更加完整、恢宏、深刻和精致。同时,从抽象方面发掘和强化了人“心”的本原性心理能量,突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超越性。陆象山及其后继者王阳明的“陆王心学”,对元、明、清三代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其“人皆可为圣人”,“百姓日用为道”的命题及其合理内核,则成为李贽、黄宗羲等思想大师诞生的诱发因素。
文学是临川文化最为灿烂的篇章。
在北宋初年荒芜的词坛上,晏殊以自己的天才最先走进词苑,揭开宋词发展的序幕,流风所及,天下景从。他上继南唐、、“花间”之遗绪,下开北宋婉约之词风,在词的发展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为宋词的发展和一代文学的兴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自己的榜样,影响、带动和培育了一大批词人,形成了以他为首,以欧阳修、晏几道、张先为主要成员的“江西词派”,由此,历来受到词家的高度评价。冯熙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左宫右微,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薛砺若的《宋词通论》介绍北宋词坛四大开祖时,把晏殊排在首位。周笃文亦在其《宋词》—著中称:“崛起于词林而成为本期领袖人物的是晏殊和欧阳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宋词,是由他们掀开扉页的。
临川学人皆能为诗。晏殊作诗逾万。王安石的诗在全国是第一流的,后期更臻园熟,绝句尤负盛名,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荆公绝句妙天下”的称誉。“江西诗派”前期25人,临川区域有谢逸、谢莲、汪革和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尧节。李觏、曾巩的诗作,风格别具。陆九渊为以朱熹为首的“理学诗派”的骨干。在斑烂绚丽的中国诗史上,临川才子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以韩愈、柳宗元为首领和以欧阳修为盟主而分别发生在中唐和北宋的两次“古文运动”,实质上是以复古为旗帜的散文革新运动。领导和参加这场运动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等唐宋8大家,在中国散文史上处于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高举改革的旗帜,各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改变了散文的历史面貌,拨正了散文的发展方向,推动了散文的健康发展,使自由活泼、接近口语,更富表现力的新散文,长期占据了散文发展史上的主流地位。他们的功绩在于,重新恢复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夺回了被骈文统治数百年的文坛主导地位,再次确立了现实主义在散文领域的优势,击退了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逆流,完成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历史任务;他们在“文以载道”的前提下,苦心孤诣地追求文章之妙,极大地丰富提高了我国古典散文的艺术水平,为后世散文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在理论方面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成为后人创作的指导思想;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拓宽了散文的题材,丰富了散文的样式,使我国散文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臻完备和成熟。
唐宋8大家,江西为3,临川区域占其2,临川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1 6世纪汤显祖的诞生及其杰出的戏剧创怍成就,是临川文化最可引以自豪和骄傲的部分。
汤显祖是王学左派著名思想家罗汝芳的弟子,李贽的敬仰者,达观的交游者,徐谓的交往者,“三袁”的同道人,在晚明宦官专权、特务横行、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他不仅仗义执言,抨击时政,勤政为民,而且以明确的反叛封建礼教的思想和“自然而然”,反对模拟形似、格律至上的艺术追求,创作了名播四海的戏剧杰作《临川四梦》。汤显祖不愧是一位站在那个时代峰巅的思想巨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戏剧大师。
中国戏曲在发展途中,经历了元杂剧、明传奇、清传奇3座高峰。汤显祖生活在明代晚期。他的戏剧创作是第2座高峰的主要体现。他上继关汉卿等戏剧艺术之传统,下开孔尚任、洪升艺术精神之源流。他的出现,有如满月升起,照亮了整个明代文坛。
他和莎士比亚一起,双星辉映,高悬于人类艺术的天空。
临川区域的文论遗产十分丰富。李觏强调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雕锼以为丽”,同时又不排斥文采的一定重要性,嘲笑泥古,力主创新,肯定文章表现利欲,甚至认为诗可以道“男女之时,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见一国之风”。王安石提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的论断,看取文章的内容,强调文章“以适用为本”,又在这个前提下,给“以刻镂绘画为之容”的形式美以一定的地位。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唯物主义思想家对文学的主张和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和现实的借鉴价值。汤显祖的理论建树甚高。他在晚明极为复杂的思想艺术斗争中,取崇尚真性情而反对假道学的“童心”之说,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一道,抨击复古主义的文学逆流,同以沈臻为代表的“吴江派”的格律至上论展开论辩,对于后来的戏剧艺术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解放意义。艾南英是明末重要的文学批评家。面对当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倾向和片面追求格调、法度、彼此标榜、刻意模仿、盲目附和的形式主义歪风,作为全国三大文学批评学派之一的豫章派的首领,艾南英与当时在文坛负有重名的钱谦益一道,对前后“七子”和“竞陵派”之流,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与钱氏相呼应,痛斥七子和竟陵“骄”、“易”、“昧”、“欺”的批评态度,提出“通经学古”、“转益多师”、“无不学而又无不言”的文学主张,强调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又尊重别人的风格,而不要作兼并古人之想,也不可作抹煞一切之论。崇尚“千古文章独一史迁,史迁而后,千有余年,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的古文标准,抨击秦汉之伪体,六朝之俪体与古文家中尚奇的一派,针对当时批评界业已存在的埧气,编选了《文剿》、《文妖》、《文腐》、《文冕》、《文戏”》5书,以提供古文范本为学习上借鉴。他倡导文章内容与形式技巧的统一,要求语言“简约”,反对艰深晦涩、诘屈聱牙之作。所有这些,都为随后的“桐城派”文论思想开了先河。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对李、王、汤三氏的文学思想作了专节评述: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把艾氏与钱谦益并列,以一节之文,论之甚详。
临川区域素称文献之邦,学术文化十分丰厚。历代学者,或从事于诗词选注,或受命于类书、丛书,工具书的编纂,或潜心于史、地、天文、医术、数学的著述。《宋史》、《辽史》、《金史》、《明史》的编修,耗费了他们的心血、汗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康熙字典》的编纂,显示了他们的才学智慧;《古今治统》、《大宋重修广韵》、《太平寰宇记》、《王荆公年谱考略》、《江西诗征》、《乡诗摭谈》、《妇人大全良方》、《世医得效方》等,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古籍名著。据查,临川区域文人著述被收入《四库全书》目录者为206部①。辉辉煌煌的中华文化史册,永远闪耀着临川区域学者的名字。
临川文化的显赫,既表现于人才的众多和文化成就的重大,也表现于历史文化名人在中央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北宋太祖、太宗以前,将相重臣多是北人,真宗、仁宗时,开始起用南人为相。北宋中叶以后,南人当宰相的渐多。从五代至明代,临川区域先后有11人为相或副相②。这是我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一个外在显现,亦是古代临川区域文化昌盛和强劲的一个政治象征。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临川区域文化都是赣文化、中华文化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倘若缺少了这一部分,民族文化有可能出现某些断层或空白。这也是无须赘言的。
正因为这样,临川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现象,向来为国人所看重。早在宋代就有人研究临川文化(宋·詹太和撰《王荆公年谱四卷》,元大德五年出版),以后临川文化名人及其著述研究者,代有其人。至现、当代、先后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作家评传、作品选注、鉴赏辞典、名人辞典、科技专著,都给临川文化名人及其著述留下了重要地位。它们或列节介绍、或专章评述临川文化大家的生平、业绩及其地位。同时,文化界还整理、出版了临川区域作家、学者的多种著作。
正因为这样,临川文化大家及其成就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特别关注。
南宋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是现存宋人诗注中极富史料价值的一种,为学术界所推重。
李壁(1159—1222),字季章,号雁湖,眉州丹稜(今四川丹棱)人,南宋著名史学家焘第6子,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后兼知枢密院事。开禧三年(1207)至嘉定二年(1209),李氏谪居抚州时写成了《王荆文公诗笺注》一书,是书以注释详备、重视实物资料和辑佚补缺为其特点。
李壁书问世后,元代大德五年(1301),刘辰翁为便于儿侄阅读遂将此书评点、删略,并由门人王常予刊行,从此这个节本便广泛流传于世,而原本几成绝迹。1984年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先生在日本讲学时于名古屋市蓬左文库发现《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朝鲜古活字本),经与现通行本核对研究,发现该本不仅附载有宋人詹太和所撰的《王荆公年谱》,而且注诗较为详细,注文比现通行本竟多出一倍左右,附有“补注”、“庚寅增注”,基本恢复了宋本原貌,是现存版本中的最佳版本,亦是人间的一个孤本。此书对研究王安石诗文作品年代及王安石生平、著述和诗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的发现,是临川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收获,亦是临川文化在国内外影响的一个表证。
日本是国外王安石研究的中心。早在明治维新前,著名学者赖山阳著《读临川集书后》一文,高度评价王安石及其诗文。明治维新后,吉田宇之助撰《王安石》一书,称王氏变法乃“良医治疾”、“良医相国”,“实为富国强兵”,赞王安石“实支那史上空前之大人物”。现、当代以来,王安石研究在东土日本,队伍益壮,著述尤丰,论文如林。东一夫、东村治兵卫、高桥作卫、佐伯富、周藤吉之,都是有名的王荆公研究者。
元代崇仁理学家吴澄,在欧美等国广有影响。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俄亥俄州的大学历史系主任葛德卫教授,专攻元代理学,致力于《吴文正公全集》和“草庐学派”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 1986年,美国一批学者赴崇仁考察了吴澄的有关遗迹和史料。
一代戏曲大师汤显祖及其剧作,更是受到世界人民的称誉。早在20世纪初叶,他的名作就不断地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广泛传播,争相上演。德国汉学家洪德升用德文翻译了《牡丹亭》(至《惊梦》止),并在德国兰心大戏院隆重演出。英国用英文翻译了《牡丹亭》中《春香闹学》 —书,刊登在英国有名的《天下》月刊杂志第8卷4号上。日本学者、戏曲史专家青木正儿从本世纪2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戏曲和汤显祖的研究,其《 中国近世戏曲史》,用大篇幅介评汤氏的生平及剧作,第一次把汤显祖和英国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原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卷四盛赞《牡丹亭》对旧道德的挑战。英、美、日诸国还不断派遣留学生来中国研究中国戏曲和汤氏剧作。
另外,危亦林、李据、龚廷贤诸氏的医著,徐奋鹏的史著,吴嵩梁、李瑞清的书画,亦在国外备享盛誉,广为流传。
值得重视的是,临川文化的强力影响和高能辐射,不但表现在对世界文化历史进程的推动上,而且表现在现、当代本区域人才涌流的激励机制上。仅以临川一县而论,且不说中国物理学“四大名旦”之一的饶毓泰,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波谱学奠基人丁渝,著述宏富、饮誉中外的《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杜甫研究专家肖涤非,蜚声海内外的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著名化学家邓从豪等,都是临川籍人氏,且不说该县在外地学习、工作的副教授、诗人、作家和副师级以上人物计有14 0余人,各学科研究生49人,留学生19人,仅自恢复高考以来的15年中,该县向各大中专学校输送的学生就多达万余人,少年班大学生61人。不少人家,一家数人上大学,读研究生,不少村庄,大学生成团出现,被称为“大学生之家”、“留学生之户”、“大学生之村”。历届全国初、高中(含省、地)各学科竞赛,临川学生获奖者居全省县级首位。
“烟波楼阁春如海,明日临川更绝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乐诗书而好文辞”的临川人民,正在接过先辈点燃的文化火炬,奋然进取,开拓未来,为世人注目的临川文化,必将出现更大的繁荣。
附注
① 《李觏集》卷第29《原文》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②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① 含“经部”39部,“史部”25部,“子部”45部,“集部”97部
② 五代的元德昭,北宋的陈彭年、元绛、晏殊、王安石、曾布,南宋的董德元、陈宗礼、曾渊子,元代的危素,明代的吴道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