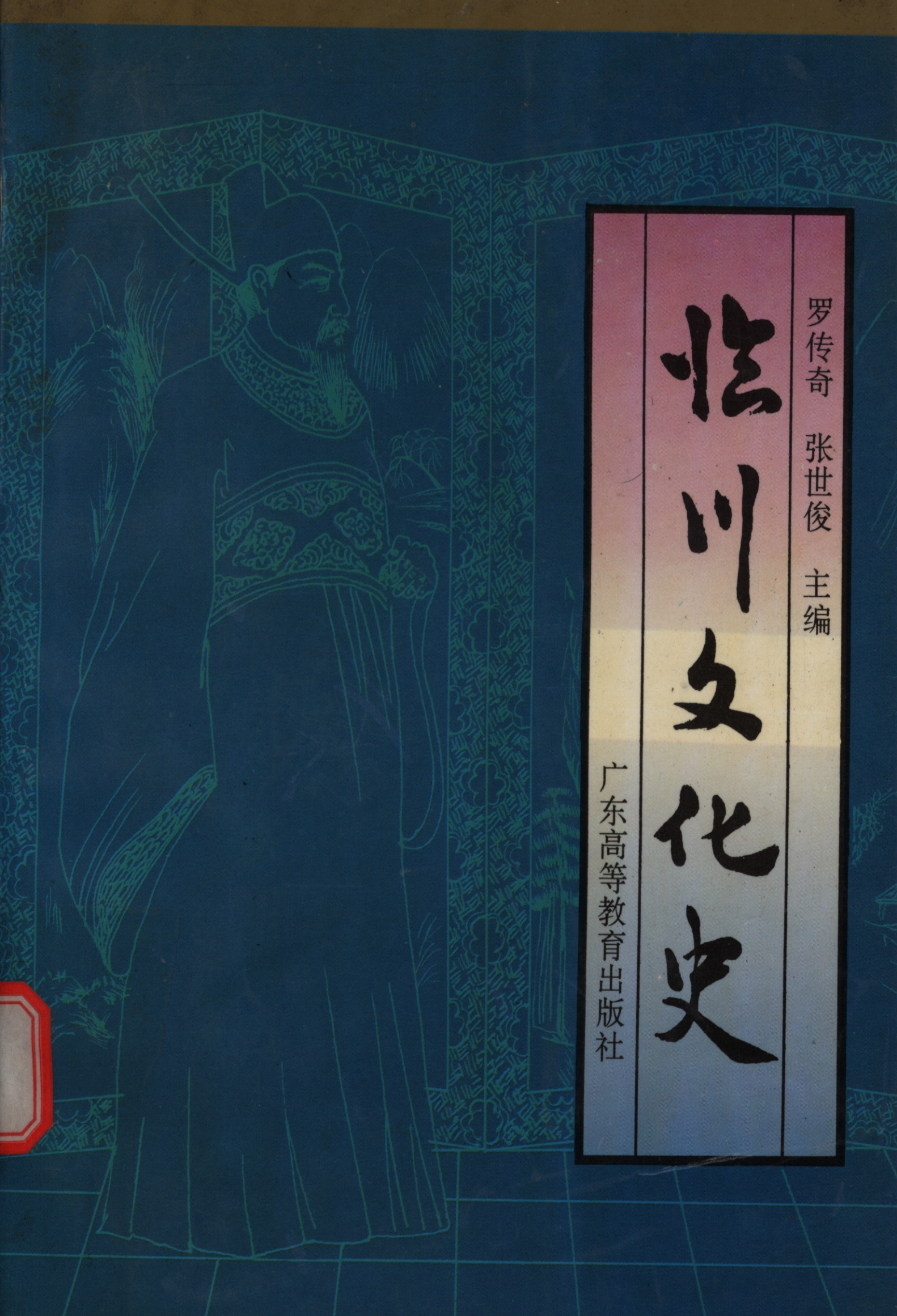第十一章 史学的成就
| 内容出处: | 《临川文化史》 图书 |
| 唯一号: | 140220020210000152 |
| 颗粒名称: | 第十一章 史学的成就 |
| 分类号: | K0 |
| 页数: | 22 |
| 摘要: | 自东晋至陈亡约300年间,长江流域经济得到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到了北宋以后,临川就跨入了全国先进行列,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历代不衰。不仅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及其光照海内外的传世之作,也产生了一批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及优秀历史著作。他们有的奉旨参加编修正史;有的整理历史文献,辑校古史;有的搜集资料修纂实录、古史和名人年谱;有的潜心研究,辨伪古史,撰写史评和史学理论,在史学领域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史学典籍,大大丰富了临川文化宝库。 |
| 关键词: | 史学家 史学流派 史学理论 |
内容
第一节史学发展概述自东晋至陈亡约300年间,长江流域经济得到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到了北宋以后,临川就跨入了全国先进行列,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历代不衰。不仅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及其光照海内外的传世之作,也产生了一批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及优秀历史著作。他们有的奉旨参加编修正史;有的整理历史文献,辑校古史;有的搜集资料修纂实录、古史和名人年谱;有的潜心研究,辨伪古史,撰写史评和史学理论,在史学领域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史学典籍,大大丰富了临川文化宝库。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一批体大思精,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史书体裁、历史文献学都有相当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宋代史学超越前代突出的地方,是史学思想的发展。在宋代众多的临川文人中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的突出的史学家有乐史、陈彭年、曾巩和吴曾等。乐史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写过不少史学著作,流传下来的有收入《四库全书》的《广卓异记》。唐人李翱著有《卓异记》3卷,记述唐代君臣卓绝盛事。但其中漏录甚多,乐史先为此书作续记3卷,以补其阙。后又复以其仅载唐代君臣之事,未为广博,因而又纂集汉魏以下迄五代之事,共为一帙,名为《广卓异记》。此书分为20卷,记载了帝王将相、王后嫔妃的重要活动。其中载录了一些权臣“贵盛之极,显达奇速”,暴露了宋代官场的腐败,官吏的贪赃枉法。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实录。晚于乐史30年的陈彭年,是北宋南城人。他在直史馆任职时著有史书《江南别录》1卷。成书前徐铉、汤锐方奉诏撰有《江南录》。陈彭年感其疏漏不全,因而自纂此书,以补其未备,故以别录为名。此书记录了南唐义祖、烈祖、元宗、后主四代事,是一部南唐的实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著名的文学家曾巩,除了在文学上建树非凡外,在史学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只因其史名为文掩盖,所以一般人对其史学成就知之甚少。他在史馆任职期间,曾负责编校过《战国策》、《新序》、《说苑》、《陈书》等古代史籍。《战国策》、《说苑》和《新序》由于他的访求采录,才免于散佚。他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和咏史诗词,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并有史学专著《隆平集》传世。曾巩的史学,当时就“见称史类”,得到朝廷的赞赏,更为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所推崇,被称之为与刘知几、郑樵相侪的“良史才”。南宋的史学家当推崇仁人吴曾。他出仕工部郎中,出知严州,去贪官,恤良民,颇有善政。他一生著述繁富,重要的史学著作有《春秋考异》、《左传发挥》、《新唐书纠谬》、《南征北伐编年》、《南北事类》等。他还著有30余万言的《能改斋漫录》。此书记载了唐宋时期不少历史事件和人物掌故。其征引繁富,考据精细,对研究唐宋两代文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南宋笔记著作中堪称佳本,可与洪迈的《容斋随笔》相媲美。
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蒙古贵族重武功而轻文治,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汉族文人遭受歧视压迫,史学领域比起两宋时期相对冷落。这时期临川区域在史学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有著名的学者虞集、著名的文史学家危素、何中等。虞集一生致力教书、编撰,博学多才,号称诗文大家。他仿效“唐宋会要”编修《经世大典》,著有《道园学古录》,史学著述有《平穑记》1卷。元统三年(1334 )冬,广东瑶民进犯贺州、富州。至元元年(1335)广西宣慰使章巴颜率兵讨平之。虞集撰《平猛记》一卷,记载巴颜平粤西瑶洞事迹的始末。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正如《四库全书》所云,此书可“备国史之揉也。”著名的历史学家危素,以毕生的精力投入史学研究中。元代至正元年(1336),出任经筵检讨,奉诏参与编纂宋、辽、金史。书成,受到元顺帝大力奖赏。入明为翰林侍讲学士,奉诏与宋濂同修《元史》。他还为其师吴澄修订了《草庐年谱》2卷。危素的历史著述和研究为历史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元末学者何冲(1266—1322),乐安人,曾应聘主讲南昌东湖、宗濂二书院。史书著有《通鉴纲目测海》3卷。何中在此书自跋中说:“朱子作纲目,续春秋,然其间书法,可商略者犹多,闲附已意,辑成纲目测海三篇, 示儿辈云云。”可知此书是为纠正朱熹《通鉴纲目》的伪异而作,洧一定的史学研究价值。
明代中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老时期,但生产力在继续发展,弛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很活跃,尤其是东南沿海和长江中午游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这时期的戒就不够高。但明代的实录可以传抄,这为私人修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方便。明人修史大多取材于实录,私人修史极多,所作史书极为繁富。在这种氛围下,临川拥现了一大批文人私修史籍。名载古籍的有徐奋鹏、邓元锡、饶秉鉴、何乔新、周孔教、李纪、姜洪、王萁等人。著名的文史学家徐奋鹏,明代临川人。他终身不仕,潜心治学,用毕生的精力写成了《古今治统》20卷、《怡思集》10卷、《辩俗》10卷,删补《毛诗朱注》等。他的《古今治统》独笔生津,不畏豪强,弥补了前人的不足,辨别了历史的真伪,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史评。 明代学者邓元锡,字汝极,号潜谷,新城人(今黎川县),官至翰林院侍诏,著有《函史》102卷,《明书》45卷。《函史》是一部仿郑樵《通志》之作的通史,起自三皇,终于元代。邓元锡认为郑樵的纪传体例因袭旧史不够划一,二十略是其所创,但其内容夸大,根据不足。邓元锡对此作了体例上的变更,其纪传的体例变更很大,分得更细。这种体例划分虽然显得芜杂,但此书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古代历史人物史迹和典章制度。《明书》是一部起于明太宗,终于明世宗的断代史。其体例仿范晔的《后汉书》,记述较具体详细。这两部史书都是研究古代历史的有价值的资料。明代学者饶秉鉴,字宪章,广昌县人,官至廉州太守。他为官清廉,颇有政声,罢官后创设“雯峰书院”,授业之余,潜心研究学术,对《春秋》一书究其本源,研精微深,博采众家之长,直抒胸臆,穷尽10载,写成《春秋提要》和《春秋会通》两书。此2书收入《四库全书》,是一份可贵的史学遗产。
与李觏、曾巩、罗起、罗近溪,邓潜谷(元锡)、朱大器等人号称抚(州)建(昌)文章7大家之一的何乔新,字延秀,号椒丘,初授礼部主事,后改任南京刑部主事,秉公执法而闻名。生平著述宏富,史学著作有《宋元史臆见》、《文苑群玉》、《续编百将传》等。
对古史颇有研究,见解深微,可供后人借鉴,受到学界称誉,时称他为椒丘先生。明代较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金溪民间文人李纪的《史略详注补遗大成》10卷。初庐陵人曾先之撰十八史略,写至宋为止。明初临川人梁孟寅增补元代史事,名为十九史略。后李纪认为旧著不完备,因而加以增补而成此书。这是一部民间文人编撰的史略,可补正史之未备。还应提及的是临川人周孔教著的《周中丞疏稿》16卷。其文集有《西台疏稿》2卷,《中州疏稿》5卷,《江南疏稿》9卷。其《西台疏稿》极论赵志皋、石星等弃日本亲朝鲜之失策,《江南疏稿》内论停职造、止加派及丁末救荒诸政事;其余则是些案牍之文。此文集当朝名臣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为之作序,是研究当朝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要史料。此外乐安人姜洪参与修撰的《宣宗实录》,金溪人王奠著的《忠义录》1 4卷,也是有价值的史书。《忠义录》取史传忠义之事,分类编辑,各节所录史实均加以品评,持论颇正,可供我们研究古代历史人物参考。
清朝是满州贵族建立的封建专制王朝。清初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出现了“康乾盛世”。但清朝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特别严酷,统治者大力提倡理学,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统治。清代文人由于惧罹文网,不敢研究明史及当代史,大都钻进故纸堆,因而考据学大兴,史学研究便向历史文献学方面转化。这一特点在临川史学方面得到反映。此期临川籍学者的史学著作较少,较突出的有临川学者李绂,他崇尚理学,一生著述甚富,著有《春秋一是》、《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阳明学录》、《穆堂初稿、续稿、外稿》、《陆象山年谱》等。金溪学者蔡上翔著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以及金溪文献学家王漠著有《补证古史》等。李绂,(1657—1750)字臣来,号穆堂,官至内阁学士,礼、吏、兵、户、工五部侍郎、广西巡抚、直隶总督等,是一代名臣。他博学多才,又是一代学者。李绂崇尚陆象山之学,著有《陆象山年谱》2卷。初《陆象山年谱》为陆门人袁燮、傅子云同编,后李子愿又重辑之。李绂认为这部年谱不全,又未载陆九龄、陆九韶之事绩,因而重加补辑,遂成此书。这是研究陆象山兄弟的重要史料。清代著名学者蔡上翔(1717—1808)字元凤,号东墅,金溪县城东门蔡家人,进士出身,曾任四川省东乡县知县,政尚严肃,深得巴蜀人民之心。他一生著作甚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王荆公年谱考略》。蔡上翔读王荆公书,“常愤后世诋毁者皆失实”,因而耗费27个春秋,“所阅正史及百家杂说,不下数千卷”,遂成此书,全书约30万字,时年已88岁。他潜心研究,旁征博引,“考其事而辨其诬”,力排众议,驳斥了700年来封建士大夫强加在王安石头上的诬陷,还其历史的真面目,为后世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运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文献学家王漠,一生博览群书,才识雄隽,尤精江西地方文献及舆地之学,著有《江西考古录》1卷,《豫章十代文献略》 50卷,以及《 尚书杂谈》、《左传异释》、《补史记世家》、《竹书纪年考证》、《古今人表》等200余卷。这些著作对古史起着拾遗补阙,辨证伪舛,考订异同的作用,是十分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二节方志的繁荣在论述史学成就时还应提到方志。方志即地方志,它是一种记述地方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作,是一种重要的地方文献,也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我国编修方志的历史悠久,早在周王朝时期,就出现了专门论述地方情况的史书,如传说中的晋《乘》、楚《椅杌》、郑《志》等。这些被称为“四方之志”的国别史,实际上就是方志的萌芽。到东汉时出现了袁康所编的《越绝书》,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这时的方志主要是反映一方风土人物的“地记”,内容很简单。隋唐时期,舆图和说明文字相结合的“图经”盛行起来,这是方志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到宋代,方志进一步发展,内容趋于完备,体例基本上定型。这时,“地记”、“图经”等基本上被“志”所取代。方志中记述的重点开始从地理情况转到社会的众多方面,“人物”和“艺文”在地方志中逐步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后来方志的一般格局。最先体现这一主要变化的是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200卷。这是一部全国性的地方总志。此书在内容和体例上突破了旧志的框框,增加了姓氏、人物、风俗、土产、艺文等人文历史内容,扩大了方志的记载范围。继《太平寰宇记》之后的又一部著名的全国性地方总志是《元丰九域志》。此志有10卷,是北宋王存、曾肇、李德刍等共同修纂的。此志前已有王曾、李宗谔修成的《九域图》。到元丰年间,州县有所变易,且虽名臼“图”,实只有文字而无图,因而朝廷乃命馆阁校勘曾肇,光禄丞李德刍等删定,而知制诰王存审其事。其中主要修纂者曾肇,字子开,是北宋建昌军南丰人,曾巩之弟,任崇文院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元丰时,奉旨删定《元丰九域志》。史称“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得到神宗的赏识。后又为《神宗实录》检讨官。《元丰九域志》虽法古旧章,以载地理为主,涉及人文较少,但仍是不可多得的方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它“深得古人辨方经野之意,叙事亦简洁有法”。且记载了被北方外族侵占的州郡,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他们恢复我国版图的愿望。这是当时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志。
北宋临川籍文人致力于方志编修的还有著名词人晏殊和文学家吕南公。晏殊悉心志书编纂,成就卓著。他颇重志书,曾云:“周公辨九州之土壤,以莫民居;萧何收天下之图籍,以定帝业。”①认为志书可起到奠民居,定帝业的作用。他一生编纂的方志计有《天圣十八路图》(即《十八路州军图》)、《方岳志》、《舆地志》等。可惜今皆不传,惟《玉海》、《咸淳临安志》等均采其书,今犹可见其概。文学家吕南公,北宋建昌南城人,他纂有《十八路地势图》,也是一部重要的地方总志。
元代方志发达,抚州出现了一位著名方志学家朱思本。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号贞一,临川县人,元朝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他广泛涉猎经史百家之书,一生著作甚丰。大德三年(1 297)写成地方总志《九域志》。《九域志》是取《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等志书中材料,参考异同,详加检校,分条析理,按《禹贡》所分九州加以记载而成。全书共80卷,是一本很有分量的地方总志。后朱思本奉诏代祀名山大川。他趁此机会,周游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南北10省,进行了1 0年的实地调查,他将考察所得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绘成了《舆地图》2卷。《舆地图》是《海内华夷图》之后,又一重要作品,流传到明代,罗洪先改编成《广舆图》。朱思本的《九域志》和《舆地图》对方志和地图的发展,都有着重要贡献。
清代方志编纂达到鼎盛,抚州又出觋了一名大方志学家李绂。李绂对方志编纂及方志理论研究方面皆有突出成就。他主编过《八旗通志》、《广西通志》,主纂过《临川县志》、《汀州府志》,还自撰过《西江志补》、《抚州续志》,并为《八旗通志》、《临川县志》订凡例,还撰有《八旗通志》各分志序、《广西通志》序、《畿辅通志》及其各分岙序、《河套志》序、《庐陵沿革表》序等四十余序。李绂通过书信往来及诗歌唱和形式,与江西巡抚白潢等商讨方志编纂及方志理论问题。关于方志的性质,他多次明确地指出:“志,固史之属也”,“邦国之志,史之属也”,“皇哉邦域志,国史所权舆也”等等,认为方志属于史学范畴。当时对于地方志性质的看法,主要有两派——地理学派、史志学派,李绂属于史志学派。关于方志的起源,李绂说:“志始见于《周礼》,小史掌邦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春秋列国皆有史,后世郡县皆有志。”认为《周礼·周官》为方志起源,是说有一定道理。关于方志的编纂,李绂主张“以诸史为宗”,并具体规定记载范围、门类设置、文辞章法等,对方志的编纂有着指导意义。关于志书的功用及特点,李绂认为志书主要应是“籍征考”与“资援据”之书,“庶几上稽前事,下协人情,籍资兴革,实关治道。”简而言之,是佐治兴文,即是用于资治,进行社会教育,保存文献,备一代之掌故,其政教之作用甚大。关于修志人员素质,李绂发前人之未发,提出“志才”与“志志”两个条件。前者指修志者必须具备的学识才干,后者指编修志书的志向、愿望及责任感。并分析二者之间关系。对修志者要求很高、很具体,认为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才能写好志书。这种主张很有见地,抓住了志书质量高低的关键。关于志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李绂认为“今昔殊形,中外异制”,理应有所侧重,各具特点。不因循守旧,很有发展进化的眼光。总之,李绂在方志编修上,硕果累累,在方志理论上,全面具体,颇具真知卓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方志学发展贡献甚大,实可称之为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抚州地方志的编修,最早的是南朝刘宋时期荀伯子纂修的《临川记》。此书在金溪人王氏《汉唐地理书抄》中有辑录,在秦荣光、章宗源、李肪、王象之、李贤、张国淦等编纂的几部志书中有记载,是研究南朝临川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抚州州县志的大量编修是起于宋代。宋代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修志的组织形式和规模都超越前代。不仅中央设立了专管修志的机构——九域图志局,而且地方也设修志局。府、州、县志由知府、知州、知县主修,文人学士或属官编写(叫纂)。方志数量大增,体例日臻全面和完备。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载,宋代抚州府志有8种之多,可惜均已失传,其中家坤翁修,周彦约纂,宋景定五年(1264)刻本的《临川志》35卷流传了很久。明人辑刻过,后也失传。今有蒲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宋代建昌军方志也有5种,都已失传。只有新安人建昌知军胡舜常修,建昌人袁州教授童宗说、建昌人抚州知府黄敷忠纂的《盱江志十卷续志十卷》,今有蒲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和刘绎的《江西通志》所载,临川县编有3部县志,崇仁县、乐安县各编有2部县志,金溪县编有1部县志,这些县志后来全部失传了。
元代方志在前代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效法唐《元和郡县志》和宋《太平寰宇记》及《元丰九域志》,修纂了著称后世的《大元统一志》。但因统治时期短,政治文化状况不佳,方志数量不多。抚州府、建昌军均未修志,所修县志有南丰县志2部,崇仁县志3部,乐安县志1部,广昌县志1部。这些县志均已失传,在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均有记载,其中部分县志在刘绎《江西通志》中也有记载。
明代我国方志得到较大发展,明王朝重视提倡修志, 并颁布了《修志凡例》,方志的编修很普遍。《抚州府志》于弘治(十三年、十六年2次)、嘉靖、崇祯先后4次纂修,《建昌郡(府)志》也有景泰、正德、嘉靖、万历先后4次之多。其所属各县,县县有志,而且还是一修再修。这些府郡县志大部分失传,只有3部府郡志、3部县志留传下来了。它们是《抚州府志》28卷,弘治十六年(1503)刻本,天一阁藏;《抚州府志》 16卷,嘉靖三十三年(1553)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建昌府志》19卷,正德十二年( 1517)刻本,天一阁藏; 《金溪县志》9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天一阁藏;《东乡县志》2卷,嘉靖十六年(1536)刻本,天一阁藏。这些州郡县志是本地区现存的最早的方志,是极其珍贵的地方文献。
清朝建立后,经济、文化曾一度繁荣,方志的编纂也达到鼎盛。统治者重视修志,组织完善,各省和府、州、县都设有志局或志馆。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方志的编纂,并对方志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而产生了方志学。此时方志体例完备谨严,志书数量极多,种类齐全,在古方志的辑佚方面也很有成绩。这些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抚州府、建昌府和各县纂修了大批志书,如抚州府志有4种,建昌府志有3种,临川县志有5种,金溪县志有7种,资溪县志有7种,黎川县志有5种,南丰县志有6种,南城县志有5种,宜黄县志有4种,崇仁县志有4种,乐安县志有7种,东乡县志有6种,广昌县志有4种,这些志书大多数保存下来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江西图书馆等处有藏本。
清朝纂修了大量方志,固然功不可泯,但另一方面,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特别是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对方志的破坏也是严重的。清朝统治者曾下令各省地方官对已有志书辩论考核,不合者删除以至禁毁,并严禁私修志书,尤其是涉及明事者,争相焚弃。乾隆时大量明代方志被付之一炬,私家志书被毁销者,也不计其数。本地区历代府县志书甚多,而明以前(尤其是明代)的志书今存无几,此实为其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述可见,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里,众多的临川籍的文人学者进行了辛勤的耕耘,他们整理古籍,编校史书,纂编方志,成绩卓著,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历史遗产,大大丰富了临川文化宝库,值得今天我们很好地研究和借鉴。
第三节曾巩对史学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里,临川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在史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印。而其中闪烁着特别耀眼的光辉,为史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者,当推著名的文史学家曾巩、危素和徐奋鹏。
曾巩除了在文学上有非凡的建树外,在史学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他编校古籍,纂撰实录,典修国史,写过许多史论文章。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推崇他为可与刘知几、郑樵相侪的“良史才”。可是,对这样一位文史大家,长期以来学术界只注意对其文学方面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他的史学成就。
曾现在嘉祐五年 (1060)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负责整理古籍,编校史书。曾巩领导的古籍整理, 前后长达9年之久,是继孔子删定六经,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百家杂史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活动,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古代书籍,经过历代战乱,散失很严重,经过这次大规模整理,使许多散乱不堪的古籍恢复了原貌,得以流传下来。曾巩整理的史籍主要有《梁书》、《陈书》、《战国策》、《新序》、《说苑》、《列女传》、《礼阁新仪》、《唐令》、《徐子中论》、《南齐书》等。他对所校勘的书籍都作了认真考证。凡有脱漏的均广泛采录以作补充,凡有舛讹的都作厘正,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作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如《战国策》,是继《春秋》、《左传》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书,汉代刘向编订时,有33篇。此书因杂有纵横诡辩之说,为儒家所排斥,传诵极少。又经历代大乱,到宋时散失严重,且“错乱相揉”,字多脱误,“大抵不可读”①,而《崇文总目》也称“十一篇者阙”。为挽救这一文化遗产,曾巩遍“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33篇复完”②,曾巩编成的这个本子竟成了《战国策》的定本,一直通行至今。又如《说苑》,是一部记述古代历史故事的杂史。它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的一些史事,杂以议论,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刘向编定的原本为20篇,到北宋时,大部分残缺。《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曾巩访之民间,从各地搜得13篇,与旧为18篇,“正其脱谬,疑其阙者”,终于使《说苑》基本恢复了原样③。 又如《新序》,也是刘向编述的古代历史故事的一部杂史。原为30卷,隋唐之世尚为全书,至宋已散失大半,所能见到的只1 0卷而已。曾巩“校正其讹舛,而缀辑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复全。”④对于篇目有异同者,曾巩必详加考定,以复原貌。还应提及的是唐代姚思廉撰的《陈书》,书成后,世罕流传,宋秘府所藏本又多数脱误。曾巩请宋神宗下诏从社会上收集到几个版本,但各本残缺都很严重,曾巩相互校髓,足足花了2年时间,才整理完毕,共为36篇。其书旧无目录,列传名氏多阙谬,曾巩又“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于是镂版印刷,“行之天下”①。如无曾巩及时搜集,作为廿四史之一的《陈书》,很可能散失殆尽而失传。其保存文献之功,卓然可传。更可贵的是,曾现在校勘整理古籍后,作了校序多篇。这些校序不仅详细介绍了书之篇目卷数和作者的生平以及整理的经过,还撮其大略,著其要旨,辨其得失,镜考源流,对书之内容、性质、价值和整理的意义等作了充分的剖析和记述,并贯穿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这俨然是一篇篇精湛透彻的书评。由此可见,曾巩没有为校书而校书,他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从中吸取某些经验教训,这反映了他的“鉴戒”、“经世”的史学思想。
熙宁元年(1068),曾巩负责校编古籍工作完毕。次年2月,宋神宗成立英宗实录院,命巩为检讨官,负责纂撰《英宗实录》。编纂先帝实录是当朝盛事,曾巩极为重视,想尽心尽力完成,因而上书神宗下诏各府州县,广收英宗年间的诏敕、奏章、告词、玉牒,以及应于《实录》内立传人物的行状、神道碑、墓志、书信等汇集于实录院,作为修《英宗实录》的基本材料。正当各项工作在紧张顺利地开展之时,曾巩遭到权贵所嫉,未满1个月,就罢去检讨官,外迁越州通判。《英宗实录》后由孙觉负责编篡,7月书成,共33卷。曾巩虽未能负责到底,但开局之功,尤其是为收集资料所作的努力,是不可抹煞的。
曾现在地方做官12年,元丰四年(1081) 63岁高龄的曾巩受命再次回京任史馆修撰,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典修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至英宗《五朝国史》。以前修国史多选文学之士,且以大臣总揽,而这次却独付于曾巩专领,任其自选撰修班子,这在中国古代官修史上是罕见的,足见对其信赖。而他也乐于此事,首先制定了编写条例,以及史料收集的范围、方法等,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编修工作。不料次年4月,神宗又下诏罢修五朝国史。曾巩典修《五朝国史》前后10个月,虽未完稿,却将所得史料撰写成史书《隆平集》 20卷,以会要体记录了宋五朝史实。“所记撰者典而赅,博而文,其词约者其文明,其文繁者其旨永。上下百余年之事,明君贤相、典章制度、赏罚兴革、人物风俗、忠良邪恶、内外舆图、营缮赋役、攻伐营屯诸事,莫不一目了然。善恶美制无所隐护”。“《宋史》、《通鉴》籍为根底”①。书中还记叙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经过和结果,对后代研究农民起义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上可见,曾巩一生长期从事编校古籍,纂修实录,典修国史等重要的史学活动。每次他都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他编校古籍,为祖国历史文化的流传作了不朽的贡献;他纂修实录、国史,为后来宋代国史的编修准备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所著《隆平集》20卷行世,至今还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参改资料。
曾现在史学方面的成就,除了编校古籍、纂修实录,典修国史外,在史学理论上也是很有建树的。他写了很多校序和读史笔记,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如《国体辨》、《邪正辨》、《问尧》、《治之难》、《论贾谊传》、《为治论》、《刑赏论》等,表达了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以史为鉴”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点。曾巩对这种史学的借鉴作用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②明确指出史学的作用就是探讨历代的治乱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后世提供治理天下的办法。为此,他提出了“知今者,莫若考古”的著名命题。这一史学思想始终贯彻在他的治史实践中。他整理《梁书》,就是为了以梁代的史事得失使当今统治者有所借鉴。他在《梁书目录序》中说:“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干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他整理《陈书》,则是因为陈代历史的“兴亡之端”“不可不考”①他典修《五朝国史》,他在编辑条例中明确规定:“善恶可劝戒,是非后世当考者,书之;其细故常行,不备书。”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以史为鉴”的史学思想。
为了使史学如实地记载古今治乱兴衰、善恶是非之道,以为后世借鉴,曾巩认为治史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史才。他说为史者,“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②对良史的要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必备“才、学、识”之长,曾现在此基础上,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 。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③曾巩提出的明理、适用、通意,发情四点要求,即“明、道、智、文”的良史的要求,比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显然是要高得多了。特别是“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一条,为刘知几所不及,这实际上是要求史家著史要经世致用,不能为史学而史学,脱离现实,于世无用。曾巩的良史说,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既是刘知几“才、学、识”三长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又有后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才、学、识、德四长理论所未包括的内容,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史学理论。
曾巩在编纂史书和撰写史论时很重视碑铭墓志。他认为“铭志之作,义近于史”①,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为此撰写铭志也应与撰写史书一样,贵在真实、公允,直书其事。可是当时一般人,为其祖先撰写碑铭墓志,“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②所以虽属恶人,无功德材之行,亦都一一请人勒铭以夸耀,以致名不符实,真假相蒙。要做到名实相符,曾巩认为关键在于“作铭者”的品德。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既能秉笔直书,又能辨清善恶是非,做到“公与是”,再加上文笔朴实优美,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勒撰铭志,才真正能传世长久。曾巩从“史”的高度来认识“铭志”,力主铭志要真实、公允,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确属高论,后来黄宗羲进一步发挥曾巩这一观点,直接把铭视作“史之类”,强调写这类文章时要用史法来衡量。正是抱着“铭志近史”的观点。曾巩在纂撰《英宗实录》和典修《五朝国史》时,非常重视铭志的史料价值,主张对那些碑铭墓志行状等资料统统加以网罗,尽量做到广博无阙遗。而在具体运用时,又严加稽核,小心谨慎,而不轻易取信。曾巩还亲自为亲朋作过许多碑铭、墓志、行状、祭文、哀辞等,这些志文记叙平实,评价公允,文笔生动,简洁可法,其中有的成为研究宋史的仅有的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曾巩生活在宋王朝由盛到衰的时代,政治腐败,制度腐朽,造成内乱不断,外患无穷。有识之士纷纷起而提出改革方案,但也有一大批守旧派认为“先王之道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而曾巩则主张“变法不变道 ”。他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异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③他一方面赞成变革法度,认为“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追先王之道哉。”①但同时对于作为封建社会的道,即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仁义、礼乐、教化等,他认为是永远不能变的。他说:“学之有统,道之有归”,治天下应“一道德、同风俗”②。可见他的历史观既有其进步性一面,也有其保守性一面。在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也表现了他这种两面性的历史观。曾巩与王安石本是挚友,有很深的交往,曾巩曾多次荐举王安石,两人都主张变革法度。曾巩也曾提出过改革礼制、官制、兵制、科举制度的建议。但他对王安石的变法革新内容和措施却不赞同,也未参与变法事宜,而是自求补外,去任地方官。朝廷派他通判越州,临行前他上书神宗,竭力强调要治国平天下,就必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把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单纯建筑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基础上,这是脱离实际的保守的。但他并非是新法的反对者,在外州任上,他也曾积极推行新法,并尽可能减少新法的流弊。可见曾巩具有变革的历史观的,不过他是要用“先生之道”来变革现实而已。
从上可知,曾现在史学的目的论上提出了“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观点,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史学鉴戒、经世的优良传统,在史才问题上,提出了“明、道、智、文”的新良史说,大大深化和发展了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理论,在我国古代史学上独树一帜;他又强调碑铭墓志的史学属性,要求它真实、公允、直笔;在历史观方面,他又具有明显的变异思想,主张历史变革,反对因循守旧。这些都是曾巩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至于他企图用“先王之道”来变革现实,在复古中求革新,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第四节危素、徐奋鹏史学思想及其成就著名的史学家危素(1300—1371?),字太朴,又字云林,金溪县黄通高桥人。生于元大德七年(1303),卒于明昭武五年(1372)。是唐末抚州刺史危全讽的后代。危素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少精五经。年长游学于著名学者吴澄、李存、范椁、虞集、揭溪斯门下研究文史,学识大有长进,才华横溢,吴澄等人十分赏识,大力引荐。他广交文学之士,名震江南。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因大臣推荐,出任经筵检讨,至正三年奉敕编纂宋、辽、金3部历史,并注释《尔雅》。为写3史,危素广涉文献,亲赴两宋都城访求摭闻遗事。为了写好宫廷斗争和后妃传,不惜用自已的俸金购买礼品馈赠宦官和皇亲国戚,亲笔访录,得悉真情,大大丰富了史实。经过危素等的潜心著述,3史遂成全史。宋、辽、金3史虽是署名元朝宰相脱脱①奉敕撰,危素只是众多编纂人员之一。实际上脱脱是总裁,危素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对“三史”的完成起了较大的作用。“三史”编修时间仓促,书成前后不足3年(134 3—1345),难免有些缺陷。《 宋史》共496卷,纪、传、志、表俱全,记载较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因卷数太多,错误也较多。然其长处在它体例完备,材料真实,志书详细,列传丰富,保存了大量的宋代史料,可供后世研习。《辽史》共116卷,在3史中修成最速,首尾不及一载,因此所存史实较简,为3史之下乘。但本记记述详细,8志反映了契丹旅游牧国家性质,列传反映贵族专政,八表最称精细,也是一部不可忽略的正史。《金史》共135卷,纪、传、志、表皆备,其所凭籍史料充足,本纪具体新颖,志书详细,而且条例整齐,叙事详实,文章简洁老练,乃3史中最为完善者。“三史”修成后,元顺帝大力嘉奖,赐给危素大批金银和宫女,危素谢绝不受。由于编史之功和政绩显著,危素由国子助教累迁至参知政事,成为朝廷重臣。后弃官居河北房山县报国寺,潜心致力于历史著作。其间他编撰过《草庐年谱》2卷。开初吴澄孙吴当为其祖编过年谱,危素是吴澄门人,他对此谱又重加订正,刻于至正乙已年间(1365)。
危素生活时代,正值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天灾频仍,饥莩遍野,民不聊生,义军四起,元王朝濒临倾覆。至正二年(1368),明军北上,深入河北一带时,危素被重新起用为翰林学士承旨。不久,都城大都(今北京)被攻破,危素感到国破家亡,在报国寺投井自杀,幸被报国寺主持大梓和尚等救起,并劝慰他说:“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为了未竟的史学著作,危素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当明兵入寺山,迫近史库,他以身护史库,声言归顺明朝,才使一部史料丰富,佐证周详的《元实录》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一功绩是不可泯灭的。
明朝初年,因危素博学,善诗文,书法也颇佳,一度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器重,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朱元璋常赐宴危素,同他坐谈中国历史和元朝遗事,并令他撰写皇陵碑文。洪武二年,又令他与宋濂等合修《元史》。《元史》是以元十三朝实录史料编修而成的,宋濂为总裁,危素是主要撰稿人之一。经6月,书成,分纪、表、志、列传,共203卷。《元史》因修史时间短,错误较多,但它根据十三朝实录写成,保存了原始资料;编制得体,能够网罗重要史料,志书详细,保存了大批珍贵资料,仍是一部重要的正史。
危素受到朱元璋器重,但被一些大臣嫉恨而进谗言。洪武四年(1370),70多岁的老人危素,被谪居和州(今安徽和县),次年病卒。
危素身经两个朝代,在历史著作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他的功劳多被湮没。加上他是降臣,历代封建统治者出于忠君思想,都不大宣扬他。《明史》对他的记载只是编入《文苑传》,寥寥数笔,贬多于褒。《金溪县志》亦把他放在不重要的地位。有关危素生平资料和著述,亦大多已佚。今天我们应该发掘、搜集、整理和研究危素的著述和有关资料,恢复这位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在史学上、文学上的应有地位。
在临川区域史学领域中还要特别提出著名的史学家徐奋鹏。徐奋鹏,字自溟,别号笔峒山人, 临川县云山巷口人。他幼年天资聪颖,博览群书,精通六艺。18岁时,参加县、府考试,均名列前茅。与大戏剧家汤显祖为挚友。汤素重其才,为之延誉。徐奋鹏为人刚直,目睹明末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民不聊生,他拒不入仕,决心闭门读书,寻求学问。几年以后,父亲去世,家境贫寒,便在村后笔架山下,造房居住,招收学士,以此度日。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立说。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有《毛诗朱注》4卷,《古今治统》天、地、人3册,《怡偃集》10卷,《辩俗》 10卷等。他的《毛诗朱注》是对朱熹的《诗注》进行删补,他深感朱注繁简不齐,而重加评注,增设图象、歌诀,使读者易读好懂,受到后人赞赏。他在史学上主要贡献的是他写的《古今治统》一书,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评。
《古今治统》是一部对历代帝王功过得失的评论专著,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改造政治的借鉴。它有三大特点: 一是体例新颖,详略得当。全书分天、地、人3册。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元末明初,属于编年体。他根据历代帝王在历史上的作用大小,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分别加以评论。有的几个帝王合论,如“太康至少康”、“夏杼至桀”、“太甲至盘庚”、“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厉王、成王”、“宣王、幽王”等;有的一帝一论,如“商汤”、“武王”、“平王”、“襄王”等;有的一帝二论,如“秦一世”、“秦二世”、“汉高祖”、“汉孝文”、“汉章帝”等;有的用附论,如“附论昌邑”、“附论新莽”;有的在评论几个帝王以后,采取合论形式,具有总结性的评论,如“五帝合论”、“三代合论”、“秦合论”。各自成篇,各有中心,又互有联系,彼此呼应。该详的详,该略的略,因帝王而异。
二是观点鲜明,分析透彻。对于那些治国有方,理民有术的开明君主,肯定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那些置民水火,残暴统治的君主,则无情地揭露他的罪恶。对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后所采取的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措施,详加介绍,予以赞扬。他评论说:“高祖登极后,正玑平衡,流化兴政,荡亡秦之毒螫,布大汉之恺悌,斯碉破觚,与其民盱盱睢睢。使萧何次律令以明刑,张苍明章程以定制,戮丁公以惕臣忠,侯雍齿以息偶语。定都也左彀函,右陇西,坐收天府之雄,酬勤也砺泰山,带黄河,以隆大封之典。善新语,几有息马论道之风。求逸才,雅有搜岩剔薮之意。时孔道未甚著,而鲁一祀,太牢开万世崇儒之声,不意铁马金戈之主,乃能开天光而肇文教也。其飞名帝祭而申锡无疆,夫岂偶然。”对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首创之功,他充分肯定:“陈胜吴广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脱耒为兵,裂裳为旗,揭竿为刃,褊袒大呼,天下从之如水流。此两人事不克终,论者或卑之,然义气激昂,为诛秦首创,昔人谓其为秦民之汤武,真快论者。”他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能如此予以评价,实在是难能可贵。他对秦二世胡亥的残酷统治作了有力的揭露:“亥也,遵凶父之业,荐作昏德,……忠谏谓之诽谤, 深计为之妖言,欲遂广情肆志之私,遂立严刑刻罚之律,于是谋大臣、灭故旧,……如此杀气 ,盈于至亲,他尚何顾忌,……用是人为怨,家为仇,而思乱者十室而五”。态度鲜明,揭露深刻。
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分析,观点也是很正确的。由于秦始皇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特色,这就必然造成失败结果。他分析说“其虎踞狼视之威,即鸱张蜂起之媒也,关中四塞,金城千里,群盗满山,赭衣载路之根也;销锋铸镝,即揭竿奋臂之兆也。”,“筑城以界胡矣,焉知胡不在万里长城之外,而在咸阳宫中耶!销兵以靖乱矣,焉知博浪有椎,赤帝子有三尺,而陈、吴有梃,以为之倡耶”。这指出了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造成了秦王朝倾覆的条件。在分析汉兴楚亡原因时,他指出:“楚汉兴亡,果有冥冥之谶乎,又岂真鸡嘟赤珠,自其孕时已定乎,又岂真龙成五彩,从望中有微乎?”他否定这些迷信的说法,认为汉兴楚亡原因,是决定于人心的向背。他说“项立义帝,以号令天下,无何复弑之,沛为义帝发丧,传檄以讨弑君之罪,天下诸侯于是不德楚而德汉;沛以义帝入关,止约法三章,以除秦苛,项乃屠秦城,杀秦觎,掘秦壕,火秦宫,天下人心于是不德楚而德汉。”这种见解,是非常正确的。
三是文笔生动,议论简洁。在赞扬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他说:“军声所临,百举百克,血盈六朝,爵吞八区,至于威震江南,吴天楚地,尽归版图,四海既一,自以为荣镜宇内,尊无与抗,谓真有恢复皇纲,廓帝纺,爰是有皇帝之称。”对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时,也备加赞扬:“高祖鞍马五、六年,三殆尽除,四海既一,而后南面称君,其得国之正,三代而下,罕与之俪。迨威加海内,有风起云飞景象,虽未免有伯心之存,而规模固自宏远矣。”对秦始皇、汉高祖统一中国的威力,作了有力的煊染,读来琅琅上口,犹如一篇篇优美的骈文。
徐奋鹏对中国史学作了很大的贡献,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史学界的赞扬,享有很高的声誉。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一批体大思精,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史书体裁、历史文献学都有相当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宋代史学超越前代突出的地方,是史学思想的发展。在宋代众多的临川文人中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的突出的史学家有乐史、陈彭年、曾巩和吴曾等。乐史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写过不少史学著作,流传下来的有收入《四库全书》的《广卓异记》。唐人李翱著有《卓异记》3卷,记述唐代君臣卓绝盛事。但其中漏录甚多,乐史先为此书作续记3卷,以补其阙。后又复以其仅载唐代君臣之事,未为广博,因而又纂集汉魏以下迄五代之事,共为一帙,名为《广卓异记》。此书分为20卷,记载了帝王将相、王后嫔妃的重要活动。其中载录了一些权臣“贵盛之极,显达奇速”,暴露了宋代官场的腐败,官吏的贪赃枉法。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实录。晚于乐史30年的陈彭年,是北宋南城人。他在直史馆任职时著有史书《江南别录》1卷。成书前徐铉、汤锐方奉诏撰有《江南录》。陈彭年感其疏漏不全,因而自纂此书,以补其未备,故以别录为名。此书记录了南唐义祖、烈祖、元宗、后主四代事,是一部南唐的实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著名的文学家曾巩,除了在文学上建树非凡外,在史学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只因其史名为文掩盖,所以一般人对其史学成就知之甚少。他在史馆任职期间,曾负责编校过《战国策》、《新序》、《说苑》、《陈书》等古代史籍。《战国策》、《说苑》和《新序》由于他的访求采录,才免于散佚。他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和咏史诗词,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并有史学专著《隆平集》传世。曾巩的史学,当时就“见称史类”,得到朝廷的赞赏,更为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所推崇,被称之为与刘知几、郑樵相侪的“良史才”。南宋的史学家当推崇仁人吴曾。他出仕工部郎中,出知严州,去贪官,恤良民,颇有善政。他一生著述繁富,重要的史学著作有《春秋考异》、《左传发挥》、《新唐书纠谬》、《南征北伐编年》、《南北事类》等。他还著有30余万言的《能改斋漫录》。此书记载了唐宋时期不少历史事件和人物掌故。其征引繁富,考据精细,对研究唐宋两代文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南宋笔记著作中堪称佳本,可与洪迈的《容斋随笔》相媲美。
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蒙古贵族重武功而轻文治,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汉族文人遭受歧视压迫,史学领域比起两宋时期相对冷落。这时期临川区域在史学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有著名的学者虞集、著名的文史学家危素、何中等。虞集一生致力教书、编撰,博学多才,号称诗文大家。他仿效“唐宋会要”编修《经世大典》,著有《道园学古录》,史学著述有《平穑记》1卷。元统三年(1334 )冬,广东瑶民进犯贺州、富州。至元元年(1335)广西宣慰使章巴颜率兵讨平之。虞集撰《平猛记》一卷,记载巴颜平粤西瑶洞事迹的始末。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正如《四库全书》所云,此书可“备国史之揉也。”著名的历史学家危素,以毕生的精力投入史学研究中。元代至正元年(1336),出任经筵检讨,奉诏参与编纂宋、辽、金史。书成,受到元顺帝大力奖赏。入明为翰林侍讲学士,奉诏与宋濂同修《元史》。他还为其师吴澄修订了《草庐年谱》2卷。危素的历史著述和研究为历史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元末学者何冲(1266—1322),乐安人,曾应聘主讲南昌东湖、宗濂二书院。史书著有《通鉴纲目测海》3卷。何中在此书自跋中说:“朱子作纲目,续春秋,然其间书法,可商略者犹多,闲附已意,辑成纲目测海三篇, 示儿辈云云。”可知此书是为纠正朱熹《通鉴纲目》的伪异而作,洧一定的史学研究价值。
明代中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老时期,但生产力在继续发展,弛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很活跃,尤其是东南沿海和长江中午游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这时期的戒就不够高。但明代的实录可以传抄,这为私人修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方便。明人修史大多取材于实录,私人修史极多,所作史书极为繁富。在这种氛围下,临川拥现了一大批文人私修史籍。名载古籍的有徐奋鹏、邓元锡、饶秉鉴、何乔新、周孔教、李纪、姜洪、王萁等人。著名的文史学家徐奋鹏,明代临川人。他终身不仕,潜心治学,用毕生的精力写成了《古今治统》20卷、《怡思集》10卷、《辩俗》10卷,删补《毛诗朱注》等。他的《古今治统》独笔生津,不畏豪强,弥补了前人的不足,辨别了历史的真伪,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史评。 明代学者邓元锡,字汝极,号潜谷,新城人(今黎川县),官至翰林院侍诏,著有《函史》102卷,《明书》45卷。《函史》是一部仿郑樵《通志》之作的通史,起自三皇,终于元代。邓元锡认为郑樵的纪传体例因袭旧史不够划一,二十略是其所创,但其内容夸大,根据不足。邓元锡对此作了体例上的变更,其纪传的体例变更很大,分得更细。这种体例划分虽然显得芜杂,但此书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古代历史人物史迹和典章制度。《明书》是一部起于明太宗,终于明世宗的断代史。其体例仿范晔的《后汉书》,记述较具体详细。这两部史书都是研究古代历史的有价值的资料。明代学者饶秉鉴,字宪章,广昌县人,官至廉州太守。他为官清廉,颇有政声,罢官后创设“雯峰书院”,授业之余,潜心研究学术,对《春秋》一书究其本源,研精微深,博采众家之长,直抒胸臆,穷尽10载,写成《春秋提要》和《春秋会通》两书。此2书收入《四库全书》,是一份可贵的史学遗产。
与李觏、曾巩、罗起、罗近溪,邓潜谷(元锡)、朱大器等人号称抚(州)建(昌)文章7大家之一的何乔新,字延秀,号椒丘,初授礼部主事,后改任南京刑部主事,秉公执法而闻名。生平著述宏富,史学著作有《宋元史臆见》、《文苑群玉》、《续编百将传》等。
对古史颇有研究,见解深微,可供后人借鉴,受到学界称誉,时称他为椒丘先生。明代较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金溪民间文人李纪的《史略详注补遗大成》10卷。初庐陵人曾先之撰十八史略,写至宋为止。明初临川人梁孟寅增补元代史事,名为十九史略。后李纪认为旧著不完备,因而加以增补而成此书。这是一部民间文人编撰的史略,可补正史之未备。还应提及的是临川人周孔教著的《周中丞疏稿》16卷。其文集有《西台疏稿》2卷,《中州疏稿》5卷,《江南疏稿》9卷。其《西台疏稿》极论赵志皋、石星等弃日本亲朝鲜之失策,《江南疏稿》内论停职造、止加派及丁末救荒诸政事;其余则是些案牍之文。此文集当朝名臣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为之作序,是研究当朝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要史料。此外乐安人姜洪参与修撰的《宣宗实录》,金溪人王奠著的《忠义录》1 4卷,也是有价值的史书。《忠义录》取史传忠义之事,分类编辑,各节所录史实均加以品评,持论颇正,可供我们研究古代历史人物参考。
清朝是满州贵族建立的封建专制王朝。清初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出现了“康乾盛世”。但清朝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特别严酷,统治者大力提倡理学,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统治。清代文人由于惧罹文网,不敢研究明史及当代史,大都钻进故纸堆,因而考据学大兴,史学研究便向历史文献学方面转化。这一特点在临川史学方面得到反映。此期临川籍学者的史学著作较少,较突出的有临川学者李绂,他崇尚理学,一生著述甚富,著有《春秋一是》、《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阳明学录》、《穆堂初稿、续稿、外稿》、《陆象山年谱》等。金溪学者蔡上翔著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以及金溪文献学家王漠著有《补证古史》等。李绂,(1657—1750)字臣来,号穆堂,官至内阁学士,礼、吏、兵、户、工五部侍郎、广西巡抚、直隶总督等,是一代名臣。他博学多才,又是一代学者。李绂崇尚陆象山之学,著有《陆象山年谱》2卷。初《陆象山年谱》为陆门人袁燮、傅子云同编,后李子愿又重辑之。李绂认为这部年谱不全,又未载陆九龄、陆九韶之事绩,因而重加补辑,遂成此书。这是研究陆象山兄弟的重要史料。清代著名学者蔡上翔(1717—1808)字元凤,号东墅,金溪县城东门蔡家人,进士出身,曾任四川省东乡县知县,政尚严肃,深得巴蜀人民之心。他一生著作甚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王荆公年谱考略》。蔡上翔读王荆公书,“常愤后世诋毁者皆失实”,因而耗费27个春秋,“所阅正史及百家杂说,不下数千卷”,遂成此书,全书约30万字,时年已88岁。他潜心研究,旁征博引,“考其事而辨其诬”,力排众议,驳斥了700年来封建士大夫强加在王安石头上的诬陷,还其历史的真面目,为后世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运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文献学家王漠,一生博览群书,才识雄隽,尤精江西地方文献及舆地之学,著有《江西考古录》1卷,《豫章十代文献略》 50卷,以及《 尚书杂谈》、《左传异释》、《补史记世家》、《竹书纪年考证》、《古今人表》等200余卷。这些著作对古史起着拾遗补阙,辨证伪舛,考订异同的作用,是十分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二节方志的繁荣在论述史学成就时还应提到方志。方志即地方志,它是一种记述地方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作,是一种重要的地方文献,也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我国编修方志的历史悠久,早在周王朝时期,就出现了专门论述地方情况的史书,如传说中的晋《乘》、楚《椅杌》、郑《志》等。这些被称为“四方之志”的国别史,实际上就是方志的萌芽。到东汉时出现了袁康所编的《越绝书》,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这时的方志主要是反映一方风土人物的“地记”,内容很简单。隋唐时期,舆图和说明文字相结合的“图经”盛行起来,这是方志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到宋代,方志进一步发展,内容趋于完备,体例基本上定型。这时,“地记”、“图经”等基本上被“志”所取代。方志中记述的重点开始从地理情况转到社会的众多方面,“人物”和“艺文”在地方志中逐步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后来方志的一般格局。最先体现这一主要变化的是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200卷。这是一部全国性的地方总志。此书在内容和体例上突破了旧志的框框,增加了姓氏、人物、风俗、土产、艺文等人文历史内容,扩大了方志的记载范围。继《太平寰宇记》之后的又一部著名的全国性地方总志是《元丰九域志》。此志有10卷,是北宋王存、曾肇、李德刍等共同修纂的。此志前已有王曾、李宗谔修成的《九域图》。到元丰年间,州县有所变易,且虽名臼“图”,实只有文字而无图,因而朝廷乃命馆阁校勘曾肇,光禄丞李德刍等删定,而知制诰王存审其事。其中主要修纂者曾肇,字子开,是北宋建昌军南丰人,曾巩之弟,任崇文院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元丰时,奉旨删定《元丰九域志》。史称“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得到神宗的赏识。后又为《神宗实录》检讨官。《元丰九域志》虽法古旧章,以载地理为主,涉及人文较少,但仍是不可多得的方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它“深得古人辨方经野之意,叙事亦简洁有法”。且记载了被北方外族侵占的州郡,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他们恢复我国版图的愿望。这是当时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志。
北宋临川籍文人致力于方志编修的还有著名词人晏殊和文学家吕南公。晏殊悉心志书编纂,成就卓著。他颇重志书,曾云:“周公辨九州之土壤,以莫民居;萧何收天下之图籍,以定帝业。”①认为志书可起到奠民居,定帝业的作用。他一生编纂的方志计有《天圣十八路图》(即《十八路州军图》)、《方岳志》、《舆地志》等。可惜今皆不传,惟《玉海》、《咸淳临安志》等均采其书,今犹可见其概。文学家吕南公,北宋建昌南城人,他纂有《十八路地势图》,也是一部重要的地方总志。
元代方志发达,抚州出现了一位著名方志学家朱思本。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号贞一,临川县人,元朝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他广泛涉猎经史百家之书,一生著作甚丰。大德三年(1 297)写成地方总志《九域志》。《九域志》是取《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等志书中材料,参考异同,详加检校,分条析理,按《禹贡》所分九州加以记载而成。全书共80卷,是一本很有分量的地方总志。后朱思本奉诏代祀名山大川。他趁此机会,周游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南北10省,进行了1 0年的实地调查,他将考察所得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绘成了《舆地图》2卷。《舆地图》是《海内华夷图》之后,又一重要作品,流传到明代,罗洪先改编成《广舆图》。朱思本的《九域志》和《舆地图》对方志和地图的发展,都有着重要贡献。
清代方志编纂达到鼎盛,抚州又出觋了一名大方志学家李绂。李绂对方志编纂及方志理论研究方面皆有突出成就。他主编过《八旗通志》、《广西通志》,主纂过《临川县志》、《汀州府志》,还自撰过《西江志补》、《抚州续志》,并为《八旗通志》、《临川县志》订凡例,还撰有《八旗通志》各分志序、《广西通志》序、《畿辅通志》及其各分岙序、《河套志》序、《庐陵沿革表》序等四十余序。李绂通过书信往来及诗歌唱和形式,与江西巡抚白潢等商讨方志编纂及方志理论问题。关于方志的性质,他多次明确地指出:“志,固史之属也”,“邦国之志,史之属也”,“皇哉邦域志,国史所权舆也”等等,认为方志属于史学范畴。当时对于地方志性质的看法,主要有两派——地理学派、史志学派,李绂属于史志学派。关于方志的起源,李绂说:“志始见于《周礼》,小史掌邦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春秋列国皆有史,后世郡县皆有志。”认为《周礼·周官》为方志起源,是说有一定道理。关于方志的编纂,李绂主张“以诸史为宗”,并具体规定记载范围、门类设置、文辞章法等,对方志的编纂有着指导意义。关于志书的功用及特点,李绂认为志书主要应是“籍征考”与“资援据”之书,“庶几上稽前事,下协人情,籍资兴革,实关治道。”简而言之,是佐治兴文,即是用于资治,进行社会教育,保存文献,备一代之掌故,其政教之作用甚大。关于修志人员素质,李绂发前人之未发,提出“志才”与“志志”两个条件。前者指修志者必须具备的学识才干,后者指编修志书的志向、愿望及责任感。并分析二者之间关系。对修志者要求很高、很具体,认为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才能写好志书。这种主张很有见地,抓住了志书质量高低的关键。关于志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李绂认为“今昔殊形,中外异制”,理应有所侧重,各具特点。不因循守旧,很有发展进化的眼光。总之,李绂在方志编修上,硕果累累,在方志理论上,全面具体,颇具真知卓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方志学发展贡献甚大,实可称之为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抚州地方志的编修,最早的是南朝刘宋时期荀伯子纂修的《临川记》。此书在金溪人王氏《汉唐地理书抄》中有辑录,在秦荣光、章宗源、李肪、王象之、李贤、张国淦等编纂的几部志书中有记载,是研究南朝临川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抚州州县志的大量编修是起于宋代。宋代是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修志的组织形式和规模都超越前代。不仅中央设立了专管修志的机构——九域图志局,而且地方也设修志局。府、州、县志由知府、知州、知县主修,文人学士或属官编写(叫纂)。方志数量大增,体例日臻全面和完备。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载,宋代抚州府志有8种之多,可惜均已失传,其中家坤翁修,周彦约纂,宋景定五年(1264)刻本的《临川志》35卷流传了很久。明人辑刻过,后也失传。今有蒲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宋代建昌军方志也有5种,都已失传。只有新安人建昌知军胡舜常修,建昌人袁州教授童宗说、建昌人抚州知府黄敷忠纂的《盱江志十卷续志十卷》,今有蒲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和刘绎的《江西通志》所载,临川县编有3部县志,崇仁县、乐安县各编有2部县志,金溪县编有1部县志,这些县志后来全部失传了。
元代方志在前代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效法唐《元和郡县志》和宋《太平寰宇记》及《元丰九域志》,修纂了著称后世的《大元统一志》。但因统治时期短,政治文化状况不佳,方志数量不多。抚州府、建昌军均未修志,所修县志有南丰县志2部,崇仁县志3部,乐安县志1部,广昌县志1部。这些县志均已失传,在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均有记载,其中部分县志在刘绎《江西通志》中也有记载。
明代我国方志得到较大发展,明王朝重视提倡修志, 并颁布了《修志凡例》,方志的编修很普遍。《抚州府志》于弘治(十三年、十六年2次)、嘉靖、崇祯先后4次纂修,《建昌郡(府)志》也有景泰、正德、嘉靖、万历先后4次之多。其所属各县,县县有志,而且还是一修再修。这些府郡县志大部分失传,只有3部府郡志、3部县志留传下来了。它们是《抚州府志》28卷,弘治十六年(1503)刻本,天一阁藏;《抚州府志》 16卷,嘉靖三十三年(1553)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建昌府志》19卷,正德十二年( 1517)刻本,天一阁藏; 《金溪县志》9卷,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天一阁藏;《东乡县志》2卷,嘉靖十六年(1536)刻本,天一阁藏。这些州郡县志是本地区现存的最早的方志,是极其珍贵的地方文献。
清朝建立后,经济、文化曾一度繁荣,方志的编纂也达到鼎盛。统治者重视修志,组织完善,各省和府、州、县都设有志局或志馆。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方志的编纂,并对方志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而产生了方志学。此时方志体例完备谨严,志书数量极多,种类齐全,在古方志的辑佚方面也很有成绩。这些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抚州府、建昌府和各县纂修了大批志书,如抚州府志有4种,建昌府志有3种,临川县志有5种,金溪县志有7种,资溪县志有7种,黎川县志有5种,南丰县志有6种,南城县志有5种,宜黄县志有4种,崇仁县志有4种,乐安县志有7种,东乡县志有6种,广昌县志有4种,这些志书大多数保存下来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江西图书馆等处有藏本。
清朝纂修了大量方志,固然功不可泯,但另一方面,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特别是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对方志的破坏也是严重的。清朝统治者曾下令各省地方官对已有志书辩论考核,不合者删除以至禁毁,并严禁私修志书,尤其是涉及明事者,争相焚弃。乾隆时大量明代方志被付之一炬,私家志书被毁销者,也不计其数。本地区历代府县志书甚多,而明以前(尤其是明代)的志书今存无几,此实为其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述可见,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里,众多的临川籍的文人学者进行了辛勤的耕耘,他们整理古籍,编校史书,纂编方志,成绩卓著,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历史遗产,大大丰富了临川文化宝库,值得今天我们很好地研究和借鉴。
第三节曾巩对史学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里,临川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在史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印。而其中闪烁着特别耀眼的光辉,为史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者,当推著名的文史学家曾巩、危素和徐奋鹏。
曾巩除了在文学上有非凡的建树外,在史学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他编校古籍,纂撰实录,典修国史,写过许多史论文章。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推崇他为可与刘知几、郑樵相侪的“良史才”。可是,对这样一位文史大家,长期以来学术界只注意对其文学方面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他的史学成就。
曾现在嘉祐五年 (1060)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负责整理古籍,编校史书。曾巩领导的古籍整理, 前后长达9年之久,是继孔子删定六经,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百家杂史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活动,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古代书籍,经过历代战乱,散失很严重,经过这次大规模整理,使许多散乱不堪的古籍恢复了原貌,得以流传下来。曾巩整理的史籍主要有《梁书》、《陈书》、《战国策》、《新序》、《说苑》、《列女传》、《礼阁新仪》、《唐令》、《徐子中论》、《南齐书》等。他对所校勘的书籍都作了认真考证。凡有脱漏的均广泛采录以作补充,凡有舛讹的都作厘正,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作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如《战国策》,是继《春秋》、《左传》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书,汉代刘向编订时,有33篇。此书因杂有纵横诡辩之说,为儒家所排斥,传诵极少。又经历代大乱,到宋时散失严重,且“错乱相揉”,字多脱误,“大抵不可读”①,而《崇文总目》也称“十一篇者阙”。为挽救这一文化遗产,曾巩遍“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33篇复完”②,曾巩编成的这个本子竟成了《战国策》的定本,一直通行至今。又如《说苑》,是一部记述古代历史故事的杂史。它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的一些史事,杂以议论,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刘向编定的原本为20篇,到北宋时,大部分残缺。《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曾巩访之民间,从各地搜得13篇,与旧为18篇,“正其脱谬,疑其阙者”,终于使《说苑》基本恢复了原样③。 又如《新序》,也是刘向编述的古代历史故事的一部杂史。原为30卷,隋唐之世尚为全书,至宋已散失大半,所能见到的只1 0卷而已。曾巩“校正其讹舛,而缀辑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复全。”④对于篇目有异同者,曾巩必详加考定,以复原貌。还应提及的是唐代姚思廉撰的《陈书》,书成后,世罕流传,宋秘府所藏本又多数脱误。曾巩请宋神宗下诏从社会上收集到几个版本,但各本残缺都很严重,曾巩相互校髓,足足花了2年时间,才整理完毕,共为36篇。其书旧无目录,列传名氏多阙谬,曾巩又“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于是镂版印刷,“行之天下”①。如无曾巩及时搜集,作为廿四史之一的《陈书》,很可能散失殆尽而失传。其保存文献之功,卓然可传。更可贵的是,曾现在校勘整理古籍后,作了校序多篇。这些校序不仅详细介绍了书之篇目卷数和作者的生平以及整理的经过,还撮其大略,著其要旨,辨其得失,镜考源流,对书之内容、性质、价值和整理的意义等作了充分的剖析和记述,并贯穿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这俨然是一篇篇精湛透彻的书评。由此可见,曾巩没有为校书而校书,他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从中吸取某些经验教训,这反映了他的“鉴戒”、“经世”的史学思想。
熙宁元年(1068),曾巩负责校编古籍工作完毕。次年2月,宋神宗成立英宗实录院,命巩为检讨官,负责纂撰《英宗实录》。编纂先帝实录是当朝盛事,曾巩极为重视,想尽心尽力完成,因而上书神宗下诏各府州县,广收英宗年间的诏敕、奏章、告词、玉牒,以及应于《实录》内立传人物的行状、神道碑、墓志、书信等汇集于实录院,作为修《英宗实录》的基本材料。正当各项工作在紧张顺利地开展之时,曾巩遭到权贵所嫉,未满1个月,就罢去检讨官,外迁越州通判。《英宗实录》后由孙觉负责编篡,7月书成,共33卷。曾巩虽未能负责到底,但开局之功,尤其是为收集资料所作的努力,是不可抹煞的。
曾现在地方做官12年,元丰四年(1081) 63岁高龄的曾巩受命再次回京任史馆修撰,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典修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至英宗《五朝国史》。以前修国史多选文学之士,且以大臣总揽,而这次却独付于曾巩专领,任其自选撰修班子,这在中国古代官修史上是罕见的,足见对其信赖。而他也乐于此事,首先制定了编写条例,以及史料收集的范围、方法等,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编修工作。不料次年4月,神宗又下诏罢修五朝国史。曾巩典修《五朝国史》前后10个月,虽未完稿,却将所得史料撰写成史书《隆平集》 20卷,以会要体记录了宋五朝史实。“所记撰者典而赅,博而文,其词约者其文明,其文繁者其旨永。上下百余年之事,明君贤相、典章制度、赏罚兴革、人物风俗、忠良邪恶、内外舆图、营缮赋役、攻伐营屯诸事,莫不一目了然。善恶美制无所隐护”。“《宋史》、《通鉴》籍为根底”①。书中还记叙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经过和结果,对后代研究农民起义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上可见,曾巩一生长期从事编校古籍,纂修实录,典修国史等重要的史学活动。每次他都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他编校古籍,为祖国历史文化的流传作了不朽的贡献;他纂修实录、国史,为后来宋代国史的编修准备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所著《隆平集》20卷行世,至今还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参改资料。
曾现在史学方面的成就,除了编校古籍、纂修实录,典修国史外,在史学理论上也是很有建树的。他写了很多校序和读史笔记,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如《国体辨》、《邪正辨》、《问尧》、《治之难》、《论贾谊传》、《为治论》、《刑赏论》等,表达了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以史为鉴”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点。曾巩对这种史学的借鉴作用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说:“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②明确指出史学的作用就是探讨历代的治乱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后世提供治理天下的办法。为此,他提出了“知今者,莫若考古”的著名命题。这一史学思想始终贯彻在他的治史实践中。他整理《梁书》,就是为了以梁代的史事得失使当今统治者有所借鉴。他在《梁书目录序》中说:“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干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他整理《陈书》,则是因为陈代历史的“兴亡之端”“不可不考”①他典修《五朝国史》,他在编辑条例中明确规定:“善恶可劝戒,是非后世当考者,书之;其细故常行,不备书。”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以史为鉴”的史学思想。
为了使史学如实地记载古今治乱兴衰、善恶是非之道,以为后世借鉴,曾巩认为治史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史才。他说为史者,“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②对良史的要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必备“才、学、识”之长,曾现在此基础上,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 。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③曾巩提出的明理、适用、通意,发情四点要求,即“明、道、智、文”的良史的要求,比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显然是要高得多了。特别是“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一条,为刘知几所不及,这实际上是要求史家著史要经世致用,不能为史学而史学,脱离现实,于世无用。曾巩的良史说,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既是刘知几“才、学、识”三长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又有后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才、学、识、德四长理论所未包括的内容,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史学理论。
曾巩在编纂史书和撰写史论时很重视碑铭墓志。他认为“铭志之作,义近于史”①,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为此撰写铭志也应与撰写史书一样,贵在真实、公允,直书其事。可是当时一般人,为其祖先撰写碑铭墓志,“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②所以虽属恶人,无功德材之行,亦都一一请人勒铭以夸耀,以致名不符实,真假相蒙。要做到名实相符,曾巩认为关键在于“作铭者”的品德。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既能秉笔直书,又能辨清善恶是非,做到“公与是”,再加上文笔朴实优美,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勒撰铭志,才真正能传世长久。曾巩从“史”的高度来认识“铭志”,力主铭志要真实、公允,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确属高论,后来黄宗羲进一步发挥曾巩这一观点,直接把铭视作“史之类”,强调写这类文章时要用史法来衡量。正是抱着“铭志近史”的观点。曾巩在纂撰《英宗实录》和典修《五朝国史》时,非常重视铭志的史料价值,主张对那些碑铭墓志行状等资料统统加以网罗,尽量做到广博无阙遗。而在具体运用时,又严加稽核,小心谨慎,而不轻易取信。曾巩还亲自为亲朋作过许多碑铭、墓志、行状、祭文、哀辞等,这些志文记叙平实,评价公允,文笔生动,简洁可法,其中有的成为研究宋史的仅有的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曾巩生活在宋王朝由盛到衰的时代,政治腐败,制度腐朽,造成内乱不断,外患无穷。有识之士纷纷起而提出改革方案,但也有一大批守旧派认为“先王之道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而曾巩则主张“变法不变道 ”。他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异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③他一方面赞成变革法度,认为“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追先王之道哉。”①但同时对于作为封建社会的道,即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仁义、礼乐、教化等,他认为是永远不能变的。他说:“学之有统,道之有归”,治天下应“一道德、同风俗”②。可见他的历史观既有其进步性一面,也有其保守性一面。在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也表现了他这种两面性的历史观。曾巩与王安石本是挚友,有很深的交往,曾巩曾多次荐举王安石,两人都主张变革法度。曾巩也曾提出过改革礼制、官制、兵制、科举制度的建议。但他对王安石的变法革新内容和措施却不赞同,也未参与变法事宜,而是自求补外,去任地方官。朝廷派他通判越州,临行前他上书神宗,竭力强调要治国平天下,就必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把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单纯建筑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基础上,这是脱离实际的保守的。但他并非是新法的反对者,在外州任上,他也曾积极推行新法,并尽可能减少新法的流弊。可见曾巩具有变革的历史观的,不过他是要用“先生之道”来变革现实而已。
从上可知,曾现在史学的目的论上提出了“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观点,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史学鉴戒、经世的优良传统,在史才问题上,提出了“明、道、智、文”的新良史说,大大深化和发展了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理论,在我国古代史学上独树一帜;他又强调碑铭墓志的史学属性,要求它真实、公允、直笔;在历史观方面,他又具有明显的变异思想,主张历史变革,反对因循守旧。这些都是曾巩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至于他企图用“先王之道”来变革现实,在复古中求革新,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第四节危素、徐奋鹏史学思想及其成就著名的史学家危素(1300—1371?),字太朴,又字云林,金溪县黄通高桥人。生于元大德七年(1303),卒于明昭武五年(1372)。是唐末抚州刺史危全讽的后代。危素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少精五经。年长游学于著名学者吴澄、李存、范椁、虞集、揭溪斯门下研究文史,学识大有长进,才华横溢,吴澄等人十分赏识,大力引荐。他广交文学之士,名震江南。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因大臣推荐,出任经筵检讨,至正三年奉敕编纂宋、辽、金3部历史,并注释《尔雅》。为写3史,危素广涉文献,亲赴两宋都城访求摭闻遗事。为了写好宫廷斗争和后妃传,不惜用自已的俸金购买礼品馈赠宦官和皇亲国戚,亲笔访录,得悉真情,大大丰富了史实。经过危素等的潜心著述,3史遂成全史。宋、辽、金3史虽是署名元朝宰相脱脱①奉敕撰,危素只是众多编纂人员之一。实际上脱脱是总裁,危素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对“三史”的完成起了较大的作用。“三史”编修时间仓促,书成前后不足3年(134 3—1345),难免有些缺陷。《 宋史》共496卷,纪、传、志、表俱全,记载较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因卷数太多,错误也较多。然其长处在它体例完备,材料真实,志书详细,列传丰富,保存了大量的宋代史料,可供后世研习。《辽史》共116卷,在3史中修成最速,首尾不及一载,因此所存史实较简,为3史之下乘。但本记记述详细,8志反映了契丹旅游牧国家性质,列传反映贵族专政,八表最称精细,也是一部不可忽略的正史。《金史》共135卷,纪、传、志、表皆备,其所凭籍史料充足,本纪具体新颖,志书详细,而且条例整齐,叙事详实,文章简洁老练,乃3史中最为完善者。“三史”修成后,元顺帝大力嘉奖,赐给危素大批金银和宫女,危素谢绝不受。由于编史之功和政绩显著,危素由国子助教累迁至参知政事,成为朝廷重臣。后弃官居河北房山县报国寺,潜心致力于历史著作。其间他编撰过《草庐年谱》2卷。开初吴澄孙吴当为其祖编过年谱,危素是吴澄门人,他对此谱又重加订正,刻于至正乙已年间(1365)。
危素生活时代,正值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天灾频仍,饥莩遍野,民不聊生,义军四起,元王朝濒临倾覆。至正二年(1368),明军北上,深入河北一带时,危素被重新起用为翰林学士承旨。不久,都城大都(今北京)被攻破,危素感到国破家亡,在报国寺投井自杀,幸被报国寺主持大梓和尚等救起,并劝慰他说:“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为了未竟的史学著作,危素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当明兵入寺山,迫近史库,他以身护史库,声言归顺明朝,才使一部史料丰富,佐证周详的《元实录》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一功绩是不可泯灭的。
明朝初年,因危素博学,善诗文,书法也颇佳,一度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器重,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朱元璋常赐宴危素,同他坐谈中国历史和元朝遗事,并令他撰写皇陵碑文。洪武二年,又令他与宋濂等合修《元史》。《元史》是以元十三朝实录史料编修而成的,宋濂为总裁,危素是主要撰稿人之一。经6月,书成,分纪、表、志、列传,共203卷。《元史》因修史时间短,错误较多,但它根据十三朝实录写成,保存了原始资料;编制得体,能够网罗重要史料,志书详细,保存了大批珍贵资料,仍是一部重要的正史。
危素受到朱元璋器重,但被一些大臣嫉恨而进谗言。洪武四年(1370),70多岁的老人危素,被谪居和州(今安徽和县),次年病卒。
危素身经两个朝代,在历史著作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他的功劳多被湮没。加上他是降臣,历代封建统治者出于忠君思想,都不大宣扬他。《明史》对他的记载只是编入《文苑传》,寥寥数笔,贬多于褒。《金溪县志》亦把他放在不重要的地位。有关危素生平资料和著述,亦大多已佚。今天我们应该发掘、搜集、整理和研究危素的著述和有关资料,恢复这位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在史学上、文学上的应有地位。
在临川区域史学领域中还要特别提出著名的史学家徐奋鹏。徐奋鹏,字自溟,别号笔峒山人, 临川县云山巷口人。他幼年天资聪颖,博览群书,精通六艺。18岁时,参加县、府考试,均名列前茅。与大戏剧家汤显祖为挚友。汤素重其才,为之延誉。徐奋鹏为人刚直,目睹明末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民不聊生,他拒不入仕,决心闭门读书,寻求学问。几年以后,父亲去世,家境贫寒,便在村后笔架山下,造房居住,招收学士,以此度日。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立说。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有《毛诗朱注》4卷,《古今治统》天、地、人3册,《怡偃集》10卷,《辩俗》 10卷等。他的《毛诗朱注》是对朱熹的《诗注》进行删补,他深感朱注繁简不齐,而重加评注,增设图象、歌诀,使读者易读好懂,受到后人赞赏。他在史学上主要贡献的是他写的《古今治统》一书,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评。
《古今治统》是一部对历代帝王功过得失的评论专著,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改造政治的借鉴。它有三大特点: 一是体例新颖,详略得当。全书分天、地、人3册。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元末明初,属于编年体。他根据历代帝王在历史上的作用大小,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分别加以评论。有的几个帝王合论,如“太康至少康”、“夏杼至桀”、“太甲至盘庚”、“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厉王、成王”、“宣王、幽王”等;有的一帝一论,如“商汤”、“武王”、“平王”、“襄王”等;有的一帝二论,如“秦一世”、“秦二世”、“汉高祖”、“汉孝文”、“汉章帝”等;有的用附论,如“附论昌邑”、“附论新莽”;有的在评论几个帝王以后,采取合论形式,具有总结性的评论,如“五帝合论”、“三代合论”、“秦合论”。各自成篇,各有中心,又互有联系,彼此呼应。该详的详,该略的略,因帝王而异。
二是观点鲜明,分析透彻。对于那些治国有方,理民有术的开明君主,肯定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那些置民水火,残暴统治的君主,则无情地揭露他的罪恶。对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后所采取的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措施,详加介绍,予以赞扬。他评论说:“高祖登极后,正玑平衡,流化兴政,荡亡秦之毒螫,布大汉之恺悌,斯碉破觚,与其民盱盱睢睢。使萧何次律令以明刑,张苍明章程以定制,戮丁公以惕臣忠,侯雍齿以息偶语。定都也左彀函,右陇西,坐收天府之雄,酬勤也砺泰山,带黄河,以隆大封之典。善新语,几有息马论道之风。求逸才,雅有搜岩剔薮之意。时孔道未甚著,而鲁一祀,太牢开万世崇儒之声,不意铁马金戈之主,乃能开天光而肇文教也。其飞名帝祭而申锡无疆,夫岂偶然。”对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首创之功,他充分肯定:“陈胜吴广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脱耒为兵,裂裳为旗,揭竿为刃,褊袒大呼,天下从之如水流。此两人事不克终,论者或卑之,然义气激昂,为诛秦首创,昔人谓其为秦民之汤武,真快论者。”他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能如此予以评价,实在是难能可贵。他对秦二世胡亥的残酷统治作了有力的揭露:“亥也,遵凶父之业,荐作昏德,……忠谏谓之诽谤, 深计为之妖言,欲遂广情肆志之私,遂立严刑刻罚之律,于是谋大臣、灭故旧,……如此杀气 ,盈于至亲,他尚何顾忌,……用是人为怨,家为仇,而思乱者十室而五”。态度鲜明,揭露深刻。
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分析,观点也是很正确的。由于秦始皇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特色,这就必然造成失败结果。他分析说“其虎踞狼视之威,即鸱张蜂起之媒也,关中四塞,金城千里,群盗满山,赭衣载路之根也;销锋铸镝,即揭竿奋臂之兆也。”,“筑城以界胡矣,焉知胡不在万里长城之外,而在咸阳宫中耶!销兵以靖乱矣,焉知博浪有椎,赤帝子有三尺,而陈、吴有梃,以为之倡耶”。这指出了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造成了秦王朝倾覆的条件。在分析汉兴楚亡原因时,他指出:“楚汉兴亡,果有冥冥之谶乎,又岂真鸡嘟赤珠,自其孕时已定乎,又岂真龙成五彩,从望中有微乎?”他否定这些迷信的说法,认为汉兴楚亡原因,是决定于人心的向背。他说“项立义帝,以号令天下,无何复弑之,沛为义帝发丧,传檄以讨弑君之罪,天下诸侯于是不德楚而德汉;沛以义帝入关,止约法三章,以除秦苛,项乃屠秦城,杀秦觎,掘秦壕,火秦宫,天下人心于是不德楚而德汉。”这种见解,是非常正确的。
三是文笔生动,议论简洁。在赞扬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他说:“军声所临,百举百克,血盈六朝,爵吞八区,至于威震江南,吴天楚地,尽归版图,四海既一,自以为荣镜宇内,尊无与抗,谓真有恢复皇纲,廓帝纺,爰是有皇帝之称。”对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时,也备加赞扬:“高祖鞍马五、六年,三殆尽除,四海既一,而后南面称君,其得国之正,三代而下,罕与之俪。迨威加海内,有风起云飞景象,虽未免有伯心之存,而规模固自宏远矣。”对秦始皇、汉高祖统一中国的威力,作了有力的煊染,读来琅琅上口,犹如一篇篇优美的骈文。
徐奋鹏对中国史学作了很大的贡献,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史学界的赞扬,享有很高的声誉。
附注
① 晏殊《十八路州军图》
① 洪迈《容斋四笔》卷1《战国策》
② 《曾巩集》卷11《战国策自录序》
③ 《曾巩集》卷11《说苑目录序》
④ 《郡斋读书志》
① 《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
① 彭期《校刻隆平集序》
② 《曾巩集》卷11《南齐书目录序》
① 《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
②③ 《曾巩集》卷11《南齐书目录序》
①② 《曾巩集》卷16《寄欧阳舍人书》
③ 《曾巩集》 11卷《战国策目录序》
① 《曾巩集》11卷《礼阁新仪目录序》
② 《曾巩集》11卷《新序目录序》
① 今本《四库全书》更正为托克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