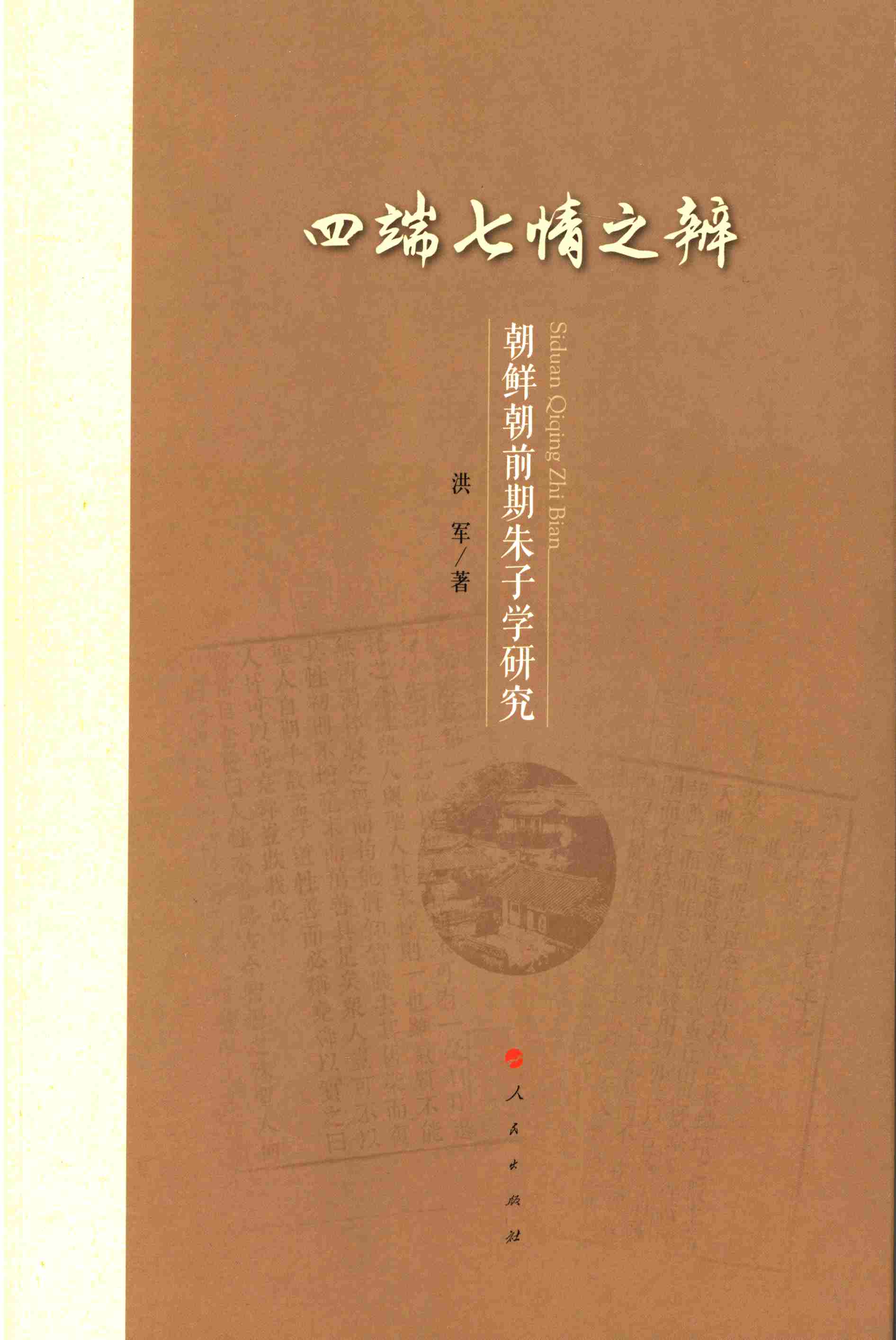第二节 “人心道心”之辨在东亚儒学史上的意义
内容
在东亚儒学史上,“人心道心”说随朱子学的传播而传入东亚各国,受到各国儒者的关注。尤其是,在韩国“人心道心”论与“四端七情”论相结合形成别具一格的心性论诠释系统。本节拟以朱子与16世纪中韩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罗钦顺、李珥的思想比较为中心,来探讨“人心道心”说在东亚地区的多元发展及其理论意义。
一、朱子的“人心道心”论及其理论意涵
人心、道心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宋儒“道统”之说的主要文献根据之一,朱子将此十六字称为“尧、舜、禹相传之密旨”①。此“十六字心传”的大意是说:人心险恶难测,道心幽微难显,唯有精一至诚,方保此心中正不偏。
对于此古圣先王相授受之心法密旨,二程对其中的人心道心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程颢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②表明,依明道之见人心与道心的关系即为人欲与天理之关系,而程颐则直接将二者关系解作私欲与正心的关系。小程子有言:“‘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③伊川以道心为正,人心为邪,所以特别强调施“精一”功夫以使道心不被人心所扰乱。进而他还主张存公灭私,明理灭欲,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④人道说受到二程的青睐,与其所含的思想意蕴密不可分。宋儒强调道德直觉和人格修养,为此提倡以道德意识主宰人的行为使之达于其宣扬的“以理节欲”之目的。人道说所涉的论域,如道德与情欲、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之间关系等正好满足了理学家的此一理论需求。同时,这也反映理学道德心性学说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但是,二程将人心与道心对立起来,将人心视作人欲、私欲,否定的人的自然需求和感性欲望的理论作解也使理学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亦重视“人心道心”论。他在继承二程的人道说的基础上,从心性论和知觉论的维度对其意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首先,朱子以为人只有一个心,若说道心是天理,人心是人欲,便有了两个心。曰:“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非有两个心。”⑤在朱子看来,心之所以有二名,只是因各自所知所觉者不同而已,其实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而且,还对二程将人心解为人欲的观点提出异议。
其次,自从“己丑之悟”之后,朱子便运用体用说对“心”作了全新解读。他以为“心”是体用之全体,不仅兼体用,而且贯动静。曰:“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无一毫私欲之间;其流行该遍,贯乎动静,而妙用又无不在焉。故以其未发而全体者言之,则性也;以其已发而妙用者言之,则情也。然‘心统性情’,只就浑沦一物之中,指其已发、未发而为言尔;非是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又是一个地头,如此悬隔也。”①认为,以心有体用而言,“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②;以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③,心是“贯彻上下,不可只于一处看”④。由此朱子的“心”既具道德心之意涵,又有知觉心之属性。故“心”在其哲学中地位极特殊,如其所言“惟心无对”⑤。
再次,朱子进一步运用心之体用说对人心、道心及其二者之关系展开了详细论述。曰: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⑥
此段引文可视为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晚年定论,此文写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其时朱子之思想已渐趋成熟。文中朱子对人道说的主要问题,作了纲要式的经典解说。一是从知觉论意义上,对人心、道心作了界定。他指出人心生于形气之私(觉于欲),而道心则原于性命之正(觉于理)。这就解答了二者皆发自一个心,何以有人道之分的问题。此一区分本身也反映了理学自身的价值诉求。二是指出不论上智之人抑或下愚之人皆有人心道心,在这方面人人皆平等。这一主张实则反映了人皆能成圣成贤的理学价值理想。三是对人心与人欲(私欲)作了区分。朱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合理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求。认为,“饥思食、寒思衣”等“人心”所包含的生存需求,圣人亦不能无。四是在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以道心来节制人心。值得注意的是,朱子虽然坚持人心与道心相分的理论,但倾向认为“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①二者的分别只是一个“交界”,彼此不因一方之存在而自行消失——问题是以何方为主导。朱子主张以道心(天理)宰制人心,即所谓“‘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乃善也”②。这可说是理学所一贯追求的价值目标。
由此可见,人道说虽与理欲论相对应,但不似理欲论那般紧张。而朱子对天理、人欲却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二者是不具共时性、共存性的两边相对之物。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着,学者需要于此体认省察之。”③朱子甚至指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④这表明,在他看来以天理战胜人欲这才是修学的重中之重。
概言之,朱子通过人心、道心说,对“心”的含义作了多维度阐发。尽管他的人道说所讨论的是心之“已发”层面问题,并非为“未发”之体,但是其理论仍然建立在体用关系之上,也可说是心之体用说的运用和心之知觉说的实现。⑤不过,在价值论层面上,朱子思想的总体倾向是重义轻利、贵理贱欲,故其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理论主张,如以存理遏欲来扩充道心及以“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等,可视为其义利观、理欲观在心性论上的具体体现。
二、罗钦顺的“人心道心”论
整庵罗钦顺被后人称为“宋学中坚”和“朱学后劲”,在明代他是能够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朱学阵营的标志性人物。而且,其代表作《困知记》问世后不久便传至朝鲜和日本,为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不过,朱熹的思想传至整庵,较之原来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变动。首先在理气论层面发生明显变化,呈现出由“理学”转向“气学”的理论动向。而且,主张去理的“实体化”,强调“理气为一物”等思潮为朱学心性论的新诠释提供了理论基础。
整庵在阐发其心性理气诸说时,对朱子的学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和补充。在理气论方面,他直接批评朱子的理气说“未归一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所谓‘理气二物,亦非判染为二’,未免有迁就之意。既有强有弱,难说不是判然。夫朱子百世之师,岂容立异?顾其言论间有未归一处,必须审求其是,乃为善学朱子,而有益于持循践履之实耳。”①他认为朱子是百世之师,之所以对其观点提出异议,主要是因其言论中有不一致之处。整庵以为向道者应矢志探求圣学中正确的东西,这样才算是善学朱子,且有益于持守与实践。于是,他以明道的道器论为依据提出自家的“理气一物”说。整庵有言:“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决也。明道尝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又曰:‘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窃详其意,盖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说个形而上下,则此理无自而明,非溺于空虚,即胶于形器,故曰‘须著如此说’。名虽有道器之别,然实非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至于‘原来只此是道’一语,则理气浑然,更无隙缝,虽欲二之,自不容于二之,正欲学者就形而下者之中,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则不是也……晦翁先生……谓‘是理不离气,亦不杂乎气’,乃其说之最精者。但质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良由将理气作二物看,是以或分或合,而终不能定于一也。”①他认为,朱子的理气论“终不能定于一”是因其始终将理气“作二物看”之故。依其之见,理须在气上认取,但是若把气认作理也是不对的——正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②。对此,他自信地说:“此言殆不可易哉!”③
整庵自谓心性理气诸说是其学问中的“大节目”④,而其心性之辨正是建立在“人心道心”之辨的基础上。
对于人心道心问题,整庵曾不无自豪声称:“人心道心之辨,仆于此用工最深,窃颇自信。”⑤又言道:“‘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后大本可得而立。’斯诚讲学第一义。”⑥可见,此论在整庵学说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重要。
在人心道心的问题上整庵亦对朱子提出质疑,指出其心性学说“未定于一”。曰:
“凡言心者皆是已发”,程子尝有是言,既自以为未当而改之矣。朱子文字,犹有用程子旧说未及改正处,如书传释人心道心,皆指为已发,中庸序中“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一语,亦皆已发之意。愚所谓“未定于一”者,此其一也。⑦
罗钦顺以为,若将人心、道心一概视作已发看“是为语用而遗体”⑧。整庵的这一指责,若从其所持之性情体用论立场看的确有其合理性。朱子本人在“中和旧说”中也使用过此一说法。但是,从“中和新说”之后对“心”的重新诠释以及对人道说所持的诠释立场来说,整庵的这一指责却有待商榷。由此可见,整庵与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不同的问题域以及诠释立场上的差异。罗钦顺的人道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整庵从寂感意义上的动静论视角对人心道心进行了界定。曰:“道心,‘寂然不动’者也,至精之体不可见,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危。”①那么,他所理解的“心”为何物呢?罗钦顺指出:“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②表明,对“心”与“性”整庵是有严格区分,而且他还主张学者为学应先明于“心性之别”。在他看来,孔子教人也无非是存心养性之事,然从未明说什么是心性,到了孟子才明言何为心性。他说:“虞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③由此亦可见,整庵对“心性之辨”重视程度,但是他也曾指出“心性至为难明”④。罗钦顺认为陆象山的错误正是未能分辨清楚心与性。而其“心性之辨”,正是通过“人心道心”之辨得到深入的诠释。
其次,整庵从动静之分、体用之别对人心道心作了理论诠释。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圣神之能事也。”⑤此段引文是整庵对人心道心问题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论述。罗钦顺同样主张心是一个,但是他以为之所以要从人心道心两方面来说是为了表明心的动静之分和体用之异。可见,整庵与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诠释立场和诠释视角有着较大差异。罗钦顺以为,以静来制动便是吉,动而不知返回本心便是凶。因此审察心之动机(“惟精”),保持人心之诚(“惟一”),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允执厥中”)。在他看来,这是“圣神之能事”亦即圣人之本领。
再次,整庵从性情论维度对人心道心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曰:“道心,性也;性者,道之体。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其体一而已矣,用则有千变万化之殊,然而莫非道也。此理甚明,此说从来不易。”①在此,整庵又将人心道心之辨转化为性情之辨——道心成了未发之体,人心则成了已发之用。对此一解,他极为自负。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仆于此煞曾下工夫体究来,直穷到无可穷处,方敢立论。万一未合,愿相与熟讲之,此处合则无往而不合矣。”②整庵问学之艰辛及学思之谨严于此可见。其“道心为性,人心为情”之说乃反复参验省察后所得的思想结晶。这既是其在心性之辨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也是其独特心性学说的立论基础。
明中叶后程朱理学日渐式微,陆王心学则日益隆盛。阳明所倡导的简易直截的“良知说”颇受士人追捧。而在整庵看来,陆王心学是阳儒而阴释,实与禅学无异。作为“朱学后劲”罗钦顺深以为忧,于是将阐明“心性之辨”,批驳心学的“良知说”作为论学的首要目标和作为卫道的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截流塞源,他还对《楞伽经》等佛教经典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对其辟佛功绩“东林八君子”之一的晚明大儒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1562—1626年,世称“景逸先生”)称赞道:“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③而他则把辟佛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儒佛之辨上。罗钦顺试图以心性之辨阐明儒佛之区别。罗氏论曰:“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盖虚灵知觉,心之妙也。精微纯一,性之真也。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④他进而指出:“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岂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见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别,彼则浑然无别矣,安得同!”⑤可见,依他之见儒佛之间最根本区别在于心性之辨上,亦可理解为在“人心道心”之辨上。佛家禅学的确在心性问题上只关注“心”,却未留意到儒家至为强调的“性”这一本体,故朱子评论说“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⑥。这是整庵“理气一物”论、“心性之辨”(“人心道心”之辨)等主张的思想史背景,学者于此不可不察。
简言之,主张“理气一物”,辨明“心性之别”是整庵之学说的理论旨要。而建立于“道心为体,人心为用”义理架构上的人心道心说则是其学问的核心纲领,整庵自谓:“拙《记》(指《困知记》——引者注)纲领只在此四字,请更详之。”①由上可见,整庵之所以重视“人心道心”之辨,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具体人文语境以及所要回应的时代话题都有密切关联。
由此可见,人心道心论的独到的理论价值和意义经由朱子之阐发才得到彰显,但未成为宋代理学的主要论题。此后,经整庵的发挥,人心道心才进入理学心性论的核心范畴之列。不过,人心道心论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还是离不开韩国儒者对之所作的创造性诠释。
三、李珥的“人心道心”论
整庵提出以“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的人道体用说之后,其主张并未受到明中叶士大夫们的积极回应和热议。但是,随着其著作《困知记》在朝鲜的流布,此说开始受到朝鲜儒者关注和重视,并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人心道心”之辨在朝鲜所激起的思想波澜,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东亚儒学史上所罕见。经过朝鲜儒者们富有创意的阐发,“人心道心”之辨才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哲学论题。
在朝鲜朝儒者的人道论中,与李滉并称为朝鲜朱子学双璧的栗谷李珥的人心道心论颇具代表性。李珥对与其同时代的整庵十分赞赏,曾称颂说:“罗整庵识见高明,近代杰然之儒也。有见于大本,而反疑朱子有二歧之见。此则虽不识朱子,而却于大本上有见矣。”②而且,他还将整庵同与其同时代的退溪李滉和花潭徐敬德作过比较,得出结论:“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③李滉和徐敬德,皆为韩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代儒学名宿,李珥对整庵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原因在于:一是其理气论与整庵较相近(二人皆取理气不离之立场);二是李珥认为整庵不仅对朱子学“有见于大本”,而且还多有“自得之味”(重视“自得之味”是二人学问之共同特点)。
不过在李珥看来,尽管整庵对朱学之“大本上有见”,但是整庵“以人心道心为体用,失其名义”,①使人感到惋惜。即便如此,李珥认为若衡之于与李滉“整庵之失在于名目上,退溪之失在于性理上,退溪之失重矣”②,他还说过整庵“虽失其名义,而却于大本上,未至甚错也”③。李珥也在接续朱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心道心”论。
首先,从强调心性理气诸说之间的一贯性立场对“人心道心”论作了解读。曰:“理气之说与人心道心之说,皆是一贯。若人心道心未透,则是与理气未透也。理气之不相离者若已灼见,则人心道心之无二原,可以推此而知之耳。”④可见,李珥的理气论是其人道说的立论根基,人道说是其理气论的直接生发。因理气之“不离”义是其理气论的主要思想倾向,故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他也以二者的不可分和相联结为其主旨,强调人心、道心的“无二原”性。这与朱子、整庵的人心、道心之相分思想是有所区别的。
其次,从主理、主气视角对人心、道心的含义作了阐发。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感动之际,欲居仁、欲由义……欲切偲于朋友,则如此之类谓之道心。感动者因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形气不为之掩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饥欲食、寒欲衣……四肢之欲安佚,则如此之类谓人心。其虽本于天性,而其发由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气,而目之以人心也。”①依李珥之见,因感动者是形气,故感动之际何方为主显得十分紧要。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主乎理”的是道心,出于耳目四肢之私而“主乎气”的则是人心。从主理、主气的角度探讨人心道心之含义,这一点颇能反映韩国儒学在讨论人间和存在的所以然根据这个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时,往往落实到性理层面上展开理气这个形上、形下问题的理论特性。②重视人间性理,是韩国儒学的根本特征。
再次,基于心之已发论,以知觉说的立场回答了“一心”何以有“二名”,即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分的问题。
在李珥的哲学中“心”属于气,故不管人心还是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规定使其人道说自然具有了知觉论的特色。他说:“心一也,岂有二乎?特以所主而发者有二名”③,又说:“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一心。其发也或以理义或为食色,故随其所发而异其名。”④“心”只有一个,这与朱子的主张相同。但是在“一心”何以有“二名”的问题上,李珥独特的心性论义理间架使其抱持与朱子不同的诠释立场。众所周知,朱子的学说以“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而李珥则以“理气之妙”、心性情意四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因此朱子的性情论可以“心统性情”说来概称,而李珥的性情论则似以“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说来指代更为恰当。最紧要的是二人对“意”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在朱子的性情论中,“意”和“情”都是从属于“心”的概念。“情”和“意”二者的关系是,大抵“情”为性之动,“意”为心之所发;“情”动是全体上论,“意”是就起一念处论。⑤因此在朱子心性论中,“意”的思量运用之含义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在李珥哲学中,“意”和“情”是两个有着明确界定的并列的哲学范畴,可视为心的两个不同境界。故其“人心道心”论是兼情意而言,如其曰:“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①,“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②需注意的是,“意”其实是在其人道说中起十分重要作用的范畴。这既是李珥与朱子性情论之区别,亦是其对朱子心性情意说的发展。相较而言,李珥的心性学说确实比朱子的理论更为细密和清晰。而且,强调“意”的商量计较作用是李珥知觉论最为显著的特点。
基于“意之商量计较”的意涵,李珥提出了极具特色的“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终始”说。他说: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③
不管根于性命之正的道心,还是源于形气的人心,皆属已发,此时气已用事。若欲不咈正理如实呈现,或知非制伏不从其欲,都要借“意”之计较、思虑、商量作用来实现。因此李珥认为,在人心之方寸之间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可变状态。在已发层面上,二者是并无固定的、严格的分别。因此,李珥为学极重“诚意”。在他看来,“情胜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④栗谷指出,若能保证“意”之“诚”,则所发之“心”皆能呈现为道心。
最后,李珥还援引“四七”论、理欲论,进一步阐释了人心道心之界说以及二者间的关系。
“四端七情”论是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的重要学说,人心道心论争的发生其实就是“四七”论由“情”论层面向“心”论层面的进一步推进,或者说“四七”论在心性领域的更深、更广意义上的展开。
在李珥哲学中,因“意”的商量计较作用,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相互转化之状态。这与其“四七”论中七情兼四端的情形有所不同,对此差异李珥指出:“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则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①他进而指出:“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矣,乌可强就而相准耶。”②在李珥哲学中的“情”不具商量计较之意,故性发为情之际,七情可以兼四端。因为依他之见,“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但是,人心、道心则已达比较而看的地步,已具对比之意,故不能兼有只能互为终始——这便是其“人心道心终始”说。
因为人心与道心是基于“意”之商量计较而存在的相对之物,李珥又由“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而提出“人心道心相对”说。他说:“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若七情则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谓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乌可分两边乎?”③
此论看似与其“人心道心终始”说矛盾,但这是李珥从天理人欲论角度对人道说的解读,可视为对“人心道心终始”说的另一种阐发。他曾说过:“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④可见,李珥对道心、人心、人欲是有明确的区分。他肯定人心亦有善,朱子所见略同。但是,人心之善与道心是否为同质之善呢?对此,李珥在《人心道心图说》中指出:“孟子就七情中别出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论者或以四端为道心,七情为人心,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七情岂可谓之人心乎?七情之外无他情,若偏指人心则是举其半而遗其半矣。”①可见,他将二者视为同质之善。在理欲论意义上,其人道说比朱子的人道说显得更为紧张和严峻,颇似“天理人欲相对”说。这也是二人“人心道心”之说的主要区别之一。同时,李珥还从理欲之辨角度,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作出自己的解释。
四、“人心道心”之辨在16世纪东亚思想界的多元发展
陈来先生曾指出:在历史上,与政治的东亚不同,从东亚文化圈的观点来看,朱子学及其重心有一个东移的过程。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在中国再没有产生有生命力的哲学家。虽然朱子学从明代到清代始终葆有正统学术的地位,而作为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在中国已经日趋没落。而与中国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刚好相反,朱子学在16世纪中期的韩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论思想深度还是学者人数皆粲然可观。16世纪朝鲜朝朱子学的兴起和发达,一方面表明了朝鲜性理学的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已经移到韩国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的生命,也为此后在东亚的进一步扩大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如果说退溪、高峰、栗谷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在16世纪已经转移到韩国,那么17世纪以后朝鲜后期实学兴起则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则进一步东移,朱子学在整个东亚实现了完全的覆盖。②诚如斯言,朱子学在东亚地区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朝鲜朝性理学的确起了非常重要之作用。像“四端七情理气”之辨、“主理主气”之争以及“四七人心道心”之辨等学术论争的相继发生,皆使朱子学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
由上述可知,人心道心作为朱子“心”论的核心范畴,与已发未发、体用及理欲等诸范畴相联系在理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说虽由二程始倡,但其独特理论价值与意义却由朱子之阐发才得到充分彰显。至16世纪,“人心道心”论经由整庵的发挥,不仅成为明代理学的主要论题,而且还进入理学心性论的核心范畴之列。但是,“人心道心”论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和核心概念,与韩国儒者富有创意的诠释与持续激辩分不开。
当罗整庵提出“道心为性,人心为情”主张时,在中国并未激起反响,但是却在朝鲜时代的性理学者中引起激烈的论辩。换言之,“人心道心”论成为一个主要的儒家哲学论题,乃由朱子开其端,整庵扬其流,朝鲜性理学者会其成。因而深入探讨朱子、整庵及李珥等中韩代表性的朱子学家的“人心道心”论,既可以看出整庵对朱子心性论的继承与修正以及朱子学心性论发展之脉络,也可以为理解朝鲜性理学提供一把钥匙,借以展现朱子学在东亚的多元发展面貌。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人心道心”之辨在东亚思想界展开的过程中相继呈现出多种理论范式。如朱子的基于知觉论和价值论面向的,“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以道心宰制人心的诠释范式;基于性情论和体用论面向的,整庵的“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的道心人心体用论诠释范式;基于理气论和“四七”论面向的,李珥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相对说诠释范式;等等。这一过程既是“人心道心”之辨义理不断得到丰富和彰显的过程,又是朱子学理论在东亚地区持续深化和多元发展的过程。这一朱子学不断“东亚化”的历史进程,最终使理学(朱子学)成为近世东亚世界里共通共享的学术文化。
一、朱子的“人心道心”论及其理论意涵
人心、道心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宋儒“道统”之说的主要文献根据之一,朱子将此十六字称为“尧、舜、禹相传之密旨”①。此“十六字心传”的大意是说:人心险恶难测,道心幽微难显,唯有精一至诚,方保此心中正不偏。
对于此古圣先王相授受之心法密旨,二程对其中的人心道心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程颢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②表明,依明道之见人心与道心的关系即为人欲与天理之关系,而程颐则直接将二者关系解作私欲与正心的关系。小程子有言:“‘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③伊川以道心为正,人心为邪,所以特别强调施“精一”功夫以使道心不被人心所扰乱。进而他还主张存公灭私,明理灭欲,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④人道说受到二程的青睐,与其所含的思想意蕴密不可分。宋儒强调道德直觉和人格修养,为此提倡以道德意识主宰人的行为使之达于其宣扬的“以理节欲”之目的。人道说所涉的论域,如道德与情欲、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之间关系等正好满足了理学家的此一理论需求。同时,这也反映理学道德心性学说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但是,二程将人心与道心对立起来,将人心视作人欲、私欲,否定的人的自然需求和感性欲望的理论作解也使理学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亦重视“人心道心”论。他在继承二程的人道说的基础上,从心性论和知觉论的维度对其意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首先,朱子以为人只有一个心,若说道心是天理,人心是人欲,便有了两个心。曰:“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非有两个心。”⑤在朱子看来,心之所以有二名,只是因各自所知所觉者不同而已,其实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而且,还对二程将人心解为人欲的观点提出异议。
其次,自从“己丑之悟”之后,朱子便运用体用说对“心”作了全新解读。他以为“心”是体用之全体,不仅兼体用,而且贯动静。曰:“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无一毫私欲之间;其流行该遍,贯乎动静,而妙用又无不在焉。故以其未发而全体者言之,则性也;以其已发而妙用者言之,则情也。然‘心统性情’,只就浑沦一物之中,指其已发、未发而为言尔;非是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又是一个地头,如此悬隔也。”①认为,以心有体用而言,“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②;以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③,心是“贯彻上下,不可只于一处看”④。由此朱子的“心”既具道德心之意涵,又有知觉心之属性。故“心”在其哲学中地位极特殊,如其所言“惟心无对”⑤。
再次,朱子进一步运用心之体用说对人心、道心及其二者之关系展开了详细论述。曰: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⑥
此段引文可视为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晚年定论,此文写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其时朱子之思想已渐趋成熟。文中朱子对人道说的主要问题,作了纲要式的经典解说。一是从知觉论意义上,对人心、道心作了界定。他指出人心生于形气之私(觉于欲),而道心则原于性命之正(觉于理)。这就解答了二者皆发自一个心,何以有人道之分的问题。此一区分本身也反映了理学自身的价值诉求。二是指出不论上智之人抑或下愚之人皆有人心道心,在这方面人人皆平等。这一主张实则反映了人皆能成圣成贤的理学价值理想。三是对人心与人欲(私欲)作了区分。朱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合理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求。认为,“饥思食、寒思衣”等“人心”所包含的生存需求,圣人亦不能无。四是在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以道心来节制人心。值得注意的是,朱子虽然坚持人心与道心相分的理论,但倾向认为“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①二者的分别只是一个“交界”,彼此不因一方之存在而自行消失——问题是以何方为主导。朱子主张以道心(天理)宰制人心,即所谓“‘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乃善也”②。这可说是理学所一贯追求的价值目标。
由此可见,人道说虽与理欲论相对应,但不似理欲论那般紧张。而朱子对天理、人欲却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二者是不具共时性、共存性的两边相对之物。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着,学者需要于此体认省察之。”③朱子甚至指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④这表明,在他看来以天理战胜人欲这才是修学的重中之重。
概言之,朱子通过人心、道心说,对“心”的含义作了多维度阐发。尽管他的人道说所讨论的是心之“已发”层面问题,并非为“未发”之体,但是其理论仍然建立在体用关系之上,也可说是心之体用说的运用和心之知觉说的实现。⑤不过,在价值论层面上,朱子思想的总体倾向是重义轻利、贵理贱欲,故其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理论主张,如以存理遏欲来扩充道心及以“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等,可视为其义利观、理欲观在心性论上的具体体现。
二、罗钦顺的“人心道心”论
整庵罗钦顺被后人称为“宋学中坚”和“朱学后劲”,在明代他是能够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朱学阵营的标志性人物。而且,其代表作《困知记》问世后不久便传至朝鲜和日本,为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不过,朱熹的思想传至整庵,较之原来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变动。首先在理气论层面发生明显变化,呈现出由“理学”转向“气学”的理论动向。而且,主张去理的“实体化”,强调“理气为一物”等思潮为朱学心性论的新诠释提供了理论基础。
整庵在阐发其心性理气诸说时,对朱子的学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和补充。在理气论方面,他直接批评朱子的理气说“未归一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所谓‘理气二物,亦非判染为二’,未免有迁就之意。既有强有弱,难说不是判然。夫朱子百世之师,岂容立异?顾其言论间有未归一处,必须审求其是,乃为善学朱子,而有益于持循践履之实耳。”①他认为朱子是百世之师,之所以对其观点提出异议,主要是因其言论中有不一致之处。整庵以为向道者应矢志探求圣学中正确的东西,这样才算是善学朱子,且有益于持守与实践。于是,他以明道的道器论为依据提出自家的“理气一物”说。整庵有言:“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决也。明道尝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又曰:‘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窃详其意,盖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说个形而上下,则此理无自而明,非溺于空虚,即胶于形器,故曰‘须著如此说’。名虽有道器之别,然实非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至于‘原来只此是道’一语,则理气浑然,更无隙缝,虽欲二之,自不容于二之,正欲学者就形而下者之中,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则不是也……晦翁先生……谓‘是理不离气,亦不杂乎气’,乃其说之最精者。但质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良由将理气作二物看,是以或分或合,而终不能定于一也。”①他认为,朱子的理气论“终不能定于一”是因其始终将理气“作二物看”之故。依其之见,理须在气上认取,但是若把气认作理也是不对的——正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②。对此,他自信地说:“此言殆不可易哉!”③
整庵自谓心性理气诸说是其学问中的“大节目”④,而其心性之辨正是建立在“人心道心”之辨的基础上。
对于人心道心问题,整庵曾不无自豪声称:“人心道心之辨,仆于此用工最深,窃颇自信。”⑤又言道:“‘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后大本可得而立。’斯诚讲学第一义。”⑥可见,此论在整庵学说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重要。
在人心道心的问题上整庵亦对朱子提出质疑,指出其心性学说“未定于一”。曰:
“凡言心者皆是已发”,程子尝有是言,既自以为未当而改之矣。朱子文字,犹有用程子旧说未及改正处,如书传释人心道心,皆指为已发,中庸序中“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一语,亦皆已发之意。愚所谓“未定于一”者,此其一也。⑦
罗钦顺以为,若将人心、道心一概视作已发看“是为语用而遗体”⑧。整庵的这一指责,若从其所持之性情体用论立场看的确有其合理性。朱子本人在“中和旧说”中也使用过此一说法。但是,从“中和新说”之后对“心”的重新诠释以及对人道说所持的诠释立场来说,整庵的这一指责却有待商榷。由此可见,整庵与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不同的问题域以及诠释立场上的差异。罗钦顺的人道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整庵从寂感意义上的动静论视角对人心道心进行了界定。曰:“道心,‘寂然不动’者也,至精之体不可见,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危。”①那么,他所理解的“心”为何物呢?罗钦顺指出:“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②表明,对“心”与“性”整庵是有严格区分,而且他还主张学者为学应先明于“心性之别”。在他看来,孔子教人也无非是存心养性之事,然从未明说什么是心性,到了孟子才明言何为心性。他说:“虞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③由此亦可见,整庵对“心性之辨”重视程度,但是他也曾指出“心性至为难明”④。罗钦顺认为陆象山的错误正是未能分辨清楚心与性。而其“心性之辨”,正是通过“人心道心”之辨得到深入的诠释。
其次,整庵从动静之分、体用之别对人心道心作了理论诠释。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圣神之能事也。”⑤此段引文是整庵对人心道心问题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论述。罗钦顺同样主张心是一个,但是他以为之所以要从人心道心两方面来说是为了表明心的动静之分和体用之异。可见,整庵与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诠释立场和诠释视角有着较大差异。罗钦顺以为,以静来制动便是吉,动而不知返回本心便是凶。因此审察心之动机(“惟精”),保持人心之诚(“惟一”),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允执厥中”)。在他看来,这是“圣神之能事”亦即圣人之本领。
再次,整庵从性情论维度对人心道心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曰:“道心,性也;性者,道之体。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其体一而已矣,用则有千变万化之殊,然而莫非道也。此理甚明,此说从来不易。”①在此,整庵又将人心道心之辨转化为性情之辨——道心成了未发之体,人心则成了已发之用。对此一解,他极为自负。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仆于此煞曾下工夫体究来,直穷到无可穷处,方敢立论。万一未合,愿相与熟讲之,此处合则无往而不合矣。”②整庵问学之艰辛及学思之谨严于此可见。其“道心为性,人心为情”之说乃反复参验省察后所得的思想结晶。这既是其在心性之辨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也是其独特心性学说的立论基础。
明中叶后程朱理学日渐式微,陆王心学则日益隆盛。阳明所倡导的简易直截的“良知说”颇受士人追捧。而在整庵看来,陆王心学是阳儒而阴释,实与禅学无异。作为“朱学后劲”罗钦顺深以为忧,于是将阐明“心性之辨”,批驳心学的“良知说”作为论学的首要目标和作为卫道的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截流塞源,他还对《楞伽经》等佛教经典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对其辟佛功绩“东林八君子”之一的晚明大儒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1562—1626年,世称“景逸先生”)称赞道:“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③而他则把辟佛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儒佛之辨上。罗钦顺试图以心性之辨阐明儒佛之区别。罗氏论曰:“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盖虚灵知觉,心之妙也。精微纯一,性之真也。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④他进而指出:“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岂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见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别,彼则浑然无别矣,安得同!”⑤可见,依他之见儒佛之间最根本区别在于心性之辨上,亦可理解为在“人心道心”之辨上。佛家禅学的确在心性问题上只关注“心”,却未留意到儒家至为强调的“性”这一本体,故朱子评论说“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⑥。这是整庵“理气一物”论、“心性之辨”(“人心道心”之辨)等主张的思想史背景,学者于此不可不察。
简言之,主张“理气一物”,辨明“心性之别”是整庵之学说的理论旨要。而建立于“道心为体,人心为用”义理架构上的人心道心说则是其学问的核心纲领,整庵自谓:“拙《记》(指《困知记》——引者注)纲领只在此四字,请更详之。”①由上可见,整庵之所以重视“人心道心”之辨,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具体人文语境以及所要回应的时代话题都有密切关联。
由此可见,人心道心论的独到的理论价值和意义经由朱子之阐发才得到彰显,但未成为宋代理学的主要论题。此后,经整庵的发挥,人心道心才进入理学心性论的核心范畴之列。不过,人心道心论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还是离不开韩国儒者对之所作的创造性诠释。
三、李珥的“人心道心”论
整庵提出以“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的人道体用说之后,其主张并未受到明中叶士大夫们的积极回应和热议。但是,随着其著作《困知记》在朝鲜的流布,此说开始受到朝鲜儒者关注和重视,并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人心道心”之辨在朝鲜所激起的思想波澜,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东亚儒学史上所罕见。经过朝鲜儒者们富有创意的阐发,“人心道心”之辨才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哲学论题。
在朝鲜朝儒者的人道论中,与李滉并称为朝鲜朱子学双璧的栗谷李珥的人心道心论颇具代表性。李珥对与其同时代的整庵十分赞赏,曾称颂说:“罗整庵识见高明,近代杰然之儒也。有见于大本,而反疑朱子有二歧之见。此则虽不识朱子,而却于大本上有见矣。”②而且,他还将整庵同与其同时代的退溪李滉和花潭徐敬德作过比较,得出结论:“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③李滉和徐敬德,皆为韩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代儒学名宿,李珥对整庵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原因在于:一是其理气论与整庵较相近(二人皆取理气不离之立场);二是李珥认为整庵不仅对朱子学“有见于大本”,而且还多有“自得之味”(重视“自得之味”是二人学问之共同特点)。
不过在李珥看来,尽管整庵对朱学之“大本上有见”,但是整庵“以人心道心为体用,失其名义”,①使人感到惋惜。即便如此,李珥认为若衡之于与李滉“整庵之失在于名目上,退溪之失在于性理上,退溪之失重矣”②,他还说过整庵“虽失其名义,而却于大本上,未至甚错也”③。李珥也在接续朱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心道心”论。
首先,从强调心性理气诸说之间的一贯性立场对“人心道心”论作了解读。曰:“理气之说与人心道心之说,皆是一贯。若人心道心未透,则是与理气未透也。理气之不相离者若已灼见,则人心道心之无二原,可以推此而知之耳。”④可见,李珥的理气论是其人道说的立论根基,人道说是其理气论的直接生发。因理气之“不离”义是其理气论的主要思想倾向,故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他也以二者的不可分和相联结为其主旨,强调人心、道心的“无二原”性。这与朱子、整庵的人心、道心之相分思想是有所区别的。
其次,从主理、主气视角对人心、道心的含义作了阐发。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感动之际,欲居仁、欲由义……欲切偲于朋友,则如此之类谓之道心。感动者因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形气不为之掩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饥欲食、寒欲衣……四肢之欲安佚,则如此之类谓人心。其虽本于天性,而其发由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气,而目之以人心也。”①依李珥之见,因感动者是形气,故感动之际何方为主显得十分紧要。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主乎理”的是道心,出于耳目四肢之私而“主乎气”的则是人心。从主理、主气的角度探讨人心道心之含义,这一点颇能反映韩国儒学在讨论人间和存在的所以然根据这个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时,往往落实到性理层面上展开理气这个形上、形下问题的理论特性。②重视人间性理,是韩国儒学的根本特征。
再次,基于心之已发论,以知觉说的立场回答了“一心”何以有“二名”,即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分的问题。
在李珥的哲学中“心”属于气,故不管人心还是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规定使其人道说自然具有了知觉论的特色。他说:“心一也,岂有二乎?特以所主而发者有二名”③,又说:“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一心。其发也或以理义或为食色,故随其所发而异其名。”④“心”只有一个,这与朱子的主张相同。但是在“一心”何以有“二名”的问题上,李珥独特的心性论义理间架使其抱持与朱子不同的诠释立场。众所周知,朱子的学说以“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而李珥则以“理气之妙”、心性情意四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因此朱子的性情论可以“心统性情”说来概称,而李珥的性情论则似以“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说来指代更为恰当。最紧要的是二人对“意”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在朱子的性情论中,“意”和“情”都是从属于“心”的概念。“情”和“意”二者的关系是,大抵“情”为性之动,“意”为心之所发;“情”动是全体上论,“意”是就起一念处论。⑤因此在朱子心性论中,“意”的思量运用之含义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在李珥哲学中,“意”和“情”是两个有着明确界定的并列的哲学范畴,可视为心的两个不同境界。故其“人心道心”论是兼情意而言,如其曰:“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①,“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②需注意的是,“意”其实是在其人道说中起十分重要作用的范畴。这既是李珥与朱子性情论之区别,亦是其对朱子心性情意说的发展。相较而言,李珥的心性学说确实比朱子的理论更为细密和清晰。而且,强调“意”的商量计较作用是李珥知觉论最为显著的特点。
基于“意之商量计较”的意涵,李珥提出了极具特色的“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终始”说。他说: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③
不管根于性命之正的道心,还是源于形气的人心,皆属已发,此时气已用事。若欲不咈正理如实呈现,或知非制伏不从其欲,都要借“意”之计较、思虑、商量作用来实现。因此李珥认为,在人心之方寸之间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可变状态。在已发层面上,二者是并无固定的、严格的分别。因此,李珥为学极重“诚意”。在他看来,“情胜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④栗谷指出,若能保证“意”之“诚”,则所发之“心”皆能呈现为道心。
最后,李珥还援引“四七”论、理欲论,进一步阐释了人心道心之界说以及二者间的关系。
“四端七情”论是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的重要学说,人心道心论争的发生其实就是“四七”论由“情”论层面向“心”论层面的进一步推进,或者说“四七”论在心性领域的更深、更广意义上的展开。
在李珥哲学中,因“意”的商量计较作用,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相互转化之状态。这与其“四七”论中七情兼四端的情形有所不同,对此差异李珥指出:“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则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①他进而指出:“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矣,乌可强就而相准耶。”②在李珥哲学中的“情”不具商量计较之意,故性发为情之际,七情可以兼四端。因为依他之见,“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但是,人心、道心则已达比较而看的地步,已具对比之意,故不能兼有只能互为终始——这便是其“人心道心终始”说。
因为人心与道心是基于“意”之商量计较而存在的相对之物,李珥又由“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而提出“人心道心相对”说。他说:“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若七情则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谓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乌可分两边乎?”③
此论看似与其“人心道心终始”说矛盾,但这是李珥从天理人欲论角度对人道说的解读,可视为对“人心道心终始”说的另一种阐发。他曾说过:“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④可见,李珥对道心、人心、人欲是有明确的区分。他肯定人心亦有善,朱子所见略同。但是,人心之善与道心是否为同质之善呢?对此,李珥在《人心道心图说》中指出:“孟子就七情中别出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论者或以四端为道心,七情为人心,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七情岂可谓之人心乎?七情之外无他情,若偏指人心则是举其半而遗其半矣。”①可见,他将二者视为同质之善。在理欲论意义上,其人道说比朱子的人道说显得更为紧张和严峻,颇似“天理人欲相对”说。这也是二人“人心道心”之说的主要区别之一。同时,李珥还从理欲之辨角度,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作出自己的解释。
四、“人心道心”之辨在16世纪东亚思想界的多元发展
陈来先生曾指出:在历史上,与政治的东亚不同,从东亚文化圈的观点来看,朱子学及其重心有一个东移的过程。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在中国再没有产生有生命力的哲学家。虽然朱子学从明代到清代始终葆有正统学术的地位,而作为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在中国已经日趋没落。而与中国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刚好相反,朱子学在16世纪中期的韩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论思想深度还是学者人数皆粲然可观。16世纪朝鲜朝朱子学的兴起和发达,一方面表明了朝鲜性理学的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已经移到韩国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的生命,也为此后在东亚的进一步扩大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如果说退溪、高峰、栗谷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在16世纪已经转移到韩国,那么17世纪以后朝鲜后期实学兴起则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则进一步东移,朱子学在整个东亚实现了完全的覆盖。②诚如斯言,朱子学在东亚地区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朝鲜朝性理学的确起了非常重要之作用。像“四端七情理气”之辨、“主理主气”之争以及“四七人心道心”之辨等学术论争的相继发生,皆使朱子学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
由上述可知,人心道心作为朱子“心”论的核心范畴,与已发未发、体用及理欲等诸范畴相联系在理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说虽由二程始倡,但其独特理论价值与意义却由朱子之阐发才得到充分彰显。至16世纪,“人心道心”论经由整庵的发挥,不仅成为明代理学的主要论题,而且还进入理学心性论的核心范畴之列。但是,“人心道心”论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和核心概念,与韩国儒者富有创意的诠释与持续激辩分不开。
当罗整庵提出“道心为性,人心为情”主张时,在中国并未激起反响,但是却在朝鲜时代的性理学者中引起激烈的论辩。换言之,“人心道心”论成为一个主要的儒家哲学论题,乃由朱子开其端,整庵扬其流,朝鲜性理学者会其成。因而深入探讨朱子、整庵及李珥等中韩代表性的朱子学家的“人心道心”论,既可以看出整庵对朱子心性论的继承与修正以及朱子学心性论发展之脉络,也可以为理解朝鲜性理学提供一把钥匙,借以展现朱子学在东亚的多元发展面貌。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人心道心”之辨在东亚思想界展开的过程中相继呈现出多种理论范式。如朱子的基于知觉论和价值论面向的,“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以道心宰制人心的诠释范式;基于性情论和体用论面向的,整庵的“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的道心人心体用论诠释范式;基于理气论和“四七”论面向的,李珥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相对说诠释范式;等等。这一过程既是“人心道心”之辨义理不断得到丰富和彰显的过程,又是朱子学理论在东亚地区持续深化和多元发展的过程。这一朱子学不断“东亚化”的历史进程,最终使理学(朱子学)成为近世东亚世界里共通共享的学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