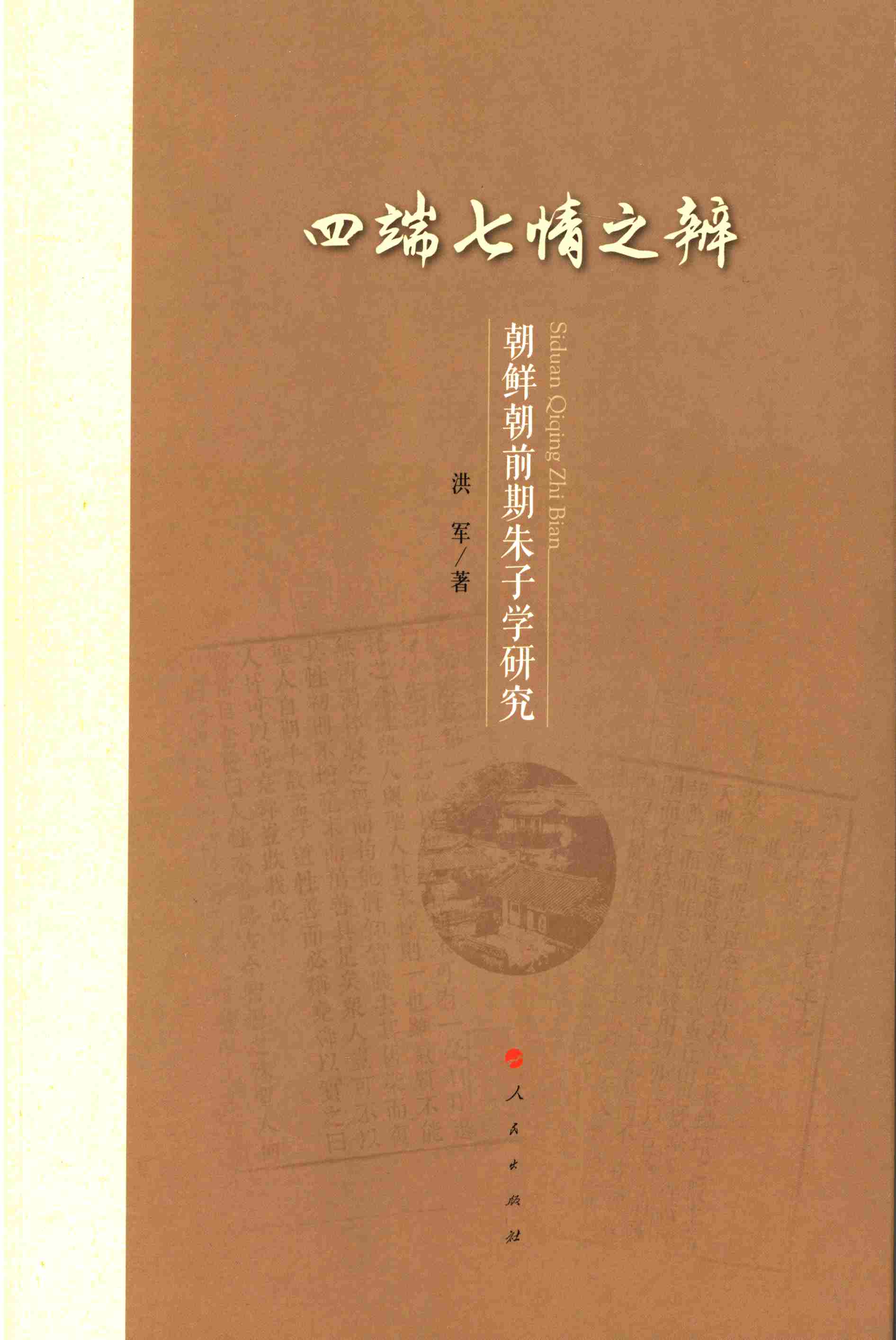第一节 “四端七情”之辨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
| 内容出处: | 《四端七情之辨》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9068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四端七情”之辨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 |
| 其他题名: | 以李滉与李珥的理论差异为中心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0 |
| 页码: | 237-25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韩国儒学具有独特的品格,在东亚儒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其中,朝鲜朝时期的性理学以其精微的逻辑和深刻的性情而被誉为东亚朱子学的奇葩。这里以李滉和李珥的四端七情理论为例,探讨韩国性理学的特色。在这一论辩中,李滉强调四端是由理主导,七情是由气发出的。他认为四端是纯善的,而七情是兼有气的,因此有善恶之分。这一理论对于韩国哲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
| 关键词: | 韩国儒学 性理学 四端七情 |
内容
韩国儒学以其独特品格在东亚儒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尤其是朝鲜朝(1392—1910年)性理学以其逻辑的精微性和性情的深刻性①被誉为东亚朱子学的奇葩。本节将通过最具代表性的李滉和李珥的四端七情理论之比较来探讨韩国性理学性情理论之特色。
一、四端七情论辩的发生及其理论渊源
“四端七情”之辨是韩国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论争。此论辩发生于朝鲜朝性理学最为兴盛的16世纪中叶。此时涌现出以李退溪、郑之云(1509—1561年)、奇大升(1527—1572年)、李栗谷、成浑(1535—1598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硕学名儒。这一性理学家群体的出现不仅使韩国性理学实现了理论的本土化,在对朱子性情学说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的思考深度方面甚至还超过了同时代的明代朱子学。①“理气四端七情”之辨的发生,主要是源于韩儒对儒家经典及朱学理论的不同理解和所持的强烈的问题意识。
《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②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被称为“四端”,代表人的四种伦理道德情感。“七情”则指,《礼记·礼运篇》所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③中的七种人的自然情感。或许因二者各自出现于不同的儒家经典,在中国四端与七情并未成为对举互言的一对哲学范畴。如以宋明儒者为例,二程(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好言四端,少言七情;阳明《传习录》虽屡言七情,然不与性对。朱子亦是谈论四端处较多,而言七情处甚少。④朱熹只是在与门生的问答中曾说过一句“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①。这是其在四端和七情问题上的最为完整的表述。此语仅见《朱子语类》,在朱子其他著作中再难找寻,而且朱子对这一句也并未进行具体的解释和阐发。朱熹在工夫上的基本立场是此心寂然不动未发时应先做涵养,待心气发而为情时则施以察识。但因气的发用较随意突然,加之气所具有的清浊粹驳之差异,其发用未必都能“中节”,即一切都合乎于一定的法度(道德原则)。故必须时时以理驭气,使其皆能发而中节。若依朱子的此一思路,应将“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理解为四端是依理而发出的情,而发者则为气——情既然属于气,在“理”上就不能言“发”。朱熹的这一句话在中国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却在16世纪的韩国性理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四端七情,理发气发”之大论辩。
在韩国哲学史上“理气四端七情”之辨的发生可追溯至与郑道传并称为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双璧的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他曾师从于丽末鲜初的大儒李穑(字颖叔,号牧隐,1328—1396年)和郑道传(字宗之,号三峰,1342—1398年)。权近出身文臣贵族家庭,曾祖父即是高丽朱子学的先驱权溥。其大作《五经浅见录》是一部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著作,而《入学图说》更是韩国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学思想的入门书,影响曾及于日本。
权氏与郑道传虽然都是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但在接受和研习朱子学方面却各有侧重。郑氏致力于对现有朱子学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并以之为据竭力批判佛教。而权近则更倾心于对朱子学理论的探究与阐发。仅就二人对韩国性理学的理论贡献而言,权氏显然大于郑氏。故权近被视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始祖。
权近以独尊儒术为基本前提对佛、道进行批判,并在批判的过程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理”的绝对权威——所谓“理为公共之道,其尊无对”①。他进而指出:“理为心气之本原,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②在此基础上,权近着重解释了五常、四端、七情等心性论方面的基本问题。其《入学图说》中首次提出的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开启韩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理论之先河。不仅如此,他的《入学图说》还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说类书籍,因此权近亦被视为韩国儒学“以图释说”理论传统的鼻祖。《入学图说》中的“天人心性分释之图”性条中写道:“昔唐韩子《原性》而本于《礼书》,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为性发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属乎性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当然之则。如其发而中节则《中庸》所谓达道之和,岂非性之发者哉!然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而得与四端并列于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见其发之有中节不中节者,使学者致察焉’。”③权近指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无异,皆属纯善;而发而不中节者必非为性之所发,则不能与四端并列。权近认为,四端可视为理之所发,而七情却并非如此,并以此区分了四端和七情。他的这一见解实乃百余年后,李滉、李珥等人进行的四七论辩之滥觞。其思想后来被李滉等人继承和发扬,在韩国哲学史上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权氏之学还远播日本,并在日本儒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理气四七”之辨发生的直接诱因则是李滉对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的《天命图》中“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的修订。
郑之云为朝鲜朝初期的大儒金安国(1478—1543年)、金正国(1485—1541年)兄弟的弟子。他世居高阳,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李滉对其十分推崇,曾赞曰:“君曾测海,我要窥藩,藉君伊始……君胡发端,弗极其致,使我伥伥,难禁老泪。”①
郑之云绘制的《天命图》是引发“理气四七”之辨的原始文本。起初李滉获此图后将图中的注释“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即,将郑氏文中的“于”改为“之”,经李滉修改的图被称为《天命新图》。李滉以为,郑氏之言对四七理气的分别太甚,极易引起纷争,所以他在语气上对之作了些改动。
李滉的这一订正,旋即引起了学界的争议。高峰奇大升即由“理气浑沦”立场出发向李滉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书信往来。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为以心性论为中心的韩国性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郑之云则是在韩国哲学史上第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和七情的性理学者,其独特的问题意识直接促发了在东亚儒学史上别具一格的“四端七情理气”之发理论的诞生。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
李滉的“四端七情”论最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之特色。然其四七理论的成熟与完善离不开与奇大升之间展开的相互问难。在论辩过程中,不仅李滉的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而且其立场亦逐步得以明晰。
李滉将郑之云的《天命图说》加以改订之后,首先向他发难的便是奇大升。奇大升曰:“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③又曰:所谓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④。因而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待,谓之纯理或兼气则有些不妥。在奇大升看来,四端虽是纯粹的天理之所发,但只是发乎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于是,他言道: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也。①奇大升以为,四端与七情皆为情,不能将二者看作具有不同性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因此以理气来分而言,四端七情便有所不妥。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子学原旨。
对于奇大升的质疑,李滉回复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②
李滉承认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也承认先儒并未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与气以论其性质之不同。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因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由此,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理)、七情(气)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他在此一问题上的主要说法有:
“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①
“四端之发,纯善,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②
“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③
第一条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第二条是己末年其59岁(1559年)时的说法。此时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论辩。后经奇大升之诘难,李滉便有了第三条的说法。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提法,可视为李滉之最终定论。
李滉在此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源和来源上的差异。这源于他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李滉曰:
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④
由此可知,首先在心性情关系上,李滉倾向于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其次,他将心规定为“理气之合”。这与朱子的“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思想相比,心的含义以及心与理、气之关系变得更为清晰。同时,此说也为其分属理气的方式论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预设了理论前提。
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李滉晚年的思想结晶。作为《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该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为李滉所作。①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范畴。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这正是性理学的主题所在。性理学道德主体论的人性学说,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②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性为体,情为用。朱熹曰:“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③李滉则与朱熹不同。他进一步发挥朱子的理气心性说,将性情问题与理气之发结合起来,使朱学心性论深化为性情论的“理气四端七情”论。此图中的中图和下图是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④而解下图同样鞭辟入里:“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⑤
由此可见,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来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及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依程朱“性发为情”之原则,解读了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及无不善之情等。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可见李滉试图兼顾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这种双重文本及其双重权威所形成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即是引发韩儒各种学术争论的根源①,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抑或气发皆可以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或放而为恶是由理发未遂和气发不中所致。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现或气发而皆中节是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面引文中的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
而且,他还以七情与四端来分论人心与道心,曰:“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②这既是李滉对朱子心论的发展,也是二人心论之差异所在。虽然其中图不带气说,但他仍然以理气论性情。李滉有言:“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③可见,李滉仍以朱子的“理气心”来论性情,并侧重于持教工夫。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学之传统,李滉亦如此。他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亦是情,而“情”皆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攸关人性之善恶。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即缘于此。李滉说过:“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④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即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通过自家内省以求致中和。李滉去世前曾屡次修订此图。“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所载本也。”①可见,此图在《圣学十图》中所占有之地位何等之重要。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认为不仅“性”可以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他说:“故愚尝妄以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即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
“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接续朱子的理气心,但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故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他说:“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这样的理解,李滉明确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
他对七情的看法则始终落在气的一边。李滉说过:“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又不能无理,所以他坚持认为,“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他的答案是:“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以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
朱子哲学主张,人是由理和气共同构成的——气构成人之形体,理则为人之本性。李滉据此提出了“四端七情分理气”说,主张道德情感(四端)发自人的本性(理),而一般生理情感(七情)则发自人的形体(气)。其“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提法表明四端与七情的内在根源是不同的,这虽然与朱熹《中庸章句》的说法不同,却令朱子学性情论未解决的问题得到了一种解决。③这亦可以视为李滉对朱子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不过,依其理气之心,四端与七情不论善还是不善,或者说不论中节还是不中节,皆依“气”而定。他说:“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矣。”④实际上四端七情皆落在气的一边。理发未遂是掩于气,理发直遂是不掩于气——遂与不遂,俱在气一边。从另一方面说,气发不中则灭其理,气发中节则不灭其理——灭理与不灭理亦俱在气的一边。因“气”的状体直接影响“理”的显否以及如何显现,所以主敬以治心气必使气顺理而作、依理而行。此又是李滉以主敬治心的最重要原因。主敬以治心气,即为其著名的主敬论思想。李滉的学说,亦被称为“主敬”哲学。
三、李珥的“四端七情”论
继李滉、奇大升之后,众多学者都对四端七情问题发表了自家见解。李珥亦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他的说法,大都是针对李滉的见解而发。
在四七问题上,李珥与李滉的分歧较明显。李珥从其“气发理乘”的理气观出发,而主张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他曾说过:“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①又说:“四端犹性之言本然之性也,七情犹性之合理气而言也。气质之性实是本性之在气质者也,非二性。故七情实包四端,非二情也。”②栗谷认为七情可包四端,四端为善一边,七情是兼气质而言性之全,四端是剔出而言性之本。朱子谓:“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③理与气之关系亦是如此。李珥进而指出:“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既非二物,又非一物。”④他接着直承朱子理气动静之说,提出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器。他说:“理无形也,气有形也;理无为也,气有为也。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⑤从“理无为而气有为”之见解自然就会产生“气发理乘”之主张。此说亦可称为“气发一途”说,实为李珥理气论之中心思想。“气发理乘”说的主旨大意即是:“大抵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无先后,无离合,何谓互发也。”⑥李珥自注曰:“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接着他又对“气发理乘”之义解释道:“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⑦
依此见解,李珥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进行了批评。他说:“四端是七情之善一边也,七情是四端之总会也。一边安可与总会分两边相对乎?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意必有在。而今者未得其意,只守其说,分开拖引,则岂不至于辗转失真乎?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专言气云尔。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李滉因此而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①在李珥看来,“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无论四端还是七情,皆为气发理乘。因理气原无先后无离合,故不可谓理气互发。
他认为,若四端是理发,为善情;而七情为气发,亦可为善情——如此则人心便有二本。李珥意识到这一问题,明确指出:
退溪先生既以善归之四端,而又曰七者之情亦无有不善,若然则四端之外亦有善情也,此情从何而发哉?孟子举其大概,故只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而其他善情之为四端,则学者当反三而知之。人情安有不本于仁义礼智而为善情者乎?善情既有四端、而又于四端之外有善情,则是人心有二本也,其可乎?……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②
这里他又将“四七”之辨从性情论延伸至心论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四七”论的讨论范围和深度。李滉认为七情发于气,是气发而理乘之,故七情并非不善,然因是发于形气,不能保证其必为善,实际上可为善亦可为恶。如前文所说:“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李滉似不曾说七情亦无有不善,如上引李珥所说。但七情说有善情,总是可以说的,若是便是四端之外有善情。若由理发者方为纯善,则由气发者之七情中之善,又从何而发?若七情不由理发而亦可为善,则必有使其善之根据。于是生发四端者为一本,而生发七情之善者又是一本——这便是有二本了。
李珥要避免此二本之失,则四端和七情便不能是各有其本的异类之情——四端必须是七情中善的一类。他说:“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则兼四端……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①情只是一情,四端是就情之合理处说,而七情则是就全部之情而言。故四端纯是善的,而七情则兼善恶。李珥此说即表示理无活动性,唯有气才活动。情属气,故四端七情皆是气发。气之活动如能依理便是善情——四端不过是七情之善者。栗谷进而指出:
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决非二性。特就气质上单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合理气而命之曰气质之性耳。性既一则情岂二源乎!除是有二性,然后方有二情耳!若如退溪之说,则本然之性在东,气质之性在西,自东而出者谓道心,自西而出者谓人心,此岂理耶。②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思想出发,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转而支持奇大升的观点。他说:“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③一方面批评李滉未能真正理会朱子之本意,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论七情还是四端皆为气发理乘。
李珥对退溪之说的批评,遭到了成浑的辩难。于是,继“退、高之辩”之后,李珥和成浑之间又展开了第二次四七大论辩,将论争推向了高潮。成浑基本上赞同李滉的立场。他指出:“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④并向李珥提出质疑道:自己亦曾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存疑,但细心玩味朱子“人心道心之异,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之说后觉得李滉的互发说亦未尝不可。“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①,明显看出成浑较肯定“理气互发”说。
李珥同成浑数次交换书信,进行辩论。结果,使李珥的性理学立场更加明了。在李珥看来,对“四七”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他说:“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发矣。”②他进而举例说:“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③可见,他认为不仅四端与七情是气发理乘,而且天地之化亦是气发而理乘。
四、李滉与李珥“四端七情”论差异之分析
陈荣捷先生曾将“四端七情理气”之辨称为,比朱子与象山(陆九渊,1139—1193年)太极之辨或与同甫(陈亮,1143—1194年)的王霸之辨更超而上之的学术论辩。其历年之久,堪与我国明清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朱子晚年定论》之辨相比拟。④可见,这场四七辩论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理论意义。
如前所述,李滉与李珥虽然同尊朱子,却在体贴和阐发朱学方面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由此各自构筑了独特的性理哲学体系。
“四七”论是二人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二人分歧之产生源于他们对朱学的不同理解和多维解读。
对李滉、李珥的理论之差异可作如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在理气之发的问题上产生了歧义。二人从不同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的性理学思想。李滉倾向于理气之“不杂”义,李珥则侧重于理气之“不离”义,对朱子之说进行了不同的发挥。
朱子思想体系的基础在于其理气论,即建立在其理气不相杂,不相离的理气观之上。李滉在继承朱子理气论的基础上,着重于对理气之不杂的一面作了“理贵气贱”、“理尊无对”的解释。李滉之重视“不杂”义侧重理气为道器之分,如其所撰《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即强调理气之分别、道器之异。对于二者“不杂”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观的最大特色。
李滉主张“理贵气贱”,认为理具“主宰”义而气则无之。他说:“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①理“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②由主宰与被主宰的理气关系而形成二者的上下位观,即上者尊贵,下者卑贱,故理贵气贱。李滉指出:“理贵气贱,然理无为气有欲。”③由于气有欲,故须主敬以治之。而且,还对理本体作了“理(太极)自有动静”的解释。于是,在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便有了“理气互发”说。
退溪还提出“理纯善气兼善恶”之说。此说实亦直承伊川、朱子而来。气有清浊,而由气之清浊而言,气有或顺理或不顺理。主敬则必以理驭气,也就是说理为主以帅其气——理是纯善,而气兼善恶,纯善之理帅气则气必顺理而呈善。这便是其“理帅气卒”思想。李滉的理贵气贱、尊理贬气的观念,与理纯善而气兼善恶之说有着内在的思想关联。
理贵气贱、理气互发乃李滉理气观的主要内容。由于理无为而气有欲,故须主敬制气以显理。
他将朱熹的理气“先后”关系转化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由此为其“四七”论打下理论基础。
李珥的性理学说同样建立在其理气论的基石之上。不过,与李滉不同,他在继承朱子理气之说的过程中则侧重于理气之不离,从这个角度对朱子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发挥。理气之妙、气发理乘以及理通气局乃其学说之主旨。
李珥在理气定义及理气的发用义(动静义)上多有独到的议论,摘录如下:
“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①
“大抵有形有为而有动有静,气也。无形无为而在动在静者,理也。理虽无形无为,而气非理则无所本,故曰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②
“夫形而上者,自然之理也。形而下者,自然之气也。有是理则不得不有是气,有是气则不得不生万物。是气动则为阳,静则为阴。一动一静者气也,动之静之者理也。阴阳既分,二仪肇辟;二仪肇辟,万化乃生。其然者气也,其所以然者理也。”③
由此可见,李珥虽然也主张理是气的主宰者,但并未像李滉那样从伦理道德意义上尊崇“理”之地位。而且,他也不赞同理本体的发用性。在他看来,“理”是使万物生生不息的所以然者。这样的理是实有之理,亦即使气之生生变化成为可能的本体,此本体虽无形却实有。此实体恒随物(气)而在,与天理一般无二。依李珥见解,诚即是天理。因万物的生生不息,须由气来表现,气虽依理而行,却是气自身之变化而显形,而生成万物。理与气不相离,二者同等重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由此,李珥基于程明道的“道亦器,器亦道”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理气之妙”说。
李珥认为,在理气恒不相离的天地变化天道流行的过程上,动静的本身是气,而理只是主宰气,使气动静。即“一动一静者气也,动之静之者理也。”“一动一静”是“其然”,“动之静之”是“其所以然”。在此种意义上,理、气二概念,气是其然,理是其所以然。理、气二义,李珥承继朱子之说,建立在“其然,所以然”之义上。一动一静是其然,动之静之是其所以然。理气二者在其发用上亦是如此。李珥进而指出:“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①此即所谓“气发理乘”之说。李珥对此二十三字所言之内容,极为肯定自信。不但天地之化是如此,人心之发亦不外此,“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②。发之者是其然,所以发者是所以然,前者是表现者,后者是使表现者得以实现的主宰者。
一动一静者是气,动之静之者是理;理是主宰者,气是听命者。气的阴阳变化而生万物实际上皆是理之所为。所以李珥说“天以实理而有化育之功”。“实理”即是诚,“诚”作为本体亦是物之终始,故能有化育之功。李珥主“诚”之用意在于先立本体。
与李滉相比较,李珥虽然在理气说的理论突破上有所不及,但在准确地传承朱子的理气之说方面却更有过之。易言之李珥的理气观思想更能反映朱子理气论之特色。
其次,理气观上的理论差异,直接导致二人在心性论上的不同见解。
李滉将心定义为“理气合而为心”③,而李珥则将心理解为“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④。由此李珥否定天命、气质二性之说,而主张一性论(气质之性),进而提倡四端、七情亦是“非二情”。李珥有言:“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⑤他进而指出:“四端犹性之言本然之性也,七情犹性之合理气而言也。气质之性实是本性之在气质者也,非二性。故七情实包四端,非二情也。”⑥他认为七情不仅可以包括四端,而且还是兼气质而言的“性之全”。李滉则接受宋儒的二性理论,倾向人心道心也应以理气分而言之。
在性情的问题上,朱子学向主“情根于性,性发为情”。即,“性为体”(性是情的内在根据),“情为用”(情是性的外发表现)。故李滉和李珥的“理气互发”说或“气发理乘”说,都与其不同的心性结构相关联。
不论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还是李珥的“气发理乘”论,都为朱子学性情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
最后,李滉与李珥之所以对朱子学有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也与两人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在韩国儒学史上,李滉为学偏向自我人格的修养,而李珥则侧重于经世致用。故李滉之学亦称为退溪“圣学”,而李珥则开韩国实学理论之先河。李滉生活于韩国历史上“士祸”频发的年代,有名的四大“士祸”即发生于此一时期。此为其学术政治生涯历史背景。据年谱嘉靖二年癸未记载:“先生二十三岁,始游太学,时经己卯之祸,士习浮薄,见先生举止有法,人多笑之。所与相从者,惟金河西麟厚一人而已。”①从其“举止有法”可见为人之端重。李珥较李滉年少35岁,而他主要生活于韩国历史上的“党争”频仍之时期。在李珥生活之世,朝政士风皆每况愈下。“权奸甚误国之后,苛政日作,百弊俱积,民生之涂炭,未有甚于今日者也。”②“己卯诸贤,稍欲有为,而馋锋所触,血肉糜纷,继以乙巳士祸,惨于己卯。自是士林狼顾胁息,以苟活为幸,不敢以国事为言。而惟是权奸之辈,放心肆意。”③“党争”与“士祸”有较大的区别。“士祸”政治可视为李滉的“尊理”、“正伦”以及“主敬”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李珥所面临的社会状况是经历多次“士祸”之后,朝纲不振、民生困苦。故李珥论政为学立说都极重实功——所谓“政贵知时,事要务实”。反映在其思想上便是主张理气之不离、变化气质之性以及追求本然性与现实性的高度一致。此即栗谷主气论的思想特色。
概言之,“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的特色。李滉和李珥理论之所以有差异是因各自依傍的文本、所持的立场以及所处历史环境之不同。李滉论学基于体用之有别,李珥则基于体用之不离,或者说前者着眼于本体,后者则侧重于流行。李滉提出“理贵气贱”、“理气互发”之论,在理气四七问题上坚守了体用有别之立场。但“理发”之义则显然不合于朱熹的“理不活动”之义。李珥则提出“理气之妙”、“气发理乘”说,笃守了其体用不离之立场。
以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的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宋儒在把先秦儒学发展为宋代理学时并没有完全弥合二者间的差异,因此在论述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这些不同说法中所蕴含的问题或矛盾,在中国儒学史上没有展开讨论,而在韩国儒学的“四七理气”之辨、“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以及此后发生的“人物性同异”论辩中却得到深入展开。①由此可见,中韩两国性理学(朱子学)因所关注的核心话题、依傍之文本以及具体的人文语境之不同造成不同的理论性格和多元的发展路径。无疑,这既是韩国性理学的特色,亦是东亚朱子学的理论特色。
一、四端七情论辩的发生及其理论渊源
“四端七情”之辨是韩国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论争。此论辩发生于朝鲜朝性理学最为兴盛的16世纪中叶。此时涌现出以李退溪、郑之云(1509—1561年)、奇大升(1527—1572年)、李栗谷、成浑(1535—1598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硕学名儒。这一性理学家群体的出现不仅使韩国性理学实现了理论的本土化,在对朱子性情学说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的思考深度方面甚至还超过了同时代的明代朱子学。①“理气四端七情”之辨的发生,主要是源于韩儒对儒家经典及朱学理论的不同理解和所持的强烈的问题意识。
《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②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被称为“四端”,代表人的四种伦理道德情感。“七情”则指,《礼记·礼运篇》所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③中的七种人的自然情感。或许因二者各自出现于不同的儒家经典,在中国四端与七情并未成为对举互言的一对哲学范畴。如以宋明儒者为例,二程(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好言四端,少言七情;阳明《传习录》虽屡言七情,然不与性对。朱子亦是谈论四端处较多,而言七情处甚少。④朱熹只是在与门生的问答中曾说过一句“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①。这是其在四端和七情问题上的最为完整的表述。此语仅见《朱子语类》,在朱子其他著作中再难找寻,而且朱子对这一句也并未进行具体的解释和阐发。朱熹在工夫上的基本立场是此心寂然不动未发时应先做涵养,待心气发而为情时则施以察识。但因气的发用较随意突然,加之气所具有的清浊粹驳之差异,其发用未必都能“中节”,即一切都合乎于一定的法度(道德原则)。故必须时时以理驭气,使其皆能发而中节。若依朱子的此一思路,应将“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理解为四端是依理而发出的情,而发者则为气——情既然属于气,在“理”上就不能言“发”。朱熹的这一句话在中国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却在16世纪的韩国性理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四端七情,理发气发”之大论辩。
在韩国哲学史上“理气四端七情”之辨的发生可追溯至与郑道传并称为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双璧的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他曾师从于丽末鲜初的大儒李穑(字颖叔,号牧隐,1328—1396年)和郑道传(字宗之,号三峰,1342—1398年)。权近出身文臣贵族家庭,曾祖父即是高丽朱子学的先驱权溥。其大作《五经浅见录》是一部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著作,而《入学图说》更是韩国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学思想的入门书,影响曾及于日本。
权氏与郑道传虽然都是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但在接受和研习朱子学方面却各有侧重。郑氏致力于对现有朱子学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并以之为据竭力批判佛教。而权近则更倾心于对朱子学理论的探究与阐发。仅就二人对韩国性理学的理论贡献而言,权氏显然大于郑氏。故权近被视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始祖。
权近以独尊儒术为基本前提对佛、道进行批判,并在批判的过程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理”的绝对权威——所谓“理为公共之道,其尊无对”①。他进而指出:“理为心气之本原,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②在此基础上,权近着重解释了五常、四端、七情等心性论方面的基本问题。其《入学图说》中首次提出的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开启韩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理论之先河。不仅如此,他的《入学图说》还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说类书籍,因此权近亦被视为韩国儒学“以图释说”理论传统的鼻祖。《入学图说》中的“天人心性分释之图”性条中写道:“昔唐韩子《原性》而本于《礼书》,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为性发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属乎性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当然之则。如其发而中节则《中庸》所谓达道之和,岂非性之发者哉!然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而得与四端并列于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见其发之有中节不中节者,使学者致察焉’。”③权近指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无异,皆属纯善;而发而不中节者必非为性之所发,则不能与四端并列。权近认为,四端可视为理之所发,而七情却并非如此,并以此区分了四端和七情。他的这一见解实乃百余年后,李滉、李珥等人进行的四七论辩之滥觞。其思想后来被李滉等人继承和发扬,在韩国哲学史上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权氏之学还远播日本,并在日本儒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理气四七”之辨发生的直接诱因则是李滉对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的《天命图》中“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的修订。
郑之云为朝鲜朝初期的大儒金安国(1478—1543年)、金正国(1485—1541年)兄弟的弟子。他世居高阳,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李滉对其十分推崇,曾赞曰:“君曾测海,我要窥藩,藉君伊始……君胡发端,弗极其致,使我伥伥,难禁老泪。”①
郑之云绘制的《天命图》是引发“理气四七”之辨的原始文本。起初李滉获此图后将图中的注释“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即,将郑氏文中的“于”改为“之”,经李滉修改的图被称为《天命新图》。李滉以为,郑氏之言对四七理气的分别太甚,极易引起纷争,所以他在语气上对之作了些改动。
李滉的这一订正,旋即引起了学界的争议。高峰奇大升即由“理气浑沦”立场出发向李滉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书信往来。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为以心性论为中心的韩国性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郑之云则是在韩国哲学史上第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和七情的性理学者,其独特的问题意识直接促发了在东亚儒学史上别具一格的“四端七情理气”之发理论的诞生。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
李滉的“四端七情”论最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之特色。然其四七理论的成熟与完善离不开与奇大升之间展开的相互问难。在论辩过程中,不仅李滉的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而且其立场亦逐步得以明晰。
李滉将郑之云的《天命图说》加以改订之后,首先向他发难的便是奇大升。奇大升曰:“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③又曰:所谓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④。因而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待,谓之纯理或兼气则有些不妥。在奇大升看来,四端虽是纯粹的天理之所发,但只是发乎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于是,他言道: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也。①奇大升以为,四端与七情皆为情,不能将二者看作具有不同性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因此以理气来分而言,四端七情便有所不妥。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子学原旨。
对于奇大升的质疑,李滉回复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②
李滉承认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也承认先儒并未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与气以论其性质之不同。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因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由此,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理)、七情(气)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他在此一问题上的主要说法有:
“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①
“四端之发,纯善,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②
“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③
第一条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第二条是己末年其59岁(1559年)时的说法。此时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论辩。后经奇大升之诘难,李滉便有了第三条的说法。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提法,可视为李滉之最终定论。
李滉在此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源和来源上的差异。这源于他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李滉曰:
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④
由此可知,首先在心性情关系上,李滉倾向于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其次,他将心规定为“理气之合”。这与朱子的“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思想相比,心的含义以及心与理、气之关系变得更为清晰。同时,此说也为其分属理气的方式论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预设了理论前提。
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李滉晚年的思想结晶。作为《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该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为李滉所作。①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范畴。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这正是性理学的主题所在。性理学道德主体论的人性学说,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②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性为体,情为用。朱熹曰:“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③李滉则与朱熹不同。他进一步发挥朱子的理气心性说,将性情问题与理气之发结合起来,使朱学心性论深化为性情论的“理气四端七情”论。此图中的中图和下图是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④而解下图同样鞭辟入里:“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⑤
由此可见,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来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及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依程朱“性发为情”之原则,解读了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及无不善之情等。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可见李滉试图兼顾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这种双重文本及其双重权威所形成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即是引发韩儒各种学术争论的根源①,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抑或气发皆可以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或放而为恶是由理发未遂和气发不中所致。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现或气发而皆中节是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面引文中的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
而且,他还以七情与四端来分论人心与道心,曰:“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②这既是李滉对朱子心论的发展,也是二人心论之差异所在。虽然其中图不带气说,但他仍然以理气论性情。李滉有言:“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③可见,李滉仍以朱子的“理气心”来论性情,并侧重于持教工夫。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学之传统,李滉亦如此。他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亦是情,而“情”皆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攸关人性之善恶。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即缘于此。李滉说过:“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④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即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通过自家内省以求致中和。李滉去世前曾屡次修订此图。“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所载本也。”①可见,此图在《圣学十图》中所占有之地位何等之重要。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认为不仅“性”可以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他说:“故愚尝妄以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即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
“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接续朱子的理气心,但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故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他说:“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这样的理解,李滉明确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
他对七情的看法则始终落在气的一边。李滉说过:“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又不能无理,所以他坚持认为,“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他的答案是:“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以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
朱子哲学主张,人是由理和气共同构成的——气构成人之形体,理则为人之本性。李滉据此提出了“四端七情分理气”说,主张道德情感(四端)发自人的本性(理),而一般生理情感(七情)则发自人的形体(气)。其“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提法表明四端与七情的内在根源是不同的,这虽然与朱熹《中庸章句》的说法不同,却令朱子学性情论未解决的问题得到了一种解决。③这亦可以视为李滉对朱子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不过,依其理气之心,四端与七情不论善还是不善,或者说不论中节还是不中节,皆依“气”而定。他说:“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矣。”④实际上四端七情皆落在气的一边。理发未遂是掩于气,理发直遂是不掩于气——遂与不遂,俱在气一边。从另一方面说,气发不中则灭其理,气发中节则不灭其理——灭理与不灭理亦俱在气的一边。因“气”的状体直接影响“理”的显否以及如何显现,所以主敬以治心气必使气顺理而作、依理而行。此又是李滉以主敬治心的最重要原因。主敬以治心气,即为其著名的主敬论思想。李滉的学说,亦被称为“主敬”哲学。
三、李珥的“四端七情”论
继李滉、奇大升之后,众多学者都对四端七情问题发表了自家见解。李珥亦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他的说法,大都是针对李滉的见解而发。
在四七问题上,李珥与李滉的分歧较明显。李珥从其“气发理乘”的理气观出发,而主张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他曾说过:“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①又说:“四端犹性之言本然之性也,七情犹性之合理气而言也。气质之性实是本性之在气质者也,非二性。故七情实包四端,非二情也。”②栗谷认为七情可包四端,四端为善一边,七情是兼气质而言性之全,四端是剔出而言性之本。朱子谓:“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③理与气之关系亦是如此。李珥进而指出:“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既非二物,又非一物。”④他接着直承朱子理气动静之说,提出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器。他说:“理无形也,气有形也;理无为也,气有为也。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⑤从“理无为而气有为”之见解自然就会产生“气发理乘”之主张。此说亦可称为“气发一途”说,实为李珥理气论之中心思想。“气发理乘”说的主旨大意即是:“大抵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无先后,无离合,何谓互发也。”⑥李珥自注曰:“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接着他又对“气发理乘”之义解释道:“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⑦
依此见解,李珥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进行了批评。他说:“四端是七情之善一边也,七情是四端之总会也。一边安可与总会分两边相对乎?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意必有在。而今者未得其意,只守其说,分开拖引,则岂不至于辗转失真乎?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专言气云尔。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李滉因此而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①在李珥看来,“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无论四端还是七情,皆为气发理乘。因理气原无先后无离合,故不可谓理气互发。
他认为,若四端是理发,为善情;而七情为气发,亦可为善情——如此则人心便有二本。李珥意识到这一问题,明确指出:
退溪先生既以善归之四端,而又曰七者之情亦无有不善,若然则四端之外亦有善情也,此情从何而发哉?孟子举其大概,故只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而其他善情之为四端,则学者当反三而知之。人情安有不本于仁义礼智而为善情者乎?善情既有四端、而又于四端之外有善情,则是人心有二本也,其可乎?……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②
这里他又将“四七”之辨从性情论延伸至心论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四七”论的讨论范围和深度。李滉认为七情发于气,是气发而理乘之,故七情并非不善,然因是发于形气,不能保证其必为善,实际上可为善亦可为恶。如前文所说:“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李滉似不曾说七情亦无有不善,如上引李珥所说。但七情说有善情,总是可以说的,若是便是四端之外有善情。若由理发者方为纯善,则由气发者之七情中之善,又从何而发?若七情不由理发而亦可为善,则必有使其善之根据。于是生发四端者为一本,而生发七情之善者又是一本——这便是有二本了。
李珥要避免此二本之失,则四端和七情便不能是各有其本的异类之情——四端必须是七情中善的一类。他说:“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则兼四端……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①情只是一情,四端是就情之合理处说,而七情则是就全部之情而言。故四端纯是善的,而七情则兼善恶。李珥此说即表示理无活动性,唯有气才活动。情属气,故四端七情皆是气发。气之活动如能依理便是善情——四端不过是七情之善者。栗谷进而指出:
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决非二性。特就气质上单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合理气而命之曰气质之性耳。性既一则情岂二源乎!除是有二性,然后方有二情耳!若如退溪之说,则本然之性在东,气质之性在西,自东而出者谓道心,自西而出者谓人心,此岂理耶。②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思想出发,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转而支持奇大升的观点。他说:“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③一方面批评李滉未能真正理会朱子之本意,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论七情还是四端皆为气发理乘。
李珥对退溪之说的批评,遭到了成浑的辩难。于是,继“退、高之辩”之后,李珥和成浑之间又展开了第二次四七大论辩,将论争推向了高潮。成浑基本上赞同李滉的立场。他指出:“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④并向李珥提出质疑道:自己亦曾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存疑,但细心玩味朱子“人心道心之异,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之说后觉得李滉的互发说亦未尝不可。“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①,明显看出成浑较肯定“理气互发”说。
李珥同成浑数次交换书信,进行辩论。结果,使李珥的性理学立场更加明了。在李珥看来,对“四七”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他说:“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发矣。”②他进而举例说:“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③可见,他认为不仅四端与七情是气发理乘,而且天地之化亦是气发而理乘。
四、李滉与李珥“四端七情”论差异之分析
陈荣捷先生曾将“四端七情理气”之辨称为,比朱子与象山(陆九渊,1139—1193年)太极之辨或与同甫(陈亮,1143—1194年)的王霸之辨更超而上之的学术论辩。其历年之久,堪与我国明清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朱子晚年定论》之辨相比拟。④可见,这场四七辩论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理论意义。
如前所述,李滉与李珥虽然同尊朱子,却在体贴和阐发朱学方面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由此各自构筑了独特的性理哲学体系。
“四七”论是二人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二人分歧之产生源于他们对朱学的不同理解和多维解读。
对李滉、李珥的理论之差异可作如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在理气之发的问题上产生了歧义。二人从不同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的性理学思想。李滉倾向于理气之“不杂”义,李珥则侧重于理气之“不离”义,对朱子之说进行了不同的发挥。
朱子思想体系的基础在于其理气论,即建立在其理气不相杂,不相离的理气观之上。李滉在继承朱子理气论的基础上,着重于对理气之不杂的一面作了“理贵气贱”、“理尊无对”的解释。李滉之重视“不杂”义侧重理气为道器之分,如其所撰《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即强调理气之分别、道器之异。对于二者“不杂”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观的最大特色。
李滉主张“理贵气贱”,认为理具“主宰”义而气则无之。他说:“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①理“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②由主宰与被主宰的理气关系而形成二者的上下位观,即上者尊贵,下者卑贱,故理贵气贱。李滉指出:“理贵气贱,然理无为气有欲。”③由于气有欲,故须主敬以治之。而且,还对理本体作了“理(太极)自有动静”的解释。于是,在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便有了“理气互发”说。
退溪还提出“理纯善气兼善恶”之说。此说实亦直承伊川、朱子而来。气有清浊,而由气之清浊而言,气有或顺理或不顺理。主敬则必以理驭气,也就是说理为主以帅其气——理是纯善,而气兼善恶,纯善之理帅气则气必顺理而呈善。这便是其“理帅气卒”思想。李滉的理贵气贱、尊理贬气的观念,与理纯善而气兼善恶之说有着内在的思想关联。
理贵气贱、理气互发乃李滉理气观的主要内容。由于理无为而气有欲,故须主敬制气以显理。
他将朱熹的理气“先后”关系转化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由此为其“四七”论打下理论基础。
李珥的性理学说同样建立在其理气论的基石之上。不过,与李滉不同,他在继承朱子理气之说的过程中则侧重于理气之不离,从这个角度对朱子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发挥。理气之妙、气发理乘以及理通气局乃其学说之主旨。
李珥在理气定义及理气的发用义(动静义)上多有独到的议论,摘录如下:
“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①
“大抵有形有为而有动有静,气也。无形无为而在动在静者,理也。理虽无形无为,而气非理则无所本,故曰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②
“夫形而上者,自然之理也。形而下者,自然之气也。有是理则不得不有是气,有是气则不得不生万物。是气动则为阳,静则为阴。一动一静者气也,动之静之者理也。阴阳既分,二仪肇辟;二仪肇辟,万化乃生。其然者气也,其所以然者理也。”③
由此可见,李珥虽然也主张理是气的主宰者,但并未像李滉那样从伦理道德意义上尊崇“理”之地位。而且,他也不赞同理本体的发用性。在他看来,“理”是使万物生生不息的所以然者。这样的理是实有之理,亦即使气之生生变化成为可能的本体,此本体虽无形却实有。此实体恒随物(气)而在,与天理一般无二。依李珥见解,诚即是天理。因万物的生生不息,须由气来表现,气虽依理而行,却是气自身之变化而显形,而生成万物。理与气不相离,二者同等重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由此,李珥基于程明道的“道亦器,器亦道”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理气之妙”说。
李珥认为,在理气恒不相离的天地变化天道流行的过程上,动静的本身是气,而理只是主宰气,使气动静。即“一动一静者气也,动之静之者理也。”“一动一静”是“其然”,“动之静之”是“其所以然”。在此种意义上,理、气二概念,气是其然,理是其所以然。理、气二义,李珥承继朱子之说,建立在“其然,所以然”之义上。一动一静是其然,动之静之是其所以然。理气二者在其发用上亦是如此。李珥进而指出:“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①此即所谓“气发理乘”之说。李珥对此二十三字所言之内容,极为肯定自信。不但天地之化是如此,人心之发亦不外此,“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②。发之者是其然,所以发者是所以然,前者是表现者,后者是使表现者得以实现的主宰者。
一动一静者是气,动之静之者是理;理是主宰者,气是听命者。气的阴阳变化而生万物实际上皆是理之所为。所以李珥说“天以实理而有化育之功”。“实理”即是诚,“诚”作为本体亦是物之终始,故能有化育之功。李珥主“诚”之用意在于先立本体。
与李滉相比较,李珥虽然在理气说的理论突破上有所不及,但在准确地传承朱子的理气之说方面却更有过之。易言之李珥的理气观思想更能反映朱子理气论之特色。
其次,理气观上的理论差异,直接导致二人在心性论上的不同见解。
李滉将心定义为“理气合而为心”③,而李珥则将心理解为“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④。由此李珥否定天命、气质二性之说,而主张一性论(气质之性),进而提倡四端、七情亦是“非二情”。李珥有言:“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⑤他进而指出:“四端犹性之言本然之性也,七情犹性之合理气而言也。气质之性实是本性之在气质者也,非二性。故七情实包四端,非二情也。”⑥他认为七情不仅可以包括四端,而且还是兼气质而言的“性之全”。李滉则接受宋儒的二性理论,倾向人心道心也应以理气分而言之。
在性情的问题上,朱子学向主“情根于性,性发为情”。即,“性为体”(性是情的内在根据),“情为用”(情是性的外发表现)。故李滉和李珥的“理气互发”说或“气发理乘”说,都与其不同的心性结构相关联。
不论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还是李珥的“气发理乘”论,都为朱子学性情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
最后,李滉与李珥之所以对朱子学有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也与两人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在韩国儒学史上,李滉为学偏向自我人格的修养,而李珥则侧重于经世致用。故李滉之学亦称为退溪“圣学”,而李珥则开韩国实学理论之先河。李滉生活于韩国历史上“士祸”频发的年代,有名的四大“士祸”即发生于此一时期。此为其学术政治生涯历史背景。据年谱嘉靖二年癸未记载:“先生二十三岁,始游太学,时经己卯之祸,士习浮薄,见先生举止有法,人多笑之。所与相从者,惟金河西麟厚一人而已。”①从其“举止有法”可见为人之端重。李珥较李滉年少35岁,而他主要生活于韩国历史上的“党争”频仍之时期。在李珥生活之世,朝政士风皆每况愈下。“权奸甚误国之后,苛政日作,百弊俱积,民生之涂炭,未有甚于今日者也。”②“己卯诸贤,稍欲有为,而馋锋所触,血肉糜纷,继以乙巳士祸,惨于己卯。自是士林狼顾胁息,以苟活为幸,不敢以国事为言。而惟是权奸之辈,放心肆意。”③“党争”与“士祸”有较大的区别。“士祸”政治可视为李滉的“尊理”、“正伦”以及“主敬”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李珥所面临的社会状况是经历多次“士祸”之后,朝纲不振、民生困苦。故李珥论政为学立说都极重实功——所谓“政贵知时,事要务实”。反映在其思想上便是主张理气之不离、变化气质之性以及追求本然性与现实性的高度一致。此即栗谷主气论的思想特色。
概言之,“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的特色。李滉和李珥理论之所以有差异是因各自依傍的文本、所持的立场以及所处历史环境之不同。李滉论学基于体用之有别,李珥则基于体用之不离,或者说前者着眼于本体,后者则侧重于流行。李滉提出“理贵气贱”、“理气互发”之论,在理气四七问题上坚守了体用有别之立场。但“理发”之义则显然不合于朱熹的“理不活动”之义。李珥则提出“理气之妙”、“气发理乘”说,笃守了其体用不离之立场。
以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的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宋儒在把先秦儒学发展为宋代理学时并没有完全弥合二者间的差异,因此在论述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这些不同说法中所蕴含的问题或矛盾,在中国儒学史上没有展开讨论,而在韩国儒学的“四七理气”之辨、“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以及此后发生的“人物性同异”论辩中却得到深入展开。①由此可见,中韩两国性理学(朱子学)因所关注的核心话题、依傍之文本以及具体的人文语境之不同造成不同的理论性格和多元的发展路径。无疑,这既是韩国性理学的特色,亦是东亚朱子学的理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