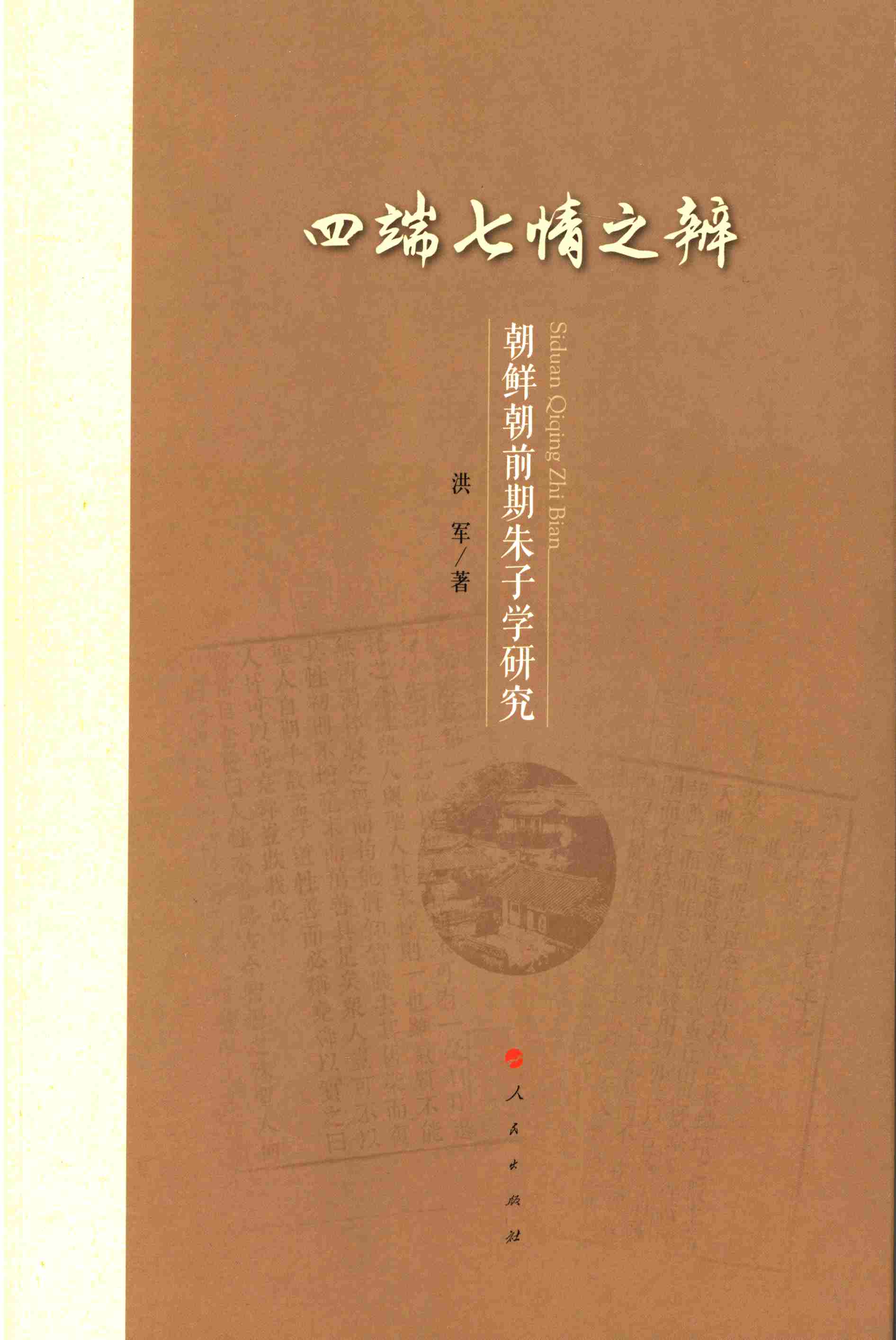内容
七情”论及其意义
“四端七情”之辨是在东亚儒学史上著名的哲学论辩,此说又与“人心道心”之辨、“主理主气”之争相联系,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高丽末开始传入到韩国的朱子学经由退溪李滉和栗谷李珥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在韩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以“主理”、“主气”为特征的岭南学派(退溪学派)和畿湖学派(栗谷学派)。二者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的两个不同发展方向。两派之间围绕“四端七情理气”之发、“四七人心道心”等问题而展开的论辩,使韩国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学说之探讨为中心的哲学轨道。
第一节 “四端七情”之辨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
——以李滉与李珥的理论差异为中心
韩国儒学以其独特品格在东亚儒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尤其是朝鲜朝(1392—1910年)性理学以其逻辑的精微性和性情的深刻性①被誉为东亚朱子学的奇葩。本节将通过最具代表性的李滉和李珥的四端七情理论之比较来探讨韩国性理学性情理论之特色。
一、四端七情论辩的发生及其理论渊源
“四端七情”之辨是韩国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论争。此论辩发生于朝鲜朝性理学最为兴盛的16世纪中叶。此时涌现出以李退溪、郑之云(1509—1561年)、奇大升(1527—1572年)、李栗谷、成浑(1535—1598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硕学名儒。这一性理学家群体的出现不仅使韩国性理学实现了理论的本土化,在对朱子性情学说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的思考深度方面甚至还超过了同时代的明代朱子学。①“理气四端七情”之辨的发生,主要是源于韩儒对儒家经典及朱学理论的不同理解和所持的强烈的问题意识。
《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②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被称为“四端”,代表人的四种伦理道德情感。“七情”则指,《礼记·礼运篇》所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③中的七种人的自然情感。或许因二者各自出现于不同的儒家经典,在中国四端与七情并未成为对举互言的一对哲学范畴。如以宋明儒者为例,二程(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好言四端,少言七情;阳明《传习录》虽屡言七情,然不与性对。朱子亦是谈论四端处较多,而言七情处甚少。④朱熹只是在与门生的问答中曾说过一句“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①。这是其在四端和七情问题上的最为完整的表述。此语仅见《朱子语类》,在朱子其他著作中再难找寻,而且朱子对这一句也并未进行具体的解释和阐发。朱熹在工夫上的基本立场是此心寂然不动未发时应先做涵养,待心气发而为情时则施以察识。但因气的发用较随意突然,加之气所具有的清浊粹驳之差异,其发用未必都能“中节”,即一切都合乎于一定的法度(道德原则)。故必须时时以理驭气,使其皆能发而中节。若依朱子的此一思路,应将“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理解为四端是依理而发出的情,而发者则为气——情既然属于气,在“理”上就不能言“发”。朱熹的这一句话在中国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却在16世纪的韩国性理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四端七情,理发气发”之大论辩。
在韩国哲学史上“理气四端七情”之辨的发生可追溯至与郑道传并称为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双璧的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他曾师从于丽末鲜初的大儒李穑(字颖叔,号牧隐,1328—1396年)和郑道传(字宗之,号三峰,1342—1398年)。权近出身文臣贵族家庭,曾祖父即是高丽朱子学的先驱权溥。其大作《五经浅见录》是一部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著作,而《入学图说》更是韩国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学思想的入门书,影响曾及于日本。
权氏与郑道传虽然都是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但在接受和研习朱子学方面却各有侧重。郑氏致力于对现有朱子学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并以之为据竭力批判佛教。而权近则更倾心于对朱子学理论的探究与阐发。仅就二人对韩国性理学的理论贡献而言,权氏显然大于郑氏。故权近被视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始祖。
权近以独尊儒术为基本前提对佛、道进行批判,并在批判的过程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理”的绝对权威——所谓“理为公共之道,其尊无对”①。他进而指出:“理为心气之本原,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②在此基础上,权近着重解释了五常、四端、七情等心性论方面的基本问题。其《入学图说》中首次提出的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开启韩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理论之先河。不仅如此,他的《入学图说》还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说类书籍,因此权近亦被视为韩国儒学“以图释说”理论传统的鼻祖。《入学图说》中的“天人心性分释之图”性条中写道:“昔唐韩子《原性》而本于《礼书》,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为性发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属乎性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当然之则。如其发而中节则《中庸》所谓达道之和,岂非性之发者哉!然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而得与四端并列于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见其发之有中节不中节者,使学者致察焉’。”③权近指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无异,皆属纯善;而发而不中节者必非为性之所发,则不能与四端并列。权近认为,四端可视为理之所发,而七情却并非如此,并以此区分了四端和七情。他的这一见解实乃百余年后,李滉、李珥等人进行的四七论辩之滥觞。其思想后来被李滉等人继承和发扬,在韩国哲学史上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权氏之学还远播日本,并在日本儒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理气四七”之辨发生的直接诱因则是李滉对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的《天命图》中“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的修订。
郑之云为朝鲜朝初期的大儒金安国(1478—1543年)、金正国(1485—1541年)兄弟的弟子。他世居高阳,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李滉对其十分推崇,曾赞曰:“君曾测海,我要窥藩,藉君伊始……君胡发端,弗极其致,使我伥伥,难禁老泪。”①
郑之云绘制的《天命图》是引发“理气四七”之辨的原始文本。起初李滉获此图后将图中的注释“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即,将郑氏文中的“于”改为“之”,经李滉修改的图被称为《天命新图》。李滉以为,郑氏之言对四七理气的分别太甚,极易引起纷争,所以他在语气上对之作了些改动。
李滉的这一订正,旋即引起了学界的争议。高峰奇大升即由“理气浑沦”立场出发向李滉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书信往来。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为以心性论为中心的韩国性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郑之云则是在韩国哲学史上第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和七情的性理学者,其独特的问题意识直接促发了在东亚儒学史上别具一格的“四端七情理气”之发理论的诞生。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
李滉的“四端七情”论最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之特色。然其四七理论的成熟与完善离不开与奇大升之间展开的相互问难。在论辩过程中,不仅李滉的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而且其立场亦逐步得以明晰。
李滉将郑之云的《天命图说》加以改订之后,首先向他发难的便是奇大升。奇大升曰:“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③又曰:所谓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④。因而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待,谓之纯理或兼气则有些不妥。在奇大升看来,四端虽是纯粹的天理之所发,但只是发乎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于是,他言道: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也。①奇大升以为,四端与七情皆为情,不能将二者看作具有不同性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因此以理气来分而言,四端七情便有所不妥。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子学原旨。
对于奇大升的质疑,李滉回复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②
李滉承认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也承认先儒并未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与气以论其性质之不同。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因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由此,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理)、七情(气)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他在此一问题上的主要说法有:
“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①
“四端之发,纯善,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②
“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③
第一条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第二条是己末年其59岁(1559年)时的说法。此时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论辩。后经奇大升之诘难,李滉便有了第三条的说法。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提法,可视为李滉之最终定论。
李滉在此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源和来源上的差异。这源于他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李滉曰:
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④
由此可知,首先在心性情关系上,李滉倾向于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其次,他将心规定为“理气之合”。这与朱子的“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思想相比,心的含义以及心与理、气之关系变得更为清晰。同时,此说也为其分属理气的方式论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预设了理论前提。
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李滉晚年的思想结晶。作为《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该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为李滉所作。①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范畴。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这正是性理学的主题所在。性理学道德主体论的人性学说,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②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性为体,情为用。朱熹曰:“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③李滉则与朱熹不同。他进一步发挥朱子的理气心性说,将性情问题与理气之发结合起来,使朱学心性论深化为性情论的“理气四端七情”论。此图中的中图和下图是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④而解下图同样鞭辟入里:“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⑤
由此可见,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来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及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依程朱“性发为情”之原则,解读了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及无不善之情等。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可见李滉试图兼顾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这种双重文本及其双重权威所形成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即是引发韩儒各种学术争论的根源①,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抑或气发皆可以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或放而为恶是由理发未遂和气发不中所致。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现或气发而皆中节是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面引文中的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
而且,他还以七情与四端来分论人心与道心,曰:“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②这既是李滉对朱子心论的发展,也是二人心论之差异所在。虽然其中图不带气说,但他仍然以理气论性情。李滉有言:“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③可见,李滉仍以朱子的“理气心”来论性情,并侧重于持教工夫。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学之传统,李滉亦如此。他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亦是情,而“情”皆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攸关人性之善恶。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即缘于此。李滉说过:“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④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即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通过自家内省以求致中和。李滉去世前曾屡次修订此图。“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所载本也。”①可见,此图在《圣学十图》中所占有之地位何等之重要。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认为不仅“性”可以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他说:“故愚尝妄以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即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
“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接续朱子的理气心,但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故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他说:“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这样的理解,李滉明确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
他对七情的看法则始终落在气的一边。李滉说过:“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又不能无理,所以他坚持认为,“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他的答案是:“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以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
朱子哲学主张,人是由理和气共同构成的——气构成人之形体,理则为人之本性。李滉据此提出了“四端七情分理气”说,主张道德情感(四端)发自人的本性(理),而一般生理情感(七情)则发自人的形体(气)。其“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提法表明四端与七情的内在根源是不同的,这虽然与朱熹《中庸章句》的说法不同,却令朱子学性情论未解决的问题得到了一种解决。③这亦可以视为李滉对朱子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不过,依其理气之心,四端与七情不论善还是不善,或者说不论中节还是不中节,皆依“气”而定。他说:“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矣。”④实际上四端七情皆落在气的一边。理发未遂是掩于气,理发直遂是不掩于气——遂与不遂,俱在气一边。从另一方面说,气发不中则灭其理,气发中节则不灭其理——灭理与不灭理亦俱在气的一边。因“气”的状体直接影响“理”的显否以及如何显现,所以主敬以治心气必使气顺理而作、依理而行。此又是李滉以主敬治心的最重要原因。主敬以治心气,即为其著名的主敬论思想。李滉的学说,亦被称为“主敬”哲学。
三、李珥的“四端七情”论
继李滉、奇大升之后,众多学者都对四端七情问题发表了自家见解。李珥亦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他的说法,大都是针对李滉的见解而发。
在四七问题上,李珥与李滉的分歧较明显。李珥从其“气发理乘”的理气观出发,而主张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他曾说过:“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①又说:“四端犹性之言本然之性也,七情犹性之合理气而言也。气质之性实是本性之在气质者也,非二性。故七情实包四端,非二情也。”②栗谷认为七情可包四端,四端为善一边,七情是兼气质而言性之全,四端是剔出而言性之本。朱子谓:“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③理与气之关系亦是如此。李珥进而指出:“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既非二物,又非一物。”④他接着直承朱子理气动静之说,提出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器。他说:“理无形也,气有形也;理无为也,气有为也。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⑤从“理无为而气有为”之见解自然就会产生“气发理乘”之主张。此说亦可称为“气发一途”说,实为李珥理气论之中心思想。“气发理乘”说的主旨大意即是:“大抵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无先后,无离合,何谓互发也。”⑥李珥自注曰:“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接着他又对“气发理乘”之义解释道:“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⑦
依此见解,李珥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进行了批评。他说:“四端是七情之善一边也,七情是四端之总会也。一边安可与总会分两边相对乎?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意必有在。而今者未得其意,只守其说,分开拖引,则岂不至于辗转失真乎?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专言气云尔。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李滉因此而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①在李珥看来,“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无论四端还是七情,皆为气发理乘。因理气原无先后无离合,故不可谓理气互发。
他认为,若四端是理发,为善情;而七情为气发,亦可为善情——如此则人心便有二本。李珥意识到这一问题,明确指出:
退溪先生既以善归之四端,而又曰七者之情亦无有不善,若然则四端之外亦有善情也,此情从何而发哉?孟子举其大概,故只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而其他善情之为四端,则学者当反三而知之。人情安有不本于仁义礼智而为善情者乎?善情既有四端、而又于四端之外有善情,则是人心有二本也,其可乎?……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②
这里他又将“四七”之辨从性情论延伸至心论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四七”论的讨论范围和深度。李滉认为七情发于气,是气发而理乘之,故七情并非不善,然因是发于形气,不能保证其必为善,实际上可为善亦可为恶。如前文所说:“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李滉似不曾说七情亦无有不善,如上引李珥所说。但七情说有善情,总是可以说的,若是便是四端之外有善情。若由理发者方为纯善,则由气发者之七情中之善,又从何而发?若七情不由理发而亦可为善,则必有使其善之根据。于是生发四端者为一本,而生发七情之善者又是一本——这便是有二本了。
李珥要避免此二本之失,则四端和七情便不能是各有其本的异类之情——四端必须是七情中善的一类。他说:“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则兼四端……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①情只是一情,四端是就情之合理处说,而七情则是就全部之情而言。故四端纯是善的,而七情则兼善恶。李珥此说即表示理无活动性,唯有气才活动。情属气,故四端七情皆是气发。气之活动如能依理便是善情——四端不过是七情之善者。栗谷进而指出:
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决非二性。特就气质上单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合理气而命之曰气质之性耳。性既一则情岂二源乎!除是有二性,然后方有二情耳!若如退溪之说,则本然之性在东,气质之性在西,自东而出者谓道心,自西而出者谓人心,此岂理耶。②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思想出发,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转而支持奇大升的观点。他说:“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③一方面批评李滉未能真正理会朱子之本意,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论七情还是四端皆为气发理乘。
李珥对退溪之说的批评,遭到了成浑的辩难。于是,继“退、高之辩”之后,李珥和成浑之间又展开了第二次四七大论辩,将论争推向了高潮。成浑基本上赞同李滉的立场。他指出:“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④并向李珥提出质疑道:自己亦曾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存疑,但细心玩味朱子“人心道心之异,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之说后觉得李滉的互发说亦未尝不可。“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①,明显看出成浑较肯定“理气互发”说。
李珥同成浑数次交换书信,进行辩论。结果,使李珥的性理学立场更加明了。在李珥看来,对“四七”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他说:“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发矣。”②他进而举例说:“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③可见,他认为不仅四端与七情是气发理乘,而且天地之化亦是气发而理乘。
四、李滉与李珥“四端七情”论差异之分析
陈荣捷先生曾将“四端七情理气”之辨称为,比朱子与象山(陆九渊,1139—1193年)太极之辨或与同甫(陈亮,1143—1194年)的王霸之辨更超而上之的学术论辩。其历年之久,堪与我国明清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朱子晚年定论》之辨相比拟。④可见,这场四七辩论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理论意义。
如前所述,李滉与李珥虽然同尊朱子,却在体贴和阐发朱学方面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由此各自构筑了独特的性理哲学体系。
“四七”论是二人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二人分歧之产生源于他们对朱学的不同理解和多维解读。
对李滉、李珥的理论之差异可作如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在理气之发的问题上产生了歧义。二人从不同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的性理学思想。李滉倾向于理气之“不杂”义,李珥则侧重于理气之“不离”义,对朱子之说进行了不同的发挥。
朱子思想体系的基础在于其理气论,即建立在其理气不相杂,不相离的理气观之上。李滉在继承朱子理气论的基础上,着重于对理气之不杂的一面作了“理贵气贱”、“理尊无对”的解释。李滉之重视“不杂”义侧重理气为道器之分,如其所撰《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即强调理气之分别、道器之异。对于二者“不杂”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观的最大特色。
李滉主张“理贵气贱”,认为理具“主宰”义而气则无之。他说:“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①理“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②由主宰与被主宰的理气关系而形成二者的上下位观,即上者尊贵,下者卑贱,故理贵气贱。李滉指出:“理贵气贱,然理无为气有欲。”③由于气有欲,故须主敬以治之。而且,还对理本体作了“理(太极)自有动静”的解释。于是,在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便有了“理气互发”说。
退溪还提出“理纯善气兼善恶”之说。此说实亦直承伊川、朱子而来。气有清浊,而由气之清浊而言,气有或顺理或不顺理。主敬则必以理驭气,也就是说理为主以帅其气——理是纯善,而气兼善恶,纯善之理帅气则气必顺理而呈善。这便是其“理帅气卒”思想。李滉的理贵气贱、尊理贬气的观念,与理纯善而气兼善恶之说有着内在的思想关联。
理贵气贱、理气互发乃李滉理气观的主要内容。由于理无为而气有欲,故须主敬制气以显理。
他将朱熹的理气“先后”关系转化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由此为其“四七”论打下理论基础。
李珥的性理学说同样建立在其理气论的基石之上。不过,与李滉不同,他在继承朱子理气之说的过程中则侧重于理气之不离,从这个角度对朱子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发挥。理气之妙、气发理乘以及理通气局乃其学说之主旨。
李珥在理气定义及理气的发用义(动静义)上多有独到的议论,摘录如下:
“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①
“大抵有形有为而有动有静,气也。无形无为而在动在静者,理也。理虽无形无为,而气非理则无所本,故曰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②
“夫形而上者,自然之理也。形而下者,自然之气也。有是理则不得不有是气,有是气则不得不生万物。是气动则为阳,静则为阴。一动一静者气也,动之静之者理也。阴阳既分,二仪肇辟;二仪肇辟,万化乃生。其然者气也,其所以然者理也。”③
由此可见,李珥虽然也主张理是气的主宰者,但并未像李滉那样从伦理道德意义上尊崇“理”之地位。而且,他也不赞同理本体的发用性。在他看来,“理”是使万物生生不息的所以然者。这样的理是实有之理,亦即使气之生生变化成为可能的本体,此本体虽无形却实有。此实体恒随物(气)而在,与天理一般无二。依李珥见解,诚即是天理。因万物的生生不息,须由气来表现,气虽依理而行,却是气自身之变化而显形,而生成万物。理与气不相离,二者同等重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由此,李珥基于程明道的“道亦器,器亦道”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理气之妙”说。
李珥认为,在理气恒不相离的天地变化天道流行的过程上,动静的本身是气,而理只是主宰气,使气动静。即“一动一静者气也,动之静之者理也。”“一动一静”是“其然”,“动之静之”是“其所以然”。在此种意义上,理、气二概念,气是其然,理是其所以然。理、气二义,李珥承继朱子之说,建立在“其然,所以然”之义上。一动一静是其然,动之静之是其所以然。理气二者在其发用上亦是如此。李珥进而指出:“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①此即所谓“气发理乘”之说。李珥对此二十三字所言之内容,极为肯定自信。不但天地之化是如此,人心之发亦不外此,“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②。发之者是其然,所以发者是所以然,前者是表现者,后者是使表现者得以实现的主宰者。
一动一静者是气,动之静之者是理;理是主宰者,气是听命者。气的阴阳变化而生万物实际上皆是理之所为。所以李珥说“天以实理而有化育之功”。“实理”即是诚,“诚”作为本体亦是物之终始,故能有化育之功。李珥主“诚”之用意在于先立本体。
与李滉相比较,李珥虽然在理气说的理论突破上有所不及,但在准确地传承朱子的理气之说方面却更有过之。易言之李珥的理气观思想更能反映朱子理气论之特色。
其次,理气观上的理论差异,直接导致二人在心性论上的不同见解。
李滉将心定义为“理气合而为心”③,而李珥则将心理解为“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④。由此李珥否定天命、气质二性之说,而主张一性论(气质之性),进而提倡四端、七情亦是“非二情”。李珥有言:“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⑤他进而指出:“四端犹性之言本然之性也,七情犹性之合理气而言也。气质之性实是本性之在气质者也,非二性。故七情实包四端,非二情也。”⑥他认为七情不仅可以包括四端,而且还是兼气质而言的“性之全”。李滉则接受宋儒的二性理论,倾向人心道心也应以理气分而言之。
在性情的问题上,朱子学向主“情根于性,性发为情”。即,“性为体”(性是情的内在根据),“情为用”(情是性的外发表现)。故李滉和李珥的“理气互发”说或“气发理乘”说,都与其不同的心性结构相关联。
不论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还是李珥的“气发理乘”论,都为朱子学性情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
最后,李滉与李珥之所以对朱子学有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也与两人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在韩国儒学史上,李滉为学偏向自我人格的修养,而李珥则侧重于经世致用。故李滉之学亦称为退溪“圣学”,而李珥则开韩国实学理论之先河。李滉生活于韩国历史上“士祸”频发的年代,有名的四大“士祸”即发生于此一时期。此为其学术政治生涯历史背景。据年谱嘉靖二年癸未记载:“先生二十三岁,始游太学,时经己卯之祸,士习浮薄,见先生举止有法,人多笑之。所与相从者,惟金河西麟厚一人而已。”①从其“举止有法”可见为人之端重。李珥较李滉年少35岁,而他主要生活于韩国历史上的“党争”频仍之时期。在李珥生活之世,朝政士风皆每况愈下。“权奸甚误国之后,苛政日作,百弊俱积,民生之涂炭,未有甚于今日者也。”②“己卯诸贤,稍欲有为,而馋锋所触,血肉糜纷,继以乙巳士祸,惨于己卯。自是士林狼顾胁息,以苟活为幸,不敢以国事为言。而惟是权奸之辈,放心肆意。”③“党争”与“士祸”有较大的区别。“士祸”政治可视为李滉的“尊理”、“正伦”以及“主敬”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李珥所面临的社会状况是经历多次“士祸”之后,朝纲不振、民生困苦。故李珥论政为学立说都极重实功——所谓“政贵知时,事要务实”。反映在其思想上便是主张理气之不离、变化气质之性以及追求本然性与现实性的高度一致。此即栗谷主气论的思想特色。
概言之,“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的特色。李滉和李珥理论之所以有差异是因各自依傍的文本、所持的立场以及所处历史环境之不同。李滉论学基于体用之有别,李珥则基于体用之不离,或者说前者着眼于本体,后者则侧重于流行。李滉提出“理贵气贱”、“理气互发”之论,在理气四七问题上坚守了体用有别之立场。但“理发”之义则显然不合于朱熹的“理不活动”之义。李珥则提出“理气之妙”、“气发理乘”说,笃守了其体用不离之立场。
以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的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宋儒在把先秦儒学发展为宋代理学时并没有完全弥合二者间的差异,因此在论述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这些不同说法中所蕴含的问题或矛盾,在中国儒学史上没有展开讨论,而在韩国儒学的“四七理气”之辨、“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以及此后发生的“人物性同异”论辩中却得到深入展开。①由此可见,中韩两国性理学(朱子学)因所关注的核心话题、依傍之文本以及具体的人文语境之不同造成不同的理论性格和多元的发展路径。无疑,这既是韩国性理学的特色,亦是东亚朱子学的理论特色。
第二节 “人心道心”之辨在东亚儒学史上的意义
——以朱子、罗钦顺、李珥的理论为中心
在东亚儒学史上,“人心道心”说随朱子学的传播而传入东亚各国,受到各国儒者的关注。尤其是,在韩国“人心道心”论与“四端七情”论相结合形成别具一格的心性论诠释系统。本节拟以朱子与16世纪中韩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罗钦顺、李珥的思想比较为中心,来探讨“人心道心”说在东亚地区的多元发展及其理论意义。
一、朱子的“人心道心”论及其理论意涵
人心、道心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宋儒“道统”之说的主要文献根据之一,朱子将此十六字称为“尧、舜、禹相传之密旨”①。此“十六字心传”的大意是说:人心险恶难测,道心幽微难显,唯有精一至诚,方保此心中正不偏。
对于此古圣先王相授受之心法密旨,二程对其中的人心道心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程颢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②表明,依明道之见人心与道心的关系即为人欲与天理之关系,而程颐则直接将二者关系解作私欲与正心的关系。小程子有言:“‘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③伊川以道心为正,人心为邪,所以特别强调施“精一”功夫以使道心不被人心所扰乱。进而他还主张存公灭私,明理灭欲,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④人道说受到二程的青睐,与其所含的思想意蕴密不可分。宋儒强调道德直觉和人格修养,为此提倡以道德意识主宰人的行为使之达于其宣扬的“以理节欲”之目的。人道说所涉的论域,如道德与情欲、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之间关系等正好满足了理学家的此一理论需求。同时,这也反映理学道德心性学说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但是,二程将人心与道心对立起来,将人心视作人欲、私欲,否定的人的自然需求和感性欲望的理论作解也使理学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亦重视“人心道心”论。他在继承二程的人道说的基础上,从心性论和知觉论的维度对其意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首先,朱子以为人只有一个心,若说道心是天理,人心是人欲,便有了两个心。曰:“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非有两个心。”⑤在朱子看来,心之所以有二名,只是因各自所知所觉者不同而已,其实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而且,还对二程将人心解为人欲的观点提出异议。
其次,自从“己丑之悟”之后,朱子便运用体用说对“心”作了全新解读。他以为“心”是体用之全体,不仅兼体用,而且贯动静。曰:“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无一毫私欲之间;其流行该遍,贯乎动静,而妙用又无不在焉。故以其未发而全体者言之,则性也;以其已发而妙用者言之,则情也。然‘心统性情’,只就浑沦一物之中,指其已发、未发而为言尔;非是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又是一个地头,如此悬隔也。”①认为,以心有体用而言,“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②;以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③,心是“贯彻上下,不可只于一处看”④。由此朱子的“心”既具道德心之意涵,又有知觉心之属性。故“心”在其哲学中地位极特殊,如其所言“惟心无对”⑤。
再次,朱子进一步运用心之体用说对人心、道心及其二者之关系展开了详细论述。曰: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⑥
此段引文可视为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晚年定论,此文写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其时朱子之思想已渐趋成熟。文中朱子对人道说的主要问题,作了纲要式的经典解说。一是从知觉论意义上,对人心、道心作了界定。他指出人心生于形气之私(觉于欲),而道心则原于性命之正(觉于理)。这就解答了二者皆发自一个心,何以有人道之分的问题。此一区分本身也反映了理学自身的价值诉求。二是指出不论上智之人抑或下愚之人皆有人心道心,在这方面人人皆平等。这一主张实则反映了人皆能成圣成贤的理学价值理想。三是对人心与人欲(私欲)作了区分。朱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合理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求。认为,“饥思食、寒思衣”等“人心”所包含的生存需求,圣人亦不能无。四是在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以道心来节制人心。值得注意的是,朱子虽然坚持人心与道心相分的理论,但倾向认为“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①二者的分别只是一个“交界”,彼此不因一方之存在而自行消失——问题是以何方为主导。朱子主张以道心(天理)宰制人心,即所谓“‘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乃善也”②。这可说是理学所一贯追求的价值目标。
由此可见,人道说虽与理欲论相对应,但不似理欲论那般紧张。而朱子对天理、人欲却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二者是不具共时性、共存性的两边相对之物。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着,学者需要于此体认省察之。”③朱子甚至指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④这表明,在他看来以天理战胜人欲这才是修学的重中之重。
概言之,朱子通过人心、道心说,对“心”的含义作了多维度阐发。尽管他的人道说所讨论的是心之“已发”层面问题,并非为“未发”之体,但是其理论仍然建立在体用关系之上,也可说是心之体用说的运用和心之知觉说的实现。⑤不过,在价值论层面上,朱子思想的总体倾向是重义轻利、贵理贱欲,故其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理论主张,如以存理遏欲来扩充道心及以“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等,可视为其义利观、理欲观在心性论上的具体体现。
二、罗钦顺的“人心道心”论
整庵罗钦顺被后人称为“宋学中坚”和“朱学后劲”,在明代他是能够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朱学阵营的标志性人物。而且,其代表作《困知记》问世后不久便传至朝鲜和日本,为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不过,朱熹的思想传至整庵,较之原来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变动。首先在理气论层面发生明显变化,呈现出由“理学”转向“气学”的理论动向。而且,主张去理的“实体化”,强调“理气为一物”等思潮为朱学心性论的新诠释提供了理论基础。
整庵在阐发其心性理气诸说时,对朱子的学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和补充。在理气论方面,他直接批评朱子的理气说“未归一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所谓‘理气二物,亦非判染为二’,未免有迁就之意。既有强有弱,难说不是判然。夫朱子百世之师,岂容立异?顾其言论间有未归一处,必须审求其是,乃为善学朱子,而有益于持循践履之实耳。”①他认为朱子是百世之师,之所以对其观点提出异议,主要是因其言论中有不一致之处。整庵以为向道者应矢志探求圣学中正确的东西,这样才算是善学朱子,且有益于持守与实践。于是,他以明道的道器论为依据提出自家的“理气一物”说。整庵有言:“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决也。明道尝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又曰:‘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窃详其意,盖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说个形而上下,则此理无自而明,非溺于空虚,即胶于形器,故曰‘须著如此说’。名虽有道器之别,然实非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至于‘原来只此是道’一语,则理气浑然,更无隙缝,虽欲二之,自不容于二之,正欲学者就形而下者之中,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则不是也……晦翁先生……谓‘是理不离气,亦不杂乎气’,乃其说之最精者。但质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良由将理气作二物看,是以或分或合,而终不能定于一也。”①他认为,朱子的理气论“终不能定于一”是因其始终将理气“作二物看”之故。依其之见,理须在气上认取,但是若把气认作理也是不对的——正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②。对此,他自信地说:“此言殆不可易哉!”③
整庵自谓心性理气诸说是其学问中的“大节目”④,而其心性之辨正是建立在“人心道心”之辨的基础上。
对于人心道心问题,整庵曾不无自豪声称:“人心道心之辨,仆于此用工最深,窃颇自信。”⑤又言道:“‘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后大本可得而立。’斯诚讲学第一义。”⑥可见,此论在整庵学说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重要。
在人心道心的问题上整庵亦对朱子提出质疑,指出其心性学说“未定于一”。曰:
“凡言心者皆是已发”,程子尝有是言,既自以为未当而改之矣。朱子文字,犹有用程子旧说未及改正处,如书传释人心道心,皆指为已发,中庸序中“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一语,亦皆已发之意。愚所谓“未定于一”者,此其一也。⑦
罗钦顺以为,若将人心、道心一概视作已发看“是为语用而遗体”⑧。整庵的这一指责,若从其所持之性情体用论立场看的确有其合理性。朱子本人在“中和旧说”中也使用过此一说法。但是,从“中和新说”之后对“心”的重新诠释以及对人道说所持的诠释立场来说,整庵的这一指责却有待商榷。由此可见,整庵与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不同的问题域以及诠释立场上的差异。罗钦顺的人道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整庵从寂感意义上的动静论视角对人心道心进行了界定。曰:“道心,‘寂然不动’者也,至精之体不可见,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危。”①那么,他所理解的“心”为何物呢?罗钦顺指出:“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②表明,对“心”与“性”整庵是有严格区分,而且他还主张学者为学应先明于“心性之别”。在他看来,孔子教人也无非是存心养性之事,然从未明说什么是心性,到了孟子才明言何为心性。他说:“虞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③由此亦可见,整庵对“心性之辨”重视程度,但是他也曾指出“心性至为难明”④。罗钦顺认为陆象山的错误正是未能分辨清楚心与性。而其“心性之辨”,正是通过“人心道心”之辨得到深入的诠释。
其次,整庵从动静之分、体用之别对人心道心作了理论诠释。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圣神之能事也。”⑤此段引文是整庵对人心道心问题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论述。罗钦顺同样主张心是一个,但是他以为之所以要从人心道心两方面来说是为了表明心的动静之分和体用之异。可见,整庵与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诠释立场和诠释视角有着较大差异。罗钦顺以为,以静来制动便是吉,动而不知返回本心便是凶。因此审察心之动机(“惟精”),保持人心之诚(“惟一”),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允执厥中”)。在他看来,这是“圣神之能事”亦即圣人之本领。
再次,整庵从性情论维度对人心道心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曰:“道心,性也;性者,道之体。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其体一而已矣,用则有千变万化之殊,然而莫非道也。此理甚明,此说从来不易。”①在此,整庵又将人心道心之辨转化为性情之辨——道心成了未发之体,人心则成了已发之用。对此一解,他极为自负。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仆于此煞曾下工夫体究来,直穷到无可穷处,方敢立论。万一未合,愿相与熟讲之,此处合则无往而不合矣。”②整庵问学之艰辛及学思之谨严于此可见。其“道心为性,人心为情”之说乃反复参验省察后所得的思想结晶。这既是其在心性之辨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也是其独特心性学说的立论基础。
明中叶后程朱理学日渐式微,陆王心学则日益隆盛。阳明所倡导的简易直截的“良知说”颇受士人追捧。而在整庵看来,陆王心学是阳儒而阴释,实与禅学无异。作为“朱学后劲”罗钦顺深以为忧,于是将阐明“心性之辨”,批驳心学的“良知说”作为论学的首要目标和作为卫道的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截流塞源,他还对《楞伽经》等佛教经典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对其辟佛功绩“东林八君子”之一的晚明大儒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1562—1626年,世称“景逸先生”)称赞道:“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③而他则把辟佛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儒佛之辨上。罗钦顺试图以心性之辨阐明儒佛之区别。罗氏论曰:“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盖虚灵知觉,心之妙也。精微纯一,性之真也。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④他进而指出:“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岂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见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别,彼则浑然无别矣,安得同!”⑤可见,依他之见儒佛之间最根本区别在于心性之辨上,亦可理解为在“人心道心”之辨上。佛家禅学的确在心性问题上只关注“心”,却未留意到儒家至为强调的“性”这一本体,故朱子评论说“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⑥。这是整庵“理气一物”论、“心性之辨”(“人心道心”之辨)等主张的思想史背景,学者于此不可不察。
简言之,主张“理气一物”,辨明“心性之别”是整庵之学说的理论旨要。而建立于“道心为体,人心为用”义理架构上的人心道心说则是其学问的核心纲领,整庵自谓:“拙《记》(指《困知记》——引者注)纲领只在此四字,请更详之。”①由上可见,整庵之所以重视“人心道心”之辨,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具体人文语境以及所要回应的时代话题都有密切关联。
由此可见,人心道心论的独到的理论价值和意义经由朱子之阐发才得到彰显,但未成为宋代理学的主要论题。此后,经整庵的发挥,人心道心才进入理学心性论的核心范畴之列。不过,人心道心论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还是离不开韩国儒者对之所作的创造性诠释。
三、李珥的“人心道心”论
整庵提出以“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的人道体用说之后,其主张并未受到明中叶士大夫们的积极回应和热议。但是,随着其著作《困知记》在朝鲜的流布,此说开始受到朝鲜儒者关注和重视,并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人心道心”之辨在朝鲜所激起的思想波澜,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东亚儒学史上所罕见。经过朝鲜儒者们富有创意的阐发,“人心道心”之辨才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哲学论题。
在朝鲜朝儒者的人道论中,与李滉并称为朝鲜朱子学双璧的栗谷李珥的人心道心论颇具代表性。李珥对与其同时代的整庵十分赞赏,曾称颂说:“罗整庵识见高明,近代杰然之儒也。有见于大本,而反疑朱子有二歧之见。此则虽不识朱子,而却于大本上有见矣。”②而且,他还将整庵同与其同时代的退溪李滉和花潭徐敬德作过比较,得出结论:“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③李滉和徐敬德,皆为韩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代儒学名宿,李珥对整庵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原因在于:一是其理气论与整庵较相近(二人皆取理气不离之立场);二是李珥认为整庵不仅对朱子学“有见于大本”,而且还多有“自得之味”(重视“自得之味”是二人学问之共同特点)。
不过在李珥看来,尽管整庵对朱学之“大本上有见”,但是整庵“以人心道心为体用,失其名义”,①使人感到惋惜。即便如此,李珥认为若衡之于与李滉“整庵之失在于名目上,退溪之失在于性理上,退溪之失重矣”②,他还说过整庵“虽失其名义,而却于大本上,未至甚错也”③。李珥也在接续朱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心道心”论。
首先,从强调心性理气诸说之间的一贯性立场对“人心道心”论作了解读。曰:“理气之说与人心道心之说,皆是一贯。若人心道心未透,则是与理气未透也。理气之不相离者若已灼见,则人心道心之无二原,可以推此而知之耳。”④可见,李珥的理气论是其人道说的立论根基,人道说是其理气论的直接生发。因理气之“不离”义是其理气论的主要思想倾向,故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他也以二者的不可分和相联结为其主旨,强调人心、道心的“无二原”性。这与朱子、整庵的人心、道心之相分思想是有所区别的。
其次,从主理、主气视角对人心、道心的含义作了阐发。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感动之际,欲居仁、欲由义……欲切偲于朋友,则如此之类谓之道心。感动者因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形气不为之掩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饥欲食、寒欲衣……四肢之欲安佚,则如此之类谓人心。其虽本于天性,而其发由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气,而目之以人心也。”①依李珥之见,因感动者是形气,故感动之际何方为主显得十分紧要。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主乎理”的是道心,出于耳目四肢之私而“主乎气”的则是人心。从主理、主气的角度探讨人心道心之含义,这一点颇能反映韩国儒学在讨论人间和存在的所以然根据这个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时,往往落实到性理层面上展开理气这个形上、形下问题的理论特性。②重视人间性理,是韩国儒学的根本特征。
再次,基于心之已发论,以知觉说的立场回答了“一心”何以有“二名”,即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分的问题。
在李珥的哲学中“心”属于气,故不管人心还是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规定使其人道说自然具有了知觉论的特色。他说:“心一也,岂有二乎?特以所主而发者有二名”③,又说:“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一心。其发也或以理义或为食色,故随其所发而异其名。”④“心”只有一个,这与朱子的主张相同。但是在“一心”何以有“二名”的问题上,李珥独特的心性论义理间架使其抱持与朱子不同的诠释立场。众所周知,朱子的学说以“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而李珥则以“理气之妙”、心性情意四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因此朱子的性情论可以“心统性情”说来概称,而李珥的性情论则似以“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说来指代更为恰当。最紧要的是二人对“意”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在朱子的性情论中,“意”和“情”都是从属于“心”的概念。“情”和“意”二者的关系是,大抵“情”为性之动,“意”为心之所发;“情”动是全体上论,“意”是就起一念处论。⑤因此在朱子心性论中,“意”的思量运用之含义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在李珥哲学中,“意”和“情”是两个有着明确界定的并列的哲学范畴,可视为心的两个不同境界。故其“人心道心”论是兼情意而言,如其曰:“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①,“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②需注意的是,“意”其实是在其人道说中起十分重要作用的范畴。这既是李珥与朱子性情论之区别,亦是其对朱子心性情意说的发展。相较而言,李珥的心性学说确实比朱子的理论更为细密和清晰。而且,强调“意”的商量计较作用是李珥知觉论最为显著的特点。
基于“意之商量计较”的意涵,李珥提出了极具特色的“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终始”说。他说: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③
不管根于性命之正的道心,还是源于形气的人心,皆属已发,此时气已用事。若欲不咈正理如实呈现,或知非制伏不从其欲,都要借“意”之计较、思虑、商量作用来实现。因此李珥认为,在人心之方寸之间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可变状态。在已发层面上,二者是并无固定的、严格的分别。因此,李珥为学极重“诚意”。在他看来,“情胜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④栗谷指出,若能保证“意”之“诚”,则所发之“心”皆能呈现为道心。
最后,李珥还援引“四七”论、理欲论,进一步阐释了人心道心之界说以及二者间的关系。
“四端七情”论是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的重要学说,人心道心论争的发生其实就是“四七”论由“情”论层面向“心”论层面的进一步推进,或者说“四七”论在心性领域的更深、更广意义上的展开。
在李珥哲学中,因“意”的商量计较作用,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相互转化之状态。这与其“四七”论中七情兼四端的情形有所不同,对此差异李珥指出:“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则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①他进而指出:“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矣,乌可强就而相准耶。”②在李珥哲学中的“情”不具商量计较之意,故性发为情之际,七情可以兼四端。因为依他之见,“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但是,人心、道心则已达比较而看的地步,已具对比之意,故不能兼有只能互为终始——这便是其“人心道心终始”说。
因为人心与道心是基于“意”之商量计较而存在的相对之物,李珥又由“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而提出“人心道心相对”说。他说:“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若七情则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谓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乌可分两边乎?”③
此论看似与其“人心道心终始”说矛盾,但这是李珥从天理人欲论角度对人道说的解读,可视为对“人心道心终始”说的另一种阐发。他曾说过:“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④可见,李珥对道心、人心、人欲是有明确的区分。他肯定人心亦有善,朱子所见略同。但是,人心之善与道心是否为同质之善呢?对此,李珥在《人心道心图说》中指出:“孟子就七情中别出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论者或以四端为道心,七情为人心,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七情岂可谓之人心乎?七情之外无他情,若偏指人心则是举其半而遗其半矣。”①可见,他将二者视为同质之善。在理欲论意义上,其人道说比朱子的人道说显得更为紧张和严峻,颇似“天理人欲相对”说。这也是二人“人心道心”之说的主要区别之一。同时,李珥还从理欲之辨角度,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作出自己的解释。
四、“人心道心”之辨在16世纪东亚思想界的多元发展
陈来先生曾指出:在历史上,与政治的东亚不同,从东亚文化圈的观点来看,朱子学及其重心有一个东移的过程。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在中国再没有产生有生命力的哲学家。虽然朱子学从明代到清代始终葆有正统学术的地位,而作为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在中国已经日趋没落。而与中国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刚好相反,朱子学在16世纪中期的韩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论思想深度还是学者人数皆粲然可观。16世纪朝鲜朝朱子学的兴起和发达,一方面表明了朝鲜性理学的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已经移到韩国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的生命,也为此后在东亚的进一步扩大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如果说退溪、高峰、栗谷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在16世纪已经转移到韩国,那么17世纪以后朝鲜后期实学兴起则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则进一步东移,朱子学在整个东亚实现了完全的覆盖。②诚如斯言,朱子学在东亚地区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朝鲜朝性理学的确起了非常重要之作用。像“四端七情理气”之辨、“主理主气”之争以及“四七人心道心”之辨等学术论争的相继发生,皆使朱子学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
由上述可知,人心道心作为朱子“心”论的核心范畴,与已发未发、体用及理欲等诸范畴相联系在理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说虽由二程始倡,但其独特理论价值与意义却由朱子之阐发才得到充分彰显。至16世纪,“人心道心”论经由整庵的发挥,不仅成为明代理学的主要论题,而且还进入理学心性论的核心范畴之列。但是,“人心道心”论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和核心概念,与韩国儒者富有创意的诠释与持续激辩分不开。
当罗整庵提出“道心为性,人心为情”主张时,在中国并未激起反响,但是却在朝鲜时代的性理学者中引起激烈的论辩。换言之,“人心道心”论成为一个主要的儒家哲学论题,乃由朱子开其端,整庵扬其流,朝鲜性理学者会其成。因而深入探讨朱子、整庵及李珥等中韩代表性的朱子学家的“人心道心”论,既可以看出整庵对朱子心性论的继承与修正以及朱子学心性论发展之脉络,也可以为理解朝鲜性理学提供一把钥匙,借以展现朱子学在东亚的多元发展面貌。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人心道心”之辨在东亚思想界展开的过程中相继呈现出多种理论范式。如朱子的基于知觉论和价值论面向的,“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以道心宰制人心的诠释范式;基于性情论和体用论面向的,整庵的“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的道心人心体用论诠释范式;基于理气论和“四七”论面向的,李珥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相对说诠释范式;等等。这一过程既是“人心道心”之辨义理不断得到丰富和彰显的过程,又是朱子学理论在东亚地区持续深化和多元发展的过程。这一朱子学不断“东亚化”的历史进程,最终使理学(朱子学)成为近世东亚世界里共通共享的学术文化。
“四端七情”之辨是在东亚儒学史上著名的哲学论辩,此说又与“人心道心”之辨、“主理主气”之争相联系,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高丽末开始传入到韩国的朱子学经由退溪李滉和栗谷李珥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在韩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以“主理”、“主气”为特征的岭南学派(退溪学派)和畿湖学派(栗谷学派)。二者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的两个不同发展方向。两派之间围绕“四端七情理气”之发、“四七人心道心”等问题而展开的论辩,使韩国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学说之探讨为中心的哲学轨道。
第一节 “四端七情”之辨在韩国儒学史上的意义
——以李滉与李珥的理论差异为中心
韩国儒学以其独特品格在东亚儒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尤其是朝鲜朝(1392—1910年)性理学以其逻辑的精微性和性情的深刻性①被誉为东亚朱子学的奇葩。本节将通过最具代表性的李滉和李珥的四端七情理论之比较来探讨韩国性理学性情理论之特色。
一、四端七情论辩的发生及其理论渊源
“四端七情”之辨是韩国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论争。此论辩发生于朝鲜朝性理学最为兴盛的16世纪中叶。此时涌现出以李退溪、郑之云(1509—1561年)、奇大升(1527—1572年)、李栗谷、成浑(1535—1598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硕学名儒。这一性理学家群体的出现不仅使韩国性理学实现了理论的本土化,在对朱子性情学说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的思考深度方面甚至还超过了同时代的明代朱子学。①“理气四端七情”之辨的发生,主要是源于韩儒对儒家经典及朱学理论的不同理解和所持的强烈的问题意识。
《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②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被称为“四端”,代表人的四种伦理道德情感。“七情”则指,《礼记·礼运篇》所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③中的七种人的自然情感。或许因二者各自出现于不同的儒家经典,在中国四端与七情并未成为对举互言的一对哲学范畴。如以宋明儒者为例,二程(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好言四端,少言七情;阳明《传习录》虽屡言七情,然不与性对。朱子亦是谈论四端处较多,而言七情处甚少。④朱熹只是在与门生的问答中曾说过一句“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①。这是其在四端和七情问题上的最为完整的表述。此语仅见《朱子语类》,在朱子其他著作中再难找寻,而且朱子对这一句也并未进行具体的解释和阐发。朱熹在工夫上的基本立场是此心寂然不动未发时应先做涵养,待心气发而为情时则施以察识。但因气的发用较随意突然,加之气所具有的清浊粹驳之差异,其发用未必都能“中节”,即一切都合乎于一定的法度(道德原则)。故必须时时以理驭气,使其皆能发而中节。若依朱子的此一思路,应将“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理解为四端是依理而发出的情,而发者则为气——情既然属于气,在“理”上就不能言“发”。朱熹的这一句话在中国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却在16世纪的韩国性理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四端七情,理发气发”之大论辩。
在韩国哲学史上“理气四端七情”之辨的发生可追溯至与郑道传并称为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双璧的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他曾师从于丽末鲜初的大儒李穑(字颖叔,号牧隐,1328—1396年)和郑道传(字宗之,号三峰,1342—1398年)。权近出身文臣贵族家庭,曾祖父即是高丽朱子学的先驱权溥。其大作《五经浅见录》是一部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著作,而《入学图说》更是韩国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学思想的入门书,影响曾及于日本。
权氏与郑道传虽然都是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但在接受和研习朱子学方面却各有侧重。郑氏致力于对现有朱子学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并以之为据竭力批判佛教。而权近则更倾心于对朱子学理论的探究与阐发。仅就二人对韩国性理学的理论贡献而言,权氏显然大于郑氏。故权近被视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始祖。
权近以独尊儒术为基本前提对佛、道进行批判,并在批判的过程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理”的绝对权威——所谓“理为公共之道,其尊无对”①。他进而指出:“理为心气之本原,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②在此基础上,权近着重解释了五常、四端、七情等心性论方面的基本问题。其《入学图说》中首次提出的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开启韩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理论之先河。不仅如此,他的《入学图说》还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说类书籍,因此权近亦被视为韩国儒学“以图释说”理论传统的鼻祖。《入学图说》中的“天人心性分释之图”性条中写道:“昔唐韩子《原性》而本于《礼书》,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为性发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属乎性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当然之则。如其发而中节则《中庸》所谓达道之和,岂非性之发者哉!然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而得与四端并列于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见其发之有中节不中节者,使学者致察焉’。”③权近指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无异,皆属纯善;而发而不中节者必非为性之所发,则不能与四端并列。权近认为,四端可视为理之所发,而七情却并非如此,并以此区分了四端和七情。他的这一见解实乃百余年后,李滉、李珥等人进行的四七论辩之滥觞。其思想后来被李滉等人继承和发扬,在韩国哲学史上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权氏之学还远播日本,并在日本儒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理气四七”之辨发生的直接诱因则是李滉对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的《天命图》中“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的修订。
郑之云为朝鲜朝初期的大儒金安国(1478—1543年)、金正国(1485—1541年)兄弟的弟子。他世居高阳,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李滉对其十分推崇,曾赞曰:“君曾测海,我要窥藩,藉君伊始……君胡发端,弗极其致,使我伥伥,难禁老泪。”①
郑之云绘制的《天命图》是引发“理气四七”之辨的原始文本。起初李滉获此图后将图中的注释“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即,将郑氏文中的“于”改为“之”,经李滉修改的图被称为《天命新图》。李滉以为,郑氏之言对四七理气的分别太甚,极易引起纷争,所以他在语气上对之作了些改动。
李滉的这一订正,旋即引起了学界的争议。高峰奇大升即由“理气浑沦”立场出发向李滉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书信往来。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为以心性论为中心的韩国性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郑之云则是在韩国哲学史上第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和七情的性理学者,其独特的问题意识直接促发了在东亚儒学史上别具一格的“四端七情理气”之发理论的诞生。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
李滉的“四端七情”论最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之特色。然其四七理论的成熟与完善离不开与奇大升之间展开的相互问难。在论辩过程中,不仅李滉的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而且其立场亦逐步得以明晰。
李滉将郑之云的《天命图说》加以改订之后,首先向他发难的便是奇大升。奇大升曰:“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③又曰:所谓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④。因而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待,谓之纯理或兼气则有些不妥。在奇大升看来,四端虽是纯粹的天理之所发,但只是发乎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于是,他言道: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也。①奇大升以为,四端与七情皆为情,不能将二者看作具有不同性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因此以理气来分而言,四端七情便有所不妥。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子学原旨。
对于奇大升的质疑,李滉回复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②
李滉承认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也承认先儒并未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与气以论其性质之不同。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因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由此,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理)、七情(气)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他在此一问题上的主要说法有:
“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①
“四端之发,纯善,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②
“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③
第一条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第二条是己末年其59岁(1559年)时的说法。此时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论辩。后经奇大升之诘难,李滉便有了第三条的说法。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提法,可视为李滉之最终定论。
李滉在此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源和来源上的差异。这源于他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李滉曰:
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④
由此可知,首先在心性情关系上,李滉倾向于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其次,他将心规定为“理气之合”。这与朱子的“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思想相比,心的含义以及心与理、气之关系变得更为清晰。同时,此说也为其分属理气的方式论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预设了理论前提。
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李滉晚年的思想结晶。作为《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该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为李滉所作。①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范畴。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这正是性理学的主题所在。性理学道德主体论的人性学说,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②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性为体,情为用。朱熹曰:“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③李滉则与朱熹不同。他进一步发挥朱子的理气心性说,将性情问题与理气之发结合起来,使朱学心性论深化为性情论的“理气四端七情”论。此图中的中图和下图是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④而解下图同样鞭辟入里:“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⑤
由此可见,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来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及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依程朱“性发为情”之原则,解读了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及无不善之情等。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可见李滉试图兼顾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这种双重文本及其双重权威所形成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即是引发韩儒各种学术争论的根源①,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抑或气发皆可以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或放而为恶是由理发未遂和气发不中所致。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现或气发而皆中节是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面引文中的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
而且,他还以七情与四端来分论人心与道心,曰:“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②这既是李滉对朱子心论的发展,也是二人心论之差异所在。虽然其中图不带气说,但他仍然以理气论性情。李滉有言:“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③可见,李滉仍以朱子的“理气心”来论性情,并侧重于持教工夫。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学之传统,李滉亦如此。他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亦是情,而“情”皆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攸关人性之善恶。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即缘于此。李滉说过:“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④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即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通过自家内省以求致中和。李滉去世前曾屡次修订此图。“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所载本也。”①可见,此图在《圣学十图》中所占有之地位何等之重要。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认为不仅“性”可以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他说:“故愚尝妄以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即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
“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接续朱子的理气心,但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故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他说:“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这样的理解,李滉明确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
他对七情的看法则始终落在气的一边。李滉说过:“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又不能无理,所以他坚持认为,“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他的答案是:“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以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
朱子哲学主张,人是由理和气共同构成的——气构成人之形体,理则为人之本性。李滉据此提出了“四端七情分理气”说,主张道德情感(四端)发自人的本性(理),而一般生理情感(七情)则发自人的形体(气)。其“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提法表明四端与七情的内在根源是不同的,这虽然与朱熹《中庸章句》的说法不同,却令朱子学性情论未解决的问题得到了一种解决。③这亦可以视为李滉对朱子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不过,依其理气之心,四端与七情不论善还是不善,或者说不论中节还是不中节,皆依“气”而定。他说:“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矣。”④实际上四端七情皆落在气的一边。理发未遂是掩于气,理发直遂是不掩于气——遂与不遂,俱在气一边。从另一方面说,气发不中则灭其理,气发中节则不灭其理——灭理与不灭理亦俱在气的一边。因“气”的状体直接影响“理”的显否以及如何显现,所以主敬以治心气必使气顺理而作、依理而行。此又是李滉以主敬治心的最重要原因。主敬以治心气,即为其著名的主敬论思想。李滉的学说,亦被称为“主敬”哲学。
三、李珥的“四端七情”论
继李滉、奇大升之后,众多学者都对四端七情问题发表了自家见解。李珥亦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他的说法,大都是针对李滉的见解而发。
在四七问题上,李珥与李滉的分歧较明显。李珥从其“气发理乘”的理气观出发,而主张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他曾说过:“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①又说:“四端犹性之言本然之性也,七情犹性之合理气而言也。气质之性实是本性之在气质者也,非二性。故七情实包四端,非二情也。”②栗谷认为七情可包四端,四端为善一边,七情是兼气质而言性之全,四端是剔出而言性之本。朱子谓:“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③理与气之关系亦是如此。李珥进而指出:“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既非二物,又非一物。”④他接着直承朱子理气动静之说,提出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器。他说:“理无形也,气有形也;理无为也,气有为也。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⑤从“理无为而气有为”之见解自然就会产生“气发理乘”之主张。此说亦可称为“气发一途”说,实为李珥理气论之中心思想。“气发理乘”说的主旨大意即是:“大抵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无先后,无离合,何谓互发也。”⑥李珥自注曰:“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接着他又对“气发理乘”之义解释道:“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⑦
依此见解,李珥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进行了批评。他说:“四端是七情之善一边也,七情是四端之总会也。一边安可与总会分两边相对乎?朱子发于理发于气之说,意必有在。而今者未得其意,只守其说,分开拖引,则岂不至于辗转失真乎?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专言气云尔。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李滉因此而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①在李珥看来,“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无论四端还是七情,皆为气发理乘。因理气原无先后无离合,故不可谓理气互发。
他认为,若四端是理发,为善情;而七情为气发,亦可为善情——如此则人心便有二本。李珥意识到这一问题,明确指出:
退溪先生既以善归之四端,而又曰七者之情亦无有不善,若然则四端之外亦有善情也,此情从何而发哉?孟子举其大概,故只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而其他善情之为四端,则学者当反三而知之。人情安有不本于仁义礼智而为善情者乎?善情既有四端、而又于四端之外有善情,则是人心有二本也,其可乎?……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②
这里他又将“四七”之辨从性情论延伸至心论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四七”论的讨论范围和深度。李滉认为七情发于气,是气发而理乘之,故七情并非不善,然因是发于形气,不能保证其必为善,实际上可为善亦可为恶。如前文所说:“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李滉似不曾说七情亦无有不善,如上引李珥所说。但七情说有善情,总是可以说的,若是便是四端之外有善情。若由理发者方为纯善,则由气发者之七情中之善,又从何而发?若七情不由理发而亦可为善,则必有使其善之根据。于是生发四端者为一本,而生发七情之善者又是一本——这便是有二本了。
李珥要避免此二本之失,则四端和七情便不能是各有其本的异类之情——四端必须是七情中善的一类。他说:“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则兼四端……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①情只是一情,四端是就情之合理处说,而七情则是就全部之情而言。故四端纯是善的,而七情则兼善恶。李珥此说即表示理无活动性,唯有气才活动。情属气,故四端七情皆是气发。气之活动如能依理便是善情——四端不过是七情之善者。栗谷进而指出:
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决非二性。特就气质上单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合理气而命之曰气质之性耳。性既一则情岂二源乎!除是有二性,然后方有二情耳!若如退溪之说,则本然之性在东,气质之性在西,自东而出者谓道心,自西而出者谓人心,此岂理耶。②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思想出发,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转而支持奇大升的观点。他说:“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③一方面批评李滉未能真正理会朱子之本意,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论七情还是四端皆为气发理乘。
李珥对退溪之说的批评,遭到了成浑的辩难。于是,继“退、高之辩”之后,李珥和成浑之间又展开了第二次四七大论辩,将论争推向了高潮。成浑基本上赞同李滉的立场。他指出:“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④并向李珥提出质疑道:自己亦曾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存疑,但细心玩味朱子“人心道心之异,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之说后觉得李滉的互发说亦未尝不可。“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①,明显看出成浑较肯定“理气互发”说。
李珥同成浑数次交换书信,进行辩论。结果,使李珥的性理学立场更加明了。在李珥看来,对“四七”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他说:“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发矣。”②他进而举例说:“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③可见,他认为不仅四端与七情是气发理乘,而且天地之化亦是气发而理乘。
四、李滉与李珥“四端七情”论差异之分析
陈荣捷先生曾将“四端七情理气”之辨称为,比朱子与象山(陆九渊,1139—1193年)太极之辨或与同甫(陈亮,1143—1194年)的王霸之辨更超而上之的学术论辩。其历年之久,堪与我国明清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朱子晚年定论》之辨相比拟。④可见,这场四七辩论在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理论意义。
如前所述,李滉与李珥虽然同尊朱子,却在体贴和阐发朱学方面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由此各自构筑了独特的性理哲学体系。
“四七”论是二人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二人分歧之产生源于他们对朱学的不同理解和多维解读。
对李滉、李珥的理论之差异可作如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在理气之发的问题上产生了歧义。二人从不同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的性理学思想。李滉倾向于理气之“不杂”义,李珥则侧重于理气之“不离”义,对朱子之说进行了不同的发挥。
朱子思想体系的基础在于其理气论,即建立在其理气不相杂,不相离的理气观之上。李滉在继承朱子理气论的基础上,着重于对理气之不杂的一面作了“理贵气贱”、“理尊无对”的解释。李滉之重视“不杂”义侧重理气为道器之分,如其所撰《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即强调理气之分别、道器之异。对于二者“不杂”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观的最大特色。
李滉主张“理贵气贱”,认为理具“主宰”义而气则无之。他说:“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于物”,①理“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本。”②由主宰与被主宰的理气关系而形成二者的上下位观,即上者尊贵,下者卑贱,故理贵气贱。李滉指出:“理贵气贱,然理无为气有欲。”③由于气有欲,故须主敬以治之。而且,还对理本体作了“理(太极)自有动静”的解释。于是,在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便有了“理气互发”说。
退溪还提出“理纯善气兼善恶”之说。此说实亦直承伊川、朱子而来。气有清浊,而由气之清浊而言,气有或顺理或不顺理。主敬则必以理驭气,也就是说理为主以帅其气——理是纯善,而气兼善恶,纯善之理帅气则气必顺理而呈善。这便是其“理帅气卒”思想。李滉的理贵气贱、尊理贬气的观念,与理纯善而气兼善恶之说有着内在的思想关联。
理贵气贱、理气互发乃李滉理气观的主要内容。由于理无为而气有欲,故须主敬制气以显理。
他将朱熹的理气“先后”关系转化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由此为其“四七”论打下理论基础。
李珥的性理学说同样建立在其理气论的基石之上。不过,与李滉不同,他在继承朱子理气之说的过程中则侧重于理气之不离,从这个角度对朱子学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发挥。理气之妙、气发理乘以及理通气局乃其学说之主旨。
李珥在理气定义及理气的发用义(动静义)上多有独到的议论,摘录如下:
“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①
“大抵有形有为而有动有静,气也。无形无为而在动在静者,理也。理虽无形无为,而气非理则无所本,故曰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②
“夫形而上者,自然之理也。形而下者,自然之气也。有是理则不得不有是气,有是气则不得不生万物。是气动则为阳,静则为阴。一动一静者气也,动之静之者理也。阴阳既分,二仪肇辟;二仪肇辟,万化乃生。其然者气也,其所以然者理也。”③
由此可见,李珥虽然也主张理是气的主宰者,但并未像李滉那样从伦理道德意义上尊崇“理”之地位。而且,他也不赞同理本体的发用性。在他看来,“理”是使万物生生不息的所以然者。这样的理是实有之理,亦即使气之生生变化成为可能的本体,此本体虽无形却实有。此实体恒随物(气)而在,与天理一般无二。依李珥见解,诚即是天理。因万物的生生不息,须由气来表现,气虽依理而行,却是气自身之变化而显形,而生成万物。理与气不相离,二者同等重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由此,李珥基于程明道的“道亦器,器亦道”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理气之妙”说。
李珥认为,在理气恒不相离的天地变化天道流行的过程上,动静的本身是气,而理只是主宰气,使气动静。即“一动一静者气也,动之静之者理也。”“一动一静”是“其然”,“动之静之”是“其所以然”。在此种意义上,理、气二概念,气是其然,理是其所以然。理、气二义,李珥承继朱子之说,建立在“其然,所以然”之义上。一动一静是其然,动之静之是其所以然。理气二者在其发用上亦是如此。李珥进而指出:“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①此即所谓“气发理乘”之说。李珥对此二十三字所言之内容,极为肯定自信。不但天地之化是如此,人心之发亦不外此,“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②。发之者是其然,所以发者是所以然,前者是表现者,后者是使表现者得以实现的主宰者。
一动一静者是气,动之静之者是理;理是主宰者,气是听命者。气的阴阳变化而生万物实际上皆是理之所为。所以李珥说“天以实理而有化育之功”。“实理”即是诚,“诚”作为本体亦是物之终始,故能有化育之功。李珥主“诚”之用意在于先立本体。
与李滉相比较,李珥虽然在理气说的理论突破上有所不及,但在准确地传承朱子的理气之说方面却更有过之。易言之李珥的理气观思想更能反映朱子理气论之特色。
其次,理气观上的理论差异,直接导致二人在心性论上的不同见解。
李滉将心定义为“理气合而为心”③,而李珥则将心理解为“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④。由此李珥否定天命、气质二性之说,而主张一性论(气质之性),进而提倡四端、七情亦是“非二情”。李珥有言:“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⑤他进而指出:“四端犹性之言本然之性也,七情犹性之合理气而言也。气质之性实是本性之在气质者也,非二性。故七情实包四端,非二情也。”⑥他认为七情不仅可以包括四端,而且还是兼气质而言的“性之全”。李滉则接受宋儒的二性理论,倾向人心道心也应以理气分而言之。
在性情的问题上,朱子学向主“情根于性,性发为情”。即,“性为体”(性是情的内在根据),“情为用”(情是性的外发表现)。故李滉和李珥的“理气互发”说或“气发理乘”说,都与其不同的心性结构相关联。
不论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还是李珥的“气发理乘”论,都为朱子学性情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
最后,李滉与李珥之所以对朱子学有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也与两人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在韩国儒学史上,李滉为学偏向自我人格的修养,而李珥则侧重于经世致用。故李滉之学亦称为退溪“圣学”,而李珥则开韩国实学理论之先河。李滉生活于韩国历史上“士祸”频发的年代,有名的四大“士祸”即发生于此一时期。此为其学术政治生涯历史背景。据年谱嘉靖二年癸未记载:“先生二十三岁,始游太学,时经己卯之祸,士习浮薄,见先生举止有法,人多笑之。所与相从者,惟金河西麟厚一人而已。”①从其“举止有法”可见为人之端重。李珥较李滉年少35岁,而他主要生活于韩国历史上的“党争”频仍之时期。在李珥生活之世,朝政士风皆每况愈下。“权奸甚误国之后,苛政日作,百弊俱积,民生之涂炭,未有甚于今日者也。”②“己卯诸贤,稍欲有为,而馋锋所触,血肉糜纷,继以乙巳士祸,惨于己卯。自是士林狼顾胁息,以苟活为幸,不敢以国事为言。而惟是权奸之辈,放心肆意。”③“党争”与“士祸”有较大的区别。“士祸”政治可视为李滉的“尊理”、“正伦”以及“主敬”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李珥所面临的社会状况是经历多次“士祸”之后,朝纲不振、民生困苦。故李珥论政为学立说都极重实功——所谓“政贵知时,事要务实”。反映在其思想上便是主张理气之不离、变化气质之性以及追求本然性与现实性的高度一致。此即栗谷主气论的思想特色。
概言之,“四端七情理气”之辨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的特色。李滉和李珥理论之所以有差异是因各自依傍的文本、所持的立场以及所处历史环境之不同。李滉论学基于体用之有别,李珥则基于体用之不离,或者说前者着眼于本体,后者则侧重于流行。李滉提出“理贵气贱”、“理气互发”之论,在理气四七问题上坚守了体用有别之立场。但“理发”之义则显然不合于朱熹的“理不活动”之义。李珥则提出“理气之妙”、“气发理乘”说,笃守了其体用不离之立场。
以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的先秦儒学与宋代理学在“性”与“情”以及“人物性同异”等问题上的差异,宋儒在把先秦儒学发展为宋代理学时并没有完全弥合二者间的差异,因此在论述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这些不同说法中所蕴含的问题或矛盾,在中国儒学史上没有展开讨论,而在韩国儒学的“四七理气”之辨、“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以及此后发生的“人物性同异”论辩中却得到深入展开。①由此可见,中韩两国性理学(朱子学)因所关注的核心话题、依傍之文本以及具体的人文语境之不同造成不同的理论性格和多元的发展路径。无疑,这既是韩国性理学的特色,亦是东亚朱子学的理论特色。
第二节 “人心道心”之辨在东亚儒学史上的意义
——以朱子、罗钦顺、李珥的理论为中心
在东亚儒学史上,“人心道心”说随朱子学的传播而传入东亚各国,受到各国儒者的关注。尤其是,在韩国“人心道心”论与“四端七情”论相结合形成别具一格的心性论诠释系统。本节拟以朱子与16世纪中韩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罗钦顺、李珥的思想比较为中心,来探讨“人心道心”说在东亚地区的多元发展及其理论意义。
一、朱子的“人心道心”论及其理论意涵
人心、道心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宋儒“道统”之说的主要文献根据之一,朱子将此十六字称为“尧、舜、禹相传之密旨”①。此“十六字心传”的大意是说:人心险恶难测,道心幽微难显,唯有精一至诚,方保此心中正不偏。
对于此古圣先王相授受之心法密旨,二程对其中的人心道心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程颢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②表明,依明道之见人心与道心的关系即为人欲与天理之关系,而程颐则直接将二者关系解作私欲与正心的关系。小程子有言:“‘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③伊川以道心为正,人心为邪,所以特别强调施“精一”功夫以使道心不被人心所扰乱。进而他还主张存公灭私,明理灭欲,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④人道说受到二程的青睐,与其所含的思想意蕴密不可分。宋儒强调道德直觉和人格修养,为此提倡以道德意识主宰人的行为使之达于其宣扬的“以理节欲”之目的。人道说所涉的论域,如道德与情欲、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之间关系等正好满足了理学家的此一理论需求。同时,这也反映理学道德心性学说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但是,二程将人心与道心对立起来,将人心视作人欲、私欲,否定的人的自然需求和感性欲望的理论作解也使理学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亦重视“人心道心”论。他在继承二程的人道说的基础上,从心性论和知觉论的维度对其意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首先,朱子以为人只有一个心,若说道心是天理,人心是人欲,便有了两个心。曰:“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非有两个心。”⑤在朱子看来,心之所以有二名,只是因各自所知所觉者不同而已,其实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而且,还对二程将人心解为人欲的观点提出异议。
其次,自从“己丑之悟”之后,朱子便运用体用说对“心”作了全新解读。他以为“心”是体用之全体,不仅兼体用,而且贯动静。曰:“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无一毫私欲之间;其流行该遍,贯乎动静,而妙用又无不在焉。故以其未发而全体者言之,则性也;以其已发而妙用者言之,则情也。然‘心统性情’,只就浑沦一物之中,指其已发、未发而为言尔;非是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又是一个地头,如此悬隔也。”①认为,以心有体用而言,“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②;以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③,心是“贯彻上下,不可只于一处看”④。由此朱子的“心”既具道德心之意涵,又有知觉心之属性。故“心”在其哲学中地位极特殊,如其所言“惟心无对”⑤。
再次,朱子进一步运用心之体用说对人心、道心及其二者之关系展开了详细论述。曰: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⑥
此段引文可视为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晚年定论,此文写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其时朱子之思想已渐趋成熟。文中朱子对人道说的主要问题,作了纲要式的经典解说。一是从知觉论意义上,对人心、道心作了界定。他指出人心生于形气之私(觉于欲),而道心则原于性命之正(觉于理)。这就解答了二者皆发自一个心,何以有人道之分的问题。此一区分本身也反映了理学自身的价值诉求。二是指出不论上智之人抑或下愚之人皆有人心道心,在这方面人人皆平等。这一主张实则反映了人皆能成圣成贤的理学价值理想。三是对人心与人欲(私欲)作了区分。朱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合理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求。认为,“饥思食、寒思衣”等“人心”所包含的生存需求,圣人亦不能无。四是在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以道心来节制人心。值得注意的是,朱子虽然坚持人心与道心相分的理论,但倾向认为“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①二者的分别只是一个“交界”,彼此不因一方之存在而自行消失——问题是以何方为主导。朱子主张以道心(天理)宰制人心,即所谓“‘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乃善也”②。这可说是理学所一贯追求的价值目标。
由此可见,人道说虽与理欲论相对应,但不似理欲论那般紧张。而朱子对天理、人欲却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二者是不具共时性、共存性的两边相对之物。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着,学者需要于此体认省察之。”③朱子甚至指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④这表明,在他看来以天理战胜人欲这才是修学的重中之重。
概言之,朱子通过人心、道心说,对“心”的含义作了多维度阐发。尽管他的人道说所讨论的是心之“已发”层面问题,并非为“未发”之体,但是其理论仍然建立在体用关系之上,也可说是心之体用说的运用和心之知觉说的实现。⑤不过,在价值论层面上,朱子思想的总体倾向是重义轻利、贵理贱欲,故其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理论主张,如以存理遏欲来扩充道心及以“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等,可视为其义利观、理欲观在心性论上的具体体现。
二、罗钦顺的“人心道心”论
整庵罗钦顺被后人称为“宋学中坚”和“朱学后劲”,在明代他是能够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朱学阵营的标志性人物。而且,其代表作《困知记》问世后不久便传至朝鲜和日本,为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不过,朱熹的思想传至整庵,较之原来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变动。首先在理气论层面发生明显变化,呈现出由“理学”转向“气学”的理论动向。而且,主张去理的“实体化”,强调“理气为一物”等思潮为朱学心性论的新诠释提供了理论基础。
整庵在阐发其心性理气诸说时,对朱子的学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和补充。在理气论方面,他直接批评朱子的理气说“未归一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所谓‘理气二物,亦非判染为二’,未免有迁就之意。既有强有弱,难说不是判然。夫朱子百世之师,岂容立异?顾其言论间有未归一处,必须审求其是,乃为善学朱子,而有益于持循践履之实耳。”①他认为朱子是百世之师,之所以对其观点提出异议,主要是因其言论中有不一致之处。整庵以为向道者应矢志探求圣学中正确的东西,这样才算是善学朱子,且有益于持守与实践。于是,他以明道的道器论为依据提出自家的“理气一物”说。整庵有言:“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决也。明道尝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又曰:‘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窃详其意,盖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说个形而上下,则此理无自而明,非溺于空虚,即胶于形器,故曰‘须著如此说’。名虽有道器之别,然实非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至于‘原来只此是道’一语,则理气浑然,更无隙缝,虽欲二之,自不容于二之,正欲学者就形而下者之中,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则不是也……晦翁先生……谓‘是理不离气,亦不杂乎气’,乃其说之最精者。但质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良由将理气作二物看,是以或分或合,而终不能定于一也。”①他认为,朱子的理气论“终不能定于一”是因其始终将理气“作二物看”之故。依其之见,理须在气上认取,但是若把气认作理也是不对的——正所谓“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②。对此,他自信地说:“此言殆不可易哉!”③
整庵自谓心性理气诸说是其学问中的“大节目”④,而其心性之辨正是建立在“人心道心”之辨的基础上。
对于人心道心问题,整庵曾不无自豪声称:“人心道心之辨,仆于此用工最深,窃颇自信。”⑤又言道:“‘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后大本可得而立。’斯诚讲学第一义。”⑥可见,此论在整庵学说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重要。
在人心道心的问题上整庵亦对朱子提出质疑,指出其心性学说“未定于一”。曰:
“凡言心者皆是已发”,程子尝有是言,既自以为未当而改之矣。朱子文字,犹有用程子旧说未及改正处,如书传释人心道心,皆指为已发,中庸序中“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一语,亦皆已发之意。愚所谓“未定于一”者,此其一也。⑦
罗钦顺以为,若将人心、道心一概视作已发看“是为语用而遗体”⑧。整庵的这一指责,若从其所持之性情体用论立场看的确有其合理性。朱子本人在“中和旧说”中也使用过此一说法。但是,从“中和新说”之后对“心”的重新诠释以及对人道说所持的诠释立场来说,整庵的这一指责却有待商榷。由此可见,整庵与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不同的问题域以及诠释立场上的差异。罗钦顺的人道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整庵从寂感意义上的动静论视角对人心道心进行了界定。曰:“道心,‘寂然不动’者也,至精之体不可见,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变之用不可测,故危。”①那么,他所理解的“心”为何物呢?罗钦顺指出:“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②表明,对“心”与“性”整庵是有严格区分,而且他还主张学者为学应先明于“心性之别”。在他看来,孔子教人也无非是存心养性之事,然从未明说什么是心性,到了孟子才明言何为心性。他说:“虞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语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曰:‘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矣。”③由此亦可见,整庵对“心性之辨”重视程度,但是他也曾指出“心性至为难明”④。罗钦顺认为陆象山的错误正是未能分辨清楚心与性。而其“心性之辨”,正是通过“人心道心”之辨得到深入的诠释。
其次,整庵从动静之分、体用之别对人心道心作了理论诠释。曰:“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惟精’,所以审其几也;‘惟一’,所以存其诚也。‘允执厥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圣神之能事也。”⑤此段引文是整庵对人心道心问题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论述。罗钦顺同样主张心是一个,但是他以为之所以要从人心道心两方面来说是为了表明心的动静之分和体用之异。可见,整庵与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诠释立场和诠释视角有着较大差异。罗钦顺以为,以静来制动便是吉,动而不知返回本心便是凶。因此审察心之动机(“惟精”),保持人心之诚(“惟一”),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允执厥中”)。在他看来,这是“圣神之能事”亦即圣人之本领。
再次,整庵从性情论维度对人心道心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曰:“道心,性也;性者,道之体。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其体一而已矣,用则有千变万化之殊,然而莫非道也。此理甚明,此说从来不易。”①在此,整庵又将人心道心之辨转化为性情之辨——道心成了未发之体,人心则成了已发之用。对此一解,他极为自负。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仆于此煞曾下工夫体究来,直穷到无可穷处,方敢立论。万一未合,愿相与熟讲之,此处合则无往而不合矣。”②整庵问学之艰辛及学思之谨严于此可见。其“道心为性,人心为情”之说乃反复参验省察后所得的思想结晶。这既是其在心性之辨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也是其独特心性学说的立论基础。
明中叶后程朱理学日渐式微,陆王心学则日益隆盛。阳明所倡导的简易直截的“良知说”颇受士人追捧。而在整庵看来,陆王心学是阳儒而阴释,实与禅学无异。作为“朱学后劲”罗钦顺深以为忧,于是将阐明“心性之辨”,批驳心学的“良知说”作为论学的首要目标和作为卫道的历史使命。为了更好地截流塞源,他还对《楞伽经》等佛教经典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对其辟佛功绩“东林八君子”之一的晚明大儒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1562—1626年,世称“景逸先生”)称赞道:“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③而他则把辟佛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儒佛之辨上。罗钦顺试图以心性之辨阐明儒佛之区别。罗氏论曰:“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盖虚灵知觉,心之妙也。精微纯一,性之真也。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④他进而指出:“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岂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见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别,彼则浑然无别矣,安得同!”⑤可见,依他之见儒佛之间最根本区别在于心性之辨上,亦可理解为在“人心道心”之辨上。佛家禅学的确在心性问题上只关注“心”,却未留意到儒家至为强调的“性”这一本体,故朱子评论说“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⑥。这是整庵“理气一物”论、“心性之辨”(“人心道心”之辨)等主张的思想史背景,学者于此不可不察。
简言之,主张“理气一物”,辨明“心性之别”是整庵之学说的理论旨要。而建立于“道心为体,人心为用”义理架构上的人心道心说则是其学问的核心纲领,整庵自谓:“拙《记》(指《困知记》——引者注)纲领只在此四字,请更详之。”①由上可见,整庵之所以重视“人心道心”之辨,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具体人文语境以及所要回应的时代话题都有密切关联。
由此可见,人心道心论的独到的理论价值和意义经由朱子之阐发才得到彰显,但未成为宋代理学的主要论题。此后,经整庵的发挥,人心道心才进入理学心性论的核心范畴之列。不过,人心道心论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还是离不开韩国儒者对之所作的创造性诠释。
三、李珥的“人心道心”论
整庵提出以“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的人道体用说之后,其主张并未受到明中叶士大夫们的积极回应和热议。但是,随着其著作《困知记》在朝鲜的流布,此说开始受到朝鲜儒者关注和重视,并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人心道心”之辨在朝鲜所激起的思想波澜,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东亚儒学史上所罕见。经过朝鲜儒者们富有创意的阐发,“人心道心”之辨才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哲学论题。
在朝鲜朝儒者的人道论中,与李滉并称为朝鲜朱子学双璧的栗谷李珥的人心道心论颇具代表性。李珥对与其同时代的整庵十分赞赏,曾称颂说:“罗整庵识见高明,近代杰然之儒也。有见于大本,而反疑朱子有二歧之见。此则虽不识朱子,而却于大本上有见矣。”②而且,他还将整庵同与其同时代的退溪李滉和花潭徐敬德作过比较,得出结论:“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③李滉和徐敬德,皆为韩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代儒学名宿,李珥对整庵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原因在于:一是其理气论与整庵较相近(二人皆取理气不离之立场);二是李珥认为整庵不仅对朱子学“有见于大本”,而且还多有“自得之味”(重视“自得之味”是二人学问之共同特点)。
不过在李珥看来,尽管整庵对朱学之“大本上有见”,但是整庵“以人心道心为体用,失其名义”,①使人感到惋惜。即便如此,李珥认为若衡之于与李滉“整庵之失在于名目上,退溪之失在于性理上,退溪之失重矣”②,他还说过整庵“虽失其名义,而却于大本上,未至甚错也”③。李珥也在接续朱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心道心”论。
首先,从强调心性理气诸说之间的一贯性立场对“人心道心”论作了解读。曰:“理气之说与人心道心之说,皆是一贯。若人心道心未透,则是与理气未透也。理气之不相离者若已灼见,则人心道心之无二原,可以推此而知之耳。”④可见,李珥的理气论是其人道说的立论根基,人道说是其理气论的直接生发。因理气之“不离”义是其理气论的主要思想倾向,故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他也以二者的不可分和相联结为其主旨,强调人心、道心的“无二原”性。这与朱子、整庵的人心、道心之相分思想是有所区别的。
其次,从主理、主气视角对人心、道心的含义作了阐发。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感动之际,欲居仁、欲由义……欲切偲于朋友,则如此之类谓之道心。感动者因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形气不为之掩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饥欲食、寒欲衣……四肢之欲安佚,则如此之类谓人心。其虽本于天性,而其发由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气,而目之以人心也。”①依李珥之见,因感动者是形气,故感动之际何方为主显得十分紧要。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主乎理”的是道心,出于耳目四肢之私而“主乎气”的则是人心。从主理、主气的角度探讨人心道心之含义,这一点颇能反映韩国儒学在讨论人间和存在的所以然根据这个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时,往往落实到性理层面上展开理气这个形上、形下问题的理论特性。②重视人间性理,是韩国儒学的根本特征。
再次,基于心之已发论,以知觉说的立场回答了“一心”何以有“二名”,即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分的问题。
在李珥的哲学中“心”属于气,故不管人心还是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规定使其人道说自然具有了知觉论的特色。他说:“心一也,岂有二乎?特以所主而发者有二名”③,又说:“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一心。其发也或以理义或为食色,故随其所发而异其名。”④“心”只有一个,这与朱子的主张相同。但是在“一心”何以有“二名”的问题上,李珥独特的心性论义理间架使其抱持与朱子不同的诠释立场。众所周知,朱子的学说以“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而李珥则以“理气之妙”、心性情意四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因此朱子的性情论可以“心统性情”说来概称,而李珥的性情论则似以“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说来指代更为恰当。最紧要的是二人对“意”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在朱子的性情论中,“意”和“情”都是从属于“心”的概念。“情”和“意”二者的关系是,大抵“情”为性之动,“意”为心之所发;“情”动是全体上论,“意”是就起一念处论。⑤因此在朱子心性论中,“意”的思量运用之含义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在李珥哲学中,“意”和“情”是两个有着明确界定的并列的哲学范畴,可视为心的两个不同境界。故其“人心道心”论是兼情意而言,如其曰:“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①,“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②需注意的是,“意”其实是在其人道说中起十分重要作用的范畴。这既是李珥与朱子性情论之区别,亦是其对朱子心性情意说的发展。相较而言,李珥的心性学说确实比朱子的理论更为细密和清晰。而且,强调“意”的商量计较作用是李珥知觉论最为显著的特点。
基于“意之商量计较”的意涵,李珥提出了极具特色的“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终始”说。他说: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③
不管根于性命之正的道心,还是源于形气的人心,皆属已发,此时气已用事。若欲不咈正理如实呈现,或知非制伏不从其欲,都要借“意”之计较、思虑、商量作用来实现。因此李珥认为,在人心之方寸之间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可变状态。在已发层面上,二者是并无固定的、严格的分别。因此,李珥为学极重“诚意”。在他看来,“情胜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④栗谷指出,若能保证“意”之“诚”,则所发之“心”皆能呈现为道心。
最后,李珥还援引“四七”论、理欲论,进一步阐释了人心道心之界说以及二者间的关系。
“四端七情”论是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的重要学说,人心道心论争的发生其实就是“四七”论由“情”论层面向“心”论层面的进一步推进,或者说“四七”论在心性领域的更深、更广意义上的展开。
在李珥哲学中,因“意”的商量计较作用,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相互转化之状态。这与其“四七”论中七情兼四端的情形有所不同,对此差异李珥指出:“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则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①他进而指出:“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矣,乌可强就而相准耶。”②在李珥哲学中的“情”不具商量计较之意,故性发为情之际,七情可以兼四端。因为依他之见,“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但是,人心、道心则已达比较而看的地步,已具对比之意,故不能兼有只能互为终始——这便是其“人心道心终始”说。
因为人心与道心是基于“意”之商量计较而存在的相对之物,李珥又由“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而提出“人心道心相对”说。他说:“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若七情则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谓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乌可分两边乎?”③
此论看似与其“人心道心终始”说矛盾,但这是李珥从天理人欲论角度对人道说的解读,可视为对“人心道心终始”说的另一种阐发。他曾说过:“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④可见,李珥对道心、人心、人欲是有明确的区分。他肯定人心亦有善,朱子所见略同。但是,人心之善与道心是否为同质之善呢?对此,李珥在《人心道心图说》中指出:“孟子就七情中别出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论者或以四端为道心,七情为人心,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七情岂可谓之人心乎?七情之外无他情,若偏指人心则是举其半而遗其半矣。”①可见,他将二者视为同质之善。在理欲论意义上,其人道说比朱子的人道说显得更为紧张和严峻,颇似“天理人欲相对”说。这也是二人“人心道心”之说的主要区别之一。同时,李珥还从理欲之辨角度,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作出自己的解释。
四、“人心道心”之辨在16世纪东亚思想界的多元发展
陈来先生曾指出:在历史上,与政治的东亚不同,从东亚文化圈的观点来看,朱子学及其重心有一个东移的过程。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在中国再没有产生有生命力的哲学家。虽然朱子学从明代到清代始终葆有正统学术的地位,而作为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在中国已经日趋没落。而与中国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刚好相反,朱子学在16世纪中期的韩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论思想深度还是学者人数皆粲然可观。16世纪朝鲜朝朱子学的兴起和发达,一方面表明了朝鲜性理学的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已经移到韩国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的生命,也为此后在东亚的进一步扩大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如果说退溪、高峰、栗谷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在16世纪已经转移到韩国,那么17世纪以后朝鲜后期实学兴起则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则进一步东移,朱子学在整个东亚实现了完全的覆盖。②诚如斯言,朱子学在东亚地区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朝鲜朝性理学的确起了非常重要之作用。像“四端七情理气”之辨、“主理主气”之争以及“四七人心道心”之辨等学术论争的相继发生,皆使朱子学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
由上述可知,人心道心作为朱子“心”论的核心范畴,与已发未发、体用及理欲等诸范畴相联系在理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说虽由二程始倡,但其独特理论价值与意义却由朱子之阐发才得到充分彰显。至16世纪,“人心道心”论经由整庵的发挥,不仅成为明代理学的主要论题,而且还进入理学心性论的核心范畴之列。但是,“人心道心”论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和核心概念,与韩国儒者富有创意的诠释与持续激辩分不开。
当罗整庵提出“道心为性,人心为情”主张时,在中国并未激起反响,但是却在朝鲜时代的性理学者中引起激烈的论辩。换言之,“人心道心”论成为一个主要的儒家哲学论题,乃由朱子开其端,整庵扬其流,朝鲜性理学者会其成。因而深入探讨朱子、整庵及李珥等中韩代表性的朱子学家的“人心道心”论,既可以看出整庵对朱子心性论的继承与修正以及朱子学心性论发展之脉络,也可以为理解朝鲜性理学提供一把钥匙,借以展现朱子学在东亚的多元发展面貌。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人心道心”之辨在东亚思想界展开的过程中相继呈现出多种理论范式。如朱子的基于知觉论和价值论面向的,“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以道心宰制人心的诠释范式;基于性情论和体用论面向的,整庵的“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的道心人心体用论诠释范式;基于理气论和“四七”论面向的,李珥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相对说诠释范式;等等。这一过程既是“人心道心”之辨义理不断得到丰富和彰显的过程,又是朱子学理论在东亚地区持续深化和多元发展的过程。这一朱子学不断“东亚化”的历史进程,最终使理学(朱子学)成为近世东亚世界里共通共享的学术文化。
附注
①参见张立文:《论韩国儒学的特点》,载《韩国研究论丛》(第十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8页。
①参见陈来:《中韩朱子学比较研究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2日。
②《孟子·公孙丑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8页。
③陈澔注:《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至于“七情”,宋明儒者还有另一种表述。即伊川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所云“喜怒哀乐爱恶欲”。(伊川曰:“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见《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77页。)伊川的这一说法来自《中庸》首章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一句,这与我国宋明儒者言性情诸说时特重《中庸》有关。韩儒亦重《四书》,但《中庸》并未成为韩国性理学家特别关注的对象。故将四七进行对别展开论辩时,早于伊川所言的,《礼运》篇的“七情”成为他们所引用的对象。如,栗谷在其《心性情图》中,亦采《礼运篇》之“七情”。由此也可以窥出,中韩儒者在诠释儒学概念范畴时所依傍之文本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导致中韩儒学思想的不同发展面向,而且还造成韩国儒学性情理论本身的复杂性。
④对于四七论辩未发生在中国的问题,陈荣捷先生指出:韩国理学家以四端与七情对论。我国理学家则否。二程虽屡言“七情”,然不与性对。只言本性至善,不言四端。两国传统如此,其故安在?朱子谓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显是以四端对七情,韩国四七之对,可谓溯源朱子。然程朱及以后理学家言情皆言《中庸》之喜怒哀乐而不言《礼记·礼运》之喜怒哀惧爱恶欲。朱子说四端处极多,说七情处甚少。予以四七之辩,不发生于我国理学,其故有二。一为性情问题,如已发、未发、中庸、中和等等,皆基于《中庸》首章而不基于《礼记》。《礼记》虽是《六经》之一,且《中庸》是其一篇。然此一篇,宋梁时代已特别受人注意。至朱子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又著《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与《中庸辑略》,《中庸》传统遂成理学一中坚。韩国无此传统,于是《中庸》之喜怒哀乐在韩不显,而《礼记》之七情占其前锋。我国另一传统为配合,汉代以来,八卦五行,均有所配。故理学家以元亨利贞配仁义礼智、春夏秋冬等等。七情则难于分配。陈先生还指出,朱子在《朱子语类》中关于四端七情的对话,只有两处。比韩国驳论早几百年,相去甚远。(参见陈荣捷:《朱子学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196页)陈先生此一论述,对于四七论辩发生的哲学史、思想史背景的认识颇有裨益。此处需注意的是,奇大升在与李滉的四七之辨中所言“七情”多为《中庸》之喜怒哀乐。而且,他还较重视《中庸》之“中节”说。
①《孟子三·公孙丑上之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3,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97页。
①权近:《心气理篇注》,《三峰集》卷10,首尔:三峰郑道传纪念事业会2009年版,第210页。
②权近:《心气理篇注》,《三峰集》卷10,首尔:三峰郑道传纪念事业会2009年版,第211页。
③权近:《天人心性分释之图》“性”条,《入学图说》,首尔:乙酉文化社1974年版,第150页。
①李滉:《祭亡友秋峦郑君之云文》,《退溪全书》(二)卷45,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8页。
②李滉:《天命图说》后叙·附图,《退溪全书》(二),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26页。
③奇大升:《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6页。
④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①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②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5—406页。
①李滉:《天命图说》后叙·附图,《退溪全书》(二),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26页。
②李滉:《与奇明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2页。
③李滉:《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4页。
④李滉:《答奇明彦·别纸》,《退溪全书》(一)卷18,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55—456页。
①在韩国儒学史上,主要论辩皆围绕“心”这一哲学范畴而展开。16世纪后半期的四七论辩、人心道心论辩、18世纪初叶的人物性同异论辩以及19世纪后半期的本心明德之主理主气论辩等,均是对“心”之发用及相关问题的辨析。这亦是韩国性理学的特色。
②参见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载《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32—243页;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③《张子之书一》,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13页。
④李滉:《心统性情图说》,《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⑤李滉:《心统性情图说》,《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①参见李明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②李滉:《答李宏仲问目》,《退溪全书》(二)卷3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26页。
③李滉:《心统性情图说》,《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④李滉:《第六心统性情图》,《进圣学十图札》,《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206页。
①李震相:《答宋康叟》,《寒洲集》卷14,《韩国文集丛刊》317,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332—333页。
②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6页。
③李滉:《后论》,《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22页。
④李滉:《改本》,《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19页。
⑤李滉:《改本》,《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19页。
⑥李滉:《改本》,《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19页。
①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6页。
②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6页。
③参见陈来:《韩国朱子学新论——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④李滉:《心统性情图说》,《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②李珥:《圣学辑要》二,《栗谷全书》(一)卷2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55页。
③《性理一·人物之性气质之性》,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7页上。
⑤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8—209页。
⑥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⑦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193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0—211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④成浑:《附问书》,《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3页。
①成浑:《附问书》,《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3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3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④参见陈荣捷:《朱子学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①李滉:《答李达李天机》,《书》,《退溪集》卷13,《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56页。
②李滉:《答奇明彦后论·别纸》,《书》,《退溪集》卷16,《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426页。
③李滉:《与朴泽之》,《书》,《退溪集》卷12,《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37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7页。
②李珥:《答安应休》,《栗谷全书》(一)卷12《书》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48页。
③李珥:《易数策》,《栗谷全书》(一)卷14《《杂著》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304—305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9页。
③李滉:《答奇明彦·别纸》,《退溪全书》(一)卷18,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55页。
④李珥:《人心道心图说》,《栗谷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82页。
⑤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⑥李珥:《圣学辑要》二,《栗谷全书》(一)卷2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55页。
①李滉:《退溪先生年谱》卷1,《退溪全书》(三)《附录》,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577页。
②李珥:《玉堂陈时弊疏》,《栗谷全书》(一)卷3《疏》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63页。
③李珥:《万言封事》,《栗谷全书》(一)卷5《疏》3,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97页。
①参见李存山:《中韩儒学的“性情之辨”与“人物性同异之辨”》,《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5期。
①朱熹:《朱子全书》(21),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6页。
②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6页。
③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6页。
④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2页。
⑤《尚书一·大禹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7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10页。
①《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4页。
②《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0页。
③《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6页。
④《程子之书一》,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39页。
⑤《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4页。
⑥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页。
①《尚书一·大禹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7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15页。
②《中庸一·章句序》,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2,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87页
③《学七·力行》,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4页。
④《学七·力行》,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5页。
⑤参见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①罗钦顺:《答林正郎贞孚》己亥秋,《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6页。
①罗钦顺:《答林次崖佥宪》壬寅冬,《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2—203页。
②罗钦顺:《困知记》续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9页。
③罗钦顺:《困知记》续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9页。
④罗钦顺:《答允恕弟》己丑夏,《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8页。
⑤罗钦顺:《答陈侍御国祥》丁酉春,《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9页。
⑥罗钦顺:《答陈侍御国祥》丁酉春,《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0页。
⑦罗钦顺:《困知记》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9页。
⑧罗钦顺:《答陈静斋都宪》丙申冬,《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5页。
①罗钦顺:《困知记》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
②罗钦顺:《困知记》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③罗钦顺:《困知记》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④罗钦顺:《困知记》卷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页。
⑤罗钦顺:《困知记》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
①罗钦顺:《答黄筠谿亚卿》,《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0页。
②罗钦顺:《答黄筠谿亚卿》,《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1页。
③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8),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
④罗钦顺:《困知记》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
⑤罗钦顺:《困知记》续卷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6页。
⑥《释氏》,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6,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15页。
①罗钦顺:《答林正郎贞孚》己亥秋,《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1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2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4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2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2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0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1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②参见张立文:《李退溪思想世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③李珥:《圣学辑要》二,《栗谷全书》(一)卷2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56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⑤参见陈淳:《北溪字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3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9页。
④李珥:《人心道心图说》,《栗谷全书》(一)卷14《说》,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82页。
①李珥:《人心道心图说》,《栗谷全书》(一)卷14《说》,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83页。
②参见陈来:《中韩朱子学比较研究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2日。
①参见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湾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