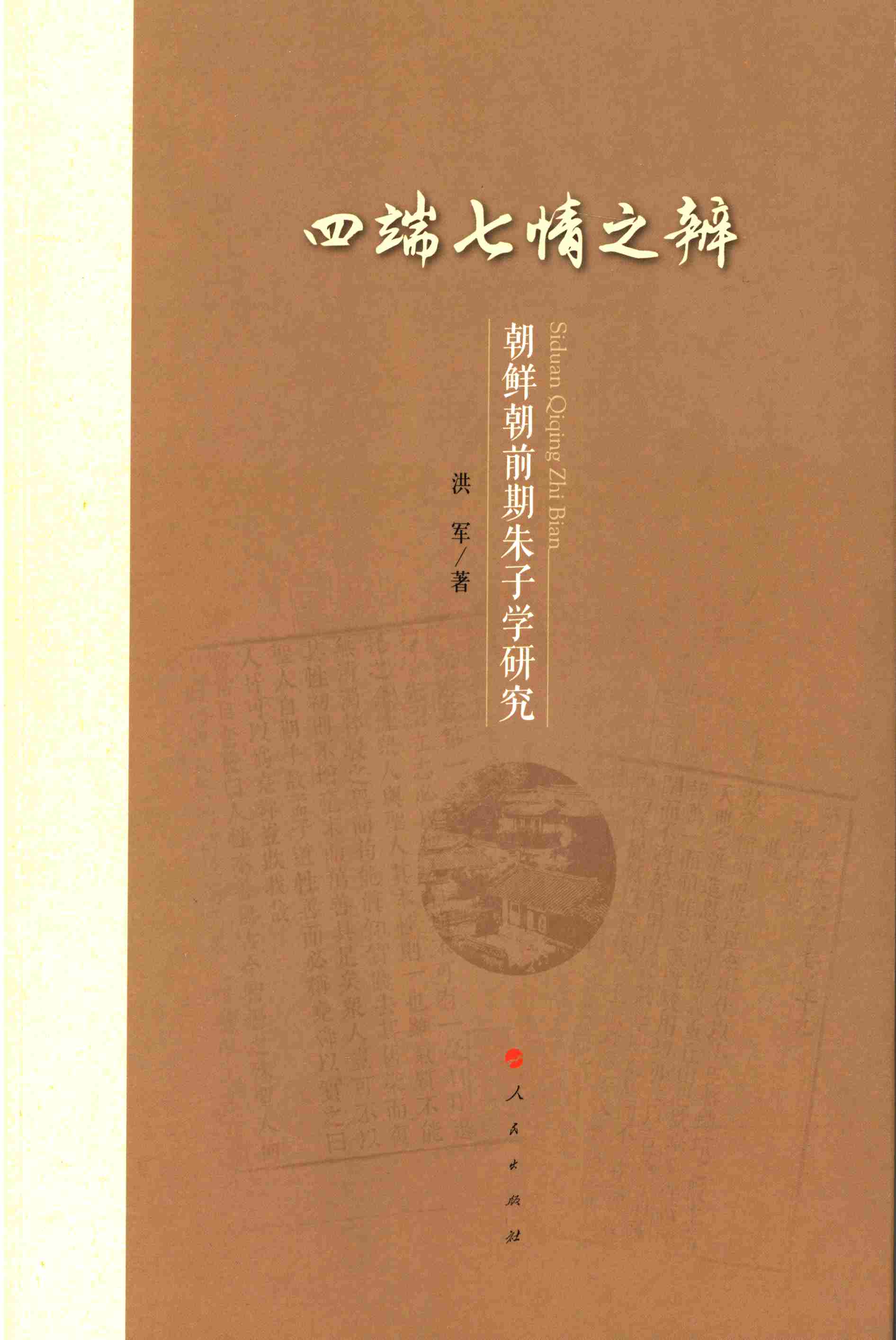内容
丁时翰(字君翊,号愚潭,1625—1707年)是朝鲜朝中期退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一生隐居,学行为后世儒者所敬仰,被称为“退溪之隔世高足”。实学开化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星湖李瀷(1681—1763年)在其《墓志铭》中写道:“瀷少而无所知识,不能叩匧从师于并世丁先生门为平生懊恨。”③朝鲜朝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1762—1836年)则评论说:“愚潭先生学术之正,议论之公,忠谠直截之风,明哲敛约之操,卓乎与山岳齐其高,烨乎与日月争其光。己巳为坤殿抗疏,仍救宋尤庵……其论理气四七之辨,一以紫阳退溪为准则,剖折精微,细入秋毫。夫道统之传,或以亲炙,或以私淑,唯德之宗,不观名位。盖自寒冈旅轩而降,真儒醇学,唯先生一人而已。义理之积于中,出处之标于世者,皆足以承嫡传于斯文。”①可见,其学说对后世之影响何等深远。
丁氏之学本于退溪李滉,因此学者亦称其心为“退陶之心”②。丁时翰曰:“退陶之学,绍述朱子,其所以集大成卫斯道者,亦与朱子略同。而朱子之后,儒学归禅。退陶之后,异言立帜。诗教之辨,传习录之跋,不得不出。四七之辨,壬午之录,又不得不著。”③丁时翰生活的年代,学界已分裂成以“主理”和“主气”④为理论特色的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作为近畿主理论学者⑤,丁时翰同李玄逸(字翼升,号葛庵,1627—1704年)一起对李滉的四七理论作了积极维护和系统阐述。⑥本节拟以李滉、李珥、丁时翰思想之比较为中心,来探讨其性理学思想之特点。
一、丁时翰的理气论
“理”与“气”是理学家为学立论的一对核心概念,因此理气问题亦可视为宋明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⑦而朱子则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讨论理学这一基本问题的哲学家。他以理气二分且又“不离不杂”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韩国性理学家们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的过程中,对理气问题①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丁时翰便曾说过:“理气之论,实是圣门极至之源头,而吾儒及异学于此焉分。”②不过,退溪、栗谷时期有关理气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理气动静和理气体用的问题而展开。丁时翰也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
李滉继承朱子“理气二分”说。他基于理气道器之分对二者“不杂”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以及“理尊无对”的观点。李滉重视理气“不杂”义的用意在于强调理对气的主宰作用。对二者“不杂”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观的特色。他曾在《非理气为一物辩证》③一文中写道:“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④进而他还认为,理与气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同,即“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他说:“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⑤、“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⑥。李滉的此一见解,既是对朱子“理先气后”、“理在事先”思想的修正,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进一步发展。他将朱熹的理气“先后”关系转变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由此为其“四七”论打下理论基础。
李珥则与李滉不同。他继承朱子理气之不离思想并对之作了进一步的解析和阐发。其“理气之妙”说、“气发理乘”说以及“理通气局”说皆独具特色。其中“理气之妙”说尤为栗谷思想之精髓——“气发理乘”说和“理通气局”说皆为“理气之妙”说的进一步阐发。
理气之“不离”亦是李珥哲学的主要理论特色。相较于李滉之“理”,李珥的“理气之妙”思想更是其哲学中“难见亦难说”处。李珥有言:“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夫理之源一而已矣,气之源亦一而已矣。气流行参差不齐,理亦流行而参差不齐。”①与李滉相比,他虽在理气说的理论突破上有所不及,却在传承朱子理气说上超而过之。
不过,到了17世纪李珥的这一思想倾向却受到李玄逸、丁时翰等南人学者的批评。丁时翰认为,古今学问道术之异皆源于人们对古圣贤所论之“理”的片面理解。在他看来,圣贤论“理”之言各有所指——有就“体”而言者,有就“用”而言者,有就其本原之理而言者,亦有就其散殊之理而言者。如果只讲“体”之寂然不动而不讲“用”之感而遂通,则徒见本原之理赋予万物而不见散殊之理各有其则,就会导致寂而不感终归于灭的后果。丁时翰继承李滉的“尊理”之思想,由此特别重视“理”之作为。“人之为学,只患于理字上见不透。若于此实见得的确,则处心行事,岂有未尽善乎。尧舜之精一执中,孔颜之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以理为主,而使人心听命焉。若以气为主而作用为性,则其祸必至于滔天。”②可见,在丁时翰的思理中只有“理”才具有“主宰”义,气则无之。他还特别强调了以气为主作用为性的严重后果。
作为主理论者,丁时翰每从维护李滉的角度对李珥之学展开批评:
今栗谷自谓有见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而推出整庵、花潭之绪余,以攻互发之说。故于人心道心,则以为皆源于理,而遂为相为终始之说,以反或原或生之意。于四端七情,则以为皆发于气,而遂为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之说,以反理发气发之意。至于理通气局,则又以为得见整庵、花潭之所未见,阐发前圣所不言之旨。而其所谓理通者,徒归寂灭虚无之地,未有安顿着落之处。而况其云所以发之理者,虽曰乘气,而每以徒具于寂然之中,不发于感通之际为言。其云理通者,虽曰无所不通,而又未免言理于窈冥,言气于粗浅,则是理是气,常隔断阻绝,不能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而终未见浑沦之中自有分开,分开之中自有浑沦之妙矣。盖其所谓理气不相离者,非真有见于理气之不相离也,只是认气为理。至以道心为本然之气,故终始迷昧于理字上。其言本原之体者,鹘囵笼罩,都没紧要,其言发见之用者,专主气字,更不言理。一向逞气骋辩,恣诋前贤,有若莠之乱苗,紫之乱朱,使从古圣贤相传之心法,既明复晦。①
李珥对整庵十分推崇②,他曾言:“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③依丁氏之见,李珥祖述整庵以“气”为重,故徒见理气之不离以及气常载理之一面。也因之无从体验浑沦之中自有分开,分开之中自有浑沦之妙。因此丁时翰批评李珥“昧于大本”。“栗谷则祖述整庵,昧于大本而所尚者气。故发于言论者,类多轻肆凌人底规模。而流弊所及,大为吾道之深害,大本之差不差,而其所发见于言行事为之间者,亦可征矣。”④而且,他还进一步批评李珥“论‘理’之言,亦似非吾儒家法”①。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丁氏继承李滉之“理帅气卒”的思想,进而发展出“理主气辅”论。“朱子‘虽在气中,理自理气自气,不相夹杂之谓性’云者,以其理气妙合之中,理常为主,气常为辅,虽在气中,不囿于气,命气而不命于气之云尔。非以为理气各在一处而不相妙合也。”②他在强调理之主宰性的同时,还对李滉的理气二分说作了有益的补充。指出虽说理为主而气为辅,理气各自不相夹杂。丁时翰特别强调了理气之不离性。
基于其“理主气辅”思想,丁氏提出自己独到的“理气体用”说。
理至有故无不异,至无故无不同,然无者未尝无,有者未尝有,则有无非有二也……理至无而至有云者,犹言无极而太极,或言自无极而为太极者。朱子辨释甚详。又于象山答书中云,不言无极,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由此观之,至无而至有不可云。至有故无不异,至无故无不同。其下两三句,虽合有无而言,不能救上句之病者,人所易知,而敬叔之不悟何哉?敬叔之见,既已如此,故以人物之性,谓有隐显体用,而以至有当显体用,以至无当隐体用。至有至无,分作隐显体用于一性之中,与分言无极太极者,何以异哉?③
“理主气辅”和“理气隐显体用”可以说是丁时翰理气论的主要内容。从以上比较可见,丁时翰理气论虽有重视二者不离性的一面,但是其主要学说仍以主理论为特色,并以此为基础对李滉的“尊理贬气”思想和“理气互发”之说进行了积极的补充和诠释。
二、丁时翰对李珥“四端七情”说的批判
如上一章所述,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基于理学的传统观念认为人都是得“气之正”者,但是由于每个人所禀之气有清浊、粹驳之不同会有“上智、中人、下愚三等之殊”①。于是,他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四端(理)与七情(气)之间的关系。李滉以为四端之情和七情是不同性质的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二者在根源和本质上皆不相同。李滉有言:“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②他认为此论与思孟程朱之旨冥然相契。
李珥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论,他更同情奇大升的观点。李珥对李滉之说的批评遭到了成浑的辩难。由二人之书信往复,李珥的“四七”论立场更加明了。依栗谷之见,对四七理气之发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发矣。”③李珥进而举例说“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④在李珥看来,不仅七情是气发理乘,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二者均为气发理乘。
针对李珥的“气发理乘”说,丁时翰提出如下批评:
理气为物,本混融无间,推之于前,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不见其终之离。而理无眹气有迹,安有无气之理或先或后,发见于事为之间者乎。然而终古圣贤于浑融无间,不可分先后,离合之中,或截而言之,或分而言之,以明此理之命气而不命于气,在气而不杂乎气者……既曰仁之端义之端,则仁发而为恻隐,义发而为羞恶,体用不离,本末相连,可见其不杂于气而一出于理。至于七情,则虽亦出于性而初无不善,但就其性在气质,浑沦理气者而为言。故几有善恶,气易用事,理难直遂,必须观理约气,然后理始显而气听命。此朱子所以有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之言。而今者(指栗谷——引者注)不察孟子剔发言理,朱子分言理气之本意,乃以四端七情滚合为一说,概而言之曰,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专以气发一途为言,而都遗却理发一款。①
依其之见,理无形而气有形,故其作用流行皆若气之所为。但因“理”至无而至有、至虚而至实,且又具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之特性,故其乘气流行皆为自然而然,不见其有所作为。当性情寂感之际,理之神用即蔼然呈露而不可掩——四端粹然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性即为显例。因此,不能仅着眼于理气之浑沦而只言“气发”不讲“理发”。
丁时翰认为,四端与七情从结构而言皆兼备了理和气。因此,四端与七情均与气相关。只是四端并不与气相互夹杂,而七情却受其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主理和主气方得区别。以此为基础,他推导出四端和七情在“所从来”处即相异的结论。这里丁时翰所持的是李滉的观点。在丁氏看来,四端与七情皆本于仁、义、礼、智之性。可见,丁时翰所言“所从来”与奇大升、李珥所谓“源头发端处”或“本源”有所不同——他虽未明言,从其语句中推断出此点。丁时翰以为人心虽无二源,但是其发现于外者可以主理、主气而言。由此可知,其“所从来”并非是“本”。丁氏更侧重于由“本”发用于外的过程,每以此指代他所描述的“就一心之中,方其萌动之开始”的时刻。此刻必是“性”与“气质”相互发生关系的时刻。于是,与气质发生何种的关系遂成区分四端和七情的关键。与“气”相关但不杂于“气”的情为四端;与气相关且在气的驱动下易流于恶的情则为七情。②据此,丁时翰对李滉之说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退溪《四七辨》云:“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栗谷所谓“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者,似本于此。而第退溪之以四端为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者,所指而言者,以其出于性之粹然在中,不杂乎形气者而为言。初不言无感而自发也。以七情为外物之触其形而动于中者所指而言者,以其出于性在气质,易感形气者而为言,亦非谓中无是理也。是以退溪旋以为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且谓“虽滉亦非谓七情不干于理,外物偶相凑着而感动”,且谓“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其本意所在,若是明白;而今者推出退溪所未有之意,说出退溪所未说之言,或以为做出许多葛藤,或以为正见之一累,已极轻肆,而终以无父而孝发,无君而忠发,不见孺子之入井而自发恻隐为心病等语,铺张抑勒,至此之极。岂其未曾虚心翫绎于退溪之说。而略绰看过胡乱说道者耶。①
这段话本是丁时翰为李滉之说所做的辩解。但从上下文以及李滉与奇大升辩论的全过程来看,李滉所言“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一语似有不妥。若谓此话代表李滉之真正立场,则其与奇大升之往复辩论便失去焦点。而丁时翰引这一句等于是否定四端是“无感而自发”。这无疑是其向李珥立场靠近,而承认四端与七情的同构型。②丁氏本人可能未意识到他的这一辩解与其初衷的自相矛盾处,学者于此则不可不察。
总之,丁时翰“四端七情”论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对李滉与李珥“四七理气”说之异同的详尽论述。丁时翰在批驳李珥“气发理乘”说的同时,对其部分见解亦有容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倾向。不过,尽管他在理气关系及四七理论的解释上有折中二李之痕迹,其思想之主旨还是反映了主理论学者的为学性格。
三、丁时翰的“人心道心”论
在韩国儒学史上由李珥与成浑推动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是继“四端七情理气”之辨之后发生的又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学术论争。
在论辩之初,成浑基于李滉“理气互发”之论提出理发即为“道心”而气发则为“人心”。“近日读朱子人心道心之说,有或生、或原之论,似与退溪之意合,故慨然以为在虞舜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理气互发之说,则退翁之见不易论也”①。所谓“或生”与“或原”,盖指朱熹所说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言。道心原于性命之正,纯善无恶;人心生于形气之私,故有善有恶。又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云。究此议论以理气之发,当初皆无不善,而气之不中乃流于恶云矣。”②因此成浑认为李滉的人心道心之说亦自不为过。
李珥同样援引朱子说法以增强说服力。他认为,朱子既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则何从而得此理气互发之说乎?在李珥看来,理气无先后离合不可谓之互发,但人心道心可以从两边来说。其《人心道心图说》有云:“道心虽不离乎气,而其发也为道义,故属之性命;人心虽亦本乎理,而其发也为口体,故属之形气。方寸之中,初无二心,只于发处有此二端。”③李珥在《答成浩原》的最后一书中指出:“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则心是气也,或原或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乎?”④可见,李珥对人心道心的说法亦承朱子之意而为言,且又时时不忘与其“气发理乘一途”之说相联系。其思想的系统性、逻辑性于此可见一斑。
李珥进而发挥朱子之说,提出自己独到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此论乃李珥对人心道心问题的基本看法。
丁时翰对于李珥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评论道:
窃详栗谷之意,概未见人心道心分言之脉络,以朱子或原或生之,为不得已之论而不之信,故每以人心道心滚合为一说。以为同出于本然之性,而以掩乎形气者,谓之人心;以不掩乎形气者,谓之道心。此非虞舜命名,朱子注释之本意也。夫上智不能无人心,则上智之人心,初不掩于形气,而以其从形气而生,故名之以人心。下愚不能无道心,则下愚之道心,虽发于气禀所拘之中,而以其本体之明有未尝息者,故名之以道心。初非以形气之掩与不掩,分言人心道心也。此是圣贤各指其所从来,使人审几用工之旨诀。而栗谷则舍而不取,既不欲相对说下。如朱子之言,而又不欲显言体用二字,以避宗主整庵之嫌。于是乎自作定论,辄以相为终始者言之。而其于道心上,言存养而不言审几。人心则直以为形气所掩而审其过不及云者,果有异于整庵体用之论乎?①
在丁时翰看来,李珥之说不过是祖述整庵学说而已,故而直言其人道说亦无异于整庵之道心人心体用论。他尖锐指出:“虽以浑沦者言之,只可言一心之中,从形气之人心,不离于性命,原性命之道心,不外于形气而已。若谓之人心道心相为终始云尔,则殊非人心道心之所以得名者也。”②依丁时翰之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仁义礼智之性蔼然流行于形气之间;人心生于形气,而视听言动之勿论非礼者乃所以听命于道心。
对于李珥“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源则只是一心”的观点,丁时翰批驳道:
所谓“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源则只是一心;其发也,或为理义,或为食色,故随其发而异其名”云者,初不外于退溪之说矣。既谓之“随其发而异其名”,则岂不可谓理发、气发乎?退溪所谓理气互发者,概以为理与气合而为心,理气混然一心之中,随所感而发,或有理发之时,或有气发之时,互相发现云尔。其言“互发”二字者,益明此心之无二本矣。今乃不察理到之言,而一向挥斥;至其何从得此之说,则又若初不知出于退溪之说者然,显有抑扬凌驾之意。此等气像,似非吾儒法门矣。①丁时翰指出因理气混然于一心之中,故心之发或有理发之时,或有气发之时。在此丁时翰对“理气互发”说作了全新的阐释,即以“互相发现”来解互发之义。他认为李珥对李滉的“理到”说未能真正理会,试图以此说来回应前者对后者的攻击。依止李滉“理气互发”之说,丁时翰不仅对李珥“气发理乘一途”说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而且还称其气象“似非吾儒法门”。其时栗谷学派在学界、政界正日益得势,而退溪学派则渐趋衰落,丁时翰对此十分忧虑,遂与李玄逸一道担当起为退溪学辩护的责任。从丁氏对李珥的批评中,我们随处可见党争之语气——此为两人党派、学派之殊异使然。
我们从比较的视角对丁时翰的理气说、“四端七情”说以及“人心道心”说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可以看出,丁氏不仅在理气关系上确有强调二者不离性的一面,而且在“四七”论方面亦有容受李珥之说的成分。但其学说之主旨仍然基于李滉的“尊理贬气”、“理气互发”之义上,而“理发”之说显然不合朱子“理不活动”之旨。各派间交互影响也是朝鲜朝性理学的特色之一。此外,还发现朝鲜朝儒学因所依文本之不同而造成的“多重文本交叠”的特色及诠释问题的复杂性一面。②在人心道心说方面其特点在于,对朱子所言理气之“心”的重视。
丁氏之学本于退溪李滉,因此学者亦称其心为“退陶之心”②。丁时翰曰:“退陶之学,绍述朱子,其所以集大成卫斯道者,亦与朱子略同。而朱子之后,儒学归禅。退陶之后,异言立帜。诗教之辨,传习录之跋,不得不出。四七之辨,壬午之录,又不得不著。”③丁时翰生活的年代,学界已分裂成以“主理”和“主气”④为理论特色的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作为近畿主理论学者⑤,丁时翰同李玄逸(字翼升,号葛庵,1627—1704年)一起对李滉的四七理论作了积极维护和系统阐述。⑥本节拟以李滉、李珥、丁时翰思想之比较为中心,来探讨其性理学思想之特点。
一、丁时翰的理气论
“理”与“气”是理学家为学立论的一对核心概念,因此理气问题亦可视为宋明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⑦而朱子则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讨论理学这一基本问题的哲学家。他以理气二分且又“不离不杂”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韩国性理学家们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的过程中,对理气问题①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丁时翰便曾说过:“理气之论,实是圣门极至之源头,而吾儒及异学于此焉分。”②不过,退溪、栗谷时期有关理气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理气动静和理气体用的问题而展开。丁时翰也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
李滉继承朱子“理气二分”说。他基于理气道器之分对二者“不杂”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以及“理尊无对”的观点。李滉重视理气“不杂”义的用意在于强调理对气的主宰作用。对二者“不杂”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观的特色。他曾在《非理气为一物辩证》③一文中写道:“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④进而他还认为,理与气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同,即“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他说:“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⑤、“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⑥。李滉的此一见解,既是对朱子“理先气后”、“理在事先”思想的修正,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进一步发展。他将朱熹的理气“先后”关系转变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由此为其“四七”论打下理论基础。
李珥则与李滉不同。他继承朱子理气之不离思想并对之作了进一步的解析和阐发。其“理气之妙”说、“气发理乘”说以及“理通气局”说皆独具特色。其中“理气之妙”说尤为栗谷思想之精髓——“气发理乘”说和“理通气局”说皆为“理气之妙”说的进一步阐发。
理气之“不离”亦是李珥哲学的主要理论特色。相较于李滉之“理”,李珥的“理气之妙”思想更是其哲学中“难见亦难说”处。李珥有言:“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夫理之源一而已矣,气之源亦一而已矣。气流行参差不齐,理亦流行而参差不齐。”①与李滉相比,他虽在理气说的理论突破上有所不及,却在传承朱子理气说上超而过之。
不过,到了17世纪李珥的这一思想倾向却受到李玄逸、丁时翰等南人学者的批评。丁时翰认为,古今学问道术之异皆源于人们对古圣贤所论之“理”的片面理解。在他看来,圣贤论“理”之言各有所指——有就“体”而言者,有就“用”而言者,有就其本原之理而言者,亦有就其散殊之理而言者。如果只讲“体”之寂然不动而不讲“用”之感而遂通,则徒见本原之理赋予万物而不见散殊之理各有其则,就会导致寂而不感终归于灭的后果。丁时翰继承李滉的“尊理”之思想,由此特别重视“理”之作为。“人之为学,只患于理字上见不透。若于此实见得的确,则处心行事,岂有未尽善乎。尧舜之精一执中,孔颜之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以理为主,而使人心听命焉。若以气为主而作用为性,则其祸必至于滔天。”②可见,在丁时翰的思理中只有“理”才具有“主宰”义,气则无之。他还特别强调了以气为主作用为性的严重后果。
作为主理论者,丁时翰每从维护李滉的角度对李珥之学展开批评:
今栗谷自谓有见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而推出整庵、花潭之绪余,以攻互发之说。故于人心道心,则以为皆源于理,而遂为相为终始之说,以反或原或生之意。于四端七情,则以为皆发于气,而遂为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之说,以反理发气发之意。至于理通气局,则又以为得见整庵、花潭之所未见,阐发前圣所不言之旨。而其所谓理通者,徒归寂灭虚无之地,未有安顿着落之处。而况其云所以发之理者,虽曰乘气,而每以徒具于寂然之中,不发于感通之际为言。其云理通者,虽曰无所不通,而又未免言理于窈冥,言气于粗浅,则是理是气,常隔断阻绝,不能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而终未见浑沦之中自有分开,分开之中自有浑沦之妙矣。盖其所谓理气不相离者,非真有见于理气之不相离也,只是认气为理。至以道心为本然之气,故终始迷昧于理字上。其言本原之体者,鹘囵笼罩,都没紧要,其言发见之用者,专主气字,更不言理。一向逞气骋辩,恣诋前贤,有若莠之乱苗,紫之乱朱,使从古圣贤相传之心法,既明复晦。①
李珥对整庵十分推崇②,他曾言:“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③依丁氏之见,李珥祖述整庵以“气”为重,故徒见理气之不离以及气常载理之一面。也因之无从体验浑沦之中自有分开,分开之中自有浑沦之妙。因此丁时翰批评李珥“昧于大本”。“栗谷则祖述整庵,昧于大本而所尚者气。故发于言论者,类多轻肆凌人底规模。而流弊所及,大为吾道之深害,大本之差不差,而其所发见于言行事为之间者,亦可征矣。”④而且,他还进一步批评李珥“论‘理’之言,亦似非吾儒家法”①。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丁氏继承李滉之“理帅气卒”的思想,进而发展出“理主气辅”论。“朱子‘虽在气中,理自理气自气,不相夹杂之谓性’云者,以其理气妙合之中,理常为主,气常为辅,虽在气中,不囿于气,命气而不命于气之云尔。非以为理气各在一处而不相妙合也。”②他在强调理之主宰性的同时,还对李滉的理气二分说作了有益的补充。指出虽说理为主而气为辅,理气各自不相夹杂。丁时翰特别强调了理气之不离性。
基于其“理主气辅”思想,丁氏提出自己独到的“理气体用”说。
理至有故无不异,至无故无不同,然无者未尝无,有者未尝有,则有无非有二也……理至无而至有云者,犹言无极而太极,或言自无极而为太极者。朱子辨释甚详。又于象山答书中云,不言无极,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由此观之,至无而至有不可云。至有故无不异,至无故无不同。其下两三句,虽合有无而言,不能救上句之病者,人所易知,而敬叔之不悟何哉?敬叔之见,既已如此,故以人物之性,谓有隐显体用,而以至有当显体用,以至无当隐体用。至有至无,分作隐显体用于一性之中,与分言无极太极者,何以异哉?③
“理主气辅”和“理气隐显体用”可以说是丁时翰理气论的主要内容。从以上比较可见,丁时翰理气论虽有重视二者不离性的一面,但是其主要学说仍以主理论为特色,并以此为基础对李滉的“尊理贬气”思想和“理气互发”之说进行了积极的补充和诠释。
二、丁时翰对李珥“四端七情”说的批判
如上一章所述,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基于理学的传统观念认为人都是得“气之正”者,但是由于每个人所禀之气有清浊、粹驳之不同会有“上智、中人、下愚三等之殊”①。于是,他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四端(理)与七情(气)之间的关系。李滉以为四端之情和七情是不同性质的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二者在根源和本质上皆不相同。李滉有言:“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②他认为此论与思孟程朱之旨冥然相契。
李珥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论,他更同情奇大升的观点。李珥对李滉之说的批评遭到了成浑的辩难。由二人之书信往复,李珥的“四七”论立场更加明了。依栗谷之见,对四七理气之发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发矣。”③李珥进而举例说“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④在李珥看来,不仅七情是气发理乘,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二者均为气发理乘。
针对李珥的“气发理乘”说,丁时翰提出如下批评:
理气为物,本混融无间,推之于前,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不见其终之离。而理无眹气有迹,安有无气之理或先或后,发见于事为之间者乎。然而终古圣贤于浑融无间,不可分先后,离合之中,或截而言之,或分而言之,以明此理之命气而不命于气,在气而不杂乎气者……既曰仁之端义之端,则仁发而为恻隐,义发而为羞恶,体用不离,本末相连,可见其不杂于气而一出于理。至于七情,则虽亦出于性而初无不善,但就其性在气质,浑沦理气者而为言。故几有善恶,气易用事,理难直遂,必须观理约气,然后理始显而气听命。此朱子所以有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之言。而今者(指栗谷——引者注)不察孟子剔发言理,朱子分言理气之本意,乃以四端七情滚合为一说,概而言之曰,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专以气发一途为言,而都遗却理发一款。①
依其之见,理无形而气有形,故其作用流行皆若气之所为。但因“理”至无而至有、至虚而至实,且又具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之特性,故其乘气流行皆为自然而然,不见其有所作为。当性情寂感之际,理之神用即蔼然呈露而不可掩——四端粹然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性即为显例。因此,不能仅着眼于理气之浑沦而只言“气发”不讲“理发”。
丁时翰认为,四端与七情从结构而言皆兼备了理和气。因此,四端与七情均与气相关。只是四端并不与气相互夹杂,而七情却受其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主理和主气方得区别。以此为基础,他推导出四端和七情在“所从来”处即相异的结论。这里丁时翰所持的是李滉的观点。在丁氏看来,四端与七情皆本于仁、义、礼、智之性。可见,丁时翰所言“所从来”与奇大升、李珥所谓“源头发端处”或“本源”有所不同——他虽未明言,从其语句中推断出此点。丁时翰以为人心虽无二源,但是其发现于外者可以主理、主气而言。由此可知,其“所从来”并非是“本”。丁氏更侧重于由“本”发用于外的过程,每以此指代他所描述的“就一心之中,方其萌动之开始”的时刻。此刻必是“性”与“气质”相互发生关系的时刻。于是,与气质发生何种的关系遂成区分四端和七情的关键。与“气”相关但不杂于“气”的情为四端;与气相关且在气的驱动下易流于恶的情则为七情。②据此,丁时翰对李滉之说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退溪《四七辨》云:“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栗谷所谓“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者,似本于此。而第退溪之以四端为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者,所指而言者,以其出于性之粹然在中,不杂乎形气者而为言。初不言无感而自发也。以七情为外物之触其形而动于中者所指而言者,以其出于性在气质,易感形气者而为言,亦非谓中无是理也。是以退溪旋以为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且谓“虽滉亦非谓七情不干于理,外物偶相凑着而感动”,且谓“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其本意所在,若是明白;而今者推出退溪所未有之意,说出退溪所未说之言,或以为做出许多葛藤,或以为正见之一累,已极轻肆,而终以无父而孝发,无君而忠发,不见孺子之入井而自发恻隐为心病等语,铺张抑勒,至此之极。岂其未曾虚心翫绎于退溪之说。而略绰看过胡乱说道者耶。①
这段话本是丁时翰为李滉之说所做的辩解。但从上下文以及李滉与奇大升辩论的全过程来看,李滉所言“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一语似有不妥。若谓此话代表李滉之真正立场,则其与奇大升之往复辩论便失去焦点。而丁时翰引这一句等于是否定四端是“无感而自发”。这无疑是其向李珥立场靠近,而承认四端与七情的同构型。②丁氏本人可能未意识到他的这一辩解与其初衷的自相矛盾处,学者于此则不可不察。
总之,丁时翰“四端七情”论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对李滉与李珥“四七理气”说之异同的详尽论述。丁时翰在批驳李珥“气发理乘”说的同时,对其部分见解亦有容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倾向。不过,尽管他在理气关系及四七理论的解释上有折中二李之痕迹,其思想之主旨还是反映了主理论学者的为学性格。
三、丁时翰的“人心道心”论
在韩国儒学史上由李珥与成浑推动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是继“四端七情理气”之辨之后发生的又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学术论争。
在论辩之初,成浑基于李滉“理气互发”之论提出理发即为“道心”而气发则为“人心”。“近日读朱子人心道心之说,有或生、或原之论,似与退溪之意合,故慨然以为在虞舜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理气互发之说,则退翁之见不易论也”①。所谓“或生”与“或原”,盖指朱熹所说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言。道心原于性命之正,纯善无恶;人心生于形气之私,故有善有恶。又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云。究此议论以理气之发,当初皆无不善,而气之不中乃流于恶云矣。”②因此成浑认为李滉的人心道心之说亦自不为过。
李珥同样援引朱子说法以增强说服力。他认为,朱子既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则何从而得此理气互发之说乎?在李珥看来,理气无先后离合不可谓之互发,但人心道心可以从两边来说。其《人心道心图说》有云:“道心虽不离乎气,而其发也为道义,故属之性命;人心虽亦本乎理,而其发也为口体,故属之形气。方寸之中,初无二心,只于发处有此二端。”③李珥在《答成浩原》的最后一书中指出:“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则心是气也,或原或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乎?”④可见,李珥对人心道心的说法亦承朱子之意而为言,且又时时不忘与其“气发理乘一途”之说相联系。其思想的系统性、逻辑性于此可见一斑。
李珥进而发挥朱子之说,提出自己独到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此论乃李珥对人心道心问题的基本看法。
丁时翰对于李珥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评论道:
窃详栗谷之意,概未见人心道心分言之脉络,以朱子或原或生之,为不得已之论而不之信,故每以人心道心滚合为一说。以为同出于本然之性,而以掩乎形气者,谓之人心;以不掩乎形气者,谓之道心。此非虞舜命名,朱子注释之本意也。夫上智不能无人心,则上智之人心,初不掩于形气,而以其从形气而生,故名之以人心。下愚不能无道心,则下愚之道心,虽发于气禀所拘之中,而以其本体之明有未尝息者,故名之以道心。初非以形气之掩与不掩,分言人心道心也。此是圣贤各指其所从来,使人审几用工之旨诀。而栗谷则舍而不取,既不欲相对说下。如朱子之言,而又不欲显言体用二字,以避宗主整庵之嫌。于是乎自作定论,辄以相为终始者言之。而其于道心上,言存养而不言审几。人心则直以为形气所掩而审其过不及云者,果有异于整庵体用之论乎?①
在丁时翰看来,李珥之说不过是祖述整庵学说而已,故而直言其人道说亦无异于整庵之道心人心体用论。他尖锐指出:“虽以浑沦者言之,只可言一心之中,从形气之人心,不离于性命,原性命之道心,不外于形气而已。若谓之人心道心相为终始云尔,则殊非人心道心之所以得名者也。”②依丁时翰之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仁义礼智之性蔼然流行于形气之间;人心生于形气,而视听言动之勿论非礼者乃所以听命于道心。
对于李珥“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源则只是一心”的观点,丁时翰批驳道:
所谓“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源则只是一心;其发也,或为理义,或为食色,故随其发而异其名”云者,初不外于退溪之说矣。既谓之“随其发而异其名”,则岂不可谓理发、气发乎?退溪所谓理气互发者,概以为理与气合而为心,理气混然一心之中,随所感而发,或有理发之时,或有气发之时,互相发现云尔。其言“互发”二字者,益明此心之无二本矣。今乃不察理到之言,而一向挥斥;至其何从得此之说,则又若初不知出于退溪之说者然,显有抑扬凌驾之意。此等气像,似非吾儒法门矣。①丁时翰指出因理气混然于一心之中,故心之发或有理发之时,或有气发之时。在此丁时翰对“理气互发”说作了全新的阐释,即以“互相发现”来解互发之义。他认为李珥对李滉的“理到”说未能真正理会,试图以此说来回应前者对后者的攻击。依止李滉“理气互发”之说,丁时翰不仅对李珥“气发理乘一途”说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而且还称其气象“似非吾儒法门”。其时栗谷学派在学界、政界正日益得势,而退溪学派则渐趋衰落,丁时翰对此十分忧虑,遂与李玄逸一道担当起为退溪学辩护的责任。从丁氏对李珥的批评中,我们随处可见党争之语气——此为两人党派、学派之殊异使然。
我们从比较的视角对丁时翰的理气说、“四端七情”说以及“人心道心”说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可以看出,丁氏不仅在理气关系上确有强调二者不离性的一面,而且在“四七”论方面亦有容受李珥之说的成分。但其学说之主旨仍然基于李滉的“尊理贬气”、“理气互发”之义上,而“理发”之说显然不合朱子“理不活动”之旨。各派间交互影响也是朝鲜朝性理学的特色之一。此外,还发现朝鲜朝儒学因所依文本之不同而造成的“多重文本交叠”的特色及诠释问题的复杂性一面。②在人心道心说方面其特点在于,对朱子所言理气之“心”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