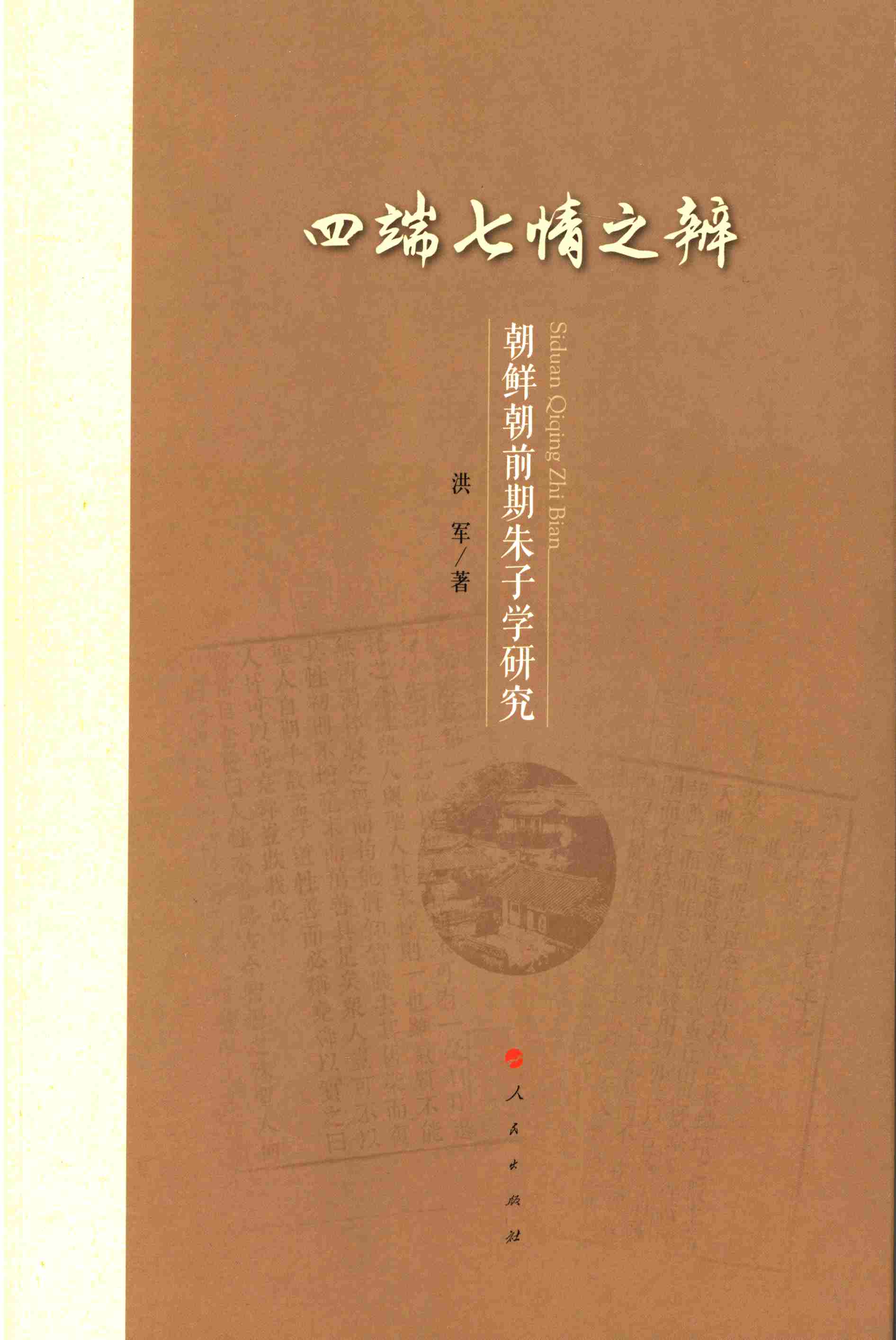第一节 宋浚吉与其“四端七情”论
| 内容出处: | 《四端七情之辨》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9056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宋浚吉与其“四端七情”论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8 |
| 页码: | 196-213 |
| 摘要: | 本文从比较朱子、李珥和宋浚吉的思想出发,对宋浚吉的理气论进行了论述。宋浚吉将理与气视为二物,并强调理对气的主宰作用。他认为理是无形无为而又纯善的形而上之存有,气是有形有为的存在。宋浚吉还借体用这对范畴来说明理的作用,将其界定为物的“所以然”。他承袭了其师沙溪金长生的理论,将道器诠释为理气,强调二者的不离不杂关系。此外,本文还提及了罗钦顺对理气为一物说的观点以及李滉和李珥对此的反对。 |
| 关键词: | 四端七情 宋浚吉 |
内容
宋浚吉(字明甫,号同春堂,1606—1672年)是17世纪韩国著名礼学家和政治家,同时亦是朝鲜朝中后期韩国性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本贯为恩津,谥文正。作为栗谷李珥的再传弟子,他在韩国儒学史上与同属畿湖学派的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年)并称为“两宋”先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宋浚吉身为畿湖学人还与以退溪李滉为宗匠的岭南学者保持密切联系,终汇诸家之长形成了颇具魅力的理论风格,为朝鲜朝礼学的形成以及性理学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本节拟从朱子、李珥和宋浚吉的思想之比较的视角,对其四七性理学说作一论述。
一、宋浚吉的理气论
理学家们大都把理气说作为其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朱子虽主理气二分,却以理本论为哲学体系之核心。而且,“理”在朱子的哲学体系中具有多种含义和用法。比如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据、事物运动变化之原因以及事物之内在规律等。另外,理又是仁义理智的总称(总名)。
李珥也同朱熹一样认为天地万物是由理和气构成。而且,他对理、气两概念还作了形上、形下的区别。李珥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则一太极而已;其气,则一阴阳而已。其为气也,有大小焉”①。他还说过“理,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②。可见其对理、气概念的认识并未超出朱子学的轨道。
李珥将“理”看作形而上之存有亦即宇宙的普遍法则和规律,使其既具事物法则规律之含义,又有伦理道德原理准则之意味。他曾说过:“对一阴一阳,天道流行,元亨利贞,周而复始,四时之错行,莫非自然之理也。”③盖以理为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之自然法则。又说过:“道学本在人伦之内,故于人伦尽其理,则是乃道学也。”④殆以理为人伦道德之准则。这与朱子对“理”概念的界定是基本相同的。
不过,在理、气两个概念的具体特性的认识上,李珥与朱子似乎又有所不同。这也是李珥为解决朱子所面临的理何以为万化之本的这一理论难题而进行的尝试。他将“理”理解为无形无为而又纯善的形而上之存有。“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宰者,理也。”⑤而且,“理气无始,实无先后之可言。但推本其所以然,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⑥。不过这里需注意的是,在李珥理气论中,理与气是“浑沦无间,无先后、无离合”⑦的关系,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在他看来,理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基础。“朱子所谓‘温和慈爱底道理者,即所谓爱之理也。’底字之字同一语意,何有不同乎!大抵性即理也,理无不善。”①“理”作为慈爱之所以然的形而上本体乃纯善之存有。“夫理上不可加一字,不可加一毫修为之力,理本善也,何可修为乎?”②因此,在人的行为中合乎理的便是善,否则即为恶。相对于理的“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气则具有“有形”、“有为”、“湛一清虚”之特性。
朱子主张气是有形与无形的统一。一方面,他认为“气聚成形”③,即有了气物才得以聚而成形(有形之物便是气);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地之间存在无形之气,比如“声臭有气无形,在物最为微妙,而犹曰无之”④。
李珥则明确提出理无形而气有形。“气局者何谓也?气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后也。”⑤作为物质的、有形象的存在,气属于与本体界相对的现象界。理作为形而上之存有,其超越性、普遍性必须通过气来呈现和实现。“有形有为而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⑥所以在李珥理气论中理与气是相互并举以显示其内涵的一对范畴。同时,气又具有“湛一清虚”性。李珥把气之本然状态解释为“湛一清虚”⑦或“湛然清虚”⑧的“浩然之气”。他说:“气之本然者,浩然之气也。浩然之气,充塞天地,则本善之理,无少掩蔽。”⑨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立场出发,认为不仅理具分殊性,而且气亦具分殊性。“一气运化散为万殊,分而言之,则天地万象各一气也;合而言之,则天地万象同一气也。”⑩由此而言,李珥的“理一之理”和“分殊之理”分别是依附或挂搭于“气一之气”和“分殊之气”的实理,作为气之本然者的浩然之气也是与“理”一样纯善之存有。而天地万物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气的有形有为之特性使其在时空的演化中出现了变异。
作为栗谷学派之嫡传的宋浚吉对朱子与栗谷皆十分推崇。他在进呈给国王的《写进春宫先贤格言屏幅跋》中便引了栗谷李珥的“道统之传,始自伏羲,终于朱子。朱子之后,又无的传”①一语,明确将朱子视为儒家道统的最后传人。同时,宋浚吉对李滉也表现出相当的尊敬。他在经筵侍讲时还多次引用李滉和郑经世(字景任,号愚伏,亦称为石潨道人或松麓,1563—1632年)等②岭南学者的言论进行讲解。他在晚年所作《记梦诗》中写道:“平生钦仰退陶翁,没世精神尚感通。此夜梦中承诲语,觉来山月满窗栊。”③表现出其洒脱不羁的治学风格。
在理气论方面,宋浚吉的学说大体承袭了其师沙溪金长生(字希元,号沙溪,1548—1631年)的理论,后者被视为李珥的嫡传弟子。金长生20岁入李珥门下受学,后又从学于龟峰宋翼弼和牛溪成浑等人。
作为金长生的弟子,宋浚吉也用形上、形下来规定理、气两个概念。他对《易》大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解释说“器即气也,道即理也,道器之分固如是”④。可谓径直以道器诠表理气。关于“理”与“道”的关系,程颐曾说过:“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⑤宋浚吉亦以为然。在他看来,“道”和“理”同实而异名,皆具万理而无形无象。
对于理、气之界定,宋浚吉仍以“有形”、“无形”以及“有迹”、“无迹”为判分的标准。他说过:“气有形可见,故曰形而下。下者,指有形、有迹而言也。理于物无所不在,而无形可见、无迹可寻。故曰形而上。上者,超乎形迹之外,非闻见所及之谓也。”⑥
与其同时的宋时烈虽亦用形上、形下区分理气,但相比而言要较宋浚吉委婉一些。宋时烈有言:“所谓道者理也,所谓器者气也”①,他还说过“自人物之形象言之,其虚而能为所以然者是理,故谓之上。其经纬错综,能此形象者是气,故谓之下云尔”②。
宋浚吉的这一解释似乎更为合理而简明。不过,也易使人产生过甚其词之感。如其所言“子思既以一道字符串费隐说,道固形而上之理也,非杂以形而下之气也”。③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一点上更近于退溪之学。栗谷之学强调的是理气之不离,亦即理与气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
在理气关系的问题上,宋浚吉仍以朱子和李珥的理气观为基础来解释理如何成为气之所以然。他认为“有是形必有是理”,而且理之于物如“诗所谓有物有则者也”④。肯定了理对于气的主宰作用和意义。接着,宋浚吉还借体用这对范畴来说明理何以是物的“所以然”。他指出:“父子、君臣是形而下之器也,是物也。父而慈、子而孝、君而义、臣而忠是形而上之道也,是则也。慈孝义忠,此所谓理之当然者,所谓费也,用也。所以慈、所以孝、所以义、所以忠,此理之所以然者,至隐存焉,所谓体也。推之万事万物莫不皆然。”⑤宋浚吉进而以“理堕气中”解释理气如何生成万物。“理堕气中,气能用事,而化生万物。即所谓气以成形,理已赋焉者也。”⑥理与气是二物还是一物以及理为“实有之一物”还是“非别有一物”始终是困扰性理学家的理论难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在这一问题上朱子的态度是既讲理气不相分离,还强调理与气“决是二物”。对此元代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吴澄(字幼清,号草庐,1249—1333年)则提出“非别有一物”说,对朱子理气论从理论结构上作出了重要修正。吴澄以为“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有此气即有此理。”①他否定理的实体性,强调理只是气之条理和规律。于此也可看出,在理的问题上朱子后学中已出现“去实体化”的转向。②此后被世人称为“朱学后劲”的罗钦顺则明确提出“理气一物”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③整庵指出理并不是形而上的实体,而只是气之运动的条理或规律。他大胆宣称:“仆从来认理气为一物。”④朱子后学的这一理论动向也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性理学家。如前文所述,《困知记》传入韩国后,李滉即从述朱之立场出发特地撰写《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驳整庵异说。他尖锐指出罗氏的“理气一物”说是“于大头脑处错了”⑤。李珥对罗氏学说的评价则稍有不同:“整庵则望见体,而微有未尽莹者,且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而其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理气为一物也,所见未尽莹故言,或过差耳。”⑥不管怎样,李滉和李珥皆反对“理气一物”说,而以朱子之理气“不离不杂”、“决是二物”为不刊之论。
宋浚吉亦追随其后而以理气为二物,从他维护李珥学说之立场中便可概见。宋浚吉以为“稷乃谓其(指栗谷——引者注)学以理气为一物,不以可笑可哀之甚乎。邪说肆行而莫之禁,则其眩乱注误,将至惑一世之人,其为祸岂不下于洪水猛兽哉”⑦。
朱子理气说的二元论结构必然会面对理气先后、理同气异、理气聚散等难以解答之问题。对此理论困境,李珥提出“理气之妙”说以为解释这些问题的理论基础。
宋浚吉则在继承朱子和李珥理气观同时,还对他们理气为二物的思想作了如下总结:“若以有形无形言,则器与道为二物;以在上在下言,亦为二物。须如此说方见得即形理在其中,道与器不相分。”①继“理堕入气”说,宋浚吉又提出理气“妙合而凝”说。他写道:
廉溪所谓阴阳一太极,即所谓器即道也。《性理群书》注错误处甚多,至或不成文理,而此条所释精粗本末则无误矣。若依李珥说,则精粗本末之下,当着吐也。若然则释阴阳太极,不成说话矣。盖大而莫能载,小而莫能破者,无非器也,而理无所不在。子思所谓费而隐,子夏所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程子所谓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与来示所引朱子语皆一义也。理固如此,本无可疑,但此所谓精粗本末无彼此一句,分明是贴阴阳太极字说,以为理与气无彼此耳。非泛论气有精粗本末也,如何。幸更细思之,先贤说话横说、竖说,各有攸当,最忌相牵强合作一说……按妙合云者,理气本浑融无间也。此乃理气混合无间隔也,乃阴静时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此乃阳动成形时也。②
对于理气妙合而凝,宋浚吉进一步解释道:妙合与凝是两项事,而《性理群书》注把妙合与凝合为一项事不符合朱子本意。他还以为《性理群书》注解把“妙合而凝”解释为妙于凝合无间断是有所未稳。“无间断也。间断字,恐未稳,以间隔释之,则未知如何。”③对于理气“浑融无间”思想,李珥总结前人关于理气关系的论述时也曾提出过,曰:“理气浑然无间,元不相离,不可指为二物。”④但是,李珥并未对“无间”一词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宋浚吉则将“无间”释为“无间隔”,表明他对名言的义理分际异常敏感。理气“浑融无间”说,是“理堕入气”说的有益的补充。
此“浑融无间”说似有类于明代理学家薛瑄(字德温,号敬轩,1389—1464年,谥文清,河东学派的缔造者)的理气“无缝隙”说。薛氏以理如日光、气如飞鸟之喻说明气有聚散而理无运动。结果还是理气看成有“缝隙”的。对于“堕入”说,罗钦顺批评道:“夫既以堕言,理气不容无罅缝矣。”①因为“堕入”一词本身隐含着理堕入气之前,理同气是被分隔着的意思。②尽管宋浚吉对理气“浑融无间”作了精心的解释和字面上的调整,但还是很难用这一主张来圆满解释理同气异、理气聚散的问题。
于是宋浚吉援引了李珥的“理通气局”说,并对此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李珥)至于理通气局之论,发先贤所未发。形状理气本体,直接分明,可以开悟后学于百世。非其学问精旨超特绝出于人者,安能及此。谓理通气局,则其分别理气,可谓极明白矣。③
“理通气局”说是栗谷为回答理同气异问题而提出。关于“理通气局”这一命题,李珥认为“理通气局四字,自谓见得,而又恐读书不多,先有此等言,而未见之也”④。尽管佛教华严宗有理事通局之说,但是以“理通气局”四字表述理气同异、理气聚散却是李珥的独见。虽然其思想也受到程伊川的“理一分殊”和朱子的“理同气异”思想的影响,但这一命题的提出更多缘于李珥对“气发理乘”思想之发挥。因此,在其文章中“理通气局”说往往与“气发理乘”说相互对举——如,“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⑤。
由上所述,在理气论方面宋浚吉承接朱子和李珥之说认为,世界万物皆由理与气构成。而且,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规定上也大体追随了栗谷的学说。他比李珥更强调道器之分别和理的“无迹、超乎形迹”之特性。在这一点上,宋浚吉似乎具有某种折中李滉与李珥理气说之倾向,其作为主气论学者的理论特色并不明显。若对宋浚吉理气说作一概括的话,可以说其理论主要由“理堕气中”说、“理气浑融无间”说、“理通气局”说组成。三者在其学说中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系统。但其对“理”的理解方面仍未超出传统的内在实体说之藩篱。
二、宋浚吉的“四端七情”论
前已述及,“四端七情”之辨是朝鲜朝性理学的中心论题之一。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家们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先是围绕理气之“发”产生了歧义。
李滉在手订郑之云的《天命图说》过程中,将“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奇大升则从自己的“理气浑沦”思想出发,对李滉之说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①在奇氏看来,所谓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②。四端虽为纯粹的天理之所发,但只是发乎七情中的苗脉而已。理气虽然有所分别(理为气之主宰、气为理之质料),但在具体事物中却混沦不可分开。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也。③
奇氏认为四端与七情皆是情,其间并无截然之别,所以二者不可分理气而论。其观点无疑与朱子的看法更为接近。
对于奇氏的质疑,李滉答复说先儒的确未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进行探讨,而理与气在具体生成的过程中也确实不可分离,但二者因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有必要分别而论。他在回信中讲道: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
李滉进而指出情有四端七情之别亦犹性有本然气禀之异。性既然可以分理气来说,情为什么就不能分理气而言呢?他认为由于四端、七情所从来各有不同,所以可分别从主理和主气的角度分而言之。“故愚尝妄以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即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最后他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此即“理气互发”说。而奇氏之说则被称为“理气共发/理气兼发”说。
与理气之“发”问题相关的另一论题为“主理”、“主气”之分的问题。李滉有言:“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③
其实,李滉、李珥等人也并非不知朱子理气“不离不杂”之义。李滉就说过:“理与气本不相杂,而亦不相离。不分而言,则混为一物,而不知其不相杂也。不合而言,则判为二物,而不知其不相离也。”④李珥亦有理气“既非二物,亦非一物”之说。比较而言李滉着重于理气之“不杂”义,而李珥则强调理气之“不离”义。两人在理气观上的差异,直接造成在四七理气论问题上的不同理解。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思想出发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转而支持奇大升的观点。他曾说过:“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①李珥一方面批评李滉未能真正理会朱子之本意,另一方面又主张不仅七情就连四端也是“气发理乘”。
李珥对李滉理论的批评,遭到成浑的辩难。于是,继“退、高之辩”李珥和成浑之间又展开了长达六年的第二次四七大论辩。成浑基本上支持李滉的观点。他指出:“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②进而坦言:“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③可见,成氏倾向于肯定李滉的“理气互发”之说。
李珥同成浑围绕四七人心道心问题进行的数年论辩中,始终坚持其“气发理乘一途”说。在他而观,对“四七理气”之发问题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李珥有言:“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④进而举例说:“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⑤可见,依其之见四端与七情均为“气发理乘”。
在“四端七情”说上,宋浚吉基本接受了李珥的主张。《同春堂年谱》中有如下的记述:
尤庵先生曰:“日知皆扩充之说,李滉、李珥之见不同矣。”先生(指宋浚吉——引者注)曰:“非但此也,四端七情之论亦不同。国初权近始发此论,其后郑之云作《天命图》而祖是说。李滉之言本于此,而有四端理发气乘,七情气发理乘之语。故李珥作书以辨之。”上曰:“分言理气,何也。”对(按:宋浚吉)曰:“此李珥所以为未安者也。四端只是拈出七情之善一边而言,不可分两边对说。若论气发理乘之,则不但七情而四端亦然。大抵人心必有感而后发,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无先后无离合,不可道互发也。”①
前已论及,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是一位朝鲜朝初期颇有影响力的性理学家,郑之云、李滉等人的很多思想端绪皆可从其性理学说中找到理论依据。所以宋浚吉认为正是权氏的学说开了“四七”论之先河。文中宋浚吉在讲述李滉与栗谷四七理论之不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宋浚吉认为在“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上不能以分言理气的方式来解释四端与七情。气是发之者,而理则为所以发者——四端只是七情之中的纯善者。
夫孟子之言四端,所以明人之可以为善也。故特举情之善一边言之,非谓四端之外更无他情也。若人情只有四端,更无不善之情则人皆为圣人也,故四端只拈出情之善者而言也。《记》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即人情善恶之总称。七情中之恶者,与四端为对则可。若以四端与七情相对则不可。李滉四七相对之论,虽因权近旧说,而未免失于照勘。义理天下之公也,学者穷格之功,只求义理之所在。若心有所疑而不为辨析,则此理终晦而不明矣。昔程子作易传,乃竭一生之精力,而朱子指其差吴处甚多。饶鲁、陈栎等至有愿为朱子忠臣,不愿为朱子佞臣等语,虽程朱之说,或未免有可疑处。况李滉之言,何可谓尽无差处乎。今以此为李珥之疵,其无识甚矣。李珥四七书,识见之超迈,言论之洞快,前古诸儒罕有及者。②
在宋浚吉看来,四端与七情并非“二情”,二者是“七包四”的关系也就是说七情作为人类情感之总称内在包含四端。他明确反对李滉将二者并立为二物的思想。
在谈论李滉与李珥理气说之不同时,他还对“气发理乘”说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盖退溪先生论四端七情云:“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栗谷先生辨之甚详。无虑数十百言,其大意曰“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者无所发。所谓气发理乘之者,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然云云”。先师(指金长生——引者注)常以栗谷之说为从。非特先师之见为然,外舅氏(指郑经世——引者注)之见亦然。弟常问之曰:“退溪、栗谷理气说不同,后学将何所的从。”答:“恐栗谷说是。试以吾身验之,如入家庙则心便肃然,是敬畏之发也。而即其肃然者,乃气也云云。”至今言犹在耳……栗谷此论真可谓百世以竢而不惑,使退陶而复作,亦必莞尔而笑。①
宋浚吉的岳父愚伏郑经世是当时岭南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宋氏引愚伏为同调以为“气发理乘”论张目。他还试图说服其他退溪门人接受这一观点。
朱子也认为四端和七情皆为性之所发的情感。他在《孟子集注》中讲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②宋浚吉对四端也有自己的解释。“有诸内而形诸外者,谓之端也。人心本善,于此可见。”③在宋浚吉看来,四端乃有诸内而形诸外者,属于已发之情——但又根于仁、义、礼、智而为人性之善。对于“性”、“理”之关系他解释道:“大抵性字从心从生,与理字不同。理堕在气中者,方谓之性。故曰‘性即理也’。盖谓在人之性,即在天之理也。”④
在四端中,宋浚吉特别重视恻隐之心。他在与愚伏先生的信中提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恻隐之心,心之生道也。”①宋浚吉强调“恻隐之心”在四端中的统摄作用。“人无恻隐之心,便是死物,犹鱼之不得水则不生也……恻隐便是初动时,才动便见三者之分界。如春不生则夏不长,秋不收而冬无所藏矣。此可见恻隐统四端也。古人观庭草庐鸣以体仁,此是天机流动活泼泼地也。”②可见,他将“恻隐之心”视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
不仅如此,宋浚吉还对仁、义、礼、智作了如下论述:
夫仁礼属于阳,义知属于阴,而阳德健、阴德顺,健顺五常乃人之所同得。而并言物者,凡物亦自得其一端,如虎狼之仁、蜂蚁之义皆是。故谓之各得其所赋之理也。③
此段引文不无泛性善论之意味,而其论说基础正是李珥的“理通气局”思想。由此可见朝鲜朝后期“人物性同异论”论辩之理论端绪。
宋浚吉对李滉与李珥的四端七情说详论其异同。他指出李滉之误,而对李珥“气发理乘”之思想则颇为推重。尽管宋浚吉在理气概念的界定和理气关系的理解上有折中二李之倾向,但从其四七理气论中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畿湖派(主气论)的为学性格。
三、宋浚吉的“人心道心”论
对性情善恶及人心道心问题的讨论可以视作四端七情问题在更深层次的展开。作为朱子学的重要论题,人心道心问题与公私、理欲之探究皆有密不可分之关系。
二程认为人心与人欲相联,而道心则与天理相通。伊川有言:“‘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④明道则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⑤伊川遂将“道心”和“人心”对立起来,以前者为正而以后者为邪。在他看来,唯有用“精一”功夫护持“道心”,才能令其不被“人心”扰乱。“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①职此之故,伊川明确主张存天理以灭人欲。
朱子也说过:“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②他将十六字心传视为古圣相传之“道”。朱子是这样理解分人心、道心之异的:“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③他进而说明:“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④“道心”为根于义理之正,而“人心”则根于耳目之欲。
仅就以已发、未发而论,则人心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点上李珥也与朱子所见略同。但是朱子主张二者皆发自“一心”,李珥主张二者发自“一性”。那么,人何以会有人心、道心两种不同的知觉?朱子认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⑤。这就是朱子独到的解释。他还纠正了伊川的说法,提出人心并非皆“恶”。“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⑥朱子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人的生存欲求和生理欲望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⑦。朱子虽然提出人心道心相分,却主张二者“不可作两物看,不可于两处求也”⑧。可见,在朱子哲学中人心道心问题虽与天理人欲问题相对应,但不似后者那样显得十分紧张。
李珥则继承朱子的学说并加以发挥,提出了“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说法。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
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①这是基于“意”的商量计较作用的,人心道心可互为转变、转换的理论。因此李珥认为人心道心可以相互转换,因而不能将其判然两分。
对于人心道心与四端七情的差异,李珥指出:“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②人心道心之名源于性命形气之别,四端七情则与此不同——后者之区别是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四端属于七情之善的一类,故而七情可兼四端。而人心与道心因含对比之意,所以无法相兼而只能互为始终。
不过,李珥认为“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③他肯定了人心亦有善的层面,此为李珥对李滉学说的有益补充。我们知道李滉以“理贵气贱”为据将人心等同人欲,进而将人欲归之为“恶”。
宋浚吉的“人心道心”说大体亦接续朱子、李珥之思路而讲。在他看来,“朱子之序,历叙上古圣王道统之传,‘危微精一’十六字,实万世心学之渊源”④。宋浚吉以为“人心修之便是道心,自道心放出便是人心”⑤,他很注意二者的相互转换性。及至晚年特别强调气之发用时的省察功夫,要求对人心时时严加防范。“深加省察如有一念之差用,力速去焉。”⑥至于人心与道心的不同,宋浚吉解释道:“心之本体而言,未发之前理为主,既发之后气用事。周子云诚无为几善恶,此人心道心分歧处也。”①这表明他同样以已发、未发来区分人心与道心。
宋浚吉之“人心道心”说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心”论。首先,他强调“心”之虚灵知觉性,而且对“虚灵知觉”也有独到的理解。《年谱》中记云:“上御养心阁。侍读官金万重讲文义曰:‘虚灵心之体,知觉人之用也’。先生曰:‘此言误矣。虚灵知觉皆心之体也。其曰具众理应万事者,具众理体也,应万事用也。’”②虚灵知觉性指的是心具有不受先见左右的能动知觉之特性。宋浚吉强调知觉是体而非用,颇有个人之体悟。
其次,宋浚吉强调心之易动性。“道之浩浩何处下手用力之方,无逾于庄敬自持。真氏之言实为明白精切。每侍先王讲此书,未尝不反复咏叹于此。夫人之一心易流而难制,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心便至于放逸矣。”③既然人心易流而难制,那么如何使其保持清明之体呢?宋浚吉主张要去“物欲”,“心无物欲以蔽之,则清明之体自然呈露矣。”④
再次,在宋浚吉的学说中“心”多次被描述为“活物”,比朱子之心更具活动性。“人心是活物。终不得不用,既不用于学问,则其所用不过宦官宫妾变嬖戏玩之事而已。”⑤这一点上与其同时代的尤庵宋时烈所见略同。宋时烈说过:“盖朱子之意,以人心道心,皆为已发者矣。此心为食色而发,则是为人心,而又商量其所发,使合乎道理者,则为道心。其为食色而发者,此心也。商量其所发者,亦此心也。何可谓两样心也?大概心是活物,其发无穷,而本体则一,岂可以节制者为一心,听命者又为一心。”⑥从“心是活物”、“其发无穷”等论说中,可以看出韩国主气论学者的“心”论特色。
朱子的“心”是一身之主宰,赅备体用,兼摄形上之性理与形下之情气。如果说“一心”具众理乃其体,那么应万事者则其用;如果说寂然不动者乃其体,那么感而遂通者则其用。其“一心”实际上涵盖形上、形下两层,既是超越层面的本然之心,又是经验层面的实然之心。此“心”一体两面,既存有又活动。实然形下的“心”具有活动作用的能力,由此体现超越形上之“心”,但又不是禅宗的“作用见性”。①在宋浚吉的心性论中,“心”更多是指实然形下之“心”,而又不同于阳明学所讲的一颗活泼泼的心。此一心论在工夫上有一特点,就是较为重视“志”的导向。“志”为“心之所之”,使“心”全副地趋向一个目的,决然必欲得之——所以特别强调“立志”之重要性。②宋浚吉亦是如此。他曾说过:“愿殿下勿以臣言为迂,必须立此大志焉。立志坚定,然后道统可继,治化可成矣。”③还说过:“诚能奋发大志,则何事不可做乎。”④
最后,宋浚吉对诸儒“心”论作了个概括:“圣贤论心不同有如此处,有如彼处。有从那边用工者,有从这边用工者,其归未尝不一。所谓从一方入,则三方入处皆在其中。”⑤这段话是宋浚吉向朝鲜国王讲解《心学图》时,针对李滉与李珥所论之不同而发的议论。从文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李滉与李珥的心论都有精深的了解。
在“人心道心”论方面,宋浚吉亦有极高的造诣。据《年谱》上曰:“讲心经。先生(指宋浚吉——引者注)于人心道心之辨,毫分缕析援据详尽。上叹曰:‘晓喻诚切也。’”⑥但从现存的文献中我们很难发现这方面的系统论述。材料的欠缺实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以上是从比较的角度对宋浚吉的理气说、“四端七情”说以及“人心道心”说作了简要论述。可以看出,在理气二物之分判上宋浚吉和李珥相比虽有过甚之感,却大体不出李珥“理通气局”之藩篱。而在“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上,宋浚吉则特别重视李珥的“气发理乘”说。至于“人心道心”说,宋氏的理论特色在于对朱子所言实然之“心”的强调。
一、宋浚吉的理气论
理学家们大都把理气说作为其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朱子虽主理气二分,却以理本论为哲学体系之核心。而且,“理”在朱子的哲学体系中具有多种含义和用法。比如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据、事物运动变化之原因以及事物之内在规律等。另外,理又是仁义理智的总称(总名)。
李珥也同朱熹一样认为天地万物是由理和气构成。而且,他对理、气两概念还作了形上、形下的区别。李珥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则一太极而已;其气,则一阴阳而已。其为气也,有大小焉”①。他还说过“理,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②。可见其对理、气概念的认识并未超出朱子学的轨道。
李珥将“理”看作形而上之存有亦即宇宙的普遍法则和规律,使其既具事物法则规律之含义,又有伦理道德原理准则之意味。他曾说过:“对一阴一阳,天道流行,元亨利贞,周而复始,四时之错行,莫非自然之理也。”③盖以理为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之自然法则。又说过:“道学本在人伦之内,故于人伦尽其理,则是乃道学也。”④殆以理为人伦道德之准则。这与朱子对“理”概念的界定是基本相同的。
不过,在理、气两个概念的具体特性的认识上,李珥与朱子似乎又有所不同。这也是李珥为解决朱子所面临的理何以为万化之本的这一理论难题而进行的尝试。他将“理”理解为无形无为而又纯善的形而上之存有。“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宰者,理也。”⑤而且,“理气无始,实无先后之可言。但推本其所以然,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⑥。不过这里需注意的是,在李珥理气论中,理与气是“浑沦无间,无先后、无离合”⑦的关系,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在他看来,理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基础。“朱子所谓‘温和慈爱底道理者,即所谓爱之理也。’底字之字同一语意,何有不同乎!大抵性即理也,理无不善。”①“理”作为慈爱之所以然的形而上本体乃纯善之存有。“夫理上不可加一字,不可加一毫修为之力,理本善也,何可修为乎?”②因此,在人的行为中合乎理的便是善,否则即为恶。相对于理的“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气则具有“有形”、“有为”、“湛一清虚”之特性。
朱子主张气是有形与无形的统一。一方面,他认为“气聚成形”③,即有了气物才得以聚而成形(有形之物便是气);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地之间存在无形之气,比如“声臭有气无形,在物最为微妙,而犹曰无之”④。
李珥则明确提出理无形而气有形。“气局者何谓也?气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后也。”⑤作为物质的、有形象的存在,气属于与本体界相对的现象界。理作为形而上之存有,其超越性、普遍性必须通过气来呈现和实现。“有形有为而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⑥所以在李珥理气论中理与气是相互并举以显示其内涵的一对范畴。同时,气又具有“湛一清虚”性。李珥把气之本然状态解释为“湛一清虚”⑦或“湛然清虚”⑧的“浩然之气”。他说:“气之本然者,浩然之气也。浩然之气,充塞天地,则本善之理,无少掩蔽。”⑨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立场出发,认为不仅理具分殊性,而且气亦具分殊性。“一气运化散为万殊,分而言之,则天地万象各一气也;合而言之,则天地万象同一气也。”⑩由此而言,李珥的“理一之理”和“分殊之理”分别是依附或挂搭于“气一之气”和“分殊之气”的实理,作为气之本然者的浩然之气也是与“理”一样纯善之存有。而天地万物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气的有形有为之特性使其在时空的演化中出现了变异。
作为栗谷学派之嫡传的宋浚吉对朱子与栗谷皆十分推崇。他在进呈给国王的《写进春宫先贤格言屏幅跋》中便引了栗谷李珥的“道统之传,始自伏羲,终于朱子。朱子之后,又无的传”①一语,明确将朱子视为儒家道统的最后传人。同时,宋浚吉对李滉也表现出相当的尊敬。他在经筵侍讲时还多次引用李滉和郑经世(字景任,号愚伏,亦称为石潨道人或松麓,1563—1632年)等②岭南学者的言论进行讲解。他在晚年所作《记梦诗》中写道:“平生钦仰退陶翁,没世精神尚感通。此夜梦中承诲语,觉来山月满窗栊。”③表现出其洒脱不羁的治学风格。
在理气论方面,宋浚吉的学说大体承袭了其师沙溪金长生(字希元,号沙溪,1548—1631年)的理论,后者被视为李珥的嫡传弟子。金长生20岁入李珥门下受学,后又从学于龟峰宋翼弼和牛溪成浑等人。
作为金长生的弟子,宋浚吉也用形上、形下来规定理、气两个概念。他对《易》大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解释说“器即气也,道即理也,道器之分固如是”④。可谓径直以道器诠表理气。关于“理”与“道”的关系,程颐曾说过:“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⑤宋浚吉亦以为然。在他看来,“道”和“理”同实而异名,皆具万理而无形无象。
对于理、气之界定,宋浚吉仍以“有形”、“无形”以及“有迹”、“无迹”为判分的标准。他说过:“气有形可见,故曰形而下。下者,指有形、有迹而言也。理于物无所不在,而无形可见、无迹可寻。故曰形而上。上者,超乎形迹之外,非闻见所及之谓也。”⑥
与其同时的宋时烈虽亦用形上、形下区分理气,但相比而言要较宋浚吉委婉一些。宋时烈有言:“所谓道者理也,所谓器者气也”①,他还说过“自人物之形象言之,其虚而能为所以然者是理,故谓之上。其经纬错综,能此形象者是气,故谓之下云尔”②。
宋浚吉的这一解释似乎更为合理而简明。不过,也易使人产生过甚其词之感。如其所言“子思既以一道字符串费隐说,道固形而上之理也,非杂以形而下之气也”。③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一点上更近于退溪之学。栗谷之学强调的是理气之不离,亦即理与气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
在理气关系的问题上,宋浚吉仍以朱子和李珥的理气观为基础来解释理如何成为气之所以然。他认为“有是形必有是理”,而且理之于物如“诗所谓有物有则者也”④。肯定了理对于气的主宰作用和意义。接着,宋浚吉还借体用这对范畴来说明理何以是物的“所以然”。他指出:“父子、君臣是形而下之器也,是物也。父而慈、子而孝、君而义、臣而忠是形而上之道也,是则也。慈孝义忠,此所谓理之当然者,所谓费也,用也。所以慈、所以孝、所以义、所以忠,此理之所以然者,至隐存焉,所谓体也。推之万事万物莫不皆然。”⑤宋浚吉进而以“理堕气中”解释理气如何生成万物。“理堕气中,气能用事,而化生万物。即所谓气以成形,理已赋焉者也。”⑥理与气是二物还是一物以及理为“实有之一物”还是“非别有一物”始终是困扰性理学家的理论难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在这一问题上朱子的态度是既讲理气不相分离,还强调理与气“决是二物”。对此元代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吴澄(字幼清,号草庐,1249—1333年)则提出“非别有一物”说,对朱子理气论从理论结构上作出了重要修正。吴澄以为“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有此气即有此理。”①他否定理的实体性,强调理只是气之条理和规律。于此也可看出,在理的问题上朱子后学中已出现“去实体化”的转向。②此后被世人称为“朱学后劲”的罗钦顺则明确提出“理气一物”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③整庵指出理并不是形而上的实体,而只是气之运动的条理或规律。他大胆宣称:“仆从来认理气为一物。”④朱子后学的这一理论动向也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性理学家。如前文所述,《困知记》传入韩国后,李滉即从述朱之立场出发特地撰写《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驳整庵异说。他尖锐指出罗氏的“理气一物”说是“于大头脑处错了”⑤。李珥对罗氏学说的评价则稍有不同:“整庵则望见体,而微有未尽莹者,且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而其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理气为一物也,所见未尽莹故言,或过差耳。”⑥不管怎样,李滉和李珥皆反对“理气一物”说,而以朱子之理气“不离不杂”、“决是二物”为不刊之论。
宋浚吉亦追随其后而以理气为二物,从他维护李珥学说之立场中便可概见。宋浚吉以为“稷乃谓其(指栗谷——引者注)学以理气为一物,不以可笑可哀之甚乎。邪说肆行而莫之禁,则其眩乱注误,将至惑一世之人,其为祸岂不下于洪水猛兽哉”⑦。
朱子理气说的二元论结构必然会面对理气先后、理同气异、理气聚散等难以解答之问题。对此理论困境,李珥提出“理气之妙”说以为解释这些问题的理论基础。
宋浚吉则在继承朱子和李珥理气观同时,还对他们理气为二物的思想作了如下总结:“若以有形无形言,则器与道为二物;以在上在下言,亦为二物。须如此说方见得即形理在其中,道与器不相分。”①继“理堕入气”说,宋浚吉又提出理气“妙合而凝”说。他写道:
廉溪所谓阴阳一太极,即所谓器即道也。《性理群书》注错误处甚多,至或不成文理,而此条所释精粗本末则无误矣。若依李珥说,则精粗本末之下,当着吐也。若然则释阴阳太极,不成说话矣。盖大而莫能载,小而莫能破者,无非器也,而理无所不在。子思所谓费而隐,子夏所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程子所谓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与来示所引朱子语皆一义也。理固如此,本无可疑,但此所谓精粗本末无彼此一句,分明是贴阴阳太极字说,以为理与气无彼此耳。非泛论气有精粗本末也,如何。幸更细思之,先贤说话横说、竖说,各有攸当,最忌相牵强合作一说……按妙合云者,理气本浑融无间也。此乃理气混合无间隔也,乃阴静时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此乃阳动成形时也。②
对于理气妙合而凝,宋浚吉进一步解释道:妙合与凝是两项事,而《性理群书》注把妙合与凝合为一项事不符合朱子本意。他还以为《性理群书》注解把“妙合而凝”解释为妙于凝合无间断是有所未稳。“无间断也。间断字,恐未稳,以间隔释之,则未知如何。”③对于理气“浑融无间”思想,李珥总结前人关于理气关系的论述时也曾提出过,曰:“理气浑然无间,元不相离,不可指为二物。”④但是,李珥并未对“无间”一词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宋浚吉则将“无间”释为“无间隔”,表明他对名言的义理分际异常敏感。理气“浑融无间”说,是“理堕入气”说的有益的补充。
此“浑融无间”说似有类于明代理学家薛瑄(字德温,号敬轩,1389—1464年,谥文清,河东学派的缔造者)的理气“无缝隙”说。薛氏以理如日光、气如飞鸟之喻说明气有聚散而理无运动。结果还是理气看成有“缝隙”的。对于“堕入”说,罗钦顺批评道:“夫既以堕言,理气不容无罅缝矣。”①因为“堕入”一词本身隐含着理堕入气之前,理同气是被分隔着的意思。②尽管宋浚吉对理气“浑融无间”作了精心的解释和字面上的调整,但还是很难用这一主张来圆满解释理同气异、理气聚散的问题。
于是宋浚吉援引了李珥的“理通气局”说,并对此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李珥)至于理通气局之论,发先贤所未发。形状理气本体,直接分明,可以开悟后学于百世。非其学问精旨超特绝出于人者,安能及此。谓理通气局,则其分别理气,可谓极明白矣。③
“理通气局”说是栗谷为回答理同气异问题而提出。关于“理通气局”这一命题,李珥认为“理通气局四字,自谓见得,而又恐读书不多,先有此等言,而未见之也”④。尽管佛教华严宗有理事通局之说,但是以“理通气局”四字表述理气同异、理气聚散却是李珥的独见。虽然其思想也受到程伊川的“理一分殊”和朱子的“理同气异”思想的影响,但这一命题的提出更多缘于李珥对“气发理乘”思想之发挥。因此,在其文章中“理通气局”说往往与“气发理乘”说相互对举——如,“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⑤。
由上所述,在理气论方面宋浚吉承接朱子和李珥之说认为,世界万物皆由理与气构成。而且,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规定上也大体追随了栗谷的学说。他比李珥更强调道器之分别和理的“无迹、超乎形迹”之特性。在这一点上,宋浚吉似乎具有某种折中李滉与李珥理气说之倾向,其作为主气论学者的理论特色并不明显。若对宋浚吉理气说作一概括的话,可以说其理论主要由“理堕气中”说、“理气浑融无间”说、“理通气局”说组成。三者在其学说中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系统。但其对“理”的理解方面仍未超出传统的内在实体说之藩篱。
二、宋浚吉的“四端七情”论
前已述及,“四端七情”之辨是朝鲜朝性理学的中心论题之一。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家们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先是围绕理气之“发”产生了歧义。
李滉在手订郑之云的《天命图说》过程中,将“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奇大升则从自己的“理气浑沦”思想出发,对李滉之说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①在奇氏看来,所谓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②。四端虽为纯粹的天理之所发,但只是发乎七情中的苗脉而已。理气虽然有所分别(理为气之主宰、气为理之质料),但在具体事物中却混沦不可分开。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也。③
奇氏认为四端与七情皆是情,其间并无截然之别,所以二者不可分理气而论。其观点无疑与朱子的看法更为接近。
对于奇氏的质疑,李滉答复说先儒的确未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进行探讨,而理与气在具体生成的过程中也确实不可分离,但二者因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有必要分别而论。他在回信中讲道: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
李滉进而指出情有四端七情之别亦犹性有本然气禀之异。性既然可以分理气来说,情为什么就不能分理气而言呢?他认为由于四端、七情所从来各有不同,所以可分别从主理和主气的角度分而言之。“故愚尝妄以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即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最后他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此即“理气互发”说。而奇氏之说则被称为“理气共发/理气兼发”说。
与理气之“发”问题相关的另一论题为“主理”、“主气”之分的问题。李滉有言:“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③
其实,李滉、李珥等人也并非不知朱子理气“不离不杂”之义。李滉就说过:“理与气本不相杂,而亦不相离。不分而言,则混为一物,而不知其不相杂也。不合而言,则判为二物,而不知其不相离也。”④李珥亦有理气“既非二物,亦非一物”之说。比较而言李滉着重于理气之“不杂”义,而李珥则强调理气之“不离”义。两人在理气观上的差异,直接造成在四七理气论问题上的不同理解。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思想出发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转而支持奇大升的观点。他曾说过:“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①李珥一方面批评李滉未能真正理会朱子之本意,另一方面又主张不仅七情就连四端也是“气发理乘”。
李珥对李滉理论的批评,遭到成浑的辩难。于是,继“退、高之辩”李珥和成浑之间又展开了长达六年的第二次四七大论辩。成浑基本上支持李滉的观点。他指出:“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②进而坦言:“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③可见,成氏倾向于肯定李滉的“理气互发”之说。
李珥同成浑围绕四七人心道心问题进行的数年论辩中,始终坚持其“气发理乘一途”说。在他而观,对“四七理气”之发问题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李珥有言:“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④进而举例说:“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⑤可见,依其之见四端与七情均为“气发理乘”。
在“四端七情”说上,宋浚吉基本接受了李珥的主张。《同春堂年谱》中有如下的记述:
尤庵先生曰:“日知皆扩充之说,李滉、李珥之见不同矣。”先生(指宋浚吉——引者注)曰:“非但此也,四端七情之论亦不同。国初权近始发此论,其后郑之云作《天命图》而祖是说。李滉之言本于此,而有四端理发气乘,七情气发理乘之语。故李珥作书以辨之。”上曰:“分言理气,何也。”对(按:宋浚吉)曰:“此李珥所以为未安者也。四端只是拈出七情之善一边而言,不可分两边对说。若论气发理乘之,则不但七情而四端亦然。大抵人心必有感而后发,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无先后无离合,不可道互发也。”①
前已论及,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是一位朝鲜朝初期颇有影响力的性理学家,郑之云、李滉等人的很多思想端绪皆可从其性理学说中找到理论依据。所以宋浚吉认为正是权氏的学说开了“四七”论之先河。文中宋浚吉在讲述李滉与栗谷四七理论之不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宋浚吉认为在“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上不能以分言理气的方式来解释四端与七情。气是发之者,而理则为所以发者——四端只是七情之中的纯善者。
夫孟子之言四端,所以明人之可以为善也。故特举情之善一边言之,非谓四端之外更无他情也。若人情只有四端,更无不善之情则人皆为圣人也,故四端只拈出情之善者而言也。《记》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即人情善恶之总称。七情中之恶者,与四端为对则可。若以四端与七情相对则不可。李滉四七相对之论,虽因权近旧说,而未免失于照勘。义理天下之公也,学者穷格之功,只求义理之所在。若心有所疑而不为辨析,则此理终晦而不明矣。昔程子作易传,乃竭一生之精力,而朱子指其差吴处甚多。饶鲁、陈栎等至有愿为朱子忠臣,不愿为朱子佞臣等语,虽程朱之说,或未免有可疑处。况李滉之言,何可谓尽无差处乎。今以此为李珥之疵,其无识甚矣。李珥四七书,识见之超迈,言论之洞快,前古诸儒罕有及者。②
在宋浚吉看来,四端与七情并非“二情”,二者是“七包四”的关系也就是说七情作为人类情感之总称内在包含四端。他明确反对李滉将二者并立为二物的思想。
在谈论李滉与李珥理气说之不同时,他还对“气发理乘”说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盖退溪先生论四端七情云:“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栗谷先生辨之甚详。无虑数十百言,其大意曰“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者无所发。所谓气发理乘之者,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然云云”。先师(指金长生——引者注)常以栗谷之说为从。非特先师之见为然,外舅氏(指郑经世——引者注)之见亦然。弟常问之曰:“退溪、栗谷理气说不同,后学将何所的从。”答:“恐栗谷说是。试以吾身验之,如入家庙则心便肃然,是敬畏之发也。而即其肃然者,乃气也云云。”至今言犹在耳……栗谷此论真可谓百世以竢而不惑,使退陶而复作,亦必莞尔而笑。①
宋浚吉的岳父愚伏郑经世是当时岭南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宋氏引愚伏为同调以为“气发理乘”论张目。他还试图说服其他退溪门人接受这一观点。
朱子也认为四端和七情皆为性之所发的情感。他在《孟子集注》中讲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②宋浚吉对四端也有自己的解释。“有诸内而形诸外者,谓之端也。人心本善,于此可见。”③在宋浚吉看来,四端乃有诸内而形诸外者,属于已发之情——但又根于仁、义、礼、智而为人性之善。对于“性”、“理”之关系他解释道:“大抵性字从心从生,与理字不同。理堕在气中者,方谓之性。故曰‘性即理也’。盖谓在人之性,即在天之理也。”④
在四端中,宋浚吉特别重视恻隐之心。他在与愚伏先生的信中提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恻隐之心,心之生道也。”①宋浚吉强调“恻隐之心”在四端中的统摄作用。“人无恻隐之心,便是死物,犹鱼之不得水则不生也……恻隐便是初动时,才动便见三者之分界。如春不生则夏不长,秋不收而冬无所藏矣。此可见恻隐统四端也。古人观庭草庐鸣以体仁,此是天机流动活泼泼地也。”②可见,他将“恻隐之心”视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
不仅如此,宋浚吉还对仁、义、礼、智作了如下论述:
夫仁礼属于阳,义知属于阴,而阳德健、阴德顺,健顺五常乃人之所同得。而并言物者,凡物亦自得其一端,如虎狼之仁、蜂蚁之义皆是。故谓之各得其所赋之理也。③
此段引文不无泛性善论之意味,而其论说基础正是李珥的“理通气局”思想。由此可见朝鲜朝后期“人物性同异论”论辩之理论端绪。
宋浚吉对李滉与李珥的四端七情说详论其异同。他指出李滉之误,而对李珥“气发理乘”之思想则颇为推重。尽管宋浚吉在理气概念的界定和理气关系的理解上有折中二李之倾向,但从其四七理气论中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畿湖派(主气论)的为学性格。
三、宋浚吉的“人心道心”论
对性情善恶及人心道心问题的讨论可以视作四端七情问题在更深层次的展开。作为朱子学的重要论题,人心道心问题与公私、理欲之探究皆有密不可分之关系。
二程认为人心与人欲相联,而道心则与天理相通。伊川有言:“‘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④明道则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⑤伊川遂将“道心”和“人心”对立起来,以前者为正而以后者为邪。在他看来,唯有用“精一”功夫护持“道心”,才能令其不被“人心”扰乱。“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①职此之故,伊川明确主张存天理以灭人欲。
朱子也说过:“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②他将十六字心传视为古圣相传之“道”。朱子是这样理解分人心、道心之异的:“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③他进而说明:“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④“道心”为根于义理之正,而“人心”则根于耳目之欲。
仅就以已发、未发而论,则人心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点上李珥也与朱子所见略同。但是朱子主张二者皆发自“一心”,李珥主张二者发自“一性”。那么,人何以会有人心、道心两种不同的知觉?朱子认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⑤。这就是朱子独到的解释。他还纠正了伊川的说法,提出人心并非皆“恶”。“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⑥朱子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人的生存欲求和生理欲望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⑦。朱子虽然提出人心道心相分,却主张二者“不可作两物看,不可于两处求也”⑧。可见,在朱子哲学中人心道心问题虽与天理人欲问题相对应,但不似后者那样显得十分紧张。
李珥则继承朱子的学说并加以发挥,提出了“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说法。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
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①这是基于“意”的商量计较作用的,人心道心可互为转变、转换的理论。因此李珥认为人心道心可以相互转换,因而不能将其判然两分。
对于人心道心与四端七情的差异,李珥指出:“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②人心道心之名源于性命形气之别,四端七情则与此不同——后者之区别是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四端属于七情之善的一类,故而七情可兼四端。而人心与道心因含对比之意,所以无法相兼而只能互为始终。
不过,李珥认为“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③他肯定了人心亦有善的层面,此为李珥对李滉学说的有益补充。我们知道李滉以“理贵气贱”为据将人心等同人欲,进而将人欲归之为“恶”。
宋浚吉的“人心道心”说大体亦接续朱子、李珥之思路而讲。在他看来,“朱子之序,历叙上古圣王道统之传,‘危微精一’十六字,实万世心学之渊源”④。宋浚吉以为“人心修之便是道心,自道心放出便是人心”⑤,他很注意二者的相互转换性。及至晚年特别强调气之发用时的省察功夫,要求对人心时时严加防范。“深加省察如有一念之差用,力速去焉。”⑥至于人心与道心的不同,宋浚吉解释道:“心之本体而言,未发之前理为主,既发之后气用事。周子云诚无为几善恶,此人心道心分歧处也。”①这表明他同样以已发、未发来区分人心与道心。
宋浚吉之“人心道心”说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心”论。首先,他强调“心”之虚灵知觉性,而且对“虚灵知觉”也有独到的理解。《年谱》中记云:“上御养心阁。侍读官金万重讲文义曰:‘虚灵心之体,知觉人之用也’。先生曰:‘此言误矣。虚灵知觉皆心之体也。其曰具众理应万事者,具众理体也,应万事用也。’”②虚灵知觉性指的是心具有不受先见左右的能动知觉之特性。宋浚吉强调知觉是体而非用,颇有个人之体悟。
其次,宋浚吉强调心之易动性。“道之浩浩何处下手用力之方,无逾于庄敬自持。真氏之言实为明白精切。每侍先王讲此书,未尝不反复咏叹于此。夫人之一心易流而难制,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心便至于放逸矣。”③既然人心易流而难制,那么如何使其保持清明之体呢?宋浚吉主张要去“物欲”,“心无物欲以蔽之,则清明之体自然呈露矣。”④
再次,在宋浚吉的学说中“心”多次被描述为“活物”,比朱子之心更具活动性。“人心是活物。终不得不用,既不用于学问,则其所用不过宦官宫妾变嬖戏玩之事而已。”⑤这一点上与其同时代的尤庵宋时烈所见略同。宋时烈说过:“盖朱子之意,以人心道心,皆为已发者矣。此心为食色而发,则是为人心,而又商量其所发,使合乎道理者,则为道心。其为食色而发者,此心也。商量其所发者,亦此心也。何可谓两样心也?大概心是活物,其发无穷,而本体则一,岂可以节制者为一心,听命者又为一心。”⑥从“心是活物”、“其发无穷”等论说中,可以看出韩国主气论学者的“心”论特色。
朱子的“心”是一身之主宰,赅备体用,兼摄形上之性理与形下之情气。如果说“一心”具众理乃其体,那么应万事者则其用;如果说寂然不动者乃其体,那么感而遂通者则其用。其“一心”实际上涵盖形上、形下两层,既是超越层面的本然之心,又是经验层面的实然之心。此“心”一体两面,既存有又活动。实然形下的“心”具有活动作用的能力,由此体现超越形上之“心”,但又不是禅宗的“作用见性”。①在宋浚吉的心性论中,“心”更多是指实然形下之“心”,而又不同于阳明学所讲的一颗活泼泼的心。此一心论在工夫上有一特点,就是较为重视“志”的导向。“志”为“心之所之”,使“心”全副地趋向一个目的,决然必欲得之——所以特别强调“立志”之重要性。②宋浚吉亦是如此。他曾说过:“愿殿下勿以臣言为迂,必须立此大志焉。立志坚定,然后道统可继,治化可成矣。”③还说过:“诚能奋发大志,则何事不可做乎。”④
最后,宋浚吉对诸儒“心”论作了个概括:“圣贤论心不同有如此处,有如彼处。有从那边用工者,有从这边用工者,其归未尝不一。所谓从一方入,则三方入处皆在其中。”⑤这段话是宋浚吉向朝鲜国王讲解《心学图》时,针对李滉与李珥所论之不同而发的议论。从文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李滉与李珥的心论都有精深的了解。
在“人心道心”论方面,宋浚吉亦有极高的造诣。据《年谱》上曰:“讲心经。先生(指宋浚吉——引者注)于人心道心之辨,毫分缕析援据详尽。上叹曰:‘晓喻诚切也。’”⑥但从现存的文献中我们很难发现这方面的系统论述。材料的欠缺实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以上是从比较的角度对宋浚吉的理气说、“四端七情”说以及“人心道心”说作了简要论述。可以看出,在理气二物之分判上宋浚吉和李珥相比虽有过甚之感,却大体不出李珥“理通气局”之藩篱。而在“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上,宋浚吉则特别重视李珥的“气发理乘”说。至于“人心道心”说,宋氏的理论特色在于对朱子所言实然之“心”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