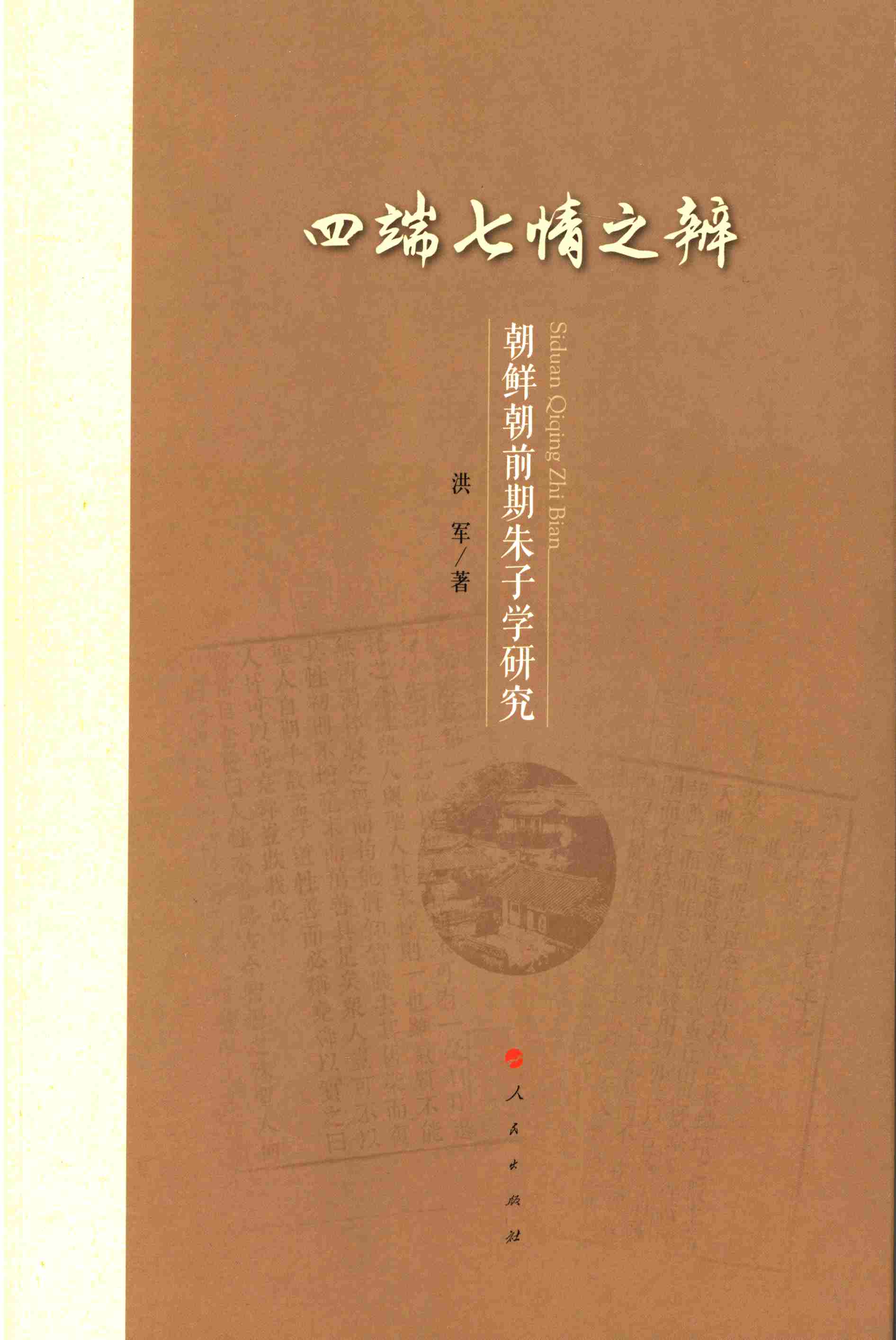内容
由于李珥和李滉对“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各自有不同的解释,故其后学也自然地划分为以李珥为宗的畿湖性理学派和以李滉为宗的岭南性理学派,即所谓“主气”派和“主理”派。而两派围绕“四端七情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的长达四百年之久的激烈论辩,又使韩国性理学具有了重视人间性理之特色。
第一节 宋浚吉与其“四端七情”论
宋浚吉(字明甫,号同春堂,1606—1672年)是17世纪韩国著名礼学家和政治家,同时亦是朝鲜朝中后期韩国性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本贯为恩津,谥文正。作为栗谷李珥的再传弟子,他在韩国儒学史上与同属畿湖学派的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年)并称为“两宋”先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宋浚吉身为畿湖学人还与以退溪李滉为宗匠的岭南学者保持密切联系,终汇诸家之长形成了颇具魅力的理论风格,为朝鲜朝礼学的形成以及性理学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本节拟从朱子、李珥和宋浚吉的思想之比较的视角,对其四七性理学说作一论述。
一、宋浚吉的理气论
理学家们大都把理气说作为其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朱子虽主理气二分,却以理本论为哲学体系之核心。而且,“理”在朱子的哲学体系中具有多种含义和用法。比如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据、事物运动变化之原因以及事物之内在规律等。另外,理又是仁义理智的总称(总名)。
李珥也同朱熹一样认为天地万物是由理和气构成。而且,他对理、气两概念还作了形上、形下的区别。李珥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则一太极而已;其气,则一阴阳而已。其为气也,有大小焉”①。他还说过“理,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②。可见其对理、气概念的认识并未超出朱子学的轨道。
李珥将“理”看作形而上之存有亦即宇宙的普遍法则和规律,使其既具事物法则规律之含义,又有伦理道德原理准则之意味。他曾说过:“对一阴一阳,天道流行,元亨利贞,周而复始,四时之错行,莫非自然之理也。”③盖以理为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之自然法则。又说过:“道学本在人伦之内,故于人伦尽其理,则是乃道学也。”④殆以理为人伦道德之准则。这与朱子对“理”概念的界定是基本相同的。
不过,在理、气两个概念的具体特性的认识上,李珥与朱子似乎又有所不同。这也是李珥为解决朱子所面临的理何以为万化之本的这一理论难题而进行的尝试。他将“理”理解为无形无为而又纯善的形而上之存有。“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宰者,理也。”⑤而且,“理气无始,实无先后之可言。但推本其所以然,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⑥。不过这里需注意的是,在李珥理气论中,理与气是“浑沦无间,无先后、无离合”⑦的关系,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在他看来,理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基础。“朱子所谓‘温和慈爱底道理者,即所谓爱之理也。’底字之字同一语意,何有不同乎!大抵性即理也,理无不善。”①“理”作为慈爱之所以然的形而上本体乃纯善之存有。“夫理上不可加一字,不可加一毫修为之力,理本善也,何可修为乎?”②因此,在人的行为中合乎理的便是善,否则即为恶。相对于理的“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气则具有“有形”、“有为”、“湛一清虚”之特性。
朱子主张气是有形与无形的统一。一方面,他认为“气聚成形”③,即有了气物才得以聚而成形(有形之物便是气);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地之间存在无形之气,比如“声臭有气无形,在物最为微妙,而犹曰无之”④。
李珥则明确提出理无形而气有形。“气局者何谓也?气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后也。”⑤作为物质的、有形象的存在,气属于与本体界相对的现象界。理作为形而上之存有,其超越性、普遍性必须通过气来呈现和实现。“有形有为而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⑥所以在李珥理气论中理与气是相互并举以显示其内涵的一对范畴。同时,气又具有“湛一清虚”性。李珥把气之本然状态解释为“湛一清虚”⑦或“湛然清虚”⑧的“浩然之气”。他说:“气之本然者,浩然之气也。浩然之气,充塞天地,则本善之理,无少掩蔽。”⑨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立场出发,认为不仅理具分殊性,而且气亦具分殊性。“一气运化散为万殊,分而言之,则天地万象各一气也;合而言之,则天地万象同一气也。”⑩由此而言,李珥的“理一之理”和“分殊之理”分别是依附或挂搭于“气一之气”和“分殊之气”的实理,作为气之本然者的浩然之气也是与“理”一样纯善之存有。而天地万物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气的有形有为之特性使其在时空的演化中出现了变异。
作为栗谷学派之嫡传的宋浚吉对朱子与栗谷皆十分推崇。他在进呈给国王的《写进春宫先贤格言屏幅跋》中便引了栗谷李珥的“道统之传,始自伏羲,终于朱子。朱子之后,又无的传”①一语,明确将朱子视为儒家道统的最后传人。同时,宋浚吉对李滉也表现出相当的尊敬。他在经筵侍讲时还多次引用李滉和郑经世(字景任,号愚伏,亦称为石潨道人或松麓,1563—1632年)等②岭南学者的言论进行讲解。他在晚年所作《记梦诗》中写道:“平生钦仰退陶翁,没世精神尚感通。此夜梦中承诲语,觉来山月满窗栊。”③表现出其洒脱不羁的治学风格。
在理气论方面,宋浚吉的学说大体承袭了其师沙溪金长生(字希元,号沙溪,1548—1631年)的理论,后者被视为李珥的嫡传弟子。金长生20岁入李珥门下受学,后又从学于龟峰宋翼弼和牛溪成浑等人。
作为金长生的弟子,宋浚吉也用形上、形下来规定理、气两个概念。他对《易》大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解释说“器即气也,道即理也,道器之分固如是”④。可谓径直以道器诠表理气。关于“理”与“道”的关系,程颐曾说过:“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⑤宋浚吉亦以为然。在他看来,“道”和“理”同实而异名,皆具万理而无形无象。
对于理、气之界定,宋浚吉仍以“有形”、“无形”以及“有迹”、“无迹”为判分的标准。他说过:“气有形可见,故曰形而下。下者,指有形、有迹而言也。理于物无所不在,而无形可见、无迹可寻。故曰形而上。上者,超乎形迹之外,非闻见所及之谓也。”⑥
与其同时的宋时烈虽亦用形上、形下区分理气,但相比而言要较宋浚吉委婉一些。宋时烈有言:“所谓道者理也,所谓器者气也”①,他还说过“自人物之形象言之,其虚而能为所以然者是理,故谓之上。其经纬错综,能此形象者是气,故谓之下云尔”②。
宋浚吉的这一解释似乎更为合理而简明。不过,也易使人产生过甚其词之感。如其所言“子思既以一道字符串费隐说,道固形而上之理也,非杂以形而下之气也”。③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一点上更近于退溪之学。栗谷之学强调的是理气之不离,亦即理与气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
在理气关系的问题上,宋浚吉仍以朱子和李珥的理气观为基础来解释理如何成为气之所以然。他认为“有是形必有是理”,而且理之于物如“诗所谓有物有则者也”④。肯定了理对于气的主宰作用和意义。接着,宋浚吉还借体用这对范畴来说明理何以是物的“所以然”。他指出:“父子、君臣是形而下之器也,是物也。父而慈、子而孝、君而义、臣而忠是形而上之道也,是则也。慈孝义忠,此所谓理之当然者,所谓费也,用也。所以慈、所以孝、所以义、所以忠,此理之所以然者,至隐存焉,所谓体也。推之万事万物莫不皆然。”⑤宋浚吉进而以“理堕气中”解释理气如何生成万物。“理堕气中,气能用事,而化生万物。即所谓气以成形,理已赋焉者也。”⑥理与气是二物还是一物以及理为“实有之一物”还是“非别有一物”始终是困扰性理学家的理论难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在这一问题上朱子的态度是既讲理气不相分离,还强调理与气“决是二物”。对此元代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吴澄(字幼清,号草庐,1249—1333年)则提出“非别有一物”说,对朱子理气论从理论结构上作出了重要修正。吴澄以为“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有此气即有此理。”①他否定理的实体性,强调理只是气之条理和规律。于此也可看出,在理的问题上朱子后学中已出现“去实体化”的转向。②此后被世人称为“朱学后劲”的罗钦顺则明确提出“理气一物”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③整庵指出理并不是形而上的实体,而只是气之运动的条理或规律。他大胆宣称:“仆从来认理气为一物。”④朱子后学的这一理论动向也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性理学家。如前文所述,《困知记》传入韩国后,李滉即从述朱之立场出发特地撰写《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驳整庵异说。他尖锐指出罗氏的“理气一物”说是“于大头脑处错了”⑤。李珥对罗氏学说的评价则稍有不同:“整庵则望见体,而微有未尽莹者,且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而其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理气为一物也,所见未尽莹故言,或过差耳。”⑥不管怎样,李滉和李珥皆反对“理气一物”说,而以朱子之理气“不离不杂”、“决是二物”为不刊之论。
宋浚吉亦追随其后而以理气为二物,从他维护李珥学说之立场中便可概见。宋浚吉以为“稷乃谓其(指栗谷——引者注)学以理气为一物,不以可笑可哀之甚乎。邪说肆行而莫之禁,则其眩乱注误,将至惑一世之人,其为祸岂不下于洪水猛兽哉”⑦。
朱子理气说的二元论结构必然会面对理气先后、理同气异、理气聚散等难以解答之问题。对此理论困境,李珥提出“理气之妙”说以为解释这些问题的理论基础。
宋浚吉则在继承朱子和李珥理气观同时,还对他们理气为二物的思想作了如下总结:“若以有形无形言,则器与道为二物;以在上在下言,亦为二物。须如此说方见得即形理在其中,道与器不相分。”①继“理堕入气”说,宋浚吉又提出理气“妙合而凝”说。他写道:
廉溪所谓阴阳一太极,即所谓器即道也。《性理群书》注错误处甚多,至或不成文理,而此条所释精粗本末则无误矣。若依李珥说,则精粗本末之下,当着吐也。若然则释阴阳太极,不成说话矣。盖大而莫能载,小而莫能破者,无非器也,而理无所不在。子思所谓费而隐,子夏所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程子所谓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与来示所引朱子语皆一义也。理固如此,本无可疑,但此所谓精粗本末无彼此一句,分明是贴阴阳太极字说,以为理与气无彼此耳。非泛论气有精粗本末也,如何。幸更细思之,先贤说话横说、竖说,各有攸当,最忌相牵强合作一说……按妙合云者,理气本浑融无间也。此乃理气混合无间隔也,乃阴静时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此乃阳动成形时也。②
对于理气妙合而凝,宋浚吉进一步解释道:妙合与凝是两项事,而《性理群书》注把妙合与凝合为一项事不符合朱子本意。他还以为《性理群书》注解把“妙合而凝”解释为妙于凝合无间断是有所未稳。“无间断也。间断字,恐未稳,以间隔释之,则未知如何。”③对于理气“浑融无间”思想,李珥总结前人关于理气关系的论述时也曾提出过,曰:“理气浑然无间,元不相离,不可指为二物。”④但是,李珥并未对“无间”一词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宋浚吉则将“无间”释为“无间隔”,表明他对名言的义理分际异常敏感。理气“浑融无间”说,是“理堕入气”说的有益的补充。
此“浑融无间”说似有类于明代理学家薛瑄(字德温,号敬轩,1389—1464年,谥文清,河东学派的缔造者)的理气“无缝隙”说。薛氏以理如日光、气如飞鸟之喻说明气有聚散而理无运动。结果还是理气看成有“缝隙”的。对于“堕入”说,罗钦顺批评道:“夫既以堕言,理气不容无罅缝矣。”①因为“堕入”一词本身隐含着理堕入气之前,理同气是被分隔着的意思。②尽管宋浚吉对理气“浑融无间”作了精心的解释和字面上的调整,但还是很难用这一主张来圆满解释理同气异、理气聚散的问题。
于是宋浚吉援引了李珥的“理通气局”说,并对此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李珥)至于理通气局之论,发先贤所未发。形状理气本体,直接分明,可以开悟后学于百世。非其学问精旨超特绝出于人者,安能及此。谓理通气局,则其分别理气,可谓极明白矣。③
“理通气局”说是栗谷为回答理同气异问题而提出。关于“理通气局”这一命题,李珥认为“理通气局四字,自谓见得,而又恐读书不多,先有此等言,而未见之也”④。尽管佛教华严宗有理事通局之说,但是以“理通气局”四字表述理气同异、理气聚散却是李珥的独见。虽然其思想也受到程伊川的“理一分殊”和朱子的“理同气异”思想的影响,但这一命题的提出更多缘于李珥对“气发理乘”思想之发挥。因此,在其文章中“理通气局”说往往与“气发理乘”说相互对举——如,“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⑤。
由上所述,在理气论方面宋浚吉承接朱子和李珥之说认为,世界万物皆由理与气构成。而且,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规定上也大体追随了栗谷的学说。他比李珥更强调道器之分别和理的“无迹、超乎形迹”之特性。在这一点上,宋浚吉似乎具有某种折中李滉与李珥理气说之倾向,其作为主气论学者的理论特色并不明显。若对宋浚吉理气说作一概括的话,可以说其理论主要由“理堕气中”说、“理气浑融无间”说、“理通气局”说组成。三者在其学说中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系统。但其对“理”的理解方面仍未超出传统的内在实体说之藩篱。
二、宋浚吉的“四端七情”论
前已述及,“四端七情”之辨是朝鲜朝性理学的中心论题之一。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家们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先是围绕理气之“发”产生了歧义。
李滉在手订郑之云的《天命图说》过程中,将“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奇大升则从自己的“理气浑沦”思想出发,对李滉之说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①在奇氏看来,所谓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②。四端虽为纯粹的天理之所发,但只是发乎七情中的苗脉而已。理气虽然有所分别(理为气之主宰、气为理之质料),但在具体事物中却混沦不可分开。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也。③
奇氏认为四端与七情皆是情,其间并无截然之别,所以二者不可分理气而论。其观点无疑与朱子的看法更为接近。
对于奇氏的质疑,李滉答复说先儒的确未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进行探讨,而理与气在具体生成的过程中也确实不可分离,但二者因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有必要分别而论。他在回信中讲道: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
李滉进而指出情有四端七情之别亦犹性有本然气禀之异。性既然可以分理气来说,情为什么就不能分理气而言呢?他认为由于四端、七情所从来各有不同,所以可分别从主理和主气的角度分而言之。“故愚尝妄以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即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最后他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此即“理气互发”说。而奇氏之说则被称为“理气共发/理气兼发”说。
与理气之“发”问题相关的另一论题为“主理”、“主气”之分的问题。李滉有言:“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③
其实,李滉、李珥等人也并非不知朱子理气“不离不杂”之义。李滉就说过:“理与气本不相杂,而亦不相离。不分而言,则混为一物,而不知其不相杂也。不合而言,则判为二物,而不知其不相离也。”④李珥亦有理气“既非二物,亦非一物”之说。比较而言李滉着重于理气之“不杂”义,而李珥则强调理气之“不离”义。两人在理气观上的差异,直接造成在四七理气论问题上的不同理解。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思想出发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转而支持奇大升的观点。他曾说过:“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①李珥一方面批评李滉未能真正理会朱子之本意,另一方面又主张不仅七情就连四端也是“气发理乘”。
李珥对李滉理论的批评,遭到成浑的辩难。于是,继“退、高之辩”李珥和成浑之间又展开了长达六年的第二次四七大论辩。成浑基本上支持李滉的观点。他指出:“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②进而坦言:“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③可见,成氏倾向于肯定李滉的“理气互发”之说。
李珥同成浑围绕四七人心道心问题进行的数年论辩中,始终坚持其“气发理乘一途”说。在他而观,对“四七理气”之发问题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李珥有言:“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④进而举例说:“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⑤可见,依其之见四端与七情均为“气发理乘”。
在“四端七情”说上,宋浚吉基本接受了李珥的主张。《同春堂年谱》中有如下的记述:
尤庵先生曰:“日知皆扩充之说,李滉、李珥之见不同矣。”先生(指宋浚吉——引者注)曰:“非但此也,四端七情之论亦不同。国初权近始发此论,其后郑之云作《天命图》而祖是说。李滉之言本于此,而有四端理发气乘,七情气发理乘之语。故李珥作书以辨之。”上曰:“分言理气,何也。”对(按:宋浚吉)曰:“此李珥所以为未安者也。四端只是拈出七情之善一边而言,不可分两边对说。若论气发理乘之,则不但七情而四端亦然。大抵人心必有感而后发,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无先后无离合,不可道互发也。”①
前已论及,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是一位朝鲜朝初期颇有影响力的性理学家,郑之云、李滉等人的很多思想端绪皆可从其性理学说中找到理论依据。所以宋浚吉认为正是权氏的学说开了“四七”论之先河。文中宋浚吉在讲述李滉与栗谷四七理论之不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宋浚吉认为在“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上不能以分言理气的方式来解释四端与七情。气是发之者,而理则为所以发者——四端只是七情之中的纯善者。
夫孟子之言四端,所以明人之可以为善也。故特举情之善一边言之,非谓四端之外更无他情也。若人情只有四端,更无不善之情则人皆为圣人也,故四端只拈出情之善者而言也。《记》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即人情善恶之总称。七情中之恶者,与四端为对则可。若以四端与七情相对则不可。李滉四七相对之论,虽因权近旧说,而未免失于照勘。义理天下之公也,学者穷格之功,只求义理之所在。若心有所疑而不为辨析,则此理终晦而不明矣。昔程子作易传,乃竭一生之精力,而朱子指其差吴处甚多。饶鲁、陈栎等至有愿为朱子忠臣,不愿为朱子佞臣等语,虽程朱之说,或未免有可疑处。况李滉之言,何可谓尽无差处乎。今以此为李珥之疵,其无识甚矣。李珥四七书,识见之超迈,言论之洞快,前古诸儒罕有及者。②
在宋浚吉看来,四端与七情并非“二情”,二者是“七包四”的关系也就是说七情作为人类情感之总称内在包含四端。他明确反对李滉将二者并立为二物的思想。
在谈论李滉与李珥理气说之不同时,他还对“气发理乘”说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盖退溪先生论四端七情云:“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栗谷先生辨之甚详。无虑数十百言,其大意曰“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者无所发。所谓气发理乘之者,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然云云”。先师(指金长生——引者注)常以栗谷之说为从。非特先师之见为然,外舅氏(指郑经世——引者注)之见亦然。弟常问之曰:“退溪、栗谷理气说不同,后学将何所的从。”答:“恐栗谷说是。试以吾身验之,如入家庙则心便肃然,是敬畏之发也。而即其肃然者,乃气也云云。”至今言犹在耳……栗谷此论真可谓百世以竢而不惑,使退陶而复作,亦必莞尔而笑。①
宋浚吉的岳父愚伏郑经世是当时岭南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宋氏引愚伏为同调以为“气发理乘”论张目。他还试图说服其他退溪门人接受这一观点。
朱子也认为四端和七情皆为性之所发的情感。他在《孟子集注》中讲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②宋浚吉对四端也有自己的解释。“有诸内而形诸外者,谓之端也。人心本善,于此可见。”③在宋浚吉看来,四端乃有诸内而形诸外者,属于已发之情——但又根于仁、义、礼、智而为人性之善。对于“性”、“理”之关系他解释道:“大抵性字从心从生,与理字不同。理堕在气中者,方谓之性。故曰‘性即理也’。盖谓在人之性,即在天之理也。”④
在四端中,宋浚吉特别重视恻隐之心。他在与愚伏先生的信中提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恻隐之心,心之生道也。”①宋浚吉强调“恻隐之心”在四端中的统摄作用。“人无恻隐之心,便是死物,犹鱼之不得水则不生也……恻隐便是初动时,才动便见三者之分界。如春不生则夏不长,秋不收而冬无所藏矣。此可见恻隐统四端也。古人观庭草庐鸣以体仁,此是天机流动活泼泼地也。”②可见,他将“恻隐之心”视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
不仅如此,宋浚吉还对仁、义、礼、智作了如下论述:
夫仁礼属于阳,义知属于阴,而阳德健、阴德顺,健顺五常乃人之所同得。而并言物者,凡物亦自得其一端,如虎狼之仁、蜂蚁之义皆是。故谓之各得其所赋之理也。③
此段引文不无泛性善论之意味,而其论说基础正是李珥的“理通气局”思想。由此可见朝鲜朝后期“人物性同异论”论辩之理论端绪。
宋浚吉对李滉与李珥的四端七情说详论其异同。他指出李滉之误,而对李珥“气发理乘”之思想则颇为推重。尽管宋浚吉在理气概念的界定和理气关系的理解上有折中二李之倾向,但从其四七理气论中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畿湖派(主气论)的为学性格。
三、宋浚吉的“人心道心”论
对性情善恶及人心道心问题的讨论可以视作四端七情问题在更深层次的展开。作为朱子学的重要论题,人心道心问题与公私、理欲之探究皆有密不可分之关系。
二程认为人心与人欲相联,而道心则与天理相通。伊川有言:“‘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④明道则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⑤伊川遂将“道心”和“人心”对立起来,以前者为正而以后者为邪。在他看来,唯有用“精一”功夫护持“道心”,才能令其不被“人心”扰乱。“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①职此之故,伊川明确主张存天理以灭人欲。
朱子也说过:“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②他将十六字心传视为古圣相传之“道”。朱子是这样理解分人心、道心之异的:“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③他进而说明:“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④“道心”为根于义理之正,而“人心”则根于耳目之欲。
仅就以已发、未发而论,则人心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点上李珥也与朱子所见略同。但是朱子主张二者皆发自“一心”,李珥主张二者发自“一性”。那么,人何以会有人心、道心两种不同的知觉?朱子认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⑤。这就是朱子独到的解释。他还纠正了伊川的说法,提出人心并非皆“恶”。“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⑥朱子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人的生存欲求和生理欲望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⑦。朱子虽然提出人心道心相分,却主张二者“不可作两物看,不可于两处求也”⑧。可见,在朱子哲学中人心道心问题虽与天理人欲问题相对应,但不似后者那样显得十分紧张。
李珥则继承朱子的学说并加以发挥,提出了“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说法。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
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①这是基于“意”的商量计较作用的,人心道心可互为转变、转换的理论。因此李珥认为人心道心可以相互转换,因而不能将其判然两分。
对于人心道心与四端七情的差异,李珥指出:“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②人心道心之名源于性命形气之别,四端七情则与此不同——后者之区别是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四端属于七情之善的一类,故而七情可兼四端。而人心与道心因含对比之意,所以无法相兼而只能互为始终。
不过,李珥认为“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③他肯定了人心亦有善的层面,此为李珥对李滉学说的有益补充。我们知道李滉以“理贵气贱”为据将人心等同人欲,进而将人欲归之为“恶”。
宋浚吉的“人心道心”说大体亦接续朱子、李珥之思路而讲。在他看来,“朱子之序,历叙上古圣王道统之传,‘危微精一’十六字,实万世心学之渊源”④。宋浚吉以为“人心修之便是道心,自道心放出便是人心”⑤,他很注意二者的相互转换性。及至晚年特别强调气之发用时的省察功夫,要求对人心时时严加防范。“深加省察如有一念之差用,力速去焉。”⑥至于人心与道心的不同,宋浚吉解释道:“心之本体而言,未发之前理为主,既发之后气用事。周子云诚无为几善恶,此人心道心分歧处也。”①这表明他同样以已发、未发来区分人心与道心。
宋浚吉之“人心道心”说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心”论。首先,他强调“心”之虚灵知觉性,而且对“虚灵知觉”也有独到的理解。《年谱》中记云:“上御养心阁。侍读官金万重讲文义曰:‘虚灵心之体,知觉人之用也’。先生曰:‘此言误矣。虚灵知觉皆心之体也。其曰具众理应万事者,具众理体也,应万事用也。’”②虚灵知觉性指的是心具有不受先见左右的能动知觉之特性。宋浚吉强调知觉是体而非用,颇有个人之体悟。
其次,宋浚吉强调心之易动性。“道之浩浩何处下手用力之方,无逾于庄敬自持。真氏之言实为明白精切。每侍先王讲此书,未尝不反复咏叹于此。夫人之一心易流而难制,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心便至于放逸矣。”③既然人心易流而难制,那么如何使其保持清明之体呢?宋浚吉主张要去“物欲”,“心无物欲以蔽之,则清明之体自然呈露矣。”④
再次,在宋浚吉的学说中“心”多次被描述为“活物”,比朱子之心更具活动性。“人心是活物。终不得不用,既不用于学问,则其所用不过宦官宫妾变嬖戏玩之事而已。”⑤这一点上与其同时代的尤庵宋时烈所见略同。宋时烈说过:“盖朱子之意,以人心道心,皆为已发者矣。此心为食色而发,则是为人心,而又商量其所发,使合乎道理者,则为道心。其为食色而发者,此心也。商量其所发者,亦此心也。何可谓两样心也?大概心是活物,其发无穷,而本体则一,岂可以节制者为一心,听命者又为一心。”⑥从“心是活物”、“其发无穷”等论说中,可以看出韩国主气论学者的“心”论特色。
朱子的“心”是一身之主宰,赅备体用,兼摄形上之性理与形下之情气。如果说“一心”具众理乃其体,那么应万事者则其用;如果说寂然不动者乃其体,那么感而遂通者则其用。其“一心”实际上涵盖形上、形下两层,既是超越层面的本然之心,又是经验层面的实然之心。此“心”一体两面,既存有又活动。实然形下的“心”具有活动作用的能力,由此体现超越形上之“心”,但又不是禅宗的“作用见性”。①在宋浚吉的心性论中,“心”更多是指实然形下之“心”,而又不同于阳明学所讲的一颗活泼泼的心。此一心论在工夫上有一特点,就是较为重视“志”的导向。“志”为“心之所之”,使“心”全副地趋向一个目的,决然必欲得之——所以特别强调“立志”之重要性。②宋浚吉亦是如此。他曾说过:“愿殿下勿以臣言为迂,必须立此大志焉。立志坚定,然后道统可继,治化可成矣。”③还说过:“诚能奋发大志,则何事不可做乎。”④
最后,宋浚吉对诸儒“心”论作了个概括:“圣贤论心不同有如此处,有如彼处。有从那边用工者,有从这边用工者,其归未尝不一。所谓从一方入,则三方入处皆在其中。”⑤这段话是宋浚吉向朝鲜国王讲解《心学图》时,针对李滉与李珥所论之不同而发的议论。从文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李滉与李珥的心论都有精深的了解。
在“人心道心”论方面,宋浚吉亦有极高的造诣。据《年谱》上曰:“讲心经。先生(指宋浚吉——引者注)于人心道心之辨,毫分缕析援据详尽。上叹曰:‘晓喻诚切也。’”⑥但从现存的文献中我们很难发现这方面的系统论述。材料的欠缺实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以上是从比较的角度对宋浚吉的理气说、“四端七情”说以及“人心道心”说作了简要论述。可以看出,在理气二物之分判上宋浚吉和李珥相比虽有过甚之感,却大体不出李珥“理通气局”之藩篱。而在“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上,宋浚吉则特别重视李珥的“气发理乘”说。至于“人心道心”说,宋氏的理论特色在于对朱子所言实然之“心”的强调。
第二节 宋时烈与其“四端七情”论
宋时烈是17世纪韩国性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推尊朱子与李珥,穷研性理,为朝鲜朝性理学、义理学、礼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节主要通过其理气论的分析,来探讨宋时烈的四端七情理论之特色。
一、宋时烈的理气论
理与气的关系问题是理学的基本问题,因而理气论在性理学家的思想体系中总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为栗谷学派之嫡传,宋时烈对朱子与栗谷推崇有加。他曾说过:“窃念孔圣以来,集群儒之大成,唯晦庵夫子,则后学之所依仿,无小大巨细,当一于是矣。”①还说过:“盖吾东理学,至栗谷而大明。栗谷以前,虽如晦斋之贤,其学如此。”②
在性理学方面宋时烈与朱子、李珥一脉相承,主张世界万物皆由理与器构成而二者有形上、形下之区分。“凡物之有形者,皆有理气。所谓道者理也,所谓器者气也。”③那么,理气又如何落实于人物之上?宋时烈认为“自人物之形象言之,其虚而能为所以然者是理,故谓之上。其经纬错综,能此形象者是气,故谓之下云尔”④。
宋时烈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规定上,也追随李珥否定理之发用性,从而肯定气之运动性。在他看来,“理是,无情意、无造作底物事”,⑤而“有形有为而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①。理永远具有主宰性。“一阴一阳者,气也;而使一阴一阳者,理也”,②理虽无形无为却能为“有形有为之主者”。③可见,宋时烈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认识上大体还是遵循了李珥的理气观。这一点可由其以下言论得到确认。
来示以此合之于栗谷所谓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之说,极亲切矣。④
栗谷所以非退溪说者,专在于“理发气随”一句,此说是非,当于中庸天命之谓性注可见矣。其曰气已成形,理亦赋焉者,与理发气随者,同乎异乎?⑤
不过,在“气”的解释上宋时烈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过“按理无穷,故气亦无穷”⑥,还说过“气之无限量,亦由理之无限量故也”⑦。在此宋时烈给“气”赋予了超时空之含义,这是对李珥气论思想的有益的补充。在李珥处,“气”具有有形之特性,此乃其“理通气局”说的立论基础。但是李珥为其“理通气局”说建立理论基础的同时,也给自己“理气之妙”思想预设了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解释理气之间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理”的无限性与“气”的有限性在其学说中无法协调,此为李珥学说在理气概念之界定上的一个理论缺陷。
宋时烈提出“理无穷,故气亦无穷”的命题,不仅弥补了栗谷理气说的理论缺陷,而且还丰富发展了朱子的“气”论思想。“气”作为与“理”相对言的理学核心概念,在朱子学的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气”的任何创新之阐释都会对朱子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朝鲜朝主气论学者在这一方面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可由宋时烈之“气”论窥其大概。
讨论朱子哲学首先会遇到理气有无先后的问题。此一问题颇能反映朱子学的理论特性。
朱子先是主张“理先气后”论。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①在他看来,天地万物皆由理与气构成——没有无理之气亦无无气之理。但就本源上说,理是先于气而存在。
到了晚年朱子开始意识到,其“理先气后”说容易引起一些不易解决的矛盾。如伊川强调“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而按理先气后论,宇宙的阴阳就必须有个开始。所以朱子对其早先的说法进行了修正。“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②终将理先气后确定为逻辑上的在先。
在理气论的这一核心问题上,李珥基本上与朱子所见略同。他说:“理气无始,实无先后之可言,但推本其所以然,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圣贤之言虽积千万,大要不过如此而已。若于物上观,则分明先有理而后有气,盖天地未生之前,不可谓无天地之理也,推之物,物皆然。”③此话尽显以理为本的李珥在理气论上的基本立场。
宋时烈在继承朱子、李珥之说的基础上也作出了自己的建树。他的理论特色是在理气论中引入了“形”这一概念并借以说明理气关系。
形而上形而下,退溪沙溪二先生所释,殊不甚安。故常以为当以形字为主而处,道字器字于形之上下,以形道器三件物事所释,井井无难矣。二先生则以形与道为二,而形与器为一似与孔子本旨不合矣。盖道则理也,器则气也。理气妙合而凝,以生万物之形,故中庸首章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是皆以理气形三字,分别言之矣。
既以理气形三字分别言,则当以道为形之上,器为形之下矣。①宋时烈在说明形与道之不同的同时也强调形与器之不同,目的在于使理气二者皆统一于形。如此则令李珥“理气之妙”说得到更好的解释。李珥的理气说中,理的无限性与气的有限性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宋时烈以理气形“三件物事说”区别三者,还特别强调了理自具于形这一点。理被赋予形是性理学家们的一般解释。宋时烈特以“自混融”和“自无间”来说明理气之共在性,其理论之前提便是“理自具于形”。
盖人物未生时,理与气本自混融而无间,故气聚成形之时,理自具于此形之中矣。故中庸注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此岂非十分分明者耶。②
宋时烈强调气聚成形之时理便自具于此形之中,其说相较理赋气说更适于说明李珥的“理气之妙”。同时也是“气发理乘”说有益之补充——宋时烈即以此否定“理发气随”说。他指出:“栗谷所以非退溪说者,专在于理发气随一句。此说是非,当于《中庸》天命之谓性注可见矣。其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与理发气随者,同乎异乎?”③
宋时烈理气说的另一个理论特点便是以体用范畴来说明李珥的“理通气局”思想。他说:“所谓气局者何谓也,阳之体非阴之体,阴之体非阳之体,则所谓局也。所谓理通者何也,阳之理即阴之理,阴之理即阳之理,则所谓通也。局故两立,通故两在。非局则通无所发见,非通则局何以原始乎。必著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后器亦道道亦器,而精微之蕴,活泼泼矣。”④李珥曾对“理通气局”说有过自己的解释。相比李珥“本末先后”说,宋时烈的“体用”说显然更具理论性。且以体用范畴来解释“理之一”与“气之局”还可使李珥“理通气局”说更具说服力。由此可见,继退溪、栗谷之学展开的朝鲜性理学至宋时烈时已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
宋时烈进而又将错综复杂的理气关系作了如下的总结。《宋子大全》有载:
理气之说,莫详于廉洛关闽。而或言理有动静,或言理无动静,或言其理气之有先后,或言其理气之无先后,其言不一。若相牴背,而学者没患于难为会通。于是尤庵先生出,总而断之,曰:“理气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从理而言者,有从气而言者,有从源头而言者,有从流行而言者。盖谓理气混融无间,而理自理,气自气,又未尝夹杂,故其言理有动静者,从理之主气而言也。其言理无动静者,从气之运理而言也。其言有先后者,从理气源头而言也。其言无先后者,从理气流行而言也。斯言一出,而众说之不齐者可齐,而穷理之士,始得其路径矣。①
理气有无先后以及有无动静等问题是关乎朱学思想性格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困扰朱子后学的理论难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关讨论直接涉及理如何生气、又如何派生万物的理学本旨,遂成朱子后学最为热衷探讨的问题。作为朱子学的忠实信徒,宋时烈对此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从理、气、源头、流行等不同的角度对相互各异的理气说进行了概括说明,进而从源头解释了理的主宰性问题。沙溪金长生的后裔金正默在《过斋遗稿》中对宋时烈观点有所记载,抄录如下:
从源头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故谓理为主宰,又谓之使动使静。②
从源头处,论其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其下所乘之机则却就流行处,论此理无形状无造作,只乘此气而运用也。言各有所当也。盖理气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从理而言者,有从气而言者,有从源头言者,有从流行言者。如不能活看,则节节泥滞也。③
以上是对朱子、李珥与宋时烈之理气论的比较分析。简要地说“理”在朱子哲学中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之特性。而在李珥哲学中则具有“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相对于理的“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气则具有了“有形”、“有为”、“湛一清虚”之特性。宋时烈在理气的解释上大体承接朱子、李珥之说,而对“气”的探讨更为深入。宋时烈“气亦无穷”、“气之无限量”的思想不仅丰富了朝鲜朝性理学,而且为朱子学“气”论之发展也作了探索。
要之,丽末鲜初传入韩国的朱子学历经几代韩国性理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其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朱子学本身得到了全新的阐发,而且韩国性理学也形成了颇具自家特色的理论体系。如以“理一分殊”为特征的朱子理气说传至李珥则发展成以“一而二、二而一”为特征的“理气之妙”说以及“理通气局”说。宋时烈则在笃守朱子、栗谷之说的基础上将其理论进一步细密化,提出了以“理、气、形三件物事”为特征的理气说,同时也对李珥的理气说作了有益的补充。宋时烈理气说尽管受到朱子和李珥学说的影响,但其自家特色也明显可见。
二、宋时烈的“四端七情”论
“心”、“性”是理学的核心范畴,因而理学也被称为“心性”之学。性理学之心性学说论域甚广,但首要问题仍是心、性、情、意等概念的定义。从其对这些概念的界定中可见性理学之特点。
关于心、性、情、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宋时烈有如下的说明:
盖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自器中泻出者也。只言虚灵而不言性情,则是无水之空器也;只言性情而不言虚灵,则是水无盛贮之处也。是三者缺一则终成义理不得,岂得谓之明德乎。盖或者之意,以所谓虚灵不昧者,为释明德之意,故有此说。而不知所谓明德者,是心性情之总名也……盖性是心之理也,情是心之动也,意是心之计较也。于一念才动处,便有计较也,心是性情意之主也。此四者虽有性情心意之分说,而只是就那混沦全体上各指其所主而言,其命名殊而意味别耳。不是判然分离,而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是一个地头,意是一个地头也。故心发性发,虽有二名,然心之体谓之性,心之用谓之情,则心性之发,果有二耶。为情为意,虽有分言,然心之才动谓之情,才动而便有计较底谓之意,则情意之用果有分耶?性之发谓之情,虽谓之性发,非无心也;心之发谓之意,虽谓之心发,非无性也……大抵性是无作为底物,心是运用底物,情是不知不觉闯然出来,不由人商量底物,意是计较谋为底物。①
宋时烈在本段引文中对心、性、情、意之意涵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重视心的知觉作用,以为“心是知觉运动的物”②,“盖心之为物,洞彻虚灵,天理全具,而又囿于形体之中,则不能无人欲之私矣。”③这说明宋时烈和朱熹一样肯定心之知觉思虑作用。他尤为看重心之虚灵义。“心之虚灵,分明是气欤,先生曰分明是气也。”④从“心是气”到“意”为计较谋为底物——宋时烈所做界说是对李珥“心”论和“意”论的继承。这表明其心性结构亦为心、性、情、意四分之逻辑结构。他也强调“心是气,而性是理。气即阴阳,而理即太极也”⑤。可以看出,在“心”论方面相较朱子,宋时烈更赞同李珥的见解。他继承了李珥“心主心性情意”以及“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的思想。
不过,宋时烈在心论方面特别重视心之虚灵性与感应性。对此他也以体用范畴进行了说明。“心有真体实用,体如鉴之明,用如能照。”⑥依性理学“体用一源”之思想,心之虚灵性与感应性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加之,在宋时烈的理气论中气具有与理一样的超时空之无限性,其心论遂为性理学“天人合一”之范例。宋时烈有言:
道体无穷,而心涵此道,故心体亦无穷。故道谓太极,心为太极。①“心为太极”虽似突兀,但若基于其“理气形三件物事说”亦可推出上述结论。理气统一于形,二者混融无间于心。“大抵心属气,性是理,理气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②
那么,心与性是否是可以合一的呢?在宋时烈看来,“心性虽可谓之一物,然心自是气,性自是理,安得谓之无彼此?”③他进而指出:“所谓性者,虽非舍气独立之物,然圣贤言性者,每于气中拈出理一边而言,今便以气并言者,恐未安。”④
“性”作为与心相对言的范畴成为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概念。朱子把性的意涵规定为仁、义、礼、智。他说:“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⑤,而“性者人之所受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⑥。以仁、义、礼、智为性是朱子学乃至整个理学的思想基础。朱子笃守孟子“性善论”,而力反荀子“性恶论”。因此他总是从性善出发对心、性关系做了论述,“性虽虚,都是实理。心虽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万理”⑦。那么“恶”何所从来呢?在此,朱子继承了张载有关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思想以及程颢的“性即气”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⑧。天地之性乃人之本质,气质之性则为人之习染,流衍而为性情才气——前者纯粹至善,后者则有善有恶。二者之关系明显是理与气的关系。
宋时烈是这样理解天地、气质之性的:
所谕天地之性,鄙意有所不然者。盖所谓性者,从心从生,则正以人物已生而言也。于天地下,此性字不得,只可谓之命也。至如张载所谓天地之性云者,亦曰天地畀之性云,非指在天之太极而言也。①他进而指出:
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此二名虽始于程、张,然孔子性相近三字已是兼本然气质而言也。孟子开口便说性善,是皆说本然。然其曰牛之性马之性,则以气质而言也。孟子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及大誓曰:“我武维扬,侵于之疆”。此上下文次序似互,然集注所不论则何敢以为然乎。朱子说颇有初晚之异,亦有《语类》、《大全》之不同,不可执一。是此而非彼,徐观义理之所安可也。②
韩国性理学者最为关心的四端七情问题便与此问题密切相关。朱子在论及四端时,曾说过“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这两句话在中国并没有引起注意。依朱子的解释,发者是情,而情则属于气,在“理”上不说发。所谓“四端是理之发”,可解释为四端是依理而发出的情,但是不能说情是从理上发出来的。李滉据此力主“理气互发”,似乎认为理亦能发。其实,依理学之本旨,“理”应为气发时所当遵循的原理,即发之所以然,而实际上的“发者”则是气。
李珥对于朱子的这个思路有相应之契会。他从“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理乘”③以及“理者,气之主宰;气者,理之所乘也”④的思想出发,认为在心所统的性情中未发为性,而已发为情。正如本然之性、气质之性都是性一样,四端、七情也都是情。本然之性不兼气质,气质之性则兼本然之性。同样,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却能兼四端。四端是专言情之善,而七情则兼言情之善恶。“凡情之发也,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理气混融,元不相离。若有离合,则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①这就是“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李珥据此解释了情之善恶的问题。他说:“性具于心,而发为情。性既本善,则情亦宜无不善,而情或有不善者,何耶?理本纯善,而气有清浊。气者,盛理之器也。当其未发,气未用事,故中体纯善;及其发也,善恶始分。善者,清气之发也;恶者,浊气之发也。其本则只天理而已。情之善者,乘清明之气,循天理而直出,不失其中,可见其为仁义礼智之端,故目之为四端;情之不善者,虽亦本乎理,而既为污浊之气所掩,失其本体,而横生或过或不及,本于仁而反害仁,本于义而反害义,本于礼而反害理,本于智而反害智,故不可谓之四端耳。”②本于“气发理乘”之思理,李珥将善恶系于气之清浊。以为“理”无偏正、通塞、清浊、粹驳之异,而所乘之“气”则或正或偏,或通或塞,或清或浊——理既乘于气,便因气禀之善恶亦有善恶。
宋时烈在笃守李珥“气发理乘”说的前提下,进一步贯彻了“七包四”的思想。
《语类》论大学正心章,问意与情如何。曰欲为这事是意,能为这事是情,此与先生前后议论,全然不同。盖喜怒哀乐闯然发出者是情,是最初由性而发者,意是于喜怒哀乐发出后因以计较商量者。先生前后论此不翅丁宁,而于此相反如此,必是记者之误也。大抵《语类》如此等处甚多,不可不审问而明辨之也。理气说,退溪与高峰,栗谷与牛溪,反复论辩,不可胜记。退溪所主,只是朱子所谓“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栗谷解之曰“四端纯善而不杂于气,故谓之理之发;七情或杂于不善,故谓之气之发”。然于七情中如舜之喜文王之怒,岂非纯善乎?大抵《礼记》及子思统言七情,是七情皆出于性者也。性即理也,其出于性也,皆气发理乘之。孟子于七情中摭出纯善者,谓之四端。今乃因朱子说而分四端七情以为理之发气之发,安知朱子之说或出于记者之误也。③七情皆为出于性者,其中发而中节合乎理者即为四端。宋时烈进一步指出:
所谓喜怒哀乐者,不出于性而何?既出于性则谓之人心可乎。序文不曰人心生于形气乎。既曰出于形气,而又以其发于性者当之,岂不自相矛盾乎。如曰四端七情皆出于性,而皆有中节不中节。其中节者,皆是道心之公,而其不中节者皆人心之危也。扩充四端之中节者,则至于保四海,推致七情之中节者,则至于育万物。子思孟子所常接受者,其揆一也。①
七情中中节合理者为四端,即是道心;不中节不合理者皆有人心之危,易流于私欲。宋时烈有言:“盖人心者,非直谓人欲也。其流易入于人欲,若流于人欲,则便为私邪。私之一字,百事之病。故朱子亦尝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王者奉三无私,以劳于天下。此实至言也。”②
宋时烈依其“人心道心”说时提出了“心是活物”的思想。“所谓人心听命于道心者,乃朱子说。如以为可疑,则其所可疑者,乃在于朱子,而不在于栗翁也。大抵吾人亦不深究朱子立言之意,故未免有疑耶。盖朱子之意,以人心道心,皆为已发者矣。此心为食色而发,则是为人心,而又商量其所发,使合乎道理者,则为道心。其为食色而发者,此心也。商量其所发者,亦此心也。何可谓两样心也?大概心是活物,其发无穷,而本体则一,岂可以节制者为一心,听命者又为一心。”③“心是活物,其发无穷”——如此说法颇有王学之色彩。宋时烈将其“气”论思想进一步贯彻到心性论领域,其“心”遂较朱子之心更具发用性与活泼性。
由此可见,四端七情问题实质是性情问题。所以顺着“四端七情”之辨自然会引出性情之辨。易言之,性情之辨可视为四七之辨的逻辑延伸。与“两宋”先生同时代的明末清初著名思想界王夫之(字而农,晚号船山,1619—1692年)则在四端七情问题上提出了“四端非情”论。他认为朱子犯了“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错误。而性情分属天人——如此混淆容易导致“情”对“性”的侵蚀。在船山看来,如尽其性则喜、怒、哀、乐、爱、恶、欲炽然充塞,其害甚大。①船山以为四端不仅是道心,而且还是性。
今以怵惕恻隐为情,则又误以为以性为情,知发皆中节之和而不知未发之中也(言中节则有节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节也,中之者情也,情中性也)。曰由性善故情善,此一本万殊之理,顺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则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将以知性之不善与?此孟子所以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见端于心者言性,而不于喜怒哀乐之中节者征性也。有中节者,则有不中节者;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固全乎善而无有不善矣。②
依其之见,应以性情、道心人心来分言四端与七情。从船山与同春的四七见解中可以看到17世纪中韩儒学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向。
总之,在宋时烈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之间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一致性。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栗谷之学的忠实继承,而且折射出韩国性理学究天人之际的思想特点。韩儒往往从“天人一贯”的立场出发,将理气关系之探讨具体落实到人间性理的问题上。四端七情以及本然之性气质之性的探讨亦犹如此。
第三节 丁时翰与其“四端七情”论
丁时翰(字君翊,号愚潭,1625—1707年)是朝鲜朝中期退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一生隐居,学行为后世儒者所敬仰,被称为“退溪之隔世高足”。实学开化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星湖李瀷(1681—1763年)在其《墓志铭》中写道:“瀷少而无所知识,不能叩匧从师于并世丁先生门为平生懊恨。”③朝鲜朝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1762—1836年)则评论说:“愚潭先生学术之正,议论之公,忠谠直截之风,明哲敛约之操,卓乎与山岳齐其高,烨乎与日月争其光。己巳为坤殿抗疏,仍救宋尤庵……其论理气四七之辨,一以紫阳退溪为准则,剖折精微,细入秋毫。夫道统之传,或以亲炙,或以私淑,唯德之宗,不观名位。盖自寒冈旅轩而降,真儒醇学,唯先生一人而已。义理之积于中,出处之标于世者,皆足以承嫡传于斯文。”①可见,其学说对后世之影响何等深远。
丁氏之学本于退溪李滉,因此学者亦称其心为“退陶之心”②。丁时翰曰:“退陶之学,绍述朱子,其所以集大成卫斯道者,亦与朱子略同。而朱子之后,儒学归禅。退陶之后,异言立帜。诗教之辨,传习录之跋,不得不出。四七之辨,壬午之录,又不得不著。”③丁时翰生活的年代,学界已分裂成以“主理”和“主气”④为理论特色的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作为近畿主理论学者⑤,丁时翰同李玄逸(字翼升,号葛庵,1627—1704年)一起对李滉的四七理论作了积极维护和系统阐述。⑥本节拟以李滉、李珥、丁时翰思想之比较为中心,来探讨其性理学思想之特点。
一、丁时翰的理气论
“理”与“气”是理学家为学立论的一对核心概念,因此理气问题亦可视为宋明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⑦而朱子则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讨论理学这一基本问题的哲学家。他以理气二分且又“不离不杂”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韩国性理学家们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的过程中,对理气问题①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丁时翰便曾说过:“理气之论,实是圣门极至之源头,而吾儒及异学于此焉分。”②不过,退溪、栗谷时期有关理气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理气动静和理气体用的问题而展开。丁时翰也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
李滉继承朱子“理气二分”说。他基于理气道器之分对二者“不杂”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以及“理尊无对”的观点。李滉重视理气“不杂”义的用意在于强调理对气的主宰作用。对二者“不杂”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观的特色。他曾在《非理气为一物辩证》③一文中写道:“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④进而他还认为,理与气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同,即“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他说:“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⑤、“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⑥。李滉的此一见解,既是对朱子“理先气后”、“理在事先”思想的修正,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进一步发展。他将朱熹的理气“先后”关系转变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由此为其“四七”论打下理论基础。
李珥则与李滉不同。他继承朱子理气之不离思想并对之作了进一步的解析和阐发。其“理气之妙”说、“气发理乘”说以及“理通气局”说皆独具特色。其中“理气之妙”说尤为栗谷思想之精髓——“气发理乘”说和“理通气局”说皆为“理气之妙”说的进一步阐发。
理气之“不离”亦是李珥哲学的主要理论特色。相较于李滉之“理”,李珥的“理气之妙”思想更是其哲学中“难见亦难说”处。李珥有言:“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夫理之源一而已矣,气之源亦一而已矣。气流行参差不齐,理亦流行而参差不齐。”①与李滉相比,他虽在理气说的理论突破上有所不及,却在传承朱子理气说上超而过之。
不过,到了17世纪李珥的这一思想倾向却受到李玄逸、丁时翰等南人学者的批评。丁时翰认为,古今学问道术之异皆源于人们对古圣贤所论之“理”的片面理解。在他看来,圣贤论“理”之言各有所指——有就“体”而言者,有就“用”而言者,有就其本原之理而言者,亦有就其散殊之理而言者。如果只讲“体”之寂然不动而不讲“用”之感而遂通,则徒见本原之理赋予万物而不见散殊之理各有其则,就会导致寂而不感终归于灭的后果。丁时翰继承李滉的“尊理”之思想,由此特别重视“理”之作为。“人之为学,只患于理字上见不透。若于此实见得的确,则处心行事,岂有未尽善乎。尧舜之精一执中,孔颜之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以理为主,而使人心听命焉。若以气为主而作用为性,则其祸必至于滔天。”②可见,在丁时翰的思理中只有“理”才具有“主宰”义,气则无之。他还特别强调了以气为主作用为性的严重后果。
作为主理论者,丁时翰每从维护李滉的角度对李珥之学展开批评:
今栗谷自谓有见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而推出整庵、花潭之绪余,以攻互发之说。故于人心道心,则以为皆源于理,而遂为相为终始之说,以反或原或生之意。于四端七情,则以为皆发于气,而遂为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之说,以反理发气发之意。至于理通气局,则又以为得见整庵、花潭之所未见,阐发前圣所不言之旨。而其所谓理通者,徒归寂灭虚无之地,未有安顿着落之处。而况其云所以发之理者,虽曰乘气,而每以徒具于寂然之中,不发于感通之际为言。其云理通者,虽曰无所不通,而又未免言理于窈冥,言气于粗浅,则是理是气,常隔断阻绝,不能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而终未见浑沦之中自有分开,分开之中自有浑沦之妙矣。盖其所谓理气不相离者,非真有见于理气之不相离也,只是认气为理。至以道心为本然之气,故终始迷昧于理字上。其言本原之体者,鹘囵笼罩,都没紧要,其言发见之用者,专主气字,更不言理。一向逞气骋辩,恣诋前贤,有若莠之乱苗,紫之乱朱,使从古圣贤相传之心法,既明复晦。①
李珥对整庵十分推崇②,他曾言:“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③依丁氏之见,李珥祖述整庵以“气”为重,故徒见理气之不离以及气常载理之一面。也因之无从体验浑沦之中自有分开,分开之中自有浑沦之妙。因此丁时翰批评李珥“昧于大本”。“栗谷则祖述整庵,昧于大本而所尚者气。故发于言论者,类多轻肆凌人底规模。而流弊所及,大为吾道之深害,大本之差不差,而其所发见于言行事为之间者,亦可征矣。”④而且,他还进一步批评李珥“论‘理’之言,亦似非吾儒家法”①。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丁氏继承李滉之“理帅气卒”的思想,进而发展出“理主气辅”论。“朱子‘虽在气中,理自理气自气,不相夹杂之谓性’云者,以其理气妙合之中,理常为主,气常为辅,虽在气中,不囿于气,命气而不命于气之云尔。非以为理气各在一处而不相妙合也。”②他在强调理之主宰性的同时,还对李滉的理气二分说作了有益的补充。指出虽说理为主而气为辅,理气各自不相夹杂。丁时翰特别强调了理气之不离性。
基于其“理主气辅”思想,丁氏提出自己独到的“理气体用”说。
理至有故无不异,至无故无不同,然无者未尝无,有者未尝有,则有无非有二也……理至无而至有云者,犹言无极而太极,或言自无极而为太极者。朱子辨释甚详。又于象山答书中云,不言无极,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由此观之,至无而至有不可云。至有故无不异,至无故无不同。其下两三句,虽合有无而言,不能救上句之病者,人所易知,而敬叔之不悟何哉?敬叔之见,既已如此,故以人物之性,谓有隐显体用,而以至有当显体用,以至无当隐体用。至有至无,分作隐显体用于一性之中,与分言无极太极者,何以异哉?③
“理主气辅”和“理气隐显体用”可以说是丁时翰理气论的主要内容。从以上比较可见,丁时翰理气论虽有重视二者不离性的一面,但是其主要学说仍以主理论为特色,并以此为基础对李滉的“尊理贬气”思想和“理气互发”之说进行了积极的补充和诠释。
二、丁时翰对李珥“四端七情”说的批判
如上一章所述,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基于理学的传统观念认为人都是得“气之正”者,但是由于每个人所禀之气有清浊、粹驳之不同会有“上智、中人、下愚三等之殊”①。于是,他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四端(理)与七情(气)之间的关系。李滉以为四端之情和七情是不同性质的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二者在根源和本质上皆不相同。李滉有言:“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②他认为此论与思孟程朱之旨冥然相契。
李珥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论,他更同情奇大升的观点。李珥对李滉之说的批评遭到了成浑的辩难。由二人之书信往复,李珥的“四七”论立场更加明了。依栗谷之见,对四七理气之发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发矣。”③李珥进而举例说“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④在李珥看来,不仅七情是气发理乘,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二者均为气发理乘。
针对李珥的“气发理乘”说,丁时翰提出如下批评:
理气为物,本混融无间,推之于前,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不见其终之离。而理无眹气有迹,安有无气之理或先或后,发见于事为之间者乎。然而终古圣贤于浑融无间,不可分先后,离合之中,或截而言之,或分而言之,以明此理之命气而不命于气,在气而不杂乎气者……既曰仁之端义之端,则仁发而为恻隐,义发而为羞恶,体用不离,本末相连,可见其不杂于气而一出于理。至于七情,则虽亦出于性而初无不善,但就其性在气质,浑沦理气者而为言。故几有善恶,气易用事,理难直遂,必须观理约气,然后理始显而气听命。此朱子所以有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之言。而今者(指栗谷——引者注)不察孟子剔发言理,朱子分言理气之本意,乃以四端七情滚合为一说,概而言之曰,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专以气发一途为言,而都遗却理发一款。①
依其之见,理无形而气有形,故其作用流行皆若气之所为。但因“理”至无而至有、至虚而至实,且又具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之特性,故其乘气流行皆为自然而然,不见其有所作为。当性情寂感之际,理之神用即蔼然呈露而不可掩——四端粹然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性即为显例。因此,不能仅着眼于理气之浑沦而只言“气发”不讲“理发”。
丁时翰认为,四端与七情从结构而言皆兼备了理和气。因此,四端与七情均与气相关。只是四端并不与气相互夹杂,而七情却受其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主理和主气方得区别。以此为基础,他推导出四端和七情在“所从来”处即相异的结论。这里丁时翰所持的是李滉的观点。在丁氏看来,四端与七情皆本于仁、义、礼、智之性。可见,丁时翰所言“所从来”与奇大升、李珥所谓“源头发端处”或“本源”有所不同——他虽未明言,从其语句中推断出此点。丁时翰以为人心虽无二源,但是其发现于外者可以主理、主气而言。由此可知,其“所从来”并非是“本”。丁氏更侧重于由“本”发用于外的过程,每以此指代他所描述的“就一心之中,方其萌动之开始”的时刻。此刻必是“性”与“气质”相互发生关系的时刻。于是,与气质发生何种的关系遂成区分四端和七情的关键。与“气”相关但不杂于“气”的情为四端;与气相关且在气的驱动下易流于恶的情则为七情。②据此,丁时翰对李滉之说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退溪《四七辨》云:“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栗谷所谓“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者,似本于此。而第退溪之以四端为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者,所指而言者,以其出于性之粹然在中,不杂乎形气者而为言。初不言无感而自发也。以七情为外物之触其形而动于中者所指而言者,以其出于性在气质,易感形气者而为言,亦非谓中无是理也。是以退溪旋以为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且谓“虽滉亦非谓七情不干于理,外物偶相凑着而感动”,且谓“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其本意所在,若是明白;而今者推出退溪所未有之意,说出退溪所未说之言,或以为做出许多葛藤,或以为正见之一累,已极轻肆,而终以无父而孝发,无君而忠发,不见孺子之入井而自发恻隐为心病等语,铺张抑勒,至此之极。岂其未曾虚心翫绎于退溪之说。而略绰看过胡乱说道者耶。①
这段话本是丁时翰为李滉之说所做的辩解。但从上下文以及李滉与奇大升辩论的全过程来看,李滉所言“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一语似有不妥。若谓此话代表李滉之真正立场,则其与奇大升之往复辩论便失去焦点。而丁时翰引这一句等于是否定四端是“无感而自发”。这无疑是其向李珥立场靠近,而承认四端与七情的同构型。②丁氏本人可能未意识到他的这一辩解与其初衷的自相矛盾处,学者于此则不可不察。
总之,丁时翰“四端七情”论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对李滉与李珥“四七理气”说之异同的详尽论述。丁时翰在批驳李珥“气发理乘”说的同时,对其部分见解亦有容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倾向。不过,尽管他在理气关系及四七理论的解释上有折中二李之痕迹,其思想之主旨还是反映了主理论学者的为学性格。
三、丁时翰的“人心道心”论
在韩国儒学史上由李珥与成浑推动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是继“四端七情理气”之辨之后发生的又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学术论争。
在论辩之初,成浑基于李滉“理气互发”之论提出理发即为“道心”而气发则为“人心”。“近日读朱子人心道心之说,有或生、或原之论,似与退溪之意合,故慨然以为在虞舜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理气互发之说,则退翁之见不易论也”①。所谓“或生”与“或原”,盖指朱熹所说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言。道心原于性命之正,纯善无恶;人心生于形气之私,故有善有恶。又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云。究此议论以理气之发,当初皆无不善,而气之不中乃流于恶云矣。”②因此成浑认为李滉的人心道心之说亦自不为过。
李珥同样援引朱子说法以增强说服力。他认为,朱子既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则何从而得此理气互发之说乎?在李珥看来,理气无先后离合不可谓之互发,但人心道心可以从两边来说。其《人心道心图说》有云:“道心虽不离乎气,而其发也为道义,故属之性命;人心虽亦本乎理,而其发也为口体,故属之形气。方寸之中,初无二心,只于发处有此二端。”③李珥在《答成浩原》的最后一书中指出:“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则心是气也,或原或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乎?”④可见,李珥对人心道心的说法亦承朱子之意而为言,且又时时不忘与其“气发理乘一途”之说相联系。其思想的系统性、逻辑性于此可见一斑。
李珥进而发挥朱子之说,提出自己独到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此论乃李珥对人心道心问题的基本看法。
丁时翰对于李珥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评论道:
窃详栗谷之意,概未见人心道心分言之脉络,以朱子或原或生之,为不得已之论而不之信,故每以人心道心滚合为一说。以为同出于本然之性,而以掩乎形气者,谓之人心;以不掩乎形气者,谓之道心。此非虞舜命名,朱子注释之本意也。夫上智不能无人心,则上智之人心,初不掩于形气,而以其从形气而生,故名之以人心。下愚不能无道心,则下愚之道心,虽发于气禀所拘之中,而以其本体之明有未尝息者,故名之以道心。初非以形气之掩与不掩,分言人心道心也。此是圣贤各指其所从来,使人审几用工之旨诀。而栗谷则舍而不取,既不欲相对说下。如朱子之言,而又不欲显言体用二字,以避宗主整庵之嫌。于是乎自作定论,辄以相为终始者言之。而其于道心上,言存养而不言审几。人心则直以为形气所掩而审其过不及云者,果有异于整庵体用之论乎?①
在丁时翰看来,李珥之说不过是祖述整庵学说而已,故而直言其人道说亦无异于整庵之道心人心体用论。他尖锐指出:“虽以浑沦者言之,只可言一心之中,从形气之人心,不离于性命,原性命之道心,不外于形气而已。若谓之人心道心相为终始云尔,则殊非人心道心之所以得名者也。”②依丁时翰之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仁义礼智之性蔼然流行于形气之间;人心生于形气,而视听言动之勿论非礼者乃所以听命于道心。
对于李珥“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源则只是一心”的观点,丁时翰批驳道:
所谓“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源则只是一心;其发也,或为理义,或为食色,故随其发而异其名”云者,初不外于退溪之说矣。既谓之“随其发而异其名”,则岂不可谓理发、气发乎?退溪所谓理气互发者,概以为理与气合而为心,理气混然一心之中,随所感而发,或有理发之时,或有气发之时,互相发现云尔。其言“互发”二字者,益明此心之无二本矣。今乃不察理到之言,而一向挥斥;至其何从得此之说,则又若初不知出于退溪之说者然,显有抑扬凌驾之意。此等气像,似非吾儒法门矣。①丁时翰指出因理气混然于一心之中,故心之发或有理发之时,或有气发之时。在此丁时翰对“理气互发”说作了全新的阐释,即以“互相发现”来解互发之义。他认为李珥对李滉的“理到”说未能真正理会,试图以此说来回应前者对后者的攻击。依止李滉“理气互发”之说,丁时翰不仅对李珥“气发理乘一途”说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而且还称其气象“似非吾儒法门”。其时栗谷学派在学界、政界正日益得势,而退溪学派则渐趋衰落,丁时翰对此十分忧虑,遂与李玄逸一道担当起为退溪学辩护的责任。从丁氏对李珥的批评中,我们随处可见党争之语气——此为两人党派、学派之殊异使然。
我们从比较的视角对丁时翰的理气说、“四端七情”说以及“人心道心”说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可以看出,丁氏不仅在理气关系上确有强调二者不离性的一面,而且在“四七”论方面亦有容受李珥之说的成分。但其学说之主旨仍然基于李滉的“尊理贬气”、“理气互发”之义上,而“理发”之说显然不合朱子“理不活动”之旨。各派间交互影响也是朝鲜朝性理学的特色之一。此外,还发现朝鲜朝儒学因所依文本之不同而造成的“多重文本交叠”的特色及诠释问题的复杂性一面。②在人心道心说方面其特点在于,对朱子所言理气之“心”的重视。
第一节 宋浚吉与其“四端七情”论
宋浚吉(字明甫,号同春堂,1606—1672年)是17世纪韩国著名礼学家和政治家,同时亦是朝鲜朝中后期韩国性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本贯为恩津,谥文正。作为栗谷李珥的再传弟子,他在韩国儒学史上与同属畿湖学派的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年)并称为“两宋”先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宋浚吉身为畿湖学人还与以退溪李滉为宗匠的岭南学者保持密切联系,终汇诸家之长形成了颇具魅力的理论风格,为朝鲜朝礼学的形成以及性理学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本节拟从朱子、李珥和宋浚吉的思想之比较的视角,对其四七性理学说作一论述。
一、宋浚吉的理气论
理学家们大都把理气说作为其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朱子虽主理气二分,却以理本论为哲学体系之核心。而且,“理”在朱子的哲学体系中具有多种含义和用法。比如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据、事物运动变化之原因以及事物之内在规律等。另外,理又是仁义理智的总称(总名)。
李珥也同朱熹一样认为天地万物是由理和气构成。而且,他对理、气两概念还作了形上、形下的区别。李珥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则一太极而已;其气,则一阴阳而已。其为气也,有大小焉”①。他还说过“理,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②。可见其对理、气概念的认识并未超出朱子学的轨道。
李珥将“理”看作形而上之存有亦即宇宙的普遍法则和规律,使其既具事物法则规律之含义,又有伦理道德原理准则之意味。他曾说过:“对一阴一阳,天道流行,元亨利贞,周而复始,四时之错行,莫非自然之理也。”③盖以理为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之自然法则。又说过:“道学本在人伦之内,故于人伦尽其理,则是乃道学也。”④殆以理为人伦道德之准则。这与朱子对“理”概念的界定是基本相同的。
不过,在理、气两个概念的具体特性的认识上,李珥与朱子似乎又有所不同。这也是李珥为解决朱子所面临的理何以为万化之本的这一理论难题而进行的尝试。他将“理”理解为无形无为而又纯善的形而上之存有。“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宰者,理也。”⑤而且,“理气无始,实无先后之可言。但推本其所以然,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⑥。不过这里需注意的是,在李珥理气论中,理与气是“浑沦无间,无先后、无离合”⑦的关系,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在他看来,理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基础。“朱子所谓‘温和慈爱底道理者,即所谓爱之理也。’底字之字同一语意,何有不同乎!大抵性即理也,理无不善。”①“理”作为慈爱之所以然的形而上本体乃纯善之存有。“夫理上不可加一字,不可加一毫修为之力,理本善也,何可修为乎?”②因此,在人的行为中合乎理的便是善,否则即为恶。相对于理的“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气则具有“有形”、“有为”、“湛一清虚”之特性。
朱子主张气是有形与无形的统一。一方面,他认为“气聚成形”③,即有了气物才得以聚而成形(有形之物便是气);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地之间存在无形之气,比如“声臭有气无形,在物最为微妙,而犹曰无之”④。
李珥则明确提出理无形而气有形。“气局者何谓也?气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后也。”⑤作为物质的、有形象的存在,气属于与本体界相对的现象界。理作为形而上之存有,其超越性、普遍性必须通过气来呈现和实现。“有形有为而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⑥所以在李珥理气论中理与气是相互并举以显示其内涵的一对范畴。同时,气又具有“湛一清虚”性。李珥把气之本然状态解释为“湛一清虚”⑦或“湛然清虚”⑧的“浩然之气”。他说:“气之本然者,浩然之气也。浩然之气,充塞天地,则本善之理,无少掩蔽。”⑨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立场出发,认为不仅理具分殊性,而且气亦具分殊性。“一气运化散为万殊,分而言之,则天地万象各一气也;合而言之,则天地万象同一气也。”⑩由此而言,李珥的“理一之理”和“分殊之理”分别是依附或挂搭于“气一之气”和“分殊之气”的实理,作为气之本然者的浩然之气也是与“理”一样纯善之存有。而天地万物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气的有形有为之特性使其在时空的演化中出现了变异。
作为栗谷学派之嫡传的宋浚吉对朱子与栗谷皆十分推崇。他在进呈给国王的《写进春宫先贤格言屏幅跋》中便引了栗谷李珥的“道统之传,始自伏羲,终于朱子。朱子之后,又无的传”①一语,明确将朱子视为儒家道统的最后传人。同时,宋浚吉对李滉也表现出相当的尊敬。他在经筵侍讲时还多次引用李滉和郑经世(字景任,号愚伏,亦称为石潨道人或松麓,1563—1632年)等②岭南学者的言论进行讲解。他在晚年所作《记梦诗》中写道:“平生钦仰退陶翁,没世精神尚感通。此夜梦中承诲语,觉来山月满窗栊。”③表现出其洒脱不羁的治学风格。
在理气论方面,宋浚吉的学说大体承袭了其师沙溪金长生(字希元,号沙溪,1548—1631年)的理论,后者被视为李珥的嫡传弟子。金长生20岁入李珥门下受学,后又从学于龟峰宋翼弼和牛溪成浑等人。
作为金长生的弟子,宋浚吉也用形上、形下来规定理、气两个概念。他对《易》大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解释说“器即气也,道即理也,道器之分固如是”④。可谓径直以道器诠表理气。关于“理”与“道”的关系,程颐曾说过:“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⑤宋浚吉亦以为然。在他看来,“道”和“理”同实而异名,皆具万理而无形无象。
对于理、气之界定,宋浚吉仍以“有形”、“无形”以及“有迹”、“无迹”为判分的标准。他说过:“气有形可见,故曰形而下。下者,指有形、有迹而言也。理于物无所不在,而无形可见、无迹可寻。故曰形而上。上者,超乎形迹之外,非闻见所及之谓也。”⑥
与其同时的宋时烈虽亦用形上、形下区分理气,但相比而言要较宋浚吉委婉一些。宋时烈有言:“所谓道者理也,所谓器者气也”①,他还说过“自人物之形象言之,其虚而能为所以然者是理,故谓之上。其经纬错综,能此形象者是气,故谓之下云尔”②。
宋浚吉的这一解释似乎更为合理而简明。不过,也易使人产生过甚其词之感。如其所言“子思既以一道字符串费隐说,道固形而上之理也,非杂以形而下之气也”。③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一点上更近于退溪之学。栗谷之学强调的是理气之不离,亦即理与气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
在理气关系的问题上,宋浚吉仍以朱子和李珥的理气观为基础来解释理如何成为气之所以然。他认为“有是形必有是理”,而且理之于物如“诗所谓有物有则者也”④。肯定了理对于气的主宰作用和意义。接着,宋浚吉还借体用这对范畴来说明理何以是物的“所以然”。他指出:“父子、君臣是形而下之器也,是物也。父而慈、子而孝、君而义、臣而忠是形而上之道也,是则也。慈孝义忠,此所谓理之当然者,所谓费也,用也。所以慈、所以孝、所以义、所以忠,此理之所以然者,至隐存焉,所谓体也。推之万事万物莫不皆然。”⑤宋浚吉进而以“理堕气中”解释理气如何生成万物。“理堕气中,气能用事,而化生万物。即所谓气以成形,理已赋焉者也。”⑥理与气是二物还是一物以及理为“实有之一物”还是“非别有一物”始终是困扰性理学家的理论难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在这一问题上朱子的态度是既讲理气不相分离,还强调理与气“决是二物”。对此元代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吴澄(字幼清,号草庐,1249—1333年)则提出“非别有一物”说,对朱子理气论从理论结构上作出了重要修正。吴澄以为“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有此气即有此理。”①他否定理的实体性,强调理只是气之条理和规律。于此也可看出,在理的问题上朱子后学中已出现“去实体化”的转向。②此后被世人称为“朱学后劲”的罗钦顺则明确提出“理气一物”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③整庵指出理并不是形而上的实体,而只是气之运动的条理或规律。他大胆宣称:“仆从来认理气为一物。”④朱子后学的这一理论动向也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性理学家。如前文所述,《困知记》传入韩国后,李滉即从述朱之立场出发特地撰写《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一文以驳整庵异说。他尖锐指出罗氏的“理气一物”说是“于大头脑处错了”⑤。李珥对罗氏学说的评价则稍有不同:“整庵则望见体,而微有未尽莹者,且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而其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理气为一物也,所见未尽莹故言,或过差耳。”⑥不管怎样,李滉和李珥皆反对“理气一物”说,而以朱子之理气“不离不杂”、“决是二物”为不刊之论。
宋浚吉亦追随其后而以理气为二物,从他维护李珥学说之立场中便可概见。宋浚吉以为“稷乃谓其(指栗谷——引者注)学以理气为一物,不以可笑可哀之甚乎。邪说肆行而莫之禁,则其眩乱注误,将至惑一世之人,其为祸岂不下于洪水猛兽哉”⑦。
朱子理气说的二元论结构必然会面对理气先后、理同气异、理气聚散等难以解答之问题。对此理论困境,李珥提出“理气之妙”说以为解释这些问题的理论基础。
宋浚吉则在继承朱子和李珥理气观同时,还对他们理气为二物的思想作了如下总结:“若以有形无形言,则器与道为二物;以在上在下言,亦为二物。须如此说方见得即形理在其中,道与器不相分。”①继“理堕入气”说,宋浚吉又提出理气“妙合而凝”说。他写道:
廉溪所谓阴阳一太极,即所谓器即道也。《性理群书》注错误处甚多,至或不成文理,而此条所释精粗本末则无误矣。若依李珥说,则精粗本末之下,当着吐也。若然则释阴阳太极,不成说话矣。盖大而莫能载,小而莫能破者,无非器也,而理无所不在。子思所谓费而隐,子夏所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程子所谓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与来示所引朱子语皆一义也。理固如此,本无可疑,但此所谓精粗本末无彼此一句,分明是贴阴阳太极字说,以为理与气无彼此耳。非泛论气有精粗本末也,如何。幸更细思之,先贤说话横说、竖说,各有攸当,最忌相牵强合作一说……按妙合云者,理气本浑融无间也。此乃理气混合无间隔也,乃阴静时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此乃阳动成形时也。②
对于理气妙合而凝,宋浚吉进一步解释道:妙合与凝是两项事,而《性理群书》注把妙合与凝合为一项事不符合朱子本意。他还以为《性理群书》注解把“妙合而凝”解释为妙于凝合无间断是有所未稳。“无间断也。间断字,恐未稳,以间隔释之,则未知如何。”③对于理气“浑融无间”思想,李珥总结前人关于理气关系的论述时也曾提出过,曰:“理气浑然无间,元不相离,不可指为二物。”④但是,李珥并未对“无间”一词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宋浚吉则将“无间”释为“无间隔”,表明他对名言的义理分际异常敏感。理气“浑融无间”说,是“理堕入气”说的有益的补充。
此“浑融无间”说似有类于明代理学家薛瑄(字德温,号敬轩,1389—1464年,谥文清,河东学派的缔造者)的理气“无缝隙”说。薛氏以理如日光、气如飞鸟之喻说明气有聚散而理无运动。结果还是理气看成有“缝隙”的。对于“堕入”说,罗钦顺批评道:“夫既以堕言,理气不容无罅缝矣。”①因为“堕入”一词本身隐含着理堕入气之前,理同气是被分隔着的意思。②尽管宋浚吉对理气“浑融无间”作了精心的解释和字面上的调整,但还是很难用这一主张来圆满解释理同气异、理气聚散的问题。
于是宋浚吉援引了李珥的“理通气局”说,并对此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李珥)至于理通气局之论,发先贤所未发。形状理气本体,直接分明,可以开悟后学于百世。非其学问精旨超特绝出于人者,安能及此。谓理通气局,则其分别理气,可谓极明白矣。③
“理通气局”说是栗谷为回答理同气异问题而提出。关于“理通气局”这一命题,李珥认为“理通气局四字,自谓见得,而又恐读书不多,先有此等言,而未见之也”④。尽管佛教华严宗有理事通局之说,但是以“理通气局”四字表述理气同异、理气聚散却是李珥的独见。虽然其思想也受到程伊川的“理一分殊”和朱子的“理同气异”思想的影响,但这一命题的提出更多缘于李珥对“气发理乘”思想之发挥。因此,在其文章中“理通气局”说往往与“气发理乘”说相互对举——如,“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⑤。
由上所述,在理气论方面宋浚吉承接朱子和李珥之说认为,世界万物皆由理与气构成。而且,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规定上也大体追随了栗谷的学说。他比李珥更强调道器之分别和理的“无迹、超乎形迹”之特性。在这一点上,宋浚吉似乎具有某种折中李滉与李珥理气说之倾向,其作为主气论学者的理论特色并不明显。若对宋浚吉理气说作一概括的话,可以说其理论主要由“理堕气中”说、“理气浑融无间”说、“理通气局”说组成。三者在其学说中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系统。但其对“理”的理解方面仍未超出传统的内在实体说之藩篱。
二、宋浚吉的“四端七情”论
前已述及,“四端七情”之辨是朝鲜朝性理学的中心论题之一。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家们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先是围绕理气之“发”产生了歧义。
李滉在手订郑之云的《天命图说》过程中,将“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奇大升则从自己的“理气浑沦”思想出发,对李滉之说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①在奇氏看来,所谓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②。四端虽为纯粹的天理之所发,但只是发乎七情中的苗脉而已。理气虽然有所分别(理为气之主宰、气为理之质料),但在具体事物中却混沦不可分开。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也。③
奇氏认为四端与七情皆是情,其间并无截然之别,所以二者不可分理气而论。其观点无疑与朱子的看法更为接近。
对于奇氏的质疑,李滉答复说先儒的确未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气进行探讨,而理与气在具体生成的过程中也确实不可分离,但二者因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有必要分别而论。他在回信中讲道: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①
李滉进而指出情有四端七情之别亦犹性有本然气禀之异。性既然可以分理气来说,情为什么就不能分理气而言呢?他认为由于四端、七情所从来各有不同,所以可分别从主理和主气的角度分而言之。“故愚尝妄以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即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最后他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此即“理气互发”说。而奇氏之说则被称为“理气共发/理气兼发”说。
与理气之“发”问题相关的另一论题为“主理”、“主气”之分的问题。李滉有言:“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③
其实,李滉、李珥等人也并非不知朱子理气“不离不杂”之义。李滉就说过:“理与气本不相杂,而亦不相离。不分而言,则混为一物,而不知其不相杂也。不合而言,则判为二物,而不知其不相离也。”④李珥亦有理气“既非二物,亦非一物”之说。比较而言李滉着重于理气之“不杂”义,而李珥则强调理气之“不离”义。两人在理气观上的差异,直接造成在四七理气论问题上的不同理解。
李珥从其“理气之妙”的思想出发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转而支持奇大升的观点。他曾说过:“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①李珥一方面批评李滉未能真正理会朱子之本意,另一方面又主张不仅七情就连四端也是“气发理乘”。
李珥对李滉理论的批评,遭到成浑的辩难。于是,继“退、高之辩”李珥和成浑之间又展开了长达六年的第二次四七大论辩。成浑基本上支持李滉的观点。他指出:“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②进而坦言:“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③可见,成氏倾向于肯定李滉的“理气互发”之说。
李珥同成浑围绕四七人心道心问题进行的数年论辩中,始终坚持其“气发理乘一途”说。在他而观,对“四七理气”之发问题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李珥有言:“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④进而举例说:“所谓气发而理乘之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⑤可见,依其之见四端与七情均为“气发理乘”。
在“四端七情”说上,宋浚吉基本接受了李珥的主张。《同春堂年谱》中有如下的记述:
尤庵先生曰:“日知皆扩充之说,李滉、李珥之见不同矣。”先生(指宋浚吉——引者注)曰:“非但此也,四端七情之论亦不同。国初权近始发此论,其后郑之云作《天命图》而祖是说。李滉之言本于此,而有四端理发气乘,七情气发理乘之语。故李珥作书以辨之。”上曰:“分言理气,何也。”对(按:宋浚吉)曰:“此李珥所以为未安者也。四端只是拈出七情之善一边而言,不可分两边对说。若论气发理乘之,则不但七情而四端亦然。大抵人心必有感而后发,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无先后无离合,不可道互发也。”①
前已论及,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是一位朝鲜朝初期颇有影响力的性理学家,郑之云、李滉等人的很多思想端绪皆可从其性理学说中找到理论依据。所以宋浚吉认为正是权氏的学说开了“四七”论之先河。文中宋浚吉在讲述李滉与栗谷四七理论之不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宋浚吉认为在“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上不能以分言理气的方式来解释四端与七情。气是发之者,而理则为所以发者——四端只是七情之中的纯善者。
夫孟子之言四端,所以明人之可以为善也。故特举情之善一边言之,非谓四端之外更无他情也。若人情只有四端,更无不善之情则人皆为圣人也,故四端只拈出情之善者而言也。《记》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即人情善恶之总称。七情中之恶者,与四端为对则可。若以四端与七情相对则不可。李滉四七相对之论,虽因权近旧说,而未免失于照勘。义理天下之公也,学者穷格之功,只求义理之所在。若心有所疑而不为辨析,则此理终晦而不明矣。昔程子作易传,乃竭一生之精力,而朱子指其差吴处甚多。饶鲁、陈栎等至有愿为朱子忠臣,不愿为朱子佞臣等语,虽程朱之说,或未免有可疑处。况李滉之言,何可谓尽无差处乎。今以此为李珥之疵,其无识甚矣。李珥四七书,识见之超迈,言论之洞快,前古诸儒罕有及者。②
在宋浚吉看来,四端与七情并非“二情”,二者是“七包四”的关系也就是说七情作为人类情感之总称内在包含四端。他明确反对李滉将二者并立为二物的思想。
在谈论李滉与李珥理气说之不同时,他还对“气发理乘”说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盖退溪先生论四端七情云:“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栗谷先生辨之甚详。无虑数十百言,其大意曰“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者无所发。所谓气发理乘之者,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然云云”。先师(指金长生——引者注)常以栗谷之说为从。非特先师之见为然,外舅氏(指郑经世——引者注)之见亦然。弟常问之曰:“退溪、栗谷理气说不同,后学将何所的从。”答:“恐栗谷说是。试以吾身验之,如入家庙则心便肃然,是敬畏之发也。而即其肃然者,乃气也云云。”至今言犹在耳……栗谷此论真可谓百世以竢而不惑,使退陶而复作,亦必莞尔而笑。①
宋浚吉的岳父愚伏郑经世是当时岭南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宋氏引愚伏为同调以为“气发理乘”论张目。他还试图说服其他退溪门人接受这一观点。
朱子也认为四端和七情皆为性之所发的情感。他在《孟子集注》中讲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②宋浚吉对四端也有自己的解释。“有诸内而形诸外者,谓之端也。人心本善,于此可见。”③在宋浚吉看来,四端乃有诸内而形诸外者,属于已发之情——但又根于仁、义、礼、智而为人性之善。对于“性”、“理”之关系他解释道:“大抵性字从心从生,与理字不同。理堕在气中者,方谓之性。故曰‘性即理也’。盖谓在人之性,即在天之理也。”④
在四端中,宋浚吉特别重视恻隐之心。他在与愚伏先生的信中提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恻隐之心,心之生道也。”①宋浚吉强调“恻隐之心”在四端中的统摄作用。“人无恻隐之心,便是死物,犹鱼之不得水则不生也……恻隐便是初动时,才动便见三者之分界。如春不生则夏不长,秋不收而冬无所藏矣。此可见恻隐统四端也。古人观庭草庐鸣以体仁,此是天机流动活泼泼地也。”②可见,他将“恻隐之心”视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
不仅如此,宋浚吉还对仁、义、礼、智作了如下论述:
夫仁礼属于阳,义知属于阴,而阳德健、阴德顺,健顺五常乃人之所同得。而并言物者,凡物亦自得其一端,如虎狼之仁、蜂蚁之义皆是。故谓之各得其所赋之理也。③
此段引文不无泛性善论之意味,而其论说基础正是李珥的“理通气局”思想。由此可见朝鲜朝后期“人物性同异论”论辩之理论端绪。
宋浚吉对李滉与李珥的四端七情说详论其异同。他指出李滉之误,而对李珥“气发理乘”之思想则颇为推重。尽管宋浚吉在理气概念的界定和理气关系的理解上有折中二李之倾向,但从其四七理气论中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畿湖派(主气论)的为学性格。
三、宋浚吉的“人心道心”论
对性情善恶及人心道心问题的讨论可以视作四端七情问题在更深层次的展开。作为朱子学的重要论题,人心道心问题与公私、理欲之探究皆有密不可分之关系。
二程认为人心与人欲相联,而道心则与天理相通。伊川有言:“‘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④明道则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⑤伊川遂将“道心”和“人心”对立起来,以前者为正而以后者为邪。在他看来,唯有用“精一”功夫护持“道心”,才能令其不被“人心”扰乱。“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①职此之故,伊川明确主张存天理以灭人欲。
朱子也说过:“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②他将十六字心传视为古圣相传之“道”。朱子是这样理解分人心、道心之异的:“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③他进而说明:“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④“道心”为根于义理之正,而“人心”则根于耳目之欲。
仅就以已发、未发而论,则人心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点上李珥也与朱子所见略同。但是朱子主张二者皆发自“一心”,李珥主张二者发自“一性”。那么,人何以会有人心、道心两种不同的知觉?朱子认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⑤。这就是朱子独到的解释。他还纠正了伊川的说法,提出人心并非皆“恶”。“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⑥朱子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人的生存欲求和生理欲望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⑦。朱子虽然提出人心道心相分,却主张二者“不可作两物看,不可于两处求也”⑧。可见,在朱子哲学中人心道心问题虽与天理人欲问题相对应,但不似后者那样显得十分紧张。
李珥则继承朱子的学说并加以发挥,提出了“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说法。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
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①这是基于“意”的商量计较作用的,人心道心可互为转变、转换的理论。因此李珥认为人心道心可以相互转换,因而不能将其判然两分。
对于人心道心与四端七情的差异,李珥指出:“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②人心道心之名源于性命形气之别,四端七情则与此不同——后者之区别是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四端属于七情之善的一类,故而七情可兼四端。而人心与道心因含对比之意,所以无法相兼而只能互为始终。
不过,李珥认为“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③他肯定了人心亦有善的层面,此为李珥对李滉学说的有益补充。我们知道李滉以“理贵气贱”为据将人心等同人欲,进而将人欲归之为“恶”。
宋浚吉的“人心道心”说大体亦接续朱子、李珥之思路而讲。在他看来,“朱子之序,历叙上古圣王道统之传,‘危微精一’十六字,实万世心学之渊源”④。宋浚吉以为“人心修之便是道心,自道心放出便是人心”⑤,他很注意二者的相互转换性。及至晚年特别强调气之发用时的省察功夫,要求对人心时时严加防范。“深加省察如有一念之差用,力速去焉。”⑥至于人心与道心的不同,宋浚吉解释道:“心之本体而言,未发之前理为主,既发之后气用事。周子云诚无为几善恶,此人心道心分歧处也。”①这表明他同样以已发、未发来区分人心与道心。
宋浚吉之“人心道心”说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心”论。首先,他强调“心”之虚灵知觉性,而且对“虚灵知觉”也有独到的理解。《年谱》中记云:“上御养心阁。侍读官金万重讲文义曰:‘虚灵心之体,知觉人之用也’。先生曰:‘此言误矣。虚灵知觉皆心之体也。其曰具众理应万事者,具众理体也,应万事用也。’”②虚灵知觉性指的是心具有不受先见左右的能动知觉之特性。宋浚吉强调知觉是体而非用,颇有个人之体悟。
其次,宋浚吉强调心之易动性。“道之浩浩何处下手用力之方,无逾于庄敬自持。真氏之言实为明白精切。每侍先王讲此书,未尝不反复咏叹于此。夫人之一心易流而难制,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心便至于放逸矣。”③既然人心易流而难制,那么如何使其保持清明之体呢?宋浚吉主张要去“物欲”,“心无物欲以蔽之,则清明之体自然呈露矣。”④
再次,在宋浚吉的学说中“心”多次被描述为“活物”,比朱子之心更具活动性。“人心是活物。终不得不用,既不用于学问,则其所用不过宦官宫妾变嬖戏玩之事而已。”⑤这一点上与其同时代的尤庵宋时烈所见略同。宋时烈说过:“盖朱子之意,以人心道心,皆为已发者矣。此心为食色而发,则是为人心,而又商量其所发,使合乎道理者,则为道心。其为食色而发者,此心也。商量其所发者,亦此心也。何可谓两样心也?大概心是活物,其发无穷,而本体则一,岂可以节制者为一心,听命者又为一心。”⑥从“心是活物”、“其发无穷”等论说中,可以看出韩国主气论学者的“心”论特色。
朱子的“心”是一身之主宰,赅备体用,兼摄形上之性理与形下之情气。如果说“一心”具众理乃其体,那么应万事者则其用;如果说寂然不动者乃其体,那么感而遂通者则其用。其“一心”实际上涵盖形上、形下两层,既是超越层面的本然之心,又是经验层面的实然之心。此“心”一体两面,既存有又活动。实然形下的“心”具有活动作用的能力,由此体现超越形上之“心”,但又不是禅宗的“作用见性”。①在宋浚吉的心性论中,“心”更多是指实然形下之“心”,而又不同于阳明学所讲的一颗活泼泼的心。此一心论在工夫上有一特点,就是较为重视“志”的导向。“志”为“心之所之”,使“心”全副地趋向一个目的,决然必欲得之——所以特别强调“立志”之重要性。②宋浚吉亦是如此。他曾说过:“愿殿下勿以臣言为迂,必须立此大志焉。立志坚定,然后道统可继,治化可成矣。”③还说过:“诚能奋发大志,则何事不可做乎。”④
最后,宋浚吉对诸儒“心”论作了个概括:“圣贤论心不同有如此处,有如彼处。有从那边用工者,有从这边用工者,其归未尝不一。所谓从一方入,则三方入处皆在其中。”⑤这段话是宋浚吉向朝鲜国王讲解《心学图》时,针对李滉与李珥所论之不同而发的议论。从文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李滉与李珥的心论都有精深的了解。
在“人心道心”论方面,宋浚吉亦有极高的造诣。据《年谱》上曰:“讲心经。先生(指宋浚吉——引者注)于人心道心之辨,毫分缕析援据详尽。上叹曰:‘晓喻诚切也。’”⑥但从现存的文献中我们很难发现这方面的系统论述。材料的欠缺实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以上是从比较的角度对宋浚吉的理气说、“四端七情”说以及“人心道心”说作了简要论述。可以看出,在理气二物之分判上宋浚吉和李珥相比虽有过甚之感,却大体不出李珥“理通气局”之藩篱。而在“四端七情理气”之发问题上,宋浚吉则特别重视李珥的“气发理乘”说。至于“人心道心”说,宋氏的理论特色在于对朱子所言实然之“心”的强调。
第二节 宋时烈与其“四端七情”论
宋时烈是17世纪韩国性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推尊朱子与李珥,穷研性理,为朝鲜朝性理学、义理学、礼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节主要通过其理气论的分析,来探讨宋时烈的四端七情理论之特色。
一、宋时烈的理气论
理与气的关系问题是理学的基本问题,因而理气论在性理学家的思想体系中总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为栗谷学派之嫡传,宋时烈对朱子与栗谷推崇有加。他曾说过:“窃念孔圣以来,集群儒之大成,唯晦庵夫子,则后学之所依仿,无小大巨细,当一于是矣。”①还说过:“盖吾东理学,至栗谷而大明。栗谷以前,虽如晦斋之贤,其学如此。”②
在性理学方面宋时烈与朱子、李珥一脉相承,主张世界万物皆由理与器构成而二者有形上、形下之区分。“凡物之有形者,皆有理气。所谓道者理也,所谓器者气也。”③那么,理气又如何落实于人物之上?宋时烈认为“自人物之形象言之,其虚而能为所以然者是理,故谓之上。其经纬错综,能此形象者是气,故谓之下云尔”④。
宋时烈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规定上,也追随李珥否定理之发用性,从而肯定气之运动性。在他看来,“理是,无情意、无造作底物事”,⑤而“有形有为而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①。理永远具有主宰性。“一阴一阳者,气也;而使一阴一阳者,理也”,②理虽无形无为却能为“有形有为之主者”。③可见,宋时烈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认识上大体还是遵循了李珥的理气观。这一点可由其以下言论得到确认。
来示以此合之于栗谷所谓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之说,极亲切矣。④
栗谷所以非退溪说者,专在于“理发气随”一句,此说是非,当于中庸天命之谓性注可见矣。其曰气已成形,理亦赋焉者,与理发气随者,同乎异乎?⑤
不过,在“气”的解释上宋时烈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过“按理无穷,故气亦无穷”⑥,还说过“气之无限量,亦由理之无限量故也”⑦。在此宋时烈给“气”赋予了超时空之含义,这是对李珥气论思想的有益的补充。在李珥处,“气”具有有形之特性,此乃其“理通气局”说的立论基础。但是李珥为其“理通气局”说建立理论基础的同时,也给自己“理气之妙”思想预设了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解释理气之间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理”的无限性与“气”的有限性在其学说中无法协调,此为李珥学说在理气概念之界定上的一个理论缺陷。
宋时烈提出“理无穷,故气亦无穷”的命题,不仅弥补了栗谷理气说的理论缺陷,而且还丰富发展了朱子的“气”论思想。“气”作为与“理”相对言的理学核心概念,在朱子学的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气”的任何创新之阐释都会对朱子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朝鲜朝主气论学者在这一方面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可由宋时烈之“气”论窥其大概。
讨论朱子哲学首先会遇到理气有无先后的问题。此一问题颇能反映朱子学的理论特性。
朱子先是主张“理先气后”论。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①在他看来,天地万物皆由理与气构成——没有无理之气亦无无气之理。但就本源上说,理是先于气而存在。
到了晚年朱子开始意识到,其“理先气后”说容易引起一些不易解决的矛盾。如伊川强调“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而按理先气后论,宇宙的阴阳就必须有个开始。所以朱子对其早先的说法进行了修正。“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②终将理先气后确定为逻辑上的在先。
在理气论的这一核心问题上,李珥基本上与朱子所见略同。他说:“理气无始,实无先后之可言,但推本其所以然,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圣贤之言虽积千万,大要不过如此而已。若于物上观,则分明先有理而后有气,盖天地未生之前,不可谓无天地之理也,推之物,物皆然。”③此话尽显以理为本的李珥在理气论上的基本立场。
宋时烈在继承朱子、李珥之说的基础上也作出了自己的建树。他的理论特色是在理气论中引入了“形”这一概念并借以说明理气关系。
形而上形而下,退溪沙溪二先生所释,殊不甚安。故常以为当以形字为主而处,道字器字于形之上下,以形道器三件物事所释,井井无难矣。二先生则以形与道为二,而形与器为一似与孔子本旨不合矣。盖道则理也,器则气也。理气妙合而凝,以生万物之形,故中庸首章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是皆以理气形三字,分别言之矣。
既以理气形三字分别言,则当以道为形之上,器为形之下矣。①宋时烈在说明形与道之不同的同时也强调形与器之不同,目的在于使理气二者皆统一于形。如此则令李珥“理气之妙”说得到更好的解释。李珥的理气说中,理的无限性与气的有限性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宋时烈以理气形“三件物事说”区别三者,还特别强调了理自具于形这一点。理被赋予形是性理学家们的一般解释。宋时烈特以“自混融”和“自无间”来说明理气之共在性,其理论之前提便是“理自具于形”。
盖人物未生时,理与气本自混融而无间,故气聚成形之时,理自具于此形之中矣。故中庸注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此岂非十分分明者耶。②
宋时烈强调气聚成形之时理便自具于此形之中,其说相较理赋气说更适于说明李珥的“理气之妙”。同时也是“气发理乘”说有益之补充——宋时烈即以此否定“理发气随”说。他指出:“栗谷所以非退溪说者,专在于理发气随一句。此说是非,当于《中庸》天命之谓性注可见矣。其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与理发气随者,同乎异乎?”③
宋时烈理气说的另一个理论特点便是以体用范畴来说明李珥的“理通气局”思想。他说:“所谓气局者何谓也,阳之体非阴之体,阴之体非阳之体,则所谓局也。所谓理通者何也,阳之理即阴之理,阴之理即阳之理,则所谓通也。局故两立,通故两在。非局则通无所发见,非通则局何以原始乎。必著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后器亦道道亦器,而精微之蕴,活泼泼矣。”④李珥曾对“理通气局”说有过自己的解释。相比李珥“本末先后”说,宋时烈的“体用”说显然更具理论性。且以体用范畴来解释“理之一”与“气之局”还可使李珥“理通气局”说更具说服力。由此可见,继退溪、栗谷之学展开的朝鲜性理学至宋时烈时已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
宋时烈进而又将错综复杂的理气关系作了如下的总结。《宋子大全》有载:
理气之说,莫详于廉洛关闽。而或言理有动静,或言理无动静,或言其理气之有先后,或言其理气之无先后,其言不一。若相牴背,而学者没患于难为会通。于是尤庵先生出,总而断之,曰:“理气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从理而言者,有从气而言者,有从源头而言者,有从流行而言者。盖谓理气混融无间,而理自理,气自气,又未尝夹杂,故其言理有动静者,从理之主气而言也。其言理无动静者,从气之运理而言也。其言有先后者,从理气源头而言也。其言无先后者,从理气流行而言也。斯言一出,而众说之不齐者可齐,而穷理之士,始得其路径矣。①
理气有无先后以及有无动静等问题是关乎朱学思想性格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困扰朱子后学的理论难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关讨论直接涉及理如何生气、又如何派生万物的理学本旨,遂成朱子后学最为热衷探讨的问题。作为朱子学的忠实信徒,宋时烈对此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从理、气、源头、流行等不同的角度对相互各异的理气说进行了概括说明,进而从源头解释了理的主宰性问题。沙溪金长生的后裔金正默在《过斋遗稿》中对宋时烈观点有所记载,抄录如下:
从源头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故谓理为主宰,又谓之使动使静。②
从源头处,论其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其下所乘之机则却就流行处,论此理无形状无造作,只乘此气而运用也。言各有所当也。盖理气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从理而言者,有从气而言者,有从源头言者,有从流行言者。如不能活看,则节节泥滞也。③
以上是对朱子、李珥与宋时烈之理气论的比较分析。简要地说“理”在朱子哲学中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之特性。而在李珥哲学中则具有“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相对于理的“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气则具有了“有形”、“有为”、“湛一清虚”之特性。宋时烈在理气的解释上大体承接朱子、李珥之说,而对“气”的探讨更为深入。宋时烈“气亦无穷”、“气之无限量”的思想不仅丰富了朝鲜朝性理学,而且为朱子学“气”论之发展也作了探索。
要之,丽末鲜初传入韩国的朱子学历经几代韩国性理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其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朱子学本身得到了全新的阐发,而且韩国性理学也形成了颇具自家特色的理论体系。如以“理一分殊”为特征的朱子理气说传至李珥则发展成以“一而二、二而一”为特征的“理气之妙”说以及“理通气局”说。宋时烈则在笃守朱子、栗谷之说的基础上将其理论进一步细密化,提出了以“理、气、形三件物事”为特征的理气说,同时也对李珥的理气说作了有益的补充。宋时烈理气说尽管受到朱子和李珥学说的影响,但其自家特色也明显可见。
二、宋时烈的“四端七情”论
“心”、“性”是理学的核心范畴,因而理学也被称为“心性”之学。性理学之心性学说论域甚广,但首要问题仍是心、性、情、意等概念的定义。从其对这些概念的界定中可见性理学之特点。
关于心、性、情、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宋时烈有如下的说明:
盖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自器中泻出者也。只言虚灵而不言性情,则是无水之空器也;只言性情而不言虚灵,则是水无盛贮之处也。是三者缺一则终成义理不得,岂得谓之明德乎。盖或者之意,以所谓虚灵不昧者,为释明德之意,故有此说。而不知所谓明德者,是心性情之总名也……盖性是心之理也,情是心之动也,意是心之计较也。于一念才动处,便有计较也,心是性情意之主也。此四者虽有性情心意之分说,而只是就那混沦全体上各指其所主而言,其命名殊而意味别耳。不是判然分离,而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是一个地头,意是一个地头也。故心发性发,虽有二名,然心之体谓之性,心之用谓之情,则心性之发,果有二耶。为情为意,虽有分言,然心之才动谓之情,才动而便有计较底谓之意,则情意之用果有分耶?性之发谓之情,虽谓之性发,非无心也;心之发谓之意,虽谓之心发,非无性也……大抵性是无作为底物,心是运用底物,情是不知不觉闯然出来,不由人商量底物,意是计较谋为底物。①
宋时烈在本段引文中对心、性、情、意之意涵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重视心的知觉作用,以为“心是知觉运动的物”②,“盖心之为物,洞彻虚灵,天理全具,而又囿于形体之中,则不能无人欲之私矣。”③这说明宋时烈和朱熹一样肯定心之知觉思虑作用。他尤为看重心之虚灵义。“心之虚灵,分明是气欤,先生曰分明是气也。”④从“心是气”到“意”为计较谋为底物——宋时烈所做界说是对李珥“心”论和“意”论的继承。这表明其心性结构亦为心、性、情、意四分之逻辑结构。他也强调“心是气,而性是理。气即阴阳,而理即太极也”⑤。可以看出,在“心”论方面相较朱子,宋时烈更赞同李珥的见解。他继承了李珥“心主心性情意”以及“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的思想。
不过,宋时烈在心论方面特别重视心之虚灵性与感应性。对此他也以体用范畴进行了说明。“心有真体实用,体如鉴之明,用如能照。”⑥依性理学“体用一源”之思想,心之虚灵性与感应性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加之,在宋时烈的理气论中气具有与理一样的超时空之无限性,其心论遂为性理学“天人合一”之范例。宋时烈有言:
道体无穷,而心涵此道,故心体亦无穷。故道谓太极,心为太极。①“心为太极”虽似突兀,但若基于其“理气形三件物事说”亦可推出上述结论。理气统一于形,二者混融无间于心。“大抵心属气,性是理,理气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②
那么,心与性是否是可以合一的呢?在宋时烈看来,“心性虽可谓之一物,然心自是气,性自是理,安得谓之无彼此?”③他进而指出:“所谓性者,虽非舍气独立之物,然圣贤言性者,每于气中拈出理一边而言,今便以气并言者,恐未安。”④
“性”作为与心相对言的范畴成为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概念。朱子把性的意涵规定为仁、义、礼、智。他说:“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⑤,而“性者人之所受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⑥。以仁、义、礼、智为性是朱子学乃至整个理学的思想基础。朱子笃守孟子“性善论”,而力反荀子“性恶论”。因此他总是从性善出发对心、性关系做了论述,“性虽虚,都是实理。心虽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万理”⑦。那么“恶”何所从来呢?在此,朱子继承了张载有关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思想以及程颢的“性即气”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⑧。天地之性乃人之本质,气质之性则为人之习染,流衍而为性情才气——前者纯粹至善,后者则有善有恶。二者之关系明显是理与气的关系。
宋时烈是这样理解天地、气质之性的:
所谕天地之性,鄙意有所不然者。盖所谓性者,从心从生,则正以人物已生而言也。于天地下,此性字不得,只可谓之命也。至如张载所谓天地之性云者,亦曰天地畀之性云,非指在天之太极而言也。①他进而指出:
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此二名虽始于程、张,然孔子性相近三字已是兼本然气质而言也。孟子开口便说性善,是皆说本然。然其曰牛之性马之性,则以气质而言也。孟子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及大誓曰:“我武维扬,侵于之疆”。此上下文次序似互,然集注所不论则何敢以为然乎。朱子说颇有初晚之异,亦有《语类》、《大全》之不同,不可执一。是此而非彼,徐观义理之所安可也。②
韩国性理学者最为关心的四端七情问题便与此问题密切相关。朱子在论及四端时,曾说过“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这两句话在中国并没有引起注意。依朱子的解释,发者是情,而情则属于气,在“理”上不说发。所谓“四端是理之发”,可解释为四端是依理而发出的情,但是不能说情是从理上发出来的。李滉据此力主“理气互发”,似乎认为理亦能发。其实,依理学之本旨,“理”应为气发时所当遵循的原理,即发之所以然,而实际上的“发者”则是气。
李珥对于朱子的这个思路有相应之契会。他从“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理乘”③以及“理者,气之主宰;气者,理之所乘也”④的思想出发,认为在心所统的性情中未发为性,而已发为情。正如本然之性、气质之性都是性一样,四端、七情也都是情。本然之性不兼气质,气质之性则兼本然之性。同样,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却能兼四端。四端是专言情之善,而七情则兼言情之善恶。“凡情之发也,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理气混融,元不相离。若有离合,则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①这就是“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李珥据此解释了情之善恶的问题。他说:“性具于心,而发为情。性既本善,则情亦宜无不善,而情或有不善者,何耶?理本纯善,而气有清浊。气者,盛理之器也。当其未发,气未用事,故中体纯善;及其发也,善恶始分。善者,清气之发也;恶者,浊气之发也。其本则只天理而已。情之善者,乘清明之气,循天理而直出,不失其中,可见其为仁义礼智之端,故目之为四端;情之不善者,虽亦本乎理,而既为污浊之气所掩,失其本体,而横生或过或不及,本于仁而反害仁,本于义而反害义,本于礼而反害理,本于智而反害智,故不可谓之四端耳。”②本于“气发理乘”之思理,李珥将善恶系于气之清浊。以为“理”无偏正、通塞、清浊、粹驳之异,而所乘之“气”则或正或偏,或通或塞,或清或浊——理既乘于气,便因气禀之善恶亦有善恶。
宋时烈在笃守李珥“气发理乘”说的前提下,进一步贯彻了“七包四”的思想。
《语类》论大学正心章,问意与情如何。曰欲为这事是意,能为这事是情,此与先生前后议论,全然不同。盖喜怒哀乐闯然发出者是情,是最初由性而发者,意是于喜怒哀乐发出后因以计较商量者。先生前后论此不翅丁宁,而于此相反如此,必是记者之误也。大抵《语类》如此等处甚多,不可不审问而明辨之也。理气说,退溪与高峰,栗谷与牛溪,反复论辩,不可胜记。退溪所主,只是朱子所谓“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栗谷解之曰“四端纯善而不杂于气,故谓之理之发;七情或杂于不善,故谓之气之发”。然于七情中如舜之喜文王之怒,岂非纯善乎?大抵《礼记》及子思统言七情,是七情皆出于性者也。性即理也,其出于性也,皆气发理乘之。孟子于七情中摭出纯善者,谓之四端。今乃因朱子说而分四端七情以为理之发气之发,安知朱子之说或出于记者之误也。③七情皆为出于性者,其中发而中节合乎理者即为四端。宋时烈进一步指出:
所谓喜怒哀乐者,不出于性而何?既出于性则谓之人心可乎。序文不曰人心生于形气乎。既曰出于形气,而又以其发于性者当之,岂不自相矛盾乎。如曰四端七情皆出于性,而皆有中节不中节。其中节者,皆是道心之公,而其不中节者皆人心之危也。扩充四端之中节者,则至于保四海,推致七情之中节者,则至于育万物。子思孟子所常接受者,其揆一也。①
七情中中节合理者为四端,即是道心;不中节不合理者皆有人心之危,易流于私欲。宋时烈有言:“盖人心者,非直谓人欲也。其流易入于人欲,若流于人欲,则便为私邪。私之一字,百事之病。故朱子亦尝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王者奉三无私,以劳于天下。此实至言也。”②
宋时烈依其“人心道心”说时提出了“心是活物”的思想。“所谓人心听命于道心者,乃朱子说。如以为可疑,则其所可疑者,乃在于朱子,而不在于栗翁也。大抵吾人亦不深究朱子立言之意,故未免有疑耶。盖朱子之意,以人心道心,皆为已发者矣。此心为食色而发,则是为人心,而又商量其所发,使合乎道理者,则为道心。其为食色而发者,此心也。商量其所发者,亦此心也。何可谓两样心也?大概心是活物,其发无穷,而本体则一,岂可以节制者为一心,听命者又为一心。”③“心是活物,其发无穷”——如此说法颇有王学之色彩。宋时烈将其“气”论思想进一步贯彻到心性论领域,其“心”遂较朱子之心更具发用性与活泼性。
由此可见,四端七情问题实质是性情问题。所以顺着“四端七情”之辨自然会引出性情之辨。易言之,性情之辨可视为四七之辨的逻辑延伸。与“两宋”先生同时代的明末清初著名思想界王夫之(字而农,晚号船山,1619—1692年)则在四端七情问题上提出了“四端非情”论。他认为朱子犯了“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错误。而性情分属天人——如此混淆容易导致“情”对“性”的侵蚀。在船山看来,如尽其性则喜、怒、哀、乐、爱、恶、欲炽然充塞,其害甚大。①船山以为四端不仅是道心,而且还是性。
今以怵惕恻隐为情,则又误以为以性为情,知发皆中节之和而不知未发之中也(言中节则有节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节也,中之者情也,情中性也)。曰由性善故情善,此一本万殊之理,顺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则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将以知性之不善与?此孟子所以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见端于心者言性,而不于喜怒哀乐之中节者征性也。有中节者,则有不中节者;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固全乎善而无有不善矣。②
依其之见,应以性情、道心人心来分言四端与七情。从船山与同春的四七见解中可以看到17世纪中韩儒学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向。
总之,在宋时烈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之间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一致性。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栗谷之学的忠实继承,而且折射出韩国性理学究天人之际的思想特点。韩儒往往从“天人一贯”的立场出发,将理气关系之探讨具体落实到人间性理的问题上。四端七情以及本然之性气质之性的探讨亦犹如此。
第三节 丁时翰与其“四端七情”论
丁时翰(字君翊,号愚潭,1625—1707年)是朝鲜朝中期退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一生隐居,学行为后世儒者所敬仰,被称为“退溪之隔世高足”。实学开化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星湖李瀷(1681—1763年)在其《墓志铭》中写道:“瀷少而无所知识,不能叩匧从师于并世丁先生门为平生懊恨。”③朝鲜朝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1762—1836年)则评论说:“愚潭先生学术之正,议论之公,忠谠直截之风,明哲敛约之操,卓乎与山岳齐其高,烨乎与日月争其光。己巳为坤殿抗疏,仍救宋尤庵……其论理气四七之辨,一以紫阳退溪为准则,剖折精微,细入秋毫。夫道统之传,或以亲炙,或以私淑,唯德之宗,不观名位。盖自寒冈旅轩而降,真儒醇学,唯先生一人而已。义理之积于中,出处之标于世者,皆足以承嫡传于斯文。”①可见,其学说对后世之影响何等深远。
丁氏之学本于退溪李滉,因此学者亦称其心为“退陶之心”②。丁时翰曰:“退陶之学,绍述朱子,其所以集大成卫斯道者,亦与朱子略同。而朱子之后,儒学归禅。退陶之后,异言立帜。诗教之辨,传习录之跋,不得不出。四七之辨,壬午之录,又不得不著。”③丁时翰生活的年代,学界已分裂成以“主理”和“主气”④为理论特色的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作为近畿主理论学者⑤,丁时翰同李玄逸(字翼升,号葛庵,1627—1704年)一起对李滉的四七理论作了积极维护和系统阐述。⑥本节拟以李滉、李珥、丁时翰思想之比较为中心,来探讨其性理学思想之特点。
一、丁时翰的理气论
“理”与“气”是理学家为学立论的一对核心概念,因此理气问题亦可视为宋明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⑦而朱子则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讨论理学这一基本问题的哲学家。他以理气二分且又“不离不杂”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韩国性理学家们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的过程中,对理气问题①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丁时翰便曾说过:“理气之论,实是圣门极至之源头,而吾儒及异学于此焉分。”②不过,退溪、栗谷时期有关理气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理气动静和理气体用的问题而展开。丁时翰也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
李滉继承朱子“理气二分”说。他基于理气道器之分对二者“不杂”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以及“理尊无对”的观点。李滉重视理气“不杂”义的用意在于强调理对气的主宰作用。对二者“不杂”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观的特色。他曾在《非理气为一物辩证》③一文中写道:“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④进而他还认为,理与气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同,即“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他说:“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⑤、“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⑥。李滉的此一见解,既是对朱子“理先气后”、“理在事先”思想的修正,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进一步发展。他将朱熹的理气“先后”关系转变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由此为其“四七”论打下理论基础。
李珥则与李滉不同。他继承朱子理气之不离思想并对之作了进一步的解析和阐发。其“理气之妙”说、“气发理乘”说以及“理通气局”说皆独具特色。其中“理气之妙”说尤为栗谷思想之精髓——“气发理乘”说和“理通气局”说皆为“理气之妙”说的进一步阐发。
理气之“不离”亦是李珥哲学的主要理论特色。相较于李滉之“理”,李珥的“理气之妙”思想更是其哲学中“难见亦难说”处。李珥有言:“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夫理之源一而已矣,气之源亦一而已矣。气流行参差不齐,理亦流行而参差不齐。”①与李滉相比,他虽在理气说的理论突破上有所不及,却在传承朱子理气说上超而过之。
不过,到了17世纪李珥的这一思想倾向却受到李玄逸、丁时翰等南人学者的批评。丁时翰认为,古今学问道术之异皆源于人们对古圣贤所论之“理”的片面理解。在他看来,圣贤论“理”之言各有所指——有就“体”而言者,有就“用”而言者,有就其本原之理而言者,亦有就其散殊之理而言者。如果只讲“体”之寂然不动而不讲“用”之感而遂通,则徒见本原之理赋予万物而不见散殊之理各有其则,就会导致寂而不感终归于灭的后果。丁时翰继承李滉的“尊理”之思想,由此特别重视“理”之作为。“人之为学,只患于理字上见不透。若于此实见得的确,则处心行事,岂有未尽善乎。尧舜之精一执中,孔颜之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以理为主,而使人心听命焉。若以气为主而作用为性,则其祸必至于滔天。”②可见,在丁时翰的思理中只有“理”才具有“主宰”义,气则无之。他还特别强调了以气为主作用为性的严重后果。
作为主理论者,丁时翰每从维护李滉的角度对李珥之学展开批评:
今栗谷自谓有见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而推出整庵、花潭之绪余,以攻互发之说。故于人心道心,则以为皆源于理,而遂为相为终始之说,以反或原或生之意。于四端七情,则以为皆发于气,而遂为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之说,以反理发气发之意。至于理通气局,则又以为得见整庵、花潭之所未见,阐发前圣所不言之旨。而其所谓理通者,徒归寂灭虚无之地,未有安顿着落之处。而况其云所以发之理者,虽曰乘气,而每以徒具于寂然之中,不发于感通之际为言。其云理通者,虽曰无所不通,而又未免言理于窈冥,言气于粗浅,则是理是气,常隔断阻绝,不能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而终未见浑沦之中自有分开,分开之中自有浑沦之妙矣。盖其所谓理气不相离者,非真有见于理气之不相离也,只是认气为理。至以道心为本然之气,故终始迷昧于理字上。其言本原之体者,鹘囵笼罩,都没紧要,其言发见之用者,专主气字,更不言理。一向逞气骋辩,恣诋前贤,有若莠之乱苗,紫之乱朱,使从古圣贤相传之心法,既明复晦。①
李珥对整庵十分推崇②,他曾言:“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③依丁氏之见,李珥祖述整庵以“气”为重,故徒见理气之不离以及气常载理之一面。也因之无从体验浑沦之中自有分开,分开之中自有浑沦之妙。因此丁时翰批评李珥“昧于大本”。“栗谷则祖述整庵,昧于大本而所尚者气。故发于言论者,类多轻肆凌人底规模。而流弊所及,大为吾道之深害,大本之差不差,而其所发见于言行事为之间者,亦可征矣。”④而且,他还进一步批评李珥“论‘理’之言,亦似非吾儒家法”①。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丁氏继承李滉之“理帅气卒”的思想,进而发展出“理主气辅”论。“朱子‘虽在气中,理自理气自气,不相夹杂之谓性’云者,以其理气妙合之中,理常为主,气常为辅,虽在气中,不囿于气,命气而不命于气之云尔。非以为理气各在一处而不相妙合也。”②他在强调理之主宰性的同时,还对李滉的理气二分说作了有益的补充。指出虽说理为主而气为辅,理气各自不相夹杂。丁时翰特别强调了理气之不离性。
基于其“理主气辅”思想,丁氏提出自己独到的“理气体用”说。
理至有故无不异,至无故无不同,然无者未尝无,有者未尝有,则有无非有二也……理至无而至有云者,犹言无极而太极,或言自无极而为太极者。朱子辨释甚详。又于象山答书中云,不言无极,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由此观之,至无而至有不可云。至有故无不异,至无故无不同。其下两三句,虽合有无而言,不能救上句之病者,人所易知,而敬叔之不悟何哉?敬叔之见,既已如此,故以人物之性,谓有隐显体用,而以至有当显体用,以至无当隐体用。至有至无,分作隐显体用于一性之中,与分言无极太极者,何以异哉?③
“理主气辅”和“理气隐显体用”可以说是丁时翰理气论的主要内容。从以上比较可见,丁时翰理气论虽有重视二者不离性的一面,但是其主要学说仍以主理论为特色,并以此为基础对李滉的“尊理贬气”思想和“理气互发”之说进行了积极的补充和诠释。
二、丁时翰对李珥“四端七情”说的批判
如上一章所述,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基于理学的传统观念认为人都是得“气之正”者,但是由于每个人所禀之气有清浊、粹驳之不同会有“上智、中人、下愚三等之殊”①。于是,他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四端(理)与七情(气)之间的关系。李滉以为四端之情和七情是不同性质的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二者在根源和本质上皆不相同。李滉有言:“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②他认为此论与思孟程朱之旨冥然相契。
李珥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论,他更同情奇大升的观点。李珥对李滉之说的批评遭到了成浑的辩难。由二人之书信往复,李珥的“四七”论立场更加明了。依栗谷之见,对四七理气之发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发矣。”③李珥进而举例说“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④在李珥看来,不仅七情是气发理乘,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二者均为气发理乘。
针对李珥的“气发理乘”说,丁时翰提出如下批评:
理气为物,本混融无间,推之于前,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不见其终之离。而理无眹气有迹,安有无气之理或先或后,发见于事为之间者乎。然而终古圣贤于浑融无间,不可分先后,离合之中,或截而言之,或分而言之,以明此理之命气而不命于气,在气而不杂乎气者……既曰仁之端义之端,则仁发而为恻隐,义发而为羞恶,体用不离,本末相连,可见其不杂于气而一出于理。至于七情,则虽亦出于性而初无不善,但就其性在气质,浑沦理气者而为言。故几有善恶,气易用事,理难直遂,必须观理约气,然后理始显而气听命。此朱子所以有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之言。而今者(指栗谷——引者注)不察孟子剔发言理,朱子分言理气之本意,乃以四端七情滚合为一说,概而言之曰,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专以气发一途为言,而都遗却理发一款。①
依其之见,理无形而气有形,故其作用流行皆若气之所为。但因“理”至无而至有、至虚而至实,且又具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之特性,故其乘气流行皆为自然而然,不见其有所作为。当性情寂感之际,理之神用即蔼然呈露而不可掩——四端粹然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性即为显例。因此,不能仅着眼于理气之浑沦而只言“气发”不讲“理发”。
丁时翰认为,四端与七情从结构而言皆兼备了理和气。因此,四端与七情均与气相关。只是四端并不与气相互夹杂,而七情却受其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主理和主气方得区别。以此为基础,他推导出四端和七情在“所从来”处即相异的结论。这里丁时翰所持的是李滉的观点。在丁氏看来,四端与七情皆本于仁、义、礼、智之性。可见,丁时翰所言“所从来”与奇大升、李珥所谓“源头发端处”或“本源”有所不同——他虽未明言,从其语句中推断出此点。丁时翰以为人心虽无二源,但是其发现于外者可以主理、主气而言。由此可知,其“所从来”并非是“本”。丁氏更侧重于由“本”发用于外的过程,每以此指代他所描述的“就一心之中,方其萌动之开始”的时刻。此刻必是“性”与“气质”相互发生关系的时刻。于是,与气质发生何种的关系遂成区分四端和七情的关键。与“气”相关但不杂于“气”的情为四端;与气相关且在气的驱动下易流于恶的情则为七情。②据此,丁时翰对李滉之说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退溪《四七辨》云:“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栗谷所谓“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者,似本于此。而第退溪之以四端为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者,所指而言者,以其出于性之粹然在中,不杂乎形气者而为言。初不言无感而自发也。以七情为外物之触其形而动于中者所指而言者,以其出于性在气质,易感形气者而为言,亦非谓中无是理也。是以退溪旋以为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且谓“虽滉亦非谓七情不干于理,外物偶相凑着而感动”,且谓“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其本意所在,若是明白;而今者推出退溪所未有之意,说出退溪所未说之言,或以为做出许多葛藤,或以为正见之一累,已极轻肆,而终以无父而孝发,无君而忠发,不见孺子之入井而自发恻隐为心病等语,铺张抑勒,至此之极。岂其未曾虚心翫绎于退溪之说。而略绰看过胡乱说道者耶。①
这段话本是丁时翰为李滉之说所做的辩解。但从上下文以及李滉与奇大升辩论的全过程来看,李滉所言“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一语似有不妥。若谓此话代表李滉之真正立场,则其与奇大升之往复辩论便失去焦点。而丁时翰引这一句等于是否定四端是“无感而自发”。这无疑是其向李珥立场靠近,而承认四端与七情的同构型。②丁氏本人可能未意识到他的这一辩解与其初衷的自相矛盾处,学者于此则不可不察。
总之,丁时翰“四端七情”论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对李滉与李珥“四七理气”说之异同的详尽论述。丁时翰在批驳李珥“气发理乘”说的同时,对其部分见解亦有容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倾向。不过,尽管他在理气关系及四七理论的解释上有折中二李之痕迹,其思想之主旨还是反映了主理论学者的为学性格。
三、丁时翰的“人心道心”论
在韩国儒学史上由李珥与成浑推动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是继“四端七情理气”之辨之后发生的又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学术论争。
在论辩之初,成浑基于李滉“理气互发”之论提出理发即为“道心”而气发则为“人心”。“近日读朱子人心道心之说,有或生、或原之论,似与退溪之意合,故慨然以为在虞舜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理气互发之说,则退翁之见不易论也”①。所谓“或生”与“或原”,盖指朱熹所说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言。道心原于性命之正,纯善无恶;人心生于形气之私,故有善有恶。又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云。究此议论以理气之发,当初皆无不善,而气之不中乃流于恶云矣。”②因此成浑认为李滉的人心道心之说亦自不为过。
李珥同样援引朱子说法以增强说服力。他认为,朱子既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则何从而得此理气互发之说乎?在李珥看来,理气无先后离合不可谓之互发,但人心道心可以从两边来说。其《人心道心图说》有云:“道心虽不离乎气,而其发也为道义,故属之性命;人心虽亦本乎理,而其发也为口体,故属之形气。方寸之中,初无二心,只于发处有此二端。”③李珥在《答成浩原》的最后一书中指出:“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则心是气也,或原或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乎?”④可见,李珥对人心道心的说法亦承朱子之意而为言,且又时时不忘与其“气发理乘一途”之说相联系。其思想的系统性、逻辑性于此可见一斑。
李珥进而发挥朱子之说,提出自己独到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此论乃李珥对人心道心问题的基本看法。
丁时翰对于李珥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评论道:
窃详栗谷之意,概未见人心道心分言之脉络,以朱子或原或生之,为不得已之论而不之信,故每以人心道心滚合为一说。以为同出于本然之性,而以掩乎形气者,谓之人心;以不掩乎形气者,谓之道心。此非虞舜命名,朱子注释之本意也。夫上智不能无人心,则上智之人心,初不掩于形气,而以其从形气而生,故名之以人心。下愚不能无道心,则下愚之道心,虽发于气禀所拘之中,而以其本体之明有未尝息者,故名之以道心。初非以形气之掩与不掩,分言人心道心也。此是圣贤各指其所从来,使人审几用工之旨诀。而栗谷则舍而不取,既不欲相对说下。如朱子之言,而又不欲显言体用二字,以避宗主整庵之嫌。于是乎自作定论,辄以相为终始者言之。而其于道心上,言存养而不言审几。人心则直以为形气所掩而审其过不及云者,果有异于整庵体用之论乎?①
在丁时翰看来,李珥之说不过是祖述整庵学说而已,故而直言其人道说亦无异于整庵之道心人心体用论。他尖锐指出:“虽以浑沦者言之,只可言一心之中,从形气之人心,不离于性命,原性命之道心,不外于形气而已。若谓之人心道心相为终始云尔,则殊非人心道心之所以得名者也。”②依丁时翰之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仁义礼智之性蔼然流行于形气之间;人心生于形气,而视听言动之勿论非礼者乃所以听命于道心。
对于李珥“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源则只是一心”的观点,丁时翰批驳道:
所谓“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源则只是一心;其发也,或为理义,或为食色,故随其发而异其名”云者,初不外于退溪之说矣。既谓之“随其发而异其名”,则岂不可谓理发、气发乎?退溪所谓理气互发者,概以为理与气合而为心,理气混然一心之中,随所感而发,或有理发之时,或有气发之时,互相发现云尔。其言“互发”二字者,益明此心之无二本矣。今乃不察理到之言,而一向挥斥;至其何从得此之说,则又若初不知出于退溪之说者然,显有抑扬凌驾之意。此等气像,似非吾儒法门矣。①丁时翰指出因理气混然于一心之中,故心之发或有理发之时,或有气发之时。在此丁时翰对“理气互发”说作了全新的阐释,即以“互相发现”来解互发之义。他认为李珥对李滉的“理到”说未能真正理会,试图以此说来回应前者对后者的攻击。依止李滉“理气互发”之说,丁时翰不仅对李珥“气发理乘一途”说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而且还称其气象“似非吾儒法门”。其时栗谷学派在学界、政界正日益得势,而退溪学派则渐趋衰落,丁时翰对此十分忧虑,遂与李玄逸一道担当起为退溪学辩护的责任。从丁氏对李珥的批评中,我们随处可见党争之语气——此为两人党派、学派之殊异使然。
我们从比较的视角对丁时翰的理气说、“四端七情”说以及“人心道心”说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可以看出,丁氏不仅在理气关系上确有强调二者不离性的一面,而且在“四七”论方面亦有容受李珥之说的成分。但其学说之主旨仍然基于李滉的“尊理贬气”、“理气互发”之义上,而“理发”之说显然不合朱子“理不活动”之旨。各派间交互影响也是朝鲜朝性理学的特色之一。此外,还发现朝鲜朝儒学因所依文本之不同而造成的“多重文本交叠”的特色及诠释问题的复杂性一面。②在人心道心说方面其特点在于,对朱子所言理气之“心”的重视。
附注
①李珥:《寿夭策》,《栗谷全书》(二)《拾遗》卷5,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558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2页。
③李珥:《节序策》,《栗谷全书》(二)《拾遗》卷5,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553页。
④李珥:《语录上》,《栗谷全书》(二)卷3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57页。
⑤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8页。
⑥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5页。
⑦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7页。
①李珥:《答安应休》,《栗谷全书》(一)卷12《书》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49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9页。
③《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4页。
④《中庸章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0页。
⑤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9页。
⑥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8—209页。
⑦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9页。
⑧李珥:《圣学辑要》三,《栗谷全书》(一)卷2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68页。
⑨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9页。
⑩李珥:《天道策》,《栗谷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310页。
①宋浚吉:《写进春宫先贤格言屏幅跋》,《国译同春堂集2》卷1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年版,第127页。
②参见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丑,“庚申入侍讲中庸及壬子,乙亥入侍昼讲等”,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45、71页。
③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壬子,正月有记梦诗”,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419页。
④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丑二十二年,乙亥入侍昼讲”,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70页。
⑤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21下,《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4页。
⑥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壬子,乙亥入侍昼讲”,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71页。
①宋时烈:《答朴景初(癸丑)》,《宋子大全》卷113,《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64页。
②宋时烈:《答李汝九(癸丑)》,《宋子大全》卷90,《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85页。
③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丑二十二年,乙亥入侍昼讲”,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71页。
④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丑二十二年,乙亥入侍昼讲”,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71页。
⑤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丑二十二年,乙亥入侍昼讲”,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71页。
⑥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丑二十二年,乙亥入侍昼讲”,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71页。
①黄宗羲:《草庐学案》,《宋元学案》卷92,《黄宗羲全集》第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4页。
②参见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397页。
③罗钦顺:《困知记》续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9页。
④罗钦顺:《与林次崖佥宪》(辛丑秋),《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6页。
⑤李滉:《答洪应吉》,《退溪全书》(一)卷13,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48页。
⑥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4页。
⑦宋浚吉:《浦渚赵公谥状》,《国译同春堂集3》卷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版,第135页。
①宋浚吉:《上愚伏郑先生》,《同春堂集·别集》卷3,《国译同春堂集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89页。
②宋浚吉:《上愚伏郑先生》,《同春堂集·别集》卷3,《国译同春堂集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89—90页。
③宋浚吉:《上愚伏郑先生》,《同春堂集·别集》卷3,《国译同春堂集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90页。
④李珥:《圣学辑要》二,《栗谷全书》(一)卷2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56页。
①罗钦顺:《困知记》卷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页。
②参见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401页。
③宋浚吉:《浦渚赵公谥状》,《国译同春堂集3》卷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版,第135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8页。
⑤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9页。
①奇大升:《高峰答退溪论四端七情书》,《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6页。
②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③奇大升:《两先生四七理气往复书上篇》卷1,《高峰集》第三辑,韩国东洋哲学会1997年版,第102页。
①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5—406页。
②李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06页。
③李滉:《改本》,《退溪全书》(一)卷16,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419页。
④李滉:《论理气》,《退溪全书》(四)《言行录》卷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18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②成浑:《附问书》,《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0页。
③成浑:《附问书》,《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3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3页。
⑤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①宋浚吉:《同春堂年谱》“戊戌十一年,己卯入侍召对”,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213页。
②宋浚吉:《浦渚赵公谥状》,《国译同春堂集3》卷2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版,第134—135页。
①宋浚吉:《答郑景式景华》,《国译同春堂集2》卷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年版,第52—53页。
②《孟子·公孙丑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8页。
③宋浚吉:《同春堂年谱》“戊戌十一年,己卯入侍召对”,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213页。
④宋浚吉:《上愚伏郑先生》,《同春堂集·别集》卷3,《国译同春堂集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90页。
①宋浚吉:《上愚伏郑先生》,《同春堂集·别集》卷3,《国译同春堂集4》,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90页。
②宋浚吉:《同春堂年谱》“戊戌十一年,己卯入侍召对”,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213页。
③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亥三十二年,辛巳入侍昼讲”,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258页。
④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6页。
⑤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6页。
①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2页。
②朱熹:《朱子全书》(21),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6页。
③《中庸一·章句序》,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2,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87页。
④《尚书一·大禹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7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09页。
⑤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页。
⑥《尚书一·大禹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7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10页。
⑦《尚书一·大禹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7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15页。
⑧朱熹:《朱子全书》(21),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7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②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③李珥:《人心道心图说》,《栗谷全书》(一)卷14《说》,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82页。
④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丑,庚申入侍讲中庸”,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45页。
⑤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亥三十二年,辛巳入侍昼讲”,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258页。
⑥宋浚吉:《同春堂年谱》“戊申四十一年,十一月己亥入侍召对”,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376页。
①宋浚吉:《同春堂年谱》“乙巳三十八年,癸亥侍召对”,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376页。
②宋浚吉:《同春堂年谱》“辛卯入侍召对夕又入侍”,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374页。
③宋浚吉:《同春堂年谱》“乙巳三十八年,乙丑入侍召对”,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341页。
④宋浚吉:《同春堂年谱》“乙巳三十八年,丙寅入侍召对”,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341页。
⑤宋浚吉:《同春堂年谱》“甲辰三十七年,上疏辞兼论君德”,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325页。
⑥宋时烈:《答李汝九(庚戌)》,《宋子大全》卷90,《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78页。
①参见郭齐勇:《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文史哲》2001年第3期。
②参见郭齐勇:《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文史哲》2001年第3期。
③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亥三十二年,庚辰入侍昼讲”,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257页。
④宋浚吉:《同春堂年谱》“乙巳三十八年,五月丙戌旨行宫即被赐对”,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329页。
⑤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巳三十八年,癸亥入侍召对”,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336页。
⑥宋浚吉:《同春堂年谱》“己巳三十八年,癸亥入侍召对”,首尔:成均馆1981年版,第336页。
①宋时烈:《与李彝仲(丁未·别纸)》,《宋子大全》卷75,《韩国文集丛刊》110,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70页。
②宋时烈:《语录(金幹)》,《宋子大全·附录》卷15,《韩国文集丛刊》11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507页。
③宋时烈:《答朴景初(癸丑)》,《宋子大全》卷113,《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64页。
④宋时烈:《答李汝九(癸丑)》,《宋子大全》卷90,《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86页。
⑤宋时烈:《答李汝九(丁巳·别纸)》,《宋子大全》卷91,《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96页。
①宋时烈:《一阴一阳之谓道》,《宋子大全》卷136,《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514页。
②宋时烈:《一阴一阳之谓道》,《宋子大全》卷136,《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513页。
③宋时烈:《一阴一阳之谓道》,《宋子大全》卷136,《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513—514页。
④宋时烈:《与李汝九(壬子)》,《宋子大全》卷90,《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81页。
⑤宋时烈:《看书杂录》,《宋子大全》卷131,《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36页。
⑥宋时烈:《浩然章质疑》,《宋子大全》卷130,《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10页。
⑦宋时烈:《栗谷别集订误》,《宋子大全》卷130,《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10页。
①《理气上·太极天地上》,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页。
②《理气上·太极天地上》,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5页。
①宋时烈:《朱子言论同异考》,《宋子大全》卷130,《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19—420页。
②宋时烈:《答郑景由(丁巳·别纸》,《宋子大全》卷101,《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94页。
③宋时烈:《看书杂录》,《宋子大全》卷131,《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36—437页。
④宋时烈:《一阴一阳之谓道》,《宋子大全》卷136,《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514页。
①宋时烈:《记述杂录(韩元震)》,《宋子大全·附录》卷19,《韩国文集丛刊》11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587页。
②金正默:《寒水斋先生行状辨》,《过斋遗稿》卷6《杂著》,《韩国文集丛刊》25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版,第309页。
③宋时烈:《答沈明仲》,《宋子大全》卷105,《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94页。
①宋时烈:《答金直卿(仲固·别纸)》,《宋子大全》卷104,《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61—462页。
②宋时烈:《答金仲固(丙辰)》,《宋子大全》卷104,《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70页。
③宋时烈:《己丑封事》,《宋子大全》卷5,《韩国文集丛刊》108,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90页。
④宋时烈:《语录》,《宋子大全·附录》卷15,《韩国文集丛刊》11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502页。
⑤宋时烈:《与李汝九(壬子·别纸)》,《宋子大全》卷90,《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82页。
⑥宋时烈:《答李汝九》,《宋子大全》卷90,《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88页。
①宋时烈:《杂著》,《宋子大全》卷131,《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30页。
②宋时烈:《与李汝九(壬子·别纸)》,《宋子大全》卷90,《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84页。
③宋时烈:《答金直卿仲固》,《宋子大全》卷104,《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63页。
④宋时烈:《答朴景初(别纸)》,《宋子大全》卷113,《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68页。
⑤朱熹:《朱子全书》(20),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91页。
⑥朱熹:《孟子或问》卷14,《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页。
⑦《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页。
⑧《性理一·人物之性气质之性》,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页。
①宋时烈:《答李汝九(戊午)》,《宋子大全》卷91,《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97页。
②宋时烈:《看书杂录》,《宋子大全》卷131,《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28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9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7页。
①李珥:《圣学辑要》二,《栗谷全书》(一)卷20,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455页。
②李珥:《人心道心图说》,《栗谷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83页。
③宋时烈:《朱子言论同异考》,《宋子大全》卷130,《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18—419页。
①宋时烈:《退溪四书质疑疑义》,《宋子大全》卷133,《韩国文集丛刊》11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66页。
②宋时烈:《年谱》,《宋子大全·附录》卷9,《韩国文集丛刊》115,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90页。
③宋时烈:《答李汝九(庚戌)》,《宋子大全》卷90,《韩国文集丛刊》11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179页。
①参见郭齐勇:《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文史哲》2001年第3期。
②转引自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③丁时翰:《墓志铭》,李瀷:《愚潭集》卷12,《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437页。
①丁若镛:《旁亲遗事》,《遗事》,《增补与犹堂全书》第1集卷17,首尔:韩国景仁文化社1987年版,第358—359页。
②“先生之心,即退陶之心也。”(丁时翰:《言行闻见录·门人赵宇鸣》,《愚潭集》卷10《附录》,《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84页)
③丁时翰:《言行闻见录·门人赵宇鸣》,《愚潭集》卷10《附录》,《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84页。
④“主理”与“主气”是韩国性理学所特有的用语。简言之,退溪学派重“理”之优位性、发用性,栗谷学派则重“气”之有为性和作用性。故将以“主理派”和“主气派”称谓来指代退溪、栗谷两派。但是,近来对此称谓学界亦有不同主张,相关讨论可参见李东熙:《朝鲜朝朱子学的哲学思维与论争》,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2006年版,第307—333页;韩国哲学思想研究会编:《论争所见韩国哲学》,首尔:艺文书院1995年版,第129—148页。
⑤参见金洛真:《愚潭丁时翰的四端七情论》,载《四端七情论》,首尔:曙光社1992年版,第169页;李基镛则更具体地指出,愚潭思想反映的是以江原道原州地区为中心的近畿南汉江圈学者的独特立场。见《愚潭丁时翰与原州》,载《愚潭丁时翰研究》,原州:江原道民日报社2009年版,第2页。
⑥“常曰,朱夫子集群贤之大成,而在吾东则惟退溪为然。然而理气之说,既明而复晦,为后学之蔀障,遂著四七辨证,壬午录。条列而证明之。”(丁时翰:《言行闻见录·门人赵宇鸣》,《愚潭集》卷10《《附录》,《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84页)
⑦参见黄宗羲(1610—1695年)亦曾曰:“理气乃学之主脑。”(见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50页)
①在朝鲜朝性理学史上理气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理论趋向和旨趣各不相同。初期以无极太极论辩为契机更多以宇宙论层面探讨理气问题,中期和后期(即性理学确立和深化时期)则以四端七情论辩、人心道心论辩以及人物性同异论辩为契机主要从人性论层面谈论理气问题。相关论述可参见尹丝淳:《朝鲜朝理气论的开展》,载《风流与和魂》,沈阳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54页;宋荣培等:《韩国儒学与理气哲学》,首尔:艺文书院2000年版;李甦平:《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②丁时翰:《与许太休曤,金士重》,《愚潭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257页。
③此文是李滉为了辩驳罗钦顺等人的“理气非异物”思想而撰写。罗氏“认理气为一物”,对此李滉认为整庵“所见于大头脑处错了”。《寒洲集》又记载:“退陶先生曰,整庵之学自谓辟异端,而阳排阴助,左遮右拦,实程朱之罪人也。”(见李震相:《年谱》,《寒洲集·附录》卷1,《韩国文集丛刊》
318,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277页)④李滉:《非理气为一物辩证》,《退溪全书》(二)卷4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331页。
⑤李滉:《天命图说》,《杂著》,《退溪集》卷8,《韩国文集丛刊》31,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209—210页。
⑥李滉:《与朴泽之》,《书》,《退溪集》卷12,《韩国文集丛刊》29,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版,第337页。
①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4页。
②丁时翰:《叙述门人赵沇》,《愚潭集》卷10《附录》,《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92页。
①丁时翰:《四七辨证·总论》,《愚潭集》卷8,《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55页。
②罗钦顺所撰的《困知记》一书何时传入朝鲜,学界尚定论。但是其学说在朝鲜朝性理学史上影响较大,尤其是其“理气一物”论思想和“道心人心体用”说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困知记》一经传入,退溪便撰《非理气为一物辩证》予以驳斥。而栗谷则对钦顺给予极高评价,曰:“整庵则望见全体,而微有未尽莹者,且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而其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理气为一物也,所见未尽莹故言,或过差耳。”(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4页)此后学界对罗氏学说的态度,大体上划分为以李滉与李珥为首的批判和同情两个阵营。了解罗氏学说对理解和把握退栗性理学有较大益处。相关研究可参见刘明钟:《栗谷哲学与罗整庵的内在式理气说》、《朝鲜儒学与罗整庵的内在式理气哲学》,载《退溪与栗谷哲学》,釜山:东亚大学校出版部1987年版;李东熙:《罗整庵与李栗谷》,载《东亚朱子学比较研究》,大邱:启明大学校出版部2005年版;赵南浩:《罗钦顺哲学与朝鲜学者的论辩》,首尔大学校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2月;崔重锡:《罗整庵与李退溪哲学思想》,首尔:图书出版SimSam文化2002年版;杨祖汉:《李栗谷与罗整庵思想比较》,载《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版;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湾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149—192、239—283页;等等。
③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4页。
④丁时翰:《四七辨证·栗谷答成浩原书》,《愚潭集》卷7,《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30页。
①“栗谷论‘理’之言,亦似非吾儒家法。而殊无笃信圣贤虚心逊志之气象,故其见诸言行之间,亦多有高自标致,轻视人物之气习。虽以所自撰石潭野史观之,可征其一二也。”(丁时翰:《与许太休嚯,金士重》,《愚潭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257页)
②丁时翰:《壬午录》,《愚潭集》卷9《杂著》,《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71页。
③丁时翰:《答李敬叔》,《愚潭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280—281页。
①李滉:《天命图说》,《退溪全书》(三)续集卷8,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143页。
②李滉:《心统性情图说》,《退溪全书》(一)卷7,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5年版,第205页。
③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3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8页。
①丁时翰:《四七辨证》,《愚潭集》卷7,《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20页。
②参见金洛真:《愚潭丁时翰的四端七情论》,载《四端七情论》,首尔:曙光社1992年版,第175—177页。
①丁时翰:《四七辨证·栗谷答成浩原书》,《愚潭集》卷7,《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28页。
②参见李明辉:《朱子性理学与韩儒丁时翰的四端七情论》,载《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240页。
①成浑:《附问书》,《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00页。
②成浑:《附问书》,《答成浩原·壬申》,《栗谷全书》(一)卷9《书》1,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192页。
③李珥:《人心道心图说》,《栗谷全书》(一)卷14,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82页。
④李珥:《答成浩原》,《栗谷全书》(一)卷10《书》2,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版,第210页。
①丁时翰:《四七辨证·栗谷答成浩原书》,《愚潭集》卷7,《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31—332页。
②丁时翰:《四七辨证·栗谷答成浩原书》,《愚潭集》卷7,《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17页。
①丁时翰:《四七辨证·栗谷答成浩原书》,《愚潭集》卷7,《韩国文集丛刊》12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3年版,第323页。
②李明辉:《朱子性理学与韩儒丁时翰的四端七情论》,载《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