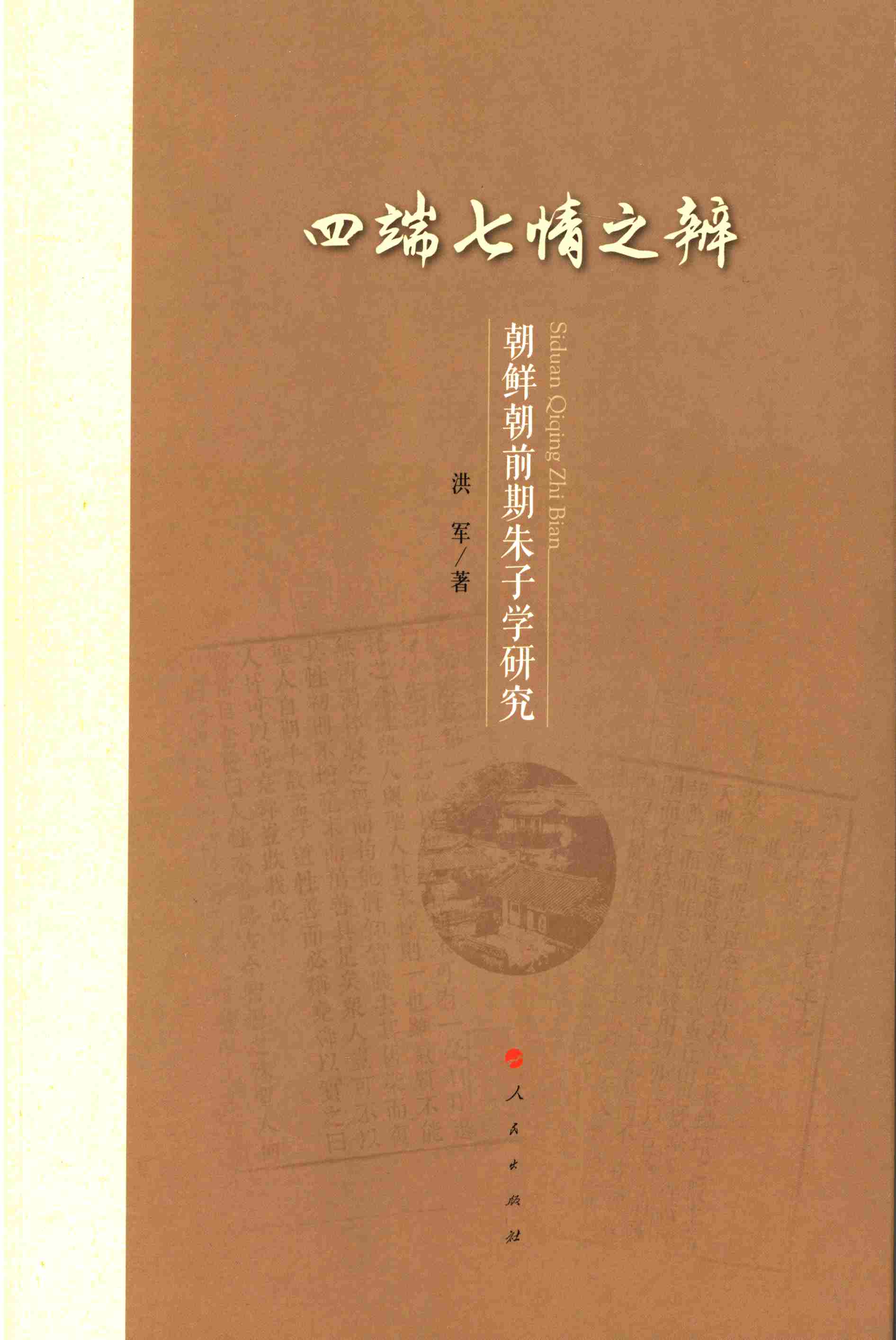第四节 李珥与其“四七人心道心”论
| 内容出处: | 《四端七情之辨》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9051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李珥与其“四七人心道心”论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31 |
| 页码: | 165-19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李珥(1536-1584年)是韩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之一。他自幼受到母亲师任堂的教育,早期就开始接触儒家经典。李珥对多种学说进行了批判和吸纳,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学说。与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相比,李珥认为理和气并非一物,而是通过“气发理乘一途”来实现的。他也将自己的学说与李滉和徐敬德的学说进行了比较,并表示对罗钦顺的学说赞赏。李珥的理气学说在韩国性理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 |
| 关键词: | 四端七情 李珥 朱子学 |
内容
李珥(字叔献,号栗谷、石潭,1536—1584年)出生于江原道江陵北坪村(乌竹轩)外氏第,籍贯为德水,谥号文成,是韩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自幼受母亲师任堂之训导,很早便接触儒家经典。《年谱》中写道:“壬寅二十一年,先生七岁……先生始受学于母夫人,间就外傅,不劳而学日就,至是文理该贯,四书诸经,率皆自通。”①其母申氏,号师任堂,是己卯士祸(1519年)的名贤申命和之女,以诗、书、画三绝而闻名于世。在母亲的良好教育下,李珥从孩提时代起即表现出其超群天资。而其8岁时(在坡州栗谷里花石亭)写下的五言律诗《花石亭》,则至今令人惊叹不已。诗云:
林亭秋已晚,骚客意无穷。
远水连天碧,霜枫向日红。
山吐孤轮月,江含万里风。
塞鸿何处去,声断暮云中。②
这首诗不仅诗句对仗工整,而且其格调浑成,虽深谙诗律者亦有所不及。③尤其是诗中的“山吐孤轮月,江含万里风”一句,很难想象出自8岁孩童之笔。李珥从13岁始在进士初试中状元及第至29岁魁生员及文科前后止,应科举试9次,均已状元及第,故又被称为“九度状元公”。
李珥16岁时其母(师任堂申氏)遽尔逝世,与母亲感情极深的他此时深感人生无常,于是三年后(19岁)脱下孝服后入金刚山摩诃衍道场修行佛法。在一次与老僧的问答中他旋觉佛学之非而决心下山,正式弃佛学儒。次年(20岁)往江陵作了“自警文”11条,第一条即谓:“先须大其志以圣人为准则,一毫不及圣人,则吾事末了。”①李珥年少李滉35岁,明宗十三年(23岁)春拜谒李滉于礼安陶山,并滞留两天向其主动请教了主一无适及应接事务之要,消释了平日积累之疑点,并给李滉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两位大儒的首次晤面,之后李滉在答门人月川赵穆的信中,曾大加赞赏李珥谓:“汉中李生珥自星山来访,关雨留三日乃去。其人明爽,多记览,颇有意于吾学,后生可畏,前圣真不我欺也。”②李珥的《行状》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写道:“二十三岁谒退溪先生于陶山,问主一无适、应接事物之要,厥后往来书札,辩论居敬穷理及庸学辑注,圣学十图等说。退溪多舍旧见而从之,尝致书曰:世间英才何限而不肯存心于古学,如君高才妙年,发轫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千万益以远大自期。”③可见,尽管这是二人初次晤对,但是对彼此的思想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他们通过书信还有过多次相互问学,由此共同开创出韩国性理学自主的理论探索与创新的全盛时代。
在韩国哲学史上,李珥与李滉并称为韩国性理学的双璧。畿湖地区的学者(指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一带的学者)大都从栗谷李珥之说,称栗谷为“东方之圣人”;岭南地区的学者(庆尚道一带的学者)则大都从退溪李滉之说,称退溪为“东方之朱夫子”。于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性理学派——栗谷学派和退溪学派,两个学派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不同的发展方向。
一、李珥的“理气之妙”论——与罗钦顺“理气一物”论之比较为中心
以东亚儒学史的视角而观,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6世纪中后叶中韩儒学史上涌现出一批具有重要理论建树和思想影响的鸿儒硕学。如这一时期的明代大儒有罗钦顺(1465—1547年)、湛若水(1466—1560年)、王守仁(1472—1528年)、王廷相(1474—1544年)等;朝鲜朝的名儒则有赵光祖(1482—1519年)、徐敬德(1489—1546年)、李彦迪(1491—1553年)、曹植(1501—1572年)、李滉(1501—1570年)、郑之云(1509—1561年)、奇大升(1527—1572年)、李珥(1536—1584年)、成浑(1535—1598年)等,皆为称誉于海内外的“杰然之儒”。可见,在东亚儒学史上这是一个名儒辈出、学说纷呈的学术至为兴盛时期。
其中,江右大儒罗钦顺则被称为“朱学后劲”、“宋学中坚”。他的学说中所呈现的新的理论动向不仅影响了其时的明代理学的演进,而且还传至域外影响了韩国性理学和日本朱子学的发展。下面将通过罗钦顺与李珥理气说的比较,来探讨李珥理气论的特色。
李珥之学,正如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年)所言“不由师传,默契道体似濂溪”①。尽管李珥学无定师,但是其立学极重视统合诸流,汇纳各家。故宋时烈又赞其谓:“遂取诸家之说,分析其同异,论正其得失,务得至当之归……其有乐浑全而恶分析,则先生(指李珥——引者注)必辩其同异于毫厘之间,其有逐末流而昧本源,则先生必一其宗元于统会之极。”②
虽然李珥生活的年代是在“破邪显正”的幌子下,对除朱子学以外的其他学派均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的时代,但他并不盲从朱子,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和自主精神。针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之说,李珥曾言道:“若朱子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何以为朱子乎?”③这种为学上的自主和批判精神,使其能够对历史上的和同时代的各家学说加以吸收和借鉴,构筑以理气“不离”之义为特色的独特性理哲学体系。
在与其同时代的中韩诸儒中,李珥唯独对罗钦顺非常赞赏,曰:“罗整庵识见高明,近代杰然之儒也。有见于大本,而反疑朱子有二歧之见。此则虽不识朱子,而却于大本上有见矣。”④表明李珥认为罗钦顺对朱学之大本,即对朱学的要领是有真切之体会。于是,将整庵罗钦顺与退溪李滉、花潭徐敬德做比较时,亦将其推为最高。曰:“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①李滉和徐敬德是与李珥同朝的另外两位大儒,在韩国哲学史上均具有重要影响。而李珥最为称赞罗钦顺的原因在于,较之李滉和徐敬德,罗钦顺不仅有见于朱学之大本,且多有自得之味。
同时,他还将罗钦顺学说同薛瑄(1389—1465年)、王守仁(1472—1529年)之学亦做过比较,曰:“罗钦顺拔萃人物,自所见少差;薛瑄虽无自见处,自可谓贤者也;王守仁则以谓朱子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之祸,其学可知。”②此处李珥对薛瑄的评价同罗钦顺对薛氏的评价内容亦大体相似,罗钦顺在《困知记》中曾写道:“薛文清学识纯正,践履笃实,出处进退,惟义之安。其言虽间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见有能及之者,可谓君子儒矣。”③由此可见,《困知记》一书对李珥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困知记》何时传入韩国,学界尚无定论。④但是该书传入韩国后,在16世纪朝鲜朝儒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不少学者撰文对之加以评说。⑤其中代表性论者有:卢守慎(字寡悔,号苏斋,1512—1590年)、李滉、奇大升、李珥等人。
不过,与罗钦顺相比李珥为学则更具开放性。比如对其时盛行于明代思想界的阳明心学李珥也并未一概排斥,而主张应“取其功而略其过”,认为这才是“忠厚之道”。⑥这显然与罗钦顺对待心学之立场差异较大。
前已言及,李珥的性理学是在对各家理论的批判、撷取中形成。其中,直接影响其理气学说形成的有三家理论——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李滉的“理气二元”论、徐敬德的“气一元”论。李珥曾对此三家学说做过详细的评论,曰:
整庵则望见全体,而微有未尽莹者,且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而气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以理气为一物也。所见未尽莹,故言或过差耳。退溪则深信朱子,深求其意。而气质精详慎密,用功亦深。其于朱子之意,不可谓不契,其于全体,不可谓无见,而若豁然贯通处,则犹有所未至,故见有未莹,言或微差。理气互发,理发气随之说,反为知见之累耳。花潭则聪明过人,而厚重不足。其读书穷理,不拘文字而多用意思。聪明过人,故见之不难;厚重不足,故得少为足。其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了然目见,非他人读书依样之比,故便为至乐。以为湛一清虚之气无物不在,自以为得千圣不尽传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气局一节。继善成性之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者也。理无变而气有变,元气生生不息,往者过来者续。而已往之气,已无所在。而花潭则以为一气长存,往者不过,来者不续,此花潭所以有认气为理之病也。虽然偏全闲,花潭是自得之见也。今之学者开口便说理无形而气有形,理气决非一物。此非自言也,传人之言也。何足以敌花潭之口而服花潭之心哉。惟退溪攻破之说,深中其病,可以救后学之误见也。盖退溪多依样之味,故其言拘而谨;花潭多自得之味,故其言乐而放。谨故少失,放故多失。①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尽管李珥为学极重“自得之味”,但是在为学性格上他仍坚守朱学的立场。故他强调,“宁为退溪之依样,不必效花潭之自得”②。二是,他认为罗钦顺气质英迈超卓故能望见朱学之全体,但是又因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故其言论确有“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李珥以为理气实际上“非为一物”,而是“一而二、二而一”妙合关系。三是,李滉能深信朱子,气质亦精详慎密,故对于朱子之意,不可谓不契。但是因于豁然贯通处有所未至,故其所见亦有未尽莹者。这里主要是指,他与李滉在理气之发问题上的分歧。在此一涉及朝鲜朝性理学的核心论题的见解上,李珥反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而是主张颇有“主气”意味的“气发理乘一途说”。四是,李珥尽管对徐敬德“理不先于气”思想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于理气不相离之妙有了然目见”,但是同时指出徐敬德之说有“认气为理之病”。李珥以为,继善成性之“理”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故主张“一气长存”之上则更有“理通气局”一节。
由此亦可概见李珥在理气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即“一而二、二而一”的“理气之妙”说、“气发理乘一途”说以及“理通气局”说等。其实李珥正是用这些学说来试图解答,朱学的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基本理论问题。其中,“理气之妙”思想既是李珥性理学的根本立场,亦是理解其性理哲学的理论要害。
要之,从李珥对罗钦顺的肯定以及对其学说的重视中可以看出,罗钦顺理气说是影响李珥理气思想形成的主要理论之一。
朱子学演进至罗钦顺,较之原来的理论发生了明显改变。首先是在理气观方面与朱熹的学说产生了较大差异。从理学史角度来看,明中叶的朱学呈现出从“理本”向“气本”发展的趋向。无疑,罗钦顺是在这一理学发展转向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
理学从二程开始,在哲学的宇宙论上,把“理”作为宇宙的普遍原理,同时又认为这个“理”是气的存在、运动的“所以然”。朱熹继承并发展这一思想,建构了以理气二分、理气“不离不杂”①为特色的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朱熹以为,“理”是不杂而又不离于气的形上实体,强调“理”作为气之所以然而具有的实体性和主宰性。这一思想在朱子后学中受到不少怀疑,罗钦顺便是对此提出异议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罗钦顺对朱熹理气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理气二分思想上。他在《困知记》一书中,写道: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所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①
周子《太极图说》篇首无极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释,可无疑矣。至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语,愚则不能无疑。凡物必两而后可以言合,太极与阴阳果二物乎?其为物也果二,则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终身认理气为二物,其源盖出于此。愚也积数十年潜玩之功,至今未敢以为然也。尝考朱子之言有云“气强理弱”,“理管摄他不得”。若然,则所谓太极者,又安能为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邪?惜乎,当时未有以此说叩之者。姑记于此,以俟后世之朱子云。②
此处所引两段引文是在其《困知记》中质疑朱熹理气二分说的主要段落。同时,从此段引文中亦可概见罗钦顺在理气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首先在对于“气”的理解上,罗钦顺明确指出“气”才是宇宙的根本存在,故主张“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虽然朱熹亦认为“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的物质形态,但是罗钦顺的主张已明显呈现出由“理本”转向“气本”的趋向。其次在对于“理”的理解上,罗钦顺则明确反对“理”在朱熹学说中具有的“实体性”、“主宰性”。依罗钦顺之见,“理”即是所谓“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亦即事物自身中的“自然之机”和“不宰之宰”。
由此罗钦顺提出“理即气之理”的主张,他说:“吾夫子赞《易》,千言万语只是发明此理,始终未尝及气字,非遗之也,理即气之理也。”①
进而在理气为“一物”还是“二物”的问题上,他则断言“仆从来认理气为一物”②。以为,理是气之运动的内在根据和法则,并不像朱熹所说的是依附于气的另一实体(物)。尽管坚守“认理气为一物”的立场,但是他同时又明确表示学者亦不能将“气”认为“理”。他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③表明,罗钦顺是反对将理气视为二元对待的两个实体,实体只是气,而“理”只是这一实体的自身的规定。即,这一实体固有的属性或条理。
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以及“理须就气上认取”思想既是罗钦顺理气论的核心要义,亦是其理气说“最为难言”的地方。对此,他也曾坦言道:“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发,最为难言,要在人善观而默识之。‘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也。”④
罗钦顺自谓其理气不二之说并非为“臆决”,而是由宗述明道而来。他说:“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决也。明道尝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又曰:‘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窃详其意,盖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说个形而上下,则此理无自而明,非溺于空虚,即胶于形器,故曰‘须著如此说’。名虽有道器之别,然实非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至于‘原来只此是道’一语,则理气浑然,更无隙缝,虽欲二之,自不容于二之,正欲学者就形而下者之中,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则不是也……晦翁先生……谓‘是理不离气,亦不杂乎气’,乃其说之最精者。但质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良由将理气作二物看,是以或分或合,而终不能定于一也。”①可见,罗钦顺对程明道学说是极为推崇。尤其是,程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和“原来只此是道”思想是罗钦顺理气浑然一体说的立论根据。若以此来衡量伊川、朱子理气说,皆有析理气为二物之嫌。此外,二程的“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②和“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③等思想,亦是罗钦顺构筑其理气说的主要理论来源。
李珥对明道的思想亦极为重视,这一点与罗钦顺相似。而且,在李珥和罗钦顺著述中所引用的二程言论大都为明道之说。宣祖五年(李珥37岁),李珥与好友成浑(字浩原,号牛溪,1535—1598年)进行理气心性问题的论辩时,曾系统阐述自己的理气观。论辩中,他还对成浑言道:“兄若不信珥言,则更以近思录、定性书及生之谓性一段,反复详玩,则庶乎有以见之矣。”④表明《近思录》及明道的《定性书》、《生之谓性章》等是李珥性理学的重要的理论来源。尤其是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的思想亦是李珥理气说的立论根据。他说:“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此言理气之不能相离。”⑤李珥的理气观,正是以理气之不相离为其理论前提。
前已述及,李珥对罗钦顺十分赞赏,称其为“拔萃人物,自所见少差”。首先,在强调理气之不相离的意义上,李珥与罗钦顺持相同的立场。他说:“夫理之源一而已矣,气之源亦一而已矣。气流行而参差不齐,理亦流行而参差不齐。气不离理,理不离气,夫如是则理气一也。何处见其有异耶?所谓理自理,气自气,何处见其理自理,气自气耶?望吾兄精思著一转,欲验识见之所至也。”①这是李珥答成浑信中的一段话。李珥发挥明道之理气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告诫成浑理气不相离之妙须通过精思与证会方能真正体会。其次,在强调理气之不相杂的意义上,李珥与罗钦顺则明显有差异。在李珥的理气说中,理作为气之根柢及造化之根源在理气关系中被赋予主宰义,具有重要地位。如,李珥曰:“夫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②,“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③。可见,在理的规定上李珥与罗钦顺是有区别的。其实,这便是李珥称罗钦顺为“望见全体,而微有未尽莹者”及“气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理气为一物也”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李珥性理学说与朱学的传承关系。较之罗钦顺,李珥在强调理气之不相离的同时,亦强调二者之不相杂。他认为理气关系是“既非二物,又非一物”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他说:“一理浑成,二气流行,天地之大,事物之变,莫非理气之妙用也。”④这就是李珥的“理气之妙”思想,也是其整个性理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
那么,何谓“既非二物,又非一物”呢?李珥对此解释道:“非一物者,何谓也?理气虽相离不得,而妙合之中,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杂,故非一物也。非二物者,何谓也?虽曰理自理,气自气,而浑沦无间,无先后,无离合,不见其为二物,故非二物也。”⑤理气一方面妙合之中互不相杂,理自理,气自气,故非为“一物”;另一方面二者又浑然无间,无先后,无离合,故亦非为“二物”。前者所强调的是理气二者各自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后者所强调的是在现实的意义上二者所具有的共时性、共存性。
接着李珥总结明道与朱子的理气关系论述,指出:
考诸前训,则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气浑然无间,元不相离,不可指为二物。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虽不相离而浑然之中实不相杂,不可指为一物。故朱子曰: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杂。合二说而玩索,则理气之妙,庶乎见之矣。①
以上引文中,亦可概见李珥为学上的特点。即,注重对各家学说的融会贯通。因理与气是相互渗透、相互蕴涵的关系,故不可指为“二物”;但二者是妙合之中,又各自有其不同的内涵和特性,故又不可指为“一物”。此种“非二物”故“二而一”、“非一物”故“一而二”的思维模式,正好反映了李珥独特的哲学思维方法。
李珥性理学中的最为紧要处,便是其“理气之妙”说。对此,他亦曾言道:“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②尽管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李珥却对此说颇为自信。他在给成浑的一封复信中,写道:“珥则十年前已窥此端,而厥后渐渐思绎,每读经传,辄取以相准,当初中有不合之时,厥后渐合,以至今日,则融会吻合,决然无疑。千百雄辩之口,终不可以回鄙见。”③表明,通过其多年努力而体贴到的理气之妙合关系,李珥已完全确信无疑。
于是,李珥从其“理气之妙”思想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理气动静说。他指出:“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④此即李珥所谓的“气发理乘”说。他对此二十三字所言之内容,极为肯定。简言之,所谓“气发理乘”是指,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气化流行)时理乘之而无所不在的存有形态。李珥此说,既是对李滉“理气互发”说的批判,亦是对朱子理气说的进一步继承与阐发。
理发气发问题是朝鲜朝前期性理学的中心论题之一,此论与“四端七情”之辨相关联,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的理论特色。
李珥在与成浑(成浑基本上持李滉的立场)的四端七情论辩中,还系统阐发了其“气发理乘”思想。曰:
气发而理乘者,何谓也?阴静阳动,机自尔也,非有使之者也。阳之动则理乘于动,非理动也;阴之静则理乘于静,非理静也。故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阴静阳动,其机自尔,而其所以阴静阳动者,理也。故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夫所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者,原其本然而言也;动静所乘之机者,见其已然而言也。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则理气之流行皆已然而已,安有未然之时乎?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无非气发理乘之也。所谓气发理乘者,非气先于理也,气有为而理无为,则其言不得不尔也。①
李珥的“气发理乘”说是以理气“元不相离”为其立论前提,加之在其哲学中“气”具有形、有为之特性而“理”却无之,故“理”不能以动静言。依他之见,理之所以流行,是乘气之流行而流行,理之有“万殊”,亦因气之流行所致。不但天地之化是如此,而且人心之发亦不外乎此。发之者是其然,是表现者;所以发者是所以然,是使表现者得以实现的主宰者。
而且,同成浑的往复论辩中,李珥则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指出:“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②文中,李珥不仅指责李滉未能正确理会朱子之意,而且还主张不仅七情是气发而理乘,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
进而,他又以“理气之妙”论为基础推出自己在理气同异思想,即“理通气局”说。那么,何谓“理之通”、“气之局”呢?李珥解释曰:
理气元不相离,似是一物,而其所以异者,理无形也,气有形也;理无为也,气有为也。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理通者何谓也?理者,无本末也,无先后也。无本末、无先后,故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是故乘气流行、参差不齐,而其本然之妙无乎不在。气之偏则理亦偏,而所偏非理也,气也。气之全则理亦全,而所全非理也,气也。至于清浊、粹驳、糟粕、煨烬粪壤污秽之中,理无所不在各为其性,而其本然之妙则不害其自若也。此之谓理之通。气局者何谓也?气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后也,气之本则湛一清虚而已曷。尝有糟粕、煨烬粪壤污秽之气哉?惟其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故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于是气之流行也,有不失其本然者,有失其本然者。既失其本然,则气之本然者已无所在,偏者偏气也,非全气也;清者清气也,非浊气也;糟粕煨烬,糟粕煨烬之气也;非湛一清虚之气也。非若理之于万物本然之妙,无乎不在也。此所谓气之局也。①此段引文集中反映了李珥理气说之基本要义。文中可以看出,他从理气关系和理气之特性着手,论述了“理通气局”、“气发理乘”及“理之偏全”等问题,阐明了其在理气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要之,所谓“理通”,是指“理同(同一理)”;“气局”,则指“气异(各一气)”。②对于“理通气局”这一命题,李珥自诩为“理通气局四字,自谓见得,而又恐读书不多,先有此等言,而未见之也”③。此说尽管亦受程朱的“理一分殊”、“理气同异”及佛教华严宗的“理事通局”说的影响,但是仅就以通局范畴表述理气之异而言确为李珥独见。而且,在他的性理哲学逻辑结构中“理通气局”与“气发理乘”说,作为说明人物性同异与性情善恶的重要命题互为对待、互为补充,共同构筑了其“四七人道”说的立论基础。
概言之,通过罗钦顺“理气一物”论与李珥“理气之妙”说的比较,可以看出16世纪中韩朱子学的不同发展面向。罗钦顺从去“理”的实体化、主宰义入手,将“理”视为“气”所固有的属性或条理,反对将理气视为二元对待的两个实体,明显表现出由“理本”向“气本”的转向。而,李珥虽然与罗钦顺同尊明道,但是仍表现出坚守朱学之为学性格,提出理气“非二物”故“二而一”、“非一物”故“一而二”的颇具特色的“理气之妙”说,对明道和朱熹思想作了有益的阐发。李珥和罗钦顺的理气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朱熹的理气学说,而且也为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路径。
二、李珥的“四七人心道心”论——与成浑“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
通过对李滉、奇大升等人的“四七”论的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出,四端七情问题其实讨论的是“性”与“情”关系问题,因此顺四端七情理气问题便可以引出有关性情善恶及人心道心问题的论议。而栗谷李珥和牛溪成浑之间围绕人心道心问题展开的第二次“四七”之论争,便是四七理气问题在更深一层意义上的,即性情层面上的展开。在韩国哲学史上李珥和成浑之间发生的第二次“四七理气”之辨,既丰富了原有的四七理气理论之意涵,又开启了对性情善恶与人心道心关系问题的新的理论探索,将“四七”论引向了新的问题域。下面,将以李珥与成浑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探讨“四七”论进一步发展之状况。
成浑(字浩原,号牛溪,1535—1598年),昌宁人,谥号文简,朝鲜朝著名性理学家。成浑幼承庭训,学业大进,15岁便博通经史文辞,为人们所叹服。其父成守琛曾受学于赵光祖,成浑则尊幕李滉且多从其说。他与李珥交情甚笃,二人围绕“四七问题”进行了长达6年的书函往复,①继“退、高之辩”之后将此一论辩又推向了高潮。
成浑的“四七”论和“人心道心”说的主要理论观点,大都集中在与李珥的往复论辩第一书和第二书。在致李珥的信中,成浑写道:“今看十图《心性情图》,退翁立论,则中间一端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云。究此议论,以理、气之发,当初皆无不善,而气之不中,乃流于恶云矣。人心道心之说,既如彼其分理、气之发,而从古圣贤皆宗之,则退翁之论,自不为过耶?”①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成浑是大抵接受李滉的立场,也认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基于此,成浑以为理发则为道心,而气发则为人心。
进而,他又曰: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二名,何欤?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理、气之发不同,而危、微之用各异,故名不能不二也。然则与所谓“四端、七情”者同耶?今以道心谓之四端,可矣;而以人心谓之七情,则不可矣。且夫四端、七情,以发于性者而言也;人心、道心,以发于心者而言也。其名目意味之间,有些不同焉。幸赐一言,发其直指,何如?人心、道心之发,其所从来,固有主气、主理之不同,在唐虞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说,圣贤宗旨,皆作两下说,则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然“气随之”、“理乘之”之说,正自拖引太长,似失于名理也。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为性情之图,则不当分开,但以四、七俱置情圈中,而曰“四端,指七情中理一边发者而言也:七情不中节,是气之过不及而流于恶”云云,则不混于理、气之发,而亦无分开二歧之患否耶?并乞详究示喻。②
文中成浑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对人心道心问题的具体看法。首先,援引朱子《中庸章句》中的或生、或原说法,主张人心、道心二者是理气之发不同、危微之用各异;其次,在四端七情与人心道心的关系上,以为道心可视为四端,但是人心不可视为七情。而且又从“性发为情”、“心发为意”之向度,称“其名目意味之间,有些不同”;再次,他从二者的“所从来”意义上,主张人心、道心亦可以主理、主气言之。这是接续李滉的说法而来,李滉曾主张四端与道心是“理之发”,七情与人心为“气之发”。但是,成浑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中的“气随之”和“理乘之”说法却表示疑义。而且,在四七关系上也表现出对“七包四”逻辑(在未发意义上)的认可倾向。
简言之,成浑则主要是站在李滉的立场,对李珥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依他之见,理与气之互发是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并向李珥提出质疑道:自己也曾对退翁的“理气互发”说存疑,但细心玩味朱子关于“人心道心之异,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之说,觉得退溪的互发说亦未尝不可。他说:“顷日读朱子人心道心之说,有或生,或原之论,似与退溪之意合,故慨然以为在虞舜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理气互发之说,则退翁之见不易论也。”①所谓“或生”与“或原”,指朱熹所说的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言。道心原于性命之正,纯善无恶;人心生于形气之私,故有善有恶。可见,成氏明显倾向于肯定“理气互发”说。
在与李珥的论辩中,成浑也试图以“理气互发”和人心、道心相互对待逻辑为基础,来阐释四端与七情、人心与道心的善恶问题,这是其性理学的特点。成浑的主要著作有《朱门旨诀》、《为学之方》、《牛溪集》(12卷)等。
下面一段文字是成浑对李珥的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的质疑,曰:
吾兄(指李珥——引者注)前后勤喻,只曰:性情之间,有气发理乘一途而已,此外非有他事也。浑承是语,岂不欲受用,以为简便易晓之学?而参以圣贤前言,皆立两边说,无有如高诲者,故不敢从也。昨赐长书中有曰:“出门之时,或有马从人意而出者,或有人信马足而出者。马从人意而出者,属之人,乃道心也;人信马足而出者,属之马,乃人心也。”又曰:“圣人不能无人心,譬如马虽极驯,岂无或有人信马足而出门之时乎?”浑究此数段,皆下两边说,颇讶其与“只有一边,气发理乘”之语稍异,而渐近于古说也。又读今书,有曰:“发道心者,气也,而非性命,则道心不发。原人心者,性也,而非形气,则人心不发。以道心原于性命,以人心生于形气,岂不顺乎?”浑见此一段,与之意合,而叹其下语之精当也。虽然,于此亦有究极之未竟者焉。吾兄必曰:气发理乘,无他途也;浑则必曰:其未发也,虽无理、气各用之苗脉;才发之际,意欲之动,当有主理、主气之可言也,非各出也,就一途而取其重而言也。此即退溪互发之意也,即吾兄“马随人意,人信马足”之说也,即“非性命则道心不发,非形气则人心不发”之言也。未知以为如何?如何?此处极可分辨,毫分缕析,以极其归趣而示之,千万至祝!于此终不合,则终不合矣。虽然,退溪互发之说,知道者见之,犹忧其错会;不知者读之,则其误人不少矣。况四七、理气之分位,两发、随乘之分段,言意不顺,名理未稳,此浑之所以不喜者也……情之发处,有主理、主气两个意思,分明是如此,则“马随人意,人信马足”之说也,非未发之前有两个意思也。于才发之际,有原于理、生于气者耳,非理发而气随其后,气发而理乘其第二也,乃理气一发,而人就其重处言之,谓之主理、主气也。①
文中成浑认为,衡之于圣贤前言,皆为立两边说,未曾有如李珥的一途论之说,并以人乘马之喻为其论说。这里他所指的圣贤应为,朱熹、陈淳等人。成浑的学说受朱、陈二人之影响也较大②,而且朱熹和陈淳的思想亦是其立论根据之一。具体而言,成浑的主张是心未发之时不能将四端与七情分别对待之,此时二者应为“混沦一体”之状态(可视为“七包四”)。已发之时才可以分别四端与七情,即发于理的为四端、道心;发于气的为七情、人心。这里亦可以看到他与李珥的细微差异,成浑不同意未发之时的“所从来”意义上的四七分别。依他之见,主理、主气是“才发之际”,即意欲动之时取其重而言之者。因此在这意义上,未发之时成浑对四七结构所持的立场又有与奇大升、李珥的“七包四”逻辑有相似的一面,表现出他的学说的折中性格。因此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他也提出折中李滉与奇大升等人主张的“理气一发”说。
针对成浑的质疑,李珥也以朱学理论为据,阐述了自己的“四七人心道心”论。他说:“‘气发理乘一途’之说,与‘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皆可通贯。吾兄尚于此处未透,故犹于退溪‘理气互发、内出外感、先有两个意思’之说,未能尽舍,而反欲援退溪此说,附于珥说耳。别幅议论颇详,犹恐兄未能涣然释然也。盖‘气发理乘一途’之说,推本之论也;‘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沿流之论也。今兄曰‘其未发也,无理、气各用之苗脉’,此则合于鄙见矣。但谓‘性情之间,元有理、气两物,各自出来’,则此非但言语之失,实是所见差误也。”①李珥此处论述极为明快,他认为所谓“气发理乘一途”之说、“或原或生”与“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皆可以通贯。成浑对此有疑问,主要是对理气问题有所未透。于是李珥从理气论与性情说之间的相一致性出发,对“四七人心道心”论作了阐明。曰:“理气之说与人心道心之说,皆是一贯。若人心道心未透,则是与理气未透也。理气之不相离者若已灼见,则人心道心之无二原,可以推此而知之耳。”②由此可以看出,李珥的理气论(“理气之妙”说)是其心性论的立论根基,人道说是其理气论的直接生发。因理气之“不离”义是其理气论的主要理论倾向,因此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他也以二者的不可分和相联结为其主旨,强调人心道心的“无二原”性。这与李滉、成浑的基于二者不同价值意义上的人心道心相分思想是有明显区别的。
进而李珥阐发了自己的四七人道说。首先,从“主乎理”、“主乎气”的向度,对人心道心的含义作了论述。曰:“夫人也,禀天地之帅以为性,分天地之塞以为形,故吾心之用即天地之化也。天地之化无二本,故吾心之发无二原矣。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感动之际,欲居仁、欲由义,欲复礼,欲穷理,欲忠信,欲孝于其亲……欲切偲于朋友,则如此之类谓之道心。感动者因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形气不为之掩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饥欲食、寒欲衣,渴欲饮……四肢之欲安佚,则如此之类谓人心。其虽本于天性,而其发由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气,而目之以人心也。道心之发,如火始燃,如泉始达,造次难见,故曰‘微’。人心之发,如鹰解鞲,如马脱羁,飞腾难制,故曰‘危’。”①依李珥之见,因外感者(感动者)是形气,故感动之际被何方为所主宰,显得十分紧要。“主乎理”的道心,是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又不为形气所掩蔽者;而“主乎气”的人心,则是出于耳目四肢之私,未直出于理之本然者。以“主乎理”、“主乎气”视角,探讨人心道心之含义,这一点颇能反映韩国儒学在讨论人间和存在的所以然根据这个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时,往往落实到性理层面上展开理气这个形上、形下问题的理论特性。②重视人间性理,是韩国儒学的根本特征。
其次,李珥从“心是气”的意义上,以知觉论的立场回答了“一心”何以有“二名”,即有人心道心之分的问题。
在李珥哲学中“心”属于气、属于已发,曰:“且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则心是气也,或原或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耶?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未有心发而性不发之理,则岂非理乘乎?‘或原’者,以其理之所重而言也;‘或生’者,以其气之所重而言也,非当初有理、气二苗脉也。”③故不管人心还是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规定使其人心道心说具有了知觉论特色。对“一心”何以有“二名”,他有以下几段论述。他说:
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①
心一也,岂有二乎?特以所主而发者有二名。②
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一心。其发也或以理义或为食色,故随
其所发而异其名。③“心”只有一个,这与朱子的主张相同。但是在“一心”何以有“二名”的问题上,李珥所持的诠释立场与朱子不同。这源于李珥独特的性情论义理架构。众所周知,朱子的性理学说以“理气二分”、“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而李珥则以“理气之妙”,心、性、情、意四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因此朱子的性情论可以“心统性情”说来概称,而李珥的性情论则似以“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说来指代更为恰当。此处,紧要处为二人对“意”概念的不同界定。在朱子性情论中,“意”和“情”都是从属于“心”的概念。“情”和“意”二者关系是,大抵“情”是性之动,“意”是心之所发;“情”是全体上论,“意”是就起一念处论。④因此在朱子心性论中,“意”的思量运用之意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在李珥哲学中,“意”和“情”是两个有明确规定的并列关系的哲学范畴,李珥曰:“意者,心有计较之谓也。情既发而商量运用者也……发出底是情,商量底是意。”⑤“情动后缘情计较者为意。”⑥“情”和“意”皆属于心之已发,而且还是心的两个不同境界。曰:“因所感而紬绎商量意境界”⑦,李珥提出其独特的“意境界”论。
故其人心、道心论是兼情、意而言,如其曰:“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不但指情也。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⑧需注意的是,“意”其实是在其人心道心说中起十分重要作用的范畴。这既是李珥与朱子性情论之区别,亦是其对朱子心、性、情、意说的发展。相较而言,李珥的心性学说确实比朱子的理论更为细密和清晰。而且,强调“意”的商量计较作用是李珥知觉论最为显著的特点。
基于“意之商量计较”意涵,李珥提出了极具特色的“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终始”说。他说: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①不管根于性命之正的道心,还是源于形气的人心,皆属已发,此时气已用事。若欲不咈乎正理如实呈现,或知非制伏不从其欲,都要借“意”之计较、思虑、商量作用来实现。因此李珥认为,在人心之方寸之间,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可变状态。在已发层面上,二者是并无固定的、严格的分别。因此,李珥为学极重“诚意”,他以为“情胜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时,“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②。指出,若能保证“意”之“诚”,则所发之“心”皆能呈现为道心。
再次,李珥还援引“四七”论、“理欲”论上的说法,进一步论述了其对人心道心问题及二者关系问题的认识。
前已论及,“四端七情”论是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的重要学说,人心道心论争的发生其实就是“四七”论由“情”论层面向“心”论层面的进一步推进,即“四七”论在心性领域的更深、更广意义上的展开。
因为在李珥性理哲学中,“意”具有商量计较作用,故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相互转换之状态。这与其“四七”论中,七情兼四端的情形有所不同,对此差异李珥指出:“圣贤之说,或横或竖,各有所指,欲以竖准横,以横合竖,则或失其旨矣。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①可见,李珥对四端与七情的基本认识是,“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故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基于其“七包四”一元思维,他又对“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李珥谓:
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者,何谓也?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闲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不但指情也。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也,乌可强就而相准耶?今欲两边说下,则当遵人心、道心之说;欲说善一边,则当遵四端之说:欲兼善恶说,则当遵七情之说,不必将柄就凿,纷纷立论也。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也;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故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则兼四端。朱子所谓“发于理”、“发于气”者,只是大纲说,岂料后人之分开太甚乎!学者活看可也。且退溪先生既以善归之四端,而又曰“七者之情,亦无有不善”,若然,则四端之外,亦有善情也,此情从何而发哉?孟子举其大概,故只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而其他善情之为四端,则学者当反三而知之。人情安有不本于仁义礼智而为善者乎?此一段当深究精思。善情既有四端,而又于四端之外有善情,则是人心有二本也,其可乎?大抵未发则性也,已发则情也,发而计较商量则意也。心为性、情、意之主,故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知其气之用事,精察而趋乎正理,则人心听命于道心也;不能精察而惟其所向,则情盛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矣。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情虽万般,夫孰非发于理乎?惟其气或掩而用事,或不掩而听命于理,故有善恶之异。以此体认,庶几见之矣。别纸之说,大概得之。但所谓“四、七发于性,人心、道心发于心”者,似有心、性二歧之病。性则心中之理也,心则盛贮性之器也,安有发于性、发于心之别乎?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①
本段引文较长,但是此段内容则是李珥对四七人心道心问题的最为系统之论述。如其文中言的“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也”中可以看出,在李珥哲学中“情”不具商量计较之义,故性发为情之际,七情可以兼四端。因为依他之见,“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但是,人心、道心则已达比较、商量之地步,已具对比之意,故不能兼有,只能互为终始,这便是其“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
因为人心与道心是基于“意”之商量计较而存在的相对之物,李珥又由“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而提出“人心道心相对”说。他说:“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若七情则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谓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乌可分两边乎?”②
此论看似与其“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矛盾,但是这是李珥从天理人欲论角度对人道说的解读,可视为对人道终始说的另一种阐发。他说:“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③可见,李珥对道心、人心、人欲是有区分,而且也肯定人心亦有善。在此李珥所持的是朱子的立场。但是,人心之善与道心是否为同质之善呢?
对此,李珥在《人心道心图说》中写道:“孟子就七情中别出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论者或以四端为道心,七情为人心,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七情岂可谓之人心乎?七情之外无他情,若偏指人心则是举其半而遗其半矣。”①可见,他是把二者视为同质之善。在“理欲”论意义上,其人道说比朱子的人道说显得更为紧张和严峻,颇似“天理人欲相对”说。这也是二人人心道心之说的主要区别之一。同时,李珥还从理欲之辨角度,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论辩的结束阶段,李珥写了首五言律诗(《理气咏》)致成浑,以阐明其理气哲学主旨。诗云:
元气何端始,无形在有形。
穷源知本合,沿派见群精。
水逐方圆器,空随大小瓶。
二歧君莫惑,默验性为情。②这首理语诗中李珥又夹注,曰:“理、气本合也,非有始合之时。欲以理、气二之者,皆非知道者也……理、气原一,而分为二五之精……理之乘气流行,参差不齐者如此。空瓶之说,出于释氏,而其譬喻亲切,故用之。”③十分形象地从本体和流行的视角,再一次强调了其“理气之妙”和“气发理乘”思想。
成浑与李珥年龄相仿,李珥19岁时二人便定交。《年谱》记云:“成先生长于先生(指李珥——引者注)一岁,而初欲师事之,先生辞焉。遂定道义之交,相期以圣贤事业终始无替。”④李珥卒后,成浑曾评其道:“栗谷尽是五百年间气也。余少时讲论,自以为朋友相抗。到老思之,则真我师也,启我者甚多。”⑤李珥37岁(成浑时年38岁)时二人围绕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及理气之发问题展开了长达6年的辩论,尽管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但是成浑对李珥的崇敬之情从其评语中以见一斑。
在朝鲜朝儒学史上由李珥和成浑之间进行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是,继“四端七情”之辨之后发生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又一学术论争。
三、李珥“四七人心道心”论的特色
李珥的“四七人道”说特色主要表现在,其“四七理气”说和心性情意论方面。
李珥的“四七理气”论是在与成浑的相互论辩和与李滉的相互问学中形成。李滉在“四七理气”论方面的基本说法是,“四七理气互发”说。成浑大抵接受李滉此一立场。
李滉曾曰:“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①此论便是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此一理论的性情论基础是,“二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二情”(四端/七情)论。由此自然可以推导出,对举分别而言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论,即主理、主气之说。
李珥反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基于其理气“一而二、二而一”思路以为,子思、孟子所言的本然之性和程子、张子所言的气质之性,其实皆为“一性”,只是所主而言者不同而已。曰:
性者,理、气之合也。盖理在气中,然后为性。若不在形质之中,则当谓之理,不当谓之性也。但就形质中单指其理而言之,则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不可杂以气也。子思、孟子言其本然之性,程子、张子言其气质之性,其实一性,而所主而言者不同。今不知其所主之意,遂以为二性,则可谓知理乎?性既一,而乃以为情有理发、气发之殊,则可谓知性乎?①可见,李珥不仅主张性为理气之合,而且还明确区分“性”与“理”概念的不同用法。这既是李珥逻辑思维细密、精微之处,也是其“四七”论的独到之处。进而他指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其实是“一性”。这里还可以看出,他的“性”论又与奇大升的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依他之见,若不知其所主之意而视其为“二性”,可谓之味于“理”者。而在“性既一”之情形下,仍主情有理发、气发之殊的话,则又可谓之味于“性”者。
李珥也认为,理为形而上者也,气为形而下者也。不过,他特别强调二者的不能相离性。因此在他而观,二者既不能相离,则其发用也只能是“一”,不可谓互有发用。曰:
若曰互有发用,则是理发用时,气或有所不及;气发用时,理或有所不及也。如是,则理气有离合,有先后,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其错不小矣。但理无为,而气有为,故以情之出乎本然之性,而不掩于形气者,属之理;当初虽出于本然,而形气掩之者,属之气,此亦不得已之论也。人性之本善者,理也,而非气则理不发。人心、道心,夫孰非原于理乎?非未发之时,亦有人心苗脉,与理相对于方寸中也。源一而流二,朱子岂不知之乎?特立言晓人,各有所主耳。程子曰:“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夫善、恶判然二物,而尚无相对各自出来之理,况理、气之混沦不离者,乃有相对互发之理乎?若朱子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何以为朱子乎?②
在李珥看来,承认“理气互发”说不仅等于承认理气有缝隙、有离合,而且还承认理气有先后、动静有终始。朱熹的“理气不杂”、“理气为二”思想,明初便遭到曹端、薛瑄、胡居仁等人的批评,他们依据程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理论,主张理在气中,坚持理气无间一体思想,反对把二者对立、割裂。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说,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理论。罗氏的《困知记》对朝鲜朝性理学及李珥“理气之妙”说的影响前文已多次论及,李珥也受此理论思潮之影响力主“理气非二”论。故他以为,四端与七情之说是朱子“特立言晓人,各有所主”而已。这与奇大升的所言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①的思想并无二致。依李珥之见,若是朱子也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
于是,他进而指出:
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而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化而理乘之也。是故,阴阳动静,而太极乘之,此则非有先后之可言也。②
在此李珥对朱子的“四七”论作了己之阐发的同时,指出李滉的错误在于只认同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他坚持,不仅四端是“气发而理乘”,七情亦是“气发而理乘”。对于李珥和李滉的“气发而理乘之”的说法,陈来先生认为,二者并不相同。他指出:李滉所说的气发是发自于形气,而李珥所说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李珥进一步说的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这是气,就是气发,而理乘载其上。由于李珥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故把恻隐说成气,说成气发,这种说法与王阳明接近,容易引出“心即气”的主张,是与朱子和李滉不同的。李珥认为,气和理的这种动载关系是普遍的,不限于四端七情,整个天地之化都是如此。③陈先生的这一论述,对于二人的理气之发说的理解及理气论差异问题的探讨颇有裨益。
要之,“性”与“理”概念的区分,“一性”、“一情”论的强调以及“七包四”立场的坚守,是李珥“四七理气”论的主要特色。
那么,李珥和李滉的“气发而理乘”思想为什么会有理论差异呢?这源于李珥独特的心性情意论。
在李珥的心性情意论逻辑结构中,“心”处于十分重要之地位,他认为,就人之一身来说心“合性与气”,而有“主宰”于身之作用。他说:
天理之赋于人者,谓之性,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谓之心。心应事物而发于外者,谓之情。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未发已发之总名……性之目有五,曰仁义礼智信;情之目有七,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之发也,有为道义而发者。如欲孝其亲,欲忠其君,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非议而羞恶,过宗庙而恭敬之类是也,此则谓之道心。有为口体而发者,如饥欲食、寒欲衣、劳欲休、精盛思室之类是也,此则谓之人心。①
文中李珥对“性”、“情”、“心”、“道心”、“人心”等作了明确之界定。此说与朱子的“心为主宰”的思想和李滉的“心兼理气”、“理气合而为心”②说法皆也有所不同。因为在李滉的性理哲学体系中理具发用性和能动性,故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而在心、身的关系上,李珥也强调心的优位性,比朱子更加明确指出心对身的主宰作用,言道:“心为身主,身为心器,主正则器当正。”③而且,在李珥性理哲学中心属于气,属于已发,故“心”在其性情论中是被探讨的主要对象。
对于“心”、“性”、“情”概念及相互关系,李滉则界定为:
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④
表明,李滉的心论结构大体延续的是朱熹的“心统性情”思路。但是,有别于朱熹的是,他的这一思想突出了理对于心之“灵”的作用,着重于解决心的知觉作用问题。
基于心之作用的独特认识,李珥又提出“心为性、情、意之主”的思想。他言道:
大抵未发则性也,已发则情也,发而计较商量则意也。心为性、情、意之主,故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知其气之用事,精察而趋乎正理,则人心听命于道心也;不能精察而惟其所向,则情盛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矣。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情虽万般,夫孰非发于理乎?惟其气或掩而用事,或不掩而听命于理,故有善恶之异。以此体认,庶几见之矣。别纸之说,大概得之。但所谓“四、七发于性,人心、道心发于心”者,似有心、性二歧之病。性则心中之理也,心则盛贮性之器也,安有发于性、发于心之别乎?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①
李珥主张“心为性、情、意之主”,故以为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需注意的是,李珥对“性”概念的界定,曰:“性者,理、气之合也。盖理在气中,然后为性。”②其实,他所言之性为“气质之性”。“心是气”,因此性、情、意皆可谓之心。但是,性和情不具计较商量义,故“意”之作用又显得十分重要。“意”不仅在其“四七人道”说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其修养论亦具有重要意义,故其曰“自修莫先于诚意”。进而,李珥还提出“人心、道心皆发于性”的主张,此说与朱熹和李滉的思想相比区别较大。
李珥心性情论中最为独特的思想为,其“性心情意一路而各有境界”论。他说:
子固历见余谈话,从容语及心性情。余曰,公于此三字,将一一理会否。子固曰,未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云者,殊未晓得。余曰,公于此难晓,则庶几有见于心性情矣。先儒此说,意有所在,非直论心性。而今之学者为此说所误,分心性为有二用,情意为有二歧,余甚苦之。今公自谓于此有疑,则庶几有真知矣。性是心之理也,情是心之动也,情动后缘情计较者为意。若心性分二,则道器可相离也;情意分二,则人心有二本矣。岂不大差乎?须知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然后可谓不差矣。何谓一路?心之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发后商量为意,此一路也。何谓各有境界?心之寂然不动时是性境界,感而遂通时是情境界,因所感而紬绎商量为意境界,只是一心各有境界。①
在心性情论方面,李珥一贯反对“分心性为有二用,情意为有二歧”。因为依他之见,若心性分二,则道器可相离也;情意分二,则人心有二本。由此他提出“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思想。如前所述,李珥的性情论为心性情意四分逻辑结构,故性境界、情境界、意境界分别代表了“一心”之不同境界,犹如人之行走,一路走下去一路上各有不同的景致呈现一般。
总之,李珥心性情论的主要特色在于对“心”之主宰作用与“意”之计较商量作用的重视以及“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论。而“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论,的确为其在心性情论上的创见。
李珥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天道策》、《人心道心图说》、《圣学辑要》、《答成浩原》等。
自从29岁时任户曹左郎开始,他一生为宦,曾官至吏曹判书,49岁时卒于京城大寺洞寓所。李珥是朝鲜朝五百年间难得的道学家、通儒。政治上,他积极建言献策主张为了朝鲜朝的中兴“因时制宜”与“变法更张”,强调“事要务实”。在社会教育方面,他不仅亲自开展私学教育,而且还制定“海州相约”、“社会契约束”以及著《击蒙要诀》、《学校模范》等为朝鲜朝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故成浑赞其曰:“栗谷于道体,洞见大原。所谓天地之化无二本,人心之发无二原,理气不可互发,此等说话,真是吾师。其爱君忧国之忠,经世救民之志,求之古人,鲜有其俦。诚山河闲气,三代人物。”①他的学说被后人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韩国儒学史上颇具影响的畿湖性理学派。
林亭秋已晚,骚客意无穷。
远水连天碧,霜枫向日红。
山吐孤轮月,江含万里风。
塞鸿何处去,声断暮云中。②
这首诗不仅诗句对仗工整,而且其格调浑成,虽深谙诗律者亦有所不及。③尤其是诗中的“山吐孤轮月,江含万里风”一句,很难想象出自8岁孩童之笔。李珥从13岁始在进士初试中状元及第至29岁魁生员及文科前后止,应科举试9次,均已状元及第,故又被称为“九度状元公”。
李珥16岁时其母(师任堂申氏)遽尔逝世,与母亲感情极深的他此时深感人生无常,于是三年后(19岁)脱下孝服后入金刚山摩诃衍道场修行佛法。在一次与老僧的问答中他旋觉佛学之非而决心下山,正式弃佛学儒。次年(20岁)往江陵作了“自警文”11条,第一条即谓:“先须大其志以圣人为准则,一毫不及圣人,则吾事末了。”①李珥年少李滉35岁,明宗十三年(23岁)春拜谒李滉于礼安陶山,并滞留两天向其主动请教了主一无适及应接事务之要,消释了平日积累之疑点,并给李滉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两位大儒的首次晤面,之后李滉在答门人月川赵穆的信中,曾大加赞赏李珥谓:“汉中李生珥自星山来访,关雨留三日乃去。其人明爽,多记览,颇有意于吾学,后生可畏,前圣真不我欺也。”②李珥的《行状》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写道:“二十三岁谒退溪先生于陶山,问主一无适、应接事物之要,厥后往来书札,辩论居敬穷理及庸学辑注,圣学十图等说。退溪多舍旧见而从之,尝致书曰:世间英才何限而不肯存心于古学,如君高才妙年,发轫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千万益以远大自期。”③可见,尽管这是二人初次晤对,但是对彼此的思想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他们通过书信还有过多次相互问学,由此共同开创出韩国性理学自主的理论探索与创新的全盛时代。
在韩国哲学史上,李珥与李滉并称为韩国性理学的双璧。畿湖地区的学者(指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一带的学者)大都从栗谷李珥之说,称栗谷为“东方之圣人”;岭南地区的学者(庆尚道一带的学者)则大都从退溪李滉之说,称退溪为“东方之朱夫子”。于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性理学派——栗谷学派和退溪学派,两个学派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不同的发展方向。
一、李珥的“理气之妙”论——与罗钦顺“理气一物”论之比较为中心
以东亚儒学史的视角而观,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6世纪中后叶中韩儒学史上涌现出一批具有重要理论建树和思想影响的鸿儒硕学。如这一时期的明代大儒有罗钦顺(1465—1547年)、湛若水(1466—1560年)、王守仁(1472—1528年)、王廷相(1474—1544年)等;朝鲜朝的名儒则有赵光祖(1482—1519年)、徐敬德(1489—1546年)、李彦迪(1491—1553年)、曹植(1501—1572年)、李滉(1501—1570年)、郑之云(1509—1561年)、奇大升(1527—1572年)、李珥(1536—1584年)、成浑(1535—1598年)等,皆为称誉于海内外的“杰然之儒”。可见,在东亚儒学史上这是一个名儒辈出、学说纷呈的学术至为兴盛时期。
其中,江右大儒罗钦顺则被称为“朱学后劲”、“宋学中坚”。他的学说中所呈现的新的理论动向不仅影响了其时的明代理学的演进,而且还传至域外影响了韩国性理学和日本朱子学的发展。下面将通过罗钦顺与李珥理气说的比较,来探讨李珥理气论的特色。
李珥之学,正如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1607—1689年)所言“不由师传,默契道体似濂溪”①。尽管李珥学无定师,但是其立学极重视统合诸流,汇纳各家。故宋时烈又赞其谓:“遂取诸家之说,分析其同异,论正其得失,务得至当之归……其有乐浑全而恶分析,则先生(指李珥——引者注)必辩其同异于毫厘之间,其有逐末流而昧本源,则先生必一其宗元于统会之极。”②
虽然李珥生活的年代是在“破邪显正”的幌子下,对除朱子学以外的其他学派均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的时代,但他并不盲从朱子,而是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和自主精神。针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之说,李珥曾言道:“若朱子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何以为朱子乎?”③这种为学上的自主和批判精神,使其能够对历史上的和同时代的各家学说加以吸收和借鉴,构筑以理气“不离”之义为特色的独特性理哲学体系。
在与其同时代的中韩诸儒中,李珥唯独对罗钦顺非常赞赏,曰:“罗整庵识见高明,近代杰然之儒也。有见于大本,而反疑朱子有二歧之见。此则虽不识朱子,而却于大本上有见矣。”④表明李珥认为罗钦顺对朱学之大本,即对朱学的要领是有真切之体会。于是,将整庵罗钦顺与退溪李滉、花潭徐敬德做比较时,亦将其推为最高。曰:“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①李滉和徐敬德是与李珥同朝的另外两位大儒,在韩国哲学史上均具有重要影响。而李珥最为称赞罗钦顺的原因在于,较之李滉和徐敬德,罗钦顺不仅有见于朱学之大本,且多有自得之味。
同时,他还将罗钦顺学说同薛瑄(1389—1465年)、王守仁(1472—1529年)之学亦做过比较,曰:“罗钦顺拔萃人物,自所见少差;薛瑄虽无自见处,自可谓贤者也;王守仁则以谓朱子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之祸,其学可知。”②此处李珥对薛瑄的评价同罗钦顺对薛氏的评价内容亦大体相似,罗钦顺在《困知记》中曾写道:“薛文清学识纯正,践履笃实,出处进退,惟义之安。其言虽间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见有能及之者,可谓君子儒矣。”③由此可见,《困知记》一书对李珥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困知记》何时传入韩国,学界尚无定论。④但是该书传入韩国后,在16世纪朝鲜朝儒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不少学者撰文对之加以评说。⑤其中代表性论者有:卢守慎(字寡悔,号苏斋,1512—1590年)、李滉、奇大升、李珥等人。
不过,与罗钦顺相比李珥为学则更具开放性。比如对其时盛行于明代思想界的阳明心学李珥也并未一概排斥,而主张应“取其功而略其过”,认为这才是“忠厚之道”。⑥这显然与罗钦顺对待心学之立场差异较大。
前已言及,李珥的性理学是在对各家理论的批判、撷取中形成。其中,直接影响其理气学说形成的有三家理论——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论、李滉的“理气二元”论、徐敬德的“气一元”论。李珥曾对此三家学说做过详细的评论,曰:
整庵则望见全体,而微有未尽莹者,且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而气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以理气为一物也。所见未尽莹,故言或过差耳。退溪则深信朱子,深求其意。而气质精详慎密,用功亦深。其于朱子之意,不可谓不契,其于全体,不可谓无见,而若豁然贯通处,则犹有所未至,故见有未莹,言或微差。理气互发,理发气随之说,反为知见之累耳。花潭则聪明过人,而厚重不足。其读书穷理,不拘文字而多用意思。聪明过人,故见之不难;厚重不足,故得少为足。其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了然目见,非他人读书依样之比,故便为至乐。以为湛一清虚之气无物不在,自以为得千圣不尽传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气局一节。继善成性之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者也。理无变而气有变,元气生生不息,往者过来者续。而已往之气,已无所在。而花潭则以为一气长存,往者不过,来者不续,此花潭所以有认气为理之病也。虽然偏全闲,花潭是自得之见也。今之学者开口便说理无形而气有形,理气决非一物。此非自言也,传人之言也。何足以敌花潭之口而服花潭之心哉。惟退溪攻破之说,深中其病,可以救后学之误见也。盖退溪多依样之味,故其言拘而谨;花潭多自得之味,故其言乐而放。谨故少失,放故多失。①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尽管李珥为学极重“自得之味”,但是在为学性格上他仍坚守朱学的立场。故他强调,“宁为退溪之依样,不必效花潭之自得”②。二是,他认为罗钦顺气质英迈超卓故能望见朱学之全体,但是又因不能深信朱子的见其意。故其言论确有“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李珥以为理气实际上“非为一物”,而是“一而二、二而一”妙合关系。三是,李滉能深信朱子,气质亦精详慎密,故对于朱子之意,不可谓不契。但是因于豁然贯通处有所未至,故其所见亦有未尽莹者。这里主要是指,他与李滉在理气之发问题上的分歧。在此一涉及朝鲜朝性理学的核心论题的见解上,李珥反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而是主张颇有“主气”意味的“气发理乘一途说”。四是,李珥尽管对徐敬德“理不先于气”思想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于理气不相离之妙有了然目见”,但是同时指出徐敬德之说有“认气为理之病”。李珥以为,继善成性之“理”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故主张“一气长存”之上则更有“理通气局”一节。
由此亦可概见李珥在理气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即“一而二、二而一”的“理气之妙”说、“气发理乘一途”说以及“理通气局”说等。其实李珥正是用这些学说来试图解答,朱学的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基本理论问题。其中,“理气之妙”思想既是李珥性理学的根本立场,亦是理解其性理哲学的理论要害。
要之,从李珥对罗钦顺的肯定以及对其学说的重视中可以看出,罗钦顺理气说是影响李珥理气思想形成的主要理论之一。
朱子学演进至罗钦顺,较之原来的理论发生了明显改变。首先是在理气观方面与朱熹的学说产生了较大差异。从理学史角度来看,明中叶的朱学呈现出从“理本”向“气本”发展的趋向。无疑,罗钦顺是在这一理学发展转向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
理学从二程开始,在哲学的宇宙论上,把“理”作为宇宙的普遍原理,同时又认为这个“理”是气的存在、运动的“所以然”。朱熹继承并发展这一思想,建构了以理气二分、理气“不离不杂”①为特色的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朱熹以为,“理”是不杂而又不离于气的形上实体,强调“理”作为气之所以然而具有的实体性和主宰性。这一思想在朱子后学中受到不少怀疑,罗钦顺便是对此提出异议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罗钦顺对朱熹理气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理气二分思想上。他在《困知记》一书中,写道: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所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①
周子《太极图说》篇首无极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释,可无疑矣。至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语,愚则不能无疑。凡物必两而后可以言合,太极与阴阳果二物乎?其为物也果二,则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终身认理气为二物,其源盖出于此。愚也积数十年潜玩之功,至今未敢以为然也。尝考朱子之言有云“气强理弱”,“理管摄他不得”。若然,则所谓太极者,又安能为造化之枢纽,品物之根柢邪?惜乎,当时未有以此说叩之者。姑记于此,以俟后世之朱子云。②
此处所引两段引文是在其《困知记》中质疑朱熹理气二分说的主要段落。同时,从此段引文中亦可概见罗钦顺在理气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首先在对于“气”的理解上,罗钦顺明确指出“气”才是宇宙的根本存在,故主张“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虽然朱熹亦认为“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的物质形态,但是罗钦顺的主张已明显呈现出由“理本”转向“气本”的趋向。其次在对于“理”的理解上,罗钦顺则明确反对“理”在朱熹学说中具有的“实体性”、“主宰性”。依罗钦顺之见,“理”即是所谓“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亦即事物自身中的“自然之机”和“不宰之宰”。
由此罗钦顺提出“理即气之理”的主张,他说:“吾夫子赞《易》,千言万语只是发明此理,始终未尝及气字,非遗之也,理即气之理也。”①
进而在理气为“一物”还是“二物”的问题上,他则断言“仆从来认理气为一物”②。以为,理是气之运动的内在根据和法则,并不像朱熹所说的是依附于气的另一实体(物)。尽管坚守“认理气为一物”的立场,但是他同时又明确表示学者亦不能将“气”认为“理”。他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③表明,罗钦顺是反对将理气视为二元对待的两个实体,实体只是气,而“理”只是这一实体的自身的规定。即,这一实体固有的属性或条理。
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以及“理须就气上认取”思想既是罗钦顺理气论的核心要义,亦是其理气说“最为难言”的地方。对此,他也曾坦言道:“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间不容发,最为难言,要在人善观而默识之。‘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有分别,若于此看不透,多说亦无用也。”④
罗钦顺自谓其理气不二之说并非为“臆决”,而是由宗述明道而来。他说:“仆虽不敏,然从事于程朱之学也,盖亦有年,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非臆决也。明道尝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又曰:‘阴阳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窃详其意,盖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说个形而上下,则此理无自而明,非溺于空虚,即胶于形器,故曰‘须著如此说’。名虽有道器之别,然实非二物,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至于‘原来只此是道’一语,则理气浑然,更无隙缝,虽欲二之,自不容于二之,正欲学者就形而下者之中,悟形而上者之妙,二之则不是也……晦翁先生……谓‘是理不离气,亦不杂乎气’,乃其说之最精者。但质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良由将理气作二物看,是以或分或合,而终不能定于一也。”①可见,罗钦顺对程明道学说是极为推崇。尤其是,程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和“原来只此是道”思想是罗钦顺理气浑然一体说的立论根据。若以此来衡量伊川、朱子理气说,皆有析理气为二物之嫌。此外,二程的“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②和“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③等思想,亦是罗钦顺构筑其理气说的主要理论来源。
李珥对明道的思想亦极为重视,这一点与罗钦顺相似。而且,在李珥和罗钦顺著述中所引用的二程言论大都为明道之说。宣祖五年(李珥37岁),李珥与好友成浑(字浩原,号牛溪,1535—1598年)进行理气心性问题的论辩时,曾系统阐述自己的理气观。论辩中,他还对成浑言道:“兄若不信珥言,则更以近思录、定性书及生之谓性一段,反复详玩,则庶乎有以见之矣。”④表明《近思录》及明道的《定性书》、《生之谓性章》等是李珥性理学的重要的理论来源。尤其是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的思想亦是李珥理气说的立论根据。他说:“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此言理气之不能相离。”⑤李珥的理气观,正是以理气之不相离为其理论前提。
前已述及,李珥对罗钦顺十分赞赏,称其为“拔萃人物,自所见少差”。首先,在强调理气之不相离的意义上,李珥与罗钦顺持相同的立场。他说:“夫理之源一而已矣,气之源亦一而已矣。气流行而参差不齐,理亦流行而参差不齐。气不离理,理不离气,夫如是则理气一也。何处见其有异耶?所谓理自理,气自气,何处见其理自理,气自气耶?望吾兄精思著一转,欲验识见之所至也。”①这是李珥答成浑信中的一段话。李珥发挥明道之理气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告诫成浑理气不相离之妙须通过精思与证会方能真正体会。其次,在强调理气之不相杂的意义上,李珥与罗钦顺则明显有差异。在李珥的理气说中,理作为气之根柢及造化之根源在理气关系中被赋予主宰义,具有重要地位。如,李珥曰:“夫理者气之主宰也,气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则气无所根柢,非气则理无所依著”②,“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③。可见,在理的规定上李珥与罗钦顺是有区别的。其实,这便是李珥称罗钦顺为“望见全体,而微有未尽莹者”及“气质英迈超卓,故言或有过当者,微涉于理气一物之病,而实非理气为一物也”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李珥性理学说与朱学的传承关系。较之罗钦顺,李珥在强调理气之不相离的同时,亦强调二者之不相杂。他认为理气关系是“既非二物,又非一物”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妙合关系。他说:“一理浑成,二气流行,天地之大,事物之变,莫非理气之妙用也。”④这就是李珥的“理气之妙”思想,也是其整个性理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
那么,何谓“既非二物,又非一物”呢?李珥对此解释道:“非一物者,何谓也?理气虽相离不得,而妙合之中,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杂,故非一物也。非二物者,何谓也?虽曰理自理,气自气,而浑沦无间,无先后,无离合,不见其为二物,故非二物也。”⑤理气一方面妙合之中互不相杂,理自理,气自气,故非为“一物”;另一方面二者又浑然无间,无先后,无离合,故亦非为“二物”。前者所强调的是理气二者各自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后者所强调的是在现实的意义上二者所具有的共时性、共存性。
接着李珥总结明道与朱子的理气关系论述,指出:
考诸前训,则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气浑然无间,元不相离,不可指为二物。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虽不相离而浑然之中实不相杂,不可指为一物。故朱子曰: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挟杂。合二说而玩索,则理气之妙,庶乎见之矣。①
以上引文中,亦可概见李珥为学上的特点。即,注重对各家学说的融会贯通。因理与气是相互渗透、相互蕴涵的关系,故不可指为“二物”;但二者是妙合之中,又各自有其不同的内涵和特性,故又不可指为“一物”。此种“非二物”故“二而一”、“非一物”故“一而二”的思维模式,正好反映了李珥独特的哲学思维方法。
李珥性理学中的最为紧要处,便是其“理气之妙”说。对此,他亦曾言道:“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②尽管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李珥却对此说颇为自信。他在给成浑的一封复信中,写道:“珥则十年前已窥此端,而厥后渐渐思绎,每读经传,辄取以相准,当初中有不合之时,厥后渐合,以至今日,则融会吻合,决然无疑。千百雄辩之口,终不可以回鄙见。”③表明,通过其多年努力而体贴到的理气之妙合关系,李珥已完全确信无疑。
于是,李珥从其“理气之妙”思想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理气动静说。他指出:“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发之以下二十三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④此即李珥所谓的“气发理乘”说。他对此二十三字所言之内容,极为肯定。简言之,所谓“气发理乘”是指,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气化流行)时理乘之而无所不在的存有形态。李珥此说,既是对李滉“理气互发”说的批判,亦是对朱子理气说的进一步继承与阐发。
理发气发问题是朝鲜朝前期性理学的中心论题之一,此论与“四端七情”之辨相关联,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的理论特色。
李珥在与成浑(成浑基本上持李滉的立场)的四端七情论辩中,还系统阐发了其“气发理乘”思想。曰:
气发而理乘者,何谓也?阴静阳动,机自尔也,非有使之者也。阳之动则理乘于动,非理动也;阴之静则理乘于静,非理静也。故朱子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阴静阳动,其机自尔,而其所以阴静阳动者,理也。故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夫所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者,原其本然而言也;动静所乘之机者,见其已然而言也。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则理气之流行皆已然而已,安有未然之时乎?是故天地之化、吾心之发,无非气发理乘之也。所谓气发理乘者,非气先于理也,气有为而理无为,则其言不得不尔也。①
李珥的“气发理乘”说是以理气“元不相离”为其立论前提,加之在其哲学中“气”具有形、有为之特性而“理”却无之,故“理”不能以动静言。依他之见,理之所以流行,是乘气之流行而流行,理之有“万殊”,亦因气之流行所致。不但天地之化是如此,而且人心之发亦不外乎此。发之者是其然,是表现者;所以发者是所以然,是使表现者得以实现的主宰者。
而且,同成浑的往复论辩中,李珥则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指出:“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之也。”②文中,李珥不仅指责李滉未能正确理会朱子之意,而且还主张不仅七情是气发而理乘,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
进而,他又以“理气之妙”论为基础推出自己在理气同异思想,即“理通气局”说。那么,何谓“理之通”、“气之局”呢?李珥解释曰:
理气元不相离,似是一物,而其所以异者,理无形也,气有形也;理无为也,气有为也。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通而气局。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理通者何谓也?理者,无本末也,无先后也。无本末、无先后,故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是故乘气流行、参差不齐,而其本然之妙无乎不在。气之偏则理亦偏,而所偏非理也,气也。气之全则理亦全,而所全非理也,气也。至于清浊、粹驳、糟粕、煨烬粪壤污秽之中,理无所不在各为其性,而其本然之妙则不害其自若也。此之谓理之通。气局者何谓也?气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后也,气之本则湛一清虚而已曷。尝有糟粕、煨烬粪壤污秽之气哉?惟其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故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于是气之流行也,有不失其本然者,有失其本然者。既失其本然,则气之本然者已无所在,偏者偏气也,非全气也;清者清气也,非浊气也;糟粕煨烬,糟粕煨烬之气也;非湛一清虚之气也。非若理之于万物本然之妙,无乎不在也。此所谓气之局也。①此段引文集中反映了李珥理气说之基本要义。文中可以看出,他从理气关系和理气之特性着手,论述了“理通气局”、“气发理乘”及“理之偏全”等问题,阐明了其在理气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要之,所谓“理通”,是指“理同(同一理)”;“气局”,则指“气异(各一气)”。②对于“理通气局”这一命题,李珥自诩为“理通气局四字,自谓见得,而又恐读书不多,先有此等言,而未见之也”③。此说尽管亦受程朱的“理一分殊”、“理气同异”及佛教华严宗的“理事通局”说的影响,但是仅就以通局范畴表述理气之异而言确为李珥独见。而且,在他的性理哲学逻辑结构中“理通气局”与“气发理乘”说,作为说明人物性同异与性情善恶的重要命题互为对待、互为补充,共同构筑了其“四七人道”说的立论基础。
概言之,通过罗钦顺“理气一物”论与李珥“理气之妙”说的比较,可以看出16世纪中韩朱子学的不同发展面向。罗钦顺从去“理”的实体化、主宰义入手,将“理”视为“气”所固有的属性或条理,反对将理气视为二元对待的两个实体,明显表现出由“理本”向“气本”的转向。而,李珥虽然与罗钦顺同尊明道,但是仍表现出坚守朱学之为学性格,提出理气“非二物”故“二而一”、“非一物”故“一而二”的颇具特色的“理气之妙”说,对明道和朱熹思想作了有益的阐发。李珥和罗钦顺的理气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朱熹的理气学说,而且也为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路径。
二、李珥的“四七人心道心”论——与成浑“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
通过对李滉、奇大升等人的“四七”论的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出,四端七情问题其实讨论的是“性”与“情”关系问题,因此顺四端七情理气问题便可以引出有关性情善恶及人心道心问题的论议。而栗谷李珥和牛溪成浑之间围绕人心道心问题展开的第二次“四七”之论争,便是四七理气问题在更深一层意义上的,即性情层面上的展开。在韩国哲学史上李珥和成浑之间发生的第二次“四七理气”之辨,既丰富了原有的四七理气理论之意涵,又开启了对性情善恶与人心道心关系问题的新的理论探索,将“四七”论引向了新的问题域。下面,将以李珥与成浑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探讨“四七”论进一步发展之状况。
成浑(字浩原,号牛溪,1535—1598年),昌宁人,谥号文简,朝鲜朝著名性理学家。成浑幼承庭训,学业大进,15岁便博通经史文辞,为人们所叹服。其父成守琛曾受学于赵光祖,成浑则尊幕李滉且多从其说。他与李珥交情甚笃,二人围绕“四七问题”进行了长达6年的书函往复,①继“退、高之辩”之后将此一论辩又推向了高潮。
成浑的“四七”论和“人心道心”说的主要理论观点,大都集中在与李珥的往复论辩第一书和第二书。在致李珥的信中,成浑写道:“今看十图《心性情图》,退翁立论,则中间一端曰:‘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云。究此议论,以理、气之发,当初皆无不善,而气之不中,乃流于恶云矣。人心道心之说,既如彼其分理、气之发,而从古圣贤皆宗之,则退翁之论,自不为过耶?”①可见,在四七理气问题上成浑是大抵接受李滉的立场,也认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基于此,成浑以为理发则为道心,而气发则为人心。
进而,他又曰: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二名,何欤?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理、气之发不同,而危、微之用各异,故名不能不二也。然则与所谓“四端、七情”者同耶?今以道心谓之四端,可矣;而以人心谓之七情,则不可矣。且夫四端、七情,以发于性者而言也;人心、道心,以发于心者而言也。其名目意味之间,有些不同焉。幸赐一言,发其直指,何如?人心、道心之发,其所从来,固有主气、主理之不同,在唐虞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说,圣贤宗旨,皆作两下说,则今为四端、七情之图,而曰“发于理”、“发于气”,有何不可乎?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耶?然“气随之”、“理乘之”之说,正自拖引太长,似失于名理也。愚意以为四、七对举而言,则谓之“四发于理,七发于气”,可也。为性情之图,则不当分开,但以四、七俱置情圈中,而曰“四端,指七情中理一边发者而言也:七情不中节,是气之过不及而流于恶”云云,则不混于理、气之发,而亦无分开二歧之患否耶?并乞详究示喻。②
文中成浑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对人心道心问题的具体看法。首先,援引朱子《中庸章句》中的或生、或原说法,主张人心、道心二者是理气之发不同、危微之用各异;其次,在四端七情与人心道心的关系上,以为道心可视为四端,但是人心不可视为七情。而且又从“性发为情”、“心发为意”之向度,称“其名目意味之间,有些不同”;再次,他从二者的“所从来”意义上,主张人心、道心亦可以主理、主气言之。这是接续李滉的说法而来,李滉曾主张四端与道心是“理之发”,七情与人心为“气之发”。但是,成浑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中的“气随之”和“理乘之”说法却表示疑义。而且,在四七关系上也表现出对“七包四”逻辑(在未发意义上)的认可倾向。
简言之,成浑则主要是站在李滉的立场,对李珥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依他之见,理与气之互发是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并向李珥提出质疑道:自己也曾对退翁的“理气互发”说存疑,但细心玩味朱子关于“人心道心之异,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之说,觉得退溪的互发说亦未尝不可。他说:“顷日读朱子人心道心之说,有或生,或原之论,似与退溪之意合,故慨然以为在虞舜无许多议论时,已有此理气互发之说,则退翁之见不易论也。”①所谓“或生”与“或原”,指朱熹所说的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而言。道心原于性命之正,纯善无恶;人心生于形气之私,故有善有恶。可见,成氏明显倾向于肯定“理气互发”说。
在与李珥的论辩中,成浑也试图以“理气互发”和人心、道心相互对待逻辑为基础,来阐释四端与七情、人心与道心的善恶问题,这是其性理学的特点。成浑的主要著作有《朱门旨诀》、《为学之方》、《牛溪集》(12卷)等。
下面一段文字是成浑对李珥的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的质疑,曰:
吾兄(指李珥——引者注)前后勤喻,只曰:性情之间,有气发理乘一途而已,此外非有他事也。浑承是语,岂不欲受用,以为简便易晓之学?而参以圣贤前言,皆立两边说,无有如高诲者,故不敢从也。昨赐长书中有曰:“出门之时,或有马从人意而出者,或有人信马足而出者。马从人意而出者,属之人,乃道心也;人信马足而出者,属之马,乃人心也。”又曰:“圣人不能无人心,譬如马虽极驯,岂无或有人信马足而出门之时乎?”浑究此数段,皆下两边说,颇讶其与“只有一边,气发理乘”之语稍异,而渐近于古说也。又读今书,有曰:“发道心者,气也,而非性命,则道心不发。原人心者,性也,而非形气,则人心不发。以道心原于性命,以人心生于形气,岂不顺乎?”浑见此一段,与之意合,而叹其下语之精当也。虽然,于此亦有究极之未竟者焉。吾兄必曰:气发理乘,无他途也;浑则必曰:其未发也,虽无理、气各用之苗脉;才发之际,意欲之动,当有主理、主气之可言也,非各出也,就一途而取其重而言也。此即退溪互发之意也,即吾兄“马随人意,人信马足”之说也,即“非性命则道心不发,非形气则人心不发”之言也。未知以为如何?如何?此处极可分辨,毫分缕析,以极其归趣而示之,千万至祝!于此终不合,则终不合矣。虽然,退溪互发之说,知道者见之,犹忧其错会;不知者读之,则其误人不少矣。况四七、理气之分位,两发、随乘之分段,言意不顺,名理未稳,此浑之所以不喜者也……情之发处,有主理、主气两个意思,分明是如此,则“马随人意,人信马足”之说也,非未发之前有两个意思也。于才发之际,有原于理、生于气者耳,非理发而气随其后,气发而理乘其第二也,乃理气一发,而人就其重处言之,谓之主理、主气也。①
文中成浑认为,衡之于圣贤前言,皆为立两边说,未曾有如李珥的一途论之说,并以人乘马之喻为其论说。这里他所指的圣贤应为,朱熹、陈淳等人。成浑的学说受朱、陈二人之影响也较大②,而且朱熹和陈淳的思想亦是其立论根据之一。具体而言,成浑的主张是心未发之时不能将四端与七情分别对待之,此时二者应为“混沦一体”之状态(可视为“七包四”)。已发之时才可以分别四端与七情,即发于理的为四端、道心;发于气的为七情、人心。这里亦可以看到他与李珥的细微差异,成浑不同意未发之时的“所从来”意义上的四七分别。依他之见,主理、主气是“才发之际”,即意欲动之时取其重而言之者。因此在这意义上,未发之时成浑对四七结构所持的立场又有与奇大升、李珥的“七包四”逻辑有相似的一面,表现出他的学说的折中性格。因此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他也提出折中李滉与奇大升等人主张的“理气一发”说。
针对成浑的质疑,李珥也以朱学理论为据,阐述了自己的“四七人心道心”论。他说:“‘气发理乘一途’之说,与‘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皆可通贯。吾兄尚于此处未透,故犹于退溪‘理气互发、内出外感、先有两个意思’之说,未能尽舍,而反欲援退溪此说,附于珥说耳。别幅议论颇详,犹恐兄未能涣然释然也。盖‘气发理乘一途’之说,推本之论也;‘或原或生’,‘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沿流之论也。今兄曰‘其未发也,无理、气各用之苗脉’,此则合于鄙见矣。但谓‘性情之间,元有理、气两物,各自出来’,则此非但言语之失,实是所见差误也。”①李珥此处论述极为明快,他认为所谓“气发理乘一途”之说、“或原或生”与“人信马足,马从人意”之说,皆可以通贯。成浑对此有疑问,主要是对理气问题有所未透。于是李珥从理气论与性情说之间的相一致性出发,对“四七人心道心”论作了阐明。曰:“理气之说与人心道心之说,皆是一贯。若人心道心未透,则是与理气未透也。理气之不相离者若已灼见,则人心道心之无二原,可以推此而知之耳。”②由此可以看出,李珥的理气论(“理气之妙”说)是其心性论的立论根基,人道说是其理气论的直接生发。因理气之“不离”义是其理气论的主要理论倾向,因此在人心道心问题上他也以二者的不可分和相联结为其主旨,强调人心道心的“无二原”性。这与李滉、成浑的基于二者不同价值意义上的人心道心相分思想是有明显区别的。
进而李珥阐发了自己的四七人道说。首先,从“主乎理”、“主乎气”的向度,对人心道心的含义作了论述。曰:“夫人也,禀天地之帅以为性,分天地之塞以为形,故吾心之用即天地之化也。天地之化无二本,故吾心之发无二原矣。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感动之际,欲居仁、欲由义,欲复礼,欲穷理,欲忠信,欲孝于其亲……欲切偲于朋友,则如此之类谓之道心。感动者因是形气,而其发也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而形气不为之掩蔽,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也。如或饥欲食、寒欲衣,渴欲饮……四肢之欲安佚,则如此之类谓人心。其虽本于天性,而其发由于耳目四肢之私而非天理之本然,故主乎气,而目之以人心也。道心之发,如火始燃,如泉始达,造次难见,故曰‘微’。人心之发,如鹰解鞲,如马脱羁,飞腾难制,故曰‘危’。”①依李珥之见,因外感者(感动者)是形气,故感动之际被何方为所主宰,显得十分紧要。“主乎理”的道心,是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正,又不为形气所掩蔽者;而“主乎气”的人心,则是出于耳目四肢之私,未直出于理之本然者。以“主乎理”、“主乎气”视角,探讨人心道心之含义,这一点颇能反映韩国儒学在讨论人间和存在的所以然根据这个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时,往往落实到性理层面上展开理气这个形上、形下问题的理论特性。②重视人间性理,是韩国儒学的根本特征。
其次,李珥从“心是气”的意义上,以知觉论的立场回答了“一心”何以有“二名”,即有人心道心之分的问题。
在李珥哲学中“心”属于气、属于已发,曰:“且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或原于性命之正,或生于形气之私。’先下一‘心’字在前,则心是气也,或原或生,而无非心之发,则岂非气发耶?心中所有之理,乃性也,未有心发而性不发之理,则岂非理乘乎?‘或原’者,以其理之所重而言也;‘或生’者,以其气之所重而言也,非当初有理、气二苗脉也。”③故不管人心还是道心皆属于已发。这一规定使其人心道心说具有了知觉论特色。对“一心”何以有“二名”,他有以下几段论述。他说:
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①
心一也,岂有二乎?特以所主而发者有二名。②
人心道心虽二名,而其原则只一心。其发也或以理义或为食色,故随
其所发而异其名。③“心”只有一个,这与朱子的主张相同。但是在“一心”何以有“二名”的问题上,李珥所持的诠释立场与朱子不同。这源于李珥独特的性情论义理架构。众所周知,朱子的性理学说以“理气二分”、“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而李珥则以“理气之妙”,心、性、情、意四分结构为基本义理间架。因此朱子的性情论可以“心统性情”说来概称,而李珥的性情论则似以“心性情意一路各有境界”说来指代更为恰当。此处,紧要处为二人对“意”概念的不同界定。在朱子性情论中,“意”和“情”都是从属于“心”的概念。“情”和“意”二者关系是,大抵“情”是性之动,“意”是心之所发;“情”是全体上论,“意”是就起一念处论。④因此在朱子心性论中,“意”的思量运用之意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在李珥哲学中,“意”和“情”是两个有明确规定的并列关系的哲学范畴,李珥曰:“意者,心有计较之谓也。情既发而商量运用者也……发出底是情,商量底是意。”⑤“情动后缘情计较者为意。”⑥“情”和“意”皆属于心之已发,而且还是心的两个不同境界。曰:“因所感而紬绎商量意境界”⑦,李珥提出其独特的“意境界”论。
故其人心、道心论是兼情、意而言,如其曰:“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不但指情也。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⑧需注意的是,“意”其实是在其人心道心说中起十分重要作用的范畴。这既是李珥与朱子性情论之区别,亦是其对朱子心、性、情、意说的发展。相较而言,李珥的心性学说确实比朱子的理论更为细密和清晰。而且,强调“意”的商量计较作用是李珥知觉论最为显著的特点。
基于“意之商量计较”意涵,李珥提出了极具特色的“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终始”说。他说:
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间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①不管根于性命之正的道心,还是源于形气的人心,皆属已发,此时气已用事。若欲不咈乎正理如实呈现,或知非制伏不从其欲,都要借“意”之计较、思虑、商量作用来实现。因此李珥认为,在人心之方寸之间,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可变状态。在已发层面上,二者是并无固定的、严格的分别。因此,李珥为学极重“诚意”,他以为“情胜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时,“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②。指出,若能保证“意”之“诚”,则所发之“心”皆能呈现为道心。
再次,李珥还援引“四七”论、“理欲”论上的说法,进一步论述了其对人心道心问题及二者关系问题的认识。
前已论及,“四端七情”论是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的重要学说,人心道心论争的发生其实就是“四七”论由“情”论层面向“心”论层面的进一步推进,即“四七”论在心性领域的更深、更广意义上的展开。
因为在李珥性理哲学中,“意”具有商量计较作用,故人心和道心时刻处于相互转换之状态。这与其“四七”论中,七情兼四端的情形有所不同,对此差异李珥指出:“圣贤之说,或横或竖,各有所指,欲以竖准横,以横合竖,则或失其旨矣。心一也,而谓之道、谓之人者,性命形气之别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专言理、兼言气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说尽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则愚见也。”①可见,李珥对四端与七情的基本认识是,“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故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兼四端,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为终始。基于其“七包四”一元思维,他又对“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李珥谓:
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者,何谓也?今人之心,直出于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顺而遂之,闲之以私意,则是始以道心,而终以人心也。或出于形气,而不咈乎正理,则固不违于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从其欲,则是始以人心,而终以道心也。盖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不但指情也。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也,乌可强就而相准耶?今欲两边说下,则当遵人心、道心之说;欲说善一边,则当遵四端之说:欲兼善恶说,则当遵七情之说,不必将柄就凿,纷纷立论也。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本然之性,则不兼气质而为言也;气质之性,则却兼本然之性。故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则兼四端。朱子所谓“发于理”、“发于气”者,只是大纲说,岂料后人之分开太甚乎!学者活看可也。且退溪先生既以善归之四端,而又曰“七者之情,亦无有不善”,若然,则四端之外,亦有善情也,此情从何而发哉?孟子举其大概,故只言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而其他善情之为四端,则学者当反三而知之。人情安有不本于仁义礼智而为善者乎?此一段当深究精思。善情既有四端,而又于四端之外有善情,则是人心有二本也,其可乎?大抵未发则性也,已发则情也,发而计较商量则意也。心为性、情、意之主,故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知其气之用事,精察而趋乎正理,则人心听命于道心也;不能精察而惟其所向,则情盛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矣。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情虽万般,夫孰非发于理乎?惟其气或掩而用事,或不掩而听命于理,故有善恶之异。以此体认,庶几见之矣。别纸之说,大概得之。但所谓“四、七发于性,人心、道心发于心”者,似有心、性二歧之病。性则心中之理也,心则盛贮性之器也,安有发于性、发于心之别乎?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①
本段引文较长,但是此段内容则是李珥对四七人心道心问题的最为系统之论述。如其文中言的“七情则统言人心之动,有此七者,四端则就七情中择其善一边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对说下矣。且情是发出恁地,不及计较,则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为终始也”中可以看出,在李珥哲学中“情”不具商量计较之义,故性发为情之际,七情可以兼四端。因为依他之见,“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但是,人心、道心则已达比较、商量之地步,已具对比之意,故不能兼有,只能互为终始,这便是其“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
因为人心与道心是基于“意”之商量计较而存在的相对之物,李珥又由“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而提出“人心道心相对”说。他说:“盖人心道心相对立名,既曰道心则非人心,既曰人心则非道心,故可作两边说下矣。若七情则已包四端在其中,不可谓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乌可分两边乎?”②
此论看似与其“人心道心相为终始”说矛盾,但是这是李珥从天理人欲论角度对人道说的解读,可视为对人道终始说的另一种阐发。他说:“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③可见,李珥对道心、人心、人欲是有区分,而且也肯定人心亦有善。在此李珥所持的是朱子的立场。但是,人心之善与道心是否为同质之善呢?
对此,李珥在《人心道心图说》中写道:“孟子就七情中别出善一边,目之以四端。四端即道心及人心之善者也……论者或以四端为道心,七情为人心,四端固可谓之道心矣,七情岂可谓之人心乎?七情之外无他情,若偏指人心则是举其半而遗其半矣。”①可见,他是把二者视为同质之善。在“理欲”论意义上,其人道说比朱子的人道说显得更为紧张和严峻,颇似“天理人欲相对”说。这也是二人人心道心之说的主要区别之一。同时,李珥还从理欲之辨角度,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论辩的结束阶段,李珥写了首五言律诗(《理气咏》)致成浑,以阐明其理气哲学主旨。诗云:
元气何端始,无形在有形。
穷源知本合,沿派见群精。
水逐方圆器,空随大小瓶。
二歧君莫惑,默验性为情。②这首理语诗中李珥又夹注,曰:“理、气本合也,非有始合之时。欲以理、气二之者,皆非知道者也……理、气原一,而分为二五之精……理之乘气流行,参差不齐者如此。空瓶之说,出于释氏,而其譬喻亲切,故用之。”③十分形象地从本体和流行的视角,再一次强调了其“理气之妙”和“气发理乘”思想。
成浑与李珥年龄相仿,李珥19岁时二人便定交。《年谱》记云:“成先生长于先生(指李珥——引者注)一岁,而初欲师事之,先生辞焉。遂定道义之交,相期以圣贤事业终始无替。”④李珥卒后,成浑曾评其道:“栗谷尽是五百年间气也。余少时讲论,自以为朋友相抗。到老思之,则真我师也,启我者甚多。”⑤李珥37岁(成浑时年38岁)时二人围绕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及理气之发问题展开了长达6年的辩论,尽管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但是成浑对李珥的崇敬之情从其评语中以见一斑。
在朝鲜朝儒学史上由李珥和成浑之间进行的“四七人心道心”之辨是,继“四端七情”之辨之后发生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又一学术论争。
三、李珥“四七人心道心”论的特色
李珥的“四七人道”说特色主要表现在,其“四七理气”说和心性情意论方面。
李珥的“四七理气”论是在与成浑的相互论辩和与李滉的相互问学中形成。李滉在“四七理气”论方面的基本说法是,“四七理气互发”说。成浑大抵接受李滉此一立场。
李滉曾曰:“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①此论便是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此一理论的性情论基础是,“二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二情”(四端/七情)论。由此自然可以推导出,对举分别而言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论,即主理、主气之说。
李珥反对李滉的“四七理气互发”说,基于其理气“一而二、二而一”思路以为,子思、孟子所言的本然之性和程子、张子所言的气质之性,其实皆为“一性”,只是所主而言者不同而已。曰:
性者,理、气之合也。盖理在气中,然后为性。若不在形质之中,则当谓之理,不当谓之性也。但就形质中单指其理而言之,则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不可杂以气也。子思、孟子言其本然之性,程子、张子言其气质之性,其实一性,而所主而言者不同。今不知其所主之意,遂以为二性,则可谓知理乎?性既一,而乃以为情有理发、气发之殊,则可谓知性乎?①可见,李珥不仅主张性为理气之合,而且还明确区分“性”与“理”概念的不同用法。这既是李珥逻辑思维细密、精微之处,也是其“四七”论的独到之处。进而他指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其实是“一性”。这里还可以看出,他的“性”论又与奇大升的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依他之见,若不知其所主之意而视其为“二性”,可谓之味于“理”者。而在“性既一”之情形下,仍主情有理发、气发之殊的话,则又可谓之味于“性”者。
李珥也认为,理为形而上者也,气为形而下者也。不过,他特别强调二者的不能相离性。因此在他而观,二者既不能相离,则其发用也只能是“一”,不可谓互有发用。曰:
若曰互有发用,则是理发用时,气或有所不及;气发用时,理或有所不及也。如是,则理气有离合,有先后,动静有端,阴阳有始矣,其错不小矣。但理无为,而气有为,故以情之出乎本然之性,而不掩于形气者,属之理;当初虽出于本然,而形气掩之者,属之气,此亦不得已之论也。人性之本善者,理也,而非气则理不发。人心、道心,夫孰非原于理乎?非未发之时,亦有人心苗脉,与理相对于方寸中也。源一而流二,朱子岂不知之乎?特立言晓人,各有所主耳。程子曰:“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夫善、恶判然二物,而尚无相对各自出来之理,况理、气之混沦不离者,乃有相对互发之理乎?若朱子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何以为朱子乎?②
在李珥看来,承认“理气互发”说不仅等于承认理气有缝隙、有离合,而且还承认理气有先后、动静有终始。朱熹的“理气不杂”、“理气为二”思想,明初便遭到曹端、薛瑄、胡居仁等人的批评,他们依据程明道的“器亦道,道亦器”理论,主张理在气中,坚持理气无间一体思想,反对把二者对立、割裂。罗钦顺的“理气一物”说,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理论。罗氏的《困知记》对朝鲜朝性理学及李珥“理气之妙”说的影响前文已多次论及,李珥也受此理论思潮之影响力主“理气非二”论。故他以为,四端与七情之说是朱子“特立言晓人,各有所主”而已。这与奇大升的所言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①的思想并无二致。依李珥之见,若是朱子也真以为理、气互有发用,相对各出,则是朱子亦误也。
于是,他进而指出:
朱子之意,亦不过曰: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云尔耳;非曰:四端则理先发,七情则气先发也。退溪因此而立论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所谓“气发而理乘之”者,可也。非特七情为然,四端亦是气发而理乘之也。何则?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化而理乘之也。是故,阴阳动静,而太极乘之,此则非有先后之可言也。②
在此李珥对朱子的“四七”论作了己之阐发的同时,指出李滉的错误在于只认同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他坚持,不仅四端是“气发而理乘”,七情亦是“气发而理乘”。对于李珥和李滉的“气发而理乘之”的说法,陈来先生认为,二者并不相同。他指出:李滉所说的气发是发自于形气,而李珥所说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李珥进一步说的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这是气,就是气发,而理乘载其上。由于李珥的气发是已发的情、意、心,故把恻隐说成气,说成气发,这种说法与王阳明接近,容易引出“心即气”的主张,是与朱子和李滉不同的。李珥认为,气和理的这种动载关系是普遍的,不限于四端七情,整个天地之化都是如此。③陈先生的这一论述,对于二人的理气之发说的理解及理气论差异问题的探讨颇有裨益。
要之,“性”与“理”概念的区分,“一性”、“一情”论的强调以及“七包四”立场的坚守,是李珥“四七理气”论的主要特色。
那么,李珥和李滉的“气发而理乘”思想为什么会有理论差异呢?这源于李珥独特的心性情意论。
在李珥的心性情意论逻辑结构中,“心”处于十分重要之地位,他认为,就人之一身来说心“合性与气”,而有“主宰”于身之作用。他说:
天理之赋于人者,谓之性,合性与气而为主宰于一身者,谓之心。心应事物而发于外者,谓之情。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未发已发之总名……性之目有五,曰仁义礼智信;情之目有七,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之发也,有为道义而发者。如欲孝其亲,欲忠其君,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见非议而羞恶,过宗庙而恭敬之类是也,此则谓之道心。有为口体而发者,如饥欲食、寒欲衣、劳欲休、精盛思室之类是也,此则谓之人心。①
文中李珥对“性”、“情”、“心”、“道心”、“人心”等作了明确之界定。此说与朱子的“心为主宰”的思想和李滉的“心兼理气”、“理气合而为心”②说法皆也有所不同。因为在李滉的性理哲学体系中理具发用性和能动性,故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而在心、身的关系上,李珥也强调心的优位性,比朱子更加明确指出心对身的主宰作用,言道:“心为身主,身为心器,主正则器当正。”③而且,在李珥性理哲学中心属于气,属于已发,故“心”在其性情论中是被探讨的主要对象。
对于“心”、“性”、“情”概念及相互关系,李滉则界定为:
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④
表明,李滉的心论结构大体延续的是朱熹的“心统性情”思路。但是,有别于朱熹的是,他的这一思想突出了理对于心之“灵”的作用,着重于解决心的知觉作用问题。
基于心之作用的独特认识,李珥又提出“心为性、情、意之主”的思想。他言道:
大抵未发则性也,已发则情也,发而计较商量则意也。心为性、情、意之主,故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其发直出于正理,而气不用事,则道心也,七情之善一边也;发之之际,气已用事,则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恶也。知其气之用事,精察而趋乎正理,则人心听命于道心也;不能精察而惟其所向,则情盛欲炽,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矣。精察与否,皆是意之所为,故自修莫先于诚意。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来矣,人心岂非二本乎?情虽万般,夫孰非发于理乎?惟其气或掩而用事,或不掩而听命于理,故有善恶之异。以此体认,庶几见之矣。别纸之说,大概得之。但所谓“四、七发于性,人心、道心发于心”者,似有心、性二歧之病。性则心中之理也,心则盛贮性之器也,安有发于性、发于心之别乎?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①
李珥主张“心为性、情、意之主”,故以为未发、已发及其计较,皆可谓之心。需注意的是,李珥对“性”概念的界定,曰:“性者,理、气之合也。盖理在气中,然后为性。”②其实,他所言之性为“气质之性”。“心是气”,因此性、情、意皆可谓之心。但是,性和情不具计较商量义,故“意”之作用又显得十分重要。“意”不仅在其“四七人道”说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其修养论亦具有重要意义,故其曰“自修莫先于诚意”。进而,李珥还提出“人心、道心皆发于性”的主张,此说与朱熹和李滉的思想相比区别较大。
李珥心性情论中最为独特的思想为,其“性心情意一路而各有境界”论。他说:
子固历见余谈话,从容语及心性情。余曰,公于此三字,将一一理会否。子固曰,未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云者,殊未晓得。余曰,公于此难晓,则庶几有见于心性情矣。先儒此说,意有所在,非直论心性。而今之学者为此说所误,分心性为有二用,情意为有二歧,余甚苦之。今公自谓于此有疑,则庶几有真知矣。性是心之理也,情是心之动也,情动后缘情计较者为意。若心性分二,则道器可相离也;情意分二,则人心有二本矣。岂不大差乎?须知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然后可谓不差矣。何谓一路?心之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发后商量为意,此一路也。何谓各有境界?心之寂然不动时是性境界,感而遂通时是情境界,因所感而紬绎商量为意境界,只是一心各有境界。①
在心性情论方面,李珥一贯反对“分心性为有二用,情意为有二歧”。因为依他之见,若心性分二,则道器可相离也;情意分二,则人心有二本。由此他提出“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思想。如前所述,李珥的性情论为心性情意四分逻辑结构,故性境界、情境界、意境界分别代表了“一心”之不同境界,犹如人之行走,一路走下去一路上各有不同的景致呈现一般。
总之,李珥心性情论的主要特色在于对“心”之主宰作用与“意”之计较商量作用的重视以及“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论。而“性心情意只是一路而各有境界”论,的确为其在心性情论上的创见。
李珥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天道策》、《人心道心图说》、《圣学辑要》、《答成浩原》等。
自从29岁时任户曹左郎开始,他一生为宦,曾官至吏曹判书,49岁时卒于京城大寺洞寓所。李珥是朝鲜朝五百年间难得的道学家、通儒。政治上,他积极建言献策主张为了朝鲜朝的中兴“因时制宜”与“变法更张”,强调“事要务实”。在社会教育方面,他不仅亲自开展私学教育,而且还制定“海州相约”、“社会契约束”以及著《击蒙要诀》、《学校模范》等为朝鲜朝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故成浑赞其曰:“栗谷于道体,洞见大原。所谓天地之化无二本,人心之发无二原,理气不可互发,此等说话,真是吾师。其爱君忧国之忠,经世救民之志,求之古人,鲜有其俦。诚山河闲气,三代人物。”①他的学说被后人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韩国儒学史上颇具影响的畿湖性理学派。